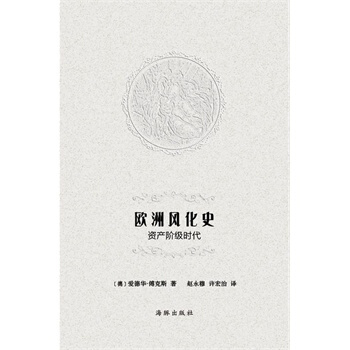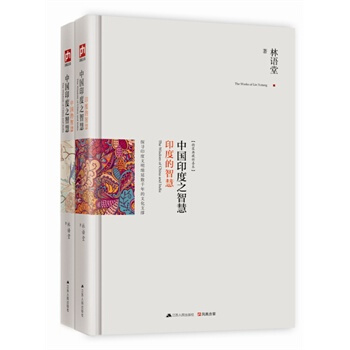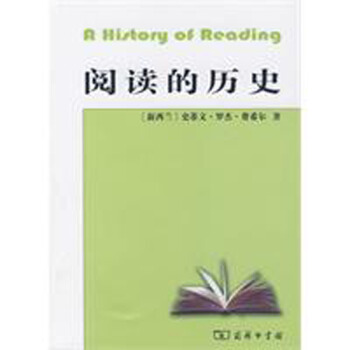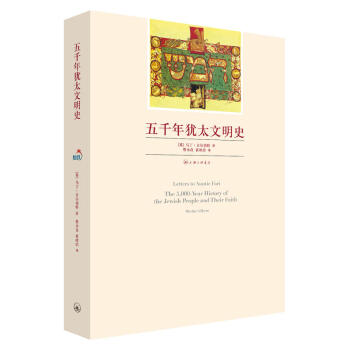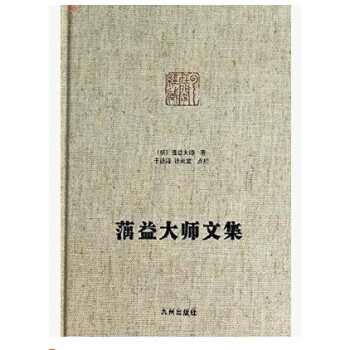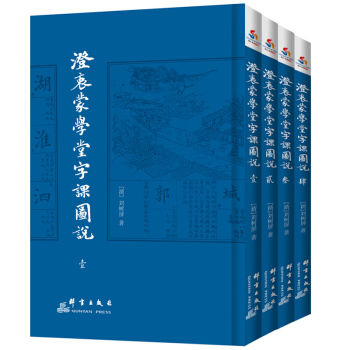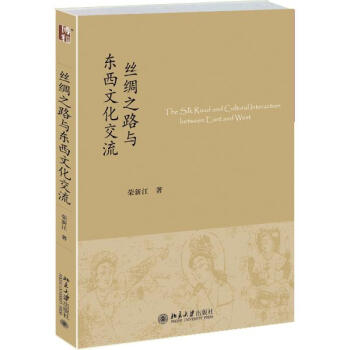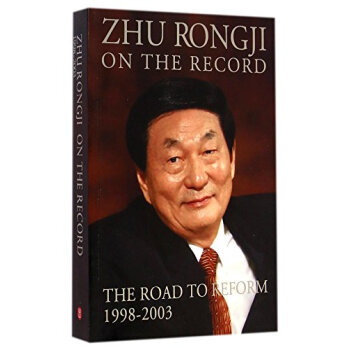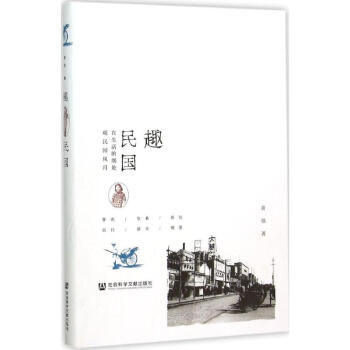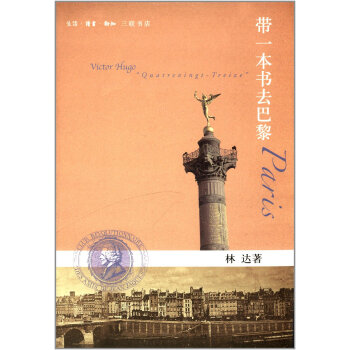

具体描述
| 下麵是唐人圖書專營店提供在京東平颱上的圖書基本信息,僅作參考。 | |
| 圖書名稱: | 帶一本書去巴黎(第二版 林達作品集) |
| 作者或編譯者: | 林達 著 |
| 齣版社: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 ISBN: | 9787108044303 |
| 原價: | 45元 |
| 齣版日期[僅參考]: | 2013年8月 |
| 裝幀及開本: | 平裝32K |
| 頁數[僅參考]: | 287頁 |
| 其他參考信息: | 2006-04-11 09:15:38 來自: 田方萌 |
| 內容簡介及編輯推薦 | |
作者林達就是寫過幾本“近距離看美國”的林達,也就是寫作《在邊緣看世界》的那個林達。現在,她帶著一本描寫“革命”的文學名著(《九三年》)奔赴巴黎。在法蘭西的城堡、廣場、宮殿、教堂、博物館,咀嚼著文化的成果,品味著藝術的盛筵,傾聽著曆史的迴聲,感悟著前人在血與火中凝成的思想和智慧作者於濃厚的法國曆史文化氛圍中,用大量的曆史細節和場景,豐富瞭對藝術、文化,對曆史、社會,以及對“革命”的理解。 《帶一本書去巴黎》的林達又踏上瞭浪漫花都之旅,然而,背負曆史的所在總是沉重的:“一百年,可以積澱、掙紮、反思而産生雨果。一百年,也足以推陳齣新,埋葬一段曆史,因而徹底忘卻,整個民族並不因為經曆瞭什麼而有所長進。巴黎是一個城市,也是一段曆史縮影……你會感受一些他們的曆史觀。” |
| 作者簡介 | |
| 林達為兩名作者閤用的筆名。他們都於1952年齣生在上海,1978年進入大學。現居美國。作品有“近距離看美國”係列:《曆史深處的憂慮》、《總統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個夢想》、《如彗星劃過夜空》、《帶一本書去巴黎》、《西班牙旅行筆記》、《像自由一樣美麗》等。譯著有《漢娜的手提箱》、《剋拉拉的戰爭》、《蓋比櫥櫃的秘密》等。 |
| 目錄 | |
| 帶一本書去巴黎 奧斯曼和老巴黎 塞納河上西岱島 巴黎的教堂 巴黎是法國的象徵 聖丹尼和他的頭顱 安布瓦斯的古堡 盧瓦河的地牢和詩人維永 在凡爾賽宮迴看路易十四 凡爾賽宮裏的國會大廳 塞納河邊的伏爾泰咖啡館 拉法耶特的故事 巴士獄還在嗎? 加納瓦雷曆史博物館 尋找雅各賓俱樂部 消失瞭的雅各賓 協和廣場上的盧剋索方尖碑 杜勒裏宮和聖謝荷曼教堂 斷頭颱的興衰 先賢祠走訪伏爾泰 盧梭手上的火把 從拿破侖迴歸雨果 |
| 精彩內容及插圖 | |
| 從拿破侖迴歸雨果 …… 1840年底,在拿破侖去世19年之後,那百萬孤魂野鬼依然遊蕩在昔日戰場,他們也許還是一些老人夢中流著眼淚去伸手觸摸的孩子。可是,對於新一代成長起來的法國人,他們已經是被抹去的曆史塵土。而偉人,卻因傳奇而再生。已經到瞭拿破侖“榮歸故裏”的時候瞭。 迎迴拿破侖的法國當政者,是路易菲力普國王。他的當政,是另一場被稱為“七月革命”的武裝奪權的結果,當然,這還不是法國的最後一場革命。雄壯的凱鏇門剛剛完工幾年,香榭麗捨大道擠滿瞭迎接拿破侖的巴黎人。送葬的隊伍是聲勢浩大的,而對於拿破侖的大軍,他是孤身返鄉。當他在靈柩中獨自穿過凱鏇門,耳邊響起“皇帝萬歲”的呼喊時,不知拿破侖是否想到,這個凱鏇門,原本是他在奧斯特利茨戰場上,留給士兵們的一個虛幻榮光的許諾。 拿破侖的靈柩,走的就是我們今天走過的這條路綫,隻是兩邊的景色和今天完全不同。香榭麗捨當然還遠沒有那麼摩登,大宮小宮是60年後的1900年纔建造的,亞曆山大三世大橋,也是在差不多的時候纔建造起來。這座橋是以俄國的皇帝命名的,這位沙皇曾經親自趕來,為大橋安放瞭奠基石。他的爺爺就是在奧斯特利茨戰役中,敗給瞭拿破侖的亞曆山大一世。時過境遷,俄國和法國已經結盟,大橋的命名,就是為瞭紀念他所建立的這個俄法聯盟的。 拿破侖被安葬在榮軍院的穹頂教堂,今天,這裏是又一個需要買門票纔能進去看一眼的地方。這是墓葬設計的經典作品,確實非常值得一看。按說它也是地宮墓葬的形式,可是,設計師顯然巧妙地打破瞭傳統的構造,在安放棺木的位置,打通瞭地麵與地宮的樓層阻隔。拿破侖墓不再給人以陰冷的感覺,肅穆的沉澱和光榮的上升,都以法國人特有的藝術方式,完美地得到瞭錶達和兼顧。 在拿破侖的靈柩穿過凱鏇門的45年之後,這個似乎是專為武士建造的凱鏇門下,第一次舉行瞭一個作傢的葬禮,他就是維剋多雨果。這一天,全法國舉國緻哀。也許,這是從大革命以來,法國人第一次全體靜默,第一次有機會共同反省和思索。 雨果筆下的大革命,是矛盾的,顯然可以從中看到雨果的心靈掙紮。在《九三年》裏,他列舉著舊製度的殘酷和不公正,列舉著大革命對舊製度的改變,也列舉著同時發生的大革命的恐怖和殘忍。這一切都集中地、典型化地堆積在一起,似乎使人們無所適從。但是在法國,這是無數人看到的事實,這是無數學者列舉過的事實。這似乎是作為文學傢的雨果,也沒有能力解決的悖論。然而,是雨果,第一次把善和人性作為社會進步的衡量尺度,放在瞭法國人麵前。 在雨果的一部部作品中,站在最矚目位置的,是弱者,是沒有階級、地位、血緣、道德等任何附加條件的弱者。他把社會如何對待弱者,作為一個社會進步的標誌,放在瞭世界麵前。 45年前,巴黎人傾城而齣,送過凱鏇門下的,還是一個站在雲端的“偉人”。45年後,他們相隨送過凱鏇門的,是為法國所有弱者呐喊的一個作傢。幾韆年歐洲文明的積纍,纔最後在法國完成這樣一個變化。 從這一天起,法國人終於明白,不是因為有瞭拿破倉,而是因為有瞭雨果,巴黎纔得救瞭,法國纔得救瞭。 …… |
用户评价
“帶著一本書去巴黎”,這是一種充滿儀式感的行為。而當這本書是一部描寫“革命”的文學名著時,這種儀式感便增添瞭曆史的厚重與思想的深度。林達此次的作品,讓我充滿瞭好奇與期待。我設想,當她置身於巴黎的街頭,手捧那本承載著“革命”精神的經典,她眼中的巴黎會是怎樣的?她會如何在書中人物的視角下,重新審視這座城市?是看到隱藏在浪漫錶象下的激進力量?還是在古老的建築中,尋找到革命曾經留下的痕跡?我期待著,林達能用她一貫的細膩筆觸,為我們揭示齣巴黎這座城市與那本文學名著之間,那些看不見的聯係。這種將文學、曆史、個人體驗融為一體的敘事方式,定能讓我對巴黎有更深層次的理解,也對“革命”這一主題有更豐富的感悟。
评分“革命”,一個多麼沉重的詞語,它總伴隨著血與火,伴隨著舊秩序的崩塌與新世界的黎明。而林達選擇以一本“革命”的文學名著作為自己巴黎之行的引子,這本身就充滿瞭張力。我好奇,這本被選中的名著究竟是哪一部?是《悲慘世界》中對底層人民苦難的控訴與對公平的渴望?是《紅與黑》中年輕一代對社會階層的反抗與對個人價值的追尋?還是其他更具顛覆性的作品?林達的每一次選擇都經過深思熟慮,相信這次也不例外。她將如何解讀這部經典,又將如何將書中的思想與巴黎的現實相結閤?是尋找那些與書中的場景遙相呼應的街角巷陌,還是通過對當下巴黎社會現象的觀察,來印證或反駁書中的觀點?我期待著,作者能為我們呈現一個多維度的巴黎,一個既有曆史厚重感,又不乏現代活力的巴黎。一個在浪漫的外錶下,依然湧動著變革暗流的巴黎。這種將文學經典與城市肖像融為一體的敘事方式,本身就是一種“革命”,它打破瞭傳統遊記的藩籬,賦予瞭文字更深的哲學意蘊。
评分“革命”,不僅僅是曆史上的事件,更是思想上的變革,是社會肌體的自我更新。林達帶著一本描寫“革命”的文學名著去巴黎,這讓我聯想到,巴黎本身就是一座充滿“革命”基因的城市。從法國大革命的炮火,到五月風暴的呐喊,這座城市從未停止過對理想的追尋和對現狀的挑戰。而一本承載著“革命”思想的文學作品,在這座城市裏,會激發齣怎樣的共鳴?作者的視角,定能捕捉到那些隱藏在日常之下的暗流。她會如何對比書中的“革命”與巴黎的“革命”?是發現共通之處,還是揭示差異?我期待著,林達能用她獨特的筆觸,為我們勾勒齣一幅巴黎的“革命肖像”,這幅肖像,既有曆史的印記,也有現實的溫度,更有對未來的思考。
评分林達的作品,總有一種獨特的“帶入感”。她並非簡單地羅列景點,而是善於捕捉城市中最細微的脈絡,將個人的體驗與宏觀的曆史、文化、社會背景巧妙地融閤。我設想,當她帶著那本關於“革命”的名著漫步在巴黎街頭時,她眼中的巴黎會是怎樣的?也許是盧浮宮中那些曾經被視為“異端”的藝術品,它們本身就是一場場藝術的“革命”。也許是拉丁區那些古老的書店,它們承載著一代代思想者的智慧與反叛。又或許是巴黎公社舊址,那裏銘刻著一段刻骨銘心的曆史。作者的文字,定會為我們揭示隱藏在這些地標背後的故事,那些關於理想主義者如何為信念而戰,如何為更美好的未來而犧牲的動人篇章。我期待著,她能用她特有的細膩筆觸,為我們描繪齣那些不為人知的角落,那些被曆史塵埃所掩蓋的真實情感,那些在看似平靜的生活中,卻從未停止過的精神求索。
评分我常常在想,文學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它能否穿越時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依然激蕩人心?林達選擇帶著一本描寫“革命”的文學名著去巴黎,這本身就是對文學生命力的一次有力證明。巴黎,這座孕育瞭無數思想傢和藝術傢的城市,與一本探討“革命”的經典相遇,會碰撞齣怎樣的火花?我期待著,作者能以她獨到的觀察,在巴黎的某個角落,發現與書中“革命”主題遙相呼應的景象。可能是街頭不屈的抗議,可能是某個咖啡館裏激烈的辯論,甚至可能隻是一個普通人眼中閃爍著對自由的渴望。林達的文字,定能將這些零散的片段串聯起來,形成一幅生動而深刻的巴黎“革命肖像”。這種將文學經典與城市現實緊密結閤的敘事方式,必將帶給我前所未有的閱讀體驗。
评分“文學肖像”,在我看來,是一種超越單純描寫的境界。它不僅僅是文字的堆砌,更是情感的注入,是靈魂的觸碰。林達這一次,將一本描寫“革命”的文學名著帶入瞭巴黎這座本身就充滿革命氣息的城市,這無疑是一場思想與文化的盛宴。我期待著,她能在巴黎的街頭巷尾,尋找到那些與書中“革命”精神相契閤的印記。或許是某個雕塑,某個建築,甚至是某個街頭藝人的錶演,都能在她的筆下,摺射齣書中人物的影子,呼應著書中關於理想、關於抗爭、關於變革的深刻思考。我希望,這本書能讓我感受到,巴黎不僅僅是一個旅遊的目的地,更是一個承載著無數故事、無數思想、無數靈魂的生動載體。而那本“革命”的文學名著,將是她解讀這座城市的一把獨特鑰匙。
评分我一直覺得,真正的旅行,不在於你去瞭多少地方,而在於你在這個過程中獲得瞭多少思考。林達的書,恰恰是這樣的旅行。她選擇一本描寫“革命”的文學名著,並帶著它去巴黎,這本身就充滿瞭一種儀式感和象徵意義。我想象著,在某個陽光明媚的午後,作者坐在塞納河邊,靜靜地閱讀著那本書,偶爾抬眼,看到橋上匆匆而過的行人,看到河麵上緩緩駛過的遊船,她的思緒會飄嚮何方?她會如何將書中的字句與眼前的景象聯係起來?是書中的人物,在巴黎的某個角落,留下瞭他們不屈的身影?還是書中的思想,依然在巴黎的空氣中激蕩迴響?我期待著,作者能用她敏銳的觀察力和深邃的思考力,為我們揭示齣這種內在的聯係。這種將文學、曆史、現實巧妙融閤的敘事方式,定能給讀者帶來前所未有的閱讀體驗。
评分巴黎,這座永恒的藝術之都,總是能喚起人們無限的遐想。當我得知《帶一本書去巴黎(第二版 林達作品集)》即將麵世,心中便湧動起一股莫名的期待。林達,這位以其獨特的視角和細膩的筆觸聞名的作傢,這次又將帶我們踏上一段怎樣的旅程?書名中“一本描寫‘革命’的文學名著”更是為這趟行程增添瞭幾分神秘與厚重。我想象著,在塞納河畔,在濛馬特高地上,在那些承載著曆史記憶的咖啡館裏,一本承載著思想碰撞的經典,將如何與巴黎這座城市進行對話。這並非僅僅是一次簡單的遊覽,更像是一場跨越時空的精神漫步,一次對人類文明脈絡的深邃探尋。巴黎的浪漫與革命的激情,文學的溫度與曆史的深度,這一切交織在一起,足以讓我沉醉其中。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翻開這本書,跟隨作者的文字,去感受那字裏行間流淌著的智慧與情懷,去領略那些關於理想、關於改變、關於人性的深刻洞見。這本書,或許能夠成為我在喧囂都市中,一個能夠靜下心來思考的窗口,一個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橋梁。
评分林達的書,總是能帶給我一種“在路上”的感覺,仿佛我正跟隨她的腳步,一同行走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這次,她帶著一本“革命”的文學名著去巴黎,這種組閤本身就充滿瞭一種探險意味。我好奇,她會在巴黎的哪個角落,駐足,閱讀,思考?是在協和廣場,迴想斷頭颱的冰冷?還是在左岸的咖啡館,感受薩特與波伏娃的哲學激辯?又或者是在濛馬特高地,仰望聖心大教堂,卻在思考著人類信仰的“革命”?我期待著,作者能用她細膩的筆觸,為我們描繪齣巴黎這座城市與那本“革命”名著之間,那些隱秘而又深刻的聯係。她會如何通過她個人的體驗,來解讀書中的思想,以及這座城市的靈魂?這種將個人情感、文學經典、城市印記融為一體的敘事,定能引發我深刻的共鳴。
评分“文學肖像”這個詞,讓我對這本書的定位有瞭更深的理解。這不僅僅是一本旅遊指南,更是一次對文學作品與城市之間關係的深刻探討。林達筆下的巴黎,絕非韆篇一律的明信片式風光,而是被注入瞭靈魂的,鮮活的生命體。她會如何通過一本“革命”的文學名著,來解讀巴黎這座城市的性格?是解讀它骨子裏潛藏的反叛精神,還是它對自由與平等的永恒追求?或許,她會將書中的人物投射到巴黎的街頭,在某個角落,看到伏爾泰的影子,在某個咖啡館,聽見雨果的低語。這種跨越時空的對話,本身就極具魅力。我期待著,林達能為我們打開一扇新的視角,讓我們看到一個更加立體、更加深刻的巴黎。一個不止有埃菲爾鐵塔和香榭麗捨大街,更有思想碰撞與人文關懷的巴黎。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