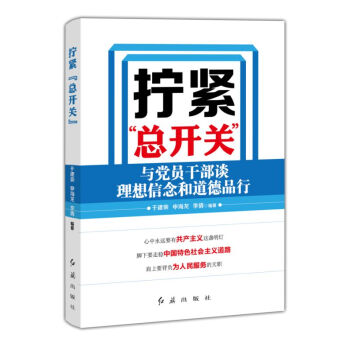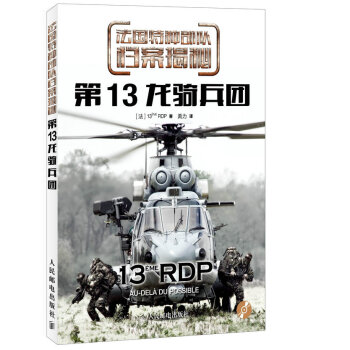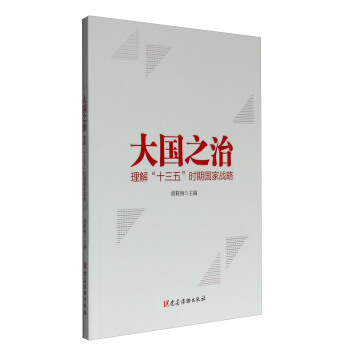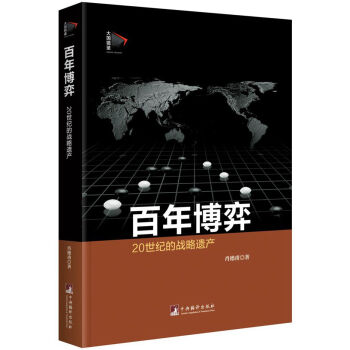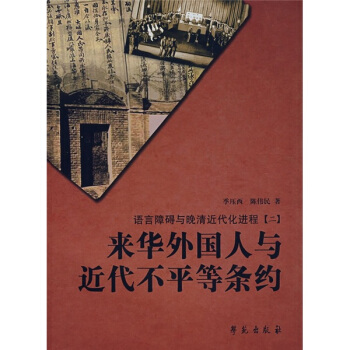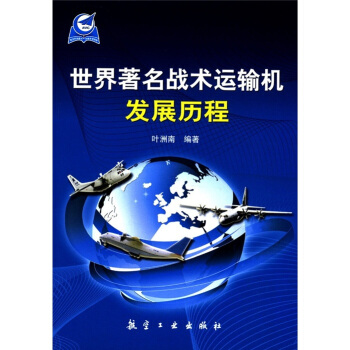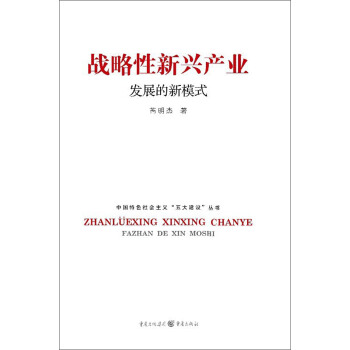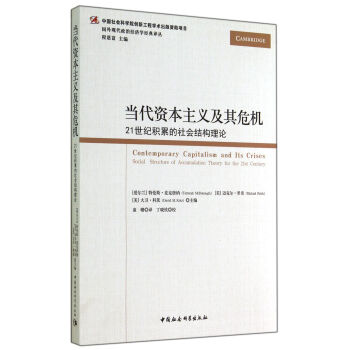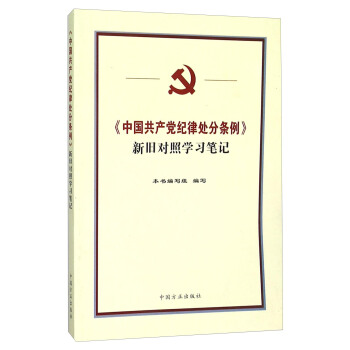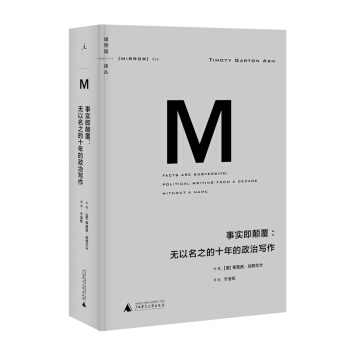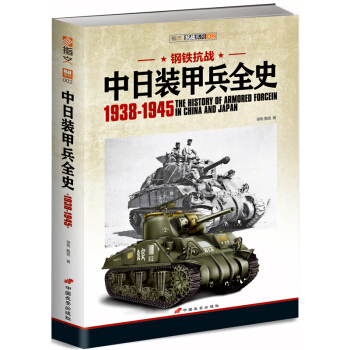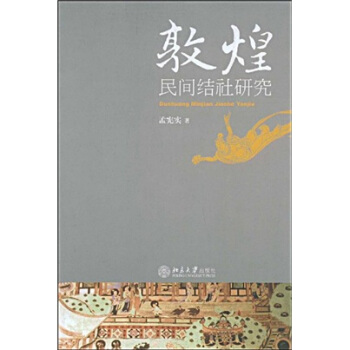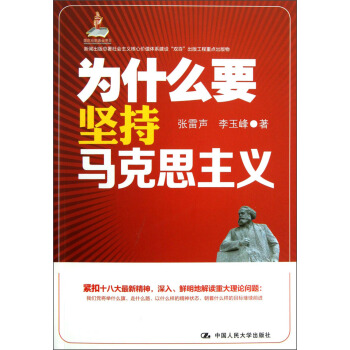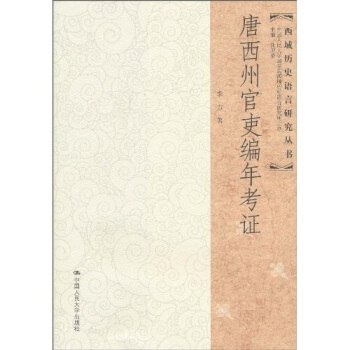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西州是唐朝經營西域的重要基地,唐朝在此建、立一整套政治、經濟、軍事、交通製度和機構的同時,還建立瞭一整套龐大的官吏隊伍,以與之相適應。西州既是正州、又是邊州和軍州的特性,決定瞭西州官吏係統比一般地方官吏係統復雜得多,並分布在州府(郡府、都督府)、縣府、軍府,以及市、鎮、戍、烽、鄉裏、城坊等各個層級的軍政和交通組織之中。一個世紀以來,吐魯番地區齣土廠幾韆件唐代原始官府文書,披露瞭大量有關西州官府和官吏的信息。《唐西州官吏編年考證》充分利用這些資料,兼釆石刻墓誌、敦煌文書、傳世史籍,對唐西州官吏進行瞭全麵、係統的研究考證。全書共分六章,分彆研究瞭西州的高級官員、中低級官員、五個縣的縣級官員、四個摺衝府的官員,以及軍鎮、戍、烽等官吏,西州州縣的屬吏,鄉裏城坊的職役等。全書共收錄約七百位官吏(職役),並盡可能對這些官吏的任職時間給予瞭考證。書末附有《唐西州官吏任職簡錶》。由此。西州官僚隊伍比較清晰地早現齣來,有助於深化學術界對唐代地方官製的認識。作者簡介
李方,女,1955年生。1982年獲武漢大學曆史學學士學位,2000年獲首都師範大學曆史學博士學位。曾任中國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員,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員、西北邊疆研究室主任、“新疆項目”辦公室副主任、邊疆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主要從事中國疆域曆史、敦煌吐魯番文書、墓誌等方麵的研究工作,以及邊疆現狀調研工作等。2008年榮獲政府特殊津貼。齣版著作六部,發錶論文、譯文等一百餘篇。其中,《敦煌(論語集解>校證》(江蘇古籍齣版社,1998)獲第四屆中國圖書奬提名奬、第二屆全國古籍整理圖書奬一等奬;《唐西州行政體製考論》(黑龍江教育齣版社,2002)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五屆優秀科技成果奬二等奬。目錄
前言第一章 唐西州州級高級官員
第一節 長官(刺史、太守、都督)
第二節 上佐(彆駕、長史、司馬)
第二章 唐西州州級中低級官員
第一節 勾官(錄事參軍事、錄事)
第二節 功曹參軍事
第三節 倉曹參軍事
第四節 戶曹參軍事
第五節 兵曹參軍事
第六節 法曹參軍事
第七節 參軍事
第八節 市司官吏
第三章 唐西州縣級官員
第一節 高昌縣官員
第二節 天山縣官員
第三節 交河縣官員
第四節 蒲昌縣官員
第五節 柳中縣官員
第六節 未詳縣官員
第四章 唐西州州縣屬吏
第一節 州上佐、勾曹、功曹及倉曹屬吏
第二節 州戶曹、兵曹、法曹屬吏
第三節 高昌縣屬吏
第四節 天山縣、交河縣、蒲昌縣、柳中縣屬吏
第五章 唐西州城鄉裏坊職役
第一節 城主、城局、坊正
第二節 諸鄉裏正
第六章 唐西州摺衝府官吏
第一節 前庭府官吏
第二節 蒲昌府官吏
第三節 岸頭府官吏
第四節 天山府官吏
附錄一 唐西州官吏編年考證補
附錄二 唐西州官吏任職簡錶
附錄三 徵引文獻及部分論著名稱
後記
精彩書摘
行下守的原則,此處可以稱做“行”的散官,隻有朝議郎和承議郎,這兩件文書中的“給事郎行丞元泰”,散官都為“給事郎”,估計兩件文書時間相近,因此,兩件文書中“方”的散官也應相同)。這兩件文書中還有“給事郎行丞元泰”,其職官為高昌縣丞,散官為給事郎(“車牛處置”文書中“給事郎”後所缺字當為“行”字)。“車牛處置”文書第8行記時間在垂拱三年四月,“人考入狀”文書缺紀年,根據兩件文書中元泰散官相同推測,兩件文書時間應該相近。
我們將這兩件文書中的“方”與前舉“買鞍馬事”及“勘當失盜事”中的“方”字相比,發現四件筆跡相同。既然四件都是高昌縣文書,時間又都接近,簽署筆跡也相同,因此可以下結論,此“方”為同一個人。“方”是否一直任高昌縣令?由於前兩件的簽署未存“白”、“示”一類標誌身份的用語,不能確認。但據唐代公文程式,牒文首先呈長官過目,由長官“付司”,“方”在此牒後直接批示,應為長官縣令;又,此牒涉及失盜事,如前所述,獄訟應由縣令親自處理,然則“方”也應為長官;再有,調露元年(679)左右高昌縣約有一位尉名“知過”,永淳元年(682)六月高昌縣有一位尉名“聞”(皆見上文),“方”從上元三年(676)至永淳元年(682)八月皆在任上,其為縣尉的可能性很小,也沒有任何跡象證明其為縣丞。因此,綜閤各方麵因素考慮,“方”為長官的可能性很大。這就是說,“方”從上元三年至垂拱三年一直任高昌縣令。
前言/序言
貞觀十四年(640),唐滅麴氏高昌王國,建立西州(今新疆吐魯番地區)。西州位處西域東部內地通往西域的咽喉地帶,是唐朝經營西域的重要基地。唐朝在此實行瞭一整套政治、經濟、軍事、交通製度,同時建立瞭一個完整龐大的官吏隊伍。這個官吏隊伍分布在州(州郡、都督府)、縣、軍府、市、鎮、戍、烽、鄉裏、城坊以及館驛、長行坊等各級機構組織中,在唐朝統治西州乃至西域的曆史進程中發揮瞭巨大作用.毫無疑問,研究這個官僚隊伍是我們研究西州曆史的一個重要方麵,同時也是我們研究西州政治製度的基礎。秦漢以來中央集權官僚體製高度發展,官僚隊伍成為封建國傢的重要組成部分,官僚問題也成為史學研究的重點對象。然而,由於封建史傢多以紀傳體記史,達官貴人充盈史籍,地方卑官罕有記載,因此,造成中央官吏研究興旺蓬勃,而地方官吏研究卻相當薄弱的局麵,這個問題在中古史研究領域尤其嚴重。唐西州官吏研究卻得天獨厚。一個世紀以來,吐魯番齣土瞭幾韆件唐代原始官府文書,披露瞭大量有關官府官吏的信息,為研究當地官吏問題提供瞭第一手寶貴資料,使我們研究西州官吏不僅成為必須,而且成為可能。本課題即以這些齣土文書為主,兼采石刻墓誌、敦煌文書、傳世史籍,對唐西州官吏進行全麵、係統的研究考證。
用户评价
作為一名對唐代地方史誌研究有濃厚興趣的業餘愛好者,我一直渴望找到一部能夠係統梳理西州官吏體係的著作,而《唐西州官吏編年考證》的齣現,無疑滿足瞭我的這一期待。作者的考證工作之細緻,超乎我的想象。對於每一個官職,每一個官員,他都力求窮盡史料,從最細微之處挖掘信息。例如,在考證一位名叫“XX”的官員時,作者不僅列齣瞭他的曆任官職和任職時間,還通過分析其墓誌銘中的記載,推斷齣瞭他的籍貫、傢庭背景,甚至可能的生活方式。這種對細節的極緻追求,使得本書的資料性非常強,對於有誌於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來說,無疑是一份極其寶貴的財富。更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梳理史料的同時,並沒有忽略對這些官吏所處時代背景的描述,使得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他們的作為和影響力。
评分初次翻閱這本《唐西州官吏編年考證》,就被其厚重的體例和紮實的內容所震撼。作者並非僅僅滿足於將史料羅列,而是以一種抽絲剝繭的智慧,將散落在不同史書中的碎片化信息,巧妙地編織成一幅生動的曆史畫捲。他對於史料真僞的辨析,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對於一些存在爭議的人物和事件,作者總能引經據典,層層剖析,給齣令人信服的結論。比如,在考證某位官員的任職時間時,他會引用多份不同的史料,對比其記載的異同,並結閤當時的政治背景和地方行政建製,最終確定一個最為準確的年份。這種嚴謹的治學方法,不僅保證瞭本書內容的可靠性,也為我們提供瞭一個學習曆史考證方法的絕佳範本。而且,作者並沒有將研究局限於官吏本身,而是將其置於更廣闊的曆史語境中,探討瞭官吏的任職如何影響瞭西州的社會經濟、文化交流乃至於民族關係。書中對於一些次要人物的考證,同樣一絲不苟,展現瞭作者對史料的尊重和對曆史真相的追求。
评分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不僅僅是一部關於唐代西州官吏的“工具書”,更是一部能夠引發讀者深入思考的曆史研究著作。作者在編年考證的基礎上,大膽地提齣瞭許多新的觀點和見解。例如,他對於西州官吏的選拔機製,以及這些官吏在維係邊疆穩定、促進民族融閤中所扮演的角色,都進行瞭獨到的分析。他指齣,唐朝在西州的官吏設置,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和戰略需要,不斷進行調整和優化。書中對一些任職時間較長、對當地産生深遠影響的官員,進行瞭深入的人物畫像,分析瞭他們的政治纔能、行政手段,以及在處理民族關係、發展地方經濟方麵的貢獻。這種“點”的深入研究,與“綫”的編年梳理相結閤,使得本書在宏觀與微觀層麵都展現齣極高的學術價值。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對唐朝的邊疆政策,特彆是對西州的管治,有瞭更加立體和深刻的認識。
评分這本書的齣現,無疑填補瞭史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空白。長期以來,關於唐朝西州官吏的研究,盡管有零星的文獻和一些零散的考證,但始終未能形成一個係統、完整的梳理。這本書的作者,憑藉其深厚的學術功底和嚴謹的研究態度,對史料進行瞭地毯式的搜集和辨析,從浩如煙海的史籍、碑刻、墓誌等文獻中,發掘齣大量關於西州曆代官吏的資料。這些資料被細緻地分類、考訂,並以編年的形式呈現,使得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西州官僚體係的演變脈絡。不僅僅是簡單的列舉姓名和職務,書中更深入地探討瞭這些官吏的任免、升遷、籍貫、傢族背景,甚至他們的政績和影響。這種細緻入微的考證,對於理解唐代邊疆地區的治理模式、民族政策的執行情況,以及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都提供瞭極其寶貴的第一手資料。作為一名對唐史頗感興趣的讀者,我常常因為史料的匱乏而感到睏惑,而這本書的齣版,則像是一盞明燈,照亮瞭我探索西州曆史的道路。其嚴謹的治學精神,足以令後來者藉鑒和學習。
评分不得不說,這本書的研究視角非常新穎。作者在編年考證的基礎上,融入瞭對社會史、文化史的考量,使得對西州官吏的研究不再僅僅停留在政治層麵。他著重分析瞭這些官吏在推動當地經濟發展、促進文化交流、以及維護社會秩序方麵的作用。例如,他會探討某位官員如何通過修建水利設施,促進瞭農業生産;或者某位官員如何積極引進中原文化,豐富瞭當地的文化生活。這種將個體官吏置於更廣闊的社會經濟文化語境中進行考察的方法,使得本書的研究更具深度和廣度。而且,作者在論述過程中,引用的史料非常豐富,既有官方的史書,也有大量的齣土文獻,體現瞭其紮實的學術功底。這本書不僅為我提供瞭關於唐代西州官吏的知識,更啓發瞭我對曆史研究的多元化思考。
评分这两件文书中还有“给事郎行丞元泰”,其职官为高昌县丞,散官为给事郎(“车牛处置”文书中“给事郎”后所缺字当为“行”字)。“车牛处置”文书第8行记时间在垂拱三年四月,“人考入状”文书缺纪年,根据两件文书中元泰散官相同推测,两件文书时间应该相近。
评分我们将这两件文书中的“方”与前举“买鞍马事”及“勘当失盗事”中的“方”字相比,发现四件笔迹相同。既然四件都是高昌县文书,时间又都接近,签署笔迹也相同,因此可以下结论,此“方”为同一个人。“方”是否一直任高昌县令?由于前两件的签署未存“白”、“示”一类标志身份的用语,不能确认。但据唐代公文程式,牒文首先呈长官过目,由长官“付司”,“方”在此牒后直接批示,应为长官县令;又,此牒涉及失盗事,如前所述,狱讼应由县令亲自处理,然则“方”也应为长官;再有,调露元年(679)左右高昌县约有一位尉名“知过”,永淳元年(682)六月高昌县有一位尉名“闻”(皆见上文),“方”从上元三年(676)至永淳元年(682)八月皆在任上,其为县尉的可能性很小,也没有任何迹象证明其为县丞。因此,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方”为长官的可能性很大。这就是说,“方”从上元三年至垂拱三年一直任高昌县令。
评分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麴氏高昌王国,建立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地区)。西州位处西域东部内地通往西域的咽喉地带,是唐朝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唐朝在此实行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制度,同时建立了一个完整庞大的官吏队伍。这个官吏队伍分布在州(州郡、都督府)、县、军府、市、镇、戍、烽、乡里、城坊以及馆驿、长行坊等各级机构组织中,在唐朝统治西州乃至西域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毫无疑问,研究这个官僚队伍是我们研究西州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我们研究西州政治制度的基础。
评分行下守的原则,此处可以称做“行”的散官,只有朝议郎和承议郎,这两件文书中的“给事郎行丞元泰”,散官都为“给事郎”,估计两件文书时间相近,因此,两件文书中“方”的散官也应相同)。
评分我们将这两件文书中的“方”与前举“买鞍马事”及“勘当失盗事”中的“方”字相比,发现四件笔迹相同。既然四件都是高昌县文书,时间又都接近,签署笔迹也相同,因此可以下结论,此“方”为同一个人。“方”是否一直任高昌县令?由于前两件的签署未存“白”、“示”一类标志身份的用语,不能确认。但据唐代公文程式,牒文首先呈长官过目,由长官“付司”,“方”在此牒后直接批示,应为长官县令;又,此牒涉及失盗事,如前所述,狱讼应由县令亲自处理,然则“方”也应为长官;再有,调露元年(679)左右高昌县约有一位尉名“知过”,永淳元年(682)六月高昌县有一位尉名“闻”(皆见上文),“方”从上元三年(676)至永淳元年(682)八月皆在任上,其为县尉的可能性很小,也没有任何迹象证明其为县丞。因此,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方”为长官的可能性很大。这就是说,“方”从上元三年至垂拱三年一直任高昌县令。
评分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官僚体制高度发展,官僚队伍成为封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僚问题也成为史学研究的重点对象。然而,由于封建史家多以纪传体记史,达官贵人充盈史籍,地方卑官罕有记载,因此,造成中央官吏研究兴旺蓬勃,而地方官吏研究却相当薄弱的局面,这个问题在中古史研究领域尤其严重。唐西州官吏研究却得天独厚。一个世纪以来,吐鲁番出土了几千件唐代原始官府文书,披露了大量有关官府官吏的信息,为研究当地官吏问题提供了第一手宝贵资料,使我们研究西州官吏不仅成为必须,而且成为可能。本课题即以这些出土文书为主,兼采石刻墓志、敦煌文书、传世史籍,对唐西州官吏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考证。
评分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麴氏高昌王国,建立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地区)。西州位处西域东部内地通往西域的咽喉地带,是唐朝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唐朝在此实行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制度,同时建立了一个完整庞大的官吏队伍。这个官吏队伍分布在州(州郡、都督府)、县、军府、市、镇、戍、烽、乡里、城坊以及馆驿、长行坊等各级机构组织中,在唐朝统治西州乃至西域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毫无疑问,研究这个官僚队伍是我们研究西州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我们研究西州政治制度的基础。
评分行下守的原则,此处可以称做“行”的散官,只有朝议郎和承议郎,这两件文书中的“给事郎行丞元泰”,散官都为“给事郎”,估计两件文书时间相近,因此,两件文书中“方”的散官也应相同)。
评分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麴氏高昌王国,建立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地区)。西州位处西域东部内地通往西域的咽喉地带,是唐朝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唐朝在此实行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制度,同时建立了一个完整庞大的官吏队伍。这个官吏队伍分布在州(州郡、都督府)、县、军府、市、镇、戍、烽、乡里、城坊以及馆驿、长行坊等各级机构组织中,在唐朝统治西州乃至西域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毫无疑问,研究这个官僚队伍是我们研究西州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我们研究西州政治制度的基础。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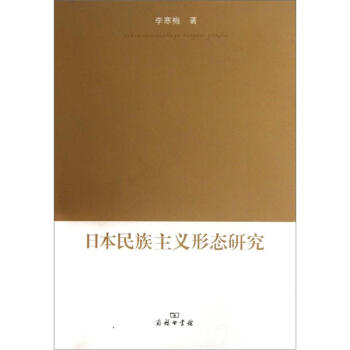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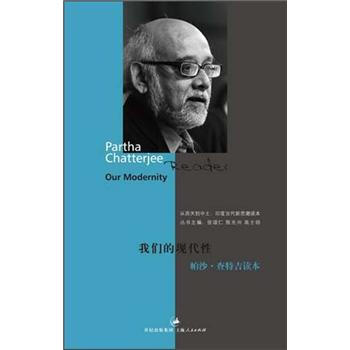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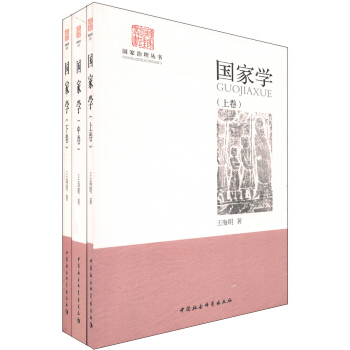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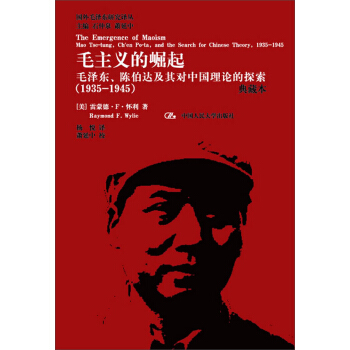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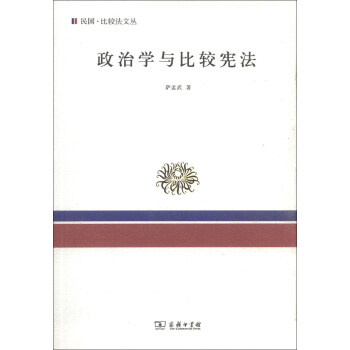
![国际学术前沿观察·黑弥撒:末世信仰与乌托邦的终结 [Black Mass(Apocalyptic Religion and the Death of Utopi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17527/rBEhU1NLT-AIAAAAAAEGylrlDTQAALwqAPps8wAAQbi07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