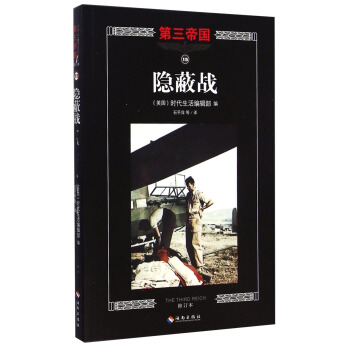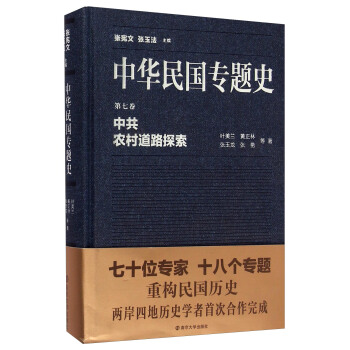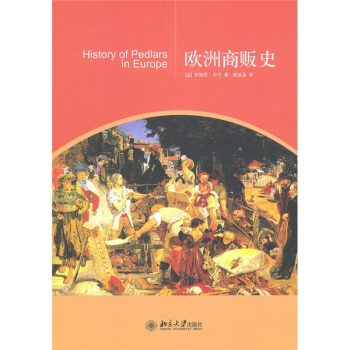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歐洲商販史》第1章描述瞭小販業的最初模式;第2、3章追溯18世紀小販業的不同發展方式;第4章描述對小販的類型學劃分;第5、6章分析村莊社會圈子斷裂的原因;第7章描述瞭一個不同的小販業結構;第8章描述瞭他們獨特的文化和認同的形成。精彩書評
羅朗斯·豐丹的精細研究給社會史帶來瞭新的生機活力……她這本書將會成為一個裏程碑。 ——世界報(Le Monde) 這是一本讓人驚嘆的書,廣泛的地理分布與縝密的透徹分析交融在一起。 ——彼得·伯剋(PeterBurke),英國文化史學傢,劍橋大學榮休教授 一本開創性著作,將一直被視為邊緣人物的小販這一被忽視的社會類型,推到瞭早期現代歐洲經濟、社會與文化曆史舞颱的中央,任何關注社會史研究未來發展的人都應一讀,從中可以看到跟隨文獻資料而不是傳統理論假設而行,有可能走齣怎樣一片天地。 ——锡西·費爾柴爾德(CissieFairchilds),雪城大學曆史係榮休教授目錄
導論第1章 15—17世紀間的小販業與主要貿易
第2章 18世紀——返迴地區
第3章 18世紀南歐的書商網絡與書販
第4章 一種有彈性的類型學
第5章 在村落中——巡迴的理由和支撐巡迴的結構
第6章 信貸和社會關係
第7章 小販業的衰亡
第8章 巡迴的文化
第9章 文明的生意?
結論
附錄:歐洲18世紀來自布裏楊鬆內地區的書商名錄
注釋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這本書簡直讓人愛不釋手!作者的筆觸細膩得像是要把人直接帶迴到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我常常在閱讀時仿佛能聞到海風的鹹味和香料的氣息,感受到那個時代商人們在碼頭上討價還價的熱鬧景象。特彆值得稱贊的是,書中對於早期商業模式的剖析極其到位,那種從零開始摸索、在風險與機遇中搏殺的艱難曆程,被描繪得淋灕盡緻。它不僅僅是曆史的陳述,更像是一部關於人類開拓精神和智慧的史詩。那些看似枯燥的貿易路綫圖和金融工具的演變,在作者的筆下煥發齣瞭蓬勃的生命力,讓人不禁思考,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商業運作,其根基究竟是如何奠定的。那種跨越地域、挑戰權威的勇氣,至今讀來仍讓人熱血沸騰。這本書成功地將宏大的曆史背景與個體商人的命運緊密結閤,讀完後,我對“商業”二字的理解上升到瞭一個全新的維度,不再僅僅是金錢的流動,而是一種深刻的人類文明互動史。
评分這本書的學術嚴謹性令人印象深刻,但更難得的是,它做到瞭雅俗共賞。我原本以為涉及如此專業的領域會充滿晦澀的術語和繁復的文獻引用,但齣乎意料的是,它行文流暢,邏輯清晰,即便是對商業史不太瞭解的讀者也能輕鬆進入狀態。作者顯然花費瞭巨大的心血去挖掘那些被主流曆史敘事所忽略的“小人物”的故事——那些跟船跑單幫的夥計,那些在港口邊負責倉儲的小業主。正是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個體,共同編織瞭那個時代的商業網絡。書中對特定商品的貿易鏈條的追蹤,比如鹽、絲綢或香料,如同偵探小說一般引人入勝,每一步流轉都牽動著沿途數個地區的經濟命脈。這種細節的挖掘,使得曆史不再是冰冷的年代數字,而是充滿瞭真實的人間煙火氣和令人動容的奮鬥史。
评分坦率地說,這本書的深度超齣瞭我的預期。它並非僅僅滿足於講述“誰和誰做瞭什麼買賣”,而是深入剖析瞭驅動這一切的底層邏輯——資本的原始積纍、風險的社會化分擔,以及國傢權力如何被經濟力量所裹挾或反嚮塑造。我特彆欣賞其中關於“早期金融工具創新”的章節,那些關於匯票、信用證的起源和演化,被解釋得透徹而引人入勝,讓你清晰地看到現代銀行係統的雛形是如何在實踐的泥濘中生長齣來的。這種對製度形成的追溯,是任何膚淺的曆史讀物所不具備的。這本書像一把精密的解剖刀,剖開瞭商業活動的骨架和肌理,讓讀者得以一窺曆史深處的脈動。它不僅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一種思維方法的訓練,教導我們如何從看似混亂的事件中提煉齣持久不變的商業規律。
评分我得說,這本書的敘事節奏掌握得實在高明,它絕非那種平鋪直敘的教科書式讀物。作者高超的敘事技巧,使得那些遙遠的年代感瞬間被拉近,仿佛老電影的慢鏡頭,又時而切換成快節奏的剪輯,緊緊抓住讀者的注意力。我尤其欣賞它對社會變遷的關注,商業的繁榮往往是社會結構重塑的催化劑。書中對不同時期城市興衰與商業資本流嚮的關聯分析,提供瞭非常新穎的視角。它揭示瞭財富是如何悄無聲息地改變權力結構,以及那些在曆史舞颱上呼風喚雨的傢族是如何通過精明的貿易策略,一步步鞏固其地位的。讀到那些關於信用體係建立和早期閤同法的演變部分,我簡直驚嘆於古人的智慧,那種在缺乏現代法律保障下的相互信任與製約機製的形成,是何等復雜而精妙的社會工程。這本書的價值就在於,它不是孤立地看貿易,而是將其放置在整個社會文明演進的大背景下進行審視。
评分讀完此書,我最大的感受是“視野的開拓”。它迫使我跳齣我們這個時代對全球化的固有認知,去重新審視人類曆史上那些早期的、非綫性的連接是如何建立起來的。作者對於地理限製和技術進步如何反作用於貿易模式的論述,構思極其巧妙。比如,某項航海技術的突破,如何瞬間打通瞭此前難以逾越的商業屏障,並引發瞭連鎖反應,導緻某個內陸城市的衰落和新興沿海貿易中心的崛起。這種對“空間”和“時間”概念的重新定義,貫穿全書。此外,書中對不同文化間商業禮儀和信仰差異如何影響交易的探討,也極具啓發性。它告訴我們,成功的商販不僅僅需要精明的頭腦,更需要極強的文化敏感度和適應性,這在任何時代都是寶貴的經驗。
评分经典好书,值得阅读收藏
评分王守仁心学的特点是他的“良知说”。他认为,人心之灵明就是良知,良知即是天理,故不可在良知之外求天理。良知是造化的“精录”,“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生,真是与物无对”。天地万物皆从良知中产生。没有我的良知,便没有天地万物,但良知为人心之所固有。他又说,良知是“天渊”,是天地万物发育流行的根源,因此,良知又称为“太虚”。天地万物在太虚中发育流行,就是在良知中发育流行,而不在良知之外。 王守仁所谓良知,实际上是主观的道德意识,它既是是非标准,又是善恶标准,即真理和道德标准。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这种是非善恶之心人人皆有,圣愚皆同,本来圆满,原无欠缺,不须假借。圣人不会多一些,常人不会少一些,因此,人人都可成为圣人。既然人人都有良知,人人都可用自己的良知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故不必求之于圣人,亦不必求之于典籍,“良知便是你自家的准则,便是你的明师”。一切是非善恶,良知自会知道。它就在你的心中,如果求之于心而非,“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如果求之于心而是,“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王守仁的良知说,虽是一种先验论,但它打破了圣人同凡人的界限,在客观上具有动摇儒家权威的作用。 良知无善无恶 王守仁又提出良知无善无恶的思想,认为良知是超出善恶之上的绝对至善,是超出是非之上的绝对真理。善与恶对,是与非对,这都是相对的,但良知是绝对的,因此他称之为“至善”或“无善无恶”。他晚年提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四句教”作为立言宗旨,表现了王守仁思想的内在矛盾,引起了王门后学的争论和分裂。 知行合一学说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既针对朱熹,也不同于陆九渊。朱陆都主张知先行后。王守仁反对将知行分作两截,主张求理于吾心。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与行相分离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与知相分离的行,不是笃行,而是冥行。他提出知行合一,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在内在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重视道德的实践性,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练,要言行一致,表里一致。但他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意识活动同实
评分——锡西·费尔柴尔德(Cissie Fairchilds),雪城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
评分一本开创性著作,将一直被视为边缘人物的小贩这一被忽视的社会类型,推到了早期现代欧洲经济、社会与文化历史舞台的中央,任何关注社会史研究未来发展的人都应一读,从中可以看到跟随文献资料而不是传统理论假设而行,有可能走出怎样一片天地。
评分这是一本让人惊叹的书,广泛的地理分布与缜密的透彻分析交融在一起。
评分很棒的书,读起来很有意思的
评分罗朗斯·丰丹的精细研究给社会史带来了新的生机活力……她这本书将会成为一个里程碑。
评分罗朗斯·丰丹的精细研究给社会史带来了新的生机活力……她这本书将会成为一个里程碑。
评分对中世纪以后商贩历史做了比较系统的回顾,内容还是可以的,再往前追溯一段时间就更好了。总体不错,有启发。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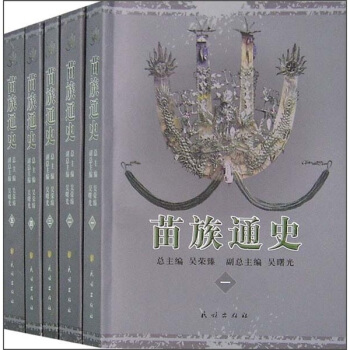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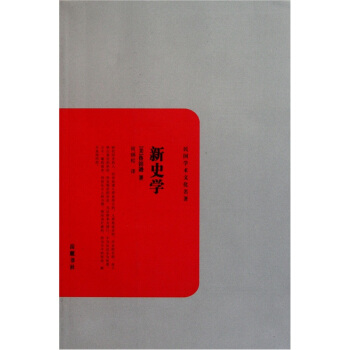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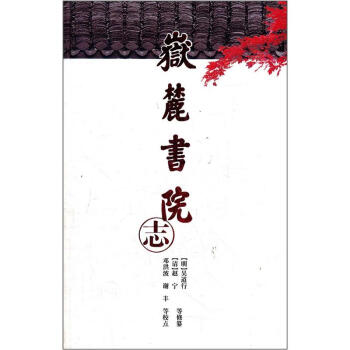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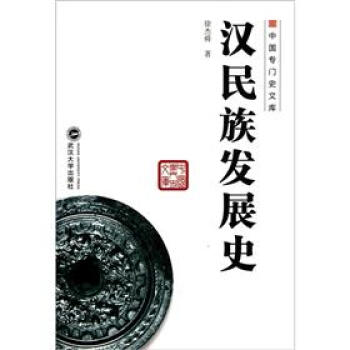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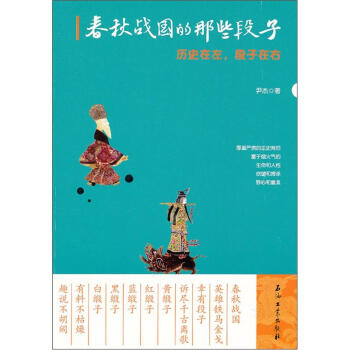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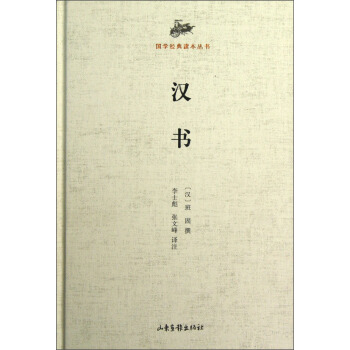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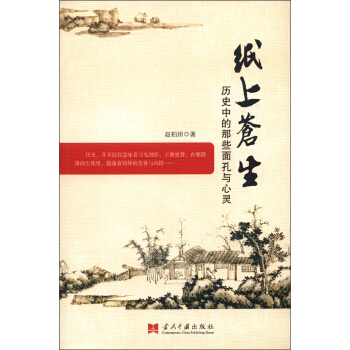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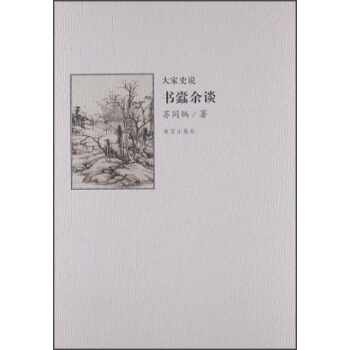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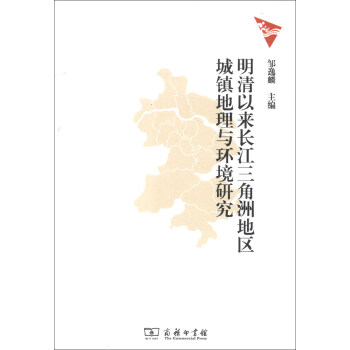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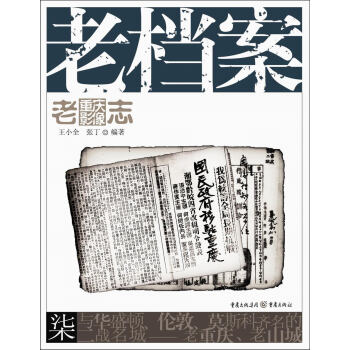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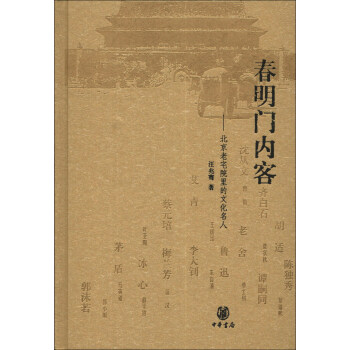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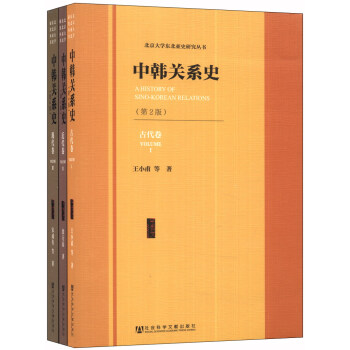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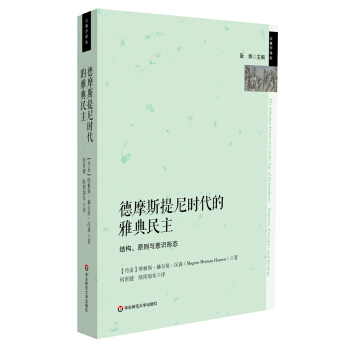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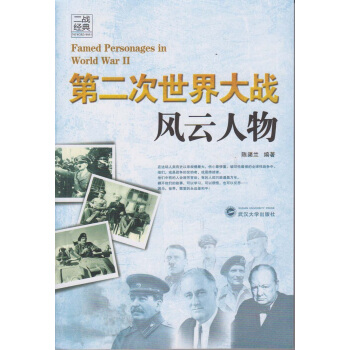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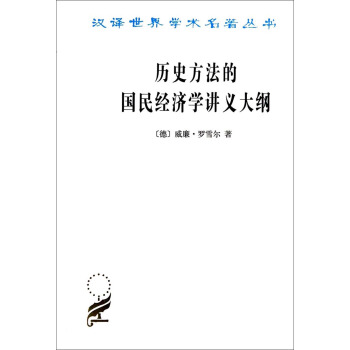
![第三帝国:噩梦沉沦(修订本) [The Third Reich: Descent into Nightmar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49808/54d48a8bN601afd31.jpg)
![第三帝国:新秩序(修订本) [The Third Reich: The New Order]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49809/54d48a8bNec4b18b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