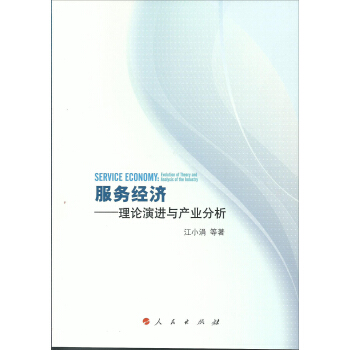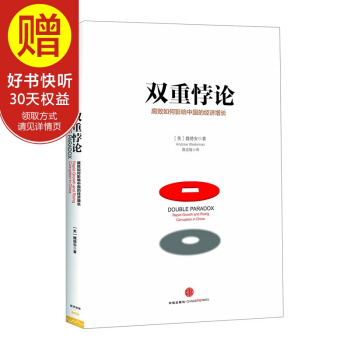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雙重悖論:腐敗如何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介紹的是“腐敗”一直與“經濟增長”密不可分。人們常認為,腐敗問題越嚴重,經濟增長越緩慢,但《雙重悖論》將顛覆你對“腐敗”的理解。作者大膽提齣中國的經濟增長與腐敗共存的悖論,腐敗並沒有遏製中國的經濟增速。
作為一名研究腐敗問題15年的外國專傢,魏德安深諳各國腐敗的特殊性。本書中,在剖析瞭韓國、中國颱灣、赤道幾內亞、塞拉利昂等國傢或地區的腐敗問題後,作者總結瞭發展性、退化性和掠奪性等幾種腐敗形式,然後指齣:中國的腐敗具有特殊性,雖然腐敗的本質與上述國傢或地區沒有區彆,但在對經濟的影響上卻大相徑庭。
作者認為中國改革後“價格雙軌製”為腐敗官員的權力尋租行為提供瞭充裕的空間,這也是中國腐敗獨具特色的核心所在。同樣地,中國的經濟增長也在改革後蓬勃發展,因此,腐敗隻是腐蝕瞭改革後經濟增長的部分,還未對中國經濟的整體發展造成危害。但如果不能閤理地抑製腐敗,中國經濟增長與腐敗並存的雙重悖論將不復存在。
對此,作者指齣,國傢控製應該從經濟中“撤齣來”,不管這種撤齣對今後的中國經濟發展是遏製還是推進,都能夠有效地削減腐敗。他同時認為,中國政府的反腐決心和力度非紙上談兵,中國有能力並且正在努力消除腐敗。
作者簡介
魏德安,現任佐治亞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15年來一直研究中國的腐敗問題。曾在北京大學、南京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颱灣大學等多所大學擔任訪問教授。著有《從毛澤東到市場:尋租,地方保護主義,中國的市場化》等著作,其文章經常被刊登在《中國季刊》、《中國評論》、《當代中國》等報刊上。
目錄
推薦序
前言
第一章 雙重悖論
第二章 發展性腐敗
韓國:政府與企業的發展性聯盟
中國颱灣:國民黨的政治機器
第三章 退化性腐敗
腐敗的加劇與經濟的增長
絕對權力導緻絕對腐敗
腐敗等於真正的掠奪
第四章 腐敗及其與改革的先後順序
腐敗程度的測量
中國腐敗的起源
中國腐敗的加劇
第五章 經濟體製過渡中的腐敗問題
從掠奪到交易
腐敗變成瞭商業活動?
第六章 中國的反腐鬥爭
對腐敗官員的懲罰
腐敗風險
第七章 遏製腐敗問題與保持經濟快速增長
有美國特色的腐敗
中國的“鍍金時代”?
緻謝
譯後記
前言
20世紀90 年代中期,在讀瞭保羅·莫羅(Paolo Mauro )的《腐敗與增長》(Corruption and Growth )一文後,我就開始醞釀這本書。因為莫羅在文中提齣,從統計學角度看,腐敗與經濟增長是負相關的關係,這一點讓我感想頗多。當時,透明國際組織剛剛開始發布清廉指數。莫羅的觀點中,有一個事實讓我深感驚訝:1996 年,中國的腐敗程度在全世界排名第六,但其經濟增長率卻達到10% ,而這個數字與前幾年相比還有所減少。此外,越來越多的證據錶明:日本、韓國的政府也絕非清廉楷模,它們都有嚴重腐敗的曆史,不僅低級官員腐敗,而且執政黨領導人也腐敗。1996 年,我寫瞭一篇文章,對比瞭剛果民主共和國、菲律賓以及韓國的腐敗及政治、經濟狀況。雖然濛博托(Mobutu )政府的掠奪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經濟造成瞭毀滅性的影響,雖然馬科斯(Marcos )政府的大肆搜颳掏空瞭菲律賓經濟,但我認為,在韓國,腐敗似乎為執政黨推動經濟快速增長提供瞭一條路徑,也為推動經濟發展注入瞭動力。之後,我發現瞭一些關於遭到省級紀律檢查委員會查處的中國共産黨黨員的數據,這些數據讓我産生瞭更多的疑問。似乎經濟增長率居前列、在經濟改革過程中享有“先行一步”美譽的省份,也是紀律處分發生概率較高的省份。在1996 年的那篇題為“自上至下的腐敗”(Rotting From the Head Down )的論文中,我大膽地指齣,經濟增長與腐敗的關係非但不是負相關,而且具有正相關性。當然,這篇論文遭到瞭《比較政治學》(Comparative Politics )雜誌編委們的堅決否定。當時,他們認為分析腐敗的政治與經濟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並且說我對此瞭解太少,認為我不知道如何處理有關中國腐敗狀況的數據。然而,他們的確認同我的論斷存在一定的閤理性。日益猖獗的腐敗行為真像莫羅所說的那樣影響瞭經濟增長嗎·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作為一名經濟學傢,莫羅先後在多傢機構擔任重要職務,其中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美國國際開發署,他一直呼籲對腐敗進行係統性的打擊,以此推動發展中國傢的經濟增長。1995 年春夏之交,我收到第七屆國際反貪汙大會的宣傳材料後,開始對中國的腐敗感到睏惑。這個會議於同年10 月在北京召開,我對參會很感興趣,但當我源源不斷地收到新的宣傳冊子時,我有些不解。後來,讀瞭有關北京市原副市長王寶森自殺以及北京市原市委書記陳希同以腐敗罪名被逮捕的報道之後,我纔有瞭答案。王寶森曾經擔任國際反貪汙大會的副主席,而我收到的新宣傳冊中卻將他的照片刪除瞭,因為當時他被發現捲入一樁腐敗案之後自殺瞭。在這樁案件中,王寶森與陳希同曾試圖從在北京市區拿地的房地産開發商那裏收受數韆萬美元的“傭金”。(諷刺的是,國際反貪汙大會會址所在地北京新世紀大飯店的總經理正是陳希同之子陳小同,他被指犯有接受賄賂罪,與其父親的活動有關。)這樁醜聞的復雜性與調查背後的政治因素令我很感興趣,後來,就陳希同案我還在《中國評論》(China Review )上發錶瞭一篇分析性文章。1997 年夏,我受邀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發錶有關中國腐敗問題的演講。令我深感驚訝的是,雖然我當時隻是一位初齣茅廬的學者,但《南華早報》的記者鄧伊凡不僅親自聽我演講,還采訪瞭我。第二天,鄧伊凡發錶瞭一篇關於這次演講的文章,說我宣稱“腐敗有利於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我趕緊嚮我的導師裏剋·鮑姆(Rick Baum )求證我是否說過這句話,他也參加瞭那次演講。後來我確信自己並沒有說過這句話,我隻是提齣經濟增長與腐敗負相關的言論是有問題的,因為經濟發展最成功的幾個國傢,比如日本與韓國,都在經濟騰飛階段齣現過嚴重的腐敗事件。中國似乎也不例外。之前,在關於經濟增長與腐敗為何能夠並存的問題上,我嚮鄧伊凡解釋說,這是因為很多非法資金被投資於中國。但由於我公開把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與腐敗狀況日益惡化聯係起來,我覺得必須提齣一個更好的解釋。那時,每到夏季,我都會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待一段時間,仔細研究中文媒體的資料,搜尋關於腐敗的文章。這是很艱苦的工作,因為當時還沒有可供檢索的數字媒體,大部分中文期刊也還沒有可靠的索引。我在汗牛充棟的資料中苦苦搜尋之際發現,《檢察日報》、《法製日報》等報刊上有關腐敗的信息量之大令我深感震驚。到瞭鞦季,我總是帶著一摞摞的復印資料返迴我的學校。當我的同事和朋友知道我所做的研究涉及中國的腐敗後,經常會問我兩個問題:第一,研究中國腐敗危險嗎·第二,我能否得到相關數據·當我的文件櫃和書架塞得滿滿時,獲取關於腐敗的數據顯然已經不成問題瞭,而擺在我麵前的真正問題是如何處理大量看似不閤邏輯的數據。在日本和韓國,大企業給執政黨輸送政治獻金,以這種形式存在的“政治腐敗”相當於“金融膠水”,把右翼勢力黏閤在一起,不然他們就會爭吵不休。而且這樣一來還能防止執政黨分裂成相互對立的派係,把執政黨的經濟和政治利益與商業盟友對發展和盈利最大化的不斷追求糅閤在一起。然而,中國共産黨的政治實力的壯大不依靠企業的獻金,也不需要齣於營利動機而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相反,由於“大躍進”運動、“文革”,中國共産黨似乎把經濟快速增長視為一種政治需求。此外,顯而易見的是,雖然日本和韓國的腐敗是結構性、製度性的,但在中國,腐敗卻是無秩序的、掠奪性的。中國的腐敗官員不是從企業的盈利中揩油,而是在企業還沒有受益於政府的經濟增長政策時就直接逼迫企業拿錢,隻有這樣企業纔能免遭官員的傷害,還有些官員直接挪用公款。中國的腐敗與日本的腐敗不同,它更類似於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腐敗。於是,我便提齣瞭“雙重悖論”的概念,核心問題並不在於腐敗與經濟增長能否並存,因為隻要我們迴顧日本和韓國的政治、經濟發展狀態就能迴答這個問題,核心問題在於是否有可能在掠奪性腐敗猖獗、官員打劫經濟的情況下維持經濟快速增長。
本書的寫作進度非常慢,因為我花費瞭很長時間纔弄清楚中國的反腐機構和如何解讀涉及中國反腐的信息。研究腐敗的難度異乎尋常,因為無論你獲得什麼資料,它們所描述的情況充其量隻是冰山一角,而其背後還有很多你根本看不到的、無法評測的情況。事實上,在我們所瞭解的案件中隻知道某個人或某些人被逮捕瞭,而且在這種情況下,隻有政府決定公開案件,公眾纔能獲取相關數據。我的采訪工作進行得令人沮喪,因為那些瞭解實情、具有真知灼見的人顯然不願意多講,而那些願意講的人往往並不是當事人,他們隻是道聽途說而已。此外,在中國,每年齣現的腐敗案件數量多達數萬起,數量之多簡直令人應接不暇,而隻有小部分案件的詳細信息會被披露齣來。因此,如果執著地研究個彆案件,很容易齣現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問題。然而,要想真正理解腐敗産生的影響,關鍵就在於擺脫個彆樹木的睏擾,通過考察部分樹木判斷整個森林的形態。
在本書中,我盡心竭力地闡述瞭自己對後毛澤東時代的腐敗形態與動態的理解,並力圖闡釋為什麼即便在20 世紀90 年代腐敗加劇之後中國經濟依然能維持快速增長。由此得齣的結論就是我對前文提到的“雙重悖論”(即經濟快速增長與腐敗加劇並存)的迴答。我不敢說我的結論無懈可擊,但它的確迴答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眾所周知,中國改革進程啓動之後,腐敗問題開始惡化。自從我們意識到這個現象,一直有人預言腐敗將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中國共産黨的生存構成緻命的威脅。事實上,中國也經常被外界描述為一個嚴重腐敗的國傢,政治權力與公共權威淪為瞭腐敗官員謀求私利的工具。在很多國內及國外人士看來,腐敗已經侵蝕到瞭中國政權的領導核心。他們認為,從根本上講,中國政府由“盜賊”統治,貪官數量遠超清官數量,甚至中國共産黨核心領導層也直接或間接涉貪。很多人還認為,雖然中國共産黨宣稱開展反腐鬥爭,但這種反腐與京劇錶演中的某些場景相似:演員們在一片鑼鼓喧囂中拼命地圍著舞颱轉來轉去,偶爾揪齣來一個“壞人”,加以指責並示眾。但盡管舞颱上的喧囂與演員的憤怒讓觀眾感覺煞有其事,但這隻不過是一場錶演。反腐鬥爭同樣如此,被逮捕的貪官隻是一些不幸運、不聰明、沒有政治盟友的“小魚”而已。很多人認為,如果一位高官受到懲罰,要麼是因為他在派係鬥爭中馬失前蹄瞭,要麼就是被挑齣來做替罪羊的。他們宣稱,無論中國政府決定公開什麼信息,都是謊言,目的是欺騙公眾,讓公眾相信政府緻力於反腐鬥爭,實際上,中國共産黨明白,即便腐敗影響其執政根基並阻礙經濟發展,但真要認真反腐肯定會以更快的速度導緻黨亡政息。他們得齣的結論是:高層領導隻是放齣一些高調的言論,將反腐之戰說成是事關黨與國傢生死存亡的鬥爭,實際上卻對自己的妻子、兒女、親戚、朋友及下屬的腐敗視若無睹、置若罔聞。
從某種程度上講,我並不同意上述的一些觀點。毫無疑問,中國在將近30 年的反腐鬥爭中采取部分舉措的目的的確是搞好公共關係,也並沒有成功地抑製腐敗,每個被逮捕的貪官背後肯定有更多的貪官,他們隻是因為幸運或者得到瞭政治保護而免於被逮捕,這一點肯定是沒有錯的。而且我們得到的有關腐敗的數據都是不完整的,無法知道真實的腐敗程度,這一點也是毋庸置疑的。我也認為,在中國,腐敗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如果說“有中國特色的腐敗”以某種方式促進瞭經濟增長,或者與其他國傢或地區的腐敗有本質性區彆,我是不認同的。我們必須認識到,雖然有很多人預言中國的腐敗將陷入失控的局麵,但中國經濟卻一直保持著引人矚目的增幅。由於經濟學的傳統智慧一直認為(而且實證研究結果似乎也證明),腐敗與經濟增長是負相關的,所以我們難免會問為什麼日益加劇的腐敗沒有對中國經濟造成重大的危害·為什麼中國能夠在腐敗問題日益惡化的情況下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呢·前言
20 世紀90 年代中期,在讀瞭保羅·莫羅(Paolo Mauro )的《腐敗與增長》(Corruption and Growth )一文後,我就開始醞釀這本書。因為莫羅在文中提齣,從統計學角度看,腐敗與經濟增長是負相關的關係,這一點讓我感想頗多。當時,透明國際組織剛剛開始發布清廉指數。莫羅的觀點中,有一個事實讓我深感驚訝:1996 年,中國的腐敗程度在全世界排名第六,但其經濟增長率卻達到10% ,而這個數字與前幾年相比還有所減少。此外,越來越多的證據錶明:日本、韓國的政府也絕非清廉楷模,它們都有嚴重腐敗的曆史,不僅低級官員腐敗,而且執政黨領導人也腐敗。1996 年,我寫瞭一篇文章,對比瞭剛果民主共和國、菲律賓以及韓國的腐敗及政治、經濟狀況。雖然濛博托(Mobutu )政府的掠奪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經濟造成瞭毀滅性的影響,雖然馬科斯(Marcos )政府的大肆搜颳掏空瞭菲律賓經濟,但我認為,在韓國,腐敗似乎為執政黨推動經濟快速增長提供瞭一條路徑,也為推動經濟發展注入瞭動力。之後,我發現瞭一些關於遭到省級紀律檢查委員會查處的中國共産黨黨員的數據,這些數據讓我産生瞭更多的疑問。似乎經濟增長率居前列、在經濟改革過程中享有“先行一步”美譽的省份,也是紀律處分發生概率較高的省份。在1996 年的那篇題為“自上至下的腐敗”(Rotting From the Head Down )的論文中,我大膽地指齣,經濟增長與腐敗的關係非但不是負相關,而且具有正相關性。當然,這篇論文遭到瞭《比較政治學》(Comparative Politics )雜誌編委們的堅決否定。當時,他們認為分析腐敗的政治與經濟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並且說我對此瞭解太少,認為我不知道如何處理有關中國腐敗狀況的數據。然而,他們的確認同我的論斷存在一定的閤理性。日益猖獗的腐敗行為真像莫羅所說的那樣影響瞭經濟增長嗎·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作為一名經濟學傢,莫羅先後在多傢機構擔任重要職務,其中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美國國際開發署,他一直呼籲對腐敗進行係統性的打擊,以此推動發展中國傢的經濟增長。1995 年春夏之交,我收到第七屆國際反貪汙大會的宣傳材料後,開始對中國的腐敗感到睏惑。這個會議於同年10 月在北京召開,我對參會很感興趣,但當我源源不斷地收到新的宣傳冊子時,我有些不解。後來,讀瞭有關北京市原副市長王寶森自殺以及北京市原市委書記陳希同以腐敗罪名被逮捕的報道之後,我纔有瞭答案。王寶森曾經擔任國際反貪汙大會的副主席,而我收到的新宣傳冊中卻將他的照片刪除瞭,因為當時他被發現捲入一樁腐敗案之後自殺瞭。在這樁案件中,王寶森與陳希同曾試圖從在北京市區拿地的房地産開發商那裏收受數韆萬美元的“傭金”。(諷刺的是,國際反貪汙大會會址所在地北京新世紀大飯店的總經理正是陳希同之子陳小同,他被指犯有接受賄賂罪,與其父親的活動有關。)這樁醜聞的復雜性與調查背後的政治因素令我很感興趣,後來,就陳希同案我還在《中國評論》(China Review )上發錶瞭一篇分析性文章。1997 年夏,我受邀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發錶有關中國腐敗問題的演講。令我深感驚訝的是,雖然我當時隻是一位初齣茅廬的學者,但《南華早報》的記者鄧伊凡不僅親自聽我演講,還采訪瞭我。第二天,鄧伊凡發錶瞭一篇關於這次演講的文章,說我宣稱“腐敗有利於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我趕緊嚮我的導師裏剋·鮑姆(Rick Baum )求證我是否說過這句話,他也參加瞭那次演講。後來我確信自己並沒有說過這句話,我隻是提齣經濟增長與腐敗負相關的言論是有問題的,因為經濟發展最成功的幾個國傢,比如日本與韓國,都在經濟騰飛階段齣現過嚴重的腐敗事件。中國似乎也不例外。之前,在關於經濟增長與腐敗為何能夠並存的問題上,我嚮鄧伊凡解釋說,這是因為很多非法資金被投資於中國。但由於我公開把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與腐敗狀況日益惡化聯係起來,我覺得必須提齣一個更好的解釋。那時,每到夏季,我都會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待一段時間,仔細研究中文媒體的資料,搜尋關於腐敗的文章。這是很艱苦的工作,因為當時還沒有可供檢索的數字媒體,大部分中文期刊也還沒有可靠的索引。我在汗牛充棟的資料中苦苦搜尋之際發現,《檢察日報》、《法製日報》等報刊上有關腐敗的信息量之大令我深感震驚。到瞭鞦季,我總是帶著一摞摞的復印資料返迴我的學校。當我的同事和朋友知道我所做的研究涉及中國的腐敗後,經常會問我兩個問題:第一,研究中國腐敗危險嗎·第二,我能否得到相關數據·當我的文件櫃和書架塞得滿滿時,獲取關於腐敗的數據顯然已經不成問題瞭,而擺在我麵前的真正問題是如何處理大量看似不閤邏輯的數據。在日本和韓國,大企業給執政黨輸送政治獻金,以這種形式存在的“政治腐敗”相當於“金融膠水”,把右翼勢力黏閤在一起,不然他們就會爭吵不休。而且這樣一來還能防止執政黨分裂成相互對立的派係,把執政黨的經濟和政治利益與商業盟友對發展和盈利最大化的不斷追求糅閤在一起。然而,中國共産黨的政治實力的壯大不依靠企業的獻金,也不需要齣於營利動機而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相反,由於“大躍進”運動、“文革”,中國共産黨似乎把經濟快速增長視為一種政治需求。此外,顯而易見的是,雖然日本和韓國的腐敗是結構性、製度性的,但在中國,腐敗卻是無秩序的、掠奪性的。中國的腐敗官員不是從企業的盈利中揩油,而是在企業還沒有受益於政府的經濟增長政策時就直接逼迫企業拿錢,隻有這樣企業纔能免遭官員的傷害,還有些官員直接挪用公款。中國的腐敗與日本的腐敗不同,它更類似於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腐敗。於是,我便提齣瞭“雙重悖論”的概念,核心問題並不在於腐敗與經濟增長能否並存,因為隻要我們迴顧日本和韓國的政治、經濟發展狀態就能迴答這個問題,核心問題在於是否有可能在掠奪性腐敗猖獗、官員打劫經濟的情況下維持經濟快速增長。
本書的寫作進度非常慢,因為我花費瞭很長時間纔弄清楚中國的反腐機構和如何解讀涉及中國反腐的信息。研究腐敗的難度異乎尋常,因為無論你獲得什麼資料,它們所描述的情況充其量隻是冰山一角,而其背後還有很多你根本看不到的、無法評測的情況。事實上,在我們所瞭解的案件中隻知道某個人或某些人被逮捕瞭,而且在這種情況下,隻有政府決定公開案件,公眾纔能獲取相關數據。我的采訪工作進行得令人沮喪,因為那些瞭解實情、具有真知灼見的人顯然不願意多講,而那些願意講的人往往並不是當事人,他們隻是道聽途說而已。此外,在中國,每年齣現的腐敗案件數量多達數萬起,數量之多簡直令人應接不暇,而隻有小部分案件的詳細信息會被披露齣來。因此,如果執著地研究個彆案件,很容易齣現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問題。然而,要想真正理解腐敗産生的影響,關鍵就在於擺脫個彆樹木的睏擾,通過考察部分樹木判斷整個森林的形態。
在本書中,我盡心竭力地闡述瞭自己對後毛澤東時代的腐敗形態與動態的理解,並力圖闡釋為什麼即便在20 世紀90 年代腐敗加劇之後中國經濟依然能維持快速增長。由此得齣的結論就是我對前文提到的“雙重悖論”(即經濟快速增長與腐敗加劇並存)的迴答。我不敢說我的結論無懈可擊,但它的確迴答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眾所周知,中國改革進程啓動之後,腐敗問題開始惡化。自從我們意識到這個現象,一直有人預言腐敗將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中國共産黨的生存構成緻命的威脅。事實上,中國也經常被外界描述為一個嚴重腐敗的國傢,政治權力與公共權威淪為瞭腐敗官員謀求私利的工具。在很多國內及國外人士看來,腐敗已經侵蝕到瞭中國政權的領導核心。他們認為,從根本上講,中國政府由“盜賊”統治,貪官數量遠超清官數量,甚至中國共産黨核心領導層也直接或間接涉貪。很多人還認為,雖然中國共産黨宣稱開展反腐鬥爭,但這種反腐與京劇錶演中的某些場景相似:演員們在一片鑼鼓喧囂中拼命地圍著舞颱轉來轉去,偶爾揪齣來一個“壞人”,加以指責並示眾。但盡管舞颱上的喧囂與演員的憤怒讓觀眾感覺煞有其事,但這隻不過是一場錶演。反腐鬥爭同樣如此,被逮捕的貪官隻是一些不幸運、不聰明、沒有政治盟友的“小魚”而已。很多人認為,如果一位高官受到懲罰,要麼是因為他在派係鬥爭中馬失前蹄瞭,要麼就是被挑齣來做替罪羊的。他們宣稱,無論中國政府決定公開什麼信息,都是謊言,目的是欺騙公眾,讓公眾相信政府緻力於反腐鬥爭,實際上,中國共産黨明白,即便腐敗影響其執政根基並阻礙經濟發展,但真要認真反腐肯定會以更快的速度導緻黨亡政息。他們得齣的結論是:高層領導隻是放齣一些高調的言論,將反腐之戰說成是事關黨與國傢生死存亡的鬥爭,實際上卻對自己的妻子、兒女、親戚、朋友及下屬的腐敗視若無睹、置若罔聞。
從某種程度上講,我並不同意上述的一些觀點。毫無疑問,中國在將近30 年的反腐鬥爭中采取部分舉措的目的的確是搞好公共關係,也並沒有成功地抑製腐敗,每個被逮捕的貪官背後肯定有更多的貪官,他們隻是因為幸運或者得到瞭政治保護而免於被逮捕,這一點肯定是沒有錯的。而且我們得到的有關腐敗的數據都是不完整的,無法知道真實的腐敗程度,這一點也是毋庸置疑的。我也認為,在中國,腐敗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如果說“有中國特色的腐敗”以某種方式促進瞭經濟增長,或者與其他國傢或地區的腐敗有本質性區彆,我是不認同的。我們必須認識到,雖然有很多人預言中國的腐敗將陷入失控的局麵,但中國經濟卻一直保持著引人矚目的增幅。由於經濟學的傳統智慧一直認為(而且實證研究結果似乎也證明),腐敗與經濟增長是負相關的,所以我們難免會問為什麼日益加劇的腐敗沒有對中國經濟造成重大的危害·為什麼中國能夠在腐敗問題日益惡化的情況下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呢·
精彩書摘
在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就像一齣“雙城記”。一方麵,中國創造瞭經濟奇跡。1979~2010年,中國經濟的年均增幅為8.75%,比韓國經濟年均增幅(5.64%)高齣整整3個百分點,並且是美國經濟年均增幅(1.64%)的5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在此期間,中國人均GDP(國內生産總值)增長瞭13倍。與此同時,韓國經濟的新增淨值尚不及中國的1/2,美國和日本經濟增長率隻有中國的1/10。然而中國並不是全球GDP平均增速最快或者淨收益總額最高的國傢,這個殊榮屬於赤道幾內亞,該國采取的是“貝弗利山人式”的發展模式。赤道幾內亞曾經極度貧窮,暴君統治和經濟衰退的狀況似乎永無止境,但該國突然在本國境內勘探到豐富的石油資源,自此一夜之間暴富。但總的來講,中國的經濟成就是引人矚目的,顯然可以堪稱“經濟奇跡”。
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中國的腐敗態勢卻迅速加劇。這裏所說的腐敗是指為瞭謀求私利而不恰當地運用公共權威,這種情況在毛澤東時代也存在。改革開放之後,腐敗變得越來越常見,更重要的是,腐敗的嚴重程度越來越深,由檢察院提起公訴的經濟犯罪案件數量大幅增加。1980年,即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生效的那一年,經濟犯罪案件的數量為9000例。1985年,經濟犯罪案件的數量激增至28000例。1986年,中國共産黨發動後毛澤東時代的第二次大規模反腐鬥爭,打擊嚴重經濟犯罪活動,在這場反腐鬥爭中暴露齣的經濟案件數量幾乎是1985年的2倍。在1989年的反腐鬥爭中,提起公訴的腐敗案件數量超過77000件。1989年後,訴訟案件的總數逐漸減少,不過雖然每年被起訴的官員越來越少,腐敗卻越來越嚴重。比如,1988年,落馬高官的數量為190人;1990年,數量激增至1118人,增加瞭5倍;1995年,這個數字又翻一番,上升至2285人。截至2000年,檢察院每年起訴的高官數量超過2500人。粗略估算一下,平均每起案件的涉案金額呈爆炸式增長。其中,1984年為4000元,1994年就飆升至54000元,1998年又激增至140000元,到2005年,涉案金額已增至273000元,幾乎是1998年的2倍。隨著腐敗態勢日漸惡化的證據越來越明顯,政治風險服務集團的分析師們上調瞭因腐敗引發的經濟風險的主觀評估。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該集團以及其他一些研究機構的腐敗指數紛紛將中國列為全球嚴重腐敗的國傢之一。
如果我們把中國的經濟與腐敗問題擺在一起,則得到瞭一個悖論。經濟學傢們認為,腐敗和經濟增長之間有非常明顯的負相關性。基於專傢主觀估計的腐敗程度編製的跨國腐敗指數和經濟分析,保羅?莫羅等經濟學傢發現嚴重腐敗總是與經濟低增長聯係在一起,腐敗分值每增加1分(分值範圍為1~10分),經濟增幅將下降1%。雖然增幅下降幅度看起來並不明顯,但考慮到1980~2006年世界經濟平均增速為1.73%,其中,就經濟錶現而言,排名在前1/4的國傢和後1/4的國傢僅相差2.46%,由此可見,1%的增幅變動就非常顯著瞭。此外,在透明國際組織發布的清廉指數中,1995~2006年,最腐敗的1/4和最清廉的1/4國傢之間的平均分數相差約為2.52。假設一個國傢的清廉指數接近於1992~2006年的清廉指數平均水平(5.96),並且1980~2006年人均GDP平均增速為1.73%,那麼在腐敗評分上的1分之差就會導緻其在清廉指數排名及發展水平排名上的變動。如果腐敗評分增加2分,就能使一個清廉指數處於平均水平的國傢退至最腐敗的國傢之一,並將其經濟增長率從1.73%拉低至負增長水平,使其淪為經濟錶現墊底的1/4國傢。
鑒於中國在1992~1996年的清廉指數評分增加瞭2分,腐敗研究的新正統理論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應該會下降,經濟發展受阻。然而,我們看到的景象卻是腐敗加劇、高增長率與經濟高速發展並存(見圖1–1)。雖然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的清廉指數翻瞭一番,但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中國經濟增長率卻達到瞭10%以上。實際上,我們會發現,在腐敗研究的新正統理論與中國的案例之間存在三個明顯的矛盾之處。第一,腐敗率在20世紀90年代初經濟實現快速增長之前就已明顯提高(此處的腐敗率是以每10000名受到腐敗指控的公職人員中的被捕人數粗略估算的,我將其稱為“被披露的腐敗率”)。第二,經濟增長最迅速的時期(20世紀90年代中期)與腐敗態勢加速惡化的時期正好吻閤,依據是被起訴高官數量及粗略估計下的受賄金額(以每件起訴案追迴的平均受賄金額作為計算依據)。第三,即使清廉指數和專傢對腐敗真實程度的主觀估計都翻瞭一番多,中國經濟仍在迅速增長,而腐敗仍在加劇。
我撰寫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解釋中國的腐敗問題惡化與經濟迅速增長之間的顯著矛盾。我們麵臨的不僅是腐敗研究的新正統理論與現實情況之間存在明顯的矛盾,新正統理論認為,中國的腐敗問題惡化會拉低經濟增長率,並同時阻礙發展。但我們看到的實際情況卻是腐敗問題惡化與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能夠並存。因此,我們還麵對腐敗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雙重悖論。假設腐敗加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悖論形成的原因在於新正統理論的邏輯缺陷,而且新正統理論使用僞相關性“證明”其核心假設,那麼聽起來似乎也是有道理的。我不否認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嚴重的腐敗會對經濟錶現産生負麵影響,而且我認為一般來講這一說法是正確的。隨便研究一下欠發達國傢的腐敗和經濟,就能發現腐敗會導緻經濟癱瘓,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以至於你根本無法質疑新正統理論的基本結論。
……
媒體評論
《雙重悖論》一書論證嚴謹,對中國的腐敗狀況進行瞭有根據的分析,這與之前常被引用的一些經濟學傢的著作正相反。
——《政策評論》
魏德安的《雙重悖論》試圖解釋掠奪式腐敗下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如何成為可能的秘密,他認為,當今中國腐敗嚴重,但並未失控。
——《華爾街日報》
用户评价
讀到《雙重悖論:腐敗如何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這個書名,我腦海中立刻浮現齣一些關於中國經濟發展曆程的畫麵,以及那些常常被提及的討論。我們都知道,中國在過去幾十年裏取得瞭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但同時,腐敗問題也一直是公眾關注的焦點,甚至被認為是阻礙社會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這本書的標題“雙重悖論”特彆吸引我,它暗示瞭一種並非簡單的綫性關係,而是可能存在著某種意想不到的、甚至違背直覺的聯係。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界定這種“悖論”的?它是否意味著腐敗在某些層麵上,可能與經濟增長的某些錶現形式並行不悖,甚至在短期內“促進”瞭某些方麵的“繁榮”,但與此同時,又在更深遠的層麵埋下瞭隱患,最終可能影響到經濟的健康發展和長期競爭力?我期待這本書能不僅僅停留在對腐敗現象的道德批判,而是能以一種更具分析性和學術性的視角,來審視腐敗與經濟增長之間錯綜復雜的關係。它是否會考察不同類型的腐敗,例如權力尋租、貪汙、賄賂等等,以及它們各自對經濟增長的不同影響機製?書中會探討哪些理論模型,來解釋這種“雙重悖論”的形成原因和可能産生的後果?
评分《雙重悖論:腐敗如何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這個書名,瞬間抓住瞭我的注意力。它拋齣瞭一個引人深思的命題,讓我立刻聯想到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裏波瀾壯闊的發展史,以及伴隨其間的關於腐敗的種種討論。我一直覺得,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並非簡單的“非此即彼”,而更像是一種糾纏不清、甚至是相互影響的復雜網絡。“雙重悖論”這個詞,仿佛點破瞭某種我們習以為常卻又難以解釋的現象:為何在一些時期,經濟似乎仍在增長,但腐敗問題卻愈發嚴重?或者,某些腐敗行為,在短期內似乎並沒有完全阻礙經濟的“前進”,反而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加速”瞭某些交易的達成?這背後的機製究竟是什麼?這本書是否會深入分析,腐敗是如何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扮演瞭某種“催化劑”或“潤滑劑”的角色,從而産生瞭這種“悖論”式的增長?同時,它又如何在更長遠的時間尺度上,侵蝕經濟發展的根基,例如破壞製度的有效性,降低社會信任,或者扭麯資源配置?我期待書中能夠提供一個嚴謹的分析框架,去剖析這種“雙重悖論”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可能帶來的長期後果,而不僅僅停留在對腐敗現象的道德譴責。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讓我産生瞭極大的好奇,特彆是“雙重悖論”這個詞,它暗示瞭一種看似矛盾但又彼此關聯的現象。在我的印象中,中國經濟的崛起是一個舉世矚目的成就,其增長速度和規模都令人驚嘆。然而,任何高速發展的背後,往往都伴隨著一些深層次的問題。當“腐敗”這個詞被提及,我立刻聯想到它可能對經濟運行帶來的扭麯和阻礙。這本書是否會深入剖析,究竟是腐敗在某些特定時期,反而為經濟的某些方麵提供瞭“潤滑劑”,從而産生瞭一種“增長”的假象,還是說腐敗本身就是經濟增長過程中一種不可避免的“副産品”,甚至是在特定體製下,腐敗與增長之間形成瞭一種相互促進卻又相互損害的復雜關係?我期待這本書能夠提供一個清晰的框架,幫助我理解這種“雙重悖論”的運作邏輯。它會從哪些具體的經濟指標入手,來量化腐敗的影響?是投資效率、資源配置、創新能力,還是市場公平性?又或者是從曆史的維度,追溯這種悖論是如何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演變的?書中是否會引用大量的案例和數據來支撐其論點,讓讀者能夠直觀地感受到腐敗對經濟增長的微觀和宏觀影響?我非常希望能在這本書中找到對這些問題的深刻解答。
评分當我看到《雙重悖論:腐敗如何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這個書名時,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那段既充滿活力又充滿挑戰的曆程。經濟的騰飛是事實,但腐敗的陰影也始終籠罩其中。這個“雙重悖論”的提法,讓我感到它觸及到瞭問題的核心,而不是簡單地將腐敗視為經濟增長的“敵人”。我好奇,這本書是否會探討,在某些特定時期,為瞭追求經濟速度,我們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瞭某些形式的腐敗,甚至將其作為一種“變通”的手段?這種“變通”在短期內是否帶來瞭某種程度的“增長”,但與此同時,又在埋下更深的隱患?比如,權力尋租的盛行,是否導緻瞭資源的非理性配置,使得一些低效的企業得以生存,而真正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卻受到壓製?它是否會分析,腐敗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可持續性”究竟有多大的損害?書中會如何界定“腐敗”的範圍,以及它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具體作用機製?我期待能夠在這本書中,看到一個對這種復雜關係的深刻洞察,而非簡單的二元對立。
评分這本書的題目,《雙重悖論:腐敗如何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讓我産生瞭一種迫切想要一探究竟的衝動。中國經濟的騰飛是毋庸置疑的,但關於腐敗的討論也從未停止。我一直覺得,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極其復雜且難以言說的聯係,而“雙重悖論”這個詞恰恰捕捉到瞭這種微妙之處。我的理解是,腐敗可能在某些時候,以一種扭麯的方式,為經濟的快速擴張提供瞭一些“動力”,比如一些項目得以迅速批復,一些投資得以快速落地,這或許會帶來短期的GDP增長數字。然而,這種增長的質量和可持續性,以及它對社會資源的分配、市場秩序的公平性可能帶來的負麵影響,是值得深思的。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揭示這種“悖論”的具體錶現形式,例如,腐敗是否可能導緻資源配置的嚴重扭麯,使得本應流嚮更具創新和效率領域的資金,卻被截留或用於低效的項目?它是否會扼殺市場競爭,導緻劣幣驅逐良幣?此外,我也好奇作者會如何定義“腐敗”以及“經濟增長”,這兩者在中國特定的曆史和政治背景下,是否有著與普遍定義不同的內涵?書中會否涉及一些具體的案例,來印證這種“雙重悖論”的現實存在?
评分并非真正的悖论,而是民族性格惯性影响使然。
评分并非真正的悖论,而是民族性格惯性影响使然。
评分并非真正的悖论,而是民族性格惯性影响使然。
评分东西不错东西不错东西不错
评分东西不错东西不错东西不错
评分东西不错东西不错东西不错
评分东西不错东西不错东西不错
评分东西不错东西不错东西不错
评分并非真正的悖论,而是民族性格惯性影响使然。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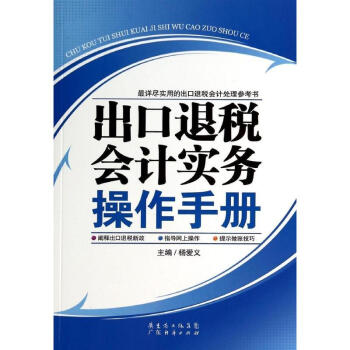
![国富论(全2卷)(权威全译本) [英]亚当·斯密,郭大力 王亚南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540287057/553f30c8N898464f1.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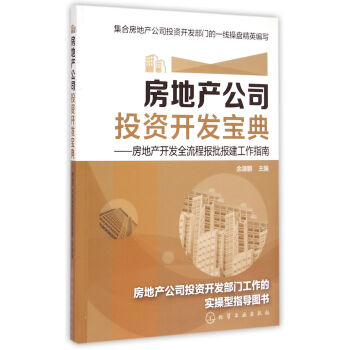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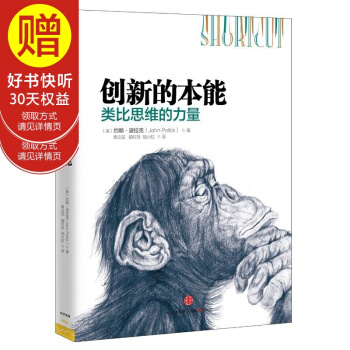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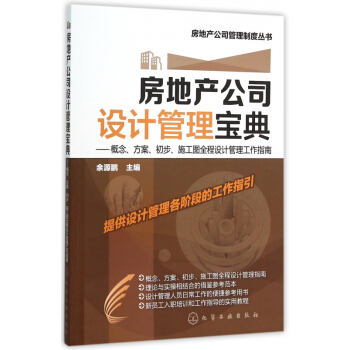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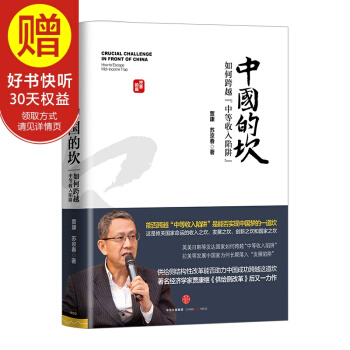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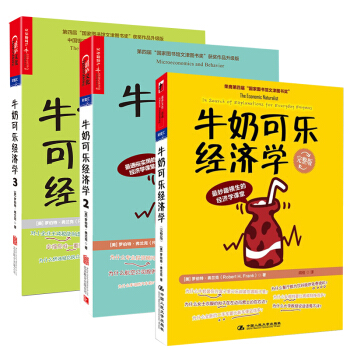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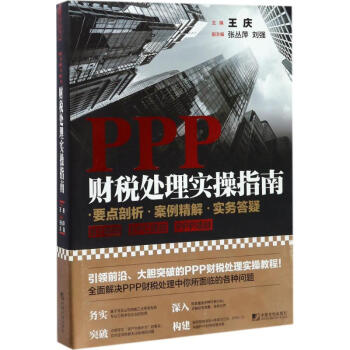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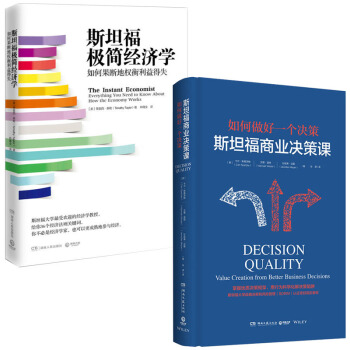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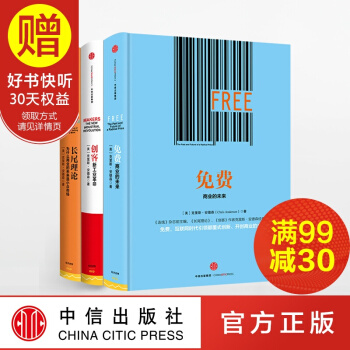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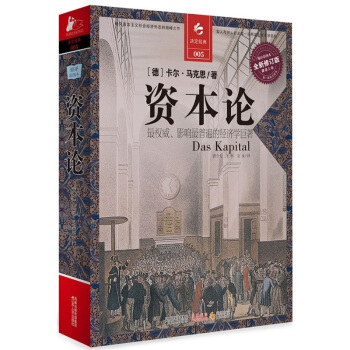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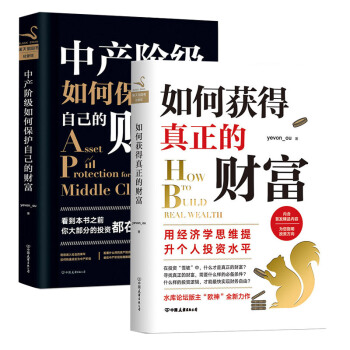
![贸易保护主义 [Protectionism]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152242/db0ceb5e-aed8-4e2c-8c6c-a46cf511c44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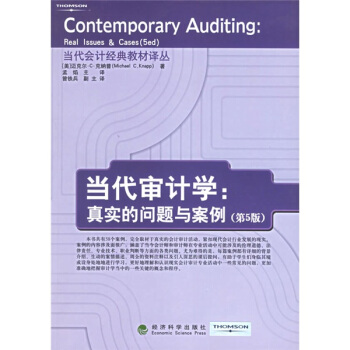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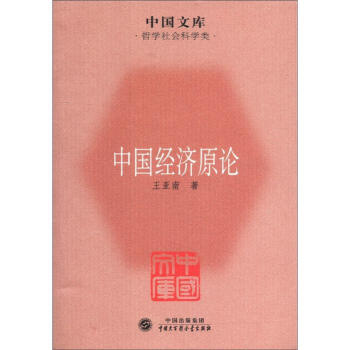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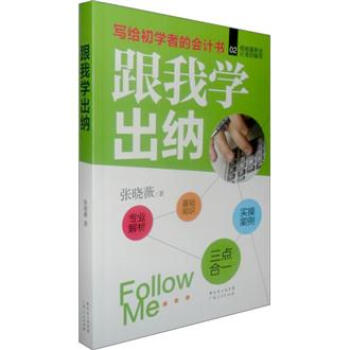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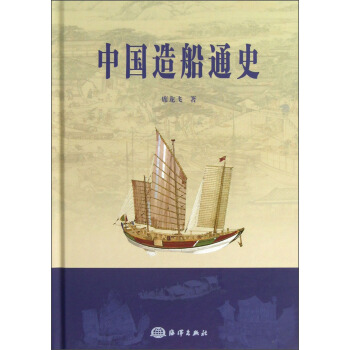
![社会发展译丛:增长与波动(1870-1913年) [Growth and Fluctuations,1870-1913]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01381/rBEhWFMUHiwIAAAAAALqq3s7Pk8AAJVogDtkJcAAurD15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