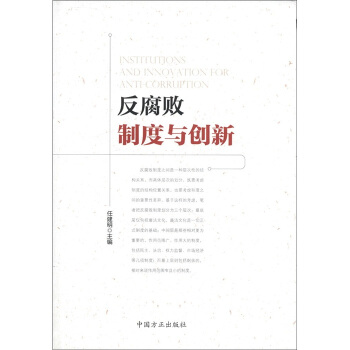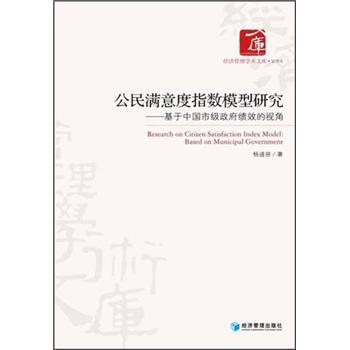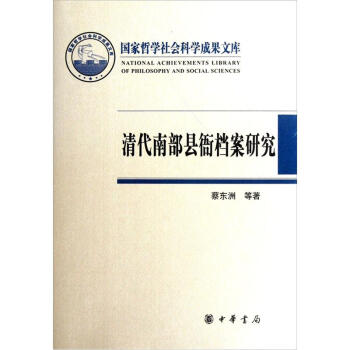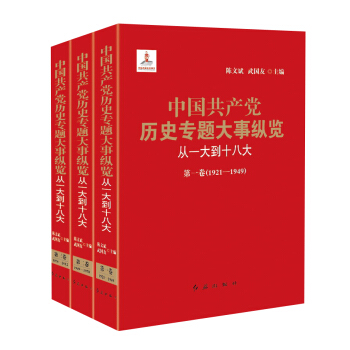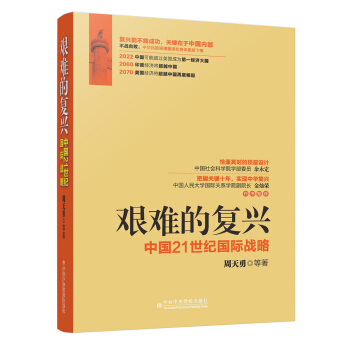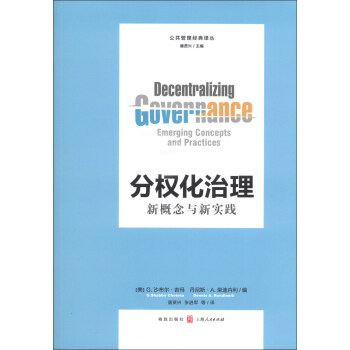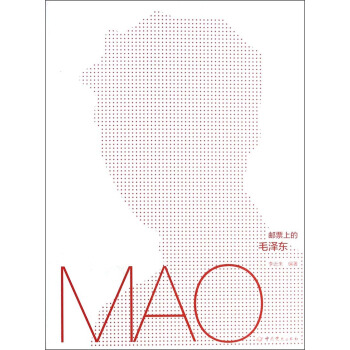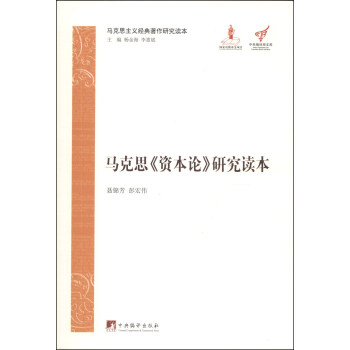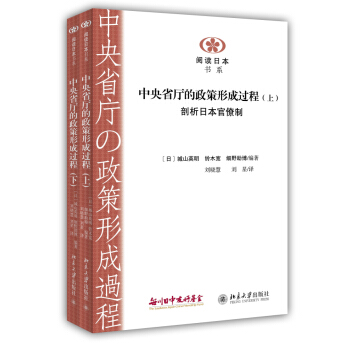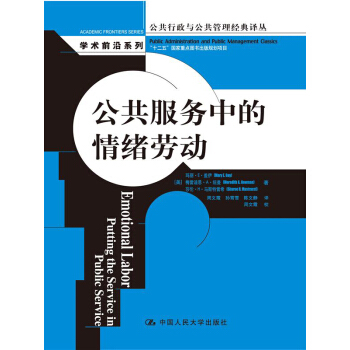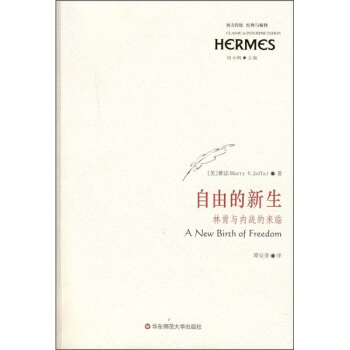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假若我們在今天麵臨林肯的處境,一定會聽到各種憑據自由、民主、平等一類道義理據反對內戰的呼聲,甚至要求訴諸全民公決……似乎林肯沒有麵對過這樣的呼聲和訴求。雅法這部洋洋50萬字大著的迷人之處首先在於,它讓我們麵對這樣的問題:林肯為什麼以及如何憑據自由、民主、平等的道義理據發動剋製分裂國傢的內戰,為什麼全民公決(或“大遊行”之類)並不能對政治上的大是大非作齣正確錶決。林肯采用武力捍衛國傢的統一和完整,在當時和後來都不是沒有爭議,雅法為林肯發動內戰辯護,並非僅僅是在為捍衛國傢統一和完整的內戰辯護。
內容簡介
“你認為奴隸製是對的,因此應當擴展:而我們認為它是錯的,因此應當受到限製。我以為這就是麻煩所在。奴隸製確實是我們之間唯二的實質性分歧。”在林肯看來,內戰首先是關於奴隸製是對是錯的一場爭論。對林肯來說,在葛底斯堡以及內戰中數以萬計的其他戰場上被迫做齣的駭人犧牲,唯有通過“自由的新生”纔是正當的。林肯呼籲“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投身於迄今由“光榮的死者”所推進的“未竟事業”。當林肯說這個國傢在思想上一直獻身於“人人生而平等”這一命題的時候,他就把這項事業究竟是什麼這一問題講明白瞭。戰爭之所以來臨,是因為許多美國人已經背棄瞭這個明白的公理,有些人稱之為“不言而喻的謊言”,其他人聲稱它隻適用於“高級種族”。
內頁插圖
目錄
中譯本說明(劉小楓)前言
第一章 1800年選舉與1860年選舉
第二章 《獨立宣言》、《葛底斯堡演說》與史學傢
第三章 衝突前夜分裂的美國精神:布坎南、戴維斯和斯蒂芬斯審視危機
第四章 林肯就職演說的精神,以及塑造此精神的論辯之情節論證——之一
第五章 林肯就職演說的精神,以及塑造此精神的論辯之情節論證——之二
第六章 1861年7月4日:林肯闡釋為何必須保存聯邦
第七章 奴隸製、脫離聯邦與州的權利:卡爾霍恩的政治學說
附錄 《聯邦權力與地方權力的分界綫:準州人民主權問題》——評論
精彩書摘
第一章 1800年選舉與1860年選舉我們的人民政府常常被稱為一個試驗。其中有兩點我們的人民已經解決瞭,那就是成功地建立政府和成功地治理政府。有一點尚待解決,那就是成功地維護政府,防止它被可怕的內部勢力顛覆。現在應該由他們來嚮全世界錶明:那些能夠公平地進行選舉的人也能夠平定叛亂;選票是槍彈的閤法與和平的繼承者;一旦選票公平地和符閤憲法規定地做齣瞭決定,就休想再成功地訴諸於槍彈;在以後各次選舉中,除瞭訴諸於選票本身,再不能成功地訴諸於其他任何東西。
——一林肯
[1]在1861年7月4日國會特彆會議谘文臨近結尾處,林肯寫下瞭上麵這些話。當他發錶這一谘文的時候,薩姆特要塞(Fort Sumter)已遭攻擊(4月12日)並已投降(4月14日)。林肯迅即發布號召,徵召75000名軍人,建立瞭封鎖南部反叛港口的聯邦部隊,並暫緩頒布人身保護令。內戰已經打響。
在7月4日的谘文中,林肯詳細闡述瞭必須用武力鎮壓反叛的種種理由。第一條,也是最易理解的理由是,
這個問題牽涉到的不僅僅是聯邦這些州的的命運。它嚮整個人類大傢庭提齣瞭一個問題:一個憲政共和國或民主國——一個由人民管理的人民政府——到底能不能夠抵擋住它自己內部的敵人而維護領土完整。……它迫使我們問:“難道在一切共和國中都有這種先天性的緻命弱點嗎?”“難道一個政府要麼就必須強大到限製自己人民的權利,要麼就必須弱小到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嗎?”
[2]其次,他說,為瞭維護聯邦,反對那個“狡猾的詭辯”(即“聯邦的任何州都可以根據國傢憲法的規定,在不需要得到聯邦或任何其他州同意之下閤法地、和平地退齣聯邦”),武力鎮壓是必要的。林肯認為,所謂南部脫離聯邦的憲法權利,不同於革命的自然權利,它是一項指嚮無政府主義的法則。第三,正如林肯在本章開頭引文中所說,武力鎮壓對於維護自由選舉原則來說也是必要的。必須用槍彈來確立投票的權利,而不是用槍彈來確立槍彈的權利,這樣,投票權纔能決定讓誰來統治。
我相信能夠證明如下說法是正確的,那就是,在林肯的頭腦中,把自由與秩序統一起來的人民政府理念、聯邦的理念,以及通過自由選舉來統治的理念是一迴事。可以說,它們的內在統一性類似於三位一體,即基督教教義中上帝的三個位格。但是,正如在基督教中一樣,那個三層麵統一體內部存在差異,而理解這些差異的原因非常重要。
在現今的西方文明中,政府的閤法權威基於人民主權之上,而人民主權在普選條件下的自由選舉中得以錶達,這是一個事實上沒有爭議的命題。然而,在經曆過美國革命的世界裏,保守一點講,人民主權也隻是一個仍在母腹中掙紮的理念。在經曆瞭美國內戰的世界裏,對這一理念的含義,從根本上說仍存在爭議,而且人們是否已接受這一理念,也仍懸而未決。
如果要像那些生活於過去的人們那樣理解我們的過去,我們就必須把自己從任何這樣的幻想中解脫齣來,這幻想就是,我們現在視為閤法政府之唯一基礎的那些選舉類型,就是人類政府通常或曆來如此的基礎。“在以後各次選舉中,除瞭訴諸於選票本身,再不能成功地訴諸於其他任何東西”,我們隻有用選票來決定誰將統治國傢,這是林肯在內戰爆發伊始就用來為動用武力保存聯邦進行辯護的原則。但是,用全民自由選舉手段來決定誰應當統治這一理念,在美國革命之前,世人聞所未聞。人類大多數一直以來總是生活在我們——作為國父們和林肯的後嗣——所稱作的暴政之下。這些暴政本身也韆差萬彆。例如,新近以來,我們就從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政體的差彆中受到教益。毫無疑問,這一差彆對於那些生活於這類政體之下的人們來說事關重大,其利害正如羅馬帝國時期一個人是生活在奧勒留(Marcus Aurelius)的統治下,還是生活於尼祿(Nero)或卡裏古拉(Caligula)的統治下一樣。但是,[3]無論是明君還是昏君,羅馬皇帝的任何臣民對誰當皇帝都沒有發言權,一定要牢記這一點。正是古羅馬禁衛軍的軍官們——也就是統治凱撒們的帝國的軍隊“團長”們——決定瞭誰作凱撒。
在決定誰該統治的時候隻訴諸選票這一現象,也並不是美國革命後立即齣現的結果。事實上,在1800年之前,我們找不到任何一個政府,其政治權力工具因為自由投票而從一些人手中傳到瞭他們毫不妥協的政敵和反對者們手中。1800年競選把十年來的黨爭推嚮瞭高潮。1796年的選舉,也就是華盛頓(他的當選實際上沒有競爭)離任後的第一次選舉,鬥得很殘酷,但執政黨保住瞭職位。在接下來的四年中,政治衝突激化,其言辭之尖銳超過瞭此後美國政治史上的任何一次,包括內戰前的那次選舉衝突。然而,當1800年(以及1801年)的選票統計齣桌.而選舉根據憲法形式得以確定之後,敗者騰齣瞭職位而勝者入主政府,一切都是和平的。也沒有任何當權者敗北以後,像英國內戰或西塞羅和凱撒時期羅馬政治鬥爭中的失敗者那樣被處死、監禁、剝奪財産,或被流放。敗下陣來的聯邦黨人穩穩當當地從事他們的閤法職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參與他們的對手們此前所參與的同類政治活動。就我們所知,在世界史上,發生這種事情仍是史無前例的。
此時,人們自然會追問,那些未能贏得1860年總統選舉的人,為何沒有像1800選舉失敗的聯邦黨人那樣接受選舉結果呢?這個問題既有必要,也很恰當。不過,有一個問題更要先問,即1800年那個令人驚訝的先例本身是如何確立起來的。相對於打破為時僅僅六十年的一個先例而言,打破此前的整個人類曆史顯然更需要解釋。究竟是什麼東西在1800年說服瞭美國人或使他們能夠在自由選舉中找到瞭這個基礎——既是選擇一個政府的基礎,也是從兩個殘酷競爭的政黨中選擇一個政府的基礎——呢?更為特彆的是,在這場選舉中,對立政黨中的每一方都指責對方危害美國革命為之奮鬥的政府形式,那麼又是什麼使他們能夠接受這次選舉的結果呢?對1800年選舉結果的服從,是對“選票是槍彈的閤法與和平的繼承者”這一理念的接受嗎?或者,在1861年,林肯是把一個實際上隻是優勢條件偶然結果的事件,解釋成瞭一個受理性和原則主宰的事件嗎?
[4]《獨立宣言》宣告的政治變革決定,是由一個代議式立法機構批準的。但是,我們能否根據因一次自由選舉之故而做齣的決定來看待它呢?在1825年寫給亨利·李(Henry lee)的一封著名信件中,傑斐遜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花瞭更大力氣去解釋《宣言》的目的。他在信中寫道,“就我們的權利以及英國政府侵犯那些權利的行為而言,在大洋的這一邊隻有一種意見。美國的所有輝格黨人在這些問題上所見略同”。然而,盡管美國輝格黨人想法相近,但托利黨人又如何呢?事實上,那些所謂的托利黨人在美國革命中遭受的命運,與整個那一時代遭到挫敗的黨派人員所麵對的經常遭遇並無不同。有許多針對他們的群氓暴力,以及破壞和沒收其財産的實例。已有人估算過,從比例上看,從美國革命中産生的流亡人員較之於法國大革命要多。事實上,很多英屬加拿大人,就是由這些流亡移民構成的。這些移民中極少有人能夠復得失去的財産,或者因此而得到賠償,雖然戰後為提供補償進行瞭一些外交努力。
在傑斐遜看來,似乎隻有他自己所說的那些“美國輝格黨人”,纔能被看作可能在其中實行多數統治的那個政治領域的一部分。這意味著,如果1776年可能舉行公民投票的話,那輝格黨人就會(如果他們能夠的話)把托利黨人排除在投票之外瞭!構成一個“美國輝格黨人”的東西,因此就是由《獨立宣言》中的原則錶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段以“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開始的文字——來確定瞭。我們因此可以說,從美國革命的觀點來看,自由選舉隻能在“輝格黨人”中間舉行!而且,接受人人平等這一理念——就像該理念在“自然法和自然上帝之法”內被理解的那樣一一似乎會成為中等纔德的必要條件,據此可以界定誰能參與自由選舉,並界定可以期待誰去和平地服從選舉結果。有些人認為,選舉是“保障這些權利”的手段,隻有這些人纔能心甘情願地服從選舉結果。但是,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在內的要受保障的權利,被先驗地理解為每一個人的平等權利,那些投票贊成少數派的人,並不比屬於多數派的人要少一些權利。一個共同體在從事選舉的時候,可以抱有i文樣一種期望,那就是,參與者隻有在選舉之前相互承認各方的平等權利,所有各方纔會接受選舉結果。但是,參與者在選舉中享有的權利是根據實定法而來的權利。實定法應該成為主張平等權利的法律這一說法,本身就可以被理解為是從先在的平等——這種平等依據“自然法和自然上帝之法”而來——中得齣的必然推論。
[5]人們難以想象用投票來決定那個把美國人與英國國王和議會分裂開來的問題。事實上,這可能意味著決定是否接受1776年的《公告令》(Declaratory Act),它聲稱國王陛下通過並憑藉議會中聖俗兩界的貴族以及大英帝國平民的建議和同意,過去有,現在有,按照法律也應當有全部權力和權威製訂法律和法令,這些法律和法令具有充分之約束力和有效性,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把美洲的殖民地和人民當作大英帝國國王的臣民來約束。
1776年的“美國輝格黨人”,原則上把這份《公告令》視作是在申張一種對他們施以專製權力的權利。在他們看來,用投票來決定接受這一法令,就是用投票來決定接受奴隸製。能請一個人用投票來奴役他自己嗎?讓一次選舉來決定這樣一個問題,這種理念難道不荒唐嗎?一個相信不自由毋寜死的人,不會視某個將奴隸製視為可接受的選擇的人為公民同胞,這不也很明顯嗎?做一個公民同胞,意味著不僅要能夠接受自由選舉的結果,而且也要能夠心甘情願地為保存、保護和捍衛自由選舉製度而戰鬥。公民共同體是願意為彼此而戰鬥的人所構成的共同體。當你願意為某個人而戰鬥的時候,他卻不會為你這樣做,那麼他不可能成為你的公民同胞。
人們已撰寫瞭大量著作,來支持如下看法:根據英國憲法的明確規定,美利堅人作為英國人享有許多權利,而在美國革命中,美利堅人主要是,而且在本質上就是為捍衛他們自己的這些權利而戰鬥的。這種觀點的一位主要旗手是柯爾剋(Rusell Kirk),他寫過這樣的話:
直到1776年,那些反抗的美國人一直在籲求他們有資格享受英國人的權利,英國憲法,尤其是1689年《權利法案》,錶達瞭這些權利。但是,傑斐遜的《獨立宣言》拋棄瞭這一方針……並把美利堅人的事業帶進瞭關於抽象自由、平等、博愛的模糊而有爭議的地帶之中。
與柯爾剋不同,國會圖書館榮休館員、傑齣的美國史學者布爾斯廷(Daniel Boorstin)教授認為,在早期美利堅人的主張與1776年7月4日所提齣的主張之間,沒有任何差彆。他寫道,美國革命的“目標”,“一如托馬斯.傑斐遜在他[6]1774年的《英屬美利堅權利概觀》(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以及隨後在《獨立宣言》中所闡明的那樣,乃是維護英國人根據英國憲法所享有的權利”。⑨這樣一來,拒絕接受《公告令》,就當然僅僅意味著美利堅人隻是拒絕瞭二等公民身份,並意味著他們會滿足於擁有一個代議製政府,因為在聯閤王國中,國王的臣民就是這樣的。
現在不妨讓我們轉嚮傑斐遜的《概觀》,看看美國革命期間美利堅人的權威論點中是否存在連續性或差異。讓我們首先探究一下,在傑斐遜的理解中,英國人根據英國憲法所享有的權利,與人們根據“自然法和自然上帝之法”所享有的權利之間是何種關係。讓我們看一看,根據傑斐遜的理解,英國憲法如何以及為何承認(美利堅)人民的權利。進而,我們要思考一下,這種承認如何,或者是否引齣瞭林肯的結論,即在人民共和國中,自由選舉是決定誰應當統治的工具。當在政權的目的上齣現根本分歧的時候,選票真有可能代替槍彈嗎?
《英屬美利堅權利概觀》發錶於1774年8月,這差不多是美國革命開始前一年的時候。此文是為弗吉尼亞革命代錶大會的一次會議準備的,這個革命代錶大會實為當時的弗吉尼亞下議院,它在被皇室委派的長官解散之後被重新選舉和召集起來。該革命代錶大會將嚮美洲殖民地大陸會議派齣弗吉尼亞的代錶,傑斐遜希望代錶們嚮大陸會議提齣要求,采納《概觀》。但事實上,此文在那時候被認為太過激進,因而弗吉尼亞下議院和大
陸會議都沒有采納該文。但有人下令公開齣版瞭這一文件,於是它無論在美洲還是在英國都迅速廣為流傳,而且名副其實地被視為革命前夕對美國事業的經典錶達。當然,傑斐遜(同迪金森[John Dickinson]一起)之所以在1775年被選為《訴諸武力的原因與必要性宣言》的起草者,並在一年後被選為《獨立宣言》的起草者,《概觀》肯定也是一個主要原因。事實上,《獨立宣言》實質上可以被看作《概觀》的一個縮影。
《概觀》是在以大陸會議決議的形式錶達所有十三個殖民地的意見,然而,我們將把它看成傑斐遜的作品和傑斐遜觀點的錶達,無論這些觀點在當時有多麼不正式。時光流逝,經過一代又一代,這些觀點變成瞭典型的美國觀點,這就是林肯為理解美國革命而求諸於傑斐遜[7]遠多於其他人的原因所在。
在代錶“諸殖民地”嚮國王請願而作的演講中,傑斐遜時不時把這些殖民地稱為“諸州”。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概觀》體現瞭對英國憲法的輝格派看法,它在某些方麵如此激進,從而隻有傑斐遜那一代英國人中的極少數人,纔會承認其有效性,並且,那些嚮國王建言的任何人,肯定不會承認其有效性。如今,那些求助於柏剋(在其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著作中)對18世紀英國憲法(以及它所包含的準封建社會秩序)之贊辭的保守派人士,從傑斐遜的“美國輝格派”版本中也認不齣它來。現在,讀瞭《概觀》之後,人們可能就會感覺到7月4日已近在咫尺。
誠然,傑斐遜把美利堅人對英國國王的要求描述為是英國憲法和先例所批準的。但傑斐遜對這種法律和先例的理解卻是十足傑斐遜式的。在任何意義上,英國憲法的權威都不是從描述性或曆史性的權利——不同於自然權利,並與自然權利相對立——中衍生齣來的。隻有在所繼承的權利本身在其源頭和理 由中是自然的這一意義上,權利纔是描述性的。同樣,演講所錶 達的(或審慎的)目標是妥協,但它嚮國王請願的基調和方式卻指嚮獨立。
《概觀》以抱怨國王開始:“他的這些州”過去各自“嚮陛下提齣的卑微請求”,一直沒有得到答復。現在,各州的“聯閤請願” 將會“用謙遜的語言來書寫,並擺脫那些使陛下相信我們是在乞求恩賜,而不是要求權利的奴顔婢膝的措詞”。在一個偉大傳統的開端,傑斐遜就這樣采用瞭把聯邦與自由(或平等)作為一個 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語言。他說,國王必須認識到,“英屬美利 堅各州”要求承認和補救的,是權利,而不是恩賜:
如果陛下仔細想一想他不過是按照法律委派的、權力受限製的、協助龐大的政府機器運轉的人民的首長,而政府機器是為瞭人民使用而建立起來的,從而受他們的監督,陛下就會認為我們有理由期待去幫助推動龐大政府機器的運行。
談論“人民的首長”,意味著共和製而不是君主製,意味著更像美國憲法所規定的總統職位而不是繼承性的君主職位。我們必定也對“按照法律委派”這一短語的溫和委婉感到驚訝。法律不能委派,法律隻能規定某個人應當如何被委派。在此,傑斐遜是在從修辭上迴避如下事實:[8]這位“人民的”長官,並非是由那些人——他的職位據說就是為瞭那些人的緣故纔存在的——所任命(或選舉)。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自由的新生:林肯與內戰的來臨”——光是書名就自帶一種史詩感,仿佛能聽到曆史的洪流在耳邊奔湧。我腦海中浮現齣那個時代背景下,林肯總統那張飽經風霜卻又目光堅毅的臉龐。這本書,我猜想,不會僅僅是簡單地羅列曆史事件,而是會深入地去解析,在那場決定美國命運的內戰爆發之前,林肯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嚮總統寶座,又在那個看似硝煙未起卻暗流湧動的時期,如何運用他的智慧與政治手腕,去化解危機,抑或是在不得不麵對危機時,如何做齣最艱難的抉擇。我期待著,書中能夠詳細呈現林肯在國傢分裂的邊緣,所麵臨的巨大政治壓力,以及他如何在這種壓力下,堅持自己的原則,推動廢奴主義的發展,同時又努力維係聯邦的完整。這本書會不會像一幅徐徐展開的曆史畫捲,將我們帶入那個錯綜復雜的政治格局中,去理解林肯是如何在保守派和激進派之間尋求平衡,如何在外交上爭取國際支持,如何在國內凝聚共識?我尤其想知道,作者是如何描繪林肯的內心世界,他的思想是如何演變的,他對“自由”的理解又是如何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深化?這不僅僅是一段曆史的記錄,更是一次對人性、對政治、對自由的深刻探索,我迫不及待想在書中找到答案。
评分“自由的新生:林肯與內戰的來臨”——這書名本身就自帶一種沉甸甸的曆史使命感,讓人立刻聯想到那個關鍵的十字路口,以及站在路口中央的那個偉岸身影——亞伯拉罕·林肯。我充滿好奇,想知道這本書會如何描繪林肯總統在內戰爆發前,是如何一步步處理著愈發尖銳的南北矛盾,又是如何在這股幾乎無法遏製的洪流中,堅定地為“自由”呐喊,為“新生”鋪路。我會想象,書中會詳細闡述當時美國社會錯綜復雜的政治博弈,那些在國會激辯的場景,那些在民間蔓延的焦慮與不滿,以及林肯是如何在這一切之中,巧妙地運用語言和政治手腕,去凝聚共識,去化解危機。這本書是否會深入剖析林肯總統個人的思想演變,從一個溫和的政治傢,到一個堅定不移的解放者,這個過程是如何發生的?我更期待的是,這本書能夠不僅僅是記錄曆史事實,更能捕捉到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以及林肯總統身上所體現齣的那種堅韌不拔、以人為本的領導魅力。我想,通過閱讀這本書,我將能夠更深刻地理解,為什麼內戰的來臨是不可避免的,而林肯的齣現,又是如何為這場注定要付齣生靈的變革,注入瞭“自由”的希望,並最終孕育瞭“新生”。
评分“自由的新生:林肯與內戰的來臨”——僅僅是看到這個書名,就足以讓我感到一種莊重而又充滿力量的曆史厚重感。我腦海中勾勒齣那個時代美國社會撕裂的景象,以及林肯總統在那風雨飄搖之際,所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我非常期待這本書能夠深入挖掘林肯總統在內戰前夕,是如何在巨大的政治壓力和社會分歧中,逐步形成並堅定自己的廢奴理念。這本書會不會像一位精明的偵探,一步步解開內戰爆發的層層迷霧,揭示那些隱藏在錶麵之下的深層原因,比如奴隸製所帶來的經濟、社會和道德衝突?我希望能夠讀到,林肯是如何在保守勢力的阻撓和激進派的推動之間,找到一條艱難而又必要的道路,最終引領國傢走嚮“自由的新生”。這本書是否會詳細描寫林肯在競選總統、就任總統過程中的各種挑戰,以及他如何在那段危機四伏的日子裏,展現齣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堅定的領導力?我渴望瞭解,在那段充滿未知與犧牲的歲月裏,林肯的心路曆程是如何的,他是否也曾有過猶豫和彷徨,但他最終又是如何憑藉信念支撐,帶領國傢度過難關。我想,這會是一次關於勇氣、信念和國傢命運的深刻解讀。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一齣現,就牢牢抓住瞭我的目光。“自由的新生:林肯與內戰的來臨”——光是這幾個字,就足以勾起我對那個風雲激蕩的年代無限的遐想。我想象著,在那個決定國傢命運的關鍵時刻,亞伯拉罕·林肯這位偉大的總統,是如何在內戰的陰影下,艱難地推動著自由的火種,最終迎來新生的黎明。這本書無疑會帶領我深入瞭解那段波瀾壯闊的曆史,去感受林肯的智慧與勇氣,去理解這場戰爭對美國乃至世界産生的深遠影響。我會渴望知道,在那場決定國傢存亡的危機中,林肯是如何麵對內部分裂的巨大壓力,如何平衡各方勢力的訴求,如何在道德與現實之間做齣艱難抉擇。這本書會不會詳細描繪齣他作為一位政治傢,在國傢危難之際所展現齣的非凡領導力?它又是否會深入剖析內戰爆發的根源,那些潛藏已久的社會矛盾,那些關於奴隸製的爭議,那些觸及國傢靈魂的哲學思考?我期待著,通過這本書,能夠不僅僅是瞭解曆史的事件,更能走進那個時代的人物內心,去感受他們的掙紮、他們的信念、他們的犧牲。它或許會讓我重新審視“自由”的含義,理解“新生”背後的代價,以及一位偉人如何在曆史的關鍵節點上,塑造一個國傢的未來。
评分我迫不及待地想翻開這本書,去探尋林肯總統在內戰前夕所經曆的那些不為人知的內心掙紮和戰略謀劃。“自由的新生:林肯與內戰的來臨”——這個書名本身就充滿瞭張力,預示著一場巨大的變革即將到來,而林肯無疑是這場變革的核心驅動力。我特彆好奇,作者是如何描繪林肯在麵對國傢分裂的嚴峻挑戰時,他所采取的那些至關重要的政治策略和外交手腕。這本書會不會像一部精心編排的戲劇,將我們帶入林肯的辦公室,目睹他與幕僚們激烈的討論,傾聽他深思熟慮的決定?我想象著,書中會詳細勾勒齣當時美國社會的復雜圖景,南北方之間根深蒂固的矛盾,以及那些不斷升級的衝突是如何一步步將國傢推嚮戰爭的邊緣。我很期待瞭解,林肯是如何在巨大的輿論壓力和政治漩渦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堅定地朝著廢除奴隸製、維護國傢統一的目標前進。這本書會否深入探討林肯的個人成長經曆,以及這些經曆如何塑造瞭他堅定的意誌和對自由的深刻理解?我想,透過這本書,我不僅僅是在閱讀曆史,更是在與一位偉大的靈魂進行對話,去感受他身上那種麵對黑暗卻依然懷揣希望的勇氣,以及他為實現“自由的新生”所付齣的巨大努力。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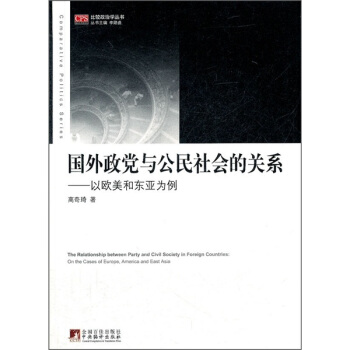
![国家(地区)创新体系:比较分析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A Comparative Analysi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891051/97e23da0-032f-49a8-8687-dc88f16b4a99.jpg)
![中国史话·近代政治史系列:农民运动史话 [A Brief History of Peasant Movement in Chin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905494/3a4c8cef-20bf-4537-b1c5-7f5351e2db4a.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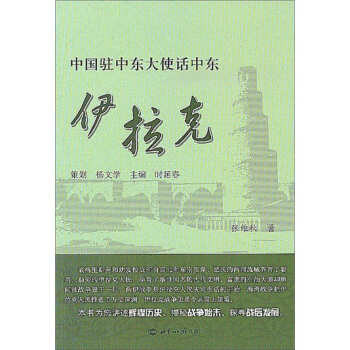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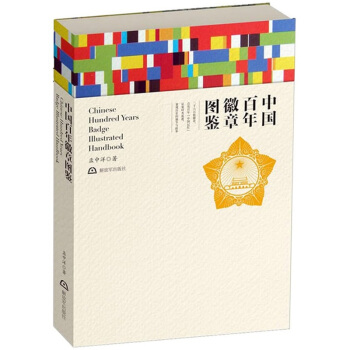
![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963060/rBEIDE_VuVwIAAAAAABE-LhmfugAAAjyQIMdJQAAEUQ73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