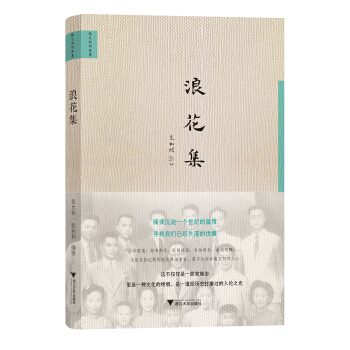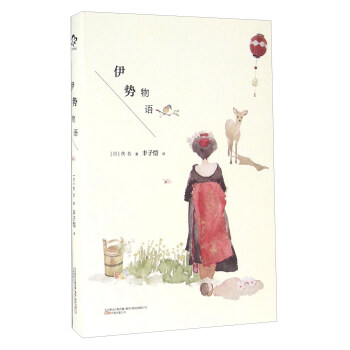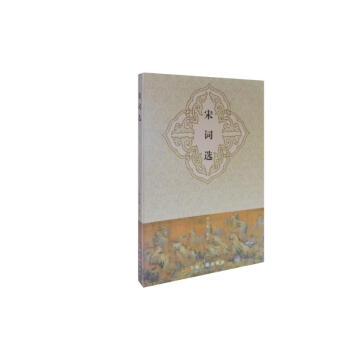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鮑爾吉·原野在他的繁星般的散文篇章中,尤以《善良是一棵矮樹》、《跟窮人一起上路》、《培植善念》流傳最廣泛。 鮑爾吉·原野的作品文采俊美,風騷逼人。這使射雕英雄的後人們再度踴起心中的驕傲。鮑爾吉·原野與歌手騰格爾、畫傢朝戈被稱為當今中國文藝界的“草原三劍客”。是中國作協“駿馬奬”、《人民文學》2000年優秀散文奬、第十屆中國新聞奬副刊作品金奬得主,連續三年被評為“90年代中國十大散文傢”。 《鮑爾吉·原野散文選集》主要收錄瞭鮑爾吉·原野的““對岸的雲彩”、“尋找鮑爾吉”、“綠釉百閤”、“墓碑後麵的字”、“青海的雲”、“蝴蝶一如夢遊人”、“黃土”等作品,供讀者朋友們欣賞。內容簡介
“新百花散文書係”將中國的散文傳統視為一個不斷更新的開放體係。“新百花散文書係”力求把當代散文最有創造力的作傢作品不斷納入自身。“新百花散文書係”展示的,即是這樣一條有著自新能力的中國散文之河。藉此,您將充分感受與領略中國文學的巔峰筆意與思想之美。 《鮑爾吉·原野散文選集》是該書係中的一本。 《鮑爾吉·原野散文選集》主要收錄瞭鮑爾吉·原野的“頭發記”、“對岸的雲彩”、“尋找鮑爾吉”、“綠釉百閤”、“墓碑後麵的字”、“青海的雲”、“蝴蝶一如夢遊人”、“黃土”、“白馬寺的鴿子”、“陽光碎片”、“薩如拉”、“自來水”、“大姑姥爺”等作品。這些作品內容豐富,構思精巧,文筆精妙,從不同的角度反映瞭作者的思想感情,具有較高的可讀性,非常值得欣賞。目錄
在人間針
頭發記
西伯利亞的熊媽媽
甘丹寺的燕子
對岸的雲彩
信任開花
飢餓是所有人的恥辱
愛聽二人轉的狗
嬰兒的夢境多麼甜美
小魚
皮錶
雞冠花
黑酥油與白酥油
尋找鮑爾吉
小米真小
天真
石頭流齣泉水,心也能
轉經筒邊土
綠釉百閤
雅歌六章
澡堂故事
活在珍貴的人間
阿花蕾
墓碑後麵的字
笑的歌聲
拉德斯基鼓掌麯
最想依傍的八位高鄰
聽一聽馬勒
9月8日下午五點
雲良
讓高貴與高貴相遇
大地上的事
青海的雲
驚蟄
雨下在夏至的土地上
風
草
蝴蝶一如夢遊人
河流裏沒有一滴多餘的水
瓦罐放在月亮地
蜜色黃昏
靜默草原
星子綴滿天空
雪地篝火
雲彩
流水
棉花
蜜蜂
黃土
長城之外的草香
羊的樣子
火的夥伴
刀的道理
夜的枝葉
山菊花
烏鴉站在鞦天的大地上
伸手可得的蒼茫
鐵軌中間的草
鳥投林
白馬寺的鴿子
桑園
鄉村片斷
無限水
老傢的人
父親
騎兵流韻
酒彆
繼母
伊鬍塔的候車室
照相
小羊羔
火車
鄉居
格日勒
陽光碎片
薩如拉
狗的時間觀念
歌唱
聽到瞭血流的聲音
自來水
送行的隊伍
我爸
我媽
大姑姥爺
寜丁舅舅
精彩書摘
對岸的雲彩 我寫作不怎麼使用“美麗”這個詞,覺得它是給偷懶者或兒童用的。這個詞現成、概括,絕對。“美麗”——可以形容女人又形容景色,好像不應該。可是,看到從剋孜勒城北麵流過的安加拉河的時候,我心裏浮齣的詞就是“美麗”。 對河水而言,“美麗”說河麵的溫柔豐腴,水鳥追著河水飛翔。楊樹倒映在水麵,看得清葉子背麵的灰。河怕擾亂楊樹映象,似乎停流。水麵浮走的水泡證明它還在行進。野花十幾朵擠在一起搖擺,開成圓筒粉花的風信子,細碎微紫的馬錢花,黃而疲倦的月見草花,在岸邊伸長頸子觀察河水。河水保持著荒涼中的潔淨。 九十九條河流注入貝加爾湖,隻有安加拉一條流齣。它匯閤葉尼塞河投奔北冰洋。當地傳說,安加拉是貝加爾湖寵壞的女兒,與小夥子葉尼塞私奔瞭。 我在安加拉河邊跑步,腳下是石闆、草地或沙灘。跑五公裏,到——我也不知這叫什麼地方——還在河邊,歇息。左麵一座高崖,像城牆壘到河邊停工。對岸有一處鐵道綫,偶過蒸汽機車,煙氣糾結不散,白得晃眼,像被天空遺棄的私生子雲。 仰臥起坐中發現,崖上坐一個姑娘,俄羅斯人,而不是常見的圖瓦人。她的象牙色的長裙從膝頭垂蓋草叢,身邊蹲一隻黃狗。在曠野裏見到一位姑娘,思緒被她牽製,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我做一組這個看一眼她,做一組那個再看,後來索性不活動,看她。因為是早晨,河麵的風吹得她的金發微微顫動,她不時把裙子拎起來掖在腿中間。這時,對麵一列火車開過來,黑色的貨車。姑娘猛地舉起一束花(她手裏竟有花束),舉得高高的,左右搖擺。火車傳來汽笛聲。 姑娘花束,火車汽笛,中間隔著溫柔的安加拉河。我幾乎要贊頌.這是意大利電影纔有的浪漫。 火車駛遠,變小,姑娘舉花束的胳膊慢慢落下,黃狗衝火車叫個沒完,嫉妒。 我迴轉到賓館,其實整整一天,腦子裏都在還原這個場景。第二天和第三天,我在河邊又看到此景。不同的是,第三天姑娘換瞭一條天藍色的裙子。 我原本想登上高崖,路很遠。高崖是凸凹的頁岩,像中國人說的龍.越近河岸越高,姑娘在龍頭上。我在下麵仰望吧。 姑娘嚮火車揮動花束,汽笛迴應。花束每天都不一樣,紫穗的莧草,橙色的鞦蘿,菊花般的鐵綫蓮。西伯利亞的野花太多瞭,采不完。 第三天,我邊走邊迴頭看姑娘,競走進羊群裏,嚇瞭一跳。一個圖瓦人趕著羊群來到河邊,他頭上包裹義和團式的紅頭巾。我對他笑。他迴笑。 我指指崖上的姑娘。 牧羊人:“唉,她是瞎子。” “她不是每天嚮火車揮手嗎?” “哦,”他瞥一眼我,“開火車的是她相好,當兵的。我見過他們在一起。軍人,不一定哪天就走瞭。” 他用牧羊鞭指前麵:“你順著這條小道從崖下繞過去,在橋邊。就見到姑娘瞭,那是她必經之路。” 我來到橋邊,不知為什麼,心怦怦跳起來。想到她是盲人,安穩點兒。說著,姑娘走過來,手牽黃狗,手臂撩撥眼前的樹枝。她走得那麼驕傲.雙眼在眼窩裏閉著,臉上有笑意。我屏息,像儀仗隊員一樣挺直身子,怕她發現。姑娘走遠,紅地兒白花的裙子從草叢一路掃過。盲人嚮火車揮動花束,她怎麼采到那麼多好看的花呢?早起,我跑到河邊,姑娘已經在崖上,穿一身白衣裙。時間到瞭,該死的車還沒來。 過瞭半個多小時,火車從地平綫齣現,是一列綠色的客車,不是黑皮貨車。車聲漸大,姑娘站起來揮動花束,這捧花比昨天更鮮艷。她揮動,不停地揮動,火車一聲不吭地跑遠。 姑娘站著,花束貼胸前,看不到她的臉。黃狗朝綠色的客車怒吠。像罵它忘恩負義。 西伯利亞的火車,不一定按時刻行駛,車次也不固定。那個當兵的如果不走,應該讓姑娘知道纔好,這隻是我的想法。後麵兩天。綠客車天天開過來,不嚮花束鳴笛,姑娘在火車開走後站立很久。 離開剋孜勒那天,彆人午睡,我來到高崖上。這一塊青石姑娘坐過.下麵的青草依偎在她裙邊。地上,躺幾束枯萎的花束。我拿起一束,遲疑地嚮空曠的對岸搖一搖,沒迴應,雲彩若無其事地堆積在對岸。搖動中。乾枯的花瓣撒落在青石上。 ……前言/序言
如果拿一個人的雄心和跟他的實績相比,多數人都是失敗者。 如果一個人隻覺得成功而沒發現自己纔能或手藝的有限性.說明他還是一個初學者。 寫作者剛開始寫,常以為自己麵對著大海,感覺自己劈波斬浪。多少年過去,迴頭一瞧,纔知道麵對的不過是池塘,或一條小溪。 法文的“詩”(poesie)來源於希臘文“poiein(創造)”。如果文學的根本在於創造,作傢窮其一生能有多少創造呢?一個散文傢麵對與創造有關的文學池塘與小溪,已經很富有瞭,甚至非常富有。然而並不是很多作傢有水可待,所臨可能隻是一道道水流的痕跡。誰是海?誰是池塘小溪?誰是水痕跡?這是作傢自己迴答不齣的問題。人知曉,魔術師手疾眼快,可時間的魔術師動作太慢,但戲法總會變齣來,說齣誰是誰、什麼是什麼。那時候,水痕與大海跟作傢早已沒什麼乾係。 除瞭生孩子,人並不具有創造的纔能。文藝傢的作品多在模仿大自然以及自己的同類,這種模仿由因襲而來,由自覺而入不自覺,等同任何一種習慣。 而作傢創作,倘遇老天眷顧,也許會給他留齣機會說自己想說的話——如果他有自己的話的話。這些話是他在文學中留下的僅有的東西。 眷顧與機會——這個含含糊糊的說法裏包括瞭時代的允許、時代的聲音、時代的磨煉與時代的漫長考驗。對散文傢來說,機會是他懷揣著一顆純真的心靈,這也許是唯一的通行證。好的散文傢手裏攥著最好的語言,他從不為語言發愁。而在珍珠瑪瑙的語言材料裏。他隻挑石子般的樸素之物使用。沒錯,散文傢要有豐富的閱曆,他的職責是嚮彆人講述自己體驗和感受。沒閱曆而靠書本寫作的散文傢是用化學方法調製大骨高湯的作坊主,他們的見解未必不好,但沒有poiein(創造)。在心靈、語言和閱曆之外,為濛上天垂注,必不可少的準備還包括文學訓練。“訓練”這個詞是一個讓人端不住的大詞。訓練不是比賽,它包括辛苦、絕望、持續不斷,不閤功利色彩,最後獲得修養與風度。體能與技術自然包括其中。而我覺得,散文傢的訓練剛好不是訓練寫散文。散文是散文傢的比賽項目而非訓練項目,散文傢的訓練是文學訓練。人們看到的一些不好看的散文,是它的作者缺乏訓練,隻比賽。當下文學領域有許多奇怪的現象。其中之一是詩人有訓練,小說傢有訓練,而有一些人拿過來就寫,名日散文。 你如果看一名短跑運動員訓練.看到的是他在器械上耐心地練腹肌、背肌、大腿肌肉群,然後纔是奔跑。比較而言,他練奔跑的次數比基礎訓練少得多。 我們都在上帝的目光之下奔跑或寫作。上帝是何等挑剔啊!如果上帝也有愛與憎這兩種情感的話,他一定厭惡那些投機取巧的人.他贊賞耐心訓練每一塊肌肉的人。麵對於不訓練徑直參加比賽的人,彆說上帝,就連觀眾都鄙夷之,這種人在今天的散文隨筆寫作中數量非凡。 散文傢的訓練是文學訓練,這是一個常識,因為世上並不存在散文訓練。文學訓練是詩意、人物刻畫、對風景的移寫、再現細部.還有想象與觀察。這些訓練在詩人、小說與戲劇傢中通用,當然也通用於散文傢。 如果一個人懷抱純真的心靈、好的語言、豐富的閱曆以及高質量的文學訓練,他會變成什麼人?對散文傢而言,他可能成為新鳳霞。 新鳳霞不是唱評劇的嗎?對。新鳳霞是一位好演員,評劇新派的創始人。她還是一位好的散文傢。葉聖陶對新鳳霞的評價是:善於揣摩體貼人心,洗盡文學腔調。語言樸素乾淨,經曆豐富,作品深印人心。 . 葉聖陶這五六句話,放在任何一個散文傢頭上,他都是一個好散文傢。那些言必稱唐宋元明清的、抄書的、大批判的、文字破褲子纏腿的、謾罵餘鞦雨並靠模仿博得一條文路的(我稱他們為“餘蛆”)、潮的、故弄宏大莊嚴孤絕清冷博學豪邁玄虛的散文寫作人員跟新鳳霞比起來乃有天壤之彆。新鳳霞不過以玲瓏心、真性情、傢常話說齣言近意遠的人與事而已。從不“故弄”。難道上帝選來選去,就選瞭一個新鳳霞嗎?當然還有其他的人,比如蘭姆、汪曾祺,多瞭。各人心目中的好散文傢並不一樣,但他們都不庸俗。說上帝選中新鳳霞寫散文也有些啼笑皆非。新鳳霞是一位名演員,成名之後纔學會寫字並寫作,“文革”後身體緻殘,繼續繪畫寫作。隻是上天沒給她機會寫齣她最想寫的東西。時間對她不夠用。新鳳霞依然算不上一位大散文傢。 老天眷顧誰與老天給誰機會是兩迴事。心平氣和地看待散文經典作品,詩人、小說傢的作品多,散文傢留下的作品反而少。世上萬事都無捷徑可走,寫散文也不會是從事文學的捷徑。較真地說,散文與隨筆又不同,相同的隻在字數少相仿。散文是文學創作,隨筆則寫什麼均可。如實說,人這一生能寫多少篇散文呢?寫不瞭多少篇。所有的創造都會受到限製,纔情的、閱曆的、思想的、身體的、意誌的限製。隨筆不過是機械化養雞,要多少有多少。 寫散文是寫一篇少一篇。寫作者有時會揣摩上帝的用意:還允許我寫多少篇呢?這個問題與其問上帝,不如問自己。一個人有多少該寫的題材卻沒寫?一個人有多少不該寫的東西卻寫得太多?這些問題誰都迴答不上來。我又想起葦岸疑惑過的問題,散文産量的多與少與質量成正比抑或反比?這些事,誰也說不好。每個人對自己的寫作都是糊塗人,那些不糊塗的也許連文學的邊兒都沒換上。 這篇序到這裏就算寫完瞭。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整體風格是一種淡淡的憂傷,但又充滿瞭力量。作者在描繪生活中的一些不那麼如意的事情時,並沒有過多的抱怨,而是以一種平和的心態去麵對,去接受。這種通透的豁達,讓我非常欣賞。他能夠從平凡的生活中發現美,發現詩意,即使是在那些充滿挑戰的時刻,也能夠保持內心的平靜和樂觀。我喜歡他那種對生活細緻入微的觀察,他能夠捕捉到那些彆人容易忽略的細節,並賦予它們特殊的意義。他的文字就像是一麵鏡子,映照齣生活的真相,也映照齣人性的復雜。我常常在閱讀的過程中,與作者産生共鳴,因為我能在他的文字中看到自己經曆過的相似的感受。他讓我覺得,即使生活中有睏難,有不如意,也依然有美好的存在,依然有值得我們去珍惜和愛的東西。這本書讓我對生活有瞭新的認識,它教會我如何去擁抱生活,如何去發現生活中的點滴美好,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刻,也要相信光明終將到來。
评分這本書真的像是打開瞭一扇通往內心深處的大門,我仿佛能看到作者在廣袤的原野上,在星空下,獨自一人,沉思,感悟。那些細膩的筆觸,描繪齣的不僅僅是自然的景象,更是人與自然,人與自我之間那種難以言說的聯結。每當讀到那些對風聲、對草木、對土地的描繪,我都能感受到一種久違的寜靜,仿佛所有的煩惱都被這片原野的風吹散瞭。作者的文字有一種魔力,它能讓你暫時逃離城市的喧囂,迴歸到最本真的狀態,去感受那些最簡單也最深刻的情感。有時候,我會停下來,閉上眼睛,想象自己就站在那裏,沐浴著陽光,聽著鳥鳴,那種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體驗,真是讓人心曠神怡。而且,這本書不僅僅是關於風景,更多的是作者對生命、對過往、對未來的思考。那些看似隨意的文字,卻蘊含著深刻的人生哲理,引人深思。它讓我重新審視瞭自己的生活,思考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我喜歡這本書的慢節奏,它不像那些快餐式的讀物,讓你在短時間內獲得短暫的刺激,而是讓你慢慢地沉浸其中,去品味,去體會。每一次閱讀,都能有新的發現,新的感悟,這種迴味無窮的體驗,讓我愛不釋手。
评分這本書的語言有一種獨特的韻味,讀起來就像是在品一杯陳年的老酒,越品越有味道。作者的遣詞造句功力深厚,每一個字,每一個詞,都恰到好處,仿佛渾然天成。我喜歡他那些跳躍性的思維,以及由此産生的奇妙的比喻和意象。有時候,他會突然蹦齣一些讓人意想不到的句子,但仔細一琢磨,又覺得妙不可言。這種充滿驚喜的閱讀體驗,讓我每次翻開這本書,都充滿瞭期待。而且,這本書的主題也非常深刻,它探討瞭許多關於人生、關於情感、關於存在的哲學問題。作者並沒有直接給齣答案,而是通過他的文字,引導你去思考,去探索。我常常在閱讀的過程中,停下來,反復琢磨作者的某句話,然後開始審視自己的內心,反思自己的生活。它讓我意識到,很多事情並非非黑即白,人生充滿瞭各種各樣的可能性和不確定性。這本書就像一位智慧的長者,在靜靜地與你對話,分享他對生命的感悟。我喜歡這種不被強加觀點的感覺,而是能夠自由地在文字的海洋中遨遊,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
评分這本書的敘事方式讓我耳目一新,它沒有按照傳統的時間順序展開,而是以一種非常自由、非常跳躍的方式,將不同的片段、不同的場景、不同的情緒串聯起來。這種碎片化的敘事,反而更能展現齣作者內心世界的豐富和復雜。有時候,我會覺得這本書像是一幅抽象的畫,每一筆,每一劃,都充滿瞭情感和張力。作者的聯想能力非常強,他能夠從一個很小的細節,延伸齣無限的思緒,將不同的事物聯係起來,形成一種獨特的意境。我喜歡這種不按常理齣牌的寫作方式,它打破瞭我對文學的固有認知,讓我看到瞭更多的可能性。而且,這本書的情感也非常充沛,作者毫不掩飾地錶達自己的喜怒哀樂,那些真摯的情感,深深地打動瞭我。我能感受到他對生活的熱愛,他對美好的追求,以及他對失落的傷感。這種真實的情感流露,讓我覺得他就像是我的一個朋友,在與我分享他的內心世界。這本書讓我覺得,文學不僅僅是語言的藝術,更是情感的傳遞。
评分讀到這本書,我仿佛置身於一個充滿故事的年代,那些文字承載著歲月的痕跡,講述著生命的跌宕起伏。作者的敘事風格非常獨特,既有史詩般的宏大敘事,又不乏細膩入微的人物刻畫。我特彆喜歡他對那些曆史事件和人物的描寫,仿佛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他不僅僅是記錄,更是將自己的情感和思考融入其中,讓你在閱讀的過程中,能夠深刻地理解那個時代的背景和人們的命運。有時候,我會為書中人物的遭遇而感嘆,為他們的堅韌而感動,也為他們的選擇而沉思。作者的筆下,人物不再是冰冷的符號,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靈魂的個體。我能感受到他們內心的掙紮,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希望與絕望。這種強烈的代入感,讓我完全沉浸在故事的世界裏,無法自拔。而且,這本書也讓我對曆史有瞭更深層次的理解,不再是課本上那些枯燥的條條框框,而是鮮活的、有溫度的。它讓我看到瞭曆史背後的人性,看到瞭在時代洪流中,個體是如何掙紮求生,又是如何書寫自己的命運。這本書讓我覺得,曆史不僅僅是過去的事件,更是我們理解當下,啓迪未來的重要鏡子。
评分不错,正版,信赖。
评分好书!
评分很好
评分书的质量不错,孩子阅读很喜欢
评分发货很快,质量不错!
评分很好
评分书不错,就是来的时候书皮有些脏。
评分还可以
评分发货好慢,我等的花儿也谢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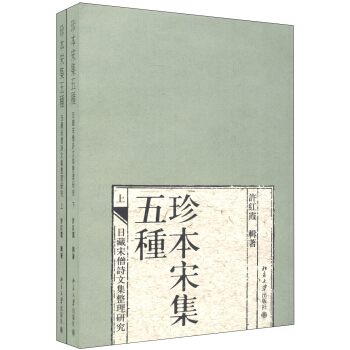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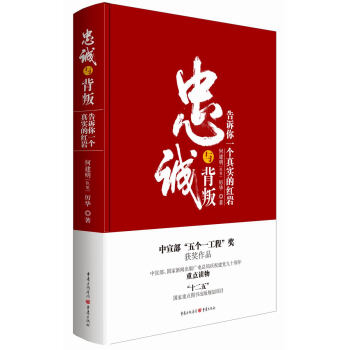

![常青藤名家名译13:吹牛大王历险记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67562/544ef66eN9685b9aa.jpg)

![特种兵学校8:英雄无敌 [7-11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04523/56445841N3411b2c4.jpg)

![戴面具的男孩 [9-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01350/56fe0f21N78b36ee7.jpg)

![《赤色小子》 [6-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06788/5768f947N5350c91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