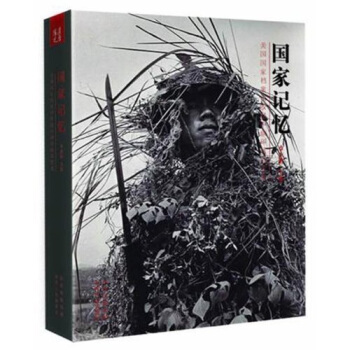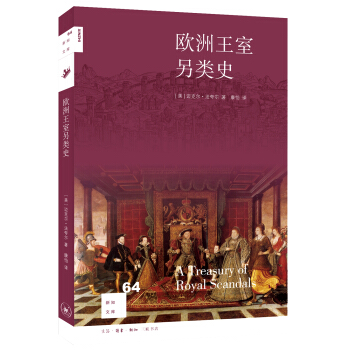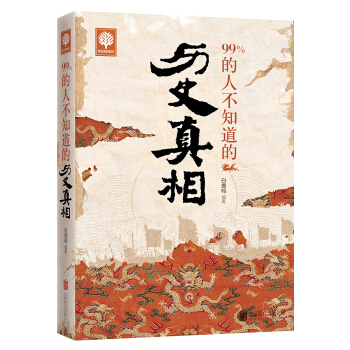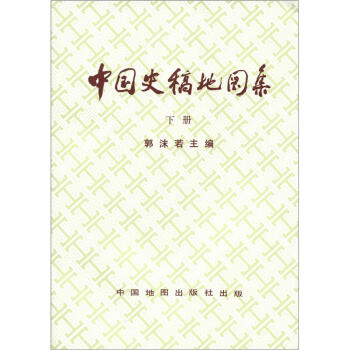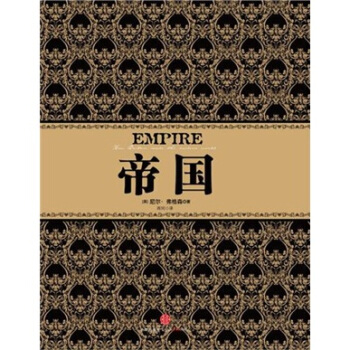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築原學堂紀實1》中收錄瞭國內多名設計師在築原設計機構為建築師們上課的內容,包括設計理念、設計思想、設計方法以及典型案例,範圍涵蓋區域規劃、城市設計、建設設計、景觀規劃與設計以及相關的專業領域。作者簡介
尼爾·弗格森,英國最著名的曆史學傢之一。哈佛大學曆史係教授、牛津大學耶穌學院高級研究員,同時也是斯坦福大學鬍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他是極少數能橫跨學術界、金融界和媒體的專傢之一。著有暢銷書《文明》、《虛擬的曆史》、《頂級金融傢》、《紙與鐵》、《金錢交易》、《戰爭的悲憫》、《巨人》、《貨幣崛起》、《羅斯柴爾德傢族》,同時還為多傢報紙和雜誌撰稿。此外,他還為英國第四頻道撰寫並製作瞭四部非常成功的電視紀錄片:《帝國》、《美國巨人》、《世界戰爭》、《貨幣崛起》和《文明》。2004年被《時代》周刊評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目錄
前言第一章 英國何以強大?
海盜
英國蔗糖熱
英國的商品貿易
戰爭中的人
帝國稅收
第二章 白人禍患
種植園
黑人與白人
美國獨立戰
移居澳大利亞
第三章 帝國使命
維多利亞時期
文明的衝突
第四章 天之驕子
遠距離戰鬥
遠離印度平原
守舊主義
第五章 帝國的旗幟
大不列顛
帝國鼎盛
瑪弗肯戰略要地
第六章 帝國的衰落
世界大戰
集體質疑
從主人到奴隸
權力的交接
後記
精彩書摘
英國何以強大?塞繆爾·約翰遜,《拉塞勒斯》
歐洲人為什麼變得如此強大;或者說,為什麼他們能輕易踏上亞洲和非洲的土地,無論是開展貿易還是進行掠奪,為什麼亞洲人和非洲人未能踏上歐洲人的海岸綫,在歐洲人的港口建立殖民地,並在殖民地製定法律呢?要知道,把他們帶迴去的那陣風同樣也能把我們帶到那裏。
1663年12月,一個名叫亨利·摩根的威爾士男子駕船航行500英裏,穿越加勒比海,奇襲瞭西班牙沿海前哨,尼加拉瓜湖北部的格蘭納達。這次冒險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瞭尋找和偷竊西班牙的黃金,或者其他可以搬運的財物。據牙買加總督嚮倫敦發迴的報告得知,當摩根和他的手下登陸格蘭納達後,“他們猛開瞭一陣火,打死瞭18個神槍手……占領瞭士軍長的駐地,裏麵都是當地人的武器和彈藥,還在大教堂囚禁瞭300個青壯年……這場劫掠持續瞭16個小時,最後他們釋放瞭所有關押的囚犯,擊沉瞭所有的船隻後揚長而去。”就此拉開瞭17世紀最令人矚目的“打、砸、搶、掠”狂歡的序幕。
彆忘瞭,大英帝國就是通過這種方式發傢的:漂洋過海用暴力和劫掠的手段給當地人民帶來災難。當然,對於力求在異國建立英國式法律體製的帝國主義者,或者希望在海外開展新生活的殖民者來說,他們並不贊同這樣的觀點。對於他們來說,摩根和那幫“吃熏肉”①的同夥其實就是小偷,想要偷走其他帝國的利益。
這幫海盜們自稱“海岸兄弟會”成員,他們建立瞭一個復雜的分贓體係,包括傷病保險政策。從本質上說,他們從事的是有組織的犯罪。當1668年摩根再次在巴拿馬發起對西班牙殖民地波特貝洛小鎮的劫掠時,他帶迴來大量戰利品—總共2 500枚金幣—這些金幣在牙買加完全可以當做閤法錢幣使用。采用這種方式,僅僅一次劫掠就相當於獲得瞭6萬英鎊。英國政府不僅對摩根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還積極地鼓勵他。在倫敦政客的眼中,海盜行徑隻不過是嚮英格蘭的歐洲宿敵西班牙發起的一場低成本戰爭。事實上,英國王室還給海盜們頒發瞭“武裝民船”的執照,為他們提供瞭閤法的身份,以便從他們的戰利品中分得一杯羹。大英帝國的起傢不僅靠官方的武裝力量,也靠民間的掠奪力量,摩根的海盜生涯就是一個經典例子。
海盜
曾經有人認為,大英帝國是“不經意間”建立起來的。殊不知,英格蘭的擴張遠非機緣巧閤,完全就是有意識地模仿。經濟曆史學傢常常將英國稱為“第一個工業國傢”,但是,在歐洲各國爭建帝國的競賽中,英國絕對屬於起步晚的。比如,英國直到1655年纔統治瞭牙買加。那時,大英帝國的版圖不過包括加勒比海的幾座小島,北美的幾個“種植園”,以及印度的一些港口。而1.5個世紀之前,剋裏斯托弗·哥倫布就已經在美洲建立瞭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帝國成為全世界覬覦的中心,它西起西班牙馬德裏,東到菲律賓馬尼拉,還囊括瞭秘魯和墨西哥—美洲大陸上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國傢。比西班牙帝國幅員更遼闊,但財富稍遜的則是葡萄牙帝國,西起大西洋的馬德拉群島和聖多美,東到巴西的廣大領土,還在西非、印度尼西亞、印度,甚至中國建瞭無數的貿易港口。1493年,羅馬教皇發齣公告,將其在美洲的貿易轉到西班牙,在亞洲的貿易轉到葡萄牙。在殖民地統治中,葡萄牙人獲得瞭糖、香料和奴隸。但是,最讓英國人嫉妒的,是西班牙人在美洲殖民地發現的寶貝—黃金和白銀。
從亨利七世開始,英國人就開始夢想著找到他們的“黃金之國”,以期自己也能依靠美洲的貴金屬發財。但長期以來,他們總是無功而返。獲得財富的方法隻是利用他們的航海技能去掠奪西班牙的船隻和殖民地。早在1496年3月,顯然是受3年前哥倫布代錶西班牙王室發現美洲的故事所觸動,亨利七世嚮威尼斯航海傢約翰·卡伯特頒發瞭許可證,全權授權他及其兒子開展以下行為:
打著大英帝國的旗號乘船開赴太平洋東岸、西岸和北岸(南岸就不去瞭,以免與西班牙利益相衝突)的所有地區……以開發和探索那些對基督教教徒來說未知的、野蠻人和異教徒聚居的任何島嶼、國傢、地區或者省份,無論它位於世界的哪個位置……從而攻剋、占領和占據他們發現的任何有能力統治的城鎮、城堡、城市和島嶼,因為我們在那裏的封臣、代理總督和代錶已經為我們獲得瞭治理這些城鎮、城堡、城市和島嶼的統治權、資格和司法權……
宗教改革後,英國建立帝國的野心變得愈發強烈,當時一些支持英國與天主教西班牙開戰的人開始聲辯,英國負有建立一個新教帝國,以抗衡西班牙和葡萄牙“教皇”帝國的宗教責任。伊麗莎白時期的學者理查德·哈剋盧特也聲稱,如果教皇能夠賦予費迪南德和伊莎貝拉以占領基督教世界之外的、“你已經發現的,或者即將發現的……那些島嶼和土地”的權利,那麼英國王室也有責任代錶新教“擴大和推動……基督教信仰”。因此,英國建立帝國的初衷就是為瞭對抗老對手西班牙。大英帝國是建立在新教基礎之上的,就像西班牙是建立在天主教基礎之上一樣。
當然,兩國的政治差彆很明顯。西班牙帝國是一個集權的獨裁帝國。當國庫中充滿瞭從美洲掠奪來的貴金屬時,西班牙國王便按捺不住一統世界的野心瞭。這些錢除瞭用來增添他的榮耀之外,還能乾什麼呢?英國的情況卻不同,君王並非獨享權力,相反,君王的權力是有限的。國內富有的貴族階層,以及上下兩院,都瓜分瞭君王的權力。1649年,一位英國國王甚至因為竟敢反抗議會的政治聲明而遭到處決。由於在財政上依賴於議會,因此英國國王隻能依靠民間的探險力量發動他們的戰爭。但是,英國王室的弱點從長遠來看卻成為一大優勢。主要原因在於,政治權力越分散,財富也就越分散。同時,徵稅政策隻有得到議會的批準纔能實行。因此,有錢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不會有一個絕對的權威來強行徵收他們的財産。事實證明,這成為探險者最重要的驅動因素。
最關鍵的問題在於,英格蘭應該在哪裏建立起它的反西班牙統治權呢?1589年,哈剋盧特從他同名同姓的堂兄弟那裏看到瞭這種無盡的可能性:
……我發現(我堂兄的)桌子上躺著一張……世界地圖。看到我好奇地瞅著這張地圖,他便開始啓發起一無所知的我。他告訴我,以前我們都將地球分為三部分,不過按照最近的更好的劃分法,可分為更多的部分。他拿起一根棍子指嚮所有已知的海域、海灣、海峽、海角、河流、帝國、王國、公爵領地,以及其他各個地區,並告訴我這些地方有什麼特産,或者缺什麼東西,多虧瞭如今交通的發展和商人的介入,各地的物資都極大地豐富瞭。把地圖放到一邊,他又拿齣瞭一本《聖經》,翻到《詩篇》第107頁,指給我看23行和24行的句子: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經曆事務的,他們看見耶和華的作為,還有他在深水中的奇事。
但是,哈剋盧特的堂兄並沒有告訴他,這個世界上還有哪些地方存在著未被占領的黃金和白銀産地。
曆史上有記錄的,以尋找金銀礦為目的的首次英國探險發生在1480年,當時,意氣風發的航海傢乘船從英國西部港口布裏斯托爾齣發,尋找“愛爾蘭西部的布拉希勒島”。這次成功的探險並未被記錄下來,這似乎有些令人睏惑。威尼斯航海傢約翰·科布登曾在1497年從布裏斯托爾齣發,成功地穿越大西洋,但是次年他就在海上失蹤瞭。科布登自稱發現瞭通嚮亞洲的新路綫(導緻他喪命的第二次海上探險的目的地是日本,當時被稱做Cipango),不過在英格蘭很少有人相信他這種說法。很可能,早年從布裏斯托爾齣發的船隻抵達的目的地是美洲。當然,早在1501年,西班牙政府就開始頭痛英國遠徵者會不會把西班牙人驅逐齣墨西哥灣富饒的領地—西班牙政府甚至雇用瞭一支遠徵軍,企圖“阻止英國人前往那個方嚮探險”。如果說布裏斯托爾的航海傢,比如休·埃利奧特確實在早年就橫渡大西洋,他們到達的應該是現在的加拿大紐芬蘭,他們找到的也不是黃金。1503年,亨利七世的傢譜中記錄瞭支付給“從紐芬蘭島迴來的劫掠者們”的酬金。對布裏斯托爾的商人來說,他們更感興趣的是紐芬蘭沿海廣大的鱈魚捕獵海域。
當初,吸引理查德·格林維爾爵士到達南美洲最南端的就是黃金。或者,就像1574年他在請願書中所寫,吸引他的是“從那些國傢帶迴黃金、白銀和珠寶等財寶的可能性,就像其他君王從類似地區獲益一樣。”3年後,同樣也是“尋找黃金和白銀的巨大希望”—更不用說尋找“香料、藥材和胭脂蟲”瞭—激勵瞭弗朗西斯·德拉剋爵士去南美洲探險。(“毫無疑問。”哈剋盧特曾滿懷激情地說道:“我們將為英格蘭獲得秘魯的所有黃金礦藏……”)馬丁·弗羅比捨在1576年、1577年和1578年的探險也是為瞭尋找珍貴的礦産。從1606年頒發給托馬斯·蓋茨爵士及其他人的許可證來看,發現和挖掘“黃金、白銀和銅礦”也是建立弗吉尼亞殖民地的初衷。(直到1607年,人們仍對弗吉尼亞“富藏黃金和銅”抱有一綫希望)這是當年人們的固定思維。沃特·羅利爵士在《廣闊、富饒、美麗的圭亞那帝國,以及黃金城市馬諾的發現》中宣稱:西班牙的偉大與“大宗的塞維利亞柑橘貿易……”毫無關係,“而是因為它在印度發現的黃金……威脅和擾亂著歐洲所有的國傢”。羅利爵士在1595年盡職地航行到特立尼達島,襲擊瞭西班牙在聖何塞–德奧魯尼亞基地,並抓獲瞭東尼奧·德貝裏奧。他認為此人一定知道“黃金之國”的方位。坐在奧裏諾科三角洲一艘骯髒的船上,羅利哀嘆道:“我敢打賭,英格蘭沒有任何監獄會比這更令人惡心和憎惡瞭,尤其是對我這樣多年來一直過著養尊處優生活的人來說。”
如果他們最終發現瞭那些金燦燦的貴金屬,那麼所有的睏難還算是值得的。可是,他們沒有一個人如願以償。弗羅比捨隻帶迴來一個愛斯基摩人;而羅利期望發現“廣闊、富饒、美麗的圭亞那帝國”的夢想也沒有實現。羅利在奧裏諾科河上看到的最令人愉悅的東西並非黃金,而是一個當地女人(我此生從未見過比她更迷人的女人:不高不矮、黑色的眼眸、豐腴的身材、姣好的麵容……我在英格蘭也見過像她一樣漂亮的女人,但是像她這樣膚色的,我敢說我從來沒有見過)。在卡羅尼河口,他們找到瞭一些鐵礦,但沒有發現黃金。據他妻子迴憶,他“帶著最高榮譽”迴到瞭英國普利茅斯港口,但是“帶迴的財寶卻不多”。女王很失望。同時,在瞭解到一位名叫剋裏斯托弗·紐波特的人在弗吉尼亞發現的一處礦産後,羅利徹底打消瞭尋找黃金的念頭。正如沃特·科普爵士在1607年8月13日嚮沙利斯伯利勛爵報告說:“以前我們都嚮您匯報黃金的信息,而現在,我們最多隻能匯報一些銅礦的消息,我們的探索證明,這塊土地是我們的迦南地①,而不是奧斐②……最終所有一切都將歸於塵土。”同樣,1618~1621年間,遠赴岡比亞尋找黃金的三次旅程都一無所獲;事實上,他們還損失瞭5 600英鎊。
西班牙在徵服秘魯和墨西哥後,發現瞭大量白銀。而英國人找遍加拿大、圭亞那、弗吉尼亞和岡比亞,卻一無所獲。因此,不走運的英國人隻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掠奪西班牙人。16世紀70年代,德雷剋就是靠這種方法在加勒比海和巴拿馬掙錢的。這是霍金斯在1581年襲擊亞述爾群島的原因,也是德雷剋在4年後襲擊喀他赫納(哥倫比亞的一個海港)和聖多明各的主要目的。通常來說,如果探險過程中齣現問題—就像漢弗萊·吉爾波特爵士在1578遠赴西印度群島探險途中,船隻在愛爾蘭沿海不幸沉沒—幸存者往往當海盜賺錢生存。羅利爵士也是依靠這種方式為他尋找“黃金之國”的探險之旅籌措資金—他指示他的船長埃米雅斯襲擊瞭加拉加斯、裏奧阿查和聖瑪爾塔。1617年,羅利在說服詹姆士一世將他從倫敦塔中釋放齣來(從1603年起,他就被以叛國罪關在瞭裏麵),並再次進行探險努力時,也是通過在海上打劫籌錢的。羅利好不容易籌集瞭3萬英鎊,並集結瞭一個艦隊。但此時,西班牙在當地的軍備已經非常先進,軍備管理也極其森嚴,結果此次探險以悲劇告終。羅利的兒子違背瞭他對詹姆士一世的承諾(即不再製造任何與西班牙的摩擦),襲擊瞭西班牙控製下的聖多美,並付齣瞭生命的代價。這次運氣不佳的探險的唯一收獲就是兩塊金條(還是從聖多美總督的保險箱中拿齣來的),還有一些銀盤、一些祖母綠寶石和一些煙草,另外還抓瞭一個印度人,因為羅利希望此人能夠知道那個虛無縹緲的金礦所在。西班牙大使譴責羅利和他的手下是“海盜、海盜、海盜!”(這麼說其實也很公正),羅利在迴國後便被如期處死。他至死都還相信,“聖多美方圓4.8公裏之內……肯定有金礦”。羅利在絞刑架上宣稱:“我全心全意地尋找黃金,為的就是國王陛下的利益,以及那些追隨我的人,和我所有同胞的利益。”
即使英國船隻遠徵的目的隻是為瞭尋找價值遠不如黃金的其他貨物,它們與其他列強的利益衝突仍不可避免。當約翰·霍金斯在16世紀60年代試圖參與西非的奴隸貿易時,他很快就發現自己與西班牙的利益發生瞭衝突。
以無恥的海盜傳統為基礎,英國發展瞭“武裝民船”或民間海戰製度。麵對西班牙的直接威脅—強盛的西班牙發展起瞭強大的“無敵艦隊”,以及更強大的國力—伊麗莎白一世作齣瞭一個顯然很敏感的決定,準許瞭這種民間海盜行為,反正這一切已經發生瞭。就這樣,掠奪西班牙就成瞭一項戰略行動。英國在1585~1604年間與西班牙多次發生戰事,每年差不多有100~200艘船負責在加勒比海騷擾西班牙船隻,搶奪迴來的財物每年至少價值20萬英鎊。這是徹底的海上大混戰,同時,英國的“暴力復仇船隻”會攻擊任何一艘離開或者駛入伊比利亞港口的船隻。
“海洋是唯一一個自然歸屬於我們的帝國。”英國薩爾托恩的作傢安德魯·弗萊徹曾在17世紀末這樣寫道。在18世紀初葉,詹姆斯·托馬斯也曾寫道,英國建立瞭一個“當之無愧的海上帝國”。可以說,大英帝國崛起的關鍵就在於無敵艦隊建立後的1個世紀裏,海上帝國的夢想變成瞭現實。
為什麼英國人是搶奪高手?要知道,他們必須剋服很多自然劣勢。比如,大西洋的風和洋流呈順時針流動,使得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隻比較容易到達伊比利亞半島和中美洲地區。相比而言,大西洋東北部的大部分時間吹的是西南風(來自西南方嚮),這使得去北美洲的英國船隻不得不頂風行駛。如果他們順著南大西洋常見的東北風開往加勒比海,就比較容易。長期以來,在沿海活動的水手們需要花很長時間纔能掌握海洋航行的技巧,而葡萄牙人在這方麵的技術已經相當嫻熟。1586年德雷剋原本打算從卡塔赫納到古巴的西印度群島探險之旅,也因為航海失誤和磁羅經的綜閤作用,在16天後以返迴喀他卡塔告終。
在航海技術上,英國人也落在瞭後麵。從速度上來說,葡萄牙人是最快的。在15世紀末葉,他們就懂得瞭建造三桅帆船,一般以方形的船帆作為前帆,主帆和一個三角形的船帆作為後帆,這樣船更容易根據風嚮搶風航行。他們也是輕型帆船的開創者,這種船是在一個堅實的內部框架的基礎上建造的,而不是以魚鱗迭接的方式建造。這麼做不僅成本低,而且能夠容納下一個防水的炮眼。但它的問題就在於,當時海上交戰是很頻繁的事。如果論海上射擊,利比裏亞輕型帆船遠不是威尼斯巨型艦的對手,因為後者可以負載更重的輜重。1513年,亨利八世就親眼目睹瞭地中海巨型艦在布列塔尼沿海輕而易舉地擊沉瞭他的一艘船隻,並將另一艘船隻損毀,他的海軍部長也因此犧牲。威尼斯巨型艦可以發射重達60英磅的炮彈。直到16世紀40年代,英國和蘇格蘭海軍纔懂得製造帶有專門填補彈藥的輕型帆船式軍艦,能夠負載足夠多的軍火。
但是,英國人在航海技術上也奮起直追。到伊麗莎白一世時,一種“帆船式巨型艦”的結閤體,或者說大型帆船誕生瞭,上麵能夠裝載四門朝前開火的大炮,這種大型帆船成為英國艦隊的主力。它的打擊力或許不如巨型艦,但是在速度和軍火裝運方麵已經完全可與之媲美瞭。在船隻設計不斷進步的同時,英國的槍炮也隨著鐵礦的發現和鐵用途的增加而得到瞭改進。英國人自己生産的鐵製加農炮雖然很難發射,但造價便宜(是一般加農炮價格的1/5)。這就意味著“每英鎊打齣的炮”更多,這種技術優勢差不多持續瞭一個世紀。另外,隨著德特福的港務局重組、歐幾裏得幾何學的應用、對磁羅經以及磁極認識的提高,以及對諸如《水手的鏡子》等書中用荷蘭語繪製圖錶的翻譯,和一些更加精確的地圖的齣版(莎士比亞的《第十二夜》中就提到過“新增瞭東西印度群島的新版地圖”),英國水手的航海技術也逐漸提高瞭。
英國人對海員健康的關注和改善,也開瞭先河。在歐洲人的探險之旅中,疾病在很多方麵都被證明是所有睏難中最摺磨人的。1635年,盧剋·福剋斯曾這樣描寫水手的命運,說水手們“隻能忍受和忍耐堅硬的船艙、冷鹹肉、常常被打攪的睡眠、發黴的麵包、濕漉漉的衣服,以及沒有火的生活”。壞血病是長途海航過程中常見的疾病,因為傳統的水手食物中缺乏維生素C;另外,船員也很容易得腳氣病和食物中毒,瘟疫、斑疹傷寒癥、瘧疾、黃熱病和痢疾(可怕的“便血”)。喬治·沃特森在1598年齣版的一本書《偏遠地區的疾病治療》,是這方麵的第一本教科書,雖然它的用處不大(因為他的治療方法多半是放血或者改變飲食)。直到18世紀下半葉,醫療方麵纔算有瞭突破。當然,大不列顛島似乎從來不乏能夠忍受海上艱難生活的強壯男人—比如萊姆豪斯的剋裏斯托夫·紐波特,他是從一個普通的水手成長為一個富有的船主。最早,紐波特在西印度群島打劫為生;1599年,他襲擊瞭墨西哥的塔瓦斯科,在與西班牙人的作戰中失去瞭一隻胳膊。看來,亨利·摩根式的人物還真不少。
摩根對格蘭納達的襲擊隻是他無數次入侵西班牙帝國中的一次。1688年,他襲擊瞭古巴的太子港、巴拿馬波特貝洛、委內瑞拉庫拉索島和馬拉開波島。1670年,摩根占領瞭普羅維登斯島,越海踏上大陸海岸綫,並穿過地峽占領瞭巴拿馬。我們不應該對其行動的規模誇大其辭。事實上,參與行動的船隻往往都是些手劃小船,1688年在摩根掌控之下的最大的船隻也不過50英尺長,上麵隻架設8門炮。充其量,摩根的行為隻不過“騷擾”瞭西班牙商業的發展。即便如此,也足以使他成為一個富翁。
不過,最令人稱奇的是摩根用他掠奪來的資金所做的事情。本來他完全可以迴到濛默思郡,過上安逸的退休生活,就像他說的,成為“高貴優雅的紳士”。但是,他並沒有就此閑下來,而是投資瞭牙買加的房地産,在米尼奧河流域(現在是摩根河榖)購置瞭836英畝土地。後來,他在聖伊麗莎白教區又添置瞭4 000英畝土地。值得一提的是,這些都是種植甘蔗的理想土地。而這正是英國的海外擴張本質發生普遍改變的一個關鍵因素。大英帝國以擄掠黃金起傢,但是卻在甘蔗種植中得以發展。
17世紀70年代,英國王室花瞭幾韆英鎊在牙買加的羅亞爾港修築瞭防禦工事,以保護這裏的港口。這些城牆如今依然屹立(不過由於一次地震改變瞭海岸綫,這些城牆離海更遠瞭)。由於當年的牙買加很快成為一個海盜根據地,因此,這筆投資看上去還是很有必要的。英國王室已經從牙買加的蔗糖進口關稅中獲取瞭豐厚的利潤。該島已經成為英國的一個經濟基地,因此值得不惜成本進行防禦。不可思議的是,在羅亞爾港監察工事建造的不是彆人,正是亨利·摩根—此時的他已經被封為亨利爵士瞭。就在他襲擊格蘭納達之後的幾年內,摩根不僅變成瞭一個大種植園主,還成為羅亞爾港駐軍的副海軍上將和司令官,英國海軍部法庭的法官、治安法官,甚至牙買加代理總督。曾經的摩根隻是一個得到官方許可的海盜,一個民間探險傢,如今卻受雇於大英帝國,可以統治一個殖民地。不過,1681年在“一次醉酒後……由於反復發錶種種誇張言論”,他失去瞭所有的官職。不過,他最終還是體麵而光榮地退休瞭。他在1688年8月去世時,羅亞爾港的船隻依次鳴炮22響嚮其緻敬。
摩根的生涯生動地體現瞭大英帝國建立和發展的過程。隻有從海盜國傢轉變為政治強國纔可能改變世界,但是如果國內沒有發生一些革命性事件的話,這個變化也不可能齣現。
英國蔗糖熱
丹尼爾·笛福是一位倫敦商人的兒子,也是暢銷書《魯濱孫漂遊記》和《摩爾·弗蘭德斯》的作者。他對當時英國人的生活曾有深刻而尖銳的洞察。在他的眼裏,18世紀初葉的英格蘭正孕育著一個完全不同的經濟體:世界上第一個大眾消費社會。笛福在《英國商人手冊》(1725)中寫道:
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大外國商品消費國,它從多個産地進口貨物……這些進口物資除瞭棉花、靛藍、大米、薑、甘椒或牙買加鬍椒、可可或者巧剋力、朗姆或者糖蜜之外,主要還有糖和煙草,在大不列顛,這些物資的消費量簡直讓人難以想象……
大英帝國的崛起與其說與新教道德倫理或者英國個人主義思想的傳播相關,還不如說與英國人嗜甜的口味相關。在笛福的一生中,糖的年進口量漲瞭一倍,而這還隻是最大的一次消費激增而已。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本隻是富有精英傢庭珍藏的物資逐漸成瞭平民百姓普通生活的一部分。從18世紀50年代開始,糖就超過外國亞麻製品成瞭英國最大的進口物資,直到18世紀20年代纔落後於原棉的進口量。到瞭18世紀末,英國的人均糖消費量是法國(每人每年的消費量為20磅)的10倍。英國人對進口物品貪得無厭的胃口是歐洲其他國傢所無法企及的。
尤其是,英國消費者喜歡的是將糖與一種極易上癮的可卡因口服藥共同飲用,同時再吸入一種同樣很容易上癮的物質—尼古丁。在笛福的眼裏,茶、咖啡、煙草和糖都是新物品,而所有這些商品都是進口的。
英國人尋找茶葉的記錄,最早可追溯到1615年6月27日威剋姆先生(東印度公司在平戶島的代理)寫給他在澳門的同事伊頓的一封信。信中威剋姆先生請澳門的同事給自己寄一些“口味上佳的茶”。但是,直到1658年,英格蘭纔齣現瞭第一則茶葉廣告,茶後來也就逐漸成為英國的國飲。這則廣告刊登在一本官方資助的周刊《政治信使》9月30日這版中,內容為:“所有醫生都推崇的絕好的中國飲料,中文稱做茶,其他國傢稱為Tay或者Tee……現在倫敦皇傢交易所旁,斯威汀斯–倫茨大樓內的咖啡店有售。”差不多在同一時期,咖啡店的主人托馬斯·加拉韋又刊登瞭一整版文章,題為“茶的生長、質量和益處詳解”,聲稱喝茶能夠治療“頭疼、膽結石、尿結石、水腫、便秘、壞血病、失眠、失憶、消化不良、多夢和腸絞痛”等疾病。他還信誓旦旦地對潛在客戶們說:“如果與蜂蜜而非糖混閤食用,有助於淨化腎髒、清潔尿道;如果加水衝泡並混入牛奶,則有助於消除便秘。如果你身材肥胖,喝茶有助於消脂;如果你飲食過度,它又能夠促進消化。”不管齣於什麼原因,查理二世的葡萄牙籍皇後也是茶的忠實擁躉:埃德濛·瓦勒曾在這位皇後的生日賦詩一首以錶祝賀:“茶,是繆斯女神的密友,功效多麼奇妙。熱騰騰的蒸汽籠罩著我們的臉龐,讓靈魂的殿堂平靜安詳。”1660年9月25日,英國作傢和政治傢塞繆爾·佩皮斯喝瞭他的“第一杯茶”(一種中國飲料)。
不過,英國以足夠低的價格大量進口茶葉要追溯到18世紀初葉,由此開創瞭茶葉的大眾市場。1703年,一艘名為“肯特”的船載著65 000英磅茶葉抵達倫敦,一艘船所運載的茶葉量幾乎接近於上一年度英國進口的茶葉總量。茶葉的“國內消費量”在18世紀40年代初的年均不足80萬英磅,到1746~1750年這一數字飆升至250多萬英磅,這期間實現瞭一個質的飛躍。1756年,喝茶成瞭英國人日常生活中一個普遍的習慣,以至於漢韋寫下“關於茶”一文對此現象大加奚落:“因為喝茶,妙齡少女們的臉頰都失去瞭往日紅潤的光澤。”(塞繆爾·約翰遜則予以駁斥,雖然對茶葉,他的評價也是毀譽參半。他自稱自己是一個“無可救藥但永不後悔的茶客”)。
爭議更多的是煙草。煙草是沃特·羅利爵士引入的,也是羅阿諾剋占領弗吉尼亞計劃(這是被人反復談論的少數幾個話題之一)失敗後的産物(見第二章)。與茶葉一樣,煙草的推廣者也堅稱煙草具有醫療功效。1587年,羅利的僕人托馬斯·埃利奧報告說,這種“草藥”在曬乾和點燃後,“會散發齣大量的煙和嗆人的氣味,從而打開身體的所有毛孔和經絡:這樣不僅防止血脈阻塞,而且……能在短期內打通經絡:因此他們能夠保持健康,遠離疾病,幫助我們的國人抵禦疾病的侵襲。”早期的一則廣告宣稱,煙草能夠“保護我們的健康,減少我們的痛苦。讓我們找到感官的享受,放鬆我們勞纍的大腦。”當然,不是每個人都信這套。對詹姆士一世來說—他在其他方麵的想法也超越瞭他的那個時代—這種燃燒的雜草 “看上去令人生厭,聞上去令人作嘔,既損害大腦,又危害雙肺。”但是,隨著弗吉尼亞和馬裏蘭州的煙草種植迅速擴大,煙草的價格也急劇下跌(從17世紀20年代每磅4英鎊36便士降至17世紀60年代每磅的1便士),煙草逐漸成瞭一種大眾消費品。17世紀20年代一般隻有紳士階層纔有資格吸煙,到瞭17世紀90年代,吸煙成瞭一種“習慣和時尚—所有農民都抽著煙鬥”。1624年,詹姆士將他對煙草的狐疑放到一邊,建立起瞭煙草貿易的皇傢壟斷權;隻要能從煙草進口中攫取的利潤迅速飆升,顯然讓國人吸入更多這種“有害”的氣體也值得,雖然全麵實行壟斷最終被證明是不可行的。
這些新的進口商品改變的不僅僅是經濟,還有國民的生活方式。笛福在他的《英國商人手冊》說:“淑女們偏好的茶室和紳士們喜歡的咖啡店似乎都是新的發明……”人們之所以喜歡這些新的飲品,是因為它們所提供的刺激不同於歐洲的傳統飲品—酒。酒可以作為一種鎮靜劑,而葡萄糖、咖啡因和尼古丁則在18世紀承擔瞭酒的功能。總的來說,這些新飲品帶給英國社會莫大的衝擊;可以說,大英帝國是建立在對糖、咖啡因和尼古丁的狂熱需求之上—這種狂熱幾乎每個人都經曆過。
同時,英格蘭—尤其是倫敦—成為這些新刺激商品在歐洲的中心。到18世紀70年代,85%的進口煙草和94%的進口咖啡實際上都被英國再進行齣口,主要齣口到北歐。這部分內容反映齣當時不同進口貨物在關稅上的差異:對咖啡徵收的沉重進口稅限製瞭國內咖啡的消費,使得茶葉行業迅速發展起來。英國人的許多特點都和他們的財政政策相關,他們喜歡喝茶勝過喝咖啡也是源於這個因素。
通過將他們從西印度和東印度進口的商品部分齣口到大陸市場,英國人賺瞭足夠的錢來滿足他們另一個長期壓抑的欲望,即服飾的革命,這也是新消費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彼得·斯塔布斯在1595年的一篇文章中評論道:“世界上沒有人比英國人對新款衣服抱有更強烈的興趣。”在他看來,英國消費者對新款服裝需求越來越多,這種需求到瞭17世紀初葉,甚至導緻瞭一整類立法的失效。這就是奢侈品禁令,該禁令規定,英國男人和女人隻能根據他們的社會地位選擇他們的穿著。笛福再一次注意到瞭這個趨勢,他在他的文章“眾人負責等於無人負責”中寫道:
……樸實的鄉村女孩搖身一變,變成瞭精緻的倫敦貴婦,會喝茶、吸鼻煙,品位越來越高、越來越挑剔。她有瞭自己的社交圈子,就像她的女主人一樣;原來寒酸襤褸的亞麻、羊毛混織小外套也換成瞭上好的絲綢衣服,至少得有4碼或5碼寬。
但在17世紀,有品位的英國消費者隻願去一個地方買衣服,那就是印度人的服裝店。從質量、設計、做工和技術方麵來說,印度織品非常符閤英國人的需求。當英國商人開始從印度購買絲綢和印花棉布,並將其帶迴英國後,幾乎在國內掀起瞭一場服飾革命。1663年,佩皮斯陪同妻子伊麗莎白到倫敦最時尚的購物區康希爾購物,“在一番精挑細選之後,我太太終於為她的新書架配瞭一塊印花棉布,也就是印染著圖案的一種印度棉布,確實非常漂亮。”在等候一位藝術傢約翰·海耶斯時,佩皮斯還特地去租瞭一套時尚的印度絲綢晨袍穿在身上。1664年,英格蘭進口的印度棉布達25萬匹。當然,孟加拉絲綢、平紋皺絲織品,以及純白薄細棉布的需求量也與印度棉布不相上下。笛福在1708年1月31日的《每周評論》中說:“這些東西不知不覺地進入瞭我的傢,我的衣櫥、我的臥室、窗簾、墊子、椅子,最後連床都鋪滿印度棉布或者印度的織品。”
這些進口織物的一大優勢在於,它們的市場簡直是無窮大的。說到底,一個人能夠消費的茶和糖都是有限的,可是他對新衣服的渴求永遠是貪得無厭的,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既然笛福筆下“樸實的鄉村女孩”都能買得起印度織物,這就意味著,喜歡暢飲茶的英國人如今不僅滿足瞭口腹之欲,穿著也更體麵、漂亮瞭。
早期進口貿易的經濟情況相對簡單。17世紀的英國人找不到多少印度人自己不生産的物品可以與印度人進行以物易物。因此,他們一般都用在其他貿易中賺到的黃金來購買印度的産品。如今,我們將這一過程的推廣稱為全球化,意思是將全世界連接成同一個市場。但是,17世紀的全球化還是在一個重要方麵與如今的全球化存在差異。把黃金運到印度,再把印度的商品運迴來,就這麼一個買賣的過程就意味著需要走19 200公裏左右的路程,而每公裏都會因風暴、沉船、海盜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而充滿危險。
然而,最大的威脅並非來自掛著骷髏頭旗幟的海盜船,而是在於,其他歐洲人也試圖在做同樣的事情。因此,亞洲即將成為爭奪市場份額這場殘酷戰爭的中心。
而這次的全球化則是由炮艦開路的。
英國的商品貿易
寬闊渾濁的鬍格利河是孟加拉恒河三角洲最大的一條支流,也是印度最古老的一條貿易動脈之一。從它在加爾各答的河口,你可以溯流而上到達恒河,隨後經過帕坦納、瓦拉納西、阿拉哈巴德、坎普爾、阿格拉和德裏。另一個方嚮在孟加拉灣,順著季候風和海道,你就能到達歐洲瞭。所以,當歐洲人到達印度做生意時,鬍格利是他們最喜歡去的地方。可以說,它就是進入南亞次大陸的經濟關卡。
如今,加爾各答北部欽蘇拉鎮還可以零星地看到一些西方古建築,它們正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公司之一—東印度公司—在印度首個前哨留下的遺跡。100多年來,該公司占領瞭亞洲貿易的交通要道,幾乎壟斷瞭從香料到絲綢的各類産品的貿易。
但是,這個是荷蘭的東印度公司,並非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欽蘇拉那些荒廢的彆墅和倉庫當初都不是為瞭英國人建造的,而是為來自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建造的。這些荷蘭人在亞洲做生意的曆史要比英國人久遠多瞭。
荷屬東印度公司成立於1602年。正是當年大規模的金融革命使阿姆斯特丹成為歐洲最先進、最有活力的城市。自從在1579年擺脫瞭西班牙的統治,荷蘭就一直站在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前端。荷蘭創建瞭公債體製,使其政府得以以很低的利率從公民手裏藉錢。它建立瞭現代央行的雛形,它的貨幣體係很健全。它的稅收體係—主要基於貨物稅—也是簡單有效的。荷屬東印度公司則是商業組織曆史上的一個裏程碑。直到1796年解散,荷屬東印度公司為它的原始股東帶來的是年平均18%的收益率,在這麼長的時間裏保持著如此高的迴報確實非常驚人。
當然,在倫敦也有一群商人籌集瞭3萬英鎊,準備“組織一次前往東印度和附近其他島嶼和國傢……的旅行”,他們隻等著獲得皇傢的壟斷授權;1600年9月,伊麗莎白一世嚮“遠赴東印度做貿易的倫敦商人公司”授予15年的東印度貿易壟斷權;次年,一支由四艘船組成的船隊開往蘇門答臘島。但是,從1595年開始,荷蘭商人已經經由好望角前往印度開展貿易瞭。到1596年,他們已在爪哇島萬丹紮下瞭根基,1606年,首批發往歐洲市場的中國茶葉就是從這裏運齣的。另外,荷屬東印度公司還是一傢永久性股份製公司,這點與英屬東印度公司不同,後者到瞭1650年纔成為永久性股份製公司。雖然比英屬東印度公司晚兩年建立,但是荷屬東印度公司很快就主導瞭與印度尼西亞摩鹿加群島的香料貿易(曾經被葡萄牙壟斷),利潤豐厚。荷蘭人做生意的規模很大:他們嚮亞洲派齣的船隻數量是葡萄牙船隻數量的5倍,是英國船隻數量的2倍。部分原因在於,荷蘭公司與英國公司不同,它根據淨收入而非淨利潤對經理們進行激勵,這就鼓勵瞭後者增加交易量。17世紀,荷蘭擴張迅速,在印度東海岸的瑪蘇裏帕特納姆、西海岸的蘇拉特以及锡蘭的賈夫納建立瞭基地。但到瞭17世紀80年代,荷蘭運迴國的貨物中最多的就是來自孟加拉的織物。欽蘇拉幾乎要成為荷蘭在印度貿易基地的首都瞭。
但是,從另一方麵來說,兩傢東印度公司也有很多共同之處。我們不應該簡單地將它們等同於現代的跨國公司,因為它們更像是由國傢許可的壟斷公司,另外,它們也比加勒比海的海盜聯盟更為復雜和微妙。創建這兩傢公司的荷蘭人和英國人都能夠在政府的壟斷政策保護下,匯集所有的資源以進行大規模、高風險的冒險事業。同時,公司也允許政府將其海外擴張項目私有化,從而將大量的風險轉嫁齣去。如果賺瞭錢,公司就要上繳一部分收益,或者更常見的是提供一些貸款,以換取許可延期。而私人投資者也大可放心,因為公司能夠百分之百地獲得市場份額。
這兩傢公司的經營模式並非第一傢,當然也不可能是最後一傢。還有一傢公司成立於1555年(從商的探險者為開拓未知的地區、領土、島嶼和地方建立的公司),它就是與俄國進行貿易的俄國公司。1592年,威尼斯和土耳其公司閤並成立利凡特公司。1588年和1592年,分彆希望在西非的塞內岡比亞和塞拉利昂獲得貿易壟斷權的公司獲得瞭授權。繼它們之後是1618年的幾內亞公司(倫敦探險者為進入西非各港口進行貿易而創建的公司),1631年,該公司重新獲得瞭為期31年的西非貿易壟斷權。到瞭16世紀60年代,一個強大的新公司—皇傢探險者非洲公司—誕生,獲得瞭幾乎持續1 000年的壟斷權許可。這是一個非常賺錢的公司,因為就是在這裏,英國人找到瞭黃金—終於找到瞭;雖然當地齣口量最大的還是奴隸。在氣候截然相反的地區,我們則能看到1670年創立的哈德遜灣公司(英格蘭探險者為進入哈德遜灣進行貿易而創建的光榮公司),壟斷瞭加拿大的皮毛貿易。1695年,蘇格蘭人效仿英格蘭人,建立瞭進入非洲和印度群島進行貿易的蘇格蘭貿易公司。1710年又建立瞭南海公司,旨在壟斷與西班牙統治下的美洲的貿易。
但是,授予這些公司的壟斷權是否真的有效呢?以兩傢東印度公司為例,麻煩就在於,它們不可能同時擁有在亞洲與歐洲進行貿易的壟斷權。那種提齣倫敦和阿姆斯特丹實行不同商品貿易的主張簡直就是荒謬之極,雖然荷蘭和英格蘭市場相距很近。1613年,英屬東印度公司在印度西北海岸的蘇拉特立足,顯然目的就是為瞭在利潤豐厚的香料貿易中分一杯羹。如果香料齣口量缺乏彈性,那麼它隻有將生意從荷屬東印度公司中搶過來纔算勝利。這就是當時許多人的假設,用當時的政治經濟學傢威廉·佩蒂的話來說:“世界各國的貿易量占比總是一定的。”東印度公司的總監約西亞·蔡爾德就希望“其他與我們在同一業務上競爭的公司不要將我們的生意搶走,希望我們的生意能夠繼續並繁榮,而他們的交易量隨之減少”。經濟就是一個零和遊戲,這就是所謂重商主義的核心。但是另一方麵,如果香料齣口量是有彈性的,那麼對英格蘭的香料供給量勢必增加,從而抑製瞭歐洲的香料價格。英屬東印度公司的首次蘇拉特貿易之旅就賺得盆滿鉢滿,利潤率高達200%。但是此後,盎格魯–荷蘭競爭還是帶來瞭一個不難預測的效應,即壓低瞭價格。那些第二批投資東印度公司(在1617~1632年間投資160萬英鎊)的人最終都虧錢瞭。
英國人這樣擠占東部貿易的舉措不可避免地引發衝突,尤其是香料貿易當時占瞭荷屬東印度公司貿易總額的3/4。早在1623年就發生瞭暴力事件,荷蘭人在印度尼西亞的安汶島謀殺瞭10位英國商人。1652~1674年間,英國人與荷蘭人交戰三次,主要目的就是為瞭爭奪齣入西歐的主航道—不僅是從西歐到達印度群島,還有到波羅的海、地中海、北美和西非要道的控製權。此前很少有因為純粹的商業利益之爭而引發的戰爭。英國人決意要在海軍力量上爭取優勢,因此,他們將商船海軍的規模擴大瞭一倍,並在區區11年間(1649~1660年)將海軍船隻的數量增加瞭216艘。1651年和1660年,《航海法》各法律條款相繼獲準,其中宣稱,來自英格蘭殖民地的商品理應由英格蘭船隻運送,目的就是以犧牲荷蘭商人的利益(多年來,荷蘭商人一直在海洋運輸貿易中占據優勢)為代價來擴張英國船隊。
然而,雖然一開始英國人取得瞭一些勝利,但荷蘭人最後還是占據瞭上風。英國人在西非沿海的所有貿易據點幾乎都被拔除瞭。1667年6月,一支荷蘭艦隊甚至北上泰晤士河,占領瞭希爾內斯和肯特郡,損毀瞭查塔姆和羅切斯特的船塢和船隻。在第二次與荷蘭人的戰爭中,英國人又被趕齣瞭蘇裏南和波拉羅恩;1673年,紐約也暫時失守,這讓許多人大吃一驚。畢竟英國人的數量是荷蘭人的2.5倍,而英國的經濟實力也更強。在第三次與荷蘭的戰爭中,英國人得到瞭法國人的支持。可是,在先進的金融體係的幫助下,荷蘭還是給瞭兩大經濟強國以狠狠的一擊。
相比而言,對英國人來說,戰爭的失敗讓英格蘭落後的金融體製不堪重負。政府在破産的邊緣苦苦掙紮:1671年,查理二世被迫延期償付一些政府債務,這就是所謂的“國庫停止支付”事件。這次金融動蕩造成瞭深遠的政治影響;因為在查理二世統治時期,倫敦與英國政治精英們之間的聯係前所未有地密切。無論是在倫敦議事廳還是王宮,或者新貴族們的豪宅中,英荷戰爭的失利都引起瞭人們的恐慌。坎伯蘭郡公爵是皇傢非洲公司的創始人之一,後來又擔任哈德遜灣公司的管理者。約剋郡公爵,也就是未來的詹姆士二世,是成立於1672年的新皇傢非洲公司(之前的公司被荷蘭人毀於一旦)的管理者。1660~1683年期間,查理二世獲得東印度公司的“自願捐款”,金額達324 150英鎊。與荷蘭之間激烈的競爭逐漸拖垮瞭復闢的斯圖爾特王朝,英國必須另尋齣路。最終他們找到瞭一個解決方案,那就是閤並(這在商業史上經常發生)—不是兩傢東印度公司之間的閤並,而是一場政治聯盟。
1688年夏,由於懷疑詹姆士二世積極恢復天主教信仰,同時也擔心他的政治野心,一個由英國新貴族組成的強大寡頭集團發動瞭政變。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得到瞭倫敦商人的支持。他們邀請荷蘭執政奧蘭治親王威廉入侵英格蘭,幾乎是兵不血刃地驅逐瞭詹姆士二世,史稱“光榮革命”。這次革命往往被描寫為一次政治事件,是英國自由主義派和議會君主製的勝利,但同時它也帶有英荷聯盟的意味。荷蘭的奧蘭治親王威廉實際上成瞭英國的領導者,而荷蘭商人也成為英屬東印度公司的大股東。發起光榮革命的人認為,他們在宗教和政治上已無須再嚮荷蘭人學習,因為與荷蘭人一樣,英國人已經有瞭自己的宗教,也建立瞭議會製政府。而他們可以嚮荷蘭人學習的是後者的現代金融。
尤其是,1688年的英荷聯盟讓英國人首次得以瞭解荷蘭幾傢重要的金融機構,以及它們先進的金融機製。1694年,英國成立英格蘭銀行,負責管理政府藉貸和國傢貨幣,與85年前創建的成功的阿姆斯特丹銀行類似(但不完全相同)。倫敦也引入瞭荷蘭的國傢公共債務體係,通過一個能夠自由買賣長期債券的證券交易所融資。這使得政府能夠以很低的利息貸款,從而增強瞭開展大規模項目—包括發動戰爭的實力。嚮來敏銳的丹尼爾·笛福很快就意識到,廉價的藉貸對一個國傢將産生什麼樣的影響:
信貸製造戰爭,也帶來和平;它能幫助我們召集軍隊、裝備海軍、打響戰役、圍攻城鎮;總之,稱它為戰爭的力量源泉比直接稱它為錢更閤適……信貸可以讓士兵不拿軍餉就上戰場,讓軍隊沒有物資供給也能行軍……它就是堅不可摧的防禦工事……它讓白紙變成錢……給國庫和銀行注滿瞭錢,隻要需要,想有多少錢就有多少錢。
復雜先進的金融機製讓荷蘭人不僅能夠為它在全球範圍內的貿易融資,也讓他們得以建立一流的海軍來保護他們的安全。如今,這些機製將在英格蘭得到更加廣泛的應用。
英荷聯盟之後,英國人在東方有瞭更大的行動自由。他們達成瞭一個交易,實際上將印度尼西亞和香料貿易留給瞭荷蘭人,而把較新的印度紡織品貿易留給瞭英國人去發展。這個交易看起來對英屬東印度公司更有利,因為紡織品市場的規模迅速超過瞭香料市場。事實上,鬍椒、肉豆蔻、肉豆蔻皮、丁香和肉桂—荷屬東印度公司的利潤來源—的需求彈性遠遠小於白棉布、印花布和棉布。這也是英屬東印度公司到瞭18世紀20年代,就在銷售額上超越其荷蘭競爭對手的原因之一;以及1710~1745年期間,英屬東印度公司隻有兩年的虧損紀錄,而荷屬東印度公司的利潤卻不斷下滑的原因之一。英屬東印度公司的總部遷到瞭利登霍爾大街,這裏是公司的兩大監管機構—董事會(持有2 000英鎊或以上東印度公司股票的股東)和業主會(持有1 000英鎊或以上股票的股東)—開會的地方。但是,反映齣這傢公司日漸興隆的真正標誌是它在畢曉普斯蓋特建立的一個巨大的倉庫,用來儲存公司從印度進口到歐洲的布匹。
進口貨物從香料變成衣料,這也意味著英屬東印度公司在亞洲貿易基地的轉移。蘇拉特於是逐漸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三大“工廠”(當時有人是這麼稱呼它們的),這些加固瞭防禦工事的貿易中心如今都是亞洲最繁榮的城市。第一個就是在印度東南海岸,夢幻般的科羅曼德海灘。東印度公司以1630年占領的海灘據點為基礎,建立瞭一個貿易基地,也許是為瞭彰顯它的英國屬權,將其命名為聖喬治貿易基地。後來,馬德拉斯城就在此興起。就在30年後,即1661年,英格蘭從葡萄牙手中奪取瞭孟買,並把它當做查理二世和布拉甘薩的凱瑟琳結婚的嫁妝送給瞭他們。最後,1690年公司又在鬍格利河東岸的蘇塔努提建立瞭一個貿易基地,後與其他兩個村莊閤並,發展成為更大的城市加爾各答。
今天,我們依然能夠發現這些英國“工廠”的遺跡,它們可以被稱為大英帝國早期的開發區。馬德拉斯貿易基地現在仍在,保存得比較完整,設有教堂、廣場、房屋和倉庫。它們的布局並無創新。實際上,與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及荷蘭貿易基地的布局大緻相同。但是,在新的英荷聯盟下,諸如欽蘇拉等城市代錶的是過去,而加爾各答代錶的是未來。
可是,英屬東印度公司剛剛解決瞭與荷蘭對手的競爭,又迎來瞭另一個更加惡劣的競爭,這次是與它們自己的員工。這就是經濟學傢所說的“代理人問題”:公司所有者所麵臨的基本睏難就是如何控製他們的員工。而這個睏難隨著股東和雇員之間地理距離的增加而增加。
我們要談的不隻是距離,還有風嚮。到瞭1700年,從波士頓到英格蘭隻需航行4~5周就可到達瞭(如果從英格蘭到波士頓,一般則要5~7周)。航行到巴巴多斯島通常需要9周左右。由於大西洋上的風嚮影響,海上貿易通常都有季節性特徵:開往西印度群島的船一般在11~1月間起航;開往北美的船則正相反,會在仲夏至9月底之間起航。但對於在歐洲與印度之間往來的船隻,航行期就要長得多;從英格蘭途徑開普敦到加爾各答,平均航行時間約為6個月。4~6月,印度洋主要颳的是西南風,10~3月風嚮逆轉,轉為東北風。要去印度就應該在春季起航,這樣鞦季你就可以返航瞭。
亞歐之間這麼長的航行期意味著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既容易實施,也很難實施。與北美貿易比較起來,規模較小的對手很難在同類貿易上與東印度公司進行競爭;因此,雖然到17世紀80年代,往來於北美洲和加勒比海之間的貿易公司有數百傢之多,但去印度做生意的人數還是比較少,畢竟這6個月航程的成本和風險讓許多人望而卻步,因此,生意就集中到瞭一傢巨擘手中。但是,在員工們得花半年時間纔能遠渡重洋完成任務的情況下,這傢巨擘要控製自己的員工也是萬分睏難的。從國內嚮印度員工發齣的指令也同樣要花這麼長時間纔能到達。東印度公司的員工享有很大的自由—可以說,大多數員工完全不受倫敦老闆們的控製。由於他們的薪水相對來說比較微薄(文職人員一年5英鎊,比英格蘭的文員高不瞭多少),因此,大多數公司員工都會毫不猶豫地在生意中撈取一些好處。因此後來有人諷刺說:“利登霍爾大街的經濟潛規則是:微薄的工資,可觀的灰色收入”。還有些員工則更過分,完全把公司的工作拋到一邊,自己做生意。這些人就是董事們最憎惡的人:無照經營者。
托馬斯·皮特就是無照經營者中的一個典型人物。他是多西特一個牧師的兒子,1673年進入東印度公司工作。到達印度後,皮特乾脆逃跑瞭,並開始從印度商人手中購買貨物,再運迴英格蘭齣售,所得的錢悉數裝入自己的腰包。公司董事會強烈要求皮特迴國,譴責他是“一個傲慢、暴躁、大膽無恥的年輕亡命之徒,隻要有機會做壞事,他就絕對不會猶豫”。但是,皮特愉快地忽略瞭命令他迴國的要求。事實上,他還與公司在孟加拉灣的負責人馬提亞·文森特做起瞭生意,並娶瞭文森特的侄女。在被公司起訴後,皮特支付400英鎊的罰金與公司瞭斷瞭此事。如今,這筆錢對他來說已經不算什麼瞭。
像皮特這樣的人在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發展中,其實起到瞭關鍵作用。也就是說,隨著隸屬於英國政府的公司貿易的發展,一個龐大的私營貿易也在不斷地發展。這就意味著英國王室授予東印度公司的盎格魯–亞洲貿易壟斷權開始動搖瞭。但這也許並非壞事,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無照經營者,一傢壟斷公司未必能讓英國和印度之間的貿易如此迅猛地擴張和興旺。確實,連公司自己也逐漸認識到,這些無照經營者—甚至包括不聽話的皮特—非但不會阻礙它的業務,甚至可能推動它的業務發展。
……
前言/序言
英國如今控製著3.5億海外殖民地居民的命運,如果沒有一支強大軍隊的保衛,這些人無法獲得有效保護,往往容易遭受掠奪和不公正的待遇。英國對殖民地居民的統治並非無懈可擊,這點毋庸置疑,不過我敢說,在此之前,沒有任何一個宗主國能夠給予其附屬國人民如此禮遇。喬治·M·朗教授,1909年
殖民主義導緻瞭種族主義、種族歧視、排外情緒,以及與之相關的狹隘的民族主義……非洲人民和非洲裔人民,以及亞裔人民和原住民都是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並且至今仍受殖民主義所帶來的惡果影響……
《德班宣言》,反對種族主義、 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的不容忍現象世界會議,2001年
曾經有這麼一個帝國,它統治著約占全球1/4的疆域和人口,以及幾乎全部的海域。不用說,這個帝國就是英國,其規模之大可謂空前絕後。這個遠眺歐洲大陸西北沿岸的多雨的群島國傢何以能在全球稱霸?不僅英國曆史關注這一問題,甚至世界曆史也需要對此獲得答案。同樣的,這也是本書希望能夠迴答的問題之一。本書所要解答的第二個問題是,這個帝國的存在究竟是人類的一大幸事,還是不幸,或許這個問題很難迴答。
如今我們普遍的說法是,總體來看英國的齣現是人類的不幸。它之所以背負如此惡名,一個主要原因可能是它曾經參與瞭大西洋販奴貿易,並支持奴隸製。這個問題不再是一個曆史問題,它已經成為政治問題,也有可能成為法律問題。1999年4月,非洲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阿剋拉召開會議,公開要求“西歐及美洲參與販奴貿易,並從販奴及殖民統治中受益的所有國傢和機構”應該作齣賠償。根據“奴隸貿易中非洲損失的人口,以及殖民統治期間非洲被掠奪的黃金、鑽石及其他礦産的價值估計”,賠償總額應該達到777萬億美元。1850年之前,1 000萬左右被運往大西洋各國為奴的非洲人中,有300萬人是乘坐英國的船隻漂洋過海的,因此,英國應承擔的賠償款可能高達150萬億英鎊。
這樣的巨額索賠看起來似乎不太現實。但是,這些觀點在2001年夏於南非德班召開的聯閤國反對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的不容忍現象世界會議上還是獲得瞭聲援。此次會議的最終報告“承認”,奴隸製和奴隸貿易是“有違人道的犯罪”,“非洲人民和非洲裔人民,以及亞裔人民和原住民”都是“受害者”。在此次大會的另一項聲明中,“殖民主義”被隨意地與“奴隸製、奴隸貿易……種族隔離……和種族滅絕”等放在一起譴責。該聲明對聯閤國各成員國提齣瞭一個號召,要求大傢“尊重曆史慘劇受害者的記憶”。它指齣:“有些國傢已經為它們曾經犯下的滔天罪行作齣瞭道歉,並進行瞭必要的賠償。”此次會議“呼籲那些尚未為恢復受害者尊嚴而作齣任何努力的國傢和個人,以閤適的方式采取行動。”
這樣的呼籲在英國也並未被人忽略。2002年5月,位於英國倫敦的智囊團的主任提議,英國女王應該“遍訪世界各國,為英國曾經所犯的罪行道歉,這是提升英國政府職能和國際地位的第一步”。對此進行報道的媒體還增添瞭這樣一條注釋:“英國在1918年的鼎盛時期統治瞭世界1/4的疆域和人口,英國批評傢聲稱,它的巨額財富是建立在壓迫和剝削之上的。”
我寫本書時,恰好在英國廣播公司的網站(一個顯然是麵嚮學生的版塊)上看到瞭一則針對英國曆史的評述,這段評述同樣也很深刻:
英國的輝煌是建立在屠殺和掠奪之上的:它的軍隊屠殺瞭無數軍備實力較弱國傢的人民,並掠奪瞭他們的國傢,雖然這種方法後來有所改變:當英勇的革命者和抗議者聖雄甘地,以及像他那樣的人開始關注人民的訴求時,窮兵黷武的製度……瓦解瞭,用機槍大肆屠殺的行為遭到瞭輿論的譴責。
近來,一位知名的曆史學傢在英國廣播公司電視颱節目中提齣瞭一個問題,可以說這個問題濃縮瞭當前人們對英國曆史的傳統思考和認識。他問道:“一個自認為自由的民族何以奴役瞭世界上如此廣大的疆域……一個自由之國何以變成瞭一個奴役之國?”為什麼“齣自善意”的英國人卻因“市場崇拜”,而犧牲瞭“共同人性”?
受益者
多虧瞭英國的殖民統治,纔讓我的親戚現在遍布世界各地—加拿大的艾伯塔、美加交界的安大略地區、菲律賓,以及澳大利亞的佩斯。多虧瞭英國的殖民統治,我的爺爺約翰纔能在他剛滿20歲時就到厄瓜多爾嚮印第安人販賣五金器具和烈酒。我奶奶的起居室牆上掛著兩幅很大的油畫,就是爺爺當年帶迴來的,美麗的安第斯山脈的風景簡直讓傢裏光彩照人,我從小就是看著這兩幅畫長大的。我還記得奶奶的展示櫃裏有兩個滿臉愁苦的印第安娃娃,似乎是不堪背上木柴的重負,它們極不協調地擺在幾個瓷器人偶旁邊。也多虧瞭英國的殖民統治,我的外公湯姆·漢密爾頓纔會在英國皇傢空軍當瞭3年多的軍官,曾在印度和緬甸與日本人作戰。他的傢信一直被我的外婆珍藏著,這些信以敏銳的觀察和雄辯的事實精彩地記錄瞭戰時英國對殖民地的統治,信中充滿瞭對自由主義的懷疑,這幾乎成為我外公的哲學理念的核心。我至今仍記得當年我翻閱外公駐防印度時所拍攝的那些照片時的喜悅,聽他給我講俯衝而下的鳶鷂鷹和炎熱氣候故事時的激動。多虧瞭英國的殖民統治,我的叔叔伊恩·弗格森在獲得建築師資格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位於加爾各答的公司工作。伊恩是在英國皇傢海軍中開始其職業生涯的;之後,他輾轉於非洲,後來又到瞭海灣各國,在國外度過瞭餘生。對我來說,伊恩就是流放者、探險傢的典型:被太陽曬得黝黑的臉龐、酗酒、極度憤世嫉俗。他也是第一個從我很小的時候起就以大人的稱謂稱呼我的人,我早就領教瞭他滿口褻瀆神靈的語言,以及他的黑色幽默。
伊恩的兄弟—我的父親也曾漂泊異鄉。1966年,我的父親在格拉斯哥學醫結束後,不顧親友的勸阻,帶上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孩子舉傢搬到瞭肯尼亞,他在內羅畢工作瞭兩年,一邊行醫,一邊教書。所以,多虧瞭英國的殖民統治,我的童年記憶裏纔有瞭非洲殖民地的故事;雖然肯尼亞已經獨立3年瞭,廣播裏也不停地播放肯尼亞第一任總統喬莫·肯雅塔以其標誌性的語調號召大傢“讓我們團結起來”,但那裏的情況從“白色禍害”開始到現在,幾乎沒有任何改變。當時,我們在那裏建造自己的平房、擁有傭人,並且偶爾說一些斯瓦希裏語。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一種堅不可摧的安全感。那真是一段美妙的時光,外齣覓食的印度豹、吉庫尤女人的歌聲、第一場雨的氣息,以及熟透芒果的滋味,這一切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記憶深處。我懷疑,這也是我母親過得最幸福的時光瞭。盡管我們後來迴到瞭格拉斯哥,不得不忍受灰濛濛的天空和寒冷潮濕的環境,不過我們的傢裏擺滿瞭從肯尼亞帶迴來的物品。沙發上鋪著羚羊皮,牆上掛著馬賽武士的肖像,還有一個雕刻粗糙卻裝飾精美的腳凳,我和姐姐總愛坐在腳凳上。我和姐姐每人都有一個斑馬皮做的鼓,一個濛巴薩産的漂亮籃子,一個羚羊鬃毛製的蒼蠅撣子,還有一個吉庫尤玩偶。事實上,我們簡直生活在一個小型的後殖民地博物館中,盡管年少的我們一無所知。我至今還珍藏著一些河馬、疣豬、大象和獅子的木雕,它們曾經都是我的 寶貝。
不管怎麼說,我們還是迴到瞭英國,此後再也沒有返迴肯尼亞。唯一沒有迴英國的是我的姑奶奶阿格尼絲·弗格森(認識的人都叫她阿吉)。她齣生於1888年,是我的曾祖父詹姆士·弗格森(他是一位園丁)和他第一任妻子的女兒。要想知道帝國的夢想有多大的改變力量,看看阿吉就明白瞭。1911年,受圖冊上美麗的加拿大牧場風光的誘惑,她和她的新婚丈夫歐內斯特·布朗決定步其兄弟的後塵:離開他們在伐夫郡的傢,離開他們的親朋好友,嚮西行進。吸引他們的是薩斯喀徹溫省160英畝無人問津的荒地。唯一的規定是,土地所有人必須在那裏定居下來,並開墾土地。傢族中曾經有人流傳這樣一種說法,阿吉和歐內斯特原本是要乘坐泰坦尼剋號齣航的,但陰差陽錯,他們並沒有上船,倒是行李被送上瞭船,隨著泰坦尼剋號一同沉沒。他們確實命大,可問題是這也意味著他們要從零開始建設他們的新生活。如果阿吉和歐內斯特認為,他們就此將告彆蘇格蘭可怕的鼕天,那麼他們很快就會發現自己上當瞭。格蘭岩是一片狂風肆虐的荒原,那裏的溫度會驟然降低,遠比陰雨連綿的伐夫郡冷多瞭。歐內斯特在給他嫂子內爾的信中說,這裏“簡直冷得可怕”。他們為自己建造的第一座房子簡陋極瞭,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一個“雞窩”。離他們最近的城鎮穆斯喬在152公裏之外。一開始,他們周邊的鄰居都是印第安人,不過他們還算友好。
不過,從他們每年聖誕節寄給親戚們的黑白照片來看,照片裏的他們和他們在“牧場的傢”,無不述說著這對夫婦白手起傢、勤勞緻富的故事。阿吉成瞭三個健康孩子的母親,當初那位遠離傢鄉的新娘臉上的愁苦已經煙消雲散。歐內斯特也因長年辛苦農作而曬黑瞭臉龐,身體也變得結實不少;他颳掉瞭鬍子,原本哭喪的臉也變得英俊起來。他們的“雞窩”不見瞭,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體麵的木製農捨。漸漸地,附近的蘇格蘭人越來越多,這化解瞭他們初到時的寂寞感。在遠離傢鄉的異地能與同鄉共度新年,確實是件令人欣慰的事,因為,“在這些蘇格蘭人來之前,他們很少有過新年的感受”。如今,他們的10個孫輩生活在加拿大的不同城市。這個國傢的人均收入已經比英國高齣瞭近10%,僅次於美國。這些也多虧瞭英國當年的殖民統治。
如果說我是在英國的帝國陰影中長大的,恐怕你聯想到的會是一片慘淡景象。但是對蘇格蘭人來說,英國的帝國統治代錶著光明的太陽。到瞭20世紀70年代,英國昔日的版圖已經所剩無幾,但是我的傢族卻依舊篤信帝國的理想,毫不懷疑它的重要性。確實,英國的帝國傳奇無處不在,無人不知,我們已經將其視為人類曆史的一部分瞭。在加拿大度假,也沒讓我們改變這種想法。天主教國傢—愛爾蘭—的持續醜化,也沒有改變我們的觀念。當時,剋萊德南部的愛爾蘭在我們的生活中仍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長大後,我還沾沾自喜地認為,格拉斯哥是(英國的)“第二大城市”;也從未質疑過賴德·哈格德和約翰·巴肯的小說;還喜歡英國特色的運動—最棒的就是“不列顛雄獅”隊在澳大利亞、新澤西以及南非的巡迴橄欖球賽(不過可惜的是,在南非的比賽後來被終止瞭)①。在傢裏,我們吃的是“英式餅乾”;在學校,我們學的是“英式射擊”。
反麵例子
不可否認,當我十幾歲的時候,身穿紅製服,頭戴圓帽盔,滿臉嚴肅的英國人統治世界的印象差不多已成一個笑話,也成為電影中的素材。可能這種原型來自濛蒂·派森電影《生活的意義》的一個片段:在與祖魯人的戰役中身受重傷、渾身血汙的“湯米”神往地歡呼道:“我是說,我殺瞭15個壞蛋,先生。現在,如果我迴去的話,我肯定會被吊死的!可是在這裏,我還能得到奬章,先生!”
1982年我考上牛津大學時,英國的帝國夢想早已被人遺忘,甚至已經沒人拿它作笑料瞭。那時,牛津的學聯還會討論一些嚴肅的話題,比如“議會對殖民統治錶示後悔”,年輕魯莽的我立即對這個議題提齣瞭反對,我的學生政治領袖生涯也因此早早地夭摺瞭。事實上,我是在那時候纔有所醒悟的:顯然,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樣,對英國的過去懷有一種甜蜜的眷念。事實上,現在的很多人看到我竟然打算為英國的帝國統治作辯護,都會心生反感。當我熱切地鑽研這一課題時,我纔發現,我和我的傢庭竟然不幸地被誤導瞭:英國的崛起所産生的成本實際上遠遠超齣瞭它所帶來的利益。它的齣現最終還是人類的一大悲劇。
在此,我沒有必要詳細闡述反對帝國主義的論點,它們歸結起來無非有兩點:第一,殖民統治給殖民地的人民帶來瞭災難;第二,殖民統治也給殖民者本身帶來瞭惡果。前者是民族主義和馬剋思主義的觀點,從《先知穆塔吉赫林》(1789年)的作者著名曆史學傢高拉姆·侯賽因·汗,到《東方主義》(1978年)的作者巴勒斯坦學者愛德華·薩伊德,包括列寜以及成百上韆的其他思想流派都體現瞭這個觀點。後者屬於自由主義觀點,最早是由亞當·斯密提齣來的。亞當·斯密認為,多年來即使是從英國自身的角度來看,大英帝國的建立也隻是“浪費金錢”。
民族主義者和馬剋思主義者的核心論點是這樣的,帝國主義就是一種赤裸裸的經濟剝削,從本質上講,殖民統治的方方麵麵,甚至包括歐洲人顯然是真心實意地理解和研究原住民文化的努力,都是為瞭最大限度地榨取被殖民者的剩餘價值。而自由主義的核心觀點則更加復雜。自由主義者認為,由於帝國主義運用瞭從軍事武力、特惠關稅到有利於宗主國商業壟斷等種種手段,從而扭麯瞭市場力量,因此,即使是對宗主國自身的長遠的經濟利益來說也是不利的。這種觀點認為,對世界經濟的其他部分來說,自由的經濟融閤要比通過帝國主義手段實行強迫性融閤更有效。因此,對英國來說,投資於國內的産業可能要比嚮遙遠的殖民地一擲韆金更有意義,因為如果沒有開拓和保衛帝國巨大版圖的開銷負擔,納稅人完全可以把這些錢花在購買現代消費品上。一位曆史學傢在《牛津大英帝國史》中甚至推算齣,如果英國在19世紀40代中期就甩掉帝國的包袱,那麼它將有望獲得的“去殖民化紅利”相當於減稅25%。這筆節省下來的稅賦可用於投資電力、汽車、耐用消費品行業,從而極大地促進傢鄉工業的現代化。
將近一個世紀以前,J·A·霍布森和倫納德·霍布豪斯等人就進行過類似的爭論。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分彆繼承瞭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的理查德·科布登與約翰·布萊特的思想衣鉢。在《國富論》(1776年)中,亞當·斯密也質疑瞭“建立一個國傢,讓整個國傢的消費者不得不從其殖民統治下的各個産品生産國購買供應給他們的所有産品”的理念。但是,最早堅信英國在進行貿易擴張的同時,必須實行徹底不乾涉外交政策的人還是科布登。他堅持認為,貿易本身就是一劑“萬能良藥”:
它就像一項有益的醫學發現,給世界各族人民帶來對文明社會的健康追求和體驗。英國嚮那些文明程度更低的社會輸齣的,不僅僅是大宗貨物,還有智慧的種子和豐碩的思想果實;而造訪過英國大規模工業基地的商人迴到自己的國傢後,也將變成一個傳播自由、和平與良政的布道者。與此同時,我們的足跡遍布歐洲各個港口的蒸汽船,以及備受各國矚目的鐵路,這些都成為我們宣傳文明體製價值最好的廣告和入場券。
科布登的核心觀點是,無論是貿易還是英國文明的傳播,都不需要帝國主義組織的強製推行。相反,使用武力可能一事無成,如果它與全球自由市場的良性法則背道而馳的話:
就我們的海外貿易而言,武力和暴力無法維持其繁榮,也不會嚴重阻礙其發展。外國客戶光顧我們的市場,並非齣於對武力的恐懼或者迫於英國外交的壓力,他們不是被我們的艦隊和軍隊擄掠來的,當然,他們來到這裏也並非齣於朋友的情誼,那句話怎麼說來著?“生意場上無友誼”。這句至理名言無論對個人還是對國傢來說,都是適用的。事實上,正是在自身利益的驅動下,歐洲和世界其他國傢的商人纔會派齣船隊來到我們的港口,滿載我們生産的産品迴國。迴顧各個曆史階段,也正是在同樣的利益驅動下,各國商人纔會爭先趕往提爾①、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隨著時間的推移,一旦某個國傢的棉花和羊毛産品的價格低於英國和世界其他地方(這是很有可能的),那麼全世界的商人同樣會蜂擁而至—即使他們可能因此葬身於遙遠的異國他鄉。沒有任何人的力量,沒有任何艦隊和軍隊可以阻止曼徹斯特、利物浦和利茲重蹈曾經輝煌的荷蘭、意大利和腓尼基前輩的命運……
在綫試讀
《帝國》內容相關黃昏時分,那條古老河流的寬闊主乾靜靜地流淌。造福於兩岸人類多年之後,在寜靜而肅穆中流嚮地平綫的盡頭……
用户评价
坦率地說,這本書的閱讀門檻並不低,它需要讀者投入相當的專注力和耐心,尤其是在涉及某些專業術語和復雜的因果鏈條時。我不得不承認,有些篇章我需要反復迴溯,甚至需要藉助外部資料來輔助理解,這絕非一本可以“輕鬆消遣”的書籍。然而,正是這種挑戰性,讓最終的領悟顯得格外珍貴和酣暢淋灕。那種豁然開朗的瞬間,是伴隨著付齣的努力而來的巨大迴報。對於那些真正渴望深入理解曆史驅動力,並且不畏懼麵對復雜信息洪流的讀者來說,這種“硬核”的體驗是無可替代的。它拒絕提供簡單的答案,而是慷慨地提供瞭一個全麵、復雜且充滿啓發的思考框架,這纔是真正優秀的曆史著作應有的擔當。
评分這本書的論證結構嚴密得像一座用邏輯磚塊砌成的堡壘,讓人找不到任何可以輕易攻破的薄弱環節。作者顯然投入瞭海量的研究精力,引用瞭令人咋舌的跨學科資料,從地緣政治學到人口統計學,再到文化人類學,他似乎無所不覺地將所有相關的證據都匯聚到瞭他的核心論點周圍。每當提齣一個大膽的觀點時,他總能立刻跟上幾頁詳實的數據支持,或者是一段極具說服力的曆史案例分析,讓人心悅誠服地接受他的邏輯推導。這種構建知識體係的方式,極大地滿足瞭我作為一個求知欲強烈的讀者對於“深度”的渴望。我尤其欣賞他那種不輕易下定論,而是傾嚮於展示復雜性的態度,這使得全書的論述充滿瞭思辨的魅力,而不是簡單的教條灌輸。
评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簡直是一場視覺盛宴,那種厚重感和紙張的質感,拿在手裏就仿佛能感受到曆史沉澱下來的分量。我特彆喜歡封麵那種略帶復古的字體排版,既有學術的嚴謹性,又不失一種引人入勝的藝術感。內頁的印刷清晰度也無可挑剔,即便是那些需要仔細辨認的圖錶和地圖,也處理得非常到位。每次翻閱,都像是在進行一次鄭重的儀式,而不是簡單地閱讀。對於我這種喜歡收藏實體書的讀者來說,它放在書架上,本身就是一件極具品味的陳設。而且,裝訂工藝看起來相當紮實,可以預見它能夠經受住反復翻閱的考驗,不會輕易散架。這種對細節的極緻追求,無疑提升瞭閱讀的整體體驗,讓人在尚未深入內容之前,就已經對作者和齣版社的專業態度肅然起敬。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件精心製作的工藝品,值得細細品味和珍藏。
评分我花瞭整整一個周末沉浸在這本書的文字脈絡中,坦白說,作者的敘事節奏掌控得如同一個技藝高超的指揮傢。他並非簡單地羅列史實,而是巧妙地將宏大的曆史演進與那些鮮活的、極具戲劇性的人物命運編織在一起。有那麼幾次,我發現自己完全忘記瞭時間流逝,完全被拉進瞭那個特定的曆史場景裏,仿佛能聽到遙遠時代的喧囂和決策者的低語。他對細節的捕捉能力令人驚嘆,一個微小的經濟數據,一個不經意的外交辭令,都被他挖掘齣其深層的曆史意涵。這種敘事手法,讓原本可能枯燥的理論分析變得生動有力,充滿瞭張力。讀完某個章節,我常常需要停下來,靠在椅背上,默默消化剛纔接收到的信息量,那種知識與情感交織産生的衝擊感,是很多純粹的學術著作難以給予的。
评分閱讀此書的過程,對我個人世界觀的衝擊是顛覆性的。它迫使我跳齣過去固有的、習慣性的曆史框架,去審視那些被主流敘事有意或無意地忽略掉的關鍵轉摺點。有些地方的論述簡直像是醍醐灌頂,讓我對我們所處的當下環境有瞭全新的理解維度。這不僅僅是關於過去的知識,更像是一把解讀現代世界運行機製的萬能鑰匙。我甚至開始重新審視自己日常接觸到的新聞和評論,嘗試用書中提供的更深層次的、長程的曆史視角去解構它們背後的驅動力。這種閱讀體驗帶來的“認知升級”,遠超瞭我對一本曆史讀物的期待,它具有一種近乎哲學思辨的力量,讓人讀完之後,看待周遭的一切都帶上瞭一層新的、更具穿透性的濾鏡。
评分书很好
评分东西蛮好,服务给点个赞
评分证券分析本身就不用过多评价了,从各种语言的翻译本,到经久不衰的销量,足以证明该书的经典地位!这次由巴博领衔翻译此书,巴博的勤奋与学养,态度与责任历来受我辈敬仰!书很厚,到手后,迫不及待开始学习翻阅,从巴博的序言文字的深入浅出足以看出整个翻译团队的重视与付出!当经典之作遇上严谨学者,用严谨态度翻译出来的书,定当是锦上添花!所谓学者,一个是要广大先贤的重要思想,二是要让这些重要思想能够到达范围更广的听众!从某种意义上,这本书和巴博这个团队就是这个搭建起精英知识与大众沟通的破冰者!很是喜欢,太赞了!郑重推荐!
评分还好的,还不错的,还可以的
评分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评分证券分析本身就不用过多评价了,从各种语言的翻译本,到经久不衰的销量,足以证明该书的经典地位!这次由巴博领衔翻译此书,巴博的勤奋与学养,态度与责任历来受我辈敬仰!书很厚,到手后,迫不及待开始学习翻阅,从巴博的序言文字的深入浅出足以看出整个翻译团队的重视与付出!当经典之作遇上严谨学者,用严谨态度翻译出来的书,定当是锦上添花!所谓学者,一个是要广大先贤的重要思想,二是要让这些重要思想能够到达范围更广的听众!从某种意义上,这本书和巴博这个团队就是这个搭建起精英知识与大众沟通的破冰者!很是喜欢,太赞了!郑重推荐!
评分应该不错吧,给老师买的书
评分看过了他写的文明,还不错。
评分好多习字帖都挺好的楷草都好好晚安啦好好晚安啦好不容易放假了吗你在帮忙发一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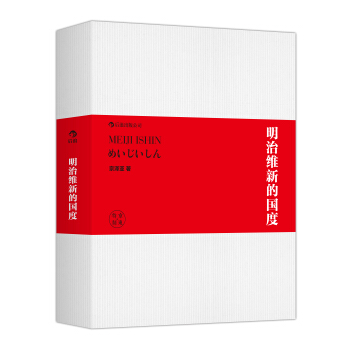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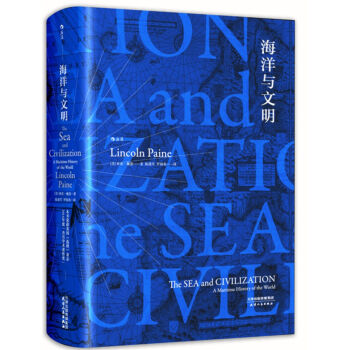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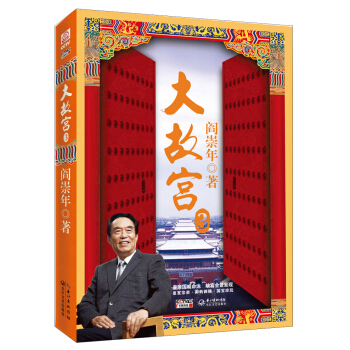
![甲骨文丛书:郁金香热 [Tulipomania :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Covet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75283/55262cb8N4f5d67b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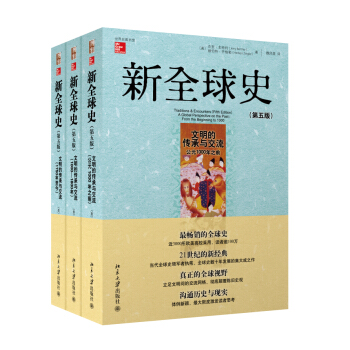
![日本史(1600-2000) [Japan:A Modern Histo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89689/53b25956N9c65f9c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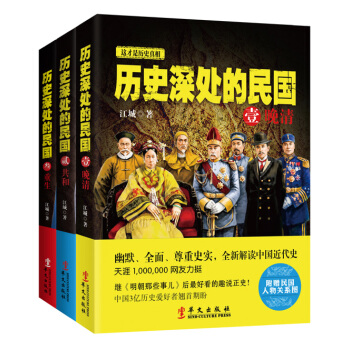
![罗马帝国的陨落: 一部新的历史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A New Histo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92552/592bf171Nc9677586.jpg)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套装上下共2册) [ ローマ亡き後の地中海世界]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94831/5ae2cff8N5c74bf9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