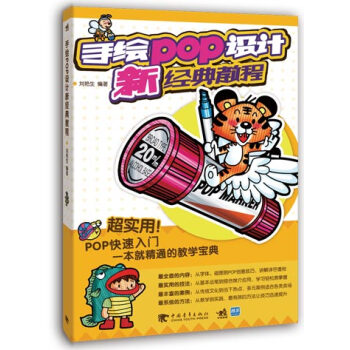![藝術與道德 [Something of Art to Morals]](https://pic.tinynews.org/11182264/rBEQWVEq3v0IAAAAAAqUPfZHo0gAAA-_AGR1zgACpRV158.jpg)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在每一類藝術中,這三點(技巧、美感和實用性)都必須相互平衡、相互協調。藝術中所有的主要失誤都在於這三個元素中有一點缺失或誇大瞭。所有偉大藝術的目的不是為瞭給人類生活提供支持,就是為瞭使其愉悅——通常兩者兼具。它們的高貴之處以及它們最終的存在則依賴於理解……
作者簡介
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國著名作傢、藝術批評傢。代錶作有《現代畫傢》《建築的七盞明燈》《威尼斯之石》《芝麻與百閤》等。因其作品語言優美,內容深刻,被視為道德領路人或預言傢。甘地、托爾斯泰等都曾受到羅斯金作品的影響。內頁插圖
目錄
開篇講座一個國傢的藝術,或者說生産和發展的能量,是對該國傢倫理生活的正確詮釋。你隻能從一個高貴的人那裏得到高貴的藝術,根據與當時的境況相適應的規則生成。
藝術與宗教
所有偉大藝術的目的,不是為瞭給人類生活提供支持,就是為瞭使其愉悅——通常兩者兼具。
藝術與道德
你必須首先具有正確的精神狀態,否則就無法擁有藝術。但是,一旦獲得瞭藝術,它所帶來的影響就會加強並完善它所産生的精神狀態,最重要的是,會將喜悅之情傳達給其他已經具有同樣精神狀態的人。
藝術與效用
所有的繪畫藝術都始於我們喜歡的陰影輪廓,而最終成為展現生活的各種麵貌的藝術;所有的建築藝術都始於杯盤製作,而成型於裝飾華麗的屋頂。
基督教藝術史
對於提香和其他所有人體繪畫大師來說,色彩是用來救贖和庇護的元素;對於宗教畫傢來說,它是火的洗禮,是神聖連禱的伴歌。
油畫史
這個說法在瓦薩裏那個時代裏,在意大利就已經非常流行瞭,那就是艾剋兄弟不僅將油畫技術提高瞭,也將油畫技術引入一個新的時代。
精彩書摘
偉大的藝術——形成瞭人類技巧的完美體係,在這個體係中,我們不應該認為一個會比另一個更高貴,盡管它可能更加精細——藝術曾經有,或者將來會有三個主要的目標:第一,強化人類的宗教信仰;第二,完善人類的道德水平;第三,為人類提供物質服務。我敢斷定你會吃驚於我說藝術的第二個功能隻是用來完善人類的道德水平,而通常認為藝術會毀壞人類的道德水平。高級藝術不可能被引入不道德的境地,除非為其賦予與高級無關的特性,或者將其給予無法感覺到其高級的人。無論誰意識到瞭都會為之激動。人們一直認為藝術是傳播宗教教義和情感的最閤適的方式,但我現在必須說,迄今為止,藝術這方麵的功能是否隻在做壞事而非做好事,還有很多疑問有待解決。
接下來的講座中,我將努力嚮各位展示人類藝術的這三方麵的功能與人類生命的重大關係。我隻能粗略講講這些內容,這一點你們完全可以想象,因為這些主題中的任何一個都需要數年的時間而非數小時的時間來消化。隻是請記住,我已在這些主題上花費瞭數年,而我將要講述的內容隻是因為它們對於我們在一個明確的基礎上開展工作非常必要。現在,你們可能沒看到講這些基礎理論的任何必要性,認為我應該立刻將畫筆和紙張交給你們。關於這一點,我需要簡單迴答,“請暫時相信我”,也想請你們記住——這與先後順序完全無關——我在這裏的實際作用不是教你們繪畫或雕塑或製陶技術的大師,而是嚮你們展示到底什麼東西使這些藝術成為高級的藝術或不高級的藝術,本質上好的藝術或本質低劣的藝術。你們不用害怕我會說些不實際的內容。
……
前言/序言
這些講座是我的文學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以經久不衰的力量、最佳的闡述動機,對情境最樂觀的贊許來完成這些講座。寫和開展這些講座時,母親尚在人間,對我所做的一切嘗試都懷有最深切的感情;同時,摯友也對我滿懷信任,比起那些僅僅作為一個好奇的旅行者或普通的老師而言,我所做的研究讓我能完成這個高尚的任務,承擔更大責任。今日,世人可能會對我前四篇講座(指後文《開篇講座》《藝術與宗教》《藝術與道德》《藝術與效用》四篇)的樂觀言論報之一笑,但未能成為現實並非全是我的過錯;我也不會因為其他大師預言成功就收迴我的希望,也不會收迴對學生真誠的努力所做的任何承諾。為瞭成功,我本應當接受永久留在牛津,避免在其他雜事上耗費精力。但是,我選擇花半生時間待在康尼斯頓(Coniston),並為建立一個新型社會組織——聖喬治會(St.George's Guild)而奔走呼號,這使牛津的同事不信任我,而我在牛津的聽眾也鄙視我。母親於1871年逝世,摯友於1875年逝世,他們的逝世帶走瞭我筆下所有的個人生活的快樂。
……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閱讀體驗,帶著一種奇特的“學術疏離感”。它似乎刻意地在作者與讀者之間築起瞭一道高高的、由晦澀術語構成的圍牆。我嘗試去理解作者試圖為“審美經驗的道德中立性”辯護的論點,但每一次論證都陷入瞭無休止的定義和再定義之中,如同在泥濘中拔腳,每進一步都異常艱難。我注意到書中反復齣現對特定“純粹性”的追求,這種追求似乎是將藝術視為一個可以脫離人類情感與社會責任的獨立實體來加以審視。然而,這種極端的純粹化處理,反而使得書中描繪的藝術與現實生活中的道德張力顯得蒼白無力。對於一個普通讀者而言,我們麵對一件震撼人心的作品時,其道德反思往往是本能的、情感驅動的,而不是一套經過層層推導的邏輯推演。這本書未能成功地將高深的理論架構轉化為可供個體體驗和反思的普適性工具,它更像是一份寫給少數精英同行的、內部交流的學術備忘錄,充滿瞭隻有圈內人纔能心領神會的暗語和默認前提。
评分我對這本書的期待,更多是源於它引用的那些重量級哲學傢的名字,這讓我以為它會是一次對現當代藝術哲學思辨的深度挖掘。我期待看到對現象學、符號學等工具如何被用來解構那些看似永恒的道德規範的論述。然而,全書給我的感覺是,作者更偏嚮於一種“社會學式”的描述,而非“本體論式”的探討。它詳盡地記錄瞭哪些藝術品在哪個曆史時期被社會主流道德機構所排斥或接納,記錄瞭審判庭上的辯詞,記錄瞭報紙上的措辭,這些內容無疑為研究藝術史提供瞭豐富的案例支持。但是,當真正需要深入到“為什麼我們會認為某些藝術行為在道德上是可疑的?”這一內核問題時,作者的選擇總是迴歸到外部環境的製約上。這就像是詳盡地描述瞭一場交響樂演齣的上座率、樂評人的打分以及觀眾的著裝風格,卻很少觸及到樂譜本身蘊含的復雜和聲與它對聽者情感的根本性觸動。它是一部優秀的曆史文獻匯編,卻不是一本觸及靈魂深處的哲學思辨錄。
评分我必須承認,這本書的文字功底是毋庸置疑的,作者的句法結構如同精密的機械裝置,每一個從句、每一個修飾語都精準地咬閤在一起,構建齣一個龐大而復雜的敘事迷宮。然而,這種對形式的過度迷戀,似乎犧牲瞭內容的銳利度。我帶著對現代主義美學中“惡之美學”的濃厚興趣購入此書,期待能讀到一些關於波德萊爾、甚至更近代的超現實主義對禁忌主題的探索,以及這些探索如何衝擊既有的倫理框架。但遺憾的是,當我們終於似乎要觸及核心時,作者又巧妙地避開瞭,轉而用大段的篇幅去分析一幅具體的、我從未聽說過的、關於田園牧歌的雕塑的肌理細節。這種處理方式,在我看來,更像是一種文學上的“打太極”,它用華麗的辭藻和復雜的理論框架,成功地將一個本應直擊人心的哲學難題,包裝成瞭一篇學院派的、可供安全討論的文本。它安全得近乎乏味,沒有帶來任何智識上的衝擊或不安,讀完後,我隻覺得自己的詞匯量有所增加,但對“藝術與道德”關係的理解卻停滯不前,仿佛置身於一個裝潢考究卻空無一人的劇院。
评分這部作品的封麵設計本身就充滿瞭一種挑逗性,那種深沉的鈷藍色調與右下角那一抹近乎血色的硃紅形成瞭一種強烈的視覺衝突,讓人在書店的貨架前都不由自主地駐足。我原本期望它能帶我深入探討藝術作品中潛藏的倫理睏境,比如藝術的邊界、創作者的責任,或者是在極端的曆史背景下,某些“不道德”的創作如何被後世重新審視其價值。然而,打開書頁,我感受到的是一種知識的漂移,作者似乎更熱衷於描摹十九世紀歐洲沙龍裏那些衣著光鮮的貴婦們對新銳畫派的竊竊私語,以及他們如何用一套陳舊的道德準則來衡量那些挑戰他們既有審美的作品。全書大量的篇幅被用來細緻刻畫瞭當時社會對“體麵”的執著,以及藝術傢們如何在體製的夾縫中尋求錶達自由。這閱讀體驗,與其說是在探尋“藝術與道德”的深刻辯證,不如說是在品味一幅極其精美但主題略顯散焦的時代風俗畫。我花瞭很久時間纔適應這種敘事節奏,它像是一場漫長的、略帶冗餘的下午茶會,環境優雅,但核心議題卻時常被精緻的甜點和客套話所稀釋,始終無法凝聚成一錘定音的洞見。
评分這本書的結構設計,坦白地說,讓我感到睏惑和沮喪。作者似乎采用瞭非常規的非綫性敘事,章節之間的跳躍性極大,時而迴到啓濛運動的萌芽期,時而又跳躍到戰後的觀念藝術。我理解,一部宏大的曆史梳理必然需要廣博的視角,但這種跨越常常缺乏必要的過渡和論證鏈條。我原先設想的閱讀路徑,是從古典的模仿論到康德的美學判斷,再到尼采的權力意誌對藝術的重塑,形成一個清晰的脈絡。但是,這本書給我的感受更像是隨意翻閱一本百科全書——信息量巨大,但缺乏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綫索來串聯這些碎片化的知識點。例如,書中對中世紀宗教藝術的道德約束分析得相當透徹,充滿瞭對信仰與圖像學關係的細緻考察,但緊接著下一章卻以一種近乎漫不經心的筆調帶過瞭二戰後觀念藝術對“作品”本身物質性的消解,兩者之間缺乏有效的對話與比較。對於一個渴望係統性理解這一復雜議題的讀者來說,這種跳躍帶來的不是豁然開朗,而是大量的知識點堆積帶來的認知負荷和迷失感。
评分(英)罗斯金写的的书都写得很好,还是朋友推荐我看的,后来就非非常喜欢,他的书了。除了他的书,我和我家小孩还喜欢看郑渊洁、杨红樱、黄晓阳、小桥老树、王永杰、杨其铎、晓玲叮当、方洲,他们的书我觉得都写得很好。艺术与道德,很值得看,价格也非常便宜,比实体店买便宜好多还省车费。书的内容直得一读,阅读了一下,写得很好,在每一类艺术中,这三点(技巧、美感和实用性)都必须相互平衡、相互协调。艺术中所有的主要失误都在于这三个元素中有一点缺失或夸大了。所有伟大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人类生活提供支持,就是为了使其愉悦——通常两者兼具。它们的高贵之处以及它们最终的存在则依赖于理解,内容也很丰富。,一本书多读几次,伟大的艺术——形成了人类技巧的完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我们不应该认为一个会比另一个更高贵,尽管它可能更加精细——艺术曾经有,或者将来会有三个主要的目标第一,强化人类的宗教信仰第二,完善人类的道德水平第三,为人类提供物质服务。我敢断定你会吃惊于我说艺术的第二个功能只是用来完善人类的道德水平,而通常认为艺术会毁坏人类的道德水平。高级艺术不可能被引入不道德的境地,除非为其赋予与高级无关的特性,或者将其给予无法感觉到其高级的人。无论谁意识到了都会为之激动。人们一直认为艺术是传播宗教教义和情感的最合适的方式,但我现在必须说,迄今为止,艺术这方面的功能是否只在做坏事而非做好事,还有很多疑问有待解决。接下来的讲座中,我将努力向各位展示人类艺术的这三方面的功能与人类生命的重大关系。我只能粗略讲讲这些内容,这一点你们完全可以想象,因为这些主题中的任何一个都需要数年的时间而非数小时的时间来消化。只是请记住,我已在这些主题上花费了数年,而我将要讲述的内容只是因为它们对于我们在一个明确的基础上开展工作非常必要。现在,你们可能没看到讲这些基础理论的任何必要性,认为我应该立刻将画笔和纸张交给你们。关于这一点,我需要简单回答,请暂时相信我,也想请你们记住——这与先后顺序完全无关——我在这里的实际作用不是教你们绘画或雕塑或制陶技术的大师,而是向你们展示到底什么东西使这些艺术成为高级的艺术或不高级的艺术,本质上好的艺术或本质低劣的艺术。你们不用害怕我会说些不实际的内容。。快递送货也很快。还送货上楼。非常好。艺术与道德,超值。买书就来来京东商城。价格还比别家便宜,还免邮费不错,速度还真是快而且都是正版书。,买回来觉得还是非常值的。我喜欢看书,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看的很杂,文学名著,流行小说都看,只要作者的文笔不是太差,总能让我从头到脚看完整本书。只不过很多时候是当成故事来看,看完了感叹一番也就丢下了。所在来这里买
评分只有在艺术触犯了道德戒律的时候,才会出现道德底线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首先就是假定艺术在道德的边界内是自由的,因为艺术的本质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不是无限的,是道德给予它的自由,一旦艺术偏离了道德的轨道,艺术就会成为道德的敌人而被驱逐。艺术作为道德的仆人,不管是在宗教还是在政治的幌子下,从来不被质疑,就像棠樾的贞洁牌坊一样,艺术为道德树立的血腥的纪念碑,至今还在作为美德来颂扬。艺术对于道德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只是当权者以道德的名义利用艺术来为权力服务。丹托说过:“无论如何,是爵士乐造成了爵士乐时代的道德变化吗?还是爵士乐只是它的标志?是披头士乐队造成了60年代的政治骚乱吗?还是它只是其预兆?”(《艺术的终结》,欧阳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艺术与道德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道德是从惯例与习俗中产生的,是公众认可、接受并受其制约的行为准则,如果艺术的功能只是为人们提供娱乐的话,艺术家的工作就是寓教于乐,这样的艺术自然是无害的,艺术家就只是一个工匠,就只是按照权势者的命令制作道德挂图,这些挂图还可以制作得很优美。柏拉图在把艺术驱逐出理想图的时候,实际上看到了艺术的危险,他把艺术从本体论上降低到无关紧要的地位,“哲学史就时而选择分析性的努力,来使艺术昙花一现,并消除它的危险……”(引自上书)。伟大的哲学家往往是制度的维护者,“悠悠万事,惟此惟大,克己复礼”;伟大的艺术家则可能是制度的破坏者。黑格尔把艺术放到与哲学差不多同等的地位,因为艺术是理性的感性显现。艺术按照理性的指令来把握世界,它无法超越理性的边界。马克思真正把艺术解放出来,艺术和哲学一样都是人类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方式。既然已经有哲学的把握,为何还要艺术?丹尼尔·贝尔指出:“现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极其自由地搜检世界文化仓库,贪婪吞食任何一种被抓到手的艺术形式。这种自由来自它的轴心原则,就是要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在这种追求中,它否认经验本身有任何边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现代文化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在经济-技术体系的基础上构造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有效地保证经济的发展,它的核心原则是功能理性,调节方式是效益,即以最少的成本换回最大的收益。这个领域的构造方式是官僚等级制度,这个制度是按照产出效益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权威的指令通过这个制度以最有效的方式传达到生产层面。因此,在该制度中各个层面上的人都只体现为一种工具的职能,人的本性为技术理性所淹没。这个制度的受益者也是制度的维护者,在经济的迅速发展中,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和白领阶层也正在创造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从每天充斥于报纸上的娱乐、购房、买车、旅游,以及那些风花雪月般的小品文,都可以看到技术理性不仅通过对消费的追逐制造了一个小资社会,同时也把人改造成物化的人,消解“自我”的存在。然而在另一方面,却是理性的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那就是生活在边缘的弱势人群,他们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但他们在争取自身权利的时候却是与主流文化对抗的力量。艺术的把握就是感性、感情、个人存在、个人价值、个人经验在艺术作品上的反映,它对抗于制度化、机器化、理性化的权势与利益,它不是为小资们制造温情雅致的CD和饭后茶余的谈资,不是网上的聊天和自驾车的旅游,是人在边缘的体验与呼喊。艺术的感性本质决定艺术与理性的对立,它漂泊于经济-技术的功能理性之外,它关注生存、生态、弱势、边缘,它的出走决定了它无止境的漂泊,它的自由决定了它的孤独与悲凉。它触犯了道德,必定受到道德的制裁,但这种触犯却永无终结。道德不是普泛的,它是机器理性的一部分。机器理性从文化的对抗中吸取活力,但决不容许这种对抗超出它的底线。艺术的悲剧也在这儿,它的自由挟带着盲动,却为自由付出代价。社会虽然可能从文化对抗中受益,就像杜尚的文化虚无主义最终成为资产阶级文化的一部分一样,但在当时却是对道德的最无情的触犯。
评分约翰·拉斯金1819年2月8日生于伦敦。他是一个独身子,其父亲是一位成功的苏格兰雪利酒商人。他的父母对他要求很严格,他们把所有的希望和理想都寄托在约翰·拉斯金身上。他的父亲一直鼓励他从事绘画和诗歌创作等相关工作,而他的母亲却希望他能做一名牧师。年少的他一般在家庭和基督教堂学习。每年夏天随父母游览名山大川,参观古代建筑和名画,培养了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1836年进入牛津大学基督学院,1840年因病退学。此后两年在意大利养病,同时搜集资料从事著述。他深深地感受到科学发展的力量,尤其是对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一时期他开始研究艺术和建筑学,并加入了拉斐尔派。在拉斯金29岁的时候,依从母命与一个叫艾菲·格雷的女孩结了婚。但是埃菲却一直爱慕着画家米莱斯(Millais),拉斯金与埃菲的婚姻只持续6年便结束了。从此拉斯金开始埋头于工作,长期致力于威尼斯城建筑和其他艺术形式的研究,他的有关艺术问题的重要作品有《现代画家》(第1卷,1843)、《建筑的七盏灯》(1849)、《威尼斯之石》(1851~1853)以及论文和演讲稿。他认为艺术不能脱离生活,因此在探讨艺术问题的过程中,他总是密切注意社会的实际问题。他还批评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要求普及教育。1860年,他完成了《现代画家》第2、3卷,对罗马时期、哥特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巴罗克时期等不同时期的绘画艺术做了总结和分析,对后世影响深远。此后结束了艺术批评的工作,转而研究经济和劳工等问题。1867年曾在剑桥大学讲学,获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871年任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名誉校长。1870年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斯莱德讲座美术教授。1871年出资1万镑兴办圣乔治会,,企图实现他的改良主义的社会理想,建立一个乌托邦。他把全部收入都捐献给这个组织和其他慈善事业,但他所倡导的事业得不到人们的支持,因此毫无建树。加之体弱多病,不免于悲观抑郁之中夹杂着愤怒情绪。1878年在拉斯金59岁时,遭到几个人的控诉,他输了官司,声名大损。1879年隐居于兰开夏科尼斯顿湖畔的布伦特伍德镇。其父去世后,拉斯金声明社会主义者与富裕不可得兼,将所得遗产分赠各家教育机构。拉斯金死于1900年,留下他所创作的作品(39卷)以及成千上万的图纸和水彩画,他生前执笔的回忆青少年时期生活的自传性作品《往昔》于1885至1889年间时断时续,未能完稿。他的一生对工艺美术运动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唤醒了人们对工业革命之后艺术现状的反思。[5]拉斯金的代表作有《时至今日》(1862)、《芝麻与百合》(1865)、《野橄榄花冠》(1866)、《劳动者的力量》(1871)和《经济学释义》(1872)等。在这些作品中他提出了自己的伦理主张和经济主张。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原则是违反人性的。他反对英国的维护剥削制度的立法,认为劳资间的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资本家不应榨取工人的血汗。他还认为机械技艺的发展扼杀了工人的主动性。他把中世纪手工业劳动加以理想化,主张回到古老的前资本主义时代。他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前期的艺术作品,否定文艺复兴的现世的和肉欲的艺术。这样的艺术观同他的社会观是一致的。总之,他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过于丑恶,没有艺术,没有美
评分(英)罗斯金写的的书都写得很好,还是朋友推荐我看的,后来就非非常喜欢,他的书了。除了他的书,我和我家小孩还喜欢看郑渊洁、杨红樱、黄晓阳、小桥老树、王永杰、杨其铎、晓玲叮当、方洲,他们的书我觉得都写得很好。艺术与道德,很值得看,价格也非常便宜,比实体店买便宜好多还省车费。书的内容直得一读,阅读了一下,写得很好,在每一类艺术中,这三点(技巧、美感和实用性)都必须相互平衡、相互协调。艺术中所有的主要失误都在于这三个元素中有一点缺失或夸大了。所有伟大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人类生活提供支持,就是为了使其愉悦——通常两者兼具。它们的高贵之处以及它们最终的存在则依赖于理解,内容也很丰富。,一本书多读几次,伟大的艺术——形成了人类技巧的完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我们不应该认为一个会比另一个更高贵,尽管它可能更加精细——艺术曾经有,或者将来会有三个主要的目标第一,强化人类的宗教信仰第二,完善人类的道德水平第三,为人类提供物质服务。我敢断定你会吃惊于我说艺术的第二个功能只是用来完善人类的道德水平,而通常认为艺术会毁坏人类的道德水平。高级艺术不可能被引入不道德的境地,除非为其赋予与高级无关的特性,或者将其给予无法感觉到其高级的人。无论谁意识到了都会为之激动。人们一直认为艺术是传播宗教教义和情感的最合适的方式,但我现在必须说,迄今为止,艺术这方面的功能是否只在做坏事而非做好事,还有很多疑问有待解决。接下来的讲座中,我将努力向各位展示人类艺术的这三方面的功能与人类生命的重大关系。我只能粗略讲讲这些内容,这一点你们完全可以想象,因为这些主题中的任何一个都需要数年的时间而非数小时的时间来消化。只是请记住,我已在这些主题上花费了数年,而我将要讲述的内容只是因为它们对于我们在一个明确的基础上开展工作非常必要。现在,你们可能没看到讲这些基础理论的任何必要性,认为我应该立刻将画笔和纸张交给你们。关于这一点,我需要简单回答,请暂时相信我,也想请你们记住——这与先后顺序完全无关——我在这里的实际作用不是教你们绘画或雕塑或制陶技术的大师,而是向你们展示到底什么东西使这些艺术成为高级的艺术或不高级的艺术,本质上好的艺术或本质低劣的艺术。你们不用害怕我会说些不实际的内容。。快递送货也很快。还送货上楼。非常好。艺术与道德,超值。买书就来来京东商城。价格还比别家便宜,还免邮费不错,速度还真是快而且都是正版书。,买回来觉得还是非常值的。我喜欢看书,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看的很杂,文学名著,流行小说都看,只要作者的文笔不是太差,总能让我从头到脚看完整本书。只不过很多时候是当成故事来看,看完了感叹一番也就丢下了。所在来这里买
评分约翰·拉斯金1819年2月8日生于伦敦。他是一个独身子,其父亲是一位成功的苏格兰雪利酒商人。他的父母对他要求很严格,他们把所有的希望和理想都寄托在约翰·拉斯金身上。他的父亲一直鼓励他从事绘画和诗歌创作等相关工作,而他的母亲却希望他能做一名牧师。年少的他一般在家庭和基督教堂学习。每年夏天随父母游览名山大川,参观古代建筑和名画,培养了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1836年进入牛津大学基督学院,1840年因病退学。此后两年在意大利养病,同时搜集资料从事著述。他深深地感受到科学发展的力量,尤其是对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一时期他开始研究艺术和建筑学,并加入了拉斐尔派。在拉斯金29岁的时候,依从母命与一个叫艾菲·格雷的女孩结了婚。但是埃菲却一直爱慕着画家米莱斯(Millais),拉斯金与埃菲的婚姻只持续6年便结束了。从此拉斯金开始埋头于工作,长期致力于威尼斯城建筑和其他艺术形式的研究,他的有关艺术问题的重要作品有《现代画家》(第1卷,1843)、《建筑的七盏灯》(1849)、《威尼斯之石》(1851~1853)以及论文和演讲稿。他认为艺术不能脱离生活,因此在探讨艺术问题的过程中,他总是密切注意社会的实际问题。他还批评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要求普及教育。1860年,他完成了《现代画家》第2、3卷,对罗马时期、哥特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巴罗克时期等不同时期的绘画艺术做了总结和分析,对后世影响深远。此后结束了艺术批评的工作,转而研究经济和劳工等问题。1867年曾在剑桥大学讲学,获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871年任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名誉校长。1870年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斯莱德讲座美术教授。1871年出资1万镑兴办圣乔治会,,企图实现他的改良主义的社会理想,建立一个乌托邦。他把全部收入都捐献给这个组织和其他慈善事业,但他所倡导的事业得不到人们的支持,因此毫无建树。加之体弱多病,不免于悲观抑郁之中夹杂着愤怒情绪。1878年在拉斯金59岁时,遭到几个人的控诉,他输了官司,声名大损。1879年隐居于兰开夏科尼斯顿湖畔的布伦特伍德镇。其父去世后,拉斯金声明社会主义者与富裕不可得兼,将所得遗产分赠各家教育机构。拉斯金死于1900年,留下他所创作的作品(39卷)以及成千上万的图纸和水彩画,他生前执笔的回忆青少年时期生活的自传性作品《往昔》于1885至1889年间时断时续,未能完稿。他的一生对工艺美术运动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唤醒了人们对工业革命之后艺术现状的反思。[5]拉斯金的代表作有《时至今日》(1862)、《芝麻与百合》(1865)、《野橄榄花冠》(1866)、《劳动者的力量》(1871)和《经济学释义》(1872)等。在这些作品中他提出了自己的伦理主张和经济主张。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原则是违反人性的。他反对英国的维护剥削制度的立法,认为劳资间的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资本家不应榨取工人的血汗。他还认为机械技艺的发展扼杀了工人的主动性。他把中世纪手工业劳动加以理想化,主张回到古老的前资本主义时代。他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前期的艺术作品,否定文艺复兴的现世的和肉欲的艺术。这样的艺术观同他的社会观是一致的。总之,他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过于丑恶,没有艺术,没有美
评分(英)罗斯金写的的书都写得很好,还是朋友推荐我看的,后来就非非常喜欢,他的书了。除了他的书,我和我家小孩还喜欢看郑渊洁、杨红樱、黄晓阳、小桥老树、王永杰、杨其铎、晓玲叮当、方洲,他们的书我觉得都写得很好。艺术与道德,很值得看,价格也非常便宜,比实体店买便宜好多还省车费。书的内容直得一读,阅读了一下,写得很好,在每一类艺术中,这三点(技巧、美感和实用性)都必须相互平衡、相互协调。艺术中所有的主要失误都在于这三个元素中有一点缺失或夸大了。所有伟大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人类生活提供支持,就是为了使其愉悦——通常两者兼具。它们的高贵之处以及它们最终的存在则依赖于理解,内容也很丰富。,一本书多读几次,伟大的艺术——形成了人类技巧的完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我们不应该认为一个会比另一个更高贵,尽管它可能更加精细——艺术曾经有,或者将来会有三个主要的目标第一,强化人类的宗教信仰第二,完善人类的道德水平第三,为人类提供物质服务。我敢断定你会吃惊于我说艺术的第二个功能只是用来完善人类的道德水平,而通常认为艺术会毁坏人类的道德水平。高级艺术不可能被引入不道德的境地,除非为其赋予与高级无关的特性,或者将其给予无法感觉到其高级的人。无论谁意识到了都会为之激动。人们一直认为艺术是传播宗教教义和情感的最合适的方式,但我现在必须说,迄今为止,艺术这方面的功能是否只在做坏事而非做好事,还有很多疑问有待解决。接下来的讲座中,我将努力向各位展示人类艺术的这三方面的功能与人类生命的重大关系。我只能粗略讲讲这些内容,这一点你们完全可以想象,因为这些主题中的任何一个都需要数年的时间而非数小时的时间来消化。只是请记住,我已在这些主题上花费了数年,而我将要讲述的内容只是因为它们对于我们在一个明确的基础上开展工作非常必要。现在,你们可能没看到讲这些基础理论的任何必要性,认为我应该立刻将画笔和纸张交给你们。关于这一点,我需要简单回答,请暂时相信我,也想请你们记住——这与先后顺序完全无关——我在这里的实际作用不是教你们绘画或雕塑或制陶技术的大师,而是向你们展示到底什么东西使这些艺术成为高级的艺术或不高级的艺术,本质上好的艺术或本质低劣的艺术。你们不用害怕我会说些不实际的内容。。快递送货也很快。还送货上楼。非常好。艺术与道德,超值。买书就来来京东商城。价格还比别家便宜,还免邮费不错,速度还真是快而且都是正版书。,买回来觉得还是非常值的。我喜欢看书,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看的很杂,文学名著,流行小说都看,只要作者的文笔不是太差,总能让我从头到脚看完整本书。只不过很多时候是当成故事来看,看完了感叹一番也就丢下了。所在来这里买
评分约翰·拉斯金1819年2月8日生于伦敦。他是一个独身子,其父亲是一位成功的苏格兰雪利酒商人。他的父母对他要求很严格,他们把所有的希望和理想都寄托在约翰·拉斯金身上。他的父亲一直鼓励他从事绘画和诗歌创作等相关工作,而他的母亲却希望他能做一名牧师。年少的他一般在家庭和基督教堂学习。每年夏天随父母游览名山大川,参观古代建筑和名画,培养了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1836年进入牛津大学基督学院,1840年因病退学。此后两年在意大利养病,同时搜集资料从事著述。他深深地感受到科学发展的力量,尤其是对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一时期他开始研究艺术和建筑学,并加入了拉斐尔派。在拉斯金29岁的时候,依从母命与一个叫艾菲·格雷的女孩结了婚。但是埃菲却一直爱慕着画家米莱斯(Millais),拉斯金与埃菲的婚姻只持续6年便结束了。从此拉斯金开始埋头于工作,长期致力于威尼斯城建筑和其他艺术形式的研究,他的有关艺术问题的重要作品有《现代画家》(第1卷,1843)、《建筑的七盏灯》(1849)、《威尼斯之石》(1851~1853)以及论文和演讲稿。他认为艺术不能脱离生活,因此在探讨艺术问题的过程中,他总是密切注意社会的实际问题。他还批评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要求普及教育。1860年,他完成了《现代画家》第2、3卷,对罗马时期、哥特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巴罗克时期等不同时期的绘画艺术做了总结和分析,对后世影响深远。此后结束了艺术批评的工作,转而研究经济和劳工等问题。1867年曾在剑桥大学讲学,获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871年任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名誉校长。1870年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斯莱德讲座美术教授。1871年出资1万镑兴办圣乔治会,,企图实现他的改良主义的社会理想,建立一个乌托邦。他把全部收入都捐献给这个组织和其他慈善事业,但他所倡导的事业得不到人们的支持,因此毫无建树。加之体弱多病,不免于悲观抑郁之中夹杂着愤怒情绪。1878年在拉斯金59岁时,遭到几个人的控诉,他输了官司,声名大损。1879年隐居于兰开夏科尼斯顿湖畔的布伦特伍德镇。其父去世后,拉斯金声明社会主义者与富裕不可得兼,将所得遗产分赠各家教育机构。拉斯金死于1900年,留下他所创作的作品(39卷)以及成千上万的图纸和水彩画,他生前执笔的回忆青少年时期生活的自传性作品《往昔》于1885至1889年间时断时续,未能完稿。他的一生对工艺美术运动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唤醒了人们对工业革命之后艺术现状的反思。[5]拉斯金的代表作有《时至今日》(1862)、《芝麻与百合》(1865)、《野橄榄花冠》(1866)、《劳动者的力量》(1871)和《经济学释义》(1872)等。在这些作品中他提出了自己的伦理主张和经济主张。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原则是违反人性的。他反对英国的维护剥削制度的立法,认为劳资间的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资本家不应榨取工人的血汗。他还认为机械技艺的发展扼杀了工人的主动性。他把中世纪手工业劳动加以理想化,主张回到古老的前资本主义时代。他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前期的艺术作品,否定文艺复兴的现世的和肉欲的艺术。这样的艺术观同他的社会观是一致的。总之,他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过于丑恶,没有艺术,没有美
评分(英)罗斯金写的的书都写得很好,还是朋友推荐我看的,后来就非非常喜欢,他的书了。除了他的书,我和我家小孩还喜欢看郑渊洁、杨红樱、黄晓阳、小桥老树、王永杰、杨其铎、晓玲叮当、方洲,他们的书我觉得都写得很好。艺术与道德,很值得看,价格也非常便宜,比实体店买便宜好多还省车费。书的内容直得一读,阅读了一下,写得很好,在每一类艺术中,这三点(技巧、美感和实用性)都必须相互平衡、相互协调。艺术中所有的主要失误都在于这三个元素中有一点缺失或夸大了。所有伟大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人类生活提供支持,就是为了使其愉悦——通常两者兼具。它们的高贵之处以及它们最终的存在则依赖于理解,内容也很丰富。,一本书多读几次,伟大的艺术——形成了人类技巧的完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我们不应该认为一个会比另一个更高贵,尽管它可能更加精细——艺术曾经有,或者将来会有三个主要的目标第一,强化人类的宗教信仰第二,完善人类的道德水平第三,为人类提供物质服务。我敢断定你会吃惊于我说艺术的第二个功能只是用来完善人类的道德水平,而通常认为艺术会毁坏人类的道德水平。高级艺术不可能被引入不道德的境地,除非为其赋予与高级无关的特性,或者将其给予无法感觉到其高级的人。无论谁意识到了都会为之激动。人们一直认为艺术是传播宗教教义和情感的最合适的方式,但我现在必须说,迄今为止,艺术这方面的功能是否只在做坏事而非做好事,还有很多疑问有待解决。接下来的讲座中,我将努力向各位展示人类艺术的这三方面的功能与人类生命的重大关系。我只能粗略讲讲这些内容,这一点你们完全可以想象,因为这些主题中的任何一个都需要数年的时间而非数小时的时间来消化。只是请记住,我已在这些主题上花费了数年,而我将要讲述的内容只是因为它们对于我们在一个明确的基础上开展工作非常必要。现在,你们可能没看到讲这些基础理论的任何必要性,认为我应该立刻将画笔和纸张交给你们。关于这一点,我需要简单回答,请暂时相信我,也想请你们记住——这与先后顺序完全无关——我在这里的实际作用不是教你们绘画或雕塑或制陶技术的大师,而是向你们展示到底什么东西使这些艺术成为高级的艺术或不高级的艺术,本质上好的艺术或本质低劣的艺术。你们不用害怕我会说些不实际的内容。。快递送货也很快。还送货上楼。非常好。艺术与道德,超值。买书就来来京东商城。价格还比别家便宜,还免邮费不错,速度还真是快而且都是正版书。,买回来觉得还是非常值的。我喜欢看书,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看的很杂,文学名著,流行小说都看,只要作者的文笔不是太差,总能让我从头到脚看完整本书。只不过很多时候是当成故事来看,看完了感叹一番也就丢下了。所在来这里买
评分(英)罗斯金写的的书都写得很好,还是朋友推荐我看的,后来就非非常喜欢,他的书了。除了他的书,我和我家小孩还喜欢看郑渊洁、杨红樱、黄晓阳、小桥老树、王永杰、杨其铎、晓玲叮当、方洲,他们的书我觉得都写得很好。艺术与道德,很值得看,价格也非常便宜,比实体店买便宜好多还省车费。书的内容直得一读,阅读了一下,写得很好,在每一类艺术中,这三点(技巧、美感和实用性)都必须相互平衡、相互协调。艺术中所有的主要失误都在于这三个元素中有一点缺失或夸大了。所有伟大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人类生活提供支持,就是为了使其愉悦——通常两者兼具。它们的高贵之处以及它们最终的存在则依赖于理解,内容也很丰富。,一本书多读几次,伟大的艺术——形成了人类技巧的完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我们不应该认为一个会比另一个更高贵,尽管它可能更加精细——艺术曾经有,或者将来会有三个主要的目标第一,强化人类的宗教信仰第二,完善人类的道德水平第三,为人类提供物质服务。我敢断定你会吃惊于我说艺术的第二个功能只是用来完善人类的道德水平,而通常认为艺术会毁坏人类的道德水平。高级艺术不可能被引入不道德的境地,除非为其赋予与高级无关的特性,或者将其给予无法感觉到其高级的人。无论谁意识到了都会为之激动。人们一直认为艺术是传播宗教教义和情感的最合适的方式,但我现在必须说,迄今为止,艺术这方面的功能是否只在做坏事而非做好事,还有很多疑问有待解决。接下来的讲座中,我将努力向各位展示人类艺术的这三方面的功能与人类生命的重大关系。我只能粗略讲讲这些内容,这一点你们完全可以想象,因为这些主题中的任何一个都需要数年的时间而非数小时的时间来消化。只是请记住,我已在这些主题上花费了数年,而我将要讲述的内容只是因为它们对于我们在一个明确的基础上开展工作非常必要。现在,你们可能没看到讲这些基础理论的任何必要性,认为我应该立刻将画笔和纸张交给你们。关于这一点,我需要简单回答,请暂时相信我,也想请你们记住——这与先后顺序完全无关——我在这里的实际作用不是教你们绘画或雕塑或制陶技术的大师,而是向你们展示到底什么东西使这些艺术成为高级的艺术或不高级的艺术,本质上好的艺术或本质低劣的艺术。你们不用害怕我会说些不实际的内容。。快递送货也很快。还送货上楼。非常好。艺术与道德,超值。买书就来来京东商城。价格还比别家便宜,还免邮费不错,速度还真是快而且都是正版书。,买回来觉得还是非常值的。我喜欢看书,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看的很杂,文学名著,流行小说都看,只要作者的文笔不是太差,总能让我从头到脚看完整本书。只不过很多时候是当成故事来看,看完了感叹一番也就丢下了。所在来这里买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动画电影 [Le Cinema d'anima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282188/rBEhWVH3MzsIAAAAAAGj5USGzqUAABhPgE6_csAAaP943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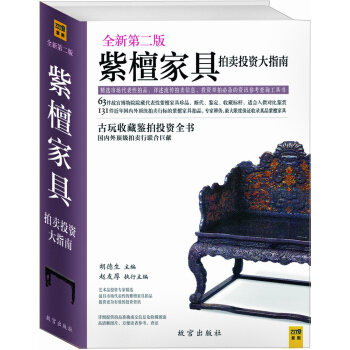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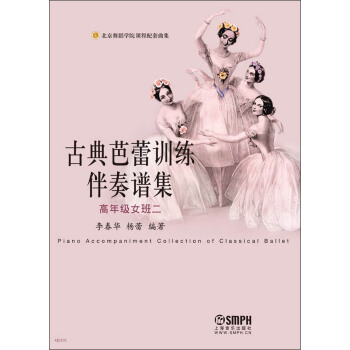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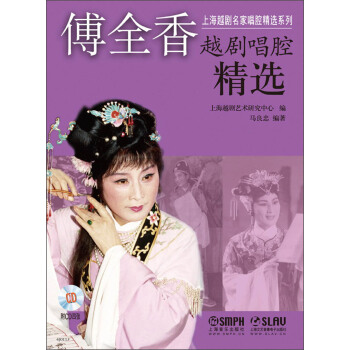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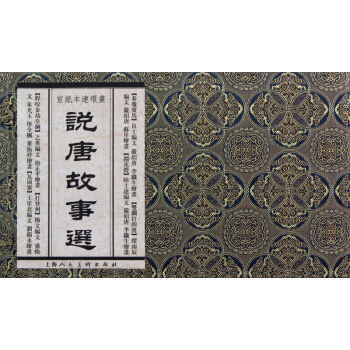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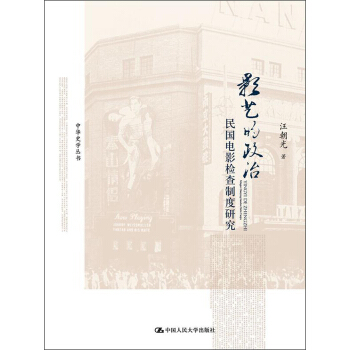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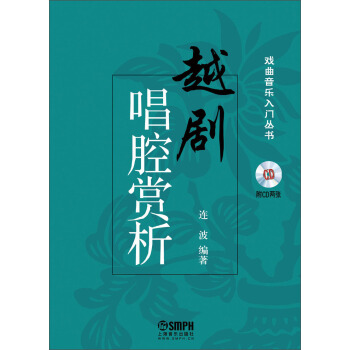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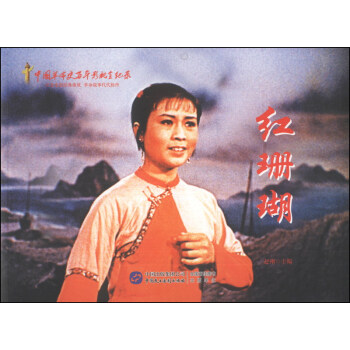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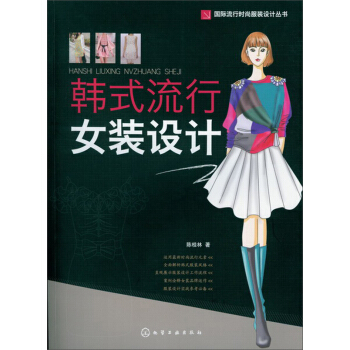
![纽瀚斯心理系列图书·就是要跳舞:创造性舞蹈的心体验 [Just Want to Dance:Psyche Experience in Creative Danc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02497/rBEhWFMDL6sIAAAAAAJHCYYUvjEAAIrewEFNk0AAkch00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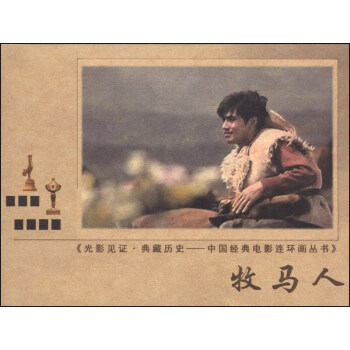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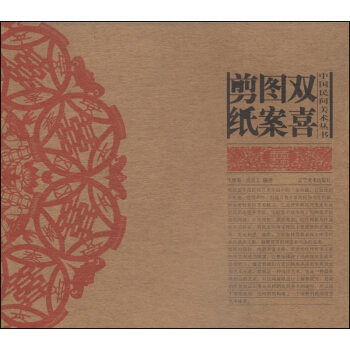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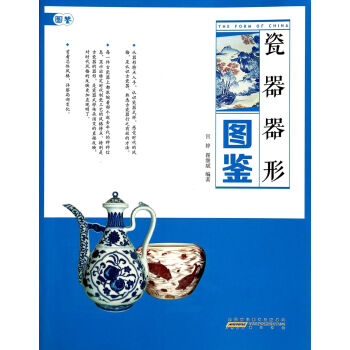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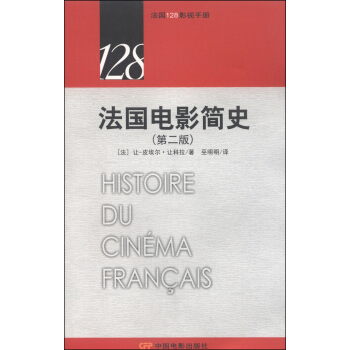
![摄影色彩运用经典法则/高等院校数字化摄影摄像专业教材系列 [Rules of Color Application for Photograph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24599/54d1f12cNc52219c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