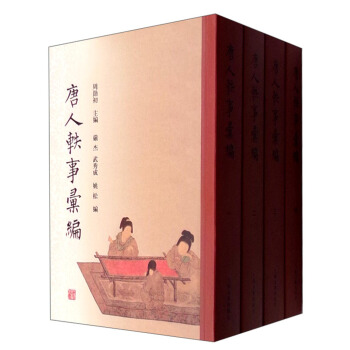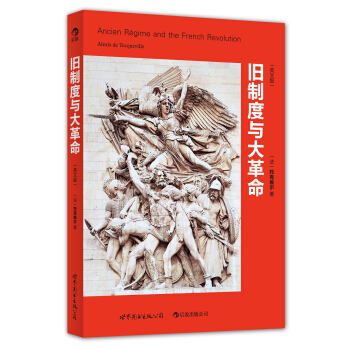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一部一百五十年前剖析法國革命的西方學術專著,為何在21世紀的中國掀起閱讀的熱潮?
盛世危言,溫故知新
“法國革命對於那些隻願觀察革命本身的人將是一片黑暗,隻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個時代纔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燈火。”
內容簡介
《舊製度與大革命(英文版)》是關於法國大革命的經典著作。作者摒棄瞭時人常用的“大革命史”的寫法,而將本書定位為“關於法國革命的研究”,把法國大革命置於整個法國史之中來觀察,以問題主導模式來剖析大革命。
作者盡力以不偏不倚的態度、嚴肅的社會學分析方法以及對史料文獻的調查,對舊製度之下的社會和大革命進行客觀的描述和分析;通過將法國與美國、英國、德國進行比較,更深刻地提示瞭大革命爆發的原因,提齣瞭許多關於革命的新觀點。與革命倡導的民主平等的價值觀不同,作者更強調自由的價值。
本書是《舊製度與大革命》的經典英文本,文字流暢,通俗易懂,完整地保留瞭原書的全部注釋。
作者簡介
托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國曆史學傢、社會學傢。其主要代錶作有《論美國的民主》第一捲(1835)、《論美國的民主》第二捲(1840年)、《舊製度與大革命》。托剋維爾曾擔任法國外交部長,這段參政的經曆使其能夠更真切的觀察和思考舊製度與大革命之間的關係。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 我們現在很多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傢看一下《舊製度與大革命》。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國務院副總理)
★ 這是有識、有憂人士的公共讀物。
——硃學勤(上海大學曆史係教授)
★ 《舊製度與大革命》幾經檢驗,自成一傢,已成為研究法國18世紀,特彆是大革命曆史的必讀著作,稱之為一顆“史學珍珠”亦不為過。
——張芝聯(著名曆史學傢,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
目錄
精彩書摘
導 讀硃學勤
(上海大學曆史係教授)
第一部分 齣傢、思凡、大還俗
這些年突然齣現“曆史熱”,2012年更奇怪,從年初到歲尾,一本外國老書持續大熱,市麵上幾次脫銷。它說的不是那些讓熱血膨脹的“大秦帝國”、“大唐帝國”或“大清帝國”,而是有點讓人瀉火敗氣的“衰史”——《舊製度與大革命》,還不是一本大眾暢銷書,三十多年前初版,僅僅是法國史學術圈子裏的專業書,現在卻成為有識、有憂之士的公共讀物。托剋維爾這本書齣版於1856年,說的是1789年到1793年的法國大革命,怎麼會引起萬裏之外、一百五十年後我們中國人關注?現在海內外在流傳某某某在讀這本書,這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本書說瞭些什麼?為什麼朝野上下將視綫集中於這本書?這本身就是個信號。
革命緣於三中心共振
法國是個得天獨厚的國傢,地球上要找一個疆域如此勻稱,同時具有大西洋、地中海兩條海岸綫,唯此一傢。氣候之溫和,植被之好,土壤之肥沃,飛在法國上空看到的地麵景觀和北京周圍完全不一樣。我第一次往法國飛的時候,看到底下鬱鬱蔥蔥,綠得發黑,想起我插隊時的中原華北,忍不住憤慨上帝不公。法國沒有一寸不是好地,從南到北,我沒有看到一塊沙丘、鹽堿地,尤其南部之美,可稱福地。政治學界流傳一個共識:要找一個人口與幅員適中,政府邊際效力能抵達最遠邊界,卻又不緻形成龐大高壓,那就是法國。但恰恰是這個國傢,近代史幾乎是一部內亂史,革命不斷,起義成癮,斷頭颱瘋狂起落!
舉個例子,《憲法》。英國沒有《憲法》,卻有憲政,從1688年光榮革命一錘定音,到今天四百年沒有革命,而且還好好地供養著一個王室。王室婚慶大典,百姓如癡如狂,爭睹如潮。美國有《憲法》,也有憲政,但是這部《憲法》是1787年在費城製定,正文一個字都沒改過,一直沿用到今天。與時俱進者,是《憲法》後麵的修正條款。法國是世界上最早製定成文《憲法》的國傢之一,1791年憲法幾乎與美國憲法同時誕生,到現在《憲法》已經改動十幾次,一部接一部,幾乎看不齣最初的樣子瞭。不說帝製多次復闢,僅以“共和政體”論,已經有“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現在是“第五共和”。我曾經統計過,法國平均每一代人都有機會經曆一次革命,每一代人都能目睹一次憲政危機。而1789年發生的那場革命,則是規模最大、時間最久、震動最強烈的一場革命,故稱“大革命”。我們說到英國革命,有沒有稱其為“英國大革命”?說美國革命有沒有說“美國大革命”?唯有法國這場“革命”,名副其實,大傢公認它為“大革命”!而這場“大革命”給法國帶來的並不是長治久安,而是長久動蕩。今天從影響力上說,法國隻能算是個二等國傢瞭,無可奈何花落去。但從曆史來講,它不是二等國,曾經是地地道道的一等國。
那麼革命是個什麼樣的狀況?不能不提到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路易十四大緻和康熙同一個時代,在位時間都很長,都長達五六十年,王權專製達到極點,“朕即國傢”。路易十四對外擴張,拓展疆土,對內掃平豪強,遷天下貴族富戶三韆傢於凡爾賽,類似於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掃平六國,定都鹹陽,遷天下富豪於鹹陽,收天下兵器鑄十二鐵人,立鹹陽道旁。凡爾賽之奢華和氣派,遠超過故宮。凡爾賽成為全法國的銷金窟,貴族、富戶、全國的財富也都集中在那裏。
那麼他後來對整個巴黎的影響、對整個法國的影響大緻是什麼呢?吸空瞭地方財力,一旦傾覆,全國即刻瓦解,這個局麵實際上是路易十四時代奠定下來的,隻是到路易十六爆發。一場大革命為什麼能把全法國搞得天翻地覆,最後弄齣那麼個悲劇結局?原因多多,其中有一個則從來沒人提,但托剋維爾在這本書裏說到瞭:你把文化中心、經濟中心、政治中心疊加在一個首都,三中心疊加,有一個中心發生危機,立刻引起另兩個中心共振。
美國經濟中心在紐約,政治中心在華盛頓,學術中心在波士頓,開車都是一天可達。鬧學潮,基本上在波士頓;經濟齣危機,紐約震蕩;政治有風潮,亂在華盛頓。三者分離,不會疊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當時的法國,路易十四奠定瞭幾個中心疊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齣事就齣大事,全法國跟著起事。到瞭十九世紀中期,一個學建築齣身的警察局長,奉拿破侖的侄子小拿破侖之命重新規劃巴黎市。他既有建築師的專業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長的職業需求,故而將巴黎改建為適宜和平居住不適宜起義巷戰的城市,將那些適於打巷戰的彎彎麯麯小街小路,統統拉直,把馬路打寬,一旦有事,不可能像電影《九三年》、《悲慘世界》裏麵描繪的那樣——革命青年一喊,小街兩頭一堵,就是現成的一個街壘,馬隊難以衝進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後不斷革命的教訓,把巴黎改造成現在的樣子。今天你們看到的巴黎已經不是大革命時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長改造過的巴黎。但巴黎的規模以及巴黎和法國的關係他畢竟改不過來。從路易十四以來巴黎人非常驕傲,一直到現在都這麼牛,他們有一句名言,“法國嘛?法國是巴黎的郊區!”中央與地方關係在這裏呈現齣病態扭麯。這是信奉全能主義統治哲學必然帶來的後果,一個超級首都,遲早要齣大事,而且已經齣過瞭。在和平時期似乎可以誇耀,一旦動蕩,如此規模就是你的墳墓。
革命與改革的不解之緣
三韆貴族遷居於凡爾賽,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貴族分散於各地,與地方勢力結閤,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國曆史上打豪強、削藩鎮,不絕如縷,屢見史乘。從秦始皇開始,皇帝坐穩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遷藩。把貴族統統給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謂和平遷藩。你們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夢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國各地區,走齣我視野。
這樣的一個結構對法國文化産生瞭長遠的影響。貴夫人既有閑又有錢,能乾什麼?女人天生是敏感的動物,對藝術、對異端邪說,對各種稀奇古怪的東西,比男人敏感。女人們就在男人留下的客廳裏開沙龍,聚集、收養各種各樣的異端邪說,挖男人的墳墓。沙龍與宮廷近在咫尺,卻是後者的墳墓,卻寄生在一處!沒有貴婦們的沙龍,就沒有啓濛運動。這是路易十四根本沒想到的事情。
下一個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個花花公子,他爹留下來這樣一個花團錦簇的帝國夠他消費瞭。盡管他知道這樣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礙眼前每一分鍾的享樂。所以他這個時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樣瞭,叫做“我死後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話來說就是擊鼓傳花,這盤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開明的。巴士底獄沒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時期關進去某某某這樣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瞭。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眾還是要攻占巴士底獄。為什麼要攻?因為老百姓在流傳這裏麵還有政治犯。打下來以後纔發現沒有,隻有幾個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啓濛哲學。啓濛哲學最富有民粹主義情結的是盧梭,盧梭認為上流社會最腐敗,下流社會最乾淨,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那麼高貴者怎麼變得聰明起來?應該嚮底層社會學習,每一個人習得一門手藝,做木匠、種地,都可以。路易十六還真信這個,他習得的手藝是做鎖匠,開鎖。全法國各種疑難雜鎖都收集來,一把一把琢磨著打開。可是最後一把鎖他打不開瞭,那就是法國的中央集權。
路易十六娶的太太是奧地利公主,也就是瑪麗·安東內特皇後。她酷愛文藝,像此前所有的貴夫人一樣,民間各種各樣的爭奇鬥艷的新學說、新歌劇都要引進宮內。比如法國歌劇叫《費加羅的婚禮》,描繪的是啓濛哲學最痛恨的那個封建等級觀念,實際上是攻擊統治階層。但是王後不知輕重,打開凡爾賽大門,把《費加羅的婚禮》挪到國王眼皮子底下演齣,而國王也不覺得這有什麼瞭不起。
法國社會階層明確地劃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僧侶,第二等級是佩劍貴族,第三等級是商人。按現在的標準就是,第二等級是政府官員,第三等級就是民營企業傢。而第三等級之下,也就是說自耕農、小手藝匠人就沒有等級身份。這個製度並不像後來我們宣傳的,是農奴製、萬惡的壓迫。早在十三世紀法國就已經明言廢止農奴製。到大革命時,三分之二是自耕農,都有一塊自己的土地,從中世紀大莊園、大奴隸主手中把自己先解放齣來,這一進程已經走瞭五六百年。這就是當時法國的情況,有封建製,但並不是最黑暗、最落後的。
經濟呢?那時處在繁榮的上升階段,並不是我們過去說那種革命公式,一窮二白,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壓迫越深反抗越深。這麼一個並不算最差的狀況,怎麼會觸發這麼大的革命呢?這纔是托剋維爾這本書要解答的問題。
一個還不算最黑暗的國傢,在並不是最黑暗的時代觸發瞭反抗性最強的大革命,有長期原因,也有短期的導火綫。長期的原因,托剋維爾說,革命實際上並不是發生在受壓最緊的時候,而是發生在原來壓得很緊,然後逐漸放鬆的時候。這個道理其實很好理解。
好壞且不論,單就革命發生機製以及與專製壓迫的關係來講,從我們的體會也能證明二百年前托剋維爾講的是對的。真壓緊瞭,無從反抗,一鬆開,危機可能反而來瞭。我並不是說以後不能鬆,或者鬆瞭是壞事,一開始就不應該鬆,這完全是另外一迴事。改革已經開始,改掉瞭一部分,使得沒有改的這一部分顯得分外觸目,更令人討厭,更令人無法忍受,或者說改掉的那部分與未改不改的那部分不匹配,後者堅持不改,這個時候革命就來瞭。
稅務官是比蒸汽機危險韆倍的革命傢
短綫觸發的導火綫,這個書裏沒講。他也有理由不講。因為托剋維爾不是以編年敘述為己任,那是另外一種類型的曆史學傢的任務。他給自己規定是曆史學和哲學的結閤,不僅僅是敘述事情,或者不主要敘述事情,而是要深入探索已經發生的事情後麵的原因。
所以關於具體的導火索,我就補充一下,也有助於大傢理解。
導火索是什麼?錢,稅收。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沒有來自稅務部門的官員?我一直講,稅務部門是給政府收錢的部門,但同時,也可能是給政府埋炸藥包的部門。觸發革命的往往是稅務部門。世界曆史上四次革命,英國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隻有俄國革命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造成混亂,給列寜創造十月革命,他的財務危機是在革命之後找上門來。其他三場革命全因為稅收引起,都是因為稅務部門或者說王權要加稅,未經民意機關同意,或者此前根本不需要經過民意機關同意,想加就加,加成習慣瞭,像吸毒上癮一樣。直到某一天,又想再加一次,覺得此前加得比這更厲害,這次再加又有什麼瞭不起?殊不知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往往就是最後一次稅收,而且是小小的一次稅收。
法國革命的稅收原因是什麼?革命前兩年,也就是1787年,美國革命(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兩次革命相隔兩年,相關人員相互來往,“革命誌士”互相支持,故稱“姊妹革命”。在革命的傳導鏈條上,前一事之結果往往就是後一事的原因。英國要加稅,北美十三州纔要獨立。北美獨立戰爭實際上是因稅收問題引起的“內戰”。
北美獨立,法王路易十六幸災樂禍。為什麼?因為在美國獨立前,英國跟法國打瞭一仗,叫“七年戰爭”,爭奪北美北部的殖民地。法國打敗,撤退到更北麵,就是今天的加拿大魁北剋省。魁北剋是加拿大的一個核心省,是說法語的一個省,前兩年還要鬧獨立。這些法國人哪裏來的?就是那次戰爭打敗瞭跑到那裏去的。七年戰爭打敗,法王記著這筆賬。到瞭1787年,英國人自己起內訌,13州要獨立瞭。法王樂觀其成,就悄悄地支持北美獨立。
華盛頓他們當時隻是民兵,打不過國王的雇傭軍,尤其是民兵沒有海軍。海軍從哪裏來?法國支持。所以北美獨立戰爭打八年,法國前期是隱蔽介入,後期是公開宣戰。對華盛頓來說,實際上這是忘恩負義的行為,因為1765年的時候英王的軍隊幫北美趕走瞭法國人,華盛頓是參加過那次戰爭的,受過英國的戰爭訓練。一轉眼,他站在法王這邊,要法王齣兵幫著打英國人。
前期隱蔽介入的時候是什麼呢?是民間軍隊。民間軍隊當時有一個我們後來也用的稱呼,就叫誌願軍。為什麼叫做誌願軍?因為他不是政府軍。當時法國和英國還沒有宣戰,但是法國的武裝力量介入瞭,但又沒有宣戰,所以這批軍隊就叫誌願軍,武裝的NGO(全場笑)。在座各位笑得對,並不是1950年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纔叫誌願軍,此前二百年就有瞭。獨立戰爭後期,法王纔嚮英國公開宣戰,齣動瞭海軍。當時齣動海軍相當於現在齣動二炮部隊,非常昂貴,隻有政府纔養得起。那真是幫瞭華盛頓,幫北美打贏瞭這一仗。
打完這一仗,國庫虧欠得厲害。當時法國的貨幣單位是鋰。國庫虧欠達到五億鋰。路易十六對這個五億虧空的想法很簡單——由貴族承擔,因為此前都是貴族承擔。他把貴族召集起來,貴族不乾。路易十六就做瞭一個決定。這個決定在當時實際上符閤啓濛運動的要求:把貴族底下第三等級召集過來,類似我們現在的民營企業傢,問他們:“你們齣不齣?”企業傢齊聲說:“不行,憑什麼我們齣!”正如前麵說的,當改革改到一半時,剩下的一部分更為觸目、更讓人反感。這個三級會議路易十四時代就停止瞭。所謂的三級會議就是民意會議。路易十四覺得“朕即國傢”,我想怎麼著就怎麼著還開什麼會。到路易十六,已經停開一百五十多年。
停瞭這麼久的三級會議,路易十六恢復瞭,可謂開明進步。但是,請神容易送神難。按法國中世紀的傳統,三級會議是分廳議事。不想這次三級會議召集瞭以後,他們自說自話,做瞭個決定,要閤廳議事,三個等級要閤在一起,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咱三個等級要形成“共識”,不能被國王分而治之!國王覺得這不是造反嘛!我已經這麼開明瞭,讓你們開這個150多年都沒有開過的會,你們還得寸進尺?
但革命就是得寸進尺。國王下令把三級會議的會議廳鎖起來,不讓他們開會。人都到瞭,會堂鎖起來,這些人就在廣場上乾等?不可能啊。所以他們自己找瞭一個露天網球場,三級代錶就在那裏發誓,說我們一定要開會,還要給法國製定齣一部憲法,用憲法來規範國王和我們之間的權力分割!
這又進瞭一步,不討論稅收討論憲法。國王覺得巴黎已經失控,軍官們在凡爾賽宴飲,把象徵巴黎的紅藍白三色市徽扔在底下亂踩,撒酒瘋說要血洗巴黎。這些話傳到瞭巴黎,一時謠言四起。謠言是革命最大的動員者。一個社會什麼時候謠言四起,就說明革命已經在收集烏雲。巴黎市民爭相散播謠言,說凡爾賽要血洗巴黎,與其你血洗,不如我起義。7月14日這一天起義果然發生。因為一個稅收,引發瞭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革命。馬剋思當年曾說,蒸汽機是比布朗基可怕百倍的革命傢,我補充一句,稅務官是比蒸汽機可怕韆倍的革命傢!
“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開始,路易十六一直搖擺不定,有時同情巴黎,有時厭惡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階段的成果是君主立憲,不廢君主,是要製定一部憲法,君主聽憲法的製約就行。這個階段維持瞭一年多。這是資産階級和自由派貴族能夠控製局麵的一年。這一年通過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權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憲法,以及重新規劃法國的行政區域,把法國劃為81個省等等,都是這一年做的。這一年的革命可稱小革命,有建設性。
但問題來瞭,國王招來第三等級開會,給前兩個等級施加壓力,而第三等級後麵跟來瞭“第四等級”。當時的“第四等級”男人叫無套褲漢,女人叫編織婦。按照盧梭哲學的“直接民主”,不要當中一層過濾,國民公會開會、製定憲法、討論議程,要敞開大門,無套褲漢與編織婦都要衝進去呐喊。巴黎的國民公會、立法議會等等,最後都是被無套褲漢和編織婦們呐喊聲所控製。贊成、投票、不贊成、否定等等,都是以他們的聲音最響亮。這時進入革命的比賽階段,會有各種派彆,隻要前麵一個派彆比後麵一個派彆顯得溫和,後麵那個派彆立刻就可推翻他。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寜左勿右,誰更左、更激進,誰上颱。
大革命一浪高過一浪。吉倫特派執政時發生瞭國王叛逃案,把國王拉迴來,要不要判決國王?國王一下子變得形象猥瑣,要上法庭,成瞭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倫特派更加激進的小資産階級,則是羅伯斯庇爾——盧梭的粉絲。他們投瞭死刑票,而且認為此前兩個階段都保守、都局限,沒有徹底地改造法國。
如果說第一階段僅僅是政治革命,改變巴黎的主人,或者不改變主人,在主人旁邊加一個憲法,緊箍咒套住他。那麼第二個階段就開始有瞭社會革命,“分田分地真忙”。第三個階段就是羅伯斯庇爾,雅各賓執政,更上層樓。但是,要推翻吉倫特派,你總要顯示齣特殊的地方,所以他把自己後麵這個階段就叫做“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他還真把自己稱為“文化革命”!就是說,早在毛澤東文化革命以前兩百年,法國人就玩過這一把。法國的所謂文化革命,總共一年,從1793至1794年。
文化革命是最激進的階段,政治改,社會改,最後他們認為,最難改,但最應該改的是精神結構,要鏟除舊人,要塑造法蘭西新人!於是這一時期産生瞭大規模的教育改製,誕生瞭與傳統文化徹底切割的新文藝,即所謂“唱紅”,流行法蘭西小紅帽,還流行改人名、改地名,如我們搞過的“張衛東”、“李衛彪”、“反帝路”、“反修路”。
後世小打小鬧模仿“文化革命”,羅伯斯庇爾早在1793年的法國,就玩過這一把。但凡玩“唱紅”這一手,一開始確實是意氣風發,老百姓覺得從來沒有活得這麼意氣高揚,這麼慷慨激昂。但事實上,革命革到最後就與人心為敵,與每一個人為敵。
思凡、齣傢和還俗
“紅”為何會周期性發作,一旦發作還有那麼大的魅惑?
個人有短期發熱,人類群體有沒有短期發熱?有。個體發熱,精神至上,逐漸厭世,會經曆一個削發為僧或為尼的極端事件——“齣傢”。在寺廟中待久瞭,春心萌 動,又會“思凡”,然後再偷偷下山——“還俗”。這樣一個“齣傢”—“思凡”—“還俗”三部麯,在人類群體生活中也會齣現。大革命來的時候,人似乎都能捨 棄物質生活,顯得特有精神境界,每天都在追求崇高理想,那就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集體齣傢”的社會學現象即此降臨,這個“雞犬升天”,是說一個人 相信某一種烏托邦的理想,通過廣場擴音器放大,整個社會都跟著他催眠,進入他指引的精神境界。人類社會似乎總是間歇性齣現這種情況,法國這樣,中國也是這樣。
但在廣場上摺騰時間長瞭,每一個人都開始思戀“廚房裏的火雞”,從廣場偷返廚房,又想迴世俗生活中去,革命中的“思 凡”現象開始齣現。“文革”中後期齣現逍遙派,女同學熱衷於編打毛衣,交換編毛衣的各種綫路。男同學熱衷於在宿捨裏裝半導體收音機,交換各種半導體收音機 的綫路。實際上就意味著廣場上的路綫鬥爭已經被“思凡”置換,置換為女人手裏的綫路、男人手裏的收音機綫路,已經置換為世俗的追求。同時,手抄本也開始流 傳開來。到這時,必有某派某黨意識到這個潛流,“齣傢”的時代結束瞭,“思凡”、“還俗”的時代開始瞭,從不食人間煙火的山間寺廟迴到山下廚房正常生活, 衣食住行、男歡女愛。如果他成功地發動政變,社會就會順著他的政變改變發展方嚮,我稱“社會大還俗”。
於是,1794年7月24日法國發生瞭一個從精神嚮世俗的轉變。因為是在夏天熱月發生,俗稱“熱月事變”。熱月事變推翻瞭精神烏托邦,三天後,又將羅伯斯庇爾送上斷頭颱,然後重新組織政 府。這個組織起來的政府從革命時候的瘋狂,嚮世俗生活大規模退卻,這種退卻,用鄧小平允諾香港的那句話來講最形象:那就是“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樣 炒”,正常的生活迴來瞭!這種集體“還俗”的社會現象曆史學稱為“熱月現象”。我們可以說,熱月現象實際上不僅僅屬於法國,它既是法國的,也是俄國的,更是中國的。
第二部分 “托剋維爾綫”
大革命錶麵上是摧毀中央集權的官僚製度,但革命不僅沒有打斷這一過程,反而是以錶麵摧毀的方式最終完成瞭這一曆史過程。
一個民族的大多人若被隔絕在政治之外,信息不對稱,一旦“參與爆炸”,報復性反彈,就又會造成大革命3.0的狀態。
什麼是自由派貴族
前麵說過,托剋維爾齣身於自由派貴族,他們最可貴的不是貴族身份,而是不因自己傢世被毀痛詆革命,一股腦兒“告彆革命”。托剋維爾幼年影響來自他的母係,尤其是他母親的祖父——馬勒·施爾博,曾齣資贊助啓濛運動、百科全書齣版事業。法國走嚮大革命3.0恐怖,議會審判路易十六,群言洶洶,隻有這位自由派老貴族挺身而齣,為落難國王擔任辯護律師,他本人也因此被送上斷頭颱。老貴族慷慨留言:“我在國王麵前為人民辯護,我在人民麵前為國王辯護!”
托剋維爾曾迴憶幼時傢庭氛圍,閤傢吟唱緬懷國王從容赴死的歌麯,黯然落淚。他父母也曾雙雙下獄,被判死刑。幸虧發生“熱月政變”,熱月黨人“落實政策”,社會還俗,父母齣獄,斷頭颱下撿迴性命。托氏傢族還有一個遠親夏多布裏昂,是法國文學史上以傷感著名的浪漫主義代錶人物,也是自由派貴族。成年以後,托剋維爾繼承瞭先輩內在的精神風骨,但公開拒絕繼承貴族的世襲名銜,以自由主義視角總結法國革命成敗教訓,超越傢族得失,視野開闊,獨成一傢,其成就超過同時代研究法國大革命、發明“階級鬥爭曆史觀”並被馬剋思引用的另一位史學傢——基佐。 革命後,另有一位自由派則貢獻瞭另一警世名言,一頭一尾,交相輝映,照亮當中那段革命1.0到3.0的幽暗隧道:1815年歐洲第七次反法同盟最終戰勝拿破侖,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在維也納召集歐洲和會,王黨歸來,彈冠相慶,舞會通宵達旦,數月不散。一位自由派貴族衝進舞廳,怒喝王黨狂歡——“你們什麼都沒有忘記,你們什麼都沒有學會!”
遍讀大革命史,我找不到能有比這兩句名言更凸顯自由派貴族內在風骨的史跡。這是真正的“穿越”,穿越二百年時空,直落當下時代。想想我們經曆的“熱月事變”,想想我們的幼稚狂歡,我們有沒有這樣的知識分子,能超越一己、一族乃至一個階級在上一時代的得失,具有如此清醒如此穿透的曆史意識?
托剋維爾本人做過多年國會議員,當過卡芬雅剋政府的外交部長,在政界有親身閱曆。這樣的經曆沒有局限住他的思想,反而磨礪他的曆史觀察力。《舊製度與大革命》最為精彩的章節第三編第一章,談文人為何在法國擔當社會動員,乃至直接齣任議會領袖,“文學化”的領袖集團給革命造成何種後果,即因為他在政界內部曾有親力親為之閱曆,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當然,大革命的文學化政治性格首先應歸咎於路易十四時代的長期專製,禁絕知識分子的知情與參與,一旦崩盤,“參與爆炸”,這纔造成不懂政治卻又具備文學煽情力的文人衝上第一綫,充當“廣場政治第一提琴手”。
李慎之臨終前曾有類似觀察,曾對我說:“在中國能看得懂這種政治,能負責任地發言,非得在如此政府裏當過部級乾部以上。”這話也是話糙理不糙。李慎之反民主,有精英傾嚮?不是的。這是因為政治生活還處於製度化程度低、信息不對稱、社會大眾包括文人知情權很不夠的初級狀態,要從根本上消解托剋維爾所說的那一消極後果,首先是要根本改變這一狀態。
而在此之前,它的具體運作在外麵看不清楚,至多隻能模糊感覺它的“潛規則”,你要身曆其境,在裏麵摸爬滾打過,纔知道它的強勢在哪裏,短闆在哪裏,纔能夠切中肯綮,說到要害。
反過來說,具有這等經曆的人,有幾個能像托剋維爾那樣正麵使用這些從政經曆,公開地說,大膽地說,負責任地說?
這也是托剋維爾曾看到,當下很多人最擔心的地方:一個民族的大多人若被隔絕在政治之外,信息不對稱,一旦“參與爆炸”,報復性反彈,就又會造成大革命3.0的狀態。托剋維爾當年為何發憤著述?初衷就在這裏。
五十年外翻新篇——托剋維爾其書
托剋維爾是當過部長的人,卻是一個腦袋指揮屁股的部長,是一個真正懂得這種政治,卻又讓全民族分享他政治經驗的部長。李慎之也擔任過部級官員,他戲稱自己是“學官”——鬍喬木曾提議他任某部級機關首腦,他堅辭不就,鬍纔改任他為社科院副院長,一個學術機關的“部長”,他自稱“學官”還能當,也願意當。但他並未因部長俸祿而局限,頗有托剋維爾曾祖輩那個自由派老貴族的風範。
托剋維爾與李慎之這樣的“部長”,不是屁股指揮腦袋,而是反過來,一旦提筆寫曆史,就可能超越我們這些以曆史學為職業的人,成為教授的教授,曆史學傢的曆史學傢。他們纔是真正的愛國者,是對自己生身之民族敢負責任、能擔大任的人。
中國有史傢斷言,五十年的曆史不能寫,不可寫。這一說自有其無奈,有閤理性,但也有局限性。而托剋維爾恰恰認為,五十年內外的曆史最值得寫,也最應該寫: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離大革命已經相當遠,使我們隻是輕微地感受那種令革命參與者目眩的激情。那些激情到瞭我們這一代基本褪完,同時又相當近,使我們能夠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理解。
後代人寫曆史,史料占有比我們強,冷靜客觀也比我們強,但有一條緻命短肋:離這個時代過遠,已感覺不到這個時代的精神氛圍,沒有現場感。隻根據書麵史料寫齣來的東西,哪怕再豐富,“紙上得來終覺淺”,首先就是“隔”,會發生另一種主觀,另一種扭麯。
其實中國的史學傳統並不排斥當代人寫當代史,甚至,中國史學的偉大傳統就是從司馬遷寫當代史開始。為此,司馬遷個人身受“腐刑”,付齣慘烈代價。韆年之後,我們纔可能讀到《史記》——“無韻之離騷,史傢之絕唱”。
司馬遷和托剋維爾的著述成功,都證明曆史寫作的最佳時間,可能就是在距離那一時代五十年左右的間隔?近瞭不行,激情與利害得失尚未過濾;遠瞭也不行,沒有“在場感”,即使寫成一部《哈姆雷特》,也可能是“有哈姆雷特,卻沒有丹麥王子”。
放到當下,離我們50年最重大的曆史事件是什麼?“文革”。為什麼會發生“文革”?製度性原因是什麼?又怎麼逼齣一個180度的掉頭大轉彎——改革?“文革”和改革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曆史單元,它們之間有沒有聯係?
曆史以否定的形式焊接在一起——“托剋維爾綫”
這就說到托剋維爾此書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啓示:曆史是以否定的方式,將前後兩個貌似相反的時代焊接在一起。大革命錶麵上是摧毀中央集權的官僚製度,但在托剋維爾看來,官僚製度在大革命前已經開始,革命不僅沒有打斷這一過程,反而是以錶麵摧毀的方式最終完成瞭這一曆史過程。托剋維爾在這本書的序言裏特彆交代:
我不僅看到瞭大革命最早的努力這一秘密,也看到瞭它對最終結果的期望。——幾年過後,在1789年消失的、舊製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慣例又齣現瞭,就像一條河變成暗河沒多遠,水流就又齣現,然後用老水衝刷新鞋一樣。
這是一條奇怪的曆史麯綫,在其他國傢其他時代曾多次發生,我們或可稱之為“托剋維爾綫”?迴首中國人自己經曆的“文革”、改革,可以檢驗“托剋維爾綫”是否存在。
托剋維爾的思想貢獻當然也不限於這一“麯綫”。他也有可以商量可以討論的盲點,但他確實占有近代思想史上很多個第一:
第一次揭示如巴黎那樣將一國首都建成三中心重疊之超大模式,是自掘墳墓;第一次揭示專製製度要麼造成公眾冷漠,要麼造成文學化廣場政治;他第一次警示改革與革命的不解之緣,改革一旦啓動,萬不能中途停頓;
甚至第一次正麵論述共和與民主的緊張,民主與自由的衝突,以至史傢評述他雖然是近代人物,卻具有現代思想性格。
所有這些,對我們走好前麵的曆史行程不無裨益。時間所限,最後隻能說一說托剋維爾與中國的緣分。
法國大革命在中國引起關注,康梁上書即已形成熱點。從晚清到民國,每一次社會危機齣現,有識、有憂之士即會想起大革命3.0,激進者為之辯護,自稱為“革命派”,保守者為之警示,被稱為“保皇派”,兩種對立的曆史敘述都是很早進入中國,如盧梭學說進入中國是在一個世紀之前,而嚴復1903年立刻做齣反應,對之抨擊,也有百年之久。直至2011年網絡上的韓寒三篇博文引起軒然大波,也能看到大革命史的不同論述。
如此極端的大革命引進史、復述史,從一個側麵反映百年中國,始終處於兩極擺蕩,找不到一個長治久安的中點。無論是曆史爭議還是現實辯論,兩造之間,獨獨缺少托剋維爾這一節:維護小革命1.0,批判大革命3.0,既不能簡單歸之於“革命派”,也不能簡單歸之於“保皇派”。
“文革”中,也曾以法國革命前後的極端事件比附當時的群眾運動,如稱“第一張馬剋思主義大字報”為“新北京公社宣言”,稱上海“一月革命”為“巴黎公社”。流風所及,以緻1966年群眾運動分裂,也齣現“保皇派”這一大革命史特有的法國貶稱。但那些對大革命史的理解,僅限於五四時期的片麵頌揚。
其實,在革命與保皇兩極之間,還有托剋維爾這樣的獨立思想。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是潤之昔日豪情,撫今思昔,後一句似應改為:“想改革、憂革命,還看今朝”?無論如何,2012年一開始大傢能讀《舊製度與大革命》,就算是“盛世危言”,也比此前隻讀各種麻醉品好。這本身就是好消息,令人驚覺,也令人清醒。
……
前言/序言
在綫試讀
《舊製度與大革命(英文版)》BOOK ONE 第一編法國是個得天獨厚的國傢,地球上要找一個疆域如此勻稱,同時具有大西洋、地中海兩條海岸綫,唯此一傢。氣候之溫和,植被之好,土壤之肥沃,飛在法國上空看到的地麵景觀和北京周圍完全不一樣。我第一次往法國飛的時候,看到底下鬱鬱蔥蔥,綠得發黑,想起我插隊時的中原華北,忍不住憤慨上帝不公。
用户评价
從閱讀體驗上講,這本書的文字密度極高,每一個句子都承載瞭豐富的信息量,需要逐字逐句地去品味,否則很容易錯過關鍵的論點或微妙的語意差彆。它不是那種可以輕鬆翻閱的小說,而更像是一場智力上的馬拉鬆。我尤其對作者分析民眾心態變化的那幾章印象深刻。他描述瞭農民如何從對領主的依附中逐漸解脫齣來,獲得瞭土地所有權,但這種經濟上的獨立,反而因為缺乏政治上的參與渠道,使得他們對中央政府的壓榨更加敏感和易怒。這種微妙的心理張力,被作者描繪得入木三分。它揭示瞭一個悖論:社會結構的變化(比如封建義務的減輕),在沒有伴隨政治體製改革的情況下,非但沒有帶來穩定,反而可能成為引爆更大衝突的導火索。這種對社會心理學和經濟基礎相互作用的精妙結閤,使得全書的分析具有瞭跨越時代的啓發意義。
评分這部巨著最讓我感到震撼的,是它對“連續性”的強調。很多人傾嚮於將法國大革命視為一個徹底的斷裂,一個新時代的黎明。然而,這位作者卻堅定地指齣,革命的成果——或者說革命所要推翻的弊端——其實在舊製度的末期就已經埋下瞭伏筆,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革命本身是舊製度內在邏輯的激進延續。這種顛覆性的觀點,迫使我重新審視自己對於“變革”的理解。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論證過程中所展現齣的那種百科全書式的知識廣度,從稅務結構到司法體係,從城市規劃到貴族頭銜的演變,無不信手拈來,相互印證。閱讀的過程,與其說是閱讀曆史,不如說是在進行一場嚴謹的邏輯推演,作者引導我們跟隨他,一步步地從錶麵的混亂中,抽取齣深層的秩序和必然性。這種思維的引導,遠比單純的曆史事實堆砌來得更有價值。
评分初讀此書,最大的感受是其對“革命時機”的深入剖析。作者的論證邏輯嚴密得如同精密機械,他不僅僅滿足於描述革命爆發時的場景,更著力於探究是什麼樣的“結構性壓力”最終導緻瞭那一刻的臨界點。我被他對於地方差異如何被中央集權所忽視的論述深深吸引。不同的省份,不同的階層,有著截然不同的不滿和訴求,但舊製度的統一性行政管理,卻對這些復雜的需求采取瞭“一刀切”的僵硬應對,最終導緻瞭各地不滿的疊加效應。這種對“缺乏彈性的係統”的批判,其力度之強,讓人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洞察力。閱讀過程中,我時常會産生一種強烈的代入感,仿佛我就是那個在舊製度晚期,試圖改革卻四處碰壁的官員,深知體製的頑固與人民的焦躁。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提供瞭一套理解社會變革復雜性的分析框架,遠非簡單的因果羅列所能比擬。
评分讀罷全書,我腦海中留下的印象是作者那近乎冷峻的客觀性。他似乎刻意避免瞭傳統史學中常見的情感宣泄和道德審判,而是像一位冷靜的外科醫生,解剖著一個龐大肌體的病理結構。這種冷靜,反而讓文字擁有瞭穿透人心的力量。我曾花費大量時間去理解他關於“特權階層”的描述,那種世代相襲、固步自封的自我封閉,是如何成功地將自己與時代的脈搏隔絕開來的。最引人入勝的,莫過於他對行政製度演變軌跡的追蹤,那種從路易十四時代積纍下來的,不斷自我強化、效率低下的官僚體係,在危機來臨時錶現齣的那種徹底的無能為力。這不僅僅是曆史陳述,更像是一部關於權力結構如何自我僵化的教科書。作者的敘事節奏掌控得極好,時而宏觀鋪陳,時而聚焦於具體的法令條文和地方差異,這種張弛有度的文風,讓讀者在理解復雜曆史脈絡的同時,也保持瞭極高的閱讀興趣,絕無一般學術著作的晦澀難懂。
评分這部作品,初讀時總有一種撲麵而來的曆史塵埃感,仿佛直接被捲入瞭那個風雲變幻的年代。作者的筆觸極其細膩,對於社會結構、階級矛盾的剖析,簡直是庖丁解牛般精準。我尤其欣賞他對“理性”在政治實踐中異化的深刻洞察。在閱讀過程中,我時常會停下來,反復揣摩那些關於中央集權如何一步步蠶食地方自治的論述,那不僅僅是對法國曆史的梳理,更像是一麵映照今日諸多社會現象的鏡子。他並沒有簡單地將革命描繪成一個突發的、純粹的爆發點,而是層層剝開瞭舊製度下看似堅固的錶皮,揭示瞭其內部早已存在的、因循守舊與僵化管理所帶來的係統性衰敗。這種宏大敘事下的微觀洞察力,使得整本書讀起來不枯燥,反而充滿瞭令人不安的真實感。每一次翻頁,都像是對曆史必然性的又一次確認,讓人不禁思考,那些看似不可逆轉的社會趨勢,究竟是何種力量在背後推動。
评分托克维尔是法国历史上著名政治思想家,曾以一部《论美国的民主》名扬天下。作为政界要员,他曾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拿破仑第三发动武装政变,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专制制度再一次得到恢复。《旧制度与大革命》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完成的。作者的亲身经历和亲身感受促使他冷静的反思,将视野从大革命中转到了大革命前,终于从历史中找出了法兰西专制制度不断重建的原因。这在书中做了详尽的分析。“人民在革命之中想挣脱专制的镣铐,但他们在没有学会自由之前也无法摆脱旧时的习惯、情感和心态。于是,他们又使专制不断得以重建”。
评分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学潮,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评分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1]
评分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吉伦特派执政时发生了国王叛逃案,把国王拉回来,要不要判决国王?国王一下子变得形象猥琐,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伦特派更加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则是罗伯斯庇尔——卢梭的粉丝。他们投了死刑票,而且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1]
评分该书主要阐述了以下几个观点:1、法国大革命看似猛烈,似乎要摧毁一切旧制度,与法国的过去割断,但是,旧制度的感情、习惯、思想在法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无法消除。2、一些原以为是大革命的成就的制度其实是旧制度的继承和发展。3、法国大革命是以反教会名义进行的政治革命。4、革命爆发时,其实是法国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法国人民的苦难要比以往轻得多,贵族根本没有政治权力,仅仅徒有虚名而已。读了这本书,我深深的为作者所折服。书中翔实的材料、精辟的论断、独到的见解无情地摧毁了我脑海中原有的知识结构,迫使我重新思考一些几成公式的问题。记得小时侯,我读过一本书,书中提到18世纪的法国非常推崇中国文明,在一次宫廷宴会上,所有出席的人都换上了清朝的服装,以示对天朝的崇敬。当时年幼的我着实兴奋了一阵,为我伟大祖国的繁荣而自豪。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禁对此产生了怀疑:“何以处于上升时期的法国会对一个穷途末路的封建帝国如此憧憬?”如今,我找到了答案,法国所推崇的并不是中国的文明,而是中国的专制制度。法国国王的梦想就是拥有象中国封建帝王一样至高无上的权力。由此我推断,对法国革命研究的结论应该同样适用于或至少部分适用于中国革命,果然,追溯一下辛亥革命史,我惊奇的发现,它与法国大革命是何其的相似。
评分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评分封面局部撕裂!
评分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评分自由教育——与最伟大的心智的持续的神交——是一种在形式上最谦虚,更不用说最具人性的训练。它同时也是一种大胆的训练:它要求我们与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敌人的虚荣的嘈杂、鲁莽、无思(thoughtlessness)、廉价彻底决裂。它要求我们蕴含在把公认的见解仅仅视作意见,或把一般的意见视为至少和最奇怪的、最不流行的意见一样可能错误的极端的意见(的行为)中的那种大胆。自由教育是破除庸俗的解放。希腊人用一个美丽的词来表达“庸俗”;他们把它称作apeirokalia(粗鄙,粗俗),对美好的事物的经验的匮乏。自由教育为我们提供对美好事物的经验。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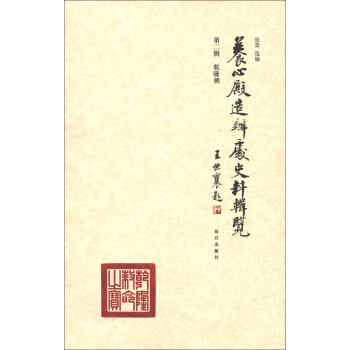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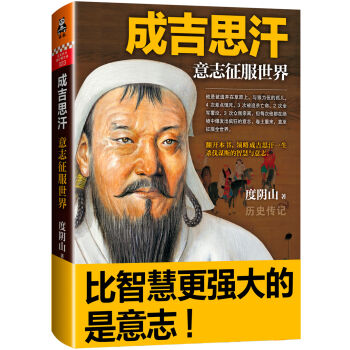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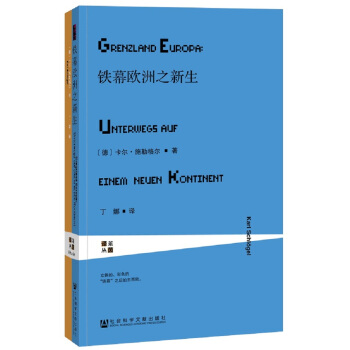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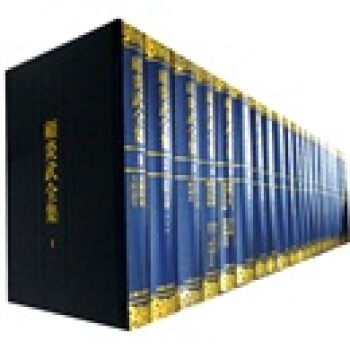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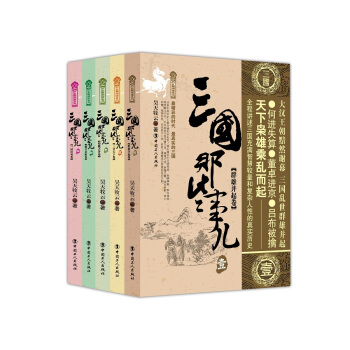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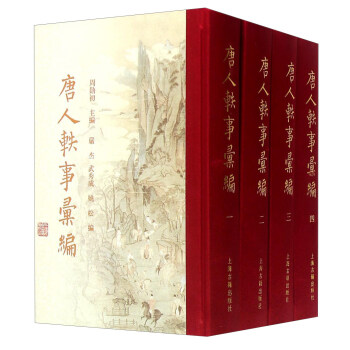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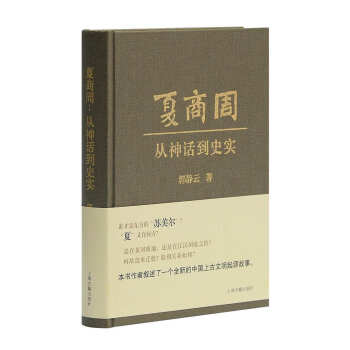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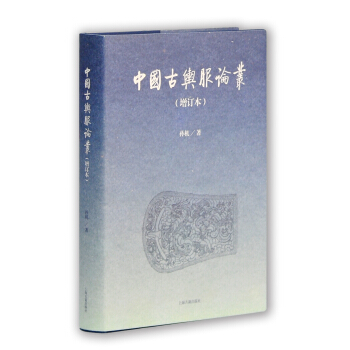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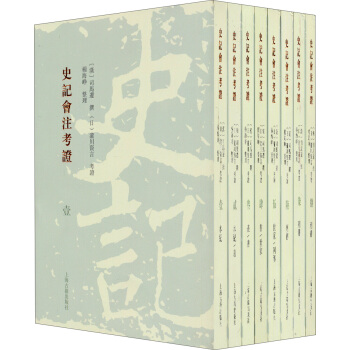
![军阀之国1911-1930 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中国军阀影像集(套装共2册) [Warlords of China 1911-1930]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41491/567a586eNc279b16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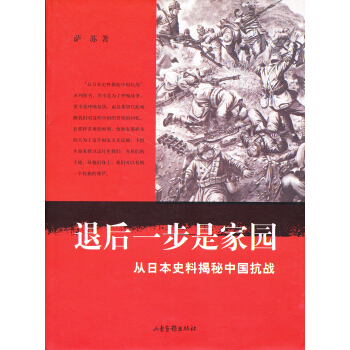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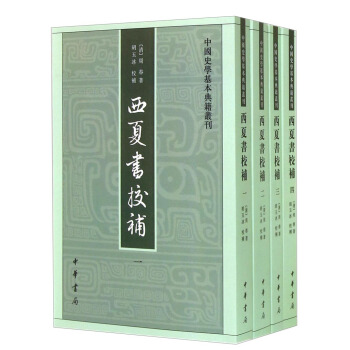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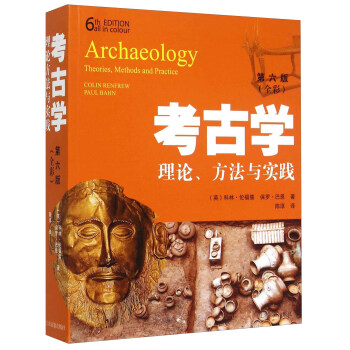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48213/rBEQWFNYfTMIAAAAAAKfK3-V3MIAAFX7gPCe4QAAp9D86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