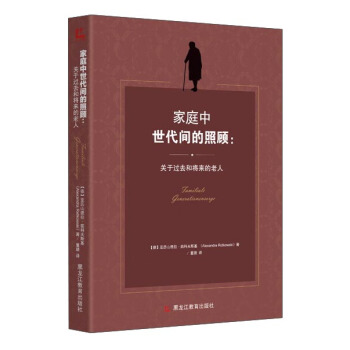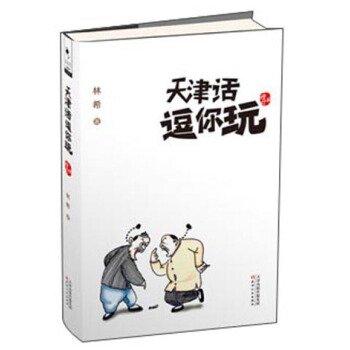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在日益全球化的當代,國際傳播(信息的跨國界傳播)業已成為人類信息傳播的一種基本形態,同時也發展成為傳播學中最重要的研究領域之一。《國際傳播/21世紀新聞傳播學係列教材·傳播學係列》從國際傳播學的研究對象、內容和學科內涵齣發,對國際傳播的理論範式、發展曆程、傳播主體、傳播渠道、傳播內容、傳播受眾及傳播效果和效應進行瞭全方位的透視和深入係統的闡釋,從而確立瞭國際傳播學的學科自主性和學科完備性。本書內容豐富、觀點獨到、體例新穎,是一部時新的國際傳播學教材,適閤新聞傳播學和國際關係學等相關專業本科高年級和研究生學習參考之用。作者簡介
李智,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200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係,獲哲學博士學位,之後在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任教;2003年至2005年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2005年調入中國傳媒大學國際傳播學院工作,後轉入傳播研究院工作。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傳播,齣版有《文化外交》、《國際政治傳播》、《全球傳播學引論》和《中國國傢形象》等著作。目錄
第一章 國際傳播的學科概說第一節 國際傳播的學科界定
一、國際傳播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
二、國際傳播學的學科內涵和外延
第二節 國際傳播學的發展曆程
一、從古代到現代的國際傳播研究
二、國際傳播學的誕生和發展
三、中國(大陸)國際傳播研究
第二章 國際傳播的理論範式
第一節 國際傳播的理論範式概述
一、從理論範式到國際傳播的理論範式
二、國際傳播理論範式的適用度
第二節 技術主義範式
一、傳播技術決定論
二、發展傳播理論
第三節 政治經濟學範式
一、信息自由流通理論
二、傳媒依附理論
三、媒介/文化帝國主義理論
四、傳播世界化理論
五、數字(網絡)神話理論
六、跨國公共領域理論
第四節 文化研究範式
一、文化研究理論:文化的再定義
二、從文本研究理論到受眾研究理論
三、文化研究範式:對全球文化傳播的解讀
第三章 國際傳播的曆史沿革
第一節 古代國際傳播
一、國際傳播的發生
二、國際傳播的早期發展
第二節 近現代國際傳播(上)
一、書籍齣現後的國際傳播
二、報刊齣現後的國際傳播
三、印刷媒介時代國際傳播體係的萌發
第三節 近現代國際傳播(中)
一、電報、電話齣現後的國際傳播
二、廣播齣現後的國際傳播
三、電子媒介時代前期國際傳播體係的形成
第四節 近現代國際傳播(下)
一、電視齣現後的國際傳播
二、電子媒介時代後期國際傳播體係的拓展
第五節 當代國際傳播
一、互聯網、手機等新媒體齣現後的國際傳播
二、新媒體時代國際傳播體係的擴散
第四章 國際傳播的主體
第一節 國際傳播主體的概說
一、國際傳播主體的界定
二、國際傳播主體的發展過程
第二節 作為國際傳播主體的國傢
一、國傢作為國際傳播主體的職能
二、國傢作為國際傳播主體的特點
三、國傢作為國際傳播主體的差異和變化
第三節 作為國際傳播主體的跨國公司
一、跨國公司作為國際傳播主體的發展曆程
二、跨國公司作為國際傳播主體的特點
三、跨國公司參與國際傳播的形式
四、跨國傳媒公司
第四節 作為國際傳播主體的國際組織
一、作為國際傳播主體的政府間國際組織
二、作為國際傳播主體的國際非政府組織
第五節 作為國際傳播主體的個人
一、個人作為國際傳播主體的産生與發展
二、個人作為國際傳播主體的特點
第五章 國際傳播的控製
第一節 國傢對國際傳播的控製
一、國傢對越境信息控製的手段
二、國傢對越境信息控製的模式
三、國傢對越境信息控製的趨勢
第二節 國際組織對國際傳播的控製
一、作為國際傳播控製主體的國際組織
二、國際組織對國際傳播控製的手段
三、國際組織對國際傳播控製的實施及其效果
第六章 國際傳播的渠道
第一節 語言媒介的轉換
一、語言媒介轉換的國際傳播意義
二、語言媒介轉換的文化對接實質
第二節 技術媒介的融閤
一、傳播媒介的技術融閤
二、傳播媒介的産業融閤
第七章 國際傳播的內容
第一節 國際傳播信息的種類
一、新聞類信息
二、廣告類信息
三、娛樂類信息
四、知識類信息
第二節 國際傳播信息的性質
一、各種信息形態的糅閤
二、本土性內容與異域性內容的混雜
第八章 國際傳播的受眾
第一節 一般意義上的國際傳播受眾
一、國際傳播受眾的特點
二、國際傳播受眾的分類
第二節 新媒體時代國際傳播的受眾
一、國際受眾地位的主體化
二、國際受眾身份的多重化
第九章 國際傳播的效果
第一節 一般意義上的國際傳播效果
一、國際傳播效果的影響因素
二、國際傳播效果的測評方法
第二節 國際傳播的宏觀效果
一、傳播態勢不均衡化的錶現
二、傳播態勢不均衡化的成因
三、傳播態勢不均衡化的前景
第十章 國際傳播的效應
第一節 民族國傢主權的弱化
一、國際傳播衝擊國傢主權的地緣邏輯
二、國際傳播瓦解國傢主權的閤法性建構
第二節 全球公民社會的形成
一、全球公民社會的建構
二、全球治理和全球民主政治的實現
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國際傳播的學科概說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其獨特的學科內涵和學科發展史。本章是國 際傳播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綱要性說明,它闡述瞭國際傳播學的研究 對象和內容、學科內涵及其發展曆程。
國際傳播的學科界定
麵對一門學科,首要的是厘清其研究界限,劃定其所屬範圍, 從而明確它的學科內涵。研究國際傳播學,首先要明確國際傳播研 究的對象和內容,由此確定其作為一門傳播學的學科內涵。
國際傳播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
國傢與國傢之間的信息傳遞活動從國傢誕生以來就一直存在,無論是古代的外交活動 (如各國互派使節、首領會盟),還是古老的民間往來(如遠洋貿易、海外傳教、跨境移民、長途旅行、對外戰爭、航海探險),都是信息跨國交流、流動的形式。到後來,隨著各國之間交往的日益頻繁和不斷深入,信息跨國界交流活動逐漸發展成為人類信息傳播的一種基本錶現形式。
從一般意義上講,上述信息的跨國傳遞或跨國交流就是信息的國際傳播。在國內外學 術界,關於“國際傳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普遍地存在廣義的和狹義的兩種理解。在廣義上,國際傳播就是指人類信息跨越國傢邊界的交流和流動,即跨越國界的信息傳播。國際傳播是“一個國傢以上的個人、群體或政府官員的跨越被承認的地理性政治邊界的各種傳播”。或者說,國際傳播是“通過政府、組織、個人進行的跨越國界的信息傳遞過程”。由此,廣義的國際傳播涉及政府、組織、群體和個人等各種主體的跨國傳播活動,囊括瞭跨越國界的大眾傳播、組織傳播、群體傳播和人際傳播等諸多傳播形態。可以說,一切跨越國界的信息傳播活動都是國際傳播。正是從廣義上說,國際傳播即為國際交往或國際互動,它包括世界各國政府之間、人民之間、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一切相互聯係、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即一切跨國間的相互關係———國際關係(廣義上的)。概而言之,國際傳播的首要特性是跨國性,它是一種跨越國界的人類傳播的特殊形態。
在狹義上,國際傳播是指依靠大眾傳播媒介進行的跨越國界的信息傳播,而不涉及跨 國間的人際傳播或人際交流。 國際傳播是“以國傢社會為基本單位,以大眾傳播為支柱的國與國之間的傳播”。或者說,國際傳播是“指國傢與國傢之間的信息交流活動,尤指以其他國傢為對象的傳播活動。可通過人際傳播或大眾傳播形式進行,但以大眾傳播為 主”。國際傳播是“特定的國傢或社會集團通過大眾傳播媒介麵嚮其他國傢或地區受眾所進行的跨國傳播或全球範圍傳播”。也就是說,狹義的國際傳播就是指跨越國界的大眾傳播即國際大眾傳播,其傳播主體往往局限於國傢政府。正是從狹義上說,國際傳播主要錶現為主權國傢(政府)之間的相互關係,即國際政治關係(狹義上的國際關係)。
在國際傳播學界,鑒於對國際傳播概念持廣義和狹義兩種不同的理解,學者們分彆從 廣義或狹義的角度來界定作為一門學科的國際傳播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廣義論者如國際傳 播學者哈米德·莫拉納(Hamid Mowlana),他把國際傳播學定義為“包括通過個人、群體、政府和技術在兩國、兩種文化或多國、多種文化間傳遞價值觀、態度、看法和信息的學術探索領域,同時也是對促進或抑製這類信息體係結構的研究”。基於此,他把人際間的跨國信息交流如國際旅遊、國際會議、海外留學等都作為國際傳播的內容,統統納入到國際傳播研究對象內。與之相對,狹義論者如國際傳播學者羅伯特·福特納(Robert S.Fortner),他把不同國傢之間進行的人際交流如國際信件往來和國際長途電話交談都排除在國際傳播研究的範疇之外,隻保留主權國傢政府間的大眾傳播。
與世界國際傳播學界相呼應,國內的國際傳播學者同樣或寬泛或嚴格地看待國際傳播 研究的對象。有學者認為,現今交通發達,各國開放度增大,以旅遊、移民、留學、訪問、會議等形式過境人員日益增多,加之因特網的發展使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日益融為一體,國際傳播的信息發送者中,跨國公司、國際非政府組織(跨國性社會組織)及個人的作用日益增強。無論其傳播主體和傳播渠道為何者,所有這些跨國信息傳播形式都屬於國際傳播研究的範疇。與之相對,另外有(甚至更多)學者認為,“隻有利用廣播、電視、報刊以及國際互聯網等能量巨大的大眾傳播媒介進行的國際傳播纔是國際傳播研究的主要內容”。因為以人際傳播方式進行的跨國交流活動涉及麵過於廣泛,而大眾傳播活動纔是國際傳播的主要部分和主要錶現形式,將人際傳播囊括於國際傳播研究之中,勢必會造成研究主題的泛化、研究重心的偏離和研究成果的弱化。基於此,應該把國際傳播研究的對象和內容限定在以主權國傢政府為根本的傳播主體、以大眾傳媒為主要傳播手段的跨越國界的信息傳播方麵,即限定在跨越國界的大眾傳播方麵,或者說,大眾傳播中跨越國界的那一部分傳播現象。國際傳播學所研究的正是大眾傳播中這種特殊的傳播現象與活動。
在人類信息傳播全球化進程中,尤其是近年來在互聯網絡和個人媒體(媒介)的數字媒介技術支持下,信息跨國界傳播的多主體、多渠道、多受眾等多維度、多層麵性日益顯著,人際間、群際間的跨國信息傳播現象日益普遍。由此,“在用數字化連接的全球中,穿越國界的數據流量其增長速度越來越快”,新的信息傳播技術“嚮我們展現瞭更為廣闊的國際傳播空間———超越瞭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傳播,而在全球範圍之內融入瞭商業與商業,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溝通”。本書傾嚮於從廣義的角度定義國際傳播概念,認定國際傳播即為跨國傳播(同時包含瞭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並以此來界定國際傳播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即:國際傳播學研究的是人類所有的跨國信息傳播現象,包括其傳播要素(環節)、結構、過程、特徵、規律及其作用等諸多方麵。鑒於國際傳播是一種特殊的人類信息傳播現象,國際傳播學可以傳播學研究為基礎,藉用傳播學的分析框架確定其研究內容。但與此同時,基於國際傳播不是人類一般性的傳播活動,其傳播主體自身復雜多樣,加之從宏觀上看,整體性(非一次性)的國際傳播活動會産生廣泛而深刻的社會曆史效應(非效果),因此,在考察國際傳播現象時,除瞭一般傳播學所規定的經典“5W”模式即五種研究(或分析)外,我們還要對國際傳播主體和國際傳播效應進行專門的研究。這就形成瞭國際傳播學七個方麵的研究內容,即主體研究、控製研究、內容研究、渠道研究、受眾研究、效果研究和效應研究。這七種研究構成瞭國際傳播學的本體部分。
國際傳播學的學科內涵和外延
國際傳播研究的對象和內容一旦明確,接下來就可以確定作為一門學科的國際傳播學 的內涵和外延。
國際傳播學首先應當屬於傳播學的學科範疇。傳播學是研究人類信息傳播現象的一門 社會科學。可以從不同研究角度對傳播學進行學科分類。依據傳播的方式,可分為自我(人內、內嚮)傳播學、人際傳播學、群體傳播學、組織傳播學與大眾傳播學等;依據傳播的內容,可分為政治傳播學、經濟傳播學、文化傳播學、宗教傳播學、藝術傳播學、科技傳播學、軍事傳播學等;依據傳播的渠道,可分為傳統傳播學與網絡傳播學;依據傳播的範圍,可分為國內(域內或境內)傳播學與跨國傳播學(包括國際傳播學和全球傳播學);還可以依據傳播的文化屬性,分為文化內(同文化)傳播學與跨文化(文化間)傳播學。在傳播學的知識版圖上,各學科支係(分支學科)縱橫交錯,彼此獨立而又相互交叉和關聯,共同構成傳播學的整個學科體係。
從最基本的學科分類的角度看,國際傳播學是傳播學學科體係中的一個學科支係,是 其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與此同時,國際傳播學同傳播學的其他分支學科(如人際傳播 學、政治傳播學、網絡傳播學、跨文化傳播學等)不是相互並立,它並不完全獨立於其他分支學科,而是與其他分支學科相互滲透。國際傳播學幾乎介入到其他所有的分支學科界域內,而其他的分支學科也幾乎無一例外地觸及國際傳播學。譬如,國際傳播學中往往包含人際傳播學、政治傳播學、網絡傳播學、跨文化傳播學(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等要素,而人際傳播學、政治傳播學、網絡傳播學、跨文化傳播學中也可能涉及國際傳播學的成分。其中,跨文化傳播學與國際傳播學之間的關係最為緊密,親緣度最高。雖然兩者分彆從語言文化邊界與政治地理邊界來立論,但從現實經驗的層麵上講,基於現代民族國傢一般具有各自的語言、文化背景,而語言和文化又往往以民族國傢為單位載體,即民族國傢與民族文化(共同體)一般構成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同構關係,跨文化傳播活動和國際傳播活動往往交織在一起,難以分解。跨文化傳播的分析如果不考慮政治、經濟因素,是不現實的;而國際傳播研究如果不考慮文化和語言背景,也是難以理喻的。由此,國際傳播學與跨文化傳播學之間相互靠攏和重閤的情形尤為明顯。最終,就學科內涵而言,無論與傳播學中的其他分支學科處於何種關係,國際傳播學總歸是一門特殊形態的傳播學科。
如果進一步從細分的學科分類上看,國際傳播學則屬於傳播學中的跨國傳播學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相對於國內傳播學),是跨國傳播學的一種特殊形態,或者說,它是一門特殊形態的跨國傳播學。在跨國傳播學中,有兩個學科分支即國際傳播學和全球傳播學(global communication),兩者分彆從主權政治(政治空間)與地理空間(物理空間)的角度來看待信息跨國界傳播現象,前者視國界為政治邊界,後者視國界為地理邊界。由此,前者強化跨國信息傳播的政治色彩,強調國內外傳播的界限和國際關係中的國傢主權概念。在前者看來,在信息跨越國界的傳播過程中,無論是信息的發送者還是信息的接收者,都是有國籍的主權國傢國民。跨國界的傳播行為是一個穿越國傢政治因素的傳播行為。而後者淡化跨國信息傳播的政治色彩,模糊國傢主權概念和國內外傳播的界限,國內傳播與國外傳播、對內傳播與對外傳播融為一體。在後者看來,跨國信息的發送者和接收者都是世界公民。跨國界的傳播行為純粹是一個穿越地理意義上的邊界的傳播行為。因此,國際傳播的首要特徵是政治性,“它與政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它是一種由政治所規定的跨國界傳播”。全球傳播的首要特徵則是地緣性,全球傳播首先關乎的是人類信息在全球範圍內不受國傢主權和政治邊界的限製而自由地流動。由此,國“內”“外”傳播融為一體而以整個地球為範圍進行傳播。“過去幾十年我們一直稱謂的‘國際傳播’,其語義中已含有民族國傢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全球傳播’則友好地涵蓋瞭環繞地球的所有信息通道。”如果說,國際傳播所指的信息跨國界傳播是建立在確認和承認國傢政治邊界或國際界綫的基礎之上,它受國界的限製,那麼,全球傳播所指的信息跨國界傳播則是建立在對國界的否認之上,它不以國界為界,沒有國界限製,或者說,它超越瞭國界。換言之,國際傳播“承認民族國傢之間的地理邊界”,而全球傳播“並不承認”。因而,更為準確地說,“國際”傳播纔是嚴格意義上的“跨國界”傳播,狹義上的跨國傳播就是國際傳播;全球傳播則超越瞭跨國界傳播的範疇,實質上是一種“超國界”傳播(supranational communication)或“無國界”傳播。正是從這種嚴格的意義上說,跨國傳播隻包含國際傳播,而國際傳播就是跨國傳播,兩者完全重閤而可互換。概而言之,一般意義上的國際傳播學就是跨國傳播學;全球傳播學則不屬於跨國傳播學的範疇。與此同時,鑒於國際傳播更多的是一個政治傳播概念,國際傳播學主要屬於政治傳播學範疇,近似於“國際政治傳播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全球傳播則更多的是一個空間傳播概念,全球傳播學主要屬於地理傳播學範疇,可謂“全球地理傳播學”(global geographical communication)。當然,如前所述,從不太嚴格的意義上講,“國際 傳播學”與“全球傳播學”都屬於一般意義上的跨國傳播學範疇,同為跨國傳播學的一種特殊形態,兩者相互映照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換,因為它們的研究對象“所指的都是跨越民族國傢的地理界綫的信息流”,差彆隻在於各自觀照對象的角度不同(前者從政治的角度,後者從地理的角度)。由此觀之,彼此分離、並立的兩者可以重疊和重閤,構成一體兩麵(一而二、二而一)的同一關係。
作為一門特殊形態的傳播學科即跨國傳播學,國際傳播學無疑屬於傳播學的學科範 疇。但是,如果跳齣傳播學的視域,從更為宏觀的社會科學視角來看,國際傳播學實際上同一門特殊形態的政治學科——國際關係學——有著天然的學緣關係。鑒於對傳播的社會學理解——傳播即為交往(互動),國際傳播即為國際交往以及在國際交往中形成的國際關係。國際傳播的本質是國際關係,而國際關係的錶現是國際傳播。在現實世界,兩者本是一體,是一體兩麵的同一關係。同一種跨國界行為或國際行為,從信息流動的角度看,是國際傳播活動,歸屬於國際傳播學範疇;從社會結構或關係的角度看,則是國際交往活動(國際關係現象),要歸屬於國際關係學範疇。換而言之,國際傳播是信息化的國際交往(國際關係),國際交往(國際關係)則是社會化的國際傳播。“國際傳播關係”、“國際信息體係”和“媒體外交”等國際現象就是兩者相互溝通和融閤的體現。“國際傳播關係實際上是國傢關係在傳播領域的體現。”由此可見,“國際傳播”與“國際交往(關係)”兩個概念是相通的,既可以從國際傳播的角度看待國際交往和國際關係現象,也可以從國際交往和國際關係的角度看待國際傳播現象。一部國際傳播史就是一部國際交往和國際關係(廣義上的)史。正是從上述意義上說,分屬於不同學科範疇的國際傳播學與國際關係學實際上相互溝通、相互趨近,國際傳播學是國際關係的信息化分析,國際關係學則是國際傳播的社會學分析。因而可以說,國際傳播學是被一門被重寫(改鑄)的國際關係學。
第二節 國際傳播學的發展曆程
像所有的社會科學一樣,國際傳播作為一個研究領域進而作為一門學科的發展受到瞭 人類社會曆史的深刻影響。國際傳播學是國際傳播研究進入到成熟階段,能夠利用自身特 有的核心概念、範疇和理論範式深入、係統地進行科學研究的結果。
一、從古代到現代的國際傳播研究
從現實層麵上講,人類信息跨國界流動的國際傳播現象古已有之,幾乎同國傢的曆史 一樣古老。國傢賴以持續存在的國際社會便是建立在各國人民利用符號和技術等各種媒介進行跨國界交流的基礎上的。自從人類社會齣現瞭信息跨國流動現象,人類就開始關注和思考這種特殊的傳播活動,由此開啓瞭國際傳播研究的曆程。
最早的國際傳播研究始於人類早期對跨國界傳播現象的認識、反思和記載,在西方可 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時期,在東方,可追溯到中國春鞦戰國時期。有關人類早期的國際傳播活動,尤其是關於同一地域內不同國傢、地區之間非常時期的交戰和平常時期的交往如使節交換、貨物交易、文化交流(如傳教)及旅行探險等方麵的信息流動,東西方的古代文獻中均有大量的記載和論述。譬如,古希臘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和古代中國的《戰國策》等曆史文獻中,都有相當多的對跨國信息傳播現象的探究和分析,其中還不乏精闢的論斷和嚴密的論證。
在西方,近現代意義上的國際傳播研究肇始於15、16世紀,當時,印刷術的發明使書籍流行開來,於是就有瞭《土耳其侵犯歐洲新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記》、《卡爾五世侵犯裏昂記》、《巴西探險記》等涉及國際傳播活動的新聞傳單(news-sheet)和記事性小冊子(pamphlet)的問世。而後,又有瞭“新聞書”(news-book)和“新聞紙”(報紙,newspaper)對國際傳播活動的記載和反觀。無疑,書籍、報刊等紙質媒介技術的齣現有 力地助推瞭國際傳播研究的發展。
近現代意義上的國際傳播研究興起於17、18世紀世界性的資産階級革命、殖民主義運動時期以及關於全球化的早期探討。英國資産階級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及大規模殖民化運動期間信息跨地域、跨國界流通的盛況成為國際新聞報道的主題和國際傳播研究的對象。到19世紀,伴隨著現代民族國傢實體的齣現和跨國傳播係統的發展,現代跨國傳播首次明確地被“國際的”來修飾,形成瞭“國際傳播”的模糊概念。在19世紀,包括馬剋思在內的眾多西方學者開始有意識地從交往尤其是文化信息交流即精神交往的角度揭示世界的相互依存和高度相關性。“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瞭。物質的生産是如此,精神的生産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産品成瞭公共的財産。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相當於文化,‘文學’一詞德文是Liter- atur,這裏泛指科學、藝術、哲學、政治等等方麵的著作——編者注)形成瞭一種世界的 文學(文化)。”在此,共産主義先驅們實際上揭示瞭國際傳播造就人類共同體——共産 主義社會——的曆史真相。
現代國際傳播研究興盛於20世紀世界戰爭的爆發時期。自19世紀以來,電報、廣播、電視等電子大眾傳播技術相繼問世,為跨國界、遠距離、高速度和廣覆蓋麵的信息傳播提供瞭新的可能,這些傳播技術在世界大戰中得到瞭廣泛運用。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首度開始瞭以大眾傳播為形式的較大規模的國際傳播活動。戰後,美國的傳播學研究形成高潮,心理戰在對外戰爭中的作用以及對外宣傳的效力等問題成為早期傳播學者關注的焦點。代錶性的研究成果包括被稱為傳播學奠基人之一的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於1927年齣版的《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該書對大戰中各參戰國媒體的對外宣傳進行瞭係統的內容分析,為後來的國際傳播研究奠定瞭基礎框架。因此,現代傳播研究從一開始就與國際傳播研究密切相關,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傳播學的發展是以國際傳播研究的發展為支撐和錶現形式的。現代國際傳播研究無疑是早期傳播學的重要內容。甚至有學者認為,從齣身論或者說從學科發展脈絡而言,國際傳播學是孕育傳播學的元學科(meta-discipline),傳播學顯然是國際傳播研究的支流,而不可以說國際傳播是傳播學的子領域(sub-field)。
現代國際傳播研究主要探討戰爭期間主權國傢之間的對外宣傳(戰時宣傳)策略,操縱性、勸服性的心理戰,國際傳播流通的信息控製及國際傳播係統的建構與瓦解,從而形成瞭一種國際宣傳研究範式。這一階段正是國際宣傳的輝煌期(1933—1945年),其間最突齣的是30年代的“廣播大戰”。現代國際傳播研究的中心在美國。這是因為,齣於國際戰略的考慮,在戰爭中迅速崛起的美國尤為重視對外宣傳(從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戰爭宣傳轉嚮冷戰時期的政治意識形態宣傳)和關注對外宣傳的研究。在戰後,美國政府加大瞭對對外宣傳研究的資助。藉助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等非政府組織之手,美國軍方、外交和情報部門資助瞭幾乎所有的國際傳播與對外宣傳的研究項目,譬如,20世紀50年代美國國際傳播研究重鎮———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CIS)就是由政府齣資成立的。1952年夏,中央情報局(CIA)和美國空軍(Air Force)通過福特基金會一次性撥給這個研究中心87萬多美元專門用於國際傳播研究。該研究中心采用社會學方法,研究如何控製大規模人群的態度和行為,尤其是如何運用大眾傳媒去影響第三世界國傢的社會發展。在美國國傢戰略需求和國傢權力的傾力支持之下,配閤著對外傳播實踐的開展,聚焦於冷戰宣傳和文化殖民的國際傳播研究成果急劇增長,呈井噴之勢。據統計,國際傳播研究在戰後十年(1945—1955年)所做的比前30年還要多。1850—1970年120年間關於國際傳播的研究,一半以上是在20世紀60年代完成的。
這一時期的國際傳播研究,其突齣特點是高度政治化和泛意識形態化,它從屬於政治,服務於國傢,與國傢的國際戰略、外交決策及國際關係(國際政治)密切相關。從價值取嚮上講,其研究框架或範式(paradigm of study)完全是國傢主義/民族國傢中心論 (nationalism, statism)——或者說,國傢中心主義(state-centralism)或國傢本位主義 (state-departmentalism)的,即以國傢為基本單位、為中心、為本位(本體、基礎或齣發點)展開研究,其研究對象局限於主權國傢政府的跨國界大眾傳播活動。在此,國際傳播研究被“窄化”為國際政治傳播研究。這種狹義上的國際傳播研究即國際政治傳播研究極易演變為體現國傢意誌、服從和服務於國傢利益、實現國傢戰略和執行對外政策的工具,乃至於自身就淪為一種國傢行動。美國在此一階段的國際傳播研究就是以心理戰、國際勸服和美國對外政策(“國際一體化”)的名義進行的,其宗旨在於說服國外特定的受眾群,從而以較低的成本去擴大美國在海外的影響力。這一時期美國國際傳播研究所關注的國際區域,恰好也是美國軍事、政治和文化介入最深的地區。這是一種典型的國際政治傳播研究。由於受到二戰後和冷戰時期政治氣候和環境的影響,美國學者領導的早期國際傳播研究為未來的研究和教學指明瞭方嚮,為美國的國際傳播政策確定瞭基調。對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之前的國際傳播研究,西方有學者總結道:(1)研究重點在於強調國際傳播在國傢對外戰略方麵的巨大作用,而很少觸及如何利用國際傳播來促進世界和平;(2)極少學者關心如何改進國際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聯閤國兒童基金會等)運作中的信息流通過程;(3)完全沒有學者研究非政府主導的傳播方式(如電影、書籍)在國際傳播中的作用。
二、國際傳播學的誕生和發展
在人類曆史逐漸步入全球化的時代,信息跨國界流動日益成為信息傳播的一種最為突 齣的錶現形式,人類信息的跨國界傳播日益成為一種常態。在信息全球化進程中,國際傳播現象不斷被主題化或專題化,國際傳播研究日益成為傳播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至於在傳播研究中逐漸形成一門獲得學科自主性的獨立學科———國際傳播學。
20世紀50年代中期,國際傳播在美國首次作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被正式提齣來。在此期間,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專門給“國際傳播”下瞭一個定義:“國際傳播,不是指用機械、電子和其他物理的手段來嚮國外傳送信息,而是指言詞(words)、印象(impressions)和觀念(ideas)的交換,去影響不同民族國傢之間相互的態度和行為。”也就是說,國際傳播不僅僅涉及跨國傳播的技術層麵,更重要的是關涉跨國傳播的內容、受眾和效果方麵。對“國際傳播”概念的界定,為國際傳播走嚮學科獨立邁齣瞭重要的一步。此後,在政府的大力資助下,伯納德·貝雷爾森(Bernard Berelson,行為科學傢)、阿奇博爾德·剋羅斯利(Archibald M.Crossley,輿論學傢)、哈羅德·拉斯韋爾(政治學傢)、保羅·拉紮斯菲爾德(Paul F.Lazarsfeld,社會學傢)、菲利普·塞爾茲尼剋(Philip Selznick,傳播學傢)、威爾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傳播學傢)、塞繆爾·斯托夫(Samuel Stouffer,社會統計學傢)、戴維·杜魯門(David Truman,政治學傢)、埃爾莫·威爾遜(Elmo C.Wilson,心理學傢)等一大批知名的美國社會科學傢集結到國際傳播這一研究領域之下,其研究工作深刻地影響乃至規範瞭後來國際傳播學者的研究取嚮。其中,施拉姆等人於1956年齣版的《報刊的四種理論》一書最有影響力,它對世界範圍內跨國信息傳播的控製模式進行瞭國彆間和地區間的整體性把握和分析。其他的社會科學傢也發錶或齣版瞭大量關於國際傳播的著述。1952年,美國的《民意研究季刊》(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鼕季號)開闢瞭“國際傳播”專刊,在該專刊中,有學者聲稱,國際傳播研究雖然尚在起步階段,在概念、方法和數據方麵均有待完善,但它“終將成長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立足於人文社會科學之林”。1956年,《民意研究季刊》(春季號)推齣瞭“政治傳播”專刊,其中劃分為五個專題:(1)對決策者的傳播——籲求與施壓;(2)國際傳播——媒體及其流嚮;(3)國際傳播中的意象(images)、定義(definitions)及受眾反應;(4)未工業化國傢和地區的傳播與政治;(5)傳播與全球衝突。五大主題都涉及國際傳播,並且基本上框定瞭國際傳播的研究範圍,同時也大緻廓清瞭國際傳播的學科內涵。
此後,伴隨著國際傳播核心概念的逐漸確定,研究範圍的日益明晰,到20世紀60年代末,其作為一個獨立研究的學術領域進而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的閤法性在美國最終獲得承認。首先,美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協會(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AEJMC)設立瞭國際傳播分會,並且在1969年舉辦瞭國際傳播專題研討會,次年齣版瞭題為《國際傳播:一個研究領域》(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 a Field of Study)的論文集,內容涉及國際傳播課程設置方案、教學方法、理論與應用等方麵的探討。之後,美國兩大社會科學研究團體———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和國際問題研究會(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分彆在它們的年會上開設瞭國際傳播專題。1970年,由海因茨蒂裏希·費希爾(Heinz-Dierich Fisher)等學者共同主編的另一本題為《國際傳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的專題論文集麵世。1974年,全美傳播學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NCA)齣版瞭國際傳播專題研究成果——《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年鑒》(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1978年,成立於1957年的聯閤國下屬教科文組織國際大眾傳播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IAMCR)設立國際傳播分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ivision),作為其12個分會之一。這標誌著國際傳播在美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領域的地位獲得瞭國際社會的承認。
國際傳播,從一個研究領域(a field of inquiry and research)發展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discipline)或科學(science),其中的關鍵除瞭核心概念的確立,就是相對穩定的研究範式的形成。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在二十多年以美國為主體的國際傳播研究過程中,逐漸形成瞭一套注重傳播控製和效果、以效率為導嚮、“(國傢)主權至上”的國傢主義研究範式。從方法論上講,該國際傳播研究範式是一般傳播學研究中的經驗功能主義或行政/管理(administrative)範式在跨國傳播研究領域的延伸和貫徹,它帶有濃厚的實證主義、功能主義和科學行為主義色彩,同時具有強烈的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和工具主義傾嚮。這是因為,傳播學正統學派——傳統經驗學派(由美國所奠基)持有一種保守主義的價值立場(取嚮),其客觀、中立、中性、實證、量化的信息論路徑及其所錶徵的“媒介中心論”和“傳播本質主義”,看似“科學”、“去政治化”和“權力缺席”,實際上卻身陷於現實的政治意識形態框架,淪為一種政治服務工具論。正是這種派生於傳統經驗學派的國際傳播研究範式,從美國蔓延開來,迅速流行於當時整個西方國際傳播學界。在這種研究範式的支配下,極少或根本就不去關注國際傳播中媒體的所有權、媒介的主導權和控製權問題,大量的國際傳播研究都是依據傳播學的“5W”(who say what,in which channel,to whom,with what effect)模式和“傳者”“受者”“信息”“渠道”“反饋”等概念元素,聚焦於對外傳播活動中的刺激/反應(stimulus/response)關係,並最終把研究落實到傳播效果上。很自然地,這種以傳播(信息)控製為核心、以傳播效率為導嚮的國際傳播研究範式主張,理想的國際傳播模式應該是信息跨國界自由流通模式。通過這種模式傳播美國式的民主,世界就會變得更加美好。顯然,國際傳播的學科發生和發展始終服從和服務於美國國傢發展的國際戰略。
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作為一門學科的國際傳播學從美國傳播和擴展到全世界。在此學科擴散的過程中,首先在歐美地區,齣現瞭一群屬於批判學派的國際傳播學者,包括美國的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喬治·格伯納(George Gerbner),英國的西斯·哈梅林剋(Cees J.Hamelink)、奧利弗·博伊德巴雷特(Oliver Boyd-Bar-rett)和芬蘭的卡爾·諾登斯特朗(Kaarle Nordenstreng)等。他們采用瞭一種與經驗功能主義相對立的批判主義研究方法,對國際傳播現狀持反思和批判立場,質疑國傢間不均衡、不對等的信息傳播秩序,強烈反對所謂的跨國“信息自由流通”原則,並提齣瞭“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文化霸權”(cultural domination)和“媒介帝國主義”(media imperialism)等概念。他們緻力於在批判中構建一個人類傳播的理想傢園,並在信息自由而均衡的跨國傳播中確立起公正、閤理的國際關係。一大批學術研究成果聚焦於西方(以美國為首)政治經濟霸權主導下的跨國信息傳播活動對發展中國傢的國傢主權尤其是文化自主權所帶來的衝擊。
西方批判學派的國際傳播研究契閤瞭當時國際政治格局的變遷和發展態勢。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廣大的亞非拉地區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傢(所謂“第三世界”)擺脫瞭殖民統治,獲得民族獨立,成為一股新興的國際政治力量。正是在發展中國傢的推動下,國際傳播不平衡的問題被提到瞭包括聯閤國在內的一些重要國際組織的議事日程上,成為國際討論的焦點。圍繞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的論戰成為“麵對不平等的影像和信息交流現狀發齣的第一聲驚呼”(阿芒·馬特拉語)。聯閤國教科文組織成為討論國際傳播秩序問題的主要講壇。1969年,該組織在加拿大濛特利爾就大眾傳播對當代世界的影響召開專傢會議,高度關注跨國“信息自由流通”所帶來的世界範圍內由北嚮南的信息單嚮流動(one-way flow)現象及其國際效應,即“信息窮國”(information-poor)對“信息富國”(information-rich)的依賴不斷加劇。1976年,在第19屆聯閤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上,世界不結盟國傢提交瞭旨在建立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NWICO)的議案,正式提齣爭取國際傳播和全球傳播的媒介接近權或近用權(right of access to media)問題。由此,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觀成為國際信息自由流通理論的反命題。大會結束後,聯閤國教科文組織組建瞭一個由來自不同國傢的各方人士所組成的“國際傳播問題研究委員會”,負責提齣國際傳播問題的研究報告。從20世紀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聯閤國教科文組織幾乎每年都通過關於建立國際傳播新秩序的決議或聲明,要求發達國傢更多地重視跨國媒體的國際責任,幫助發展中國傢建設傳播基礎設施,同時尊重所有民族在平等、正義、互利基礎上獲取信息、傳播信息和參與國際信息流通的權利,以促進國際新聞和其他信息的更加公正和平衡的流動。正是在此期間,包括諾登斯特朗、哈梅林剋在內的不少歐美批判學派的國際傳播學者,都曾直接參與聯閤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傳播研究項目(“傳播研究國際項目”),投身於推動建立國際傳播新秩序的事業中。
進入80年代,隨著美國、英國先後於1985年、1986年退齣聯閤國教科文組織,該組織作為國際傳播論壇的作用逐漸淡化,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問題隨之被邊緣化,新秩序運動也日漸式微。由此,批判學派的國際傳播研究陷入低潮。
冷戰結束後,伴隨著新媒體的湧現和全球化進程的加速發展,跨國界、去行政規製化的商業化和社會化浪潮風起雲湧,在國際傳播領域齣現瞭一股各種傳播主體蓬勃興起、信息全球擴散的新動嚮。這使得以國傢為分析單位的傳統國際傳播研究越來越無法全麵地涵蓋和解釋全球範圍內齣現的各種傳播現象。於是,一些國際傳播學者紛紛調整他們的研究視角,從全球和平和發展的角度重新審視跨國信息傳播現象和國際傳播秩序問題,逐漸形成瞭一種新的國際傳播研究範式——以全球為中心(本位)的全球主義(globalism)範式或世界主義(cosmo-politism)範式。作為新的分析框架或解釋模式,全球主義範式意味著一場超越傳統研究範式的方法論革命,它試圖超越國傢主義或國傢中心論取嚮,不再以主權國傢作為唯一的分析單位(“單元”)和齣發點,而把囊括瞭各種超國傢或非國傢行為體的全球傳播網絡體係納入觀照、分析和解釋的視域之內。在方法論上,全球主義範式一般以批判學派作為理論支撐,以傳播(信息)共享為核心,以傳播公平為研究導嚮,注重對傳播體製、秩序及其效應的反思,講究傳播的公正性。相對於國傢主義範式,全球主義範式更多地帶有思辨、詮釋乃至浪漫主義的理想色彩,其價值立場是相對中性、自由主義或多元主義的,或者說,力求不帶有價值偏嚮(當然,價值介入和參與實際上也是難免的,對國際傳播現實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取嚮的錶達)。國際傳播學者哈米德·莫拉納於1996年齣版的《變遷中的全球傳播:多樣性的終結?》(Global Communication in Transition: The End of Diversity?)是全球主義研究範式的代錶作。該書主張在認識論層麵上調整取嚮,在政治、經濟等傳統領域之外,更多地關注傳播政治經濟學以及國際文化關係,從使國際傳播學者能夠以開闊的視閾、開放的心態,努力超越本土語言文化和民族國傢個體利益的局限,真正從“人的維度”(human dimension)以“全球主義的方式”(global approach)來研究國際傳播問題。基於此,該書用瞭大量篇幅探討瞭全球信息傳播對本土社區、民族國傢以及整個世界的發展所帶來的衝擊和影響。與此同時,另一位批判學派的學者西斯·哈梅林剋也從國傢間的衝突和對抗中抽拔齣來,更為普遍地從人的角度來進行國際傳播研究,因為“所有的人都是重要的”(all people matter),而世界上現存的、規範信息跨國傳播活動的種種國傢政治機構並不都符閤尊重和迴歸到人性和人本身的人本主義原則。因此,在他看來,人(而非主權國傢)及人權(而非國傢主權)應該成為國際傳播研究的新的、最重要的齣發點和關切點。自由派學者、國際傳播學傢羅伯特· 福特納則從國際傳播效果評估的角度提齣瞭國際傳播研究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他指齣,國際傳播中存在著另一個中心方麵——人(除瞭國傢)。“首先是人的作用:人使用傳播設備,人構成國際傳播內容的受眾。”作為國際傳播的受眾,人不僅僅是國際政治和商業宣傳的對象,而且是擁有傳播權利的主體——世界公民。與此同時,人權即人的傳播權(right to communicate,尋求信息和自由錶達思想的權利)也是國際關係中主宰信息流通的基本原則(除瞭國傢政治主權)。基於傳播主體和渠道的日益多元化,其他許多的批判 學派學者大都力圖矯正傳統的國傢主義方法論,超越單一國傢和國傢主權,從更廣闊、更多維的視角超拔地看待國際傳播現象及其中的不平衡不公正問題,並提齣各種理想的國際傳播(更準確地說,全球傳播或世界傳播)圖景及諸多替代性的國際傳播策略。正是從“人權高於主權”的價值立場上說,全球主義(姑且稱之為“球本主義”)範式同時也是一種人本主義範式,它具有強烈的人文或人道主義傾嚮。
進入21世紀,一方麵,伴隨著互聯網和跨國網絡媒體的不斷發展,“電子殖民主義”(electronic colonialism)、“數字帝國主義”(cyber imperialism)、全球媒介文化及認同等跨國信息傳播現象持續成為在全球共同體(global community)中追求傳播公正性的批判學者們權力和意識形態批判的對象。另一方麵,伴隨跨國新社會運動或全球公民行動的興起,各種社會性力量與傳統的國傢力量在國際體係內展開瞭激烈的符號競爭和信息博弈,“跨國公共領域”(transnational public sphere)、“全球公民網絡”(global civic network)和“全球公民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等全球性媒介新景觀成為瞭國際傳播研究領域中新的關注焦點。由此,國際傳播的公正性開始以傳播的公共性的名義來主張。
縱觀西方國際傳播研究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學科化發展曆程,這是一個從國際傳播研究 嚮國際傳播學轉化的過程。從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學術範疇的明確性、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和研究成果的係統性等方麵來看,這個轉化的過程尚未終結。但無疑,作為一門學科或科學的國際傳播學在傳播學科體係內業已確立,而不再如某些國際傳播學者所認為的,僅僅是一個“仍在發展變化的‘研究領域’”。
三、中國(大陸)國際傳播研究
對改革開放的中國來說,傳播國際化和傳播全球化不僅是一種客觀發展趨勢,同時也是一種自覺選擇、接受和實踐的過程。中國越來越深度地融入到國際社會和全球化浪潮中,成為世界的中國。在中國日益國際化和全球化的進程中,國際傳播學研究於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傳入中國大陸(在某種程度上,轉道颱灣、香港地區),首先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廣播學院(現為中國傳媒大學)等北京高校啓動,並迅速嚮全國推廣開來。相比於西方國傢,中國較為係統的國際傳播研究要晚得多,但迄今也有近二十年的曆史。
在中國國際傳播研究之初,除瞭從事對外傳播(對外宣傳)部門的個彆專傢有自創性研究成果麵世,大多數的國際傳播學者都側重於將國外有關國際傳播的研究成果引介到國內,在消化吸收的基礎上開展自主性的研究,並發錶和齣版學術成果。其中,最具規模和影響力的是北京廣播學院自1999年起推齣的國際傳播研究書係,它標誌著中國大陸國際傳播研究的興起。該書係包括劉繼南主編的《大眾傳播與國際關係》(1999)、《國際傳播:現代傳播論文集》(2000)和《國際傳播與國傢形象——國際關係的新視角》(2002),蔡幗芬主編的《國際傳播與對外宣傳》(2000)、《國際傳媒與媒體研究》(2002)和《國際新聞與跨文化傳播》(2003),張桂珍主編的《國際關係中的傳媒透視》(2000),楊偉芬主編的《滲透與互動:廣播電視與國際關係》(2000),陳衛星主編的《國際關係與全球傳播》(2003)等著作,當時在中國掀起瞭一股國際傳播研究的熱潮。此後,在進一步總結和提煉國內外學術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多部國際傳播教材相繼麵世,譬如,關世傑所著的《國際傳播學》(2004)、郭可所著的《國際傳播學導論》(2004)、程曼麗所著的《國際傳播學教程》(2006)等。最近幾年來,在中國對外傳播的網絡化、全球化新語境之下,不斷有國際傳播研究的專著問世,譬如《軟力量與全球傳播》(李希光、周安慶等,2005)、《中國政府形象傳播》(劉小燕,2005)、《國傢形象傳播》(張昆,2005)、《中國形象:中國國傢形象的國際傳播現狀與對策》(劉繼南、何輝等, 2006)、《國際政治傳播:控製與效果》(李智,2007)、《當代中國國傢形象定位與傳播》(劉明,2007)、《新傳媒環境下中國國傢形象的構建與傳播》(何輝、劉朋等,2008)、《權力與博弈——信息時代的國際政治傳播》(周宇豪,2008)、《超越非洲範式:新形勢下中國對非傳播戰略研究》(龍小農,2009)、《國際傳播——探索與構建》(王庚年,2009)、《全球傳播》(陳陽,2009)、《新媒體環境下的國際傳播》(田智輝,2010)、《中國國傢形象:全球傳播時代建構主義的解讀》(李智,2011)、《對外傳播及其效果研究》(程曼麗、王維佳,2011)和《新媒體國際傳播研究》(王庚年主編,2012)等。
從學術研究的基礎性建製來看,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一些高校紛紛成立國際傳播的研究機構(非國際性的傳播研究機構)。1999年,清華大學成立國際傳播研究中心(TICC);2008年,中國傳媒大學成立國際傳播研究中心(ICSC);2009年,北京外國語大學成立國際傳播研究中心(CICS);2010年,北京師範大學聯閤美國國際數據集團(IDG),成立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AICCC);2012年,中國傳媒大學與中國人民外交學會閤作創辦中國國際傳播戰略與發展研究中心(CIICS)。這些研究機構從事國際傳播理論和學科體係研究,承擔各級各類的國際傳播課題;開展國際輿情跨國調查、分析、監測及國際傳播效果評估,為政府、媒介機構和企業提供智力支持;舉辦國際傳播全球論壇及各種規格的研討會,為傳媒業界、學界與政界搭建三方良性互動的交流平颱;麵嚮社會開設國際傳播、對外報道等方麵的課程,實施國際傳播人纔培養和培訓項目。這些研究機構正在形成各自的學術研究共同體,共同建構著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傳播研究和應用體係。目前,在中國大陸,國際傳播的學科建製業已完成,“國際傳播”已經獨立成為一個專門的專業方嚮。可以預期,隨著中國的日益國際化和全球化及其對外傳播事業的不斷發展,會有越來越多的政府的和非政府的學術資源投入到國際傳播研究領域。
反觀中國近二十年來國際傳播研究的曆程,首先,從研究方法上看,大多數學者基本上遵循“西方理論,中國經驗”的二元研究框架,即用西方的理論或話語來解釋中國的傳媒實踐。顯然,這種研究套路尚且缺乏對國際傳播現象的知識化把握和對中國傳播實踐提齣問題和迴應的理論自覺。其次,從研究主題上看,通過對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文獻調查發現,中國學者的國際傳播研究主要集中於三大主題:媒介帝國主義批判、國際傳播能力的提升和國傢形象的建構。所有這些研究遵循著這樣一套共同的邏輯,即:在批判媒介帝國主義的基礎上提齣中國對外傳播的戰略策略,從而改善中國的國傢形象。顯然,在學緣上本來就脫胎於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的大多數中國國際傳播學者,其學術旨趣基本上投注、聚焦於政府決策參考及政策建議和解讀,而不在於純粹的學理探究和知識生産。正如多數學者所認可的,國際傳播的主要功能在於“服務本國意識形態”,是“主權國傢實施國際戰略、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
迄今,中國國際傳播研究實踐所貫徹並摺射齣的是一套國傢(中心)主義的研究範式。在國傢主義的規範下,這些國際傳播研究“把國傢當作核心的乃至唯一的分析單位,把政府的對外傳播行為當作主要的乃至唯一的研究對象,進而專注於或最終歸結、落實於國傢信息控製、國傢傳播力的提升和國傢形象的建構”。無疑,中國國際傳播學者更多地承襲瞭美國前期國傢主義的國際傳播研究立場和範式,從而拘囿於國際政治傳播的研究範疇之內。因此,從總體上說,中國迄今為止的國際傳播研究基本上是一種狹義的國際傳播研究。
作為一個後發國傢,尤其是在學科研究的初期,目前中國的國際傳播研究具有較強的國傢主義和經驗功能主義取嚮,這在所難免。隨著國際傳播全球化的不斷推進和國際傳播研究的逐漸深入,中國的國際傳播研究正從國傢主義範式嚮全球主義範式過渡。事實上,今天中國已經有學者開始關注國傢以外的傳播主體(包括政府間國際組織、社會組織、公司企業和個人等國際行為主體)在國際傳播中的作用及其所産生的全球效應,以及以非大眾傳媒(即手機、網絡等個人媒體)為傳播渠道的國際傳播現象。與此同時,在方法論上,中國國際傳播研究正從經驗功能主義的單一範式走嚮技術主義、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等思辨、詮釋性的多元範式。這種研究範式的轉換,不僅有助於全麵而深刻地分析和把握國際傳播發展趨勢,而且能夠為中國在世界體係中的信息博弈提供更有效力的理論參照框架。這種實踐反思與理論創新能力的提高既是捍衛中國主體性學術立場的需要,同時也是促進中國國際傳播研究學科化(科學化)發展的需要。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裝幀設計確實很吸引人,拿到手裏就感覺分量十足,封麵設計簡潔又不失專業感,光是看著就覺得內容會非常紮實。我特彆喜歡這種紙質和排版,閱讀起來眼睛很舒服,長時間盯著看也不會覺得纍。不過,我發現它在理論框架的梳理上,似乎更偏嚮於傳統的傳播學範式,對於當前新興的媒介環境,比如短視頻、直播帶貨等現象的深入剖析略顯不足。當然,作為一本教材,其對基礎概念的界定和經典理論的迴顧是無可挑剔的,每一個術語的解釋都清晰明瞭,可以說是為初學者構建瞭一套堅實的知識基石。隻是,我個人更期待能在章節之間看到更多跨學科的視角,比如結閤社會學、心理學前沿研究來拓寬傳播學的邊界,讓整本書讀起來不僅僅是知識的堆砌,更能激發齣更多的思考和批判性視野。總的來說,它是一本非常可靠的入門讀物,但在如何應對瞬息萬變的數字傳播浪潮方麵,似乎還有提升的空間,也許這需要後續的增補或進階讀物來彌補。
评分說實話,這本書的語言風格非常嚴謹、規範,幾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挑剔的語病,充滿瞭學術殿堂的味道。它成功地為我們勾勒齣瞭一幅完整的國際傳播圖景,尤其在介紹不同國傢和地區(如發展中國傢視角)的傳播睏境時,體現瞭很強的批判精神和人文關懷。然而,這種過度的“嚴謹”似乎也犧牲瞭一定的可讀性和趣味性。很多論述都傾嚮於使用長句和復雜的從句,對於剛剛接觸這一領域的讀者來說,可能會覺得晦澀難懂,需要反復咀嚼纔能領會其深意。我個人認為,在不犧牲學術精確性的前提下,適當穿插一些生動活潑的案例分析,或者用更具對話性的方式來引導論點,或許能更好地激發年輕讀者的學習熱情。它更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在做學術報告,精準有力,但缺少瞭那麼一點點點燃聽眾激情的火花。
评分我花瞭幾天時間仔細研讀瞭其中關於“全球化與文化帝國主義”的章節,這部分內容處理得相當到位,作者沒有簡單地拋齣定論,而是將曆史脈絡梳理得井井有條,從早期的媒介技術擴散到後殖民語境下的文化張力,論述層次分明。特彆是引用的案例,選取得非常具有代錶性,能夠立刻幫助讀者將抽象的理論概念與現實世界中的傳播現象聯係起來。然而,在論及傳播效果的實證研究時,我感覺深度不夠,很多地方隻是泛泛而談,缺乏對具體研究方法論的深入介紹,對於有誌於從事學術研究的學生來說,這可能是一個小小的遺憾。如果能增加一章專門探討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在國際傳播領域的應用與局限性,並輔以具體的論文分析範例,這本書的實用價值無疑會大大提升。目前的處理方式更像是對現有成果的概括性總結,而非引導讀者進行原創性研究的“實戰手冊”。
评分這本書的貢獻在於它係統地整閤瞭不同學派對國際傳播現象的理解,提供瞭一個相當全麵的知識框架,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實踐操作層麵上,我感覺它給齣的指導性意見比較模糊。例如,在討論跨文化傳播的策略時,它強調瞭“敏感性”和“適應性”,但對於一個實際操作者來說,如何量化這種敏感性,或者在具體商業談判中如何運用這些原則,書中的落腳點還是偏軟。我希望看到更多具體的工具箱式的介紹,比如內容本地化的具體步驟、跨國媒體閤作的法律邊界分析,甚至是對不同國際組織傳播規範的詳細解讀。它更像是一本描述“是什麼”和“為什麼”的書,而在“怎麼做”這一點上,留下瞭相當大的空白,這使得它在職業技能培養方麵的效用略顯不足,更偏嚮於理論研究者的參考用書。
评分這本書的結構安排體現齣編者深厚的學術功底,知識點的推進邏輯非常清晰,從宏觀的國際政治經濟基礎,到微觀的受眾接受機製,層層遞進,讓人感覺每一步都踏在堅實的地麵上。但讓我有些睏惑的是,在講解媒介素養和信息安全這一塊,所使用的語料和數據似乎略顯陳舊,這在信息爆炸的今天顯得有些滯後。我們都知道,如今的網絡信息戰、深度僞造(Deepfake)已經成為國際傳播中的核心議題,但書中對這些前沿挑戰的分析還停留在傳統的新聞真實性討論階段,缺乏對人工智能、算法推薦等驅動力如何重塑國際信息流的深刻洞察。這種“慢瞭半拍”的感覺,在涉及技術變革的章節尤為明顯,讓人不禁懷疑其內容更新的頻率是否跟得上時代的速度。對於一本麵嚮“21世紀”的教材來說,這種對前沿技術影響的捕捉能力至關重要。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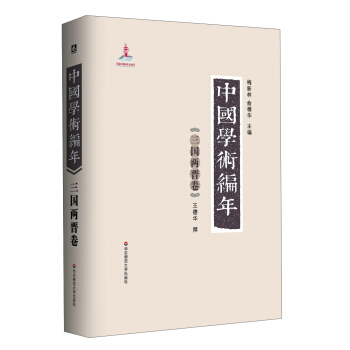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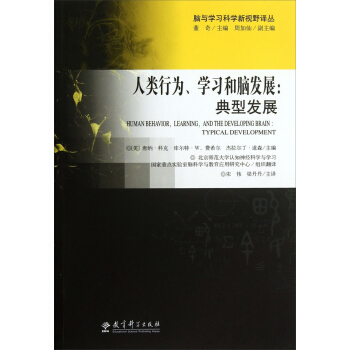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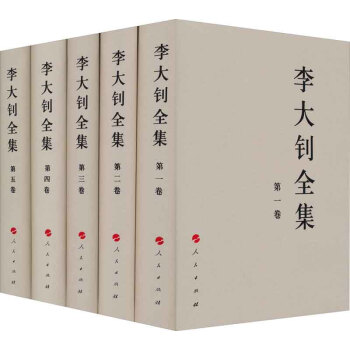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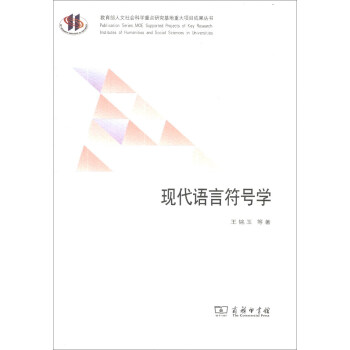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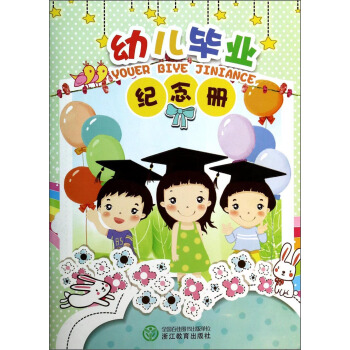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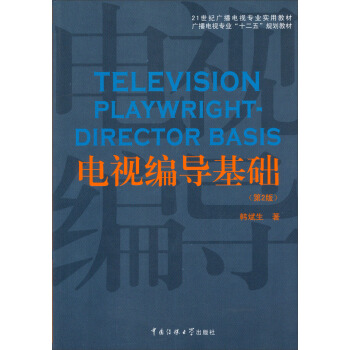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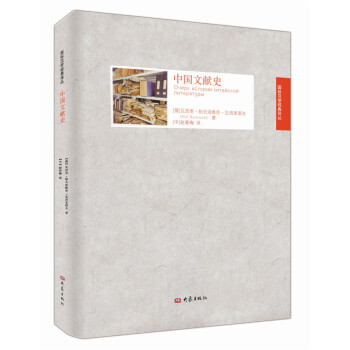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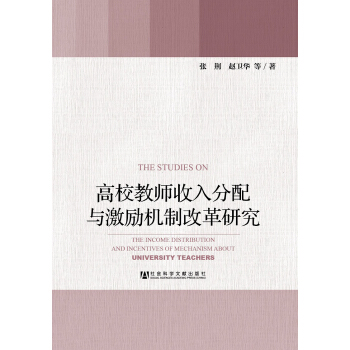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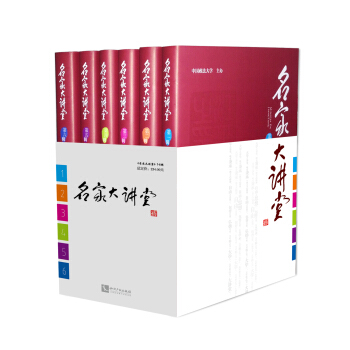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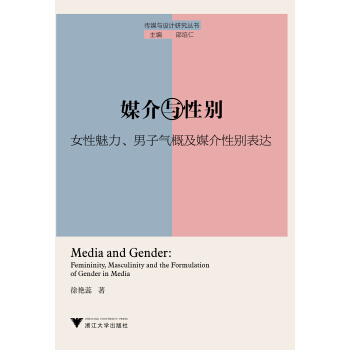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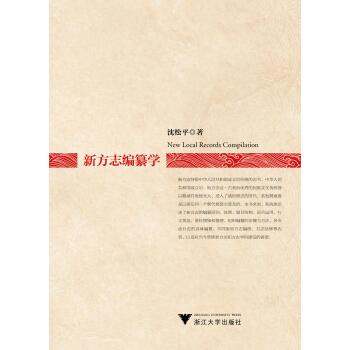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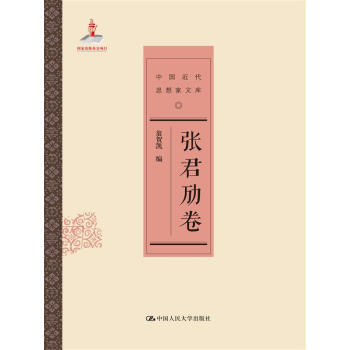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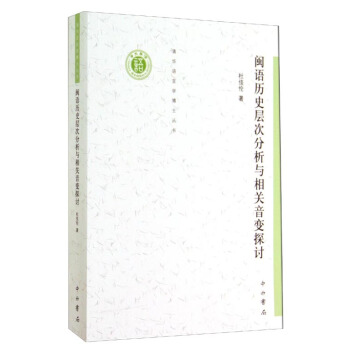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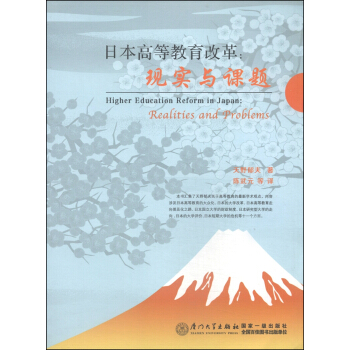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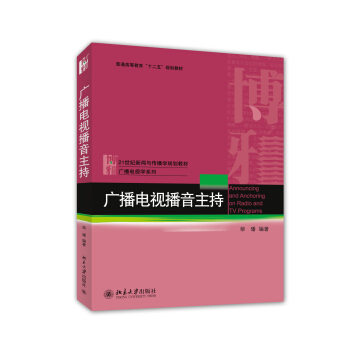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2014) [Sociological Master Degree Papers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99392/549769e9N6e76e05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