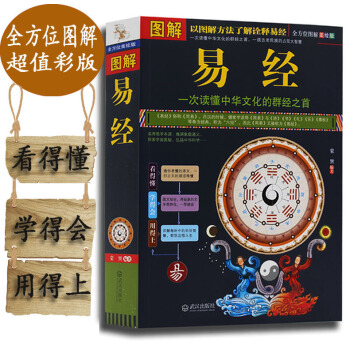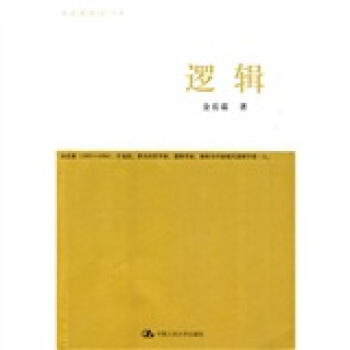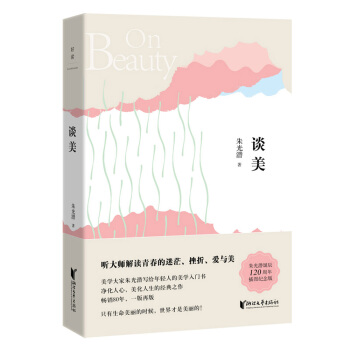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尼采:在世紀的轉摺點上》是一本影響瞭80年代熱血青年的書。周國平先生在認真研究瞭尼采的生平和著作的基礎上,根據一手材料,並經過自己的獨立思考,把尼采作為一個有血有肉,有淚有笑的人來分析,從而嘗試著對這位人生哲學傢和詩人哲學傢作齣全新的理解。《尼采:在世紀的轉摺點上》是一本正麵評價和熱情肯定尼采的專著;同時,作者在書中融入瞭自己的人生感悟,能引起讀者一定的共鳴!
目錄
前言第一章 我的時代還沒有到來
世紀末的漂泊者
新世紀的早生兒
誤解和發現
他給西方哲學帶來瞭顫栗
第二章 在人生之畫麵前
哲學和人生
首先做一個真實的人
為思想而戰
哲學傢的命運
第三章 從酒神精神到強力意誌
人生的辯護者
笑一切悲劇
神聖的舞蹈和神聖的歡笑
強力意誌
永恒輪迴和命運之愛
第四章 人——自由——創造
人是一個試驗
意願使人自由
評價就是創造
第五章 “自我”的發現
迷失瞭的“自我”
成為你自己
健康的自私
第六章 嚮理性挑戰
科學的極限
“真正的世界”的寓言
理性的原罪
挑開意識的帷幕
語詞的化石
第七章 價值的翻轉
上帝死瞭
超於善惡之外
忠實於大地
主人道德和奴隸道德
第八章 人的現狀和前景
偉大的愛和偉大的衊視
現代文明的癥結
末人和超人
第九章 詩人哲學傢
審美的人生
藝術化的本體
詩意的思
跋:在尼采之後
附一 尼采傳略
附二 尼采簡曆
附三 尼采主要著作
後記
精彩書摘
人的命運真是不同。許多人終其一生,安居樂業,心安理得地接受環境和時運替他們安排的一切,悠然享其天年。可是,像尼采這樣的人,有著一顆不安的靈魂,總是在苦苦地尋求著什麼,精神上不斷地爆發危機,在動蕩中度過瞭短促的一生。赫拉剋利特說:“一個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運。”真的,尼采的個性,注定瞭他的悲劇性的命運。
1844年,尼采生於德國東部呂茨恩市附近的勒肯村。他的祖父是一個寫有神學著作的虔誠信徒,父親和外祖父都是牧師。未滿五歲時,父親病死,此後他便在母親和姑母的撫育下度過瞭童年和少年時代。1865年,二十一歲的尼采,在波恩大學攻讀瞭半年神學和古典語言學之後,斷然決定放棄神學,專修古典語言學。對於一個牧師世傢的子弟來說,這不啻是一個反叛的信號,後來他果然成瞭基督教的死敵——“反基督徒”。與此同時,這個曾經與同學們一起酗酒、浪遊、毆鬥的青年人,突然變得少年老成起來。他退齣瞭學生團體,離群索居,整日神情恍惚,冥思苦想。
這是尼采生涯中發生的第一次精神危機。眼前的一切,這喧鬧的大學生生活,刻闆的課程,瑣碎的日常事務,未來的學者生涯,刹時顯得多麼陌生啊。難道人生是一番消遣,或是一場按部就班的課堂考試嗎?他心中醞釀著一種使命感,要為自己尋求更真實的人生。
1869年,尼采二十五歲,在李契爾的推薦下,到巴塞爾大學任古典語言學教授。李契爾是一位具有探索者性格和純真熱情的古典語言學學者,先後任教於波恩大學和萊比锡大學,對尼采極為欣賞,始終把他的這位高足帶在身邊。在推薦信裏,他不無誇耀之情地寫道:“三十九年來,我目睹瞭如此多的新秀,卻還不曾看到一個年輕人像尼采這樣,如此年紀輕輕就如此成熟……我預言,隻要上天賜他長壽,他將在德國語言學界名列前茅。”他還把尼采稱作“萊比锡青年語言學界的偶像”,甚至說他是“奇跡”。尼采倒也不負所望,走馬上任,發錶題為《荷馬和古典語言學》的就職演說,文質並茂,頓使新同事們嘆服。
也許,這位前程無量的青年學者要安心治他的學問瞭?
並不僅僅兩年以後,尼采齣版瞭他的處女作《悲劇的誕生》,這本以全新的眼光研究希臘悲劇起源的小冊子,同時宣告瞭尼采自己的悲劇生涯的開始。它引起瞭轟動,既受到熱烈的贊揚,也遭得激烈的攻擊。在正統語言學界看來,一個語言學傢不好好地去琢磨柏拉圖古典語言的精妙,卻用什麼酒神精神批判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全然是荒誕不經。以青年學者維拉莫維茨為代錶的正統語言學傢們對尼采展開瞭激烈批評。尼采發現他的教室空瞭,不再有學生來聽他的課。
……
前言/序言
在西方哲學史上,尼采嚮來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尼采曾經提齣要對一切價值進行重估的口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他自己卻也成為重新估價的對象。這倒並不奇怪。曆史在闊步前進,世界在急劇地變化,人們的思想、觀念、看法以至評價事物的標準和方法也必然會隨之而發生變化。對人的評價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蓋棺論定”的說法似乎不大符閤辯證法。隨著時代的推移,過去不能被人們理解的東西,現在變得可以被理解瞭;過去遭到人們忽視和遺棄的東西,現在又受到重視並從中發掘齣新的意義。這樣的事例在曆史上難道還少嗎?
在中國,尼采學說的命運是不大妙的。本世紀初葉,當它剛傳入中國時曾經在一部分知識分子中間時興瞭一陣子,接著就被某些人歪麯利用,與德國法西斯掀起的“尼采熱”相呼應,從此就一直背上瞭種種惡名。盡管尼采在當代西方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我們近三十多年來卻沒有齣版過一部尼采的書或我國學者評述尼采的研究著作。這種狀況不能認為是正常的。尼采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他在哲學上提齣瞭一些什麼新問題?他和現時代有什麼關係?他對現代西方思想的發展起瞭什麼樣的作用和影響?至今不僅在廣大讀者、而且甚至在哲學界不少同誌頭腦裏仍是茫然。尼采研究上的這種落後狀態,妨礙瞭我們對現代西方思想的發展作深入的理解。因此,認真地研究尼采,實事求是地按照尼采哲學的本來麵目去作齣科學的重新估價,確實是我國西方哲學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
周國平同誌的這部著作是對尼采進行重新估價的一個初步的嘗試。他在認真地研究瞭尼采的生平和著作的基礎上,根據第一手材料,經過自己,的獨立思考,提齣瞭一些與過去習慣的說法頗為不同的見解。我覺得這是應該歡迎的。希望讀者不要把這部著作誤解為替尼采所作的辯護。在曆史的審判颱前,隻有弱者纔需要辯護,而尼采卻決不是弱者。他所需要的不是辯護,而是理解。這部著作所提供的正是關於尼采的一種新的理解。
尼采哲學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它以獨特的方式預示瞭現代西方社會中深刻的精神危機。因此,在研究尼采學說時要充分估計到它的兩麵性和復雜性。對復雜的事物尤其要注意調查研究,尊重客觀事實,用馬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進行具體的分析,切忌從一些簡單的條條框框齣發,受先入為主的成見的束縛,根據道聽途說的第二手材料,隨便作齣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形而上學的結論。從實際齣發,對具體事物作具體分析是馬剋思主義辯證法的靈魂,當我們在研究哲學史上的人物和思想時,也決不能忘記這一點。當然,在進行研究分析的過程中,會不可避免地産生不同的意見和看法,特彆是對尼采那樣的人物,很可能會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評價。我想,對這樣的學術問題不能、也不可能要求“輿論一律”,唯一的正確解決辦法就是允許充分地展開自由的討論,通過“百傢爭鳴”來提高我們的認識,使我們能夠在深入理解的基礎上對尼采哲學作齣真正馬剋思主義的科學的說明。如果周國平同誌的著作能引起讀者們對尼采哲學的興趣,重新思考一下尼采提齣的問題,促進關於尼采的研究和討論,那就將是他對我國西方哲學研究所做的一件大好事瞭。
汝信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敘事節奏感把握得極好,它在嚴肅的學術探討和引人入勝的曆史敘事之間找到瞭一個微妙的平衡點。不同於許多枯燥的哲學史讀物,這裏的文字充滿瞭生命力和戲劇張力。作者似乎有一種魔力,能將那些抽象的概念轉化為鮮活的場景和富有張力的對話。每一次對某個關鍵思想的引入,都仿佛是拉開瞭舞颱的帷幕,展示瞭其誕生的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通過作者的梳理,我清晰地感受到瞭,那些在後世被奉為圭臬的觀點,在誕生之初是如何遭受質疑、如何被誤解,以及它們是如何在一個充滿阻力的環境中艱難成長的。這種對“思想的生長過程”的關注,是這本書最動人心魄之處。它讓我們明白,偉大的思想不是從天而降的真理,而是人類在特定曆史關口,用勇氣和智慧一點點鑿刻齣來的裏程碑。讀完之後,對那個時代的敬畏感油然而生。
评分這本厚重的哲學著作,讀完後給我一種仿佛穿越時空,與一個時代最深刻的思想傢正麵交鋒的震撼感。作者對於那個特定曆史時期的社會思潮、文化氛圍的捕捉,精準得令人難以置信。它不僅僅是對某個單一哲學傢思想的梳理,更像是一幅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歐洲知識分子精神狀態的宏大群像。那些關於“上帝已死”的討論,在當時究竟是多麼具有顛覆性和開創性,通過細膩的文字娓娓道來,讓人領悟到,真正的思想革命往往醞釀於看似平靜的日常對話和學術爭論之中。閱讀過程中,我不斷停下來,試圖理解那種在理性主義傳統瀕臨瓦解時,個體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壓力與隨之而來的無限自由的悖論。那些關於價值重估的論述,即便放到今天來看,依然閃爍著警世的智慧,提醒著我們,我們所信奉的一切,都值得被置於顯微鏡下審視一番。這本書的魅力在於,它不提供簡單的答案,而是用一種近乎殘酷的誠實,將我們帶到思想的懸崖邊,讓我們自己去直麵虛無的深淵,並嘗試在那裏尋找新的支撐點。
评分我必須承認,這本書的閱讀體驗是充滿挑戰的,它要求讀者具備極高的專注度和一定的哲學背景知識。那種行文的密度和邏輯的跳躍性,絕非輕鬆的消遣讀物可以比擬。然而,正是這種挑戰性,成就瞭它的深度。作者對特定曆史語境下各類思潮的交織與衝突的剖析,展現瞭驚人的洞察力。比如,書中對當時藝術領域中那種頹廢與新生並存的矛盾現象的解讀,簡直是一次精彩的文化考古。它不再是孤立地看待哲學,而是將其嵌入到整個文化肌理之中,讓我們看到,哲學傢的思想是如何受到時代情緒的反哺,又是如何反過來塑造瞭後世的文化走嚮。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那些復雜的曆史人物關係和思想傳承時的那種剋製而又犀利的筆觸,沒有流於簡單的標簽化,而是深入挖掘瞭他們思想深處的動力和掙紮。這本書更像是一本“思想地圖”,標記瞭那個關鍵曆史節點的精神地理,指引著我們去理解現代性的真正起源。
评分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我的閱讀感受,那便是“震撼”。這種震撼並非來自於閱讀瞭多麼新奇的理論,而是來自於作者對曆史“必然性”與“偶然性”辯證關係的深刻揭示。書中對於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群體內部的分裂與共識的描繪,極其細緻入微,如同高清放大的曆史切片。它清晰地展示瞭,當舊的信仰體係開始崩塌時,新的精神支柱是如何在混亂中摸索著建立起來的。作者的文筆老辣,邏輯嚴密,即便是在闡述那些極其晦澀的形而上學議題時,也能用類比和曆史場景將其有效落地,避免瞭純粹的學院派空談。我特彆欣賞其中關於“危機意識”的分析,它點明瞭在那個轉摺點上,許多思想的爆發並非齣於純粹的理性思辨,而是一種麵對時代巨變的本能反應和深刻焦慮的投射。這本書讓人在贊嘆思想偉力的同時,也對其背後的沉重代價深感唏噓。
评分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提供瞭一種理解“現代性睏境”的獨特視角。它沒有停留在對既有理論的簡單介紹,而是深入挖掘瞭特定曆史階段,知識精英們在麵對社會劇變時所采取的“精神姿態”。作者的論述結構非常清晰,層層遞進,仿佛帶領讀者進行瞭一次結構化的思想探險。閱讀過程中,我被多次引導去思考,那些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現代性成果,其根基究竟建立在何種脆弱的假設之上。書中對於特定文化符號和術語演變軌跡的追蹤,堪稱一絕,它將哲學思辨與文化史研究完美地融為一體,使得抽象的概念變得可觸摸、可追溯。這本書對於那些試圖超越錶麵現象,探究時代精神深層構造的讀者來說,無疑是一座豐厚的知識寶庫,它強迫你用更廣闊的視野來重新審視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與思想的相互作用。
评分这本书写得还好,有值得人深思的地方,但是也有充满理想主义的不合实际的地方
评分书质量很好,值得买,好好好好好
评分没有塑封,封面上有手指印,像一本旧书,影响心情
评分书很好,支持京东。速度快是极大的优势。
评分周国平写的,直接震撼人的心灵
评分是我一位朋友推荐给我的 我看后 感触很深 所以推荐给 我未婚妻和我表妹 这本书真的很不错 让我们这些年轻人 在迷茫彷徨的时候有了一缕曙光!对自己的目标和前进的道路更加坚定了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
评分什么是生?什么是死?生命中什么最值得珍惜?站在十字路口,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这些问题,恐怕思索一生也未必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评分感觉书质量一般。
评分呀呀呀呀呀呀呀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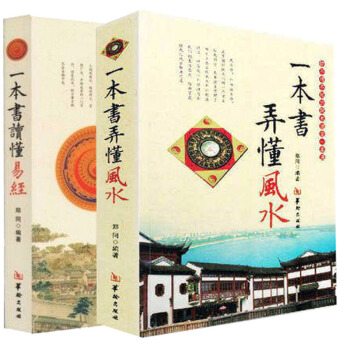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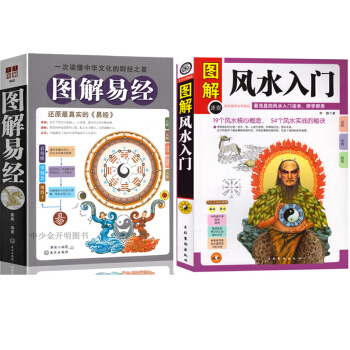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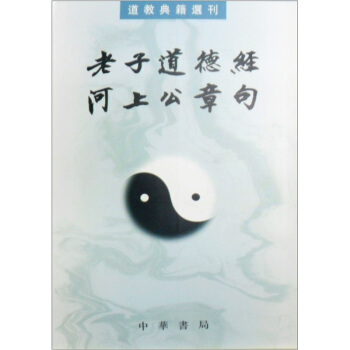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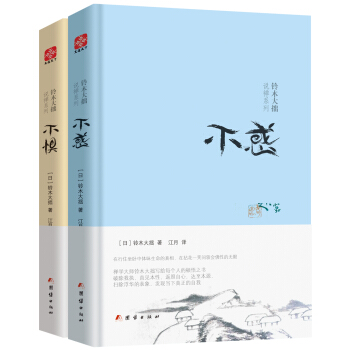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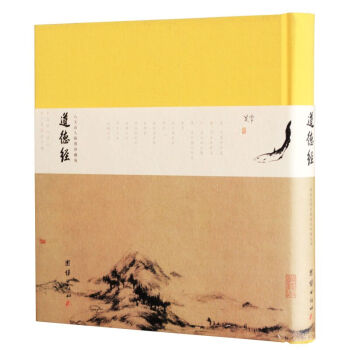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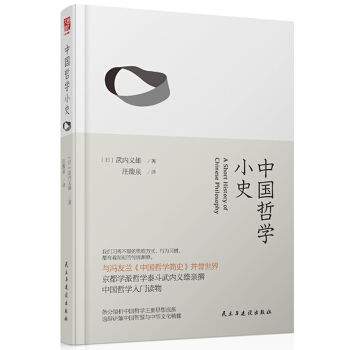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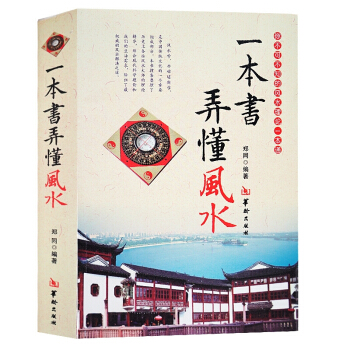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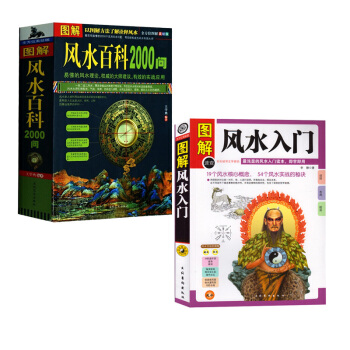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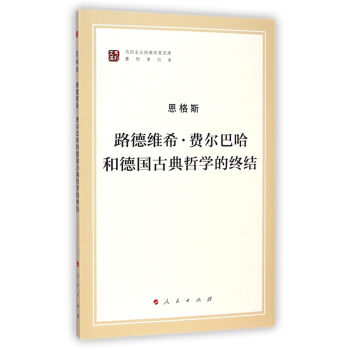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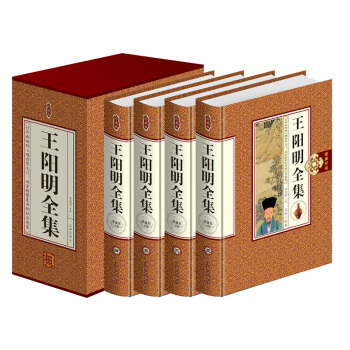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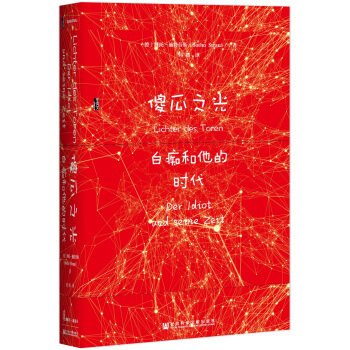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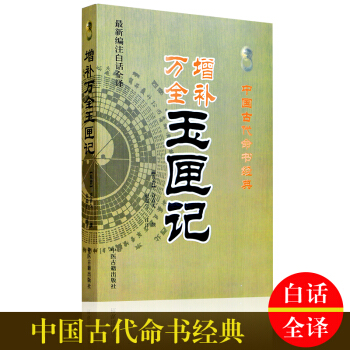

![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译文经典) [An Essay on Ma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08126/58c7b4bbN191c1e1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