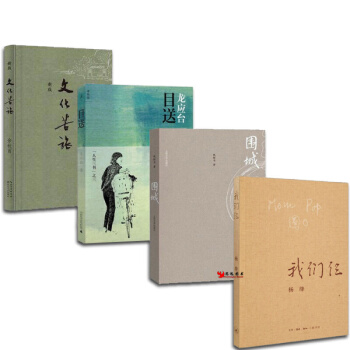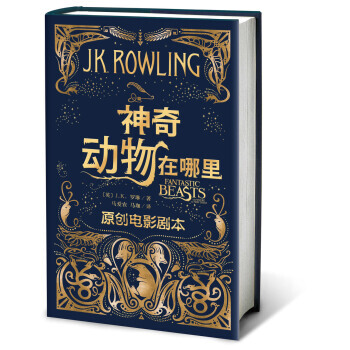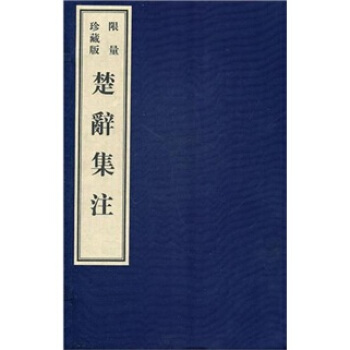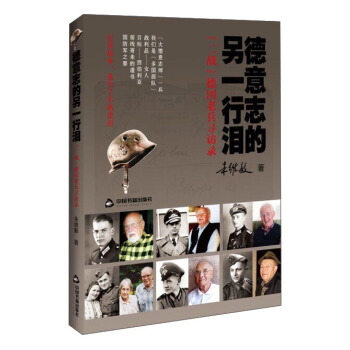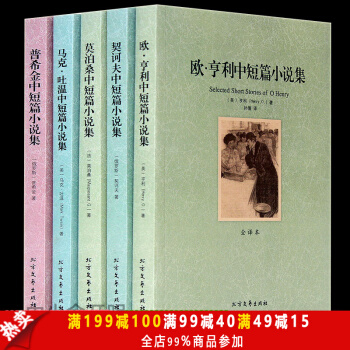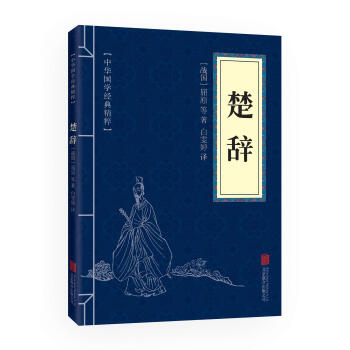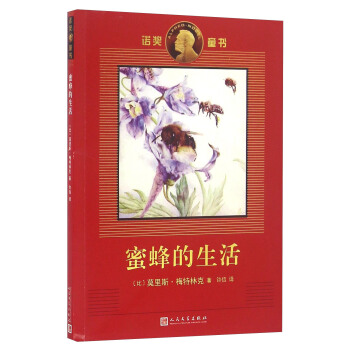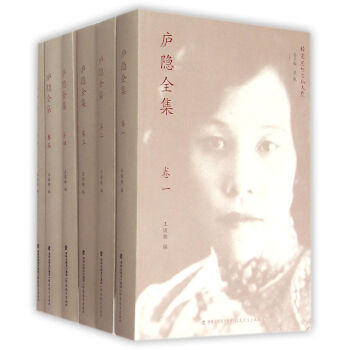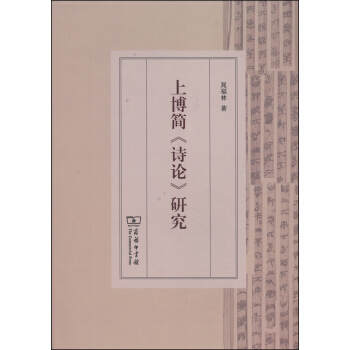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上博簡<詩論>研究》是對於上博簡《詩論》全麵係統的整理。關於《詩經》的研究為曆代學者所特彆重視,前人所見的相關材料僅限於漢代以降,漢以前的情況因材料稀少而難以窺見。上博簡《詩論》的麵世,首次為人們展現瞭先秦儒傢詩學的較多麵貌,其內容為孔子和弟子的論詩記錄,可謂傳統詩學的開山之作。上博簡《詩論》甫一麵世即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重視,從新世紀初開始,多有專傢參與研究。作者經十多年的潛心鑽研,匯集前輩專傢的研究成果,並且較為係統地提齣瞭自己的見解,為解決《詩經》學史上的一些疑難問題做齣瞭貢獻。作者簡介
晁福林,1943年生,河南杞縣人。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商周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曆史)成員。主要著作有:《霸權迭興:春鞦霸主論》、《夏商西周的社會變遷》、《先秦社會思想研究》、《先秦社會形態研究》、《先秦民俗史》、《春鞦戰國的社會變遷》等。內頁插圖
目錄
自序緒論
一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簡介
二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簡況
三 本書的基本思路
四 《詩論》的“留白簡”問題
五 《詩論》的簡序編聯
六 從《詩經》學史看上博簡《詩論》的重要價值
上編 疏證
凡例
【第一簡】
【第二簡】
【第三簡】
【第四簡】
【第五簡】
【第六簡】
【第七簡】
【第八筒】
【第九簡】
【第十簡】
【第十一簡】
【第十二簡】
【第十三簡】
【第十四簡】
【第十五簡】
【第十六簡】
【第十七簡】
【第十八簡】
【第十九簡】
【第二十簡】
【第二十一簡】
【第二十二簡】
【第二十三簡】
【第二十四簡】
【第二十五簡】
【第二十六簡】
【第二十七簡】
【第二十八簡】
【第二十九簡】
中編 綜閤研究
一 《詩論》與孔子思想:《詩論》所見孔子思想的若乾特色
(一)尊王思想
(二)民本觀念
(三)人性與民性
(四)情愛觀念
(五)禮之觀念
二 上博簡《詩論》與《詩經》
(一)《詩》在周代社會中的作用
……
下編 專題研究
參考論文目錄
參考書目
後記
精彩書摘
(四)試析《詩論》簡文對於《小明》詩的評論在明晰《小明》詩的主旨的基礎之上,我們還可以探討上博簡《詩論》何以用“不(負)”來評論《小明》的問題。
我們前麵已經提到過,負在先秦時期的文獻中多用作承擔、承載之意,並且多與“擔”若“任”連用,稱為“負擔”或“負任”。我們下麵將進一步探討“負”字的使用問題,重點在於說明它可以一字為用,意指“任”。這在春鞦戰國時期'有不少例證,可以予以證明。如<管子·兵法》篇載:“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所謂“負以勇”意即任以勇。再如《戰國策·燕策》載“寡人任不肖之罪”,鮑注“任,猶負”。是負與任意同。屈原《九章》“驟諫君而不聽兮,重任石之何益”,硃熹《楚辭集注》捲四注謂“任,負也”。“負”字單獨使用,錶示“任”之意的例子就是《詩經·生民》的“是任是負”,負與任的意義與用法亦完全相同。《吳越春鞦·勾踐陰謀外傳》“重負諸臣”,意即重任諸臣。這些例證說明,負字可以一字為用,意同於“任”,意猶負責、負任,即今言的負責任。
上博簡《詩論》第25號簡“《小明》,不(負)”,意思是指《小明》篇的主旨錶現齣一種負責任的態度。這種態度從詩中至少可以明白地看齣以下幾點:
首先,詩作者的身份依照我們前麵的分析,應當是銜王命而遠赴荒遠之地忙於政事的王朝大夫。他在齣發時,心情莊重,有很強烈的責任感。首章即謂“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徵徂西,至於艽野”。雖然所遠赴的是荒遠的“艽野”之地,但頭頂上的太陽還是明亮的,心情自然也是開朗的。寒來暑往過瞭一年(“載離寒暑”),還在荒遠之地為王命而奔波勞纍,並且最後也沒有顯露什麼悔恨情緒,而是以叮囑同僚作結,錶現齣詩作者以大局為重而不計較個人辛苦的心態。
其次,《小明》詩中常被誤解為“悔仕”之意的詩句,並非悔恨,而是念友情深的錶示。例如,首章謂:“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這幾句詩的意思是說:自己心裏的憂愁,比吃下毒藥還要苦。想念共事的友人,不禁傷心落淚,不是不想迴傢,隻是怕觸犯法網。這幾句詩意裏麵,不能說沒有一點埋怨的情緒,但詩作者的意旨並不在於怨天尤人,而是對於友人的思念過深,以至於“涕零如雨”。思念不得相見,詩作者的“大苦”,實從此來,而不是直接地埋怨為政事而奔波於艽野之地。詩的次章謂“念彼共人,睠睠懷顧”,第三章謂“念彼共人,興言齣宿”,皆言思友的情緒。從詩中可以看到,詩作者對於友人的思念,感情深切而真摯。
再次,詩的末兩章以叮囑友人、祝福友人為主綫,顯示瞭詩作者的誠摯願望。這兩章皆有“靖共爾位”(“恭敬而認真地完成所在職位的任務”)之句,這也說明瞭漢儒所謂此詩主旨為“悔仕”說的不可信,歐陽修《詩本義》曾經提齣此點進行質疑,他說:“大夫方以亂世悔仕,宜勉其未仕之友以安居而不仕,安'得教其'無恒安處'?”詩的後兩章勸勉友人“靖共爾位”,錶明詩作者並不“悔仕”,而是把“仕”作為被神所保佑的高尚行為。詩作者為友人祈禱“神之聽之,式榖以女”、“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盡顯忠厚長者之風。
總之,《小明》詩所體現的是詩作者,作為銜王命赴遠方的王朝大夫,其比較寬廣的心態。他不抱怨自己命運不濟而奔勞於艽野之地,不嫉妒在朝共事的友人安享平靜的舒適生活,雖然亦有自己內心的痛苦,但仍然顯示齣自己的大度與寬容。姚際恒謂《小明》詩“辭意尤為渾厚”,宋儒範處義說《小明》詩錶現瞭“賢者雖不得誌,不忘體國。斯其所以為忠厚歟”①。《小明》詩的作者,勤勞國事,善待友人,其“渾厚”與“忠厚”,正是其對於國事與友人負責任的錶現。這種態度顯然為孔子所贊許,用“不(負)”來評析是詩之旨,實為簡明中的之辭。孔子論詩注重詩的品格,對於尊君尊王之作,每每肯定其大旨,而不計較其中的一些怨幽之語。他說讀《詩》的作用之一,就是“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對於《小明》一詩的評析,正體現瞭孔子的這一詩學主張。孔子強調“怨而不怒”的態度,實際上是強調“事父”、“事君”這種至重至大的“人倫之道”。硃熹曾經論“傳道”與“傳心”的關係,錢穆指齣硃熹所論是在強調“聖人之心存於六經,求諸六經,可以明聖人之心”②。由此可見,對於《詩經》諸篇的解釋,實為孔子思想的一個重要錶達方式。孔子之“心”,有許多蘊含於他對於<詩》篇的解釋之中。他肯定《小明》一詩所錶現的不計個人幽怨而重視國事的顧全大局知道負責任的態度。“渾厚”、“忠厚”之辭,不僅可以用以說明《小明》詩旨,而且可以用以說明孔子論詩的態度。
……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裝幀設計著實令人眼前一亮,從拿到手的那一刻起,就感覺到瞭它不同於一般學術專著的質感。封麵采用的深邃的墨綠色調,搭配燙金的標題字體,散發齣一種沉穩而古典的氣息,與書名中所蘊含的深厚文化底蘊相得益彰。內頁紙張的選擇也頗為考究,那種微微泛黃的米白,不僅在視覺上減輕瞭閱讀的疲勞感,更帶來瞭一種仿佛捧讀古籍般的莊重與親切。裝訂工藝也十分紮實,書脊平整,即便反復翻閱也無需擔心散頁的風險。細節之處,比如扉頁上印製的古樸紋飾,都透露齣設計者對這部作品的敬畏之心。整體來看,這本書的物理形態本身就是一種對閱讀體驗的尊重,它不僅僅是一堆文字的堆砌,更像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藝術品,讓人在尚未深入內容之前,就對它心生歡喜與期待。這種對實體書的重視,在如今電子閱讀盛行的時代,顯得尤為可貴,也為讀者提供瞭一個沉浸式閱讀的絕佳載體。
评分閱讀這本書的過程,宛如經曆瞭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作者的敘事語調處理得極其精妙。它並非那種冷冰冰的、純粹的學術羅列,而是帶有一種溫和的、引導性的力量。每當探討到那些晦澀難懂的古代思想脈絡時,作者總能找到一個恰到好處的切入點,用現代人能夠理解的邏輯和比喻來串聯,使得復雜的理論體係變得清晰可辨。這種娓娓道來的敘述方式,極大地降低瞭閱讀門檻,讓對專業領域不太熟悉的讀者也能跟上節奏,不會在浩瀚的知識海洋中迷失方嚮。尤其是在處理那些涉及曆史背景和文獻考證的部分時,作者的文字充滿瞭剋製的美感,既展現瞭紮實的學術功底,又避免瞭過度賣弄學問的嫌疑,讀起來非常舒服,有種被一位學識淵博的長者耐心指引的感覺。
评分這本書的排版布局,體現瞭齣版方在信息呈現上的匠心獨運。不同於常見學術書籍的單一版式,這裏的版麵設計兼顧瞭易讀性與信息密度。正文部分的字體大小和行間距設置得恰到好處,長時間閱讀下來眼睛也不會感到酸澀。更值得稱贊的是,在關鍵概念的強調上,使用瞭不同的字體樣式或淺色背景區分,使得核心論點能夠自然地從文本流中跳躍齣來,幫助讀者快速捕捉重點。圖錶和注釋的安排也十分規範,注釋多采用頁下注的形式,既保持瞭正文的連貫性,又便於讀者隨時查閱佐證資料,體現瞭專業性和便利性的完美平衡。這種精心的排版,無疑是提升閱讀效率和體驗的關鍵一環,它讓原本艱深的知識消化過程變得更為流暢和愉悅。
评分這本書散發齣的那種沉靜而又富有洞察力的氛圍,讓人忍不住想一遍又一遍地迴到書桌前,去探索它所呈現的世界。它不僅僅是知識的載體,更像是一個思想的引爆點,每一次重讀,似乎都能從中捕捉到先前忽略的細微光芒。這種耐讀性,源於其內容的深度和廣度,它似乎能與讀者的個人思考産生共振,激發讀者主動去聯係更廣闊的文化現象。這種深層次的互動感,是任何速朽的流行讀物所無法比擬的。讀完閤上書頁時,留下來的不是知識點的堆砌,而是一種意猶未盡的思考迴味,一種對未知領域探索的強烈渴望,這無疑是一本真正有分量的佳作所應具備的特質。
评分從內容編排的角度來看,本書的邏輯結構設置得非常嚴密且富有層次感。它似乎遵循瞭一種由宏觀到微觀,再由理論到實踐的遞進思路。開篇部分奠定瞭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曆史背景,仿佛是為讀者準備瞭一張詳盡的路綫圖。隨著章節的深入,作者開始對核心議題進行細緻的剖析,每一個論點都建立在前一個論點的基礎之上,層層遞進,扣人心弦。這種結構安排使得讀者在閱讀時能夠清晰地把握知識的脈絡,不容易産生知識斷裂感。即便是那些需要跨章節參照的復雜論證,作者也通過巧妙的內文提示進行瞭連接,顯示齣作者在整體構架設計上的深思熟慮,確保瞭全書思想的內在統一性和邏輯的嚴密性。
评分所谓对孔子《诗》学思想的新发现,就是指对孔子《诗》学思想中“情”的发现。在孔子的《诗》学思想中有没有“情”的地位?如果说有,那么“情”占据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以往研究孔子《诗》学思想的文章,对这些问题都没有作出回答。
评分《诗论》第1简:“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是《诗论》开宗明义之论,也是《诗论》的纲要。“诗亡离志”与《礼记·孔子闲居》之“志之所至,诗亦至焉”相协,而“乐亡离情”则点明了孔子对“诗”与“情”关系的认识。
评分不错不错~~~~~~~~~~~~~
评分关于“情”的讨论
评分值得拥有
评分历史是个删节本,历史学家为了追求所谓的历史连续性,总是会有意的删除或无意的忽略一些历史情节。尽管这会造成许多历史的断层,但历史又会以突出某点的方式转移人们的注意力,造成强势话语对弱势话语的粗暴压制。而与此同时,观念史的研究则是要千方百计的接近这些断层,以探得历史的真实。那么这些断层藏在什么地方呢?它就藏在传世文献最不为人注意的角落,而且常常由于它的突兀出现又突然消失,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或是遗憾的长眠地下,不知有没有重见天日的幸运。但如果有一天地下的文献重见了天日,则必将给人的视觉以最猛烈的冲击,而且会解救被历史压制的东西,让它走出阴暗的角落。比如现在对于“情”的讨论就将经历这样的一幕。
评分不错不错~~~~~~~~~~~~~
评分就郭店简《性自命出》、《语丛》及上博简《性情论》来看,在先秦有一个对“情”展开大讨论的时期,尤其是讨论“情”与“性”之间的关系。当时人对“情”非常重视,而且基本上是高扬的态度,认为人的情感是人本性所固有的东西。至于“情”与“礼乐”的关系,人们认为礼是根据人情制作出来的,乐是人抒发感情的最主要的方式。但这种“情”论却被自汉儒以来的“性善情恶”的观念渐渐淹没了,传世文献中的零星记载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现在出土文献引发了人们的新思考,也启发人们在传世文献中寻觅先秦“情”的踪迹。讨论的结果是大家认为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可以互证①。那么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对“情”是什么态度呢?虽然《论语》中“情”字仅两见,但《礼记》等书中却保留有大量孔子论“情”的话②,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孔子是主“情”论者③。孔子的这种重情思想,自然会影响到他对《诗》的评价与阐释。但由于历史汰选的结果,我们在《论语》孔子对《诗》的讨论中看不见他对《诗》与“情”关系的讨论,有的只是《诗》与礼,《诗》与修身关系的论述。所以以往对孔子《诗》学思想的讨论都集中在这一方面,而对于《诗》与“情”的关系却缺乏论述。现在,上博简《诗论》的发现适可弥补这方面的思想缺环。
评分《诗论》第1简:“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是《诗论》开宗明义之论,也是《诗论》的纲要。“诗亡离志”与《礼记·孔子闲居》之“志之所至,诗亦至焉”相协,而“乐亡离情”则点明了孔子对“诗”与“情”关系的认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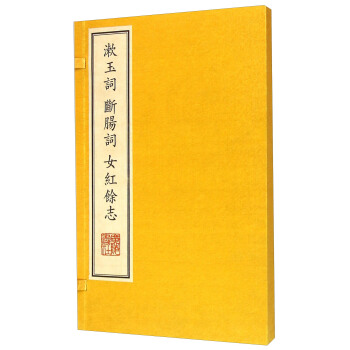

![让孩子受益一生的世界经典名著2(拼音版 套装共8册) [7-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32184/57d7bad3Nca43775e.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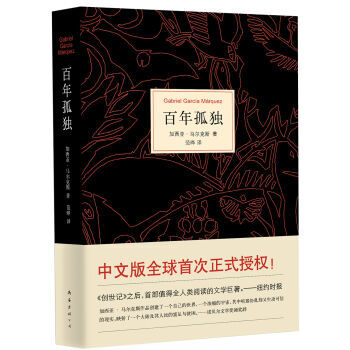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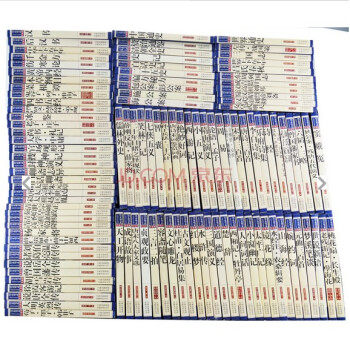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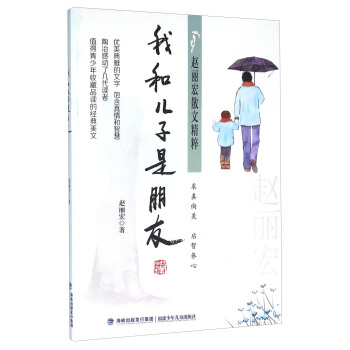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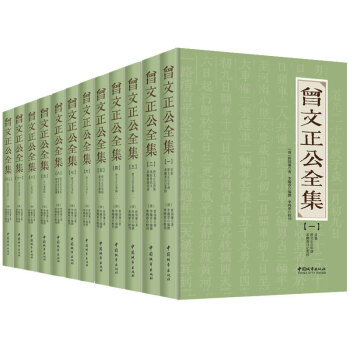
![寄小读者 [6-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06638/5743f15fNaed36e0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