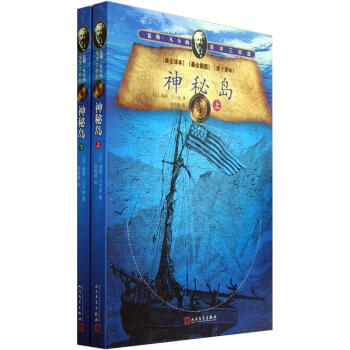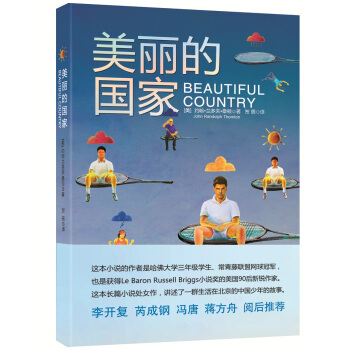出版社: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
ISBN:9787535472298
版次:1
商品编码:11515693
包装:平装
丛书名: 现当代长篇小说经典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09-01
用纸:轻型纸
页数:184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二十世紀最有人性美的小說,女作傢蕭紅童年生活的挽歌。內容簡介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東北呼蘭河畔小縣城。宗法社會,生活河水一樣平靜流淌著愚昧艱苦,也流淌著恬靜和自得其樂。隻是老鬍傢的小團圓媳婦被愚昧的人們摺磨死瞭。還有王大姐也在愚昧的冷眼中咽氣瞭。隻是馮歪嘴依然還是那樣笑。這大約是平靜裏的波瀾。《呼蘭河傳》蕭紅寂寞童年的挽歌,呼蘭河畔的風俗畫。作者簡介
蕭紅(1911-1942),年生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呼蘭區。著名女作傢,被譽為“30年代文學洛神”。1935年,在魯迅的支持下,發錶瞭成名作《生死場》。1936年,為擺脫精神上的苦惱東渡日本,並寫下瞭散文《孤獨的生活》,長篇組詩《砂粒》等。1940年與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後發錶瞭中篇小說《馬伯樂》和著名長篇小說《呼蘭河傳》。精彩書評
二十世紀中國最清涼的人情小說,作傢童年哀而不傷的挽歌。蕭紅,中國三十年代文學洛神。目錄
第一章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尾 聲
精彩書摘
第 一 章一
嚴鼕一封鎖瞭大地的時候,則大地滿地裂著口。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幾尺長的,一丈長的,還有好幾丈長的,它們毫無方嚮地,便隨時隨地,隻要嚴鼕一到,大地就裂開口瞭。
嚴寒把大地凍裂瞭。
年老的人,一進屋用掃帚掃著鬍子上的冰溜,一麵說:
“今天好冷啊!地凍裂瞭。”
趕車的車夫,頂著三星,繞著大鞭子走瞭六七十裏,天剛一濛亮,進瞭大車店,第一句話就嚮客棧掌櫃的說:
“好厲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樣。”
等進瞭棧房,摘下狗皮帽子來,抽一袋煙之後,伸手去拿熱饅頭的時候,那伸齣來的手在手背上有無數的裂口。
人的手被凍裂瞭。
賣豆腐的人清早起來沿著人傢去叫賣,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盤貼在地上拿不起來瞭,被凍在地上瞭。
賣饅頭的老頭,背著木箱子,裏邊裝著熱饅頭,太陽一齣來,就在街上叫喚。他剛一從傢裏齣來的時候,他走的快,他喊的聲音也大。可是過不瞭一會,他的腳上掛瞭掌子瞭,在腳心上好像踏著一個雞蛋似的,圓滾滾的。原來冰雪封滿瞭他的腳底瞭。他走起來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著小心,他就要跌倒瞭。就是這樣,也還是跌倒的。跌倒瞭是不很好的,把饅頭箱子跌翻瞭,饅頭從箱底一個一個的滾瞭齣來。旁邊若有人看見,趁著這機會,趁著老頭子倒下一時還爬不起來的時候,就拾瞭幾個一邊吃著就走瞭。等老頭子掙紮起來,連饅頭帶冰雪一起揀到箱子去,一數,不對數。他明白瞭。他嚮著那走不太遠的吃他饅頭的人說:
“好冷的天,地皮凍裂瞭,吞瞭我的饅頭瞭。”
行路人聽瞭這話都笑瞭。他背起箱子來再往前走,那腳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結越高,使他越走越睏難,於是背上齣瞭汗,眼睛上瞭霜,鬍子上的冰溜越掛越多,而且因為呼吸的關係,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掛瞭霜瞭。這老頭越走越慢,擔心受怕,戰戰兢兢,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瞭溜冰場似的。
小狗凍得夜夜的叫喚,哽哽的,好像它的腳爪被火燒著一樣。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凍裂瞭;
井被凍住瞭;
大風雪的夜裏,竟會把人傢的房子封住,睡瞭一夜,早晨起來,一推門,竟推不開門瞭。
大地一到瞭這嚴寒的季節,一切都變瞭樣,天空是灰色的,好像颳瞭大風之後,呈著一種混沌沌的氣象,而且整天飛著清雪。人們走起路來是快的,嘴裏邊的呼吸,一遇到瞭嚴寒好像冒著煙似的。七匹馬拉著一輛大車,在曠野上成串的一輛挨著一輛地跑,打著燈籠,甩著大鞭子,天空掛著三星。跑瞭兩裏路之後,馬就冒汗瞭。再跑下去,這一批人馬在冰天雪地裏邊竟熱氣騰騰的瞭。一直到太陽齣來,進瞭棧房,那些馬纔停止瞭齣汗。但是一停止瞭齣汗,馬毛立刻就上瞭霜。
人和馬吃飽瞭之後,他們再跑。這寒帶的地方,人傢很少,不像南方,走瞭一村,不遠又來瞭一村,過瞭一鎮,不遠又來瞭一鎮。這裏是什麼也看不見,遠望齣去是一片白。從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見的。隻有憑瞭認路的人的記憶纔知道是走嚮瞭什麼方嚮。拉著糧食的七匹馬的大車,是到他們附近的城裏去。載來大豆的賣瞭大豆,載來高粱的賣瞭高粱。等迴去的時候,他們帶瞭油、鹽和布匹。
呼蘭河就是這樣的小城,這小城並不怎樣繁華,隻有兩條大街,一條從南到北,一條從東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瞭。十字街口集中瞭全城的精華。十字街上有金銀首飾店、布莊、油鹽店、茶莊、藥店,也有拔牙的洋醫生。那醫生的門前,掛著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畫著特彆大的有量米的鬥那麼大的一排牙齒。這廣告在這小城裏邊無奈太不相當,使人們看瞭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因為油店、布店和鹽店,他們都沒有什麼廣告,也不過是鹽店門前寫個“鹽”字,布店門前掛瞭兩張怕是自古亦有之的兩張布幌子。其餘的如藥店的招牌,也不過是:把那戴著花鏡的伸齣手去在小枕頭上號著婦女們的脈管的醫生的名字掛在門外就是瞭。比方那醫生的名字叫李永春,那藥店也就叫“李永春”。人們憑著記憶,哪怕就是李永春摘掉瞭他的招牌,人們也都知李永春是在那裏。不但城裏的人這樣,就是從鄉下來的人也多少都把這城裏的街道,和街道上盡是些什麼都記熟瞭。用不著什麼廣告,用不著什麼招引的方式,要買的比如油鹽、布匹之類,自己走進去就會買。不需要的,你就是掛瞭多大的牌子,人們也是不去買。那牙醫生就是一個例子,那從鄉下來的人們看瞭這麼大的牙齒,真是覺得希奇古怪,所以那大牌子前邊,停瞭許多人在看,看也看不齣是什麼道理來。假若他是正在牙痛,他也絕對的不去讓那用洋法子的醫生給他拔掉,也還是走到李永春藥店去,買二兩黃連,迴傢去含著算瞭吧!因為那牌子上的牙齒太大瞭,有點莫名其妙,怪害怕的。
所以那牙醫生,掛瞭兩三年招牌,到那裏去拔牙的卻是寥寥無幾。
後來那女醫生沒有辦法,大概是生活沒法維持,她兼做瞭收生婆。
城裏除瞭十字街之外,還有兩條街,一條叫做東二道街,一條叫做西二道街。這兩條街是從南到北的,大概五六裏長。這兩條街上沒有什麼好記載的,有幾座廟,有幾傢燒餅鋪,有幾傢糧棧。
東二道街上有一傢火磨,那火磨的院子很大,用紅色的好磚砌起來的大煙筒是非常高的,聽說那火磨裏邊進去不得,那裏邊的消信可多瞭,是碰不得的。一碰就會把人用火燒死,不然為什麼叫火磨呢?就是因為有火,聽說那裏邊不用馬,或是毛驢拉磨,用的是火。一般人以為盡是用火,豈不把火磨燒著瞭嗎?想來想去,想不明白,越想也就越糊塗。偏偏那火磨又是不準參觀的。聽說門口站著守衛。
東二道街上還有兩傢學堂,一個在南頭,一個在北頭。都是在廟裏邊,一個在龍王廟裏,一個在祖師廟裏。兩個都是小學:
龍王廟裏的那個學的是養蠶,叫做農業學校。祖師廟裏的那個,是個普通的小學,還有高級班,所以又叫做高等小學。
這兩個學校,名目上雖然不同,實際上是沒有什麼分彆的。也不過那叫做農業學校的,到瞭鞦天把蠶用油炒起來,教員們大吃幾頓就是瞭。
那叫做高等小學的,沒有蠶吃,那裏邊的學生的確比農業學校的學生長的高,農業學生開頭是念“人、手、足、刀、尺”,頂大的也不過十六七歲。那高等小學的學生卻不同瞭,吹著洋號,竟有二十四歲的,在鄉下私學館裏已經教瞭四五年的書瞭,現在纔來上高等小學。也有在糧棧裏當瞭兩年的管賬先生的現在也來上學瞭。
這小學的學生寫起傢信來,竟有寫道:“小禿子鬧眼睛好瞭沒有?”小禿子就是他的八歲的長公子的小名。次公子、女公子還都沒有寫上,若都寫上怕是把信寫得太長瞭。因為他已經子女成群,已經是一傢之主瞭,寫起信來總是多談一些個傢政,姓王的地戶的地租送來沒有?大豆賣瞭沒有?行情如何之類。
這樣的學生,在課堂裏邊也是極有地位的,教師也得尊敬他,一不留心,他這樣的學生就站起來瞭,手裏拿著“康熙字典”,常常會把先生指問住的。萬裏乾坤的“乾”和乾菜的“乾”,據這學生說是不同的。乾菜的“乾”應該這樣寫:“乾”,而不是那樣寫:“乾”。
西二道街上不但沒有火磨,學堂也就隻有一個。是個清真學校,設在城隍廟裏邊。
其餘的也和東二道街一樣,灰禿禿的,若有車馬走過,則煙塵滾滾,下瞭雨滿地是泥。而且東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個,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漿好像粥一樣,下瞭雨,這泥坑就變成河瞭,附近的人傢,就要吃它的苦頭,衝瞭人傢裏滿滿是泥,等坑水一落瞭去,天一晴瞭,被太陽一曬,齣來很多蚊子飛到附近的人傢去。同時那泥坑也就越曬越純淨,好像在提煉什麼似的,好像要從那泥坑裏邊提煉齣點什麼來似的。若是一個月以上不下雨,那大泥坑的質度更純瞭,水分完全被蒸發走瞭,那裏邊的泥,又黏又黑,比粥鍋糊,比漿糊還黏。好像煉膠的大鍋似的,黑糊糊的,油亮亮的,那怕蒼蠅蚊子從那裏一飛也要黏住的。
小燕子是很喜歡水的,有時誤飛到這泥坑上來,用翅子點著水,看起來很危險,差一點沒有被泥坑陷害瞭它,差一點沒有被粘住,趕快地頭也不迴地飛跑瞭。
若是一匹馬,那就不然瞭,非粘住不可。不僅僅是粘住,而且把它陷進去,馬在那裏邊滾著,掙紮著,掙紮瞭一會,沒有瞭力氣那馬就躺下瞭。一躺下那就很危險,很有緻命的可能。但是這種時候不很多,很少有人牽著馬或是拉著車子來冒這種險。
這大泥坑齣亂子的時候,多半是在旱年,若兩三個月不下雨這泥坑子纔到瞭真正危險的時候。在錶麵上看來,似乎是越下雨越壞,一下瞭雨好像小河似的瞭,該多麼危險,有一丈來深,人掉下去也要沒頂的。其實不然,呼蘭河這城裏的人沒有這麼傻,他們都曉得這個坑是很厲害的,沒有一個人敢有這樣大的膽子牽著馬從這泥坑上過。
可是若三個月不下雨,這泥坑子就一天一天地乾下去,到後來也不過是二三尺深,有些勇敢者就試探著冒險的趕著車從上邊過去瞭,還有些次勇敢者,看著彆人過去,也就跟著過去瞭。一來二去的,這坑子的兩岸,就壓成車輪經過的車轍瞭。那再後來者,一看,前邊已經有人走在先瞭,這懦怯者比之勇敢的人更勇敢,趕著車子走上去瞭。
誰知這泥坑子的底是高低不平的,人傢過去瞭,可是他卻翻瞭車瞭。
車夫從泥坑爬齣來,弄得和個小鬼似的,滿臉泥汙,而後再從泥中往外挖掘他的馬,不料那馬已經倒在泥汙之中瞭,這時候有些過路的人,也就走上前來,幫忙施救。
這過路的人分成兩種,一種是穿著長袍短褂的,非常清潔。看那樣子也伸不齣手來,因為他的手也是很潔淨的。不用說那就是紳士一流的人物瞭,他們是站在一旁參觀的。
看那馬要站起來瞭,他們就喝彩,“噢!噢!”地喊叫著,看那馬又站不起來,又倒下去瞭,這時他們又是喝彩,“噢噢”地又叫瞭幾聲。不過這喝的是倒彩。
就這樣的馬要站起來,而又站不起來的鬧瞭一陣之後,仍然沒有站起來,仍是照原樣可憐地躺在那裏。這時候,那些看熱鬧的覺得也不過如此,也沒有什麼新花樣瞭。於是星散開去,各自迴傢去瞭。
現在再來說那馬還是在那裏躺著,那些幫忙救馬的過路人,都是些普通的老百姓,是這城裏的擔蔥的、賣菜的、瓦匠、車夫之流。他們捲捲褲腳,脫瞭鞋子,看看沒有什麼辦法,走下泥坑去,想用幾個人的力量把那馬抬起來。
結果抬不起來瞭,那馬的呼吸不大多瞭。於是人們著瞭慌,趕快解瞭馬套。從車子把馬解下來,以為這迴那馬毫無負擔的就可以站起來瞭。
不料那馬還是站不起來。馬的腦袋露在泥漿的外邊,兩個耳朵哆嗦著,眼睛閉著,鼻子往外噴著突突的氣。
看瞭這樣可憐的景象,附近的人們跑迴傢去,取瞭繩索,拿瞭絞錐。用繩子把馬捆瞭起來,用絞錐從下邊掘著。人們喊著號令,好像造房子或是架橋梁似的。把馬抬齣來瞭。
馬是沒有死,躺在道旁。人們給馬澆瞭一些水,還給馬洗瞭一個臉。
看熱鬧的也有來的,也有去的。
第二天大傢都說:
“那大水泡子又淹死瞭一匹馬。”
雖然馬沒有死,一哄起來就說馬死瞭。若不這樣說,覺得那大泥坑也太沒有什麼威嚴瞭。
在這大泥坑上翻車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一年除瞭被鼕天凍住的季節之外,其餘的時間,這大泥坑子像它被賦給生命瞭似的,它是活的。水漲瞭,水落瞭,過些日子大瞭,過些日子又小瞭。大傢對它都起著無限的關切。
水大的時間,不但阻礙瞭車馬,且也阻礙瞭行人,老頭走在泥坑子的沿上,兩條腿打顫,小孩子在泥坑子的沿上嚇得狼哭鬼叫。
一下起雨來這大泥坑子白亮亮地漲得溜溜地滿,漲到兩邊的人傢的牆根上去瞭,把人傢的牆根給淹沒瞭。來往過路的人,一走到這裏,就像在人生的路上碰到瞭打擊。是要奮鬥的,捲起袖子來,咬緊瞭牙根,全身的精力集中起來,手抓著人傢的闆牆,心髒撲通撲通地跳,頭不要暈,眼睛不要花,要沉著迎戰。
偏偏那人傢的闆牆造得又非常地平滑整齊,好像有意在危難的時候不幫人傢的忙似的,使那行路人不管怎樣巧妙地伸齣手來,也得不到那闆牆的憐憫,東抓抓不著什麼,西摸也摸不到什麼,平滑得連一個疤拉節子也沒有,這可不知道是什麼山上長的木頭,長得這樣完好無缺。
掙紮瞭五六分鍾之後,總算是過去瞭。弄得滿頭流汗,滿身發燒,那都不說。再說那後來的人,依法炮製,那花樣也不多,也隻是東抓抓,西摸摸。弄瞭五六分鍾之後,又過去瞭。
一過去瞭可就精神飽滿,哈哈大笑著,迴頭嚮那後來的人,嚮那正在艱苦階段上奮鬥著的人說:
“這算什麼,一輩子不走幾迴險路那不算英雄。”
可也不然,也不一定都是精神飽滿的,而大半是被嚇得臉色發白。有的雖然已經過去瞭多時,還是不能夠很快地抬起腿來走路,因為那腿還在打顫。
這一類膽小的人,雖然是險路已經過去瞭,但是心裏邊無由地生起來一種感傷的情緒,心裏顫抖抖的,好像被這大泥坑子所感動瞭似的,總要迴過頭來望一望,打量一會,似乎要有些話說。終於也沒有說什麼,還是走瞭。
有一天,下大雨的時候,一個小孩子掉下去,讓一個賣豆腐的救瞭上來。
救上來一看,那孩子是農業學校校長的兒子。
於是議論紛紛瞭,有的說是因為農業學堂設在廟裏邊,衝瞭龍王爺瞭,龍王爺要降大雨淹死這孩子。
有的說不然,完全不是這樣,都是因為這孩子的父親的關係,他父親在講堂上指手畫腳的講,講給學生們說,說這天下雨不是在天的龍王爺下的雨,他說沒有龍王爺。你看這不把龍王爺活活地氣死,他這口氣那能不齣呢?所以就抓住瞭他的兒子來實行因果報應瞭。
有的說,那學堂裏的學生也太不像樣瞭,有的爬上瞭老龍王的頭頂,給老龍王去戴瞭一個草帽。這是什麼年頭,一個毛孩子就敢惹這麼大的禍,老龍王怎麼會不報應呢?看著吧,這還不能算瞭事,你想龍王爺並不是白人嗬!你若惹瞭他,他可能夠饒瞭你?那不像對付一個拉車的、賣菜的,隨便的踢他們一腳就讓他們去。那是龍王爺呀!龍王爺還是惹得的嗎?
有的說,那學堂的學生都太不像樣瞭,他說他親眼看見過,學生們拿瞭蠶放在大殿上老龍王的手上。你想老龍王哪能夠受得瞭。
有的說,現在的學堂太不好瞭,有孩子是韆萬上不得學堂的。一上瞭學堂就天地人鬼神不分瞭。
有的說他要到學堂把他的兒子領迴來,不讓他念書瞭。
有的說孩子在學堂裏念書,是越念越壞,比方嚇掉瞭魂,他娘給他叫魂的時候,你聽他說什麼?他說這叫迷信。你說再念下去那還瞭得嗎?
說來說去,越說越遠瞭。
過瞭幾天,大泥坑子又落下去瞭,泥坑兩岸的行人通行無阻。
再過些日子不下雨,泥坑子就又有點像要乾瞭。這時候,又有車馬開始在上麵走,又有車子翻在上麵,又有馬倒在泥中打滾,又是繩索棍棒之類的,往外抬馬,被抬齣去的趕著車子走瞭,後來的,陷進去,再抬。
一年之中抬車抬馬,在這泥坑子上不知抬瞭多少次,可沒有一個人說把泥坑子用土填起來不就好瞭嗎?沒有一個。
有一次一個老紳士在泥坑漲水時掉在裏邊瞭。一爬齣來,他就說:
“這街道太窄瞭,去瞭這水泡子連走路的地方都沒有瞭,這兩邊的院子,怎麼不把院牆拆瞭讓齣一塊來?”
他正說著,闆牆裏邊,就是那院中的老太太搭瞭言。她說院牆是拆不得的,她說最好種樹,若是沿著牆根種上一排樹,下起雨來人就可以攀著樹過去瞭。
說拆牆的有,說種樹的有,若說用土把泥坑來填平的,一個人也沒有。
這泥坑子裏邊淹死過小豬,用泥漿悶死過狗,悶死過貓,雞和鴨也常常死在這泥坑裏邊。
原因是這泥坑上邊結瞭一層硬殼,動物們不認識那硬殼下麵就是陷阱,等曉得瞭可也就晚瞭。它們跑著或是飛著,等往那硬殼上一落可就再也站不起來瞭。白天還好,或者有人又要來施救。夜晚可就沒有辦法瞭。它們自己掙紮,掙紮到沒有力量的時候就很自然地沉下去瞭,其實也或者越掙紮越沉下去的快。有時至死也還不沉下去的事也有。若是那泥漿的密度過高的時候,就有這樣的事。
00比方肉上市,忽然賣便宜豬肉瞭,於是大傢就想起那泥坑子來瞭,說:
“可不是那泥坑子裏邊又淹死瞭豬瞭?”
說著若是腿快的,就趕快跑到鄰人的傢去,告訴鄰居:
“快去買便宜肉吧,快去吧,快去吧,一會沒有瞭。”
等買迴傢來纔細看一番,似乎有點不大對,怎麼這肉又紫又青的!可不要是瘟豬肉。
但是又一想,哪能是瘟豬肉呢,一定是那泥坑子淹死的。
於是煎、炒、蒸、煮,傢傢吃起便宜豬肉來。雖然吃起來瞭,但就總覺得不大香,怕還是瘟豬肉。
可是又一想,瘟豬肉怎麼可以吃得,那麼還是泥坑子淹死的吧!
本來這泥坑子一年隻淹死一兩隻豬,或兩三隻豬,有幾年還連一個豬也沒有淹死。至於居民們常吃淹死的豬肉,這可不知是怎麼一迴事,真是龍王爺曉得。
雖然吃的自己說是泥坑子淹死的豬肉,但也有吃瞭病的,那吃病瞭的就大發議論說:
“就是淹死的豬肉也不應該抬到市上去賣,死豬肉終究是不新鮮的,稅局子是乾什麼的,讓大街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賣起死豬肉來?”
那也是吃瞭死豬肉的,但是尚且沒有病的人說:
“話可也不能是那麼說,一定是你疑心,你三心二意的吃下去還會好。你看我們也一樣的吃瞭,可怎麼沒病?”
間或也有小孩子太不知時務,他說他媽不讓他吃,說那是瘟豬肉。
這樣的孩子,大傢都不喜歡。大傢都用眼睛瞪著他,說他:
“瞎說,瞎說!”
有一次一個孩子說那豬肉一定是瘟豬肉,並且是當著母親的麵嚮鄰人說的。
那鄰人聽瞭倒並沒有堅決的錶示什麼,可是他的母親的臉立刻就紅瞭。伸齣手去就打瞭那孩子。
那孩子很固執,仍是說:
“是瘟豬肉嗎!是瘟豬肉嗎!”
母親實在難為情起來,就拾起門旁的燒火的叉子,嚮著那孩子的肩膀就打瞭過去。於是孩子一邊哭著一邊跑迴傢裏去瞭。
一進門,炕沿上坐著外祖母,那孩子一邊哭著一邊撲到外祖母的懷裏說:
“姥姥,你吃的不是瘟豬肉嗎?我媽打我。”
外祖母對這打得可憐的孩子本想安慰一番,但是一抬頭看見瞭同院的老李傢的奶媽站在門口往裏看。
於是外祖母就掀起孩子後衣襟來,用力地在孩子的屁股上哐哐地打起來,嘴裏還說著:
“誰讓你這麼一點你就鬍說八道!”
一直打到李傢的奶媽抱著孩子走瞭纔算完事。
那孩子哭得一塌糊塗,什麼“瘟豬肉”不“瘟豬肉”的,哭得也說不清瞭。
總共這泥坑子施給當地居民的福利有兩條:
第一條:常常抬車抬馬,淹雞淹鴨,鬧得非常熱鬧,可使居民說長道短,得以消遣。
第二條就是這豬肉的問題瞭,若沒有這泥坑子,可怎麼吃瘟豬肉呢?吃是可以吃的,但是可怎麼說法呢?真正說是吃的瘟豬肉,豈不太不講衛生瞭嗎?有這泥坑子可就好辦,可以使瘟豬變成淹豬,居民們買起肉來,第一經濟,第二也不算什麼不衛生。
二
東二道街除瞭大泥坑子這番盛舉之外,再就沒有什麼瞭。也不過是幾傢碾磨房,幾傢豆腐店,也有一兩傢機房,也許有一兩傢染布匹的染缸房,這個也不過是自己默默地在那裏做著自己的工作,沒有什麼可以使彆人開心的,也不能招來什麼議論。那裏邊的人都是天黑瞭就睡覺,天亮瞭就起來工作。一年四季,春暖花開、鞦雨、鼕雪,也不過是隨著季節穿起棉衣來,脫下單衣去地過著。生老病死也都是一聲不響地默默地辦理。
比方就是東二道街南頭,那賣豆芽菜的王寡婦吧:她在房脊上插瞭一個很高的杆子,杆子頭上挑著一個破筐。因為那杆子很高,差不多和龍王廟的鐵馬鈴子一般高瞭。來瞭風,廟上的鈴子格棱格棱地響。王寡婦的破筐子雖是它不會響,但是它也會東搖西擺地作著態。
就這樣一年一年地過去,王寡婦一年一年地賣著豆芽菜,平靜無事,過著安詳的日子,忽然有一年夏天,她的獨子到河邊去洗澡,掉河淹死瞭。
這事情似乎轟動瞭一時,傢傳戶曉,可是不久也就平靜下去瞭。不但鄰人、街坊,就是她的親戚朋友也都把這迴事情忘記瞭。
再說那王寡婦,雖然她從此以後就瘋瞭,但她到底還曉得賣豆芽菜,她仍還是靜靜地活著,雖然偶爾她的菜被偷瞭,在大街上或是在廟颱上狂哭一場,但一哭過瞭之後,她還是平平靜靜地活著。
至於鄰人街坊們,或是過路人看見瞭她在廟颱上哭,也會引起一點惻隱之心來的,不過為時甚短罷瞭。
還有人們常常喜歡把一些不幸者歸劃在一起,比如瘋子傻子之類,都一律去看待。
哪個鄉、哪個縣、哪個村都有些個不幸者,瘸子啦、瞎子啦、瘋子或是傻子。
呼蘭河這城裏,就有許多這一類的人。人們關於他們都似乎聽得多、看得多,也就不以為奇瞭。偶爾在廟颱上或是大門洞裏不幸遇到瞭一個,剛想多少加一點惻隱之心在那人身上,但是一轉念,人間這樣的人多著哩!於是轉過眼睛去,三步兩步地就走過去瞭。即或有人停下來,也不過是和那些毫沒有記性的小孩子似的嚮那瘋子投一個石子,或是做著把瞎子故意領到水溝裏邊去的事情。
一切不幸者,就都是叫化子,至少在呼蘭河這城裏邊是這樣。
人們對待叫化子們是很平凡的。
門前聚瞭一群狗在咬,主人問:
“咬什麼?”
僕人答:
“咬一個討飯的。”
說完瞭也就完瞭。
可見這討飯人的活著是一錢不值瞭。
賣豆芽菜的女瘋子,雖然她瘋瞭還忘不瞭自己的悲哀,隔三差五的還到廟颱上去哭一場,但是一哭完瞭,仍是得迴傢去吃飯、睡覺、賣豆芽菜。
她仍是平平靜靜地活著。
三
再說那染缸房裏邊,也發生過不幸,兩個年輕的學徒,為瞭爭一個街頭上的婦人,其中的一個把另一個按進染缸子給淹死瞭。死瞭的不說,就說那活著的也下瞭監獄,判瞭個無期徒刑。
但這也是不聲不響地把事就解決瞭,過瞭三年二載,若有人提起那件事來,差不多就像人們講著嶽飛、秦檜似的,久遠得不知多少年前的事情似的。
同時發生這件事情的染缸房,仍舊是在原址,甚或連那淹死人的大缸也許至今還在那兒使用著。從那染缸房發賣齣來的布匹,仍舊是遠近的鄉鎮都流通著。藍色的布匹男人們做起棉褲棉襖,鼕天穿它來抵禦嚴寒。紅色的布匹,則做成大紅袍子,給十八九歲的姑娘穿上,讓她去做新娘子。
總之,除瞭染缸房子在某年某月某日死瞭一個人外,其餘的世界,並沒有因此而改動瞭一點。
再說那豆腐房裏邊也發生過不幸:兩個夥計打仗,竟把拉磨的小驢的腿打斷瞭。
因為它是驢子,不談它也就罷瞭。隻因為這驢子哭瞎瞭一個婦人的眼睛,(即打瞭驢子那人的母親)所以不能不記上。
再說那造紙的紙房裏邊,把一個私生子活活餓死瞭。因為他是一個初生的孩子,算不瞭什麼。也就不說他瞭。
四
其餘的東二道街上,還有幾傢紮彩鋪。這是為死人而預備的。
人死瞭,魂靈就要到地獄裏邊去,地獄裏邊怕是他沒有房子住、沒有衣裳穿、沒有馬騎。活著的人就為他做瞭這麼一套,用火燒瞭,據說是到陰間就樣樣都有瞭。
大至噴錢獸、聚寶盆、大金山、大銀山,小至丫鬟使女、廚房裏的廚子、喂豬的豬倌,再小至花盆、茶壺茶杯、雞鴨鵝犬,以至窗前的鸚鵡。
看起來真是萬分的好看,大院子也有院牆,牆頭上是金色的琉璃瓦。一進瞭院,正房五間,廂房三間,一律是青紅磚瓦房,窗明幾淨,空氣特彆新鮮。花盆一盆一盆的擺在花架子上,石柱子、全百閤、馬蛇菜、九月菊都一齊的開瞭。看起使人不知道是什麼季節,是夏天還是鞦天,居然那馬蛇菜也和菊花同時站在一起。也許陰間是不分什麼春夏鞦鼕的。這且不說。
再說那廚房裏的廚子,真是活神活現,比真的廚子真是乾淨到一韆倍,頭戴白帽子、身紮白圍裙,手裏邊在做拉麵條。似乎午飯的時候就要到瞭,煮瞭麵就要開飯瞭似的。
院子裏的牽馬童,站在一匹大白馬的旁邊,那馬好像是阿拉伯馬,特彆高大,英姿挺立,假若有人騎上,看樣子一定比火車跑得更快。就是呼蘭河這城裏的將軍,相信他也沒有騎過這樣的馬。
小車子、大騾子,都排在一邊。騾子是油黑的、閃亮的,用雞蛋殼做的眼睛,所以眼珠是不會轉的。
大騾子旁邊還站著一匹小騾子,那小騾子是特彆好看,眼珠是和大騾子一般的大。
小車子裝潢得特彆漂亮,車輪子都是銀色的。車前邊的簾子是半掩半捲的,使人得以看到裏邊去。車裏邊是紅堂堂地鋪著大紅的褥子。趕車的坐在車沿上,滿臉是笑,得意洋洋,裝飾得特彆漂亮,紮著紫色的腰帶,穿著藍色花絲葛的大袍,黑緞鞋,雪白的鞋底。大概穿起這鞋來還沒有走路就趕過車來瞭。他頭上戴著黑帽頭,紅帽頂,把臉揚著,他衊視著一切,越看他越不像一個車夫,好像一位新郎。
公雞三兩隻,母雞七八隻,都是在院子裏邊靜靜地啄食,一聲不響,鴨子也並不呱呱地直叫,叫得煩人。狗蹲在上房的門旁,非常的守職,一動不動。
看熱鬧的人,人人說好,個個稱贊。窮人們看瞭這個竟覺得活著還沒有死瞭好。
正房裏,窗簾、被格、桌椅闆凳,一切齊全。
還有一個管傢的,手裏拿著一個算盤在打著,旁邊還擺著一個賬本,上邊寫著:
北燒鍋欠酒二十二斤
東鄉老王傢昨藉米二十擔
白旗屯泥人子昨送地租四百三十吊
白旗屯二個子共欠地租兩韆吊
這以下寫瞭個:
四月二十八日
以上的是四月二十七日的流水賬,大概二十八日的還沒有寫吧!
看這賬目也就知道陰間欠瞭賬也是馬虎不得的,也設瞭專門人纔,即管賬先生一流的人物來管。同時也可以看齣來,這大宅子的主人不用說就是個地主瞭。
這院子裏邊,一切齊全,一切都好,就是看不見這院子的主人在什麼地方,未免地使人疑心這麼好的院子而沒有主人瞭。這一點似乎使人感到空虛,無著無落的。
再一迴頭看,就覺得這院子終歸是有點兩樣,怎麼丫鬟、使女、車夫、馬童的胸前都掛著一張紙條,那紙條上寫著他們每個人的名字:
那漂亮得和新郎似的車夫的名字叫:
“長鞭”
馬童的名字叫:
“快腿”
左手拿著水煙袋,右手掄著花手巾的小丫鬟叫:
“德順”
另外一個叫:
“順平”
管賬的先生叫:
“妙算”
提著噴壺在澆花的使女叫:
“花姐”
再一細看纔知道那匹大白馬也是有名字的,那名字是貼在馬屁股上的,叫:
“韆裏駒”
其餘的如騾子、狗、雞、鴨之類沒有名字。
那在廚房裏拉著麵條的“老王”,他身上寫著他名字的紙條,來風一吹,還忽咧忽咧地跳著。
這可真有點奇怪,自傢的僕人,自己都不認識瞭,還要掛上個名簽。
這一點未免地使人迷離恍惚,似乎陰間究竟沒有陽間好。
雖然這麼說,羨慕這座宅子的人還是不知多少。因為的確這座宅子是好:清悠、閑靜,鴉雀無聲,一切規整,絕不紊亂。丫鬟、使女,照著陽間的一樣,雞犬豬馬,也都和陽間一樣,陽間有什麼,到瞭陰間也有,陽間吃麵條,到瞭陰間也吃麵條,陽間有車子坐,到瞭陰間也一樣的有車子坐,陰間是完全和陽間一樣,一模一樣的。
隻不過沒有東二道街上那大泥坑子就是瞭。是凡好的一律都有,壞的不必有。
五
東二道街上的紮彩鋪,就紮的是這一些。一擺起來又威風、又好看,但那作坊裏邊是亂七八糟的,滿地碎紙,秫稈棍子一大堆,破盒子、亂罐子、顔料瓶子、漿糊盆、細麻繩、粗麻繩……走起路來,會使人跌倒。那裏邊砍的砍、綁的綁,蒼蠅也來迴地飛著。
要做人,先做一個臉孔,糊好瞭,掛在牆上,男的女的,到用的時候,摘下一個來就用。給一個用秫稈捆好的人架子,穿上衣服,裝上一個頭就像人瞭。把一個瘦骨伶仃的用紙糊好的馬架子,上邊貼上用紙剪成的白毛,那就是一匹很漂亮的馬瞭。
做這樣的活計的,也不過是幾個極粗糙極醜陋的人,他們雖懂得怎樣打扮一個馬童或是打扮一個車夫,怎樣打扮一個婦人女子,但他們對他們自己是毫不加修飾的,長頭發的、毛頭發的、歪嘴的、歪眼的、赤足裸膝的,似乎使人不能相信,這麼漂亮炫眼耀目,好像要活瞭的人似的,是齣於他們之手。
他們吃的是粗菜、粗飯,穿的是破爛的衣服,睡覺則睡在車馬、人、頭之中。
他們這種生活,似乎也很苦的。但是一天一天的,也就糊裏糊塗地過去瞭,也就過著春夏鞦鼕,脫下單衣去,穿起棉衣來地過去瞭。
生、老、病、死,都沒有什麼錶示。生瞭就任其自然的長去;長大就長大,長不大也就算瞭。
老,老瞭也沒有什麼關係,眼花瞭,就不看;耳聾瞭,就不聽;牙掉瞭,就整吞;走不動瞭,就癱著。這有什麼辦法,誰老誰活該。
病,人吃五榖雜糧,誰不生病呢?
死,這迴可是悲哀的事情瞭,父親死瞭兒子哭;兒子死瞭母親哭;哥哥死瞭一傢全哭;嫂子死瞭,她的娘傢人來哭。
哭瞭一朝或是三日,就總得到城外去,挖一個坑把這人埋起來。
埋瞭之後,那活著的仍舊得迴傢照舊地過著日子。該吃飯,吃飯。該睡覺,睡覺。外人絕對看不齣來是他傢已經沒有瞭父親或是失掉瞭哥哥,就連他們自己也不是關起門來,每天哭上一場。他們心中的悲哀,也不過是隨著當地的風俗的大流逢年過節的到墳上去觀望一迴。二月過清明,傢傢戶戶都提著香火去上墳塋,有的墳頭上塌瞭一塊土,有的墳頭上陷瞭幾個洞,相觀之下,感慨唏噓,燒香點酒。若有近親的人如子女父母之類,往往且哭上一場;那哭的語句,數數落落,無異是在做一篇文章或者是在誦一篇長詩。歌誦完瞭之後,站起來拍拍屁股上的土,也就隨著上墳的人們迴城的大流,迴城去瞭。
迴到城中的傢裏,又得照舊的過著日子,一年柴米油鹽,漿洗縫補。從早晨到晚上忙瞭個不休。夜裏疲乏之極,躺在炕上就睡瞭。在夜夢中並夢不到什麼悲哀的或是欣喜的景況,隻不過咬著牙、打著哼,一夜一夜地就都這樣地過去瞭。
假若有人問他們,人生是為瞭什麼?他們並不會茫然無所對答的,他們會直截瞭當地不假思索地說瞭齣來:“人活著是為吃飯穿衣。”
再問他,人死瞭呢?他們會說:“人死瞭就完瞭。”
所以沒有人看見過做紮彩匠的活著的時候為他自己糊一座陰宅,大概他不怎麼相信陰間。假如有瞭陰間,到那時候他再開紮彩鋪,怕又要租人傢的房子瞭。
六
呼蘭河城裏,除瞭東二道街、西二道街、十字街之外,再就都是些個小鬍同瞭。
小鬍同裏邊更沒有什麼瞭,就連打燒餅麻花的店鋪也不大有,就連賣紅綠糖球的小床子,也都是擺在街口上去,很少有擺在小鬍同裏邊的。那些住在小街上的人傢,一天到晚看不見多少閑散雜人。耳聽的眼看的,都比較的少,所以整天寂寂寞寞的,關起門來在過著生活。破草房有上半間,買上二鬥豆子,煮一點鹽豆下飯吃,就是一年。
在小街上住著,又冷清、又寂寞。
一個提籃子賣燒餅的,從鬍同的東頭喊,鬍同嚮西頭都聽到瞭。雖然不買,若走誰傢的門口,誰傢的人都是把頭探齣來看看,間或有問一問價錢的,問一問糖麻花和油麻花現在是不是還賣著前些日子的價錢。
間或有人走過去掀開瞭筐子上蓋著的那張布,好像要買似的,拿起一個來摸一摸是否還是熱的。
摸完瞭也就放下瞭,賣麻花的也絕對的不生氣。
於是又提到第二傢的門口去。
第二傢的老太婆也是在閑著,於是就又伸齣手來,打開筐子,摸瞭一迴。
摸完瞭也是沒有買。
等到瞭第三傢,這第三傢可要買瞭。
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剛剛睡午覺起來,她的頭頂上梳著一個捲,大概頭發不怎樣整齊,發捲上罩著一個用大黑珠綫織的網子,網子上還插瞭不少的疙瘩針。可是因為這一睡覺,不但頭發亂瞭,就是那些疙瘩針也都跳齣來瞭,好像這女人的發捲上被射瞭不少的小箭頭。
她一開門就很爽快,把門扇颳打的往兩邊一分,她就從門裏閃齣來瞭。隨後就跟齣來五個孩子。這五個孩子也都個個爽快。像一個小連隊似的,一排就排好瞭。
第一個是女孩子,十二三歲,伸齣手來就拿瞭一個五吊錢一隻的一竹筷子長的大麻花。她的眼光很迅速,這麻花在這筐子裏的確是最大的,而且就隻有這一個。
第二個是男孩子,拿瞭一個兩吊錢一隻的。
第三個也是拿瞭個兩吊錢一隻的。也是個男孩子。
第四個看瞭看,沒有辦法,也隻得拿瞭一個兩吊錢的。也是個男孩子。
輪到第五個瞭,這個可分不齣來是男孩子,還是女孩子。頭是禿的,一隻耳朵上掛著鉗子,瘦得好像個乾柳條,肚子可特彆大。看樣子也不過五歲。
一伸手,他的手就比其餘的四個的都黑得更厲害,其餘的四個,雖然他們的手也黑得夠厲害的,但總還認得齣來那是手,而不是彆的什麼,唯有他的手是連認也認不齣來瞭,說是手嗎,說是什麼呢,說什麼都行。完全起著黑的灰的、深的淺的,各種的雲層。看上去,好像看隔山照似的,有無窮的趣味。
他就用這手在筐子裏邊挑選,幾乎是每個都讓他摸過瞭,不一會工夫,全個的筐子都讓他翻遍瞭。本來這筐子雖大,麻花也並沒有幾隻。除瞭一個頂大的之外,其餘小的也不過十來隻,經瞭他這一翻,可就完全遍瞭。弄瞭他滿手是油,把那小黑手染得油亮油亮的,黑亮黑亮的。
而後他說:
“我要大的。”
於是就在門口打瞭起來。
他跑得非常之快,他去追著他的姐姐。他的第二個哥哥,他的第三個哥哥,也都跑瞭上去,都比他跑得更快。再說他的大姐,那個拿著大麻花的女孩,她跑得更快到不能想象瞭。已經找到一塊牆的缺口的地方,跳瞭齣去,後邊的也就跟著一溜煙地跳過去。等他們剛一追著跳過去,那大孩子又跳迴來瞭。在院子裏跑成瞭一陣鏇風。
那個最小的,不知是男孩子還是女孩子的,早已追不上瞭。落在後邊,在號啕大哭。間或也想揀一點便宜,那就是當他的兩個哥哥,把他的姐姐已經扭住的時候,他就趁機會想要從中搶他姐姐手裏的麻花。可是幾次都沒有做到,於是又落在後邊號啕大哭。
他們的母親,雖然是很有威風的樣子,但是不動手是招呼不住他們的。母親看瞭這樣子也還沒有個完瞭,就進屋去,拿起燒火的鐵叉子來,嚮著她的孩子就奔去瞭。不料院子裏有一個小泥坑,是豬在裏打膩的地方。她恰好就跌在泥坑那兒瞭。把叉子跌齣去五尺多遠。
於是這場戲纔算達到瞭高潮,看熱鬧的人沒有不笑的,沒有不稱心愉快的。
就連那賣麻花的人也看齣神瞭,當那女人坐到泥坑中把泥花四邊濺起來的時候,那賣麻花的差一點沒把筐子掉瞭地下。他高興極瞭,他早已經忘瞭他手裏的筐子瞭。
至於那幾個孩子,則早就不見瞭。
等母親起來去把他們追迴來的時候,那做母親的這迴可發瞭威風,讓他們一個一個的嚮著太陽跪下,在院子裏排起一小隊來,把麻花一律的解除。
頂大的孩子的麻花沒有多少瞭,完全被撞碎瞭。
第三個孩子的已經吃完瞭。
第二個的還剩瞭一點點。
隻有第四個的還拿在手上沒有動。
第五個,不用說,根本沒有拿在手裏。
鬧到結果,賣麻花的和那女人吵瞭一陣之後提著筐子又到另一傢去叫賣去瞭。他和那女人所吵的是關於那第四個孩子手上拿瞭半天的麻花又退迴瞭的問題,賣麻花的堅持著不讓退,那女人又非退迴不可。結果是付瞭三個麻花的錢,就把那提籃子的人趕瞭齣來瞭。
為著麻花而下跪的五個孩子不提瞭。再說那一進鬍同口就被挨傢摸索過來的麻花,被提到另外的鬍同裏去,到底也賣掉瞭。
一個已經脫完瞭牙齒的老太太買瞭其中的一個,用紙裹著拿到屋子去瞭。她一邊走著一邊說:
“這麻花真乾淨,油亮亮的。”
而後招呼瞭她的小孫子,快來吧。
那賣麻花的人看瞭老太太很喜歡這麻花,於是就又說:
“是剛齣鍋的,還熱忽著哩!”
七
過去瞭賣麻花的,後半天,也許又來瞭賣涼粉的,也是一在鬍同口的這頭喊,那頭就聽到瞭。
要買的拿著小瓦盆齣去瞭。不買的坐在屋子一聽這賣涼粉的一招呼,就知道是應燒晚飯的時候瞭。因為這涼粉一個整個的夏天都是在太陽偏西,他就來的,來得那麼準,就像時鍾一樣,到瞭四五點鍾他必來的。就像他賣涼粉專門到這一條鬍同來賣似的。似乎在彆的鬍同裏就沒有為著多賣幾傢而耽誤瞭這一定的時間。
賣涼粉的一過去瞭。一天也就快黑瞭。
打著撥浪鼓的貨郎,一到太陽偏西,就再不進到小巷子裏來,就連僻靜的街他也不去瞭,他擔著擔子從大街口走迴傢去。
賣瓦盆的,也早都收市瞭。
揀繩頭的,換破爛的也都迴傢去瞭。
隻有賣豆腐的則又齣來瞭。
晚飯時節,吃瞭小蔥蘸大醬就已經很可口瞭,若外加上一塊豆腐,那真是錦上添花,一定要多浪費兩碗包米大雲豆粥的。一吃就吃多瞭,那是很自然的,豆腐加上點辣椒油,再拌上點大醬,那是多麼可口的東西;用筷子觸瞭一點點豆腐,就能夠吃下去半碗飯,再到豆腐上去觸瞭一下,一碗飯就完瞭。因為豆腐而多吃兩碗飯,並不算吃得多,沒有吃過的人,不能夠曉得其中的滋味的。
所以賣豆腐的人來瞭,男女老幼,全都歡迎。打開門來,笑盈盈的,雖然不說什麼,但是彼此有一種融洽的感情,默默生瞭起來。
似乎賣豆腐的在說:
“我的豆腐真好!”
似乎買豆腐的迴答:
“你的豆腐果然不錯。”
買不起豆腐的人對那賣豆腐的,就非常的羨慕,一聽瞭那從街口越招呼越近的聲音就特彆地感到誘惑,假若能吃一塊豆腐可不錯,切上一點青辣椒,拌上一點小蔥子。
但是天天這樣想,天天就沒有買成,賣豆腐的一來,就把這等人白白地引誘一場。於是那被誘惑的人,仍然逗不起決心,就多吃幾口辣椒,辣得滿頭是汗。他想假若一個人開瞭一個豆腐房可不錯,那就可以自由隨便地吃豆腐瞭。
果然,他的兒子長到五歲的時候,問他:
“你長大瞭乾什麼?”
五歲的孩子說:
“開豆腐房。”
這顯然要繼承他父親未遂的誌願。
關於豆腐這美妙的一盤菜的愛好,竟還有甚於此的,竟有想要傾傢蕩産的。傳說上,有這樣的一個傢長,他下瞭決心,他說:
“不過瞭,買一塊豆腐吃去!”這“不過瞭”的三個字,用舊的語言來翻譯,就是毀傢紓難的意思;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我破産瞭!”
八
賣豆腐的一收瞭市,一天的事情都完瞭。
傢傢戶戶都把晚飯吃過瞭。吃過瞭晚飯,看晚霞的看晚霞,不看晚霞的躺到炕上去睡覺的也有。
這地方的晚霞是很好看的,有一個土名,叫火燒雲。說“晚霞”人們不懂,若一說“火燒雲”就連三歲的孩子也會呀呀地往西天空裏指給你看。
晚飯一過,火燒雲就上來瞭。照得小孩子的臉是紅的。把大白狗變成紅色的狗瞭。紅公雞就變成金的瞭。黑母雞變成紫檀色的瞭。喂豬的老頭子,往牆根上靠,他笑盈盈地看著他的兩匹小白豬,變成小金豬瞭,他剛想說:
“他媽的,你們也變瞭……”
他的旁邊走來瞭一個乘涼的人,那人說:
“你老人傢必要高壽,你老是金鬍子瞭。”
天空的雲,從西邊一直燒到東邊,紅堂堂的,好像是天著瞭火。
這地方的火燒雲變化極多,一會紅堂堂的瞭,一會金洞洞的瞭,一會半紫半黃的,一會半灰半百閤色。葡萄灰、大黃梨、紫茄子,這些顔色天空上邊都有。還有些說也說不齣來的,見也未曾見過的,諸多種的顔色。
五秒鍾之內,天空裏有一匹馬,馬頭嚮南,馬尾嚮西,那馬是跪著的,像是在等著有人騎到它的背上,它纔站起來。再過一秒鍾。沒有什麼變化。再過兩三秒鍾,那匹馬加大瞭,馬腿也伸開瞭,馬脖子也長瞭,但是一條馬尾巴卻不見瞭。
看的人,正在尋找馬尾巴的時候,那馬就變靡瞭。
忽然又來瞭一條大狗,這條狗十分凶猛,它在前邊跑著,它的後麵似乎還跟瞭好幾條小狗仔。跑著跑著,小狗就不知跑到哪裏去瞭,大狗也不見瞭。
又找到瞭一個大獅子,和娘娘廟門前的大石頭獅子一模一樣的,也是那麼大,也是那樣的蹲著,很威武的,很鎮靜地蹲著,它錶示著衊視一切的樣子,似乎眼睛連什麼也不睬,看著看著地,一不謹慎,同時又看到瞭彆一個什麼。這時候,可就麻煩瞭,人的眼睛不能同時又看東,又看西。這樣子會活活把那個大獅子糟蹋瞭。一轉眼,一低頭,那天空的東西就變瞭。若是再找,怕是看瞎瞭眼睛也找不到瞭。
大獅子既然找不到,另外的那什麼,比方就是一個猴子吧,猴子雖不如大獅子,可同時也沒有瞭。
一時恍恍惚惚的,滿天空裏又像這個,又像那個,其實是什麼也不像,什麼也沒有瞭。
必須是低下頭去,把眼睛揉一揉,或者是沉靜一會再來看。
可是天空偏偏又不常常等待著那些愛好它的孩子。一會工夫火燒雲下去瞭。
於是孩子們睏倦瞭,迴屋去睡覺瞭。竟有還沒能來得及進屋的,就靠在姐姐的腿上,或者是依在祖母的懷裏就睡著瞭。
祖母的手裏,拿著白馬鬃的蠅甩子,就用蠅甩子給他驅逐著蚊蟲。
祖母還不知道這孩子是已經睡瞭,還以為他在那裏玩著呢!
“下去玩一會去吧!把奶奶的腿壓麻瞭。”
用手一推,這孩子已經睡得搖搖晃晃的瞭。
這時候,火燒雲已經完全下去瞭。
於是傢傢戶戶都進屋去睡覺,關起窗門來。
呼蘭河這地方,就是在六月裏也是不十分熱的,夜裏總要蓋著薄棉被睡覺。
等黃昏之後的烏鴉飛過時,隻能夠隔著窗子聽到那很少的尚未睡的孩子在嚷叫:
“烏鴉烏鴉你打場,
給你二鬥糧……
…………”
那漫天蓋地的一群黑烏鴉,呱呱地大叫著,在整個的縣城的頭頂上飛過去瞭。
據說飛過瞭呼蘭河的南岸,就在一個大樹林子裏邊住下瞭。明天早晨起來再飛。
夏鞦之間每夜要過烏鴉,究竟這些成百成韆的烏鴉過到哪裏去,孩子們是不大曉得的,大人們也不大講給他們聽。
隻曉得念這套歌,“烏鴉烏鴉你打場,給你二鬥糧。”
究竟給烏鴉二鬥糧做什麼,似乎不大有道理。
九
烏鴉一飛過,這一天纔真正地過去瞭。
因為大昴星升起來瞭,大昴星好像銅球似的亮晶晶的瞭。
天河和月亮也都上來瞭。
蝙蝠也飛起來瞭。
是凡跟著太陽一起來的,現在都迴去瞭。人睡瞭,豬、馬、牛、羊也都睡瞭,燕子和蝴蝶也都不飛瞭。就連房根底下的牽牛花,也一朵沒有開的。含苞的含苞,捲縮的捲縮。含苞的準備著歡迎那早晨又要來的太陽,那捲縮的,因為它已經在昨天歡迎過瞭,它要落去瞭。
隨著月亮上來的星夜,大昴星也不過是月亮的一個馬前卒,讓它先跑到一步就是瞭。
夜一來蛤蟆就叫,在河溝裏叫,在窪地裏叫。蟲子也叫,在院心草棵子裏,在城外的大田上,有的叫在人傢的花盆裏,有的叫在人傢的墳頭上。
夏夜若無風無雨就這樣地過去瞭,一夜又一夜。
很快地夏天就過完瞭,鞦天就來瞭。鞦天和夏天的分彆不太大,也不過天涼瞭,夜裏非蓋著被子睡覺不可。種田的人白天忙著收割,夜裏多做幾個割高粱的夢就是瞭。
女人一到瞭八月也不過就是漿衣裳,拆被子,捶棒槌,捶得街街巷巷早晚地叮叮當當地亂響。
“棒槌”一捶完,做起被子來,就是鼕天。
鼕天下雪瞭。
人們四季裏,風、霜、雨、雪的過著,霜打瞭,雨淋瞭。大風來時是飛沙走石,似乎是很瞭不起的樣子。鼕天,大地被凍裂瞭,江河被凍住瞭。再冷起來,江河也被凍得鏘鏘地響著裂開瞭紋。鼕天,凍掉瞭人的耳朵,……破瞭人的鼻子……裂瞭人的手和腳。
但這是大自然的威風,與小民們無關。
呼蘭河的人們就是這樣,鼕天來瞭就穿棉衣裳,夏天來瞭就穿單衣裳。就好像太陽齣來瞭就起來,太陽落瞭就睡覺似的。
被鼕天凍裂瞭手指的,到瞭夏天也自然就好瞭。好不瞭的,“李永春”藥鋪,去買二兩紅花,泡一點紅花酒來擦一擦,擦得手指通紅也不見消,也許就越來越腫起來。那麼再到“李永春”藥鋪去,這迴可不買紅花瞭,是買瞭一貼膏藥來。迴到傢裏,用火一烤,黏黏糊糊地就貼在凍瘡上瞭。這膏藥是真好,貼上瞭一點也不礙事。該趕車的去趕車,該切菜的去切菜。黏黏糊糊地是真好,見瞭水也不掉,該洗衣裳的去洗衣裳去好瞭。就是掉瞭,拿在火上再一烤,就還貼得上的。一貼,貼瞭半個月。
呼蘭河這地方的人,什麼都講結實、耐用,這膏藥這樣的耐用,實在是閤乎這地方的人情。雖然是貼瞭半個月,手也還沒有見好,但這膏藥總算是耐用,沒有白花錢。
於是再買一貼去,貼來貼去,這手可就越腫越大瞭。還有些買不起膏藥的,就揀人傢貼乏瞭的來貼。
到後來,那結果,誰曉得是怎樣呢,反正一塌糊塗去瞭吧。
春夏鞦鼕,一年四季來迴循環地走,那是自古也就這樣的瞭。風霜雨雪,受得住的就過去瞭,受不住的,就尋求著自然的結果。那自然的結果不大好,把一個人默默地一聲不響地就拉著離開瞭這人間的世界瞭。
至於那還沒有被拉去的,就風霜雨雪,仍舊在人間被吹打著。
第 三 章
一
呼蘭河這小城裏邊住著我的祖父。
我生的時候,祖父已經六十多歲瞭,我長到四五歲,祖父就快七十瞭。
我傢有一個大花園,這花園裏蜂子、蝴蝶、蜻蜓、螞蚱,樣樣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黃蝴蝶。這種蝴蝶極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紅蝴蝶,滿身帶著金粉。
蜻蜓是金的,螞蚱是綠的,蜂子則嗡嗡地飛著,滿身絨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圓圓地就和一個小毛球似的不動瞭。
花園裏邊明晃晃的,紅的紅,綠的綠,新鮮漂亮。
據說這花園,從前是一個果園。祖母喜歡吃果子就種瞭果園。祖母又喜歡養羊,羊就把果樹給啃瞭。果樹於是都死瞭。到我有記憶的時候,園子裏就隻有一棵櫻桃樹,一棵李子樹,為因櫻桃和李子都不大結果子,所以覺得他們是並不存在的。小的時候,隻覺得園子裏邊就有一棵大榆樹。
這榆樹在園子的西北角上,來瞭風,這榆樹先嘯,來瞭雨,大榆樹先就冒煙瞭。太陽一齣來,大榆樹的葉子就發光瞭,它們閃爍得和沙灘上的蚌殼一樣瞭。
祖父一天都在後園裏邊,我也跟著祖父在後園裏邊。祖父戴一個大草帽,我戴一個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當祖父下種,種小白菜的時候,我就跟在後邊,把那下瞭種的土窩,用腳一個一個地溜平,哪裏會溜得準,東一腳的,西一腳的瞎鬧。有的把菜種不單沒被土蓋上,反而把菜子踢飛瞭。
小白菜長得非常之快,沒有幾天就冒瞭芽瞭,一轉眼就可以拔下來吃瞭。
祖父鏟地,我也鏟地;因為我太小,拿不動那鋤頭杆,祖父就把鋤頭杆拔下來,讓我單拿著那個鋤頭的“頭”來鏟。其實哪裏是鏟,也不過爬在地上,用鋤頭亂勾一陣就是瞭。也認不得哪個是苗,哪個是草。往往把韭菜當做野草一起地割掉,把狗尾草當做榖穗留著。
等祖父發現我鏟的那塊滿留著狗尾草的一片,他就問我:
“這是什麼?”
我說:
“榖子。”
祖父大笑起來,笑得夠瞭,把草摘下來問我:
“你每天吃的就是這個嗎?”
我說:
“是的。”
我看著祖父還在笑,我就說:
“你不信,我到屋裏拿來你看。”
我跑到屋裏拿瞭鳥籠上的一頭榖穗,遠遠地就拋給祖父瞭。說:
“這不是一樣的嗎?”
祖父慢慢地把我叫過去,講給我聽,說榖子是有芒針的。狗尾草則沒有,隻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
祖父雖然教我,我看瞭也並不細看,也不過馬馬虎虎承認下來就是瞭。一抬頭看見瞭一個黃瓜長大瞭,跑過去摘下來,我又去吃黃瓜去瞭。
黃瓜也許沒有吃完,又看見瞭一個大蜻蜓從旁飛過,於是丟瞭黃瓜又去追蜻蜓去瞭。蜻蜓飛得多麼快,哪裏會追得上。好在一開初也沒有存心一定追上,所以站起來,跟瞭蜻蜓跑瞭幾步就又去做彆的去瞭。
采一個倭瓜花心,捉一個大綠豆青螞蚱,把螞蚱腿用綫綁上,綁瞭一會,也許把螞蚱腿就綁掉,綫頭上隻拴瞭一隻腿,而不見螞蚱瞭。
玩膩瞭,又跑到祖父那裏去亂鬧一陣,祖父澆菜,我也搶過來澆,奇怪的就是並不往菜上澆,而是拿著水瓢,拼盡瞭力氣,把水往天空裏一揚,大喊著:
“下雨瞭,下雨瞭。”
太陽在園子裏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彆高的,太陽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睜不開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鑽齣地麵來,蝙蝠不敢從什麼黑暗的地方飛齣來。是凡在太陽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連大樹都會發響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對麵的土牆都會迴答似的。
花開瞭,就像花睡醒瞭似的。鳥飛瞭,就像鳥上天瞭似的。蟲子叫瞭,就像蟲子在說話似的。一切都活瞭。都有無限的本領,要做什麼,就做什麼。要怎麼樣,就怎麼樣。都是自由的。倭瓜願意爬上架就爬上架,願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黃瓜願意開一個謊花,就開一個謊花,願意結一個黃瓜,就結一個黃瓜。若都不願意,就是一個黃瓜也不結,一朵花也不開,也沒有人問它。玉米願意長多高就長多高,他若願意長上天去,也沒有人管。蝴蝶隨意的飛,一會從牆頭上飛來一對黃蝴蝶,一會又從牆頭上飛走瞭一個白蝴蝶。它們是從誰傢來的,又飛到誰傢去?太陽也不知道這個。
隻是天空藍悠悠的,又高又遠。
可是白雲一來瞭的時候,那大團的白雲,好像灑瞭花的白銀似的,從祖父的頭上經過,好像要壓到瞭祖父的草帽那麼低。
我玩纍瞭,就在房子底下找個陰涼的地方睡著瞭。不用枕頭,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臉上就睡瞭。
二
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
祖父是個長得很高的人,身體很健康,手裏喜歡拿著個手杖。嘴上則不住地抽著旱煙管,遇到瞭小孩子,每每喜歡開個玩笑,說:
“你看天空飛個傢雀。”
趁那孩子往天空一看,就伸齣手去把那孩子的帽給取下來瞭,有的時候放在長衫的下邊,有的時候放在袖口裏頭。他說:
“傢雀叼走瞭你的帽啦。”
孩子們都知道瞭祖父的這一手瞭,並不以為奇,就抱住他的大腿,嚮他要帽子,摸著他的袖管,撕著他的衣襟,一直到找齣帽子來為止。
祖父常常這樣做,也總是把帽放在同一的地方,總是放在袖口和衣襟下。那些搜索他的孩子沒有一次不是在他衣襟下把帽子拿齣來的,好像他和孩子們約定瞭似的:“我就放在這塊,你來找吧!”
這樣的不知做過瞭多少次,就像老太太永久講著“上山打老虎”這一個故事給孩子們聽似的,哪怕是已經聽過瞭五百遍,也還是在那裏迴迴拍手,迴迴叫好。
每當祖父這樣做一次的時候,祖父和孩子們都一齊地笑得不得瞭。好像這戲還像第一次演似的。
彆人看瞭祖父這樣做,也有笑的,可不是笑祖父的手法好,而是笑他天天使用一種方法抓掉瞭孩子的帽子,這未免可笑。
祖父不怎樣會理財,一切傢務都由祖母管理。祖父隻是自由自在地一天閑著;我想,幸好我長大瞭,我三歲瞭,不然祖父該多寂寞。我會走瞭,我會跑瞭。我走不動的時候,祖父就抱著我;我走動瞭,祖父就拉著我。一天到晚,門裏門外,寸步不離,而祖父多半是在後園裏,於是我也在後園裏。
我小的時候,沒有什麼同伴,我是我母親的第一個孩子。
我記事很早,在我三歲的時候,我記得我的祖母用針刺過我的手指,所以我很不喜歡她。我傢的窗子,都是四邊糊紙,當中嵌著玻璃。祖母是有潔癖的,以她屋的窗紙最白淨。彆人抱著把我一放在祖母的炕邊上,我不假思索地就要往炕裏邊跑,跑到窗子那裏,就伸齣手去,把那白白透著花窗欞的紙窗給通瞭幾個洞,若不加阻止,就必得挨著排給通破,若有人招呼著我,我也得加速的搶著多通幾個纔能停止。手指一觸到窗上,那紙窗像小鼓似的,嘭嘭地就破瞭。破得越多,自己越得意。祖母若來追我的時候,我就越得意瞭,笑得拍著手,跳著腳的。
有一天祖母看我來瞭,她拿瞭一個大針就到窗子外邊去等我去瞭。我剛一伸齣手去,手指就痛得厲害。我就叫起來瞭。那就是祖母用針刺瞭我。
從此,我就記住瞭,我不喜歡她。
雖然她也給我糖吃,她咳嗽時吃豬腰燒川貝母,也分給我豬腰,但是我吃瞭豬腰還是不喜歡她。
在她臨死之前,病重的時候,我還會嚇瞭她一跳。有一次她自己一個人坐在炕上熬藥,藥壺是坐在炭火盆上,因為屋裏特彆的寂靜,聽得見那藥壺骨碌骨碌地響。祖母住著兩間房子,是裏外屋,恰巧外屋也沒有人,裏屋也沒人,就是她自己。我把門一開,祖母並沒有看見我,於是我就用拳頭在闆隔壁上,咚咚地打瞭兩拳。我聽到祖母“喲”地一聲,鐵火剪子就掉瞭地上瞭。
我再探頭一望,祖母就罵起我來。她好像就要下地來追我似的。我就一邊笑著,一邊跑瞭。
我這樣地嚇唬祖母,也並不是嚮她報仇,那時我纔五歲,是不曉得什麼的,也許覺得這樣好玩。
祖父一天到晚是閑著的,祖母什麼工作也不分配給他。隻有一件事,就是祖母的地櫬上的擺設,有一套锡器,卻總是祖父擦的。這可不知道是祖母派給他的,還是他自動的願意工作,每當祖父一擦的時候,我就不高興,一方麵是不能領著我到後園裏去玩瞭,另一方麵祖父因此常常挨罵,祖母罵他懶,罵他擦的不乾淨。祖母一罵祖父的時候,就常常不知為什麼連我也罵上。
祖母一罵祖父,我就拉著祖父的手往外邊走,一邊說:
“我們後園裏去吧。”
也許因此祖母也罵瞭我。
她罵祖父是“死腦瓜骨”,罵我是“小死腦瓜骨”。
我拉著祖父就到後園裏去瞭,一到瞭後園裏,立刻就另是一個世界瞭。決不是那房子裏的狹窄的世界,而是寬廣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麼大,多麼遠,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長的又是那麼繁華,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隻覺得眼前鮮綠的一片。
一到後園裏,我就沒有對象地奔瞭齣去,好像我是看準瞭什麼而奔去瞭似的,好像有什麼在那兒等著我似的。其實我是什麼目的也沒有。隻覺得這園子裏邊無論什麼東西都是活的,好像我的腿也非跳不可瞭。
若不是把全身的力量跳盡瞭,祖父怕我纍瞭想招呼住我,那是不可能的,反而他越招呼,我越不聽話。
等到自己實在跑不動瞭,纔坐下來休息,那休息也是很快的,也不過隨便在秧子上摘下一個黃瓜來,吃瞭也就好瞭。
休息好瞭又是跑。
櫻桃樹,明是沒有結櫻桃,就偏跑到樹上去找櫻桃。李子樹是半死的樣子瞭,本不結李子的,就偏去找李子。一邊在找,還一邊大聲的喊,在問著祖父:
“爺爺,櫻桃樹為什麼不結櫻桃?”
祖父老遠的迴答著:
“因為沒有開花,就不結櫻桃。”
再問:
“為什麼櫻桃樹不開花?”
祖父說:
“因為你嘴饞,它就不開花。”
我一聽瞭這話,明明是嘲笑我的話,於是就飛奔著跑到祖父那裏,似乎是很生氣的樣子。等祖父把眼睛一抬,他用瞭完全沒有惡意的眼睛一看我,我立刻就笑瞭。而且是笑瞭半天的工夫纔能夠止住,不知哪裏來瞭那許多的高興。把後園一時都讓我攪亂瞭,我笑的聲音不知有多大,自己都感到震耳瞭。
後園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開花的。一直開到六月。花朵和醬油碟那麼大。開得很茂盛,滿樹都是,因為花香,招來瞭很多的蜂子,嗡嗡地在玫瑰樹那兒鬧著。
彆的一切都玩厭瞭的時候,我就想起來去摘玫瑰花,摘瞭一大堆把草帽脫下來用帽兜子盛著。在摘那花的時候,有兩種恐懼,一種是怕蜂子的勾刺人,另一種是怕玫瑰的刺刺手。好不容易摘瞭一大堆,摘完瞭可又不知道做什麼瞭。忽然異想天開,這花若給祖父戴起來該多好看。
祖父蹲在地上拔草,我就給他戴花。祖父隻知道我是在捉弄他的帽子,而不知道我到底是在乾什麼。我把他的草帽給他插瞭一圈的花,紅通通的二三十朵。我一邊插著一邊笑,當我聽到祖父說:
“今年春天雨水大,咱們這棵玫瑰開得這麼香。二裏路也怕聞得到的。”
就把我笑得哆嗦起來。我幾乎沒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等我插完瞭,祖父還是安然的不曉得。他還照樣地拔著壟上的草。我跑得很遠的站著,我不敢往祖父那邊看,一看就想笑。所以我藉機進屋去找一點吃的來,還沒有等我迴到園中,祖父也進屋來瞭。
那滿頭紅通通的花朵,一進來祖母就看見瞭。她看見什麼也沒說,就大笑瞭起來。父親母親也笑瞭起來,而以我笑得最厲害,我在炕上打著滾笑。
祖父把帽子摘下來一看,原來那玫瑰的香並不是因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緣故,而是那花就頂在他的頭上。
他把帽子放下,他笑瞭十多分鍾還停不住,過一會一想起來,又笑瞭。
祖父剛有點忘記瞭,我就在旁邊提著說:
“爺爺……今年春天雨水大呀……”
一提起,祖父的笑就來瞭。於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滾來。
就這樣一天一天的,祖父,後園,我,這三樣是一樣也不可缺少的瞭。
颳瞭風,下瞭雨,祖父不知怎樣,在我卻是非常寂寞的瞭。去沒有去處,玩沒有玩的,覺得這一天不知有多少日子那麼長。
三
偏偏這後園每年都要封閉一次的,鞦雨之後這花園就開始凋零瞭,黃的黃、敗的敗,好像很快似的一切花朵都滅瞭,好像有人把它們摧殘瞭似的。它們一齊都沒有從前那麼健康瞭,好像它們都很疲倦瞭,而要休息瞭似的,好像要收拾收拾迴傢去瞭似的。
大榆樹也是落著葉子,當我和祖父偶爾在樹下坐坐,樹葉竟落在我的臉上來瞭。樹葉飛滿瞭後園。
沒有多少時候,大雪又落下來瞭,後園就被埋住瞭。
通到園去的後門,也用泥封起來瞭,封得很厚,整個的鼕天掛著白霜。
我傢住著五間房子,祖母和祖父共住兩間,母親和父親共住兩間。祖母住的是西屋,母親住的是東屋。
是五間一排的正房,廚房在中間,一齊是玻璃窗子,青磚牆,瓦房間。
祖母的屋子,一個是外間,一個是內間。外間裏擺著大躺箱,地長桌,太師椅。椅子上鋪著紅椅墊,躺箱上擺著硃砂瓶,長桌上列著座鍾。鍾的兩邊站著帽筒。帽筒上並不掛著帽子,而插著幾個孔雀翎。
我小的時候,就喜歡這個孔雀翎,我說它有金色的眼睛,總想用手摸一摸,祖母就一定不讓摸,祖母是有潔癖的。
還有祖母的躺箱上擺著一個座鍾,那座鍾是非常希奇的,畫著一個穿著古裝的大姑娘,好像活瞭似的,每當我到祖母屋去,若是屋子裏沒有人,她就總用眼睛瞪我,我幾次的告訴過祖父,祖父說:
“那是畫的,她不會瞪人。”
我一定說她是會瞪人的,因為我看得齣來,她的眼珠像是會轉。
還有祖母的大躺箱上也盡雕著小人,盡是穿古裝衣裳的,寬衣大袖,還戴頂子,帶著翎子。滿箱子都刻著,大概有二三十個人,還有吃酒的,吃飯的,還有作揖的……
我總想要細看一看,可是祖母不讓我沾邊,我還離得很遠的,她就說:
“可不許用手摸,你的手髒。”
祖母的內間裏邊,在牆上掛著一個很古怪很古怪的掛鍾,掛鍾的下邊用鐵鏈子垂著兩穗鐵包米。鐵包米比真的包米大瞭很多,看起來非常重,似乎可以打死一個人。再往那掛鍾裏邊看就更希奇古怪瞭,有一個小人,長著藍眼珠,鍾擺一秒鍾就響一下,鍾擺一響,那眼珠就同時一轉。
那小人是黃頭發,藍眼珠,跟我相差太遠,雖然祖父告訴我,說那是毛子人,但我不承認她,我看她不像什麼人。
所以我每次看這掛鍾,就半天半天的看,都看得有點發呆瞭。我想:這毛子人就總在鍾裏邊呆著嗎?永久也不下來玩嗎?
外國人在呼蘭河的土語叫做“毛子人”。我四五歲的時候,還沒有見過一個毛子人,以為毛子人就是因為她的頭發毛烘烘地捲著的緣故。
祖母的屋子除瞭這些東西,還有很多彆的,因為那時候,彆的我都不發生什麼趣味,所以隻記住瞭這三五樣。
母親的屋裏,就連這一類的古怪玩藝也沒有瞭,都是些普通的描金櫃,也是些帽筒、花瓶之類,沒有什麼好看的,我沒有記住。
這五間房子的組織,除瞭四間住房一間廚房之外,還有極小的、極黑的兩個小後房。祖母一個,母親一個。
那裏邊裝著各種樣的東西,因為是儲藏室的緣故。
壇子罐子、箱子櫃子、筐子簍子。除瞭自己傢的東西,還有彆人寄存的。
那裏邊是黑的,要端著燈進去纔能看見。那裏邊的耗子很多,蜘蛛網也很多。空氣不大好,永久有一種撲鼻的和藥的氣味似的。
我覺得這儲藏室很好玩,隨便打開那一隻箱子,裏邊一定有一些好看的東西,花絲綫、各種色的綢條、香荷包、搭腰、褲腿、馬蹄袖、綉花的領子。古香古色,顔色都配得特彆的好看。箱子裏邊也常常有藍翠的耳環或戒指,被我看見瞭,我一看見就非要一個玩不可,母親就常常隨手拋給我一個。
還有些桌子帶著抽屜的,一打開那裏邊更有些好玩的東西,銅環、木刀、竹尺、觀音粉。這些個都是我在彆的地方沒有看過的。而且這抽屜始終也不鎖的。所以我常常隨意地開,開瞭就把樣樣,似乎是不加選擇地都搜瞭齣去,左手拿著木頭刀,右手拿著觀音粉,這裏砍一下,那裏畫一下。後來我又得到瞭一個小鋸,用這小鋸,我開始毀壞起東西來,在椅子腿上鋸一鋸,在炕沿上鋸一鋸。我自己竟把我自己的小木刀也鋸壞瞭。
無論吃飯和睡覺,我這些東西都帶在身邊,吃飯的時候,我就用這小鋸,鋸著饅頭。睡覺做起夢來還喊著:
“我的小鋸哪裏去瞭?”
儲藏室好像變成我探險的地方瞭。我常常趁著母親不在屋我就打開門進去瞭。這儲藏室也有一個後窗,下半天也有一點亮光,我就趁著這亮光打開瞭抽屜,這抽屜已經被我翻得差不多的瞭,沒有什麼新鮮的瞭。翻瞭一會,覺得沒有什麼趣味瞭,就齣來瞭。到後來連一塊水膠,一段繩頭都讓我拿齣來瞭,把五個抽屜通通拿空瞭。
除瞭抽屜還有筐子籠子,但那個我不敢動,似乎每一樣都是黑洞洞的,灰塵不知有多厚,蛛網蛛絲的不知有多少,因此我連想也不想動那東西。
記得有一次我走到這黑屋子的極深極遠的地方去,一個發響的東西撞住我的腳上,我摸起來抱到光亮的地方一看,原來是一個小燈籠,用手指把灰塵一劃,露齣來是個紅玻璃的。
我在一兩歲的時候,大概我是見過燈籠的,可是長到四五歲,反而不認識瞭。我不知道這是個什麼。我抱著去問祖父去瞭。
祖父給我擦乾淨瞭,裏邊點上個洋蠟燭,於是我歡喜得就打著燈籠滿屋跑,跑瞭好幾天,一直到把這燈籠打碎瞭纔算完瞭。
我在黑屋子裏邊又碰到瞭一塊木頭,這塊木頭是上邊刻著花的,用手一摸,很不光滑,我拿齣來用小鋸鋸著。祖父看見瞭,說:
“這是印帖子的帖闆。”
我不知道什麼叫帖子,祖父刷上一片墨刷一張給我看,我隻看見印齣來幾個小人。還有一些亂七八糟的花,還有字。祖父說:
“咱們傢開燒鍋的時候,發帖子就是用這個印的,這是一百吊的……還有五十吊的十吊的……”
祖父給我印瞭許多,還用鬼子紅給我印瞭些紅的。
還有帶纓子的清朝的帽子,我也拿瞭齣來戴上。多少年前的老大的鵝翎扇子,我也拿瞭齣來吹著風。翻瞭一瓶莎仁齣來,那是治胃病的藥,母親吃著,我也跟著吃。
不久,這些八百年前的東西,都被我弄齣來瞭。有些是祖母保存著的,有些是已經齣瞭嫁的姑母的遺物,已經在那黑洞洞的地方放瞭多少年瞭,連動也沒有動過,有些個快要腐爛瞭,有些個生瞭蟲子,因為那些東西早被人們忘記瞭,好像世界上已經沒有那麼一迴事瞭。而今天忽然又來到瞭他們的眼前,他們受瞭驚似的又恢復瞭他們的記憶。
每當我拿齣一件新的東西的時候,祖母看見瞭,祖母說:
“這是多少年前的瞭!這是你大姑在傢裏邊玩的……”
祖父看見瞭,祖父說:
“這是你二姑在傢時用的……”
這是你大姑的扇子,那是你三姑的花鞋……都有瞭來曆。但我不知道誰是我的三姑,誰是我的大姑。也許我一兩歲的時候,我見過她們,可是我到四五歲時,我就不記得瞭。
我祖母有三個女兒,到我長起來時,她們都早已齣嫁瞭。可見二三十年內就沒有小孩子瞭。而今也隻有我一個。實在的還有一個小弟弟,不過那時他纔一歲半歲的,所以不算他。
傢裏邊多少年前放的東西,沒有動過,他們過的是既不嚮前,也不迴頭的生活,是凡過去的,都算是忘記瞭,未來的他們也不怎樣積極地希望著,隻是一天一天地平闆地、無怨無尤地在他們祖先給他們準備好的口糧之中生活著。
等我生來瞭,第一給瞭祖父的無限的歡喜,等我長大瞭,祖父非常地愛我。使我覺得在這世界上,有瞭祖父就夠瞭,還怕什麼呢?雖然父親的冷淡,母親的惡言惡色,和祖母的用針刺我手指的這些事,都覺得算不瞭什麼。何況又有後花園!後園雖然讓冰雪給封閉瞭,但是又發現瞭這儲藏室。這裏邊是無窮無盡地什麼都有,這裏邊寶藏著的都是我所想象不到的東西,使我感到這世界上的東西怎麼這樣多!而且樣樣好玩,樣樣新奇。
比方我得到瞭一包顔料,是中國的大綠,看那顔料閃著金光,可是往指甲上一染,指甲就變綠瞭,往胳臂上一染,胳臂立刻飛來瞭一張樹葉似的。實在是好看,也實在是莫名其妙,所以心裏邊就暗暗地歡喜,莫非是我得瞭寶貝嗎?
得瞭一塊觀音粉。這觀音粉往門上一劃,門就白瞭一道,往窗上一劃,窗就白瞭一道。這可真有點奇怪,大概祖父寫字的墨是黑墨,而這是白墨吧。
得瞭一塊圓玻璃,祖父說是“顯微鏡”。他在太陽底下一照,竟把祖父裝好的一袋煙照著瞭。
這該多麼使人歡喜,什麼什麼都會變的。你看他是一塊廢鐵,說不定他就有用,比方我撿到一塊四方的鐵塊,上邊有一個小窩。祖父把榛子放在小窩裏邊,打著榛子給我吃。在這小窩裏打,不知道比用牙咬要快瞭多少倍。何況祖父老瞭,他的牙又多半不大好。
我天天從那黑屋子往外搬著,而天天有新的。搬齣來一批,玩厭瞭,弄壞瞭,就再去搬。
因此使我的祖父、祖母常常地慨嘆。
他們說這是多少年前的瞭,連我的第三個姑母還沒有生的時候就有這東西。那是多少年前的瞭,還是分傢的時候,從我曾祖那裏得來的呢。又哪樣哪樣是什麼人送的,而那傢人傢到今天也都傢敗人亡瞭,而這東西還存在著。
又是我在玩著的那葡蔓藤的手鐲,祖母說她就戴著這個手鐲,有一年夏天坐著小車子,抱著我大姑去迴娘傢,路上遇瞭土匪,把金耳環給摘去瞭,而沒有要這手鐲。若也是金的銀的,那該多危險,也一定要被搶去的。
我聽瞭問她:
“我大姑在哪兒?”
祖父笑瞭。祖母說:
“你大姑的孩子比你都大瞭。”
原來是四十年前的事情,我哪裏知道。可是藤手鐲卻戴在我的手上,我舉起手來,搖瞭一陣,那手鐲好像風車似的,滴溜溜地轉,手鐲太大瞭,我的手太細瞭。
祖母看見我把從前的東西都搬齣來瞭,她常常罵我:
“你這孩子,沒有東西不拿著玩的,這小不成器的……”
她嘴裏雖然是這樣說,但她又在光天化日之下得以重看到這東西,也似乎給瞭她一些迴憶的滿足。所以她說我是並不十分嚴刻的,我當然是不聽她,該拿還是照舊地拿。
於是我傢裏久不見天日的東西,經我這一搬弄,纔得以見瞭天日。於是壞的壞,扔的扔,也就都從此消滅瞭。
我有記憶的第一個鼕天,就這樣過去瞭。沒有感到十分的寂寞,但總不如在後園裏那樣玩著好。但孩子是容易忘記的,也就隨遇而安瞭。
四
第二年夏天,後園裏種瞭不少的韭菜,是因為祖母喜歡吃韭菜餡的餃子而種的。
可是當韭菜長起來時,祖母就病重瞭,而不能吃這韭菜瞭,傢裏彆的人也沒有吃這韭菜,韭菜就在園子裏荒著。
因為祖母病重,傢裏非常熱鬧,來瞭我的大姑母,又來瞭我的二姑母。
二姑母是坐著她自傢的小車子來的。那拉車的騾子掛著鈴當,嘩嘩啷啷的就停在窗前瞭。
從那車上第一個就跳下來一個小孩,那小孩比我高瞭一點,是二姑母的兒子。
他的小名叫“小蘭”,祖父讓我嚮他叫蘭哥。
彆的我都不記得瞭,隻記得不大一會工夫我就把他領到後園裏去瞭。
告訴他這個是玫瑰樹,這個是狗尾草,這個是櫻桃樹。櫻桃樹是不結櫻桃的,我也告訴瞭他。
不知道在這之前他見過我沒有,我可並沒有見過他。
我帶他到東南角上去看那棵李子樹時,還沒有走到眼前,他就說:
“這樹前年就死瞭。”
他說瞭這樣的話,是使我很吃驚的。這樹死瞭,他可怎麼知道的?心中立刻來瞭一種忌妒的情感,覺得這花園是屬於我的,和屬於祖父的,其餘的人連曉得也不該曉得纔對的。
我問他:
“那麼你來過我們傢嗎?”
他說他來過。
這個我更生氣瞭,怎麼他來我不曉得呢?
我又問他:
“你什麼時候來過的?”
他說前年來的,他還帶給我一個毛猴子。他問著我:
“你忘瞭嗎?你抱著那毛猴子就跑,跌倒瞭你還哭瞭哩!”
我無論怎樣想,也想不起來瞭。不過總算他送給我過一個毛猴子,可見對我是很好的,於是我就不生他的氣瞭。
從此天天就在一塊玩。
他比我大三歲,已經八歲瞭,他說他在學堂裏邊念瞭書的,他還帶來瞭幾本書,晚上在煤油燈下他還把書拿齣來給我看。書上有小人、有剪刀、有房子。因為都是帶著圖,我一看就連那字似乎也認識瞭,我說:
“這念剪刀,這念房子。”
他說不對:
“這念剪,這念房。”
我拿過來一細看,果然都是一個字,而不是兩個字,我是照著圖念的,所以錯瞭。
我也有一盒方字塊,這邊是圖,那邊是字,我也拿齣來給他看瞭。
從此整天的玩。祖母病重與否,我不知道。不過在她臨死的前幾天就穿上瞭滿身的新衣裳,好像要齣門做客似的。說是怕死瞭來不及穿衣裳。
因為祖母病重,傢裏熱鬧得很,來瞭很多親戚。忙忙碌碌不知忙些個什麼。有的拿瞭些白布撕著,撕得一條一塊的,撕得非常的響亮,旁邊就有人拿著針在縫那白布。還有的把一個小罐,裏邊裝瞭米,罐口濛上瞭紅布。還有的在後園門口攏起火來,在鐵火勺裏邊炸著麵餅瞭。問她:
“這是什麼?”
“這是打狗餑餑。”
她說陰間有十八關,過到狗關的時候,狗就上來咬人,用這餑餑一打,狗吃瞭餑餑就不咬人瞭。
似乎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我沒有聽進去。
傢裏邊的人越多,我就越寂寞,走到屋裏,問問這個,問問那個,一切都不理解。祖父也似乎把我忘記瞭。我從後園裏捉瞭一個特彆大的螞蚱送給他去看,他連看也沒有看,就說:
“真好,真好,上後園去玩去吧!”
新來的蘭哥也不陪我時,我就在後園裏一個人玩。
五
祖母已經死瞭,人們都到龍王廟上去報過廟迴來瞭。而我還在後園裏邊玩著。
後園裏邊下瞭點雨,我想要進屋去拿草帽去,走到醬缸旁邊(我傢的醬缸是放在後園裏的),一看,有雨點拍拍的落到缸帽子上。我想這缸帽子該多大,遮起雨來,比草帽一定更好。
於是我就從缸上把它翻下來瞭,到瞭地上它還亂滾一陣,這時候,雨就大瞭。我好不容易纔設法鑽進這缸帽子去。因為這缸帽子太大瞭,差不多和我一般高。
我頂著它,走瞭幾步,覺得天昏地暗。而且重也是很重的,非常吃力。而且自己已經走到哪裏瞭,自己也不曉,隻曉得頭頂上拍拍拉拉的打著雨點,往腳下看著,腳下隻是些狗尾草和韭菜。找瞭一個韭菜很厚的地方,我就坐下瞭,一坐下這缸帽子就和個小房似的扣著我。這比站著好得多,頭頂不必頂著,帽子就扣在韭菜地上。但是裏邊可是黑極瞭,什麼是看不見。
同時聽什麼聲音,也覺得都遠瞭。大樹在風雨裏邊被吹得嗚嗚的,好像大樹已經被搬到彆人傢的院子去似的。
韭菜是種在北牆根上,我是坐在韭菜上。北牆根離傢裏的房子很遠的,傢裏邊那鬧嚷嚷的聲音,也像是來在遠方。
我細聽瞭一會,聽不齣什麼來,還是在我自己的小屋裏邊坐著。這小屋這麼好,不怕風,不怕雨。站起來走的時候,頂著屋蓋就走瞭,有多麼輕快。
其實是很重的瞭,頂起來非常吃力。
我頂著缸帽子,一路摸索著,來到瞭後門口,我是要頂給爺爺看看的。
我傢的後門坎特彆高,邁也邁不過去,因為缸帽子太大,使我抬不起腿來。好不容易兩手把腿拉著,弄瞭半天,總算是過去瞭。雖然進瞭屋,仍是不知道祖父在什麼方嚮,於是我就大喊,正在這喊之間,父親一腳把我踢翻瞭,差點沒把我踢到竈口的火堆上去。缸帽子也在地上滾著。
等人傢把我抱瞭起來,我一看,屋子裏的人,完全不對瞭,都穿瞭白衣裳。
再一看,祖母不是睡在炕上,而是睡在一張長闆上。
從這以後祖母就死瞭。
六
祖母一死,傢裏繼續著來瞭許多親戚,有的拿著香、紙,到靈前哭瞭一陣就迴去瞭。有的就帶著大包小包的來瞭就住下瞭。
大門前邊吹著喇叭,院子裏搭瞭靈棚,哭聲終日,一鬧鬧瞭不知多少日子。
請瞭和尚道士來,一鬧鬧到半夜,所來的都是吃、喝、說、笑。
我也覺得好玩,所以就特彆高興起來。又加上從前我沒有小同伴,而現在有瞭。比我大的,比我小的,共有四五個。我們上樹爬牆,幾乎連房頂也要上去瞭。
他們帶我到小門洞子頂上去捉鴿子,搬瞭梯子到房簷頭上去捉傢雀。後花園雖然大,已經裝不下我瞭。
我跟著他們到井口邊去往井裏邊看,那井是多麼深,我從未見過。在上邊喊一聲,裏邊有人迴答。用一個小石子投下去,那響聲是很深遠的。
他們帶我到糧食房子去,到碾磨房去,有時候竟把我帶到街上,是已經離開傢瞭,不跟著傢人在一起,我是從來沒有走過這樣遠。
不料除瞭後園之外,還有更大的地方,我站在街上,不是看什麼熱鬧,不是看那街上的行人車馬,而是心裏邊想:是不是我將來一個人也可以走得很遠?
有一天,他們把我帶到南河沿上去瞭,南河沿離我傢本不算遠,也不過半裏多地。可是因為我是第一次去,覺得實在很遠。走齣汗來瞭。走過一個黃土坑,又過一個南大營,南大營的門口,有兵把守門。那營房的院子大得在我看來太大瞭,實在是不應該。我們的院子就夠大的瞭,怎麼能比我們傢的院子更大呢,大得有點不大好看瞭,我走過瞭,我還迴過頭來看。
路上有一傢人傢,把花盆擺到牆頭上來瞭,我覺得這也不大好,若是看不見人傢偷去呢!
還看見瞭一座小洋房,比我們傢的房不知好瞭多少倍。若問我,哪裏好?我也說不齣來,就覺得那房子是一色新,不像我傢的房子那麼陳舊。
我僅僅走瞭半裏多路,我所看見的可太多瞭。所以覺得這南河沿實在遠。問他們:
“到瞭沒有?”
他們說:
“就到的,就到的。”
果然,轉過瞭大營房的牆角,就看見河水瞭。
我第一次看見河水,我不能曉得這河水是從什麼地方來的?走瞭幾年瞭。
那河太大瞭,等我走到河邊上,抓瞭一把沙子拋下去,那河水簡直沒有因此而髒瞭一點點。河上有船,但是不很多,有的往東去瞭,有的往西去瞭。也有的劃到河的對岸去的,河的對岸似乎沒有人傢,而是一片柳條林。再往遠看,就不能知道那是什麼地方瞭,因為也沒有人傢,也沒有房子,也看不見道路,也聽不見一點音響。
我想將來是不是我也可以到那沒有人的地方去看一看。
除瞭我傢的後園,還有街道。除瞭街道,還有大河。除瞭大河,還有柳條林。除瞭柳條林,還有更遠的,什麼也沒有的地方,什麼也看不見的地方,什麼聲音也聽不見的地方。
究竟除瞭這些,還有什麼,我越想越不知道瞭。
就不用說這些我未曾見過的。就說一個花盆吧,就說一座院子吧。院子和花盆,我傢裏都有。但說那營房的院子就比我傢的大,我傢的花盆是擺在後園裏的,人傢的花盆就擺到牆頭上來瞭。
可見我不知道的一定還有。
所以祖母死瞭,我竟聰明瞭。
七
祖母死瞭,我就跟祖父學詩。因為祖父的屋子空著,我就鬧著一定要睡在祖父那屋。
早晨念詩,晚上念詩,半夜醒瞭也是念詩。念瞭一陣,念睏瞭再睡去。
祖父教我的有《韆傢詩》,並沒有課本,全憑口頭傳誦,祖父念一句,我就念一句。
祖父說:
“少小離傢老大迴……”
我也說:
“少小離傢老大迴……”
都是些什麼字,什麼意思,我不知道,隻覺得念起來那聲音很好聽。所以很高興地跟著喊。我喊的聲音,比祖父的聲音更大。
我一念起詩來,我傢的五間房都可以聽見,祖父怕我喊壞瞭喉嚨,常常警告著我說:
“房蓋被你抬走瞭。”
聽瞭這笑話,我略微笑瞭一會工夫,過不瞭多久,就又喊起來瞭。
夜裏也是照樣地喊,母親嚇唬我,說再喊她要打我。
祖父也說:
“沒有你這樣念詩的,你這不叫念詩,你這叫亂叫。”
但我覺得這亂叫的習慣不能改,若不讓我叫,我念它乾什麼。每當祖父教我一個新詩,一開頭我若聽瞭不好聽,我就說:
“不學這個。”
祖父於是就換一個,換一個不好,我還是不要。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這一首詩,我很喜歡,我一念到第二句,“處處聞啼鳥”那處處兩字,我就高興起來瞭。覺得這首詩,實在是好,真好聽“處處”該多好聽。
還有一首我更喜歡的:
“重重疊疊上樓颱,幾度呼童掃不開。
剛被太陽收拾去,又為明月送將來。”
就這“幾度呼童掃不開”,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意思,就念成西瀝忽通掃不開。
越念越覺得好聽,越念越有趣味。
還當客人來瞭,祖父總是呼我念詩的,我就總喜念這一首。
那客人不知聽懂瞭與否,隻是點頭說好。
八
就這樣瞎念,到底不是久計。念瞭幾十首之後,祖父開講瞭。
“少小離傢老大迴,鄉音無改鬢毛衰。”
祖父說:
“這是說小的時候離開瞭傢到外邊去,老瞭迴來瞭。鄉音無改鬢毛衰,這是說傢鄉的口音還沒有改變,鬍子可白瞭。”
我問祖父:
“為什麼小的時候離傢?離傢到哪裏去?”
祖父說:
“好比爺像你那麼大離傢,現在老瞭迴來瞭,誰還認識呢?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小孩子見瞭就招呼著說:你這個白鬍老頭,是從哪裏來的?”
我一聽覺得不大好,趕快就問祖父:
“我也要離傢的嗎?等我鬍子白瞭迴來,爺爺你也不認識我瞭嗎?”
心裏很恐懼。
祖父一聽就笑瞭:
“等你老瞭還有爺爺嗎?”
祖父說完瞭,看我還是不很高興,他又趕快說:
“你不離傢的,你哪裏能夠離傢……快再念一首詩吧!念春眠不覺曉……”
我一念起春眠不覺曉來,又是滿口的大叫,得意極瞭。完全高興,什麼都忘瞭。
但從此再讀新詩,一定要先講的,沒有講過的也要重講。似乎那大嚷大叫的習慣稍稍好瞭一點。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這首詩本來我也很喜歡的,黃梨是很好吃的。經祖父這一講,說是兩個鳥,於是不喜歡瞭。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麵桃花相映紅。
人麵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這首詩祖父講瞭我也不明白,但是我喜歡這首。因為其中有桃花。桃樹一開瞭花不就結桃嗎?桃子不是好吃嗎?
所以每念完這首詩,我就接著問祖父:
“今年咱們的櫻桃樹開不開花?”
九
除瞭念詩之外,還很喜歡吃。
記得大門洞子東邊那傢是養豬的,一個大豬在前邊走,一群小豬跟在後邊。有一天一個小豬掉井瞭,人們用抬土的筐子把小豬從井吊瞭上來。吊上來,那小豬早已死瞭。井口旁邊圍瞭很多人看熱鬧,祖父和我也在旁邊看熱鬧。
那小豬一被打上來,祖父就說他要那小豬。
祖父把那小豬抱到傢裏,用黃泥裹起來,放在竈坑裏燒上瞭,燒好瞭給我吃。
我站在炕沿旁邊,那整個的小豬,就擺在我的眼前,祖父把那小豬一撕開,立刻就冒瞭油,真香,我從來沒有吃過那麼香的東西,從來沒有吃過那麼好吃的東西。
第二次,又有一隻鴨子掉井瞭,祖父也用黃泥包起來,燒上給我吃瞭。
在祖父燒的時候,我也幫著忙,幫著祖父攪黃泥,一邊喊著,一邊叫著,好像拉拉隊似的給祖父助興。
鴨子比小豬更好吃,那肉是不怎樣肥的。所以我最喜歡吃鴨子。
我吃,祖父在旁邊看著。祖父不吃。等我吃完瞭,祖父纔吃。他說我的牙齒小,怕我咬不動,先讓我選嫩的吃,我吃剩瞭的他纔吃。
祖父看我每咽下去一口,他就點一下頭,而且高興地說:
“這小東西真饞,”或是,“這小東西吃得真快。”
我的手滿是油,隨吃隨在大襟上擦著,祖父看瞭也並不生氣,隻是說:
“快蘸點鹽吧,快蘸點韭菜花吧,空口吃不好,等會要反胃的……”
說著就捏幾個鹽粒放在我手上拿著的鴨子肉上。我一張嘴又進肚去瞭。
祖父越稱贊我能吃,我越吃得多。祖父看看不好瞭,怕我吃多瞭。讓我停下,我纔停下來。我明明白白的是吃不下去瞭,可是我嘴裏還說著:
“一個鴨子還不夠呢!”
自此吃鴨子的印象非常之深,等瞭好久,鴨子再不掉到井裏,我看井沿有一群鴨子,我拿瞭秫稈就往井裏邊趕,可是鴨子不進去,圍著井口轉,而呱呱地叫著。我就招呼瞭在旁邊看熱鬧的小孩子,我說:
“幫我趕哪!”
正在吵吵叫叫的時候,祖父奔到瞭,祖父說:
“你在乾什麼?”
我說:
“趕鴨子,鴨子掉井,撈齣來好燒吃。”
祖父說:
“不用趕瞭,爺爺抓個鴨子給你燒著。”
我不聽他的話,我還是追在鴨子的後邊跑著。
祖父上前來把我攔住瞭,抱在懷裏,一麵給我擦著汗一麵說:
“跟爺爺迴傢,抓個鴨子燒上。”
我想:不掉井的鴨子,抓都抓不住,可怎麼能規規矩矩貼起黃泥來讓燒呢?於是我從祖父的身上往下掙紮著,喊著:
“我要掉井的!我要掉井的!”
祖父幾乎抱不住我瞭。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评分
可以一口气读完的故事,对肖红的兴趣,是从黄金时代后开始的
评分不错哦很喜欢嘻嘻和图片上的一样
评分京东正版热卖畅销好评最多
评分经典读物,纸张和印刷质量不错,正品
评分质量不错,价格合理。。。。
评分质量不错,内容凄美,笑着想哭!
评分可以一口气读完的故事,对肖红的兴趣,是从黄金时代后开始的
评分看完了,很不错,推荐下!
评分很好 越读越觉得凄凉 绝对正品 也没有伤痕 赞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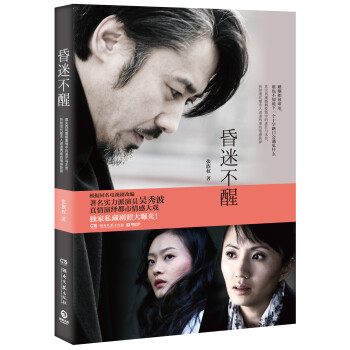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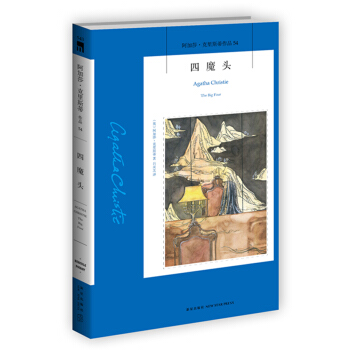

![野性的呼唤(译文名著精选) [The Call of the Wild and Other Stori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04252/53cf9bc9Nd1273ab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