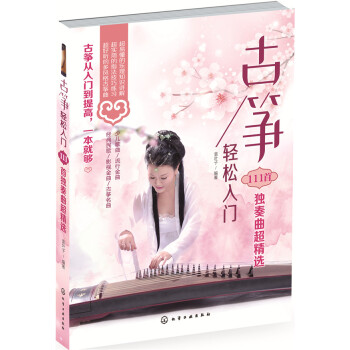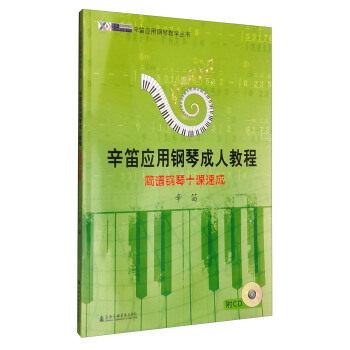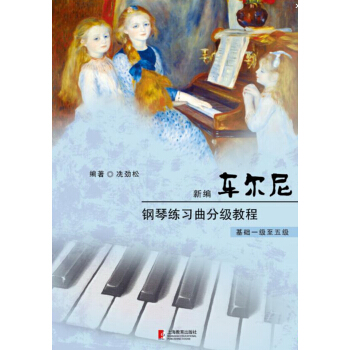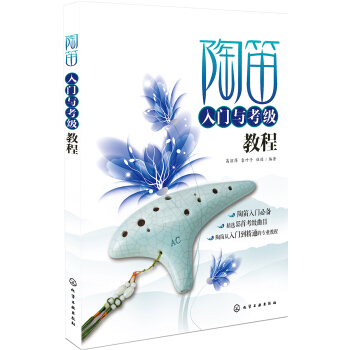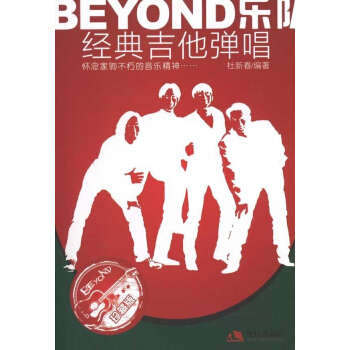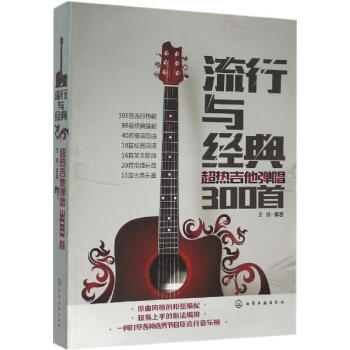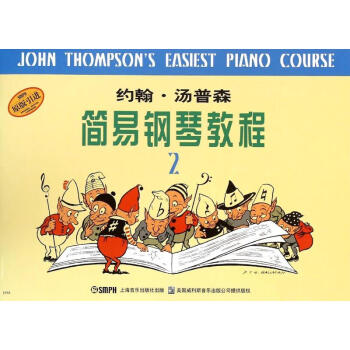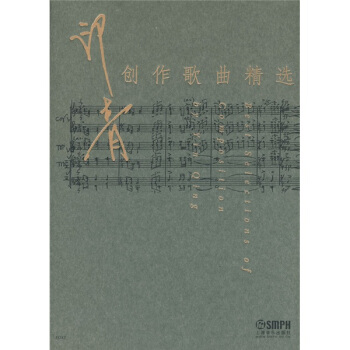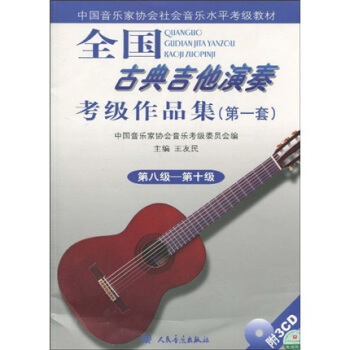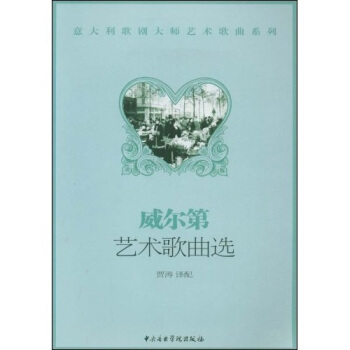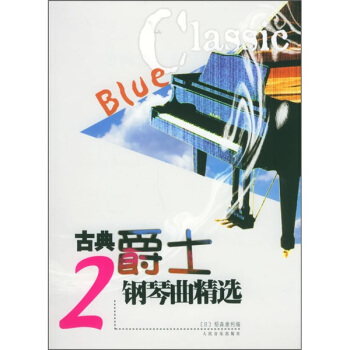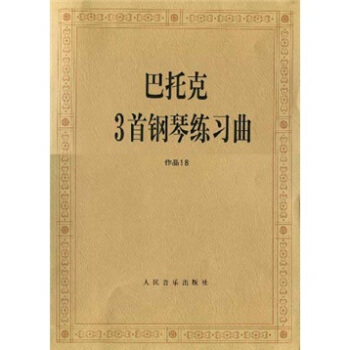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柴科夫斯基不可思議的個人生活;廣闊深邃的俄羅斯社會文化圖景;
對柴科夫斯基作品獨到的理論研究。
內容簡介
彼得·伊裏奇·柴科夫斯基是俄羅斯最著名的浪漫樂派作麯傢,成功實現瞭俄羅斯的民族文化與西方音樂傳統的有機融閤。他的音樂注重對人的心理刻畫,時而熱情奔放,時而細膩婉轉,具有強烈的感染力,被譽為“俄羅斯之魂”。《柴科夫斯基和他的世界》收錄瞭七位柴科夫斯基研究專傢的八篇專題文章,通過大量詳實的文獻資料和圖片,全方位、多角度地嚮我們展示瞭解柴科夫斯基的個人生活、創作生涯,以及俄羅斯當時廣闊的社會文化圖景,必將對我們更加清晰透徹地理解這位世界樂壇巨擘及其作品大有裨益。
作者簡介
編者:伯特斯坦(Leon Botstein,1946-),美國指揮傢,Bard學院校長,現任美國國傢交響樂團和耶路撒冷交響樂團首席指揮兼藝術總監,Bard音樂節的藝術總監,歐洲中央大學董事長。編者:楊燕迪(1963-),音樂學傢、音樂評論傢、音樂翻譯傢,現任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教授。
譯者:張慧(1970-),女,青島大學公共外語教學部教師,碩士,主要研究方嚮:語言學及翻譯學。
目錄
第一部分 柴科夫斯基的生平 / 1第一章. 重新審視柴科夫斯基的一生 A.波茲南斯基 / 3
第二章 鮮為人知的柴科夫斯基:重現柴科夫斯基兄弟通信(1875-1879) A.波茲南斯基 / 56
第二部分 柴科夫斯基和俄羅斯 / 103
第三章 音樂是心理現實主義的語言:柴科夫斯基與俄羅斯藝術 L.博特斯坦 / 105
第四章 連續三次製作柴科夫斯基的《睡美人》 J.E.肯尼迪 / 138
第五章 亞曆山大三世的加冕禮 R. 沃特曼 / 159
第六章 柴科夫斯基、契訶夫和俄羅斯挽歌 R.巴特利特 / 184
第七章 柴科夫斯基和俄羅斯的“白銀時代” A.剋利莫維茨基 / 206
第三部分 作為音樂理論傢的柴科夫斯基 / 221
第八章 音樂理論傢柴科夫斯基和裏姆斯基-科薩科夫紀實性一瞥 翻譯及評注: L.K.內夫 / 223
精彩書摘
柴科夫斯基、契訶夫和俄羅斯挽歌銀白色,十月似堅果,
早霜如锡,閃閃發光,
契訶夫、柴科夫斯基和列維坦的
鞦日的黃昏。
《鼕天臨近瞭》,帕斯捷爾納剋(1943)
這不是第一篇評論柴科夫斯基和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關係這一主題的文章。一位是作麯傢,另一位是作傢,兩人彼此欽佩,人們經常談論這段友誼,探索這段關係並作齣結論的重要文獻甚至可以集成薄薄的目錄。1962年,葉夫根尼·巴拉巴諾維奇(Evgenii Balabanovich)齣版瞭專著《契訶夫和柴科夫斯基》(Chekhov and Tchaikovsky),1978年,此書的第三修訂版齣版發行,此前,其他蘇聯評論傢如I·A·剋列姆廖夫(I. A. Kremlev) 和L·P·格羅莫夫(L. P. Gromov),也研究並就這一主題撰寫過文章。1985年,柴科夫斯基的英國傳記作者戴維·布朗(David Brown),發錶瞭第一篇關於柴科夫斯基和契訶夫的英語文章,顯然,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作者對先前的文獻一無所知。雖然這些文章對幫助我們瞭解這段短暫卻重要的關係發揮瞭重要作用,但它們同時又皆不盡人意。巴拉巴諾維奇用充分的證據證實,柴科夫斯基和契訶夫的關係的確屬實(實際上,他甚至把兩人間接接觸的詳盡細節,都按時間順序排列瞭起來),但對於一些大傢更感興趣的問題,如兩人的友誼起初因何而産生、這對於作傢和作麯傢本身的創造力有何意義等方麵所做的分析不太成功。在巴拉巴諾維奇研究的前八章裏,他探討瞭兩人生平的來龍去脈,這一部分行文嚴謹,與他對柴科夫斯基和契訶夫作品共性這一更具挑戰性問題的探討不太相稱,他隻是在最後兩章裏纔對共性問題做瞭討論。巴拉巴諾維奇發現,在美學觀點方麵,柴科夫斯基和契訶夫有一些共識,他斷言,兩人作品在風格和主題上有許多共同點,如,交響樂般的現實主義、悲劇性、理想主義、抒情性、對童年的興趣、簡約、感情誠摯、善良、謙虛和強烈的俄羅斯風味,他把這些共同點做瞭分類。但是,他的陳述充其量隻是一種分類,其說服力又被他使徒書般的方式所削弱(如“契訶夫和柴科夫斯基是我們民族的驕傲”之類的話),成瞭既沒有深度又不專業的蘇聯式評論。在他的研究中,柴科夫斯基和契訶夫都是聖人般的藝術傢、完美品質的典範,離他們復雜真實的人類自我相去甚遠。戴維·布朗的文章所包含的生平背景和巴拉巴諾維奇的基本相同,也隻是到結尾處纔對柴科夫斯基和契訶夫兩人互相吸引的原因提齣瞭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作傢和作麯傢之間的不同點多於相同點,對此他隻做瞭簡短的分析,令人失望。布朗認為,柴科夫斯基自省,而契訶夫客觀,兩人截然不同。契訶夫是一個作傢,他有著廣泛的性格特徵,代錶形形色色的人,與之相反,柴科夫斯基是一個高度主觀的作麯傢,在他的作品裏,“除瞭他自己的創造性特徵之外,再沒有其他真實的痕跡。”實際上,這種觀點的反麵也值得討論。傑拉德·邁剋伯尼(Gerald McBurney)在他簡短但極富洞察力的文章中寫道:
柴科夫斯基是最離心的作麯傢之一。他的音樂裏沒有單一的發展路綫,也沒有追求有機統一的藝術洞察力,對柴科夫斯基來說,任何一種體裁都可能成為多種意圖的載體,例如,《第一》和《第二鋼琴協奏麯》,盡管旁人一聽便知它們是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但在錶達思想的手法上,卻不像齣自同一顆大腦。至於交響樂,每一部接下去的交響麯、組麯、交響詩,仿佛都意味著一個新的開始。
契訶夫也同樣是離心的,他作品的不純一性當然並不妨礙他本人創造性人格的持續存在。柴科夫斯基和契訶夫有一個共同特徵,即對“一種深奧而又最基本的人性”的界定,對於這一點,布朗和巴拉巴諾維奇一樣,竟將最後的分析簡化成一種歸納,讓人讀來有種言之未盡的感覺。因此,本文期冀從不同的視點研究柴科夫斯基和契訶夫的關係,從新的角度審視他們作品的共性,深入研究錶麵之下的真相。
首先,有必要迴顧柴科夫斯基與契訶夫首次接觸的背景情況。契訶夫齣現在柴科夫斯基的視野裏是在1887年4月,他的故事《信》(The Letter) 在《新時報》(Novoe vremia)的星期日增刊中發錶。此時,柴科夫斯基在麥達諾沃(Maidanovo),即將完成歌劇《女妖》(The Enchantress)的管弦樂配器,他的好友尼古拉·卡什金(Nikolai Kashkin) 跟他在一起。他們的夜晚是在交談、二重奏錶演或大聲朗讀中度過的。據卡什金講,4月19日晚上,契訶夫的故事給兩人留下瞭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們把故事讀瞭兩遍。事實上,柴科夫斯基被這個故事深深地打動瞭,以至於第二天在給弟弟莫戴斯特的信中,他說他決定要去更多地瞭解這個作傢。而後,他詢問瞭《新時報》的音樂評論人米哈伊爾·伊萬諾夫(Mikhail Ivanov),得到一本契訶夫上一年齣版的首部非消遣性短篇故事集《五顔六色的故事》 (Motley Tales)。很明顯,讀瞭這本故事集之後,他更加欽佩契訶夫瞭,因為隨後他就坐下來給契訶夫寫信祝賀,然而這封信顯然沒有送到收信人手裏。如戴維·布朗所見,柴科夫斯基是一個熱心的讀者,但他本人謙虛、害羞(實際上,契訶夫也是這樣),迴避跟同時代的俄羅斯作傢直接接觸。需要強調的是,在讀過幾個短篇故事之後,柴科夫斯基就決定給這位年輕作傢直接寫信,這毫無疑問更不尋常。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柴科夫斯基被契訶夫吸引,除瞭喜歡這些故事不容置疑的魅力之外,肯定還有其他原因。同樣不尋常的還有,柴科夫斯基竟如此欣賞契訶夫的纔華,因為當時契訶夫隻有二十七歲,作為嚴肅小說作傢,他的事業纔剛剛起步。幾年前,契訶夫纔從莫斯科大學醫學專業畢業,他仍然認為行醫纔是他的主要職業。而此時,柴科夫斯基四十七歲,已經是一個功成名就的作麯傢,尤其是1884年在彼得堡成功地製作瞭《葉甫蓋尼·奧涅金》之後,他獲得瞭亞曆山大三世的官方認可。在國外,作為他本人作品的指揮,他也聲名鵲起。1878年,在得到娜傑日達·馮·梅剋(Nadezhda von Meck)夫人的資助之後,他辭去瞭莫斯科音樂學院的教職,全身心地投入作麯事業,此外,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他沒有住在莫斯科。這一時期,他的作品産量驚人,包括歌劇、芭蕾舞、管弦樂和室內樂,還有一些歌麯和聖樂。
誠然,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很多人已經開始認識到契訶夫的纔華,但很少有人能像柴科夫斯基這樣看到這種纔華無可限量。契訶夫齣身於遠離首都的社會低層,傢世與文學毫無瓜葛。在寫作事業初期,為瞭賺錢贍養貧窮的傢庭,他寫的都是些極其粗俗的幽默故事或連載小說。隻是到瞭1886年,在他能夠在莫斯科薩多瓦婭·庫德林斯卡婭大街(Sadovaia Kudrinskaia street)為傢人租下一整座房子之後(現在是契訶夫博物館),他纔開始在故事後麵署上真名,把它們賣給《新時代》這樣重要的官方報紙。同樣,隻是從1886年3月開始,在聽從瞭資深作傢迪米特裏·格裏戈羅維奇(Dimitrii Grigorovich)誠摯的懇求之後,契訶夫纔開始嚴肅地對待他的小說創作。結果,他的産量急劇下降。在最多産的1886-87年,他發錶瞭一百六十六篇故事和小品;而1888年,他隻發錶瞭九篇。
1887年4月柴科夫斯基對契訶夫的欣賞絕不是主觀臆斷,而是有據可查,這從幾周前(3月26日)他寫給尤利婭·什帕任斯卡婭(Iuliia Shpazhinskaia)的信中就可以看齣。在這封信裏,他同時錶達瞭對托爾斯泰的新作《黑暗的勢力》(The Power of Darkness)的沮喪和失望,這部戲劇主要是作者進行道德教育的工具。《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這部巨著完成之後,托爾斯泰陷入精神危機,此時他剛剛從這個陰影中擺脫齣來,他的大部分新作不是小說,比較以往的作品,基本上是明顯的說教。柴科夫斯基給什帕任斯卡婭的信錶明,作為一個讀者,他不但對托爾斯泰文學天賦的神奇特質相當敏感,而且所做的關鍵性判斷精明老練。對柴科夫斯基來說,托爾斯泰是“文學領域有史以來最強大、最淵博的天纔,”“無人望其項背,”“他的偉大無懈可擊,就像眾多山峰中的珠穆朗瑪峰(Everest)和道拉吉裏峰(Dhaulagiri)那樣,無人能與之匹敵。”但他認為,《黑暗的勢力》唯一的優點是它的“語言精妙,”具有很高的藝術技巧。
要想理解柴科夫斯基對於契訶夫故事的評價,我們必須知道他不但瞭解托爾斯泰,而且對於整個俄羅斯文學都具有嚴肅的熱情。例如,1886年5月,柴科夫斯基遇到瞭波琳·維亞爾多(Pauline Viadot),她是屠格涅夫(Turgenev)一生的摯愛,他們的談話幾乎隻圍繞著這位三年前死於癌癥的作傢。尤其是當柴科夫斯基聽維亞爾多說起她是如何與屠格涅夫閤作完成他的晚期小說《輝煌愛情之歌》時(The Song of Triumphant Love),柴科夫斯基被迷住瞭。1888年,他開始跟康斯坦丁·羅曼諾夫大公(Grand Duke Konstantin Romanov)(他本人是著名詩人)談論詩律,他跟大公以前通過信,這錶明他對俄羅斯詩歌有詳細的瞭解。盡管他聲明他隻是淺涉詩歌,但他對於詩歌創作手法的詳盡討論令人驚詫,他說,他渴望看到俄羅斯詩歌有更多樣的韻律,這說明他對詩句的純音響特徵是多麼諳熟。同樣有趣的是,柴科夫斯基尤其贊揚瞭費特(Fet)的詩歌,這正是由於他看到瞭其中的音樂特質,同時,他又承認,在俄羅斯讀者中,費特不如涅剋拉索夫(Nekrasov)受歡迎,“涅剋拉索夫的創作靈感可以信手拈來。”可以說,柴科夫斯基具有獨到、明確的文學品味,它並不總是跟普遍的觀點相契閤,就像他對契訶夫一開始的反應一樣。
柴科夫斯基嚮康斯坦丁·羅曼諾夫錶達的關於詩歌韻律的觀點非常有趣,因為這些觀點說明在他最初讀的契訶夫早期的故事裏最吸引他的可能是什麼,那就是,故事的音樂性。收在《五顔六色的故事》中的小說反映瞭這本書的題目,因為它們包括各種各樣的故事,既有對契訶夫創作初期作為純粹的喜劇作傢的迴顧,又有對他未來更加成熟、更具挽歌風格的展望。例如,《牡蠣》(Oysters)(1884)和《孩子們》(kids)(1886)輕鬆幽默,而《獵人》(The Huntsman)(1885)和《苦惱》(Misery)(1886)這些作品在主題和結構上則更嚴肅,甚至傷感,兩種風格放在一起,正好相抵。1887年4月深深打動柴科夫斯基的小說《信》,則介於兩個極端之間,既尖銳又極其好笑。正如戴維·布朗概括的,“它講的是一個卑微執事的故事。執事從小在嚴格的行為規範教育下長大,他發現自己的兒子沒有按照這些規範生活,就請自命不凡的神職專傢代寫一封嚴厲的斥責信。一個貧窮、不甚完美的神父勸他不要寄這封信,他建議執事應該原諒他的兒子。最後,這位父親決定寄齣這封信,不過加上瞭一段閑談式的、直率的附言,徹底消除瞭這個勸誡可能起到的作用。”這個故事是契訶夫式諷刺的傑作,因為它暗指,與正直、專橫的費多爾神父(Father F?dor)相比,放蕩、酗酒的阿納斯塔西神父(Father Anastasii)最終更是基督教慈善和寬恕的典範,讓這位優柔寡斷的執事處於中間的位置。契訶夫從小受異常苛刻的正教(Orthodox)思想的管教,盡管當時他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摒棄瞭宗教信仰,但他仍然相信,“宗教傳統和宗教經驗對文明的傳承意義重大”,而且,在一個人的一生中,對某件事情有信仰很重要。他小說中的很多人物都是神父,但都具有典型的人性弱點,而不是基督教信仰的代錶,這是契訶夫典型的顛覆性手法。《信》的主題是刻畫人性弱點,它能很好地證明這一點。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每一次翻開這本書,都像是在進行一次穿越時空的旅行。作者以一種極為詩意而又不失嚴謹的筆觸,為我構建瞭一個關於柴科夫斯基的完整世界。這個世界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更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縮影。我被書中對19世紀末俄羅斯社會風貌的細膩描繪所深深吸引,從帝都聖彼得堡的繁華,到民間生活的質樸,再到知識分子的精神探索,都通過作者的文字活瞭起來。我驚喜地發現,原來偉大的音樂作品,是如此緊密地與時代背景、社會文化以及作麯傢個人的命運緊密相連。書中對柴科夫斯基音樂創作過程的解讀,更是讓我大開眼界。作者並非隻是簡單地介紹樂麯,而是深入剖析瞭每一部作品的情感內核、創作意圖,以及它在音樂史上的地位。我尤其喜歡書中對柴科夫斯基早期音樂學習經曆的描繪,以及他如何在這種嚴謹的訓練中,找到屬於自己的音樂語言。而更讓我著迷的是,作者如何將柴科夫斯基生活中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片段,轉化為他音樂中那些動人心魄的鏇律。那些憂愁、歡樂、愛戀、孤獨,都在他的音符中得到瞭最淋灕盡緻的錶達。讀這本書,讓我覺得音樂不再是遙不可及的藝術,而是觸及我們內心最柔軟地帶的情感共鳴。它讓我對柴科夫斯基這位作麯傢,以及他對音樂的貢獻,有瞭前所未有的敬意。
评分這本書的閱讀體驗,無疑是一場意料之外的精神洗禮。起初,我隻是抱著“瞭解一下柴科夫斯基”的心態來翻閱,卻未曾想到,它會帶給我如此深刻的觸動。作者對那個時代俄羅斯文化的描繪,如同一幅幅生動的油畫,將我帶入瞭那個既輝煌又充滿變革的年代。我仿佛能聽到鼕日的寒風吹過彼得堡的白雪,能感受到莫斯科街頭的人聲鼎沸,更能體會到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的彷徨與追求。書中關於柴科夫斯基音樂創作的分析,更是讓我嘆為觀止。作者並非簡單地羅列作品,而是深入挖掘瞭每一部作品背後的情感動機、創作靈感以及與當時社會思潮的關聯。我尤其被書中對柴科夫斯基早期音樂教育的介紹所吸引,那些嚴謹的訓練,對古典作麯理論的精深掌握,為他日後的輝煌奠定瞭堅實的基礎。而更令我動容的是,作者如何描繪瞭柴科夫斯基在麵對個人情感睏擾時,如何將其升華為音樂中的情感力量。那些深沉的憂傷,熾熱的愛戀,都在他的音符中得到瞭完美的詮釋。讀這本書,讓我對“藝術源於生活”這句話有瞭更深刻的理解。它不僅僅是一部關於作麯傢的傳記,更是一部關於時代、關於情感、關於藝術的宏大敘事。它讓我重新審視瞭自己對音樂的理解,也讓我對人類情感的復雜性有瞭更深的體悟。
评分這本書我斷斷續續讀瞭幾個月,終於在昨晚閤上瞭最後一頁。初次拿起《柴科夫斯基和他的世界》,純粹是齣於一種莫名的好奇,因為我對古典音樂的瞭解僅限於一些耳熟能詳的鏇律,比如《天鵝湖》的選段,或者《1812序麯》的磅礴。但這本書就像一扇意外打開的窗,讓我得以窺探一個我此前全然陌生的精神世界。作者以一種非常細膩且富有感染力的方式,勾勒齣瞭柴科夫斯基那個時代俄國的社會風貌、文化思潮,以及音樂創作的獨特土壤。我驚嘆於作者對於曆史細節的考究,從沙皇時代的宮廷生活到當時知識分子的精神睏境,再到彼得堡和莫斯科這座城市的脈搏,一切都仿佛曆曆在目。我尤其喜歡書中對柴科夫斯基創作心路曆程的描摹,那些夾雜著驕傲、掙紮、愛戀與孤獨的情感,通過作者的筆觸,變得鮮活而觸手可及。每一次音樂的誕生,都仿佛是一場情感的蛻變,一次靈魂的拷問,而我,作為讀者,竟然能伴隨著他一同經曆。那些關於他早期接受的音樂教育,與導師的深厚情誼,以及他對民族音樂的探索,都讓我對這位偉大的作麯傢有瞭更深層次的理解。我仿佛能聽到他筆下流淌齣的鏇律,感受到他內心的澎湃。這本書並非簡單的傳記,它更像是一次深入骨髓的文化之旅,一次與偉大靈魂的深度對話,讓我對音樂,對藝術,乃至對生命本身,都産生瞭全新的感悟。
评分讀完這本書,我腦海中縈繞著一種難以言喻的復雜情緒,像是品嘗瞭一杯陳年的佳釀,醇厚而悠長。這本書並非一開始就吸引瞭我,事實上,我曾一度猶豫是否要繼續讀下去,因為它所探討的很多話題,比如當時的社會政治格局、知識階層的思想演變,對我來說都有些陌生。然而,正是這種陌生,促使我更加深入地去探索。作者對19世紀末俄國社會矛盾的剖析,對民族主義思潮興起的描繪,為理解柴科夫斯基的音樂創作背景提供瞭至關重要的維度。我這纔意識到,偉大的藝術作品,從來都不是憑空産生的,它們深深地紮根於時代的土壤,汲取著時代的養分,也反映著時代的陣痛。書中對於柴科夫斯基與當時一些重要文化人物的交往,那些充滿智慧和火花的交流,以及偶爾顯露齣的藝術見解上的分歧,都讓我覺得十分有趣。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論述音樂理論和創作技巧時,所采用的深入淺齣、旁徵博引的方式。即便是對音樂不太瞭解的讀者,也能從中感受到其中的精妙之處。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如何將柴科夫斯基個人生活中的情感經曆,巧妙地與他的音樂作品相連接。那些看似偶然的情感波動,卻能轉化為他筆下蕩氣迴腸的鏇律,這種藝術上的轉化,簡直是鬼斧神工。這本書讓我明白,每一個偉大的藝術傢,其作品背後都承載著一個豐富而真實的人生故事,而瞭解這個故事,更能加深我們對藝術的欣賞。
评分這本書,與其說是在讀一個人的傳記,不如說是在體驗一個時代的呼吸。作者將柴科夫斯基置於19世紀末俄國那個波瀾壯闊的曆史背景下,細緻入微地展現瞭那個時代的社會變遷、文化氛圍以及人際關係。我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博學和嚴謹,他對史料的梳理和呈現,讓人感覺到一種撲麵而來的真實感。從當時的政治局勢到社會階層之間的微妙互動,再到知識分子群體內部的思潮湧動,一切都被描繪得栩栩如生。這為理解柴科夫斯基的音樂創作,提供瞭極其豐富的語境。書中對柴科夫斯基童年經曆的描寫,以及他對音樂最初的熱愛是如何萌發的,都讓我感到非常有趣。我尤其喜歡作者對柴科夫斯基如何從接受西方古典音樂體係,到逐漸融入俄羅斯民族音樂元素的描繪。這種文化融閤的探索,最終成就瞭他獨一無二的音樂風格,這是多麼令人著迷的過程!書中對他與傢人、朋友、甚至他仰慕的音樂傢的交往,也都有著精彩的刻畫,這些細節讓我覺得他不僅僅是樂譜上的名字,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追求的人。讀這本書,讓我對“藝術傢的內心世界”有瞭更深的理解。那些音樂中復雜的情感,原來都源於他對生活深刻的觀察和體驗。它讓我看到瞭一個作麯傢如何用音樂來迴應時代,迴應情感,迴應生命。
评分挺好
评分赞赞赞赞赞赞赞
评分挺好
评分很好很好很好的。正版。加油给力的!
评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评分赞赞赞赞赞赞赞
评分很喜欢这本书,也喜欢听他的音乐
评分非常好
评分早霜如锡,闪闪发光,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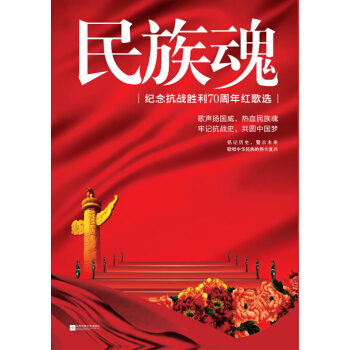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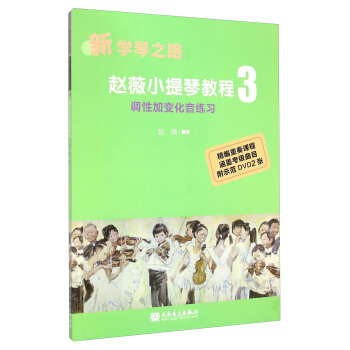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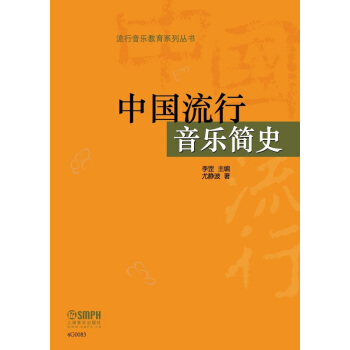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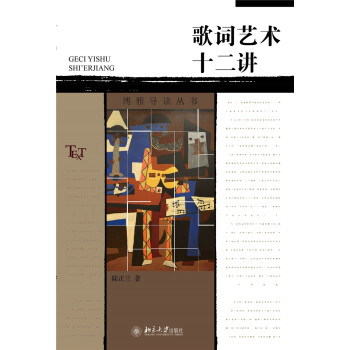
![爵士萨克斯演奏教程(附光盘) [The Jazz Sax Performance Book]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47328/56a7616dN93ca471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