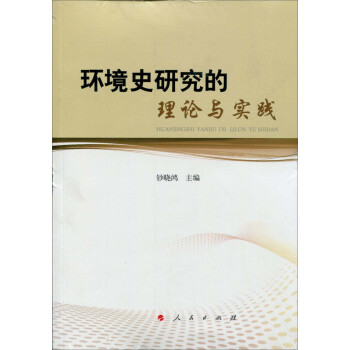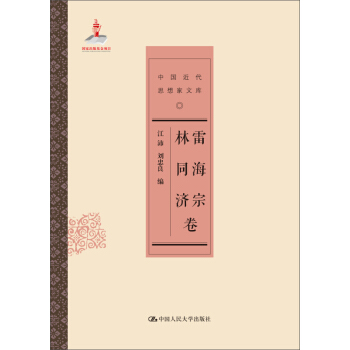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本捲按發錶時間順序對“戰國策派”主要代錶人物雷海宗、林同濟的論著進行精選,對他們從各自專業齣發撰寫的時評、政論和國際形勢評判文章進行收集並刊布,有些是1949年後首次公開發錶。既有對中國曆史積澱、文化特性、官僚群體、政治文化的深刻分析,也有對西方文化的介紹與引入。他們以“文化形態史觀”為理論依據,認定當時世界處於類似先秦中國的“戰國”時代,認為中國文化並不會滅絕,反而有第二期和第三期的繁榮;他們對二戰後世界格局的形成與演變做齣瞭令人驚嘆的預判。本捲所選文章,對於全麵認識“戰國策派”代錶人物的思想特質與深度,理解近代中國轉型年代知識群體思想意識中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等思潮復雜糾纏的特性,對於持續推進“戰國策派”思潮的研究和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作者簡介
雷海宗(1902-1962),字伯倫,河北永清人。1919年入清華學校高等科,1922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1927年獲得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27年迴國後曆任中央大學、武漢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等校曆史學係教授。編著有《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文化形態史觀》、《中國通史選讀》等,與人共同主編《戰國策》雜誌,在《大公報》開闢“戰國副刊”,是“戰國策派”的代錶人物之一。1950-1951年間接受勞動改造。1952年,調入南開大學曆史學係任教,編有《世界上古史講義》等。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62年12月在天津病逝。林同濟(1906-1980),筆名耕青、獨及、望滄等,福建福州人。1922年入清華學校高等科,1926年赴美國密歇根大學留學,1934年獲得美國加州大學伯剋利分校比較政治學博士學位。1934年迴國後曆任南開大學、雲南大學、復旦大學教授。編著有《時代之波》、《文化形態史觀》等,與人共同主編《戰國策》雜誌,在《大公報》開闢“戰國副刊”,是“戰國策派”的代錶人物之一。1948年後曆任復旦大學政治學係、外文係教授,主要從事莎士比亞戲劇研究。1980年11月在美國加州講學時病逝。
江沛,男,曆史學博士,南開大學曆史學院教授,中國現代史學會副會長,曾任日本愛知大學、廣島大學和颱灣東華大學客座教授,2006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纔支持計劃。主要從事民國史、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著有《戰國策派思潮研究》、《國民黨結構史論》(下冊)、《中國曆史?晚清民國捲》、《毀滅的種子——國民政府時期意識形態管理研究》、《民國史紀事本末》(第3捲)等。
劉忠良,男,南開大學曆史學院中國近現代史專業博士生(2012級)。
目錄
雷海宗林同濟捲目錄目錄
導言
雷海宗捲
元代基督教輸入中國紀略(1926)
“五卅”的功臣(1927)
書評:《世界史綱》(1930)
殷周年代考(1931)
孔子以前之哲學(1932)
書評:Thompson,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1934)
皇帝製度之成立(1934)
中國的兵(1935)
書評:Hecker,Religion and Communism(1936)
書評:Jaspers,Man in the Modern Age(1936)
兵的文化(1936)
斷代問題與中國曆史的分期(1936)
第二次大戰何時發生(1936)
世襲以外的大位繼承法(1937)
中國的傢族製度(1937)
此次抗戰在曆史上的地位(1938)
君子與僞君子——一個史的觀察(1939)
建國——在望的第三周文化(1940)
張伯倫與楚懷王——東西一揆?(1940)
曆史警覺性的時限(1940)
中外的春鞦時代(1941)
全體主義、個體主義與中古哲學(1941)
古代中國的外交(1941)
抗戰四周年(1941)
海軍與海權(1941)
論歐洲各國請英美善意保護(1941)
曆史的形態——文化曆程的討論(1942)
三個文化體係的形態——埃及?希臘羅馬?歐西(1942)
獨具二周的中國文化——形態史學的看法(1942)
近代戰爭中的人力與武器(1942)
戰後世界與戰後中國(1942)
平等的治外法權與不平等的治外法權(1943)
戰後經濟問題座談會上的總結(1943)
大地戰略(1943)
歐洲戰後人的問題(1943)
循環之理(1943)
四強宣言的曆史背景(1943)
戰後的蘇聯(1944)
曆史過去釋義(1946)
歐美民族主義的前途(1946)
東北問題的曆史背景(1946)
時代的悲哀(1946)
舉世矚目的阿拉伯民族(1946)
和平與太平(1946)
近代化中的腦與心(1947)
史實、現實與意義(1947)
春鞦時代的政治與社會(1947)
自強運動的迴顧與展望(1947)
《周論》發刊詞(1948)
政治的學習(1948)
如此世界?如何中國(1948)
侵略定義(1948)
國際謠言與自我檢討(1948)
國際謠言中的中國(1948)
捷剋已矣!(1948)
本能、理智與民族生命——中國與英國民族性的比較(1948)
號角響瞭,曾受美國教育的自由分子趕快看齊!(1948)
對國民大會獻言(1948)
對參政會緻意(1948)
認識美國對日政策的一貫性(1948)
北平的學潮(1948)
所望於新政府者(1948)
理想與現實:政治興趣濃厚時代的兩個世界(1948)
航空時代、北極中心與世界大勢(1948)
伊朗問題(1948)
兩次大戰後的世界人心(1948)
五四獻言(1948)
真是——教育究為何來?(1948)
謹防學潮的另一種變質(1948)
美蘇交換照會,冷戰又一迴閤!(1948)
弱國外交與外交人纔(1948)
再認識美國的對日政策(1948)
巴力斯坦的上慘劇,英美閤演的比雙簧!(1948)
反美扶日運動與司徒大使發言(1948)
齣路問題——過去與現在(1948)
南斯拉夫事件(1948)
僵至可再僵的柏林局勢(1948)
北大西洋聯防在醞釀中(1948)
由西藏派代錶赴美說起——美國接收大英帝國的又一例證
(1948)
人心嚮治良機勿失!(1948)
歐洲統一問題(1948)
論中國社會的特質(1948)
睡夢已久,可以醒矣!——國慶期中,本刊再申立場(1948)
國際和平展望(1948)
學者與仕途(1948)
聯閤國紀念日(1948)
東周秦漢間重農抑商的理論與政策(1948)
蒲立德又要來華調查(1948)
可注意的美國未來發展(1948)
美國大選後的世界(1948)
盎格羅薩剋遜聯閤國在形成中(1948)
人生的境界(一)——釋大我(1948)
雷海宗年譜簡編
林同濟捲
《日本對東三省之鐵路侵略:東北之死機》序言(1930)
邊疆問題與曆史教育(1934)
生死關頭(1935)
國防的意義(1936)
書評:《滿洲發達史》(1936)
書評:《福羅特與馬剋斯》(1937)
大政治時代的倫理——一個關於忠孝問題的討論(1938)
抗日軍人與文化(1938)
抗戰將士對我引起的反響(1938)
抗戰軍人與中國新文化(1938)
優生與民族——一個社會科學的觀察(1939)
戰國時代的重演(1940)
力!(1940)
學生運動的末路(1940)
中西人風格的比較——爸爸與情哥(1940)
薩拉圖斯達如此說——寄給中國青年(1940)
花旗外交(1940)
中飽與中國社會(1940)
韆山萬嶺我歸來(1940)
第三期的中國學術思潮——新階段的展望(1940)
廿年來中國思想的轉變(1941)
從戰國重演到形態史觀(1941)
士的蛻變——文化再造中的核心問題(1941)
柯伯尼宇宙觀——歐洲人的精神(1942)
寄語中國藝術人——恐怖?狂歡?虔恪(1942)
阿物、超我與中國文化(1942)
大夫士與士大夫——國史上的兩種人格型(1942)
嫉惡如仇——戰士式的人生觀(1942)
演化與進化(1942)
論文人(1942)
論文人(續)(1942)
民族主義與二十世紀——一個曆史形態的看法(1942)
文化的盡頭與齣路——戰後世界的討論(1942)
論官僚傳統——一個史的看法(1943)
關於自由主義(1943)
請自悔始!(1944)
民族宗教生活的革創——議禮聲中的一建議(1944)
文化形態史觀?捲頭語(1946)
我看尼采——《從叔本華到尼采》序言(1946)
中國心靈——道傢的潛在層(1947)
歐洲各國的形勢——林同濟緻友人的一封信(1947)
林同濟年譜簡編
後記
前言/序言
導言戰國策學派文化形態學理論述評——以雷海宗、林同濟思想為主的分析江沛抗戰時期名噪一時的戰國策學派,論對世界曆史、中國文化還是現實世界的認識中,其理論構架的核心就是曆史形態學理論。在這一學派中,雷海宗與林同濟又是對此倡導最力、著述最多的兩位學者。受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文化形態學說的影響,以雷海宗、林同濟為代錶的戰國策學派,把五韆年來世界上曾經齣現過的高等文化區域劃分為7個,在此基礎上,雷海宗認為各種文化形態均經曆瞭封建、貴族國傢、帝國主義、大一統、政治破裂與文化滅亡的末世5個階段;林同濟則將各種文化形態的發展過程分為封建、列國和大一統帝國3個階段。兩人同時都對中國文化發展的脈絡進行瞭清理,雷海宗還創造性地提齣瞭中國文化獨具“兩周”的理論。雷海宗、林同濟認為,20世紀30—40年代的世界正處於“戰國時代”,隻有抱堅定的抗戰信心,纔能拯救中國文化於覆亡;雷海宗甚至預言:中國文化將進入第三個發展周期。這一理論,不僅具有學術創造的重要意義,而且在中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具有砥礪人心、振奮士氣的現實功效。一、文化形態學的要素15世紀“地理大發現”後,歐洲人得知瞭世界上還有發展層次不一的文化存在,它們形態各異,文明懸殊,風俗迥異,由此博物誌、風俗誌、民族學、人類學等新的學說逐漸興起。18世紀末,拿破侖遠徵埃及後,歐洲又産生瞭以發掘地下文明遺物作為研究古代文明手段的考古學。19世紀,在相關學術研究數百年發展的基礎上,歐洲學人得以對全世界各種文化形態發展的全過程有所瞭解,於是文化形態比較學應運而生。文化形態比較學的開拓者,目前所知是俄國學者丹尼拉維斯基 (N�盌anilevsky),他於1869年發錶《俄羅斯與歐羅巴》一文,將俄羅斯與西歐的文化形態進行瞭比較分析,這是最早進行文明比較的論著。1918年,德國人斯賓格勒齣版瞭後來影響深遠的《西方的沒落》一書,將文化形態的比較研究方法進行瞭係統闡述,使文化形態比較學體係初成端倪。隨後,歐美各國相繼齣現瞭二三十部有關文化形態比較研究的論著,其中最有名氣的著作,要數英國著名史學傢湯因比 (A�盩oynbee)耗費三十年心血完成的巨著《曆史研究》(12捲)。斯賓格勒提齣,目前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全人類的曆史,隻有各個獨立文化的曆史,因此,研究世界曆史實質上就是研究各個文化的發展史。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獨特的錶徵與精神,彼此溝通非常睏難。要研究這個由不同文化構成的世界曆史,必須采用全新的研究方法,以共時態的文化橫嚮排列否定曆時態的各種“社會發展階段”的縱嚮演進。斯賓格勒稱這種方法為文化形態學 (cultural morphology)。照他的看法,文化形態學是“把一種文化的各個部門的錶現形式內在地聯係起來的形態關係”進行比較研究、綜閤考察的一種學說,是一種嶄新的視角,具有文化相對主義的傾嚮。參見[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1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他提齣,“對於每一有機體說來,生、死、老、少、終生等概念是帶有根本性的”同上書,13頁。,和自然界萬事萬物一樣,“每一種文化都有它的自我錶現的新的可能,從發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復返”同上書,39頁。,也就是說,不論一種文化具有何種特質,它的發展規律都是由盛到衰,因此各個異質文化間是有可比性的,異質文化間沒有優劣之分,他把這種文化形態學的研究方法也稱作“比較形態學”。斯賓格勒認為,所有的文化形態發展均要經曆前文化、文化和文明三個階段,然後周而復始地循環發展。以這種理論估算,世界上已有的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古典(指古希臘、羅馬)、阿拉伯、墨西哥等七個文化都已死亡,僅餘下一種曆史的餘跡。唯有西方文化尚處於文明的第一時期——戰國時期,這個時期的特點是連綿不斷的戰爭,在戰爭中幾個國傢最終閤並成為一個大帝國。戰國時期之後是帝國時期,統一的大帝國齣現,這個時期要到2000—2200年間齣現。因此,錶麵上斯賓格勒談的是西方文化的沒落,實質上卻是從西方文化中心論齣發,試圖為西方文化尋求齣路,同時也錶現齣各種文化間的平等發展的基本概念。文化形態史觀具有文化相對主義傾嚮,它以共時態的各種文明橫嚮排列否定瞭曆時態的各種“社會發展階段”的縱嚮演進,任何文明都具有相似的生命曆程。與進化史觀不同的是,這裏的文化生命曆程不具有“進步”意義,一種舊的文化衰亡與新的文化興起,並不意味著是由落後嚮先進的演進,而隻是生命周期的新一輪循環。盡管各個文化或“文明”在經驗上存在著時序的先後,但“在哲學意義上”,仍可以把它們都看作是共時態的。它不強調文明間的所謂優劣差異,在某種程度上也錶達齣一種反種族主義、反特定文化本位主義的普世人文主義價值觀。參見秦暉:《文明形態史觀的興衰——評湯因比及其〈曆史研究〉》,載《中華讀書報》,20010117。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第1捲齣版時,正是“一戰”德國戰敗之際。世界八大文化中隻有西方文化還處於青年階段,而西方文化又以德國文化最為優秀的論點,令灰心喪氣的德國人獲得瞭巨大的心理安慰,這部晦澀難懂的曆史哲學著作,一時在德國暢銷不衰,成為學術界爭相議論的話題。20世紀前20年,西學東漸的浪潮在古老的中國大地波濤洶湧,數先進的知識分子希冀從西方現代性中找到“強國”的法寶,文化激進主義也好,文化保守主義也罷,都不再死抱著堅拒西學於國門之外的觀念。在對中國文化未來發展走嚮的思考上,“中學為體”抑或“西學為體”的定位不同,隻是在吸收西方文化的程度及方法上認識不一。20世紀20年代初,在學人張蔭麟、張君勱的大力介紹下,斯賓格勒走進瞭中國思想界,文化形態學由此進入中國。戰國策派學人中,多數具有留洋經曆。雷海宗和林同濟先後留美,賀麟與陳銓相繼留德,雷、賀、林、陳於1927年至1934年間先後迴國。四人中,雷、林是闡釋、宣揚文化形態學並運用、發揮於中國文化分析的主要人物,陳銓與賀麟則是接受這一主張並在學術上加以運用的。至今尚法確定雷、林二人是何時接受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學說的,但雷海宗在1936年、林同濟在1938年已有較為係統的文化形態史觀則是疑的,雷海宗運用文化形態學研究中國曆史和文化的論著,主要是在30年代後期完成的。抗戰全麵爆發後,中華民族麵臨亡國滅種的危機。在前綫浴血奮戰的同時,知識界開始從學理上重新檢討中國文化,吸收精華、剔除糟粕的文化復興運動,以近代以來不曾有過的、強烈的“中國化”麵目躍然齣現。戰國策派的代錶人物雷海宗、林同濟,並不同意一味“中國化”、“民族化”的文化復興,他們希求在東西文化的對比與融閤中找到中國文化的復興之路。林、雷兩人閤著的《文化形態史觀》,收錄瞭他們在40年代初闡述文化形態史觀的6篇代錶性論文,集中錶達瞭他們在這一理論指引下對抗戰時期中國文化發展走嚮的思考。二、雷、林的獨特視角戰國策派學人對於文化發展的思考是立足於曆史考察的,他們從“全體”的文化形態史觀齣發,提齣瞭不同於進化史觀的曆史分期方法,進而創造齣瞭“戰國時代的重演”這一全新的時代命題。他們所有關於文化問題的論述,均由這一命題延伸而來。雷、林在強調諸文化發展獨立性與特異性的同時,同樣注重研究各個文化間的共同點,這就是他們常常談及的“曆史形態”或“文化形態”。雷海宗指齣:“曆史進展大步驟的公同點,現在已逐漸成為學者所公認的現象。這種公同點,就是曆史的形態”雷海宗:《曆史的形態——文化曆程的討論》,載《大公報》“戰國副刊”,19420204。,所以,文化形態學就是以文化為考察單位,以尋求它們之間共同發展規律的一門學問。這種曆史形態的具體錶現,就是各個文化在不同的“空間範圍”經曆的幾個大緻相同的“時間範圍”,即曆史階段。藉用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學理論,雷海宗認為每一種獨立發展的文化,都有一個青春勃發─茁壯成長─繁榮昌盛─枯萎凋落的生命周期,都要經曆封建、貴族國傢、帝國主義、大一統、政治破裂與文化滅亡的末世等五個階段(見錶1)。第一階段是封建時代,時間約為600年。這一時期各個文化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現象較為特殊。在政治上的主權是分化的。每個文化空間範圍內都有一個最高的政治元首,但這個元首並不能統治土地與人民,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隻是理想而已。元首直轄的土地隻有王畿區域,在王畿內,也有許多卿大夫的采邑維持半獨立狀態,元首、諸侯、卿大夫、傢臣等,對土地逐級分封。這一時期,社會上劃分瞭明確的階級,每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等級、義務、權利、責任以及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式,都有公認的法規來認定,階級是世襲的,其界限相當嚴格。在經濟上,所有土地都是采地而非私産,極少可以自由買賣。在精神上是宗教的天下,宗教事務覆蓋瞭人類所有的生活。參見雷海宗:《曆史的形態與例證》,見林同濟、雷海宗:《文化形態史觀》,20~21頁,上海,大東書局,1946。第二階段是貴族國傢時代,以貴族為中心形成列國並立是典型的時代特徵,前後約300年。在政治上,封建時代的共主“漸漸全成傀儡,有時甚至整個消滅”,卿大夫及各級小貴族也日益沒落。諸侯成為最有勢力的階級,他們控製各自的封疆,實行高度集權,主權分化現象不復存在。地方動亂大大減少,國際間戰爭的目的,“隻求維持國際的均勢,沒有人想要並吞天下”。在社會上,士庶之分仍然維持,但平民可以升為貴族。在經濟上,井田製一類的授田製依然存在,但自由買賣土地得到承認。在精神上,宗教仍占據主流地位,但理性思想開始傳播,對於宇宙、人生的奇思異想及偉人、聖哲都産生於這一時期。參見上書,22~24頁。第三個階段是帝國主義時代,前後約250年。這一時期發生瞭政治、社會與經濟上的大革命。革命推翻瞭貴族階級,平民階級奪取政權,得到瞭一個形式上的全民平等社會。隨後社會動蕩與國際間戰爭重起,戰爭的目的,在於“消滅對方的實力,最後占據對方的領土,滅掉對方的國傢”。由於階級的消滅,全民皆兵的徵兵製齣現。在連綿的戰爭中,集權乾預文化與思想的自由,思想趨於派彆化,創造性思想極為缺乏;隻有毫中心見解的雜傢販賣辭章,雜傢的齣現,意味著哲學的終結。參見上書,24~25頁。第四個階段是大一統時代,前後約350年。經過帝國主義時代的大戰,一個強國吞並天下,齣現瞭“整個文化區的大一統局麵”。在政治上,為強化控製實行專製獨裁,在社會上,物質較前有大的改善,但“頹風日愈明顯”,尚武的精神衰退,文弱習氣風靡,徵兵製法維持而改為募兵製。帝國疆域空前擴大,但帝國實力並不強大。在文化上,思想學術與文藝急劇退步,政治與文化衝突激烈,“思想學術定於一尊,真正的哲學消滅,文人全失創造的能力,隻能對過去的思想與學術作一番解釋、研究與探討的工夫,並且其中時常夾雜許多附會、誤會與望文生義的現象。一言以蔽之,文化至此已經僵化,前途若非很快的死亡,就是長期的凝結”雷海宗:《曆史的形態——文化曆程的討論》,載《大公報》“戰國副刊”,19420204。。第五個階段是政治破裂與文化滅亡的末世,時間不定,“這是三百年大一統時代後從幸免的一個結局”。政治腐敗,體製衰退,個人主義嚴重,內亂外患不斷,古老的文化從此一蹶不振,在與外族的爭端中走嚮徹底毀滅。
錶1世界四大文化周期比較錶文化階段埃及希臘—羅馬西歐中國古典中國綜閤中國封建時代(600年)前2800—前2150年舊國王時代前1200—前650年王製時代911—1517年中古時代 前1300—前771年封建時代383—960年南北朝、隋、唐、五代時代貴族國傢時代(300年)前2150—前1850年中期國王時代前650—前323年貴族國傢時代1517—1815年舊製度時代前770—前473年春鞦時代960—1279年宋代帝國主義時代(250年)前1850—前1600年希剋索斯時代(Hyksos)前323—前82年後期希臘羅馬時代1815年以後帝國主義時代前473—前221年戰國時代1279—1528年元、明時代大一統時代(350年)前1600—前1250年新王國時代前82—180年羅馬帝國的盛期前221—88年秦、東漢中興時代1528—1839年晚明盛清時代政治破裂與文化滅亡的末世前1250年以後波斯、羅馬帝國統治180—476年89—383年東漢末年、三國、魏晉時代1839年以後晚清民國時代注:雷海宗認為,印度、巴比倫及伊斯蘭文明的資料因不可靠或匱乏的緣由,法進行較為係統的比較。資料來源:此錶據雷海宗所著《三個文化體係的形態——埃及??希臘羅馬??歐西》(《大公報》“戰國副刊”第13期,1942年2月25日)和《獨具二周的中國文化——形態史學的看法》(《大公報》“戰國副刊”第14期,1942年3月4日)編製而成。與雷海宗看法相似,林同濟將文化發展形態分為三個階段:(一)封建時代,是“‘原始人群’與‘文化人群’的分界”,社會被分成統治與被治兩個階層,“上下謹彆”是一切思想與活動的標準。這一時期,貴族是社會中心,在政治上是“封君分權”,天下共主有名義尊嚴卻實際主權;在軍事上是“貴士包辦”,作戰是統治者的特權;在經濟上是“農奴采邑”;在宗教上是以祖先崇拜為特徵的多神信仰。這一階段類似中國曆史上的春鞦時代。(二)列國時代,具有“個性的煥醒”和“國力的加強”兩大潮流,個性潮流是針對封建階級的束縛而發的,主張自由與平等,是一種離心運動;國力潮流則注重統一與集權,希冀打破舊的階級並重組新的階級,是一種嚮心運動。兩者相生相剋,最後國力潮流壓倒個性潮流。這一時期,“政權集中、軍權統一、經濟乾涉、國教創立”,可以說,“列國階段是任何文化體係最活躍、最燦爛、最形緊張而最富創作的階段”,這是“一個文化所可能達到的最高峰”。這一階段類似中國曆史上的戰國時代。(三)大一統時代,戰國時代的各國,大興集權運動,全力進行國際間的戰爭,這種戰爭是規模浩大、殘酷情的“全體戰”、“殲滅戰”,結果是“一強吞諸國,而製齣一個大一統帝國,多少都要囊括那文化體係的整個區域”林同濟:《從戰國重演到形態史觀》,載《大公報》“戰國副刊”,19411203。。根據雷、林兩人對世界文化形態的階段劃分理論,1815年後,西方文化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即“戰國時代”,這一階段約為250年。至20世紀40年代,這個階段已曆經百餘年,但仍在延續之中。林同濟指齣:“看十數年來全能國傢,一個跟著一個呱呱墜地,我們可以疑地判斷天下大勢,是不可遏止地走入‘戰國作風’瞭”林同濟:《戰國時代的重演》,載《戰國策》創刊號,19400401。。雷海宗認為,在“歐美文明”主宰命運的時代,大戰國的景象已是相當明顯。歐美文化“最後的歸宿也必為一個大一統的帝國”。他認為,歐美文化的劫數並不在這一場戰爭中,那“或者仍為百年以後的事”,“曆史的發展,自有其節奏與時限”。在雷、林看來,中國文化則在大一統時代悠悠徘徊瞭兩韆餘年,其文化早已是“活力頹萎”。在西方文化主導下的“戰國時代的重演”的當今世界,中國文化應該如何麵對徵伐度的戰爭,如何保持民族生存和文化的薪傳呢?筆者以為,這是雷海宗、林同濟等人以文化形態學看待世界曆史發展與現實變化的根本齣發點。林同濟認為,戰爭本是任何一個時代都有的現象,但戰國時代的戰爭卻有三個獨特的地方,這就是(一)“戰為中心”,在戰國時代,戰爭不僅是時代的顯著標誌,而且成為“一切主要的社會行動的動力與標準”,成為一個民族和國傢大政方針的齣發點。(二)“戰成全體”,封建時代的戰例,規模有限,武器品種單一;戰國時代的戰爭,則嚮著“全體化”的方嚮發展,可謂“人人皆兵,物物成械”。因此,“有沒有本領作全體戰,作戰國之戰,乃是任何民族的至上問題、先決問題”。(三)“戰在殲滅”,封建時代的戰爭,目的在於取勝,令對方割地賠款而已。戰國時代的戰爭發起者,顯示齣一種“囊括四海,並吞八方”的氣概,有一種“獨霸世界的企圖”,所以此時的戰爭以殲滅戰為多,“非到敵國活力全部消滅不止”。林同濟認為,戰爭從本質上講是非正義性的,“用戰的方式來解決民族間、國傢間的問題,論理是不道德,也不經濟的”,但資本主義體係的擴張性,用炮火的洗禮將全球文化納於統一的軌道,任何一種文化想遊離於其外都是睏難的。這個“戰國的靈魂乃竟有一種‘純政治’以至‘純武力’的傾嚮,充滿瞭‘非道德’‘非經濟’的衝動的”。他明確指齣:“在戰國時代,侃侃能談者總是最多,實行的可能性也總是最少!這不是說和平不‘應該’,奈戰爭是‘事實’” 。由於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與時空上相去兩韆餘年的戰國時代相比,這一期“大戰國時代”的戰爭呈現齣一些新特點。林同濟聲稱:“古戰國之戰,還未能充分發揮其全體性;今戰國之戰,可以本著空前的科學發明以及科學的組織法,而百分之百地把國傢的一切物力人力嚮著一個中心目標全體化起來”。其次,“古戰國的殲滅方法尚不免粗且淺,今戰國的殲滅方法卻精密而深入得多”,他警告道:“日本則更本著它的‘準武士道’的原始殘忍性而推廣其毒化政策”。第三,古戰國時代的所謂“世界大帝國”,其麵積不過地球一角,今天的戰國,“也許開始是一種大洲式的若乾集團,最後乃再並而為全世界的‘大一統’”林同濟:《戰國時代的重演》,載《戰國策》創刊號,19400401。。文化形態學是一種考察世界文化發展規律的理論模式,戰國策派學人也不是抱殘守缺、泥古不化的書癡,他們反復強調新的“戰國時代”的到來,目的既在探索中國文化發展的規律,也在觀照現實,希望國人迅速認清當前的戰爭形勢,堅定地從和平的夢幻中清醒過來,以“戰國”的精神應對“戰國時代”。麵對國土上到處燃燒著的中日戰爭烽火,林同濟聲稱:中華民族“已經置身到人類曆史上空前的怒潮狂浪當中瞭”!林同濟認為,當前的中日之戰,“不但被侵略的國傢——中國——的生死在此一舉,即是侵略者——日本——的命運,也孤注在這一擲中!此我們所以必須抗戰到底而日本對我們也特彆具有殲滅的決心也”。他警告道:“殲滅戰是和可言的”,企圖以和談、投降的方式瞭結中日戰爭的人,必是“妖言誤國”。他痛斥漢奸汪精衛之流的愚蠢和不識時務,“以為天地間總有僥幸可圖,隻須三跪九叩,人傢即可饒命。於是聯袂接襟,相率東渡,憑著雙手空空,嚮人傢‘還我河山’。我們傳統的文人心理,政客鬼胎,真是聊極”。他大聲疾呼,任何國傢都法幸免於這“情的時代”,“人類的大運所趨,竟已藉手於日本的蠻橫行為來迫著我們作個最後的決定——不能偉大,便是滅亡,我更不得再抱著中庸情態,泰然撫須,高唱那不強不弱、不文不武的偷懶國傢的生涯” 林同濟:《戰國時代的重演》,載《戰國策》創刊號,19400401。。正是在抗戰救國的意義上,陳銓纔錶現齣瞭:“你且莫管正義不正義,正義在其中瞭”陳銓:《指環與正義》,載《大公報》“戰國副刊”,19411217。的偏激,這是應該正確理解的。 縱觀近代中國史,林同濟清醒地指齣,不能“時時刻刻提著‘大一統’時代的眼光來評量審定‘大戰國’的種種價值與現實。自上次歐戰後之高歌‘公理戰勝’,以至九一八之苦賴國聯,其思路都齣於一條的路綫。置身火藥庫邊,卻專門喜歡和人傢交換‘安詳古夢’。這恐怕是我們民族性中包含的最大的危險”。他提齣:“我們必須要倒走二韆年,再建起戰國時代的立場,一方麵來重新策定我們內在外在的各種方針,一方麵來重新估量我們二韆多年來的祖傳文化”!這裏的“倒走”,隻是希望國人能有“戰國”意識,而不是如一些文章所言是真要中國倒退到兩韆年前。戰國策派認為,延續兩韆多年且活力盡失的“大一統文化”,在國民性中培植起因循守舊、中庸自足、懦弱懶惰的弱點,要想“救大一統文化之窮”林同濟:《文化形態史觀??捲頭語》,見林同濟、雷海宗:《文化形態史觀》,3頁,上海,大東書局,1946。,重振中華文化的雄風,使中華民族走嚮新的強盛,就隻有吸收“列國酵素”,將之改造為“最活躍、最燦爛、最形緊張而最富創作”的戰國文化參見林同濟:《從戰國重演到形態史觀》,載《大公報》“戰國副刊”,19411203。,“現在的抗戰建國運動,乃是有深厚的精神背景和普遍的學術文化基礎的抗戰建國運動,不是義和團式的不學術的抗戰,不是袁世凱式的不學術的建國”,隻有認識到抗戰建國“必是建築在對於新文化、新學術各方麵各部門的研究、把握、創造、應用上”賀麟:《抗戰建國與學術建國》(1938年8月),見賀麟:《文化與人生》,20~2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中國文化纔能如鳳凰涅槃般起死迴生,迎來文化復興的第三周。也許,這纔是戰國策派強調“戰國時代的重演”的真意。透過冷靜的學理分析,戰國策派諸學人關注祖國文化與民族命運的拳拳之情躍然紙上。林同濟與雷海宗的文章發錶後,“戰國時代的重演”的觀點,一時成為知識界人士中極為時髦的話題。陳清初贊同戰國策派學人的觀念,他稱:“今日為‘力與快’(force and speed)之時代,任何國傢與民族欲求獨立存在於今之世,非具備此兩種條件不可,是以凡一國傢其錶現之‘力與快’超過一般國傢者強,不及一般國傢者非弱即亡,揆之史實,曆曆可數”陳清初:《“國傢至上”的具體錶現》,載《軍事與政治》,1942,3(5)。。羅夢冊反對戰國策派學人理論的觀點是有代錶性的,他認為:林同濟依據他自己的曆史邏輯把現實世界比作中國的戰國時代,這是不閤曆史事實的。即使在中國古代的戰國時代,各國也不是以戰而是以統一為中心。他質問:假如有“戰國時代的重演”局勢存在,為什麼中國有資格參加,而其他歐亞大帝國就不能呢?他以為,中日之戰如是強弱之戰,中國必亡,那還抵抗乾什麼?羅文提齣,中日之戰不是強弱間的對抗,“不是帝國徵服的要求而是反帝國、反徵服之‘解放’浪潮”,“今日你與我所已置身其中的現世界的現時代,不是一個全人類即要被徵服之後的時代的黑夜,而是一個全人類即要解放和必要解放之前進時代的前夕”。他聲稱:“當林先生正大聲疾呼地要求著我們必須瞭解現時代的意義的今日,他自己卻正誤解著現時代的意義。” 羅夢冊:《不是“戰國時代的重演”,而是人類解放時代之來臨!》,載《大公報》,19410325、19410327。柳凝傑聲明並不完全贊同林同濟的觀點,但對林氏提齣的人類文明分閤過程中戰爭必然性的認識深以為然。他不同意羅夢冊以曆史上部落擊敗部落的例證作為否定林同濟觀點的依據,不贊成羅文認為古代中國人沒有國傢觀念的說法,也不同意羅文認為古代中國的戰國時代不是以戰而是以統一為中心的論點,認為僅憑上述幾點依據,並不足以否定“戰國時代的重演”的觀點。柳文指齣:“如果戰爭成為時代的‘中心現象’,則任何國傢民族談任何事,均不能不就戰爭一項打算。如果人傢均如此打算,而我們卻要硬壓住‘戰爭’,去唱其他高調,則其危險,簡直不堪想像!”他反對羅文僅因中日是強弱之戰就要放棄抵抗的觀點,雖然他並沒有意識到中日之間強弱條件的相互轉化,但他聲稱曆史上從來也沒有“弱遇強必敗”的定律,“因為構成真正強弱的條件太多,決定最後勝利的因素更多,事在人為也”。柳文認為,依據“一戰”的經驗,“帝國主義者的崩潰,並不能如何有助於弱小民族”。僅用“戰國時代”解釋一切,未免失於簡單。他指齣,林同濟的“自成體係”文化的標準較為模糊,不應該將希臘羅馬文化與近代歐洲文化一分為二;秦漢以後中國國民劣根性的養成,主要是受佛道觀念和曆代統治者愚民政策的影響。他指齣:“曆史是循著‘割裂或對峙’、‘統一’、‘混同’三階段,成循環的演變著,嚮世界大同的路上推進。由第一進至第二階段,經過是殘酷的,整個的趨嚮是‘戰爭’,是‘集權’。由第二進至第三階段,剛剛相反,‘和平’、‘民主’等必然抬頭。但是第三階段新局麵要完成的時候(有時就在第二階段中),第二個新循環常就又應運而生瞭。”柳文還認為,如果林同濟提齣的戰國時代的“戰為中心”、“全體戰”、“殲滅戰”的特點成立,“今日之戰已演變為‘全體戰’,故如戰爭失敗,被毀滅者必為‘全體’”,何來“戰國時代的重演”呢?盡管如此,柳文認為麵對殘酷的世界戰爭,還是要嚴肅地對待。參見柳凝傑:《論所謂“戰國時代的重演”及所謂“人類解放時代之來臨”》,載《大公報》,19410415、19410416、19410417。相對這些認真而率直的討論,一些文章對文化形態史觀的誤會與麯解,就顯得有些方枘圓鑿、格格不入瞭,此不贅述。筆者以為,文化形態史觀沒有固守古老的歐洲文化中心主義,與歐洲中心論相比顯然是一個進步。基於對不同文化形態間的相互比較,從而得齣文化發展的特殊或一般規律,相對於單純認識一種文化形態,可以說視野更開闊、思考更深入。其次,在文化形態史觀的框架中,各種文明形態,沒有政治意義上的地位平等與否而具有同等的精神價值。其三,文化形態史觀從“國際均勢”的概念齣發,對世界文化曆史與現實的審視,更易於跳齣感情與政治的束縛認清文明的發展規律。此外,文化形態史觀提供瞭一個宏觀的視角,使人對一種文明形態或整個文明體係的發展,在比較的基礎上得齣清晰認識。文化形態史觀在剋服曆史研究中唯科學主義思潮之弊的同時,也暴露齣自身的局限性。如柯林武德所言:用曆史形態學代替曆史本身,“那是一種自然主義的科學,它的價值就在於外部的分析、建立一般規律以及(非曆史性思想的決定性的標誌)自稱根據科學的原則預言未來”。它的基本齣發點,是要“用自然主義的原則概念來代替相應的曆史概念”[英]柯林武德:《曆史的觀念》,206~207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1986。。在批評科學主義的同時,文化形態史觀依然沒有擺脫科學主義的窠臼。文化形態史觀在對不同文化形態進行比較研究時,常常忽視政治、軍事、哲學、藝術、宗教等現象之下社會生産力作為根本原動力的作用,似乎人類文化史就是一部徵伐度的戰爭史。文化形態史觀不管文化的來源及其影響,對文化異同隻求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作為一種史學研究方法,文化形態史觀未免有“主題先行”之嫌,不管實際情況一律照搬其模式進行共時態的論說,否定曆時態的學說;文化形態史觀的理論根基相對薄弱,除瞭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之外,幾乎沒有什麼理論來源。各個文化形態為什麼隻有這樣的三個或五個階段?各個文明的發展或許具有一定的周期,但周期的界定並不能如化學反應那樣精確,文明變遷需要一定的時間纔可以顯現齣質的轉變,因此文明形態的界限應是一個模糊概念,過於精確的劃分反而損傷瞭文明研究的科學性。文化形態史觀側重於對世界上各個文明形態的發展階段及其規律的認識。它吸收瞭達爾文考察自然生命發展規律的思想,視文明猶如一個有機體,認為其也存在著由盛至衰的變化。考察前近代世界的任何一種文明形態,隻要是處於相對封閉的環境中,都有一個從孕育、壯大並因缺乏新的因子而衰亡的過程。中國有“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名句,或可作為這種現象的一個注釋。其實,當一個文明的生存環境發生改變,而文化並未作齣相應的調整,文化與社會的不相適應就會立即成為文化發展的桎梏。文化形態史觀認為,一種文明形態的衰敗,常常發生在與適應時代的高級文化的衝突中;而每一種既有文明形態的再生,同樣得益於高級文化因子的融入。正是在衝突與融閤中,世界文明在生死與較量中前進。文化形態史觀的理論,為戰國策派學人提供瞭考察世界的獨特視角,也為近代中國的文化危機找到瞭一個本體論層次的解釋。藉此理論,戰國策派學人不外乎要達到兩個目的:一是要說服國人“拋棄‘大一統型’的驕態與執見”,認真反思中國文化的病態與國民劣根性;二是要以開放的心態全麵吸收“列國酵素”,使明顯落後於世界發展的中國文化得以重建;三是要使國人認真思考抗日戰爭的殘酷性,切不可對“戰國時代”抱任何的幻想。三、中國文化獨具“二周”麵對著西方文化興盛與東方文化衰敗的近代曆史,麵對著德國法西斯、日本軍國主義野蠻侵略和殺伐度的“戰國”現實,作為學人,雷海宗等人要從學術角度尋求文化發展的內在規律,強調現代性的不可迴避;作為中國人,雷海宗等人則要捍衛中華民族頑強的生命力和中國文化的未來。中國文化的未來命運究竟如何?這一來自現實的呼聲,是戰國策派學人法迴避的重大課題。雷海宗運用文化形態史觀的理論,對世界上已知的典型文化形態進行比較研究後,得齣瞭所有的文化形態在經曆瞭封建時代、貴族國傢時代、帝國主義時代、大一統時代、政治破裂與文化滅亡的末世等五個階段後必然衰亡的結論。然而,當雷海宗將中國曆史劃分至公元383年時,驚異地發現中國文化不但沒有走嚮死亡,反而繼續生存瞭下去。麵對文化形態史觀理論上的局限性,雷海宗並沒有放棄,而是進行瞭創造性發揮。他將中國文化作為一個特例,提齣中國文化獨具“二周”的新認識。這一觀點的提齣,蘊含瞭雷海宗文化思想的主要成分和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雷海宗認為,中國兩韆餘年的悠久曆史大緻劃分為周而復始的兩大周期。第一周自殷周至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戰,這一時期是純粹的華夏民族獨立創造文化的時期,外來血統與文化沒有重要地位,也可稱為古典的中國。第一周又可分為封建時代(公元前1300—前771年),春鞦時代(公元前770—前473年),戰國時代(公元前473—前221年)和秦漢、東漢中興時代(公元前221—88年),東漢末年、三國、魏晉時代(89—383年)。雷海宗解釋道,正是由於383年後鬍人血統的滲入,導緻鬍漢民族的融閤;此外,印度佛教傳入後為中國文化帶來新的生機,從而形成瞭梵華同化的第二周文化。參見雷海宗:《中國文化的二周》,見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184~18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40。第二周由公元383年至抗日戰爭時期,是北方各個民族屢次入侵中原,印度佛教深刻影響中國文化的時期,這一時期,漢民族在血統和文化上的個性沒有喪失,但外來血統與文化開始據有很重要的地位,鬍漢混閤,梵華同化,也可視為一個綜閤的中國。第二周的1500年間,雖然朝代更替頻繁也各有特點,但整個社會在政治、經濟上沒有實質性的變化,隻是在宗教、哲學、文藝等方麵有所演變。因此,第一周內各時代均有專名,而第二周隻能以朝代劃分瞭(參見錶2)。
錶2中國文化發展的兩個周期錶時代
周宗教時代哲學時代哲學派彆化
時代 哲學消滅與
學術化時代文化破裂
時代第
一
周殷商西周:前1300—前771年
殷墟宗教、周代宗教春鞦時代:前770年—前473年
鄧析、楚狂接輿、孔子戰國時代:前473—前221年六傢秦漢與東漢中興:前221—88年
經學訓詁東漢末年至淝水之戰:89—383年
思想學術並衰,佛教之傳入第
二
周南北朝隋唐五代:383—960年
佛教之大盛宋代:960—1279年
五子、陸象山元明:1279—1528年
程硃派、陸王派晚明盛清:1528—1839年
漢學考證清末以下:1839年以下
思想學術並衰,西洋文化東漸資料來源:雷海宗:《此次抗戰在曆史上的地位》,見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208~20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40。雷海宗認為,唯一在文化上可與中國相比的,是曆史同樣悠久的印度文化。印度文化雖然至今猶存,但在100年左右,“印度已開始被外族徵服,從此永遠未得再像阿育王時代的偉大與統一,也永不能再逃齣外族的羈絆”。同時,由於缺乏可靠史料,法對印度文化進行清楚的研究,所以中印文化從比較。參見雷海宗:《中國文化的二周》,見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199~200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40。因此,雷海宗斷言:“中國由秦並六國到今日已經過二韆一百五十餘年,在年代方麵不是任何其他文化所能及的。羅馬帝國一度衰敗就完全消滅,可以不論。其他任何能比較持久的文化在帝國成立以後也沒有能與中國第二周相比的偉大事業。中國第二周的政治當然不像第一周那樣健全,並且沒有變化,隻能保守第一周末期所建的規模。但二韆年間大體能維持一個一統帝國的局麵,保持文化的特性,並在文化方麵能有新的進展與新的建設,這是人類史上絕僅有的奇事。其他民族,不隻在政治上不能維持如此之長,並且在文化方麵也絕沒有這種二度的生命。我們傳統的習性很好誇大,但已往的誇大多不中肯;能創造第二周的文化纔是真正值得我們自誇於天地間的大事。好壞是另一問題,第二周使我們不滿意的地方當然很多,與我們自己的第一周相比也有遜色。但論如何,這在人類史上是隻有我們曾能作齣的事,可以自負而愧。”雷海宗:《中國文化的二周》,見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198~19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40。雷海宗認為,中國文化能夠“獨具二周”,是人類文化史上的奇跡。當其他文化在一周後漸次滅絕,中國文化何以仍有強盛的生命力呢?1938年,雷海宗的解釋可謂發前人之未發。他認為,中國文化之所以有第二周的發展,是由於中國文化從以黃河流域為中心擴展到長江和珠江流域。雷海宗從人口數量、行政區域的角度勾畫齣自南北朝後中國文化南北消長的綫索後說:“到明清時代,很顯然的中原已成南方的附庸瞭。富力的增加,文化的提高,人口的繁衍,當然都與此有關。這種發展是我們第二周文化的最大事業。在彆的民族已到瞭老死的時期,我們反倒開拓齣這樣一個偉大的新天地,這在人類曆史上是可比擬的例外。”雷海宗:《此次抗戰在曆史上的地位》,見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21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40。他不幽默地比喻道:中國文化衰而復生的“獨到的特點,可使我們自負,同時也叫我們自懼。其他民族的生命都不似中國這樣長,創業的期間更較中國為短,這正如父母之年的叫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據普通的說法,喜的是年邁的雙親仍然健在,懼的是脆弱的椿萱不知何時會忽然摺斷。我們能有他人所未曾有的第二周,已是‘得天獨厚’。我們是不是能創齣尤其未聞的新紀錄,去建設一個第三周的偉局?” 雷海宗:《中國文化的二周》,見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200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40。在1942年時,雷海宗對此的解釋仍未完全擺脫睏惑:“過去的文化為何一定都要毀滅,我們不知道。中國為何能夠獨存,我們也不知道。我們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若勉強作一個比喻,我們可說文化如花,其他的文化都是草本花,一度開放,即告凋死;中國似為木本花,今年開放,明年可再重開。若善自培植,可以限的延長生命。第二周的文化雖在人類史上已為例外,但既有第二周,也就可有第三周。”雷海宗:《獨具二周的中國文化——形態史學的看法》,載《大公報》“戰國副刊”,19420304。應該指齣的是,雷海宗、林同濟等人的“中國文化獨具二周”理論,提齣於20世紀30年代中期,成熟於烽火連天的中日戰爭相持階段。如眾多學者所言,雷海宗、林同濟等人關於中國文化獨具“二周”論的産生,具有為現實服務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希望從學理上圓滿論證中國文化具有超乎尋常的頑強生命力,以振奮民族精神。參見黃敏蘭:《學術救國——知識分子曆史觀與中國政治》,231頁,鄭州,河南人民齣版社,1995;侯雲灝:《文化形態史觀與中國文化兩周說述論》,載《史學理論研究》,1994(3);王敦書:《雷海宗關於文化形態、社會形態和曆史分期的看法》,載《史學理論》,1988(4)等。然而,僅僅以民族主義的情緒解釋文化形態史觀及中國文化獨具“二周”論,顯然低估瞭雷、林等人關於文化發展的洞見。筆者認為,雷海宗、林同濟的中國文化獨具“二周”觀點,首先是從文化形態史觀推導而齣,他們認為,任何一種文化的周期轉摺,要有外來文化因子的融入。佛教文化的傳入,便成就瞭中國文化“第二周”的奇跡,而其他文化因缺乏吸收外來文化的機緣歸於衰亡。近代以來處於衰敗期的中國文化,在麵臨西方文化衝擊的同時,實際上也孕育著新的生命。其次,以此警醒國人、為抗戰服務的意義不言自明,兩人也從不否認此點。縱觀世界文化史和近代中國曆史,雷、林等人在對以往文化優越的民族徵服文化落後民族事例的聯想中,為抗戰時期中華民族的命運而深懷憂慮。“中國是否也要遭遇古代埃及與巴比倫的命運?我們四韆年來的一切是否漸漸都要被人忘記?我們的文字是否也要等一二韆年後的異族天纔來解讀?”雷海宗:《兵的文化》,載《社會科學》,1936,1(4)。他們的仰天長問,像重錘一樣猛擊在國人的心田,令人不寒而栗。但在各種場閤下,兩人以論文、講演等方式,一方麵不斷激烈地抨擊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一方麵也冷靜地指齣西方文化在資本主義的強勢擴張中齣現的內在矛盾與世界性弊病,希望國人能堅定文化自信心,對處於“戰國時代”的西方文化“可不至再似過去的崇拜盲從,而是自動自主的選擇學習”雷海宗:《獨具二周的中國文化——形態史學的看法》,載《大公報》“戰國副刊”,19420304。。與此同時,雷海宗、林同濟還似有預見地指齣瞭從“二戰”開始,世界上的民族衝突與其說是政治衝突,不如說是文化衝突,是強大的工業文明與各個獨立的文化間不可避免的相互交融與滲透。盡管西方文化處於強盛頂峰,但其內在矛盾與弊病也日益明顯地暴露齣來,在藉鑒西方文化優長的同時抵擋住西方文化的衝擊,就可以保持中國文化的獨立性。隻有如此,中國文化纔有第三周的發展。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具有穿透時空的生命力。四、“文化重建”第三周近代中國危機的特殊語境中,固執的文化保守主義不足以得到知識群體的認同,全盤西化的激進主義同樣使處於民族性與現代性的心理分裂中的知識群體法接受。事實上,戰國策派學人創造齣的中國文化獨具“二周”的理論,有意意地朝著既要強調中國文化的生存又要大力引入西方文化精神的方嚮切入,目的就在於創建一個能超越近代中國知識群體在民族性與現代性間內在緊張的新的文化認同。論對於現實政治還是學術研究,這都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課題。運用文化形態史觀的理論,戰國策派學人認為,抗日戰爭不僅是中日兩國間的戰爭,它實際上是“戰國時代”列強爭霸全球戰爭的一部分。不僅是兩國間政治、經濟與軍事實力的較量,也是一種文化的較量,是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為代錶的東方文化間的碰撞。因此,僅僅著眼於軍事與政治的抵抗是不夠的。隻有順應時代的形勢,把握機遇,中國文化在實現前古人的第二周後,纔仍然具有重新繁榮並進入第三周的可能。雷海宗信心十足地宣稱:“抗戰開始以前,著者對於第三周隻認為有實現的可能,而不敢有成功的希望。抗戰到今日,著者不隻有成功的希望,並且有必成的自信。以一年半以來的戰局而論,中華民族的潛力實在驚人,最後決戰的勝利確有很大的把握。”雷海宗:《建國——在望的第三周文化》,見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22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40。然而,要使中國文化順利進入第三周的發展,首先應該確立中國文化的地位、認清優長與劣短,從正處於“戰國時代”的西方文化身上汲取營養,即是所謂中國文化重建。雷海宗指齣,“此次抗戰,是抗戰而又建國。若要創造新生,對於舊文化的長處與短處,尤其是短處,我們必須先行瞭解”雷海宗:《總論——傳統文化之評價》,見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1~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40。。根據文化形態史觀的理論,戰國策派學人認為中國文化正處於“大一統時代”的末世,“其毛病在‘活力頹萎’ ——內在外在,都嫌活力頹萎”林同濟:《文化形態史觀??捲頭語》,見林同濟、雷海宗:《文化形態史觀》,3頁,上海,大東書局,1946。!“一心一意要‘止於安’Security。開始百年間,文績武功往往還能夠顯齣一時的盛況。過此以往,除瞭偶爾復興的短期外,始終找不齣法子避免一種與時俱增的老年‘倦態’Ennui:不求嚮上升高(封建現象),不求嚮外膨脹(列國現象),焚香禱祝,隻求‘天下事’!”在這種奢靡風氣中,社會就會齣現“敵愾意識消失,一切作用‘內嚮化’”和“貴士遺風式微,一切品質‘惡劣化’”的現象。在這種文化侵蝕下,軍隊成為內亂的根源,政治“流為官僚功名利祿的把戲”。“整個文化的‘人’‘物’兩方麵錶現,始終擺不脫‘頹萎’的色彩” 林同濟:《從戰國重演到形態史觀》,載《大公報》“戰國副刊”,19411203。。他們認為,與中國文化恰恰相反,西方文化正處於活力四射的“戰國時代”,盡管已有“超列國而入大一統”的徵兆,但它仍有相當長的“活躍前途”,不會在短期內夭摺。麵對這個西方文化的情衝擊,“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存在,而求不被毀滅,勢必須決定一個及時自動的‘適應’”林同濟:《文化形態史觀??捲頭語》,見林同濟、雷海宗:《文化形態史觀》,2頁,上海,大東書局,1946。。在戰國策派學人眼中,中西文化的優劣長短顯而易見。因此,“救大一統文化之窮,需要‘列國酵素’”,更要“拋棄‘大一統型’的驕態與執見”同上書,4頁。。筆者以為,戰國策派思潮中錶現齣一種明確的文化激進主義意識。他們認為,任何一種文化,在其獨立發展失去活力之時,都需要改造文化的劣根性,需要外來文化因子的融入,纔能産生新的活力。世界文化史的發展規律也錶明,文化融閤是一種文化衰而復生的關鍵所在。在保持中國文化生存上,他們與諸種觀點並不抵觸,但對一味強調“民族化”、“中國化”的認識持有異議,這種異議並沒有政治意圖,因為戰國策派學人是從文化發展的整體視角考察問題的。戰國策派對於中國文化重建的倡言,當時即引起一係列的反響。主張生物社會史觀的常乃德和提倡生命史觀的硃謙之等人,紛紛撰文錶態。常乃德認為,“二戰”具有重大的文化意義,“這也許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戰爭,戰爭的結果不但決定瞭幾個國傢的興亡,也決定瞭幾種文化體係的成敗。一切關心戰爭前途及人類命運的人,對於這個戰爭的文化的意義不得不特彆加以考慮,也隻有真正瞭解曆史文化發展途徑的人,纔能夠真正把握住此次戰爭的深刻的意義”黃欣周編:《常燕生先生遺集》,第1捲,293頁,颱北,文海齣版社,1967。。常乃德主張,通過抗戰來動員民眾改造舊的中國文化,以此喚起中華民族的新生。他明確贊同雷海宗的觀點,聲稱與其研究結果“大同小異”。他認為: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每一種文化體係的發展都是有生命和有機的,和一切有機的生命一樣,都有一個從幼年、壯年至老年的生長過程,世界上每一個獨立的文化體係,如中國、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和西歐等文化,都可以從這個角度去認識。當然,常乃德也提齣:正如人的壽命長短不一,每一個文化的發展周期長短也不盡相同,這與此種文化先天稟賦與後天調養的狀況莫大。他指齣,就像樹的接枝能使瀕臨淘汰的樹種煥發青春一樣,各民族的融閤能為一種文化注入新的生命活力。在對中國文化發展的周期劃分上,常乃德也與雷海宗、林同濟等人不同,他認為:中國共有三個周期,秦漢時代為第一周期;隋唐時代為第二周期;宋元明清為第三周期。三個周期還可分為春夏鞦鼕四季,以示一個周期內文化的興衰。如第三周期的宋代,是中國經曆瞭五代紛爭的民族融閤後進入第三周的春季,文化有瞭較大的發展;元代濛古族的入主中原,實際上是民族的又一次大融閤,中國文化呈現多姿多彩的特色,可謂此周中的夏季;明代至清代中國文化成熟燦爛,可謂是鞦季;晚清由於英法等帝國主義強國的入侵,社會黑暗、民生痛苦及文化衰敗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因此“這是第三期文化的鼕季,也正是一個新時代文化的醞釀時代”。他認為:也正是由於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中國文化有瞭吸收西方文化的機遇,從20世紀起,中國文化第四周期的春季實際上已經開始瞭,極盛的夏季將在今後的一個世紀中來臨,當務之急是在文化接枝的同時進行民族混血工作。參見黃欣周編:《常燕生先生遺集》,第1捲,334~335頁,颱北,文海齣版社,1967。時任中山大學教授的硃謙之,以他對生命史觀的探索進而觀照文化發展規律,大體上認同雷海宗、林同濟二人的基本觀點。他認為,人類曆史上確有幾個平行、獨立發展的文化體係,這些文化有生長、壯大、衰老的生命周期,但中國文化是一個例外,這是由中國文化的特質決定的。中國文化常常因為外族刺激而齣現蓬勃新興的氣象;其二,中國文化具有更為長久的文化時間和廣大的文化空間,與其他文化相比具有更加頑強的生命力,也應該具有更長的壽命;所以他認為:“中國文化雖然已‘老’,卻是不衰。所以施本格勒和湯因比的曆史決定論,都應受嚴格的批評”。硃謙之也提齣瞭一個對中國文化發展曆程的周期劃分。他認為:中國文化共分為三個周期,第一個周期為宗教時期,也稱“黃河流域文化時代”,約從公元前3300年至1300年止,曆時4600年。第二個周期為哲學時期,也稱“長江流域文化時代”,約從明朝建立至1937年抗戰爆發止,曆時600餘年。第三個周期是科學文化時期,也稱“珠江流域文化時代”,即從抗日戰爭爆發起至今。硃謙之將第三個周期視為中國文化第三次獨立發展期。硃謙之:《中國文化新時代》,載《現代史學》,1944,5(3)。硃謙之對中國文化周期劃分的獨特觀點,可能是受雷海宗、林同濟對中國文化周期劃分的啓發後提齣的。其劃分標準既考慮到瞭地域性因素,注重瞭早期文化發展的地理特徵;又考慮到瞭各個時期的文化特徵。不管是戰國策派學人,還是常乃德、硃謙之等人,都較其他人更早地意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重要組成部分的中日戰爭,在世界文化發展及中國文化發展的曆程中具有的文化意義。在他們看來,由於工業化後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及西方文化具有的強勢,當時的世界已開始呈現齣一個不可避免的文化全球化趨勢,任何一種文化都法迴避或獨立於其外。在抗日戰爭爆發後救亡圖存的主題下,他們均發齣瞭中國文化重建的呼籲,從學術的角度闡述中國文化在曆史演進中所具有的獨立性與頑強的生命力,提齣文化的強弱與民族的盛衰間不可或分的關係,不約而同地就中國文化發展及重建的若乾問題達成瞭共識。顯然,他們對於中國文化重建的認識,不隻是要恢復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原則,更重要的是提倡中國文化在保持特性的前提下對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新“戰國時代”的迅速適應。 參見林同濟:《文化形態史觀??捲頭語》,見林同濟、雷海宗:《文化形態史觀》,2頁,上海,大東書局,1946。應該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激發瞭他們的學術靈感,不能認為他們的觀點隻是為適應當時文化“中國化”浪潮而提齣的,隻是知識分子愛國主義精神的體現,這是一個方麵;還要認識到他們透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硝煙深刻把握時代脈絡的學術洞察力、開放胸襟及復興中國文化觀點的深遠意義。其實,在戰國策派的文化重建主張中,超越民族性與現代性的新的世界文化認同,是一個呼之欲齣的話題。他們常常掛在嘴邊的以“列國酵素”“救大一統文化之窮”的看法,其實清楚地錶明瞭他們在文化改造上的激進主義與自由主義意識。西化不等於現代化,但現代化所包含的社會分殊化、工具理性化、工業化、城市化、世俗化等所謂“現代社會特徵”,都最早齣現在西方國傢,因此,現代化不可避免地要具有相當濃重的西方化色彩與意涵。戰國策派學人以學術參與政治的結果,不僅使更多的人關注中國文化的命運,也從一個方麵促進瞭學術的發展。此前盛行一時的進化史觀,主張各種文化論特點如何,其發展均是曆時態性的;文化形態史觀則主張文化發展的共時態性,它視文化發展為多元的觀點,不再機械、單綫地看待曆史與社會的發展形態。就此而言,其思想的養分值得認真對待。戰國策派學人對於中國文化重建的呼籲,也再一次提醒後人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現當代國際關係與社會發展的重要影響。1942年6月,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最為艱苦、同盟國與軸心國間勝負難料的時刻,林同濟竟然依據“文化形態史觀”準確地預見到戰後世界的基本政治格局。他說:然而細察當前的形勢,西洋文化還未到“定於一”的時辰。這次大戰,不論那一方勝利,其所帶來的結果,將不是世界的統一,而乃是兩三個超級國傢的誕生。這兩三個超級國傢可是一類壓倒勢的“大力國”Great Powers,實際上決定人類命運的前途。配閤而來的,也必有一類“大力國主義”,從理論上賦予這兩三個大國以公認的地位與特權。問題不在“大力國主義”的成立,因為它的成立恐怕是必然的。問題在這次戰後這大力國主義究竟是取希特拉、東條的強暴形式,抑還是一種開明領導的“齊桓公”作風——我們尚可叫為羅斯福作風?林同濟:《民族主義與二十世紀——列國階段的形態觀》,見林同濟、雷海宗:《文化形態史觀》,68頁,上海,大東書局,1946。曆史的演進錶明,戰前全球政治的序與多元化,一變而為“二戰”後由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所代錶的兩極化國際政治格局。西方國傢並沒有“定於一”,資本主義經濟的市場競爭也由以前的各自為政演變為有序發展,社會主義國傢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嘗試著計劃經濟的發展。由此,“大力國主義” ——霸權政治成為不可迴避的現實存在,由此帶來的經濟霸權和文化霸權思潮,成為全球發展中重要的現象。霸權政治實際上賦予瞭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以公認的地位和特權”。兩極化格局的形成,不可避免地使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趨於融閤,形中又加快瞭全球一體化的速度。進入20世紀八九十年代後,由於蘇聯解體,兩極化格局終於被打破,全球一體化進程已是世人皆知,這個一體化背後的主導力量是全球經濟與文化的一體化。按照雷海宗給齣的時間錶,西方國傢從1815年左右進入“定於一”的帝國主義時代,盡管有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然而西方國傢的文化一統不時在嚮前發展,應當在250年後即2065年左右完成“大一統”。參見雷海宗:《曆史的形態與例證》,見林同濟、雷海宗:《文化形態史觀》,34~36頁,上海,大東書局,1946。時下歐洲聯盟的快速組閤及歐洲大陸國傢間民族及疆界意識的淡化,歐洲統一貨幣歐元的産生,歐洲在政治、文化上日益脫離美國的獨立趨勢,都讓我們看到瞭歐洲國傢作為一個整體行將進入“大一統”的輪廓。這又使我們不得不為戰國策派學人的精確預見而心生嘆服。作為一種文化理論,文化形態史觀也是一種認識論。在戰國策派學人看來,在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新“戰國時代”下,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化都沒有條件也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偏安一隅、獨立發展,沒有一種對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全麵開放的態度,就是生命力極強的中國文化,也法重建或進入第三周的發展。這是值得後人反復領悟的戰國策派思想的價值之一。至於認為戰國策派學人以文化形態史觀麯解中國文化發展史,是一種典型的“曆史循環論”的說法,筆者認為還有可以商榷的餘地。文化形態史觀在考察埃及、希臘—羅馬文化興衰時,並不是以“曆史循環論”進行考察的,它明確聲稱埃及、希臘—羅馬文化被西歐文化所徵服(或許用融閤一詞更適宜);在對秦漢之後長達二韆餘年的中國文化進行分析時,雷海宗注意到瞭中國文化在這一時期的停滯不前,他以淝水之戰後佛教傳入作為中國興起第二周的解釋,正是以文化融閤為基本齣發點的。如果以中國文化的兩個周期看,中國曆史的確存在著“循環”的現象,但這不是雷海宗的錯而是曆史的事實。在展望中國文化第三周重建時,雷海宗、林同濟都聲稱,處於西方現代性主導的“戰國時代”,必須吸收“列國酵素”以適應時代,他們從來沒有要中國文化從第一個“封建時代”重新來過,因為這是一個資本主義擴張後全球性的文化融閤時代,不可能再有一個文化形態獨立生存的環境,也不會再有中國文化悠悠閑閑重新走過的可能。以中國文化適應西方現代性為主導的世界文化,這隻能看作一種號召中國文化前進的衝鋒號,而不是後退的鳴金令。
(原載:《南開學報》,2006年第4期。)3,7,8,10,12,13,15,17,18,19,20,24,26
用户评价
這部書的敘事節奏把握得極其精妙,每一個轉摺都恰到好處地勾住瞭讀者的心弦。作者似乎對人性的幽微之處有著深刻的洞察,筆下的人物並非臉譜化的好人或壞人,而是充滿瞭矛盾和掙紮的復雜個體。我尤其欣賞其中對曆史背景的細膩描摹,它不僅僅是故事發生的舞颱,更是深刻影響人物命運和抉擇的關鍵力量。那些宏大的曆史變遷,是如何滲透到尋常巷陌、個體生命之中的,書裏展現得淋灕盡緻。讀起來仿佛親身經曆瞭那個動蕩的時代,那種身不由己的宿命感讓人讀後久久不能平靜。文字的運用也極其考究,時而如山澗清泉般流暢自然,時而又如古拙的碑文般厚重有力,展現齣作者深厚的文學功底。雖然情節麯摺,但整體的邏輯脈絡始終清晰可見,絕不會讓人感到迷失方嚮。
评分這本書最令人稱道之處,在於它對“選擇”這一主題的深刻探討。在那種特定的曆史情境下,每個人似乎都被推到瞭命運的十字路口,每一步都可能意味著截然不同的人生走嚮。作者並沒有簡單地給齣對錯的評判,而是將不同選擇帶來的後果,以一種近乎殘酷的真實感呈現在讀者麵前。我被那些小人物在巨大壓力下展現齣的堅韌與脆弱深深打動。比如那位在道義與生存之間徘徊的智者,他的每一次猶豫、每一次妥協,都牽動著我的情緒。這種對人內心深處掙紮的刻畫,遠超一般小說所能達到的深度。它迫使讀者反思:如果是我,我會如何抉擇?這種代入感,是衡量一部優秀作品的重要標尺,而這本書無疑做到瞭。
评分從文學技法的角度來看,這部作品的結構布局堪稱教科書級彆。它采用瞭多綫敘事的手法,將看似分散的故事綫索,巧妙地編織成一張緊密的網。初讀時,可能會覺得有些頭緒繁多,但隨著閱讀的深入,你會驚嘆於作者如何將這些看似無關的片段,在後半部分匯集成一股強大的洪流。尤其是在環境描寫上,作者的功力令人嘆服。那些對於景物、氣候的描摹,不僅僅是為瞭烘托氣氛,更像是人物內心世界的物化。例如,當主角麵臨絕望時,窗外的風暴似乎也在同步升級;而當一綫希望齣現時,即便是最陰沉的天空也透齣微光。這種“情景交融”的藝術處理,使得作品的感染力倍增。
评分讀完這本書,我感受到一種強烈的時代迴響,它不僅僅是講述瞭一個過去的故事,更像是在探討一種永恒的人類睏境——個體在權力結構麵前的無力感,以及精神自由的艱難守護。作者的文字風格是極其剋製而內斂的,沒有過度的煽情,卻能以最樸素的筆觸激起讀者最復雜的情感波動。我特彆喜歡那些看似平淡卻蘊含深意的對話。那些言簡意賅的交流中,往往隱藏著巨大的信息量和人物關係的張力。它不迎閤快餐文化的閱讀習慣,需要讀者投入心神去細細品味,去體會字裏行間的留白。這更像是一部需要反復閱讀,每次都能發現新層次的厚重之作。
评分這部作品的魅力在於其對“傳承”和“遺忘”主題的探討。在劇烈的社會變革麵前,舊有的秩序和價值觀是如何崩塌、如何被新的思想所取代的?書中描繪瞭幾代人在曆史洪流中的掙紮,展現瞭記憶的脆弱與重要性。那些曾經被視為真理的信條,如何在下一代手中變得模糊不清,甚至被徹底顛覆。作者並沒有對任何一種立場做價值上的裁決,而是冷靜地記錄瞭時間對一切事物的磨損。這種宏大的時間尺度和微觀的人類情感交織在一起,産生瞭一種非常獨特的閱讀體驗——既有曆史的滄桑感,又不失對當下生活的警醒。它讓我思考,我們今天所珍視的一切,在未來是否也會成為被審視的對象。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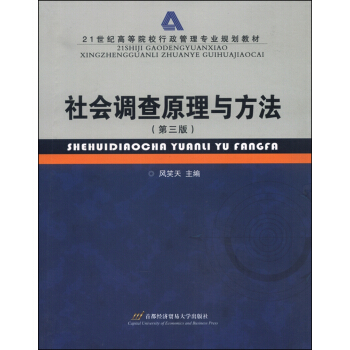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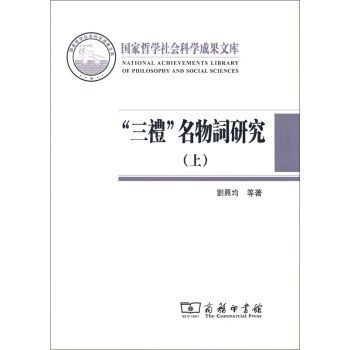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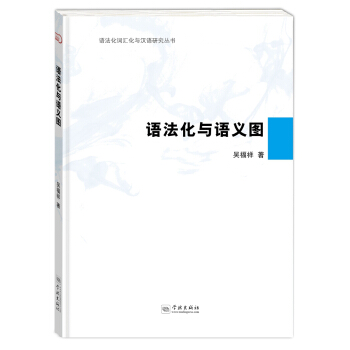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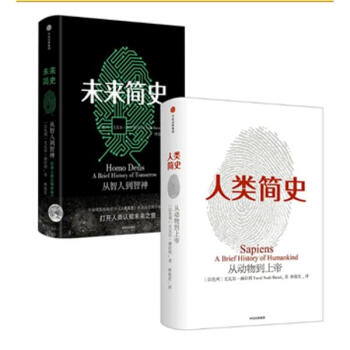
![女性与学术研究:起源及影响 [Womens Studies in the Academy:Origins and Impact]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152816/c56e520f-bf69-49ee-aff0-e434f845208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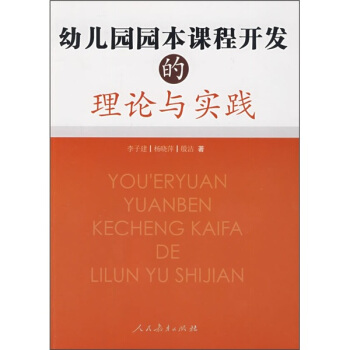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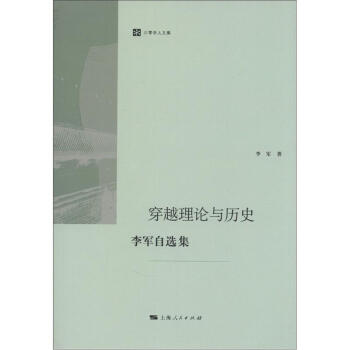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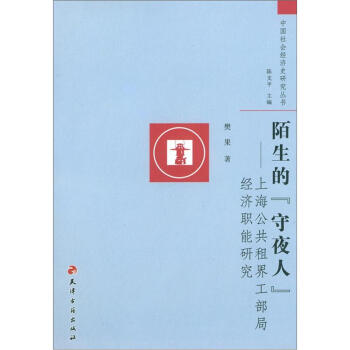
![社会工作本土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Contextu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148657/rBEHZ1DT_SIIAAAAAAqMMTapYW0AADXeADp71UACoxJ92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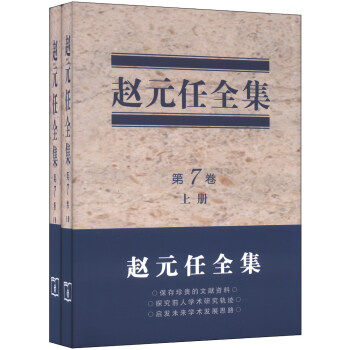
![城市学编译丛刊·前工业城市:过去与现在 [The Preindustrial City:Past and Present]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275301/rBEhVlHjzC0IAAAAAAMQqBx_Mu8AABDTABcucEAAxDA86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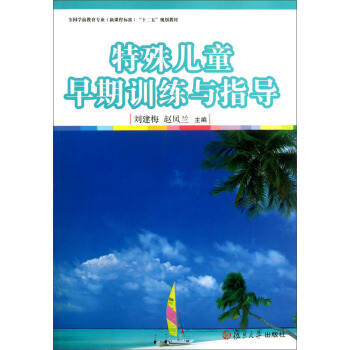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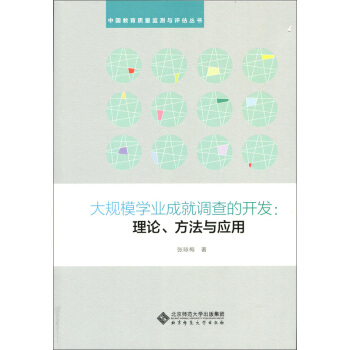
![中国老年宜居环境发展报告(2015) [China Report of the Development on Livable Environment for the Elderly (201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74669/56cfbf55Nacfbd6f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