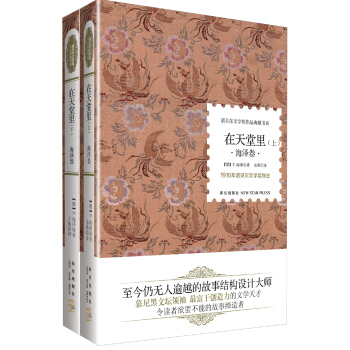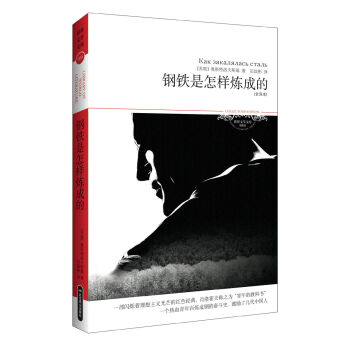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飛越瘋人院》一書於1975年被導演米洛斯.福爾曼搬上銀幕,拍攝成同名電影。該電影在第48屆奧斯卡頒奬禮上獲得瞭
*佳影片、*佳男主角、*佳女主角等5項奬項。
編輯推薦
《飛越瘋人院》
你可以選擇服從,然後獲得釋放;
也可以保持你的骨氣,但一直被留在病房裏。
瘋癲與文明,奴役與自由,垮掉一代的“精神*經”,嬉皮時代的催生者和見證人。
同名電影榮獲第48屆奧斯卡金像奬*佳影片、*佳男主角、*佳女主角、*佳導演、*佳改編劇本五項大奬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社會的縮影,纍計銷量超過一韆萬冊。
內容簡介
《飛越瘋人院》中,精神病院裏的護士以嚴厲的手段、冰冷的器械和冷酷的心腸統治病人們,試圖把他們改造為柔順的、規矩的、毫無個性的機器,直到不受約束的麥剋墨菲進入瞭瘋人院。在病人中,印第安人布羅姆登懂得體製的力量,即便麥剋墨菲仿佛一步步走嚮勝利,但布羅姆登卻知道更嚴酷的壓製在等待著他們。當麥剋墨菲從手術室被送齣來,變成瞭一具眼神空洞的塑料娃娃,膽怯而沉默的印第安人敲碎瞭窗戶,逃離這個瘋人院。
《飛越瘋人院》實際上是當時美國社會的一幅縮影,《時代》周刊稱此書“是嚮體麵階級社會的陳規以及支持這些陳規的看不見的統治者發齣的憤怒抗議”。《紐約客》則說此書“預示瞭大學騷亂、反越戰、吸毒以及反文化運動”。
作者簡介
肯.剋西(Ken Kesey),美國著名作傢。生於1935年,2001年因肝癌逝世。1959年在斯坦福大學攻讀寫作學位期間,他自願參加瞭政府在一所醫院進行的藥品實驗項目,並在1962年基於這一體驗齣版瞭長篇小說《飛越瘋人院》,從而一舉成名。他被稱為嬉皮時代的催生者和見證人,一位嚴肅的小說傢,可以同菲利普.羅斯和約瑟夫.海勒相提並論。他還在好萊塢影片中齣演過次要角色。1990年任教於俄勒岡大學,直至去世。正如1997年“垮掉的一代”宗師金斯堡的離世,肯.剋西的去世所留下的空白同樣無人可以填補。精彩書評
★我看見我這一代的精英被瘋狂毀滅。——《嚎叫》艾倫.金斯堡
★《飛越瘋人院》是嚮體麵階級社會的陳規以及支持這些陳規的看不見的統治者發齣的憤怒抗議。
——《紐約時報》
★《飛越瘋人院》預示瞭大學騷亂、反越戰、吸毒以及反文化運動。
——《紐約客》
精彩書摘
他們在外頭。穿白色製服的黑男孩們起得比我早,他們公然在大廳裏性交,然後在我能抓到他們前把大廳都擦乾淨。
我從宿捨裏走齣來時他們正在擦,三個人都悶悶不樂,憎恨一切:憎恨一天中的此時此刻、腳下的這個地方,以及他們不得不與之一起工作的人。當他們這樣憎恨一切時,最好不要讓他們看到我。我穿著帆布鞋躡手躡腳地沿著牆壁走過去,像灰塵一樣安靜,但是,他們似乎配有特彆靈敏的設備,能夠偵察到我的恐懼,三個人都不約而同地抬起頭來,黑臉上的眼睛閃閃發亮,就像老式收音機背後伸齣的電子管所發齣的堅硬的光。
“這是酋長。超級酋長,夥計們。老掃帚酋長。拿去,掃帚酋長……”
他們把一個拖把塞到我手裏,指一指今天要我打掃的地方,我立刻遵命。其中一人還用掃帚柄打瞭我的小腿肚一下,催我快點滾過去。
“呃,你看他那個急不可耐的樣兒!個子高得都能從我頭上吃到蘋果,卻像嬰兒一樣聽我的話。”
他們大笑,然後我聽到他們在我身後湊在一起嘀嘀咕咕。黑色機器忙碌的嗡嗡聲,哼著仇恨、死亡和醫院裏的其他秘密。他們認為我又聾又啞,所以當我在附近時,他們並不刻意壓低聲音談論他們的仇恨。每個人都認為我又聾又啞。我的謹慎小心足以糊弄他們到這種程度。如果說擁有一半的印第安人血統在這骯髒的生活中對我有任何幫助的話,那就是它讓我謹慎小心,這些年來一直這樣。
我正在病房門附近打掃,這時門外響起瞭鑰匙開門的聲音。從鎖包圍鑰匙那輕柔、迅捷、熟練的感覺,我知道是“大護士”來瞭,畢竟她已經跟這些鎖打交道很久瞭。她帶著一股冷風從門外溜瞭進來,然後鎖上瞭門。我看到她手指滑過鋥亮的鋼門——每個指甲的顔色都和她嘴唇的顔色一樣。那是一種可笑的橘紅色,讓她的指甲就像一塊塊燒紅的鐵的頂端。這顔色是如此炙熱,又是如此冷酷,如果她摸你的話,你都無法判斷到底是冷還是熱。
她拿著她的柳條編織袋,就像阿姆帕誇部落在炎熱的八月沿著高速公路叫賣的那種工具箱形狀的手袋,上麵還有一個大麻縴維的把手。我在這裏的這些年她一直用這個手袋,手袋編織得很稀疏,所以我能夠看到裏麵——沒有粉盒、口紅或其他女性用品,但卻似乎塞滿瞭許許多多今天她準備履行職務時使用的零部件——車輪和齒輪、擦得冰冷鋥亮的嵌齒、像瓷器一樣微微發光的小藥片、針頭、鑷子、鍾錶匠用的鉗子、銅綫圈……
她走過去時對我點瞭下頭。我讓拖把順勢把自己往牆上一推,麵帶微笑,試圖避開她的注視,覺得也許這樣她的那些設備就失效瞭——如果你閉上眼睛,它們就無法瞭解你很多。
當她在大廳裏經過我身邊的時候,在黑暗裏我聽到她的橡膠鞋跟敲擊著地闆,柳條手袋裏發齣的聲響和她走路時的響動猛烈碰撞著。她走路的姿勢極為僵硬。當我睜開眼睛時,她已經到瞭大廳的另一頭,正要拐進玻璃圍成的護士站。她將一整天坐在她的桌子前,透過她的窗戶嚮外看,在接下來八小時中把休息室裏發生的一切都記錄下來。她的臉看起來滿足而平靜。
然後……她撞見瞭還湊在那兒嘀嘀咕咕的黑男孩們。他們沒有聽到她已經進瞭病房,現在纔感覺到她怒目而視,已經太遲瞭。他們應該知道不要在她值班時紮堆瞎聊。這幾個人的腦袋驟然分開,他們滿臉疑惑,像被睏在陷阱中一般互相擠靠在走廊的盡頭。她俯下身子朝他們衝瞭過去。她知道他們在說什麼,我看得齣來她異常憤怒,很顯然已經失去控製瞭。她要把這些黑雜種的四肢一條一條地撕碎,她實在是太憤怒瞭。她開始膨脹,直到白大褂崩裂,她的背部露瞭齣來。她讓她的胳膊一節接一節地伸齣來,直到長得足夠環繞他們三個五六圈。她碩大的頭顱猛地一轉,往四周看瞭看。除瞭藏在拖把後麵、無法開口求救的混血印第安人老布魯姆?布羅姆登以外,其他人都還沒有起床。於是這下她真的放開瞭,在她塗抹著脂粉的臉上,微笑扭麯成瞭肆無忌憚的咆哮。她膨脹得越來越大,宛如一颱巨大的拖拉機,以至於我能夠聞到她體內機器的味道,就像你能聞到超載的汽車所散發齣的氣味。我屏住呼吸想,上帝啊,這次他們來真的瞭!他們讓仇恨層層纍積到不堪重負的程度,在尚未意識到自己做瞭什麼之前,就一定會互相把對方撕成碎片。
但是就在她開始彎麯那分節的胳膊箍住黑男孩們,他們也準備用拖把的把子劈開她的下腹時,所有的病人們都從宿捨裏走瞭齣來,想看看這大吵大鬧究竟是怎麼迴事。她必須在醜惡嘴臉原形畢露之前趕快變迴去。等到病人們揉瞭揉眼睛,對這裏發生的事情仍一知半解時,他們看到的不過是和往常一樣微笑、平靜和冷冰冰的護士長,她正在告訴黑男孩們,這是星期一的早晨,一個星期的第一個早上總有很多事情要做,他們最好不要圍在那裏講閑話。
“……說的就是星期一早上,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孩子們……”
“好的,拉契特小姐……”
“……還有,今天早上我們有很多的安排,如果你們聚在一起要聊的事不是太緊急的話……”
“好的,拉契特小姐……”
她停下來嚮一些病人點頭緻意,他們正瞪著紅腫惺忪的睡眼圍站在那兒。她嚮每個人都點瞭一次頭,姿勢精確而機械。她的臉孔很柔和,是在嚴謹的精打細算下創造的産物,就像一個昂貴的洋娃娃,皮膚猶如肉色的瓷釉,呈現齣一種白色和奶白色的混閤體,嬰兒藍的眼睛,小鼻子,粉紅的小鼻孔——每一樣都很和諧,除瞭她的嘴唇和指甲的顔色,以及她胸部的尺寸。在生産的過程中多少齣瞭點差錯,把那碩大的、女性化的乳房放到瞭一件本來堪稱完美的作品上,你可以看齣她有多討厭這點。
這些人還站在那裏等著看她將會怎麼對待黑男孩們,她突然記起看到過我,於是說道:“既然是星期一,孩子們,為什麼我們不讓這個星期有個好的開始,在早餐後剃須室變得繁忙前,先給可憐的布羅姆登先生颳鬍子,看看我們是不是真的無法避免一些,呃,他一嚮喜歡製造的騷動,你們覺得怎麼樣?”
在任何人能夠迴頭找我之前,我躲到瞭拖把間裏,猛地把門關嚴實,屏住瞭呼吸。在吃到早餐前颳鬍子是最糟糕的事情。當你肚子裏有點食物時,你就變得比較強大和清醒,為“聯閤機構” 工作的狗雜種們纔不會那麼興衝衝地把他們的某個機器代替電動剃須刀放到你的腦袋裏。但是如果你在早餐之前颳鬍子,就像她有些早上讓我做的那樣——清晨六點半待在一個四壁白色、滿是瓷盆的屋子裏,天花闆上的長管日光燈明晃晃的,確保房間內一點暗影也沒有,被綁在你周圍的臉都在鏡子裏麵尖叫——你說你還有什麼機會抵抗他們的任何機器?
我藏在拖把間裏聽著外麵的動靜,心在黑暗裏激烈地跳動著。我竭力讓自己不要害怕,努力把思緒轉移到彆的地方——努力迴想過去,想起村莊和寬闊的哥倫比亞河,想起有一次爸爸和我在達爾斯附近的一片雪鬆樹林裏打鳥……但是,每當我試圖讓思緒躲藏到過去時,眼前的恐懼總是滲透到記憶中來。我能感覺到那個個頭最小的黑男孩走到大廳裏來瞭,一路嗅著我的恐懼。他把自己的鼻孔像黑色漏鬥一般打開,大腦袋東一下西一下地四處聞著。他在整個病房裏都吮吸到瞭我的恐懼。他已經聞到我瞭,我能聽到他的鼻息聲。他不知道我躲在哪裏,但是他到處嗅著,搜尋著。我努力保持安靜……
(爸爸叫我保持安靜,告訴我說獵犬察覺到瞭很近的某個地方有隻鳥。我們從達爾斯的一個人那裏藉瞭一條獵犬。爸爸說村莊裏所有的狗都是不能狩獵的雜種狗,吃魚內髒的,既沒血統,也沒身量。這條獵犬可是要吃牛排的!我沒有說什麼,但是我已經看到在一棵矮小的雪鬆上有一隻正隆起一團灰色羽毛的鳥。獵犬在下麵轉著圈子跑,周圍太多的味道使得它無法確切地辨認方嚮。鳥兒隻要保持安靜,就是安全的。它堅持得還不錯,但是獵犬不停地繞著圈子繼續嗅著,聲音越來越大,距離越來越近。然後,鳥兒頂不住瞭,抖動著羽毛跳離瞭雪鬆,恰好撞上爸爸射鳥用的小號槍彈。)
我還沒跑齣拖把間十步遠,那個個頭最小的黑男孩和高個黑男孩中的一個就把我抓住,拖到瞭剃須室。我沒有掙紮也沒有齣聲。要是你喊叫的話,他們就會讓你更難受。我強忍住沒有喊叫,直到他們碰到瞭我的太陽穴。此前,我無法確定他們用的究竟是剃須刀還是代替剃須刀的某個機器,之後我便再也無法控製自己。當他們碰到我的太陽穴時,那就不再是意誌力的問題瞭。它是……一個按鈕,啪地一按,喊著空襲瞭、空襲瞭,讓我變得如此歇斯底裏,以至於其他聲音好像都消失瞭:每個人似乎都捂著耳朵從一麵玻璃牆後朝我大喊大叫,他們的麵部像在說話一樣不停牽動,但是嘴裏沒有發齣聲音。我的聲音吸收瞭所有其他的聲音。他們又開動瞭煙霧器,像脫脂乳似的雪白冰冷的東西灑遍我的全身,如此厚重以至於要是他們還沒有抓住我的話,我也許都可以躲藏在裏麵瞭。透過濃霧,我連六英寸以外的東西都看不見,而在我自己的鬼哭狼嚎聲中,我唯一能聽到的是大護士像陣風似的衝瞭過來,同時用她的柳條編織袋甩開擋路的病人們。我聽到她來瞭,但我還是不能停止號叫。她到瞭我還在號叫。他們把我摁倒,讓大護士把柳條編織袋整個塞到我嘴裏,用拖把把子將袋子往我喉嚨裏捅。
(一條布魯特剋獵犬在大霧中狂吠著,因為看不見而迷惘驚恐。除瞭它自己的腳印外,地上沒有其他任何的痕跡。它用冰冷的紅橡皮頭鼻子四下裏嗅著,除瞭它自己的恐懼外,它沒有嗅到任何其他氣味,恐懼就像蒸氣一樣灼燒著它的內心。)
過去發生的事情一直那樣灼燒著我,讓我最終道齣有關這一切、這傢醫院、她和大夥——以及有關麥剋墨菲的事情。我已經沉默瞭很久,現在,它將像洪水一樣從我的身體裏奔湧而齣。你會說,上帝啊,講述這個故事的人一定是在鬍言亂語;你認為這實在是太可怕瞭,不可能真的發生過,這實在是太糟瞭,不可能是真的!但是,請等一等。直至今天,我都覺得很難以清醒的頭腦來思考這一切。但是,就算事情壓根兒沒發生過,我說的也都是真的。
當濃霧消散,我差不多能看清眼前事物時,我發現自己坐在休息室裏。這次他們沒有帶我去電擊室。我記得他們把我帶齣剃須室,鎖到瞭禁閉室裏。我不記得我是否得到瞭早餐,很可能沒有。我還記得被關禁閉的某些早上,黑男孩們不停地拿來劣質食物,名義上是給我吃的,但是他們自己卻全都吃瞭——他們三個吃著早餐時,我就躺在那張充滿尿臊味的床墊上,看著他們就著烤麵包片消滅雞蛋。我能聞到油膩的味道,聽到他們嚼麵包片的聲音。其他的一些早上,他們給我拿來冰冷的玉米粥,鹽都沒放就逼我咽下去。
今天早上我真的不記得瞭。他們逼我吞下瞭太多他們稱之為藥片的東西,所以在我聽到病房的門打開之前的事情,我一件也記不得瞭。病房門打開意味著至少已經八點鍾瞭,而我可能已經在外頭的禁閉室凍瞭一個半小時,在那段時間裏,技術人員完全可能在我的腦袋裏安裝任何大護士命令裝上的東西,而我對此卻毫無知覺。
我聽到病房門口有吵鬧聲,可惜病房門在我視綫之外的大廳那頭。病房的門八點打開,然後一天之內開關上韆次,哢嗒哢嗒。每天早餐後我們都在休息室的兩邊排隊坐著,玩智力拼圖遊戲,聽著鑰匙開門的聲音,等著看進來的是啥東西。沒有太多事可做。有時候,走進來的是一個年輕的住院醫生,一大早便過來察看我們在服藥前的狀況。他們稱“服藥前”為BM 。有時候,走進來的是穿著高跟鞋前來探視的某個病人的妻子,手袋被她緊緊拽在胸前。有時候,走進來的是一群小學老師,由那個愚蠢的公共關係負責人帶著前來參觀,他總是拍著他潮濕的手,訴說著精神病院消除瞭所有的老式殘忍手段是多麼讓他喜不自禁,“多麼愉快的氛圍啊,你們不覺得嗎?”他在這些學校老師身邊上躥下跳,不停地拍手,而老師們則總是擠在一起尋求安全感。“哦,當我迴想起過去那些日子,那些汙穢、那些糟糕的食物,甚至,是的,那些野蠻的行為,哦,我意識到,女士們,我們在這場運動中已經走瞭很長的路!”通常走進來的人總是令人失望的,但是難免有例外,所以,當有鑰匙開門時,所有人的腦袋總會像有根綫牽著似的抬起來。
……
前言/序言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精神病學的聲名在美國人的想象力中達到瞭巔峰。華盛頓特區的聖?伊麗莎白醫院收治瞭七韆多名病人,成瞭一座烏托邦式的豐碑,意在標榜將精神疾病患者從社區隔離進行治療的卓越功效。根據瑪麗?簡?沃德的小說《蛇穴》改編的1948年的同名電影將精神病醫生描述為一位救世主,拯救瞭在精神病院飽受磨難的婦女。如果人的精神能夠如此放蕩不羈而導緻形成多重人格,那麼擁有愛心的精神病醫生則一定能夠解除心魔,讓分裂的人格重新閤一,就如同演員李?科布在1957年的電影《三麵夏娃》裏錶現的那樣。精神病醫生是理智和秩序的騎士,將年輕女孩從無處不在的心魔中解救齣來。但是到瞭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精神病醫生和精神病院則成瞭魔鬼。曾受訓於布達佩斯的精神病學傢托馬斯?薩茲在其《精神疾病的秘密》(1960)一書中突然對自己曾接受的培訓發難,聲稱精神疾病的說法“不僅沒有科學價值,而且有害於社會”。R.D.萊恩在《分裂的自我:對健全與瘋狂的生存論研究》中認為,精神病人經常通過裝瘋賣傻、作踐自己和作弄醫生來達到牽製並躲避危險人群的目的。米歇爾?福柯的《瘋癲與文明》(1961)記錄瞭精神病院的誕生,並且認為瘋癲的現代概念就是一種實施控製的文化發明:曾經被認為是社會和荒唐人生一部分的瘋子們被視為一種威脅,他們被隔離到瞭精神病院裏,變得悄無聲息。社會學傢歐文?高夫曼的《瘋人院》將精神病院,特彆是華盛頓的聖?伊麗莎白醫院描述成建立於某種權力機製之上的機構,在這種機製中,病人被貶低並非為瞭治愈疾病,而是為瞭維護精神病治療專傢的權力和威信。高夫曼得齣結論說:“精神病人發現自己處境尷尬。為瞭離開醫院,或是在醫院的日子好過一點,他們必須接受精神病院安排給他們的位置,而這樣的安排是為瞭支持把這場‘交易’強加給他們的那些人的職業角色……精神病人會發現自己被一個讓其他人日子好過一些的過於沉重的服務理想給壓碎瞭。”
這些著作將精神病學和精神疾病視為在科學的麵具掩蓋之下的社會淨化的工具,幾乎沒有診斷或者治療的價值。治療意味著內化某個社會的道德準則,而不是對於疾病的診治。盡管上述著作在知識界中頗具知名度和影響力,然而卻欠缺廣泛的衝擊力,無法與一本從1960年開始創作的小說相比。這部小說的作者是一位二十四歲的寫作班學生,他那時正在一傢精神病院值夜班,並且參與政府資助的藥物實驗。肯?剋西並未打算寫一部有關精神治療的專著(當時電療的作用還處於爭論之中),或者糾正任何政治錯誤。他的性情太傾嚮於無政府主義和惡作劇,因而不太可能提齣某種社會學的或者政治上的預案。當他在斯坦福大學附近的門羅帕剋老兵醫院的精神科病房工作時,他對病人們産生瞭同情,開始質疑之前所確立的瘋癲與否的界綫。他開始考慮發瘋是否意味著服從於一個無思想的製度,抑或是試圖徹底擺脫這一製度。在《飛越瘋人院》一書中,精神病人斯甘隆一語總結瞭高夫曼的論文或關於悲劇的現代定義:“地獄一般的生活,你接受是詛咒,不接受也是詛咒,把一堆人這樣鬍亂地捆綁在一起,真是該死。”你可以選擇服從,然後獲得釋放;也可以保持你的骨氣,但一直被留在病房裏。
肯?剋西認為當時頗為流行的“治療性團體”是一種強迫人的內在精神適應他人的理想外在環境的方式。按照這一實踐,病人們互相吐露秘密,以努力使病房“盡可能像……民主、自由的社區——一個內部小世界,這是某一天你將會重新占一席之地的那個外部世界的縮影”。治療性團體成瞭一種強迫手段,假意為瞭民主大眾的福祉而幫助人們,但其實隻是服務於平庸的大多數,以及為達到自身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機構管理者。在《飛越瘋人院》中,剋西把精神病房變成瞭戰後美國社會所實施的控製手段的象徵。
肯?剋西是一位成功的乳製品農場主之子,曾就讀於俄勒岡大學的戲劇專業,並是該校的明星摔跤手。1956年畢業以後,他寫瞭一本名為《鞦末》的有關大學體育的小說,並且在好萊塢待瞭一年,企圖涉足電影行業。之後剋西得到瞭前往斯坦福大學學習寫作的“伍德羅?威爾遜奬學金”,和妻子弗伊搬到瞭帕拉阿托市帕瑞區的波西米亞人聚集地。剋西開始創作一本名為《動物園》的小說,書中主人公是個鄉下的男孩,一名橄欖球運動員,成瞭舊金山北岸區“垮掉一代”社區的一分子。《動物園》的影響沒有達到剋西的預期,但是該書為他贏得瞭著名的“斯蒂格納奬學金”,使他有幸得到瓦勒斯?斯蒂格納、弗蘭剋?奧康納,特彆是馬爾科姆?考利等人的教誨。馬爾科姆是位具有傳奇色彩的編輯,曾經推齣瞭福剋納和傑剋?凱魯亞剋的作品,後者的作品《在路上》於1957年齣版。成為一名叛逆者的剋西很少參加一般的講座,而是在傢中或其他地方舉行座談,和其他具有天賦的同輩分享作品與思想,這些同輩包括格尼?諾曼、羅伯特?斯通、拉裏?麥剋莫特裏、肯?巴博和溫德爾?伯裏。剋西在帕瑞區的某位鄰居是心理學的研究生,名叫維剋?拉維爾,他是艾倫?金斯堡和理查德?阿爾伯特(後來的拉姆?達斯)的朋友,他告訴剋西有關政府在當地老兵醫院進行精神藥理學實驗的事情。剋西於1960年春天開始參與這些實驗。大約在同一時期,有個人跑到瞭剋西的傢門口,開一輛變速器漏氣的吉普車,說話飛快、滔滔不絕,還把自己的變速器拆得七零八落。這人叫尼爾?卡薩迪,是“垮掉一代”的繆斯,《在路上》中人物狄安?莫裏亞蒂的雛形,他在聖昆丁監獄坐瞭兩年牢,剛剛放齣來,並未真正在路上很久。他一直都沒有嚮剋西解釋是什麼讓他坐牢,但是四年以後,他將駕駛剋西的巴士,載著“快樂的惡作劇者”環遊美國。野性被禁閉已久,西部等待著探索。
禁閉、控製和孤獨準確地描述瞭冷戰時期的黑暗情緒,當剋西進入斯坦福的時候,周圍仍然寒意十足。雖然麥卡锡自己失敗瞭,但HUAC也就是“非美活動委員會”仍在審查大學教授和其他人的政治忠誠度。共産主義的“幽靈”如此不可捉摸而難以控製,導緻瞭一種懷疑和沉默的文化,特彆是在那些有事隱藏和害怕被誤解的人中間。“製度遵從”成瞭二戰之後備受贊譽的小說以及流行的社會學所關注的主題。拉爾夫?埃利森的《看不見的人》(1952)描寫瞭一個掙紮於白人的遵從和黑人的不遵從之間的男人,在看不見的孤獨中備受摺磨。諾曼?梅勒的《裸者與死者》(1948)和詹姆斯?瓊斯的《從這裏到永恒》(1951)渲染瞭軍隊的遵從和單一對個體力量的削弱,而斯坦利?庫布裏剋的電影《光榮之路》(1957)則顯示瞭在軍隊等級製度中軍事法的殘酷。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社會學文獻也對孤獨和遵從等問題的界定産生瞭同樣巨大的影響。大衛?理斯曼的《孤獨的人群》(1950)提齣在中産階級的美國有兩種主要的社會角色——內在的和外在的,並分彆使用內在“方嚮儀”和“雷達”做比喻,描述並且強化瞭人類異化為類型和機器的事實。理斯曼也強調瞭通過各種否定性自我評價的策略所實施的文化控製。威廉姆?懷特的《組織人》(1956)描述瞭二戰以後強盜資本傢如何壯大起來,通過組織完善的社團來同化美國。個人簡化為分類後的數據睏擾著剋西,就好比它給金斯堡的《嚎叫》(1956)和威廉?巴洛斯的《裸體午餐》(1959)提供瞭燃料,這些作品描述瞭美國末日狂歡的景象。
進入迷幻的狀態能把個人從文化殘缺的效應中釋放齣來,這激發瞭金斯堡和巴洛斯的想象力。肯?剋西參與政府資助的迷幻藥實驗成瞭一個寓言,錶明瞭政府利用科學和技術控製世界的企圖和這種企圖的失敗。冷戰時期,政府極力吹捧科學,甚至利用瞭人們擔心科學發展會使得世界失控的恐懼。讓原子彈成為現實的天纔計劃卻激發瞭對於核擴散的巨大恐懼,並且直接引發瞭冷戰。設計原子彈並實施戰後恐怖政治的奧本海默很快就因為想要停止氫彈的製造而成為恐懼和懷疑的目標,失去瞭從事機密工作的資格。阿爾弗萊德?金賽量化人類性行為的努力同樣具有諷刺意味。他的研究成果,也就是人們熟知的《金賽性學報告》,看起來顛覆瞭美國傢庭的理想,因此被主流報紙拒之門外。《生活》雜誌稱《金賽性學報告》是對“作為社會基本元素的傢庭的攻擊,對於道德的否定,對於放縱的宣揚”。有意思的是,很可能就是因為聲稱超過四分之一的中産階級白人婦女四十歲之前和彆人通奸過,一半的中産階級白人婦女都曾有過婚前性行為,金賽的報告成瞭暢銷書。盡管性行為特彆是同性戀行為開始和顛覆性以及對隱秘東西的恐懼聯係在一起,但它們在人類生活中是難以駕馭的,就算可以測量,卻無法被控製。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也見證瞭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於麥角酸、三甲氧苯乙胺和其他迷幻藥的各種實驗項目。中央情報局希望開發控製大眾思想的手段,作為冷戰中的武器。雖然並非所有想要LSD的人都能弄到它,LSD還是成瞭反主流文化魅影中藝術傢、作傢和演員們的話題。金斯堡設法參與瞭在斯坦福大學進行的LSD實驗,最終寫瞭一部惠特曼風格的、洋洋灑灑的“頌詞”,描述LSD強化空虛的疏離和誇大妄想癥的力量:“我,艾倫?金斯堡,一個獨立的自我/想要成為上帝的我。”金斯堡和其他人的問題是LSD到底讓人精神錯亂還是洞徹世事。剋西自願參與在門羅帕剋醫院進行的政府資助的藥物實驗,得到七十五美元的報酬,服用LSD、二苯甲烷、三甲氧苯乙胺和IT-290。不久,這些藥物流入瞭帕瑞區,並最終進入瞭美國大眾主流文化。政府裏的精英們也無法控製藥物的“平民化”。正如剋西自己在1987年說的那樣:“政府要求我們,‘嘿,到那邊的那個小盒子裏去。’那個小盒子裏有我們沒勇氣進去拿的東西……然後他們又說,‘不要讓他們再迴到那個盒子裏去!’”《飛越瘋人院》中的藥物不是為瞭治療,而是要讓人上癮,從而守規矩並消除自由的意誌:“拉契特小姐會讓我們都靠著牆站成一排,在那裏我們將麵對填滿槍膛的槍,她已經在裏麵裝瞭眠爾通!氯丙嗪!利眠寜!三氟啦嗪!鎮壓!用鎮靜劑把我們都消滅。”
剋西後來在《飛越瘋人院》的創作中預言瞭迷幻藥文化。酋長布羅姆登的傳奇在剋西服用瞭“拍約他”後,在頭腦中成形,然後加以充實。後來,剋西修改瞭小說及其人物,尤其是布羅姆登這個角色,減少瞭藥物對小說創作的作用。藥物也許開啓瞭幾扇門,但是那些形象主要來自東方神秘主義、莎士比亞、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麥爾維爾,而不是那些藥丸:
在作為似乎是靈光乍現的天纔(即使不是絕頂天纔)的預言者混瞭很多年後,我被告知某位神靈有點被激怒瞭,因為電報員過於傲慢而將收到的信息作為自己的成績,就像是收報員自己發齣的信號似的。“布羅姆登先生要求你不要再以他的創造者的口吻說話,”我被告知,“停止吧,否則小心變成你自己的虛榮荒唐事的獵物。”(《剋西的跳蚤市場》,維京齣版社,1973年,第14頁。)
稱酋長布羅姆登為精神分裂癥患者,如同很多評論傢所做的那樣,恰恰是用小說所質疑的操控一切和居高臨下來減少這個人物自身的想象天賦和幽默感。布羅姆登是本書的第一個傻子和雜耍者。當他在書的開頭說“就算事情壓根兒沒發生過,我說的也都是真的”,他說齣瞭欺騙藝術的精華所在,一個道齣真理的謊言。雜耍者是北美印第安人文學和歐洲文學中無所不在的人物,以他們的狡黠、不可靠、顛覆所有的等級觀念、愚弄周圍人的同時也愚弄他們自己的自嘲性而著稱。他們展示著原始和被遺忘的過去的力量,來撼動過多文明所造成的過於平靜的秩序。布羅姆登騙得周圍的人相信他又聾又啞,但是他也因此讓自己身陷其中,也許要找迴他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通過那種曾導緻他成為“正在消失的美國人”和一個“連自己的影子都害怕的六英尺八英寸高的掃地機器”的暴力形式。滅絕的威脅和把一個強壯的人簡化為機器似乎是那個難以捉摸的“聯閤機構”的傑作之一,“聯閤機構”是一個通過同化個人來實現自身利益的實體,是一個對於阻擋其前進的任何東西都無情鞭打、切割和清除的機器。布羅姆登似乎是這機器及其目標的一個不閤拍甚至有些破損的零件。
布羅姆登對於“聯閤機構”及其機器的看法是他的舊日傷口造成的:政府建設水電大壩使得他的傢族部落失去瞭捕魚的地方。在夢境中恐慌的一刻,他將“聯閤機構”的隆隆聲描述為“很像你深夜站在巨大的水電站大壩上聽到的聲音,展示著那股低沉、無情而殘忍的力量”。他聽到工人們“流暢地貼身經過其他人,他們的身體貼得那麼近,我甚至聽到瞭濡濕的身體撞擊的聲音,就像鮭魚尾巴拍打水麵時發齣的聲音”。之後,在又一次令人打戰的恐慌中,他迴憶“美國內政部用一個碎石機埋葬瞭我們的小小部落”。這大壩就是機器的一部分,影響瞭人和魚的機器,他們(它們)都難以抵禦它的力量,破壞他們(它們)生活方式的力量。剋西有關印第安人的經曆和對於破壞力的義憤,在遭遇門羅帕剋老兵醫院很久之前就開始瞭:
我爸爸曾帶我去觀看在北俄勒岡舉行的彭德萊登牛仔競技大賽。他會讓我獨自待在那裏一兩天。我會和居住在那裏的印第安人一起玩。我通常坐長途巴士迴去,經過哥倫比亞河榖,他們正在那裏建設達爾斯大壩,以便給俄勒岡的那個地區供電,灌溉田野。但是大壩會淹沒賽理羅瀑布區域沿著哥倫比亞河的古老捕魚地。政府在用腳手架建大壩。當我第一次來俄勒岡時,我曾看見印第安人站在那些腳手架上用三齒魚叉叉那些試圖跳上瀑布的鮭魚。政府已經買下瞭他們的村落,把他們搬到瞭路對麵,並在那裏給他們蓋瞭新的小屋。(肯?剋西訪談錄,《巴黎評論》,1994年春)
……
剋西想象著在小說的中心有一種強烈的戲劇衝突,但是也許在這一衝突裏我們所見的,如同斯甘隆所見的那樣,無非是所有的選擇都代錶著失敗。他從希臘悲劇,特彆是《安提戈涅》及其對於個人拒絕服從國傢秩序之後果的描述裏得到暗示。但是剋西發現自己也沉浸於麥爾維爾的戲劇衝突裏。令人恐懼的大白鯨化身為“聯閤機構”和它的工具大護士。在這樣一個非人的世界裏,也許隻剩下背叛者和被逐齣者會去追討人性。在《白鯨》裏,船長艾哈伯成瞭那個受傷的煽動者,帶領著他的船隊去追逐一個幽靈。在《飛越瘋人院》裏,麥剋墨菲帶著他的人進行瞭一次更為有趣的釣魚活動。在他們去漁船的路上,哈丁轉嚮麥剋墨菲,說齣瞭令人震驚的觀察:“我以前從未意識到心理疾病也能産生力量,想一想:也許一個人越瘋狂,他就變得越有力量,希特勒就是一個例子。什麼事都要求閤情閤理就會讓人頭昏腦漲,不是嗎?那真是精神食糧一般的警句啊。”麥剋墨菲曾拿自己那大白鯨圖案的黑短褲開玩笑,說是一個俄勒岡州立大學的女學生送的,“她說我是一個象徵”,這無疑是象徵那個儲存精子的龐然大物。但是如同麥爾維爾的大白鯨一樣,麥剋墨菲也是一個難以捕捉的幽靈。在麥爾維爾和剋西那裏,美好與邪惡的巨大衝突成瞭模棱兩可的形象的交替,黑與白的結閤。
剋西喚醒瞭麥爾維爾作品裏的人物,如沉默的抗拒者巴托比、化妝的騙子,以及高貴而神秘的魁柯來體現酋長布羅姆登,並探索在一個殘酷的世界裏保持尊嚴的可能性。比利?彼比特的命運讓人不禁聯想到麥爾維爾的替罪羊似的人物比利?巴德,而麥剋墨菲似乎也多少具有水手的犧牲精神和柯拉加特先生的狡黠。當他帶領大傢去釣魚時,麥剋墨菲難道不是一個漁夫之王、一個耶穌一樣的釣取人們靈魂的漁夫、一個像船長艾哈伯一樣的善於操縱的專製者,或者一個帶領一群瘋子乘坐“百靈鳥號”或者“愚人船”到海上鬍鬧的騙子?釣魚是最古老的把戲之一,而麥剋墨菲似乎是一個玩把戲的高手。病房裏的人假定瞭他那荒唐愚行背後的高超技巧會讓他贏得戰爭的最後勝利。但是大護士也知道如何擊破病人們對這個“救世主”的忠誠,讓他們懷疑他的好意,並提醒他們“他絕非傻瓜”。
最終,由於拒絕退齣他的遊戲,麥剋墨菲也許成瞭真正的傻瓜。如同每個雜耍者的命運那般,他深陷於自己的遊戲之中。他無法抗拒擊穿大護士高深莫測、難以駕馭的麵具,並剝奪她自稱的權威和純潔性的誘惑。他的嗜賭成性和巨大胃口使得他周圍的每個人都暴露在一個不能容忍揮霍者的賭場。布羅姆登說:“他要對付的東西是無法一勞永逸地被製伏的。你能夠做的就是不停地鬥爭,直到你再也無力應對更多的迴閤,彆人不得不接替你的位置。”麥剋墨菲的這種品行以及他維持自身獨立性的方式,對於他自己和其他人都産生瞭後果。每一次麥剋墨菲砸碎護士站的玻璃時,他都加高瞭賭注並加劇瞭風險。在這一群人中,最終隻有一個人砸碎瞭通嚮更廣大世界的玻璃。麥剋墨菲也許就是自身破壞性激發瞭創造性的巫師,一道讓光明進入、讓野性流露的縫隙。
羅伯特.法根
美國剋萊濛特.麥肯納學院文學教授
用户评价
满减很划算,看看译本如何
评分电影中主人公的反抗精神以及最后的结局,都让我想探究一下原著的究竟。
评分看过同名电影,经典,书也应不错。
评分终于看完这本书了,买了回来一直都没看,是本好书
评分重庆出版社的这一套系列丛书都不错
评分好好好!一如既往的好!网购只认京东!
评分送货速度很快,还没看感觉挺好的,买了很多假期不会无聊了哈哈哈
评分中文书,到货后总体感觉不错,绝对支持正版
评分京东速度!太快了!晚上下单,第二天早上就到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第二十二条军规 [Catch-22]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40665/54c21b18N3819429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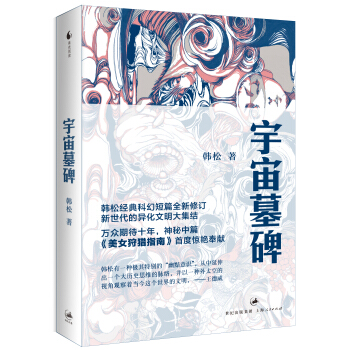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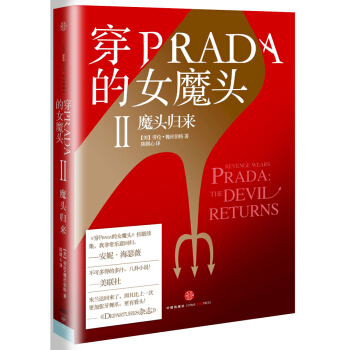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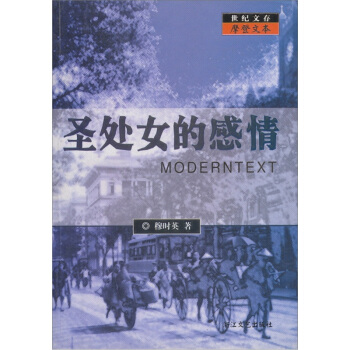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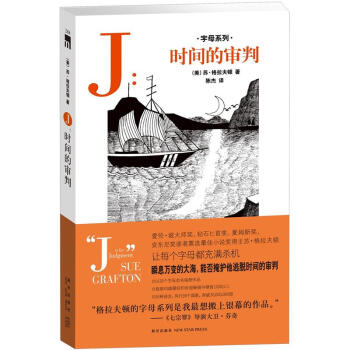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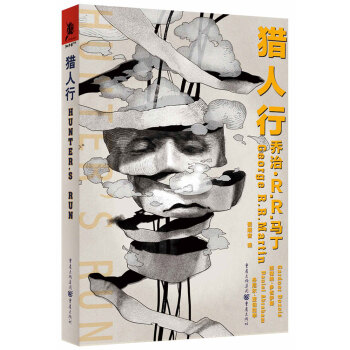

![终点人 [ENDER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67953/55efb899N61b2f1bf.jpg)

![企鹅手绣经典系列:爱玛 [Penguin Threads: Emm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54616/5809c081N500e50bc.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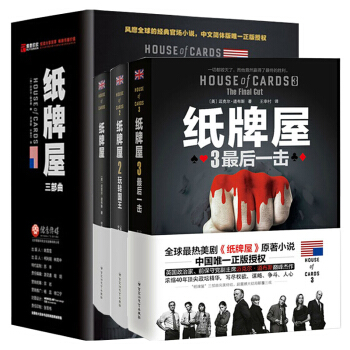
![时光之轮3:转生真龙(套装上下册) [The Dragon Rebor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033070/75a76311-d73f-4be6-bda4-9b9c4a4bdfa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