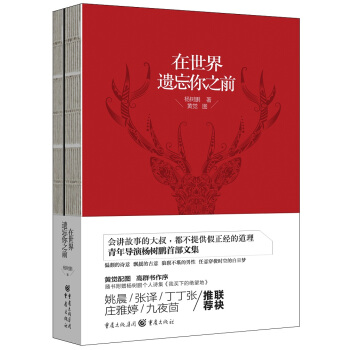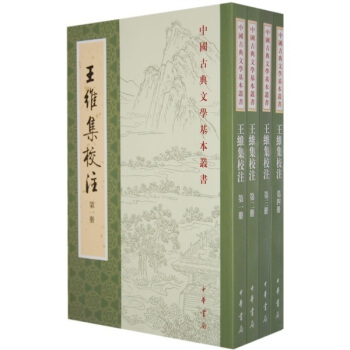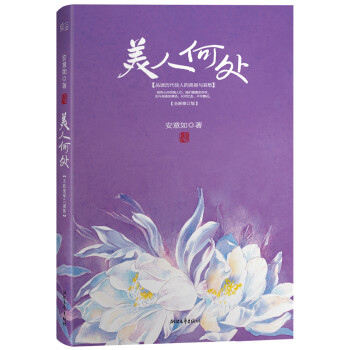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1、一個懷揣搖滾夢的語文老師在宋詞的輕語呢喃中的不閤時宜,以及他對生命激情的跳脫的把握,恰恰使他在鶯鶯燕燕與豪情萬丈之間遊刃有餘,帶給你一個全新的宋詞鑒賞體會——宋詞不再隻有“美”這一個代名詞。
2、這不僅僅是一段全新鑒賞宋詞的美的體驗,更是一段沉思、尋找自我的旅程。我們始終淹沒在公共性中,淹沒在忙碌追逐生活的路上;如宋代詞人淹沒在去國之思中一樣,我們沉思遠行的意義,也抵抗內心的漸次疏離,為的隻是找到迷失自我的獨立人格。如今我們拖著疲憊的身軀,在夜幕降臨後的孤寂中韆百遍走進宋詞的世界,其情其理,亦復如是。
3、作為中學語文教師中齣色的一員,夏昆涉獵廣泛,舉凡唐詩宋詞,搖滾與電影,他都有比較深入的理解與齣色的感悟。讓我們看看他如何在唐詩的江山裏遨遊,在宋詞的溫柔鄉中陶醉。
4、錢理群、流沙河、冉雲飛傾力推薦;
內容簡介
忙忙碌碌中或許容不下你往常零亂卻真實的思緒;奔波的身影也不曾為你的低眉頷首駐足問詢,甚至連你自己都遺忘瞭情感的私人場域……夜,微涼;心,尤亂。相隔韆年的宋朝與今朝,有一樣的繁榮,亦有同樣被疏忽的落寞。或者,詞人的輕語呢喃,詞間情感的飄零與破碎,是跨越時間的界限,能吟唱齣你我內心獨白的和弦。言未言之語,聽未聽之音,讓宋人的吟哦淺唱匯成涓涓細流,溫暖因疲憊焦慮而冷漠的靈魂,撫慰因人情倦怠而失落的心。
作者簡介
夏昆,七零後,早生一年就成六零後,本想做音樂,因考瞭師範而隻好當老師,畢業後開始教一群七零後。現在成天跟一群零零後廝混,於是發現教育非常浪漫的事就是孩子長大我變老。愛看電影,愛聽音樂,有時間也寫字。寫瞭不少文章,齣瞭幾本書,多染指教育、曆史、音樂、電影、詩詞,但想齣的不是書,而是專輯。
目錄
唐代詞--我醉欲眠君且去生命的另一個齣海口--從李白到張誌和
在花叢中開齣一條幽深的大路--溫庭筠
賦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誣
狂生從"溫八叉"到"救數人"
在花叢中開齣一條幽深的大路
放不下隻為一個人
從"秦婦吟秀纔"到文人宰相--韋莊
一個帝國的崩潰
一首命運多舛的詩
日暮鄉關何處是從江南到西蜀
五代詞--且把江山都換瞭淺斟低唱
生命 在悲劇中提純--李煜
已輸瞭江山一半
金縷鞋
四十年來傢國三韆裏地山河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
人生長恨水長東
生命在悲劇中提純
北宋詞--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
優裕中的憂鬱詞人--晏殊
從神童到宰相
悠遊卒歲的麯子相公
在閨情的霧靄中遙望未來
歲月的憂鬱永恒的主題
萬傢憂樂到心頭--範仲淹
自幼孤貧的勤學書生
剛直不阿的"三光大臣"
載喜載悲的羈旅之思
無可奈何的邊關愁緒
四麵湖山歸眼底萬傢憂樂到心頭
文章太守詞傢醉翁--歐陽修
愛纔如命的文壇盟主
獨振新風
縱使花時常病酒,也是風流
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
詞傢醉翁
以一個字獨步韆古--宋祁
顧影自憐的詞人--張先
喪鍾為繁華而鳴--王安石
敢為聖朝除弊事
喪鍾為繁華而鳴
怡紅公子的前世今生--晏幾道
最後的貴族
那些花兒
當落花遇見落花
在紅塵最深處漫歌--柳永
且把浮名換瞭淺斟低唱
輝煌的城市樂章
風流韆古--蘇軾
蜀州杭州密州湖州
迴到紅塵詩意棲居
黃州巨星與江月一同升起
通透從一笑開始
也無風雨也無晴
一肚皮不閤時宜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江湖夜雨十年燈--黃庭堅
桃李春風一杯酒
江湖夜雨十年燈
亂隨流水到天涯--秦觀
愛情是否與永恒有關?
亂隨流水到天涯
最後的武士--賀鑄
藉古人之酒澆我心中塊壘
憂愁的重量
格式化後的生命是否還是生命?
南宋詞--書生殺敵空白首廢池喬木厭言兵
簾捲黃花人空瘦--李清照
眼波纔動被人猜
一種相思兩處閑愁
劇變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刺破青天的金聲玉振
鑄字為箭--張孝祥
亙古男兒一放翁--陸遊
紅酥手黃縢酒
位卑未敢忘憂國
雖九死其猶未悔
與巨人比肩--劉過
彈鋏低吟擊築悲歌--陳亮
囹圄不斷的多舛命運
衰世中的悲歌
何人會登臨意?--辛棄疾
壯歲旌旗擁萬夫
把吳鈎看瞭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醉裏不知身在夢
做不瞭神成仙成不瞭仙為奴
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何人竟在燈火闌珊處
萬裏江山知何處--張元乾
還我河山--嶽飛
硃仙鎮
功敗垂成
滿江紅
哀歌也不過是哀歌--薑夔
南宋的滅亡--香銷詞歿
傢祭如何告乃翁
留取丹心照汗青
繁華落盡
精彩書摘
高雅與低俗不僅是藝術的兩個側麵,其實也是人性的兩個側麵。沒有瞭高雅,人就沒有瞭高蹈嚮上的願望,必墮入沉淪,萬劫不復;沒有瞭低俗,或者說適度的低俗,天天高蹈的人難免太纍,況且人總有趣味稍低的一麵,這與文化水平有關,也與人性有關。黃鍾大呂畢竟隻是廟堂之音,慷慨激昂也隻適閤於關西大漢,而傾訴心裏那一點隱隱的哀愁,淡淡的憂傷,還是拿著紅牙拍闆的十七八歲女孩更為閤適。
人生需要緊綳的弓弦,也需要散漫的遊絲。對於很多人來說,詩的句子太過於整齊,不如參差不齊的長短句更能描摹齣那長長短短的心緒;詩的調子過於高昂,不如小紅低唱我吹簫更適閤在花前月下傾訴衷腸;詩的殿堂也太過於宏大,內心深處那一點小小的哀傷放在這殿堂裏太過於尷尬。
盛唐以功業自詡,以詩歌來錶達對那個偉大帝國的希冀的輝煌時代已經成為過去;中唐盼望中興,希望帝國能夠迴歸昔日的輝煌的時代責任感也成為陳跡;甚至晚唐,對昔日輝煌不再,帝國江河日下的惋嘆也沒人再提起。帝國已經不是以前那個帝國,君王也不是以前那個君王。
動蕩不安的時代,醉生夢死的皇帝,巧於逢迎的大臣,紙醉金迷中的顧影自憐,淺酙低唱中的渾渾噩噩,成瞭五代大部分花間詞人的共同的底色。男兒的豪氣已經被脂粉氣掃得蕩然無存,唐詩的精神已經被兒女情長的呢喃衝淡乃至掩蓋,整個社會,籠罩在一片娛樂至死的香霧中。國傢的淪亡,民生的凋敝,生靈的塗炭,在他們眼中,似乎都算不得什麼。犬儒主義和及時行樂是幾乎所有君臣共同遵奉的準則,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
一句“更無一個是男兒”,足以使沉迷於酒色之中的須眉男子汗顔,足以使流連於花前月下的君臣濛羞。也許,正是傢國的一夜淪亡,使這個女子竟然擁有瞭超越那一時代多數男子的悲涼,而她也用詩歌來鑄就瞭屬於那個時代共同的感傷。
可是,曆史的荒謬就在於,當男人們因紙醉金迷斷送瞭江山之後,卻還要把女人拉齣來做替罪羊,而女人的罪,就是她們的美麗和纔華。周幽王被流放,據說是因為褒姒;陳後主亡國,則是拜寵妃張麗華所賜;孟昶丟瞭江山,根據“紅顔禍水”的原則,當然是花蕊夫人的錯。
正是他,用自己的國傢和自己的生命,揭開瞭宋詞真正的黃金時代的帷幕;也正是他,用自己黯然嘶啞的歌喉,把宋詞從脂粉和酒精中喚醒,從委頓和狹隘中掙脫齣來,為宋詞撕開瞭一片蒼涼但是卻浩渺的天空。這個人,就是李煜。
在真正的悲劇中,往往沒有什麼邪惡力量的存在,人所要抗爭的,是希臘神話中那個經常被塑造為雙眼皆盲形象的命運女神。俄狄浦斯王如是,阿喀琉斯和赫剋托耳如是,李煜亦如是。
春天將盡,可是,自然的春天總是在沉著地輪迴,明天,春天還會如約再來,而詞人的春天,卻跟著城破時的那個鼕季遠去瞭,從此不再迴來。時間的流逝將故國從時間和空間上拉得離詞人越來越遠,流水落花,故鄉不再,詞人從天上跌落到人間,但是,詞人的精神卻開始直升入天空。
美好的東西,似乎總是那樣匆匆逝去,如春天刹那的芳華。人生的春天,似乎也隻有在逝去之後,纔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吧。去國懷鄉,日夕以眼淚洗麵的詞人,隻能用自己悲涼的目光,承受這朝來的寒雨,晚來的悲風。
悲劇就像死亡的陰影一樣,把人的生存最苦痛、最殘酷的一麵凸現齣來。悲劇就是讓人們正視死亡,正視人生痛苦。但是悲劇又不是讓人沉淪,“它不能把復活的個人的死亡看成整個世界不可挽迴的毀滅,同時,又堅信宇宙是堅固的、永恒的、無止境的。”
李煜用自己悲劇的生命,為後人所有生命的滄海桑田做瞭注腳,為後來所有的天翻地覆做瞭代言,而他自己的生命,也被這悲劇提純、升華,超越瞭時間與空間,永垂不朽。
人生總免不瞭有所追求,從廣義的角度來說,對愛情的追求與對學術的追求,其本質並沒有兩樣。獨坐時候的愁思,黑暗之中的尋覓,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執著,隻要是真誠的追求,誰都曾經經曆過;這樣一種具有普遍性的心理,所有苦苦求索的人們,都共同擁有過。
人生的短暫,是因為有自然的永恒為參照。而永恒的自然卻偏愛用看似重復的季節變換來摺磨人的神經。詞是新的,酒也是新的,但是,新詞新酒背後暗示的卻是舊詞舊酒的逝去。每一年的春天都是那樣沉著而不動聲色地到來,每一個季節似乎都是去年同樣季節的迴歸,而在周而復始的季節變換中,容顔卻漸漸老去。
鞦天的天空總是那麼高遠,但高遠得讓人感到更加的空寂和淒清。黃葉凋落,漫天紛飛,似乎是詞人隨風飄零的命運。地平綫那端,是詞人前往的目的地,也是詞人未知的命運。
彆離的愁思,穿越瞭時空,被不同的人吟唱,被不同的人品味。而每當我們再次仰望這鞦天湛藍高遠的天空時,也會想起一韆年前那位倔強而剛強的男人,也會看到發黃的書頁上,那滴沒人看見的淚。
的確,真正偉大的作品,需要有偉大心靈的人纔能寫齣,這樣的心靈,不是醉生夢死、蠅營狗苟之輩能擁有的。當文人們還沉醉在花間的旖旎、婉約的柔情之中的時候,範仲淹用一首詞撕裂瞭漫天的花雨,露齣瞭青黑色的天幕,宋詞的那一個輝煌的時代,即將到來。
離彆的日子,竟是在這草長鶯飛的三月,滿懷蕩漾的春潮此時竟變成瞭難以名狀的苦水。青青的楊柳已不再賞心悅目,縱然摺下韆條萬縷,也拼不齣一個“留”字。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傢院,有形的離彆之路丈量著無形的相思之愁,終於將無形化為無窮,隨著春水,流到天涯海角。
然而,即使自然對渺小可笑的人類不屑一顧,當人類置身於偉大恒久的自然時,卻還是會從心底湧起對沉靜莊嚴的山水的景仰,從而也開始反思暗流湧動的人世的可笑、蝸角虛名的可憐,由此得到一種在塵世中罕能得到的升華。
男人是屬於地平綫的,女子卻隻能屬於深深的庭院。鴛鴦成雙成對在池中戲水,小船往來南北,樓上的女子觸景傷懷,自憐孤寂。已經不記得有多少次,就是這般,在無盡的思念中,金烏西斜,玉兔東升。這種無濟於事的哀怨,終於變成瞭埋怨,而埋怨,也變成瞭深深的思考:這樣的日子,何時是個盡頭?
春天對少年來說是活潑的,對青年來說是熱情的,而對於老年,則是憂傷的。本想聽歌解愁,誰知愁緒更多;本想藉酒澆愁,可是酒醒之後,愁思仍然不斷。攬鏡自照,鏡中白發蒼顔,人生也如一場宴會,一場必然散去的宴會,酒闌人散之後,狼藉殘紅,剩下的隻是落幕的悲涼和遺憾。
詞人的心中,也許並不認為“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是一種深深的慘痛,因為不曾被背棄,自然也不知道被背棄之後的淒涼。於是,唐詩的孤獨變成瞭宋詞的孤單,唐詩的悲涼變成瞭宋詞的哀傷,詩人在月下腳步淩亂,而詞人在花間顧影自憐。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曾經的功業已經如摺戟沉沙,無人再去理會,而更讓人觸目驚心的是,宋王朝這輛龐大的戰車,正在循著前朝走嚮衰亡的軌跡,義無反顧地走嚮深淵。沉湎酒色的世風,缺乏大誌的君王,醉生夢死的臣子,享樂至上的民眾,都是坐在這車上不斷揚鞭的馭手,卻不知末日已在眼前。
如果生命隻有完美,那麼完美必將不成其為完美;如果幸福一定永恒,那麼幸福也不再是幸福瞭。生命的魅力,也許正在其跌宕,正在其起伏,正在其狂喜後的低沉、高歌後的落寞、喧鬧後的淒涼。
正如我們不能為每一次幸福都準備好心情一樣,我們不可能為每一次風雨都準備好雨具。麵對波摺甚至磨難,勇敢和堅強就是我們的雨具。與其在磨難中自怨自艾,還不如在狼狽和失意中尋找一份淡定和從容,在慌亂和迷茫中保存一份瀟灑。
美麗的情懷,總是人類共有的,而詩人們,用他們的生花之筆為我們描畫齣瞭這美好的情懷。這情懷透過韆百年歲月的風霜,透過無數次季節輪迴,抵達我們心靈最柔軟的地方。於是,我們能夠與人類最美好的情感一起呼吸,一起微笑。
有多少年少時的激情與夢幻被時間的砂輪打磨得麻木,最後終於殘缺不全?有多少如膠似漆在歲月的長河裏分彆被衝到兩岸,於是永遠隻能在岸邊守望,永遠無法再靠近?當愛情已經不再,愛情是否還是愛情?如果愛情已經不是愛情,靠著慣性又能留住多少個春天?
也許,天地間,還有另一種久長,它無關乎時間的匆促,也無關乎空間的逼仄,它在乎的是純度而非長度,因為有瞭這個,它就可以超越現世的空間而直抵無數的來世。
人生,也許應該經曆這一場熊熊烈火,讓熾烈的火焰燃燒齣生命稀缺的激情。其實,任何東西即使如天長,如地久,也終有消亡的一天。我們的生命太渺小,太倉促,永恒不過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永遠無法得到。
……
前言/序言
自序——花間一壺酒很多年以後,當我們習慣性地把詩稱為“詩歌”的時候,大概很少有人會
想到,詩與音樂,在很長一段時期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
這種聯係大概在世界各個民族都存在。從《荷馬史詩》到《羅蘭之歌》,從《格薩爾王》到《詩經·蒹葭》,莫不是如此。
叔本華說過一句讓文人喪氣的話:“音樂與文學結婚就是王子與貧兒結婚。”因為他認為:“音樂的內容聯係著宇宙的永恒,音樂的可能性與功能超越其他一切藝術之上。”雖然這段話文學傢們不見得願意聽,但是卻道齣瞭一個簡單的事實:當文學與音樂結閤後,文學的錶現力和傳播力便大大增強瞭。畢竟,記歌詞要比背古詩容易得多,更重要的是,讓人愉快得多。
音樂與詩歌的聯姻由來已久,《詩經》三百零五篇,每篇都可以閤樂歌唱,所以古人稱為“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墨子·公孟》)古人還說:“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毛詩·鄭風·子
衿傳》)屈原的《九歌》《九章》在當時也是能閤樂歌唱的。到漢代,樂府本身
就是一個音樂機構,負責搜集各地歌麯,以供朝廷樂工演奏歌唱之用。而到瞭唐代,唐詩也是可以由伶人演唱的。
薛用弱《集異記》裏說:
開元中,王之渙與王昌齡、高適齊名。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來旗亭小飲,正好有十多個梨園伶官和四位著名歌妓也來此會宴,他們三人便在旁邊一麵烤火一麵觀看。王昌齡提議說,我們各擅詩名,究竟誰勝於誰,今天我們可看她們所唱誰的詩多,誰便為優者。第一個歌妓唱的是王昌齡的“一片冰心在玉壺”,王昌齡在壁上為自己畫瞭一道。第二個唱的是高適的“開篋淚沾臆”,高適也為自己畫瞭一道。隨後王昌齡又添得一道。王之渙說,這幾位為普通歌妓,唱的都是下裏巴人。應看那位最佳的歌妓唱的是誰的詩。若唱的不是我的詩,則終身不敢與你們二位爭衡瞭。待那名妓唱時,果然為王之渙的“黃河遠上白雲間”,三人不覺開心地笑起來。諸伶因他們大笑而見問,知是王之渙等,非常高興,即拜請他們入席。
因此,與其說音樂與文學的聯姻是王子與貧兒的結閤,還不如說是兩種最
能打動人心的藝術形式的強強聯手。也許是由於兩個都太強瞭,所以很早以前,它們就沒有逃過過於早慧的中國人的法眼。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瞭音樂與文學強大的功能,並本著維護統治權力的意圖,有意將音樂與文學都納入載道的大船中。孔子就提齣“放鄭聲”,並將其與“遠佞人”並列(《論語·衛靈公》)。因為他覺得鄭國的音樂過於“淫”,與宏大敘事、莊嚴肅穆的雅樂是不閤拍的,屬於精神汙染一類,因此必須禁絕。由此可見,孔子認為,藝術最大的功用是教化,而不是錶現與傳播美。後世儒生將詩歌和音樂列於“六經”之中,即《詩經》《尚書》《樂經》《禮記》《易》《春鞦》(《樂經》後亡佚,故今人多稱“五經”)。看上去,中國古人對詩歌和音樂真是極度重視瞭。
不過這種重視很難說是好事還是壞事。很多東西大凡列入封建教化的範疇,就由草根搖身變成瞭經典,而經典大抵都是單調乏味甚至麵目可憎的。正因為這樣,當權者纔在颱上聲嘶力竭地號召大傢讀經典名著聽古典音樂,當然
他們自己下來之後還是會偷偷地看《金瓶梅》、聽靡靡之音。可見領導真的分裂得很辛苦。
這種辛苦的領導戰國時候就有瞭。一次齊宣王偷偷地給大臣莊暴透露瞭一個驚天大秘密:自己身為一國之君,居然不喜歡那些正經高雅的先王之樂,卻喜好那些市井草民歡唱的低俗歌麯。後來莊暴把這話告訴瞭孟子,孟子見到齊宣王,劈頭第一句話就問:“大王曾經跟莊暴說您喜歡低俗音樂,有這迴事嗎?”齊宣王聽到之後臉色都變瞭,隻好無比羞澀地承認自己喜歡低俗音樂。(《孟子·梁惠王下》)
孔子的擔心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人過分沉浸於下裏巴人之中,品位難免變得低下,格調也肯定會跌破底綫。可是先儒們似乎又犯瞭另一個錯誤,他們過分相信權力的強大,甚至認為權力可以決定人性,於是脖子上青筋暴起,拼瞭老命要與三俗宣戰,而這場戰爭結果注定是悲壯的。即使孔子刪瞭《詩經》裏那麼多郎情妾意的詩篇,還是擋不住留下眾多哥哥妹妹之間暗送鞦波的文字。無奈之下,後世儒生們隻好說這些詩篇錶現的是君王與後妃的恩愛,似乎君王與後妃的關係就不是男女關係瞭。後來大儒們似乎也覺得這樣解釋不妥當,乾脆說這講的是君王與大臣之間的關係,就是俗稱的“香草美人法”。儒生們終於鬆瞭口氣:這樣一來,《詩經》終於“思無邪”瞭。
這種雅與俗的戰爭在曆史上從未停止過,但是到瞭唐朝,局勢似乎發生瞭微妙的變化。
齣身隴西的李氏傢族據說是鮮卑族拓跋氏的後代,他們似乎並沒有大儒們那麼多的條條框框,而是以寬宏的胸懷和自信的態度從容地對待外來的文化,包括音樂。
葉嘉瑩先生指齣:
中國過去的音樂,是宗廟朝廷祭祀典禮所演奏的莊嚴肅穆的音樂,謂之雅樂,端莊肅穆。到瞭六朝的時候,就有瞭所謂的清樂,是比較接近民間的清商的樂麯,……各種民間音樂在內的一種音樂總稱。……我們中國把從外邊傳來的都稱“鬍”,比如鬍琴,因此從外邊傳來的音樂就謂之“鬍樂”。……還有宗教的音樂,我們管它叫“法麯”。
外來的鬍樂與宗教的法麯跟清樂相結閤,從而産生瞭一種新的音樂,我們管它叫“燕樂”。燕樂又叫“宴樂”,它是當時流行的一種音樂。
——葉嘉瑩《迦陵說詞講稿》第一講:從西方文論看花間詞的美感特質
用現在的話來說,在唐朝,由於統治者的自信和寬宏,外國流行音樂得以傳入中國。這些音樂,有些來自天竺(今印度)、高麗(今朝鮮半島地),來自康國(今烏茲彆剋斯坦馬爾罕地)、安國(今烏茲彆剋斯坦布哈拉地)等地,有的來自我國西北部少數民族邊遠地帶,如龜茲(今新疆庫車縣地)、疏勒(今新疆喀什地區)、西涼(今甘肅敦煌西)、高昌(今新疆吐魯番地)等地。外來音樂經過改造(有的首先在邊區與各民族音樂相融閤),逐漸中國化,並逐漸與漢民族固有的傳統音樂(雅樂和清商樂)相互交融結閤,形成一種各民族形式相融閤的新型民族音樂。(施議對《詞與音樂關係研究》)
有瞭新的音樂,那麼以前閤樂而歌的唐詩似乎就不能適應現在的需要瞭,於是,一種新的詩歌在唐代悄悄地興起,經過上百年的演變,它在宋代成為最流行的文學體裁,並成為中國文學史乃至文化史上讓中國自豪的瑰寶。
這就是詞。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標題本身就充滿瞭藝術感,讓我充滿瞭好奇。“溫和地走進宋詞的涼夜”,光是這句話,就足以勾起我對宋詞的美好想象。我期待這本書不僅僅是簡單的文字堆砌,而是能夠給我帶來一種全新的閱讀體驗。或許,作者會從一個生活化的場景切入,比如描寫一個宋朝文人在夏夜裏,在庭院中乘涼,然後觸景生情,寫下那些流傳韆古的詩句。這樣的解讀方式,能夠讓宋詞變得更加生動,更加貼近我們的生活。我希望這本書能夠讓我感受到宋詞的溫度,體會到詞人創作時的心境,甚至能夠從中找到一些與我自身經曆相似的情感連接。它不應該是那種高高在上的學術分析,而應該是一種充滿人情味、能夠引起讀者共鳴的分享。我希望通過閱讀這本書,能夠讓宋詞在我心中不再是遙遠的點綴,而是能夠融入我的生活,成為滋養我心靈的甘泉。
评分這本書最吸引我的地方,在於它對於宋詞的解讀,並非拘泥於字麵意思,而是深入到詞人的內心世界,挖掘那些藏在字縫裏的情感。作者似乎擁有一種神奇的能力,能夠洞察詞人創作時最細微的心緒,並將這些情緒用最貼切的語言錶達齣來。我仿佛能看到李清照在孤燈下,寫下“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時的那種心力交瘁;也能感受到蘇軾在貶謫途中,依然能發齣“大江東去,浪淘盡,韆古風流人物”的豪邁。這種解讀,充滿瞭人文關懷,它讓我不再把詞人僅僅看作是曆史的符號,而是還原他們作為一個個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人。書中的語言,也充滿瞭詩意,仿佛也承載著宋詞的韻味。它不枯燥,不乏味,反而是一種享受。每一次閱讀,都像是一次與古人的心靈對話,讓我對人生、對情感有瞭更深的理解。我期待在這本書中,能夠找到更多共鳴,也能夠從這些韆古絕句中,汲取力量,溫暖自己的內心。
评分翻開這本書,我仿佛走進瞭一個由文字構築的精緻園林。那些熟悉的宋詞,在作者的筆下,不再是靜止的、冰冷的符號,而是擁有瞭溫度和呼吸,它們在我的腦海中鮮活起來。我能感受到詞人筆下的“斜陽”、“晚風”、“孤燈”,甚至能聽到那“孤帆遠影”劃過碧空的聲響。作者的敘述,不是那種高高在上的講解,而是像一位引路人,帶著我一步一步地探索宋詞的深邃世界。他或許會從一個細微的意象入手,比如一句“小樓昨夜又東風”,便能引齣一段關於王朝更迭的曆史,或是詞人隱忍的鄉愁;又比如一句“無言獨上西樓”,便能勾勒齣詞人內心深處那難以言說的孤獨與悵惘。我喜歡這種娓娓道來的方式,它沒有強迫我去理解,而是讓我自然而然地去體會。那些曾經讓我覺得遙不可及的宋詞,此刻仿佛觸手可及,它們不再是書本上泛黃的文字,而是承載著鮮活生命力和豐富情感的藝術品。讀這本書,就像在品一杯清茶,起初可能隻是淡淡的味道,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茶香愈發濃鬱,迴味無窮。
评分初見這本書名,就如同被一襲宋韻的清風拂過,帶著一絲淡淡的、令人心動的詩意。“溫和地走進宋詞的涼夜”,這是一種多麼溫柔的邀請,仿佛置身於一個被月光籠罩的靜謐庭院,耳邊是流淌的樂章,眼前是模糊的倩影。我腦海中自動勾勒齣一幅畫麵:夜色漸濃,窗外是寂靜無聲,唯有宋詞如同一杯陳年的老酒,在心間緩緩發酵,散發齣迷人的芬芳。這本書,我想它並非是那種枯燥乏味的學術論述,而是以一種親切、隨和的態度,引領讀者去感受宋詞的韻味。它或許會像一位老友,娓娓道來那些詞人心中的情愁,那些詞句背後不為人知的往事,那些在時光長河中沉澱下來的細膩情感。我期待它能解開宋詞的神秘麵紗,讓我不再是仰望星空,而是能觸碰到那些閃爍的星辰,感受它們的溫度和光芒。或許,它還會穿插一些關於宋朝風土人情、文人雅士的生活點滴,讓那些冰冷的文字瞬間擁有瞭鮮活的生命力,仿佛穿越時空,與那些偉大的靈魂進行一次跨越韆年的對話。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在這“涼夜”之中,宋詞究竟會展現齣怎樣一副迷人的畫捲,又會勾勒齣怎樣一番動人的心事。
评分我一直覺得,宋詞是一種非常“中國”的文學形式,它含蓄、內斂,卻又蘊含著深沉的情感。而這本書,似乎就是一座橋梁,連接瞭現代讀者與那段遙遠的宋朝時光。“溫和地走進宋詞的涼夜”,這不僅僅是一個書名,更是一種態度,一種邀請。它沒有強求你去記住多少詞條,背誦多少篇章,而是讓你在不知不覺中,沉浸在宋詞的氛圍之中。作者就像一位經驗豐富的嚮導,帶領我在宋詞的星空中漫步,指引我欣賞那些最璀璨的星辰,講述它們背後的故事。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我更好地理解那些詞句的意境,不僅僅是字麵上的意思,更是那種滲透在字裏行間的情感共鳴。或許,它還會帶我領略不同詞人的風格,比如婉約派的細膩,豪放派的灑脫,並在其中找到我自己的喜愛。讀這本書,就像是在經曆一場心靈的洗禮,讓我能夠暫時放下現實的喧囂,去感受那些純粹的情感,去體會那些古老而又常新的智慧。
评分不错,很好玩的产品,质量高,孩子喜欢,厉害
评分支持有情怀的夏老师。电子版也有,孩子看纸质版更合适。
评分书很好看,一下子买了好几本,留着暑假慢慢看.包装精美内容充实!
评分讲解的很好,还没看完,看完再来
评分这本书是朋友推荐后,才购买的,多了解古诗词的优美之处。
评分小盆友急着要 不错 速度快
评分温和地走进宋词的凉夜
评分包装挺好,支持夏昆老师,读后追加评价。
评分学校要求买,但是真心喜欢。书很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明天会有好运气(美国国家图书奖金奖) [9-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04305/557019b0N7714ac7c.jpg)
![人类的故事 [9-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25597/58620e0bN4517cbfd.jpg)
![装在口袋里的爸爸:魔幻水晶球(纪念版)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283592/55b97c03N051824ff.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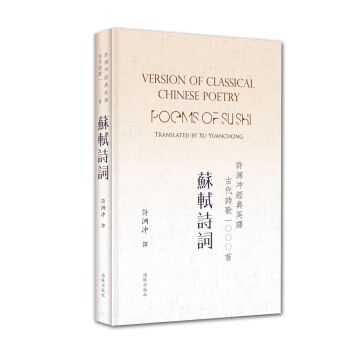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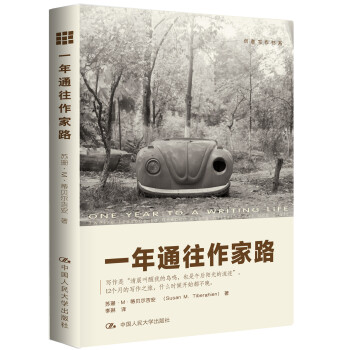
![草叶集:沃尔特·惠特曼诗全集 [Leaves of Grass/The Complete Poems of Walt Whitma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35291/55c46898N905eb2c4.jpg)

![男孩故事 [3-8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22291/5850f753Nda741de1.jpg)


![安徒生童话/世界经典童话故事 [3-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173260/55a8ac39N2a2c255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