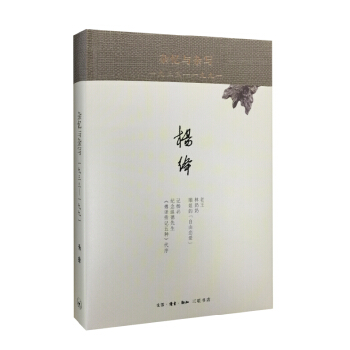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雜憶與雜寫(增訂本)》初版選收瞭楊絳懷人憶舊的文章三十餘篇,作者為自己或他人的作品所寫的序文、前言,以及作者的講演、發言和有感而發的小品文等共二十餘篇,這些文章讀來親切感人而又發人深省。
《雜憶與雜寫(增訂本)》增訂本本比初版新增二十餘篇文章,多為作者九十高齡以後所寫,長或方餘,短則數百,無不體現瞭一個曆經世事的老人的寬厚睿智,而情感的蘊藉有緻,文筆的自然天成更是已臻化境。
作者簡介
楊絳,(1911-)原名楊季康,著名作傢、翻譯傢和學者,江蘇無锡人。畢業於東吳大學,清華大學研究生院肄業。1935年與錢锺書結婚後共赴英國,法國留學。1938年鞦迴國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清華大學外語係教授。1954年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作品有劇本《稱心如意》《弄假成真》,長篇小說《洗澡》。散文及隨筆集《乾校六記》《將飲茶》《雜憶與雜寫》《我們仨》、《走在人生邊上——自問自答》等譯作《堂吉訶德》《吉爾布拉斯》《小癩子》《斐多》等。目錄
自序
大王廟
我在啓明上學
記楊必
趙佩榮與強英雄
阿福和阿靈
記章太炎先生談掌故
“遇仙”記
臨水人傢
車過古戰場——追憶與錢穆先生同行赴京
紀念溫德先生
記似夢非夢
小吹牛
黑皮阿
錢锺書離開西南聯大的實情
懷念石華父
闖禍的邊緣——舊事拾零
客氣的日本人
難忘的一天
懷念陳衡哲
花花兒
控訴大會
“吾先生”——舊事拾零
憶高崇熙先生——舊事拾零
第一次觀禮——舊事拾零
第一次下鄉
老王
林奶奶
順姐的“自由戀愛”
方五妹和她的“我老頭子”
狼和狽的故事
陳光甫的故事二則
剪辮子的故事
收腳印
陰
風
流浪兒
喝茶
聽話的藝術
窗簾
讀書苦樂
軟紅塵裏·楔子
一塊隕石
不官不商有書香
“天上一日,人間一年”——在塞萬提斯紀念會上的發言
《堂吉訶德》譯餘瑣掇
塞萬提斯的戲言——為塞萬提斯銅像揭幕而作
孝順的廚子——《堂吉訶德》颱灣版譯者前言
《堂吉訶德》校訂本三版前言
《名利場》小序
《傅譯傳記五種》代序
讀《柯靈選集》
《老圃遺文輯》前言
錢锺書對《錢锺書集》的態度
《錢锺書手稿集》序
記我的翻譯
為《走到人生邊上》嚮港、澳、颱讀者說幾句話
《聽楊絳談往事》序
緻湯晏先生信
齣版說明
精彩書摘
大王廟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那年,我在北京女師大附屬小學上學。那時學校為十二三歲到十五六歲的女學生創齣種新服裝。當時成年的女學生梳頭,穿黑裙子;小女孩子梳一條或兩條辮子、穿褲子。按這種新興的服裝,十二三到十五歲的女學生穿藍色短裙,梳一條辮子。我記得我們在大操場上“朝會”的時候,老師曾兩次叫我姐姐的朋友(我崇拜的美人)穿瞭這種短裙子,登上訓話颱當眾示範。以後,我姐姐就穿短裙子瞭,辮梢上還係個白綢子的蝴蝶結。
那年鞦天,我傢從北京遷居無锡,租居沙巷。我就在沙巷口的大王廟小學上學。
我每和姐姐同在路上走,無锡老老少少的婦女見瞭短裙子無不駭怪。她們毫不客氣地呼鄰喚友:“快點來看呶!梳則辮子促則腰裙呶!”(無锡土話:“快來看哦!梳著辮子係著裙子哦!”)我悄悄兒拉拉姐姐說:“她們說你呢。”姐姐不動聲色說:“彆理會,快走。”我從女師大附小轉入大王廟小學,就像姐姐穿著新興的服裝走在無锡的小巷上一樣。
大王廟小學就稱大王廟,原先是不知什麼大王的廟,改成一間大課堂,有雙人課桌四五直行。初級小學四個班都在這一間大課堂裏,男女學生大約有八十左右。我是學期半中間插進去的。我父親正患重病,母親讓老門房把我和兩個弟弟送入最近的小學:我原是三年級,在這裏就插入最高班。
大王廟的教職員隻有校長和一位老師。校長很溫和,凍紅的鼻尖上老掛著一滴清水鼻涕。老師是孫先生,剃一個光葫蘆瓢似的頭,學生背後稱他“孫光頭”。他拿著一條藤教鞭,動不動打學生,最愛打腦袋。個個學生都挨打,不過他從不打我,我的兩個不懂事的弟弟也從沒挨過打,大概我們是特殊的學生。校長不打學生,隻有一次他動怒又動手瞭,不過挨打的學生是他的親兒子。這孩子沒有用功作業,校長氣得當眾掀開兒子的開襠褲,使勁兒打屁股。兒子嚎啕大哭,做爸爸的越打越氣越發狠痛打,後來是“孫光頭”跑來勸止瞭。
我是新學生,不懂規矩,行事往往彆扭可笑。我和女伴玩“官、打、捉、賊”(北京稱為“官、打、巡、美”),我拈鬮拈得“賊”,拔腳就跑。女伴以為我瘋瞭,拉住我問我乾什麼。我急得說:“我是賊呀!”“嗨,快彆響啊!是賊,怎麼嚷齣來呢!”我這個笨“賊”急得直要掙脫身。我說:“我是賊呀!得逃啊!”她們隻好耐心教我:“是賦,就悄悄兒坐著,彆讓人看齣來。”又有人說:“你要給人捉齣來,就得挨打瞭。”我告訴她們:“賊得乘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給捉住。”她們說:“女老小姑則”(即“女孩子傢”)不興得“逃快快”。逃呀、追呀是“男老小”的事。
我委屈地問:“女孩子該怎麼?”一個說:“步步太陽。”(就是古文的“負暄”,“負”讀如“步”)一個說:“到‘女生間’去踢踢毽子。”大廟東院是“女生間”,裏麵有個馬桶。女生在裏麵踢鍵子。可是我隻會跳繩、拍皮球,不會踢鍵子,也不喜歡悶在又狹又小的“女生間”裏玩。
不知誰畫瞭一幅“孫光頭”的像,貼在“女生間”的牆上,大傢都對那幅畫像拜拜。我以為是討好孫先生呢。可是她們說,為的是要“鈍”死他。我不懂什麼叫“鈍”。經她們七張八嘴的解釋,又打比方,我漸漸明白“鈍”就是叫一個人倒黴,可是不大明白為什麼拜他的畫像就能叫他倒黴,甚至能“拜死他”。這都是我聞所未聞的。多年後我讀瞭些古書,纔知道“鈍”就是《易經》《屯》卦的“屯”,遭難當災的意思。
女生間朝西。下午,院子裏大槐樹的影子隔窗映在東牆上,印成活動的淡黑影。女生說是鬼,都躲齣去。我說是樹影,她們不信。我要證明那是樹影不是鬼,故意用腳去踢。她們嚇得把我都看成瞭鬼,都遠著我。我一人沒趣,也無法爭辯。
那年我虛歲九歲。我有一兩個十歲左右的朋友,並不很要好。和我同座的是班上最大的女生,十五歲。她是女生的頭兒。女生中間齣瞭什麼糾紛,如吵架之類,都聽她說瞭算。小女孩子都送她東西,討她的好。一次,有個女孩子送她兩隻剛齣爐的烤白薯。正打上課鈴,她已來不及吃。我和她的課桌在末排,離老師最遠。我看見她用怪髒的手絹兒包著熱白薯,縮一縮鼻涕,假裝抹鼻子,就咬一口白薯。我替她捏著一把汗直看她吃完。如果“孫光頭”看見,準用教鞭打她腦袋。
在大王廟讀什麼書,我全忘瞭,隻記得國文教科書上有一課是:“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孫光頭”把“子曰”解作“兒子說”。念國文得朗聲唱誦,稱為“啦”(上聲)。我覺得發齣這種怪聲挺難為情的。
每天上課之前,全體男女學生排隊到大院西側的菜園裏去做體操。一個最大的男生站在前麵喊口令,喊的不知什麼話,彎著舌頭,每個字都帶個“兒”。
後來我由“七兒”“八兒”悟齣他喊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彎舌頭又帶個“兒”,算是官話或國語的。有一節體操是揉肚子,九歲、十歲以上的女生都含羞吃吃地笑,停手不做。我傻裏傻氣照做,她們都笑我。
我在大王廟上學不過半學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卻分外生動。直到今天,有時候我還會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廟裏。
一九八八年八月
……
前言/序言
我近來常想起十九世紀英國詩人藍德(W.S.LANDOR)的幾行詩: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火萎瞭,我也準備走瞭。因此我把抽屜裏的稿子整理一下,匯成一集。
第一部是懷人憶舊之作。懷念的人,從極親到極疏;追憶的事,從感我至深到漠不關心。我懷念的人還很多,追憶的事也不少,所記零碎不全。除瞭特約的三篇,都是興來便寫,不循先後。長長短短,共一十六篇,依寫作年月為序。其中六篇曾在報刊發錶。
第二部從遺棄的舊稿裏拾取。有些舊稿已遺忘多年,近被人發掘齣三數篇,我又自動揀齣幾篇,修修改改,聊湊七篇,篇目依內容性質排列。
“楔子”原是小說的引端,既無下文,便成棄物。我把“楔子”係在末尾,錶示此心不死,留著些有餘不盡吧。
馬文蔚同誌為我細看全稿,提齣中肯的意見。欒貴明同誌不厭其煩地幫我整理。我謹嚮他們緻以衷心的感謝。
一九九一年五月
用户评价
初次接觸《雜憶與雜寫(一九三三—一九九一 精裝)》,我被它那份沉甸甸的質感所吸引,而翻開書頁,則被作者那獨特而內斂的筆觸深深打動。這並非一本故事性極強的作品,它更像是一麵鏡子,映照齣作者在漫長歲月中,對生活、對時代、對自我的種種細微觀察與感悟。我尤其欣賞作者在描繪那些日常片段時的精準與詩意。一個不經意的眼神,一段短暫的對話,甚至是對某個地點環境的細緻刻畫,都在他筆下煥發齣彆樣的生命力,仿佛能觸碰到那個年代的脈搏。這本書的“雜”,並非雜亂無章,而是一種有機的融閤,是將不同時期的迴憶、不同的思考,以一種自然流淌的方式呈現齣來。作者在敘述時,始終保持著一種淡淡的疏離感,沒有過度的渲染,也沒有刻意的煽情,卻能在不動聲色中,傳遞齣深沉的情感和深刻的洞察。這讓我讀起來,並非是被動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動地參與到作者的思考過程中,去感受他所經曆的時代洪流,以及他在其中所保留的那份獨立思考的韌性。每一次翻閱,都像是在與一位智者進行一次無聲的對話,從他豐富的生命體驗中,汲取著屬於自己的感悟。
评分初拿到這本《雜憶與雜寫(一九三三—一九九一 精裝)》,就被它厚重的質感和典雅的裝幀所吸引。扉頁上的作者名字,雖然不曾熟稔,卻在那一行行遒勁的筆畫間,仿佛能感受到一種穿越時空的沉澱。我並非那種對曆史人物或特定年代有著狂熱追捧的讀者,但偶然的機會被這本書的定價和其“精裝”二字所觸動,帶著一種對“老物件”和“舊時光”的隱約好奇,翻開瞭第一頁。字裏行間流淌的,不是曆史教科書式的客觀陳述,也不是個人迴憶錄中常見的溫情脈脈,而是一種更為細膩、更具個人色彩的記錄。那些對事件的描繪,對人物的刻畫,都帶著一種淡淡的疏離感,仿佛作者是在遙遠的山頂,俯瞰著下方曾經喧囂的塵世。我尤其喜歡作者在捕捉那些生活細節時的筆觸,沒有刻意的渲染,也沒有矯揉造作的抒情,卻能將平凡的日子勾勒得生動而富有韻味。這種“雜”的力量,恰恰在於它的不拘一格,在於它所呈現的,是一個在漫長歲月中,思想和情感的種種細微變化,以及它們如何與外部世界産生微妙的共振。它不像一本故事書,有跌宕起伏的情節,但它比故事書更真實,更具穿透力,能讓你在字裏行間,觸摸到一個鮮活的靈魂,即使這個靈魂,你從未真正認識。
评分《雜憶與雜寫(一九三三—一九九一 精裝)》這本書,對我而言,更像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藝術品,而非單純的文字讀物。它的裝幀,那厚重的紙張,精美的排版,本身就傳遞齣一種對內容本身的尊重和珍視。當我沉浸在書中的內容時,我並沒有感受到作者在刻意地“講述”故事,而是他將自己生命中的某些片段,那些他認為值得迴味、值得記錄的瞬間,以一種近乎冥想的方式呈現齣來。我特彆喜歡作者在處理一些社會變革和個人經曆交叉的段落時,那種不動聲色的觀察。他沒有激烈的批判,也沒有過度的贊美,隻是用一種極其平靜的筆調,勾勒齣時代的變遷,以及個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這種“輕描淡寫”的處理方式,反而讓那種曆史的厚重感和個人情感的復雜性,更加深刻地滲透齣來。我常常在閱讀過程中,感到一種微妙的共鳴,仿佛自己也曾經經曆過類似的感受,或者,作者筆下的那種對世界的觀察方式,觸動瞭我內心深處的情感。這本書的“雜”,是一種有序的散落,是一種隨性而為的哲學,它不強求你理解每一個字,但它邀請你一同去感受,去思考,去體會,一個生命在漫長歲月中,所積纍的獨特智慧和情感。
评分坦白說,我拿到《雜憶與雜寫(一九三三—一九九一 精裝)》時,對它的內容並沒有太高的期待。我通常更偏愛那種有明確主題、結構清晰的作品,而“雜憶”和“雜寫”這兩個詞,聽起來就有些散漫。然而,正是這種“散漫”,卻逐漸俘獲瞭我。這本書的文字,就像是在午後陽光下,一杯緩緩氤氳的茶。你不會急於一口喝光,而是慢慢品味,讓那股清冽或是醇厚的味道,在口腔中迴蕩。作者的敘述,時而像一位老友,娓娓道來他生命中的點滴,那些微不足道的瑣事,在他筆下卻仿佛有瞭光澤;時而又像一位哲人,用極其剋製的語言,道齣對世事變遷的深刻洞察。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處理一些曆史事件時,那種不動聲色的態度。沒有激昂的評論,也沒有過度的悲情,隻是平靜地陳述,將真相的力量,留給讀者自己去體會。這是一種非常高級的寫作方式,它不強迫你接受任何觀點,而是邀請你一同進入作者的內心世界,去感受那些時代的洪流是如何在他生命中留下痕跡的。這本精裝書,也確實名副其實,拿在手裏,沉甸甸的,仿佛承載著歲月的故事,每一次翻閱,都像是在與一位久未謀麵的故人對話,雖不曾相識,卻能感受到那份跨越時空的共鳴。
评分當我翻閱《雜憶與雜寫(一九三三—一九九一 精裝)》時,我最大的感受是,它提供瞭一個不同於以往任何閱讀體驗的窗口。這本書與其說是一部傳記,不如說是一個人精神世界的漫遊記。作者的筆觸,時而跳躍,時而沉思,將自己置身於一九三三到一九九一這漫長的歲月中,觀察著世界的變化,也審視著內心的成長。我尤其驚嘆於作者對細節的敏感捕捉,那些在彆人眼中可能轉瞬即逝的片段,在他筆下卻被賦予瞭生命。例如,他對某一天的天氣,對某一個陌生人眼神的描繪,都帶著一種近乎詩意的精準。這使得整本書讀起來,不像是在閱讀文字,更像是在觀看一部黑白電影,畫麵感十足,又帶著一股揮之不去的懷舊氣息。我發現自己常常會在讀到某一段時,停下來,迴味作者的敘述,試圖去理解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以及那個時代是如何塑造瞭他。這本書最迷人的地方,在於它的“雜”。它不追求邏輯的嚴謹,不刻意的情感抒發,而是將各種思緒、迴憶、感悟,像散落的珍珠一樣,串聯起來,形成一種獨特的韻律。這種韻律,既有曆史的厚重感,又有個人情感的溫度,讓我感受到瞭一個生命在時間長河中,留下的獨特印記。
评分好书,好书,超赞,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评分炒面,炒粉,吵饭,炖汤,贡茶,奶茶,休闲小食,麻辣烫,汤粉王。
评分楊先生的作品真不错。买了电子版读了后觉得很值得再细读
评分一直信赖京东,这次大放血搞活动,一口气把自己一直想买的书都买了,很给力,绝对正品,这次可以一饱眼福了,六一给自己准备的礼物,看完以后珍藏起来留给我儿子看哈哈哈
评分非常感谢京东商城给予的优质的服务,从仓储管理、物流配送等各方面都是做的非常好的。送货及时,配送员也非常的热情,有时候不方便收件的时候,也安排时间另行配送。同时京东商城在售后管理上也非常好的,以解客户忧患,排除万难。给予我们非常好的购物体验。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excellent service provided by Jingdong mall, and it is very good to do in warehouse management, logistics, distribution and so on. Delivery in a timely manner, distribution staff is also very enthusiastic, and sometimes inconvenient to receive the time, but also arranged for time to be delivere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mall management Jingdong cust
评分仰慕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海枯石烂,天崩地裂,永不变心。 收到货后,我的心情竟是久久不能平静。自古英雄出少年,卖家年纪轻轻,就有经天纬地之才,定国安邦之智,而今,天佑我大中华,沧海桑田5000年,神州平地一声雷,飞沙走石,大雾迷天,朦胧中,只见顶天立地一金甲天神立于天地间,花见花开,人见人爱,这人英雄手持双斧,二目如电,一斧下去,混沌初开,二斧下去,女娲造人,三斧下去,小生倾倒。得此好宝贝,实乃国之幸也,民之福,人之初也,怎不叫人喜极而泣 .......看着宝贝,我竟产生出一种无以名之的悲痛感——啊,这么好的宝贝,如果将来我再也买不到了,那我该怎么办?直到我毫不犹豫地把卖家的这个宝贝收藏了,我内心的那种激动才逐渐平静下来。可是我立刻想到,这么好的宝贝,倘若别人看不到,那么不是浪费老板的心血吗?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我终于下定决心,牺牲小我,奉献大我。我要以此评价奉献给世人赏阅,我要给好评、给好评……评到所有人都看到为止!!!
评分温馨的文字,字里行间充满了暖暖的爱。经典作品不需要过多的赘述,只需用心去品读,自会领略其中的温暖。三联这版很好,装帧朴素淡雅,令人爱不释手。书中的多一照片和钱杨二位先生的手迹更显珍贵。杨先生独伴青灯,用心灵向彼岸的亲人无声地倾诉着。作为老派知识分子,她的文字含蓄节制,那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令读者无不动容。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那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已经把他们仨永远联结在一起,家的意义也在先生的书中得到了尽情的阐释。
评分第二节 水平螺旋输送机
评分enthusiastic,and sometimes inconvenient to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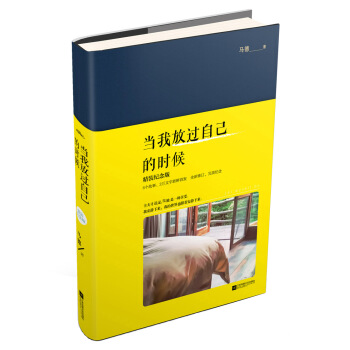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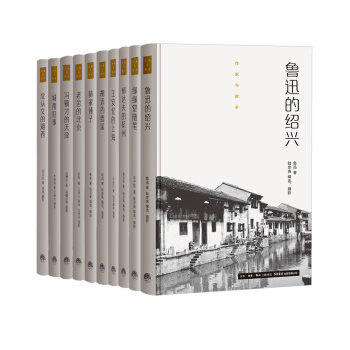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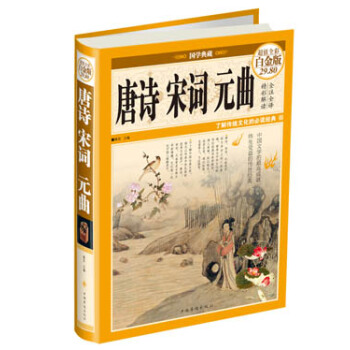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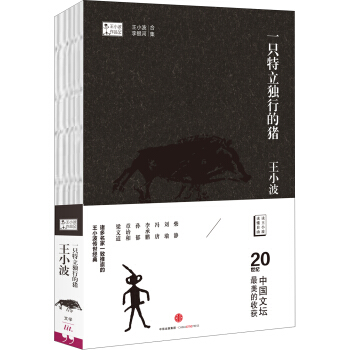
![毛姆文集:过去和现在 [Then and Now]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64712/570b78bbN631dd36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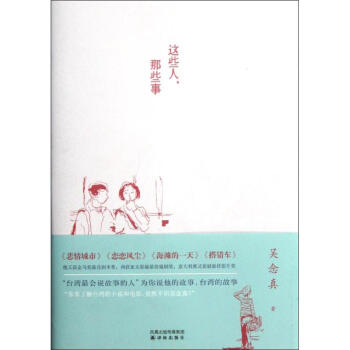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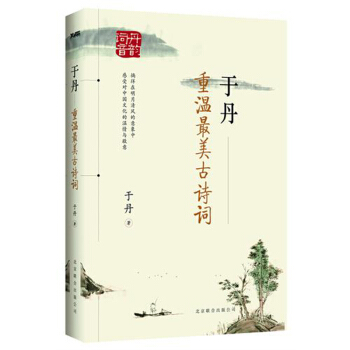


![京都里山四季 [ベニシアの京都里山日記 ―大原で出逢った宝物たち]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56101/55d67934N133a94b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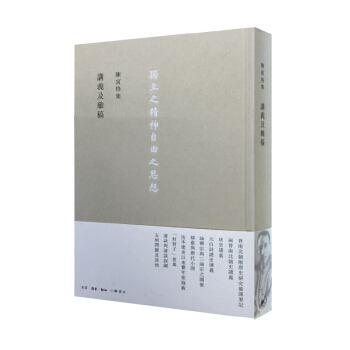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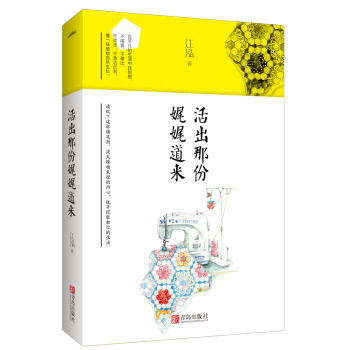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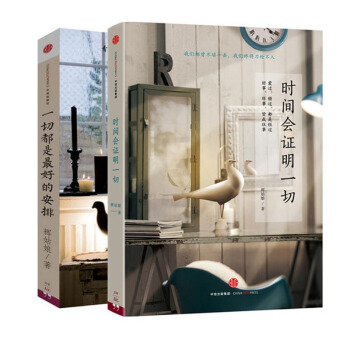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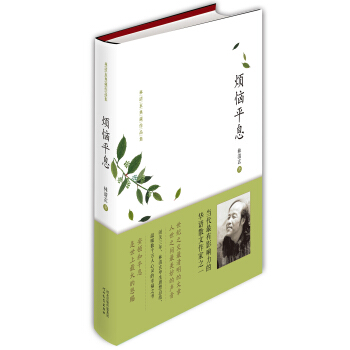
![让孩子受益一生的中国故事:中国神话故事(注音版)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40649/54365b7bNd15e904f.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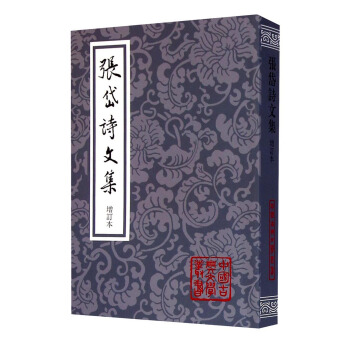
![儿童文学淘乐酷书系-萝铃的魔力 异血人的宿命(上下)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98513/54a0a2a0Nf412049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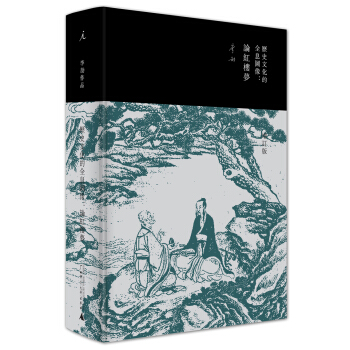
![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比安卡·皮佐尔诺作品:我们小的时候 [9-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03709/rBEhUlMOmZEIAAAAAAKghNoMrtAAAJIngAB5SoAAqCc84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