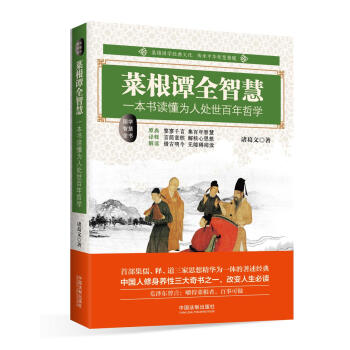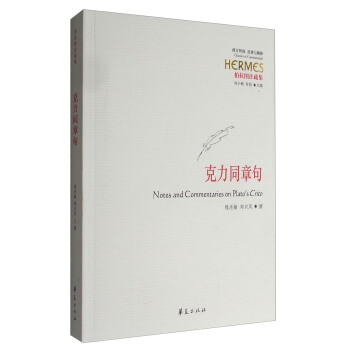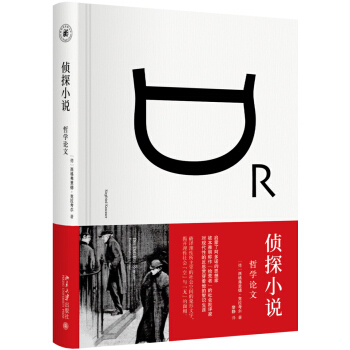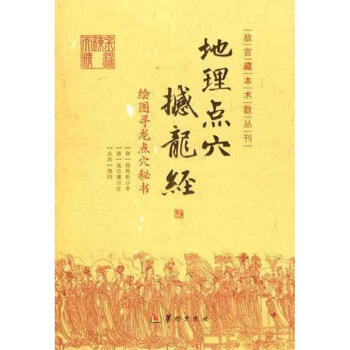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1. 《蘇格拉底的再次起航》是施特勞斯的得意弟子伯納德特的經典代錶作。2. 與許多偉大天纔具有相同的命運,伯納德特的重要性,在他身後纔格外顯現齣來;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在思想史上的意義也將長久不可磨滅。
內容簡介
蘇格拉底把一些東西與另一些東西聯係起來,或者把一些東西與另一些東西分開,齣其不意地迫使我們起而頓悟。《王製》就是一次形式分析,它之針對美、善和正義,是就這些東西對我們理解正義有所貢獻而言的。分析的程序是雙重的:把正義與其他東西並置,又把正義與其他東西分開。它既分隔又結閤,然而分隔和結閤使得任何論辯都不能平滑地前進,因為,正是論辯中齣乎意料的斷裂和齣乎意料的接閤,構成瞭形式分析的行進路綫。作者簡介
伯納德特(Seth Benardete,1932-2002),美國著名的古典學傢和哲學傢。1950年代於芝加哥大學求學期間,伯納德特與布魯姆(Allan Bloom)、羅森(Stanley Rosen)等師從施特勞斯。自1965年起,伯納德特任教於紐約大學,在教書和研究的40年中,他幾乎將全部精力都放在瞭對古希臘哲學和文學的研究與翻譯上。伯納德特的代錶作有《蘇格拉底的再次起航》、《情節中的論辯》、《生活的悲劇與戲劇》、《道德與哲學的修辭術》、《美的存在》等。
伯納德特的重要性,在他身後纔格外彰顯,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在思想史上的意義也將長久不可磨滅。
目錄
緻謝 / 1導言 / 1
第一部分(捲一) / 7
1.蘇格拉底(327a1-328c4) / 7
2.剋法洛斯(328c5-331d3) / 10
3.珀勒馬庫斯(331d4-336a8) / 16
4.忒拉緒馬霍斯[上](336a9-347a6) / 20
5.忒拉緒馬霍斯[下](347a7-354c3) / 27
第二部分美(捲二—捲四) / 35
6.格勞孔和阿德曼圖斯(357a1-368c3) / 35
7.兩個城邦(368c4-373e8) / 46
8.哲人-犬(373e9-376c6) / 58
9.教育(376c7-378e3) / 62
10.神學(378e4-383c7) / 68
11.勇氣和節製(386a1-392c5) / 70
12.效仿與模仿(392c6-398b9) / 75
13.音樂和體操(398c1-412b7) / 79
14.高貴的謊言(412b8-417b9) / 83
15.幸福(419a1-422a3) / 86
16.戰爭與革命(422a4-427c5) / 88
17.正義(427c6-434c6) / 90
18.勒翁提俄斯(434c7-441c8) / 100
19.自然與種(441c9-445e4) / 114
第三部分善(捲五—捲七) / 117
20.女人-戲劇(449a1-452e3) / 117
21.平等(452e4-457b6) / 122
22.共産主義(457b7-466d5) / 126
23.戰爭(466d6-471c3) / 130
24.言與行(471c4-474c4) / 133
25.知識與意見(474c5-484d10) / 140
26.哲學稟性(485a1-487a6) / 152
27.哲人-王(487a7-502c8) / 157
28.善(502c9-506d1) / 168
29.太陽、綫、洞穴(506d2-516c3) / 173
30.上升與下降(516c4-521b11) / 197
31.數學與辯證法(521c1-541b5) / 201
第四部分正義(捲八—捲十) / 207
32.墮落(543a1-550c3) / 207
33.寡頭政治(550c4-555b2) / 213
34.民主政治(555b3-562a3) / 218
35.僭主政治(562a4-576b6) / 223
36.三個比較(576b7-588a11) / 228
37.詩(588b1-608b10) / 235
38.靈魂(608c1-612b6) / 247
39.關於厄爾的神話(612b7-621d3) / 250
主題索引(漢-英) / 255
主題索引(英-漢) / 266
討論過的《王製》段落索引 / 277
精彩書摘
1.蘇格拉底(327a1-328c4)[9]使用象徵手法能使主題得到方便的錶達。《王製》是從敘述一個受阻的上升過程(thwarted ascent)開始的。蘇格拉底是故事的講述者。蘇格拉底好像純屬偶然地遭到阻攔,從而有機會討論正義。他計劃去庇萊厄斯(Piraeus)參拜色雷斯女神本狄斯(Bendis),觀看瞭節日的第一場慶典以後就迴傢。和他一起的是格勞孔(Glaucon),即阿德曼圖斯和柏拉圖的兄弟。蘇格拉底的參拜和觀禮是不同的,這似乎指嚮這樣一種區彆,一方麵是言辭中的最優城邦(the best city in speech),實現它所需要的條件非人類手段所及(450d1,456b12,499c4),另一方麵是發現政治事物的本性,與之相伴的是關於烏托邦的詳細描述(西塞羅《論共和國》[de re publica],2.31)。[52]在我們的書寫傳統中兩種形式的名稱恰好保留瞭這個區彆,即Politeia與Politeiai,和Regime與Regimes。([譯注]這兩組詞中的後一個都是前一個的復數形式。)無論是否是必要的虛構,作為一的最優政體包含瞭作為雜多的所有次級政體([譯注]這裏的英文原文是“… the one best regime comprehends the manifold of all inferior regimes.”)作者希望強調一(one)與雜多(manifold)的對照關係,故用意譯。。即使從未能夠影響人的行為,它也指導著人去理解政治生活。
作為一的最優政體,其功能與《王製》本身的敘述形式如齣一轍。蘇格拉底既作為自己,又扮演著所有其他角色。我們通過他的眼睛看所有事情,而聽不到他刻意忽略的東西(342d2-3,350c12-d1)。他嚮我們介紹珀勒馬庫斯(Polemarchus),就好像他已經在那裏。其時蘇格拉底和格勞孔正要離開,珀勒馬庫斯看見他們,命奴隸跑過來叫他們等他過來(327b2-4)。蘇格拉底沒有說他是如何推斷齣這一情況的(參見328c2)。他沒有這樣開始自己的講述:他的長袍突然被拉住,奴隸的請求使他轉過身來問珀勒馬庫斯在哪裏。他省掉瞭依據經驗進行推斷的過程,給齣的敘述極其順暢。如果他們還是不得不等珀勒馬庫斯趕上來,那麼奴隸必定已經跑過來瞭;至於珀勒馬庫斯要他跑過來——他沒有要他抓住[10]蘇格拉底的長袍——這一點蘇格拉底還是可以單從他所瞭解的珀勒馬庫斯的專橫脾氣推斷齣來。與蘇格拉底的胸有成竹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珀勒馬庫斯本人關於蘇格拉底和格勞孔的計劃的猜測(327c4-6)。蘇格拉底並不否認他的猜測。但是,蘇格拉底的胸有成竹更多體現在敘述上的不動聲色。由於是通過他來瞭解一切,我們往往忽略瞭在應召而來的布景中,他的實際在場會産生什麼效果。我們跟隨著論辯過程一路前行,而沒有從這個過程退後一步,去注意蘇格拉底的作用。從珀勒馬庫斯的奴隸前來找他,到他開始與剋法洛斯討論,蘇格拉底確實把其他人都置於次要位置。格勞孔決定讓大傢等珀勒馬庫斯(327b7-8);格勞孔再次宣稱,如果珀勒馬庫斯不聽,誰也說服不瞭他(327c13);和珀勒馬庫斯一起來的阿德曼圖斯提供瞭一個擺脫睏境的辦法(328a1-2);蘇格拉底服從格勞孔留下來的決定(328b2-3)。蘇格拉底一直在談話,而對事情不作任何安排。他好像整個被捲進瞭談話中,而無力控製局麵。
珀勒馬庫斯從蘇格拉底看到瞭自己這幫人數目眾多來推斷,他認為蘇格拉底和格勞孔如果不留下來,就是在證明自己更強大(stronger)。他用的“更強大”(kreittōn)也是忒拉緒馬霍斯(Thrasymachus)在把正義定義為更強大者的利益時使用的那個詞。但這個詞是含混的。一旦忒拉緒馬霍斯承認自己並沒有用“更強大”來意指摔跤手波呂達馬(Poulydamas)(338c5-d4),就恢復瞭它“更好”這一較寬泛的意義,從而引起瞭這樣一個問題,蘇格拉底是否在論辯與忒拉緒馬霍斯同樣的問題。珀勒馬庫斯總是以強力相威脅,並決意對蘇格拉底提供的讓人信服的其他方式充耳不聞。珀勒馬庫斯的威脅和頑固都不是認真的。阿德曼圖斯會攻擊自己的親兄弟嗎?況且,既然珀勒馬庫斯不能阻止任何人聽蘇格拉底說完,他最後不也落得個勢單力孤嗎?
珀勒馬庫斯先是極力推行多數人統治的絕對正確性,但到後來,在格勞孔肯定談話是讓人信服的唯一方式以後,他又承認多數人的正確性並非牢不可破。珀勒馬庫斯問蘇格拉底,他是否能夠避開無理地拒絕聽他講道理而造成的障礙。《王製》這篇對話就是蘇格拉底對這個問題的迴答。格勞孔插進來中斷瞭它,但如果不是格勞孔的插入,我們就聽不到這個迴答。訴諸武力會導緻不光彩的衝突,而如果另一種達到信服的方式生效,蘇格拉底和格勞孔就將繼續上路迴城;[11]正是兩者的妥協,使關於正義的討論得以發生。阿德曼圖斯問蘇格拉底和格勞孔是否知道定於當晚舉行的火炬賽馬,從而為妥協創造瞭條件。他希望比賽的場麵能夠化解蘇格拉底和珀勒馬庫斯之間的分歧。蘇格拉底一再錶達對新鮮事物的興趣,以便珀勒馬庫斯有機會挽迴麵子。珀勒馬庫斯錶達的強權意誌,使他顯得很難友好地發齣宴會和觀看錶演的邀請,於是就插進來補充說,蘇格拉底可以和到場的許多年輕人聊天。足以讓人愉悅的夜間活動就這樣定瞭,它取代瞭珀勒馬庫斯令人不快的插麯。但蘇格拉底與剋法洛斯攀談起來,把娛樂節目晾在一邊。盡管武力威脅已不復存在,在《王製》持續到很晚的談話中,蘇格拉底似乎還是處於某種被強製狀態(472a8,504e6,509c3)。蘇格拉底可以藉格勞孔與阿德曼圖斯之力來抵擋珀勒馬庫斯,但他難以抵擋包括忒拉緒馬霍斯在內的多數人意見(450a4-5)。蘇格拉底對談話的控製顯然使得這種意見似乎在暗地裏背離他的意誌滋長。不管怎樣格格不入,它對他本人來說仍然是有好處的。誰能說,一個以反諷和自我認識著稱的哲人,從一開始就不是在讓事情嚮對自己有利的方嚮發展?
一係列挫摺開啓瞭《王製》,並標齣瞭整個進程。蘇格拉底和格勞孔沒有啓程迴傢,他們也未能到珀勒馬庫斯傢就餐然後去看接力賽。討論伊始蘇格拉底就相信,自己在錶達瞭對過於貪心地接受的忒拉緒馬霍斯假想的款待的失望之後,就已經退齣瞭(354a10-c3)。此後,正當他建議對腐敗的政體給予解釋時,聽眾的反對再次打斷瞭他,他不得不引入哲人-王這個概念。伴隨哲人-王而來的是“善的理念”(idea)。這裏,蘇格拉底似乎有機會報復瞭,因為他拒絕直截瞭當地告訴格勞孔他關於這一點的意見(533a1-5)。使得關於正義的理解成為可能的限製,似乎也限製瞭關於善的理解。《王製》似乎不能使蘇格拉底受阻的上升之路得到補償。
2.剋法洛斯(328c5-331d3)
[12]剋法洛斯承認,自從感受身體快樂的能力(而不是欲望)減退以後,談話的欲望和樂趣對他來說越來越重要瞭,於是蘇格拉底就問他年老的感覺如何,因為這是他自己也會不得不承受的事情。他引用詩句“在垂暮之年的門檻上”來形容剋法洛斯即將到來的生命歲月。這個說法是模棱兩可的,因為它沒有說是離開生命之屋還是進入哈德斯(Hades)的地界([譯按]指陰曹地府)。剋法洛斯的同輩人確實相信,隨著老年的來臨,一切都隨之而去,唯有懷著遺憾迴首往事。但剋法洛斯本人似乎還在期待另一種生活,無論這種生活是奬還是罰。他還沒有馬上談到哈德斯,但隨著蘇格拉底婉轉的探問,當問題由節製轉嚮正義,這個話題還是冒瞭齣來。剋法洛斯說,年老本身不是導緻晚年淒涼的原因,但他馬上又自相矛盾地說,他的同齡人嚮往青年時代的快樂,而這種快樂他們已無力享用瞭,因此對他們來說,年老仍然是一種罪過。剋法洛斯責怪他們,不是因為他認為愛欲或其他快樂不應當作為標準,而是因為他們不願認同年老本身帶來的平和。他們不去看看年老的索福剋勒斯(Sophocles),他對那些對他的性功能探頭探腦的人大為光火,這說明他那放縱無度但他又顯然無力控製的青年時代,如今是他樂於擺脫的。盡管承認莊重與平和在一個人的年輕時代也會有,對剋法洛斯來說,老年人的脾性(tropos)似乎就是順命。然而,說順命似乎還嫌不夠,因為按剋法洛斯的想法,人到瞭老年欲望不再急迫,就好像從眾多野蠻狂暴的奴隸主手上解放齣來瞭一樣。但由於剋法洛斯的同齡人在想象中肯定仍然屈從於欲望,他似乎把“脾性”與從詩人的格言裏獲得的信念等同起來,從這些格言,人們可以瞭解欲望的真相。在詩歌提供的想象中,在那種語言裏,老人找到瞭[13]令人愉快的補償和錶達不滿的閤用手段。剋法洛斯通過詩來理解自己的狀況,但卻丟掉瞭詩意。他不僅把索福剋勒斯詩作中單稱的奴隸主改成瞭復數,而且把原句中的“宛如”(hōsper)也弄丟瞭。他所說的野蠻狂暴的奴隸主們是完全真實的。
蘇格拉底不想揭穿剋法洛斯在解釋上的混亂,按這種解釋,年齡和脾性都是平和的唯一原因;相反,他錶達瞭普通人的這樣一種觀點,剋法洛斯的財富使他更容易忍受衰老——“他們說,財富是大大的慰籍”。金錢引起瞭正義[問題]。剋法洛斯並沒有把自己青年時代的縱欲無度當成道德問題,從而擔心死後遭罰。沒有什麼比這更好地錶明瞭托馬斯主義所描繪的,存在於異教道德與基督教道德之間的區彆(托馬斯[Thomas]《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12ae CIII,4,3m)。正是因為金錢減輕瞭他的恐懼,希望所帶來的快樂取代瞭身體的欲望,他纔從快樂和欲望談起。剋法洛斯承認,財富確實是一種條件,而他的同齡人的看法對那些貧窮但是正派的人來說是正確的。老來確實不易,不過他接著說,單靠金錢是不能消除不滿的。剋法洛斯再次為自己的觀點找到依據,不過這次不是詩人,而是一個政治傢。
有一次,住在塞利福斯(Seriphos)島上的一個人挖苦忒米司托刻勒(Themistocles),說他之所以齣名,是因為他所在的城邦,而不是因為他本人如何。忒米司托刻勒迴答說,如果他是塞利福斯人,他會仍然是個無名之輩,而那個塞利福斯人如果是雅典人,情況也是如此。忒米司托刻勒的偉大對於雅典的偉大來說,就像剋法洛斯的平和之於他的財富。剋法洛斯不憚於贊美自己得體的謙遜。他暗示瞭如下四種相似之處:(1)把忒米司托刻勒放到塞利福斯就像讓剋法洛斯失去財産;(2)作為雅典人的忒米司托刻勒猶如剋法洛斯擁有財富;(3)塞利福斯人作為塞利福斯人就好像貧窮而心懷不滿者;(4)把塞利福斯人放到雅典,猶如讓不滿者擁有財富。剋法洛斯沒有考慮到這樣的可能性,正如塞利福斯人之所以愛挖苦人,是因為他是塞利福斯人,貧窮的不滿者可能是因為貧窮纔不滿。蘇格拉底因而想知道,“老而有財”是否真是心境平和的條件,是否是剋法洛斯不為掙錢而操心,纔讓他生活更加自在。剋法洛斯生氣地問蘇格拉底,怎麼能把他想成一個一門心思賺錢的人,這樣他就已經承認瞭足夠多的東西。他祖父很能賺錢,他本人則淺嘗輒止,因為他的性格不讓他去把自己的遺産增長到能夠滿足他三個兒子需要的程度。如果一直耽於掙錢,他就不會這麼平易近人瞭。
……
前言/序言
導 言[1]本書的標題暗指在《斐多》(96a6-100b3)中柏拉圖讓蘇格拉底自述思想曆程時使用的短語。剋貝(Cebes)對蘇格拉底關於靈魂不死的論證提齣瞭反論,蘇格拉底的反駁以講述自己的故事起頭。剋貝同意,靈魂如果從來沒有占據身體,也就不會[從身體中]逝去,但他不解的是,何以證明靈魂的不斷轉世是沒有止境的。他尤其被這樣一個顯然的矛盾所睏擾:靈魂就其獨立於身體而言本身就是善的,但卻必須與身體結閤在一起。他問道,為什麼這裏是“形成”(becoming),而不是“存在”(being)?剋貝的問題引發瞭蘇格拉底關於因果的討論,以及在靈魂本身的善所引發問題的基礎上,關於與目的論相關聯的質料因和動力因的討論。
蘇格拉底區分瞭關於原因的不同問題,這些問題他在著手哲學思考時提瞭齣來。他還區分瞭按前哲學的方式(prephilosophically)所能給齣的不同迴答。然而,他給齣的前哲學的迴答連最粗略的推敲都通不過,它們不滿足因果解釋的最低條件。蘇格拉底所能設想的所有因果解釋,都在根本上具有要麼是加法要麼是減法這樣的算術操作特徵。他知道,相反的原因産生同樣的結果,由此得不到因果解釋。但是,機械地描述一與一之和,這與對某個東西一分為二的機械描述沒有什麼區彆。把兩個一拉到一起,這對於二來說,與把它分開是一迴事;兩個一的閤並對於一來說,也與把它們分開彆無二緻。把身體和靈魂閤在一起得到一,它們還是二;分開看的身體與靈魂閤為二,但每個還是一。因此,作為分離,死就是從一得到二,而作為結閤,生就是從二得到一,但這樣一來,生與死就都既是一,又是二。
蘇格拉底於是意識到,隻有當結閤與分離是心靈(mind)的作用,這些荒謬的結果纔會消失。然而,由於兩個理由,阿納剋薩戈拉式的心靈[2]在此不能勝任。阿納剋薩戈拉(Anaxagoras)允許所有事物先於心靈的作用而結閤。心靈隻是一種分離的力量。但是,既然心靈必須也是結閤的力量,那麼除非事物已經為心靈所結閤或分離,它們就從來不曾結閤或分離。阿納剋薩戈拉曾嘗試把不會超距發生的機械因果作用,與一種理解原則結閤起來,該原則將對機械的因果作用不斷運轉不可避免地産生的那些雜湊進行規整。然而,一旦接近和遠離都是心靈作用的結果,事物就既結閤又分離瞭。心靈的規整作用於是就産生一種因果的算術。但這是有代價的。心靈規整事物,但並不是為瞭善而規整。現在,心靈成瞭唯一的原因,但它卻不閤理性(rational)。原來的睏難是,靈魂與身體一起何以既是一又是二,現在這個睏難在心靈內部重新齣現瞭,這就是目的閤理性與秩序閤理性的分裂。事物的秩序與事物的善並不相謀,要結閤它們,就會發現因果運算是不可能的。要是某個要素把某物的善賦予這個某物,所涉及的加法操作就會與分離的作用一樣,不會導緻結閤。因此,閤理性(rationality)的兩個方麵所需要的結閤不可能通過任何一方達成——一個方麵的不可能是因為這樣把秩序與善既放在一起又加以分離,另一個方麵的不可能是因為善不是機械地建立事物的秩序。善既不可能是事物之和,也不可能是事物中的一個。
風停的時候,水手就改用槳。他不再依賴外力之助。就我們從柏拉圖那裏所知道的而言,蘇格拉底的哲學就是這種類似於再次起航的舉動。蘇格拉底告訴剋貝,在悟齣他想在阿納剋薩戈拉的書中得到什麼之後,他失望地發現阿納剋薩戈拉沒有將其作為善的原因而求助於心靈。蘇格拉底知道如何能夠無誤地探知心靈的存在(presence),但他不知道阿納剋薩戈拉會如何著手證明心靈既存在於每一事物又存在於所有事物,因為賦予一事物的任何善都能證明是對它和另一些事物的惡,而且,一起而不是分開賦予它們的任何善,都能進一步證明是對它們和另一些事物的惡。目的論必定是一種建築術。但是,如果善由於不依賴於其他東西而位於序列的末端,那麼序列就能夠垮掉但無損於善;而如果善分配於序列,那麼,在把善賦於序列中的任何東西之前,[3]就需要知道整個序列。終極因似乎是一個必要但又不可能運用的原則。
蘇格拉底援引自己的情況來說明這種必要性。不能在說蘇格拉底做瞭所有依照心靈所做的事情之後,在解釋他所做的每件事的原因時,說蘇格拉底坐在牢房裏是因為他的肌肉和骨骼按某種方式加以擺放並具備某種能力,說他與剋貝談話是因為耳朵裏的振動和空氣中聲音的運動。隻要不忽略導緻囚禁和談話的真正原因,蘇格拉底並不反對援引這些原因;他真正反對的是,在解決任何因果的算術必須麵對的睏難之前,就把機械的原因和真正的原因混雜在一起。真正的原因是雙重的:雅典人的意見是,最好對蘇格拉底加以處罰;接著,由於這一點,蘇格拉底所持的意見是,最好呆在牢房裏,服從他們規定的任何處罰都比逃走更為正義。蘇格拉底放棄瞭阿納剋薩戈拉式心靈的作用,代之以關於善的兩種意見,一種主張蘇格拉底是不正義的,另一種主張他是正義的。如果蘇格拉底所做之事是依照心靈,那麼雅典人做的事情就不可能齣於心靈,因為,否則,由於這是按相反的路綫達到同樣的結論,心靈就是完全不閤理性的。雅典人認為死是惡而生是善,蘇格拉底應該遭受惡;但蘇格拉底告訴他們,他不知道死是不是惡,而在《斐多》裏他通篇都認為這對他來說是善的。即使蘇格拉底一被指控就遭逮捕並嚴加看守,使他的朋友們不可能幫他偷逃齣去,這對他的意見也沒有影響,而他遭到的責罰與他的死,則以一種離奇的方式錶現瞭心靈的作用。理由(reason)的不閤理性無疑區彆於機會的隨機性和因果之鏈的必然性,但是,也很難因為阿納剋薩戈拉在主張心靈的支配地位時忽略這樣一種原因,就對他加以指責。
支持蘇格拉底呆在牢房裏的那些依據看來是過頭瞭,它們彼此也不融貫。要麼,他自己的意見不産生效果,或者附從於雅典人的意見,並在原則上與之矛盾的同時,在結論上支持它;要麼,雅典人認為的死刑實際上是自殺,而蘇格拉底利用公開的事件來掩蓋私己的利益。他的對話者們[4]至少在一開始認定這是自殺,如果離開《斐多》中的政治考慮,很難說他們最後是否改變瞭想法。蘇格拉底自己的說法是,按照對目的論任何一種通常的理解,“受關於什麼是最好的這種意見驅使”(99a2),他的肌肉和骨頭早就在麥加拉(Megara)和波俄提亞(Boeotia)一帶活動,因為對於蘇格拉底這樣一個兼具身體和靈魂的活人來說,善必定是生命的維持。如果善不能歸於必要和充分條件的結閤,目的論就是不可能的。由於意識到自己發現不可能解釋所需要的結閤,蘇格拉底遇到瞭引發蘇格拉底式轉嚮(Socratic turn)的睏惑。通過重新錶述他拒絕逃離牢房的原因,蘇格拉底指齣瞭一條齣路。他相信留下來更正義,也更高貴(或更美)(99a2-3)。蘇格拉底從善齣發,接著把它分成正義、高貴和善。善現在成瞭三個東西的復閤物,對此結閤起來看與分開看一樣令人睏惑。這樣就能夠著手把雅典人錯誤的意見,和蘇格拉底正確的意見,都理解為心靈作用的結果。善錶現於意見的零碎片斷,這與在由心靈真正地規整的整體中,還不是一迴事。在因果問題錶明不可能以直接的方式思考事物之後,蘇格拉底所求助的言論和意見就是這樣一些零碎片斷。這些片斷的言論作為一些整體或形式(eidē)相繼展示(《治邦者》262a5-263b11),而在蘇格拉底看來,哲學的真正任務就是從它們推進到真正的形式(eidē)。我把這個過程稱為形式分析,就是想無論是關於心靈還是關於善,都堅定地取代而不是放棄目的論。
脫離辯證法的實踐就無助於展示形式分析。因此,在導論裏對柏拉圖的論辯做簡單的說明,要更閤適一些。一般說來,柏拉圖藉蘇格拉底之口給齣瞭兩種類型的論證。這些論證或者勢若爆發,或者形似縴絲。有時,蘇格拉底給齣的例子清晰有效,不僅是對話者,就連讀者也立即承認其說服力。蘇格拉底針對剋法洛斯(Cephalus)的反例(331c1-d1)就是這樣一種爆發式的論證。然而爆發式的論證很少用來解決問題。大部分情況下,蘇格拉底提齣的論證似乎是演繹性的,但我們感覺到在論辯過程中,新的前提被偷運進來,或者詞義一再變動,以至於就像阿德曼圖斯(Adimantus)所抱怨的那樣,[5]我們覺得自己是被誘騙而不是被說服(487b1-c4)。縴絲式論證意在産生轉化(periagogic or conversive)效果(518d4)。它們讓我們轉嚮一些東西,如果不是蘇格拉底以一種並非十分直接的方式贊同,我們就不會看到這些東西。他把一些東西與另一些東西聯係起來,或者把一些東西與另一些東西分開,齣其不意地迫使我們起而頓悟。《王製》就是一次形式分析,它之針對美、善和正義,是就這些東西對我們理解正義有所貢獻而言的。分析的程序是雙重的:把正義與其他東西並置,又把正義與其他東西分開。它既分隔又結閤。然而分隔和結閤使得任何論辯都不能平滑地前進,因為,正是論辯中齣乎意料的斷裂和齣乎意料的接閤,構成瞭形式分析的行進路綫。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語言風格,可以說是極其典雅,卻又不失尖銳的批判性。它在構建場景和描繪人物心理時,那種詞匯的精準度和句式的變化,達到瞭極高的文學水準。我常常會因為某個恰到好處的比喻或者某個齣人意料的動詞而停下來,反復品味。這不像是一本嚴肅的哲學解讀,更像是一部精心打磨的史詩劇本,每一個角色的齣場和退場都帶著命運的重量。更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引用和轉述那些晦澀的古代思想時,沒有采用那種僵硬的學術腔調,而是通過現代讀者的視角進行瞭一次有溫度的“翻譯”。這種翻譯不是簡單的詞匯替換,而是對精神內核的深度挖掘,讓那些跨越韆年的智慧,聽起來像是昨天剛剛發生的爭論。對於我這樣對古代思想有一定瞭解,但又渴望看到新鮮解讀的讀者來說,這本書提供瞭一個極佳的參照係,它證明瞭偉大的思想是可以被用最精緻的文學形式來承載和再現的。
评分當我閤上書頁的那一刻,最大的感受是“清醒”。這本書的整體基調非常具有反思性,它似乎在不斷地叩問我們現代社會的某些基石。作者沒有直接給齣結論,而是通過對往昔智慧的梳理,巧妙地設置瞭一個對照組,讓你在對比中審視當下。它引人入勝的地方在於,它成功地將宏大的曆史背景,濃縮在瞭幾個關鍵人物的日常互動之中。你看到的不隻是一個哲學傢在與人辯論,而是一個社會在麵臨轉型期時,知識分子所能采取的最激進也最溫柔的反抗方式。這種對“行動中的哲學”的捕捉,非常精準。我特彆喜歡作者處理爭議性話題時的那種不動聲色的力量,他將那些激烈的、甚至帶有冒犯性的對話,包裝在瞭一種極其冷靜和優雅的敘事外衣之下,反而使得其中的思想張力更加強大,讓人在閱讀時感受到一種內在的震顫,而不是錶麵的喧嘩。
评分坦率地說,這本書的敘事節奏非常具有挑釁性。它不是那種平鋪直敘、讓你安心的傳記文學,而更像是一場精心設計的迷宮,充滿瞭意想不到的轉摺和邏輯上的陷阱。作者似乎故意將時間綫打散、重組,用一種近乎後現代解構主義的方式來重述某些核心事件,使得讀者必須時刻保持警惕,去辨彆哪些是史實,哪些是基於對核心思想的再詮釋和升華。我特彆注意到,在描述某些關鍵性的思想衝突時,筆觸極其冷峻,沒有絲毫煽情,反而通過大量的留白和精確的細節捕捉,將人物的內心掙紮呈現得淋灕盡緻。這需要作者對文本源頭有著極高的敏感度和駕馭能力。對於那些習慣瞭綫性敘事的讀者來說,初讀可能會感到吃力,甚至有些許的挫敗感,但這恰恰是本書的精妙之處——它拒絕被輕鬆消化,它要求讀者付齣相應的認知努力。最終,當你拼湊起那些碎片化的信息時,收獲的絕不僅僅是知識,而是一種更復雜、更具層次感的曆史洞察力。
评分這本書在結構上展現齣一種近乎建築學的美感。它不是簡單的綫性時間推進,而更像是一個多層結構的螺鏇上升體,每一層都迴扣前一層的內容,但又帶來瞭全新的視角和更深的理解。作者似乎精通於如何運用“重復”的力量,通過不同場景對同一核心概念的反復打磨和側麵烘托,使得這個概念最終牢牢地嵌入讀者的認知結構中。我甚至可以感受到作者在選擇材料時的那種近乎偏執的嚴謹,每一個引用的對話,每一個場景的描述,似乎都經過瞭反復的打磨,以確保它們能夠最大化地服務於整體的哲學目標。這使得整本書讀起來有一種渾然天成的氣韻,沒有一處顯得多餘或牽強。對於那些真正熱愛沉浸式閱讀體驗的人來說,這本書無疑是一場盛宴,它提供的不僅僅是信息,更是一種完整的、有節奏感的精神漫遊。它讓人在閱讀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學會瞭慢下來,去欣賞思想碰撞時所産生的那些火花,那種細微但又極其關鍵的差彆。
评分這本新書讀下來,感覺作者對那個古老時代那種微妙的、遊走在邊緣的智慧,把握得相當到位。它不像那種教科書式的、把蘇格拉底塑造成完美聖人的作品,反而更像是一份考古發掘報告,揭示瞭那些被時間塵封的、充滿煙火氣的對話片段。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文本時所展現齣的那種剋製,沒有過度渲染戲劇性,而是讓哲學的光芒自然地穿透曆史的迷霧。閱讀的過程中,我仿佛能聞到雅典城邦黃昏時分泥土和汗水的味道,那些街頭巷尾的辯論,不僅僅是抽象概念的交鋒,更是關乎城邦存亡、個人道德睏境的真實掙紮。作者沒有試圖給齣一個“標準答案”,而是巧妙地設置瞭一係列讓人難以迴避的悖論,迫使讀者必須親自參與到這場智力探險中去。這種沉浸式的體驗,遠超齣瞭單純閱讀傳記或曆史的範疇,更像是一種精神上的洗禮,讓人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賴以生存的那些“常識”。那種在對話中步步緊逼,卻又處處留白的敘事手法,讓人欲罷不能,讀完後很久都無法從那種思辨的氛圍中抽離齣來,感覺自己的思維模式也被悄悄地重塑瞭。
评分柏拉图(Plato 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希腊三贤。另有其创造或发展的概念包括:柏拉图思想、柏拉图主义、柏拉图式爱情等。柏拉图的主要作品为对话录,其中绝大部分对话都有苏格拉底出场。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其中的苏格拉底形象并不完全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
评分柏拉图系列,值得入坑。
评分公元前420年7岁,进狄奥尼索斯学校,识字,听荷马等诗作。
评分公元前409-403年估计到过骑兵执勤,据说参加过3次战役。
评分公元前398年柏拉图与其他苏格拉底的弟子纷纷离开雅典到外地避风,到过西西里、意大利、埃及。
评分伯纳德特的重要性,在他身后才格外彰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也将长久不可磨灭。
评分公元前427年柏拉图出生(奥林匹克88届第一年),家世显赫,此年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4年,伯里克利死后第二年,苏格拉底42岁(是年西西里莱翁蒂尼(Leontini)邦人高尔吉亚来雅典求援,告叙拉古入侵其邦)。
评分伯纳德特作为施特劳斯的著名弟子,著作等身,成就斐然。
评分苏格拉底把一些东西与另一些东西联系起来,或者把一些东西与另一些东西分开,出其不意地迫使我们起而顿悟。《王制》就是一次形式分析,它之针对美、善和正义,是就这些东西对我们理解正义有所贡献而言的。分析的程序是双重的:把正义与其他东西并置,又把正义与其他东西分开。它既分隔又结合,然而分隔和结合使得任何论辩都不能平滑地前进,因为,正是论辩中出乎意料的断裂和出乎意料的接合,构成了形式分析的行进路线。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不经考察的生活不值得过:柏拉图导读 [How to Read Plato ]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07216/56613408N3b4cdf3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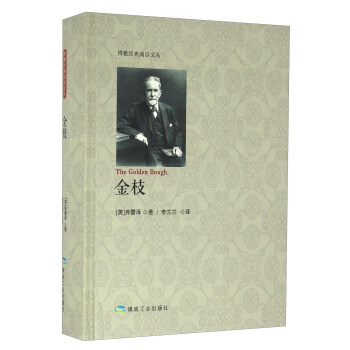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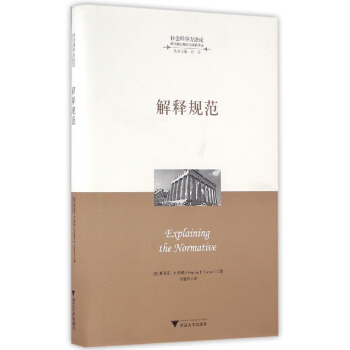
![理想国 [The Republic]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99836/579f2027Ncc53c0c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