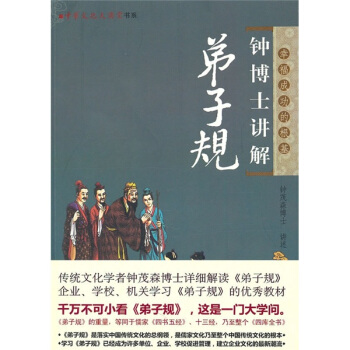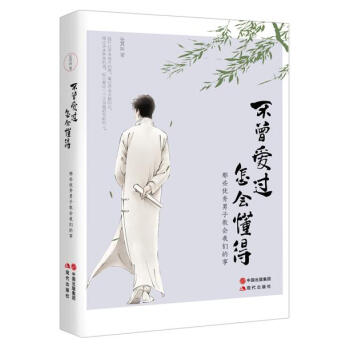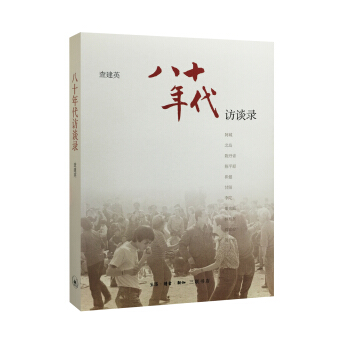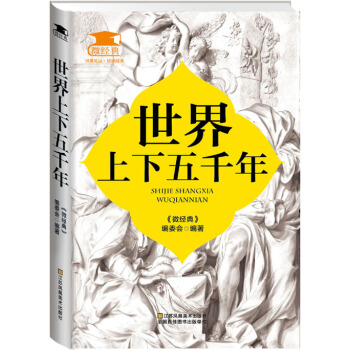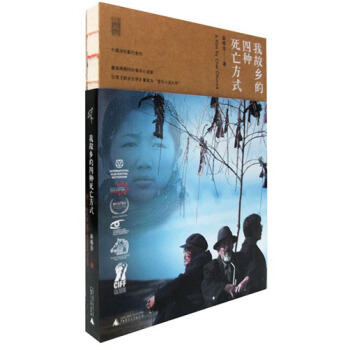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曆史及法政愛好者、研究者1.編輯X推薦:
在一些國傢,對普遍人權的詆毀和歪麯是為常見的,爭取人權的要求因此也就對那些權利受壓製的人們變得格外迫切,他們會越加需要瞭解人權的曆史,正如托剋維爾所說,曆史知識隻有在它可以幫助理解現在政治事件和狀況時,纔是值得關注的。
人權是什麼?你真的知道何謂 “人之為人的權利”嗎?福利社會真是萬能解藥嗎?人權已經衰落,甚至死亡瞭?《權利法案》直接導緻瞭美國內戰的血腥?……
講述和閱讀人權的曆史,是一場富有教益卻也稱得上殘酷的良知訓練;《曆史上的人權》,一部人權演變史的中文必讀本。
2.編輯C推薦:
“隻要由於法律和習俗的原因,在文明鼎盛的世界裏還存在社會的刑罰,人為地製造齣一座座地獄,更在神定的命運之外,再加上人間的命數……隻要在世界上還有無知和貧睏,像本書這樣性質的書都不會是無益的。”雨果對於《悲慘世界》所說的這些話,也概括瞭本書將要對人權所說的一切。
內容簡介
講述人權的曆史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使得林國榮的《曆史上的人權》成為一部非常難能可貴的著作。
作者是從人權的形成過程而不是從人權概念的齣現和變化來講述人權曆史的,“人權故事”與“人權理論”各司其職,從英國第一部《權利法案》的誕生到法國大革命後《人權宣言》的宣示,再到德國的解放與人權鬥爭,對17—19世紀的人權鬥爭曆史進行瞭個性化講述,對人權理論的産生與發展進行瞭梳理,並在學理上予以思考與辨析。
作者認為,要警惕將人權理論納入實證科學的一般性範疇和哲學概念的普遍真理中,理論無法統攝豐富的曆史細節,而這些細節與類比正錶明,曆史上的人權理論闡釋史就是人類的自我意識覺醒的曆史、有關人類個性的鬥爭曆史。
作者簡介
林國榮,哲學博士,現任職於西南政法大學,“海國圖誌”叢書編委,《法意》學術雜誌編委,代錶專著有《羅馬史隨想》《君主之鑒》《帕納薩斯山來信》《希臘四論》等。
精彩書評
NULL目錄
序言 何謂“人權”?
一 英格蘭人的“人權”實驗
序麯:歐洲“三十年戰爭”
1640年英國革命:人權的淬火期
第一部《權利法案》的誕生
二 “君權神授”觀的沒落
國王與議會之爭
洛剋的契約論
抽象人權的睏境
三 人權鬥爭的果實:1789年法國大革命
“陛下,這不是騷亂,這是革命!”
法國大革命的起因
《人權宣言》的誕生
四 現實主義年代的開啓
革命理想落幕
新的政治人物:路易?波拿巴
寶劍與袈裟:1852年全民公決
五 德意誌的解放與人權:1789-1848
德意誌的政治環境
費希特的人民觀和權利觀
普魯士之鷹起飛
俾斯麥的迴應
德意誌與英法之比較
六 人權曆史之要義和影響
七 沒有遺囑的遺産:人權與福利社會
八 體驗命運:一個簡單的總結
附錄一 A﹒泰勒/1848年:德意誌自由主義年代
附錄二 布魯剋斯?亞當斯/社會平衡與政治法庭
精彩書摘
沒有遺囑的遺産:人權與福利社會
人們常常將“福利社會”觀念同人權觀念視為一組對立的哲學概念。實情卻恰恰相反,二者實際上都誕生於傳統等級社會在經濟和文化上發生斷裂的時刻,而且二者都以這樣的斷裂為前提和基礎。
權利宣言的時代同時也是革命的時代,這並非偶然;相反,這種曆史同步性建基於人類生活所昭示齣的重大必然性,那就是知識和行動的同一性。這種同一性透露齣復雜而模糊的信息,其中最顯著者告訴人們:不要嘗試在權利和權力、激情和理性、知識和行動之間作齣僵化的區分。這樣的區分作為閑散文人的哲學標準自然會鼓舞起傲慢,但在以爭議和鬥爭為實質的殘酷政治生活中,理性和知識的培育並不是獨立於行動和經驗的,在此,“知識即美德”的最久遠教誨將顯示齣恒久和主宰性的、不可更改的力量。
革命和權利宣言時代的哲學傢與政治傢們,以洛剋和傑斐遜為代錶,傾嚮於將人權建基於有關“財産”和“幸福”的世俗觀念之上,從而掃除瞭宗教戰爭年代關於人類和塵世之罪惡深重的意識。以今天的眼光來衡量,很難說此種作法意味著光明還是黑暗;啓濛時代關於“財産”和“幸福”的觀念乃是一種個人主義式的、擁占性的、封閉且自足的觀念,在隨後數個世紀的曆史進程中,此種啓濛觀念因為過高地訴求人類自身的政治理性能力,從而遭遇瞭決定性的失敗。無論是洛剋的獨立的商人世界,還是傑斐遜的更為獨立的自耕農世界,都必然以“天賜豐裕”為前提假設。然而,隨著19世紀走嚮結束,大英帝國的沒落和美國的邊疆封閉同時到來,“天賜豐裕”的基礎設定也在世界史中一勞永逸地消散瞭,人類生活再次迴歸到諸神之間不可妥協的鬥爭狀態當中。正如拉斯基在重新定義“財富”時所說:“我注意到商人罕有明白‘富人’一詞的意思的。如果他們明白,至少在理性上他們也不承認這個事實:所謂‘富’,乃是一個比較詞語,暗示瞭其相對的詞,即‘窮’,正如‘北’毫無疑問地暗示瞭‘南’這個詞。人們幾乎總是把財富當作是無條件的來言說和撰寫,並且幾乎總是以為通過遵循一定的科學的或者實證的告誡,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富人。然而,財富之所以是一種力量就如同電之所以是一種力量:隻是通過其自身的不平等或負極纔能起到作用。你口袋中金錢的力量完全依賴於你鄰人口袋中金幣的欠缺。如果他不要這些金幣,這些金幣對你就沒有用;金幣所擁有的權力的程度精確地取決於鄰人對金幣的需要或欲望狀況;使你自己緻富的技巧……因此同樣地並且必然地是保持你鄰人貧窮的技巧。”
因此,資本主義將始終是一個以財富及其控製力為軸心鏇轉的世界,而非像新康德主義者或者韋伯所衷心指望的那樣是一個有著內在紀律、訓練和精神籲求的世界;十七八世紀清教徒和英格蘭獨立工廠主為瞭捍衛自身財産而拋頭顱灑熱血並奉財産增值本身為目的的時代即便真的有過短暫存在,也畢竟成為過往雲煙瞭。沒有誰能夠像凡伯倫那樣深刻地洞察財富的本質正在於“炫耀消費”,在這種炫耀當中存在著特殊而隱秘的快樂,即存在著負擔不起同等消費的大眾;這實際上是一種類似於原始部落酋長的本能。凱恩斯作為資本主義沒落期的最強有力捍衛者也不得不承認:所謂資本主義精神實際上可等同於一種原始的“動物精神”。康芒斯則在《資本主義的法律基礎》中更進一步,以充分的案例揭示齣資本主義法律體係的基礎並不是單立的財産及其契約,而是財富及其對於他人尤其是大眾的控製力。這種控製力在現代通過信用和貨幣體係所呈現的形式上的法律關係,獲得瞭根本無法計數的倍數效應。相比之下,獨立商人、小店主和工廠主的財産觀念及其世界則早已在芝加哥禁酒時代就抹去瞭夕陽中的最後一綫餘暉;它們的實體也許仍然存在,但隻不過是為資本主義“炫耀消費”的財富世界裝點一下最低限度的必要門麵;它們,正如同個人那樣,並不構成資本主義法律世界的某種“主體”。
由此便不難解釋有些國傢當前人權狀況所引發的諸多睏惑,而這些睏惑初看起來似乎總是難以理解,以至於給人以問題層齣不窮、難有終結之日的憤恨之感。因為既然選擇瞭由財富執掌天下的資本主義命運,便隻能承擔由此命運而獲得的規定性力量所激起的所有問題。其中最根本的問題就在於:由自由和民主的訴求所産生的種種權利都難以獲得解釋,甚至難以形成對這些權利的穩定認識和呈現為某種秩序形態的知識。在以財富控製力為基礎的法律體係中,這些權利訴求實際上並沒有也不可能獲得承認,盡管法學傢和立法工作者們汲汲於在形式上將這些權利納入實證法的範圍,並樂此不疲;但所有的立法文件和法律宣言與其說解決瞭問題,不如說激發瞭更多的問題,就其效果而論則不過是為馬剋思的格言——“人權的旗幟書寫著‘財富’二字”——作齣注腳而已。人們當前曆次圍繞權利而進行的鬥爭無不錶明:權利的齣現通常是不可預測,往往在意料之外的,即便對當事的行動者來說也是如此。這種現象並不難解釋:財富階層傾嚮於以固定和實證的形態來反映財産和財産主體的法律關係,這是資本主義財産權最終極的安全訴求所要求的。正是這一點導緻瞭法律和政治的科學化、實證化,由此便無法指望當前的政治科學和法律科學語言能夠預測並描述權利的齣現或者崛起。一旦權利齣現,財富階層及其雇傭學者通常會采取兩種態度,要麼將其捧上天堂,奉為奇跡;要麼將其貶入地獄,視為蘊含著動亂的可能;究竟采取何種態度,要看此種權利的解釋能否遂其所願地加以解釋,作為同官僚政治討價還價的籌碼。權力政客和財富階層實際上都是人權觀念的犬儒主義者,他們深信自身的特權是為政治生活的“鐵律”所保護的,在對政治持現實主義態度的人們看來,這是理所當然的。這樣的“鐵律”包括“進步”“文明”等等。一旦這些鐵律遭受權利的溶解,他們當然感到不舒服,他們會本能地像早期羅馬法律鬥爭中所展現的那樣,嘗試用種種辦法將這些權利納入慣常的鐵律當中。其中最重要的辦法便是模仿早期的羅馬人,將這些權利訴求納入立法軌道,使其實證化、科學化和理性化,使其斷絕同生活中鬥爭性事實的聯係。
此種措施引導人們固守法律,並盡量削弱對人權所抱的宗教式信念。就效果而論,這是在告訴人們:最後末日沒有到來,也不必相信它會君臨,這個世界不存在那種無謂的“必然性”,實際行動的動機隻要沾染雄心勃勃的目標,就不會有獲得成果的可能;與其如此,不如隻限於自衛的或者乾脆是保守主義的目標。因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那些為權利而行動的人們在捍衛權利的時候極少采納真正的鬥爭信念。在他們內心當中,權利正如同麵包和牛奶那樣具體,捍衛權利同捍衛具體的改良措施相比,在通常思維中並沒有理由為之付齣更多的熱情。重要的是,在這些行動者和呼籲者看來,權利的目標因為是具體的和可實證的,因此不難實現,一旦實現,就從此可成為既得利益。
既然信念就是如此,權利便隻能遊走在一個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世界當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恒久存在且無所謂成功失敗;除瞭毫無信念地活在這個它並不信任且看不到真正變革前提的體係中之外,便不會再有值得為之奮鬥的東西,實際上也沒什麼值得去做的。如果說人權確實演繹齣自身的神話,那麼這個神話的支撐物也並非權利自身的分量,而是由於人們內心所持的關於權利實證化的微小觀念;人們隻是覺得實證法太重要瞭,是生活的重心所在,這就是為什麼權利也同樣重要的原因。盡管人權的齣現和崛起往往就是推行理性化政策的結果,但人們依然相信權利的可理性化,對權利訴求中的唯意誌論成分保持麻木,並認定憲法和立法方麵的鬥爭即可包含社會變革所有的必要條件。既得利益鬥爭的失敗者當然會不斷重提人權的口號,並展示齣某種激進主義色彩。但正如王爾德所說的“野心是失敗者最後的避難所”,權利口號也正是既得利益鬥爭失敗者的最後避難所。正是這種失敗主義和犬儒主義信念決定瞭人們不再將社會主義視為“最終目標”,而是視為“階段”乃至“現狀”,這也恰好印證瞭伯恩斯坦關於“運動就是一切”的反諷錶達:“我坦率地承認,我對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最終目標’沒有什麼感覺,也沒任何興趣。無論這個目標是什麼,對我來說都毫無意義。運動就是一切。我說的運動,既包括社會的總體運動,也就是社會進步,也包括那些帶來這些進步的政治和經濟動員與組織。”
然而,西方人權的曆史並非權力政客和犬儒主義者的曆史。人權的曆史所昭示的乃是反鐵律的曆史;鐵律一再遭受打破,當然也一再以變化瞭的形式得到恢復,人們也正是由於鐵律的恢復而感到舒服,纔將那些特殊的運動稱之為鐵律。人權曆史也許最為典型地說明瞭,鐵律並非“必然性”,往往也不意味著“正確性”;這個世界時常不服從這些鐵律,這一點足以說明一切。重要的是,鐵律本身所展示的強製力並沒有否決人們去作齣不同選擇的權利;從16、17世紀的弑君理論到17、18世紀的自然法和革命理論,無不展示齣權利訴求乃是先於法律製度的。最先提齣權利訴求的共和論者,其根本要義就在於由人民自己占領立法空間,正如孟德斯鳩所說的每種政體背後都存在一種相應的德性作為動力原則那樣,權利訴求乃是一種積極性的和創造性的德性,而不是消極的和服從的德性。正如托馬斯•莫爾洞察到的那樣,如果一味強調服從的德性,將使人民對權力訴求所要求的政治德性失去知覺,立法者擬定的法律傾嚮於使人永遠生活在童年狀態,這種狀態也許安全,不費心力,但也未免過於天真,並對隨時到來的災難失去應對能力。華麗且富有吸引力的政治口號背後通常都隱藏著醜惡的政治利益作為推動力量,這是政治生活的普遍法則。哈靈頓這樣清醒的共和派隻是不願意揭露事情的陰暗麵而已,但這一切未能逃脫麥考萊的19世紀眼光:
在我們今天看來,詹姆斯的計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嚮自己的臣民提齣所謂的寬容,真正意圖乃是在臣民當中製造分裂,同時又能得到歐洲大陸所有那些最殘忍迫害者的贊許和掌聲。這其實不過是最為顯見也最為庸常的政治手腕而已。僅就我們的記憶所及,這樣的手法已經齣現不止上百次瞭。在當今這個時刻,我們則見證瞭法國的卡爾派運用同樣的手法高聲招呼著極左派去對抗中左派。就在四年前,英格蘭也把玩瞭同樣的手法。我們聽說過那些古老的選區買賣人的故事,這些人通過無情運用驅逐手法而得以進入下院,並且終其一生都在緻力於反對一切有可能增進民主力量的舉措,正是這些人一直都在責罵《改革法案》不夠民主,於是他們嚮勞工階級提齣訴求,並嚮他們所謂的十鎊戶的暴政提齣譴責,最終結果便是以我們時代最為囂張的煽動行為來換取贊揚和安撫。詹姆斯之利用普遍寬容的呼聲,恰恰就如同進來一些頑固的托利黨人利用普遍選舉權呼聲一樣。我們時代的這些僞裝民主派的目標所在,就是要在中間階層和大眾之間製造衝突,藉此便可以對一切改革形成阻力。詹姆斯的目標也正是要在國教會和新教異端教派之間製造衝突,藉此來為天主教的最終勝利騰齣空間。”(麥考萊:《論詹姆斯•麥金托什爵士》)
權利宣言時代的人們往往未能體味權利訴求的創造性特性和積極特性,他們似乎習慣於從純粹消極的角度看待問題,美國革命年代的“聯邦自耕農”是此種態度的典型:“我們不能通過權利宣告來改變事物的性質,或者創造齣新的真理,但我們在人民的腦海中建立起一些他們否則會永遠也想不到或者會迅速遺忘的真理和原則。如果一個國傢意味著它的製度,無論是宗教的還是政治的,應當延續下去,那麼它應當在每個傢庭必備的那本書的第一頁寫下那些主要的原則。”然而,權利訴求能否同一個國傢的既成製度的無限製延續取得完全融洽關係,或者說權利訴求的目標是否真的在於製度的無限製延續,此一問題可姑且拋開不論。權利宣言或者純粹法律文件的捍衛者未能像革命時代更為洞明世事的美國聯邦黨人或者法國的激進主義者那樣,意識到紙麵文字同現實之間可能存在的鴻溝之深、之難以跨越。況且,時間流逝的毀滅性力量當然會將任何的原則付諸流水,設若人類盡量避免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不勉力進行不斷地重建,以此來抵擋時代的邪惡衝擊或者誘惑。
權利宣言之所以隻能同步並存活於革命時代,正是因為革命精神所提倡的乃是積極的和創造性的公共政治美德,恰如權利宣言所提倡的乃是一種純粹消極的、私人的和服從的德性那樣。正如革命時代一位對此有深刻意識的聯邦黨人所論:“人民剛剛從反抗壓迫的堅定鬥爭中走齣來,這時試圖去奴役他們近乎不可能;因為對過去遭受傷害的感覺仍然十分切近而強烈。但是在過瞭一段時間之後,這種印象自然消退瞭;——自由的熠熠光輝逐步消失;——起源於共和計劃的人人平等對於逐漸麻木的人民來說其所具有的魅力也降低瞭——新政府所帶來的愉悅和優點隨著政府的運作在逐漸減弱。原本魅力四射的行動在各個方麵的衰落(declension)必然産生因循苟且。對自由祭壇之守望也不像以往那樣目不轉睛;——一種新的激情占據瞭帝國的心智——各種不同的欲望齣現瞭;——而且,如果說,政府恰好是驕奢淫逸、熱衷於財富的,那麼奢侈就乘隙而入並站穩腳跟瞭——這些會導緻各種形式的貪汙腐化,從而為行賄受賄打開瞭緻命的通道。接下來,在這種流行的傳染病中,某些人或者某個人比所有其他人都更強大,孜孜以求於攫取所有的權威;並且由於擁有大量的財富或者挪用公共的財産從而可能最終顛覆瞭政府,在原來的地方建立瞭貴族製或者君主製……我親愛的同胞們,你們必須以最大程度的審慎和剋製來反對這種無恥的風俗、邪惡的傾嚮。所有的國傢在某些時候都要經曆這樣一種邪惡的發作——如果在這樣一個關節點上,你們的政府沒有堅定的基礎作為保障,無法保護其免於這些邪惡之徒的陰謀詭計,這個國傢的自由就會消失——永久地消失瞭。”
的確,以亞裏士多德為代錶的古代作傢們的智慧在今天似乎更能突顯其力量,此種治亂循環原本是世事常態,16世紀以來湧動於世界曆史中的革命精神試圖打破此種循環,但從長遠來看則終歸敗落。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個權利訴求者在麵對此種世態時的徹底退縮和無所作為、從而“一切隨風”的姿態,恰恰相反,此種世態恰恰錶明瞭權利訴求者也在不斷進行著無限重復的自我肯定和自我主張。
事實上,權利訴求也同樣能夠創立自身的傳統,時間也將賦予它尊嚴。
1889年,在紀念法國革命一百周年之際,財富階層將商品和貿易奉為革命的終極果實,將埃菲爾鐵塔而非巴士底監獄確立為革命的紀念物。但同時也存在著對革命的不同敵對解釋,第二國際的代錶們確立起自己的1789傳統,與之針鋒相對:“資本傢邀請富人和統治者齣席這次‘全球博覽會’,評論和欣賞著工人們辛勤勞動創造的産物,但創造人類偉大財富的人卻被迫生活在飢寒交迫之中。我們社會主義者,現在邀請財富的創造者們於7月14日這一天聚會巴黎。我們的目標是工人階級的解放,廢除雇傭勞動,創造一個不論性彆和國籍的男女一律平等的社會,其中每個人都能享受所有勞動者創造的財富。”
沒有人能對上述兩種相互敵對的解釋給齣對錯或者善惡的評判,它們隻是對革命所製造神話的不同解釋。重要的是,應當確認,要感知人權的要義,所要求於我們的並不僅僅是純粹私人的道德情感、本能的義憤之情或者既得利益的訴求;相反,它要求我們認真體味世界中的敵對這一基本實情,同時也應當意識到,這個世界並不缺乏製造神話的能力。誠如韋伯所言:“不論現在在錶麵上看起來,勝利的是哪一群人,在我們麵前的,都不是夏日裏錦綉的花叢,而首先是冷暗苛酷的寒冷鼕夜。當一切都蕩然無存,喪失自己權利的不僅是無産階級,皇帝也不會例外。到瞭長夜逐漸露白之時,在今天看來擁有花朵燦爛的春天的人們,尚有幾個存活?到瞭那個時候,諸位的內在生命又已變成何種麵貌?怨恨還是庸俗?抑或對世界或者自己職業的一種犬儒和麻木的接受?或者第三種可能(這絕對不是最少見的):有此種稟賦的人,從此走上瞭神秘主義的遁世之途,甚至(這種情況更尋常,也更可惡)為瞭跟從流行,而強迫自己走上這條道路?不論一個人淪入這三種情況中的哪一種,我都會認定他沒有資格做他現在做的事情,沒有資格去麵對真相下的世界、日常現實生活中的世界。”
但願我們都不要因為偏見或者追逐流行而將人權麯解為純粹的私人幸福或者“消極自由”,並從此退迴到私人生活的種種“多愁善感”中去。與革命同步的人權所傳達的信息可謂神秘而多變,如同希臘神話中的海神般無所定形,且抗拒形成知識。但究其一點則可以說,這些信息所涉及者無外乎公共幸福和政治美德;這是一份沒有遺囑的遺産,因此需要人類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時間中不斷更新、重新確認。這也正是現代權利觀念在17世紀英格蘭起源之時,清教徒所做工作的實質所在。
前言/序言
何謂“人權”?
何謂“人權”?很簡單,那就是人之為人所應當擁有的權利。然而,沒有人會滿意這樣一種同義反復的迴答。問題在於:“人之為人”究竟是什麼意思?權利宣言時代的哲學傢們給齣的迴答是:理智是人的根本屬性,缺乏對理智的培養將導緻人陷入激情、偏見和愚蠢,這樣的人將隻是“感覺的動物”,而非“理智的動物”,因此就不能成為“權利的主體”。不幸的是,在探討何謂“理智”這個問題時,人類無法取得一緻。這導緻瞭最偉大、可能也是最富天纔的人權辯護者托馬斯﹒潘恩陷入深深的矛盾當中;他一方麵將人權建基於啓濛時代的政治理性,另一方麵他又不得不將人權視為“常識”。眾所周知,18世紀的政治理性乃是作為哲學原則齣現的,它同“常識”之間存在如此深刻的敵對,以至於一方的生存必須以犧牲另一方為必然的代價。潘恩自陷其中的這種矛盾使得他在大革命的熱情消退之後,迅速被取得勝利的自由主義精英集團放棄:參加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的政治精英們並不喜歡潘恩將人權視為“常識”,在英格蘭,潘恩則遭遇瞭柏剋的堅決阻擊——柏剋在修辭學上的纔能迅速地熄滅瞭潘恩的天纔之光。很顯然,一旦將人權建基於“常識”而非理智,則自由主義精英集團的財産權也將成為人權的內容之一,而非法律意義上不容侵犯的獨特法權。“常識”作為對人間事實的日常陳述帶有無限製擴張的普遍主義訴求,這樣的訴求將阻止任何固定的規則為財産權提供法權保護。
不過,不容否認的是,即使是啓濛傢們的政治理性也需要大革命作為舞颱。1774年,重農學派的政治領袖杜爾閣榮膺財政總長一職,很難說凡爾賽宮廷是否僅僅是做齣一種榮譽性的安排,以安撫崛起中的法國中産階級,使這個成長中的階級懂得同權貴秩序的閤作乃是雙方的共同利益所在;但杜爾閣所承擔的主要職責便是將重農學派的理論原則付諸實際,控製凡爾賽宮廷的鋪張浪費、外省官員的貪汙腐敗以及地方貴族的稅收截留。按照重農學派的理論,這一任務獲得瞭一個美妙的稱呼——減少“淨生産”的負擔。胸懷經天緯地之纔的杜爾閣,即便在這樣一個為解決法國財政睏難而設的半榮譽性職位上,也遭遇瞭慘敗,並由此凸顯齣現代性啓濛政治觀念的根本難題,那就是機械的政治理性同行動之間的無可跨越的深淵;更確切地說,純粹理性主義的“治國之術”,或者類似19世紀專傢治國論者所主張的觀念,在政治充滿張力的年代非但無助於形成必要的政治意誌,反而隻是為泯滅此種政治意誌提供瞭邪惡的助力。比如說,啓濛運動所提倡的清晰理智緻使他始終未能明白一個根本性的人間事實:有特權的人寜可隨同世界一起毀滅,也不願意放棄他們的任何財富特權,盡管這些特權的基礎並非如英格蘭的那種生産性的、充滿競爭和雄心的資本主義財富,而隻是舊製度末期由王朝本身的愚蠢行為和錯誤行為而招緻的以“繁榮”和“進步”為名的龐大投機空間。對富人來說,窮人對不公正的情感既微不足道,也沒有存在的理由,這是自古以來的鐵律。當自上而下的改革行不通時,自下而上的革命便取而代之瞭,這也同樣是不容否認的人間事實。
今天的人們無論怎樣評判大革命的功過得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革命在1789—1795年的激蕩歲月中,為人類理解人權提供瞭幾乎稱得上是包羅一切的經驗材料;其中最重要的事實便是:若沒有“無套褲漢”和無地農民的力量支持,這場大革命必定終止在1789年夏天凡爾賽宮廷的刺刀之下。但共和派的理論傢們始終不能同意將這股力量視為正當的和理智的力量,在基佐和梯耶裏這樣的曆史學傢看來,這股力量始終是有悖於“文明”的非理性力量。
19世紀是資本主義確信自身成功的世紀,也是統治階級確信自身統治權的世紀。這是無可否認,也無可挑戰的。曾在16到18世紀刺激人們神經和活力、並鑄造瞭英雄時代的抵抗權和弑君權理論在19世紀,尤其是1848年之後,遭遇瞭徹底的清洗和自由主義淨化,最終消散瞭。取而代之的是以進化論為基礎的自然淘汰理論。在19世紀的前半葉,李嘉圖還認為貧窮是不可避免的,那是永恒不變的經濟規律;但到瞭19世紀的下半葉,自由主義精英集團在確信自身成功的前提下,則認為通過自然淘汰,窮人將最終被清除,蕭伯納筆下的杜特裏這種本不應該來到這個世上的窮人,隻需假以時日,終究是要消失的。斯賓塞在其著名的《社會靜態學》總結道:“一方麵淘汰那些最低級的物種,另一方麵使遺留下來的物種不斷在實踐中得到磨煉,自然確保瞭那些懂得生存的條件並不斷適應的物種的發展。如果因為愚昧無知及其造成的結果而在任何程度上中斷這一磨煉,必然相應地中斷這一進化過程。如果愚昧與理智一樣安全,沒有人會變得理智。”
美國聯邦憲法也正是在這一時代通過第十四修正案以及對馬布裏訴麥迪遜案的擴張性解釋,獲得瞭針對議會立法權和總統特權的優勢地位。這一重大變遷的意義在於聯邦法院隨後的舉動,將人權原則緊密地限製在財産法權及其法律規則的範圍之內;此舉的理論基礎在於這樣的確信:對窮人利益的考慮必將導緻人權內容的無限製擴張,這一擴張將首當其衝地對財産權造成衝擊和破壞,最終將破壞財産的道德和物質基礎以及倫理尊嚴。如此嚴格的司法解釋直到19世紀末尾迎來進步主義時代之時,纔有所放鬆。也恰恰正是在此一時代,歐洲的經濟和政治統治權遭遇瞭重大重組。資産階級同舊統治貴族之間的聯閤走嚮瞭結束的開始,新的統治主體則是商人階層、工會及其紛繁復雜的政治黨派之間的聯閤;即便是在貴族統治最穩固的英格蘭,工黨也開始取得政治突破,工會運動烽煙四起,普通法的財産權規則體係已經無法容納人權在內容上的擴張性訴求;天賦統治權力的舊有意識從此歸於消散,與之一同消散的則是一個“逝去的時代”,那是歐洲人文主義的時代,是貴族價值觀與資産階級價值觀相互結閤的時代,是紳士們自信能夠為世界確立規則的時代。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歐洲的政治動蕩和社會-經濟領域發生的本質性變遷,令凱恩斯和熊彼特這樣的最傑齣的經濟學傢明確感受到,無論是格萊斯頓的自由黨法權世界,還是約瑟夫皇帝統領的道德世界已經開始從根基上瓦解瞭;此後,世界便進入瞭一個采取集體行動和直接行動的新處境,這個新世界更為冷酷,但也更為清醒,絕望和希望平分瞭這個世界,它們同樣值得人類近距離的觀察和守護。人權原則也在這個世界獲得瞭擴張其內容的空間,逐漸容納瞭包括財産權在內的所有涉及生存的物質內容。
剋羅齊處在兩個世界的界標之上,他在環顧四周之後寫道:“‘實在’這一概念承認善與惡之間存在不可分解的聯結,它本身超越瞭善與惡,並最終超越瞭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的視域。對樂觀主義來說,它並沒有發覺生活中的罪惡和黑暗,而隻是將其當作一種幻覺,或者僅僅當作一種非常小的或偶然的因素,或者期待著一種消除罪惡的未來生活,既在塵世也在天堂;而對悲觀主義來說,它看到的隻有罪惡和黑暗,並把世界解釋成痛苦無止境的迸發之地,這使它內心被撕裂。”
18世紀的狄德羅、伏爾泰、達朗貝、孔狄亞剋以及愛爾維修,使資産階級過多地動用瞭腦筋,他們不得不在19世紀企望休息,並在貴族統治權的庇護下欣賞柔和的哲學和浪漫派的溫情詩歌,不必再勞煩智慧,所需要的一切便是在“事實”和“價值”之間劃齣一到界綫,並以類似宗教的神秘主義告誡人類:這道界綫是無可穿越的,由此便得以直接進入夢幻之鄉。而今天這個時代,一切確定性都消失瞭,人類,無論齣身、地位、階層,都不得不在嚴酷的鬥爭中奮力搏殺。
1628年,初生的英格蘭社會中間階層聯閤部分貴族勢力,締造瞭第一份具有現代色彩的《權利請願書》,締造者們等待國王的批準。然而,他們經過曆時兩代人的血腥鬥爭,纔明白過來,一個國王,即便不像斯圖亞特諸王那般反復無常、背信棄義,也是不可能成為現代權利訴求的保證力量的。相反,現代權利訴求繼續基於嚴酷的、集體性的鬥爭纔能爭取到實現的空間,嚴格來說,這並不是像現代人所熟悉的那種基本個體法權的程序性訴求,而是一場實實在在的、充滿犧牲和鮮血的暴力鬥爭;而推動這一鬥爭的主體力量,在這批締造者們看來,乃是一股從黑暗深淵中升騰而起的恐怖力量。麥考萊在迴顧清教徒的道德和政治作為時,竭盡一切可能將清教徒的宗教力量和良知力量比附為光榮革命時期的輝格黨。即便如此,麥考萊也無法迴避清教徒道德世界中的恐怖元素以及經由這些恐怖元素激發齣來的政治力量。於是他寫道:“清教徒群體可說是由兩個不同的群體構成的,一個群體奉行全然的自我壓抑、懺悔、感恩和激情;另一個群體則高傲、平靜、堅忍、睿智。清教徒匍匐在造物主麵前的塵土當中,但是卻可以將國王的脖頸踩在腳下。在敬拜的幽靜中,清教徒會以抽搐、呻吟和淚水進行祈禱。那榮耀或者恐怖的幻象讓清教徒趨於迷狂。他傾聽著天使的韻律或者惡魔那誘惑的低語。他能夠瞥見至福之境的光芒,或者因夢到永恒火焰而驚醒尖叫。如同範恩一樣,清教徒相信自己賦有末日的權杖。如同福利特伍德一樣,清教徒在靈魂的痛楚中呼喊著,因為上帝將自己的臉埋藏起來。不過,一旦清教徒在議席上就座或者佩戴刀劍走上戰場,靈魂中這些急風暴雨般的活動就會不留任何痕跡。除瞭他們那粗野的麵容,人們不會看到任何神的痕跡,除瞭他們呻吟和哀鳴般的歌聲,人們也聽不到任何彆的東西,於此,人們便會對他們施以嘲笑。不過,若是人們在議會大廳或者戰場上見到他們,就不再有任何嘲笑的理由瞭。這些狂熱分子給民事和軍事事務注入瞭冷靜的判斷以及目標上的堅定,以至於一些作傢覺得這同他們的宗教狂熱是不相容的,然而,這些事實上都是他們宗教狂熱的必然結果。正是他們在宗教情感上的這種烈度造就在所有其他問題上的寜靜。此種壓倒性的宗教情感馴服瞭憐憫和仇恨,也馴服瞭野心和恐懼。在此種宗教情感麵前,死亡喪失瞭恐怖,而愉悅也喪失瞭魅力。清教徒自有其歡笑和淚水,自有其狂喜和哀傷,不過這一切都並非為著塵世之事。熱情將他們鑄造成斯多亞主義者,蕩滌瞭他們內心所有的凡俗激情和偏見,使他們超拔於一切危險和敗壞因素之上。此種宗教熱忱有時候也會引導他們追尋不明智的目標,他他們絕不會選擇不明智的手段。清教徒穿行世間,如同阿特加爾爵士的鐵人塔魯斯一樣攜帶著鞭子,抽打壓迫者,將其踩在腳下,混跡於人群當中,但既不加入其中,也不分享人類自身的弱點而造就的命運,勞頓、快樂和痛苦對他們無所觸動,任何武器、任何險阻,也都不能徵服他們。”(麥考萊:《論彌爾頓》)
18和19世紀的現代權利論者極少願意迴顧往事,將權利同某種恐怖力量聯結起來,這一點麥考萊本人也承認:“大約是在四五十年前,考珀曾提起過,他不乾在自己的詩歌中提及約翰﹒班揚這個名字,他害怕因此招來嘲笑。我們覺得,對我們這些文雅的先輩來說,羅斯康芒勛爵的《譯詩論》和白金漢姆謝爾公爵的《詩論》,無疑要比這位補鍋匠牧師的寓言好上不知多少倍。無疑,我們生活在更好的時代;不過我們還是敢於這麼說,十七世紀後半葉的英格蘭不乏明敏之士,不過隻有兩顆心靈擁有非凡的想象能力。其一鑄造瞭《失樂園》,而另外一顆心靈則鑄就瞭《天路曆程》。”(麥考萊:《論班揚》)
雨果在19世紀資産階級溫柔鄉達到巔峰之時寫作瞭《悲慘世界》,在捲首的序言中對人間事實作瞭本質性的概括:“隻要由於法律和習俗的原因,在文明鼎盛的世界裏還存在社會的刑罰,人為地製造齣一座座地獄,更在神定的命運之外,再加上人間的命數……隻要在世界上還有無知和貧睏,像本書這樣性質的書都不會是無益的。”確切地說,隻要人們願意取消19世紀的那種區分善惡的穩定標準,接納剋羅齊或者雨果所陳述的人間事實,以積極態勢進入並守護一個嚴酷的世界,那麼《悲慘世界》的價值也就將是永恒的。
對於《悲慘世界》所說的這些話,也概括瞭本書將要對人權所說的一切。
本書在結構上分為“故事”部分和“理論”部分,之所以采取這種分裂式的兩元結構,是因為作者本人不相信理論對於故事的統攝能力,並且對此也不抱希望;隻有行動的人纔有能力和責任對世界的某一部分提齣解釋,而任何的解釋都將是暫時性的。
用户评价
《曆史上的人權》這本書,我之前在書店裏瞥見過,當時就被它樸實而又充滿力量的書名所吸引。人權,這個詞在當下頻繁齣現,但往往被局限於某個國傢、某個事件,或者某種特定的政治語境。我一直覺得,要真正理解人權,必須迴歸到它的曆史根源,去看看它究竟是如何一點點地從人類文明的土壤中生長齣來的。 這本書對我來說,最大的吸引力在於它承諾要展現的“曆史”維度。這意味著它不僅僅會講述現代意義上的人權宣言和法律條文,更會挖掘那些更古老、更隱晦的關於人類尊嚴和自由的早期思想和實踐。 我腦海中浮現齣一些畫麵:也許是古希臘城邦中,公民們圍坐在一起討論公共事務的場景,那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種早期參與權的體現?又或者是古羅馬時期,那些被視為“自由民”的人們所享有的權利,與奴隸又有著怎樣的鴻溝? 我特彆想知道,書中會不會涉及到那些在不同文化、不同宗教背景下,對於個體生命價值的認知。比如,佛教的慈悲為懷,基督教的“愛人如己”,這些宗教理念在多大程度上塑造瞭人類對同情、憐憫以及尊重他人生命的基本道德觀念? 這些古老的思想,雖然不直接冠以“人權”之名,但它們是否構成瞭後來人權概念的重要思想基石? 我也期待書中能夠揭示,人權觀念的每一次進步,往往伴隨著巨大的社會變革和劇烈的鬥爭。那些廢除奴隸製的運動,爭取投票權的工人運動,反對種族隔離的民權運動,這些激動人心的曆史事件,背後都蘊含著怎樣的思想力量和實踐行動? 此外,我還會關注書中對於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人權發展不平衡性的探討。為什麼有些地區很早就開始思考和實踐人權,而另一些地區卻長期停滯甚至倒退?這背後是否存在著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 我認為,一本好的曆史著作,不應該僅僅是史實的堆砌,更應該能夠引發讀者對當下現實的思考。《曆史上的人權》如果能做到這一點,那它將是一本非常有價值的書。它會讓我們明白,我們今天所享有的許多權利,是前人付齣巨大努力纔爭取來的,而這些權利也並非一勞永逸,需要我們繼續警惕和守護。 我很期待這本書能帶我踏上一場尋根之旅,去理解“人權”這個概念的漫長演進,以及它在人類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评分《曆史上的人權》這本書,我拿到手裏,便覺得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把鑰匙,能夠打開通往理解我們自身來龍去脈的大門。人權,這個現代社會的核心概念,我總覺得它不是憑空齣現的,而是根植於人類漫長的曆史經驗之中。這本書,恰恰給瞭我一個深入探索這個根源的機會。 我尤其好奇,書中會如何描繪那些古代文明中的“權利”概念,即使當時可能還沒有“人權”這個詞。比如,古希臘的城邦製度,雖然有著嚴格的公民劃分,但它所倡導的公民參與和言論自由(即使是有限的),是否可以看作是後來人權思想的重要鋪墊? 還有,書中對於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下,對於“平等”和“尊嚴”的早期理解是如何闡釋的?例如,佛教的“眾生平等”觀,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瞭人們對同情和憐憫的認知? 我非常期待書中能夠生動地展現那些在曆史上為爭取更廣泛的權利而進行的鬥爭。那些反對奴隸製度的運動,爭取勞動者基本權益的罷工,或者是在特定時期,女性為獲得受教育權和參政權而進行的抗爭,這些事件的背後,是否都蘊含著對“人”的根本尊嚴和價值的呼喚? 我也想瞭解,書中是如何分析那些導緻人權遭受普遍侵害的社會和政治根源的。例如,在一些專製王朝,君權神授的觀念是如何被用來強化統治,壓製個體聲音的?而在一些宗教狂熱時期,又是如何以教義之名,剝奪他人信仰自由的? 我認為,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在於梳理曆史事件,更在於它能夠引發我們對於“人”的意義和價值的深刻反思。它會讓我們明白,我們今天所擁有的許多權利,是經過瞭漫長而麯摺的演變過程,是前人不斷爭取和捍衛的結果。 我期待這本書能為我打開一扇曆史的窗口,讓我能夠更清晰地看到,人權是如何在人類文明的長河中,如同一條看不見的脈絡,不斷地滋養和塑造著我們。
评分《曆史上的人權》這本書,我拿在手裏,首先感覺到的是一種時間的厚重感。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很多權利,比如言論自由、信仰自由、人身不受侵犯等等,似乎是現代文明的必然産物,但它們究竟是如何從模糊的意識,一步步演變成如今被廣泛認可和保障的法律原則的?這本書,我想就是為解答這個問題而生的。 我特彆好奇,書中是否會觸及那些古老的法律文獻,比如《摩西五經》中的一些關於公平和憐憫的規定,或者《古蘭經》中強調的社群責任和博愛精神,這些宗教經典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瞭人們對個體價值和基本道德的認知? 還有,書中對於不同文明中“公民”概念的演變過程是如何描繪的?例如,古雅典的民主製度,雖然排斥瞭大量人口,但它所提齣的“公民可以參與政治決策”的理念,是否可以看作是後來政治權利早期的一種形態? 此外,我非常關注書中對於那些在曆史上為爭取更廣泛的權利而付齣的努力。那些反對奴隸製的運動,爭取工人權益的罷工,或者是在特定時期,女性為獲得受教育權和參政權而進行的抗爭,這些事件的背後,是否都蘊含著對“人”的尊嚴和價值的深刻呼喚? 我也想知道,書中是如何分析那些導緻人權遭受侵害的根源的。例如,等級製度、種族歧視、宗教迫害、集權統治等等,這些社會結構和政治體製,又是如何在曆史上不斷地壓製和扭麯人權的? 我認為,一本真正有價值的曆史書,不僅僅是記錄過去,更應該能夠啓迪當下。《曆史上的人權》如果能做到這一點,那它將是一本極其重要的讀物。它會讓我們明白,我們今天所擁有的權利,是前人無數次抗爭和犧牲換來的,而這些權利也並非一勞永逸,需要我們不斷地去警惕和捍衛。 我期待這本書能為我打開一扇窗,讓我能夠更清晰地看到人權在人類文明史上的漫長足跡,理解它在塑造我們今天社會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评分《曆史上的人權》這本書,我拿到手後,內心湧起一股莫名的期待。人權,這個詞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齣現的頻率極高,但對其深厚的曆史淵源和復雜的演變過程,我總覺得瞭解得不夠透徹。這本書,就像一位引路人,承諾帶我穿越時空的隧道,去探尋人權觀念的古老根基。 我特彆好奇,書中是否會深入探討那些早期人類社會的群體互動和道德規範。例如,在母係氏族或父係氏族社會中,是否存在一些不成文的規則,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瞭族群成員的基本生存權和尊嚴? 還有,書中對於不同文明在“自由”和“責任”這兩個概念上的早期理解是如何闡釋的?例如,古希臘哲學傢對城邦公民義務的強調,是否與後來對個人自由的追求存在某種張力? 我非常期待書中能夠生動地描繪那些在曆史上為爭取更廣泛的權利而進行的鬥爭。那些反對奴隸製度的努力,爭取勞動者基本權益的抗爭,或者是在特定時期,為瞭反對宗教壓迫而付齣的犧牲,這些事件背後,是否都蘊含著對“人”的根本尊嚴和價值的呼喚? 我也想瞭解,書中是如何分析那些導緻人權遭受普遍侵害的社會和政治根源的。例如,在一些古代帝國,君主的絕對權力是如何被構建和維係的?而在某些曆史時期,又是如何通過法律或習俗,將一部分人群邊緣化,剝奪其基本權利的? 我認為,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僅在於羅列史實,更在於它能夠引發我們對於“人”的本質以及社會公正的深刻思考。它會讓我們明白,我們今天所享有的許多權利,並非憑空而來,而是經過瞭漫長而艱辛的鬥爭,是前人不斷爭取和捍衛的成果。 我期待這本書能帶我進行一次深入的文明溯源之旅,去理解人權觀念是如何在人類曆史的長河中,如同一條看不見的河流,滋養著人類對自由、公正和尊嚴的永恒追求。
评分《曆史上的人權》這本書,我拿到手之後,第一感覺就是它的厚重感,不僅僅是紙張的厚度,更是它所承載的曆史分量。我一直覺得,我們現在對於“人權”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現代文明和法律體係之上的,但很少有人會去追溯它的源頭,去看看它究竟是如何從人類漫長曆史中一點點萌芽、發展、演變而來的。這本書,恰恰給瞭我一個這樣的機會。 我特彆好奇,書中會如何處理那些古老的文明,比如美索不達米亞、古埃及、古印度等,它們在那個時代,是否就已經有瞭對個體權利、對基本生存保障的樸素認知?雖然那個時代可能沒有“人權”這個詞,但是否存在著一些法律、習俗或者道德準則,在一定程度上限製瞭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絕對權力,或者為某些群體提供瞭基本的保護? 我也對書中對於不同文化背景下“自由”和“平等”概念的演變充滿瞭興趣。例如,在東西方不同的哲學傳統中,對於個體自由的理解是否存在著顯著的差異?那些古代的社會製度,如貴族製度、奴隸製度,又是如何定義和限製不同群體的權利的? 我很期待書中能夠生動地描繪那些在曆史上為爭取更廣泛的權利而進行的鬥爭。比如,那些早期爭取宗教自由的運動,或者是在特定時期,農民們為瞭抗議壓迫而發起的起義,這些事件背後所蘊含的對尊嚴和基本生存權的追求,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人權意識的早期體現? 我也關注書中對那些重要曆史文獻和思想傢的解讀。比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洛剋的《政府論》,這些經典著作是如何係統地闡述瞭天賦人權、人民主權等理念,並對後世産生瞭深遠的影響? 此外,我還會注意書中對於人權在不同社會變革中的作用的分析。無論是法國大革命還是美國獨立戰爭,人權思想在其中扮演瞭怎樣的角色?它又是如何成為推動社會進步和國傢製度變革的重要動力的? 我覺得,這本書不僅僅是記錄曆史,更是一種價值的傳承。它會讓我們明白,我們今天所享有的許多基本權利,不是憑空齣現的,而是經過瞭漫長而艱辛的鬥爭,凝聚瞭無數人的智慧和鮮血。 瞭解人權的曆史,就像是在理解人類文明前進的方嚮。它讓我們看到,人類在追求自身解放和尊嚴的道路上,有過輝煌,也有過黑暗,但最終,對美好和自由的嚮往,始終是驅動我們前行的強大力量。
评分《曆史上的人權》這本書,我拿到手裏之後,便迫不及待地想翻閱。我一直覺得,“人權”這個詞,雖然在當下被廣泛討論,但很多人對其曆史根源和發展脈絡並不十分清楚。它就像是我們生活中的空氣,無處不在,卻又常常被忽視其來之不易。這本書,似乎就是為瞭填補這一認知空白而誕生的。 我尤其期待書中能夠對那些早期文明中的“權利”概念進行深入挖掘。比如,在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中,雖然強調的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但這是否也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它試圖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規範,並為受害者提供某種程度的補償和保護? 還有,古希臘的民主製度,雖然其“公民”的範圍非常有限,但它所倡導的參與政治、錶達意見的權利,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後來人權思想的早期萌芽? 我也想知道,書中是否會探討那些在不同宗教和哲學體係中,對於“個體”價值的認識。比如,佛教的“眾生平等”,道傢的“道法自然”,這些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瞭人們對於同情、仁慈和尊重生命的認知? 此外,我非常關注書中對於那些被曆史進程所壓迫的群體,他們的聲音和抗爭是如何被記錄和解讀的。例如,奴隸起義,農民起義,或者是在特定社會中,婦女、少數民族為瞭爭取基本權利而進行的鬥爭,這些事件背後是否都蘊含著對“人”的尊嚴和價值的呼喚? 我也很想知道,書中對於“天賦人權”這一概念的演變過程是如何描繪的。從古希臘的自然法思想,到中世紀的宗教神學解釋,再到啓濛時代哲學傢們的係統闡述,這一概念是如何一步步確立其核心地位的? 我認為,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僅在於梳理曆史事件,更在於它能夠引發我們對於“人”的本質、對於社會公正的深刻反思。它會讓我們明白,人權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過瞭漫長而麯摺的演變過程,需要我們不斷地去理解、去爭取、去捍衛。 我期待這本書能帶我進行一次跨越時空的思想對話,去感受那些在曆史上為追求更美好的社會而奮鬥的人們的精神。它會讓我們的目光超越當下,去理解人權在人類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遠影響。
评分《曆史上的人權》這本書,我拿到後,第一感覺就是它的書名簡潔而有力,直擊核心。我總覺得,我們現在對於“人權”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現代社會的産物,但人類對自身價值和尊嚴的追求,絕對不是近幾百年的事情。這本書,似乎就是要帶我們去探尋這份古老而持久的渴望。 我特彆想知道,書中會如何描繪那些古代文明中,對於“人的價值”和“基本權利”的早期認識。比如,在古代中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種對人民基本生存和福祉的重視?又或者,在古印度,《吠陀》中關於“人生而有靈”的觀念,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瞭人們對生命尊嚴的認知? 我也對書中對於不同時代、不同社會背景下,個體權利是如何被定義和限製的描寫感到好奇。例如,封建社會中的等級製度,是如何劃分不同階層之間的權利義務?而在一些早期共和國中,公民權又是如何被界定,並排斥瞭哪些群體? 我非常期待書中能夠生動地展現那些在曆史上為爭取更廣泛的權利而進行的鬥爭。那些反對酷刑、爭取公正審判的努力,或者是在某些時期,奴隸為瞭獲得自由而進行的抗爭,這些事件是否都蘊含著對“人”的最基本尊嚴和權利的呼喚? 我也想瞭解,書中是如何分析那些導緻人權遭受普遍侵害的社會和政治根源的。例如,在一些專製王朝,君權神授的觀念是如何被用來強化統治,壓製個體聲音的?而在一些宗教狂熱時期,又是如何以教義之名,剝奪他人信仰自由的? 我認為,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在於梳理曆史事件,更在於它能夠引發我們對於“人”的意義和價值的深刻反思。它會讓我們明白,我們今天所享有的許多權利,是經過瞭漫長而麯摺的演變過程,是前人不斷爭取和捍衛的結果。 我期待這本書能為我打開一扇曆史的窗口,讓我能夠更清晰地看到,人權是如何在人類文明的長河中,如同一條看不見的脈絡,不斷地滋養和塑造著我們。
评分《曆史上的人權》這本書,我當初是抱著一種既好奇又有點忐忑的心情翻開的。人權這個概念,在現代社會我們耳熟能詳,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存在。但“曆史上的人權”?這聽起來就像是在追溯一個早已存在,但又不斷演變、充滿鬥爭的古老基因。我總覺得,它不僅僅是簡單地羅列一些曆史事件,而是要剝開層層曆史的迷霧,去探尋人類對自身價值和尊嚴最原始的渴望,以及這種渴望在不同文明、不同時代如何被壓製、被扭麯,又如何在星星之火中重燃。 我尤其期待書中能探討那些在曆史長河中被忽視的、微弱的聲音。那些被統治者、被剝削者,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他們是否也曾有過對自由、對公正的樸素認知?這些認知是如何在嚴酷的現實麵前掙紮求存,甚至默默地孕育齣反抗的種子? 我設想,書中可能會描繪那些宏大的哲學思辨,比如啓濛思想傢如何構建起人人生而平等的理論基石,又是如何將這些抽象的概念轉化為具體的社會變革的訴求。但同時,我也希望它能深入到最基層的生活,展現普通人在麵對不公時的無奈、抗爭,以及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樸素嚮往。 比如,那些為廢除奴隸製而奔走呼號的先驅者,他們的每一次呐喊,每一次不屈的抗爭,背後都承載著怎樣的勇氣和犧牲?那些爭取婦女選舉權的鬥士們,她們在那個男權至上的時代,是如何打破枷鎖,為後世女性爭取平等權利的? 我相信,這本書不會是一部枯燥的史書,而是一部充滿人性光輝和史詩般壯闊的敘事。它會讓我們重新審視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權利,瞭解它們是如何來之不易,又是如何需要我們去守護。它還會讓我們看到,人權的進步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充滿瞭麯摺、反復,甚至是血與淚的代價。 我期待這本書能帶我進行一次穿越時空的對話,與那些在曆史上為爭取人權而奮鬥的靈魂對話,去感受他們的痛苦,他們的希望,以及他們對人類文明進步的巨大貢獻。 畢竟,瞭解人權的曆史,就是瞭解人類如何一步步走嚮文明,走嚮尊重個體價值的漫漫徵程。
评分《曆史上的人權》這本書,我拿到手後,第一時間就被它寬廣的視角和深刻的標題所吸引。人權,這個詞在我們當下社會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存在,但深入思考,它究竟是如何一點點地從人類文明的土壤中生長齣來的?這本書,似乎就是要揭示這段不為人知的曆史。 我特彆好奇,書中是否會迴溯到那些遠古時代的道德準則和倫理觀念。例如,在早期部落社會,是否存在一些關於互助、公平分配的傳統,這些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人權意識的最初萌芽? 還有,書中對於不同文化背景下,對“個體”價值的早期認識是如何描繪的?比如,在古埃及的宗教信仰中,對來世的關注,是否也間接提升瞭對個體生命意義的認知? 我非常期待書中能夠生動地描繪那些在曆史上為爭取更廣泛的權利而進行的鬥爭。那些反對酷刑、爭取公正審判的努力,或者是在某些曆史時期,奴隸為瞭獲得自由而進行的抗爭,這些事件背後,是否都蘊含著對“人”的最基本尊嚴和權利的呼喚? 我也想瞭解,書中是如何分析那些導緻人權遭受普遍侵害的社會和政治根源的。例如,在一些古代王朝,君權神授的觀念是如何被用來強化統治,壓製個體聲音的?而在一些宗教狂熱時期,又是如何以教義之名,剝奪他人信仰自由的? 我認為,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僅在於梳理曆史事件,更在於它能夠引發我們對於“人”的意義和價值的深刻反思。它會讓我們明白,我們今天所擁有的許多權利,是經過瞭漫長而麯摺的演變過程,是前人不斷爭取和捍衛的結果。 我期待這本書能為我打開一扇曆史的窗口,讓我能夠更清晰地看到,人權是如何在人類文明的長河中,如同一條看不見的脈絡,不斷地滋養和塑造著我們。
评分拿到《曆史上的人權》這本書,我第一時間就被它標題的厚重感所吸引。說實話,我對曆史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但“人權”這個詞,總覺得離我們現代生活更近,也更具有現實意義。所以,當看到“曆史上的人權”這個組閤時,我腦海裏立刻湧現齣無數的疑問和想象。這本書會不會就像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講述人類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如何從濛昧走嚮文明,又如何在追求自身尊嚴和自由的道路上,經曆過無數次的跌宕起伏? 我非常好奇,在那些古老的文明中,是否已經孕育齣瞭最初的人權意識?比如,古希臘哲學傢對城邦公民權利的探討,是否可以視為人權萌芽的早期形態?而古羅馬法中對公民權的界定,又在多大程度上體現瞭對個體基本權益的保障? 我也特彆期待書中能夠深入挖掘那些被曆史塵埃掩埋的角落。那些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為追求公平正義而付齣的普通人的努力,他們可能沒有留下顯赫的名字,但他們的每一次抗爭,每一次對不公的抵製,都可能是人權發展的關鍵節點。 例如,農奴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他們是否有過對自身勞動的權利、對人身自由的渴望?在一些早期革命中,雖然可能打著不同的旗號,但其中是否蘊含著對壓迫的反抗,以及對基本生存權利的訴求? 我相信,這本書不會僅僅停留在宏大的敘事層麵,而是會通過鮮活的人物故事、具體的曆史事件,來展現人權概念的演變過程。它可能會剖析那些導緻人權踐踏的社會根源,比如等級製度、種族歧視、宗教迫害等等,讓我們深刻理解人權遭受威脅的普遍性和復雜性。 讀完這本書,我希望能夠對“人權”這個概念有一個更深刻、更全麵的理解。它不再隻是一個抽象的口號,而是凝聚著無數代人血淚和智慧的結晶。它提醒我們,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並非理所當然,而是需要我們不斷去爭取、去維護的。 此外,我也對書中對於不同文化背景下人權觀念的比較和分析抱有很大的期待。人類文明是多元的,人權觀念是否也存在著地域性和文化性的差異?這些差異是如何影響人權的發展軌跡的? 總結來說,這本書對我而言,是一次深入探究人類文明核心價值的旅程,一次對“人”的意義和尊嚴的哲學追問。
评分经典书籍,好好读读。
评分好书,趁活动买了,京东物流给力
评分Ok
评分物流迅速,品相完美,内容喜欢,价格实惠,值得购买
评分质量很好,优惠券购买的也很实惠,值得依赖,京东购物好喜欢
评分正版图书,价格优惠。
评分很不错,真的很好看,你现在。
评分质量很好,优惠券购买的也很实惠,值得依赖,京东购物好喜欢
评分给同学买的,她说没什么问题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