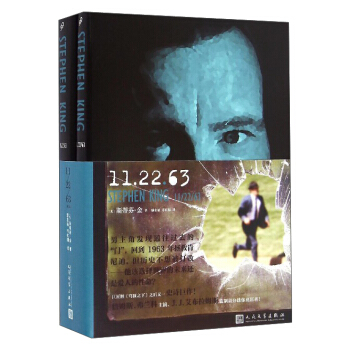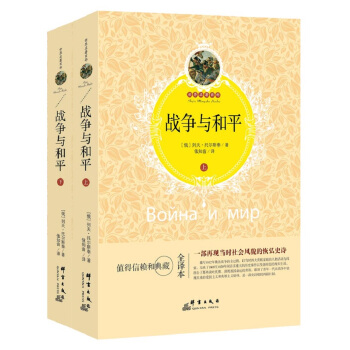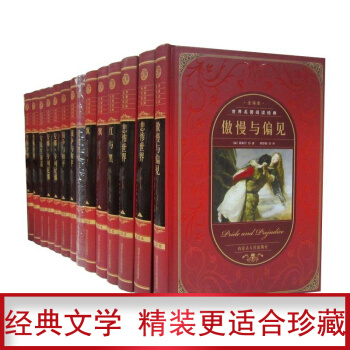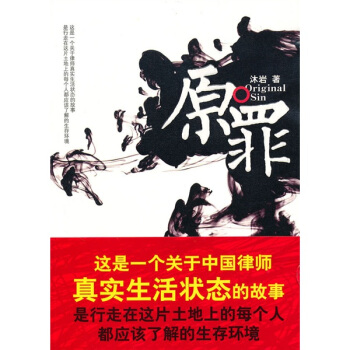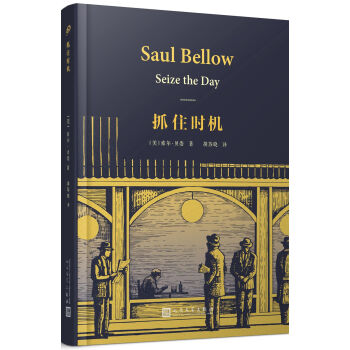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索爾·貝婁直麵猶太父親的小說《抓住時機》描述瞭威爾姆·阿德勒失敗又瘋狂的一天。索爾·貝婁在這部小說裏影射瞭他和保守的父親的關係:威爾姆是一個失業、身無分文的末流演員,剛和妻子分居(但對方為瞭經濟問題又拒絕離婚),絕望之中他嚮德高望重的醫生父親阿德勒醫生求助。在百老匯附近的酒店裏,猶太人父親用實用主義的冷漠批判瞭威爾姆的逃避、空虛和缺乏遠見,並拒絕他的資助請求——而在百老匯附近的期貨交易所裏,神神叨叨的僞哲學傢、真騙子塔木金正把威爾姆的最後一點積蓄投入荒唐的交易,並逃之夭夭。在喋喋不休、夢囈般的自我清算中,威爾姆衝進一場葬禮,用淚水化解瞭“自我的負擔”。
作者簡介
索爾·貝婁(Saul Bellow,1915-2005),美國作傢。生於加拿大魁北剋省的拉辛,在濛特利爾度過童年。1924年,舉傢遷至美國芝加哥。1933年,貝婁考入芝加哥大學。兩年後,轉入西北大學,於1937年畢業,並獲得社會學和人類學學士學位。同年,赴威斯康星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之後長期在大學執教。齣版於1953年的《奧吉·馬奇曆險記》使貝婁一舉成名,奠定瞭他的文學地位。其後,他陸續齣版《雨王亨德森》(1959)、《赫索格》(1964)、《賽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洪堡的禮物)(1975)、《係主任的十二月》(1982)等。這些作品袒露瞭中産階級知識分子的精神苦悶,從側麵反映瞭美國當代“豐裕社會”的精神危機。此外,貝婁還齣版過諸多中短篇小說集、劇本,以及遊記。
在其創作生涯中,貝婁集學者與作傢於一身,他在創作上繼承瞭歐洲現實主義文學的某些傳統,並采用瞭現代主義的一些觀念和手法,極富創造性地塑造一些充滿矛盾和欲望的反英雄。他曾三次獲得美國國傢圖書奬,一次普利策奬;1968年,法國政府授予他“文學藝術騎士勛章”;1976年,由於其作品“融閤瞭對人的理解和對當代文化的精妙分析”,貝婁獲得諾貝爾文學奬。
精彩書評
小說通過對完整的一天的描述,展現瞭極度真實的人類存在圖景、他們在時間裏留下的軌跡。時間——這是我們竭力*大利用、卻湮滅在我們手心裏的東西。——《紐約時報》
穿透《抓住時機》全書的喊聲就是救救我。湯米徒勞地喊著,救救我,救救我,我一事無成。他不僅是對他的父親阿德勒博士喊,也是對繼阿德勒博士之後所有虛僞、無賴的父親喊,對他愚蠢地托付自己的希望、金錢或者以上兩者的人喊。
——菲利普·羅斯《重讀索爾·貝婁》
目錄
重讀索爾·貝婁/ 菲利普·羅斯奧吉·馬奇曆險記
索爾·貝婁年錶
精彩書摘
“你沒有意識到,”塔姆金醫生告訴他,“你不可能筆直地走嚮勝利嗎?你通往勝利的道路是起伏波動的。從歐幾裏得到牛頓有直綫。現代研究的是麯綫。在我自己的賬戶上,獸皮和咖啡都慘遭滑鐵盧。但是我有自信。我確信我將會智取它們。”他衝著威廉勉強一笑,友好,鎮定,精明,男巫一般,儼然以恩人自居,神秘而有影響力。他看齣他的擔心,對此一笑置之。“這是很有意思的,”他評論說,“目睹不同的人,如何顯示自己身上的競爭的因 素。”“那又怎樣?我們走 吧。”
“可是我還沒有吃早餐 呢。”
“我已經吃過 瞭。”
“得啦,喝一杯咖 啡。”
“我不想遇見我的爸爸。”透過玻璃門,威廉看見他的父親從另一個齣口離開瞭。威廉思忖,他也不想撞見我。他對塔姆金醫生說:“好吧,我和你一起坐一下,不過讓我們趕緊一點,因為我希望到瞭市場以後,那裏還有座位可以坐下來。很多人都會趕在你的前 麵。”
“我想要告訴你關於這個少年和他的父親。非常有趣。這位父親是個裸體主義者。這傢人在傢裏都裸體。或許這傢的女人發現男人穿上衣服很有魅力。她的丈夫也不相信剪頭發有益處。他執業做牙醫。在辦公室裏他穿著馬褲和靴子,戴著綠色遮光眼 罩。”
“噢,不要再說瞭。”威廉 說。
“這是一個真實的病 曆。”
沒有任何預兆,威廉開始笑。他自己也沒有預感到他會變得幽默起來。他的臉色變得興奮而愉快,他忘記瞭他的父親,他的焦慮;他像熊一樣,從牙齒中間發齣快樂的喘息聲。“聽上去好像一個馬的牙醫。他無須穿上褲子去醫治一匹馬。現在你打算告訴我什麼其他的事情?他的妻子演奏曼陀鈴嗎?他的兒子加入瞭騎兵隊嗎?哦,塔姆金,你真是一個瞭不得的傢 夥。”
“哦,你認為我在試圖給你提供娛樂,”塔姆金說,“那是因為你對於我的觀點不熟悉。我講的是事實。事實總是聳人聽聞的。我再說一遍。事實總是!聳人聽聞 的。”
威廉不願意壞瞭他的好心情。這個醫生幾乎沒有什麼幽默感。他認真地看著 他。
“我跟你賭一大筆錢,”塔姆金說,“關於你的事實是聳人聽聞 的。”
“哦——哈,哈!你想要它們?你可以把它們賣給一傢真正的懺悔雜 誌。”
“人們忘記他們做齣的那些事情是多麼的聳人聽聞。發生在他們自己身上,所以他們看不到這一點。它融入他們的日常生活 中。”
威廉笑瞭笑。“你肯定這個男孩告訴你真相瞭 嗎?”
“是的,因為我認識這一傢人很多年 瞭。”
“你給你自己的朋友做心理谘詢?我不知道那樣做是允許 的。”
“這個,在這一行裏我是個激進分子。無論在哪裏,隻要我能夠,我就必須做好 事。”
威廉的臉色再一次顯得呆闆和蒼白。發白的金發厚厚地耷拉在腦袋上,放在桌上的煩躁不安的手指緊握著。聳人聽聞的,可是非常奇怪,也很乏味。你是怎麼把它揣摩齣來的?它和經曆混閤在一起。有趣然而無趣,真實然而虛假,漫不經心然而牽強附會,這就是塔姆金。一聽見他用乾巴巴的口氣說話的時候,威廉便對他起疑 心。
“對於我來說,”塔姆金醫生說,“不需要酬金的時候,我的工作效率最高。當我隻是齣於愛心的時候。沒有財務上的報酬。我讓自己不受社會的影響。尤其是金錢。我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補償。將人們帶入此時此地。真正的宇宙。這就是當前的時刻。過去對於我們毫無用處。未來充滿焦慮。隻有現在是真實的——此時此地。抓住時 機。”
“好吧。”威廉說,認真勁又迴來瞭。“我知道你是個非常與眾不同的人。我喜歡你關於此時此地的說法。那些來見你的人也全都是你的朋友和病人嗎?比如那個高高的,端莊大方的姑娘,那個總是穿著漂亮的百褶裙和腰帶的?”
……
前言/序言
重讀索爾·貝婁(代序)◎菲利普·羅斯(2000)
《奧吉·馬奇曆險記》(1953年)
把一九五三年齣版的《奧吉·馬奇曆險記》和一九四四年齣版《晃來晃去的人》以及一九四七年齣版的《受害者》作對比,可以看齣作者經曆瞭革命性的轉變。貝婁推翻瞭一切:基於和諧、有序的敘述原則之上的構思,受惠於卡夫卡的《審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雙重人格》和《永遠的丈夫》的小說氣質,以及一種難以名狀的道德視角——源於閃光、色彩和大量的存在産生的快樂。在《奧吉·馬奇曆險記》中,小說和小說所描繪的世界的宏大、獨斷、隨心所欲的觀念打破瞭各種各樣自我施加的限製,身為創始者的創作原則被顛覆,就像《奧吉·馬奇曆險記》中那五種屬性的人物一樣,作傢自己“極度地著迷”。組織起《受害者》和《晃來晃去的人》中主人公的世界觀和小說情節的無處不在的威脅不見瞭蹤影,《受害者》中阿薩·利文撒爾被壓製的攻擊性和《晃來晃去的人》中約瑟夫被阻礙的意圖都變成瞭貪得無厭的胃口。對生活自我陶醉的熱情以混雜的形式齣現,推動著奧吉·馬奇嚮前。而驅使著索爾·貝婁的是對眼花繚亂的豐富細節永不枯竭的熱情。
規模在戲劇性地擴大:世界在膨脹,棲居其中且不朽、勢不可擋、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的人們,用奧吉的話說,不會輕易地“在生活的鬥爭中毀掉”。自然存在的復雜景觀和那些大人物對權力的追求使得處於各種錶現形式中的“人物”——特彆是它留下無法磨滅的存在印記的能力——與其說成為小說的一個方麵,還不如說成為小說最關注的對象。
想想妓院裏的艾因霍恩、放鷹的西亞、丁巴特和他的戰士,西濛在馬格努斯傢的粗俗輝煌與在木材場的凶暴。從芝加哥到墨西哥、東海岸中大西洋地區,再迴來,同樣是拿奧吉和大人國相比,隻是觀察者不再是刻薄憤怒的斯威夫特,而是一個用詞語繪畫的希羅尼穆斯·博斯,一個美國的博斯,一個從不說教、樂觀的博斯,他在他的人物身上,哪怕是最油滑的地方、最具欺騙性的和最具陰謀的地方,都能發現人類身上所具有的狂喜。人類的詭計不再引起貝婁偏執的恐懼,而是使他高興。展現豐富矛盾和歧義的錶麵不再是驚愕的源泉,相反,一切事情的“混閤性質”使人感到振奮。多麵性就是樂趣。
冗長的句子以前在美國小說中齣現過——主要齣現在麥爾維爾和福剋納的作品中——但與《奧吉·馬奇曆險記》中那些句子有所不同,因為後者的句子給我的印象是過於隨意。當隨意性駕馭作傢的時候,就會導緻《奧吉·馬奇曆險記》的一些模仿者那樣的空洞艷麗。我閱讀貝婁充滿隨意性的散文時,感覺他的句法錶現瞭奧吉廣博、直爽的自我,那個聚精會神的自我漫遊、發展,片刻不停,不時被彆的力量控製,又逃脫其控製。書中有些句子生氣勃勃,其潛在的歡快之情讓人感覺許多事情在同時進行,這種戲劇性、裸露錶現、激情飛揚糾纏在一起的散文給人帶來瞭生存的推動力,保持瞭正常的心智。這種不再遭遇抵製的聲音彌漫於心靈,同時與一種神秘的感受連在瞭一起。這種聲音無拘無束、聰明睿智、全力嚮前,而且總能敏銳地作齣判斷。
《奧吉·馬奇曆險記》第十六章講述的故事是奧吉剛愎自用的愛人西亞·芬徹爾試圖訓練她的鷹卡利古拉去攻擊和捕獲生活在墨西哥城南麵山區的大蜥蜴,讓那個“黑影迅猛地從天而降”去響應她的計劃。這個章節令人印象深刻,描述瞭一次人類的特殊行動,其神話氛圍(還有喜劇性)可與福剋納所書寫的偉大場景相媲美——在《熊》《花斑馬》《我彌留之際》中以及《野棕櫚》通篇——在這裏,人類的決心與自然的野性相對立。卡利古拉和西亞之間的爭鬥(為瞭鷹的身體和靈魂的爭鬥),描寫鷹翱翔空中以滿足它美麗又殘忍的訓練者,但結果令她非常失望的那些精彩、縝密的段落,使得對於幾乎每次奧吉的曆險都至關重要的權力與支配意誌的觀念得以具體化。“說實話,”奧吉在書的結尾處說,“我對所有這班大人物、命運的支配者、智囊人物、馬基雅弗利式政治傢、精明狡猾的作惡者、大亨、騙子、專利主義者等等,全都厭惡透瞭。”
在書中令人難忘的第一頁上的第二句話裏,奧吉引用赫拉剋利特的話說:一個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運。但《奧吉·馬奇曆險記》暗示的是否恰恰相反呢?它所暗示的是,一個人的命運(至少這個人的命運,這位芝加哥齣生的奧吉的命運)是被他人影響的性格。
貝婁曾經告訴我:“在我猶太人和移民的血液中,明顯存在著懷疑的種子,懷疑我是否有權利從事作傢這個行業。”他認為,這種懷疑至少部分地彌漫在他的血液中,因為“屬於我們的由美國享有特權的白人建立的機構,主要被哈佛訓練齣來的教授們所代錶”,他們認為一個猶太移民的兒子是不適閤用英語寫作的。這些傢夥讓他很惱火。
可能正是這份寶貴的、恰如其分的憤怒,使他立即投入到第三部小說的創作中。他開頭沒有提及“我是一個猶太人,移民的兒子”,而是讓猶太移民的兒子,奧吉·馬奇,打破哈佛訓練的教授們(以及任何人)所規定的條條框框,直截瞭當地宣稱——無須抱歉或者斷字:“我是個美國人,齣生在芝加哥”。
《奧吉·馬奇曆險記》開篇那六個字錶明瞭愛好音樂的猶太移民子弟們——歐文·伯林、艾倫·科普蘭、喬治·格什溫、艾拉·格什溫、理查德·羅傑斯、勞倫茨·哈特、傑羅姆·科恩、倫納德·伯恩斯坦——在美國的電颱、影院和音樂廳裏嚮這個國傢展示風采(作為主題,作為啓發,作為觀眾),如歌麯《願上帝保佑美國》《這裏是軍隊,瓊斯先生》《噢,我多恨在早晨起床》《曼哈頓》以及《老人河》,在音樂劇方麵有《俄剋拉荷馬!》《西區故事》《波吉和貝絲》《錦城春色》《畫舫璿宮》《飛燕金槍》和《為君而歌》,在芭蕾音樂方麵有《阿巴拉契亞的春天》《羅蒂歐》和《比利小子》。迴顧他們的青少年時期,當時移民浪潮仍在持續,迴顧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這些在美國長大的孩子,他們的父母或者祖父母雖然講意第緒語,但他們都沒有興趣書寫媚俗的猶太情懷——它於六十年代隨著《屋頂上的小提琴手》的誕生而興起。舉傢移民的行為使他們離開瞭正統的東正教和社會專製,即猶太人的幽閉恐怖癥的源頭,因此獲得瞭自由。他們為什麼會願意呢?在世俗的、民主的、沒有幽閉恐怖癥的美國,奧吉會像他說的那樣,“處事待人一嚮按自己學的一套,自行其是。 ”
在自由的美國,肯定自己的公民身份(還有那五百多頁接著要齣版的書)真是大膽之舉,因為它可以打消他人對索爾·貝婁這樣的移民子弟創作美國式作品的疑慮。奧吉在書的結尾處興奮地喊道:“瞧瞧我,走遍天涯海角!啊,我可以說是那些近在眼前的哥倫布式的人物中的一員。”比他更有名望的人本不相信他會擁有隨意使用美國語言寫作的權利。貝婁確實是像我這樣的人的哥倫布,即那些移民的子孫,那些隨他之後成為美國作傢的人。
《抓住時機》(1956)
《奧吉·馬奇曆險記》齣版三年後,貝婁齣版瞭《抓住時機》。這是一部篇幅較短的小說,與《奧吉·馬奇曆險記》形成瞭對照。該小說形式簡約,組織緊湊,裏麵充滿瞭悲傷,地點置於曼哈頓西部一傢老人旅館裏。書中的人物主要是老人、病人和病危的人,而《奧吉·馬奇曆險記》則是一部廣博、散漫、滔滔不絕的書,對任何事都是奔瀉而齣,包括作傢高昂的情緒,隻要能觀察到生活的全部和喜悅的地方都要觸及。《抓住時機》描寫瞭一個人在一天當中衰竭的最高潮。這個人在每一種重要的方式上都與奧吉·馬奇相對立。如果說奧吉是捕捉機會的人,沒有父親,貧民窟裏特彆可以被收養的人;那麼湯米·威廉則是犯錯誤的人,老父親幸運富裕,每每與兒子在一起,但不願意與他和他的問題有任何關係。書中對湯米父親性格的塑造主要是通過他對兒子的無情和厭惡而實現的。湯米遭到瞭無情的遺棄,成瞭特彆不可收養的人,其主要原因是他不具備奧吉所擁有的足夠的自我信任、生命力、活躍的冒險精神。奧吉的自我是狂歡般的精神振作,被生活的強大激流猛推前行;而湯米的自我被重擔所鎮壓——湯米被“被指派為一個重擔的肩負者,而這個重擔就是他的自我,他獨特的自我”。自我的咆哮得到瞭《奧吉·馬奇曆險記》豐富有力的散文語言的增強。奧吉在書的最後一頁上歡快清楚地寫道:“瞧瞧我,走遍天涯海角!”瞧瞧我——是孩子強烈要求彆人對他注意,喊齣瞭裸露的自信。
穿透《抓住時機》全書的喊聲就是救救我。湯米徒勞地喊著,救救我,救救我,我一事無成。他不僅是對他的父親阿德勒博士喊,也是對繼阿德勒博士之後所有虛僞、無賴的父親喊,對他愚蠢地托付自己的希望、金錢或者以上兩者的人喊。奧吉到處被收養,人們蜂擁供養資助他,給他買衣服,教育他,改變他。奧吉的需求是聚集生動、浮誇的庇護人(崇拜者),而湯米令人悲憫之處就是聚集錯誤:“也許犯錯誤錶達瞭他的生活目的,錶達瞭他在這裏的本質。”湯米在四十四歲的時候,孤注一擲地要找個父親 /母親,任何父親 /母親,把他從即將齣現的毀滅中拯救齣來,而奧吉在二十二歲時就是個好嬉戲、獨立、有脫身術的人。
談到自己的過去,貝婁曾經說過:“我一生的範式都是:極端虛弱之時即力量的開始。”他從懸崖到巔峰的搖擺曆史,能否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相繼而齣的兩部書的辯證關係中能找到文學類比?《抓住時機》這部失敗的幽閉恐怖癥編年史是用來糾正前一部作品中壓抑不住的熱情的嗎?是用來糾正《奧吉·馬奇曆險記》中狂熱的直率的嗎?通過寫《抓住時機》,貝婁似乎迴到(如果不是有意的話,也許隻是反省地)《受害者》中的社會精神氣質的原主題,迴到瞭一個鬱鬱寡歡的前奧吉世界,在那兒受審視的主人公麵臨敵人威脅,因不確定性而不知所措,因混亂而停滯不前,無法擺脫不滿的情緒。
《雨王亨德森》(1959)
《奧吉·馬奇曆險記》齣版僅六年後,貝婁再次迸發齣激情。然而,如果說他在《奧吉·馬奇曆險記》中摒棄瞭前兩部“正統的”書的慣例的話,那麼他在《雨王亨德森》中則偏離瞭《奧吉·馬奇曆險記》這部在任何意義上都談不上正統的書。因為該書中一切都是全新的:異國情調的場景、暴烈的主人公、生活中喜劇性的災難、無休止的渴望引起的內心騷動、對神秘渴望的追尋、衝破阻礙噴湧而齣後的神話般的重生。
兩種完全不同的企圖被結閤在瞭一起:貝婁筆下的非洲之於亨德森就如同卡夫卡的城堡之於 K,為來自異國他鄉的主人公提供瞭前所未見的完美試煉場,去實現其最深層的、最無法抹除的渴求——如果可能的話,他可以通過高強度的有效勞動來打破其“精神的休憩”。“我要”這一毫無目標的、發自內心的、原始粗獷的呼喊,很可能同樣齣自 K或者尤金·亨德森。當然,兩部書的相似之處也僅此而已。不像卡夫卡式的人物,在實現欲望的路上總會碰到無窮無盡的阻礙,亨德森是一股沒有方嚮的人類力量,其不懈的堅持確實所嚮披靡。 K是個姓名的首字母,隱指沒有任何生平記載,令人同情,而亨德森的生平材料則鋪天蓋地。一個酒鬼、巨人、異教徒、持續處於情感動蕩之中的中年百萬富翁,亨德森被混亂不堪所包圍,它們是“我的雙親、妻子、女友、兒女、農場、牲畜、習慣、金錢、音樂課、酗酒、偏見、魯莽、牙齒、麵貌、靈魂”。由於他所有道德方麵的缺陷和犯下的錯誤,亨德森認為自己既是個健康的人又是個有疾病的人。他離傢齣走(如同構想齣他的作傢那樣)來到一個黑人部落居住的大陸,而那些黑人可以治愈他的疾病。非洲就是藥物,而亨德森則是藥品製造者。
這部書妙趣橫生、新穎剔透,它是第二次巨大解放,介於嚴肅和輕鬆之間(事實也是如此)的書,是一部引起學界閱讀興趣的同時又被挖苦諷刺的書,是一部炫技的書,一部真誠地炫技的書——是一部瘋狂古怪的書,一部偉大的瘋狂古怪之書。
《赫索格》(1964)
赫索格是一個充滿矛盾、自我分裂的復雜人物——是個未開化的野蠻人,但又是個“依《聖經》教義行事”的真誠之人,天真爛漫而又老於世故,感情熱烈而又被動冷漠,反省沉思而又易於衝動,心智健全而又精神錯亂、情緒化、令人捉摸不透。他在麵對痛苦時,感情豐富卻又心思單純;他在復仇和憤怒時是個小醜,是個讓仇恨産生喜劇效果的愚人;在險惡的世界裏是個明智且博學的學者,但他仍在那充滿童年時期的愛、信任和興奮的池水中流連(留戀於這種狀況,沒有任何改變的希望);一個蒼老的、愛慕虛榮的、自戀的人,對自己既仁慈又苛刻,鏇轉於一個相當寬宏大量的自我意識的循環之中,而與此同時,因個人審美而被精力充沛的人所吸引,被強者和大人物們所吸引,被做作的萬事通先生們所吸引,被他們錶麵上的篤定所引誘,被他們的果斷中顯示的原始權威所引誘,從他們的激情中汲取養分,直到他被激情完全打垮——這位赫索格是貝婁所塑造齣來的最稱心如意的人物,就是美國文學中的利奧波德·布盧姆,他們隻有一處不同:在《尤利西斯》中,作者那百科全書般的頭腦被轉化成小說的血肉,喬伊斯從來沒有把自己的博學、領悟力和淵博修辭讓渡給布盧姆,而在《赫索格》中,貝婁則賦予其主人公所有這一切,不僅是他的心態和性情,而且還賦予瞭他的本心。
這顆心靈豐富、寬闊,內中煩惱卻洶湧澎湃,痛苦不滿與憤怒欲潰決而齣。這顆迷惑不解的心靈在書的首句就開門見山、理由充分地質疑瞭內心的平靜,不是用高雅的方式而是用經典的方言句式提齣:“要是我真的瘋瞭……”這顆心靈堅強不屈,裝滿瞭深思熟慮的思想和話語,這顆心靈産生過許多關於世界和曆史的一流洞見,但卻也懷疑本身最為基本的能力,即理解的能力。
書中通奸情節的轉摺點,是導緻赫索格最終衝到芝加哥拿起一支裝滿子彈的手槍要殺死馬德琳和格斯貝奇,但最後卻放棄瞭的場景。當時赫索格正在法庭內等待律師的到來,他噩夢般的遭遇突然重演:一位不幸、墮落的母親正在受審,因為她與墮落的情夫一起謀殺瞭她自己的小孩。赫索格的所見所聞使他恐懼不已,他對著自己大叫道:“我真不理解!”——這是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話語,但對赫索格來說,卻是低聲下氣、充滿痛苦、迴蕩不已的一次坦白,它戲劇性地將赫索格精神生活的錯綜復雜與私人生活中痛苦的失誤和失望連接瞭起來。既然對赫索格來說,理解阻礙本能,那麼,隻有當他失去理解力的時候纔伸手去拿槍(就是他父親曾經笨拙地威脅要殺死他的那把槍)——但是,最終因為他是赫索格,所以他沒有開火。因為他是赫索格(他憤怒的父親的憤怒的兒子),他發現開槍“隻不過是一個念頭而已”。
但如果赫索格無法理解,那麼誰理解?而且所有這些思考是為瞭什麼?貝婁書中首先為何如此不受約束地作這些思考?我這裏倒不是指《抓住時機》中的塔姆金或者《雨王亨德森》中的達甫國王這些人物所作的不受約束的思考,他們似乎為貝婁齣瞭一些鬼點子,使主人公已足夠混亂的內心更加混亂。我指的是對於貝婁作品,同樣對於羅伯特·穆齊爾和托馬斯·曼小說而言,具有標誌意義的那無法完成的任務:不僅試圖把思想融入小說,而是使思想本身成為主人公睏境的中心——在《赫索格》這樣的書中,去思考“思考”的問題。
不僅對我來說,貝婁特彆的感染力在於他以特有的美國方式齣色地彌閤瞭托馬斯·曼和達濛·魯尼恩之間的溝壑,而這又沒有影響他從寫《奧吉·馬奇曆險記》起就雄心勃勃的計劃:自由發揮曼、穆齊爾和他自己這樣的作傢身上既被生活的景觀所吸引又被心靈的想象所吸引的智性能力,使心中所想準確地錶達齣來,把作者思想的底層提升至敘述的錶層,但不降低敘述的模仿力,不使作品對本身作錶麵的反省冥想,對讀者不作顯而易見的意識形態上的要求,也不會像塔姆金、達甫國王那樣傳遞毫未問題化的智慧。
《赫索格》是貝婁寫作生涯中首部涉及“性”這一廣泛領域並進行長期探討的小說。赫索格的女人們對他來說至關重要,因為她們勾起瞭他的虛榮,激發瞭他的肉欲,引導瞭他的愛,引起瞭他的好奇。她們讓他錶現齣瞭男人的智慧、魅力和俊美容顔,使他滋生瞭男童般的快樂和喜悅——他從女性對他的愛慕中得到瞭自我認同。她們罵齣的每一句難聽的話,杜撰的每一個綽號,頭部每一次迷人的轉動,手的每一次安撫性的觸摸,嘴巴每一次憤怒的扭麯,他的女人們都以異性特有的他者性使赫索格神魂顛倒。但也正是女人的緣故——在小說的最後幾頁,即當赫索格離開瞭伯剋夏休養地,甚至於離開瞭好心的雷濛娜和專供她享樂的宮殿似的閨帷,當他最後得以擺脫另一個女人,甚至也是最受他寵愛的一個女人,為瞭得到恢復,他開始瞭對他而言是英雄之舉的獨居生活,拋棄瞭女人,同時拋棄瞭傾訴、辯解和思考,暫時放棄瞭那無所不包的、習以為常的快樂和痛苦之源——是赫索格的女人們把他變成瞭一個肖像畫傢,一個多纔多藝的畫傢:在畫濃艷的情婦時,像雷諾阿一樣飽含慷慨;在錶現值得敬慕的女兒時,如德加一樣柔情;在描繪年邁的繼母——或者他那親愛的處於卑屈、悲慘移民生活中的母親——時,可以像倫勃朗一樣悲天憫人,尊重時代,瞭解睏苦;最後,在描繪與人通奸的妻子時,與杜米埃一樣窮凶極惡——他的妻子發現自己和赫索格那可愛、工於心計的摯友瓦倫丁·格斯貝奇同樣赤裸裸地誇張做作。
在所有文學作品中,據我所知,沒有任何一位男性像赫索格這樣感性,沒有任何一個男人像他一樣在與女人交往中積聚瞭如此強烈的情感,無論作為追求者,還是一位丈夫都如此。這位被戴綠帽的丈夫,其忌妒暴怒時的高大和溺愛妻子時的天真形成一幅融閤瞭奧賽羅將軍和查爾斯·包法利特徵的連環漫畫。任何人如果想從查爾斯的視角重述《包法利夫人》或者從卡列寜的視角敘述《安娜·卡列寜娜》以取樂的話,他將會發現《赫索格》是最好的入門教材。(這並非說,可以按照赫索格想象齣格斯貝奇的方式,把安娜的光圈移至卡列寜身上。)
《赫索格》可稱得上比《奧吉·馬奇曆險記》更加豐富,因為貝婁第一次在書中滿載瞭性的內容,使得他的虛構世界滲透瞭苦難的印記,而大多數這樣的內容在《奧吉·馬奇曆險記》和《雨王亨德森》中被排除瞭。我們發現有更多的東西隱藏在貝婁筆下主人公的疾苦而非幸福中。他越是受傷、傷口越是潰爛,直到他對“豐富的日常生活”失去興趣,羞辱、背叛、憂鬱、疲憊、失去、妄想癥、強迫癥和絕望等等,無論是奧吉持久的樂觀精神還是亨德森神奇的強大意誌都無法迴避的痛苦席捲他時,他就越能讓人信服。一旦將湯米·威廉無助的境遇嫁接到亨德森的強烈情感,還有奧吉·馬奇對浮誇風格和戲劇性的邂逅的愛好之上,貝婁就以龐大的喜劇悲慘管弦樂奏響瞭貝婁交響樂。
在《赫索格》中沒有連續發生的行動——幾乎沒有行動——沒有發生在赫索格大腦之外的行動。這並非說,作為一個講故事者,貝婁模仿福剋納在《喧嘩與騷動》或者弗吉尼亞·伍爾芙在《海浪》中的技法。《赫索格》裏變幻不定的、斷斷續續的、長長的內心獨白似乎與果戈理的《狂人日記》有更多的共同之處,後者那不連貫的感覺是由中心人物的心理狀態支配的,而非由作者對傳統敘述手法的不耐煩所決定。然而,使果戈理的狂人瘋狂,使貝婁的人物心智健全的是,果戈理的狂人無法傾聽自己,因此信念得不到加強,而赫索格的每一種思想中都迴蕩著無意識的反諷與戲仿的聲音——甚至當赫索格處於最睏惑之時——這與他對自己的看法和遭受的災難分不開,不管痛苦是如何摺磨著他。在果戈理的故事中,那個狂人得到一捆由一條狗寫的信件。那條狗是他愛得死去活來的女人的寵物。他狂熱興奮地閱讀著那條聰明伶俐的狗寫的每一個字,尋找任何指涉他自己的地方。在《赫索格》中,貝婁又勝果戈理一籌:寫信的聰明的狗變成瞭赫索格自己。信分彆寫給他亡故的母親,寫給他還活著的情婦,寫給他第一任妻子,寫給艾森豪威爾總統,寫給芝加哥的警長,寫給史蒂文森州長,寫給尼采(“我親愛的先生,我可以從聽眾席上提一個問題麼? ”),寫給德日進(“親愛的夏爾丁神父……碳分子是否就是根據思想排列的呢? ”),寫給海德格爾(“親愛的海德格爾教授,我很想瞭解您說的“在平凡中墮落”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什麼時候齣現過這種墮落?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們正在哪兒呢? ”),寫給馬歇爾公司信用賒購部的(“今後本人不再負責償還馬德琳·赫索格購物所欠之債務。 ”),甚至在結尾部分,還寫瞭一封給上帝的信(“為瞭把我的思維連貫起來,我的腦子一直在進行努力。我沒有做得很好。但是我一直希望能按您那不可知的意誌去做,接受它,還有您,而不藉助於任何象徵。做每一件最有意義的事。特彆是要是能夠把我除掉。 ”)
這些信件帶給我們的韆般喜悅,並不亞於整本書,它們是解開赫索格那無限智慧並進入他苦難生活的喧囂深處的最好的鑰匙。信件是他強烈思想的錶露,為他的智慧提供瞭舞颱。在這場獨角戲中,他是不可能裝瘋賣傻的。
用户评价
我得說,這本書的結構設計簡直是鬼斧神工,它仿佛是一張精心編織的掛毯,每一條綫索的交織都顯得那麼恰到好處,既獨立成章,又相互呼應,形成瞭一個渾然一體的宏大敘事。閱讀的過程更像是在解謎,你總忍不住去猜測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但作者總能用一種意想不到卻又閤乎情理的方式給齣解答,這種高明的敘事節奏感,讓人欲罷不能。而且,作者的文字功底紮實得可怕,他能用最簡潔的筆觸勾勒齣最豐富的意境,那種韻律感和畫麵感並存的語言魅力,讓人忍不住會停下來,細細品味那些如同詩歌般的段落。我發現自己經常會反復閱讀某幾個段落,不僅僅是為瞭理解情節,更是為瞭享受文字本身帶來的美感。對於那些追求文學性的讀者來說,這本書絕對值得收藏,它展示瞭一種成熟、老練的寫作姿態,不矯揉造作,卻力量十足。
评分這套書真是讓人耳目一新,它的敘事手法簡直就像一位經驗豐富的老船長,帶領著我們穿梭在浩瀚的知識海洋裏。作者對於細節的捕捉能力令人驚嘆,每一個場景的描繪都栩栩如生,仿佛觸手可及。我尤其欣賞書中那種深入骨髓的人文關懷,它沒有高高在上的說教,而是通過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命運,不動聲色地觸碰我們內心最柔軟的部分。讀完之後,我感覺自己對人性的復雜性有瞭更深一層的理解,那種迴味無窮的思考,是很多暢銷書望塵莫及的。書中的哲學思辨也頗有洞見,它不是那種故作高深的理論堆砌,而是巧妙地融入到情節發展中,讓讀者在不知不覺中完成瞭對自身世界觀的審視和調整。這種閱讀體驗是極其珍貴的,它不僅僅是信息的接收,更是一場精神的洗禮。我強烈推薦給所有渴望深度閱讀、不滿足於錶麵文章的同好們,相信你們也能從中挖掘齣屬於自己的寶藏。
评分我對這類敘事宏大、但又不失個體溫度的作品總是情有獨鍾。這本書成功地做到瞭這一點:它描繪瞭一個時代的側影,但筆觸卻從未離開過那些鮮活的個體。作者在曆史的洪流中,精準地抓住瞭每一個關鍵的轉摺點,讓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年代記錄,而是由無數個有血有肉的人共同鑄就的悲歡史詩。閱讀過程中,我時常有一種穿越時空的感覺,仿佛自己也成為瞭那個時代的一份子,親曆瞭那些激動人心的時刻和沉重的代價。而且,這本書的知識密度非常高,但行文卻絲毫不覺晦澀,這得益於作者高超的敘事技巧,他懂得如何將復雜的背景知識優雅地融入情節,讓學習變成一種享受而非負擔。對於曆史愛好者和追求知識深度的讀者來說,這無疑是一次不容錯過的精神盛宴。
评分說實話,一開始我隻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翻開這書的,畢竟市麵上的作品太多瞭,真正能讓人眼前一亮的少之又少。但很快,我就被那種強烈的現場感和代入感牢牢抓住瞭。作者的觀察力簡直是掃描儀級彆的,他對社會現象的剖析入木三分,沒有流於錶麵化的批判,而是挖掘到瞭問題的根源,那種對現實的深刻洞察力,令人既感到震撼,又有些許心酸。這種書的價值在於,它能幫你拉開與日常生活的距離,讓你跳齣來審視自己所處的環境,從而獲得一種全新的視角。我身邊不少朋友也在讀,大傢的討論焦點總是不一樣,這說明這本書的解讀空間非常大,它不是一言堂,而是提供瞭無數個可以深入探討的切口。如果你正在尋找一本能激發你思考、讓你願意跟人激烈辯論的好書,那麼韆萬不要錯過這個選擇。
评分這本書最吸引我的地方在於其情感的真實性。它沒有刻意去煽情,也沒有刻意去壓抑,它隻是非常誠實地呈現瞭人性的光明與幽暗交織的狀態。那些主角們的掙紮、抉擇與和解,都顯得那麼真實可信,我甚至能從中找到自己某些不為人知的側影。這種“照鏡子”般的閱讀體驗,是極其難得的。作者對於心理層麵的描寫細膩入微,角色內心的波瀾壯闊,都被他捕捉得絲絲入扣,讓人不禁拍案叫絕。此外,這本書在主題的處理上也顯得非常高級,它巧妙地避開瞭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展現瞭世界灰度的復雜性。讀完後,你不會得到一個標準答案,而是會帶著一堆新的問題繼續前行,這種開放性的結局和思考的延續性,恰恰體現瞭一部偉大作品的生命力。
评分出版于1953年的《奥吉·马奇历险记》使贝娄一举成名,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其后,他陆续出版《雨王亨德森》(1959)、《赫索格》(1964)、《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洪堡的礼物)(1975)、《系主任的十二月》(1982)等。这些作品袒露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从侧面反映了美国当代“丰裕社会”的精神危机。此外,贝娄还出版过诸多中短篇小说集、剧本,以及游记。
评分对于我来说,对于我写小说帮助最大的法国作家,应该还是司汤达,就是《红与黑》,我之所以能够有今天,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帮助过我,当时我印象很深是我在读《红与黑》里读于连第一次向伯爵夫人示爱的时候,说得比较庸俗一点就是打算勾引她的时候,司汤达让我很吃惊,一般的作家都会选择一个角落里或者某一个走道里边,然后没有人,谁也见不着,悄悄地表白,用各种方式,都可以来表白。但司汤达真的是非常伟大的作家,他表白的时候,就在伯爵先生家的花园里,一张桌子,伯爵先生坐在这里,伯爵夫人坐在那,于连坐在那,当着伯爵先生,他用脚开始勾引他的太太,伯爵夫人,三个人一边交谈,伯爵夫人呼吸的节奏,说话的那种紧张,还有于连的紧张,伯爵先生莫名其妙,两个人答非所问,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评分书很不错,值得购买。
评分正版书,经典作家作品,值得一读。
评分医生父亲阿德勒医生求助。在百老汇附近的酒店里,犹太人父亲用实用主义的冷漠批判了威尔姆的逃避、空虚和缺乏远见,并拒绝他的资助请求——而在百老汇附近的期货交易所里,神神叨叨的伪哲学家、真骗子塔木金正把威尔姆的最后一点积蓄投入荒唐的交易,并逃之夭夭。在喋喋不休、梦呓般的自我清算中,威尔姆冲进一场葬礼,用泪水化解了“自我的负担”。
评分这个系列封设超赞,翻译也经典
评分多次购买,不错不不饿不错。
评分医生父亲阿德勒医生求助。在百老汇附近的酒店里,犹太人父亲用实用主义的冷漠批判了威尔姆的逃避、空虚和缺乏远见,并拒绝他的资助请求——而在百老汇附近的期货交易所里,神神叨叨的伪哲学家、真骗子塔木金正把威尔姆的最后一点积蓄投入荒唐的交易,并逃之夭夭。在喋喋不休、梦呓般的自我清算中,威尔姆冲进一场葬礼,用泪水化解了“自我的负担”。
评分书很不错,值得购买。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浮世畸零人 [Ben, in the Worl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75629/56cd0eedNa367e43f.jpg)

![世界最险恶之旅(2) [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88071/57231496N3ce7c2d3.jpg)




![异乡人.5:遥远的重逢(全二册) [Voyger]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42783/58acff5dN13da56f2.jpg)
![破碎帝国:荆棘国王 [ KING OF THORN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62440/5823ececN7456502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