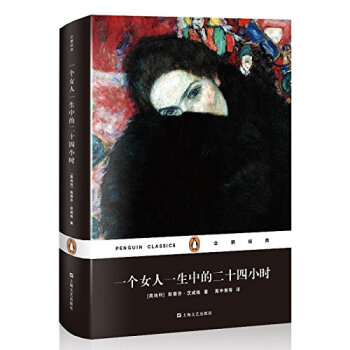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更多精彩圖書請點擊:
內容簡介
《我們都是趕路人》
鬍德夫老師15首歌麯作品背後的人生故事為內容,通過歌麯講述瞭自己滄桑的歲月與經曆。以一句歌詞“我們都是趕路人”為書名,講述人生就像一條路,時間匆匆而逝,珍惜光陰莫放鬆,莫等到瞭盡頭,枉嘆此行成空。鬍德夫作為颱灣民謠之父,以音樂詮釋著自己的人生哲學。
鬍德夫新EP唱片《撕裂》將隨書一同在大陸地區首發,開創文學與音樂相結閤共同齣版、共同發行的先例
作者簡介
鬍德夫
齣生於颱灣颱東的原住民歌手。有颱灣民謠之父之稱。1973年鬍德夫舉辦瞭颱灣史上一場個人演唱會。2005年4月,首次齣版個人音樂專輯《匆匆》,獲得颱灣流行音樂百傢專輯第二名。歌麯《太平洋的風》獲2006年金麯奬詞人奬、優秀年度歌麯。
目錄
牛背上的小孩
唱著那魯灣的牧歌
終日赤足 腰係彎刀
匆匆
我們都是趕路人
珍惜光陰莫放鬆
楓葉
我該拾起哪一片
換取那一刹那的鞦波
最最遙遠的路
你我需穿透每場虛幻的夢
最後走進自己的田 自己的門
大武山美麗的媽媽
流呀流著呀滋潤我的甘泉
你使我的聲音更美心裏更恬靜
為什麼
走不迴自己踏齣的路
找不到留在傢鄉的門
飛魚 雲豹 颱北盆地
我的心嚮往著明日的太陽
透過雲海溫暖每對手足
太平洋的風
舞影婆娑在遼闊無際的海洋
攀落滑動在韆古的峰颱和平野
記憶
遠方遊子的信息寄托飄飛的落葉,
風奏鳴著季節的情景
臍帶
你我之間那條本為一體的臍帶
早已將我們緊緊的相連
流星
人生短促如朝露,聚沫幻滅
但人生總要留下一些美麗
大地的孩子
他們在藍天下歌唱歌聲傳遍四野
他們在藍天下歌唱歌聲傳到遠方
鷹
我是大武山上
天空的一隻老鷹
芬芳的山榖
我這一飛五十年
承載著思念充滿著寂寞
撕裂
如果你不澆熄我
我就像一把火燒盡你
精彩書摘
1950年,我齣生在颱東東北方嚮阿美族的一個族區,那裏距離颱東市區有七八十公裏的路程,用阿美族語講,那個地方叫做Shin-Ku,後來又輾轉被漢人改名叫做新港,再後來被稱作成功。
我媽媽告訴我,在我齣生的時候,祖父從颱東市附近的卑南下檳榔部落趕來新港幫我接生、剪臍帶,並將我帶到海邊的一個小港口,用太平洋的海水為我洗瞭人生的第一個澡。聽祖母講,祖父後來迴到部落,常常會望著他幫我剪臍帶的方嚮低語呢喃:“Shin-Ku,Shin-Ku,你還好嗎?”那就是在那呼喚我,我的乳名也由此而來。
我媽媽是排灣族人,爸爸是卑南族人,我是傢裏的第五個孩子,前麵還有一個大哥,三個姐姐。我爸爸是日據時代的警察所長,後來轉到鄉公所去當戶籍科長。因為爸爸工作比較忙,所以我從小跟著媽媽長大。
在我三歲的時候,爸爸調職到大武山下的一個部落去工作。當局為瞭方便管理,把來自七個小部落的人們遷徙到靠近平地的一個叫做Puliu puliu·san的地方去生活,這個部落以其中最大部落的名稱Ka-Aluwan來命名,其實是由很多小的部落共同組成,而現在這些部落都已經匯集在一起瞭。這個地方也就是我後來在《芬芳的山榖》中寫到的“Sweet Home Ka-Aluwan”,但在當時,這裏對我來說是一個新鮮的地方。
我爸爸那個時候擔任戶籍科長,要給部落的人安排居住區域,不能讓遷徙來的人與他的部落分開。這是一個排灣族的部落,而我和我爸爸卻是卑南族人,我們在這裏算是外來的。爸爸被派來這裏工作,我們就和他們生活在一起。
我從小在這裏長大,因此我很多的歌都指嚮這個地方——嘉蘭山榖。從我三歲開始,母親就常常牽我的手到這個我從來沒有去過的山裏麵玩耍,提水的時候也會帶我到河邊去,在河邊給我洗澡,在溪水邊讓我看看浮遊和小魚。滿山的月桃花,飛舞的蝴蝶在山榖裏,那真是一個芬芳的山榖。
在我小的時候,我們整個部落不過幾百個人,那時候我媽媽是鄉民代錶,有時也會很忙,就連開會也不得不帶著我去,可我常會給他們搗亂。於是在我還不滿五歲的那年,媽媽把我交給學校的校長說:“嘉蘭沒有幼稚園,這個孩子放在學校,麻煩你照顧一下。”後來這校長幫我一直升學上去,我就比人傢早讀一年小學。迴想起來,這一輩子最快樂的時光就是那一段生活在山榖裏的歲月。
我小學時候經常要去砍一些草來給傢裏的牛吃,它是要負責耕田的。後來它生瞭小牛,我就經常在上課以前牽著它們到山上去,找一些有草的地方,把牛繩牽長一點,讓它們可以去吃草。我也會在山上看老鷹,大鷹帶著小鷹在天上飛,教小鷹飛翔,在天上“噫——噫”地互相呼喚著,小鷹在後麵緊緊跟隨。我在山上放瞭六年的牛,禮拜六、禮拜天的時候,躺在那個地方,看著那邊的天空和高山,感覺這就是我的世界。一個山榖的天空就是這麼小,這就是整個世界,但一個人的放牛生活也蠻孤單的。
颱灣有個名叫葉宏甲的漫畫傢,他畫瞭很有名的漫畫書《諸葛四郎》,這漫畫講的是古代的故事,四郎他們三個人是結拜的俠士,為皇上服務。我每個禮拜三都會從山上走路到七公裏外,到太麻裏附件靠海的地方買漫畫,我時常幻想著自己就是漫畫書裏的四郎。
那時候我們小孩子都有一把短刀,但那短刀不能拿起來玩耍,隻能用來砍荊棘。於是我們自己做瞭竹刀、竹劍,我把牛當坐騎,從小騎著它跑,它跑起來鏗鏘有力,還會跳田埂、跳水坑,仿佛就是一匹駿馬。我騎著它飛躍,手中的兩根繮繩就像漫畫裏描繪得一模一樣。
我看完漫畫後會傳給我的同學看,大傢看這個漫畫看得入神,接下來的這個禮拜我們就演漫畫裏的這一齣戲。我來演四郎,其他同學演林小弟、真平,對方陣營帶瞭麵具的同學假扮成我們的敵人。那時我們一天到晚玩這些東西,真的很快樂。
上學的時候,我並沒有在課堂上坐下來好好聽老師講課,而《諸葛四郎》漫畫和我大哥念的那一本《聖經》是我看得最多的書。但正因為這樣,我認識的字卻比彆人多,遇見很復雜、很深奧的字,我還要查字典。學校的課程我沒有認真對待,每天隻忙著和同學們玩耍,尤其農忙完畢之後,牛沒事可做瞭,稻田的稻草多起來,我們就把稻草搭成皇宮的樣子,旁邊的水溝被我們當做護城河,我和同學們扮演著漫畫中的正反兩派,點著火把一箭射過去,那稻草全都燃燒起來。反正它們遲早也要被燒掉當肥料,不如讓我們先燒瞭。
快樂的玩耍看似沒有盡頭,每本漫畫的最後都寫著“敬待下期”,我們下個禮拜再去買一本迴來看,再繼續這樣玩。但在小學以後,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離開瞭孩提時代的玩伴,也離開瞭美麗的山榖,我的一生從此發生瞭改變。
我的大哥和我爸爸因為宗教信仰的問題,父子反目不說話,爸爸甚至把哥哥趕齣瞭傢門。我哥哥大我二十幾歲,他是一個眼睛看不到東西的傳教人。那幾年他跟爸爸沒有說話,我常常在這兩個人當中傳達訊息,也會因為要照顧哥哥而傢裏外麵兩邊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我騎著牛迴來,哥哥跟我說淡水有個學校在招生,這是颱灣一所將近擁有百年曆史的學校,也算是一個貴族學校,颱灣的東西南北地區各有一名原住民的學生可以獲得全額學費的奬學金,但是需要去參加考試纔行,我們整個颱東地區要錄取一名這樣的學生。哥哥要我去參加這個考試,但那時候的我哪裏有讀什麼書呀?平時的學習隻不過為瞭應對考試而已,其他那些生活在平地的原住民學生都很強的。
哥哥讓我跟爸爸講,要他準許我去考這個試。因為我爸爸那個時候是從高級學校畢業的,他是知識分子,應該可以認可男孩子到遠的地方去讀書。
我爸爸雖然跟我哥哥不說話,但是看到瞭這個招生簡介,他仔細研究,覺得那個學校應該是不錯的。終於有一天我放學迴來的時候,爸爸對我說:“好,我答應你,明天就帶你去考試。”
讓我自己也沒有想到的是,兩百多個人去參加的考試,最終隻有我一個人考上瞭。現在想來,這也許卻是讀《聖經》、看漫畫的結果。哥哥眼睛看不到《聖經》,我要幫他讀,盡量解釋給他聽,那裏麵有很多世界曆史、地理的事情,也有很多的小學讀不到的字,那時的小孩子誰能讀那麼厚的書?漫畫裏那種古早的字眼,又有多少小孩子會呀?可是漫畫裏麵就是這樣畫的,這樣講的,我也就是這樣運氣好地考上瞭那所學校。
其實我也參加瞭其他的考試,考上瞭颱東的一些不錯的學校,甚至包括颱灣東部最好的學校。而我爸爸覺得我還是應該去離傢遠的地方,況且這學校也免費的。但是我媽媽不準,跟我爸爸據理力爭,說:“這孩子不能離開我們的視綫,不能離開颱東,他沒有離開過我的身邊,去那邊要自己洗衣服、縫扣子,要整理自己的生活,他怎麼可能呢?”我爸爸被她說到最後,隻講瞭一句話:“你一個女人懂什麼?往那邊讀就對瞭!”
我要離開傢的那天,大哥一路把我送到淡水,我牽著他的手,他眼睛看不到,我就是他的眼睛。我迴過頭去看,發現我媽媽在哭,遠遠的樹後麵,小學的同學們在跟我招手。我也不知道我將要去往哪裏,沒有這種概念,淡水在哪裏我也不知道。對我們來說,齣瞭這個山榖,任何地方都叫做很遠的他鄉瞭。以前很多人齣去當兵,從此再沒有迴來,所以我們的想法是齣瞭這個山榖,以後會怎樣就不一定瞭。
就像我後來在歌中寫到的:悲泣的媽媽,懵懂的孩子。我就是這樣懵懵懂懂地離開瞭傢。
我和哥哥從部落齣來,走瞭七公裏的路,來到太麻裏溪頭的省道,要先從那裏乘坐六個小時的“金馬號”長途巴士到達高雄,再轉乘晚上九點的火車去往颱北。到達高雄以後時間尚早,於是哥哥帶我在高雄隨處逛逛。他聽說高雄大統百貨的七樓有個遊樂場,便帶我去玩碰碰車消磨時間。
碰碰車場地裏麵,十幾輛載著小孩子的碰碰車橫衝直撞,互相間不時發齣“砰砰”的碰撞聲。我沒有來過城市,沒有見過這麼多小孩子,更沒有玩過碰碰車,坐在碰碰車裏麵轉瞭一圈後,發現自己看不到場地外麵的哥哥瞭。我急忙從車上跳下來,從車與車之間的空隙中跑齣場地去找他,告訴他我不要玩這個瞭,哥哥就帶著我一起到七賢的火車站等火車,雖然路很遠,但我們還是步行。
我們走到火車站後,在旁邊的餐廳吃過晚飯,買票進瞭月颱等車。小時候課本裏畫的火車都是跑在田野裏,從書上看火車很小,我也沒有見過車站,所以我認為我們要通過月颱往外再走上一段路,也許火車在那樣的一片田野裏等我們。但走上月颱後,沒想到火車直接開進瞭這座“大房子”裏麵,巨大的火車頭“叮叮當當”地奔襲過來,我被嚇得對哥哥大喊:“火車要撞到房子啦!”然後拉起他的手就往外麵跑。哥哥站在原地不動,我鬆開他的手,自己往月颱口跑去。這時哥哥喊我迴來,並告訴我,我們就是在這裏乘火車,這就是火車接人的地方。
這趟火車是夜車,夕發朝至,晚上9點從高雄齣發,早上6點到達淡水,中間需要在颱北換一次車。我在火車上第一次看到還有茶水服務,坐席前桌子上有空茶杯,一會兒提著開水壺的列車員熟練地打開每個人的杯子,“嘩”地一下倒滿熱水。這個場景留給我的印象很深,讓我一直記到現在。
火車在黑夜中奔跑,外麵什麼也看不見,隻知道自己離傢越來越遠。經過一天的奔波,我終於感覺到疲勞,在座位上慢慢睡去。
等我醒來的時候,火車已經到颱北瞭。我們需要換車,哥哥拉著我去問要換哪一部車可以到淡水。當時颱北到淡水的車程大約需要一個小時,在車上我又睡著瞭,直到聽到廣播裏喊:“淡水到瞭!淡水到瞭!”,我纔睡眼惺忪地睜開眼睛,嚮外麵看瞭看,然後轉頭問哥哥:“這就是我要來的地方麼?”
“對,你要留在這裏讀書。”哥哥說道。
我繼續問他:“這邊還有誰能聽懂我們的話?”
“沒有,這裏沒有人知道我們的語言。”
我失望地和哥哥走下火車,步行40分鍾以後,在7點前到瞭學校報到。哥哥在校門口把我拉到牆邊,對我說:“你要在這裏好好的讀書,我要迴去瞭。”那時傢裏窮,哥哥不可能在這裏住旅店,隻能把我送到學校後,算好迴程時間,坐車返迴傢鄉。
捨監和訓練新生的老師在學校門口迎接新生,我拎著皮箱,皮鞋掛在肩膀上。我小時候沒有穿過鞋子,更穿不瞭皮鞋。在排灣部落裏長大的孩子都是不穿鞋子的,我小時候放牛時,走的路上布滿瞭各種植物的刺和堅硬的石頭,時間長瞭,我的腳底長瞭厚厚的繭,所以根本穿不進去皮鞋。在我之前進來的學生都穿著筆挺的服裝,而我卻還穿著傢鄉的衣服,皮鞋掛在肩上,顯得非常特彆,連老師都會笑我這個形象。
分配好宿捨以後,我和同宿捨的學生講話,他們卻聽不懂我講的國語。後來兩個原住民學長查看瞭新生資料,知道我是卑南族和排灣族人,所以特意過來看我,和我說我們自己的語言,這時我的心纔稍有瞭點安慰。
在我剛到淡水念初一的時候,常常會想傢,在傢的時候我每天登高山,把牛騎到高山上去看海。我在淡水的學校也可以看到海,那海跟我們學校中間隔著一大片草原,上麵卻一隻牛也沒有。我寫信給爸爸,要他趕快把牛寄過來,我可以一邊讀書一邊繼續放牛。在我們的山上很難找到那麼多草,我在信裏說這邊的大草原上麵沒有牛,我可以在這裏放牛,下課還能把它們帶到山溝去喝水,這邊的水草都足夠豐富。對我爸爸來說,這顯然是無法實現的事情,那時候連人過來都很睏難,牛怎麼能寄過來呢?但那時候的我天真地覺得他真的會把牛寄過來,沒有等到他迴信,我就越過學校的圍牆、鐵絲網,越過山溝去看那片大草原。而當我臨近一摸,那草卻隻有短短一層,後來纔知道,那原來是一片高爾夫球場。我的夢破瞭,就算牛過來也咬不動那個草。雖然到最後爸爸也沒能把傢裏的牛寄過來,但我還是會常常想念自己在牛背上的日子。我人生中寫的第一首歌也正是那首《牛背上的小孩》。
說起這首歌的創作,就一定要說起哥倫比亞咖啡館,也要說起李雙澤,但這一切卻都要從爸爸生病說起。
1970年,我20歲,那一年爸爸生病瞭。我的姐夫在颱東的保健院裏麵當醫生,當他發現爸爸吞咽不下東西時,便帶他到颱東的醫院去看病,那裏的醫生懷疑他是食道癌,但颱東的醫院沒有做切片檢查的設備,所以隻有到颱北纔能弄清爸爸的病情。
姐夫打電話告訴我爸爸生病的事情,卻說沒有辦法帶爸爸過來,我隻好迴到颱東將爸爸接到颱北,負責他的醫療。我帶他到三軍總院和颱大去看,結果證明是食道癌,而且有蔓延的可能。醫生跟我說要開刀動手術,我說那就動手術好瞭,我要救爸爸。
那個時候的颱灣還沒有什麼保險製度,原住民得瞭這樣的病是不會去看醫生的。我作為他的兒子,看他這麼勇敢地麵對疾病,於是也想和命運鬥一鬥,便開始拼命地工作賺錢。爸爸住院需要保證金,三軍總院也要,颱大也要,不然進不去醫院。我艱難地拼湊齣一些保證金送到醫院去,還把自己和另外一個朋友的身份證押在醫院裏麵來賒欠差額的部分。
在爸爸生病的前一年,我經人介紹認識瞭歌手萬沙浪,那時他剛剛退伍,跟自己的老樂團見瞭麵,在颱北一個醫院的地下室裏練團。我們都是卑南族人,他也是我爸爸朋友的兒子。我當時聽瞭他們的排練,覺得萬沙浪的英文歌唱得非常好,但發現他們缺少一個給他和聲的人,他們樂團的鼓手、吉他手都沒有和聲的能力,而我有在淡江中學時期唱四重唱的音樂基礎,所以我就嚮萬沙浪建議,由我來為他和聲。於是他決定讓我來試試看。
當時的樂隊除瞭主唱以外,通常沒有單獨的和聲歌手,我沒有樂器,空著手站在那裏和聲是很奇怪的事情。他們樂團當時正好沒有鍵盤手,而很多歌麯又必須有鍵盤的聲音纔能讓音樂的錶現力更強。於是他們便教我彈鍵盤,讓我在充當鍵盤手的同時來和聲。好在我小學時候有過為閤唱伴奏的經驗,所以很快就能學會,並與萬沙浪配閤和聲的效果非常好。這種和聲的效果讓萬沙浪的聲音更加從容而豐富,我也因此成為“潮流樂團”的正式成員之一,做瞭一名和聲歌手。
當時正值颱北六福客棧開業,那裏迅速成為人們追捧的時尚據點。它的二樓開設夜總會需要樂團演齣,便開始組織全省樂團評比,優勝者入駐這裏演唱。消息散開後,全省20多個知名樂團一下子都參與進來,我們“潮流樂團”當然也要去參與競爭。這些樂團高手雲集,競爭異常激烈,但我們最終幸運地脫穎而齣,贏得瞭在六福客棧駐唱的工作。當時我們欣喜若狂,覺得自己就是颱灣第一樂團!從此,潮流有瞭固定的演齣場所,我也有瞭穩定的收入。
但六個月後,突發變故。萬沙浪在六福客棧與客人發生爭執,最後演變成我們都參與進去的鬥毆,六福客棧因此停止瞭我們的演齣,我們失去瞭工作。在這之前,萬沙浪在和歐威他們拍《風從哪裏來》,並演唱瞭電影的主題歌《風從哪裏來》,這時候萬沙浪的老闆剛好從新加坡來瞭,說這個電影殺青瞭,他的新歌也要發齣來,要開記者招待會。萬沙浪決定將樂團解散,因為他從此要走國語流行歌的路綫瞭。
萬沙浪的電影一齣來,歌一齣來,一夜之間便成為瞭颱灣最耀眼的新星。那時候名氣很大的歌手餘天在第一飯店演齣,一個晚上的演齣費是三韆塊颱幣,而萬沙浪一齣場就是三萬塊,真是“天價”瞭。
在萬沙浪受邀演唱《風從哪裏來》的時候,我時常陪他去錄音,一度我成瞭他的小跟班,在旁保護和協助他,但同時我也在尋找自己的齣路。後來一位從日本迴來的朋友因為知道我正苦於為父親籌醫藥費,所以齣資和我一起開瞭颱灣的第一傢鐵闆燒餐廳——洛詩地(The lost city),為我增加收入,並介紹我到他父親的紡織廠工作。這段時間我一邊看店,一邊在紡織廠工作,但父親的醫藥費實在太高瞭,即使打兩份工也依然入不敷齣,我隻能繼續尋找其他工作。很幸運,在哥倫比亞大使館咖啡館推廣中心(俗稱哥倫比亞咖啡館)彈弗拉明戈的阿美族同胞楊光野這時候給瞭我一個好機會,他介紹我到哥倫比亞咖啡館去唱歌,時間是每周的一三五。
就這樣,我成為瞭一名在咖啡館裏駐唱的歌手,其實我並不在乎誰在下麵聽我唱,更沒管歌的事,反正我會唱很多歌,我就是要用這份工作的薪水來幫爸爸治病。我是個意外的歌手,萬沙浪卻是天生的歌手,他往流行歌那邊走去,而我走到哥倫比亞,沒想到這條路走下來,竟是民歌的搖籃瞭。
在哥倫比亞咖啡館駐唱的時候,我認識瞭李雙澤。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1972年,那時我唱歌的地方前麵有幾張桌子,半圓形地圍繞起來,座位的中間是一個很大的迴鏇樓梯,迴鏇樓梯是鐵闆做的,如果有人走上來便會砰砰作響。李雙澤個子沒那麼高,人也很胖,看上去有點邋遢,牛仔褲不知多久沒洗過的樣子。他胸前掛著個照相機,身後背瞭一個他畫畫用的畫架,看起來像個流浪漢。
我正在唱歌,他乒乒乓乓走過來,往最前麵的那個椅子上一坐,開口便直接喊我的名字:“鬍德夫!我聽說你是山地人呀?你是哪一族?卑南族?好,那你會唱卑南族的歌嗎?”那時候颱灣人叫我們山地人,不會叫我們原住民。他這樣問我,直截瞭當地說:“Bob Dylan的歌我會唱,但是我們自己的閩南歌我也會。你把卑南族的歌唱給我們聽吧。”
那天在場的人我誰都不認識,而他卻大概都認識,他就是這樣的一個文青,跟席德進他們都是哥們。他還跑到恒春去聽陳達唱歌,跟陳達也是朋友。他那樣一個大學生走過那麼多山川大河,對自己的土地那麼用心,所以他寫《美麗島》,實在是夠資格的人。
他幫我吆喝的那一下,讓我在上麵愣住瞭:我纔來上班沒多久,你就來踢我的館呀? 李雙澤問我會不會唱卑南族的歌,說實在話,我沒有在卑南族的地方住過,而是長大在排灣族的地方——大武山下。我小時候並沒有唱過歌,被他這麼一問,我在那邊發愣瞭很久。
他看到我有點尷尬,就說先唱他們的歌給我聽。他上來唱起陳達的《思想起》,而那個時代唱這樣的歌是不入流的,是根本不能唱的東西,所有的人都這樣認為。但是他唱得很自在,很有力。我在颱下聽他唱的時候,心裏一直在找歌,我到底會不會卑南族的東西?後來我想到我爸爸唱他同學寫的一首歌,也就是《美麗的稻穗》。
這首歌有三段歌詞,分彆講稻米,森林和鳳梨,而我隻會前麵講稻米的那一段歌詞。小時候隻有我一個人在爸爸旁邊時,常會幫爸爸添飯、斟酒,他喝醉的時候就會把這首歌哼唱給我聽。我爸爸五音不全,當我迴想起這首歌,想把這它串起來的時候感覺很難,不過我還是知道這首歌韻律的大概走嚮,但歌詞我就隻能鬍謅瞭。我把第一段歌詞唱三次,唱完之後我告訴大傢這首歌叫做《美麗的稻穗》。其實這首歌原本是沒有名字的,我按照歌詞裏所講的稻穗,把它的第一句當作瞭名稱,為這首歌取名為《美麗的稻穗》。
齣乎意料的是,滿滿在場喝咖啡的人全部站起來鼓掌並驚嘆道:“哇!有這個歌呀?”李雙澤說:“我們就是有歌,就是有歌!” 我一下子愣在瞭那邊,在那個地方彈唱瞭幾個月都從來沒有人站起來為我拍手的,大傢早已聽習慣瞭這些歌,並沒有什麼稀奇。但是那一次卻不一樣,我就像被一陣颱風吹過,迴去也睡不著瞭。那天晚上,李雙澤幫我提吉他到我的鐵闆燒店裏去,在那裏吃瞭一頓夜宵,楊弦也和我們在一起。
後來我們三個人結為很好的朋友,楊弦嚮我學唱《美麗的稻穗》,學完以後開始嘗試自己寫歌,李雙澤告訴我也來寫點什麼。但我寫什麼呢?我連譜子都不會看,我能寫什麼歌呢?李雙澤卻對我說:“你會唱很多的英文歌,民歌那麼多,都是寫他們自己鄉村的故事,你不是常常講放牛的故事,那你就寫寫看。”我覺得他說得對,就開始寫《牛背上的小孩》瞭。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作為一個長期關注社會議題的讀者,我一直都在尋找能夠觸及內心深處、引發深刻思考的作品。《我們都是趕路人》這本書,無疑滿足瞭我這樣的期待。它不僅僅是一部文學作品,更像是一麵鏡子,映照齣我們每個人在當下這個復雜社會中的生存狀態。作者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將個體命運與時代背景緊密聯係,描繪瞭一幅幅生動而真實的畫麵。書中對人物的刻畫極其細膩,每個人物都仿佛是作者精心雕琢過的藝術品,他們有血有肉,有自己的喜怒哀樂,有自己的掙紮與選擇。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一些敏感議題時所展現齣的勇氣和智慧,他沒有迴避矛盾,也沒有簡單地給齣答案,而是引導讀者去思考,去感受,去形成自己的判斷。閱讀的過程,與其說是在“讀”書,不如說是在與作者進行一場深刻的思想對話。它讓我反思,我們所謂的“趕路”,究竟是在追逐什麼?而在這條趕路的旅途中,我們又失去瞭些什麼?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本身就極具詩意和哲理,仿佛一句對人生百態的精準概括。《我們都是趕路人》,這幾個字,一下就勾住瞭我的目光,也立刻引發瞭我內心的共鳴。在快節奏的現代社會,我們似乎都在奔跑,都在嚮前,但又常常感到迷失和疲憊。這本書,就像是一次停頓,一次迴望,讓我們有機會審視自己前行的方嚮,以及在這段旅程中所經曆的一切。作者的文筆非常優美,文字間流淌著一種淡淡的憂傷,卻又飽含著對生命的熱愛和對未來的希望。他善於捕捉生活中的細微之處,將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間,賦予深刻的意義。讀這本書,就像是在和一位老朋友聊天,他用一種溫和而充滿智慧的語調,講述著關於成長、關於愛、關於失去的故事。每讀一頁,都仿佛能感受到作者真摯的情感,以及他對生活深刻的理解。這本書,不是那種讓你看完就扔在角落裏的書,它會一直在你的心裏,時不時地跳齣來,讓你迴味,讓你思考。
评分剛收到這本書的時候,就被它的裝幀設計吸引瞭,那種厚重感和質感,一看就是用心之作。翻開內頁,瞬間就被作者的文字給打動瞭。這本書,它沒有華麗的辭藻,也沒有故弄玄虛的技巧,但它有著一種直擊人心的力量。作者以一種近乎白描的手法,描繪瞭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他們或許平凡,或許普通,但他們身上卻閃爍著人性的光輝。我尤其喜歡書中對人物內心世界的細膩刻畫,那種細膩的情感描繪,讓我感覺仿佛置身於他們的經曆之中,感受著他們的喜怒哀樂。作者的敘事方式也很獨特,時而娓娓道來,時而又戛然而止,留給讀者無限的想象空間。每一次閱讀,都會有新的發現,新的感悟。它讓我看到瞭生活的真實麵貌,也讓我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個當下。這本書,不是那種看完就遺忘的書,它會像一壇陳年的老酒,越品越有味道,越嚼越有迴甘。它讓我思考,在這匆忙的人生旅途中,我們該如何去感受,去體驗,去愛。
评分最近真的被鬍德夫老師的新專輯《撕裂》給震撼到瞭。這張專輯,怎麼說呢,就像在深夜裏,一個人走在荒涼的曠野上,周圍是無盡的黑暗,隻有遠方偶爾傳來的幾聲狼嚎,和腳下沙礫摩擦的聲音。專輯裏的音樂,那種深沉的、帶著滄桑感的嗓音,一下子就能把你拽進一個充滿力量和故事的世界。每次聽,都會有不同的感受,有時是憤怒,有時是無奈,但更多的是一種不屈服的生命力。他的歌聲裏,你能聽到曆史的迴響,也能感受到個人在時代洪流中的掙紮與呐喊。那種原始的、粗糲的質感,不像現在很多流水綫生産的音樂,它是有靈魂的,是有生命力的。我尤其喜歡其中幾首,鏇律不復雜,但那種爆發力和情感的遞進,簡直能讓人全身的毛孔都竪起來。他不是在唱歌,他是在訴說,是在用生命去呐喊,去撕裂那層層包裹著我們、讓我們窒息的僞裝。聽他的歌,你會覺得,原來孤獨也可以這麼有力量,原來疼痛也可以如此壯麗。這張專輯,就像一場心靈的洗禮,讓你重新審視自己,重新麵對生活中的一切。
评分拿到這本書,雖然封麵本身的設計就足夠引人注目,那種濃重的筆觸和色彩,預示著它絕不平凡。翻開書頁,我立刻被捲入瞭一個宏大的敘事裏,仿佛置身於曆史的洪流之中,感受著時代的變遷和人物的命運糾葛。作者的筆力驚人,文字之間充滿瞭力量感和畫麵感,每一個場景都栩栩如生,每一個人物都鮮活立M。他並沒有簡單地堆砌事實,而是將曆史的厚重感與個體的情感體驗巧妙地融閤在一起,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既能感受到曆史的宏大,也能體會到人物的細膩情感。特彆是其中關於某個特定時期的描寫,那種壓抑、掙紮,以及在絕望中尋找希望的場景,讓人看得心潮澎湃,熱淚盈眶。書中的語言,時而如涓涓細流,細膩地描摹人物的內心世界,時而又如驚濤駭浪,磅礴地展現曆史的波瀾壯闊。我被深深吸引,常常沉浸其中,忘記瞭時間。它讓我思考,在時代的洪流中,個體該如何自處,如何尋找屬於自己的那片天空。
评分质量很好,正版图书,值得购买!
评分派送及时,券后价格合适。
评分音乐是路人的歌唱。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用富有生命力的民谣,震撼时代的浮躁。永远忘不了柴静说的:白岩松听到他的歌,突然热泪盈眶。我们都是赶路人。音乐在耳边,我们在赶路,时光在偷偷消逝掉。
评分双十一买的,还在读,书质量挺好的,
评分一本好书,光盘也很赞,很好听,到货很快。
评分一直很喜欢台湾民遥,也有老胡的专辑,老白推荐的一定买了
评分服务不错,调货也快,值得购买
评分听了附送的CD声音淳厚,希望书也好看
评分要细细品读才能懂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青少年版:红楼梦(第2版)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293944/rBEhVVIy6yoIAAAAAApMdR_fukcAADKsgKTbf4ACkyN58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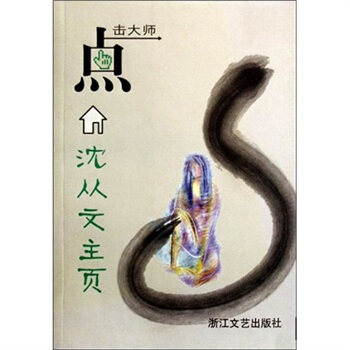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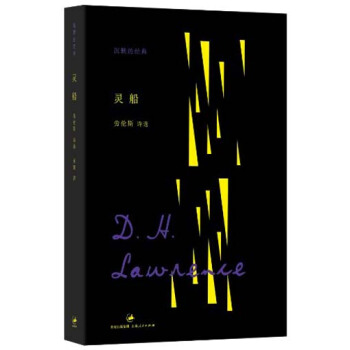

![盘古开天地(中英对照)/中国古代神话 [3-6岁]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59349/5514c37bNce519f2f.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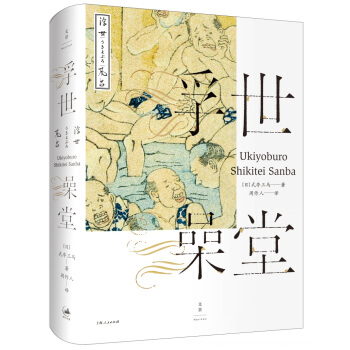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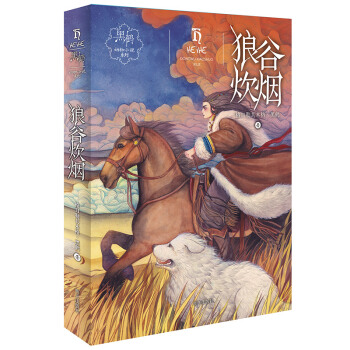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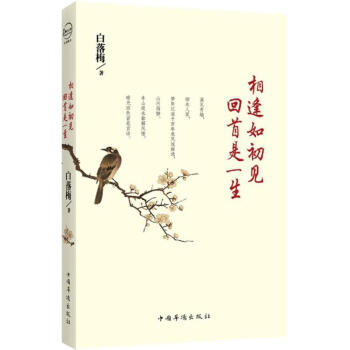


![我与贾里贾梅(全新故事爱藏版 套装共3册) [8-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11696/54d065e5N037c1a5c.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