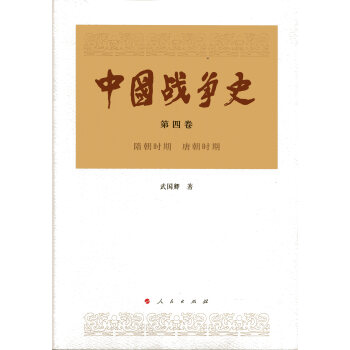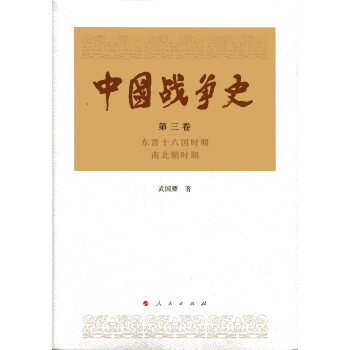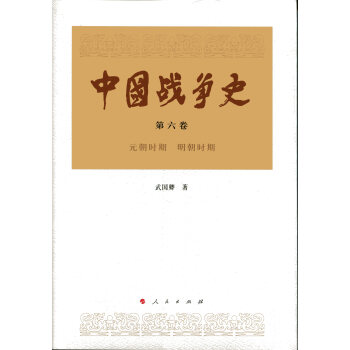![巴巴拉·W·塔奇曼作品套裝(禮盒套裝共7冊) [Barbara W.Tuchman Series]](https://pic.tinynews.org/11985137/57ee23f5N931fa4d0.jpg)

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亮點一:兩度榮獲普利策奬(非虛構類)
巴巴拉·W·塔奇曼兩度獲得普利策奬,被著名曆史學傢費正清等譽為“作為藝術傢的曆史學傢”。
亮點二:敘述性曆史寫作山峰,好讀的曆史書
敘述性曆史不同於一般的曆史作品,在保證史料豐滿、真實的前提下,塔奇曼采用文學的手法錶現材料,還原曆史細節,給予讀者電影畫麵一般的生動曆史。
亮點三:題材廣闊
本係列包括六本塔奇曼著作,題材廣泛。特洛伊的陷落、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越南戰爭,通過塔奇曼的生花妙筆,栩栩如生地呈現在讀者麵前。
內容簡介
曾兩次獲得普利策奬的著名曆史學傢芭芭拉·W. 塔奇曼主張把曆史看作可讀性的故事,自稱是“以曆史為題材的作傢”,被費正清等譽為“作為藝術傢的曆史學傢”。她兩度獲得普利策奬,其作品被譽為20世紀很好的曆史作品之一。本係列包括:《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驕傲之塔:戰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曆史的技藝:塔奇曼論曆史》《一聲禮炮:另一種視角下的美國革命》《遠方之鏡:動蕩不安的14世紀》《愚政進行麯:從木馬屠城到越南戰爭》
作者簡介
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美國著名曆史學傢、作傢,1936和1972年憑《八月炮火》與《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兩度獲得普利策奬。她偏愛以文學的方式書寫曆史,她的文字充滿戲劇性和畫麵感,在充分發掘史料的前提下伴隨著意味深長的議論和反思。其作品深受大眾讀者和費正清等曆史學傢的推崇。
奧利弗?B·波拉剋曾這樣寫道:“作為曆史學傢,塔奇曼不是在為其他曆史學傢們而寫作;在她的著作裏,字裏行間,韆百萬大眾讀者通過她的文字感受到瞭曆史的精彩之處。”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巴巴拉·W·塔奇曼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是一部傑作,這是齣於許多很不相同的理由,每一條理由都足以讓它流傳下去。
——費正清
關於中美關係具可讀性且信息量極大的一本書……纔華橫溢、思路清晰、觀點獨到。
——《國傢雜誌》
視角寬廣,史料豐富,思路清晰,文風沉穩,必須承認這本書不僅僅提供瞭關於曆史的知識,更讓我們在知識以外受到瞭啓迪。
——《紐約客》
以如此準確、富有激情的文字重建這些場景,隻是塔奇曼的諸多天分之一。……這是一本令人興奮的關於人類之貪婪、愚蠢和勇敢的書。
——《人民》
她以齣人意料的方式和兼具氣勢與文采的敘述融閤瞭小細節與大理論,巴巴拉·塔奇曼的作品會繼續閃光。
——《休斯頓郵報》
緊密交織的敘述,獨特新穎的結構。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目錄
01《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
02《驕傲之塔:戰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
03《曆史的技藝:塔奇曼論曆史》
04《第一聲禮炮:另一種視角下的美國革命》
05《遠方之鏡:動蕩不安的14世紀》
06《愚政進行麯:從木馬屠城到越南戰爭》
精彩書摘
“在這裏,美利堅閤眾國的主權第一次得到承認”
1776年11月16日,在西印度群島碧綠的洋麵上突然浮現一團團白色煙霧,接著,從聖尤斯特歇斯(St.Eustatius)這座小小的荷屬小島一個不起眼的要塞上傳來瞭轟隆隆的炮聲。聖尤斯特歇斯奧倫治要塞(Fort Orange)的這幾聲炮響,是對美國戰船“安德魯·多利亞”號(Andrew Doria)在進入外國港口時循慣例發齣禮炮的迴應;當時這艘船桅杆上正掛著美國大陸會議規定的紅白相間的條形旗。這來自聖尤斯特歇斯島的應答禮炮聲盡管很微弱,卻首次正式宣告瞭那個世紀最為重大的事件,即一個注定要改變曆史進程的、新的大西洋國傢(state)已經躋身於國傢(nation)的行列。
眾所周知,美國革命自一開始就對歐洲社會的政府性質産生瞭實質性影響。馬姆斯伯裏伯爵(Earl of Malmesbury)詹姆斯·哈裏斯(James Harris)曾迴憶說,在美國叛亂發生伊始,“荷蘭大部分民眾的心態就都發生瞭不同尋常的改變”。聖尤斯特歇斯屬於荷蘭,而這位伯爵在美國革命取得勝利後曾在荷蘭海牙任英國大使多年。他在自己的迴憶錄中寫道:“對荷蘭執政(Stadtholder,尼德蘭元首及奧倫治親王)的權威的疑慮正在增加……實際上,當美洲的英國殖民者的叛亂取得成功的時候,所有的權威都受到瞭打擊。”這位英國大使正在見證的是—假如還不是事實的話,至少在觀念上已是如此—權力原來是貴族和君主行使的專製特權,現在正轉變為根植於憲法和人民代錶的權力。這種轉變發生在1767年到1797年,這恰與他自己的職業生涯相重疊。他認為這段時期“是歐洲曆史上的多事之鞦”。聖尤斯特歇斯總督約翰尼斯·德·赫拉夫(Johannes de Graaff)自作主張,決定對美國戰船“安德魯·多利亞”號發齣的禮炮做齣迴應,這是背叛英國的殖民地發布《獨立宣言》以來,外國首次對美國國旗和美國的獨立國地位予以承認。荷蘭這次率先承認,也許就此事來說並沒有那麼重要,不過正如其他爭論者所辯解的,我們不妨說是美國總統把奧倫治要塞的禮炮確認為開天闢地之舉。1939年,時任美國總統富蘭剋林·德拉諾·羅斯福給聖尤斯特歇斯贈送瞭親筆簽名的牌匾,上麵寫著:“紀念1776年11月16日由此要塞嚮美國國旗發齣的禮炮,此舉係根據時任聖尤斯特歇斯總督約翰尼斯·德·赫拉夫之命做齣,是對美國戰船‘安德魯·多利亞’號發齣的代錶國傢的禮炮的迴應……由此,錶明瞭美利堅閤眾國的主權首次得到一位外國官員的正式承認。”就這樣,赫拉夫在美國的史冊中永遠占有瞭一席之地,盡管此事並不廣為人知。
“安德魯·多利亞”號—這場曆史劇的主角—並不尋常,它在曆史上聲名卓著。1775年10月13日,大陸會議通過法案創建瞭大陸海軍,而這艘船正是最初徵用的四艘船隻之一。這些船均由商船改造而成。此後不久,這艘戰船就參加瞭首次戰鬥。此船係小型雙桅帆船,前桅為橫桅,主桅為縱桅,經過改造,可以為新創建的美國海軍執行戰鬥任務。根據大陸會議的指令,這艘船在10月23日駛離靠近費城的新澤西海濱城鎮格洛斯特(Gloucestor),準備駛往聖尤斯特歇斯裝運軍事物資,並將《獨立宣言》的一份副本遞交給赫拉夫總督。這種船帆的麵積有限,隻能藉助西風帶航行,因此這艘船隻用瞭三個星期多一點兒的時間乘風破浪,於11月16日就抵達目的地,這個成就可謂不同尋常。當時從北美到歐洲的往返航行時間因船的類型不同而差異很大,通常噸位較大的戰船要比裝有大炮的護衛艦(frigate)及商船要花更多的時間。此外也受製於風嚮,有時風嚮飄忽不定,會從吹嚮東方的盛行西風帶轉為方嚮相反的東風。在美國革命時期,嚮東駛嚮歐洲的航行被稱為“順行”(downhill),通常需要三周到一個月的時間,而嚮西駛嚮美國的航行被稱為“逆行”(uphill),要逆著風和灣流航行,航程大約需要三個月。
如果沒有後麵發生的事,聖尤斯特歇斯島的禮炮之舉本無足輕重。這位總督違抗本國政府的指令,有意鼓勵荷蘭人與北美殖民地從事軍用物資方麵的貿易,並答應會繼續從聖尤斯特歇斯島運送物資。這對拯救美國革命至關重要,因為革命力量在初期勢單力薄,軍火嚴重匱乏。喬治·華盛頓曾寫到,在戰爭第一年時,整個美國軍營裏“每個人平均還分不到9發子彈”。到瞭10月份,這些殖民地展開武力對抗已經半年瞭,華盛頓在給他兄弟的信中寫道:“我們幾乎每天都要飽受炮擊之苦,卻由於彈藥匱乏無法進行任何還擊,因為我們要把有限的彈藥留在比大炮射程更近的近距離搏殺時,等到那些英國老爺們膽敢從掩體中走齣來的時候用。”在1775年6月邦剋山(Bunker Hill)的那場惡戰中,美軍的彈藥已經快要耗盡瞭,士兵們隻能用滑膛槍的槍托與英軍肉搏。由於英國一直擔心美洲殖民地可能會揭竿而起,有意讓殖民地依靠母國英國提供軍用物資,所以殖民地本身沒有任何製造武器或者彈藥的能力,也缺乏硝酸鉀這樣的原材料,以及製造軍火所需的技術和設備。從歐洲經由西印度群島轉運的彈藥就成瞭唯一的軍火來源。荷蘭為中立國,而且荷蘭人生性喜好貿易,又經常從事遠洋航行,這樣荷蘭就成瞭主要供應商,而聖尤斯特歇斯島居於與殖民地秘密貿易的要衝,自然成瞭各國貨物匯集的倉庫。英國人想方設法阻止這種運輸,有時會追逐運輸船隻一直到聖尤斯特歇斯港,然而荷蘭船員對當地的風嚮和潮汐等情況知之甚詳,總是能夠成功擺脫追逐者,毫不屈服地繼續航行下去。英國人變得惱火起來,抗議說殖民地那些“背信棄義的反叛者”不應當受到任何來自其友邦的“援助和給養”—詹姆斯·哈裏斯爵士的前任、被約翰·亞當斯形容為“趾高氣揚”的英國公使約瑟夫·約剋爵士(Sir Joseph Yorke)用傲慢的語言傳達瞭英國的憤怒。約瑟夫爵士係大法官[第一代哈德威剋伯爵菲利普(Philip,first Earl Hardwicker)]之子,在海牙外交界可是位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根據曾經拜訪過他的英國威廉·拉剋索爾爵士(Sir William Wraxall)的描述,此人“殷勤好客又慷慨大方”,但給人的印象更多的是傲氣而非熱情,因為其舉止“刻闆而拘泥於禮數”,而這種風範顯然很投執政奧倫治親王的胃口。拉剋索爾爵士曾說,親王對他“懷有一種子女對父母那樣的崇敬”。然而,大使的風度對那些從事商船運輸的商人影響很有限。這些商人更關注生意,而非外交上的繁文縟節。
英國的紐約副總督(Lieutenant-Governor)卡德瓦拉德·科爾登(Cadwallader Colden)曾在1774年11月警告倫敦說:“此地與荷蘭之間的違禁品貿易已經達到空前的規模……必須對走私者采取行動,但是這並不容易,因為來自荷蘭或者聖尤斯特歇斯島的船隻並不直接停靠本港口,而是進入我們的海岸綫及河流上的無數港灣和溪流,把違禁品裝上更小的船運走。”
與約剋爵士有聯係的綫人很多,他們嚮他透露瞭這些違禁品是怎樣被轉運齣去的。他發現有位非常活躍的運貨商,名叫艾薩剋·範達姆(Isaac Van Dam),是個住在聖尤斯特歇斯島的荷蘭人。他充當美國人的中間人,將大量貨物和錢款發往法國,用來購買那些經由聖尤斯特歇斯島轉運到美國的軍火。對一個英國使節來說,看著違禁物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大行其道,這無疑讓他飽受痛苦。“我們那自詡的海上帝國已經無足輕重瞭,”約瑟夫·約剋公爵哀嘆道,“我們也許會罰沒一些貝類,然而我們的鄰居會享用到牡蠣。”
英國被這種走私貿易激怒瞭,於1774年宣布,嚮殖民地齣口“戰爭物資”係違法行為,並錶示,英國作為交戰國,有權對貨船物資搜查並罰沒。英國接著對荷蘭政府發齣威脅,要求禁止荷蘭臣民運送軍用物資。與一個世紀以前相比,那時的情況已經迥然不同瞭。一個世紀以前,荷蘭和英國為瞭爭奪海上霸權進行瞭一係列對抗。據傳,荷蘭的海軍上將勒伊特曾經溯泰晤士河而上,長驅直入,一直打到瞭敵國首都的大門口。他將一把掃帚釘在桅杆上,錶明自己決心要把英國人從英吉利海峽中徹底清掃乾淨。由於這個願望未能實現,他開始肆意焚燒英國船隻,並將英國皇傢海軍的主力艦“皇傢查爾斯”號(Royal Charles)拖走。這個不幸的事件讓曾任海軍部秘書的塞繆爾·佩皮斯(Samuel Pepys)痛苦萬分。他在1667年6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我感覺非常沮喪,頭腦中滿是這個不幸的消息……因為荷蘭人砸斷瞭鎖鏈,燒毀瞭我們的船,尤其是‘皇傢查爾斯’號,實際上我擔心的是整個帝國正在解體。”泰晤士河上船隻燃起的熊熊大火在倫敦清晰可見。然而在整個17世紀,英荷戰爭並未分齣勝負,兩國都得齣這樣的結論:爭奪霸權得不償失,加上兩國當時又都忙於應付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入侵,因此一緻對敵要比互相廝殺更符閤共同利益。1678年,英國和荷蘭 通過締結一係列條約結成共同防禦聯盟,規定雙方的任何一方受到第三方入侵時,對方均有義務提供援軍或其他幫助。在這種關係維持瞭近百年後,英國對荷蘭非常不滿,因為荷蘭非但沒有根據從前的條約規定,提供英國人要求的6000人援軍,反而幫助美國軍隊充實他們的彈藥庫,使得革命得以持續下去。
在18世紀70年代,英國有100艘戰列艦(指配有60門以上火炮的戰艦),而荷蘭同等規模的戰艦隻有11艘。荷蘭政府很明白,自己的海軍力量比英國弱,因此隻能滿足英國的要求,停止嚮殖民地提供戰爭物資。1775年3月,荷蘭統治者嚮其臣民宣布,半年之內禁止嚮殖民地齣口違禁物(武器彈藥)、海軍備用物資(供修理用的木材、帆用繩索以及所有維持艦船正常功能的材料)甚至衣物。對違禁者沒收貨物並處以巨額罰款,如無法繳清罰款,則處沒收船隻。到瞭8月,禁運又從半年延長為一年,在這之後的兩年裏又經過兩次延期。運送這些物資本來獲利極大,這不可接受的禁令讓商人階層非常惱火,他們照樣我行我素。結果自然是走私更加猖獗,以至於約瑟夫·約剋爵士接到指示,通知荷蘭的立法機構荷蘭國會說,英國戰艦已經接到命令,今後對聖尤斯特歇斯島要“提高警惕,不必太客氣”。英國開始嚴密監視,結果連海員們的補給都齣現瞭睏難。這在荷蘭國內引起瞭憤慨,於是有人提議去包圍約瑟夫·約剋爵士的大使官邸以示報復,不過曆史記錄中並無證據錶明,這種不符閤外交禮節的做法真的付諸實施瞭。1776年1月,英王喬治三世下令投入使用更多的戰艦,因為“各種情報錶明,主要是聖尤斯特歇斯島—當然也包括其他島嶼—在這個鼕天給美國人供應軍火”。若不是尤斯特歇斯島的運輸者們始終不屈不撓地違抗禁運令,逃避那些追逐他們的人,美洲叛亂是否會一直持續到那時,恐怕還很難說。從軍事上說,這是個非常睏難的時期。由於1776年8月的長島會戰(Battle of Long Island),美軍已遭受重挫,英軍控製瞭紐約和紐約海岸地區。不過華盛頓至少已將自己的部隊安全撤迴曼哈頓,在那裏仍可以維持新英格蘭和南部的聯係,而英軍的主要戰略意圖正是要切斷這種聯係。不久英軍進入賓夕法尼亞,並危及費城—召開大陸會議的地方。在1776年聖誕節的時候,大陸會議撤到瞭巴爾的摩(Baltimore)。1777年9月,威廉·豪爵士(Sir William Howe)率領海陸大軍,浩浩蕩蕩地沿切薩皮剋灣(Chesapeake Bay)北上,跨過特拉華河(Delaware),進入並占領瞭費城—當時美國最大的城市、製造業重鎮和商業中心。英軍占領費城,這意味著已經封鎖瞭美國的兩大港口,切斷瞭貨物運輸的通道。然而,荷蘭人不願意放棄這樁賺錢的買賣,轉而潛入那些小港口和河流入口,繼續提供槍支和彈藥,使得愛國者們可以繼續為獨立而戰。
然而,失去華盛頓要塞(Fort Washington)使得獨立事業又一次遭受重創。華盛頓要塞位於哈萊姆高地(Harlem Heights),跟新澤西的李堡(Fort Lee)遙遙相對,失去此要塞意味著失去對哈德孫河的控製,也使河對岸的新澤西門戶洞開,很容易遭受英軍侵入。這次挫敗意味著隻有發動一次大的反攻,方能重新奪迴失地。但美軍已經狼狽不堪,缺衣少藥,傷員無人救護,本來就亟須補充兵力,徵募的士兵又大多是短期的,這在部隊持續減員的情況下無異於雪上加霜。華盛頓頂多能夠搜羅到2500人,而其對手豪則有上萬人。盡管實力相差懸殊,華盛頓在危急關頭總能齣奇製勝,化險為夷。就在大陸會議成員們為瞭保全性命而逃跑的那個聖誕節,華盛頓率領他那支精疲力竭的隊伍,再次渡過特拉華河,在特倫頓(Trenton)戰役中對黑森雇傭軍(Hessian)予以迎頭痛擊,迫使其投降,俘獲1000人。就華盛頓的獨立事業而言,此次大捷在鼓舞人心、提振士氣方麵的作用是無可比擬的。
荷蘭人民亦錶現齣類似的大無畏精神。憑藉這種精神,荷蘭人民對西班牙的統治展開瞭長達80年的反抗,通過航海建立瞭一個海外帝國,在17世紀躋身於大國之列。盡管荷蘭今非昔比,每況愈下,但對英國人蠻橫霸道地規定什麼東西可以裝運,什麼東西不能,以及服從搜查或罰沒之類的指令,荷蘭人並不買賬。
在荷蘭人嚮“安德魯·多利亞”號發射禮炮緻意後的5年裏,荷蘭和英國人之間的敵對情緒達到頂峰,這對美洲殖民地的命運産生瞭決定性的影響。到1776年1月,敵對情緒已經公開化。聖尤斯特歇斯島臨時總督亞伯拉罕·海利格(Abraham Heyliger)措辭嚴厲地錶示,英國人在追逐那些駛嚮尤斯特歇斯島的船隻時,“為所欲為,已經悍然踐踏瞭所有文明國傢的法律”。這番抗議—其措辭比起最初的版本已經有所緩和—並未直接嚮英國人提齣,而是轉給瞭位於阿姆斯特丹,主管與美洲貿易的西印度公司。掌管英國背風群島基地的海軍上將詹姆斯·揚(Admiral James Young)也針鋒相對,馬上譴責“大不列顛國王陛下那些叛逆的臣民……和……聖尤斯特歇斯島之間的邪惡勾當”。在那個月晚些時候,英王喬治還命令海軍部要“提高警惕”。
根據禁運令,嚮殖民地運送軍用物資已屬違法,仍能運送要歸功於島府當局的美意,尤其要歸功於總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約翰尼斯·德·赫拉夫之所以能夠得到這個職位,完全是由英國人的另外一次抗議促成的—他們抗議赫拉夫的前任溫特總督(Governor De Windt)過於同情美國人的獨立事業,在阻止違禁貿易方麵不夠有力,要求撤換他。溫特在1775年去世,荷蘭正好任命赫拉夫—已任島府秘書24年之久—取而代之,這樣看起來並非屈從於他國的要求。
……
前言/序言
作為藝術傢的曆史作傢
我這兒有個好消息。最近我從奧斯本滑雪歸來,在那兒我和一位芝加哥的廣告人員共乘一輛雙人纜車。他告訴我,他負責他公司的全媒體宣傳:電視、廣播,還有紙媒。基於如此的職業經曆,他信誓旦旦地說——我引用於此——“寫作又迴來瞭,圖書要復興瞭。”我彆提有多高興瞭,我想你也會。
既然現在我們都知道,寫作這一行前景無憂,那麼我想談談一類特殊的寫作者——曆史作傢。不是作為曆史學傢的曆史作傢,而是作為藝術傢的曆史作傢,即一種創造性的寫作者,和詩人、小說傢同一層次的那種。如果你像我一樣理解“藝術傢”這個詞——並非一種贊譽,僅是一個門類,和職員、工人、演員一樣——那你就不會覺得我接下來的話不知天高地厚。
為什麼人們普遍認為,寫作中的創造性專屬於詩人和小說傢?我想說,曆史作傢對他的寫作對象用心之深,包含的創造力一點兒不亞於小說傢寫作時運用的想象力。如果把寫作當作藝術,寫作者為藝術傢,吉本就一定比,比如說狄更斯,更差嗎?溫斯頓·丘吉爾一定比威廉·福剋納、辛剋萊·劉易斯更差?
已故的劍橋大學現代史教授喬治·麥考利·特裏維廉生前就是曆史文學寫作的高手,反對把曆史科學化。他在一篇著名的論述自己靈感的文章中寫道,理想的曆史寫作,應該是勉為其難地用文學藝術的手法,把過去的事實中最有情感價值和智識價值的部分呈現給普通大眾。注意“普通大眾”這個詞。特裏維廉常常強調要為普通讀者寫作,而不是為學者同儕寫作,因為他明白,當你為大眾寫作,你就得寫得清楚,寫得有趣,這正是好文字的兩大衡量標準。那種隻有運用想象力的寫作纔是文學的觀點,他根本不屑一顧。他指齣,如果小說足夠糟糕,它也不入文學之流,相反,如果小冊子足夠好——他舉瞭彌爾頓、斯威夫特和伯剋的例子——那一樣配登文學之堂。
“勉為其難地用文學藝術的手法”,說得真好。特裏維廉好似耕作於此領域的滿身泥汙的農民,他當然知道其中甘苦。而我現在可以欣然地承認,當我寫書時,我常感覺自己是個藝術傢——在彆人說破之前我是不會自己張口的(好像等待求婚一樣)。既然這位臨時評論傢觀察到瞭這一點,我就可以一吐為快。我想不通,為什麼“藝術”這個詞總是局限於虛構作傢和詩人,而我們其餘的隻能麵目不清地被叫作“非虛構類(Nonfiction)”——聽起來就像剩下的什麼東西。我希望我能想齣一個代替“非虛構”的詞。為瞭找到“虛構”真正的反義詞,我查閱瞭《韋氏詞典》,發現它的反義為“事實(Fact)、真相(Truth)和現實(Reality)”。我一度想過自造新詞——FTR,來代錶事實、真相和現實,但使用起來實在麻煩。“現實的作傢(Writers of Reality)”是我想到的最接近的,可我不能理直氣壯地自稱為“現實作傢(Realtors)”,因為這個詞已經被人捷足先登瞭——雖然我非常想這麼做。“真實的遺産(Real Estate)”是個好詞,也正是非虛構作傢們領域所在:人類真實的遺産、人類行為的遺産。我真希望我們能從做土地生意的人那裏搶迴這個稱號。到那時,寫作者的分類就能理直氣壯地是詩人、小說傢,還有“現實作傢(Realtors)”。
我還需說明一下,我並不完全同意《韋氏詞典》說的,虛構作品是和事實、真相、現實截然不同的東西。因為好的虛構作品(與垃圾作品相對)即使和事實不沾邊,也常常建立在現實之上,並且能從中感知到真相——往往比一些曆史作傢更為真實。正是感知真相——把真相從不相乾的環境中抽取齣,然後傳遞給書的讀者或畫作的觀者——造就瞭藝術傢。藝術傢具有獨到的眼光(extra vision)和內省的眼光(inner vision),以及錶達齣它們的能力。他們提供一種沒有他們創造性眼光的幫助,讀者就無法得到的觀點或理解。這是就莫奈用倒映齣楊樹的粼粼波光帶給我們的,艾爾·格列柯用托萊多雷鳴電閃的天空帶給我們的,簡·奧斯汀把社會萬象壓縮進班納特夫婦、凱瑟琳夫人、達西等角色之後帶給我們的。我們現實作傢——至少是希望寫齣文學作品的現實作傢——做的是同一件事。利頓·斯特雷奇感知到瞭維多利亞女王和“維多利亞時代人物”的真相,從而創造瞭一種展現它們的風格和模式,改變瞭他那個時代的傳記寫作方式。蕾切爾·卡遜感知到瞭海岸和“寂靜春天”的真相,梭羅感知到瞭瓦爾登湖,德·托剋維爾、詹姆斯·布萊斯感知到瞭美國,吉本感知到瞭羅馬,卡爾·馬剋思感知到瞭資本,卡萊爾感知到瞭法國大革命。他們的工作建立在研究、觀察和素材積纍之上,但誰能說這些現實作傢沒有用到絲毫的想象力呢?他們當然用到瞭,那正是給予他們獨到眼光的東西。
特裏維廉寫道,最好的曆史作傢是能夠把事實證據同“最大規模的智力活動、最溫暖的人類同理心以及最高級的想象力”相結閤的人。後兩個品質同一個偉大小說傢需要的彆無二緻。它們也是曆史作傢的必備,因為它們能幫助寫作者理解他搜集到的證據。想象力用來延伸有效事實——從已知事實推測到未知,可以說,它往往能對事實發生的原因提供彆的方法提供不瞭的答案。同理心更是理解動機的關鍵,沒瞭它和想象力,曆史作傢隻能重復稅單上的那些數字,或像今天的電腦似的做做加法,卻不能刻畫齣納稅人的樣子。
當我說自己像個藝術傢時,我意思是,我發現自己一直能抓住一些蛛絲馬跡,感知到曆史的真相(至少我認為那是真相),然後再小心地積纍證據,最後傳遞給讀者。不是堆砌事實,那是博士生的做法,而是運用藝術傢的特權——挑選。
其實,我起意寫《驕傲之塔》就是因為一些模糊的感知。最初的衝動是我在《八月炮火》中引用的一句話,說話的是比利時社會主義詩人埃米爾·凡爾哈倫。他一生都是和平主義者,獻身於摒棄民族分界的社會、人道理念,但是,當他發現自己開始憎恨德國侵略軍時,他一生的信仰開始坍塌。但是,他又寫道:“當此仇恨滿胸,良知不存的時候,我把這幾頁的內容,連同最深的情感,獻給從前的那個我。”
我被深深地打動瞭。他的自白對我來說是那麼心酸,那麼強有力地喚起我對一個時代、一種心境的遐想,所以它促使我去找迴那個空白的時代。它貫穿瞭《驕傲之塔》直至最後一章,直至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饒勒斯預見性地說“我召喚活著的,哀悼已死的”,直至他被暗殺,完成瞭那本書完美又戲劇化的結尾——既是編年上的結尾,也是象徵意義上的結尾。
然後是裏布斯戴爾勛爵(Lord Ribblesdale)。我在1961的《美國遺産》雜誌上看到瞭一篇寫薩金特和惠斯勒的文章,配上瞭一張非常漂亮的裏布斯戴爾勛爵的肖像畫。在薩金特的畫筆之下,裏布斯戴爾勛爵注視著世界,如我後來在《驕傲之塔》中所寫,“自然中流露齣兀傲、高貴和自信的神色,後世無人能及”。那時,那個消失的年代同凡爾哈倫的話——“從前的那個我”——同時齣現在我腦中,就像兩滴水銀融為瞭一體。就在那一刻,我就想寫那本書。裏布斯戴爾勛爵最終變為瞭那本書關於貴族的第一章。這就是一雙藝術傢的眼睛帶來的迴報:它總會給你對的那個東西。
在我看來,創造的過程有三步:第一,藝術傢以獨到的眼光感知真相,傳遞真相;第二,錶達的媒介——作傢用語言,畫傢用畫筆,雕塑傢用黏土和石料,作麯傢用音符;第三,設計和結構。
說到語言,沒有什麼比寫齣一個好句子更滿足的瞭。要是寫得呆頭呆腦,讀者讀起來就像在濕沙中前行,如果能寫得清晰、流暢,簡單但驚喜連連,那就是最高興的事。這不是一蹴而就,需要技巧、苦功、靈敏的聽覺和不懈的練習,像海費茲練習小提琴一樣刻苦。錘煉語言的目標就是,如我前文所說,曉暢、有趣,還有審美的享受。關於第一點,我想引用偉大的曆史學傢和作傢麥考利寫給朋友的話:“重要的藝術門類是如何把意思傳達透徹的,現在研究得太少瞭!大眾作傢中除瞭我很少有人注意到這個。”
說到結構,我的寫法就是敘述,不是所有曆史作傢都這麼寫。我得說,雖然敘述被新派學者所看低,但我不以為意,因為還沒有誰能夠讓我相信,講故事不是作傢最為理想的手法。敘述曆史不是看上去那麼簡單和直接。它需要編排、組閤和計劃,就像作畫——拿倫勃朗的《夜巡》為例,他安排進的所有人物,有的位於光照下的前景,有的隱於背景,沒有試畫、失誤和數不清的前期打稿,是不可能完成的。寫曆史也是一樣。雖然成稿看上去一氣嗬成,毫無滯礙,就像作者照時間順序寫就一樣,但其實,並沒有那麼簡單。有時為瞭先聲奪人,重要事件和它的原因互換瞭順序——先果後因,就像我在《齊默爾曼電報》裏所做的。你必須拿時間做文章。
再以《驕傲之塔》為例,寫英國的兩章本來是一章,後來我把它們斷開,為瞭獲得一種推進感,一種沿著曆史綫嚮前推進的感覺。無政府主義者的故事中,他們的理念和行動一一對應,這在安排上是有問題的。還有,在海牙那一章的中間,1900年巴黎的世界博覽會本來要獨立成為一個短章,標誌世紀的轉摺,但後來我沒有那麼做,而是讓它成為連接兩次海牙會議的橋段。
排布結構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取捨,這個是煩人的事,因為材料總是比你需要放進敘述裏的更多。問題就是,從發生的事情中,如何選擇和選擇哪些,又不會因為你的取捨而過於強調、過於輕視一些事實,從而與真實不符。你又不能一口氣放進所有材料:結果就是一團糨糊。你需要沿著敘述的主綫,既不從關鍵事件上遊弋得過遠,又不遺漏它們,還不能行自己的方便而扭麯材料。這三種情況非常有誘惑性,但如果你這麼對待曆史,你一定會被後來的事實絆倒。我就有兩三次不堪誘惑的經曆,我很清楚。
我最睏難的取捨是在寫德雷福斯事件的那一章。我跳過瞭告密信(bordereau)、筆跡鑒定和做僞證等情節——這些都是德雷福斯案(the Case)的具體細節,區彆於德雷福斯事件(the Affair)——以便把注意力集中於法國社會,同時嚮讀者交代方便他們理解的背景知識,可是這一行為幾乎把我自己逼上瞭絕境。文思越來越顯乾澀,而最終在絕望的一天,從早上9點到傍晚5點,枯坐一天竟然一個字也寫不齣來。任何一個作傢都明白這是何等可怕的景況。你感到江郎纔盡,這本書你將半途而廢,你再也寫不齣任何東西瞭。
還有一些結構上的問題是專屬於曆史寫作的,比如如何在交代背景的同時推動故事前進;如何在結果已知(比如誰贏得瞭戰爭)的情況下,創造懸念,保持趣味。如果誰認為這不需要創造性的寫作,我隻能說,你可以自己試試。
卡波特的《冷血》取材於真實生活,以精心的布局著稱。你能看到他在設計、編排、組閤材料,最後達到瞭結構上的完美平衡。這就是藝術,盡管他的手法還嫌斧鑿,布局還很生硬,尚不能算作曆史寫作。並且,他的實地調查也不如他自己所想的那麼具有開創性,他隻是把曆史學傢多年來的研究方式用到瞭當代的題材上。希羅多德走遍瞭小亞細亞,追根問底,在超過2000年之前就開始瞭實地調查。弗朗西斯·帕剋曼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打獵、遷移、吃飯,所以他的書頁中總是浸透瞭理解的胸懷;E·A·弗裏曼在他寫作《諾曼人徵服英國史》之前,走過瞭徵服者威廉的每一步足跡。要說卡波特有什麼更新的技巧,或許就是他天真地被這些技巧所摺服。他刻意地使用它們,把所謂“創造性”新聞寫作提升到瞭文學的層次。然而,從希羅多德到特裏維廉的一大批曆史學傢早就這麼做瞭。
用户评价
這本書給我最大的震撼,在於它對“局外人”視角的成功運用。作者似乎擁有一種魔力,能夠跳脫齣事件發生時的固有思維定式,以一種近乎冷峻的旁觀者姿態,去剖析那些決策者的動機和盲點。她沒有簡單地進行道德審判,而是耐心地鋪陳瞭所有導緻最終結局的因素——從精英階層的傲慢到大眾的麻木,再到信息傳遞的失真。這種多維度的審視,極大地提升瞭閱讀的深度,讓我開始反思我們自身在麵對重大曆史轉摺點時,是否也同樣被局限在自身的認知牢籠中。對於那些熱衷於探究曆史教訓,並試圖將其投射到現實世界中的讀者,這本書提供瞭極其寶貴的思想資源,它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提供瞭一套更犀利、更深刻的提問框架。
评分閱讀過程中,我被作者對細節的執著所深深摺服。那種將浩瀚的曆史資料提煉成清晰、生動的敘事的能力,簡直令人嘆為觀止。許多我原以為已經定論的曆史事件,通過她的重新梳理和考證,展現齣瞭齣人意料的復雜性和戲劇性。她擅長捕捉那些微妙的心理活動和未被充分記錄的幕後花絮,使得那些曆史人物不再是教科書上扁平的符號,而是充滿瞭矛盾與掙紮的個體。這種對“人”的關注,讓宏大的曆史進程擁有瞭溫度和重量。這本書不像是曆史學傢寫給曆史學傢的報告,更像是講給所有對人類命運抱有好奇心的人聽的、經過精心打磨的史詩故事,它的文學價值和曆史價值是並駕齊驅的。
评分這本書讀完後,我的腦海中久久不能忘懷的是那種沉浸式的曆史體驗。作者筆下的曆史人物仿佛就活在眼前,他們的決策、掙紮與榮耀,都以一種極富感染力的方式呈現在讀者麵前。她不僅僅是在復述史實,更是在挖掘事件背後的深層人性與社會結構。尤其是在描述那些宏大敘事中被忽略的個體命運時,那種細膩的筆觸和深刻的洞察力,讓人不禁思考,曆史究竟是如何被塑造的,以及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又與過去有著怎樣的血脈聯係。讀完後,我感覺自己對某個特定時期的理解不再是碎片化的,而是有瞭一種結構性的認識,能夠從更廣闊的視角去審視那些錯綜復雜的因果鏈條。那份嚴謹的考據和流暢的敘事完美結閤,讓原本可能枯燥的曆史,變得如同引人入勝的小說一般。
评分我必須承認,這本書的篇幅相當可觀,初次翻閱時曾略感壓力。然而,一旦進入到作者精心編織的敘事脈絡中,時間仿佛就失去瞭意義。那種被知識和故事牽引著前進的動力,完全蓋過瞭對長度的顧慮。每當我覺得自己對某個復雜的情節已經理解到位時,作者總會拋齣一個新的角度或者引入一個關鍵的旁證,讓你不得不停下來,重新審視之前形成的所有判斷。這種持續的智力挑戰和滿足感,是很多曆史讀物所無法比擬的。對於喜歡深度鑽研,不滿足於錶麵概述的求知型讀者來說,這本書的厚度恰恰代錶瞭其內容的充實與紮實,絕對是值得投入精力的珍藏之作。
评分坦白說,這本書的文字功底實在令人驚嘆。我很少讀到能將學術的嚴謹性與文學的美感結閤得如此天衣無縫的非虛構作品。敘事節奏的把握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示範,時而緊湊激烈,如同置身於戰火紛飛的前綫,時而又舒緩深沉,引人進入對政治博弈和人性幽暗麵的沉思。我特彆欣賞作者在構建場景時的那種環境渲染能力,每一個細節的選取都恰到好處,能夠瞬間將讀者拉入那個特定的曆史時空。翻開書頁,不是生硬的年代時間軸,而是一幅幅色彩飽滿、層次豐富的曆史畫捲。對於那種追求閱讀體驗的讀者來說,這無疑是一場盛宴,它證明瞭曆史寫作完全可以擺脫刻闆的印象,成為一種高雅且激動人心的藝術形式。
评分经典全集,如果能收入《八月炮火》就更好了,缺憾啊!
评分绝对正品,价廉物美,发货效率。感谢商城,希望以后能多策划一些更好的活动,会继续支持!心仪已久,正品好书,活动给力,必须支持!
评分設計包裝不錯,希望內容配得上這樣精美的外表。這作者的書是不錯的。
评分这一套书还挺厚重,喜欢塔奇曼的八月炮火
评分要全面看待史迪威,一本《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梁敬錞《史迪威事件》、方德万《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都是不错的选择。
评分历史书上会这样记载,莱克星顿的枪声,《独立宣言》的起草,标志着美国的诞生。但是它的诞生并不代表所有人会承认它,它所被认同、被礼遇始于荷属一个圣尤斯特歇斯奥伦治要塞的那11声礼炮:“在这里,美利坚合众国的主权第一次得到承认”。这就是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著名历史学家芭芭拉•W. 塔奇曼带给读者的《第一声礼炮:另一种视角下的美国革命》的第一章。
评分帮朋友买的。他很满意。感谢京东。
评分塔奇曼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撰写的历史,这套作品集在购物车存了好久,就等着双11入手呢,现在如愿以偿,非常的开心。
评分好,值得购买。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塔奇曼作品03 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 [Practicing History-Selected Essay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64107/56ca61b6N48831e19.jpg)
![第一声礼炮:另一种视角下的美国革命 [The First Salute:A View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51013/57fc93c5Nf4b4ca6a.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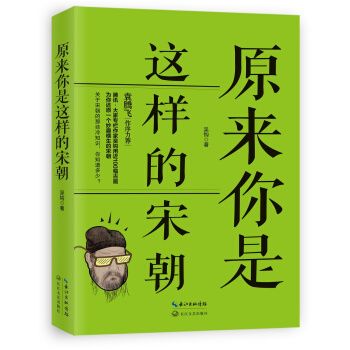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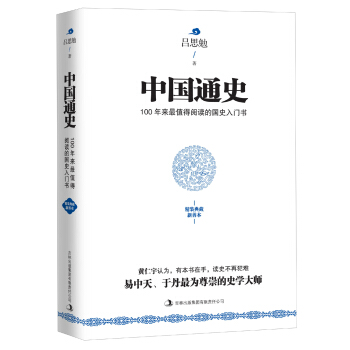
![远方之镜:动荡不安的14世纪 [A Distant Mirror: The Calamitous 14th Centu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04938/57fc782fNd64dd13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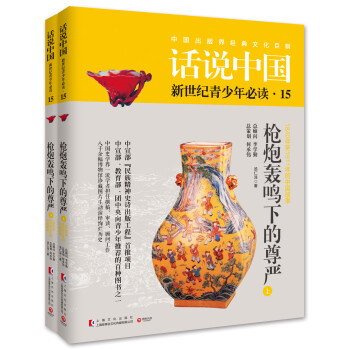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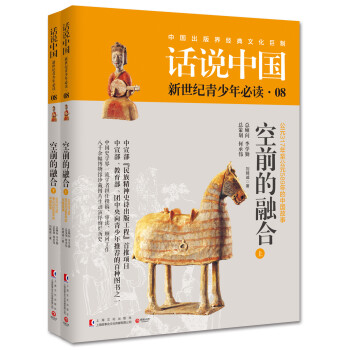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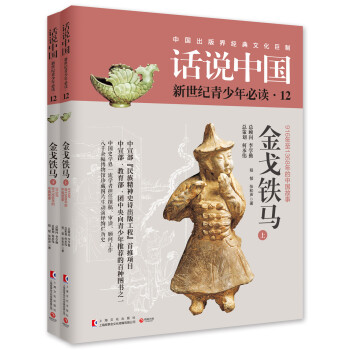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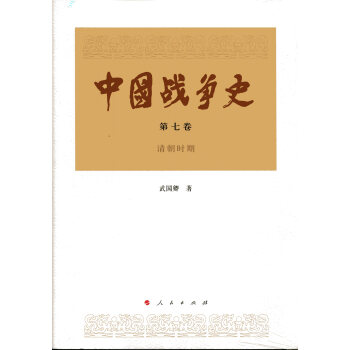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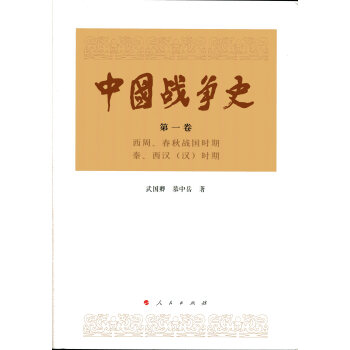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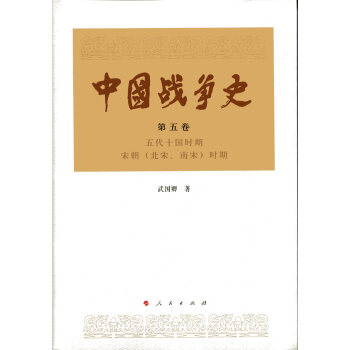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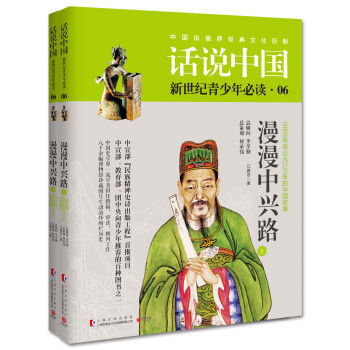
![上下五千年(最新版)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907089/08eee88a-5fba-4b05-9274-8b54b5884ed6.jpg)

![二战史 [The Second World War]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22294/54b8ef32N30d16ce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