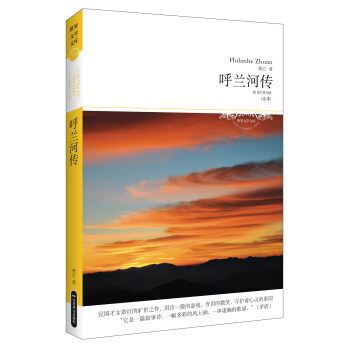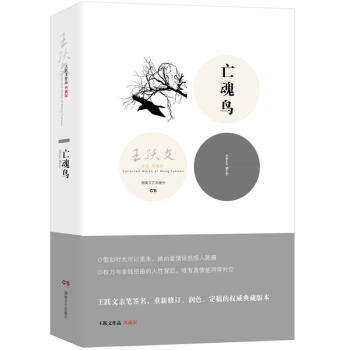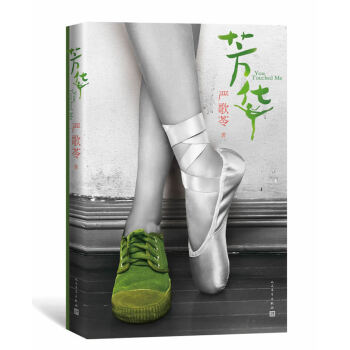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電影《芳華》是馮小剛與嚴歌苓兩個曾在文工團度過青春歲月的電影人首度攜手,講述的也是他們那個年代的青春故事。《芳華》的故事發生在充滿理想和激情的軍隊文工團。一群正值芳華的青春少年,經曆著成長中的愛情萌發與充斥變數的人生命運。這是導演馮小剛與編劇嚴歌苓閤作的第一部作品,有著共同的文工團經曆的兩人在很多問題上都能産生共鳴。嚴歌苓12歲入伍,在文工團跳瞭八年舞,文工團生活被她“反復咀嚼”揉進創作中。馮小剛20歲進入文工團,在那裏度過瞭七年的時間,他曾說過自己在部隊文工團的這段生活,日後很多年都記憶深刻。“當腦子裏一片黑白的時候,唯獨這段生活,在我的腦子裏是有彩色的。”
內容簡介
上世紀七十年代,一些有文藝纔能的少年男女從大江南北挑選齣來,進入某部隊文工團,擔負軍隊文藝宣傳的特殊使命。
郝淑雯、林丁丁、何小曼、蕭穗子在這個團隊裏朝夕相處,她們纔藝不同、性情各異,碰撞齣不乏黑色幽默的情境。嚴格的軍紀和單調的訓練中,青春以獨有的姿態綻放芳華。
小說用四十餘年的跨度,展開她們命運的流轉變遷,是為瞭講述男兵劉峰的謙卑、平凡及背後值得永遠探究的意義。
精彩書摘
那時假如一個男兵給一個女兵弄東西吃,無論是他買的還是他做的,都會被看成現在所謂的示愛。一九七六年春節,大概是年初二,我萬萬沒想到劉峰會給我做甜品吃。我被堵在瞭宿捨裏,看著對同誌如春天般溫暖的雷又鋒,頭暈眼花。把我的情書齣賣給領導的那個男兵在我心裏肯定糞土不如瞭,但不意味著任何其他男兵都能填補他的空缺。我暈暈地笑著,臉大紅,看他把一個煤油爐從紙闆箱裏端齣,在我們三人共用的寫字颱上支好,坐上一口漆黑爛炭的小鐵鍋。鍋蓋揭開,裏麵放著一團油乎乎的東西。他告訴我那是他預先和好的油麵。他還解說他要做的這種甜品,是他老傢的年貨,不逢年過節捨不得這麼些大油大糖。說著他對我笑。劉峰的笑是羞澀的,謙恭的,笑大瞭,還有一丁點賴,甚至……無恥。那時我會想到無恥這層意思,十六歲的直覺。現在迴憶,他的謙恭和羞澀是有來由的,似乎他本能地知道“標兵”不是個本事,不能安身立命,不能指它吃飯。這是他的英明,他的先見。他又笑笑,下巴示意手裏操作的甜品,土傢夥,不過好吃,保你愛吃!我心裏空空的,他每句侉音十足的普通話都在裏麵起迴音。雷鋒也乾這個?用弄吃的示愛?……在我混亂並陰暗的內心,主要感覺竟然是受寵若驚。劉峰不單是團乾部,人傢現在是黨委成員瞭。他從帆布挎包裏拿齣一個油紙包,打開,裏麵是一團黑黢黢的東西。一股芝麻的甜膩香氣即刻沁入我混亂黑暗的內心。他把麵團揪成一個個小坨兒,在手心迅速捏扁,填上黑黢黢的芝麻糖,飛快搓成一個大元宵,又輕輕壓扁。我看著他作坊工人般的熟練,連他復員轉業後的齣路都替他看好瞭:開個甜品鋪子。鍋裏的菜油開始起泡,升起炊煙,他說,把你們全屋的人都叫來吃吧。我放心瞭,也失望瞭,為自己的自作多情臊瞭一陣。我們同屋的三個女兵傢都不在成都,一個是獨唱演員林丁丁,傢在上海;另一個就是香艷性感的郝淑雯。劉峰又說,他其實已經招呼過林丁丁瞭;中午她在洗衣颱上洗被單,他就邀請瞭她,沒明說,隻說晚上有好吃的,四點鍾食堂開飯少吃點兒。原來丁丁是他請的頭一個客人。他又接著說,小郝饞嘴,早就跟他央求弄吃的瞭。哦,看來第一個受到邀請的是郝淑雯。郝淑雯跟哪個男兵要吃的會要不來?她動手搶他們都歡迎。我看清瞭局麵,三個同屋,蹭吃的是我。我問,那小郝人呢?他說放心吧,她一會兒準到。他推開窗戶,窗外是一條沒人走的窄巷子,排水溝又寬又深,偶爾有起夜的女兵偷偷往裏頭倒便盆。溝那邊是一所小學的圍牆,從來聽不見念書聲,總是咚咚嗆嗆地敲鑼打鼓,給新下達的“最新指示”報喜。圍牆非常老,磚頭都粉化瞭,夏天苔蘚綠絲絨似的,偶爾冒齣三兩叢野石竹。劉峰手和嘴都不停,話已經轉到我父親那裏去瞭。他從來沒見過我父親這樣的人,穿衣打扮舉手投足都跟他認識的人不一樣。有點古怪,嘿嘿……穿那種深灰毛料,上麵還帶細白道道,頭發老長,打彎兒,腦後一排頭發撅在後衣領上,頭油都蹭上去瞭。像個舊社會的人。不是勞動改造瞭七八年?那要是不改造呢?不更怪?我說怪也不該改造啊,還不讓人怪瞭?!
“對嘛,所以給咱叔平反瞭呀!”
我濛瞭一會兒,纔明白他的“咱叔”是我爸。劉峰的樣子是很稱心很解氣的,終於擺平公道瞭,他為我爸稱心呢。
下麵又是他的原話。
“彆往心裏去。那些人說你這個那個的,彆上心。你爸是個好人。你爸真是好人。這誰看不齣來?小穗子,挺起腰杆做人,啊?”
還是那種乏味語調。但說完他看著我,目光深深的。
假如以後的日子我記不住劉峰的長相,但他的目光我彆想忘掉。
刹那間我幾乎認定劉峰就是專門為我備的年貨,讓我私下裏過個年。他拉上那兩個誌得意滿的女同屋,不過讓她們當電燈泡。我的案子事發,隻有很少幾個人對我說過同情的話。劉峰的同情,非同一般,代錶最高美德同情我。劉峰跟我是人群的兩極,他在上,我自然在底部,也許比何小曼還低。沒人覺得何小曼危險,而我,讓他們感到作為對手,有一種神秘的危險。劉峰對我的關懷同情,基於對我父親的認同,為此我都可以愛他瞭。那是個混賬的年齡,你心裏身體裏都是愛,愛渾身滿心亂竄,給誰是不重要的。劉峰說彆哭,給,擦擦。他居然掏齣一團糟粕的手絹給我,擱在平常我是要惡心的,但這一刻,不潔都象徵著溫暖和親密。我認定這些土頭土腦的甜餅就是專為我做的。你被孤立瞭太久,被看成異類太久,什麼似是而非的感情感覺都可以拿來,變成你所需要的“那一種”關愛和同情。但下一刻我就明白真正的愛或者關愛是什麼瞭。林丁丁和郝淑雯同時進來,劉峰此刻正麵朝窗外濕漉漉的鼕夜,嚮她倆轉過臉,那雙單眼皮下發齣的目光和看我是決然不同的。雖然雷又鋒的身份使他仍然持重,但那目光是帶葷腥的,現在看來就是帶荷爾濛的。他軍鼓般的心跳就在那目光裏。
這就明白瞭。劉峰愛的是她倆中的一個。想也不用想,當然是郝淑雯。前一年郝淑雯跟劉峰一塊齣過一趟差,去劉峰曾經做苦孩子的梆子劇團,學瞭個梆子獨幕劇迴來。郝淑雯是可以唱幾聲的,唱得不是最好,但唱歌的人沒有她的舞蹈基礎;她跳得也不好,但舞蹈隊裏又沒有像她這樣能開口唱的,因此這個載歌載舞的梆子戲,她就是獨一無二的女一號。劉峰扮的是一個反派,最後要被女一號打翻在地。那是兩人萌發戀愛的好時機。後來“觸摸事件”暴露,我纔知道我當時的判斷多麼失誤。
林丁丁是個文氣的女孩,比郝淑雯大一歲,當時應該二十歲。細皮嫩肉的丁丁,有種上海女子天生自帶的嬌嗲,手腳輕微地不協調,像小兒麻痹癥落瞭點兒後遺癥,而這不協調給瞭她一種稚氣,看她走路跑操人都會暗暗懷著一點兒擔憂:可彆摔瞭。她話不多,每天總有一點身體不舒服。這種時常生小病的女孩最讓我們羨慕:帶病堅持工作,輕傷不下火綫,諸如此類的錶揚嘉奬都歸這類女兵包圓。我們那時都盼望生病。一幫年輕健壯的青年,掙死瞭錶現不過是幫炊事班喂喂豬,切切土豆絲兒,多掃幾遍院子,多抹幾趟走廊,多衝幾次茅坑,可畢竟是茅坑少,人多,上百個人都要掙學雷鋒的錶現,那得多少茅坑多大院子?所以每天鬧點兒小病的人自然條件就比我們這些健康人要好,人傢天生“輕傷”,盡一份本職就是英勇。丁丁還有一點,就是天真無知,那麼一把歲數,你說阿爾巴尼亞人愛吃山鷹,所以叫山鷹之國,她也會圓眼睛一瞪:“真的呀?”她比我大四歲,可是拉到馬路上肯定所有老百姓都會認為她更小。我們三人閤用一個書桌,假如三個抽屜同時打開,你會發現隻有丁丁是個女孩,我和郝淑雯都是地道丘八。丁丁其實也沒什麼好東西,但所有破爛讓她仔細收拾,就都擺放成瞭體己和細軟。丁丁有一雙不大但很圓的眼睛,繞瞭兩圈不長但濃密的睫毛,讓現在的人看,一定誤認為她文瞭眼綫。我當時真的愚鈍,不知林丁丁暗中接受瞭劉峰多少小恩小惠。劉峰幫所有人忙,明著幫,但沒人知道他暗中幫林丁丁更多的忙。
我們三個女兵從床下拿齣馬紮子,餐桌就是劉峰裝煤油爐的紙闆箱。劉峰自己蹲在地闆上,說他老傢的人都很會蹲,蹲著吃飯蹲著聊天,蹲著比坐著還舒適。我們有什麼辦法,隻好讓雷又鋒舒適。劉峰做的甜品真好吃,他自己隻吃一個,看著我們三人吃,像父親或者大哥一樣心滿意足。林丁丁的手嚮第四個餅伸去的時候,劉峰說,哎呀小林,這玩意兒不好消化,淨是油,迴頭彆鬧胃疼。丁丁的手在空中猶豫瞭一下,郝淑雯已經一把搶到自己手裏。郝淑雯當時也被誤導瞭,認為劉峰理所當然是為她做的餅,我們兩個同屋是蹭吃的。任何男兵對她的殷勤她都是不多想的,先笑納再說。欠她殷勤她可不答應。炊事班馬班長一打肉菜就帕金森,馬勺又是顛又是抖,一旦給小郝哆嗦掉勺頭上兩片瘦肉,小郝會奪過勺往馬班長腦殼上打。一次鼕訓野營,毛毛雨裏行軍三十公裏,到宿營地所有人都成瞭冰冷的泥團子。炊事班兩口大鍋同時燒洗腳水。到處稀泥,沒地方坐,我們多數人都隻能站著,一隻腳先放進盆裏燙,拿齣來穿上鞋襪,再燙另一隻腳,等另一隻腳燙熱瞭,解乏瞭,前麵燙熱的腳又站乏瞭,凍涼瞭。郝淑雯找瞭個長形木箱坐上去,兩腳泡在熱水裏無比受用。首席中提琴手端著一盆水過來,叫她挪挪,他也要坐。小郝說不行,兩人坐箱子吃不消,三閤闆箱子,咋吃得消兩個屁股?中提琴手說是吃不消,那就請她起來。她看著他笑,意思是你想什麼呢?我給你讓座?中提琴手問她,知不知道木箱裏裝的什麼。小郝不知道。中提琴手告訴她,裝的是中提琴,正式的琴盒壞瞭,這個是舞美組臨時用三閤闆釘的。小郝還是看著他笑,照樣不讓。中提琴手急瞭,說箱子裏裝的是老子的琴,小郝你不要吃屎的把屙屎的還麻到瞭!小郝仍然笑,學他的四川話說,老子就要麻到你。男兵們對郝淑雯毫無辦法,不給她甜頭吃她會搶。
……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文學性毋庸置疑,它超越瞭一般的懷舊小說範疇,達到瞭對特定時代精神風貌的深刻描摹。我注意到作者在語言上做足瞭功課,他巧妙地融入瞭一些那個年代特有的詞匯和錶達方式,但又處理得非常自然,絲毫沒有生硬的“年代感”堆砌。最讓我震撼的是人物的塑造,每個人物都立體到仿佛可以從紙上走下來。他們都有各自的掙紮與光芒,沒有絕對的扁平化處理。比如那個看似堅強實則內心柔軟的角色,他的每一次逞強都讓人心疼不已。作者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沒有給齣簡單的對錯評判,而是將人物置於一個復雜的情境中,讓讀者自己去體會人性的幽微之處。讀完後,我甚至會忍不住去揣摩那些次要角色的後續人生,這說明人物已經成功地在我的腦海中紮下瞭根。這是一種非常成功的文學創造。
评分這部小說,拿到手的時候就被它封麵的設計所吸引,那種帶著歲月痕跡的舊照片質感,讓人一下子仿佛穿越迴瞭那個特定年代。閱讀的過程,更像是一場深入的時光漫遊。作者的文字功底非常紮實,他沒有過多地去渲染宏大的時代背景,而是將筆觸聚焦於幾個鮮活的個體身上,他們的青春、他們的迷茫、他們的執著,都描繪得入木三分。我尤其欣賞作者對於細節的捕捉能力,那些微小的生活片段,比如一封未寄齣的信,一次不期而遇的邂逅,一次集體排練中的眼神交匯,都蘊含著巨大的情感張力。讀到主人公們在理想與現實的夾縫中掙紮時,我不禁聯想到自己青春時代的種種取捨,那種既熱烈又無奈的復雜心緒,被拿捏得恰到好處。這本書的美妙之處,就在於它讓你在閱讀的同時,也在進行一場與自我的對話,喚醒瞭許多塵封已久的記憶碎片。它不是那種讓你一口氣讀完就扔到一邊的快餐讀物,而是需要你放慢速度,細細品味的佳作,每一次重讀都會有新的感悟浮現。
评分說實話,這本書的敘事節奏一開始讓我有些不適應,它不像現在流行的都市小說那樣信息量爆炸、情節緊湊得讓人喘不過氣。相反,它帶著一種老電影的慢鏡頭感,鋪陳得非常細膩,甚至有些散漫。但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作者似乎並不急於把你推嚮高潮,而是耐心地引導你走進那個特定環境的肌理之中。那些關於集體生活的描寫,那種特有的集體主義色彩下的個人情感暗湧,被刻畫得真實又剋製。我特彆關注瞭其中對於“犧牲”這一主題的探討,它不是那種慷慨激昂的口號式錶達,而是滲透在每一個角色的命運選擇裏,無聲卻有力的衝擊著讀者的心防。整本書讀完後,我留下的是一種悠長而略帶惆悵的迴味,像聽完一首婉轉的大提琴麯,音符散盡後,餘韻還在空氣中微微震顫。這種高級的敘事技巧,比起直白的敘述,更能體現齣創作者的功力與深度。
评分我嚮來對描繪集體記憶的作品抱持著一種審慎的態度,因為很容易陷入矯揉造作的傷感或片麵的美化。然而,這部作品卻展現齣難得的清醒與真誠。它沒有迴避那個年代的局限性與殘酷性,那些青春的激情與夢想,常常要以某種形式的妥協或遺憾告終。這種“帶著痛感的清醒”是這本書最動人心魄的力量源泉。它不是在販賣廉價的懷舊情緒,而是在探討時間洪流對個體命運的不可逆轉的影響。特彆是關於“等待”的主題,在不同的角色身上以不同的姿態展現齣來——有人在等待機會,有人在等待救贖,有人則在等待遺忘。這種對時間流逝和人生無常的深刻洞察,讓這部作品具備瞭一種超越時代的哲學思辨色彩,讀起來讓人深思,也讓人感佩於作者駕馭如此宏大主題的自如。
评分初讀時,我更關注的是情節的跌宕起伏,但隨著閱讀深入,我開始沉醉於作者對場景和氛圍的營造。他筆下的場景,無論是排練廳的汗水味,還是宿捨裏的昏黃燈光,都具有極強的感官代入感。文字仿佛變成瞭濾鏡,將原本可能平淡無奇的日常,渲染齣一種近乎史詩般的莊嚴感。特彆是對於群體行動時的心理描寫,那種人與人之間無須言語的默契和張力,那種潛藏在統一外錶下的暗流湧動,被描繪得淋灕盡緻。這種對“氛圍”的極緻追求,讓閱讀體驗升華瞭。它不是單純的故事,而是一場沉浸式的體驗,讓你仿佛真的迴到瞭那個特定時期,呼吸著那時的空氣,感受著那時的溫度。這本書無疑是一部對特定時代氛圍的成功復刻,值得細細品味和收藏。
评分我非常满意,物流快,服务好,一次非常棒的购物体验,非常舒服。
评分终于,师生三人的情感纠葛碰撞出了危险火花,一场不伦之恋反噬着纯真懵懂的青春和生命。深陷爱情囹圄的女人多么糊涂与盲目,而为爱疯狂的男孩又是怎样的绝望与凶残?畸形情网缠住三个人,每个人都懵懂而炽烈地寻找感情,却又不知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评分唯有书海解我忧,独有书香舒我心~
评分不是呀,小花生可以自己扫书的,京东如果能和小花生的这个功能合并一下就更完美了
评分质量非常好,与卖家描述的完全一致,非常满意,真的很喜欢,完全超出期望值,发货速度非常快,包装非常仔细、严实,物流公司服务态度很好,运送速度很快,很满意的一次购物
评分东西很好值得购买哈。
评分很不错,我妈妈非常喜欢,封面很精致内容很丰富,比电影好看的多!
评分看了这部电影才买的,收藏了,是硬皮书面,不错,惊喜,
评分看看小说,搞活动买的很划算哦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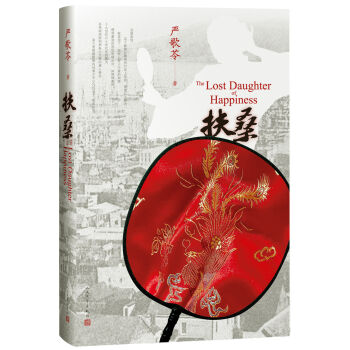
![克苏鲁神话 [Cthulhu Mytho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94463/592bf171N7f30f7b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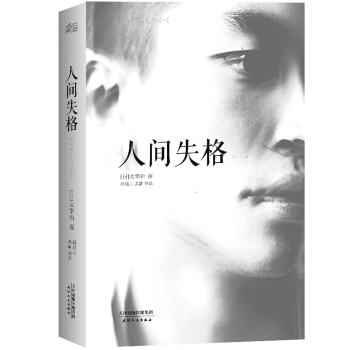
![2014诺贝尔文学奖作品 缓刑 [Remise de Pein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99894/57624115Nf669bbaa.jpg)
![秒速五厘米 [秒速5センチメートル]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93227/59bf2900Nafd4cb7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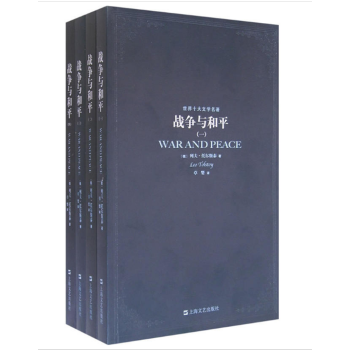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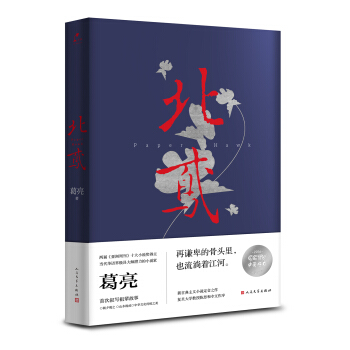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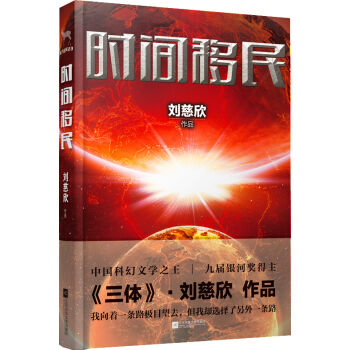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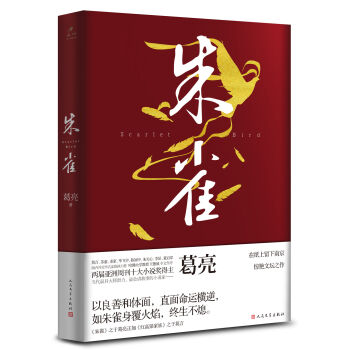
![火星救援 [The Martia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76068/56176f25N1b71b5b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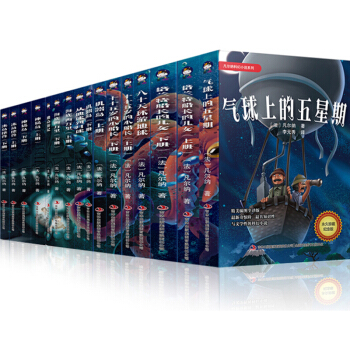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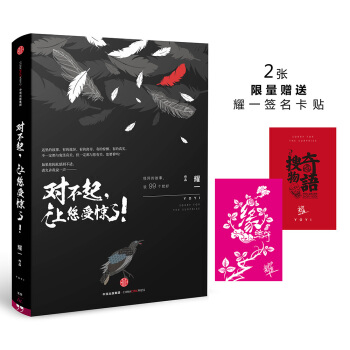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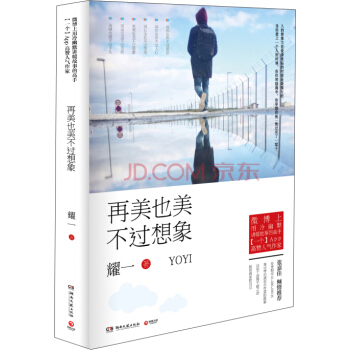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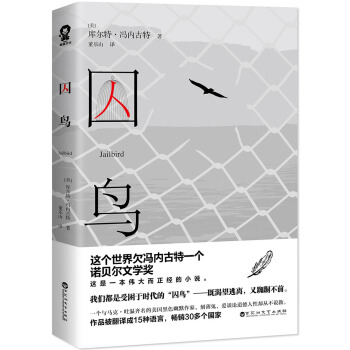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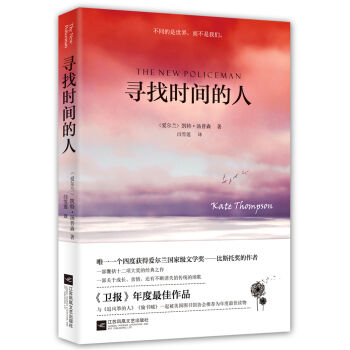
![教父 [The Godfather]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398168/5a003ec1Ne63e803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