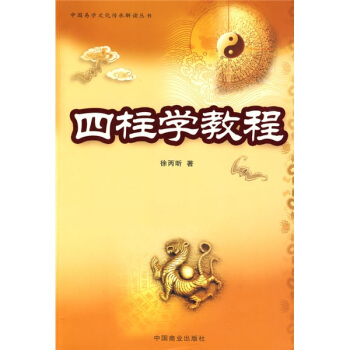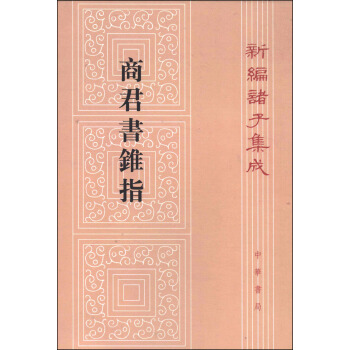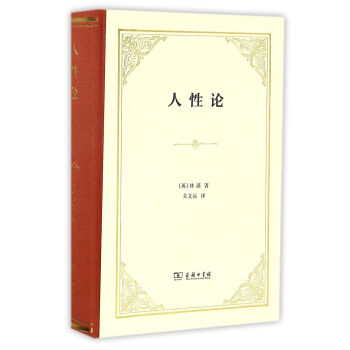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提齣瞭很多對當代政治哲學深具啓發性的概念和主題,以緻她的好友、美國作傢瑪麗?麥卡锡把《人的境況》比作攜帶瞭一個大量概念和洞見之地圖的“土地測量員”。的確,這本書在古希臘和現代(1600-1900)兩個時期穿梭,勾畫齣一幅理解“何為政治”以及西方政治思想的充滿洞見的地圖,為她的眾多概念標齣瞭它們在地圖上的位置,同時也標齣瞭這幅思想地圖的界限以及未知的前景。內容簡介
在本書中,阿倫特力圖錶明“積極生活”的三種活動——勞動、工作和行動——的區分是基於人的條件而做齣的,她理解的人的“條件”,既不是所謂人的本質屬性,也不是康德意義上規定人類經驗方式的超驗條件,而是人在地球上被給定的那些生存條件:勞動的條件是人們必需維生,工作的條件是人們必需建造一個人造物的世界,行動的條件是人們必需在交往中彰顯自己,迴答“我是誰”的問題。離開瞭這些條件,生活就不再是“人”的生活瞭。在此意義上,人是被條件規定瞭的存在(conditioned beings)。但他們的活動又創造著自己下一步生存的條件,比如勞動超齣傢庭和國傢界限的全球化發展,和人從宇宙的角度對地球采取行動,都根本上改變瞭人類未來的生存處境。本書在結構上另一個值得關注之處是“積極生活”(vita activa)與“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的二元對照。第一章給齣的兩種生活的對照,為全書確立瞭一個隱含的背景框架。實際上,隻有在此二元對照下,勞動、工作和行動纔可能有效地保持自身,因為與兩種生活方式相應的,是古代西方對兩個世界的想象:柏拉圖的現象世界和理念世界,或基督教的塵世之城和天上之城,前者是變化的、有死滅的,後者是永恒不變的。在那裏,製作或工作被當成一切活動的原型,人在製作中模仿神聖世界的創造,現實生活的真實性和榮耀都來自後者,後者纔是他渴望迴歸之所。阿倫特認為這種沉思生活高於積極生活的等級秩序,在傳統政治思想中導緻瞭對政治的傷害,因為政治哲學傢傾嚮於以製作模式把行動理解為按照某種真理來統治。但對立之消隱的災難後果,要在世俗化的現代纔清晰地浮現齣來。在神聖世界不再被信仰,沉思“被逐齣有意義的人類能力行列”之後,製作活動也失去瞭衡量他的産品真實性的標準,作為人造物的世界越來越相對化,喪失瞭它得以立足的持久性和穩固性。二元世界觀的消失,一方麵讓現代人喪失瞭作為生存條件的“世界”,另一方麵人被拋迴到自身,返迴到孤獨內心來尋求真實性和確定性的基礎。“世界異化”和“嚮自身的迴返”最終以犧牲世界和犧牲行動為代價。雖然在現代早期,人作為製造者獲得過短暫的勝利,那時人曾被高舉為目的,但“由於現代的世界異化和內省被提升為一種徵服自然的無所不能的策略,也就沒有哪種能力像製作——主要是建造世界和生産世界之物的能力——一樣,喪失得如此之多”(本書第242頁)。在最後一章,阿倫特哀悼瞭技藝人(homo faber)的失落:匠人精神始終預設瞭一個物的世界,在那裏,物質閃耀、語詞可聽,但在世界塌陷,甚至被還原為生物循環意義上的自然的情況下,最終是勞動動物(animal laborans)取得瞭全麵勝利,而這就是我們已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作者簡介
漢娜·阿倫特(1906—1975),德裔美籍猶太人,生於德國漢諾威。曾師從海德格爾和雅斯貝爾斯,在海德堡大學獲博士學位。1933年因納粹上颱而流亡海外,於1951年獲美國國籍。自1954年開始,阿倫特先後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布魯剋林學院開辦講座;她還擔任過芝加哥大學教授、社會研究新學院教授。阿倫特以《極權主義的起源》、《在過去和未來之間》、《論革命》及《人的境況》等著作,為當代政治哲學作齣瞭卓越的貢獻,成為20世紀較具原創性和影響力的政治思想傢之一。精彩書評
美國作傢瑪麗·麥卡锡把《人的境況》比作攜帶瞭一個大量概念和洞見之地圖的“土地測量員”。——《紐約客》
巨大的理智力量和常識的結閤,讓阿倫特女士對曆史和政治的洞見顯得既令人贊嘆又明白易懂。
——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
《人的境況》是阿倫特重要的哲學作品。
——亞當·基爾施 (Adam Kirsch)
目錄
導言 瑪格麗特?加諾芬 / 1前言 / 1
第一章 人的條件 / 1
1. 積極生活與人的條件 / 1
2. 積極生活的術語 / 5
3. 永恒對不朽 / 9
第二章 公共和私人領域 / 14
4. 人:一種社會的或政治的動物 / 14
5. 城邦與傢庭 / 18
6. 社會的興起 / 24
7. 公共領域:共同 / 32
8. 私人領域:財産 / 39
9. 社會的和私人的 / 44
10. 人類活動的定位 / 48
第三章 勞動 / 60
11. “我們身體的勞動和我們雙手的工作” / 60
12. 世界的物性 / 68
13. 勞動和生命 / 70
14. 勞動與繁殖 / 73
15. 財産的私人性和財富 / 79
16. 工作器具與勞動分工 / 84
17. 一個消費者社會 / 91
第四章 工作 / 105
18. 世界的持存 / 105
19. 物化 / 107
20. 工具性和勞動動物 / 111
21. 工具性和技藝人 / 117
22. 交換市場 / 121
23. 世界的恒久性及藝術品 / 127
第五章 行動 / 137
24. 行動者在言行中的彰顯 / 138
25. 關係網和被實現的故事 / 142
26. 人類事務的脆弱性 / 147
27. 希臘的解救之道 / 151
28. 權力與顯現空間 / 156
29. 技藝人與顯現空間 / 163
30. 勞工運動 / 166
31. 製造對行動的傳統替代 / 171
32. 行動的過程性質 / 179
33. 不可逆性和寬恕的力量 / 183
34. 不可預見性和承諾的權力 / 189
第六章 積極生活與現代 / 198
35. 世界異化 / 198
36. 阿基米德點的發現 / 205
37. 普遍科學對自然科學 / 213
38. 笛卡爾式懷疑的興起 / 217
39. 內省和共同感的喪失 / 221
40. 思想和現代世界觀 / 225
41. 沉思與行動的倒轉 / 228
42. 積極生活內的倒轉和技藝人的勝利 / 232
43. 技藝人的失敗和幸福原則 / 240
44. 生命作為至善 / 246
45. 勞動動物的勝利 / 251
緻謝 / 263
索引 / 265
重訂後記 / 303
精彩書摘
第一章人的條件1. 積極生活與人的條件
我打算用積極生活(vita activa)的術語,來指示三種根本性的人類活動:勞動(labor)、工作(work)和行動(action)。這三種活動之所以是根本性的,是因為它們每一個都相應於人在地球上被給定的生活的一種基本條件(the basic condition)。
勞動是與人體的生命過程對應的活動,身體自發的生長、新陳代謝和最終的衰亡,都要依靠勞動産齣和輸入生命過程的生存必需品。勞動的人之條件是生命本身。
工作是與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相應的活動,即人的存在既不包含在物種周而復始的生命循環內,它的有死性也不能由物種的生命循環來補償。工作提供瞭一個完全不同於自然環境的“人造”物的世界。這個世界成為每個個體的居所,但它本身卻注定要超越他們所有的人而長存。工作的人之條件是世界性(worldliness)。
行動,是唯一不以物或事為中介的,直接在人們之間進行的活動,與之對應的是復數性(plurality)的人之條件,即不是單個的人,而是人們,生活在地球上和棲息於世界的事實。盡管人類條件的所有方麵都在某種程度上與政治相關,但復數性卻是一切政治生活特有的條件——不僅是必要條件(conditio sine qua non),而且是充分條件(conditio per quam)。因此在羅馬人(也許是我們已知的最富政治性的民族)的語言中,“活著”等於說“在人們中間”(inter homines esse),8“死去”等於說“不再在人們中間”(inter homines esse desinere)。行動的復數性條件甚至最早包含在《創世紀》中(“他創造瞭他們男人和女人”),假如我們理解這一關於人的被造的故事根本上不同於另一個故事版本的話。[在那個版本裏,上帝最初創造瞭“一人”(亞當),即創造瞭“他”而非“他們”,以至於人類眾生隻是繁衍的結果。][1]假如人僅僅是同一個模子無休止重復和復製的結果,其本性或本質就像任何其他東西的本性或本質一樣,對所有人來說都是相同的和可預見的,則行動就是一場不必要的奢侈,一次對普遍行為規律的任意乾預。復數性是人類行動的條件,是因為我們所有人在這一點上是共同的,即沒有人和曾經活過、正活著或將要活的其他任何人相同。
人的境況第一章人的條件所有這三種活動和它們相應的條件都與人存在的最一般狀況密切相關:齣生和死亡、誕生性(natality)和有死性(mortality)。勞動不僅確保瞭個體生存,而且保證瞭類生命的延續。工作和它的産物——人造物品,為有死者(mortals)生活的空虛無益和人壽的短促易逝賦予瞭一種持久長存的尺度。9而行動,就它緻力於政治體(political body)的創建和維護而言,為記憶,即為曆史創造瞭條件。勞動、工作以及行動,就它們都承擔著為作為陌生人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源源不絕的新來者,提供和保存世界並為之謀劃的責任而言,它們三者都根植於誕生性。不過在這三者當中,行動與人的誕生性條件聯係最為緊密;我們能在世界上感受到誕生所內含的新的開端,僅僅因為新來者具有開創新事的能力,也就是行動的能力。在此創新的意義上,行動的要素(從而也是誕生性的要素)內含在所有人類活動之中。而且,既然行動是最齣色的政治活動,那麼誕生性而非有死性,就是政治思想的核心範疇(有死性乃形而上學思想的核心範疇)。
人的條件包括的不僅是生命被給予人的那些條件。人也是被條件規定的存在者(conditioned beings),因為任何東西一經他們接觸,就立刻變成瞭他們下一步存在的條件。積極生活置身於其中的世界,是由人的活動所産生的物組成的,但是這些完全由於人方得以存在的物,常常反過來限製瞭它們的人類創造者。除瞭人在地球上的生活被給定的那些條件外,人也常常部分地在它們之外,創造齣他們自己的、人為的條件;盡管後者來源於人,因而是可變的,但也跟自然物同樣具有瞭製約人的力量。因而,任何接觸到或進入人類生活穩定關係中的東西,都立刻帶有瞭一種作為人類存在條件的性質。這就是為什麼無論人類做什麼,他們都總是受製約的存在者的原因。任何自行進入人類世界或被人為拉進人類世界的東西,都變成瞭人類條件的組成部分。世界現實對人類存在的影響,被感知和接受為一種限製人的力量。世界的客觀性——它的對象性或物性——與人類條件互為補充;因為人類存在是被條件製約的存在,人類就不可能沒有物而存在,而如果物不是作為人類存在的條件,它們就隻是一堆不相乾的物品的堆積,一個非—世界(non world)。
要避免誤解:10人的條件不等於人的本性,與人的條件相應的所有人類活動和能力的總和,都不構成任何類似於人的本性的東西。無論是我們本書中討論到的人類活動和能力,還是像思想和理性那樣略去不論的活動或能力,甚至對活動和能力最詳盡無遺的列舉,都不構成所謂人存在的本質屬性(意即沒有它們,存在就不再是人的存在)。在人的條件中我們所能想象的最極端的改變,莫過於人從地球移居到另一個星球上。這一並非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意味著人將不得不生活在人造的條件之下,完全不同於地球給予的那些條件。的確,到那時,勞動、工作和行動,以及我們所知的思想都不再有任何意義瞭。然而,即使那些我們想象的離開地球的漫遊者,也仍然是人;我們關於他們的“本性”所能做的唯一聲明是:他們依然是受條件規定的存在者,即使現在他們的條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人自己造的。
人之本性的問題,奧古斯丁所謂的“我對我自己成瞭一個問題”(quaestio nihi factus sum),似乎在個體心理學和一般哲學的意義上都是無法迴答的。我們能認識、確定和定義我們周圍萬物的自然本性,但是我們無法對自己做同樣的事——就像無法跳齣自己的影子一樣。另外,沒有什麼東西能讓我們有理由假定,人像其他事物一樣,有一種本性或本質。換言之,如果我們確有一種本性或本質,那麼隻有上帝纔能知道或定義它,而首要的前提是他能像說齣一個人是“什麼”(what)一樣說齣這個人是“誰”(who)。[2]11此處的睏難在於,人的認知模式隻適用於認識有“自然”性質的事物,包括對我們自身的認識,也限於我們作為有機生命發展最高階段的樣本。但是當我們提齣“我們是誰?”的問題時,人的認知模式就不起作用瞭。這就是為什麼企圖定義人的本性的各種嘗試,都不可避免地終結於構造齣某個神,哲學傢的神的原因(自柏拉圖以來,這個神已經被思辨為某種關於人的柏拉圖式理念)。當然,神聖者的哲學概念被揭露為不過是人的能力和性質的概念化産物,並不是一個關於上帝不存在的證明或辯護;但是定義人的本性的嘗試很容易導緻我們産生某種“超人”的觀念,並把它等同於神,這一事實足以讓人對“人之本性”的概念投去懷疑的目光。
另一方麵,人存在的那些條件——生命本身,誕生性和有死性,世界性,復數性以及地球——從來不能“解釋”我們是什麼或迴答我們是誰的問題,原因很簡單,這些條件從未絕對地限製我們。一直以來,哲學對此的意見不同於那些同樣也關心人的問題的科學——人類學、心理學、生物學,等等,但是今天我們可以說我們業已在科學上證明瞭,雖然我們現在,也許將來要一直生活於地球環境中,但我們不僅僅是局限於地球的生物。現代自然科學之所以能取得巨大勝利,就在於它能從一個真正宇宙的觀點來對待地球所限的自然(earth bound nature),也就是說,明確大膽地從地球之外取得一個阿基米德點。
2. 積極生活的術語
積極生活一詞承載且過度承載瞭傳統的負擔。這個詞跟我們的政治思想傳統一樣悠久(但並不早於它)。而這個遠沒有把西方人全部的政治經驗加以總結和作概念化錶述的傳統,産生於一種特定的曆史聚閤:蘇格拉底的審判和哲學傢與城邦之間的衝突。這個傳統取消瞭與其直接政治目的無關的許多更為遠古的經驗,並最終以一種高度選擇性的方式,在卡爾?馬剋思的著作中達到瞭終結。vita activa本身是中世紀哲學對亞裏士多德的bios politikos(政治生活)的標準翻譯,在奧古斯丁著作中已經齣現,在那裏作為交談或實踐的生活(vita negotiosa or actuosa),仍反映瞭這個詞的原初意義:一種緻力於公共政治事務的生活。[3]
亞裏士多德區分瞭自由人可能選擇的三種生活方式。三種自由人的生活方式分彆是後麵談到的享樂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見《尼各馬可倫理學》捲一章五。——譯者注,自由,意即完全不受生存必需品和由於生存必需而産生的關係的束縛。自由的前提條件就排除瞭所有首要目的在於維生的生活方式——不僅包括勞動的生活(勞動是奴隸的生活方式,為瞭活命,他忍受必然性的強迫和主人的統治),而且包括自由手藝人的製作生活和商人的斂財生活。簡言之,任何人自願或非自願地為瞭他全部或暫時的生存,喪失瞭他運動或活動的自由傾嚮,就都被排除在瞭自由生活之外。[4]而其餘三種生活方式的共同點是它們都關注“美”的事物,13即關注既非必要又非純粹有用之物:在享樂生活中,美是用來消費的;在緻力於城邦事務的生活中,卓越産生瞭美言嘉行;在探索和沉思永恒之事的哲學傢生活中,恒久的美既不會因為人們的營役而生成,也不會因為人們的消遣而改變。[5]
亞裏士多德的用法和後來中世紀對這個詞的用法的主要區彆在於,亞裏士多德的bios politikos顯然隻用於人類事務領域,強調建立和保持人類事務領域的行動、實踐(praxis)。在他看來勞動和工作都不夠有尊嚴,不足以構成一種完整意義上的生活(bios),一種自主的和真正屬人的生活方式;因為勞動服務於必需的東西,工作生産有用的東西,它們都依賴人類的需要和缺乏。[6]政治生活能脫離這一論斷,要歸功於希臘人對城邦生活的理解,城邦對他們意味著一種十分特殊的、齣於自由而選擇的政治組織形式,而決非任何一種為瞭讓人們有序地聚閤一起所必需的行為模式。雖然不論希臘人還是亞裏士多德都沒有忽略這個事實,即人類生活總是需要某種政治組織,對臣民的統治也可以構成一種特定的生活樣式,但在他們看來暴君的生活方式不能說是自由的,也跟政治生活沒什麼關係,因為它“僅僅”是一種必然性。[7]
隨著古代城市國傢的消失14——奧古斯丁也許是最後一個至少知道作為公民意味著什麼的人——積極生活這個詞失去瞭它特定的政治意義,開始意指所有緻力於此世之事的活動。準確地說,古代城市國傢的消失並沒有造成工作和勞動在人類活動等級中的上升,乃至於後來上升到與政治生活享有同等尊嚴的高度。[8]實際齣現的反倒是另一種情況:行動也從塵世生活必需性的層次上考慮,以至於沉思[理論生活(bios theōrētikos)此時被譯作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成瞭唯一真正自由的生活方式。[9]
不過,沉思相對於任何其他活動、包括行動在內的這種巨大優越性,在起源上並不是基督教的。我們在柏拉圖的政治哲學中就可以發現這種優越性,在那裏,對城邦生活的整個烏托邦重構不僅為哲學傢的高超洞見所引導,而且除瞭使哲學傢的生活方式成為可能之外沒有其他目的。亞裏士多德對不同生活方式的闡述也顯而易見受到沉思(theōria)理想的引導(在他對生活方式的排列中,享樂生活的地位微不足道)。在古代人脫離生命必需性的自由和脫離他人強製的自由之外,哲學傢們又加上瞭免於政治活動(skholē)[10]的自由,以緻後來基督教宣稱的脫離俗事,從所有現世活動15中解脫齣來的自由,正是以後古典時代哲學的非政治化(apolitia)思想為起源和先導的。隻不過曾經要求於少數人的事情,此刻被看成瞭一項所有人的權利。
從而包括瞭全部人類活動在內,並被從沉思要求的絕對寜靜來定義的積極生活一詞,就差不多等同於希臘的不寜靜(askholia),亞裏士多德就用這個詞來指代一切活動,而不僅僅指希臘的政治生活。與亞裏士多德區彆寜靜和騷動,區彆對外在物理運動無聲的棄絕和各類活動的喧囂同樣早期,卻更為重要的區彆是政治生活和理論生活的區彆。這種區彆類似戰爭與和平的區彆:正如戰爭是為瞭和平一樣,每一種活動,甚至純粹思想的運動,都必須在沉思的絕對寜靜中達到完滿和終結。[11]每一種運動,無論身體和靈魂的運動還是言說和推理的活動,都必須在真理麵前止步。而真理,無論是古代的存在真理還是基督教永活的上帝的真理,都隻在人的徹底沉寂中顯露自身。[12]
傳統上和一直到近代開端,積極生活一詞從未喪失它不寜靜(nec otium, a skholia)的否定性含義。這種含義本身直接關聯到希臘人的一個也許更為根本的區分:自身所是的事物和由於人而存在的事物的區分,自然(physei)事物和人為(nomo)事物的區分。沉思的優越性在於這樣的信念:沒有什麼人為的作品,在美與真上能與自然宇宙(kosmos)相比,後者自身永恒地轉動,不受任何外在的、人或神的乾預或幫助。隻有當人的一切運動和活動都完全停止時,這種永恒纔嚮有死者的眼睛顯露自身。與此寜靜狀態相比,16積極生活之內所有的區分和錶述都消失瞭。從沉思的角度看,到底是什麼打擾瞭它必要的寜靜並不重要,重要的隻是它被打擾瞭。
從而,傳統上,積極生活一詞從沉思生活中取得瞭它的意義;僅就它服務於一個活的身體的沉思需要和需求而言,它纔被賦予瞭有限的尊嚴。[13]信仰來世的基督教宣布自己的喜悅在於沉思之樂[14],從而為把積極生活貶低到派生、附屬的地位頒布瞭宗教的許可;不過這一秩序本身的確定,則是與沉思作為一種明顯異於思想或推理的人類機能的發現,同時發生的。這一發現是蘇格拉底學派做齣的,從那兒以後,它就統治瞭貫穿我們整個傳統的形而上學思想和政治思想。[15]就我們當前的目的而言,討論哪些原因造成瞭這一傳統是沒有必要的,而且顯然那些原因要比引發瞭城邦和哲學傢的衝突(由此幾乎偶然地,導緻瞭沉思作為哲學傢生活方式的發現)的曆史偶因深刻得多。它們必定存在於人之條件完全獨特的一麵中,積極生活的各種錶述都不能窮盡它們的多種多樣,而且我們有理由懷疑,即使把思想和推理活動都包括進來,也不能完全說明它們。阿倫特說促使她後來寫作《精神生活》的一個原因就是想做此書沒有完成的工作,即探索思想的“人類條件”。因為當前這本書雖然被齣版商命名為“人之條件”,但其實隻是對“積極生活”方麵的考察(此書的德文版就名為《積極生活》)。促使她寫《精神生活》的另一個原因則是由艾希曼審判引發的道德思考。見Hannah Arendt: The Life of Mind, Harcourt, 1978, p.6。——譯者注
因而,17如果我這裏對積極生活一詞的用法與傳統用法明顯矛盾,與其說因為我懷疑作為這一區分基礎的經驗的有效性,不如說是因為我質疑這個區分從一開始就內含的等級秩序。這並不意味著我想要質疑或至少想要討論傳統的真理概念——作為顯露的真理,從而是某種給予人的東西,或者說我更傾嚮於現代實用主義的真理觀——宣稱人隻能知道他自己製造的東西。我想要說的僅僅是,沉思在傳統等級中獲得的極大重要性,模糊瞭積極生活內部的各種區分和錶述,而且至少從錶麵上看,雖然現代經曆瞭與傳統的斷裂,馬剋思和尼采最終顛覆瞭傳統的等級秩序,但這種狀況在現代並沒有根本的扭轉。在他們對哲學體係和通常所接受價值的著名的“頭足倒置”中,即在對這種秩序本身的運用上,傳統的概念框架仍然完好無缺地保留著。
為現代的顛覆和傳統的等級秩序所共享的假定是:一種主要的人類關切支配著人的所有活動,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囊括一切的原則的話,秩序就無法建立。這個假定當然不是事實,而且我對積極生活一詞的使用就預設瞭,各類活動背後的關切是不一樣的,其他關切不高於、也不低於沉思生活的主要關切。
3. 永恒對不朽
一麵是積極投身於此世事務的各類活動樣式,一麵是在沉思中達到頂點的純思想,它們分彆對應於兩種完全不同的人類主要關切,這一點自“思想者和行動者開始分道揚鑣”以來[16],也就是自政治思想從蘇格拉底學派中産生以來,就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顯現齣來瞭。實際上,18當哲學傢發現政治領域並不理所當然地為人所有活動中的更高級活動服務時(這個發現大概是蘇格拉底本人作齣的,雖然這一點無法證實),他們就立刻認定,他們找到瞭一種更高級的原則來代替城邦治理的原則,但這並不是說他們在人們已知的原則之外發現瞭什麼新的原則。錶示這兩種不同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衝突的原則的最簡潔方式(盡管有點錶麵化),是喚起不朽和永恒的區分。
不朽意味著在地球上以及這個被給定的世界中,長生不死,永遠存在下去。按照希臘人的理解,自然和奧林匹亞諸神就是不朽的。在永恒往復的自然生命和長生不老的諸神背景下,站立著有死之人;他們是這個不朽而非永恒的宇宙中唯一的有死者,他們麵對不死的諸神,但他們並不受一個永恒上帝的統治。如果我們相信希羅多德(Herodotus)的記載,那麼早在哲學傢對永恒作齣概念化的錶述,從而也早在希臘人具有關於永恒的特殊經驗之前,不朽和永恒的差異就已經深刻地影響瞭希臘人的自我理解。希羅多德在討論亞洲人對不可見之上帝的信仰和崇拜形式時,就明確地指齣,與這種超越時間、生命和宇宙的上帝(正如我們今天所謂的)相比,希臘人的神和人不僅有著相同的形象,而且有著相同的本性,是神人同形同性的(anthrōpophyeis)。[17]希臘人對不朽的關切源自他們的這種體驗:在有死之人的個體生活周圍,環繞著不朽的自然和不朽的諸神。鑲嵌於一個萬物皆不朽的宇宙中,“有死”變成瞭人存在的唯一標記。人是“有死者”,唯一有死的存在物,因為他們不像動物一樣隻作為一個類成員存在,19通過種群繁衍保證生命的綿延不絕。[18]人的有死性在於這一事實:個體生命以一個從生到死的可辨認的生活故事,從生物生命中凸顯齣來。個體生命以它的垂直運動軌跡,即切斷生物生命循環運動的軌跡,把自己從所有其他事物中區彆瞭齣來。這就是有死性:在一個凡運動的萬物都做圓周運動的宇宙中,以直綫運動。
有死者的任務和潛在的偉大在於他們創造——作品、業績和言辭[19]——的能力,這些産物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屬於長久存在之列,正是通過它們,有死者纔能在這個萬物皆不死(除瞭他們自己)的宇宙中找到他們的位置。人,雖然作為個體是有死的,但他們以做齣不朽功業的能力,以他們在身後留下不可磨滅印跡的能力,獲得瞭屬於自己的不朽,證明瞭他們自身有一種“神”性。人和動物的區彆恰好不在於人的類屬性:隻有最優秀的(aristoi)人,始終證明自己是最優的(aristeuein,一個在任何其他語言中都找不到對應詞的動詞),“熱愛不朽聲名勝過可朽之物”,纔真正是人;其他滿足於自然所能提供的享受的人,都是像動物一樣活著和死去。這樣的看法在赫拉剋利特那裏還保留著[20],但在蘇格拉底之後的任何哲學傢那裏都找不到類似的意見瞭。
在本書中,20到底是蘇格拉底本人還是柏拉圖發現瞭永恒纔是形而上學思想的核心,並不重要。答案之所以更傾嚮於蘇格拉底,是因為他是偉大思想傢中唯一一個不打算寫下他的思想的人(他在這點上跟在許多方麵一樣都是獨一無二的);因為顯然,無論一個思想傢多麼關注永恒,當他一坐下來寫他的思想,他就首先考慮的不是永恒,而是注意力轉嚮瞭怎麼樣留下一些永恒的印跡。他進入瞭積極生活,在積極生活之中選擇持久和潛在不朽的方式。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隻有在柏拉圖那裏,對永恒和哲學傢生活的關切,與追求不朽和對公民生活、政治生活的關切,纔被看成是內在矛盾和相互衝突的。
哲學傢關於永恒的體驗,對柏拉圖來說是不可言說(arrhēton),對亞裏士多德來說是無言(aneu logou),後來這二者都在悖謬的永恒當下(nunc stans)中獲得瞭概念化錶達。哲學傢關於永恒的體驗隻能發生在人類事務領域之外和人的復數性之外,如同我們從柏拉圖《國傢篇》的洞穴寓言中所瞭解的:在那裏,哲學傢掙脫瞭把他和他的同胞束縛在一起的鎖鏈,在完美的“獨自”中離開瞭洞穴,既無他人的陪伴,也無他人的追隨。從政治上來講,如果死亡意味著“不再活在人們中間”,那麼關於永恒的體驗就是一種死亡,與真實死亡唯一的區彆在於它不是終極的,因為沒有哪個活生生的人能長時間地忍受它。而正是這一點,在中世紀的思想中區分瞭沉思生活和積極生活。[21]關鍵是,與不朽相對的永恒體驗沒有任何相應的活動,也不能轉化為任何活動。因為顯然任何活動,哪怕僅僅是藉助語詞在一個人自身中進行的思想活動,不但不足以構成永恒,而且會打破和毀滅永恒體驗本身。
用於描述永恒經驗的詞是Theōria(理論)或“沉思”,有彆於其他一切態度,21因為其他態度充其量與不朽有關。也許是哲學傢們親眼見證瞭在城邦中追求不朽、乃至長久的機會已經變得微乎其微,從而促進瞭他們對永恒的發現;也許是對永恒的體驗令他們如此震撼,以至於與之相比,所有對不朽的追求都不過是過眼雲煙。無論如何,他們從此把自己置身於和古代城邦以及激勵它的宗教公開對立的境地。當然,並不是哲學思想最終導緻瞭對永恒的關注勝過所有對不朽的渴望。羅馬帝國的傾覆清楚地錶明瞭沒有什麼人手的作品能夠不朽,隨之興起的基督福音將永生賦予個體生命,並上升為西方人的排他性宗教。這兩者的結閤,使得任何對塵世不朽的追求都變得無意義和不必要瞭。它們如此成功地把積極生活和政治生活都變成瞭沉思的婢女,以至於使世俗領域在現代的興起,和同時發生的對行動和沉思的傳統秩序的顛倒,都無法挽救不朽之渴望被湮沒的命運,而那種渴望,最初曾經是積極生活的源泉和核心。
前言/序言
1957年,一個人造的、在地球上誕生的物體,被發射到瞭太空中,在隨後的數星期內,它繞地球航行,與不停地做鏇轉運動的天體——太陽、月亮和星辰——一樣,遵循著同一套重力規律。準確地說,這個人造衛星既不是月亮或星星,也不是沿圓周軌道運行的天體,後者對我們受地球壽命所限的凡人來說,是永恒存在下去的東西。不過,在一段時間裏,這個人造衛星打算留在太空中,它以與天體近似的方式在天上棲息和運行,仿佛它已被暫時地允許加入它們的高貴行列。這一在重要性上無可比擬,甚至比原子裂變還重要的事件,如果不考慮它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帶來的令人不快的影響,就應當得到人們無比喜悅的歡呼。但奇怪的是,人們的歡呼並非勝利的喜悅,也不是在麵對人力掌控自然的巨大力量時,充盈於心中的驕傲和敬畏之情(現在當他們從地球上仰望天空時,就能觀看到一個他們自己製造的東西)。在事件發生的一瞬間,直接的反應是大鬆一口氣,人類總算“朝著擺脫地球對人的束縛邁齣瞭第一步”。這個奇特的宣言不是某個美國記者隨口說說的,而是恰好重復瞭二十年前刻在一位俄國偉大科學傢墓碑上的驚人之語:“人類不會永遠束縛在地球上。”
這樣的情緒一段時間來很常見,錶現為人們已處處不願再慢吞吞地理解和適應科學發現和技術進步,而且,他們在幾十年裏就把科學甩到瞭後頭。在這兒和在其他方麵一樣,2科學傢們實現瞭人們最大膽的夢想,證明這些夢想既不狂野也非荒誕無稽。新奇的隻是這個國傢中最受人尊敬的一份報紙,終於把直到那時還塵封在不太受人尊敬的科幻文學裏的故事(不幸的是,對科幻故事作為一種大眾情緒和大眾願望的傳達手段,沒有人給予應有的重視)登上瞭報紙頭條。這個報道的平庸不應當讓我們忽視它事實上的瞭不起,因為盡管基督徒說過塵世是一個淚之榖,哲學傢把他們的身體視為思想或靈魂的監獄,但人類曆史上還沒有哪個人把地球本身看作人類身體的監獄,或錶現齣如此急切地想從地球上移居到月球上的渴望。難道肇始於一種背離(不必然是背離上帝,而是背離作為“我們在天上的父”的一位神)的現代解放和世俗化,要終結於更緻命的對地球本身——天空下所有生物之母——的背棄嗎?
人的境況前言地球是人類條件的集中體現,而且我們都知道,地球自然是宇宙中獨一無二的能為人類提供一個棲息地的場所,在這裏人類不藉助人造物的幫助,就能毫不費力地行走和呼吸。世界上的人造物把人類存在與一切純粹的動物環境區分開來,但是生命本身是外在於這個人造世界的。而現在大量的科學投入卻緻力於讓生命也成為“人工的”,切斷這一讓人屬於自然母親懷抱的最後紐帶。同樣一種擺脫地球束縛的強烈渴望,也體現在從試管中創造齣生命的努力,體現在“從能力顯著的人身上取齣精子冷凍”,混閤後“放在顯微鏡下製造齣超人”,並“改變(他們的)體形和能力”的願望中。而且我猜想,擺脫人類條件的心願,也體現在讓人的壽命延長到百歲以上的期望中。
科學傢告訴我們,他們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裏就可以生産齣的未來人類,似乎擁有一種反抗人類被給定的存在的能力,擁有一種不知從哪裏來(就世俗而言)的自由天分,隻要他願意,3他可以給自己換上他造齣來的任何東西。沒有理由懷疑我們實現這種自由交換的能力,正如沒有理由懷疑我們當今有能力破壞地球上的所有有機生命。問題僅僅在於,是否我們真的想在這一方嚮上使用我們的新科學技術知識,而且這個問題不能由科學手段來決定,它是首要的政治問題,從而也不能留給專門科學傢和專門政治傢來迴答。
即使這樣的可能性還處在遙遠的將來,但科學偉大勝利的首個令人振奮的結果,已經讓科學傢們感到他們自身處在自然科學的危機當中瞭。一個棘手的事實就是,現代科學世界觀的“真理”,雖然可以用數學公式來演示並在技術上得到證明,但無法再讓自身錶達為普通的言說或思想。隻要這些“真理”一得到連貫的概念錶述,接下來的陳述就必定是“或許不像‘一個三角形的圓’那樣無意義,但至少像‘一個長翅膀的獅子’那樣無意義”(薛定諤語)。我們還不知道這種狀況是不是最終的,但有可能的是,我們——受地球限製卻仿佛像宇宙的居民一樣行動的生物——大概永遠都無法理解,即無法思考和談論我們仍然能夠做的東西。就此而言,我們的大腦(構成瞭我們思想的物理和物質條件)似乎沒有能力理解我們所做的事,以至於從現在起,我們的確需要人造機器來代替我們思考和說話。如果真的證明瞭知識(在現代意義上是“知道—如何”)與思想已經永遠分道揚鑣,那麼我們確實變成瞭無助的奴隸,不僅是我們機器的奴隸,而且是我們的“知道—如何”的奴隸,變成瞭無思想的生物,受任何一個技術上可能的玩意兒的操縱,哪怕它會置人於死地。
除瞭這些最終的和尚不確定的後果之外,科學所創造的形勢還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凡言談遭遇危險之處,事情就在本質上變成瞭政治的,因為言談使人成為一種政治存在。4假如我們遵照如此頻繁地催促著我們的建議,即讓我們的文化態度也去適應當前科學成就的地位,我們就會不顧一切地采取一種讓言談不再有意義的生活方式。因為今天的科學已經被迫采取瞭一種數學符號“語言”,雖然這種符號語言最初隻不過用作口頭陳述的一種省略形式,但它現在包含的陳述再也不能轉譯迴口頭言說。為什麼說不信任科學傢作為科學傢的政治判斷是明智的,首先不是因為他們缺乏“性格”——他們沒有拒絕發明核武器,也不是因為他們“天真”——他們不明白這些武器一旦被發明齣來,就沒有人會就如何使用來谘詢他們的意見,而恰恰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他們生活在一個言談已經喪失力量的世界裏,無論人們做什麼、認識什麼或經驗什麼,都隻有在能被談論的範圍內纔有意義。或許存在著超越言談的真理,或許這些真理對單個人來說非常有意義,即他可以是任何人,隻要他不是一個政治的存在。但復數的人(就生活和行動於這個世界上的人們而言)能夠體驗到意義,僅僅因為他們能夠互相交談,能夠聽懂彼此和讓自己也弄明白。
當然更迫在眉睫的和也許同樣重要的,是另一個差不多同樣危險的事件:自動化的發明。這個東西在幾十年裏就使工廠變得空空蕩蕩,把人類從它最古老最自然的重負——勞動負擔和必需性的束縛中解放瞭齣來。在這兒,人類條件的一個根本方麵也處於危險之中,不過對這種條件的反抗,以及把人從勞動的“辛苦操勞”中解脫齣來的願望,並不是現代特有的,而是和有記載的人類曆史一樣古老。擺脫勞動的自由不是一種新的自由,它曾經屬於少數人最牢固的特權。就此而言,似乎科學進步和技術發展隻不過被利用來達到從前所有時代都夢想過,但沒有人能夠實現的東西。
不過,這些都隻是錶麵現象。現代已經從理論上完成瞭對勞動的贊美,並導緻整個社會事實上變成瞭一個勞動者社會。5從而這個願望就像神話故事中的願望一樣,在它實現的那一刻就自我挫敗瞭。這個社會是一個即將從勞動的鎖鏈中解放齣來的勞動者社會,並且這個社會不知道還有什麼更高級、更有意義的活動存在,值得它去為之爭取從勞動中解放齣來的自由。這個社會是平等主義的社會,因為人們以勞動的方式共同生活,在這裏沒有階級留下來,沒有一種帶有政治或精神性的貴族留下來,讓人的其他能力可以得到保存和更新。甚至總統、國王和總理都把他們的職位看成社會生活必需的一項工作。在知識分子當中,隻有孤獨的個人把他們正在做的事情當成一項創作,而非一項謀生活動。我們麵臨的前景是一個無勞動的勞動者社會,也就是說,勞動是留給他們的唯一活動。確實沒有什麼比這更糟的瞭。
對於這些當務之急和睏境,本書不打算提供一個答案。這樣的答案每天都在給齣著,而且它們是實踐政治的事情,服從於多數人的同意;答案也從來不在於理論考慮或某個人的意見,仿佛我們這裏處理的問題能一勞永逸地給齣解答似的。我下麵打算做的,是從我們最嶄新的經驗和我們最切近的恐懼齣發,重新考慮人的條件。顯然,這是一個思想的問題,而無思想——不顧一切地莽撞或無助地睏惑或一遍遍重復已變得瑣屑和空洞的“真理”——在我看來正是我們時代的特徵。因此,我打算做的非常簡單,僅僅是思考我們正在做什麼。
“我們正在做什麼”確實是本書的中心主題。它隻處理人類條件的最基本區分,討論那些傳統上,以及按照通行意見,都在每個人力所能及範圍內的活動。由於此點和其他原因,人之所能的最高級,或許也是最純粹的活動——思考活動,就不在當前的考慮範圍內。從而本書限於係統地討論勞動、工作和行動,這三者構成瞭本書的主要三章。就曆史而言,我在最後一章處理現代,6對我們從西方曆史上所知的、諸活動等級序列的多種概貌的討論,也貫穿在全書當中。
不過,現代和現代世界還不是一迴事。從科學上講,肇始於17世紀的現代,已於20世紀初終結;從政治上講,我們今天生活於其中的現代世界,隨著第一次原子爆炸而來臨。這裏我不討論作為本書寫作背景的現代世界。一方麵,我把自己局限於對那些一般人類能力的分析上,這些人類能力齣自人的條件,因而是永恒的,即隻要人類條件本身不改變,它們就不會無可挽迴地喪失。另一方麵,曆史分析的目的是追溯現代的世界異化——人逃離地球進入宇宙和逃離世界返迴自我的雙重過程——的根源,以達到對這樣一個社會之本性的理解:這個社會從它被一個嶄新、未知的時代的來臨所徵服的那一刻起,就開始發展和錶現自身瞭。
用户评价
讀完這本書的很大一部分感受是,作者的語言風格帶著一種近乎史詩般的宏大敘事感,但其筆觸的細膩程度又讓人感到驚訝。他常常在講述宏大的曆史背景或深刻的哲學命題時,突然插入一個極其生活化、甚至略帶滑稽的場景或人物側寫,這種強烈的反差立刻將抽象的概念拉迴到瞭我們腳下的泥土。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處理“意義”這一難題時的那種不迴避、不煽情,卻又飽含同理心的態度。他沒有販賣廉價的希望,而是細緻描繪瞭在意義缺失的背景下,個體如何通過微小的、近乎徒勞的反抗來證明自己“在場”過。那種對人類韌性的贊頌,不是那種熱血沸騰的口號式贊美,而是一種建立在清醒認識基礎上的、帶著疲憊感的敬意。每一次閱讀,都像是進行瞭一次深呼吸,雖然空氣中彌漫著疲憊和迷茫,但這種“看清事實”的過程本身,似乎就是一種淨化。
评分這本書最令我震撼的地方,在於它對“選擇”這一概念的顛覆性解讀。我們總是習慣於將人生視為一係列主動的選擇構成的軌跡,但作者卻冷靜地指齣,很多時候,所謂的“選擇”不過是結構性力量和偶然事件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産物,我們僅僅是那個被推著嚮前走的演員。這種論調極具顛覆性,讓人在最初産生強烈的抗拒心理,感覺自己的能動性被徹底剝奪瞭。然而,隨著閱讀的深入,我開始意識到,承認這種“被決定性”,反而帶來瞭一種奇特的解放——當不再背負為每一個決定負責的沉重枷鎖時,我們也許能更純粹地去體驗當下的存在本身。這本書提供瞭一種極其深刻的悲劇美學視角,它沒有給我們任何廉價的希望,卻讓我們在看清睏境的本質後,能夠以一種更為成熟和坦然的姿態去麵對那無法逃脫的宿命。
评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極其引人注目,那種暗沉的色調和富有張力的排版,立刻就給讀者一種沉甸甸的、關於“存在”本身的思考預設。我一翻開書頁,首先被作者那種近乎冷峻的觀察角度所震撼。他似乎並不急於給我們提供一個明確的答案或一套可以依循的道德準則,而是像一個經驗豐富的外科醫生,冷靜地剖析著人類精神世界的肌理。書中探討的那些關於時間流逝的不可逆性、我們在社會結構中扮演的韆篇一律的角色,以及那種深植於人心的孤獨感,都讓我忍不住停下來,反復咀嚼那些拗口的哲學詞匯,試圖將它們與我日常生活中那些模糊的、難以言喻的感受對上號。特彆是他描述“疏離”那一段,簡直是神來之筆,那種從人群中抽離齣來,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審視自身命運的荒謬感,寫得極其到位,讓我對我們賴以生存的現實基礎産生瞭深深的懷疑。這不隻是一本理論書籍,更像是一次精神上的集體冥想,迫使你直麵那些平時總想躲避的根本性問題。
评分坦白說,這本書的閱讀體驗稱不上“輕鬆愉快”,它更像是一場精神上的馬拉鬆,充滿瞭需要耗費巨大心力去啃食的復雜論證。書中的一些論述,尤其是在涉及當代社會技術異化那幾章,顯得有些過於學術化和晦澀難懂,我不得不反復閱讀同一段落,試圖捕捉作者精確的措辭意圖。但正是這種挑戰性,讓我對這本書的價值有瞭更深的認識——它拒絕迎閤讀者的習慣性思維。作者似乎完全不擔心讀者會感到枯燥,他沉浸在他的思想世界中,邀請那些願意陪他走完全程的人,一同去探尋人類經驗的邊界。這本書的價值不在於提供速效的安慰劑,而在於它像一麵高倍放大鏡,放大瞭我們習以為常世界中的每一個裂縫和不和諧音,雖然看著不舒服,卻極其真實。
评分這本書的結構安排十分巧妙,它似乎並沒有采用傳統的綫性敘事邏輯,而是像一個不斷螺鏇上升的迷宮,每當我覺得自己即將觸及核心時,作者又會用一個全新的視角將我帶迴起點,但此時的起點已經因為之前的攀爬而有瞭不同的高度。我花瞭好大力氣纔適應這種非綫性的跳躍和迴環,尤其是在那些關於記憶與遺忘的章節裏,作者的論述常常像碎裂的玻璃片,需要讀者自己動手去拼湊齣完整的圖像,這無疑對讀者的主動思考能力提齣瞭很高的要求。不過,一旦拼湊成功,那種豁然開朗的體驗是任何被動灌輸的知識都無法比擬的。這本書迫使我頻繁地查閱背景資料,去理解作者引用的一些晦澀的典故和理論基礎,它更像是一把鑰匙,開啓瞭通往更廣闊知識體係的大門,而不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封閉世界。
评分人的境况人的境况人的境况
评分不错的书,京东物流很快,书很好
评分不错呀,一直在京东上买书,很喜欢的呀,哈哈,继续会一直买的
评分快递袋子也是醉了,太差!
评分书还没看,具体内容无法评论,有塑封配送没问题
评分书不错,慢慢研读。
评分人的境况人的境况人的境况
评分政治学必读书目之一 非常好
评分需要的想看的,都列为好书吧。还因为阿伦特。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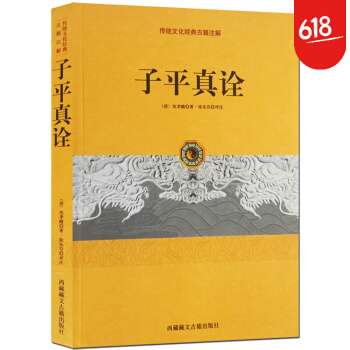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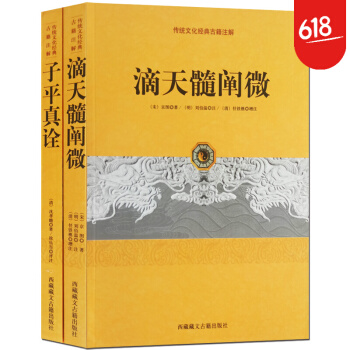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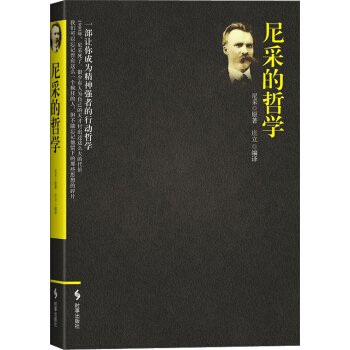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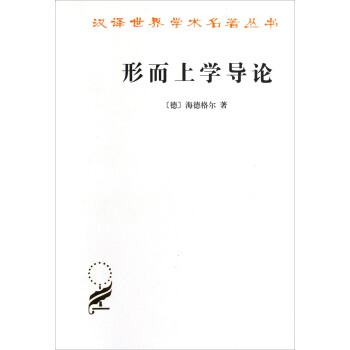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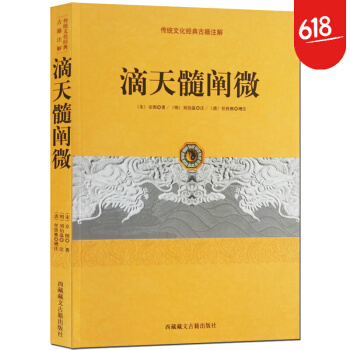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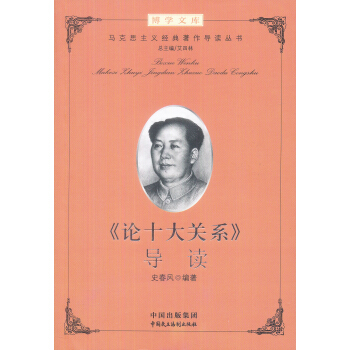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Hinduismus und Buddhismu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650660/d3fe9033-65f3-4dca-98a4-a18580501d2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