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鄭振鐸被遺忘的傑作,生命力經久不衰的新詞史
內容簡介
本書是20世紀30年代鄭振鐸計劃撰寫的《中國文學史》之一部分,作者將詞的起源與漢唐的樂府掛鈎,按照中晚唐詞、五代詞、敦煌捲子中所見詞和變文、北宋詞、南宋詞的順序,梳理瞭詞作為文學形式的産生、發展、極盛乃至最終形成固定體例的過程。每講一個時代,鄭振鐸都會引用大量詞作,以形象細緻的語言闡明各時期詞風的不同,以及詞在當時取得瞭怎樣的新發展。由於鄭氏有縱貫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史的雄心,又有不凡同時儕輩的眼光,他在這部詞史中提齣瞭很多創見,有些觀點至今仍有學術價值。可惜的是,由於曆史原因,本書被學術界長期遺忘,甚至連作者本人及親屬也不復記憶。直至本次整理齣版,這部傑齣的文學史著作纔得以重新與讀者見麵,可謂難得的機緣。
作者簡介
鄭振鐸(1898-1958),福建長樂人,我國現代傑齣的作傢、詩人、學者、翻譯傢、收藏傢,中國現代文博事業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並開始發錶作品,與瀋雁冰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曾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小說月報》主編、上海大學教師、《公理日報》主編等職。1927年旅居英、法。迴國後,曆任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暨南大學等校教授,。1937年參加文化界救亡協會,與鬍愈之等人組織復社,主編《民主周刊》。1949年後,曾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副主席,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等職。鄭氏生平著作甚多,文學史領域的專著有《文學大綱》《中國文學史》《中國通俗文學史》《中國文學論集》《俄國文學史略》等多種,另著有短篇小說集《傢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雜記》等。
目錄
第一章詞的起源(1)第二章五代文學(31)
第三章敦煌的俗文學(92)
第四章北宋詞人(154)
第五章南宋詞人(243)
後記(339)
精彩書摘
第一章詞的起源一
六朝樂府的生命自經瞭晉隋至唐中葉的一個長時期之後,便盛極而衰。到瞭五代之時,歌唱者皆尚“詞”。歐陽炯所謂“則有綺筵公子,綉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縴縴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花間集》序。。正足以見當時的盛況。至宋則流傳更廣,上自朝廷,下至市井,嫻雅如文人學士,豪邁如武夫走卒,無不解歌者。詞的流行真可謂“至矣,甚矣,衊以復加矣”。但到瞭後來,詞也漸漸成為不可歌瞭。僅足資紙上之唱和,不復供宴前的清歌,僅足為文人學士的專業,不復為民間俗子所領悟;語益文,辭益麗,離民間日益遠,於是遂有“麯”代之而興,而詞的黃金時代便也一去而不復迴。
二
在未說到本文之前,有一點是不可不先說明白的,即詞與五七言詩之間是不發生什麼關係的。她的發展,也並不妨礙到五七言詩的發展。她與五七言並沒有相繼承的統係。這正與六朝時代的樂府一樣。樂府也是與五言詩平行發展起來的。他們各走著一條路,各不相乾,也各不相妨。在文體的統係上說起來,詞乃是六朝樂府的同類,卻不是五七言的代替者。我們曉得,詩歌有兩種。一種是可歌的,一種是不可歌的。可歌的便是樂府,便是詞,便是麯;不可歌的便是五七六言的古律詩。不可歌的詩歌,係齣於不必有音樂素養的文人之手,隻以抒情達意為主,並沒有另外的目的;可歌的詩麯,其目的,一方麵是抒寫情意,一方麵卻是有瞭一種自娛或娛人的應用目的的。他們有的為宗廟朝廷的大樂章,有的為文人學士傢宴春集的新詞麯,有的則為妓女階級娛樂顧客的工具。因此,不可歌的詩歌,其發展是一條綫下去的;可歌的詩歌,其發展便跟隨瞭音樂的發展而共同進行著。音樂有瞭變遷,他們便也有瞭變遷。漢人樂府不可歌瞭,便有六朝樂府代之而起,六朝樂府不可歌瞭,便有詞代之而起,詞不可歌瞭,便有南北麯代之而起。雖然在樂府詞麯已成為不可歌之物之時,仍有人在寫樂府詞麯,那卻是昧於本意,迷戀於古物的文人們所做的不聰明的事。例如,許多人以詞為“詩餘”,便是一個構成這種錯誤的實證。瀋括的《夢溪筆談》說: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麯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弦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麯中,不復用和聲。硃熹也說:古樂府隻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瞭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麯子便是。
——《硃子語類》百四十他們這個主張影響很大。《全唐詩》第十二函第十冊,在“詞”之題下,亦注道:唐人樂府原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並和聲歌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麯拍者為填詞。方成培的《香研居詞麈》也這樣的主張著:“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雜以散聲,然後可被之管弦。如陽關必至三疊而後成音,此自然之理也。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興焉。”這幾個人的見解都是以詞為“詩餘”,為由五七言詩蛻變而成的。這種見解,其主要的來因,乃誤在以唐人所歌者胥為五七言詩。我們且看,唐人所歌者果盡為五七言詩乎?王灼的《碧雞漫誌》說:“唐史稱李賀樂章數十篇,諸工皆閤之管弦。又稱李益詩每一篇成,樂工慕名者爭以賂取之,被諸聲歌,供奉天子。舊史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見於樂府。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旗亭畫壁,伶官招妓聚宴。以此知唐之伶妓以當時名士詩詞入歌麯,皆常事也。”然既雲“閤之管弦”,既雲“往往見之樂府”,則可見五七言詩的入樂乃是偶然的事,並不是必然的事。文人既以詩篇入樂為可誇耀的事,則五七言詩篇之不常入樂,更為可知。按崔令欽的《教坊記》,共錄麯名三百二十五;又《詞律》所錄者凡六百六十餘體;又《欽定詞譜》所錄者凡八百二十六調。在這許多麯調中,據《苕溪漁隱叢話》,則在宋時“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闋,是七言八句詩並七言絕句詩而已”。而統唐、宋能歌與否的詞體而總計之,也隻有《怨迴紇》《紇那》《南柯子》《三颱令》《清平調》《欸乃麯》《小秦王》《瑞鷓鴣》《阿那》《竹枝》《柳枝》《八拍蠻》諸麯而已。以這許多絕非五七六言古律絕詩的詞調,乃因瞭偶有寥寥幾首的閤於五七六言古律絕詩的詞式,便以為她是齣於五七六言詩的,真是未免太過武斷瞭。《舊唐書·音樂誌》說:“太常舊相傳,有宮商角徵羽宴樂五調歌詞各一捲。或雲貞觀中侍中楊仁恭妾趙方等所詮集。詞多鄭、衛,皆近代詞人雜詩。至縚(韋縚)又令太樂令孫玄成更加整比為七捲。”但他們所集的,“工人多不能通”。工人所通的卻是另外的一種新的麯調,嶄新的麯調;這種嶄新的麯調便是詞,便是代替六朝樂府而起的新歌麯的詞。成肇麐說:十五國風息而樂府興,樂府微而歌詞作,其始也皆非有一成之律以為範也。抑揚抗墜之音,短修之節,連轉於不自已,以蘄適歌者之吻。而終乃上躋於雅頌,下衍為文章之流彆。詩餘名詞,蓋非其朔也。唐人之詩未能胥被弦管,而詞無不可歌者。
——《七傢詞選序》他這話確能看齣詞的真正來源來。王應麟的《睏學紀聞》裏有寥寥的幾句話:“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麯者,古樂府之末造也。”這幾句話也恰是我們所要說的。但“樂府之末造”一語,卻頗有語病。詞是代替樂府而起的可歌之詩歌,卻不是樂府的末造,也不是樂府的蛻變。她是另有其來源的。
……
前言/序言
導言陳福康
在“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史上,鄭振鐸是發齣“要求一本比較完備些的中國文學史”呼籲的第一人;不僅如此,他還身體力行,很早就從事中國文學史的撰著工作。他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共齣版過四種中國文學史(或與中國文學史有關的)專著:一是《文學大綱》四大冊的中國部分(按,《文學大綱》實際是史上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學通史,其中約四分之一篇幅寫的是中國,已有學者指齣,《文學大綱》中國部分若獨立齣來,實是一部體係完整的中國文學史。不僅如此,我認為此書的中國文學部分,實際還是一九二○年代國內最優秀的一部中國文學史);二是《中國文學史(中世捲第三篇上)》按即本書原書名。——編者一冊,為斷代史性質;三是《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四冊,為通史性質;四是《中國俗文學史》二冊,為分類史性質。總計字數約一百五十萬字(《文學大綱》外國文學部分以及各書插圖所占篇幅均不算在內),又有非常高的學術價值,在新文學工作者中,以一人之力做齣如上成績的,沒有第二個人。
鄭振鐸的《文學大綱》《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三部書,幾十年來被眾多齣版社多次重印,學界幾乎無人不知。而那本《中國文學史(中世捲第三篇上)》,知道的人就很少瞭。那是怎樣的一本書呢?須從頭道來。
鄭振鐸於一九二三年下半年起,開始撰寫《文學大綱》。邊寫邊在《小說月報》上連載(其中有些補充章節則發錶於《一般》等刊物上),後交商務印書館齣版。第一冊於一九二六年底齣版,接著鄭振鐸因大革命失敗而避難歐洲,全書的跋即作於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赴法國的遠洋輪上。最後的第四冊是一九二七年十月齣版的。應該說,在《文學大綱》寫成和齣版以後,鄭振鐸就産生瞭再撰著一部詳盡的《中國文學史》的念頭。一九二八年六月,他從西歐迴國,應上海復旦大學等校之聘,講授中國文學史。同時,繼續主編《小說月報》。一開始,他已經公布要撰寫一部《西洋藝術史》以供《小說月報》連載,但後來撰寫《中國文學史》的欲望超過瞭寫《西洋藝術史》,以至後者終於未能寫齣,而從一九二九年三月號《小說月報》起,開始發錶《中國文學史》的“中世捲第三篇”。至年底,共發錶瞭五章。最早發錶的是第三章《敦煌的俗文學》,文末有鄭振鐸於一九二九年二月寫的附記,說明此章是“去年九月間匆促寫成”,可知他迴國不久就開始《中國文學史》的撰寫瞭。
這五章在《小說月報》上發錶後,鄭振鐸經過少許修訂,於一九三○年五月由商務印書館齣版單行本,書名為《中國文學史(中世捲第三篇上)》。作者在同年三月一日寫的該書《後記》中說:“全書告竣,不知何日,姑以已成的幾章,刊為此冊。我頗希望此書每年能齣版二冊以上,則全書或可於五六年後完成。”從這裏我們已可窺知原書計劃之宏大。但是,這個“中世捲第三篇上”是什麼意思呢?原書共擬分幾冊?由於全書僅齣版此一冊,後來作者在北平齣版《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時計劃已有更改,因此人們一直無從詳知。一直到我在鄭振鐸遺稿中幸運地看見瞭他在一九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此時該書已經付印)修訂的《中國文學史草目》,方纔解開瞭這個啞謎。
根據這個《草目》,我們知道鄭振鐸當時擬寫的《中國文學史》,上下五韆年,自上古(公元前三韆年)至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夕。共分“古代捲”“中世捲”“近代捲”三捲。從上古至西晉末年為古代捲,共分三篇,每篇各一冊;從東晉初至明中期正德年間為中世捲,共分四篇,每篇各二冊;明嘉靖初至“五四”前為近代捲,共分三篇,第一篇三冊,後二篇各二冊。這樣,全書共有十篇,約一百章,擬分十八冊齣版。大緻估計,全書完成將有三百萬字左右。這是何等氣勢磅礴的前無古人的文學史撰寫計劃!可惜的是,這個計劃最終未能完成。而其“中世捲第三篇”,內容是五代、兩宋期間的文學史,計劃分上下兩冊,已齣的此書即為上冊。上冊共五章,題目為:《詞的啓源》《五代文學》《敦煌的俗文學》《北宋詞人》《南宋詞人》。除瞭敦煌文學及五代文學中涉及的詩、散文等以外,主要講的都是有關“詞”的曆史,正如作者在此書《後記》中說的,“這一冊所敘者以‘詞’為主體”。因此,盡管此書作為斷代文學史(五代兩宋文學史)也僅成半部,令人不無遺憾;但卻頗有單獨存在的價值——可以當作一部詞史來讀。(宋以後,“詞”仍有一定的發展,但已趨衰落,影響小瞭。)
鄭振鐸在《文學大綱》中已經提齣,中古時期中國詩的發展可分為兩個時期,即詩(近體、律體)的時期與詞的時期,並將“自五代時‘詞’之一體的開始發展起,至宋元之間此種詩體之衰落為止”,稱作中世“第二詩人時代”。必須指齣的是,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鄭振鐸在《小說月報》上發錶《文學大綱》的有關章節,對詞史作瞭簡明的論述後,關於這一特殊詩體的發展史的研究,幾年來一直沒有什麼進展。在本書之前齣版的其他各種文學史中,雖然也提到瞭詞,但都很簡略。曾在報上指齣《文學大綱》幾處小誤,並稱也對宋詞研究深有興趣的鬍雲翼,在一九二六年齣版瞭專著《宋詞研究》,書中明確說明:“本書行世前,尚無此類專著”。鬍氏此書約十萬來字,除瞭通論部分外,主要是作傢評傳。鬍氏此書有一定學術價值,但作為通論、評傳尚可,卻顯然不是一本“詞史”。因為它主要是鑒賞、評述性質,而缺少曆史觀念。要論“詞史”的話,我們其實不能不推鄭振鐸《中國文學史(中世捲第三篇上)》為正式齣版的第一本。在鄭著此書問世後,有關詞史的專著纔開始多瞭起來,如一九三一年齣版瞭劉毓盤的《詞史》此書在一九二○年代曾作為北京大學講義,內部少量印行,約八萬餘字。,王易的《詞麯史》,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其第三冊專論詞與麯),一九三三年齣版瞭鬍雲翼的《中國詞史略》《中國詞史大綱》、鄭賓於的《中國文學流變史》(其下冊專談詞),等等。但是,從史料的豐富性與立論的正確性等方麵看,一九三○年代齣版的一些詞史似均未能超過鄭振鐸這本書。
此書約有十七萬字,其中專論詞的部分有十四萬字。(而《文學大綱》有關詞的部分的文字,不及這一字數的十分之一。)本書論及詞作者近二百名,引錄詞作約三百七十首,即使將這些詞作單獨抽齣作為一本“詞選”,也是相當豐富的瞭。由此可見本書的內容是相當詳贍的。而在見解上,書中更有不少獨創。
例如,關於詞的來源,《文學大綱》未及論述,本書則認為有“兩個大來源”,即“鬍夷之麯”與“裏巷之麯”,一個是西域來的,一個是取之民間的。作者不同意曆來認為詞是“詩餘”的說法,也不同意詞是“古樂府的末造”的說法,認為這些說法“是完全違背瞭文體的生長與演變之原則的”,也是不符閤史實的。他指齣:“詞自有它的來曆、它的發源、它的生命。”“它不是舊詩體的藉屍還魂,也不是舊詩體的枯楊生稊,更不是舊詩體的改頭換麵。新詩體是一種嶄新的東西。”它新就新在敢於大膽攝取域外文學與民間文學的養料,因此就“與五七言詩大異其麵目與性質”。關於中國文學接受外來影響與民間養料的問題,是當時的很多研究者所諱言或忽視的。鄭振鐸強調指齣這些,恢復瞭曆史的本來麵目,很有意義。本書第一章《詞的啓源》先在《小說月報》上發錶時,著名詞學傢、鄭振鐸的小學同學夏承燾就給予瞭很高的評價。夏承燾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日記:“閱《小說月報》二六六號鄭振鐸《詞的啓源》,謂詞與五、七言詩不發生關係。據《舊唐書·音樂誌》‘自開元以來,歌者雜用鬍夷裏巷之麯’句,謂‘裏巷與鬍夷之麯,乃詞之二大來源’。又謂依腔填詞,始於裴談、溫庭筠。以絕細膩之筆,寫無可奈何之相思離緒,始為文人之戀歌,而非民間之情麯。餘所見鄭君文字,此篇最不苟者矣。”近年,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古典文學研究室精選編集瞭一本一九一一年至一九四九年的《詞學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齣版社齣版),即收入鄭振鐸《詞的啓源》,並置於全書首篇。亦可見其學術價值。
關於詞的發展,書中認為大緻可分為四期。一是胚胎期,即“引入瞭鬍夷裏巷之麯而融冶為己有”的時期,這時的詞是有麯而未必有辭的。二是形成期,即“利用瞭鬍夷裏巷之麯以及皇族豪傢的創製,作為新詞”的時期,“麯舊而詞則新創”。三是創作期,即詞作傢“進一步而自創新調,以譜自作的新詞,不欲常常襲用舊調舊麯”,這時的麯與詞(辭)有一部分均是新創的。四是模擬期,即作傢“隻知墨守舊規,依腔填詞,因無彆創新調之能力,也少另闢蹊徑的野心”,“詞的活動時代已經過去瞭”。他認為唐初至開元天寶時為詞史發展的第一期,開元天寶至唐末為第二期,五代至南宋末為第三期,元初至清末為第四期。這是發前人未發的見解,與魯迅後來關於詞從興起到衰落的宏觀見解在精神上頗為一緻。鄭振鐸不僅從宏觀上將詞史分為四個發展期,在具體分析時他又將北宋詞的發展與南宋詞的發展分彆分為三個階段。他認為北宋詞經曆瞭從清雋健樸,到奔放雄奇,到循規蹈矩這樣三個階段;南宋詞則經曆瞭奔放,改進,凝固(雅正)這樣三個階段。他指齣,這些變化跟詞這一文體本身的發展規律、文人在其間所起的作用等有關;而且也跟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有關。例如,南宋詞第二階段以後漸趨僵化,就因為這時它“不僅與民眾絕緣,也且與妓女階級絕緣”,成為“差不多已不是民間所能瞭解的東西瞭”;這時的詞失去豪邁的氣概,也是當時統治階級“升平已久”“晏安享樂”的社會現象的反映。鄭振鐸的這些分析與見解,體現瞭卓越的史識,已可略見唯物史觀的星星光芒瞭。
書中通過獨立思考,對鬍適有關學術觀點作瞭爭鳴。例如,鬍適據《杜陽雜編》,以為《菩薩蠻》調齣於大中初,因此斷定相傳為李白所作的《菩薩蠻》決非真品。但鄭振鐸指齣,《菩薩蠻》一調實已見諸《教坊記》,鬍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亦提到開元時即有此調,因此李白當然有填寫此詞的可能。雖然,這到底是不是李白所作,至今尚無定論,鄭振鐸也沒有絕對肯定;但他強調指齣不能用孤證來推翻一切他證,這顯然比鬍適要慎重得多。鬍適還認為五代的詞都是無題的,因為其內容都很簡單,不是相思便是離彆,不是綺語便是醉歌,所以用不著什麼標題。鄭振鐸不同意這種皮相的看法,指齣:“花間詞人的作品,誠多詠離情閨思之作。然離情閨思之作,原是一切抒情詩中最多的東西,不獨花間詞為然。且這一期中,也不完全是離情閨思、宴席歌麯之作。”那麼,為什麼“無題”呢?他認為,這是詞創作初期的一種現象,“大多數的詞牌名,已是它們的題目瞭,它們的內容也和詞牌名往往是相閤的,所以更無需乎另立什麼題目。”例如,當時《更漏子》寫的便大多與更漏聲有關,《楊柳枝》便與楊柳有關,《天仙子》便與仙女有關,等等。發展瞭一段時間後,詞的內容與詞牌不大切閤瞭,但尚未完全離開詞牌所含的意思,例如《漁父》,填詞者未必直接歌詠漁傢生活,但仍含有該詞牌原有的鄙薄功名、甘隱江湖的意味。再發展到後來,內容與詞牌沒有必然的聯係瞭,這時纔必須另外再有一個題目。鄭振鐸的這些論述,顯微燭隱,無疑比鬍適高齣一籌。
在具體作傢作品分析評論中,書中也時有新見。例如,關於王安石在宋詞史上的地位,前人均無特彆的好評,鄭振鐸在《文學大綱》中也不過附帶一說而已。但此書中不僅肯定他在政治上變法圖強的精神,而且認為他正因為有這種精神,其詞“宜乎氣格與彆的詞人們不同”,盛贊其“脫盡瞭《花間》的習氣,推翻盡瞭溫、韋的格調、遺規,另有一種桀傲不群的氣韻”,“無論在格式上,在情調上”,都“大膽無忌的排斥盡舊日的束縛”。因此,鄭振鐸認為,王安石在詞史上的地位是“為蘇、辛作先驅,為第二期的詞的黃金時代作先驅”。這是非常獨到的創見,鄭振鐸自己也指齣,這是“很少人注意及之”的。書中對柳永的詞作瞭十分細緻的藝術分析,並將其與《花間集》作瞭藝術上的比較,指齣《花間集》的風格在於“不盡”,“有餘韻”;而柳永則在於“盡”,在於“鋪敘展衍,備足無餘”。他認為這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境界,不好隨便評其優劣;“但這第二種的境界,卻是耆卿(柳永)所始創的,卻是北宋詞的黃金時代的特色,卻是北宋詞的黃金期作品之所以有異於五代詞,有異於第一期作品的地方。所以五代及北宋初期的詞,其特點全在含蓄二字,其詞不得不短雋;北宋第二期的詞,其特點全在奔放二字,其詞不得不鋪敘展衍,成為長篇大作。當時雖有幾個以短雋之作見長的作傢,然大多數的詞人,則皆趨於奔放之一途而莫能自止。這個端乃開自耆卿。”這樣精闢的分析,在當時其他論著中極為少見。不僅說透瞭柳永詞的藝術特點,而且更進一步闡明瞭詞從前期到黃金時期轉化之際藝術風格上的變化脈絡,以及柳永在其間所起的作用等。
除瞭關於詞史以外,本書關於敦煌文學的論述在當時也是開創性的。陳子展對此就有高度評價。陳子展在一九二九年齣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第八章《敦煌俗文學的發見和民間文藝的研究(上)》之後,特地專門加瞭一段附記,指齣鄭振鐸此書《敦煌的俗文學》一章,“是介紹敦煌發見的俗文學最詳實而又最有見解的一篇文字”。並深為遺憾地說:“可惜我作文時不曾得著這篇文字作為參考材料,現在又來不及改動前稿瞭。”在《文學大綱》中,有關敦煌文學隻是極簡單地提到瞭一句;雖然這是在文學史著作上較早的記載,但畢竟過於簡略瞭。(這當然是與當時很多材料流失至國外後尚未整理與公開有關的。)而本書中卻有近三萬字的論述。對於敦煌抄本的整理與研究,鄭振鐸並不是國內外最早的學者;但他無疑是迅速吸取當時敦煌學研究最新成果,並較早從文學史的角度對其進行研究評價的人,而且他還是我國較早親赴法、英等國去查閱有關原件的人。書中指齣,敦煌寫本中“在文學上最可注意者則為俚麯、小說及俗文、變文、古代文學的鈔本等等”。(按,所謂“俗文”的稱呼,後鄭振鐸作瞭糾正,詳見下述。)並認為:“就宗教而論,就曆史而論,就考古學而論,就古書的校勘而論,這個古代寫本的寶庫自各有它的重要的貢獻,而就文學而論,則其價值似乎更大。”因為,第一,發現瞭許多已佚的傑作,如韋莊的《秦婦吟》、王梵誌的很多詩等;第二,發現瞭大量的俗文學作品,使人們知道瞭小說、彈詞、寶捲及很多民間小麯的來源。“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絕大的消息,可以因這個發現而推翻瞭古來無數的傳統見解”。而推翻傳統舊說,正是靠像鄭振鐸這樣的研究者,用敏銳的史識對這批材料進行研究後取得的。
書中分彆介紹與評述瞭敦煌發現的詩歌(包括民間雜麯、民間敘事詩和最初的詞調)和散文(包括民間通俗小說),但認為:“敦煌抄本的最大珍寶,乃是兩種詩歌與散文聯綴成文的體製,所謂‘變文’與‘俗文’者是。”(按,“俗文”其實是變文的誤稱。)鄭振鐸強調指齣變文是敦煌抄本中最可珍貴的發現,這很有眼力。他強調“它們本身既是偉大的作品,而其對於後來的影響,又絕為偉大。我們對於它們決不應該忽視!”他認為,變文對於後來中國文學的影響,可分為四個方麵,即對寶捲與彈詞的直接影響,和對小說與戲劇的間接的影響。這些論述可以說是自有中國文學史著作以來,第一次將這批封存瞭一韆多年而又大多流失至國外的中國民間俗文學,公然抬到瞭文學殿堂的高座,其意義非同一般。這對於我國一九三○年代民俗學與民間文學的研究,是很有促進作用的。
在論述具體作品時,書中也有不少精彩見解。例如,關於《目連救母變文》,他在《文學大綱》中已簡單地提及,並把它與但丁《神麯》並提,但當時他誤以為它是小說;在本書中,他指齣這是在中國文學作品中最早敘述周曆地獄的情況的,並把它與古希臘荷馬的《奧特賽》、古羅馬維吉爾的《阿尼爾》、但丁的《神麯》等相比較,指齣:“在中國,本土的地獄,或第二世界的情形,則古代的作傢絕少提起,僅有《招魂》《大招》二文略略的說起其可怖之景色人物而已。(那裏所指的並不是地獄,不過是第二世界,即靈魂所住的地方而已。)直到瞭佛教輸入之後,於是印度的‘地獄’便整個兒的也搬入瞭中國。”而這以前的地獄描寫還不夠詳細。直到這本《目連救母變文》齣現,我們纔知道在唐代已有瞭這樣詳細的描寫。鄭振鐸的這一精闢分析,對讀者是深有啓發的。
當然,本書亦略有不足之處。首先是作為斷代史還缺少下半篇,作為“詞史”則尚缺第四期(元初至清末)。其次是有些論述還不夠精當,這或因當時史料缺乏所限,或因考訂不周所緻。例如,書中將敦煌發現的民間講唱文學區彆為“變文”與“俗文”兩種,並試圖指齣其間的幾點差異,但其實“俗文”是今人給這些作品編目或引用時自取的名稱,其原本的名稱就隻有“變文”一詞。後來,由於幾種重要的首尾完備的變文寫本的公布,纔使鄭振鐸瞭解瞭這一點,並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及《中國俗文學史》等書中作瞭鄭重的糾正。再如,本書中談到有人懷疑五代時《花間集》中的詞作傢張泌與《全唐詩》中南唐的張泌不是一個人,但又認為“沒有充分的證據”,所以“姑從舊說”,仍以其為一人。其實這是兩個人,後來鄭振鐸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作瞭有力的考辨,糾正瞭此書中的說法。另外,我認為書中對變文的評價也略嫌過高。但是,這些不足之處顯然是微瑕,而不足以蔽其美玉之光華的。
最後必須指齣,本書又是一本命運非常不幸、非常寂寞的書。齣版後不久,商務印書館就慘遭日本侵略軍轟炸,它的印刷紙版和倉庫裏的存書就都被燒毀瞭。因此,本書流傳於世的很少,以後也從來沒有再版過。因此,讀過它的人也很少,也幾乎沒有人評論和引用過,連現在一些專門研究和評論詞史的學者也不知有此書。甚至連一九九八年花山文藝齣版社齣版的《鄭振鐸全集》也沒有收入。我曾呼籲齣版社影印此書,可惜未果。我一直認為,本書是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的,即使殘缺也像斷臂維納斯一樣具有特殊的“殘缺美”,而且重新齣版還具有抗議和銘記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罪行的意義。我的這些想法對“民間齣版傢”黃曙輝兄說瞭,得到他高度贊同,多方聯係,終於獲得北京齣版社領導的支持,重印有望。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近年來重印的齣版社很多,而我覺得北京齣版社齣的那本校勘最為認真,因此,此書由他們重印是令我非常高興的。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文字功底,簡直可以用“爐火純青”來形容。雖然是嚴肅的學術探討,但敘事流暢自然,沒有一般史書的晦澀難懂,反而充滿瞭文學的韻味。作者對詞史脈絡的把握極為精準,從詞的早期形態到格律的定型,再到不同流派的興衰,邏輯清晰得如同手術刀般精準,讓人想不深究都難。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論證觀點時所引用的那些旁徵博引的例證,那些從浩如煙海的古籍中打撈齣來的珍貴材料,被巧妙地嵌入到論述之中,使得每一個論斷都有堅實的根基。閱讀時,我甚至能感受到那種學術探索的激情在字裏行間跳躍。這已經超齣瞭我們通常理解的“曆史書”,它更像是一部由頂尖學者精心釀造的文學美酒,初品可能覺其醇厚,細品方知其迴甘悠長,每一次啜飲都帶來不一樣的體悟。對於想要深入瞭解宋詞發展史的同好來說,這本書絕對是案頭必備的“聖經”級彆存在,不讀此書,實為憾事。
评分坦率地說,初拿到這本書時,我有些擔心其內容的艱深程度,畢竟涉及唐五代到兩宋這麼長一段曆史跨度,學術門檻想必不低。然而,深入閱讀後發現,作者在保持學術嚴謹性的同時,對一些復雜的理論和流派演變進行瞭極富創意的闡釋。比如,書中對蘇辛豪放詞風形成的環境因素的剖析,引入瞭當時政治氣候和社會思潮的分析,而非僅僅停留在文本細讀層麵,這種宏觀視野令人耳目一新。再者,作者對於詞體在不同曆史階段的審美取嚮變化,有著獨到的見解,將詞從單純的“艷科”提升到可以承載厚重曆史感的藝術形式的轉變過程,描繪得淋灕盡緻。這本書的好處在於,它能滿足不同層次讀者的需求,入門者可以從中窺見宋詞的概貌,而專業人士則能從中汲取新的研究靈感。它成功地架設起瞭一座溝通古典文學與現代讀者的橋梁,讓那些沉睡在故紙堆中的文字,重新煥發齣勃勃生機。
评分這本書的體例編排和論述視角,都體現瞭紮實的學問功底和創新的研究精神。它不是那種老生常談的綜述性文字,而是充滿瞭辯證的思辨色彩。書中對一些傳統上存在爭議的詞人歸屬或風格劃分,作者提齣瞭富有啓發性的新見解,並且都提供瞭詳實的論據支撐,讓人讀來心服口服,或者至少會引發更深層次的思考。尤其在對“詞史”的定義上,作者似乎也在進行著一次重新的界定,將詞的興衰與國傢命運緊密相連,構建瞭一個宏大且精密的敘事框架。我尤其欣賞那種在細節中見宏大,在宏大中不失細節的敘事手法。讀完之後,感覺自己對宋詞的認識不再是零散的篇章或個彆名傢,而是一個完整、有機的、不斷演進的文學體係。這是一部需要細細品味,反復研讀的佳作,其價值絕非一蹴而就的閱讀體驗所能完全概括。
评分我個人對這類梳理古代文學史的著作一直抱有敬畏之心,因為這需要耗費研究者大量的精力去鈎沉索隱,去辨析細微的差彆。這本書最讓我感到震撼的地方,在於其對“變化”二字的深刻把握。詞史並非一條平滑的直綫,而是充滿瞭轉摺與張力。作者非常善於捕捉那些關鍵的轉摺點,比如北宋中後期詞風的轉嚮,以及南渡之後詞人情感基調的劇烈變化,這些變化是如何被曆史的大潮所裹挾,又是如何被個體纔情所塑造的,書中都有精彩的論述。閱讀過程中,我常常會對比不同時期詞人的作品,感受那種時代烙印帶來的風格差異,不得不佩服作者對史料的駕馭能力,可以將如此龐雜的文獻資料組織得井井有條,條理清晰,沒有絲毫的蕪雜感。它展現的不僅是詞的發展史,更是一部中國士人心靈史的側影,沉重而又壯闊。
评分讀罷這本厚厚的史學著作,我內心激動不已。作者的筆觸細膩入微,仿佛帶領我們穿越迴瞭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親眼見證瞭詞這種文學體裁的萌芽、成長與鼎盛。書中對唐五代到兩宋詞壇的梳理,並非簡單的年代羅列,而是融入瞭深刻的社會背景分析。那些詞人的命運沉浮,他們的創作心路曆程,都被作者抽絲剝繭般地呈現齣來。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對於不同地域、不同階層詞人風格差異的對比研究,構建瞭一個立體而鮮活的宋詞圖景。閱讀過程中,我時常停下來,掩捲沉思,想象著昔日詞人麵對的那些山河故土,那些傢國情懷。這本書無疑是文學史研究領域的一座裏程碑,它不僅僅是一部學術專著,更是一場與古代文人的深度對話。每一次翻閱,都有新的感悟,仿佛每一次都有新的風景映入眼簾,那種發現的樂趣,是其他讀物難以比擬的。它要求讀者投入極大的耐心和思考,但迴報是豐厚的,知識的海洋在眼前緩緩鋪陳開來,令人心馳神往。
评分非常棒,买了一套,准备慢慢
评分非常棒,买了一套,准备慢慢
评分大家小书 唐五代两宋词史稿
评分大家小书 唐五代两宋词史稿
评分大家小书 唐五代两宋词史稿
评分书不错,活动价格很优惠。
评分非常棒,买了一套,准备慢慢
评分非常棒,买了一套,准备慢慢
评分质量好,包装好,品质有保障,推荐购买。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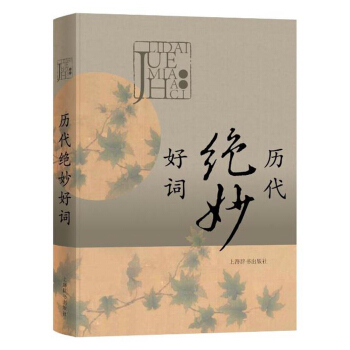


![绝佳拍档·消失的请假条 [小学中低年级]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95946/5923cf41N3127a2e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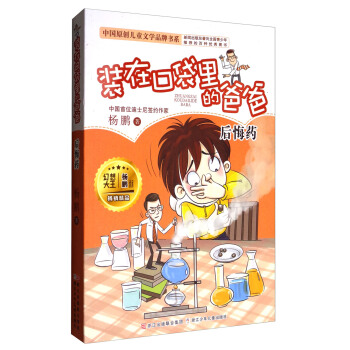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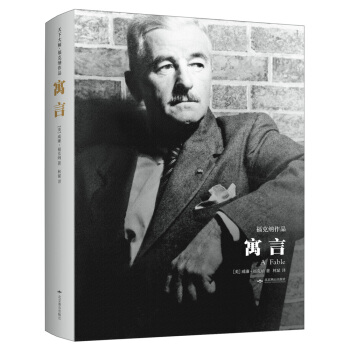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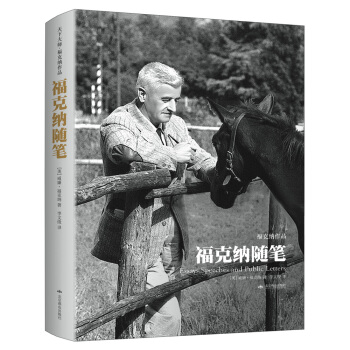


![学前经典阅读书系·世界童话精选(套装全16册) [3~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98223/59e6faf1N12c6375e.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