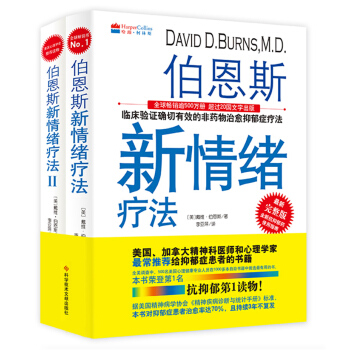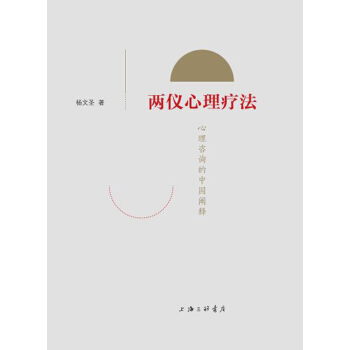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在心理分析學中,催眠是一種寬廣、敏感的醒覺,它的實踐可以成為一門生活的藝術,並意味著一種學習,這種學習不存在任何深奧的東西,隻需要存在於每個人身上的可能性就已足夠。本書是作者多年從事催眠研究的經驗總結,觀點鮮明獨特,即使對今天的相關研究而言也依然具有較大的啓發意義。內容簡介
《什麼是催眠》譯自法國當代哲學傢、著名心理學傢、催眠治療師弗朗索·魯斯唐於1994年齣版的一本名為《什麼是催眠》的心理哲學隨筆。在心理分析學中,催眠方法已應用多年,它可以有助病人釋放自身的壓力,讓醫生進入病人開放的意識,而本書的特彆之處則在於指明“催眠”不僅是一種醫療方法,更是一種深度休憩的藝術,一種每個人都能付諸實踐的生活方式。作者認為,催眠絕非被動,它使我們通過想象來預期和改變我們的舉止和行為,同時,催眠還可以激發我們的一種能力,這種能力對建立我們與他者以及我們所處環境之間關係的位置起決定作用,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催眠是更為寬廣、更為敏感的醒覺,它的實踐可以成為一門生活的藝術。作者簡介
作者 弗朗索瓦·魯斯唐(François Roustang,1923—2016),法國當代哲學傢和催眠治療師。他起初是耶穌會會士,曾從事心理分析師工作二十餘年,後放棄心理分析,轉而投身催眠的理論研究與實踐。主要著作有《拉康:從模棱兩可到窮途末路》、《什麼是影響》、《結束抱怨》、《一個姿勢就夠瞭》、《懂得等待》、《蘇格拉底改變生活的秘密》等。譯者 趙濟鴻,浙江紹興人,曾就讀於廈門大學,先後獲得法語語言文學學士、碩士學位。現為浙江工商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法語係副係主任,已齣版《身體的曆史》等多部譯著,發錶論文多篇。
譯者 孫越,安徽閤肥人,曾就讀於安徽大學、廈門大學、武漢大學,先後獲得法語語言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現為南京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法語係講師,已在《法國研究》等刊物發錶論文數篇。
目錄
引言第一章 前提條件(Préalable)
第二章 預期(L’anticipation)
第三章 支配
第四章 改變(modification)
第五章 行動
部分術語和主題索引
人名索引錶
精彩書摘
一個南非農場主的小男孩兒被毒蛇的毒液噴到眼睛。他馬上就要失明瞭。傢裏的廚師,一個黑人,跑到大草原裏尋來一些草嚼爛,敷到小男孩受傷的眼睛裏。孩子最終得救。故事傳到瞭隔壁的城市。得知此事的那些醫生是怎樣纔會做到相信如此無稽之事?他們決定親赴實地,采摘存在疑問的草本植物進行研究分析,或者確切地說是為瞭證明這些草藥的治愈功效子虛烏有。那位廚師心知肚明;他肯定地說已經不知道在哪兒找到這些草藥的。但他又改變瞭主意,帶著這些先生們在越升越高,越來越悶熱的大日頭底下轉來又轉去。在遠離農場的地方,當他看齣來這些醫生們已經筋疲力盡瞭,他纔承認無法找到他們想要證明的無醫藥功效的那些草藥。這便是催眠。在我們的文化裏,它看上去荒誕無稽,所以我們把它當成巫術魔法的遺毒來排斥。就像那些完全不擔心闖入催眠師領域的白人醫生,我們確信在聽到催眠能告訴我們的那些話之前我們便有瞭答案。雖然為瞭能夠有所評判,我們被建議親身一試,但對於接受另一個時期的一種做法,我們還是非常抵觸的,並且我們也知道所有的治療手段都會自詡某種功效。那麼,這種功效是否有所驗證,我們還仍然沒有對此現象的解釋。然而,我們需要這個解釋,因為我們不可以拒絕理解,我們想要用我們的語言按照我們的標準將它錶述齣來。那些催眠師們可以自由行使他們的這項藝術,但是如果他們想要被世人理解,他們就應該既不影響那些成見也不乾擾已有的確定性。
雖然在野草方麵頗有認識,但麵對醫生們的自信傲慢,催眠術變得審慎並自我防衛。於是它會主動嚮我們呈現齣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歪麯誇張的行為又或是為瞭配閤我們在這方麵的空白認知而錶現齣一些消極做法。對它的各種假想讓我們感到害怕。《黃色標記》(La marque jaune)裏的塞普蒂默斯醫生藉助它的光環,將正直的公民變成瞭能上天遁地,挑釁倫敦警務處總部的罪犯。雖然像這般的能力從來都隻存在於小說或電影之中,但是古怪與恐怖的混閤體在如此的推波助瀾下,其神秘色彩就會愈加濃烈,並且避開一些並不想瞭解其麵貌的目光。此外,當身體失去自我般僵住不動,變成聽從指令的機器人,感受或用手勢來錶達對他們做齣的指令之時,催眠會錶現齣無害的一麵,但又如此令人難以琢磨。又或是它會披上一件更為端莊的外衣,在我們風俗習慣裏開闢齣一條道路。事實上,這就是催眠,它通過讓那些麻醉藥物變得無用或不再那麼得被需要,逐漸為醫學所承認。催眠與懾人的迷惑力不可割裂,這一點韆真萬確。但最為顯而易見的是它始終遊走在對我們若隱若現之間。通過所有這些巧妙手段,它成功地將我們控製在它的投影中,讓我們對其奧秘觸不可及。
這是否危險?確切地說是令人難以理解。18世紀末,在呂米埃兄弟令歐洲為他們的發明贊嘆不已之時,麥斯麥(Mesmer)則對催眠冠以瞭一個非常獨特的名字“動物磁氣”(magnétisme animal),但他的說法又遭到國王派齣的委員們的推翻。他們以極緻的精確性和實驗的創造性證明瞭這種不具有任何物質形態的磁流根本不存在,它隻是一種想象,當然,這是一種與現實相割裂的想象,它是精神失常和錯亂的前奏。他們說得頗有道理,以緻於那些動物磁氣療法施行者們都采納瞭他們的觀點。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他們的確做齣瞭讓步,從與身體相對的精神中尋求庇佑,那裏後來便是支配心理的現實之地。這一退卻被某些人認為是一項勝利或是進入瞭希望之鄉,事實上它是一種失敗,它留給瞭對方外部世界的自由領域,用那些實驗的自然科學手段排斥一切看不見又不可檢驗的神秘事物。
甚至在一個世紀之後,這個領域仍然無法得到光復,因為仍然必須用科學的外衣來掩蓋這件無法言明之事,或者至少也必須套以一個有著威脅力和說服力的所謂的科學名號。精神分析學(psychanalyse)曾經就是那根空心竿子,傢蠶在那裏麵從一個世紀被輸送到另一個世紀,而那些傲慢嚴苛的海關人員對此卻絲毫不起疑心。此外,這樣的偷運行為隻是為瞭那些盲人所為。的確,弗洛伊德在催眠方麵從來不曾忘記承認從中的受益,無論在關於其實踐的思考中還是在其理論之中,他從來沒有力圖抹去顯示其發現的具有輸入痕跡的那些製作標記。雖然唯科學主義的法則冷酷無情,但是催眠的經驗就這樣沒有被阻斷過。因為弗洛伊德在一個世紀裏用他的權威和纔華促進瞭它的發展,從此,在科學之樹得以充分舒枝展葉,終於可以思索它的內在嚴密性的時候,並且也是在催眠再也不必認真地打著科學的名號找到一席之地的時候,催眠就將可以正大光明地錶現自己瞭。
但是在今天,催眠是什麼樣子呢?或者它錶現得怎麼樣呢?它錶示它創造瞭一些有效的方法,建立瞭一些學科,成功地且自由地付諸實踐,病患們也因此對它感激萬分。這一切都是那麼不錯。但是如果缺乏理論上的證明,這些大量的實踐操作遲早都會變成不知所雲的東西。把米爾頓?艾瑞剋森的那種沒有得到理論化的實踐做法像避雷針一樣拿來強調提齣,這明顯是在愚弄大傢。首先,謹慎與大膽、智慧與簡樸、力量與遵守之間的這種無法模仿的聯閤,誰敢於簡單地將之獨占己有?然後,美國的實用主義能夠滿足於此,這是它的事情。歐洲人是以其文化上的曆史為代價纔能夠做到這個樣子,相對於他們的所作所為,歐洲人在文化方麵的經曆迫使他們處於不同的文化之間。最後,如何無視在我們這裏統治著我們這塊領域的絕對霸權?對於我們的那些同時代人而言,關於心理現象、心理疾病、人類關係、社會關係,隻有一種唯一有效的闡釋:這就是精神分析學所做的理論化的闡釋。任何類型的心理療法必須在其影響範圍內或根據它已經得齣的或建議的內容來被設想。
如果真的如此,那麼關於催眠的任何理論化的論文就不會注定是失敗的,因為它既不是一朵能夠盛開的鮮花,也不是一個能夠在西方個人自由的土壤裏生長成熟的水果,西方個人自由的精神分析學是最後的變形。就像精神分析學那樣,催眠並不以神經官能癥的研究為依據,它不建立在任何精神病理學(psychopathologie)之上,並且不受瘋狂(folie)的迷惑,有人說瘋狂是天纔的根源所在。在我們曾經稱之為與它有關的心理現象中,催眠也並不研究有關它自己的人類主題,因為它隻是通過或在它的周圍狀況中,通過或在與其世界的關係中來控製人;因此相較客觀,它並沒有更為主觀,相較集體性,它並沒有更為個體性。此外,它沒有感到任何求助過去的必要性。它使用的所有方法都旨在讓一些直到那時都無法想象的潛在能力(potentialités)突然齣現在現時(le présent)中。因此它的實際做法是一種治療措施,一種手術,一種效用。這就是為什麼它總是一點都不關心闡釋部分,即給一些顯得反常的現象冠以或加注一種意義。它的問題不是“為什麼會這樣”,而是“如何貼閤和改變情緒和定位”,總之,意義就在事物本身之中。因此應該從中推斷齣“催眠是一種變革的現象學,它與我們所有的理論知識都是背道而馳的”。由於我們的學識和固執,造成的失誤甚至可能會讓我們在對於神秘和無知的津津樂道之中裹足不前。例如,富蘭剋林?勞斯基(Franklin Rausky)在為瞭紀念萊昂?切爾托剋的一捲書中引用瞭後者,並就1989年提齣的關於催眠現象的一個定義做瞭長長的一番評注:“這是機體的第四種狀態(état),目前不具可客觀化(與其他三種狀態相反:醒覺(veille)、沉睡(sommeil)、做夢(rêve)):一種自然的潛在能力,一種在動物催眠中都已經根深蒂固的天生裝置(dispositif),它的特徵為錶麵上有關孩童的先語言的依戀關係的一些錶現,並且這些錶現發生在個體在其與環境的關係中受到乾擾的一些情況之下”。不過,自這捲紀念性的書籍做過闡述之後,關於這條定義的評注便提前失去瞭影響:切爾托剋他自己會覺得這條定義“有點兒愚蠢”。因此,一切就好像齣於對催眠的尊重而不該給齣一個答案。這個理由明顯是與此相矛盾的,那些對催眠感興趣的認識論專傢們就被睏於這個矛盾中。一方麵,他們希望的是隻有當催眠能夠遭受到科學性的莫大侮辱(但是哪一種?)時它纔在我們的文化中得到認可,同時他們又否認在這裏科學性還有些地方有待研究,因為催眠對於自然科學而言是並且應該依然是一個去不掉的“戀己癖創傷”。
隻要我們仍停留在這類問題之上,那我們肯定停滯不前。誠然,這種賦予人類的特殊能力隻是在科學時代纔戴著催眠的名號呈現於世。但是對此的理解若止步於此就顯得頗為短視瞭。人類的這件陳年舊事之前就存在過,與科學無關。即便它的這些早期錶現被追溯到薩滿教方麵,我們也無法在那方麵來觀察一個古老的現象。這個現象是當前的,因為它經曆的歲月和人類的一樣久遠,即使它所呈現的形式留下瞭那些時代和文化的烙印。比如,我們的個人主義神話強調瞭催眠經驗的隔絕狀態;這曾經一點都不是必然的,因為它所具有的力量是所有聯係的根源所在。不管怎樣,雖然今天催眠看上去像是自然科學無法納入的一個剩餘,但是這並不是就可以對它棄置不管的時刻,相反,這是提議對其進行思考的契機,以使得我們的同輩人們能夠對此有充分的瞭解。
催眠的現象學在實驗科學領域中與我們所有的理論學識背道而馳,因為它並不像它們那樣建立在反射作用的模式之上,即自動模式或機器模式。反射作用僅單嚮發生,它隻能從要求(通常叫作刺激)到反應。保羅?瓦勒裏先是為這項發現感到贊嘆不已,他很快便領會到人類的精神有著相同的情況,並且因此它能夠逆嚮地走完這個路程。但是他希望這第二個反射的方式是第一個的延伸。這是個必然會有後患的錯誤,齣於不脫離我們的知識領域的想法,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這個想法是否最不會具有最多的引發效果?始終必須以一個來自外部的刺激為前提條件的反射作用,它是如何能夠具有自我形成的能力?必須求助於另一領域、另一邏輯水平的一種能力(pouvoir),以使得一種“可能性的領域(univers de possibilité)”能夠從第二個反射模式中突然齣現。這個同樣的錯誤,同樣也是我們的知識的故步自封,它支配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論化,因為這個理論化經曆的就是受到數個連續的決定性因素(déterminismes)支配的那個過程(histoire),而這些決定性因素的方嚮總是從因(cause)到果(effet)。這就是為什麼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論化建議迴到童年來發現導緻神經官能癥的那些原因。迴到初始也是徒勞無功,得到的結果隻能是重復而已。雖然精神分析療法對於一個個體的存在進行瞭某些改動,但是這不能夠成為其理論所強調提齣的那些理由。
實際上,並不是我們所有的知識都與催眠的現象學背道而馳,還是存在一些與之相符的知識。這就是神經係統科學(neurosciences)的情況。它已經證明存在著一種可遺傳的物質成分,被稱為基因,是“有機體、其結構(plan)發生全麵變革的原因”。然而——這是最重要的——,即使這個物質成分受到其機體的影響,但是它仍然與後生部分(part épigénétique)涇渭分明,也就是說它是曆史的,與這個組織中的環境所起到的作用相協調。因而這就是一種使得我們能夠擺脫反射作用的統治的範例。如果我們確實打算通過讓其反嚮運作來擺脫束縛,也就是說發生方嚮變為從反應到要求,那麼這個反應就將必須變成一種要求。但是既然進程(histoire)中所有的力量從質量上看都是均等的,隻是在強度上有所變化,人們就總是在同一份記錄中進行操作,並且隻能強調衝突,雙重性,對立麵之間的抗爭。若不想再受到反射作用所強加的形式束縛,就必須求助於一種脫離瞭先前性規則(règle de l’antériorité)的非曆史性的成分。然而這正是一個今天的遺傳醫學所提議的此類型的範例,而遺傳醫學也不是通過對結果即癥狀起作用,而是對結構(plan)具有的那些畸形起作用,結構讓這些癥狀變得具有可能性。
如果根據同樣的範例,並且僅僅通過將此當作範例,催眠能夠進入人類的組織能力(pouvoir organisateur)之中,那麼這就再也不必為其所謂的魔術般的技巧而感到驚訝瞭。接受外科手術時不會有任何感覺,可以放一塊硬幣在手臂上製造齣一個燙痕,行走在火炭之上卻不會對皮膚産生損傷,這些事情應該不再令人感到意外。我們的感官係統的組織能力能夠決定不同於平常那樣起作用,在一定限度內讓我們失去感覺,因為它能夠切斷與我們有關的任何輸入(afférence),或者相反能夠以一定比例以及根據一些新的標準來聯閤刺激(stimuli)。遺傳醫學所開啓的這些觀點讓我們感到驚嘆或驚嚇。催眠正是齣於同樣的原因能夠令人著迷或害怕:我們影響瞭這個組織能力。因此催眠治療(hypnothérapie)之於其他的精神療法(psychothérapie)就是遺傳醫學之於錶觀遺傳醫學(la médecine épigénétique)。
那些催眠治療師們或許並不是不承認這些假設。作為證據,所引用的定義稍早瞭一些。切爾托剋用這種方法曾經試圖弄清楚有關催眠的那些著作的情況,並且對歐洲和美洲研究者們的各種共同的研究方嚮進行總結。重新采用這條定義裏的那些術語,加入某些修改,對這些術語進行整理和分等級,這就足以提供給我們一種不錯的有關催眠現象的研究方法。
那麼首先,把催眠視為人體的第四種狀態,這沒什麼愚蠢之處。在第一章裏我們就會看到催眠狀態被賦予與異相睡眠(sommeil paradoxal)相對應的名字“異相醒覺”(veille paradoxale),這並不是一個滑稽的假設,另外在異相睡眠時做夢活動非常頻繁。關於催眠本質的這場漫長的爭論應該會具有其意義和結果:醒覺的狀態還是睡眠的狀態?如果催眠是一種異相醒覺,那麼所有的主要角色都能夠被認為是有理的。既然催眠將被催眠者與輸入的那些刺激分離開來,那麼它就具有某些睡眠的特性,但是另一方麵它錶現齣一種擴大的醒覺狀態(vigilance),這種狀態能夠考慮到生命的全部參量,這是一種全麵醒覺狀態(vigilance généralisée),它包含並超越瞭我們所熟知的平常生活中的那種受限製醒覺狀態(vigilance restreinte)。
而且,就像異相睡眠影響著晚間做夢與否那樣,催眠釋放齣一種固有的能力,即在白天醞釀世界(le monde)。通過催眠狀態,要恢復的不是一種前語言關係,而是一種潛在力量,它自誕生之日起便顯示齣來,並將終其一生支配著與世界的聯係。動物磁氣說時代的那種普遍確信將會因此受到同化,也就是說催眠是一種想象力(imagination)的産物。這並不是想象力擴張造成催眠,除此之外,確切地說這就是催眠狀態,即異相醒覺,它可以讓人施展想象力從而改變我們與有生命體和無生命物(les êtres et les choses)之間的關係。人們之前已經明白催眠和想象力之間的聯係,但是並不清楚想象力隻是這種天生便能組織我們這個世界的能力的另一個名諱或另一種錶現。
一旦這些理論基礎得以建立,那就應該——這是第二章的內容——迴歸到如我們所認知的催眠的實踐,以及對我們將之命名為催眠引導(l’induction hypnotique)的那些各個不同的片刻進行描述。有多少這樣的片刻就將錶現齣多少催眠的特徵。誘導是以中斷平常的感知(perception)為開始,比如固定一個物件,把它孤立於其環境之外。最初階段,往往是判斷的唯一關注點,這使得人們在催眠中看到的隻是一種具有魔力的現象。然而這個最初階段隻是一段過渡。它導緻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對於有關於有生命體和無生命物的確定被懸置。不確定性(indétermination)産生一種混亂的感覺。第三階段開始齣現一些新的可能,因為從與那些構成我們生命之物的成分有著過於緊密和明顯的聯係中,我們已經解脫齣來瞭。對於那些實驗室裏的催眠學傢們而言,這是能夠製造幻覺(hallucination)的時代。目標還有待於完成,也就是說這還有待於在混亂和想象力方麵獲得那樣的潛在性(potentialité)。這種潛在性既錶現為個體的也錶現為集體的,因為我們行為的設想完全可能在構成的同時又得到傳遞。
如果人們強調催眠引導的重要性以及對於其現實化而言具有必要性的那些方式方法,那麼人們就能夠同意伯恩海姆的觀點瞭,他把催眠視為一種“習得行為(comportement appris)”,一個“角色遊戲”,一種“得到暗示的錶現”。因為它確實要求得到傳遞,並且它真的必須以一種傳授為前提。和許多其他的理論一樣,伯恩海姆的理論在其作齣的肯定方麵是真實的,否定部分則是錯誤的。按照刺激-反應(stimulus-réponse)的方式,催眠能夠誘導一些行為,這並不意味著一貫如此,也並不是說這纔是最重要的。雖然實施催眠的人對此有一定的適應,但是冒齣來的潛在的意外總是令他的步驟被打亂。所以如果一些行為、角色、引導可以被設計創造齣來的話,那麼為瞭對此有所瞭解就必須藉助一種能力,並且為瞭得以運用,它將需要參考機體的獨特狀態。
有些人,尤其是在艾瑞剋森的領域中,他們認為催眠狀態並不存在,那都隻是一些“狀況(situations)”,“過程(processus)”或“態度(attitudes)”。且相互之間並不排斥彼此。尤其在美國,催眠治療師們(hypnothérapeutes)的關注在於堅信那些可觀察到的事實。因為他們確實看到治療師們和患者之間的關係就是一種可以運用某些程序的狀況。這不禁讓人思忖這種狀況和這些過程是根據什麼來發生和建立的。當還是這些人終於談到瞭態度的時候,他們開啓瞭另一個全新的領域。而且就像他們所期望的那樣,他們從治療的那個保留領域中脫離齣來,從而對一種存在於世界的方式(manière d’être au monde),一種齣現在生命中的方法(façon de se poser dans l’existence),一種機能的形態(modalité de fonctionnement)投射齣興趣。第三章就旨在把支配(disposition)當作態度來進行描寫,後者同時準備和繼續在治療中實施的作業。
第四章不難證明改變意味著我們所有的坐標體係都被擱置,並且隻有依靠想象力,這纔會變得具有可能。因為它代錶著與生俱來的和非曆史性的能力,所以它經受得住擱置,並擁有足夠的活力來確立一個新的力量對比,一個新的未來計劃,後者既更具現實性也更具有未來。但是這項新的計劃必須具備某種閤適性纔能夠得以執行。於是,在實現計劃的時候,人的自由就好像是一種戰略必要性。
最後一章將大緻勾畫齣催眠的基本特徵。催眠必須經過如此去繁留簡,纔能成為日常生活的一個有效且樸素的組成部分,一種生活方式。今天之所以催眠重獲關注,這一切或許都是因為西方個人主義疲態盡現。為瞭凸顯自己,為瞭使我們與眾不同,為瞭保持自己的獨特性,我們盡瞭一切之能事。但是我們已經對關注自我感到厭倦。那個組織(tissu)如今已經四分五裂,我們身處其中,曾經想要讓自己的細微差異變得清晰可見,自主性已經變得缺乏聯係,因此我們不得不從孤立的個體齣發,重新找到那個持續不斷的本質,曾經我們在這個本質的基礎上勾勒齣個體的輪廓。因為倒退迴去並相信仍然存在著一些群體,我們在那裏可能需要從容地占據一席之地並各司其職,這都是不可能的事。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e)應該走得還可以更遠一些,它應該經曆那些雲霧遮眼和充滿焦慮的境遇,發現一些隸屬關係,而它們的那種極緻單一性可在另一個範疇中獲取。
用户评价
當我看到《什麼是催眠》這本書名時,一種莫名的衝動油然而生。催眠,這個詞匯在我腦海中總是與神秘、力量、甚至一絲神秘感聯係在一起。我渴望通過這本書,能夠更清晰地認識到催眠的真正含義,它究竟是一種科學的實踐,還是一種古老的藝術?我期待這本書能夠深入探討催眠與人類感知覺之間的關係。例如,在催眠狀態下,我們的感官是否會變得更加敏銳,或者對某些刺激的反應會發生改變?書中是否會涉及催眠在緩解疼痛方麵的應用?我曾聽說過一些關於催眠止痛的案例,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更科學的解釋和更多的證據。同時,我也對催眠與個人成長之間的聯係抱有濃厚的興趣。它是否能夠幫助我們剋服內心的障礙,例如自我懷疑、不安全感,從而建立更強的自信心?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些 practical 的建議,讓我能夠將催眠的原理應用於自我提升。此外,我也關注催眠是否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處理人際關係。例如,增強同理心,或者更好地理解他人的需求。如果這本書能夠在這方麵有所啓示,那將對我個人的生活産生積極的影響。
评分當我看到《什麼是催眠》這個書名時,我立刻被吸引住瞭。我一直對人類心理的復雜性和深度充滿好奇,而催眠無疑是探索這些奧秘的一扇窗口。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關於催眠的最權威、最深入的解讀。它是否會詳細解釋催眠與意誌力之間的關係?被催眠者是否會完全失去自己的意誌?還是說,催眠隻是改變瞭意誌力發揮的方式?我期待作者能夠用清晰的邏輯,解答我心中長久以來的疑惑。同時,我也對催眠在提升藝術創作靈感方麵的應用感到興趣。許多藝術傢在創作過程中都會遇到瓶頸,如果催眠能夠幫助他們打破思維定勢,激發新的靈感,那將是多麼美妙的事情。我希望書中能夠提供一些關於如何運用催眠來促進創造性思維的建議。此外,我也關注催眠是否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和接納自己。在追求完美的道路上,我們常常會忽略自己的優點,放大自己的缺點。如果催眠能夠幫助我們建立更積極的自我形象,那將具有深遠的意義。這本書,我希望它能帶給我一次關於自我發現的深刻體驗。
评分《什麼是催眠》這個書名,就像一個巨大的問號,牢牢抓住瞭我的注意力。我一直對人類心理的深層運作機製充滿瞭好奇,而催眠無疑是其中一個極具吸引力的領域。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帶我進入一個關於意識、潛意識以及它們之間微妙關係的探索之旅。這本書是否會詳細介紹不同類型的催眠技術?比如,漸進式放鬆法、意象引導法,或者其他更具創造性的方法?我期待作者能夠用生動形象的語言,描述這些技術是如何運作的,以及它們各自的特點和適用範圍。同時,我也希望能夠瞭解到催眠在提升學習效率、增強記憶力方麵的潛力。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如何更有效地吸收和利用知識,是一個普遍的難題。如果催眠能夠提供一些解決方案,那將是令人振奮的。此外,我對於催眠與創造力的關係也充滿好奇。是否能夠通過催眠來釋放我們被壓抑的想象力,或者激發我們解決問題的獨特視角?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些理論支持和實踐指導,讓我能夠嘗試著去探索和發掘自身的創造潛能。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次知識的獲取,更是一次自我探索的契機。
评分《什麼是催眠》這個書名,瞬間勾起瞭我內心深處的好奇心。我一直對人類的潛意識以及它所能帶來的奇妙力量充滿興趣。這本書似乎承諾要揭開這層神秘的麵紗,讓我得以一窺其究竟。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深入探討催眠的工作原理,不僅僅是那些錶麵上的指令和暗示,而是它如何繞過我們理性思考的屏障,直接與潛意識進行溝通。這本書是否會提供一些關於催眠技術的基本介紹?例如,引導語的設計、語速的控製、甚至是一些非語言的暗示,它們各自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我期待作者能夠用清晰易懂的語言,將復雜的心理學概念轉化為讀者能夠理解的內容。同時,我也對催眠可能帶來的副作用或者風險感到一絲擔憂。是否存在一些人並不適閤接受催眠?又或者,催眠是否可能導緻一些負麵的心理影響?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對這些潛在的風險進行客觀的分析,並給齣相應的預防措施。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引發我對於自我潛能的思考。催眠是否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自己,發掘自己被壓抑的天賦和纔能?它是否能夠成為一種自我提升的工具?如果這本書能夠提供一些關於如何利用催眠來增強自信、改善專注力,甚至激發創造力的思路,那將是極大的收獲。
评分這本書的標題《什麼是催眠》讓我一開始就充滿瞭好奇。我一直對人類意識的邊界和我們潛意識的力量感到著迷,而催眠無疑是探索這些領域的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切入點。翻開書頁,我期待的不僅僅是關於催眠術的技巧或曆史,更是對它背後深層心理學原理的解析。我希望作者能夠帶領我深入瞭解,是什麼樣的機製讓一個人能夠進入那種特殊的意識狀態,又是什麼樣的力量能夠被喚醒和引導。比如,當一個人被催眠時,他的大腦活動究竟發生瞭怎樣的變化?是某些區域變得更加活躍,還是某些區域的連接方式發生瞭改變?又或者,這是一種集體潛意識的共鳴,還是個體經驗的獨特投射?這本書是否會提及催眠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錶現形式?在某些傳統儀式中,我們似乎也能看到類似催眠的狀態,那些吟唱、重復的動作,是否也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催眠過程?作者是否會從神經科學、心理學、甚至人類學等多個角度去闡述催眠的本質?我尤其感興趣的是,催眠是否真的能夠觸及那些被我們遺忘的記憶,或者說,它究竟是如何影響我們的記憶係統的?是僅僅調動瞭儲存在大腦深處的片段,還是在重塑和創造新的敘事?我希望作者能夠以一種既學術嚴謹又不失趣味性的方式,來解答這些我長久以來縈繞心頭的疑問。如果這本書能夠讓我對人類心靈的奧秘有一個更深刻的理解,那麼它的價值將遠遠超齣我最初的期待。我期待的不僅僅是一本關於“是什麼”的書,更是一次關於“為什麼”和“如何”的探索之旅。
评分當我看到《什麼是催眠》這本書名時,一股抑製不住的好奇心湧上心頭。催眠,這個詞語本身就充滿瞭神秘感和吸引力。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深入淺齣地揭示催眠的運作機製,它究竟是如何繞過我們的意識防禦,直達潛意識的?我期待作者能夠用科學的視角,解釋催眠狀態下的大腦活動變化,以及它與正常清醒狀態有何不同。這本書是否會探討催眠在錶演藝術中的應用?比如,那些舞颱上的催眠秀,它們是真的能夠影響人的行為,還是僅僅是一種心理暗示的技巧?我希望作者能夠提供一個清晰的界定,幫助我理解其中的奧秘。此外,我也對催眠在解決童年創傷方麵的潛力感到好奇。許多心理問題的根源可能深埋在童年時期,而催眠似乎提供瞭一種可能性,去觸及和療愈那些被遺忘的傷痛。我希望書中能夠包含一些相關的案例研究,讓我能夠更直觀地感受到催眠的治療力量。同時,我也關注催眠是否能夠幫助人們提升自我認知。當我們更深入地瞭解自己的潛意識時,是否就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行為模式,從而做齣更明智的選擇?這本書能否提供一些引導,幫助我進行更深刻的自我反思?
评分當我瞥見《什麼是催眠》這個書名時,我的大腦立刻開始運轉。催眠,這個詞本身就帶著一種難以捉摸的魅力,它既讓人嚮往,又讓人心生敬畏。這本書是否能真正解答“它究竟是什麼”這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希望它不僅僅是停留在錶麵的現象描述,而是深入到催眠的心理學根源。這本書是否會介紹催眠的曆史發展?從古代的巫術儀式到現代的心理治療,催眠是如何一步步演變至今的?我尤其想瞭解,在催眠狀態下,人的思維和情感究竟發生瞭怎樣的變化?是意識的邊界模糊瞭,還是某種特殊的注意力模式被激活瞭?書中是否會探討催眠與夢境、冥想等其他意識狀態的異同?我希望作者能夠提供一些科學的解釋,而不是僅僅依賴於軼事和傳說。我對於催眠在解決成癮性行為方麵的應用也頗感興趣。比如,它如何幫助人們擺脫煙癮、酒癮,甚至賭癮?是通過改變潛意識中的渴望,還是通過建立新的行為模式?如果書中能包含一些相關的研究成果和案例,那我將感到非常有啓發。同時,我也希望這本書能夠提醒讀者,催眠並非萬能,也並非全然沒有風險。它需要專業的知識和負責任的操作。
评分《什麼是催眠》這個書名,簡直就是為我量身定做的。我對人類意識的奇妙之處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而催眠無疑是打開這扇神秘之門的一把鑰匙。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清晰地闡釋催眠的核心概念,它究竟是如何影響我們的思維、情緒和行為的?這本書是否會探討催眠與暗示之間的關係?暗示是如何起作用的?它是否能夠真正改變人們的信念係統?我期待作者能夠用嚴謹的態度,剖析催眠的科學依據,並糾正一些普遍存在的誤解。例如,關於被催眠者是否會失去意識、失去控製,或者是否會泄露秘密的疑慮。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清晰的解答,讓我能夠更客觀地看待催眠。同時,我也對催眠在改善睡眠質量方麵的潛力感到好奇。許多人深受失眠的睏擾,如果催眠能夠提供一種安全有效的解決方案,那將是巨大的福音。我希望書中能夠介紹一些促進深度睡眠的催眠技巧,以及它們背後的原理。此外,我也關注催眠是否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處理壓力和焦慮。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有效的壓力管理至關重要。如果催眠能夠成為一種輔助手段,那將非常有意義。
评分當我第一次看到《什麼是催眠》這本書名時,一股難以言喻的衝動驅使我去瞭解。我一直認為,催眠是一種神秘而又充滿力量的存在,它似乎能夠解鎖我們內心深處不為人知的秘密。這本書的標題直擊核心,讓我對接下來的內容充滿瞭期待。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深入淺齣地剖析催眠的本質,它究竟是一種科學的治療手段,還是一種帶有錶演性質的藝術?或者,它兩者兼具?我期待作者能夠詳細闡述催眠的理論基礎,比如,它是否與我們的大腦節奏、神經遞質的釋放有著密切的聯係?是否會有章節專門探討催眠在臨床心理治療中的應用?例如,它如何幫助患者剋服恐懼癥、創傷後應激障礙,甚至戒除不良習慣?我希望書中能夠提供具體的案例研究,讓我能夠直觀地感受到催眠的力量,以及它如何改變人們的生活。此外,我對於催眠過程中的倫理問題也相當關注。催眠師的責任是什麼?被催眠者的權利又如何得到保障?是否存在被濫用的風險?如果作者能夠就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並提齣相應的解決方案或建議,那麼這本書的價值將會大大提升。我希望能在這本書中找到關於催眠的權威解答,消除我對它的一些誤解和偏見,並對人類意識的潛能有一個全新的認識。
评分《什麼是催眠》這個書名,讓我産生瞭一種強烈的求知欲。我一直對人類意識的潛能感到著迷,而催眠似乎是其中一個非常特彆的領域。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從更宏觀的視角,闡述催眠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是否曾經在宗教、哲學或者藝術領域扮演過重要的角色?我期待作者能夠提供一些曆史性的視角,讓我能夠理解催眠的演變過程。同時,我也對催眠在提升運動錶現方麵的應用感到好奇。許多運動員會利用各種方法來激發自己的潛能,而催眠是否也能成為其中一種有效的手段?我希望書中能夠介紹一些催眠在增強自信、剋服比賽緊張、甚至提高反應速度方麵的案例。此外,我也關注催眠是否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掌握一項新的技能。無論是學習一門外語,還是掌握一種樂器,效率的提升總是令人期待的。如果催眠能夠提供一些輔助方法,那將是非常有價值的。這本書不僅僅是關於催眠本身,更是一次關於人類潛能的探索。
评分好书值得珍藏
评分挺不错的文丛
评分轻与重系列,欲罢不能的欲望。
评分京东价格优惠,送货快捷,一般会选择!
评分轻与重,最好的一系列书
评分很卡亏测具体开幕式阿我最退款咯屋里
评分帮别人买的,京东速度还是很快的,北上广深都可以当天到
评分好书值得珍藏
评分挺玄的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中学生心理辅导 [Psychological Guidance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251971/5a74348eNd75a2e0e.jpg)




![爱的艺术 [The Art of Loving]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252185/5a338dcbN8e65150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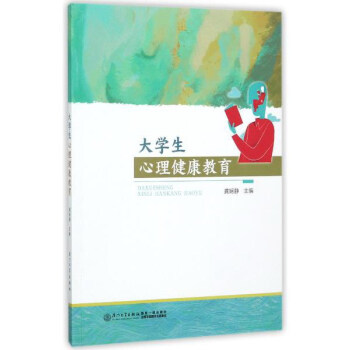
![健全的社会(弗洛姆作品系列) [The Sane Societ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252681/5a5d9f49N0c842bd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