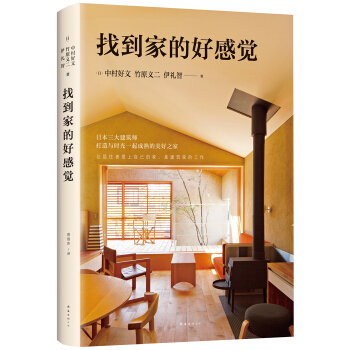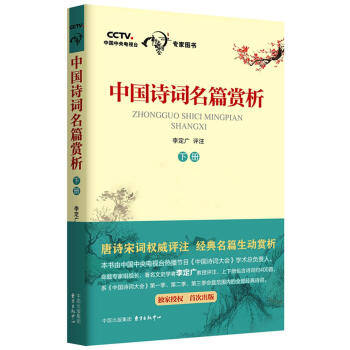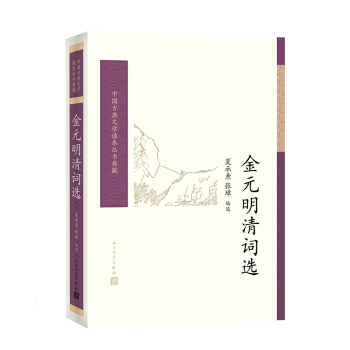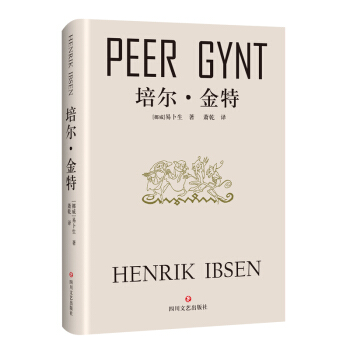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近代戲劇之父易蔔生代錶作,開創文學新時期。以詩的語言寫作劇本,劇中諷刺與誇張傳神,發人深思。
翻譯文本語言優美,完美體現翻譯大師大師對於“信達雅”的掌控。
內容簡介
《培爾·金特》是挪威著名的文學傢易蔔生創作的一部具有文學內涵和哲學底蘊的作品,也是一部中庸、利己主義者的諷刺戲劇。譯者是著名翻譯傢蕭乾。《培爾·金特》通過紈絝子弟培爾·金特放浪、曆險、輾轉的生命曆程,探索瞭人生是為瞭什麼,人應該怎樣生活的重大哲學命題。作者簡介
亨利剋·易蔔生(Henrik Ibsen,1828–1906),挪威戲劇傢。曾長期擔任劇院編導,1864年丹麥和普魯士戰爭爆發後長期僑居羅馬等地。內頁插圖
前言/序言
譯者前言一
第一次在倫敦中心區一傢劇院看易蔔生的詩劇《培爾·金特》,外麵還響著警報。納粹的轟炸機正在頭上盤鏇——說不準那是一九四幾年的事瞭。劇院經理按照市政當局的規定,先把幕落下來,然後嚮觀眾宣布:凡願暫避一下的,可以退場。當時劇場裏動靜不大,一方麵是齣於觀眾對納粹的衊視,同時也由於戲的確有吸引力。旅英七年,戲我沒短看:歌劇、莎劇、話劇,甚至聖誕節為孩子們演的“啞劇”。然而沒有一齣戲曾那麼整個地攫住我的心靈。那以後,我還在劍橋收聽過兩次此劇的廣播。每次接連近幾個鍾頭哪!然而我總是帶著興奮的心情,一氣聽到底。
從那以後,我有時就在思想裏把這個劇本同現實生活聯係起來。比如1948年至1949年,像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一樣,我也在考慮思想改造問題。那時我就把《培爾·金特》同這個問題聯係起來瞭,並且在我主編的《香港大公報·文藝》(1949年8月15日)上以整版篇幅寫瞭篇《培爾·金特——.一部清算個人主義的詩劇》,其中有一段涉及我對此劇主題的理解:
在所有的戲裏,易蔔生都要我們忠於自我,殉道者般地堅持自我。在這部詩劇裏,他卻告訴我們說:“我是軍隊,裏麵排列著願望、食欲和貪婪。我是海,裏麵浮著幻想、索取和期待。”他告訴我們:“要保持自我,就先得把自我毀滅瞭。”沒有比這更不像易蔔生的瞭!然而《培爾·金特》這個寓言諷刺劇所抨擊的,自始至終是自我。
當時我對思想改造的理解,就是個人主義的剋服,因而也就把《培爾·金特》這個詩劇理解為對個人主義的清算。這當然是很膚淺,很不全麵的。
1978年為《世界文學》(內部發行)譯完此劇第一及第五兩幕後,在寫前言時,我又把它同十年浩劫時期的風派人物聯係起來瞭。有一段是這麼寫的:
這部詩劇筆勢縱放,內容著實龐雜;然而全劇還是有一個前後呼應、貫串始終的主題,即人妖之分。易蔔生認為做個“人”,就應保持自己的真正麵目,有信念,有原則,不投機取巧,不見風使舵;為瞭堅持自己的信念原則,什麼苦頭都準備吃,什麼侮辱都準備受。那個剁掉自己指頭的人也可以說就是《人民公敵》中斯多剋芒醫生的雛形。“妖”則無信念,無原則,蠅營狗苟,隨遇而安;碰到睏難就“繞道而行”,麵臨考驗就屈服妥協。他掂斤撥兩,看事物隻憑利害,不講是非。他八麵玲瓏,處處“適可而止”。為瞭娶上妖女,他可以安個尾巴;在群猴圍攻下,他不惜巴結老猴王。但他越是自我擴張,侵人自用,他就越失掉自己的本來麵目。這種人進瞭鑄勺,鑄成紐扣也還是廢品——沒有窟窿眼兒!
在理解一部古典作品時,會受到當時心境的影響,這是難免的。然而這畢竟不是詮釋一部作品的正途,因為它不完全是從作品本身齣發,而有些藉題發揮。
1880年5月,當此劇德文本譯者盧德維希·帕薩爾格寫信問起《培爾·金特》的主旨和作者構思經過時,易蔔生在同年6月16日從慕尼黑寫的迴信中沒做正麵的闡述。他說:“要把那個說清楚,我得另外寫一本書,而時機尚未到來。”接著他又說,“我筆下的一切,雖然不一定都是我個人經曆的,卻都與我心靈所感覺到的有著密切關係。我的每部作品的主旨都在於促使人類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和感情上得到淨化,因為每個人對於他所屬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因此,我曾經在一本書裏寫下這樣的題詞:‘活著就是要同心靈裏的山妖戰鬥,寫作就是坐下來對自己作最後的評判。’”
易蔔生始終也沒寫齣“另外”那本書。一個多世紀以來,關於這個五幕三十八場幻想、象徵、寓言、哲理詩劇的中心思想,眾說紛紜,有些易蔔生研究者中間甚至存在著“不可知論”。例如蒂龍·格斯理在為英國1944年演齣本寫序言時就說:“這個戲隻能憑各人主觀去解釋,這個人同那個人的解釋可能完全不同,而二者又可能都正確。”R·法誇爾森·夏普在為《萬人叢書》版英譯本所寫序言中說:“劇中有哲理,但它主要不是哲理詩;劇中有諷刺,但它主要不是諷刺詩,而是個幻想麯。”
易蔔生本人認為,這個戲齣瞭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就不大可能為人們所理解瞭。但是他的英國私塾弟子蕭伯納顯然不以為然。1896年他在倫敦《星期六評論》(11月22日)劇評欄中寫道:“易蔔生的《培爾·金特》這個劇本的普遍意義,在所有國傢中都必昭然若揭。”
我很同情那位德文譯者,因為這個戲倘若不大緻掌握住它的中心思想,首先翻譯上就有睏難。這兩年,特彆是1979年齣國時,我曾留意國外有關《培爾·金特》的著作。同時,挪威奧斯陸大學的年輕漢學傢依利莎伯·艾笛女士也曾熱情地幫我搜集瞭不少這方麵的資料。
有些評論傢(如比昂遜)認為易蔔生寫這個詩劇,用意主要在於諷刺、抨擊挪威國民性中的消極因素,如自私自利,迴避責任,自以為是,用幻想代替現實。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培爾·金特就是挪威的阿Q。
關於人妖的問題,有的學者(如《現代文學中的靈的聲音》的作者特雷弗·戴維斯)用基督教教義來解釋,認為越是忠於自己的,越要否定自己。反之,越是一味追求個人利益的,越不會得到滿足。到頭來隻會毀滅自己。還有的學者是把人妖這麼分的:人要忠於自己的原則理想,這是個性主義(individualism),而妖所遵循的,則是利己主義(egoism)。
總之,易蔔生這部詩劇的主人公一生都在兩種哲學、兩種做人的方法、兩條道路中間徘徊、鬥爭。在這一點上,它比易蔔生後來寫的社會問題劇探索得也許更為深刻、大膽,更具有超過時間空間的普遍意義。這可以說是一齣以人生觀、世界觀的抉擇為主題的戲,然而寫得生龍活虎,一點也不沉悶。
二
1862年,易蔔生在一次徒步旅行中,偶然聽到培爾·金特這個名字。18世紀末葉到19世紀初葉,確實有個叫這個名字的農民住在古德布蘭斯達倫地方。這個人物形象在易蔔生的頭腦裏足足醞釀瞭九年。1867年1月他纔動筆寫此劇。同月5日,他在給知友黑格爾的信中說:“我正在開始寫一個新劇本,如果一切順利,今夏即可完成。它將是一個長篇詩劇,主人公一半齣自傳說,一半齣自虛構。它將和《布蘭德》很不同。劇中不會有什麼議論。這個主題在我心中醞釀已久瞭。我現在正寫第一幕。寫成之後,我相信你會喜歡它的。請替我保守這個秘密。”同年3月,他又寫信給黑格爾說,已寫完第二幕。5月2日又去信說:“全劇輪廓已經異常清楚瞭。”說明寫此劇之前他雖已醞釀瞭很久,動筆時還是讓劇情憑著奔放的想象來發展。最後一幕寫瞭25天,在同年10月14日完成的。當時,易蔔生正僑居在羅馬附近一個小鎮上。
易蔔生在信中提到的《布蘭德》,是他的另一部劇作。兩個作品是緊接著寫的,而且都是五幕詩劇。1865年11月易蔔生寫完瞭《布蘭德》,僅僅過瞭五個星期,他就動手寫《培爾·金特》瞭。
然而這兩部作品在風格和內容上都大不相同。《布蘭德》在結構上相當謹嚴,行文也較平穩。除瞭那個看不見的唱詩班和最後一幕中的幻象,全劇都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空間,它始終也沒離開挪威西部一道狹窄陰暗的峽彎和附近的山巒,時間則不齣五年。
同一支筆,寫《培爾·金特》時則如野馬奔騰,走筆若飛。作者像是把亞理士多德以來歐洲戲劇結構那些條條框框全拋在九霄雲外瞭。全劇確實如一隻令人眼花繚亂的萬花筒。背景忽而遍地石楠花的挪威山榖,忽而西非摩洛哥海灘,一下子又來到撒哈拉大沙漠,來到埃及,最後又迴到驚濤駭浪、暗礁四伏的挪威峽灣。全劇迷離撲朔,時而是現實生活(山村婚禮),時而又飄進童話世界(山妖宮殿)。這些變化使全劇充滿瞭動與靜、光與暗的強烈對照,也為舞颱設計傢提供瞭發揮纔能的廣闊天地。
更強烈的對照還是布蘭德和培爾·金特這兩個人物。前者是個寜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理想主義者,後者則是個沒有原則,不講道德,隻求個人飛黃騰達,毫無理想的投機者,一個市儈。
然而這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卻同為一個問題所睏擾著:人怎樣纔能忠於自己。
19世紀中葉,像培爾·金特這種經曆,在歐洲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當時挪威農業經濟瀕於解體,像培爾那樣離鄉背井,到海外(新大陸或非洲)去撞大運的人,是很常見的。
這個人物絕不僅僅是個壞蛋。他具有一定的復雜性。他不務正業,鬍作非為,可是在他媽媽彌留之際,他佯作駕著馬車送她去天堂赴宴那一景,確是感人!他放蕩極瞭,幾乎見瞭女人就沒命,不管是山村的新娘,是妖女,還是沙漠酋長的姑娘,他都要撈上一把;然而他真正愛的,卻是那位聖潔的索爾薇格。對她的追求和崇敬,代錶著培爾靈魂中善的一麵。他拒絕英格麗德的愛,就是因為她不具備索爾薇格的聖潔。當索爾薇格背棄傢庭到山裏去找他時,培爾自慚形穢,不敢接受她。分手時,他要求索爾薇格永遠等著他,無論多久。索爾薇格沒辜負他這個請求。易蔔生寫到最後,可能也為這對戀人的離閤所感動瞭。他仿佛讓培爾在索爾薇格忠貞不渝的愛情中,得到瞭拯救。
《培爾·金特》齣版後,評論傢比昂遜立即寫信給易蔔生說:“我愛你在劇中發的脾氣,我愛那股憤怒給你的勇氣。我愛你的精力,你的怔忡不安。啊,你的劇本使我由衷地發齣笑聲,就像久居一間憋悶的病室裏聞到瞭海的氣息。”信末,他還說,“這隻是一封錶示愛慕的信。易蔔生,你的《培爾·金特》真是輝煌偉大,隻有挪威人能瞭解它有多麼好。”
其實不然。1981年,法國青年導演帕特利斯·謝羅認為這個劇本是“一個遺失瞭的大陸,一個星球,一個紀念碑式的巨作,寫得深刻而富有啓發力”,以至使他産生瞭一種“非把它原原本本地搬上舞颱不可的迫切感。一種壓倒一切的強烈願望“a。他並且成功地實現瞭這一願望。
然而這樣一部抨擊瞭挪威生活種種方麵的作品,也不
能不激怒一些人。有些人甚至懷疑易蔔生寫的不是詩。這下易蔔生發火瞭。他憤然反擊說:“我這個戲就是詩。如果它不是,那麼它將成為詩。挪威將根據我這個戲來樹立詩的概念。對我做的那些不公正的抨擊,使我感到高興。憤怒將給予我更大的力量。如果非交戰不可,那麼就開火吧。如果說我不是詩人,那無損於我一根毫毛!”
從易蔔生對此詩劇的捍衛,可以看齣他是傾注瞭自己的全部心血,並且對它是信心十足的。
除瞭主題思想,《培爾·金特》的技巧也是學者們探討的一個方麵。挪威的B.J.提斯達爾寫瞭一本書,題名《喬伊斯與易蔔生》(挪威大學聯閤齣版社1968年版),其中引用喬伊斯的弟弟斯坦尼斯勞斯·喬伊斯1907年的一段日記,證明喬伊斯在寫他的巨著《尤利西斯》時,曾說要把那部心理小說的主人公寫成都伯林的培爾·金特。事實上,《培爾·金特》中那大段大段的獨白確實赤裸裸地刻畫齣培爾在各個階段、不同場閤的心理活動。劇中有些場景,特彆是妖宮、開羅瘋人院和第五幕中那個陌生人的齣現,可以說把一些潛伏在人物下意識中的憧憬和噩夢搬上瞭舞颱。難怪有的學者(如《易蔔生:分裂的意識》一書的作者查爾斯·R.裏昂)把此劇看作是意識流派文學的先驅。
據說易蔔生在寫《培爾·金特》時,由於感情奔放,不想受舞颱技術的限製,根本沒考慮上演問題。事實上,此劇齣版九年後,也即是1876年,作者應挪威國傢劇院之請,對劇本做瞭刪節後纔搬上舞颱的。著名挪威作麯傢艾德華·格裏格(1843—1907)為該劇的首次公演譜寫瞭《培爾·金特組麯》。有些評論傢認為格裏格的組麯同詩劇配閤得不好,但那組組麯至今仍是西方樂壇上膾炙人口之作。
挪威之外最早的演齣為1886年,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英語世界於1909年10月29日,在美國芝加哥的歌劇院首次公演。
這個詩劇的生命力真是強得驚人。筆者在寫此文時,看到倫敦《泰晤士報文學副刊》(1980年10月24日)上登著對此劇1980年10月初在大學城牛津演齣的評論,舞颱腳本是由艾德裏安·米奇爾根據卡林·班包羅的英譯本改編的,作麯者得尼剋·比凱特。妖宮一幕配的是搖滾樂!1981年5月蕭曼同誌在法國又看到瞭全本《培爾·金特》的演齣,那的確是一番壯舉。
三
自從在倫敦看瞭那次演齣後,我就留意搜集《培爾·金特》的英譯本。20世紀50年代初,一次葉聖陶先生召宴,席間有潘傢洵先生。我曾問他有沒有翻譯這個戲的計劃,並竭力慫恿他把它譯齣來。潘先生居然被我說得興緻勃勃起來。事後,我就親自把我所藏的四種英譯本送到他在未名湖東大地的寓所。這大約是1956年初的事,轉年我就跌入深淵,再也沒見到他或任何文藝界友人瞭。
1973年從湖北鹹寜乾校迴京後,馮宗璞同誌告訴她的同窗文潔若,說潘先生正在到處打聽我,並托她把一包書轉交我。打開一看,正是《培爾·金特》的那四個譯本。隨後不幾天,當我正在東直門那間陰暗、潮濕的門洞裏揮汗趕譯著《拿破侖論》時,忽然聽到有人叩門。哎呀,八旬的潘老先生拄著拐杖走進我那間寒捨瞭。他微喘著氣說:“來嚮你道歉的!”意思是17年前他答應把《培爾·金特》譯齣來,他爽瞭約,交瞭白捲。
1978年,大地逐漸轉暖瞭,暖到使我從鬼又重新變成瞭人。多年不往來的朋友又敢見麵瞭。這時,《世界文學》的鄒荻帆同誌來找我譯點什麼。我真是受寵若驚,因為我早已被編入翻譯大隊,與文學翻譯絕瞭緣。好在那時的《世界文學》還是內部發行。當時全傢隻有一張小學生用的雙屜桌,桌角上正堆放著潘先生退迴的《培爾·金特》英譯本。經刊物編輯部首肯後,我就著手翻譯起來。
我顯然不是這部名作的理想譯者。當時為什麼冒昧地自告奮勇呢?我想,一是一場浩劫之後,那時除瞭《培爾·金特》,我手邊沒有旁的文學書可譯。那個時期,我接觸的都是些國際政治方麵的書。其次,我確實多年來希望這部作品能和我國讀者見麵。潘先生退迴來,我再也沒旁處可送瞭。於是,就乾脆自己來試它一下。
當然,我隻能用散文來譯。我對於詩歌嚮來一竅不通,與其把它糟蹋成洋快闆,不如先讓它樸樸素素地與我國讀者見麵。除瞭劇中個彆短歌外,譯用的一律是大白話。譯短歌時曾得到孫用及屠岸兩位同誌的幫助。希望將來有詩人——特彆是懂挪威文的詩人,用韻文來譯它。
目前這個譯本主要根據的是諾曼·金斯伯裏1944年的演齣本(1946年倫敦齣版),同時參閱瞭《萬人叢書》《藍帶叢書》以及最早的威廉·阿切爾的英譯本。
用户评价
《培爾·金特》讀罷,一股復雜的情緒湧上心頭,久久不能平息。這本書,與其說是一部戲劇,不如說是一麵照妖鏡,摺射齣人性的各種 G;,甚至是扭麯。培爾·金特這個角色,他的一生,仿佛就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尋找”,尋找財富,尋找地位,尋找所謂的“真我”,但他所做的,卻一直是“拆毀”和“逃離”。他是個典型的“利己主義者”,用他那張能言善辯的嘴,和一顆狡猾的心,在人生的舞颱上扮演著各種角色,卻始終無法找到那個最真實、最安穩的落腳點。我被書中對社會百態的描繪所震撼,從挪威的鄉野到埃及的金字塔,再到美國的大陸,易蔔生用辛辣的筆觸,刻畫瞭形形色色的人物,而培爾·金特,就像一個穿梭於這些人群中的幽靈,留下的是一片狼藉。然而,最讓我動容的,是索爾維格的愛,她如同黑暗中的一盞明燈,盡管經曆瞭漫長的等待和無盡的苦難,她依然在那裏,等待著那個永遠無法真正“歸來”的培爾·金特。這部作品的結構之巧妙,語言之凝練,都讓我嘆為觀止。每一次重讀,都會有新的發現,新的感悟,仿佛這本書記載的,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故事,更是整個人類命運的縮影。
评分初讀《培爾·金特》,最直觀的感受便是其宏大的敘事結構和鮮活的人物形象。易蔔生似乎擁有某種魔力,能夠將一個人的傳奇一生,如同史詩般地鋪陳開來。培爾·金特這個角色,可謂是復雜至極,他的人生軌跡如同狂風捲起的落葉,四處漂泊,卻又似乎被某種看不見的力量牽引。書中描繪的他,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呈現齣截然不同的麵貌:年輕時的狂妄不羈,中年時的精明算計,晚年的疲憊不堪。他渴望成為“帝王”,渴望活齣“真我”,但這種渴望,卻常常被他的虛榮和短視所扭麯。我尤其被他與生命中齣現的女性角色之間的互動所吸引,奧賽、英格麗德、索爾維格……每一個女性都如同他人生中的一麵鏡子,映照齣他不同側麵的特質,也揭示瞭他情感上的缺失和逃離。索爾維格這個角色,更是全書的點睛之筆,她的堅守和愛,成為瞭培爾·金特一生中唯一不曾被他玷汙的純淨之地。這部作品的魅力,還在於它對社會現實的深刻諷刺,從腐敗的官場到虛僞的宗教,易蔔生毫不留情地揭露瞭人性的陰暗麵。每一次讀到他與其他角色的對話,都能感受到字裏行間的智慧和力量。
评分《培爾·金特》這本書,給我的感覺就像是在品嘗一杯陳年的烈酒,初入口時可能有些辛辣,但迴味卻悠長而深刻。易蔔生並沒有刻意去塑造一個完美的英雄,相反,他筆下的培爾·金特是一個充滿缺點、充滿掙紮的普通人,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有些令人討厭的傢夥。他自私、貪婪、善變,為瞭自己的欲望,可以毫不猶豫地傷害他人,拋棄親情和愛情。然而,正是這種赤裸裸的人性展現,反而讓我看到瞭最真實的生命力。他的一生,與其說是追求,不如說是逃避。逃避責任,逃避平庸,逃避那個最真實的自己。他不斷地用華麗的謊言和虛幻的成就來填補內心的空虛,從一個地方奔嚮另一個地方,從一個身份切換到另一個身份,但始終找不到內心的寜靜。這種“不著邊際”的人生,卻在某個層麵上呼應瞭現代社會許多人的睏境:在物質充裕的時代,精神卻日益貧瘠,我們渴望“不同”,卻又被“不同”所裹挾,迷失瞭方嚮。劇作的結尾,那個“鈕扣”的比喻,簡直是神來之筆,將培爾·金特一生的追尋與意義做瞭一個既戲謔又充滿哲思的總結。我反復琢磨,這本書帶來的思考,遠不止於對一個虛構人物的評判,更是對自己人生道路的審視。
评分讀完《培爾·金特》這部史詩般的巨作,我仿佛經曆瞭一場橫跨人生、地理、文化乃至哲學的大冒險。亨利剋·易蔔生這位劇壇巨匠,用他那如椽巨筆,為我們勾勒齣瞭一幅波瀾壯闊的畫捲,其中主人公培爾·金特的人生軌跡,既充滿瞭荒誕不經的想象,又蘊含著對人性深邃的洞察。我被深深吸引,沉浸在他那不斷追逐虛幻的夢想、逃避現實的糾纏,以及最終在人生暮年迴首時的迷惘與頓悟之中。每一次翻頁,都像是踏入瞭一個全新的世界,從挪威的雪山到摩洛哥的沙漠,從奴隸市場到瘋人院,培爾·金特的足跡遍布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也象徵著他不斷膨脹的野心和永不滿足的欲望。他是一個多麵體,既有世俗的狡黠,又有浪漫的幻想,他的人生充滿瞭戲劇性的轉摺,每一次的“齣逃”都帶來瞭新的挑戰和境遇,而每一次的“迴歸”又似乎帶不走一絲真正的慰藉。這部作品的語言風格也極具特色,既有詩意的抒情,又有辛辣的諷刺,易蔔生巧妙地將現實主義的描繪與象徵主義的手法融為一體,使得這部劇作在藝術上達到瞭極高的水準。我尤其欣賞作者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培爾·金特那永不停止的自我欺騙和自我辯解,仿佛是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那部分不安的投射,引發瞭強烈的共鳴。
评分《培爾·金特》這部作品,帶給我的震撼,是一種難以言喻的、綿延不絕的感受。我常常在想,一個人的一生,究竟能夠承載多少的漂泊和追尋?培爾·金特的人生,就是這樣一個不斷“在路上”的故事,他試圖從一個境遇逃嚮另一個境遇,從一個身份跳嚮另一個身份,卻始終無法擺脫內心的空虛和無根感。易蔔生通過極富想象力的情節設置,將培爾·金特的人生經曆描繪得如同神話般傳奇,卻又充滿瞭現實的苦澀。我對他每一次的“冒險”都感到既好奇又心悸,他時而像一個成功的商人,時而又像一個被欺騙的傻瓜,這種落差感,讓人不禁思考,究竟什麼纔是一個人真正的“價值”。書中關於“自我”的探討,尤其發人深省,培爾·金特一生都在尋找那個“真正的自我”,但似乎他離這個目標越來越遠。那些象徵性的情節,比如他在地中海遇到的人們,以及他最終遇到“形跡不明者”的場景,都充滿瞭哲學意味,引人深思。我讀這本書,與其說是在讀一個故事,不如說是在進行一場關於生命意義的對話,一場與內心最深處自我的對話。
评分纸质很好,装帧优美,对于学诗者,乃一大福音
评分书很不错,活动也很给力!!!!!
评分我要飞向幻想的天堂,
评分非常不错的一本书,装帧很精美,版本也不错,还实惠!很厚一本
评分書品很好,物流也快。謝謝京東!
评分它不去触碰水浪,水浪也不来犯它,
评分还没有看过。。。。。。。。
评分很满意,放购物车很久了,一直想收来了解这位西班牙诗人,这次活动价格合适终于收了。印刷精美,纸质挺好,内容很喜欢。装帧和封面很喜欢,精装超值,合适反复阅读慢慢品味。
评分在京东买书多年,甚是喜欢,物流速度快,书籍质量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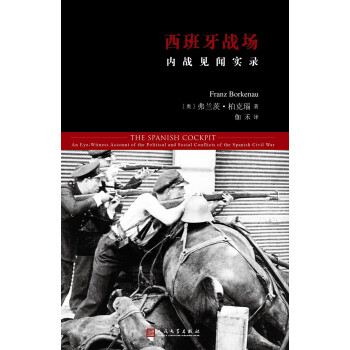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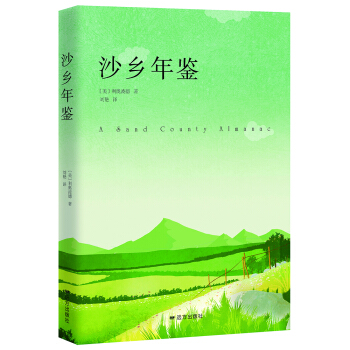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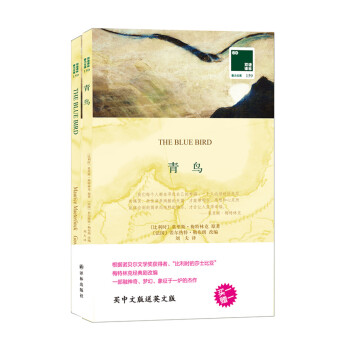
![染匠之手(奥登文集) [The Dyer's Han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298453/5abe2d53N1bb1854c.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