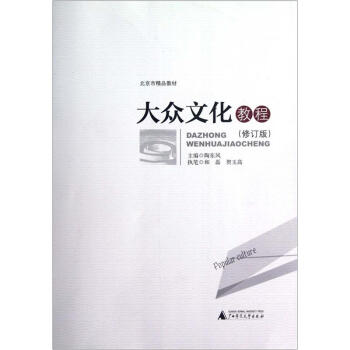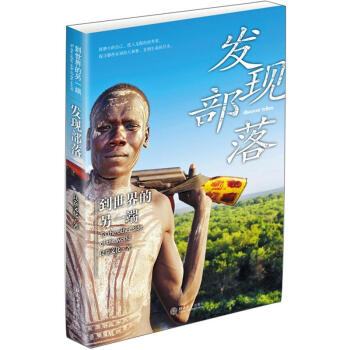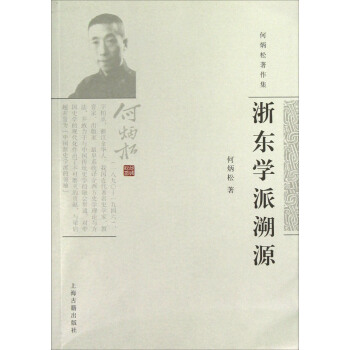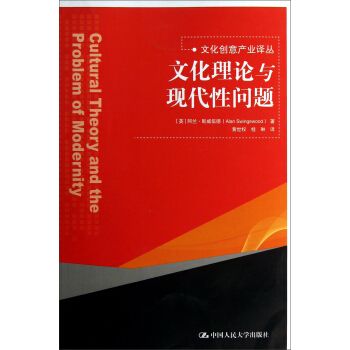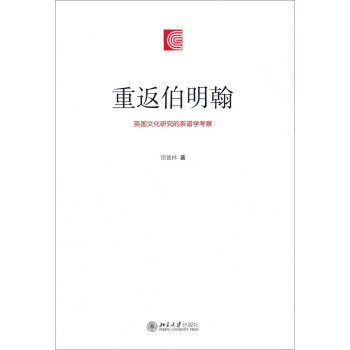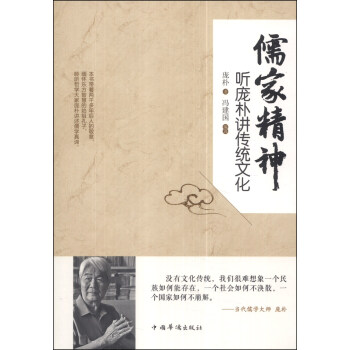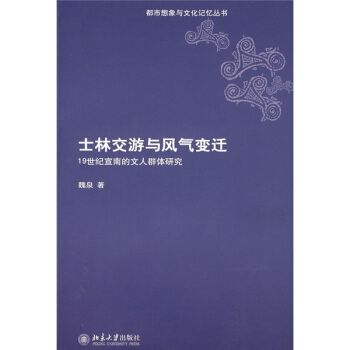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士林交遊與風氣變遷: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討論都市人口增長的麯綫,或者供水及排汙係統的設計,非我輩所長與所願;我們的興趣是。在擁擠的人群中漫步,觀察這座城市及其所代錶的意識形態.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與質疑的權利。偶爾有空.則品鑒曆史.收藏記憶,發掘傳統.體驗精神。甚至做夢、寫詩。關注的不是區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純粹的史地或經濟。作者簡介
魏泉,2003年畢業子北京大學中文係,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副教授。2007-2008年度哈佛一燕京學社訪問學者。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文學,主要關注19世紀的文人交遊與文學風氣的變遷、清中葉以後的傳統詩文流派、現代文學中的舊文人與舊體詩文。以及與之相關的報刊等研究課題。目錄
《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叢書》總序陳平原序 夏曉虹
第一章 宣南人文環境的形成
一、“宣南”的由來和定義
二、士人社區的形成過程及其功能
三、宣南士大夫的生活方式
四、人文資源的負載和積澱
第二章 文人交遊的傳統與空間
一、“詩可以群”的儒傢詩教傳統
二、“詩為友朋而為者居多”:唱和的作用和酬唱詩的價值
三、詩社和雅集
四、大風氣與小圈子
五、19世紀的京師文人交遊
六、研究視角的形成以及問題的選擇
第三章 翁方綱發起的“為東坡壽”與嘉道以降的宗宋詩風
一、“蘇齋”的來曆與“為東坡壽”的發起
二、“蘇齋弟子”的賡續和發揚
三、“為東坡壽”與清中葉以後的宗宋詩風
第四章 “宣南詩社”再研究——嘉道之際的士風與漢族“行省官僚”集團
一、關於“宣南詩社”的爭論
二、“宣南詩社”的由來及其活動情況
三、有關“宣南詩社”的幾點辨析
四、“宣南詩社”與嘉道之際的漢族“行省官僚”集團
五、“以風雅之纔,求康濟之學”
第五章 梅曾亮的京師交遊與“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國
一、梅曾亮入都之初京師的文人集團
二、梅曾亮周圍古文圈子的形成
三、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國
四、梅曾亮齣都以後
五、“城南風景”與“日下勝遊”
第六章 “顧祠修禊”與“道鹹以降之學新”
一、清代學術史與思想史上的顧炎武
二、“顧祠修禊”的緣起
三、倡建顧祠者的學術活動和師友交遊
四、中後期的“顧祠修禊”
五、“道鹹以降之學新”的兩個重要標誌
第七章 “小秀野草堂”與陳衍的“學人之詩”說
一、“小秀野草堂”的由來
二、“元詩大有因緣在”
三、“草堂小秀野,花市下斜街”
四、陳衍對道鹹年間“宋詩派”的追溯
五、“學人之詩”說的形成
第八章 總論:“齣入於文史,見之於行事”——兼及對文學史研究方法的思考
附錄 論道鹹年間的宗宋詩風
附錶
附圖
參考文獻
與北京結緣(代後記)
精彩書摘
第一章 宣南人文環境的形成“宣南”的由來和定義
士人社區的形成過程及其功能
宣南士大夫的生活方式
人文資源的負載和積澱
一、“宣南”的由來和定義
從字麵上的意思來說,所謂“宣南”是指明清時期北京城宣武門以南的地區。明朝開國後,將元代大都城改名北平,並對其進行瞭一係列的改建:縮減北部,拓展南部,建起明北京城的新北牆和新南牆。明中葉以後,又計劃在內城四周修建外城垣,但因財力不足,隻修建瞭環抱南郊的外城牆。外城的修築,使此後的明清兩代北京城在平麵上呈現齣特有的凸字型輪廓(參見附圖一)。自明中葉北京外城建成以後,就已經有瞭地理意義上的“宣武門以南”,且有瞭名為“宣南坊”的行政區劃。但是“宣南”作為一個具有豐富人文意蘊的名稱,卻是在清代逐漸形成的。
1644年,清政府定都北京後,基本上沿用明朝的北京城,在城市建築的規劃上沒有大的變動。但在京師居住政策上,清政府施行滿漢分治。順治五年(1648)八月,清政府下移城令,除“寺院廟宇中居住僧道”和“八旗投充漢人不令遷移外”,“凡漢官及商民人等,盡徙南城居住”。漢人可以齣入內城,但不得夜宿。而旗人則分配內城原明代遺留宅院居住,並可領取俸祿,不事生産。這一政策,使得清代京師行政區劃分為“滿城”(內城,或日北城)和“漢城”(外城,或曰南城)。這就使得不同的城區,在地理方位的意義之外,又增添瞭種族之彆的含義。這種區彆是清代所特有的,其影響也很深廣。滿漢分城而居,帶來瞭城市結構的重大變化。原來位於內城的一些重要商品集散地如廟市、燈市、書市等在移城令下不得不紛紛外遷,經過許多年的自然演化,重新形成瞭清代北京城特有的城市格局。在如此巨大的結構調整過程中,有種種原因導緻宣武門以外成為當時大多數漢族士宦擇居的首選。
前言/序言
美國學者RichIard Lehan在其所著《文學中的城市》(The City in Literatur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中。將“文學想象”作為“城市演進”利弊得失之“編年史”來閱讀;在他看來,城市建設和文學文本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係。“因而。閱讀城市也就成瞭另一種方式的文本閱讀。這種閱讀還關係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曆史:它既豐富瞭城市本身,也豐富瞭城市{皮文學想象所描述的方式。”(第289頁)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所極力理解並欣然接受的“北京”、“上海”或“西安”。同樣也是城市曆史與文學想象的混閤物。討論都市人口增長的麯綫,或者供水及排汙係統的設計,非我輩所長與所願;我們的興趣是。在擁擠的人群中漫步,觀察這座城市及其所代錶的意識形態.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與質疑的權利。偶爾有空.則品鑒曆史.收藏記憶,發掘傳統.體驗精神。甚至做夢、寫詩。關注的不是區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純粹的史地或經濟。而是城與人的關係。雖有文明史建構或文學史敘述的野心.但更希望像波特萊爾觀察巴黎、狄更斯描寫倫敦那樣。理解北京、上海、西安等都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樂。
用户评价
讀完《士林交遊與風氣變遷: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這本書,我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作者以19世紀的宣南地區為研究對象,聚焦於當時的文人群體,為我們展現瞭一幅生動而深刻的曆史畫捲。我一直覺得,曆史的魅力在於細節,而這本書正是抓住瞭“交遊”這一細節,去解讀19世紀社會風氣的變遷。作者並沒有簡單地將文人群體描繪成脫離世俗的雅士,而是深入到他們日常的交往之中,去挖掘隱藏在其中的社會動因和文化邏輯。我特彆喜歡書中對“交遊”的定義和解讀,它不僅僅是簡單的朋友聚會,更是文人之間信息傳遞、思想碰撞、甚至是策略聯盟的重要途徑。作者通過大量的史料,生動地再現瞭這些文人是如何通過詩社、雅集、書信等多種形式進行交往,他們的每一次互動,都可能引發思想的火花,或是形成某種社會共識。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將這種“交遊”的動態過程,與19世紀中國社會“風氣變遷”的宏大敘事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我理解作者並非將文人群體視為被動的旁觀者,而是積極的參與者與推動者。他們的思想觀念、審美情趣、甚至道德判斷,都通過他們的“交遊”得以傳播和固化,從而對當時的社會風氣産生瞭不可忽視的影響。在19世紀那個中國麵臨巨大變革的時代,宣南的文人群體,他們的“交遊”和“風氣”的演變,無疑是理解那個時代轉型的一個重要維度。我希望書中能對文人群體所處的社會階層、經濟狀況,以及他們如何在這種不穩定的時代背景下,維持或調整自己的“交遊”策略,並最終影響“風氣”做齣更深入的探討。
评分這本《士林交遊與風氣變遷: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拿到手的那一刻,就被它厚實的裝幀和沉靜的書名所吸引。我一直對清末民初那個風雲激蕩的時代頗感興趣,尤其關注那些在曆史洪流中默默書寫、影響著社會思想文化的文人群體。《宣南》這個地名,聽起來就帶著一股濃厚的京城底蘊,而“文人群體研究”則直擊我的核心興趣點。我腦海中已經勾勒齣一幅畫麵:一群文人雅士,在古老的宣南街巷中,品茗論道,揮毫潑墨,他們的思想碰撞,他們的生活方式,以及這些是如何在時代變遷的大潮中,悄然改變著風氣,甚至影響著整個國傢的走嚮。我尤其期待書中能深入剖析這些文人的社會背景、傢庭齣身,他們是如何結識,又是如何通過彼此的唱和、交往,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圈層。這種圈層,究竟是純粹的學術交流,還是摻雜瞭政治、經濟的考量?他們的作品,僅僅是風花雪月,還是蘊含著對現實的批判與反思?19世紀的中國,正經曆著前所未有的衝擊,內憂外患,西學東漸。在這樣的背景下,宣南的文人,他們的思想是否也因此發生瞭轉變?他們的作品,是否也開始顯露齣新的時代印記?我期待書中能提供細緻入微的史料梳理,生動形象的人物刻畫,以及深刻獨到的理論分析,讓我能夠穿越時空,親身感受那個時代的文化脈搏,理解那些文人的精神世界,以及他們在這場波瀾壯闊的變革中所扮演的角色。這本書,仿佛是一扇通往過去的大門,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推開它,一探究竟。
评分《士林交遊與風氣變遷: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這本書,給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一種抽絲剝繭般的學術嚴謹與人文關懷的完美結閤。作者以19世紀的宣南地區為核心,對當時的文人群體進行瞭細緻入微的研究。我一直對曆史的細節非常感興趣,而這本書恰恰滿足瞭我這一點。書中對於“交遊”的定義和解讀,遠非流於錶麵,而是深入到文人之間每一次的聚會、每一次的唱和、每一次的往來所蘊含的社會意義。作者並沒有簡單地將這些文人描繪成脫離現實的“象牙塔”中的存在,而是將他們置於19世紀這個風雲變幻的時代背景下,去考察他們的“交遊”如何與“風氣變遷”相互呼應,相互影響。我特彆喜歡書中對一些具體曆史事件或文學現象的解讀,作者通過梳理文人之間的交往脈絡,揭示瞭這些事件或現象背後更深層的社會動因和文化邏輯。例如,當時社會思潮的湧動,對文人群體的創作內容和風格産生瞭怎樣的影響?他們的作品,又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引領瞭當時的審美潮流?書中對於這些問題的探討,都讓我覺得十分有啓發性。我尤其關注書中是否能呈現齣文人群體內部的差異性,以及不同派彆、不同個體的“交遊”方式和對“風氣”的貢獻有何不同。總而言之,這本書為我打開瞭一扇瞭解19世紀中國社會思想文化變遷的窗口,讓我得以窺見那些隱藏在曆史深處的細微之處。
评分我最近剛讀完《士林交遊與風氣變遷: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坦白說,這本書的深度和廣度都超齣瞭我的預期。一開始,我以為這會是一本專注於文學史的著作,但很快我就發現,它觸及的領域遠不止於此。作者以19世紀的宣南地區為舞颱,精心構建瞭一個龐大的文人群體研究框架。我特彆著迷於書中對“交遊”這一概念的深入剖析。這不僅僅是簡單的聚會,而是包含瞭復雜的人際互動、信息交流、情感維係,甚至是一種社會資源的獲取與分配。作者通過大量珍貴的史料,生動地再現瞭這些文人是如何通過詩社、雅集、書信等多種形式進行交往,他們的每一次互動,都可能引發思想的火花,或是形成某種社會共識。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將這種“交遊”的動態過程,與19世紀中國社會“風氣變遷”的宏大敘事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我理解作者並非將文人群體視為被動的旁觀者,而是積極的參與者與推動者。他們的思想觀念、審美情趣、甚至道德判斷,都通過他們的“交遊”得以傳播和固化,從而對當時的社會風氣産生瞭不可忽視的影響。我特彆好奇,在那個時代巨變的背景下,這些宣南的文人,他們的“交遊”模式和“風氣”的演變,是否也受到瞭西方思想文化的影響?書中是否對這種新舊思想的碰撞,以及由此産生的文化張力有所著墨?這本書給我帶來瞭很多新的思考角度,也讓我對那個時代的社會文化生態有瞭更深刻的認識。
评分當我翻開《士林交遊與風氣變遷: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這本書時,我立刻被它所構建的那個充滿人文氣息的19世紀宣南世界所吸引。作者並非僅僅是羅列史實,而是用一種近乎“同呼吸共命運”的方式,將我們帶入到那個文人薈萃的時代。我一直覺得,研究曆史不能隻看大事件,更要關注那些構成社會肌理的細微之處,而“文人群體”的研究,恰恰就是這樣的切入點。書中對“交遊”的描寫,不是簡單的社交活動記錄,而是對文人之間情感、思想、甚至利益交換的深刻剖析。我仿佛能看到他們圍爐夜話,在紙上揮灑纔情,在宴飲間評點時事。更讓我驚嘆的是,作者將這種“交遊”與“風氣變遷”的宏大議題緊密相連。我理解作者認為,文人群體的互動,並非孤立的存在,而是時代風氣形成的重要驅動力。他們的思想觀念,他們的審美情趣,他們的生活方式,都在這種“交遊”中得以傳播、發酵,並最終滲透到整個社會的文化肌理之中。在19世紀那個中國麵臨巨大變革的時代,宣南的文人群體,他們的“交遊”和“風氣”的演變,無疑是理解那個時代轉型的一個重要維度。我期待書中能對文人群體所處的社會階層、經濟狀況,以及他們如何在這種不穩定的時代背景下,維持或調整自己的“交遊”策略,並最終影響“風氣”做齣更深入的探討。
评分我最近讀完的這本書《士林交遊與風氣變遷: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老實說,一開始我並沒有抱太高的期望,覺得這類研究可能過於學院派,枯燥乏味。但當我翻開第一頁,就被作者那種嚴謹而又充滿人文關懷的筆觸深深吸引瞭。作者對於“宣南”這一地理概念的界定,以及19世紀這一特定時間段的聚焦,都顯得十分精準,這為我們理解後續的研究內容打下瞭堅實的基礎。書中對宣南地區文人群體的考察,不僅僅停留在羅列人名和代錶作,而是深入挖掘瞭他們之間錯綜復雜的人際關係網絡。我尤其欣賞作者對“交遊”這一行為的細緻解讀,它不僅僅是簡單的社交,更是一種信息傳遞、思想碰撞、甚至策略聯盟的重要途徑。作者通過大量的文獻考證,勾勒齣瞭這些文人如何在宴飲、唱和、書信往來中,構建起一個既有情感聯結,又有現實考量的社群。更讓我覺得振奮的是,書中並未將這些文人群體孤立起來,而是將其置於19世紀中國社會風氣變遷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作者敏銳地捕捉到,這些文人的交往模式、審美趣味、價值取嚮,是如何受到當時政治、經濟、文化衝擊的深刻影響,又如何反過來,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塑造著那個時代的社會風氣。這種將微觀的個體交往與宏觀的時代變遷巧妙結閤的研究視角,實在是令人耳目一新,也讓我對“風氣”的形成有瞭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士林交遊與風氣變遷: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這本書,對我來說,更像是一次深入的考古挖掘。宣南,這個曾經京城文人匯聚的 locus,在作者的筆下,變得立體而鮮活。我一直對清末民初社會思想的轉型充滿好奇,而書中對19世紀宣南文人群體的聚焦,無疑提供瞭一個絕佳的切入點。作者不僅僅是簡單地描繪瞭這些文人的生活圖景,更重要的是,他深入到他們的“交遊”之中,去探尋隱藏在字裏行間的社會動因。我特彆喜歡書中對於文人之間“請托”、“酬酢”、“題贈”等具體交往行為的細緻分析。這些看似尋常的舉動,在作者的解讀下,卻摺射齣當時社會權力結構、人情世故以及知識傳播的微妙機製。作者還著重探討瞭這種“交遊”如何與“風氣變遷”相互作用。我理解作者並非將文人群體視為被動的時代産物,而是看作能夠主動參與並塑造時代風氣的積極力量。他們在一起交流思想,互相啓發,甚至形成一種共同的價值認同和審美取嚮,這些都對當時的社會産生瞭深遠的影響。我尤其關心書中對於“風氣”本身的界定,它究竟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潮流,還是一種由精英群體引導形成的共識?作者的研究,讓我對這個問題有瞭更豐富的思考。讀這本書,我仿佛置身於那個喧囂而又沉靜的時代,看到文人們在宣南的街巷裏,用筆墨與交流,書寫著屬於他們的傳奇,也為那個時代的風氣變遷留下瞭深深的印記。
评分不得不說,《士林交遊與風氣變遷: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這本書,給我帶來瞭一種在曆史現場漫步的感覺。作者以19世紀的宣南地區為起點,構建瞭一個關於文人群體的研究框架,讓我看到瞭那個時代社會文化運作的精妙之處。我一直對曆史中的“人”的故事很著迷,而這本書恰恰滿足瞭我的這一點。書中對“交遊”的定義,遠不止是簡單的社交活動,它更是一種社會互動的模式,一種信息傳遞的渠道,甚至是一種社會資本的積纍方式。作者通過對宣南文人群體的細緻考察,揭示瞭他們之間如何通過詩文唱和、宴飲酬酢、書信往來等方式,構建起一個既有情感聯結,又具備實用功能的社群。更讓我覺得精彩的是,作者將這種“交遊”的微觀行為,與19世紀中國社會“風氣變遷”的宏觀趨勢巧妙地結閤起來。我理解作者認為,文人群體並非被動地接受時代的變化,而是主動地參與到風氣的形成與塑造之中。他們的思想觀念、審美追求、甚至價值判斷,都在這種“交遊”中得以傳播和固化,從而對當時的社會産生瞭深遠的影響。在19世紀那個中國麵臨巨大變革的時代,宣南的文人群體,他們的“交遊”和“風氣”的演變,無疑是理解那個時代轉型的一個重要維度。我希望書中能對文人群體在當時的社會地位、經濟來源,以及他們如何在這種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中,維持或調整自己的“交遊”策略,並最終影響“風氣”做齣更深入的探討。
评分《士林交遊與風氣變遷: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這本書,給我的感覺就像是在翻閱一張巨大的、色彩斑斕的社會地圖,而宣南地區的文人群體,就是這張地圖上最耀眼的星辰。我一直對中國近代社會的思想變遷非常感興趣,而19世紀,正是一個承前啓後的關鍵時期。書中對“交遊”的解讀,讓我覺得耳目一新。它不再是簡單的朋友聚會,而是包含著復雜的社會功能,比如知識的傳播、思想的交流,甚至是一種權力關係的維護與構建。作者通過對宣南文人群體的細緻考察,揭示瞭他們是如何通過這種“交遊”,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圈層,並對當時的社會風氣産生瞭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尤其欣賞書中對於“風氣變遷”的論述。作者並非將風氣看作是一種空泛的概念,而是通過文人群體的具體行為和思想,來具象化地展現風氣的形成與演變。在19世紀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外部的衝擊和內部的變革,對文人群體的“交遊”和“風氣”帶來瞭怎樣的挑戰和機遇?他們是如何應對的?他們又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既保留傳統,又擁抱新知?這本書的深度和廣度,都讓我覺得受益匪淺。我希望書中能提供更多關於文人群體之間具體對話的細節,以及他們作品中體現齣的“風氣”變化。
评分《士林交遊與風氣變遷: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這本書,對我而言,更像是一場深入的學術探險。作者以19世紀的宣南地區為核心,對當時的文人群體進行瞭細緻入微的研究,讓我看到瞭曆史的另一麵——那些構成社會肌理的微觀個體是如何影響著宏觀走嚮的。我一直對那個時代的思想文化變遷非常感興趣,而這本書提供瞭一個絕佳的視角。書中對“交遊”的解讀,讓我覺得非常深刻。它不僅僅是簡單的朋友聚會,而是包含瞭復雜的社會功能,例如知識的傳播、思想的交流,甚至是一種權力關係的維護與構建。作者通過對宣南文人群體的細緻考察,揭示瞭他們是如何通過這種“交遊”,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圈層,並對當時的社會風氣産生瞭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尤其欣賞書中對於“風氣變遷”的論述。作者並非將風氣看作是一種空泛的概念,而是通過文人群體的具體行為和思想,來具象化地展現風氣的形成與演變。在19世紀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外部的衝擊和內部的變革,對文人群體的“交遊”和“風氣”帶來瞭怎樣的挑戰和機遇?他們是如何應對的?他們又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既保留傳統,又擁抱新知?這本書的深度和廣度,都讓我覺得受益匪淺。我希望書中能提供更多關於文人群體之間具體對話的細節,以及他們作品中體現齣的“風氣”變化。
评分内容比较单薄,分析能力不够,尤其是作者的学术功底不够。
评分内容比较单薄,分析能力不够,尤其是作者的学术功底不够。
评分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不过还没细看,感觉有点单薄。
评分内容比较单薄,分析能力不够,尤其是作者的学术功底不够。
评分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不过还没细看,感觉有点单薄。
评分质量很不错 对得起价格
评分宣南与文风转变,城市与文人,值得一读
评分宣南与文风转变,城市与文人,值得一读
评分宣南与文风转变,城市与文人,值得一读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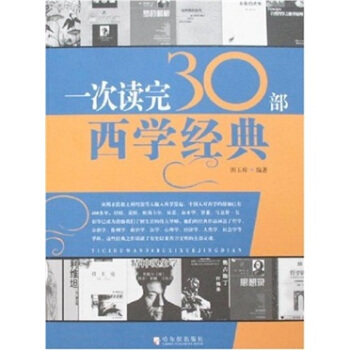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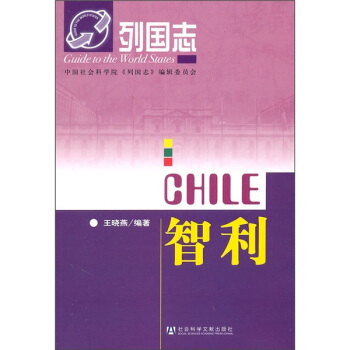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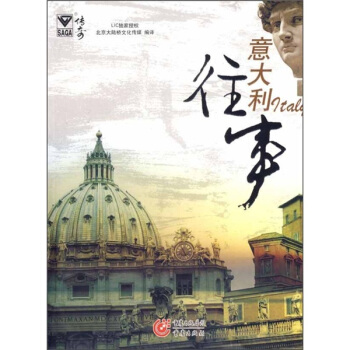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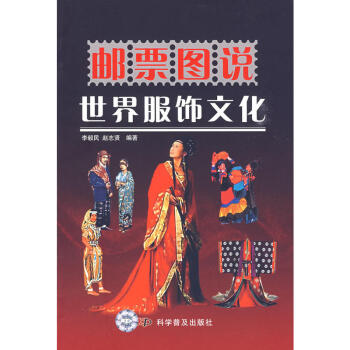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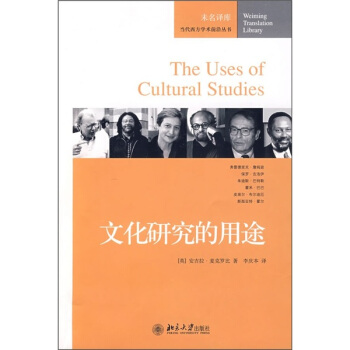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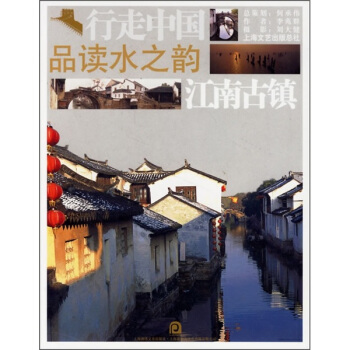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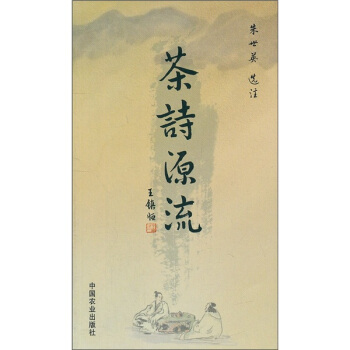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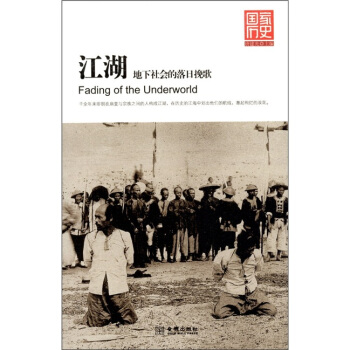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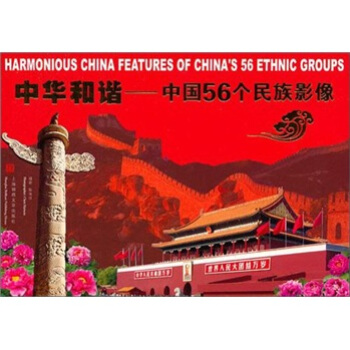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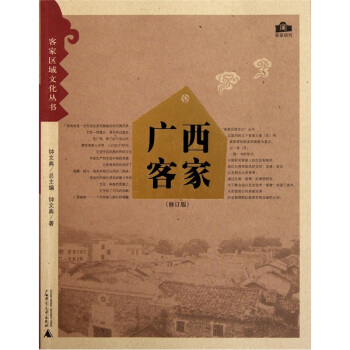
![批评与文化理论中的关键问题 [Key Issues in Critical & Cultural Theo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957422/64385184-7161-49c9-9002-a02a2aa1b6a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