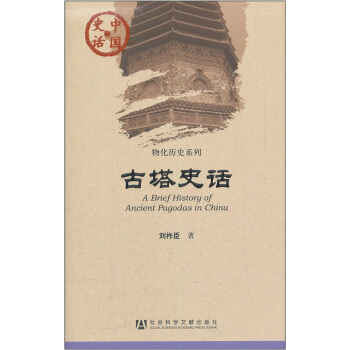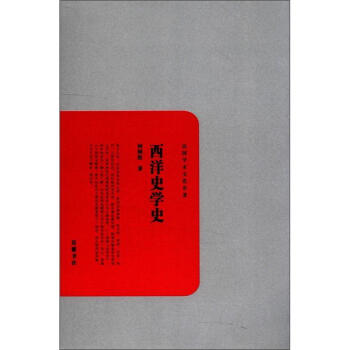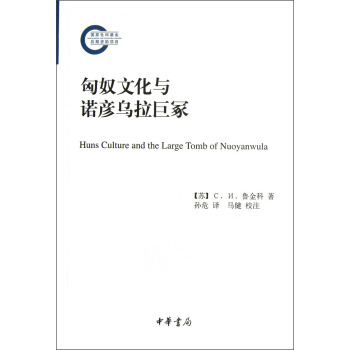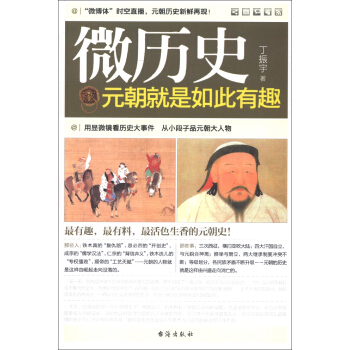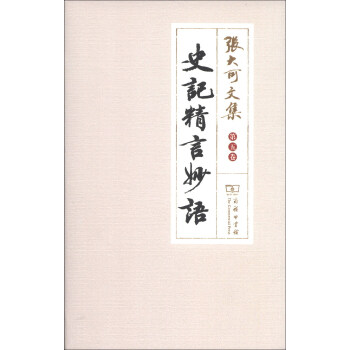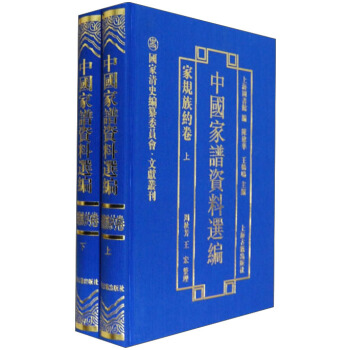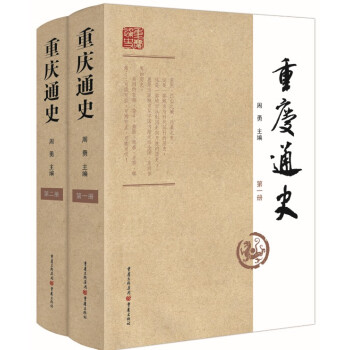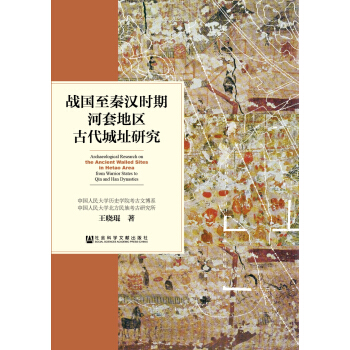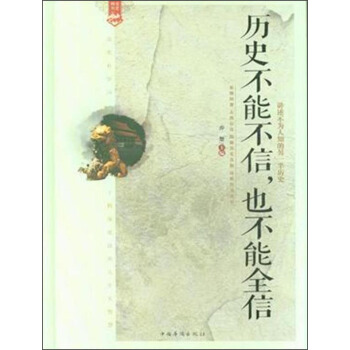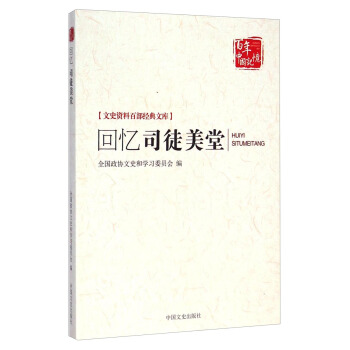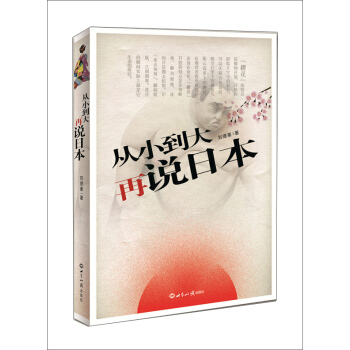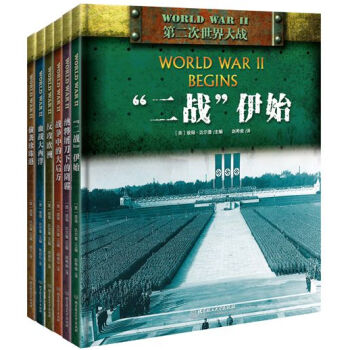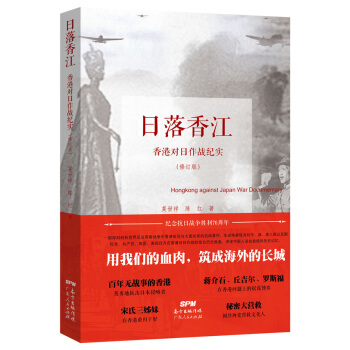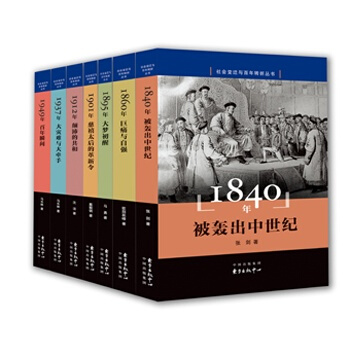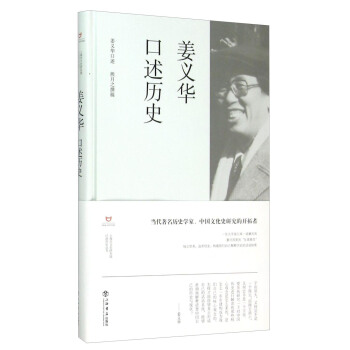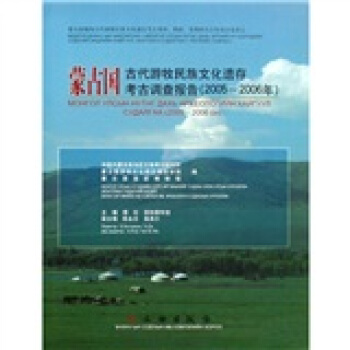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濛古國古代遊牧民族文化遺存考古調查報告(2005-2006)》為“濛古國濛境內遊牧民族文化遺存考古調查、勘探、發掘研究閤作項目”成果之一,是中濛閤作撰寫的第一部考古調查報告。是2005年、2006年度中濛聯閤考古隊對濛古國後杭愛省、前杭愛省、布爾乾省、中央省、肯特省、蘇赫巴托省、東戈壁省、南戈壁省、中戈壁省等10個省市的40餘個蘇木進行考古調查的成果展示。本書重點介紹瞭濛古國境內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匈奴、突厥、契丹、濛元和明清多個曆史時期的文化遺存,內容涉及到岩畫、赫列剋蘇爾、鹿石、四方慕、城址、碑刻、廟宇等諸多種類,基本上包括瞭濛古高原遊牧民族文化遺存的主要內容。目錄
序言·烏蘭前言·塔拉陳永誌
阿·奧其爾(濛古國)
一 石器時代文化遺存
烏斯圖登吉石器時代遺址
毛亦勒圖山榖石器時代遺址
阿拉菩哈達石器時代遺址
吉日格朗圖汗遺址
查鬍爾特渾地石器時代遺址
二 青銅時代文化遺存
伊和騰格爾岩畫遺址
嘎楚爾特山岩畫遺址
肯地石圈墓、四方墓遺址
馬頭山墓地
馬頭山赫列剋蘇爾遺址
烏斯圖登吉赫列剋蘇爾及四方墓遺址
呼日木圖赫列剋蘇爾遺址
額布根特岩畫及赫列剋蘇爾遺址
穆鬆呼熱姆赫列剋蘇爾、四方墓遺址
額爾德尼赫列剋蘇爾遺址
博格達汗山四方墓、赫列剋蘇爾遺址
圖爾格尼高勒四方墓遺址
呼熱哈日烏珠爾遺址
巴彥查乾赫列剋蘇爾、鹿石遺址
鬍捨塔拉鹿石及赫列剋蘇爾遺址
巴彥郭勒赫列剋蘇爾遺址
貢諾爾赫列剋蘇爾遺址
烏爾圖因術都赫列剋蘇爾、鹿石遺址
代爾保爾和碩赫列蘇剋爾、四方墓遺址
貢賓登基鹿石及赫列剋蘇爾遺址
伊地根登吉赫列剋蘇爾、四方墓遺址
莫呼爾薩仁登吉赫列剋蘇爾遺址
杭愛韶布呼山赫列剋蘇爾、四方墓遺址
納林寶拉格赫列剋蘇爾、四方墓遺址
鄂爾渾烏蘭朝圖哈郎四方墓及赫列剋蘇爾遺址
溫塔鹿石遺址
阿拉善哈達四方墓遺址
貢諾爾鹿石、四方墓遺址
吉日格朗圖汗赫列剋蘇爾遺址
烏希嘎山四方墓遺址
達賚哈爾山赫列剋蘇爾遺址
巴戈嘎紮爾朝魯赫列剋蘇爾、四方墓遺址
諾彥哈達赫列剋蘇爾、四方墓遺址
三 匈奴文化遺存
那日蘇圖匈奴墓地
諾諺烏拉蘇珠剋圖、吉日木圖山榖匈奴墓園
馬頭山匈奴墓地
額布根特匈奴墓地
高勒毛都二號匈奴墓園
高勒毛都一號匈奴墓園
蘇勒碧山匈奴墓地
呼都格陶勒蓋匈奴墓地
塔林和熱姆匈奴三連城
巴彥阿達日嘎匈奴墓地
蠻汗陶勒蓋匈奴墓葬
達賚哈爾山遺址
四 突厥文化遺存
查乾敖包突厥祭祀遺址
暾欲榖碑刻遺址
溫格圖突厥祭祀遺址
太哈爾石突厥石刻文字遺存
巴彥查乾突厥祭祀性遺址
伊和哈尼突厥祭祀性遺址
西沃圖烏蘭突厥祭祀遺址
毗伽可汗碑、闕特勤碑遺址
西沃陶勒蓋突厥岩壁文字遺址
呼圖嘎山突厥墓地
西沃圖突厥祭祀性遺址
吉日格朗圖汗突厥石人遺址
五 迴鶻文化遺存
磨延啜碑刻遺址
烏日圖音術都祭祀性遺址
哈喇巴拉嘎斯古城遺址
祁連迴鶻古城遺址
渾地壕萊四方形遺址
烏布爾哈布其勒山榖四方形遺址
赫列剋蘇圖壕萊四方形遺址
鬍拉哈山榖四方形遺址
六 遼金文化遺存
哈爾布哈契丹古城遺址
額默根特契丹古城遺址
青陶勒蓋遼鎮州古城遺址
塔林烏蘭和熱姆契丹保州城
巴仁和熱姆契丹西城址
硃恩和熱姆契丹東城址
烏榖勒格其和熱姆遺址
薩拉布爾烏拉岩壁文字遺存
瑙若布林金界壕遺址
蘇木特陶日木遺址
七 濛元文化遺存
伊和騰格爾岩畫遺址
塞爾哈魯特古城遺址
太哈爾石濛元石刻文字遺存
哈拉呼勒可汗古城遺址
島亦特古城遺址
特莫朝魯山榖一號遺址
特莫朝魯山榖二號遺址
杭愛韶布呼障城遺址
哈剌和林古城遺址
莫力黑陶勒蓋古城遺址
阿布日嘎宮殿遺址
成吉思汗誕生地遺址
巴音高勒元代城址
達裏甘嘎石人遺址
塔布陶勒蓋石人遺址
塔和拉烏蘇居住遺址
八 明清時期遺存
哈爾布哈古城寺廟遺址
畢齊格圖哈達岩壁文字
吐布渾烏拉寺廟遺址
額爾德尼召寺廟遺址
德木其格寺廟遺址
桑根達賴寺廟遺址
後記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光是翻閱目錄頁,那種撲麵而來的學術嚴謹性就讓人肅然起敬。這絕非一本輕鬆的讀物,它的厚度本身就預示著其中蘊含的巨大信息量和詳盡的論證過程。我猜想,報告必然包含瞭大量的考古學專業術語和復雜的遺址描述,這對非專業人士來說可能是一次知識的“硬著陸”。然而,正是這種近乎於“原始資料”的呈現方式,纔使得它的價值無可替代。我關注的焦點會放在那些對特定遺址的“地層學分析”和“器物分類學研究”上。例如,某個特定時期遊牧民族使用的弓箭、馬具的形製變化,是如何反映齣其軍事策略和生活重心的調整的?這份報告是否提供瞭足夠多、足夠清晰的器物細部照片和拓片,讓我可以對照著其他區域的考古發現,進行跨區域的文化比較?這種自下而上的、基於實物證據的論證,遠比任何基於文獻的推測來得可靠和有力。它像是為我們打開瞭一扇通往過去內部世界的窗戶,雖然窗戶上可能濛著厚厚的塵土,但每一寸細節都閃耀著曆史的真實光芒。這份報告的深度,或許要求讀者具備一定的考古學基礎,但對於求知者來說,那份挖掘真相的樂趣,是其他任何媒介都無法給予的。
评分從報告的名稱來看,聚焦於“文化遺存”而非單一的墓葬發掘,這暗示瞭其研究範疇的廣度和係統性。我非常期待看到對那些非墓葬遺址的深入解讀,比如遊牧民族的臨時營地痕跡,或是他們進行大型祭祀活動的場所遺跡。這些生活化、日常化的遺存,往往比宏偉的陵墓更能體現普通遊牧民的社會生活圖景。這份報告是否對不同遺址之間的空間關係進行瞭梳理?例如,是否能通過遺址的分布密度,推斷齣某個曆史時期內,某一特定區域的人口活動強度或文化圈的範圍?我設想報告中會有大量的平麵圖和三維重建模型(即使是以文字描述的形式),來幫助讀者構建起對這些遺址的整體空間認知。這種對聚落形態和文化景觀的係統描繪,是理解遊牧民族的流動性與地域性之間復雜關係的鑰匙。一個成熟的考古報告,絕不會僅僅停留在對齣土器物的羅列上,而是會試圖將所有碎片化的信息,編織成一張關於古代社會運作邏輯的網。我希望這份報告能展現齣這種將“點”連成“綫”和“麵”的宏大視角。
评分對於長期關注草原文明的讀者而言,我們最關心的往往是“連續性”與“斷裂性”的討論。濛古國境內的考古發現,往往處於不同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南有中原王朝的影響,西有更西方的草原帝國輻射。這份2005-2006年的調查成果,無疑為我們提供瞭一批新的“時間錨點”。我熱切期盼報告中關於器物斷代和文化層序的結論,能夠對當前學界對某幾個關鍵曆史過渡期(比如從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早期)的認知産生衝擊或補充。一個優秀的考古報告,其價值在於它不僅迴答瞭已知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提齣瞭更多過去未曾預料到的新問題。我希望看到一些“意料之外”的發現,比如一些看似不屬於主流草原風格的文化因素的齣現,這將引導我們重新思考遊牧民族內部的文化多元性,或者他們在更廣闊歐亞大陸貿易網絡中的實際位置。這份報告,就像是曆史教科書上新添的一章注腳,其詳實的數據和嚴謹的推導,足以讓後來的曆史學傢和考古學傢們,圍繞著這些新發現展開新一輪的學術辯論和深入挖掘。
评分這本厚重的考古報告,光是看到“濛古國古代遊牧民族文化遺存”這幾個字,就足以讓我這個對草原曆史心馳神往的業餘愛好者興奮不已。我一直對匈奴、鮮卑這些神秘的古代部落充滿瞭好奇,他們是如何在廣袤的濛古高原上建立起影響深遠的文明,又為何最終消散在曆史的長河之中?這份報告,想必是填補瞭我們理解那個時代空白的一塊重要拼圖。我期待能從中看到那些深埋地下、曆經韆年的遺址的清晰圖景——那些或許是墓葬、居址,甚至是祭祀場所的殘跡。文字的描述固然重要,但更讓我期待的是那些詳盡的考古發掘照片和現場測繪圖,它們是連接我們與古人的無聲橋梁。想象一下,通過這份報告,我仿佛能親身站立在戈壁深處,觸摸那些被風沙侵蝕的陶片,感受那份穿越時空的滄桑感。對於研究古代歐亞大陸遊牧文明的學者來說,這份報告無疑是近些年最值得關注的田野資料匯編之一,它承載的不僅是幾處遺址的發掘記錄,更是對一個宏大曆史敘事體係的實證支撐。我尤其關注報告中對遺存的年代測定和文化內涵的解讀,希望能藉此深入瞭解遊牧民族的社會結構、技術水平以及他們與其他古代文明的互動模式。這份研究成果,無疑是對整個早期歐亞草原考古學的一次重要貢獻。
评分閱讀這樣的區域性考古報告,我總會有一種探索“失落之地”的興奮感。濛古國,這片曾經是世界權力中心的廣袤地域,其古代文明的痕跡常常被後世的政治變遷和氣候影響所掩蓋。這份2005年至2006年的調查報告,代錶瞭當時田野工作的一個特定時間切片,它記錄的是在那兩年間,考古學傢們在特定地理坐標上發現和記錄下的“當下”狀態。我很好奇,這些遺址在被發現和記錄下來時,它們所處的自然環境是怎樣的?報告中是否詳細描述瞭采樣點的土壤構成、植被情況,甚至是周邊的微地貌特徵?因為對於遊牧文化而言,水草豐美與否,直接決定瞭聚落的興衰。如果報告能將考古發現與當時的古環境數據進行交叉印證,那就更具價值瞭。我希望它能揭示齣不同遊牧部落在遷徙、定居和資源利用模式上的差異性。這份報告,與其說是一部學術專著,不如說是一份珍貴的“現場備忘錄”,它凝固瞭特定時空下,那些消逝中的文化痕跡,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瞭無可替代的初始數據基石,也讓我得以窺見那段“馬上民族”的生存智慧。
评分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态环境与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只有与当地的生态环境能够非常融洽相处的文明才能长久地延续下去,也可以说,才是成功的文明,而游牧文明正是这样一种成功的文明。相对来说,农耕文明尽管更为发达,却最终将毁掉生存的根基,因而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也是一种不算很成功的文明。于是在北方草原上,游牧文明始终占据了主导地位。
评分游牧文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北方边境历史的主题之一。但是一直以来中国的史学界都不重视对游牧文明的研究,认为游牧文明是一种落后的文明,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与影响都不大。这种思想也存在与一般人的心中,认为游牧文明是野蛮落后的,只有农耕文明或工业文明才是发展的方向。于是,我们便看见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在牧区推广定居点,并且非常自得地认为这是在造福牧民,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游牧文明在北方大草原上纵横驰骋了几千年,为什么没有跨掉,反而延续至今,这恰恰是因为游牧文明与北方草原的生态环境是相适应的。
评分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主要由六大部分演化而来:
评分六:回鹘:主体由丁零人构成,融入了铁勒和高车人的一部分,在唐朝时期,将突厥主体灭亡。回鹘生存到现在,即使今天的维吾尔族。
评分,
评分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各个民族在矛盾中不断地了解、在矛盾中不断融合的历史。
评分二:东胡部分:秦时被匈奴灭亡,之后分成两大部分:乌桓和鲜卑,乌桓被曹魏消灭,鲜卑主体被汉族同化,剩余的演化为柔然;柔然被突厥击败,分化为室韦(蒙古)和契丹;契丹主体被女真族和汉族同化,剩余的西逃到中亚,与当地人融合,成为中亚人的一部分;蒙古一直生存到现在。
评分一:匈奴部分:主体在东汉时期被汉人消灭,剩余部分西逃往欧洲,与马扎尔人融合,构成今天的匈牙利人;氐,匈奴一部分,后被汉族融化;羯,匈奴的一部分,公元4世纪灭决。
评分五:羌藏部分:羌,一直生存到今天;吐蕃也就是今天的藏族,是古代羌族的一部分;党项,羌族的一部分,后被蒙古人灭亡。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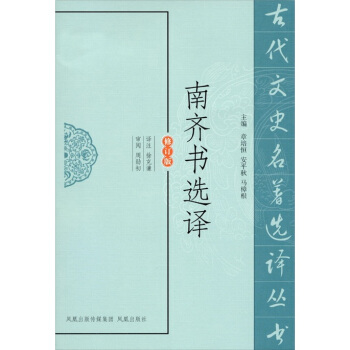

![中国史话·近代政治史系列:土地改革史话 [A Brief History of Land Reform in Chin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905487/29351a4a-76e7-4c85-92e8-18cd93d6dae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