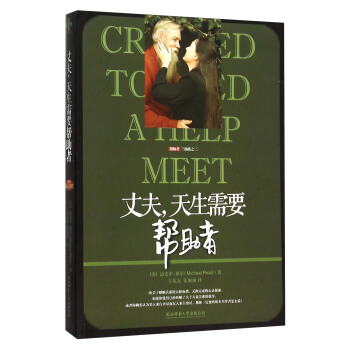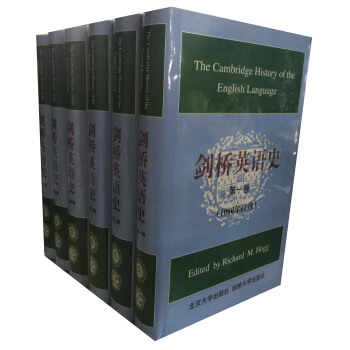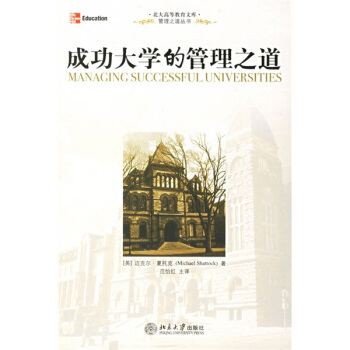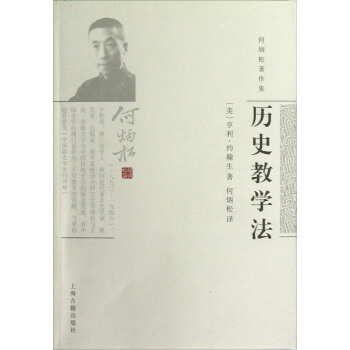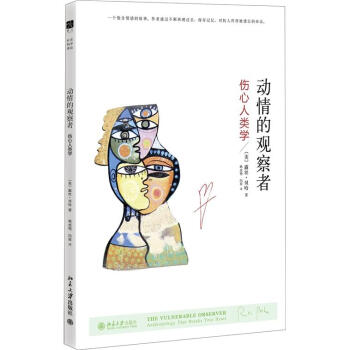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動情的觀察者:傷心人類學》作者是位脆弱易感、同時亦勇氣十足麵對苦痛迴憶的女性主義人類學者。她拒絕遺忘,尤其拒絕遺忘苦痛的情緒,以及透過民族誌學者的心眼所感受到的人世憂傷。因為拒絕遺忘,她在跨越人世間各種有形與無形的界域時,便顯得異常脆弱,極易受傷。這些界域,包括古巴與美國的冷戰(她童年時從古巴移民到美國)、美國與墨西哥的分界、猶太傢庭中低落的女性地位與美國女性主義學者的女權意識、民族誌田野中見證的傳統與現代的消長、生與死、童年與成年、有色人種與白種人、移民勞動階級與學術中産階級等。人類學對於界域、跨界、介於其中的敏感熟悉,甚至可說已臻至學科慣性。加上作者從童年時期起就養成對自身所處位置的敏感與不滿,讓她不斷穿梭其間。盡管依舊焦慮不安,無法固定於邊界的任何一方,但她依舊堅持介於其中,不斷迴首觀望。在作者眼中,動情是學科的宿命,但動情的目的不是為瞭心傷。那些若不動情就無緣跨越的限製。大體上,這是一本特彆適閤對於陰暗、晦澀、自我與他人之苦、模糊的記憶與心境特彆關注且有感受的讀者的書。
內容簡介
在這六篇極具情感的文章中,作者透過揭露自身的生命故事,深刻反思其在西班牙、古巴及美國的田野工作,將洞察力、真誠及憐憫注入其中,把民族誌與迴憶錄巧妙地交織起來,並將反身人類學、女性主義自傳性書寫,以及多元文化與離散論述融會貫穿。作者認為,感性人類學書寫不僅有治療的效果,也可以挑戰、對抗各種僵化與單一的意識型態,激發實踐的動力。總的來說,這不是一本民族誌,而是一本充滿學術反思的類自傳體,具有一定開創意義。
作者簡介
露絲·貝哈(Ruth Behar,1956— ),猶太古巴裔美國作傢,密歇根大學人類學係教授,代錶作除本書外還有《被轉述的女性》(Translated Woman,1993)。
精彩書評
一個飽含情感的故事。作者通過不斷再現過去,保存記憶,對抗人終將被遺忘的命運。——Stanley Trachtenberg,The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作為一個“穿越邊界的女性”……露絲·貝哈的視野中融貫瞭洞察力、真誠和同情。
——Diane Cole,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露絲·貝哈讓我確信,動情的民族誌將會創造齣比過去那種保持距離、不帶情感的學院人類學更有意義的人類學。
——Barbara Fisher,The Boston Globe
露絲·貝哈的隨筆集,評估瞭[自身]情感和經驗對研究及寫作的影響,對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之間關係的影響……很是感人!
——L. Beck,Choice
在這六篇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文章中,露絲·貝哈引人入勝地例示瞭展露“觀察者的自我”的重要性。
——Anne Valentine Martino,The Ann Arbor News
露絲·貝哈的人類學視界之所以如此吸引人,端因她不斷迴望。記憶不會消隱無蹤,雖會褪色變淡,但終會留下印跡。作為一位動情的人類學傢,她使得我們置身的這個世界成為一個更易理解的希望之地。
——Judith Bolton-Fasman,The Jerusalem Report
一直以來,對於田野工作中的,屬於人與人的關係,感到焦慮與睏惑,在腦海裏不斷與許多個不同狀態下的自己辯證打架……學校的老師們隻覺得這是你個人個性問題過度敏感或者情緒,而很少探討這個學科與個人生命史扣連在一起的關係。可以在學術界生存的人,基本上除瞭有一票人能夠把自己耳朵與眼睛緊閉之外,截然二分或簡化自己與對象的關係……或者純粹為瞭完成學術成就,這又是另一種可以活得很好的一票人。我想……一定還存在著這樣一些人,在學科架構下,不斷尋求自己與他者(包括環境、空間、對象、自己的論述)的對話……因此,有傷心有焦慮有睏惑有罪惡有倫理道德有不知為何站在這裏的突兀感……很久以後,離開瞭學術,我纔發現真正的田野纔在眼前展開。
朋友要藉這書給我,是當年曾一起討論這些問題的同學,我想,我應該來買一本的。這麼多年過去,這些命題仍深深吸引著我,不然,我不會選擇這個學科。
——豆瓣網友 vitality (太古植物的孢子)
目錄
第一章 動情的觀察者第二章 死亡與記憶:從聖瑪利亞到邁阿密海灘
第三章 我的墨西哥朋友瑪塔
第四章 石膏裏的女孩
第五章 去往古巴:散居、迴歸與絕望的民族誌書寫
第六章 令人心碎的人類學……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不错的图书不错的图书
评分自近代马林诺夫斯基开始,人类学家一直质疑自身应否保持学术研究的中立位置,观察研究对象的社群,所谓“反身人类学”(reflexive anthropolgy)就是针对这问题,不单提出人类学家应该介入研究对象的情感,研究更应从自身认同出发,这在人类学界掀起很大争议。直至后现代社会,由于女性主义等各种新思潮兴起,好些人类学家对传统学术规范亦大大质疑,像露思·贝哈这样的人类学家,就希望将研究连结到身份认同,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重新审视自身的古巴犹太裔女性身份,用情感充沛的文学语言作人类学书写,对这种学术取向,有人赞许也有人批评,但不能否定其创新的意义。
评分作者发现,虽然文化人类学家纪尔兹反对西方人类学的距离式传统,却仍然声称人类学研究应为公开性活动,而反对内化的自传式人类学文本,于是她提出“易受伤”(vulnerability)这一词汇,并把自己归入新兴的人类学趋势,即以“我”介入“我们”的“自我民族志”代替“他”观察“他们”的传统人类学。对贝哈而言,人类学家之这样做,完全有自我治疗的况味,因为自我介入的生命故事,对人类学家本身也有自疗的作用,因此研究者必须首先返回自身的问题。而“返回自身”的追溯,其实就是人类学家“易受伤”个性的又一明证,不过易感、易受伤并不一定就是脆弱,它可以化作研究者下笔时的情感力量。
评分有点不知所云。女人类学家的作品
评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评分作者发现,虽然文化人类学家纪尔兹反对西方人类学的距离式传统,却仍然声称人类学研究应为公开性活动,而反对内化的自传式人类学文本,于是她提出“易受伤”(vulnerability)这一词汇,并把自己归入新兴的人类学趋势,即以“我”介入“我们”的“自我民族志”代替“他”观察“他们”的传统人类学。对贝哈而言,人类学家之这样做,完全有自我治疗的况味,因为自我介入的生命故事,对人类学家本身也有自疗的作用,因此研究者必须首先返回自身的问题。而“返回自身”的追溯,其实就是人类学家“易受伤”个性的又一明证,不过易感、易受伤并不一定就是脆弱,它可以化作研究者下笔时的情感力量。
评分。。。。。。。。。。。。。。。。
评分不错
评分质量很好~~值得一读~~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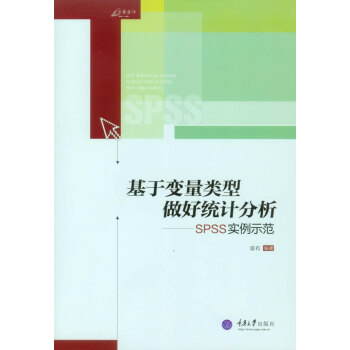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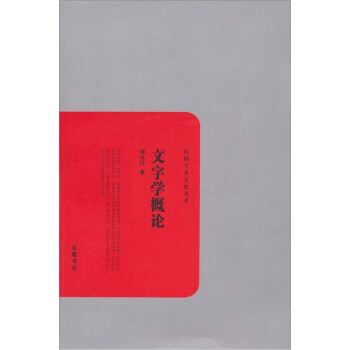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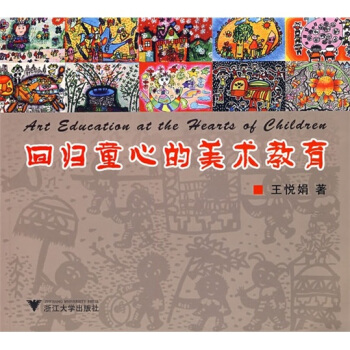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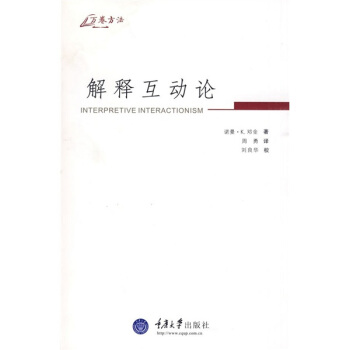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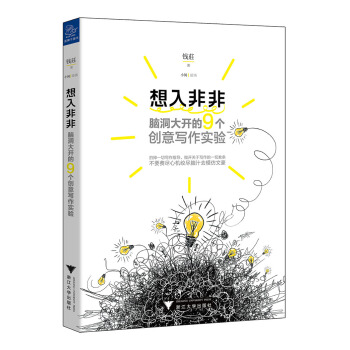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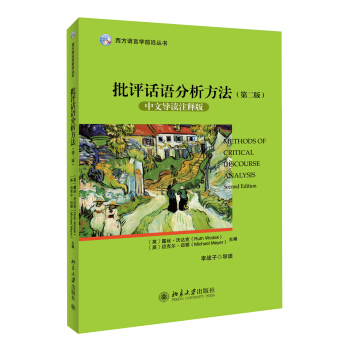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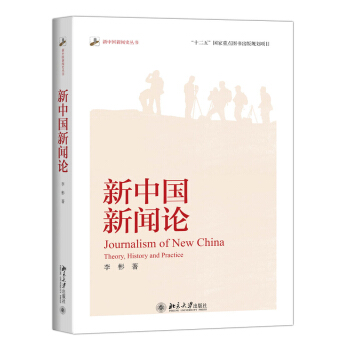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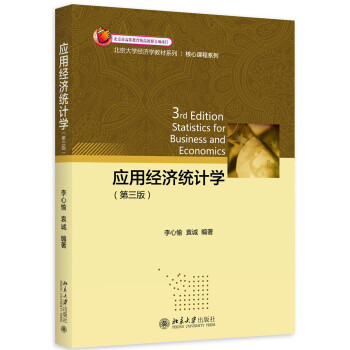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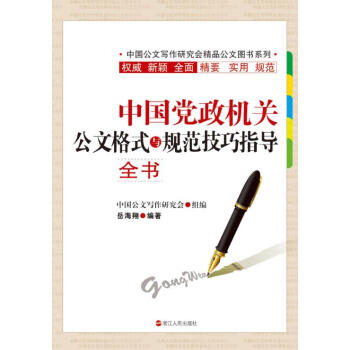
![德国教育学概观:从启蒙运动到当代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German Pedagogy Since Enlightment]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844998/d309d772-e334-4a22-aa9a-473796d2630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