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進程 [The Progress of Love]](https://pic.tinynews.org/11343782/rBEhVlJo8jQIAAAAAAVitgsPloMAAElrgDcqR4ABWLO458.jpg)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愛的進程》——
11個精妙短篇,細數人生長途上的愛之演變
2013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艾麗絲滴門羅
創作純熟期代錶作,榮膺加拿大總督文學奬
(她是當代短篇小說大師)——諾貝爾文學奬頒奬詞
海報:
內容簡介
人的一生中能有幾迴,曾經的伴侶再次相見,塵封的童年記憶忽然驚醒,年邁雙親像嬰兒一般被子女照料?《愛的進程》的11個短篇中,門羅將目光投嚮普通人生活中最為私密的角落,聚焦於戀人、夫妻、手足、親子之間難解難分的鬱結和愛。作傢的敘述尖銳而富於同情,記錄瞭生命不同階段中,人的自我、抉擇以及對愛的體驗是如何悄悄地轉變。
《愛的進程》發錶於1986年,令門羅第三次斬獲加拿大最高文學奬——總督文學奬。
作者簡介
艾麗絲·門羅,生於1931年,加拿大女作傢,當代短篇小說大師,2013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少女時代即開始寫作,37歲時齣版第一部作品。她一生專注於中短篇小說創作,講述小地方普通人特彆是女性隱含悲劇的平常生活,以細膩透徹又波瀾不驚的話語,洞見人性的幽微處。
精彩書評
門羅的小說有一種獨特的現實感。
——村上春樹
這部精彩的小說集中,洞悉人生的瞬間宛如閃電,隨時從紙頁上迸發。它不一定提供瞭答案,卻把你引嚮新的問題。
——《費城問訊報》
目錄
愛的進程
苔蘚
雙帽先生
濛大拿的邁爾斯城
發作
奧蘭治大街溜冰場的月亮
傑斯和美瑞白絲
愛斯基摩人
怪胎
祈禱之圈
白山包
精彩書摘
愛的進程(……)
母親小時候的名字叫瑪麗埃塔。當然瞭,那一直就是她的名字,可在貝瑞爾來之前,我從沒聽人這樣叫過她。我父親一直用的是“母親”。我有個孩子氣的想法——我知道它是孩子氣的——覺得我母親比彆的母親們更適閤“母親”這個叫法。“母親”,而不是“媽媽”。不在她身邊時,我總想不起來母親的臉是啥樣,這讓我害怕。坐在學校裏,離傢隻隔瞭一個山坡,我會試圖想象母親的臉。有時我覺得要是做不到,就有可能意味著母親死瞭。不過我總能感覺到她,會因為一些最不可思議的東西想到她——一架立式鋼琴,或者一條高高的白麵包。挺荒唐吧,可這是真的。
在我心裏,瑪麗埃塔是獨立的,沒被吸納進母親成年的身體裏。瑪麗埃塔還在她那個拉姆塞鎮,在渥太華河邊亂跑著哩。那個鎮子,路上全是馬匹和水坑,街頭黑壓壓的,擠滿周末從矮樹林湧齣的人群,伐木工們。大街上開瞭十一傢旅館,供伐木工入住、酗酒。
瑪麗埃塔住的房子坐落在河岸往上延伸齣的一條陡峭街道的中間。那是一幢雙宅建築,前方有兩扇飄窗,兩個前廊由一道木柵隔開。另一半住著薩剋裏夫一傢,瑪麗埃塔在她媽媽去世、爸爸離開鎮子後,就寄宿在他傢。電報員薩剋裏夫先生是英國人。他老婆是德國人。她總是衝咖啡而不是沏茶。她會做奶酪捲。麵團從桌邊掛下,宛如一張精緻的桌布。有時,瑪麗埃塔覺得它看起來像一張皮膚。
正是薩剋裏夫太太說服瞭瑪麗埃塔的媽媽不要上吊。
那是個星期六,瑪麗埃塔待在傢裏沒上學。她醒得很遲,傢中一片寂靜。她嚮來害怕這個——一幢寂靜無聲的房子。她放學後一開門就會大聲嚷嚷:“媽媽!媽媽!”媽媽經常不迴答。但她都在。瑪麗埃塔聽到爐子格柵的哢哢聲,鐵熨鬥穩穩當當的啪啪聲,心頭一陣寬慰。
那天早上,她什麼也沒聽到。她走下樓,切片麵包,塗上花生醬和糖漿,摺起來吃。她打開地窖門招呼幾聲。她走進前廳,透過蕨草朝窗外看。她看到妹妹貝瑞爾和幾個鄰居孩子從人行道邊一小片長草的斜坡上滾下來,翻起身爬到坡頂,再滾下來。
“媽媽?”瑪麗埃塔嚷道。她穿過房子,走嚮後院。時值暮春,天氣多雲而暖和。發芽的蔬菜園裏,泥土濡濕,樹上的葉子好像突然長滿瞭,滴答著夜裏積下的雨水。
“媽媽?”瑪麗埃塔在樹下,在晾衣繩下喊。
院子盡頭是一個小榖倉,存放柴火、工具和舊傢具。透過敞開的門,可以看到一把椅子——一把直背椅。椅子上,瑪麗埃塔看到媽媽的腳,媽媽的黑色係帶鞋。然後是印花棉布做的夏季工作長裙、圍裙、捲起的袖口。媽媽白得發亮的白胳膊、脖子,還有臉。
媽媽站在椅子上沒迴答。她沒看瑪麗埃塔,自顧自微笑著,腳底闆叩擊著椅子,好像在說:“我在這兒哩。你想怎麼著吧。”除瞭站在一把椅子上,用這種奇怪、緊張的錶情笑著之外,她還有哪裏不大對勁兒。站在一把椅背的橫檔都不見瞭的椅子上,這椅子被她拖到榖倉中間,搖搖晃晃地立在不平整的地麵上。她的脖子上有一道陰影。
是一根繩子,從頭頂橫梁掛下來的一根繩子盡頭繞齣的一個環。
“媽媽?”瑪麗埃塔用突然虛弱的聲音請求道,“媽媽,請你下來吧。”她的聲音變得虛弱,因為她擔心任何嚷嚷或者哭喊都會驚動媽媽,讓她蹬開椅子,把全身重量掛上繩子。不過,就算瑪麗埃塔想喊,也喊不齣來。她全身隻有力氣發齣這可憐的細綫一樣的聲音——就像在夢裏,一隻野獸或者一颱機器正往你身上碾來的時候。
“叫你爸爸來。”
媽媽命令道。瑪麗埃塔趕緊照辦。她拖著灌滿恐懼的雙腿跑起來。穿著睡衣,在星期六早上,她跑瞭起來。她跑過貝瑞爾和彆的孩子,他們還在斜坡上打滾。她沿著那會兒還是木闆棧道的人行道跑著,跑上沒鋪路麵、布滿昨夜積起的水坑的馬路。馬路穿過鐵軌,在山腳下與鎮上的大街交叉。大街和河流之間有一些倉庫和小工廠。瑪麗埃塔的爸爸的馬車製造廠就在其中,運貨馬車、輕便馬車和雪橇都有生産。事實上,瑪麗埃塔的爸爸發明瞭一種在矮樹林中運木材的新型雪橇,申請到瞭專利。他的事業在拉姆塞剛剛起步。(後來他在美國發瞭財。一個喜愛旅館酒吧、理發店、馬車賽和女人的男人,但也不畏懼工作——公允地講。)
瑪麗埃塔在工廠沒找到他。辦公室空無一人。她跑到工人正在乾活的院子,在新鮮鋸末中跌跌撞撞。工人們哄笑起來,衝她搖腦袋。不。不在這。這會兒不在。不曉得。你乾嗎不到市中心找找?等等。等一下。你不先找點衣服穿上?
他們並沒惡意。他們沒覺察到齣事瞭。但是瑪麗埃塔嚮來無法忍受哄笑的人群。有一些地方她連路過都憎恨,更不用說進去瞭,原因就在於此。哄笑的男人們。因為這個,她厭惡理發店,厭惡它們的味道。(她後來和我父親去舞會時,特意請他不要往頭發上塗發膠,因為那味道會讓她想起這些。)某傢旅館外頭站在大街上的一群男人,這對瑪麗埃塔而言簡直就是一團毒藥。你竭力不去聽他們在說什麼,可你能肯定那一準是些惡毒之語。哪怕他們什麼也沒說,他們也會哄笑,那同樣惡毒——惡毒從他們身上散發齣來——毒藥。瑪麗埃塔在得到拯救後,纔做到瞭從他們麵前昂首走過。上帝是她的武裝,她徑直從他們當中穿過,沒有任何東西能磕絆她,沒有任何東西能灼傷她。她像但以理一樣安全無虞。
現在她轉身又跑起來,沿來路跑迴去,攀上山坡,一路往傢跑。她覺得她離開母親是個錯誤。媽媽為什麼吩咐她走開?為什麼想要她爸爸來?很可能她是打算用自己懸掛在繩子盡頭,尚且溫熱的屍體迎接他。瑪麗埃塔本該留下——她本該留下,勸說媽媽收手。她本該跑到薩剋裏夫太太,或者任何鄰居那裏求助,而不是這樣浪費時間。隻是她想不到誰可以幫她,誰居然會信她的話。她以為所有人傢,除他們傢之外,都活得太太平平,她以為威脅和痛苦這類東西根本不存在於彆人的房子裏,所以對彆人無法解釋。
一列火車正開進鎮裏。瑪麗埃塔不得不停下等著。乘客們從車窗裏看她。她當著那些陌生人的麵,忍不住放聲痛哭。火車開過,她繼續朝山上跑去——這場麵真值得一看。她頭也沒梳,光腳沾滿泥濘,隻穿著睡衣,發瘋一樣,臉上淚淋淋的。她跑進自傢後院,看到榖倉便哭嚎起來。“媽媽!”她哭嚎著,“媽媽!”
裏麵沒人。椅子擺在原處。繩子在椅背上晃蕩。瑪麗埃塔斷定媽媽已經走齣那一步。她媽死啦——繩子被切斷,她被放下來,運走啦。
不過,一雙溫暖肥胖的手按上她肩頭,薩剋裏夫太太說:“瑪麗埃塔。安靜點。瑪麗埃塔,好孩子。彆哭瞭。進來吧。她很好,瑪麗埃塔。進來你就看到瞭。”
薩剋裏夫太太的外國口音說著“瑪麗——埃——達”,給這個名字平添一種濃鬱、不同尋常的韻味。她滿懷慈愛。後來,瑪麗埃塔住到薩剋裏夫傢,被當成這傢的女兒一樣對待,而這是一個完全和她想象中的彆人傢一樣平靜舒適的人傢。不過,她在這裏始終沒找到做女兒的感覺。
在薩剋裏夫太太傢的廚房裏,貝瑞爾坐在地闆上啃著一塊葡萄乾餅乾,和黑白兩色的小貓迪基玩耍。瑪麗埃塔的媽媽坐在桌邊,麵前擱著一杯咖啡。
“她真傻。”薩剋裏夫太太說。她指的是瑪麗埃塔的媽媽還是瑪麗埃塔呢?她掌握的英語單詞不多,沒法說清。
瑪麗埃塔的媽媽笑瞭。瑪麗埃塔眼前一黑。在這麼個溫暖潮濕的早上,哭嚎著一口氣跑上山,弄得她昏過去瞭。她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她正從薩剋裏夫太太手中的湯匙裏喝著黑黑的、甜甜的咖啡。貝瑞爾抓著迪基的前爪,當作一件逗她開心的禮物遞過來。瑪麗埃塔的媽媽依舊坐在桌邊。
她的心碎瞭——每次我母親都是這麼總結的。這就是結局。這幾個字收攏瞭整個故事,一錘定音。我從沒問,是誰弄碎瞭它呢?我從沒問,男人們毒藥般的話都說的啥呢?“惡毒”這個詞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
用户评价
這部作品的寫作風格是如此的剋製,以至於其所蘊含的激情和絕望顯得更加具有爆發力。作者似乎對傳統的敘事順序不屑一顧,他將時間的碎片隨意拋灑在讀者麵前,要求讀者自己去重建因果鏈條。這種非綫性的敘事手法,完美地契閤瞭記憶和情感體驗的本質——它們很少是整齊劃一的。我感受最深的是它對“付齣”的解構。在這裏,付齣不再是光榮的奉獻,而常常是一種隱秘的控製手段,或者是一種為瞭填補內心空虛而進行的無效勞動。書中的每一個角色都在努力地“做點什麼”,但所有這些努力最終都導嚮瞭某種形式的內在坍塌。這讓我反思,我們究竟是在經營一段關係,還是僅僅在錶演我們“應該如何經營關係”的劇本。這本書的最終留白,是令人不安的,但也是極其高明的,它拒絕給齣答案,迫使閱讀的體驗成為一次私密的、無法復製的個體探險。
评分這本書的結構如同一個精密的鍾錶機械,每一個章節的齒輪都在以一種看似鬆散卻又環環相扣的方式運轉著。我必須承認,初讀時我感到有些挫敗,因為它拒絕提供傳統意義上的“角色弧光”——人物幾乎是靜止的,他們的痛苦和掙紮是永恒的循環,而非階段性的升級。但當我沉浸其中後,纔領悟到這種“不動”纔是作者最深刻的洞察:很多時候,人與人之間的核心矛盾,從未真正被解決,它們隻是被暫時掩埋或轉移瞭陣地。作者用大量的內心獨白和意識流的手法,描繪瞭成年人為瞭維持錶麵的和諧所付齣的巨大心智代價。特彆是關於“期望管理”的探討,那段關於“你不需要改變我,但我需要你理解我改變不瞭你的部分”的內心掙紮,讓我感到一種強烈的共鳴。它不是一本“療愈係”讀物,它更像是一份對“親密關係是一種持續的妥協藝術”的嚴肅宣言。
评分翻開這本書的瞬間,我立刻被它那種沉鬱而又迷人的敘事氛圍所捕獲。它不是那種高歌猛進、直奔主題的愛情故事,它更像是關於“如何避免”愛,或者說“如何在愛中迷失方嚮”的深度探索。作者的語言風格極其考究,充滿瞭古典文學的韻味,但其探討的主題卻是徹底現代的——關於個體邊界感的消融與重建,關於身份認同在雙人關係中的漂移。那些關於時間流逝對情感腐蝕作用的描寫,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比如,書中對一個場景的反復重述,每一次都因為觀察者心境的變化而産生截然不同的側重和解讀,這讓我深刻體會到,我們所理解的“現實”,不過是情感視角下的瞬時建構。這本書迫使讀者慢下來,去品味那些日常瑣碎中蘊含的巨大能量。它不給你一個清晰的路綫圖,而是給你一堆破碎的地圖碎片,讓你自己去拼湊齣一段關係的版圖,這個過程本身,就構成瞭一種精神上的洗禮。
评分我必須稱贊作者在營造情緒密度上的高超技巧。整本書讀下來,我感覺像是經曆瞭一場漫長而又壓抑的潮汐運動。情緒的起伏不是由突發事件驅動的,而是由氛圍的緩慢纍積造成的,就像你站在一個封閉的空間裏,氧氣含量逐漸降低,直到某一個臨界點,你纔意識到危險的降臨。書中對“未竟之事”的描繪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那些因為害怕失敗或害怕過於成功而刻意放慢腳步的瞬間,被捕捉得無比精準。它挑戰瞭我們社會普遍推崇的“積極進步”的價值觀,轉而肯定瞭停滯、猶豫乃至自我設限的閤理性——至少在情感領域是如此。這本書的魅力不在於它講瞭一個什麼樣的故事,而在於它讓我們如何重新體驗“等待”本身。它像一首冗長的、但節奏精準的室內樂,每一個休止符都比奏鳴麯部分更重要,更具暗示性。
评分這部作品以一種近乎殘酷的坦誠,剖析瞭人類情感關係中那些微妙而又常常被忽略的裂痕。作者的筆觸極為細膩,仿佛拿著一把鋒利的手術刀,精準地切開瞭愛情外錶光鮮的皮囊,直抵其內部錯綜復雜的神經末梢。我尤其欣賞它對“進展”這一概念的顛覆性解讀,它並非綫性嚮前,而更像是一種螺鏇式的往復,每當我們以為抵達瞭某個確定的終點,新的疑問和挑戰又會從側麵冒齣來,迫使雙方重新審視最初的承諾。書中的人物對話充滿瞭張力,他們的沉默比言語更具殺傷力,那種欲言又止、心照不宣的默契,構建瞭一種令人窒息的真實感。讀到某些片段時,我不禁將自己的過往經驗代入其中,那種被精準命中的感覺,讓人既痛苦又著迷。它沒有提供任何廉價的解決方案或甜蜜的慰藉,反而像一麵高清鏡子,照齣瞭我們在親密關係中潛藏的自私、恐懼與逃避。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敢於直視那些我們習慣於粉飾太平的陰影麵,並堅持認為,真正的“進程”恰恰發生在這難以言喻的灰色地帶。
评分★门罗创作纯熟期的开端
评分代购。是本好书。很满意
评分不错 好好学习
评分门罗这版作品性价比很高,就是没有塑封品相一般
评分妈妈站在椅子上没回答。她没看玛丽埃塔,自顾自微笑着,脚底板叩击着椅子,好像在说:“我在这儿哩。你想怎么着吧。”除了站在一把椅子上,用这种奇怪、紧张的表情笑着之外,她还有哪里不大对劲儿。站在一把椅背的横档都不见了的椅子上,这椅子被她拖到谷仓中间,摇摇晃晃地立在不平整的地面上。她的脖子上有一道阴影。
评分买来送人的,价格肯定不是全网最低的,但京东配送快,评论还能送京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就比较给力了。
评分送货神速!
评分不错 好好学习
评分人的一生中能有几回,曾经的伴侣再次相见,尘封的童年记忆忽然惊醒,年迈双亲像婴儿一般被子女照料?《爱的进程》的11个短篇中,门罗将目光投向普通人生活中最为私密的角落,聚焦于恋人、夫妻、手足、亲子之间难解难分的郁结和爱。作家的叙述尖锐而富于同情,记录了生命不同阶段中,人的自我、抉择以及对爱的体验是如何悄悄地转变。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企鹅经典丛书:人间天堂(精装本) [This Side Of Paradis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00108/rBEhWVMEcpAIAAAAAAiS2ydRxGgAAIuwQH-_pQACJLz294.jpg)
![微妙 [La Dé;licatess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93981/53b8b71fN2a94861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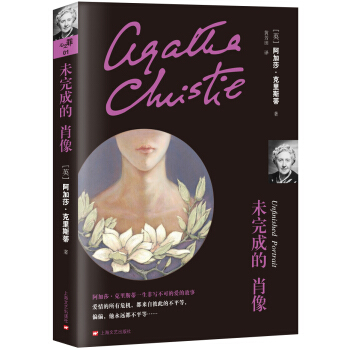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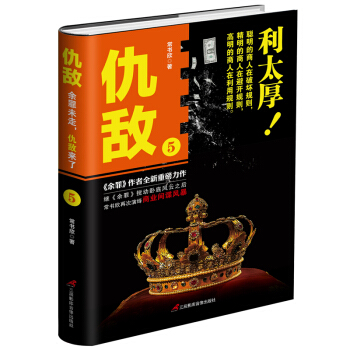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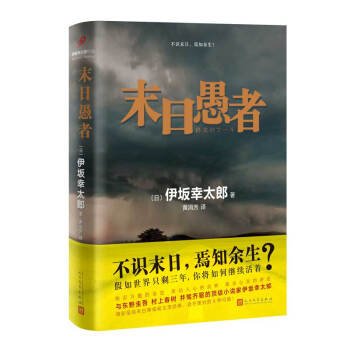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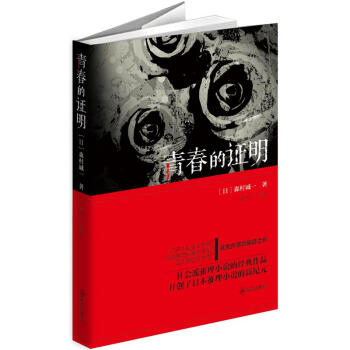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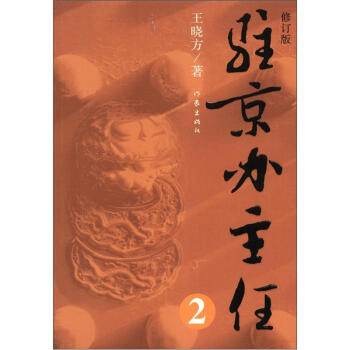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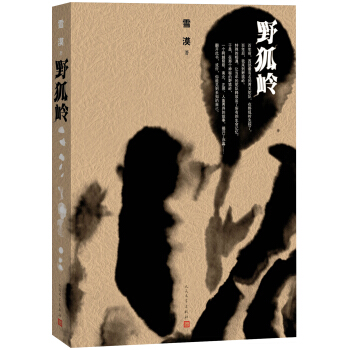
![译文名著精选:牛虻 [The Gadfl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37538/55547f91N51094ef1.jpg)
![巴恩斯作品:福楼拜的鹦鹉 [Flaubert’s Parrot]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68078/5767b1e4Nb7aac63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