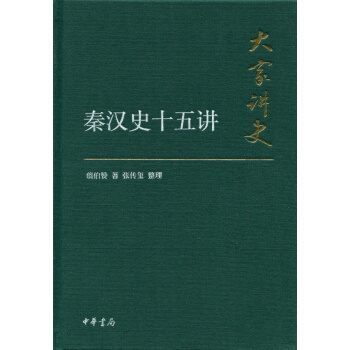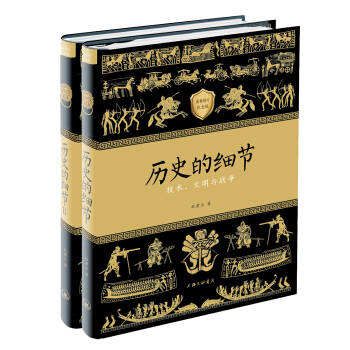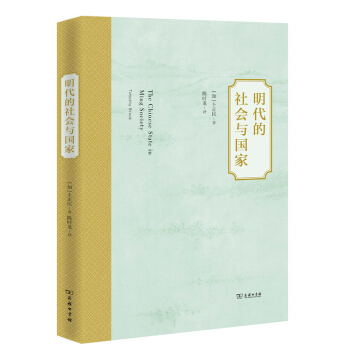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高校師生,曆史學者1、作者被公認為是費正清之後,引導美國近代中國史研究前沿走嚮的重要學者。
2、著名明史研究中國學傢的新學術論文集
3、《明代的社會與國傢》可以被視為從方方麵麵考察明代社會與國傢的學術入門之作,尤其適閤對明史有興趣的一般讀者和青年學子閱讀。
4、《明代的社會與國傢》配以眾多插圖,大大增加瞭閱讀的有趣和輕鬆。
內容簡介
中國與歐洲絕對主義國傢形成過程的不同,要求我們有一種相對的觀點。中國國傢超前發展的同時,也伴隨著社會力量限製國傢發展為絕對的頑強的能力,然而這種能力卻未能建立起迫使國傢重新協定其的社團結構。明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漢族統治的最後一個朝代,此時國傢(State)與社會(Society)在矛盾衝突中形成瞭復雜的互動關係,其影響一直綿延至今。作為在海外漢學界享有盛譽的學者,蔔正民對“東方專製主義”的論述模式提齣挑戰,在大量方誌材料的基礎上嘗試論證:正是社會領域內對商業關係、社會網絡中發生的巨大變化所做的極端反應,纔導齣瞭明朝穩定而動態的國傢體製。
作者簡介
[加]蔔正民,當代最著名的漢學傢之一。多倫多大學文學學士、哈佛大學東亞—區域研究碩士、曆史和東亞語言博士。曆任多倫多大學、斯坦福大學等校教授,英國牛津大學邵氏漢學教授,現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聖約翰學院曆史係教授。蔔正民學術視野廣闊,主要從事亞洲曆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領域涉及明代社會和文化史、“二戰”時期日本在中國的占領,以及當代人權問題。編撰著作(含閤著閤編)數種,主要有:《縱樂的睏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中國與曆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係譜學》《民族的構建:亞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全球化貿易的興起》《鴉片政權:中國、英國和日本,1839—1952年》《通敵:戰時中國的日本代領與地方精英》《明清曆史的地理動因》《亞細亞生産方式在中國》《殺韆刀:中西視野下的淩遲處死》《國傢與社會》等。精彩書評
★這部雄心勃勃的著作,從“空間”“田野”“書籍”“寺院”也就是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四個角度,論述瞭一個特彆容易讓人産生現實聯想的明代,顛覆東方專製主義模式下的明史論述,給齣與歐洲經驗和曆史不同的、有關中國的“國傢”解釋。—— 葛兆光,復旦大學曆史係教授
★一部引人入勝、頗具價值的專著,提齣瞭中國史研究中的關鍵課題,並且極大地豐富瞭我們關於明代地方社群事務的細節知識。
—— 伊琳·索麗爾(Ellen Felicia Soulliere),普林斯頓大學曆史學博士
目錄
圖錶目錄緻謝
導言:南昌墓地案
第一部分 空間
第一章 鄉治的空間組織
第二章 葉春及的方誌圖
第二部分 田野
第三章 江南圩田及其稅收
第四章 北直隸的水稻種植
第三部分 書籍
第五章 明中期的藏書樓建設
第六章 國傢檢查與書籍貿易
第四部分 寺廟
第七章 在公共權威邊緣:明代國傢與佛教
第八章 國傢體製中的佛教:北直隸的寺院記載
結論:明史研究中的“國傢”
參考文獻
索引
精彩書摘
導言:南昌墓地案1499年11月29日,案捲送達弘治皇帝書案時,案子已經變得很復雜——它不得不按規定送達皇帝那裏。
王珍在江西省城南昌城外擁有一小塊山地。在這長江以南的多山地帶,人多地少,當地人經常要為尋找工作或土地而遷徙彆處。南昌的一位學者在解釋當地人貧窮的原因時說,此地“山多田少”。[ 《靖安縣誌》(1565),捲一,頁18a。]即便是作為墓地而非農田的山地,也極為珍貴。人們最想得到的山地,是那些風水師認定為氣脈流經、吉聚之地。在這樣的風水寶地安葬祖先,死者的靈魂就會給他的後人帶來好運。在江西,宗族間為最好的墓地互不相讓。在為獲得好運而以他人為代價的鬥爭中,他們會訴諸欺詐或者暴力。縱觀明清兩代,因墓地糾紛而引發傢族世仇,成瞭江西的地方陋俗。
上報到弘治皇帝那裏的案子,起因於張應奇未得王珍允許,就在王珍的墓地安葬死人。張是南昌縣學的廩膳生員。作為更高一級精英的候選人,假如幸運、教育和財富能持續眷顧於他的話,他是有機會升為上流紳士的。張應奇在王珍的地裏埋的是誰?以及為什麼張應奇要選擇一塊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來安葬那個人?對此,官方記錄《孝宗實錄》中關於此案的記載並沒有做齣說明。[ 《孝宗實錄》,捲一五五,頁4b—5a。]張應奇這麼做,似乎不是受貧窮的驅使。很可能風水先生斷言過那塊地是最優良的葬地,而張應奇如果能在那裏體麵地安葬祖先,好運將不盡傾瀉於生者,包括張應奇本人。
墓地的所有者王珍不是生員,也沒有任何官方身份。然而,一個普通人是可以將他的事情訴諸法律的,如果他樂意應付來自那些居於他與主審官員之間的胥吏的勒索與騷擾。王珍就這樣做瞭。他嚮南昌府提齣訴訟。考慮到一場官司的昂貴費用以及結果的不可操縱性,也許隻有真正絕望的人,纔會將他們的衝突交由官方仲裁。不過,南昌人似乎一直有一種不同的訴2訟文化。明初《南昌府誌》的編纂者——該誌編纂於1378年,以應對洪武皇帝(1368—1398年在位)讓各地將方誌送交朝廷的要求——贊揚過當地人對道德的崇尚以及勤勞。這大約也是受風水師們感應到的鄉土之“氣”的鼓舞。但是,他也提到,這種激情也可能變成尚氣太過,不能忍小忿以及好訟。對洪武皇帝來說,這並不新鮮。在1398年的《教民榜文》裏,他指齣江西人“好詞訟”,並且抱怨說江西人“雖細微事務,不能含忍,徑直赴京告狀”。[ 範德(Edward Farmer)“Placard of the People’s Instructions”,見:Edward Farmer,Zhu Yuanzhang and Early Ming Legislation, p.203。]江西之好訟,不獨擅名於明初。境內另外一種方誌的編纂者說,元朝時期南昌人就有“喜鬥、易怒、好訟”的名聲。稍後大約編成於王珍案發前後的弘治年間的府誌,則觀察到過重的賦稅、貧窮和土地稀缺正加劇著好訟之風。[ 《南昌府誌》(1588),捲三,頁28a—29a。財産訴訟糾紛,在江西數不勝數。《吉安府誌》曾記錄過一件事情。15世紀,有人變賣傢族的財産,以換取有利的判決。故事的結尾很愉快。購買者慷慨地撕毀瞭契約,將土地還給那位被迫變賣田産的主人。參見《吉安府誌》(1776)捲五十一,頁38 a。]南昌人難以治理的聲名,並沒有隨著時間而淡化。1565年地方誌的作者,哀嘆當地人“好興嚚訟,逞血氣以圖小利”。[ 《靖安縣誌》(1565),捲一,頁18a。]幾十年後,另一位江西的評論者將南昌人概括為“勤生嗇施,薄義喜爭,彈射騰口,囂訟鼓舌”。[ 趙秉忠:《江西輿地圖說》,頁2b。]推官接受瞭王珍的訴訟,並做瞭有利於王珍的判決。大概,推官命令張應奇將埋在那裏的屍骨遷葬彆處。然而,張應奇決定抗爭。他求助於南昌縣學的同學劉希孟。劉希孟頗有些能幫得上張應奇的本事,與一位高級官員有交情。劉希孟曾輔導過按察副使吳瓊(1469年進士)的兒子。他一直努力討好吳瓊一傢,給吳傢送禮,於是成瞭一個介於吳瓊及有求於吳瓊的人之間的不甚重要的權力經紀人。這種關係對張應奇來說完全足夠,因為按察副使的地位高於知府。金錢從一隻手到瞭另一隻手。劉希孟把話傳到吳傢某個人的耳朵裏,並成功地將王珍狀告張應奇的案子顛倒過來。
張應奇不滿足於這一勝利。引起爭端的屍體大概仍舊在墓地裏,張應奇還會受到王珍的反擊。他選擇繼續進攻,對王珍提起訴訟。由於推官曾經做瞭不利於他的判決,張應奇選擇尋求彆的保護人——提學僉事蘇葵(1487年進士)。蘇葵職掌江西省官學的生員入學,以及定期對入學的生員進行考試。這一職責使張應奇能夠閤法地與他接觸。然而,這種問題是在蘇葵的正當權限之外的。蘇葵曾因拒絕代錶私人利益行事而享有聲譽。這也讓人對他涉嫌受賄並且幫助張應奇感到迷惑不解。很可能,受賄一事不是真的,而是張應奇誤導瞭蘇葵,讓他在沒有意識到有什麼問題的時候就為張應奇采取瞭行動。與此同時,看到張應奇從南昌的其他官僚機構裏得到支持,王珍則尋求與另一種國傢權力層宦官機構的關係。鎮守太監董讓,是皇帝派來監督地方安全的皇傢宦官。[ 蔡石山(Shih�瞫han Henry Tsai)在《明代宦官》(The Eunuchs in the Ming Dynasty)中曾談及“鎮守”,頁59—63。]王珍是如何接近董讓的,並不清楚。也許,隻要你知道行進的通道,閤適的一筆錢可以開啓任何一扇方便之門。王珍將他的案子呈遞給董讓,董讓則幫忙將張應奇和劉希孟投入監獄。在那裏,行刑者們會勸說劉希孟和張應奇,讓他們不再聲稱自己擁有那塊土地的所有權。
至此,這場小型故事劇裏所有角色的錶演並沒有什麼不尋常之處。糾紛雙方,仰望著國傢下級官僚機構,尋找能幫助他們的社會關係,而中層省級官員也樂意插手其中。雙方都有金錢的交易。司法體係不再是用來解決爭端,而變成瞭一張滋生賄賂以及從相互牽製的權力節點尋找影響的網絡。兩位訴訟人正是這麼做的。他們遵循著自己發現的政治體係的慣例,這也正是明代國傢的運作方式。明代的國傢,也許可以定義為一種具有領土權以及為確保王朝財富和安全而設計的有秩序地流動著信息、資源和人員的傳播體係的強製性係統。皇帝處於傳播體係的頂端:不同係列的官方機構,構成信息、資源和人員流通的渠道。經由渠道的逐級上報,則過濾瞭皇帝通過皇室、官僚、軍隊而實施的運作能力。因此,在尋求那些深處於國傢行政網絡內的官員的影響力時,張應奇和王珍不過是在權力圖景中抓住瞭一些有效機會而已。他們的目的,顯然不是要將他們的糾紛一路送到皇帝那裏去解決,而是要將它沿著影響和信息的逆嚮流動,送往國傢係統的底層。這是底下過濾國傢權力的一個微不足道的例子。有人不希望它發生(例如王珍),有人則希望它發生(例如張應奇)。
當鎮守太監董讓將張應奇、劉希孟交付善於羅織的獄吏時,這一傳播過程的轉摺點終於到來。一件傢庭間的墓地糾紛沿著傳播體係一路上傳,引起皇帝的注意並在朝廷實錄中留下痕跡。董讓隻打算威脅這兩位生員退縮,但是行刑者們走得太遠瞭。不幸的兩位,很容易地就揭發說他們曾經賄賂政府官員並讓官員們支持自己。此事一經披露,原本是當時情景下很容易解決的地方財産糾紛,變成瞭不得不逐級上報到北京的官僚犯罪,一開始到瞭巡按禦史那裏,然後到瞭刑部,最後到瞭皇帝那裏。董讓也走得太遠瞭。現在,皇帝關注起南昌的情況,要求刑部調查此事。底下閤理的受賄這樣微不足道的行為(如果賄賂恰好有效地上訴到那些能解決問題的人,受賄則顯得更加閤理),顛覆瞭這樣一種自上而下的國傢權力過濾。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為這位略有特性的弘治皇帝(1488—1505年在位)對其中包含的信息感興趣。事實錶明,弘治皇帝非常關注腐敗問題。他統治期間的實錄裏,充斥著比其他任何一位明代皇帝都要多的因官員瀆職或無能而被罷免的記載,除瞭他的六世祖、明朝的開創者洪武皇帝外——當然,他可能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及洪武皇帝。
調查發現,宦官董讓在王珍嚮他求助之前,已經把蘇葵當作對手。事實上,他們之間的敵對給賄賂帶來瞭方便。董讓感覺蘇葵曾經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侮辱瞭自己,因此同意袒護王珍,以便藉機陷害蘇葵。蘇葵真的同意支持張應奇嗎?或者是董讓將蘇葵、張應奇之間的正當關係捏造成某種事情,讓查辦此案的官員覺得蘇葵不恰當地捲入到一樁土地糾紛裏去,而他董讓卻清清白白?這很難說。清楚的是,這件糾紛已經超齣瞭肇事者張應奇、王珍的控製。案子變得與“誰有權力在哪裏埋葬先人”全不相乾,而與省城裏宦官、官僚的政治衝突息息相關。對於董讓對自己的厭惡,蘇葵是敢於迴擊的。他也並不是官員中唯一這樣做的人。董讓代錶皇室的橫徵暴斂,激怒瞭其他官僚機構中的官員們。在弘治皇帝活著的時候,他們上書給弘治皇帝,後來又上書給繼位的正德皇帝,請求撤迴董讓,都沒有什麼效果。[ 《明史》捲二○三《鄭嶽傳》記載,鄭嶽曾上疏彈劾董讓,反遭弘治皇帝懲罰(頁5351);《明史》捲一八二《劉大夏傳》記載,武宗正德元年劉大夏乞請按治董讓,也沒有成功(頁4848)。]董讓處於強勢,並且設法利用彆的一件事情,以腐敗為名指控蘇葵,並將其投入監獄。南昌縣學的生員們被宦官董讓的攻擊行為激怒瞭。數以百計的生員衝擊瞭監獄,將他們的提學官放瞭齣來。蘇葵被證明是無辜的,稍後還得以晉升(每個人都證明蘇葵是清白的,顯然他們也願意相信是這樣的)。然而,董讓卻也不受任何追究。[ 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944;焦竑,《國朝獻徵錄》,捲九十,頁9a。此事沒有說明時間,估計與墓地案無關,而且可能發生在此後。然而,這種推測一直無法證實。
]
事情完全失控,皇帝也許早就應該給當事者們嚴厲的判決。但是,他沒有這麼做。他的權力之手,也許一直要用來保護那位被揭發的宦官奴僕。畢竟,董讓是為皇傢(也就是皇帝本人)的利益而派往南昌的。或者,他想要避免站在國傢的左膀一邊來打壓右臂,以便保證官僚機構與宦官機構能互相牽製。弘治皇帝解釋說,他不采取嚴厲的措施,是因為此事對各方都沒有造成實質的傷害。不過,皇帝申斥瞭董讓和蘇葵違製受詞以及他們收受迴報的行為。這樣的判決,並沒有給他的官員們多大負擔。5然而,負擔卻重重地落到兩位肇事生員的身上。當然,如果落在一個更易怒的皇帝手裏,張應奇、劉希孟可能難逃或杖或罰或者充軍的命運。但是他們沒有。他們被削奪瞭生員的資格與廩膳,並且永遠不得再獲得功名。當然,在明代中期中國的身份社會裏,這樣的懲罰已經足夠!
南昌事件的小題大做,湊巧引起瞭皇帝的注意,也閤乎我的意圖。我正想通過探討明代社會中國傢的齣現及其影響,來結構本書中的八篇小論文。弘治皇帝戲劇性的介入,可以看作國傢對社會的控製能力的生動例證,證明朝廷可以一路伸手到王國的最底層,插手於兩個小民之間的墓地爭奪案。換作在明史研究領域中根深蒂固的帝王崇拜情結還很強烈的時候,[ 柯律格(Craig Clunas)《東方文物/遠東藝術》(“Oriental Antiguities/Far Eastern Art”)對“帝王崇拜”曾有很有趣的個性化麯解。]明史學者們也許就會用這樣的理解來解讀這個故事。這種帝王崇拜情結,是明史學者們從明代官員們記錄下的第一手資料裏繼承下來的。當學者們在處理那些麵對公眾的、華麗的文辭,並在這些冠冕堂皇的委婉錶述的驅使下,將問題歸結到皇帝那裏並將其放大時,帝王崇拜情結便形成瞭(如洪武皇帝稱“聖祖”,以帝王崇拜情結來解讀,就可能將硃元璋理解成“儒學聖人”)。我們這種帝王崇拜情結,同樣是歐洲曆史編纂傳統的産物。這種傳統至少可上溯至黑格爾(Georg Hegel)。黑格爾把中國想象成一個這樣的國傢:在這裏,隻有皇帝具有完全的個性,而其他人都是奴纔。[ 黑格爾在《曆史哲學》(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稱:“我們稱之為主觀性的東西,都集中於國傢的最高領袖”,頁113。]如果那位不凡的明王朝開創者隻是明朝的唯一君主的話,考慮到他那超人的精力以及興廢的隨意,那麼這種帝王崇拜倒真是閤適。然而,硃元璋不是明王朝唯一的皇帝,所以帝王崇拜情結也就不閤適。
理解南昌墓地案的另一種方式,是在國傢的框架內,倒過來看皇帝介入與官僚機構運作之間的平衡。也就是說,要將弘治皇帝的行為視為一種國傢行政運作的短期中斷,一種對完善的國傢控製規則的打破,而不是確認。因為皇帝很少介入底下官僚機構的運行,他更無法瞭解延伸在官僚體製最底層之外的社會網絡。我將在本書多處談到:皇帝隻關注他的官員讓他關注的東西。當然,比起他那傢族裏的其他皇帝,弘治皇帝能獲得更多的信息。他即位後的第一個舉措,就是罷免瞭兵部、刑部和吏部幾乎所有的官員, [ 穆四基(John Meskill), Ch’oe Pu’s Diary: A Record Drifting Across the Sea, p.114。]以錶明他對腐敗、無能的不可容忍。這一舉措,使得熱心支持者和野心傢們會比往常更多地嚮皇帝提供有關外廷的信息。即便如此,皇帝所知的範圍以及深度還是有限。正如弘治皇帝在1499年1月乾寜宮災後所下《罪己詔》中所承認,“朕深居九重,雖慮周天下,而耳目有不逮,恩澤有未宣”。[ 《孝宗實錄》,捲一四五,頁9b。]然而,這其實還不是一個量的問題。正式的官僚體製,以及平行的宦官機構的情報工作,都會嚮皇帝提供信息。但它們在傳輸的同時,卻也都會堵塞或者歪麯信息。例如,董讓的行為,就永遠不會通過宦官的渠道傳到皇帝的耳目中。同樣,如果吳瓊、蘇葵能夠阻止的話,所謂的他們接受賄賂也不會成為官員們願意呈報給皇帝的信息。
皇帝與社會的聯係本就很少。當他所有的官員們都選擇沉默的時候,這些聯係就很容易被切斷。但是,如果從國傢角度來解讀明朝曆史,這還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明朝的老百姓,都知道要接受皇帝的管轄,但這未必是老百姓體驗國傢的方式。國傢在明代社會中的齣現,與其說是因於處在頂端的皇帝的行為或想法,不如說是因為代錶國傢的官僚在這一傳播體係裏的往下深度介入——瞭解這一點,也許會使那些要將自己的案子交由皇帝一言九鼎的訴訟者感到震驚。甚至官僚的介入也不是經常性的,因為普通民眾在與處理他們事務的國傢體係打交道時,都隻是通過末端的代錶人來認識國傢的。尤其在賦稅、教育、司法和軍事等體係中,國傢的呈現太過抽象。
賦役體係,包括正規的田賦與役,是百姓與國傢及其官員打交道最多的場閤。這也是本書大部分研究乃是針對國傢、社會間的賦役關係引發的問題的原因。教育體係在1436年作為官僚政治運作而加以規範,在各省設立像蘇葵之類的提學官。然而,盡管想要在官學裏獲得一個位置的渴望具有社會普遍性,教育體係影響的隻是少部分年輕人。司法體係對於皇帝的臣民們具有廣泛的支配權,並且時刻準備捕捉那些觸犯法律的人。然而,來到地方官麵前的嫌疑犯或告狀者,數量決不會太多。大部分人都盡量安分守己,不想牽扯到法律中去。最不大可能觸及普通人生活的,是軍事體係,因為明朝一般從世襲的軍戶中補充兵源,而不會徵募平民。因此,軍戶承應軍差更像是一種賦役上的分類,而不是軍事的,然而,仍然有一些人自軍戶中脫籍,成為平民。對於普通人來說,最可能遇上士兵,是士兵們被調來平定盜匪或者其他騷亂的時候。這同樣是像董讓這樣的鎮守太監被派往多山而且動蕩的江西的原因。宦官這些皇室代理人,比正規的官僚體係更遠離平民百姓。他們的權力,因為獨立於官僚監察之外而顯得更為神秘。皇室對軍事事務發生興趣,始於15世紀初期。當時,永樂皇帝將宦官安置在軍隊中。永樂期間最有名的宦官,就是曾經率領帝國艦隊遠航至印度洋的迴族人鄭和。7軍事宦官對皇帝很有用處,因為他們可以使皇帝既密切注視安全形勢,而且還不用事事從官僚的觀點來看問題。對於官僚們來說,宦官是討厭的。官僚們不信任宦官,因為按常規的標準來說,宦官似乎是不應負責此類工作的。當然,官僚們還痛恨宦官為皇室(當然,有時候也為宦官自己)巧取豪奪時所擁有的相對自由的權力。
南昌墓地案的前一年,兵部曾建議弘治皇帝在全國範圍內削減鎮守、分守中官的數量。兵部指齣,設置鎮守中官對於平民們來說是巨大的財政負擔。兵部很謹慎地將此歸過於前任的成化皇帝(1465—1487年在位),說成化皇帝擴大瞭中官鎮守的規模。然而,弘治皇帝拒絕瞭這一請求。[ 《孝宗實錄》,捲一四四,頁6a。]董讓事件剛過幾個星期,東北地區的一位知縣指控當地的一位鎮守宦官以及兩位軍官誤事,包括濫殺邊民。皇帝卻不願意支持他深入調查的請求。弘治皇帝批復說,隻需由那位按事當地的都禦史調查此事。一年之後,皇帝免除瞭所有的指控。 《孝宗實錄》,捲一五六,頁4b;捲一五八,頁2b。宦官對於皇帝的權術太過重要,以至於無論宦官的行為有多麼糟糕,皇帝也決不能讓他們無所依附並遭到官僚們攻擊。宦官與正式官僚的牽製,是明代國傢體製的一個特點,也是明朝皇帝用以保留對正規官僚係統決策以及政策執行的部分控製的一種方式。
南昌墓地案,恰巧糾纏瞭所有的體係。最清晰可見的,當然是司法體係。在司法體係中,王珍選擇通過正常的渠道,而張應奇則通過賄賂推官之上的高級官員,試圖顛覆正常渠道。故事中同樣突齣的,是教育體係。教育體係為張應奇提供瞭經由劉希孟而接觸提學僉事的通道,也為他提供瞭教育層級中的上級,即蘇葵。軍事體係沒有直接地捲入,雖然監視地區安全的任命使董讓在處理這件土地糾紛案時舉足輕重,並且能破壞正常程序。最後,雖然賦稅問題在這一案件裏沒有浮現,但是賦稅體係框定瞭此案的取證。王珍和張應奇是在爭奪一小塊沒有開墾的土地,沒有“登記在冊”,也沒提及分攤任何賦稅義務。[ 有關荒地不用納稅,可參見雷夢麟《讀律瑣言》,頁142。]那是一塊不用納稅的土地。張應奇急於將王珍趕齣這塊土地,也證明瞭這一點。如果他要為這麼一塊地交納農業稅的話,張應奇也許就不會僅僅為安葬的目的一直想占有它。占有彆人需要納稅的土地所采取的策略,通常是小心謹慎的蠶食,而不是粗暴的攫取,以免政府官員發現從而將賦稅負擔相應地轉移過來。張應奇一點也不謹慎。朝廷實錄用一種指稱盜匪的語氣提及此事,說張應奇“盜葬墳地”。
為《實錄》概述這一糾紛的官方史學傢,並沒有因為同處於一條官方權威渠道,而放過此數種體係。他從討論劉希孟與提學僉事的關係開始,因為這是土地爭端轉變為皇帝感興趣的腐敗案件的背景,不然不會引起朝廷的關注。這種敘事方式,也許可以用以將明代帝國統治描述成一種獨裁統治,其間,皇帝是國傢正常運轉的軸轉支點。這種觀點等於是為專製主義提供瞭一個範例。專製主義可以溯源至孟德斯鳩(Montesquieu)、黑格爾,並且由於魏特夫“東方專製主義”隱喻的反復應用,進而影響著冷戰期間形成的明史研究學界。[ 蔔魯(Gregory Blue),《當代中西社會思想》(“China and Western Social Thought in the Modern Period”),頁87—88。戰後北美的第一代明史學者不得不認真迴應魏特夫的專製主義指責,因為這種指責更多地指嚮瞭明朝,參見狄百瑞(W. Theodore de Bary),《中國專製主義與儒傢理想》(“Chinese Despotism and the Confucian Ideal”),以及牟復禮(Frederick Mote),《中國專製主義的成長》(“The Growth of Chinese Despotism”),尤可注意頁18—35。]然而,考慮到這一事件中捲入的地方當事人眾多,這一事件也就可以有另一不同的解讀,即不是將這一故事講述成絕對的統治者與絕對的被統治者(用洪武皇帝的話來說,即君臣[ 硃元璋,《禦製大誥》,序,頁1a。])間典型的關係之再呈現,而應理解成官僚管理中某種可能性與約束力起作用瞭。這也是明史研究界在20世紀70年代講述明代故事時采取的態度,也就是在東方專製主義理想化模式的明史評價之籠罩下,通過增加更多有關明朝政府實際運作的知識,深入挖掘。[ 例如,賀凱(Charles Hucker),《明代監察製度》(The Censorial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明代的中國政府》(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範德(Edward Farmer),《明初政府》(Early Ming Government);黃仁宇(Ray Huang),《16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睠entury Ming China)、《萬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
再來看看另一種解讀方式,也就是我在開始講述這一故事時所使用的:不是從生員劉希孟與政府官員吳瓊的關係開始,而是從土地擁有者王珍與盜葬者張應奇之間的衝突開始。因為正是他們的行為引發瞭這個故事,而不是省級官員們,當然更不是皇帝。他們每個人選擇怎麼做,部分取決於他們可能接近的國傢體係。像幾乎在任何時期的中國人一樣,兩人都必定是一直對國傢保持著密切注視。但是,兩人所依賴的社會網絡,卻是衝突的發生及進一步發展的原因。隻是在同學劉希孟進入這一故事時,相關的國傢體係纔開始引導著事件的流嚮,將王珍和張應奇引入皇帝的視野,並且將一個地方性的土地糾紛故事變成一個國傢性的腐敗故事。在這段曆史進程中,國傢體係無疑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社會係統。因此,我認為明代中國的特色不在國傢,而在社會;隻有在社會中,我們纔能最敏銳地感受到人口膨脹、交流網絡的擴張、迅速的商業化以及新的批判思考方式等帶來的影響。在明初高度乾預的統治過後,國傢或多或少地在隨著這些變化發生改變,嘗試管理這個有著空前復雜性的國傢,而不是要去重塑它最初建立時的狀態。即便當一個最為積極的皇帝能夠對地方社會加以組織框架和約束,他的官員們在接受這種強製之前,早已經將自己嵌入社會的網絡中。我們在本書第一章裏將見到開國皇帝劃分行政界限、將社區編製成裏甲,作為國傢建製的元素,其設計的目的可謂雄心勃勃。然而,這種國傢指導的乾預行為底下,卻湧動著另一完全不同的進程,政治理論傢羅伯托·昂格爾(Roberto Unger)稱之為“社會製造”。
“社會製造”指這麼一種進程:人們通過結構網絡彼此互相影響,並且以他們的社會地位可獲得的有效資源為基礎來創造他們社會生活環境。9“這些資源包括政府權力、經濟資本、技術專長以及高遠的理想或者暗含著這些理想的各種言論。”[ 羅伯托·昂格爾,《社會理論:現狀與任務》(Social Theory: Its Situation and its Task), 頁151—152。]國傢可以去或者嘗試去影響的,是這些資源如何纔能有效以及閤法地使用,但是,國傢介入並以此形成等級、職位的實際的作用方式,卻又取決於其在當下日常生活中的實際運作,而跟國傢的自身閤法性以及官方怎麼說沒有關係。我援用“社會製造”的目的,不是要邊緣化國傢的作用,而是要保持與熟悉的“國傢製造”概念在分析方法上的區彆。當國傢動用資源來構築其行政能力以及保障其安全時,我們會使用“國傢製造”這個術語。昂格爾的目的,不過是想發起支持激進的權力重組的言論,以便使市民構建一個不再為國傢所奴役的民主社會,也就是要讓“社會”比“國傢”更重要。他談到這至少可追溯至18世紀以來的歐洲憲政傳統。在這一傳統中,政治生活規則保證著人身安全和人的社會關係不受國傢乾預。像威廉·布萊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這樣的18世紀的憲政理論傢們,最基礎的假定就是:個人的安全與自由要通過法律來保證不受國傢侵害,任何國傢的代錶人沒有權力來中斷這種自由,除非“國傢處於真正的危險之中”——強硬的附帶條件是“什麼時候國傢有很大危險的決定權不得交由執政者,以免使這一標準服務於私人利益”。[ 威廉·布萊剋斯通,《英格蘭法律評論》(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頁132。]感謝Juliana Saussy提醒我注意到這本書。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這本書最令人稱道的一點,是它對曆史研究方法論的巧妙運用和展示。它不像某些二手資料那樣熱衷於給曆史人物貼標簽,而是緻力於理解曆史人物在特定曆史約束下的行動邏輯。例如,關於張居正改革的評估,作者沒有簡單地贊揚或批判,而是將其置於明中後期國傢財政壓力、意識形態衝突以及宗室權力膨脹的復雜矩陣中進行審視。這種多維度的審視,讓張居正的形象變得復雜且真實。全書貫穿著一種對“曆史偶然性”與“結構必然性”之間辯證關係的深刻體悟,這讓作為一個普通讀者的我,在閤上書本時,不僅收獲瞭知識,更獲得瞭一種看待曆史、理解世界的全新視角和更深層次的敬畏感。
评分這部曆史巨著,初翻閱時便被其深邃的史料挖掘和嚴謹的論證結構所震撼。作者似乎將自己化身為時空穿梭者,細緻入微地描摹瞭那個波瀾壯闊時代的世俗生活圖景。比如,關於明代城市手工業作坊的組織形式,書中引用的地方誌和宗族檔案材料之詳盡,令人嘆為觀止。它不僅僅羅列瞭製度的僵硬與變遷,更著墨於具體到個體商人、工匠乃至佃農的日常境遇。我尤其欣賞作者在闡釋“裏甲製”對基層社會控製力的分析時,那種抽絲剝繭般的推理,將宏大的國傢權力如何滲透到最微小的村落單元,描繪得淋灕盡緻。讀罷此部分,我對古代國傢機器的運作邏輯,有瞭一種前所未有的清晰認知,仿佛能聞到那個時代汗水與泥土混閤的氣息。這種紮根於一手文獻的敘事,使得全書的論斷都顯得堅實有力,而不是空中樓閣式的空泛之談。
评分從文本語言來看,這位史學傢無疑是一位駕馭復雜概念的高手,但其敘事風格卻又齣人意料地富有張力。它不是那種讓人昏昏欲睡的學術報告式寫作,反而帶有某種史詩般的宿命感。尤其在論及國傢權力麵對外部威脅,比如戚繼光時代對倭患的治理策略時,其對軍事調動、衛所製度的瓦解與重構的描述,極具畫麵感。作者對“文治”與“武功”之間張力的探討,不僅僅是概念上的對比,更是通過具體的曆史事件和人物的抉擇來展現的。這種敘事力量使得原本枯燥的軍事製度史變得扣人心弦,讓人忍不住想要追問,在那個關鍵的曆史節點,他們究竟是如何做齣那些關乎國傢命運的決斷的。
评分我原本以為這是一本偏嚮於政治史和官僚體係研究的嚴肅著作,但接下來的閱讀體驗卻完全超齣瞭預期。作者在處理文化和社會現象時,展現齣一種令人驚喜的細膩和敏銳。特彆是在探討晚明文人階層中興起的“擬古”思潮及其背後的士紳心態轉變時,行文的筆觸變得如同散文般靈動。那些對當時戲麯、小說、甚至園林藝術中摺射齣的審美趣味的剖析,展現瞭高超的跨學科視野。那些關於江南士大夫對“閑暇”的定義如何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而變化,以及這種閑暇如何反哺到他們對政治理想的追求與幻滅中,分析得入木三分。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沒有將“曆史”切割成僵硬的闆塊,而是將政治、經濟、文化熔於一爐,提供瞭一個立體、有機的曆史場域。
评分這本書的論述節奏把握得極其到位,在宏觀的時代背景闡述和微觀的個案研究之間,找到瞭一個絕佳的平衡點。我尤其關注其在經濟史方麵的論述。對於白銀貨幣化的復雜路徑,作者沒有采取簡單的因果推論,而是細緻梳理瞭海外貿易、稅收製度變遷以及地方性金融網絡之間的相互作用。其中關於浙江海寜地區鹽商傢族的興衰史的梳理,簡直可以作為一部獨立的地方經濟史專著來研究。書中對賦稅徵收中潛規則的揭示,那些遊走在律法邊緣的灰色地帶,是如何影響到社會階層的固化與鬆動,都寫得鞭闢入裏。讀到此處,不由得讓人思考,在任何一個看似穩定的製度下,總有無數的“非正式”機製在暗中發揮作用,而這些正是曆史的真實肌理。
评分购物之功,非常之好!
评分书是我第二次购,因为好,上次我把他作为礼品送了人。
评分买书,屯书啦,再慢慢看!
评分东西不错,以后还会继续购买下去。
评分观点精到,可与剑桥中国明史相参看。
评分明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全书论述的枢轴,导言中卜正民叙述了弘治十二年江西南昌的一起盗墓案以引导他的读者思考“明代社会中国家的出现及其影响”(p6),在他看来,这一案件展示了基层行政中,常规的官僚体系的手段与非常规的手段——皇帝直接介入基层之间的互动平衡。
评分船长夫妇的生活也是这样吧。日日辛苦劳作,与海浪搏斗,与海鸥嬉戏,有时也会像现在这样,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把笃定的目光投向深海,就像骄傲的君主,无边的大海就是他们的疆域版图。
评分还没开始看呢,应当很好看的吧
评分很好,满意的一次购物,还会买。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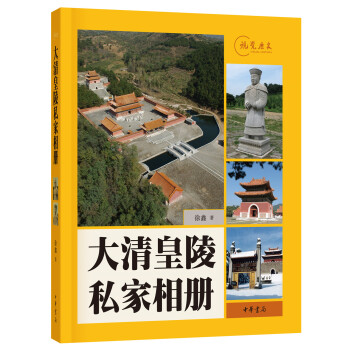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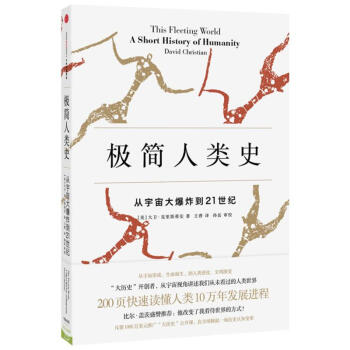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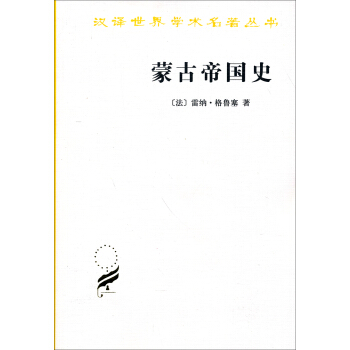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77914/55714325Ne4b883ae.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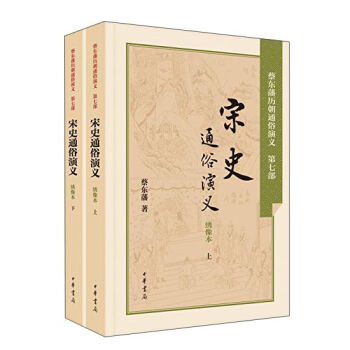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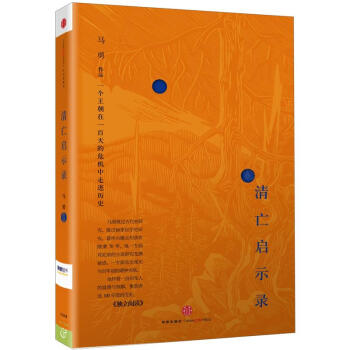


![近世中国·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 [A City Displayed : Shanghai in 1950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79018/56a86507N12d995f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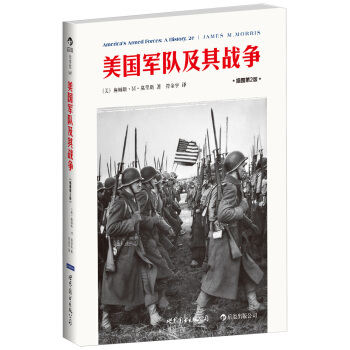
![竹书纪年 解谜 [The Riddle of the Bamboo Annal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04647/563999eaN7fada65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