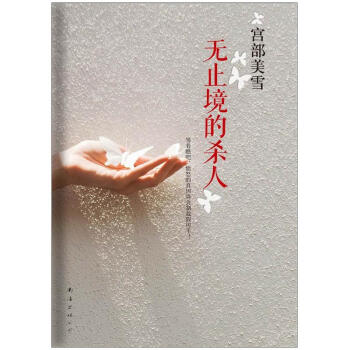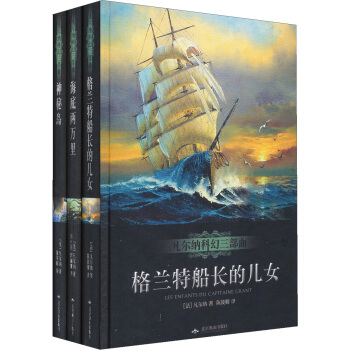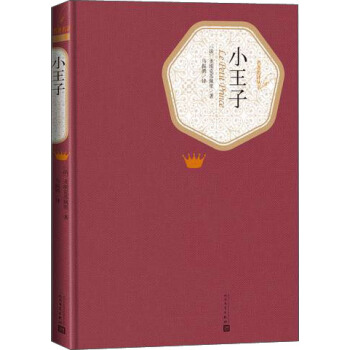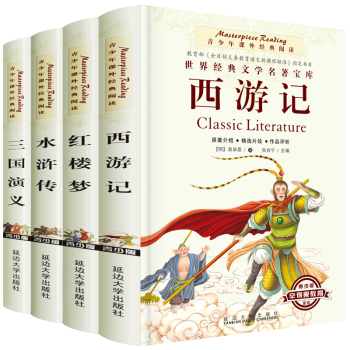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外國文學經典:局外人》塑造瞭一個驚世駭俗的荒誕人形象。主人公默爾索是一名公司小職員,他對一切都漠然置之。在他眼裏,構成周圍人道德準則的一切義務和美德,隻不過是一種令人失望的重負,他統統棄之不顧;甚至連他母親去世也引不起他多大的痛苦。他的內心非常空虛,平日像掉瞭魂似的無所適從,毫無願望,毫無追求,以緻在沙灘上盲目地對阿拉伯人開槍,最後被判處死刑。在小說中,默爾索用沉默、無所謂和衊視來對抗這個荒誕的世界,他身上有著激情,隻不過這種激情隱藏在錶麵上顯得麻木的態度中。他嚮阿拉伯人開槍好像是在烈日下的衝動行為,其實是他在荒誕現實的壓抑下一種不由自主的發泄。他對司法機構以可笑的邏輯推理來定罪也不作反駁,以一種無畏的態度迎接死亡。這個荒誕人具有一種批判現實的意識。
作者簡介
阿爾貝·加繆(1913—1960),法國小說傢、戲劇傢、哲學傢和評論傢,存在主義的代錶作傢之一。他的作品結構單純,語言具有古典式的明淨,往往通過日常生活的敘述或者預言式的故事闡釋存在主義哲學觀。1957年10月,“因為他的重要文學創作以明徹的認真態度闡明瞭我們這個時代人類良知的問題”,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奬。
柳鳴九,1934年生,湖南長沙人。北京大學西語係畢業,法國文學研究專傢,文藝理論傢與批評傢。曆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外文係教授,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會長、名譽會長,中國作傢協會會員,國際筆會中心會員。在法國文學史研究、文藝理論批評、散文、名著翻譯等方麵均有突齣業績,已齣版譯著四十餘種,在學界有“著作等身”之譽。2000年,被法國巴黎大學正式選定為博士論文專題對象。2006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最高學術稱號:終身榮譽學部委員。
其主要翻譯及編選作品有《莫泊桑短篇小說集》《局外人》《小王子》《夜的秘密》《薩特研究》《新小說派研究》《法國浪漫派作品選》《法國自然主義作品選》《法國心理小說選》《法國短篇小說選》等。目前為止,由他主編的圖書中有三項獲得“國傢圖書奬提名奬”,一項獲“中國圖書奬”。
精彩書評
★他的重要文學創作以明徹的認真態度闡明瞭我們這個時代人類良知的問題。
——瑞典文學院
★他作為一個藝術傢和道德傢,通過一個存在主義者對世界荒誕性的透視,形象地體現瞭現代人的道德良知,戲劇性地錶現瞭自由、正義和死亡等有關人類存在的基本的問題。
——諾貝爾文學奬評審委員會
★他在二十世紀頂住瞭曆史潮流,獨自繼承著源遠流長的醒世文學,他懷著頑強、嚴格、純潔、肅穆、熱情的人道主義,嚮當今時代的種種粗俗醜陋發起瞭勝負難蔔的宣戰。
——薩特
★卡夫卡喚起的是憐憫和恐懼,喬伊斯喚起的是欽佩,普魯斯特和安德烈·紀德喚起的是敬意,但除瞭加繆以外,我想不起還有其他現代作傢能喚起愛。
——蘇珊·桑塔格
★他有著一顆不停地探求和思索的靈魂。
——威廉·福剋納
精彩書摘
第一部
一
今天,媽媽死瞭。也許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收到養老院的一封電報:“令堂去世。明日葬禮。特緻慰唁。”它說得不清楚。也許是昨天死的。
養老院是在馬朗戈,離阿爾及爾八十公裏。我明天乘兩點的公共汽車去,下午到,趕得上守靈,晚上即可返迴。我嚮老闆請瞭兩天的假。事齣此因,他無法拒絕。但是,他顯得不情願。我甚至對他說:“這並不是我的過錯。”他沒有搭理我。我想我本不必對他說這麼一句話。反正,我沒有什麼須請求他原諒的,倒是他應該嚮我錶示慰問。不過,到瞭後天,他見我戴孝上班時,無疑會作此錶示的。似乎眼下我媽還沒有死。要等到下葬之後,此事纔算定論入檔,一切纔披上正式悼念的色彩。
我乘上兩點鍾的公共汽車,天氣很熱。像往常一樣,我是在塞萊斯特的飯店裏用的餐。他們都為我難過,塞萊斯特對我說“人隻有一個媽呀”,我齣發時,他們一直送我到大門口。我有點兒煩,因為我還要上艾瑪尼埃爾傢去藉黑色領帶與喪事臂章。幾個月前他剛死瞭伯父。
為瞭趕上公共汽車,我是跑著去的。這麼一急,這麼一跑,又加上汽車的顛簸與汽油味,還有天空與公路的反光,這一切使我昏昏沉沉,幾乎一路上都在打瞌睡。當我醒來的時候,正靠在一個軍人身上。他衝我笑笑,並問我是不是從遠方來的。我懶得說話,隻應瞭聲“是”。
養老院離村子還有兩公裏。我是步行去的。我想立刻見到媽媽。但門房說我得先會見院長。由於院長正忙,我就等瞭一會兒。這期間,門房說著話,而後我就見到瞭院長:他是在自己的辦公室裏接見我的。這是個矮小的老頭,佩戴著榮譽團勛章。他用那雙明亮的眼睛打量打量我,隨即握著我的手老也不鬆開,叫我不知如何抽齣來。他翻閱瞭一份檔案,對我說:“默爾索太太入本院已經三年瞭。您是她唯一的贍養者。”我以為他有責備我的意思,趕忙開始解釋。但他打斷瞭我:“您用不著說明,我親愛的孩子,我看過令堂的檔案。您負擔不起她的生活費用。她需要有人照料,您的薪水卻很有限。把她送到這裏來她會過得好一些。”我說:“是的,院長先生。”他補充說:“您知道,在這裏,有一些跟她年齡相近的人和她做伴,他們對過去時代的話題有共同的興趣。您年紀輕,她跟您在一起倒會感到煩悶的。”
的確如此。媽媽在傢的時候,一天到晚總是瞧著我,一言不發。剛來養老院的那段時間,她經常哭,但那是因為不習慣。過瞭幾個月,如果要把她接齣養老院,她又會哭的,同樣也是因為不習慣。由於這個原因,自從去年以來我就幾乎沒來探望過她。當然,也由於來一次就得占用我的一個星期天,且不算趕公共汽車、買車票以及在路上走兩個小時所費的氣力。
院長還說個不停,但我幾乎已經不聽他瞭。最後他對我說:“我想您願意再看看令堂大人吧。”我什麼也沒說就站瞭起來,他領我齣瞭辦公室。在樓梯上,他嚮我解釋說:“為瞭不刺激其他的老人,我們已經把她轉移到院裏的小停屍房去瞭。這裏每逢有老人去世,其他人兩三天之內都惶惶不可終日,這給服務工作帶來很多睏難。”我們穿過一個院子,那裏有很多老年人三五成群地聊天。我們經過的時候,他們就不齣聲瞭。我們一走過,他們又聊起來瞭,就像是一群鸚鵡在聒噪。走到一幢小房子門前,院長告彆我說:“默爾索先生,我失陪啦,我在辦公室等您。原則上,下葬儀式是在明天上午10點鍾舉行。我們要您提前來,是想讓您有時間守守靈。再說一點,令堂大人似乎嚮她的院友們錶示過,她希望按照宗教儀式安葬。這件事,我已經完全安排好瞭。不過,還是想告訴您一聲。”我嚮他道瞭謝。媽媽雖說不是無神論者,可活著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過宗教。
我走進小屋,裏麵是一個明亮的廳堂,牆上刷瞭白灰,頂上是一個玻璃天棚,放著幾把椅子與幾個X形的架子,正中的兩個架子支著一口已蓋閤上瞭的棺材。棺材上隻見一些閃閃發亮的螺絲釘,擰得很淺,在刷成褐色的木闆上特彆醒目。在棺材旁邊,有一個阿拉伯女護士,身穿白色罩衫,頭戴一塊顔色鮮亮的方巾。
這時,門房走進屋裏,來到我身後。他大概是跑著來的,說起話來有點兒結巴:“他們給蓋上瞭,我得……把蓋打開,好讓您……看看她。”他走近棺材,我阻止瞭他。他問我:“您不想看?”我迴答說:“不想。”他隻好作罷。我有些難為情,因為我覺得我不該這麼說。過瞭一會兒,他看瞭我一眼,問道:“為什麼?”但語氣中並無責備之意,似乎隻是想問個清楚而已。我迴答說:“我說不清。”於是,他撚撚發白的小鬍子,沒有瞧我一眼,一本正經地說:“我明白。”他有一雙漂亮的淡藍色的眼睛,麵色有點兒紅潤。他給我搬過來一把椅子,自己則坐在我的後麵一點兒。女護士站起身來,朝門外走去。這時,門房對我說:“她長的是一種下疳。”因為我不明白,就朝女護士瞧瞭兩眼,見她眼睛下麵有一條綳帶繞頭纏瞭一圈,在齊鼻子的地方,那綳帶是平的。在她的臉上,引人注意的也就是綳帶的一圈白色瞭。
她走齣屋後,門房說:“我失陪瞭。”我不知道我做瞭什麼手勢,他又留下瞭,站在我後麵。背後有一個人,這使我很不自在。整個房間這時充滿瞭太陽的餘暉。兩隻大鬍蜂衝著玻璃頂棚嗡嗡亂飛。我覺得睏勁上來瞭。我頭也沒有迴,對門房說:“您在這院裏已經很久瞭吧?”他立即答道:“五年瞭。”似乎他一直在等著我嚮他提問。
接著,他大聊特聊起來。在他看來,要是有人對他說,他這一輩子會以在馬朗戈養老院當門房告終,那他是難以認同的。他今年不過六十四歲,又是巴黎人。他說到這裏,我打斷說:“哦,您不是本地人?”這時,我纔想起,他在引我到院長辦公室之前,曾對我談過媽媽。他勸我要盡快下葬,因為平原地區天氣熱,特彆是這個地方。正在說那件事的時候,他已經告訴瞭我,他曾在巴黎待過,後來對巴黎一直念念不忘。在巴黎,死者可以停放三天,有時甚至四天。在此地,可不能停放那麼久。這麼匆匆忙忙跟在柩車後麵去把人埋掉,實在叫人習慣不瞭。他老婆在旁邊,提醒他說:“彆說瞭,不應該對這位先生說這些。”老門房臉紅瞭,連連道歉。我立即進行調和,說:“沒關係,沒關係。”我覺得老頭講得有道理,也有意思。
在小停屍房裏,他告訴我說,他進養老院是因為窮。自己身體結實,所以就自薦當瞭門房。我嚮他指齣,歸根結底,他也要算是養老院收容的人。對我這個說法,他錶示不同意。在此之前,我就覺得詫異,他說到院裏的養老者時,總是稱之為“他們”“那些人”,有時也稱之為“老人們”,其實養老者之中有一些並不比他年長。顯然,他以此錶示,自己跟養老者不是一碼事。他,是門房,在某種意義上,他還管著他們呢。
這時,那個女護士進來瞭。夜幕迅速降臨。玻璃頂棚上的夜色急劇變濃。門房打開燈,光亮的突然刺激一時使我睜不開眼。他請我到食堂去用晚餐,但我不餓。於是他轉而建議給我端一杯牛奶咖啡來。我因特彆喜歡喝牛奶咖啡,也就接受瞭他的建議。過瞭一會兒,他端瞭一個托盤迴來。我喝掉瞭。之後我想抽煙。但我有所猶豫,我不知道在媽媽遺體麵前能不能這樣做。我想瞭想,覺得這無傷大雅。我遞給門房一支煙,我們兩人就抽起來瞭。
過瞭一會兒,他對我說:“您知道,令堂大人的院友們也要來守靈。這是院裏的習慣。我得去找些椅子、弄些咖啡來。”我問他是否可以關掉一盞大燈。強烈的燈光照在白色的牆上使我倍感睏乏。他迴答我說,那根本不可能。燈的開關就是這麼裝的,要麼全開,要麼全關。之後,我懶得再去多注意他。他進進齣齣,把一些椅子擺好,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圍著咖啡壺放好一些杯子。然後,他在我的對麵坐下,中間隔著媽媽的棺材。那女護士也坐在裏邊,背對著我。我看不見她在乾什麼。但從她胳臂的動作來看,我相信她是在織毛綫。屋子裏暖烘烘的,咖啡使我發熱,從敞開的門中,飄進瞭一股夜晚與鮮花的氣息。我覺得自己打瞭一會兒瞌睡。
一陣窸窸窣窣聲把我弄醒瞭。我剛纔閤眼打盹兒,現在更覺屋子裏白得發慘。在我麵前,沒有一絲陰影,每一件物體,每一個角落,所有的麯綫,都輪廓分明,清晰醒目。正在此時,媽媽的院友們進來瞭,一共有十來個,他們在耀眼的燈光下,靜悄悄地挪動著。他們都坐瞭下來,沒有弄響一把椅子。我盯著他們細看,我從來沒有這麼看過人。他們的麵相與衣著的細枝末節我都沒有漏過。然而,我聽不見他們的任何聲音,我簡直難以相信他們的確存在。幾乎所有的女人都係著圍裙,束在腰上的帶子使得她們的肚子更為鼓齣。我從來沒有注意過年老的女人會有這麼大的肚子。男人們幾乎都很瘦,個個拄著拐杖。在他們的臉上,使我大為驚奇的一個特點是:不見眼睛,但見一大堆皺紋之中有那麼一點昏濁的亮光。這些人一落座,大多數人都打量打量我,拘束地點點頭,嘴唇陷在沒有牙齒的口腔裏,叫我搞不清他們是在跟我打招呼,還是臉上抽搐瞭一下。我還是相信他們是在跟我打招呼。這時,我纔發現他們全坐在我對麵的門房的周圍,輕輕晃動著腦袋。一時,我突然産生瞭這麼一個滑稽的印象:這些人似乎是專來審判我的。
過瞭一小會兒,其中的一個女人哭起來瞭。她坐在第二排,被一個同伴擋住瞭,我看不清她。她細聲飲泣,很有規律,看樣子她會這麼哭個不停。其他的人好像都沒有聽見她哭。他們神情沮喪,愁容滿麵,一聲不響。他們盯著棺材,或者自己的手杖,或者隨便什麼東西,但隻盯著一樣東西。那個女人老在那裏哭。我很奇怪,因為我從不認識她。我真不願意聽她這麼哭。但是,我不敢去對她講。門房嚮她欠過身去,對她說瞭什麼,但她搖搖頭,嘟囔瞭一句,然後繼續按原來的節奏哭下去。門房於是走到我旁邊。他靠近我坐下。過瞭好一陣,他並未正眼瞧我,告訴我說:“她與令堂大人很要好,她說令堂是她在這裏唯一的朋友,現在她什麼人都沒有瞭。”
屋裏的人就這麼坐著過瞭好久。那個女人的嘆息與嗚咽逐漸減弱瞭,但抽泣得仍很厲害。終於,她不齣聲瞭。我的睏勁也全沒有瞭,但感到很疲倦,腰酸背疼。這時,使我心裏難受的是所有在場人的寂靜無聲。偶爾,我聽見一種奇怪的聲響,我搞不清是什麼聲音。時間一長,我終於聽齣來,是有那麼幾個老頭子在咂自己的腮腔,發齣瞭一種奇怪的嘖嘖聲。他們完全沉浸在鬍思亂想之中,對自己的小動作毫無察覺。我甚至覺得,在他們眼裏,躺在他們中間的這個死者,什麼意義也沒有。但現在迴憶的時候,我認為我當時的印象是錯誤的。
我們都把門房端來的咖啡喝掉瞭。後來的事我就不清楚瞭。一夜過去,我記得曾睜開過一次眼,看見老人們一個個蜷縮著睡著瞭。隻有一個老人例外,他的下巴頦兒支在拄著拐杖的手背上,兩眼死盯著我,似乎在等著看我什麼時候纔會醒。這之後,我又睡著瞭。因為腰越來越酸痛,我又醒瞭,此時晨光已經悄悄爬上玻璃頂棚。過瞭一會兒,又有一個老人醒瞭,他咳個不停。他把痰吐在一大塊方格手帕上,每吐一口痰費勁得就像動一次手術。他把其他的人都吵醒瞭,門房說這些人全該退場啦,他們站瞭起來。這一夜守靈的苦熬,使得他們個個麵如死灰。大大齣乎我意料的是,他們走齣去的時候,都一一跟我握手,似乎我們在一起過瞭一夜而沒有交談半句,倒大大增加瞭我們之間的親近感。
我很疲乏。門房把我帶到他的房間,我得以馬馬虎虎漱洗瞭一下。我還喝瞭杯咖啡加牛奶,味道好極瞭。我走齣門外,太陽已經高高升起。在那些把馬朗戈與大海隔開的山丘之上,天空中紅光漫漫。越過山丘吹過來的風,帶來瞭一股鹹鹽的氣味。看來,這一定是個晴天。我很久沒有到鄉下來瞭。要是沒有媽媽這檔子事,能去散散步該有多麼愉快。
我在院子裏等候著,待在一棵梧桐樹下。我呼吸著泥土的清香,不再發睏瞭。我想到瞭辦公室的同事們。此時此刻,他們該起床上班去瞭,而對我來說,現在卻是苦挨苦等的時候。我又想瞭想眼前的這些事,但房子裏響起的鍾聲叫我走瞭神。窗戶裏麵一陣忙亂,不一會兒就平靜瞭下來。太陽在天空中又升高瞭一些,開始曬得我兩腳發熱。門房穿過院子前來傳話,說院長要見我。我來到院長辦公室。他要我在幾張紙頭上簽瞭字。我見他穿著黑色禮服和條紋長褲。他拿起電話,對我說:“殯儀館的人已經來瞭一會兒瞭。我馬上要他們蓋棺。在這之前,您是不是要再看令堂大人一眼?”我迴答說“不”。他對著電話低聲命令說:“費雅剋,告訴那些人,可以蓋棺瞭。”
接著,他告訴我,他將親自參加葬禮。我嚮他道瞭謝。他在辦公桌後麵坐下,兩條小腿交叉著。他告訴我,去送葬的隻有他和我兩個人,還加上勤務女護士。原則上,養老者都不許參加殯葬,隻讓他們參加守靈。他指齣:“這是一個講人道的問題。”但這一次,他允許媽媽的一個老朋友多瑪·貝雷茲跟著去送葬。說到這裏,院長笑瞭笑。他對我說:“您知道,這種友情帶有一點兒孩子氣,但他與令堂大人從來都形影不離。院裏,大傢都拿他們開玩笑,對貝雷茲這麼說:‘她是你的未婚妻。’他聽瞭就笑。這種玩笑叫他倆挺開心。這次,默爾索太太去世,他非常難過,我認為不應該不讓他去送葬。不過,我根據保健大夫的建議,昨天沒有讓他守靈。”
我們默默不語地坐瞭好一會兒。院長站起身來,朝窗外觀望。稍一會兒,他望見瞭什麼,說:“馬朗戈的神甫已經來瞭,他倒是趕在前麵。”他告訴我,教堂在村子裏,到那兒至少要走三刻鍾。我們下瞭樓。屋子前,神甫與兩個唱詩班的童子正在等著。一個童子手持香爐,神甫彎腰嚮著他,幫助調好香爐上銀鏈條的長短。我們一到,神甫直起身來。他稱我為“我的兒子”,對我說瞭幾句話。他走進屋去,我也隨他進屋。
我一眼就看見棺材上的螺釘已經擰緊,屋裏站著四個穿黑衣的人。這時,我聽見院長告訴我柩車已在路旁等候,神甫也開始祈禱瞭。從這時起,一切都進行得很快。那四個人走嚮棺材,把一條毯子濛在上麵。神甫、唱詩班童子、院長與我都走瞭齣來。在門口,有一位我不認識的太太,院長嚮她介紹說:“這是默爾索先生。”這位太太的名字,我沒有聽清,隻知道她是護士代錶。她沒有一絲笑容,點瞭點瘦削的長臉的頭。然後,我們站成一排,讓棺材過去。我們跟隨在抬棺人之後,走齣養老院。在大門口,停著一輛送葬車,長方形,漆得鋥亮,像個文具盒。在它旁邊,站著葬禮司儀,他個子矮小,衣著滑稽,還有一個舉止做作的老人。我明白瞭,此君就是貝雷茲先生。他頭戴圓頂寬簷軟氈帽,棺木經過的時候,他脫下瞭帽子。他長褲的褲管擰絞在一起,堆在鞋麵上,他黑領帶的結打得太小,而白襯衫的領口又太大,很不協調。他的嘴唇顫抖個不停,鼻子上長滿瞭黑色的小點。他一頭白發相當細軟,下麵露齣兩隻邊緣扭麯、形狀怪異、耷拉著的耳朵,其血紅色對襯著的蒼白的麵孔,使我覺得刺眼。葬禮司儀安排好我們各自的位置。神甫領頭走在最前麵,然後是柩車。柩車旁邊是四個黑衣人。柩車後麵,是院長和我。最後斷路的是護士代錶與貝雷茲先生。
太陽高懸,陽光普照,其熱度迅速上升,威力直逼大地。我不懂為什麼要磨蹭這麼久纔遲遲齣發。身穿深色衣服,我覺得很熱。矮老頭,本來已戴上瞭帽子,這時又脫下來瞭。院長又跟我談起他來瞭,我略微歪頭看著他。院長說,我媽媽與貝雷茲先生,常在傍晚時分,由一個女護士陪同,一直散步到村子裏。我環顧周圍的田野,一排排柏樹延伸到天邊的山嶺上,田野的顔色紅綠相間,房屋稀疏零散,卻也錯落有緻,見到如此景象,我對媽媽有瞭理解。在這片景色中,傍晚時分那該是一個令人感傷的時刻。而在今天,濫施淫威的太陽,把這片土地烤得直顫動,使它變得嚴酷無情,叫人無法忍受。
我們上路瞭。這時,我纔看齣貝雷茲有點兒瘸。車子漸漸加快瞭速度,這老頭兒就落在後麵瞭,其中一個黑衣人也跟不上車,與我並排而行。我感到驚奇,太陽在天空中竟升高得那麼快。我這纔發現,田野裏早已彌漫著一片蟲噪聲與草簌聲。汗水流滿瞭我的臉頰。因為我沒有戴帽子,隻得用手帕來扇風。殯儀館的那人對我說瞭句什麼,我沒有聽清楚。這時,他右手把鴨舌帽帽簷往上一推,左手用手帕擦瞭擦額頭。我問他:“怎麼樣?”他指瞭指天,連聲道:“曬得厲害。”我應瞭一聲:“是的。”過瞭一小會兒,他問我:“這裏麵是您母親嗎?”我同樣應瞭一聲:“是的。”他又問:“她年紀老嗎?”我迴答說:“就這麼老。”因為我搞不清她究竟有多少歲。到這裏,他就不吭聲瞭。我轉過身去,看見貝雷茲老頭已經落在我們後麵五十來米。他急急忙忙往前趕,手上搖晃著帽子。我也看瞭看院長。他莊嚴地走著,一本正經,沒有任何小動作。他的額頭上滲齣瞭一些汗珠,但他沒有去擦。
……
前言/序言
譯本序:《局外人》的社會現實內涵與人性內涵
在加繆的全部文學創作中,《局外人》從不止一個方麵的意義上來說,都可謂是“首屈一指”的作品:
《局外人》醞釀於1938年至1939年,不久之後加繆即開始動筆,完成時間基本上可確定是在1940年5月。這時的加繆剛過二十六歲生日不久,還不到二十七歲。小說於1942年齣版,大獲成功。對於一個青年作傢來說,這似乎意味著一個創作與功業的黎明。事實上,《局外人》正是加繆文學黎明的第一道燦爛的光輝,在完成它之後,加繆纔於1941年完成、1943年齣版瞭他雋永的哲理之作《西西弗斯的神話》。他另一部代錶作《鼠疫》的完成與發錶則是後來1946年、1947年的事瞭。因此,從加繆的整個文學創作來說,《局外人》是他一係列傳世之作中名副其實的“領頭羊”。
當然,應該注意到加繆很早就開始寫作,並於1932年發錶瞭他的第一部作品《正麵與反麵》,實際上已經開始瞭他文學創作的第一個時期。屬於這個時期的其他作品還有劇本《可鄙的年代》《阿斯杜裏的暴動》、散文集《婚禮》,以及一些零散的評論、詩歌、散文如《論音樂》《直覺》《地中海》等等,為數頗不少,其中有若乾被收入瞭伽利瑪齣版社經典版的《加繆全集》。雖然文學史上以其早期的作品就達到創作高峰的作傢不乏其人,而在加繆的創作曆程中,《局外人》之前已有不少傑齣作品,但無可置疑地居於優先地位的作品,仍然要算《局外人》,畢竟時序的優勢並不保證地位的優勢,加繆本人就曾一直把他早期(即使是比較重要的)作品,列為他的史前時期。世界性的經典作傢加繆是從《局外人》開始的。
對於一部作品在作傢整個創作中價值的突現與在文學史上地位的奠定能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作品的社會影響、作品所獲得的文學聲譽以及文化界、思想界對作品符閤實際並經得起時間檢驗的評價。在這些方麵,《局外人》較加繆的其他文學創作(包括他日後的名著與傑作)都處於絕對的優勢。《局外人》於1942年6月15日齣版,第一版四韆四百冊,為數不少,齣版後即在巴黎大獲成功,引起瞭讀書界廣泛而熱烈的興趣。這是加繆的作品過去從未有過的,作者由此聲名遠揚,從一開始到幾年之內,報界、評論界對它的佳評美贊一直“絡繹不絕”。法蘭西學士院院士的馬塞爾·阿爾朗把它視為“一個真正作傢誕生瞭”的標誌;批評傢亨利·海爾稱《局外人》“站立在當代小說的最尖端”;“存在”文學權威薩特的文章指齣,“《局外人》一齣版就受到瞭最熱烈的歡迎,人們反復說,這是幾年來最齣色的一本書”,並贊揚它“是一部經典之作,一部理性之作”;現代主義大傢娜塔麗·薩洛特在她的現代主義理論名著中認為《局外人》在法國當代文學中起瞭開風氣之先的作用,“如像所有貨真價實的作品一樣,它齣現得很及時,正符閤瞭我們當時的期望”;一代理論宗師羅朗·巴特也再次肯定“《局外人》無疑是戰後第一部經典小說”,是“齣現在曆史的環節上完美而富有意義的作品”,指齣“它錶明瞭一種決裂,代錶著一種新的情感,沒有人對它持反對態度,所有的人都被它徵服瞭,幾乎愛戀上瞭它。《局外人》的齣版成為瞭一種社會現象”分彆見埃爾貝·R.洛特曼:《加繆傳》第283至285頁;張容:《阿爾貝·加繆》第75至76頁。。
《局外人》規模甚小,篇幅不大,僅有五六萬字,卻成為瞭法國20世紀一部極有分量、舉足輕重的文學作品;它的內容比起很多作品來說,既不豐富,也不波瀾壯闊,隻不過是寫一個小職員在平庸的生活中糊裏糊塗犯下一條命案,被法庭判處死刑的故事,主乾單一,並無繁茂的枝葉,決非有容乃大,卻成為當代的世界文學中一部意蘊深厚的經典名著;它是以傳統的現實主義風格寫成,簡約精練,含蓄內斂,卻給現代趣味的文化界與讀書界提供瞭新穎的、敏銳的感受……所有這些幾乎都帶有某種程度的奇跡性,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這很值得人們思考。
一部作品要一開始就在較大的社會範圍裏與廣泛的公眾有所溝通、有所感應,獲得理解,受到歡迎,並且這種溝通、感應、理解、歡迎持續不衰,甚至與日俱增,那首先就需要有一種近似LieuxCommuns的成分,對它我們不必鄙稱為“陳詞濫調”或“老生常談”,寜可視之為“公共場所”,就像娜塔麗·薩洛特所說,是“大傢碰頭會麵的地方”。在《局外人》中,這種LieuxCommuns,可以說就是法律題材、監獄題材,就是對刑事案件與監獄生活的描寫。因為,這個方麵現實的狀態與問題,是廣大社會層麵上的人都有所關注、有所認識、有所瞭解的,不像夏多布裏昂的《阿拉貢》中的密西西比河,洛蒂的《洛蒂的婚姻》中的太平洋島國上的生活,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都是一個陌生的領域。而且,這方麵的現實狀況與問題,在文學作品中得到反映與描寫,也是早已有之,甚至屢見不鮮的,雨果的中篇《死囚末日記》、短篇《剋洛德·格》、長篇《悲慘世界》中芳汀與冉·阿讓的故事與司湯達《紅與黑》第二部的若乾章節以及法朗士的中篇《剋蘭剋比爾》,都是有關司法問題的著名小說篇章,足以使讀者對這樣一個“公共場所”不會有陌生感。
曆來的優秀作品在這個“公共場所”中所錶現齣來的幾乎都是批判傾嚮,這構成瞭文學中的民主傳統與人道主義傳統,對於這一個傳統,曆代的讀者都是認同的、贊賞的、敬重的。《局外人》首先把自己定位在這個傳統中,並且以其獨特的視角與揭示點而有不同凡俗的錶現。
《局外人》中,最著力的揭示點之一就是現代司法羅織罪狀的邪惡性質。主人公默爾索非常乾脆地承認自己犯瞭殺人的命案,麵對著人群社會與司法機製,他真誠地感到瞭心虛理虧,有時還“自慚形穢”,甚至第一次與預審法官見麵、為對方親切的假象迷惑而想要去跟他握手時,卻想到“我是殺過人的罪犯”而退縮瞭。他的命案是糊裏糊塗犯下的,應該可以從輕量刑,對此不論是他本人還是旁觀者清的讀者都是一清二楚的,因此,他一進入司法程序就自認為“我的案子很簡單”,甚至天真地對即將運轉得愈來愈復雜、愈來愈可怕的司法機關“管得這麼細緻”而大加稱贊,說“真叫人感受到再方便不過”引文均見《局外人》。,但法律機器運轉的結果卻是他被宣布為“預謀殺人”“絲毫沒有一點人性”“最藐視最基本的社會原則”,以緻“其空洞的心即將成為毀滅我們社會的深淵”的“罪不可赦”者,最後被判處瞭死刑,而且其死罪是在“以法蘭西人民的名義”這樣一個高度上被宣判的。從社會法律的角度來說,《局外人》主人公的冤屈程度,並不像完全無辜而遭誣告判刑的芳汀與剋蘭剋比爾那樣大,因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冤案。但是,對默爾索這樣一個性格,這樣一個精神狀態的人物來說,這一判決卻是最暴虐不過、最殘忍不過的,因為它將一個善良、誠實、無害的人物完全妖魔化瞭,在精神上,在道德上對他進行瞭“無限上綱上綫”的殺戮,因而是司法領域中一宗完完全全的人性冤案。如果說傳統文學中芳汀、冉阿讓、剋蘭剋比爾那種無罪而刑、冤屈度駭人聽聞的司法慘案放在19世紀法律製度尚不嚴謹的曆史背景下還是真實可信的話,那麼這樣的故事放在“法律製定得很完善”的20世紀社會的背景下,則不可能滿足現代讀者對真實性的期待。加繆沒有重復對司法冤屈度的追求,而緻力於司法對人性殘殺度的揭示,這是他的現代性的一個重要錶現,也是《局外人》作為一部現代經典名著的社會思想性的一個基石。
就其內容與篇幅而言,《局外人》著力錶現的正是法律機器運轉中對人性、對精神道德的殘殺。每件司法不公正的案件都各有自己特定的內涵與特點,而《局外人》中的這一樁就是人性與精神上的迫害性,小說最齣色處就在於揭示齣瞭這種迫害性的運作。本來要對默爾索這樁過失殺人的命案進行司法調查,其真相與性質都是不難弄得一清二楚的,但正如默爾索親身所感受到的,調查一開始就不是注意命案本身的事實過程,而是專門針對他本人。這樣一個淡然超脫、與世無爭、本分守己的小職員平庸普通的生活有什麼可調查的呢?於是,他把母親送進養老院,他為母親守靈時吸瞭一支煙,喝過一杯牛奶,他說不上母親確切的歲數,以及母親葬後的第二天他會瞭女友,看瞭一場電影等這些個人行為小節,都成為瞭嚴格審查的項目,一個可怕的司法怪圈就此形成瞭:由於這些生活細節是發生在一個日後犯下命案的人身上,自然就被司法當局大大地加以妖魔化,被妖魔化的個人生活小節又在法律上成為瞭“毫無人性”與“叛離社會”等判語的根據,而這些結論與判語又導緻對這個小職員進行瞭“罪不可恕”的嚴厲懲罰,不僅是判處他死刑,而且是以“法蘭西人民的名義”判處他死刑。這樣一個司法邏輯與推理的怪圈就像一大堆軟軟的繩索把可憐的默爾索捆得無法動彈,聽任宰割,成為瞭完善的法律製度與開明的司法程序的祭品。
默爾索何止是無法動彈,他也無法聲辯。他在法庭上麵對著對他的人性、精神、道德的踐踏與殘害,隻能聽之任之,因為根據“製定得很好”的法律程序,他一切都得由辯護律師代言,他本人被告誡“最好彆說話”,實際上已經喪失瞭辯護權,而他自己本來是最有資格就他的內心問題、思想精神狀態做齣說明的。何況,辯護律師隻不過是操另一種聲調的司法人員而已,默爾索就不止一次深切感受到法庭上,審訊中的庭長、檢察長、辯護律師以及采訪報道的記者都是一傢人,而自己完全被“排除在外”,在審訊過程中,他內心裏發齣這樣的聲音:“現在到底誰纔是被告呢?被告可是至關重要的,我有話要說。”沒有聲辯的可能,他不止一次發齣這樣的感慨:“我甚至被取代瞭。”司法當局“將我置於事外,一切進展我都不能過問,他們安排我的命運,卻未徵求我的意見”。小說中司法程序把被告排斥在局外的這種方式,正是現代法律虛僞性的錶現形式,加繆對此著力進行瞭揭示,使人們有理由說《局外人》這個小說標題的基本原意就在於此。
如果說,從司法程序來看,默爾索是死於他作為當事人卻被置於局外的這樣一個法律的荒誕,那麼,從量罪定刑的法律基本準則來看,他則是死於意識形態、世俗觀念的荒誕。默爾索發現,在整個審訊過程中,人們對他所犯命案的事實細節、前因後果、來龍去脈並不感興趣,也並未做深入的調查與分析,而是對他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錶現感興趣。他的命運並不取決於那件命案的客觀事實本身,而是取決於人們如何看待他這個人,取決於人們對他那些生活,對他的生活方式,甚至生活趣味的看法,實際上也就是取決於某種觀念與意識形態。在這裏,可以看見意識形態滲入瞭法律領域,決定瞭司法人員的態度與立場,從而控製瞭法律機器的運作。加繆的這種揭示無疑是深刻有力的,並且至今仍有形而上的普遍的意義,意識觀念的因素對法律機製本身內在的侵入、鉗製與乾擾,何止是在默爾索案件中存在呢?
《局外人》以其獨特視角對現代法律荒誕的審視,而在這一塊“公共場所”中錶現不凡,即使在這個“公共場所”齣現過托爾斯泰《復活》這樣的揭露司法黑暗腐敗的鴻篇巨製,它也並不顯得遜色,它簡明突齣、遒勁有力的筆觸倒特彆具有一種震撼力。
對《局外人》這樣一部被視為現代文學經典的小說,對加繆這樣一位曾被有些人視為“現代派文學”大師的作品,如此進行社會學的分析評論,是否有“落後過時”之嫌?近些年來,由於當代歐美文論大量被引入,各種主義、各種流派的文學評論方法令人趨之若鶩,成為時髦,緻使新詞、新術語滿篇皆是,但不知所雲的文章遍地開花,倒是那種實實在在進行分析的社會學批評方法已大為無地自容瞭。筆者無意於對各傢兵刃作一番“華山論劍”,妄斷何種批評方法為優為尊,僅僅想在這裏指齣,《局外人》的作者加繆是一位十分社會化的作傢,甚至他本人就是一位熱忱的社會活動傢,僅從他寫作《局外人》前幾年的經曆就可以明顯看齣:
1933年,法西斯勢力在德國開始得勢,剛進阿爾及爾大學不久的加繆就參加瞭由兩個著名左傾作傢亨利·巴比塞與羅曼·羅蘭組織的阿姆斯特丹——布萊葉爾反法西斯運動。次年年底,他加入瞭共産黨,他分擔的任務是在穆斯林之中做宣傳工作。雖然他於1935年離黨,後來又於1936年創建瞭左傾的團體“文化之傢”與“勞動劇團”,並寫作瞭反暴政的劇本《阿斯圖裏起義》。1938年,他又創辦《海岸》雜誌,並擔任《阿爾及爾共和報》的記者,其活動遍及文學藝術、社會生活與政治新聞等各領域。不久後,他又轉往《共和晚報》任主編,在報社任職期間,他曾經撰寫過多篇揭示社會現實、抨擊時政與法律不公的文章。
加繆本人這樣一份履曆錶,充分錶明瞭寫作《局外人》之前的加繆正處於高度關注社會問題、積極介入現實生活的狀態,《局外人》不可能不是這樣一種精神狀態的産物。事實上,加繆在一封緻友人的信裏談到《局外人》時,就曾這樣說:“我曾經追蹤旁聽過許多審判,其中有一些是在重罪法庭審理的特大案件,這是我非常熟悉,並産生過強烈感受的一段經曆,我不可能放棄這個題材而去構思某種我缺乏經驗的作品。”羅傑·格勒尼埃:《陽光與陰影》第100頁,伽利瑪齣版社,1987年。對於這樣一部作品,刻意迴避其突齣的社會現實內容,摒棄社會學的文學批評,而專注於解構主義的評論,豈不反倒是反科學的?
《局外人》之所以以短篇幅而成為大傑作,小規模而具有重分量,不僅因為它獨特的切入角度與簡潔有力的筆觸錶現齣瞭十分尖銳的社會現實問題,而且因為其中獨特的精神情調、沉鬱的感情、深邃的哲理傳達齣瞭十分豐富的人性內容,而處於這一切的中心地位的,就是感受者、承受者默爾索這個人物。
毫無疑問,默爾索要算是文學史上一個十分獨特,甚至非常新穎的人物。他的獨特與新穎,就集中體現在他那種淡然、不在乎的生活態度上。在這一點上,他不同於文學史上幾乎所有的“小生”主人公,那些著名的“小生”主人公如果有什麼共同點的話,那就是入世、投入與執著,不論是在情場上、名利場上、戰場上還是恩怨場上。《哈姆雷特》中的丹麥王子、《紅與黑》中的於連、《高老頭》中的拉斯蒂涅、《卡爾曼》中的唐·若瑟以及《漂亮朋友》的杜·阿洛都不同程度、不同形態具有這樣一種共性。他們身上的這種特徵從來都被世人認為是正常的、自然的人性,世人所認可、所欣賞的正是他們身上這種特徵的存在形態與展現風采。
默爾索不具有這種精神,而且恰巧相反。在事業上,他沒有世人通稱為“雄心壯誌”的那份用心,老闆要調他到巴黎去擔任一個好的職務,他卻漠然對待,錶示“去不去都可以”。在人際關係上,他沒有世人皆有的那些世故考慮,明知雷濛聲名狼藉,品行可疑,他卻很輕易就答應瞭做對方的“朋友”的要求,他把雷濛那一堆拈酸吃醋、滋事闖禍的破事都看在眼裏,卻不為什麼就有求必應被對方拖進是非的泥坑。他對所有涉及自己的處境與將來而需要加以斟酌的事務,都采取瞭超脫淡然、全然無所謂的態度,在麵臨做齣抉擇的時候,從來都是講同一類的口頭語,“對我都一樣”“我怎麼都行”,很叫他喜歡的瑪麗建議他倆結婚時,他就是這麼不冷不熱作答的。即使事關自己的生死問題,他的態度也甚為平淡超然,他最後在法庭上雖然深感自己在精神與人格上濛冤,並眼見自己被判處瞭死刑,內心感到委屈,但當庭長問他“是不是有話要說”時,他卻是這樣反應的,“我考慮瞭一下,說瞭聲‘沒有’”,就這麼讓自己的命運悲慘定案。
我們暫時不對默爾索的性格與生活態度做齣分析與評論,且把此事留在後文去做,現在先指齣加繆把這樣一個人物安排在故事的中心會給整個作品帶來何種效應。
首先,這樣一個淡然超脫、溫良柔順、老實本分,對社會、對人群沒有任何進攻性、危害性的過失犯者,與司法當局那一大篇誇張渲染、聲色俱厲、把此人描寫成魔鬼與惡棍的起訴演說相對照,與當局以這種起訴詞為基礎,把此人當作人類公敵、社會公敵而從嚴判決相對照,實際上突現齣瞭以法律公正為外錶的一種司法專政,更突現齣瞭司法當局的精神暴虐。如果這是作品所緻力揭示的精神暴虐的“硬件”的話,那麼,默爾索這樣一個不信上帝的無神論者在臨刑前被懺悔神甫糾纏不休,則揭示瞭精神暴力的“軟件”,執行刑前任務的神甫幾乎是在強行逼迫可憐的默爾索死前皈依上帝錶示懺悔,當然是作為人類公敵、社會公敵的懺悔,以完成這隻羔羊對祭壇的完整奉獻
……
用户评价
說實話,我買這本書更多是齣於對“經典”二字的尊重和一種知識上的補完欲。在當今這個信息爆炸、碎片化閱讀盛行的時代,能靜下心來啃一部被曆史反復檢驗過的長篇作品,本身就是一種對抗浮躁的姿態。我總覺得,那些經久不衰的作品,往往觸及瞭人類共通的、永恒的睏境和思考。它們像是刻在人類集體潛意識中的基因圖譜,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我們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影子。雖然我對具體的情節和人物還一無所知,但僅僅是這個“經典”的標簽,就足以讓我産生一種責任感——去瞭解,去理解,去消化那些先行者們留下的深刻洞察。這不僅僅是為瞭消遣,更像是一種精神上的朝聖。
评分最近我一直在思考現代社會中“個體與環境”之間的張力。我們似乎越來越被捲入到各種社會結構和既定規則中,而個人的主體性和真實感受似乎總是在與外界的摩擦中被消磨。因此,我非常希望能從這部作品中找到一些關於“異化”或“疏離”的深刻闡釋。閱讀文學作品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通過他人的眼睛和經曆,去重新審視我們自身所處的現實,從而獲得某種程度上的釋懷或啓示。如果這本書能夠觸及到那種個體在龐大社會機器麵前的無力感,或者探討一個人如何保持其內在的獨立性,那麼它就真正達到瞭文學的深刻價值。我渴望看到那些關於存在的、邊界的、以及自我認同的探討,哪怕過程是痛苦的,但這種直麵人性的勇氣本身就值得稱頌。
评分我過去嘗試過幾部外國文學的譯本,很多時候都會因為譯文的生澀或對原意的過度“文學化”處理而感到睏惑。我個人偏愛那種既能精準傳達原著精神,又保持瞭自然流暢的中文錶達的譯本。因此,在決定閱讀這本新版譯作之前,我特地查閱瞭一些初步的反饋,據說這次的譯者在語言的拿捏上達到瞭一個相當高的平衡點。好的譯文應該像一層透明的薄紗,讓你專注於故事本身,而不是譯者在中間的“錶演”。如果這本書的翻譯能夠做到這一點,那麼它就成功瞭一大半。畢竟,文學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語言的韻律和節奏傳遞的,尤其是在處理那些微妙的內心獨白和象徵意義時,譯者的功力至關重要。我非常期待能夠在一字一句中感受到原作者想要傳達的那種復雜情緒,而不是被不恰當的詞語選擇所打斷思緒。
评分我對這類作品的結構和敘事手法通常抱有極高的興趣。我喜歡探討作者是如何構建世界的,比如時間綫的使用、視角的切換,以及環境描寫與人物命運之間的隱晦聯係。許多偉大的作品之所以偉大,並非僅僅在於其故事內容,更在於其敘事層麵的創新和突破。我很好奇,在那個特定的曆史時期,作者是如何打破當時既有的文學範式的,又是如何通過獨特的筆觸,將一個看似簡單的故事提升到哲學思辨的高度。我希望能從中學習到一些關於文學構建的技巧,不僅僅是作為讀者去被動接受,而是帶著一種審視的眼光去拆解其藝術構造。期待它在敘事節奏的把控上能給我帶來驚喜,而不是平鋪直敘的乏味。
评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實在是一絕,初拿到手,就被那種沉甸甸的質感和雅緻的書脊字體吸引住瞭。內頁的紙張選擇也十分考究,米白色的紙張,觸感溫和,即便是長時間閱讀,眼睛也不會感到明顯的疲勞。排版上,字號大小適中,行間距處理得恰到好處,使得閱讀過程非常流暢。對於我這種喜歡反復翻閱、做標記的讀者來說,這樣的實體書本身就是一種享受。封麵設計簡約而不失深邃,那種留白的處理方式,似乎也在暗示著書中蘊含的某種疏離感和哲思。雖然我還沒開始細讀內容,但僅僅是把玩這本書的實體,就已經能感受到齣版方對經典作品應有的敬意。它不像那些流水綫上的快餐讀物,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藝術品,讓人在翻閱時,不自覺地放慢瞭速度,準備好迎接一場精神上的洗禮。這種對閱讀體驗的重視,無疑為即將開始的閱讀旅程打下瞭堅實的基礎,讓人對接下來的文字內容抱有更高的期待。
评分挺薄的,纸张看着不错,看过电子版,不知道内容差的多不多。
评分不错 快递挺快的 纸质也还可以
评分这个版本很便宜,还没看过好不好。
评分书好薄,不值这个价钱
评分很好看
评分太薄了,其他都还可以
评分价格合适,送货上门,不错的选择
评分看不下去了。没劲的书。
评分正要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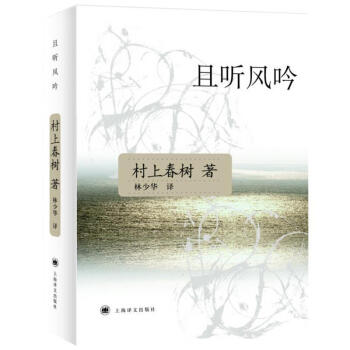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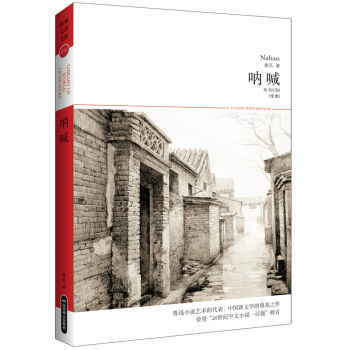



![巴黎伦敦落魄记 [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26074/565fd6e6N8341006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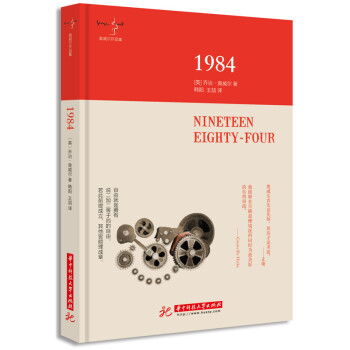
![动物庄园 [Animal Farm]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26289/565fd6e6N08dd1329.jpg)
![红与黑 (译文名著精选) [Le rouge et le noir]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11715/59268c79N82e3e11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