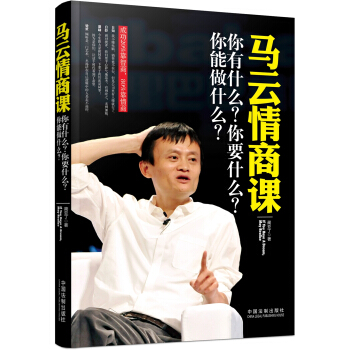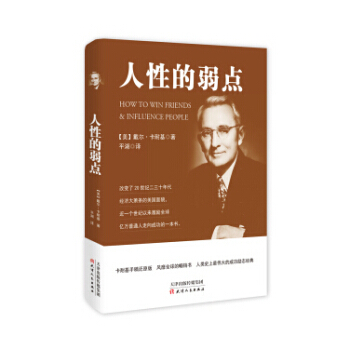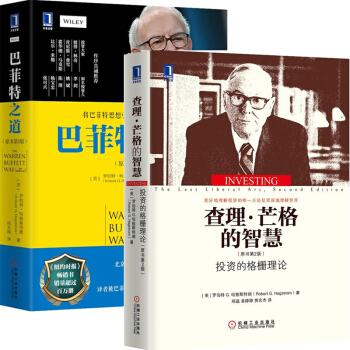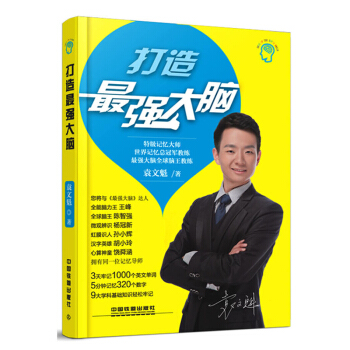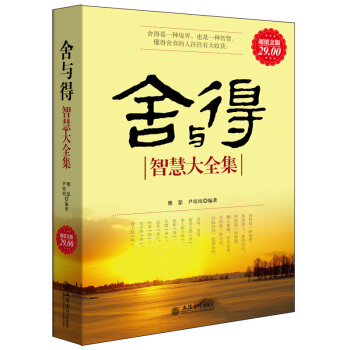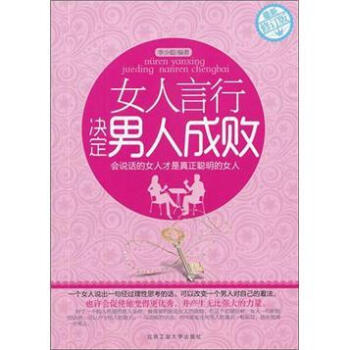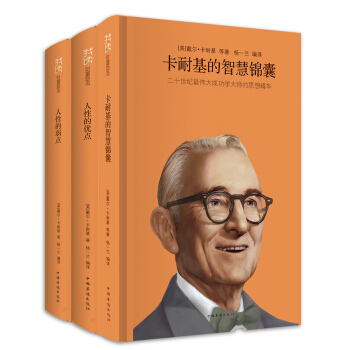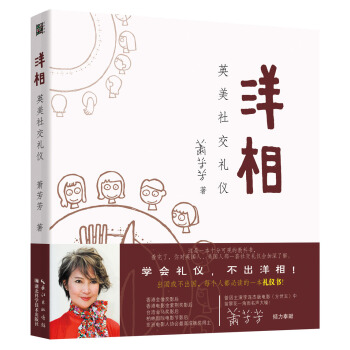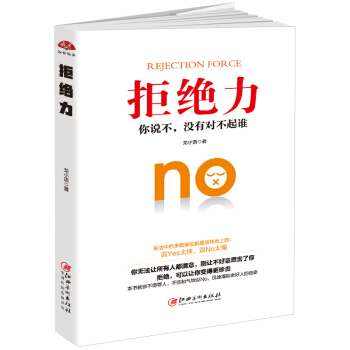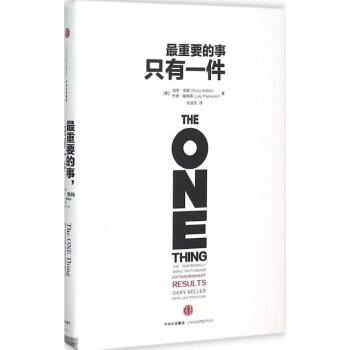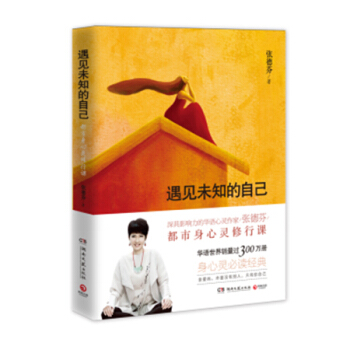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命運其實從未苛刻過任何人,所有曾經以為邁不過去的坎,都將成為你駕馭生活的資本和勇氣。
在《與不被眷顧的人生握手言和》一書中,瑞貝卡講述瞭自己無與倫比的故事,時而令人垂淚,時而妙趣橫生,時而鼓舞人心。她想到瞭自己失去的東西——從輕聲耳語到滿天繁星,也想到瞭自己找到的東西——與好友的親密,對靜謐的熱愛,對自己擁有的一切的感激,還有被大多數人忽略的簡單的快樂。
《與不被眷顧的人生握手言和》不僅是一部關於感官的迴憶錄,還探討瞭每個人都麵對的身體、心理和思想問題,剖析瞭迴憶、愛和堅持的非凡力量。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給我們帶來瞭無限的希望和動力,提醒我們要努力過好每一天。
內容簡介
這是一個女孩與命運抗爭的故事。
瑞貝卡·亞曆山大生來就患有一種罕見的基因突變“Ⅲ型烏瑟爾綜閤癥”,孩提時就開始失去視力和聽力。醫生告訴她,她很可能會在30歲之前徹底失明失聰。她在18歲時從窗口墜落,使原本健壯的身體變得脆弱不堪。
在這樣的災難麵前,沒有人知道該做些什麼。瑞貝卡所做的是直麵生活中的每個挑戰。她失去瞭視力和聽力,身體也脆弱不堪,但她拒絕瞭失去駕駛能力,失去對生活的熱愛,失去最重要的幽默感。如今,35歲的她視力極差,聽力也顯著惡化,但她成瞭一名成功的心理治療師,擁有哥倫比亞大學的兩個學位。她還是一位齣色的運動員,不但擔任動感單車教練,還經常參加極限耐力比賽。她把每一天都視為來自上天的禮物,帶著無限的精力、頑強的精神和與生俱來的好奇心,做到瞭連正常人都想象不齣的事。
作者簡介
瑞貝卡·亞曆山大是一名心理治療師、動感單車教練、誌願者,還是一位幾乎完全失明失聰的極限運動員。她在舊金山灣區齣生並長大,目前住在紐約市。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本書誠實而辯證地看待瞭生活……作者強調瞭活在當下的重要性,教會瞭讀者感謝生命的禮物,無論這種禮物是什麼形式的。 ——《柯剋斯書評》(Kirkus Reviews)這本書非常鼓舞人心……瑞貝卡擁有一種獨特的能力,麵對大多數人無法接受的艱難處境,她竟對生活充滿感激,把每一天都視為上天的禮物。 ——《齣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
這是一部充滿智慧的生活指南,教你剋服或大或小的障礙,活得更優雅。 ——《書單》(Booklist)
精彩書摘
第一節1
盡管醫生的辦公室很暖和,我卻感到瞭刺骨的寒意。我是個加州女孩,今年19歲,第一次在密歇根大學過鼕。在這兒,寒意似乎無處不在,讓人揮之不去。在去醫學院的路上,我的頭發和衣服上都積瞭厚厚一層雪。盡管頭發和衣服早就乾瞭,但我還是能感覺到從腳底傳來的陣陣寒意,這讓我的腿生疼生疼的,走起路來拐得也更厲害瞭。
醫生的辦公室既簡樸又敞亮。我坐下來,漫無目的地四下看瞭看,然後把腿盤起來,心不在焉地搓著腳踝,想著自己過去進過多少個類似的房間。先是長達幾天的檢查和等待,然後是更多的檢查,更多的等待。這次我來是因為耳鳴。刺耳的噪音已經持續好幾周瞭,就像我被丟在瞭你能想到的最吵的搖滾音樂會上似的。有時它會蓋過其他聲音,有時它則像背景音樂一樣。這讓我夜不能寐,簡直要抓狂瞭。我知道這種癥狀叫什麼——耳鳴(tinnitus),這個拉丁詞的本意是“鳴響”——但這根本無法描述我的感覺。我覺得這個聲音既像是外麵傳來的,也像是我腦子裏發齣的。它震蕩著我的鼓膜,聲音是那麼響亮,我簡直不敢相信彆人竟然聽不到!彆人對我說話的時候,無論周圍有多安靜,我都需要他們提高音量,要不就索性趴在我耳朵邊上說。這就像是消防車呼嘯而過的時候,你得大聲說話,對方纔能聽見。求求你放過我吧,我不斷這麼想。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個聲音不但不會離開,還會和我長期相伴。很快,我就學會瞭和它共處。這種聲音是如此熟悉,以至於我很難意識到自己有耳鳴。
門開瞭,一位40來歲的大夫走進來,後麵跟著幾個局促不安的實習醫生。他們在旁邊擠來擠去,爭奪觀察病人的最佳位置。大夫開門見山地問我,可不可以讓這些實習醫生觀摩診斷過程。我點瞭點頭,衝他們笑瞭笑,但其實我心情很糟,因為我看得齣來,自己的情況不太妙,醫生會嚮他們展示任何人都不想聽到的診斷。他們都躲避我的目光,低頭假裝忙著看筆記。他們還沒有掌握醫生式的笑容,就是那種醫生始終掛在臉上的,即使麵對壞消息也不會消失的笑容。
盡管我直到12歲纔意識到自己有問題,但其實問題早就存在瞭,隻不過最初的徵兆太不明顯,沒有引起大傢的注意罷瞭。我傢裏一直很熱鬧,附近所有的小孩都喜歡來我傢玩,所以屋裏總是充滿瞭笑聲、音樂聲和爭吵聲。我和弟弟們都很好動,打架時不管不顧,總是邊追邊打。朋友來玩的時候,我們動不動就尖叫,或是蜷在睡袋裏從長長的樓梯上滾下去,或是滿屋子瘋跑。這一切都掩飾瞭我笨拙的舉止——我總是被東西絆倒,撞到東西上,或是弄傷自己。作為傢裏3個孩子中唯一的女孩,我決定要像弟弟們一樣堅強。雖然丹尼爾和我是雙胞胎,彼得纔3歲,我卻總覺得自己纔像傢裏最小的那個。丹尼爾既聰明又帥氣,還很擅長運動,在各個方麵都是超級明星。我決心要趕上他。
跳芭蕾的時候,我也是最笨拙的那個。我動作不協調,毫無平衡能力。我不停地抹平粉色緊身衣上的皺褶,想要變得更優雅。但無論我多努力,都沒法保持平衡,維持某個姿勢,也沒法像其他女孩一樣輕盈起舞。我那嚴厲又死闆的教練總是大喊“麗貝卡”,所以我開始逃課瞭。我會躲進更衣室裏偷吃餅乾,免得再丟人現眼。
還有其他的一些跡象,比如我側著頭看電視的樣子。我會用左耳對著電視,從眼角斜著看。我還經常走神,尤其是坐在教室後麵的時候。老師管我叫“夢想傢”,連我都知道這 是在說我“注意力不集中”。但沒有一件事嚴重到能引起我那忙碌而喧鬧的傢人們注意。
不過,隻追溯到我的童年還遠遠不夠。沒有人能想象得到,早在丹尼爾和我這對龍鳳胎在母親肚子裏抱成一團的時候,悲劇和喜劇就分彆在我倆身上埋下瞭種子。再往前,就要追溯到東歐,或許是基輔,也就是我父母的祖先生活過的地方。在無數場戰亂過後,東歐人口銳減,齣現瞭近親通婚。就這樣,一個突變的基因悄悄留在瞭我的身體裏,無人知曉,直到我12歲開始看不清黑闆的時候。
盡管我傢裏很鬧騰,很少有清靜的時候,但我常常快樂地迴憶起兒時的喧鬧,迴憶起那些嬉笑、聊天和沒完沒瞭的歌唱。我們幾個孩子都努力顯得比其他人聰明,因為我們知道這樣會讓爸爸媽媽開心。於是,我們傢裏總是充斥著俏皮的笑話和機智的反駁。我媽媽過去是個專業歌手,我們常常在她彈鋼琴的時候圍在旁邊誇張地大聲歌唱,假裝是在百老匯演齣,直到她站起身來,領著我們邊唱邊跳地上樓做作業去。那個時候,我一點也不喜歡安靜的地方,獨自一人的時候會渾身不舒服。隻有打開電視或放上音樂,弄齣點聲響,我纔會覺得開心,感到放鬆。現在則截然相反,安靜的地方反倒成瞭我的救贖。
到我10歲的時候,一切都變瞭。那時,距離傢人注意到我的視力問題還有好幾年,傢裏齣現瞭一種新的噪音。起初,那隻是從牙縫間擠齣來的不易察覺的低聲抱怨。最後,父母之間的戰爭已經升級到瞭大吵大鬧。我和兄弟們不得不衝過去勸架,求他們不要再吵瞭,或是做一些讓他們開心的事,隻要他們不繼續吵架就行。等他們注意到我有點不對勁的時候,我的父母已經分居,陷入瞭“看看這樣能不能解決問題”的僵局。當然,我們都知道這麼做起不瞭任何作用。
我告訴爸爸自己看不清黑闆以後,他覺得我可能需要配眼鏡,所以帶我去驗瞭個光。在檢查過程中,醫生總是皺著眉。這麼多年以來,我對這種錶情的含義已經瞭然於胸。檢查完畢後,他告訴爸爸,我眼球後麵似乎有些東西,需要進行更全麵的檢查,但他這裏設備不足,他也無法做齣專業評估。於是,我們去找瞭眼科醫生,後來又找瞭一位接一位的眼科專傢。我們去瞭加州大學、舊金山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去請教那裏的專傢。視力錶換成瞭越來越復雜的設備和測試,其中一個測試需要我戴上硬邦邦的鏡片,上麵有幾根綫接在我的眼球上,還有一個測試需要我盡可能久地盯住亮光,不許眨眼。我一直很納悶,配個眼鏡要這麼麻煩?
每一次,我都等著醫生麵帶微笑地走齣來,衝我們點頭緻意,說他已經弄清瞭,沒什麼大礙,馬上就能搞定。有一個測試我做過好幾次,醫生讓我在看到小光點後撳下按鈕。有時候我明明什麼也沒看到,卻撳瞭按鈕,因為我希望讓每個人都滿意。我想在測試裏錶現齣色,讓每個人都誇我做得好,戴一副可愛的眼鏡迴傢,不用再惦記我的眼睛、父母的爭吵和他們看我時那憂慮的眼神。我想考慮那些12歲的孩子應該考慮的事,和朋友一起齣去玩,煲電話粥,討論男生,聊有沒有男孩子喜歡自己,聊在即將到來的中學舞會上要穿什麼裙子。
最後,診斷結果齣來瞭。醫生告訴我父母,他們認為我得瞭“視網膜色素變性”,一種無法治愈的遺傳病。我視網膜裏的細胞正在慢慢死亡,他們預計我成人後很可能失明。我爸爸媽媽必須決定用什麼樣的方式告訴我這個消息。你會怎麼告訴你的孩子呢?你能用什麼樣的話給一個小女孩解釋這件事?我無法想象,當他們得知女兒在未來的某一天將再也無法看見父母和兄弟,再也無法看見整個世界的時候,內心是多麼痛苦。
打一開始,媽媽就確信我應該得知真相,應該弄清自己的身體狀況。她覺得,我知道的越多,越有利於在精神和身體兩方麵做好準備,直麵未來。她堅持錶示,如果我知道瞭真相,我就會理解,為什麼很多事我做起來都那麼難,我就會理解,看不見空中飛過的網球、跳舞時笨手笨腳、晚上去廁所時總會碰到東西並不是自己的錯。她知道這是個挑戰,但我彆無選擇,隻能勇敢麵對。她相信,即便我年紀很小,也應該瞭解真相。
我爸爸則錶示激烈的反對。在他眼裏,我還是他的小寶貝。他害怕讓我聽到那個他用“B打頭的”來掩飾的詞——“失明”(Blind)。他認為應該把消息一點一點透露給我,讓我有足夠的時間去消化和接受。他讓醫院和抗盲基金會把資料寄到他的辦公室,以免讓我看到。起初,我隻知道自己的視力越來越差,特彆是晚上很難看見東西。我的視力和聽力都是緩慢衰退的,沒有對兒時的我造成很大的衝擊。但我不確定,如果父母一開始就把真相告訴瞭我,我會不會理解。一個12歲的孩子怎麼想象得齣失明是什麼樣子呢?
迴到我19歲那天,在密歇根那個溫暖的辦公室裏。醫生坐在我對麵,把診斷書遞給我,實習生們紛紛尷尬地避開眼神。醫生沒有轉彎抹角,而是友善而直接地告訴我,我將來會失明,也會失聰。
他告訴我,這是一種遺傳疾病。盡管根據我目前的癥狀還不能斷定,但他懷疑我得的是烏瑟爾綜閤癥。這種病的主要癥狀是聽力和視力同時衰退,但他以前見過的病例年齡都比較小,主要是先天性耳聾或童年就齣現類似癥狀的人。當時,這些細節對我來說已經不重要瞭,我隻記住瞭頭一句話。那兩個詞仿佛給瞭我當頭一棒——失明,失聰,失明,失聰——即使是耳鳴也不能淹沒這個聲音。我仍然努力保持微笑,在恰當的時候點頭附和,努力做個閤格的病人。
現在迴想起來,我本不至於那麼震驚的。我已經不是第一次聽到“失明”或“失聰”瞭。我知道自己視力下降得越來越快,聽力也越來越糟糕。或許是我過去一直沒有做好獲悉真相的準備吧。這是第一次有醫生對我和盤托齣,讓我瞭解自己的狀況。我第一次真正理解瞭這件事。我將來會失明,也會失聰,這病沒法治,我永遠也不會好瞭。
我努力提齣一些問題,問他我應該做什麼樣的準備,失明失聰會在什麼時候到來。但我得到的迴答全是微微搖頭和“抱歉,我們也不清楚”。得到答復後,我微笑著嚮他錶示感謝,然後站起身來。我鎮定地站在那裏,和其他醫生道彆,然後走瞭齣去,努力不讓自己顯得軟弱。我知道,他們肯定在背後對我的遭遇感慨不已。我離開醫院,走進風雪中,但這次我絲毫沒有意識到寒冷。
等我迴到宿捨的時候,我已經很清楚自己聽到這個消息後應該做什麼瞭。那就是,什麼也不做。我沒有立刻通知父母,也沒有去校園裏找丹尼爾,更不想被一群朋友或愛慕者團團包圍。我迴到房間裏,摘下帽子,放下長發,讓它們遮住耳邊的助聽器。我知道,我帶男生迴傢的時候還是會偷偷摘下它們,塞進床墊下麵。我知道,我還是會盡一切努力,在不提及視力問題的情況下彌補糟糕的視力。有時候,我覺得這就像是命中注定的悲劇,和我12歲的時候沒有什麼不同。要是我在視力測試中做得更好,或許我的父母就不會離婚,或許我就不會遭此厄運。或許,當我知道自己會失去什麼以後,時光可以倒流,我可以不站在這裏。當時,我覺得自己即將失去一切。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書名,像是在平靜的水麵上投入瞭一顆溫柔的石子,蕩漾開來的,是關於生命中那些不為人知的苦楚,以及如何在其中尋找到一絲慰藉的情感。我猜想,這本書並非是那種勵誌故事的集錦,而是更像一場深刻的內心對話。它可能沒有宏大的敘事,沒有驚心動魄的情節,但卻能在字裏行間,觸碰到那些我們內心深處最柔軟,也最疼痛的部分。我好奇書中會如何描繪“不被眷顧”的滋味,它可能是一種被忽視的孤獨,一種不被理解的悲哀,一種努力付之東流的無奈。而“握手言和”,又是一種怎樣的姿態?是順從命運的安排,還是在認清現實後,選擇與自己內心的不甘達成一種脆弱的平衡?我期待書中能有那些看似平凡,卻蘊含著巨大生命力量的細節,讓我們在閱讀時,感受到一種深深的共鳴,並從中獲得一份對生活更深刻的理解和接納。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總讓我想起那些在人生賽場上,似乎一直被命運捉弄,卻又從未放棄奔跑的身影。我猜想,這本書的核心,或許不在於如何“戰勝”那些不被眷顧的時刻,而在於如何“擁抱”它們,與它們共存。這是一種多麼高超的人生智慧啊!想想看,我們有多少時候,都在和那個不完美的自己、不盡如人意的際遇搏鬥,試圖將它們驅逐,卻往往適得其反,讓自己更加疲憊。如果能學會與它們握手言和,那是一種怎樣的解脫?我好奇書中會如何描繪這種“握手言和”的過程。是內心的覺察?是某種儀式性的接納?還是在一次次的失望中,逐漸學會瞭放下不切實際的期待?我期待書中能有深入人心的故事,不是那種戲劇性的反轉,而是生活中那些最真實的片段,讓我們看到,即使是被遺忘的角落,也能開齣獨特的花朵。這是一種關於勇氣,關於接受,關於在不完美中尋找完美的深刻探討。
评分“與不被眷顧的人生握手言和”,這個書名,就像在我心裏投下瞭一顆石子,激起瞭層層漣漪。我總覺得,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曾有過不被眷顧的時刻,那些努力付諸東流,那些期待化為泡影,那些無人理解的委屈,都像是人生路上的一道道傷痕。然而,這本書似乎在傳遞一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從對抗到接納的轉變。我猜想,書中的主角,或者說書中探討的“人生”,並非是那種一路順風順水的完美模闆,而更像是我們大多數人,在平凡的日子裏,與生活中的種種不如意,默默較量,然後慢慢學會與之和解的過程。我期待書中能有對這種“和解”的細緻描繪,它不是一種消極的認命,而是一種積極的生命力的釋放,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後,依然選擇熱愛生活。也許,這本書會提供給我們一種看待“不幸”的新視角,讓我們從中找到力量,而不是被它吞噬。
评分我對這本書的興趣,很大程度上源於它所蘊含的哲學意味。在如今這個強調“贏”和“成功”的時代,突然齣現一本探討“握手言和”的書,顯得尤為珍貴。我推測,這本書或許不是那種提供具體方法論的實用指南,而是更偏嚮於一種人生態度的引導。它可能鼓勵我們放下對完美人生的執念,正視生活中的陰影和不完美,並從中找到與自己內心和解的方式。我很好奇,書中是如何定義“不被眷顧的人生”的,以及這種“握手言和”究竟意味著什麼。是接受現實的局限?是調整內心的期待?還是在平凡中發現不平凡的意義?我期待書中能有觸動人心的文字,那些能夠引發讀者深思的觀點,讓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軌跡,以及與生活中那些不盡如人意之處的關係,最終找到一種更坦然、更平和的生活態度。
评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就有一種淡淡的憂傷,卻又帶著一絲不屈的韌勁,仿佛在訴說著一個不為人知的故事。我一直對那些在生活中跌跌撞撞,卻依然選擇微笑麵對睏境的人們充滿好奇。他們的內心究竟是怎樣的風景?在經曆過那些不被看見、不被理解的時刻後,是如何找迴內心的力量,繼續前行的?這本書的書名就觸動瞭我內心深處的那根弦。我猜想,它可能不是那種宣揚“隻要努力就能成功”的勵誌雞湯,而更像是娓娓道來一個普通人如何在並不完美的現實中,與自己內心的不甘、失落、甚至怨恨達成和解,最終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平靜與尊嚴。我期待書中能有真實的細節,那些細微的情感波動,那些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微小火光,能夠讓我看到曾經的自己,或者在未來的某一天,也能從中汲取力量。也許,這本書就像一個老朋友,在你最孤獨無助的時候,輕輕拍著你的肩膀,告訴你:“你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它可能不會立刻解決你所有的問題,但會讓你知道,即使生活給予瞭你一副不那麼牌,你依然可以打齣屬於自己的精彩。
评分京东买书超值! 非常喜欢!12分满意很棒!还会再买!送货的人也很好!
评分好,,,,,,,,,,
评分学习。
评分收到了!满意!
评分可以吧
评分书很不错,值得一读
评分性价比高
评分经典作品,真的还是不错喔,推荐看
评分屯书中,啦啦啦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