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宗教報告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圖書介紹

发表于2025-03-06
類似圖書 點擊查看全場最低價
齣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
ISBN:9787509782910
版次:1
商品編碼:11825974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5-11-01
頁數:248
字數:184000
正文語種:中文
澳門宗教報告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pdf 下載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相關圖書
澳門宗教報告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pdf 下載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澳門宗教報告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本書是2013年10月在澳門召開的“宗教與可持續社區”學術研討會的成果文集。書中展示的是宗教研究所發生的“範式的轉變”,即更多注意宗教在現代社會的意義與作用。書中特彆關注巴哈伊教的社區建設經驗。在各種宗教與可持續社區關係研究中,巴哈伊信仰的可持續社區理念值得我們特彆關注,其在全世界所進行的社會實踐所積纍的經驗,也值得總結和藉鑒。作者簡介
邱永輝,女,1961年4月生,籍貫四川。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當代宗教研究室主任。“當代宗教發展態勢研究”創新工程項目首席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南亞學會副會長。長期從事當代宗教和印度宗教文化研究。1978年2月考入四川大學曆史係,1982年初畢業,獲曆史學學士學位。1982年初開始世界地區(國彆)史專業研究生階段學習,主攻方嚮為印度史,至1984年底畢業,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史學碩士學位。從1984年底至2001年7月,就職於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研究範圍包括當代印度政治、社會和宗教文化。其間,曾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人類學社會學係和印度尼赫魯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中心進修訪問。1986年12月始任助理研究員,1993年晉升為副研究員。2000年7月晉升為研究員,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南亞基地政治社會研究方嚮學術帶頭人。2001年9月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陳進國,男,1970年生,福建永春人。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1989-1996年廈門大學哲學係哲學學士、碩士,1998-2002年廈門大學曆史係博士,2002-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後。1996-2002年廈門大學颱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閤著《透視中國東南:文化經濟的整閤研究》(2002),專著《信仰、儀式與鄉土社會:風水的曆史人類學探索》(2005)、《隔岸觀火:泛颱海區域的信仰生活》(2008)等。《宗教人類學》輯刊主編。
目錄
中國宗教團體及其社會管理 (代序)【卓新平】/1導 論 澳門的宗教治理與宗教生態【陳進國】/1
上編 澳門宗教團體的治理——法律架構與治理實踐
澳門基本法與宗教信仰自由【駱偉建 江 華】/15
澳門宗教團體的管治架構初探【鄭慶雲】/26
澳門佛教團體的弘法活動和管理模式【賈晉華 白照傑】/35
“石破花開”:澳門基督新教教會的治理與發展【遊偉業】/49
天主教修會的革新: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對修會的訓道及實踐【葉傢祺 陳玉葉】/65
培養宗教團體的治理能力——澳門巴哈伊的若乾經驗【江紹發】/81
探討澳門巴哈伊團體廉正理念【陸 堅】/101
下編 澳門宗教調研報告——新興宗教與民間信仰
巴哈伊教的慈善理念及其在澳門的實踐
——以“巴迪基金會”為個案的研究報告【邱永輝】/123
一貫道在澳門的傳播與發展——以發一崇德的活動為例【陳進國】/173
澳門地區民間信仰管窺【葉 濤】/189
後 記/232
前言/序言
中國宗教團體及其社會管理 (代序)卓新平
卓新平,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所長,中國宗教學會會長。
探究宗教團體的治理,重要且必要的關聯就是分析、研究中國宗教團體發展的曆史與現狀,以及其與中國社會和政治體製的內在關係或關聯。在中國社會處境及文化氛圍中,人們很容易發現中國宗教團體在組織建構上的特色,以及其社會存在和社會作用的特點。然而,這些顯而易見、與世界其他國傢尤其是西方國傢宗教團體的不同,卻未曾得到係統、認真的梳理和解讀。其界說之難不僅在於中國宗教團體的構建本身,更在於其與中國社會政體的關係。這種政體本身,以及政教關係的與眾不同,使我們對中國宗教團體的社會管理問題不能簡單與他者類比,而必須找齣中國自己的特點,以此說明中國獨有的特色。
一 中國的宗教團體與中國的政教關係
對於宗教團體的治理問題,取決於我們對宗教本質及其社會存在與作用的基本認知和評價。也就是說,宗教團體的管理隻是手段,它勢必反映這種治理的目的,即究竟是要推動宗教的發展,還是要限製宗教的存在;是要擴大宗教的社會影響,還是想減少、削弱這種影響;是要對宗教加以思想、政治、社會、法律層麵的掌控,還是使宗教更加自由、自然地生存與發展。所以說,宗教團體的治理問題是“工具理性”的問題,它反映且也必然服從於關涉宗教的“價值理性”問題。在當代中國,憲法保障瞭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各種宗教在改革開放30多年來已經獲得巨大發展,但是,尚有幾個最為根本的問題仍未解決,人們對之分歧較大、解說眾多,很難達成共識。
其問題之一即是對宗教的評價問題。這種對宗教的價值判斷、基本定義至關重要,目前中國大陸還未能將以基本法、上位法的方式來解決宗教立法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其根本原因就是對“怎樣看宗教”沒有達成共識,故而影響到對宗教“怎麼辦”的具體立法和政策管理等舉措,人們對這種“立法”究竟是“保護宗教”還是“限製宗教”認識不清、分歧頗大,所以立法機構隻能對宗教立法問題加以暫時“懸置”,其結果是影響到我們從根本上思考、討論、實施如何“依法管理宗教”的問題。人們由此提齣瞭是否有“法”可“依”,“法”是什麼性質之法,以及如何對之實施等疑問,需要我們進一步澄清和說明。
其問題之二即“宗教信仰自由”與“宗教自由”有無區彆及如何關聯。中國大陸社會談得較多的是“宗教信仰自由”,而對“宗教自由”的錶述則頗為謹慎。個中原因在於“宗教信仰”主要是在“思想”層麵,任何社會製度和管理舉措很難從根本上真正限製人的“思想自由”,也就是說,這些製度和舉措很容易管到人們之“行”和“言”,卻很難限製其之“思”和“想”。而“宗教自由”則不僅包括其思想信仰層麵,也包括其社會行動層麵。所以,不少人認為“宗教信仰”有著絕對的思想自由,而宗教包括的社會組織團體及其言行則隻有相對的自由,因為其社會機構及言行有著社會製度、秩序、法律和政策等製約,並不是絕對自由所能錶達的。其中“宗教自由”的空間及限度,則依賴於相關宗教的社會存在及其公共秩序對它的要求。這裏既涉及宗教可能獲得的自由,也涉及宗教與國傢法律和社會規範的關聯及由此而必須具有的社會治理和國傢法律的製約。
其問題之三即政府如何管理宗教,如何處理好多層麵的政教關係。人們談到政教關係時一般會論及“政教閤一”“政教分離”“政教協約”這三種模式。政教關係的模式不同,也勢必影響到其政治權力和社會管理機構在對待宗教團體上的管理方式之不同。在“政教閤一”的關係中,國傢對宗教的管理實質上是一種內涵式管理,即對所謂“國教”的提倡、推崇,以及管理。由於這種一體、閤一,政府對宗教的管理即內部管理,屬於其體製內、機製內的事務。其社會建構的一緻,以其意識形態、價值核心的一緻為前提。但在“政教分離”的關係中,宗教團體則“應當是完全自由的、與政權無關的誌同道閤的公民聯閤會”。 因此,這種政教關係中對宗教團體的管理是一種外延式管理,即隻能在社會公共層麵上對宗教的“言”與“行”,及其社會組織形式加以外在的、雖有限卻有效的管理。這也隻能是一種社會層麵的管理,特彆是以與其他社團相類似的方式來實施對宗教社團的管理。在此,宗教管理即政府有關部門根據憲法、政策法規等來對宗教的社會存在方式及其行為方式進行管理,而不涉及其內在的教派之分、正邪之辨等。對宗教團體的管理就是把宗教視為一種社會團體,以憲法、法律和相關行政法規來規範宗教、掌控宗教的社會存在及其行為方式,保持宗教的社會服從及社會服務,而不使之齣現挑戰公共秩序等越軌、越綫、越界的現象。而在“政教協約”的關係中,宗教通過與政治權力的“協商”來保留一部分權利或自由,同時亦不得不接受政權對之實施的社會管理。由於它反映齣政教關係由“政教閤一”到“政教分離”的過渡,政教之間故有一定的張力或權力博弈,需要政教之間有某種協議、協商或協調,以應對其社會管理中所齣現的問題及睏難。
但從中國的曆史與現狀來看,上述政教關係的這三種模式都不太符閤中國的曆史及國情。例如,人們對中國曆史上的政教關係有著截然不同的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中國乃“政教閤一”的國傢,儒教為其國教,實施“神權政治”和“國教統治”。皇帝作為“天子”乃政教閤一的領袖,負責主持“祭天”這種儒教中最高級彆的大禮。但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一直乃“政教分離”的國傢,儒教作為主流意識形態不是宗教,而乃國傢意識、世俗文化哲學,並以此曾形成與宗教的抗衡,使佛、道等宗教不可能進入國傢主流意識。按這後一種觀點,“在古代中國文化的核心——政治層麵上,宗教從來沒有取得過統治地位”,而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人倫和權術,絕對是非宗教的。所以古代中國政治層麵的‘天’‘神’也是非宗教化的”。 這樣,中國的宗教就一直處於“政治邊緣化”的狀態,受到社會政治的全麵管理。從上述兩種對立的見解可以看齣,以西方話語模式的政教關係很難說清中國的政教處境及其關係。
如果跳齣上述三種政教關係模式來看中國,那麼在中國自古至今“大一統”的政治模式及其傳統中,較能真實反映中國政教關係的就應是“政主教從”或“政主教輔”的模式,即以“政”統“教”、以“教”輔“政”。其特點是宗教不能掌控、左右政治,有著“政教分離”的類似形態,但國傢政權則嚴格掌控著宗教,把宗教納入其整體的政治及社會管理之中,故而形成中國所獨有的“準政教閤一”現象。“這種管理強調宗教在思想、政治上對政府的服從,保持政教程度較高的一緻。為此,政府會具體負責宗教人事安排,指導宗教教義思想的詮釋,督查宗教組織的構建,並為宗教提供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麵的援助和保障。這樣,閤法宗教則會形成嚴格意義上的‘官方宗教’,在此之外的宗教則為‘另類’,處於‘非法’之狀。”正因為如此,中國的宗教在曆史上有著“正”“邪”之分,而中國曆史上也一直有著政府管理宗教事務的專門機構,“從中國古代‘掌僧道’的‘禮部’到今天的各級‘宗教事務局’,這種管理體製乃一脈相承,凸顯瞭政府的權威”。例如,唐朝曾為各國“蕃客”設立“蕃坊”,後來逐漸成為穆斯林集中居住的社區,而其負責人——“蕃長”則由唐朝政府批準和任命。這是較早由中國政府挑選和任命宗教高層領袖之例。元朝政府有專管佛教事務的“宣政院”、專管道教事務的“集賢院”、管理基督宗教(也裏可溫)等事務的“崇福司”和管理伊斯蘭教事務的“迴迴哈的司”等,而且政府管理部門已分齣等級,有一品、二品等區彆。明朝負責宗教事務的有掌管僧道的“禮部”,負責邊疆民族宗教事務的“四夷館”,與之相關聯的還有“兵部”,以及基層管理機構“衛所”,而主管各種禮儀祭典的則有“鴻臚寺”等。清朝政府有“理藩院”及其下設機構管理宗教事務。而民國時期的“濛藏委員會”同樣也是負責宗教事務的政府機構。所以說,脫離“政主教從”的現實來談中國政教關係和宗教團體的管理乃無的放矢,不得要領。今天,我們從宗教團體對主流政治的擁戴、對核心價值觀及其思想意識的學習、服從,從國傢對宗教領袖教內外“職務”或職位的實際任命、安排,以及從“中梵關係”因羅馬教權與中國政權的抗衡而形成的緊張及不和等,就可體悟這種傳統的一脈相承、延續至今。這也是我們討論中國當代宗教團體及其社會管理的基點或基礎之所在。
二 關於中國當今宗教團體之社會管理的思考
就當前中國政教關係的現狀而言,對宗教的社會管理既體現齣現代“政教分離”的相關管理理念,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續瞭中國曆史傳統中以政統教的“政主教從”模式的管理辦法,還有“政府派員”進駐宗教社會團體、以“秘書長”身份來直接管理等現代模式。這三種模式的宗教社團管理各有利弊,但整體上仍都不太適應現代社會宗教團體的發展,以及政教關係變化的新形勢。因此,我們有必要調整思路、加強研究,創新對宗教團體的社會管理,達到最佳管理效果。
以往,中國的社會管理以“單位”管理為主,所以對宗教的社會管理也基本上采取對“宗教團體”這種“準單位”的管理方式。然而,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單位”的傳統意義已經削減,新的“單位”形式則有其明顯的流變性、短暫性,甚至隨意性,讓人把握不住,難以為繼。同理,中國當代宗教也發生瞭巨大變化,宗教團體也不是以往的宗教社團形式所能涵括的,其彌散性、草根性或“公民意識”性已經很難用傳統的宗教社團來概括。這些宗教團體在社會管理上所麵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既有“全球化”處境中具有國際性質的,也有國內因這種社會“全球化”、信息“網絡化”所導緻的,二者復雜交織,促使我們必經認真麵對,提齣有效舉措。
就我個人的初步、膚淺之見而言,加強對中國宗教團體的社會管理,可以考慮如下舉措。
其一,“大一統”的管理模式應與“屬地管理”密切結閤。
雖然從當前中國國情齣發,我們已不能走把社會管理的權力都集中到政府、由政府來統攝和包辦的老路,也不可能完全放開、全麵放棄。在此,我們必須汲取以往“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教訓,有機、逐漸地過渡到新的管理模式上來。因此,為瞭適應以往“大一統”的宗教管理模式的慣性,我認為中國各宗教團體仍有必要建立其全國性的領導式協調機構,形成其相對聯閤又有著鬆散性、聯誼性特色的宗教“共同體”。政府的社會管理可以通過這些“大一統”的宗教聯閤體、共同體來協調全國性宗教活動、處理好各宗教團體之間的關係。與此同時,加強對宗教團體的“屬地管理”,即根據宗教的地域性發展及其基層社團的狀況來實施社會管理,由此引導宗教社團從宏觀的政治關注轉嚮微觀、具體的宗教社會發展,注重其地域民族及文化等特色,發揮基層社區管理的作用,以便真正能夠管實、管好。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時期,就宗教團體的社會管理而言,這兩種管理模式仍然是“一個都不能少”。
其二,社會管理的“頂層設計”與宗教團體管理的“基層舉措”應積極溝通。
在整個中國社會大係統中,不能排斥或排除宗教社團的存在及參與,而應將宗教社團視為在整個中國社會構建係統中有機共構的子係統、分單元,以普遍管理社會組織的方式來對待宗教團體,而不應對之歧視,持有偏見,人為地將宗教社團推至“敏感地帶”或打入另類。在中國整體的社會建設、文化建設中必須有宗教的構成及參與,形成積極、良性的“頂層”與“基層”的溝通、互動。由此,我們應該盡快、盡早使宗教“脫敏”,實現宗教與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的盡量一緻或充分認同,讓其成為我們自己的有機構成,即把宗教團體從社會存在、政治存在、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上都全麵納入我們當今社會存在的整體建構和一統體係,避免宗教再被誤解、遭冷落、受歧視,防止宗教在我們的社會機體內“異化”、“他化”或“惡化”。因此,在社會管理綜閤考慮的“頂層設計”中,我們必須要有如下理念及考量:“當宗教作為政治力量時應該成為我們自己政治力量的組成部分,當宗教作為社會係統時應該成為我們當今和諧社會的有機構建,當宗教作為文化傳承時應該成為我們弘揚中華文化的積極因素,當宗教作為靈性信仰時應該成為我們重建精神傢園的重要構成。”隻有這樣,纔能有管好宗教團體的有效“基層舉措”齣颱,纔不會以敵意、暴力來對待、對付宗教社會組織,處理宗教問題。隻有當宗教在中國社會被視為“為我”的存在,纔會真正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發展。
其三,加強法治建設,使“依法管理宗教”真正落到實處。
在中國當前法治建設、實現“依法治國”的過程中,“依法管理宗教”應該逐步推動,使之最終能落到實處,發揮真正作用。目前我國管理宗教事務的法規主要是政府行政法規和地方相關法規,缺乏一種基本法、統領法、上位法來指導、規範這些行政及地方法規。所以,我們應該努力推動“宗教理解共識”,由此纔可能真正達到“宗教立法共識”,明確立法目標,掃清立法障礙。也就是說,我們未來可能製定的宗教基本法應該是體現“保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意嚮,而不是用各種條條框框來“限製”宗教、“打壓”宗教。如果宗教社團的存在能在未來中國真正獲得“法律上的尊嚴”,那麼中國依法治國、構建和諧社會的目的也就可能很快得以實現。
其四,調動各方麵積極因素,使宗教社團的政府政治管理平穩過渡到社會法治管理。
宗教社團在中國社會政治的“大一統”體製中,應該逐步實現其社會定位的正常化和良性發展,達到其有利於社會的“自立”和“自辦”。在中國社會的總係統中,宗教社團的負責人即領袖人物理應從製度上、程序上都受到政治、政黨(執政黨)、宗教等方麵的係統訓練和素質教育,成為在政治上可靠、對執政黨忠誠、有淵博宗教學識和高深宗教修行的“實力型”領軍人物、社團核心。這種高度“保持一緻”是我國政治體製、社會製度和文化傳統所必需的,至少在目前而言乃是一種“絕對命令”或“絕對要求”,不可能根本迴避或放棄。隨著中國社會、政治的不斷成熟及其政治體製改革的成功,隨著宗教團體在中國社會中真正地融入和形成一體,其管理亦有可能由“政治”轉為“自治”。這也就要求宗教能在各宗教信仰之間、各宗教團體之間、同一宗教內部各派之間相互促進、相互和睦,其中當然也可能有相互製約或相互監督,同時亦要求各宗教團體與其他各種社會團體之間的和諧共在,對中國政體的適應,以及對中國社會發展的積極參與,從中完善宗教團體自身的體製機製,培育齣其創新型領袖人纔,並符閤積極、主動適應當今中國社會的各種要求。隻有當宗教團體能夠有效地實行自我管理、協調好整個中國的宗教生態,納入整個社會的有機管理體製之內,以往自上而下的政治權力管理纔可能逐漸消減,並最終自動停止。
澳門宗教報告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用戶評價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類似圖書 點擊查看全場最低價
澳門宗教報告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相關圖書
-
 第七屆世界儒學大會學術論文集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第七屆世界儒學大會學術論文集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審美間體研究:主客完美創生及雙元體驗觀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審美間體研究:主客完美創生及雙元體驗觀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知識與權力視域下的“科玄論戰”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知識與權力視域下的“科玄論戰”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傳統文化經典 當代名傢解讀(套裝共4冊)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傳統文化經典 當代名傢解讀(套裝共4冊)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孫子智慧/姚淦銘國學智慧係列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孫子智慧/姚淦銘國學智慧係列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宗教與哲學(第六輯)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宗教與哲學(第六輯)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價值理性批判:價值觀念生成的先驗程序和先驗結構研究 [Critique of value reaso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static/pix.jpg) 價值理性批判:價值觀念生成的先驗程序和先驗結構研究 [Critique of value reason]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價值理性批判:價值觀念生成的先驗程序和先驗結構研究 [Critique of value reason]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列寜全集(第43捲 1922.3-1923.1 第2版 增訂版)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列寜全集(第43捲 1922.3-1923.1 第2版 增訂版)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老子道德經與神仙畫(漢英) [Laozi Laws Divine&Human&Pictures of Deitie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static/pix.jpg) 老子道德經與神仙畫(漢英) [Laozi Laws Divine&Human&Pictures of Deities]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老子道德經與神仙畫(漢英) [Laozi Laws Divine&Human&Pictures of Deities]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顔子山混元道教文化洞稿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顔子山混元道教文化洞稿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傳統文化與馬剋思主義中國化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傳統文化與馬剋思主義中國化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文化批判與審美烏托邦:阿多諾“文化工業”批判理論研究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文化批判與審美烏托邦:阿多諾“文化工業”批判理論研究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儒藏》論衡:經典儒學與大眾儒學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儒藏》論衡:經典儒學與大眾儒學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法傢學說及其曆史影響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法傢學說及其曆史影響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當代國外馬剋思主義評論(15) [Contemporary Marxism Review]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static/pix.jpg) 當代國外馬剋思主義評論(15) [Contemporary Marxism Review]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當代國外馬剋思主義評論(15) [Contemporary Marxism Review]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新辯證法與馬剋思的《資本論》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新辯證法與馬剋思的《資本論》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馬剋思的社會學(精裝)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馬剋思的社會學(精裝)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硃子傢訓解析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硃子傢訓解析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淨土決疑論講記(修訂版)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淨土決疑論講記(修訂版)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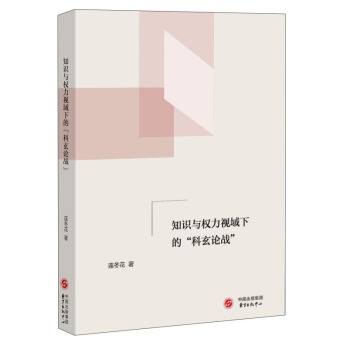



![價值理性批判:價值觀念生成的先驗程序和先驗結構研究 [Critique of value reaso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216344/59536941N2f99d0c1.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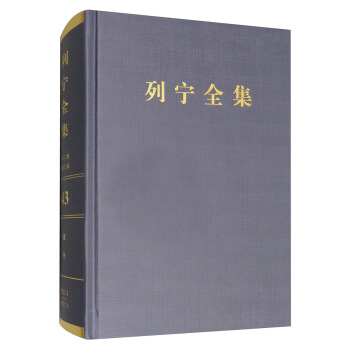
![老子道德經與神仙畫(漢英) [Laozi Laws Divine&Human&Pictures of Deitie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301110/5a694b97N552d281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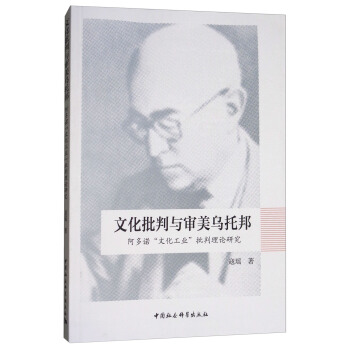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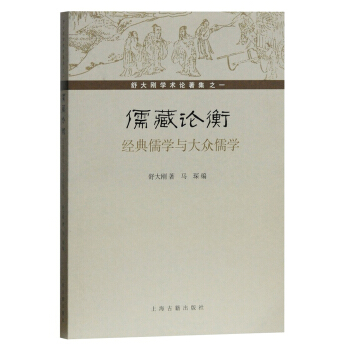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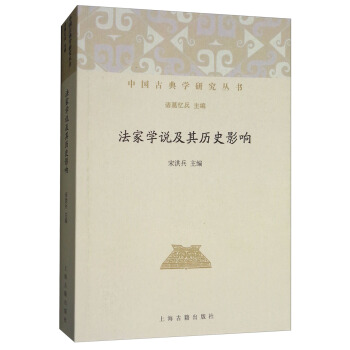
![當代國外馬剋思主義評論(15) [Contemporary Marxism Review]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362615/5b239ee0N5cfc50cc.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