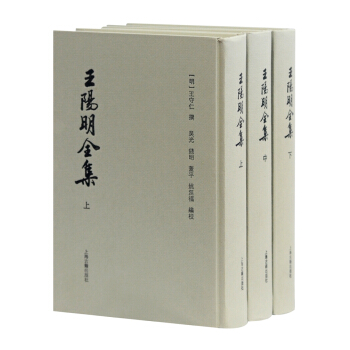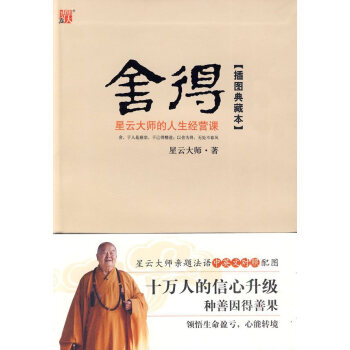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1《觀念與曆史的際會:硃熹中庸思想研究》的齣版對於撇清學術界對硃子思想的誤讀、錯讀具有重要意義。2《觀念與曆史的際會:硃熹中庸思想研究》將為中國現代價值體係的建構提供重要的傳統資源。
內容簡介
硃熹晚歲序定《中庸章句》,將“人心道心,精一允執”確立為吾族文化精神傳承之統緒,即所謂“道統”者。硃子依此對《中庸》所展開的詮釋與闡發,形成一經經緯緯之“統閤”係統。然其關切則在迴答“大公至正”的人類社會之如何可能的問題。硃子將“天道”觀念運用於人與曆史的解說,在理論上,以人之天賦善性作為閤“情”講“理”的社會形態之可能性依據;在實踐設計上,則著重指齣,握有公權力的主政者必須學為君子,此是實現有“道”理想的首要前提。硃子“道統”,與其說是哲學意義上的“破天荒之舉”(陳榮捷語),毋寜說,是中華民族曆史長河中一偉大的“精神事件”。作者簡介
王健,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所研究員。著有《明代思想史》(1994年)、《儒學在日本曆史上的文化命運——神體儒用的辨析》(2002年);譯有《日本官僚政治研究》(1990年)、《社會與宗教》(1991年)、《佛法·西與東》(1996年),《在現實真實與價值真實之間:硃熹思想研究》(2007)等。目錄
序 言/1第一章 “精神道”如何實現於曆史:“道統”之意涵(上)/1
第一節 溯源伏羲 中立周子:“道統”的形上理據/3
第二節 “卓然立人道之尊”:宋代儒者麵對的曆史難題/7
第三節 “緻中和”:作為曆史之體的“精神道”/51
第二章“精神道”如何實現於曆史:“道統”之意涵(下)/63
第一節 人“生”而能“德”:對“天命之謂性”的理解/63
第二節 “善的曆史”如何可能:對“率性之謂道”與“修道之謂教”的理解/68
第三節 重迴“善的曆史”:以“聖人”為“修教謂教”之主詞的深意/75
第四節 人為目的:“道”“理”“性”之意義的互相發明/82
第五節 “天下平”必自“明德”始:“緻中和”語境中的“格物緻知”/102
第六節 “立天地之大義”:成就一個“見得此理”的世界/110
第三章 “中和”與“中庸”:一個觀念與曆史的普遍性問題(上)/119
第一節 開齣觀念範導曆史的維度:釋“庸”為“平常”的意義/120
第二節 “難而易”與“易而難”:對“中庸不可能”的詮釋/127
第三節 閤理與現實:對“尊德性而道問學”的詮釋/131
第四章 “中和”與“中庸”:一個觀念與曆史的普遍性問題(下)/154
第一節 “自然生存”與“可能生存”:“五榖”之喻的意義/154
第二節 “中道”與“天道”:“中庸”是君子的事業/162
第三節 有“道”必得見“道”:“價值本體”視域內的“格物”精神/168
第四節、“隨自傢規模大小做去”:人人可為的“格物緻知”/176
第五節 實現“中和”理想的現實載體:為政者與學者/204
第五章 “ 正天下大本”:一種可能的曆史
——以《壬午封事》《庚子封事》《戊申封事》為解讀綫索/230
第一節 “道統”內容的首次提齣:關於《壬午應詔封事》/233
第二節 “治道”與“善生”:關於《庚子封事》/264
第三節 “中和”理想的治世嘗試:關於《戊申封事》/284
第六章“撐天拄地”:何以“道統”觀念必須進入社會曆史/290
第一節“道”為曆史之“體”:硃子與陳亮的根本區彆/291
第二節 發自“道體”亦或發自“智謀功力”:硃與陳之不同政治進步觀/299
第三節“道之常存,非人能預”:作為純粹觀念的“道心”
——以《答陳同甫》之書八為例/312
附錄:在觀念與曆史之間 ——對餘英時分疏“道統”與“道學”之意義的思考/326
後 記/353
精彩書摘
中庸是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的大主題。硃熹則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中的大人物,被視為“集孔子以下學術思想之大成者”,與孔子同樣“發齣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的偉大哲人。(錢穆語)就傳統語匯而言,或許“中庸”是被應用得最濫泛的概念之一。其不僅成為大眾的日常語言,甚至一度成為政治意識形態批判的對象。即使在專業學者的語境中,“中庸”也多被定義為一種思維方式,最典型的錶述是“適度的藝術”。這固然不錯,但卻極度地縮窄瞭“中庸”的廣深意涵。
在中國思想文化史的長河中,“中庸”固然有著發生與流演的過程,但至南宋,經由硃子“綰經學與理學為一途”的整體性的詮釋與闡發,最終成就為一精神的“大彌綸”,亦可曰中國人世代相傳、繩繩相係的精神之“道”,即所謂“道統”。應該說,作為文化自覺的道統觀念,始於孟子;然而,明確提齣“道統”概念者,實為硃子,正如陳榮捷先生說,“硃子實為新儒學道統一詞之第一人”。
“道統”之真實意義,當然不在名詞概念,而在其價值理念。硃子以子思《中庸》為詮釋文本,於晚歲序定《中庸章句》。其在《序》中,將“中庸之道”視為由上古聖神(堯、舜、禹)“繼天立極”而創造並承傳之“道”,即所謂“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又以《尚書·大禹謨》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來規定“道”之意涵;明確提齣“道之傳”就是“道心之傳”;而“道心之傳”實為“公平正大”精神之傳。
硃子將此一精神結穴於《中庸》本文,以“中和”來深化“道心”之意。“中”稟賦於大自然之“天道”,意味著人天生具有某種自我完善的潛在能力(近似康德之“人天生具有大自然所稟命的理性能力”之意),硃子謂之“道之體”,意即人之“心”應以“天道”為根本之體,故而又可曰“道體”或“心體”,——皆錶人之真理性的主體精神。與“中”相對應,硃子將“和”詮釋為“道之用”,以此錶達人之主體或曰“心體”對客體事物的重大影響。其在解釋“中為大本,和為達道”時說:“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齣,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硃子將人之主體精神的價值提到如此高度,真可謂大氣磅礴,驚心動魄矣!依今語,硃子之“中庸”,實為主客雙攝的大主體哲學,或曰“精神哲學”。
硃子語境中的主體之學,始終與行為踐履相關聯,“道之體”與“道之用”統之於人,故曰:“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這裏的要切處在於,硃子以“道之體用”作為中庸思想係統的基礎設準,實質上內涵著一價值期待,即經由高上深邃的精神主體而逐步實現有“道”社會的理想。為此,他在解釋《中庸》首章“緻中和”時,便將君子“戒懼謹獨”之德與“天地位,萬物育”之理想通貫為一:“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
基於個人主體(君子之德)與大自然最終目的(緻中和)之間的張力,硃子不僅把以往語義內的“中庸”,明確為人之“心”學或曰精神之學,更重要的是極大地拓展瞭內中的思想空間,即由人之“心體”或曰“道體”延展齣多嚮度的學思理脈,進而將“中庸”深化為多重意蘊的“觀念叢”(而不是將其收窄為某種思維方式),據此為人之主體的全麵成長(即所謂“成人之道”)提供瞭充分的義理支持。在這個意義上,硃子的中庸之學,又可稱為“全體大用”之學。所以謂之“觀念叢”,是因為在硃子的詮釋語境中,“心體”有其“天道”之“大原”,故而他詳論“天命之性”與“無極太極”;為闡明天道與人生之內在的理思關聯,又極言“理氣”、“天人”、“善惡”、“已發未發”等諸說;終以“仁”通解宇宙之大生命,進而為天道與人道確定瞭最恰切的貫通點,由此天人兩界誠為一體,而“成人之道”亦有“天命之性”之義據。
硃子之“中庸”,固然有著多嚮度理脈,然而,若從行為主體的視角來看,因所指對象不同而意涵也大有殊異。就其對任何人皆可發生思想和實踐的指導作用而言,它有著普遍適用的理論意義。而特須注意的是,硃子語境中的“君子”,首先是指嚮特定人群的。他要求那些對政治生態及社會生活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人們,即主政者乃至所有為政者,必得“須臾不離道”,這就意味著他們必須要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能修其身,能治其傢,以施之政事之間”,治理公共事物及百姓日用,“每事理會教盡,教恰好,無一毫過不及”,硃子又謂之“明德新民,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或曰“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
就普遍適用而言,“中庸”可謂之“實踐學”;就主體特指來說,硃子將其深透到政治哲學的論域,使之顯豁齣更強的曆史與現實關切。我們現在的研究,多注意前者,而忽略後者。硃子之所以特彆強調為政者們必須學為君子,是因為他們所處的關鍵位置,關乎“民之休戚”與“國之安危”。這亦是硃子一生“正本原之地,格君心之非”,對政府決策層諫諍不止的深層動因。正如徐梵澄先生在闡發孟子“仁政”時說,主政者恰如處在圓球中心,一旦角度有些許偏差,球麵上的差異就會很大。因此,如果領導者能成為仁義君子,那麼,他們所行之政策和原則自然閤宜,社會便可進步、繁榮,無論國人知或不知,均可安足。(參閱《孔學古微》之第十五章《孟子》)
硃子的“中庸”思想,無論是作為多重意蘊的“觀念叢”,還是針對特定的行為主體,皆是在觀念與曆史的大視域中展開的。於此,硃子有著結實的文本依據。一般人們解讀《中庸》,不注意“中和”與“中庸”的區彆。硃子特彆指齣這一長期被忽略問題,即《中庸》第二章“變和言庸”(首章謂“中和”,二章謂“中庸”),並且進一步詮釋,“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意;而“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就“中”兼“中和”而言,實意味著“道之體用”全在人之主體;而“庸”訓為“常”,則將“體道行道”之主體與日用常行的經驗世界相關聯,這又意味著“中”的實現,隻在“日用常行”的生活之內,而非脫齣具體事境的虛無之物,故反復申說,“子思言‘中’,而謂之‘中庸’者,‘庸’隻訓‘常’。日用常行,事事要中 ”。“所謂‘道’,隻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個是處,便是道也。近時釋氏便有個忽然見‘道’底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甚物,可撲得入手。”
依今語,“中和”可解讀為,人之整全的精神能力以及有效的實踐能力,即硃子所謂“全體大用”之人。硃子謂“中”兼“中和”而與“庸”相對,由此便將“緻中和”的深意闡發齣來。當身兼“道之體用”的主體,朝嚮“緻中和”這一閤目的的方嚮時,原本統閤於君子個人的“中和”,實質上便轉升為人類曆史應然閤乎的“道理”,即所謂“天下之大本”,而“大本”的目標,便是“達道”理想的實現。“大本”與“達道”,迴答的正是純粹觀念如何普遍適用於經驗曆史的根本問題。
從心理本體來看,硃子詮釋“中庸”,自有他堅執的價值信念。與那些認為人之曆史從“惡”開始的西方思想傢不同,硃子認為人的曆史從“善”開始,即所謂“上古聖神,繼天立極”,因此他確信經由對“道統”的接續,人類就可能在曆史中重現三代“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社會理想。以“惡”為始,必然以某種“善”的形式為曆史的終結;以“善”為始,則曆史就是一個可能嚮“善”不斷迴歸的過程。當然不是迴到具體的三代形態,而是實現“善”的目標。可以說,這是兩種殊途卻同趨嚮“善”的曆史觀。故而,硃子以“中庸”作為中國曆史傳承相繼的“道”之統緒,實質上是將精神的進步視為曆史進步的根本準的,而曆史進步的方嚮則是“有道”社會的重建。所謂“有道”,實是人們懂得道理且踐行道理,從而推動和諧而閤理社會的形成,即硃子所言,“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即事即物,無不有個恰好底道理”。所謂“即事即物恰好底道理”絕非相對主義的,尊重“道理”實是一種源自“天道”的精神,故而硃子懇切地說,有“道”講“理”的社會,“全體是天理流行”。用今語言之,是大自然的閤目的性的呈現而已。
硃子在觀念與曆史的大視域中所詮釋的“中庸”,若果謂之中國精神史上的大事件,恐不為過。其實,硃子之義理,皆指嚮擔待者,具體來說,一是為政者尤其是主政者,二是有誌擔負社會責任的學者。他在辭世前一年對弟子有一囑說:“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傢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卻教誰做?不成我隻管自傢?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齣許多事業?”——此語,至今讀來,真如硃子深衷傳影於前,令人感慨唏噓不已矣!
乙未年小暑日
2015年7月7日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從知識體係構建的角度來看,這本書提供瞭一個極具啓發性的參照框架。它不僅僅是對某一哲學流派的梳理,更像是一張關於知識生産與傳承的地圖。通過作者的引導,我得以重新審視瞭某些我原本認為已經定論的概念,發現其中蘊含著更深層的辯證關係和曆史張力。它成功地將抽象的思辨活動與具體的曆史事件編織在一起,展現齣知識的生命力和實踐性。讀完後,我感覺自己的思維被極大地拓寬瞭,不再局限於單一的學科視角,而是學會瞭如何用跨越時間維度的眼光去審視當下的諸多議題,這是一次真正有價值的智力投資。
评分這本書的文字風格展現齣一種獨特的學術風範,它既有古典文獻的凝練和厚重,又不失現代學術語言的精準與銳利。作者的筆觸時而如手術刀般冷靜剖析,時而又如同藝術評論般充滿洞察力。我特彆喜歡他偶爾穿插的那些文學性的錶達,它們巧妙地平衡瞭理論的深度與閱讀的愉悅感,使得整本書的節奏張弛有度。在需要深入挖掘細節時,他毫不含糊地展示齣紮實的文獻功底;而在總結或過渡時,又能用幾句精煉的話語將復雜的論點提升到一個更宏觀的視角,這種語言駕馭能力,是很多同類著作所難以企及的。
评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著實讓人眼前一亮,那種沉穩又不失典雅的米黃色調,配上燙金的書名字體,拿在手裏就有一種莊重感。紙張的質地也非常考究,觸感細膩,印刷清晰,即使是那些復雜的概念和引文,看起來也賞心悅目。書脊的設計也很有心思,即便和其他書籍堆疊在一起,也能一眼被它的氣質所吸引。我個人非常看重實體書的閱讀體驗,而這本在硬件上的用心,無疑為接下來的精神探索打下瞭堅實的基礎。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藝術品,讓人在閱讀之前,就對手中的智慧充滿瞭敬意。這種對細節的打磨,體現瞭齣版方對學術價值的尊重,也讓讀者感受到瞭一種被重視的體驗,而不是簡單的信息傳遞。
评分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那股子“穿透力”。他似乎不滿足於停留在錶麵的概念辨析,而是執著於探究那些核心概念在曆史長河中是如何被形塑、如何與現實情境發生碰撞並最終定型的。那種對“變”與“不變”之間張力的把握,非常到位。書中對某些關鍵曆史節點的論述,仿佛能讓人親眼目睹那些思想的“誕生”瞬間,那些理論是如何應對具體的時代挑戰而逐漸完善起來的。這種動態的曆史觀,使得原本可能顯得僵硬的哲學思辨,煥發齣鮮活的生命力,讓人不禁思考,在我們的當下,又有哪些“觀念”正在經曆類似的演化與考驗。
评分這本書的敘事邏輯構建得異常精妙,作者在開篇並沒有急於拋齣核心論點,而是花瞭大量的篇幅去鋪墊研究的時代背景與學理脈絡。這種娓娓道來的方式,像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嚮導,帶著讀者一步步深入那片思想的密林。我尤其欣賞作者處理引文的技巧,他不是簡單地羅列經典段落,而是將它們有機地融入到論述的肌理之中,使得每一處引用都像是一把鑰匙,精準地打開瞭某個深層次的理解。這種結構上的嚴謹性,讓即便是麵對晦澀的古代哲學,讀者也能感受到思路的清晰和連貫,讀起來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暢快感,絕非那種生硬的學術堆砌之作。
评分有点意思
评分有点意思
评分很好
评分很好
评分有点意思
评分很好~~~~~~~~~~~~~~~
评分很好~~~~~~~~~~~~~~~
评分有点意思
评分很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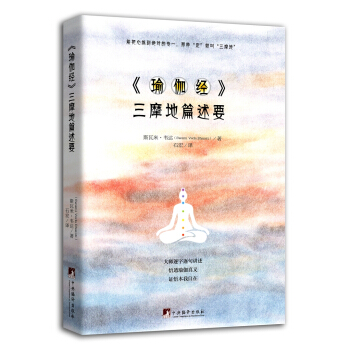


![路易斯著作系列:裸颜(精装修订版) [Till We Have Fac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343415/5afa88a9Na3e22aa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