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第2版)論述涉及國傢和地方、英雄和傳奇、動員結構、技術革新、勞動等五六十年時代文化的各個層麵;受國外學界肯定,已經輸齣英文版(美國杜剋大學齣版社)和俄文版(俄羅斯東方齣版社)。
內容簡介
《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第2版)從國傢和地方、英雄和傳奇、動員結構、技術革新、勞動等不同方麵對1949—1966年期間中國社會主義文學與文化想象進行瞭多種角度的討論,這些討論既在文學之中,又在文學之外,這和作者近年來一直強調的打通文本內部/外部的研究有關,也可以視之為當代文學研究方法論上的新的實踐。顯然,作者努力使文學重迴公共領域,因此,在本書中,文學史始終處在和社會政治史積極對話的過程中間。作者在強調瞭中國革命的正當性的同時,並沒有刻意迴避無理性的一麵,而是嚴肅討論這一正當性如何或因何生産齣瞭它的無理性,這一討論也使本書進入瞭現代性的核心部分。尤其本書的結尾,直接討論瞭50—70年代社會主義實踐的危機以及危機的剋服問題,從而為進入1980年代提供瞭理論上的可能性。本書既是一部文學史的研究著作,也是對中國社會主義曆史進行重新思考的一次思想旅程。作者簡介
蔡翔, 1953年12月生於上海,1970年下鄉插隊,1974年迴城做工,1978年考入上海師範大學中文係。曾任《上海文學》雜誌社執行副主編,現為上海大學中文係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當代文學和文化研究,兼及散文隨筆寫作。已齣版主要著作有:《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精神漫遊》《日常生活的詩情消解》《神聖迴憶》《迴答今天》《何謂文學本身》等十餘種。目錄
目?錄導?論? “革命中國”及其相關的文學錶述 1
第一章? 國傢/地方:革命想象中的衝突、調和與妥協 23
一、“地方”風景的敘述以及“風景”再建的睏惑 26
二、動員和改造中的“地方” 37
三、脫域、在地和“地方”的保存或者現代性的轉換 57
結語 70
第二章? 動員結構、群眾、乾部和知識分子 74
一、動員結構 74
二、群眾 91
三、乾部 100
四、知識分子 117
結語 124
第三章? 青年、愛情、自然權利和性 127
一、青年或者“青年政治” 128
二、愛情或者“愛情故事” 145
三、性或者“性的敘述” 160
結語 167
第四章? 重述革命曆史:從英雄到傳奇 169
一、“平凡的兒女,集體的英雄” 170
二、傳奇和一個故事的旅行 187
三、“讀者”和“市場” 196
四、為何或者怎樣重述革命曆史 208
結語 220
第五章? 勞動或者勞動烏托邦的敘述 224
一、《地闆》的政治辯論和法令的“情理”化 227
二、《改造》以及改造的故事 235
三、《創業史》和“勞動”概念的變化 248
四、《萬紫韆紅總是春》:女性解放還是性彆和解 264
結語 272
第六章? “技術革新”和工人階級的主體性敘事 275
一、弱者的武器和工匠精神 275
二、“文化訴苦”與“技術革新” 288
三、反智主義還是反專業主義 302
結語 324
第七章? 1960年代的文化政治或者政治的文化衝突 326
一、物質豐裕和物的焦慮 328
二、“脫離領土”的運動和“重建領土”的努力 337
三、生活小事和國傢大事 356
結語:“文學青年”為何再次齣現 364
結束語? 社會主義的危機以及剋服危機的努力 368
一、什麼是社會主義危機 369
二、剋服危機的努力 380
三、1980年代的知識轉型 388
結語 392
主要參考文獻 394
後記 397
精彩書摘
第一章節選一、“地方”風景的敘述以及“風景”再建的睏惑
我所要討論的“風景”,其分析模式藉助於柄榖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中的“風景之發現”以及霍爾的某些論述。在柄榖行人看來,對對象(風景)的描述,並不僅僅隻是一種單純的對自然的模仿行為,恰恰相反,這一所謂對象,隻是存在於敘述之中,而所謂敘述也永遠隻是一種主體的敘述,或者說,客體並不先於主體而存在,而隻是主體敘述之物。而在霍爾所謂的文化構成主義的理論中,物自身並不産生意義,而是“通過我們對事物的使用,通過我們就它們所說、所想和所感受的,即通過我們錶徵它們的方法,我們纔給予它們一個意義”,或者說,意義“産生於我們圍繞這些‘物’編織敘述、故事(及幻想)之時”,也因此,“正是通過文化和語言,意義的生産和循環纔能發生” 。然而,進一步的問題則在於,這一“我們”或“主體”,又是如何産生的。正是在這裏,柄榖行人引入瞭“裝置”這一概念,在柄榖行人看來,主體或主體性同樣不是先驗的存在,而是一個被不斷建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充斥著國傢、社會、製度、政治、意識形態等等力量的介入,也正是這諸種力量的介入,纔構成瞭某種生産性的“裝置”。這一“裝置”生産並建構瞭個人的主體或主體性,同時也相應地生産並建構瞭主體的敘述之物。因此,所謂對象,也就是主體的敘述之物,總是和敘述者的主體性有著某種隱秘的聯係,換句話說,我們看到的,可能就是我們想要看到的東西。為瞭強調這一點,柄榖行人通過“風景”闡述瞭風景之發現的重要意義,並藉助對《難忘的人們》的分析錶明,“風景是和孤獨的內心狀態緊密聯接在一起的。這個人物對無所謂的他人感到瞭‘無我無他’的一體感,但也可以說他對眼前的他者錶示的是冷淡。換言之,隻有在對周圍外部的東西沒有關心的‘內在的人’(inner man)那裏,風景纔能得以發現。風景乃是被無視‘外部’的人發現的” 。而這一所謂“內在的人”正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現代性的産物(個體、自我、主體性,等等),因此,“風景”實際之發現,“是在某種製度中齣現的” 。柄榖行人著重討論的,顯然是想通過對“風景”的分析來指齣:“所謂風景乃是一種認識性的裝置,這個裝置一旦成形齣現,其起源便被掩蓋起來瞭。”
我並不在意柄榖行人對日本文學中的“風景”的具體分析,我藉助於這一概念以及這一概念背後的理論,隻是想說明,我同樣不把中國當代文學(1949—1966)中的“風景”看成一種純粹的“自然”描寫。而是想通過對“風景”的分析,來討論1949年以後,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傢的建構衝動,是如何介入當代文學的“風景”之發現中,以及隱藏其中的“國傢”和“地方”之間復雜的互動關係,同時由於階級政治的進入,所造成的“地方”風景再建的敘述睏難和內在的悖論語境。
孟悅在《〈白毛女〉演變的啓示——兼論延安文藝的曆史多質性》一文中,通過對《白毛女》的個案研究,討論瞭“解放區政治文化的生産過程”,以及這一“生産過程”中的“政治文學中的非政治性實踐”。孟悅所謂的“非政治性實踐”可能指的是在“政治話語”(“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敘事層麵下,還隱藏著某種“非政治的、具有民間文藝形態的敘事慣例”。或者說,“政治話語塑造瞭歌劇《白毛女》的主題思想,卻沒有全部左右其敘事的機製”,“而倒是在某種程度上以一個民間日常倫理秩序的道德邏輯作為情節的結構原則”。 而在這一敘事結構中,地主黃世仁不僅作為階級政治的敵人而存在,同時也作為“民間倫理秩序的敵人”而存在(“一係列的闖入和逼迫行為不僅冒犯瞭楊白勞一傢,更冒犯瞭一切體現平安吉祥的鄉土理想的文化意義係統……作為反社會的勢力,黃世仁在政治身份明確之前早已就是民間倫理秩序的天敵”)。孟悅進一步指齣的是,在歌劇《白毛女》中,“民間倫理邏輯的運作與政治話語之間的互相作用就錶現在這裏:民間倫理秩序的穩定是政治話語閤法性的前提。隻有作為民間倫理秩序的敵人,黃世仁纔能進而成為政治的敵人”。孟悅的這一解釋,對當代文學史的研究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不僅“闖入者”構成瞭當代文學一個相當普遍的結構模式,同時所謂的“多質性”既存在於延安文藝之中,也相對地存在於1949—1966的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之中。
這一敘事上的“多質性”固然有其復雜的構成因素,但同時也可能與中國革命的特殊性質有著某種隱秘的關聯。中國革命不僅深深地根植在鄉村之中,因此對鄉土理想常取一種尊重或妥協的姿態,同時,由於中國革命的階段性性質(比如,民族革命/階級革命,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等等),盡管階級政治始終是一種主導性的權力訴求,但並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其他的政治性訴求以及相關的文學—文化想象。因此,在這一“多質性”的政治語境中,所謂的“他者”也並不完全相同,有時甚至是多重的。而在這一“多重的”的“他者”規定下,所建構起來的政治主體,也就勢必含有“多質性”的特點。當然,這並不是說,這一所謂的“多質性”始終處在某種平衡甚至靜止的狀態,恰恰相反,這一“多質性”所導緻的正是思想—文化的激烈鬥爭,也正是經由這樣的鬥爭,政治話語纔能確立自己的“霸權”地位。因此,所謂的“改造”或“自我改造”,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這一“多質性”的政治語境所緻,並且,預伏瞭“自我否定/不斷革命”的可能性。
但是,這一“多質性”的政治語境,在某種意義上,也導緻瞭中國革命的“妥協”姿態,所謂“現代性知識”(政治話語)常常會主動或被動地吸納某種“地方性知識”(民間倫理),同時將其有效地轉化為自身的敘事資源。當然,這一吸納的過程同樣也充滿瞭矛盾和衝突。
理解中國革命的“多質性”,也許可以幫助我們不至於簡單片麵地理解洪子誠先生關於中國當代文學“一體化”的論述 ,而是把所謂的“一體化”視為某種充滿矛盾和衝突的當代文學史的建構過程。同時,中國革命的這一“多質性”特徵,也相應地導緻瞭當代文學內在的復雜結構,以及敘事上的多重視角或者某種意義上的多樣化。比如說,在某種“階級政治”的視角中,“地方”風景可能難以再現。李六如《六十年的變遷》寫季交恕大革命失敗後,乘船到上海,“船越駛近岸,無數高樓和燈火,煞像是默默蹲著的一群巨獸,想要吃人似的閃動著眼光” 。所謂良辰美景,均不再現。顯然,在這一政治視角下,所謂“地方”實暗喻舊中國,並成革命之對象,其“風景”自然相應隱匿不見。但是,如果注入其他的革命元素,比如“民族”視角,“地方”風景的敘述就不僅可能,而且在復雜的、多質的政治語境中,往往會齣現相異的風景形態。
在當代作傢中,孫犁極其擅長寫景,比如《荷花澱》,小說開頭就寫:“月亮升起來瞭。院子裏涼爽得很,乾淨得很。女人坐在當中,手指上纏絞著柔滑修長的葦眉子。葦眉子又薄又細,在她麵前跳躍著。這女人編著席。不多一會兒,在她身子下麵就編成瞭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潔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潔白的雲彩上。她有時望望澱裏,澱裏也是一片銀白世界。水麵籠起一層薄薄的透明的霧,風吹過來,帶著新鮮的荷葉荷花香。”這一類的寫景手法,在孫犁的其他作品中也常可見到,並為論者稱贊。《風雲初記》寫鞦分居所:“鞦分在小屋的周圍,都種上菜,小屋有個嚮南開的小窗,晚上把燈放在窗颱上,就是船傢的指引。她在小窗前麵栽瞭一架絲瓜,長大的絲瓜從濃密的葉子裏垂下來,打到地麵。又在小屋的西南角栽上一排望日蓮,叫它們站在河流的旁邊,輾轉思念著遠方的行人……”再寫春兒:“這時候,春兒躺在自己傢裏炕頭上,睡得很香甜,並不知道在這樣夜深時,會有人想念她。她也聽不見身邊的姐姐長久的翻身和夢裏的熱情的喃喃。養在窗外葫蘆架上的一隻嫩綠的蟈蟈兒吸飽瞭露水,叫得正高興;葫蘆沉重地下垂,遍體生著像嬰兒嫩皮上的絨毛,露水穿過絨毛滴落。架上麵,一朵寬大的白花,挺著長長的箭,嚮著天空開放瞭。蟈蟈叫著,慢慢爬到那裏去。” 但是,這一優美的“地方”風景,因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而麵臨著被破壞的危險,在《風雲初記》接下來的敘述中,我們看到的另一種景象則是,因為戰爭,“夜晚,逃難的人們,就在熄滅的柴火堆旁邊睡下瞭,橫倒竪臥。河水洶湧地流著,衝刷著河岸,不斷有土塊坍裂的隆隆的聲音。月光照著沒邊的白茫茫大水和在水中抖顫的趴倒的莊稼。遠近的村莊,擔著無比的驚惶和恐怖,焦急和無依的痛苦,長久不能安眠。在高四海的小屋裏,發齣小孩子的撕裂喉嚨的哭聲。‘日本!日本!’在各個村落,從每一個小窗口裏,都能聽見人們在睡夢裏,用牙齒咬嚼著這兩個字”。我們看到,孟悅通過《白毛女》而總結齣來的“闖入/破壞”的敘事結構,相當普遍地進入瞭中國的當代小說,並且往往以一種“異己”的形象齣現。隻是,在孫犁或其他的以抗日戰爭為背景的作品中,比如袁靜和孔厥的《新兒女英雄傳》,這一“異己”者更多地以民族敵人的形象齣現。而在這一敘事結構中,“風景”,尤其是“地方”風景往往承擔著極其重要的敘事功能。而所謂“地方”風景的建構,也正有賴於“闖入/破壞”這一“他者”規定下的政治語境。並且,由於“民族話語”的強烈介入,政治話語的控製在某種程度上也開始齣現鬆動,“地方”(民間倫理,鄉土生活理想,等等)不僅不再機械地成為革命或改造的對象,相反,在這一語境中,反而成為需要保衛或捍衛的“傢園”。
在某種意義上,所謂“地方”,在這一語境中,已經悄悄地轉喻為“本土”。按照柄榖行人的說法,民族—國傢的建構,僅僅依靠社會契約來進行錶徵是遠遠不夠的,而必須通過想象來構築某種“共通的感情”,或者說恢復那種“失掉的相互扶助之相互性”,但是,這一“共通的感情”在現代民族—國傢中,已經不可能訴諸“血緣”,所以“隻好訴諸‘大地’”,並且往往通過“風景”之發現,或對“風景”的贊美來完成民族—國傢的錶徵 。
顯然,在“民族”話語的支持下,“地方”不僅可能轉喻為“本土”,同時,通過對“地方”風景的敘述,還得以構築共同體內部的“共通的感情”。但是,這一訴諸“大地”的民族—國傢的錶徵,卻內蘊著某種階級和解的危險性。在傳統的馬剋思主義者的眼中,這種危險性不僅存在,而且經由民族—國傢的錶徵,極可能導緻階級話語的被顛覆。比如,在圍繞“巴黎公社牆”的真僞性上,“巴黎公社之友協會”曾復信一位持有疑問的女孩,並堅定地錶明自己的立場:“親愛的朋友:您把位於甘必大林蔭道街心花園靠拉雪茲神父墓地的那座大型雕塑當成瞭公社戰士牆,該雕塑是莫羅—沃蒂耶的作品,它錶現一位憂傷的婦女——法蘭西,讓公社社員和凡爾賽分子在死亡裏和解。本協會成立的宗旨是維護公社英烈的榮耀,故始終拒絕這種把被槍殺的三萬巴黎人與槍殺者並列的象徵。” 顯然,在階級話語的製約下,需要追問的,始終是“誰的國傢”,從而拒絕在“法蘭西婦女”這一民族—國傢的錶徵中達成階級的和解。但是,民族話語和階級話語卻始終並置在社會主義國傢內部,這顯然源自於列寜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實踐,從“世界革命”到“國傢革命”,社會主義就勢必繼承既有的現代民族—國傢形式。安德森就指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生的每一次成功的革命,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等,都是用民族來自我界定的;通過這樣的做法,這些革命紮實地植根於一個從革命前的過去繼承來的領土與社會空間之中。”因此,安德森支持埃裏剋·霍布斯鮑姆的說法:“馬剋思主義運動和尊奉馬剋思主義的國傢,不論在形式還是實質上都有變成民族運動和民族政權——也就是轉化成民族主義——的傾嚮。沒有任何事實顯示這個傾嚮不會持續下去。”同時,安德森還以“民族資産階級”這個概念為例,提齣自己的疑問:“如果以生産關係來界定,資産階級明明是一個世界性的階級,那麼,為什麼這個特定部分的資産階級在理論上是重要的。” 這一現象也導緻瞭厄內斯特·蓋爾納不無幽默的說法:“馬剋思主義者們一般認為,曆史的精神或者人類的意識犯瞭一個極為愚蠢的錯誤。喚起人們覺悟的信息是針對階級的,但是,由於某個可怕的郵政錯誤,卻使它傳到瞭國傢手裏。” 但是,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階級話語始終是一個強大的“在者”,並時時監視著民族話語的發展,而一旦這一民族話語偏離階級話語的監控,階級話語便會與之進行爭鬥。比如,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國民黨官方提倡民族主義文學運動,但是這一混亂不堪的官方民族主義文學即遭到魯迅和瞿鞦白等左翼作傢的猛烈抨擊和辛辣諷刺 ,同時這一鬥爭也始終貫穿在左翼文學內部,比如“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衝突,即著名的“兩個口號”之爭。中國革命的這一具體實踐,使得情形並非如蓋爾納嘲弄的那樣,是把送給階級的信息錯誤地送到瞭民族的手裏,恰恰相反,“在中國,郵遞員似乎把給階級和民族的‘覺醒的消息’送到瞭同一個地方” 。而與此相聯係的則是,階級話語同時也參與到“地方”風景的敘述之中,並形成瞭相對復雜的敘事結構。
嚴格地說,即使在民族話語的“本土”意義上,我們也很難說,當代文學有關“地方”的風景敘述,完全就是現代性的産物。實際上,將“風景”暗喻為“故國”之思,在古代文學亦已有之。比如,丘遲的《與陳伯之書》:“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 ,就可視為一例。我更傾嚮於認為,所謂當代文學中的風景“實際之發現”,乃是依靠下層視角的引入,或者說,敘事者依靠下層(勞動)人民的視角,而重新“發現”瞭“地方”風景。也正是在這樣的風景敘述中,民族話語與階級話語纔獲得瞭某種默契以及高度的統一性。
實際上,在孫犁的《荷花澱》中,我們已經能感覺到這一下層視角的存在,隻是因瞭短篇小說的篇幅限製,或者在其創作時間(1945年)仍然受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規約,所謂“階級話語”並未明顯突齣,在作品中,這一下層視角隱蔽得較深,倒反而成全瞭小說的藝術性。1949年以後,所謂“階級話語”開始重新統攝全局,包括對革命曆史的重新敘述,這時候所謂的“地方”風景,就必須以階級的觀點來重新進行辯證。這樣。我們就能看到,比如,在孫犁的《風雲初記》中,就齣現瞭這樣的“風景”描寫:“在村正北有一所大莊基,連場隔院。左邊是住宅,前後三進院子,都是這幾年……一色的洋灰灌漿,磨磚對縫,遠遠望去,就像平地上起瞭一座惡山。右邊是場院,裏邊是長工屋,牲口棚,磨房碾房,豬圈雞窩。土牆周圍,栽種著白楊、垂柳、桃、杏、香椿,堆垛著麥秸、秫秸、高粱茬子。五六匹大騾子在樹陰涼裏拴著,三五個青石大碌在場院裏滾著。”一邊是由“長工屋”等構成的“風景”,另一邊則是地主住宅形成的“惡山”。這一區彆,顯然是因為這所“大莊基”屬於地主田大瞎子,而“田大瞎子(那年暴動,他跟著縣裏的保衛團追剿農民,打傷瞭一隻眼睛)在村裏號稱‘大班’,當著村長。他眼下種著三四頃好園子地,雇著四五個長工”。這樣的“風景”敘述,顯然滿足瞭“階級話語”的需要,而在這樣的敘述中,真正要完成的,則是“民族話語”和“階級話語”的相互融閤。也就是說,“民族敵人”同時必須是“階級敵人”,或者,反過來說,“階級敵人”勢必成為“民族敵人”。因此,一種較為通常的敘述模式是,這類“敵人”往往具有鎮壓農民或者反共的血腥曆史,而在民族戰爭中,又自然地賣身投靠侵略者。無論是《風雲初記》或者其他的相似題材的小說,比如梁斌的《紅旗譜》 《播火記》,這一敘述模式都得到瞭堅決的貫徹。也因此,在所謂的“抗戰題材”的小說中,“侵略者”的描寫有時候並不復雜,反而落墨更多的是那些“漢奸”,而一般來說,這些“漢奸”大都具有“民族/階級”敵人的雙重身份。經由這樣的“風景”處理,“闖入/破壞”不僅是民族的,也是階級的。比如《播火記》寫韆裏堤:“莊稼浴著露水,草上披滿瞭露珠,堤岸上開滿瞭紅的、白的小花。……牛沿著堤坡,一步一步吃著,一直吃到鎖井村東,韆裏堤拐彎的地方。嚴萍覺得纍瞭,跑上堤壩,順著河流嚮東一看,通紅的日頭,從水麵上鑽齣來,照得河水通紅火亮。天上映齣錦緞般的彩雲。一時高興,跑到堤上,跳起腳尖喊:‘春蘭,春蘭,來!’春蘭把牛拴在樹上,跑上來說:‘乾什麼,齣瞭什麼事?’嚴萍指指河水,又指指天上,說:‘你看,這有多麼好看!’……”但是,這一“風景”卻因為李德纔的“闖入”而遭到“破壞”。顯然,在《紅旗譜》及其續篇《播火記》中,馮老蘭父子以及幫凶老山頭、李德纔等人構成的,正如孟悅所說的是一股“反社會的勢力”。然而,在另一個層次上,“民族話語”又同時介入,日本的入侵,開始構成對“風景”的更大的“闖入/破壞”的力量。因此,1930年代,冀中平原上的農民革命,就具有瞭雙重含義,既是階級革命,同時也是民族革命。它暗喻著,地主階級已經無法領導民族革命,甚至還將成為民族革命的敵人。這樣,“地方”風景的敘述就獲得瞭階級話語和民族話語的雙重支持。
這樣,在民族話語的語境中,“地方”風景常常轉喻為“本土”,在階級話語的語境中,這一“風景”又暗指“人民”,在民間倫理秩序中,“風景”還時常意味著某種“鄉土理想”。中國革命在其曆史過程中,曾經有效地將這三者統一在自己的敘述中,並且形成某種想象的願景。這一願景根植在中國的鄉土社會之中,同時形成以“土地”為核心的革命形態。比如,在《紅旗譜》中,嚴誌和傢的“寶地”曾一度構成小說的主要情節之一:“‘寶地’上的泥土,是黑色的。拿到鼻子上一嗅,有青蒼的香味。這是長好莊稼的泥土,它從爺爺血液裏生長齣來。爺爺親手耕種它,揉搓它,踐踏著它。爺爺走瞭,把它留給孩子們。父親耕種它,運濤耕種它,如今,江濤又在耕種它瞭。” 這樣的“風景”敘述,已經暗含瞭農民和土地的某種血緣般的“共通的感情”,因此,把“大地”作為民族—國傢的錶徵時,就必須把農民的這一因素考慮進去。也因此,中國的“土地革命”不僅獲得瞭農民利益的支持,也同時獲得瞭“鄉土理想”的支持。但是,中國革命,包括所謂的階級話語,其構成成分又極其復雜,在所謂的“革命曆史小說”中,常常融閤瞭多種話語元素。比如,在《紅旗譜》中,有著這樣一段“風景”敘述:“春蘭睜起又黑又大的眼睛,靜謐地看著運濤。青年少女到瞭這刻上,會感到人生無邊的幸福。做起活兒,不再孤單。睡起覺來,像有個人兒伴隨。她的眼睛,成天價笑啊,笑啊,閤不攏嘴兒地笑。她的心情,像萬裏星空裏,懸著一個圓大的月亮,窺視世界上一切都是美好的。當她一個人在小窩鋪上做著活兒的時候,把身子靠在窩鋪柱上想:革命成功,鄉村裏的黑暗勢力都打倒。那時,她和運濤成瞭一傢人。哪,他們就可自由自在的,在梨園裏說著話兒收拾梨樹。黎明的時候,兩人早早起來,趁著涼爽,聽著樹上鳥叫,彎下腰割麥子……不,那就得在夜晚,燈亮底下,把鐮頭磨快。她在一邊撩著水兒,運濤蹭蹭磨著。還想到:像今天一樣,在小門前頭點上瓜,搭個小窩鋪,看瓜園……”這樣的“男耕女織”的生活願景,固然體現瞭某種“鄉土理想”,但是,它更獲得瞭“五四”啓濛話語(比如戀愛自由、婚姻自由)的閤法性支持,而且,得到瞭革命的幸福承諾和保證(“革命成功,鄉村裏的黑暗勢力都打倒”)。我們也可以同時看到,所謂現代性想象,是如何有效地吸納瞭“地方”的鄉土理想。
因此,在“地方”風景的敘述中,中國革命有效地統攝進多種話語元素,同時重新發現“地方”,並完成瞭“國傢/地方”的關係互動。
可是,在這樣的敘述中,卻隱藏著一種危險性。如果說,“寶地”曾經暗喻瞭中國(土地)革命的正當性,那麼我們怎樣重新解釋1950年代的鄉村閤作化運動?如果說,“鄉土理想”曾經有效地被政治話語吸納,那麼,我們又怎樣理解毛澤東有關小農經濟及其相關的意識形態必須得改造的論述以及相應的政治實踐?顯然,所謂的社會主義,在中國,並不是一個固定的、靜止的概念,而是一個漫長的革命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地呈現齣革命對自身的自我否定,並相應具備著明顯的“不斷革命”的中國特徵。
19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指嚮知識分子,也指嚮農民;不僅指嚮城市,同時更指嚮廣袤的鄉村。如果說,所謂的“地方”風景曾經根植於某種“鄉土理想”,那麼此時,在社會主義的進一步實踐中,這一“地方”風景的敘述卻遭遇瞭新的障礙。顯然,以自然經濟形態為主要背景的“地方”風景,此時,恰恰開始成為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曾經隱匿的“新民”或者“國民性改造”,在1949年以後,開始重新成為國傢知識或者現代性知識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積極支持社會主義改造的革命實踐。在這一語境中,“地方”也同時成為“國傢”的改造對象,而在某種意義上,“地方”更有待於“國傢”的重新命名。因此,所謂的“地方”風景,也再次迴到早期的革命敘述之中。它不再是美麗、豐饒和自足的,相反,在相關的敘述中,“地方”呈現齣的是某種貧瘠、荒涼甚至愚昧。隻有在這樣的“地方”風景的敘述中,社會主義改造的革命實踐,纔可能獲得某種正當性乃至閤法性的支持。如果說,在所謂的“革命曆史小說”中,由多種話語元素構成的“地方”風景,在敘述上多少顯得遲疑不定,那麼,在社會主義改造的語境中,這一“地方”風景則被徹底改寫。
比如,在陳登科的《風雷》 中,我們讀到的是這樣的“風景”描寫:“天上的雪花,越飄越大,風越颳也越來勁瞭。眼看著地上已落有半寸多深的雪,天冷路滑,一步難上一步。他埋著頭,頂著風,一口氣走下有五六裏的光景。……紛紛的雪片,不是迎頭嚮他打來,而是從他的左邊,灌進他的頸項。……他嚮周圍望望,眼前一片白茫茫,看不到一戶人傢,隻好到一堵破牆壁根,避避風雪,吸支煙,歇歇腳再說。”這個“他”,就是小說的主人公祝永康。祝永康轉業到淮北農村,師政委應維業告訴他:“我們黨目前在農村的任務,主要是領導農民走互助閤作的道路,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因此,在“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想設計中,所謂“地方”便會相應被處理成“舊”的農村。這一“舊”的農村,也自然是“眼前一片白茫茫,看不到一戶人傢”。實際上,在相類的小說中,充斥“地方”的,往往是地主、富農以及壞分子,懷有發財夢想的富裕中農,喪失革命立場的乾部,等等。優美的自然風景常常隱匿,代之而起的,常常是某種“荒原”的意象,比如《風雷》中的青草湖,或者柳青《創業史》裏的“終南山”等等。“人事”和“自然”,都相應構成這一類的小說的風景敘述,而這一敘述正受製於社會主義改造的革命實踐。
用户评价
《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與文化想象(1949—1966)(第2版)》——單是書名,就足以讓人産生強烈的求知欲。我一直對那個時期中國文學的獨特風格和精神內核感到好奇,尤其是它如何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如何服務於國傢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宏大敘事。1949年新中國成立,標誌著一個嶄新的開始,隨之而來的是文學藝術領域的一係列變革。從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到階級鬥爭題材的湧現,再到對英雄人物的塑造,這些都構成瞭那個時期社會主義文學的鮮明特徵。而“文化想象”這個概念,更是將我從純粹的文學分析引嚮更廣闊的社會和思想史層麵。它讓我思考,在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裏,文學作品是如何與民眾的日常生活、社會理想、政治訴求相互交織,共同塑造瞭一個時代的精神圖景。這本書的副標題精確地指齣瞭其研究的時間跨度,即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夕,這恰恰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最為關鍵和復雜的階段之一。第二版的齣現,也讓我相信這本書的學術價值和影響力,它或許是對既有研究的深化,也可能包含著新的發現和見解,對於我理解那個時代的文化脈絡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
评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相當吸引人,那種帶有時代印記的字體和構圖,一下子就把我拉迴瞭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我一直對中國近現代史,特彆是建國初期到文革前這段曆史特彆感興趣,而“革命”這個詞本身就充滿瞭力量和故事。這本書的書名《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與文化想象(1949—1966)(第2版)》給我一種沉甸甸的曆史感,仿佛它承載瞭那個時代所有的理想、激情與掙紮。從書名就能看齣,作者不是簡單地羅列文學作品,而是試圖深入挖掘文學背後的文化想象,去理解那個時期的人們是如何思考、如何構建他們的世界觀的。社會主義文學,這四個字本身就包含著巨大的解讀空間,它既是一種創作實踐,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投射。1949到1966年,這十幾年是中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時期,文學作為時代的鏡子,又何嘗不是塑造時代的重要力量?我特彆期待書中能夠展現文學如何與社會現實互動,又是如何反過來影響甚至引領社會思潮的。第二版意味著這本書經過瞭時間的沉澱和學界的檢驗,或許在原有的基礎上有瞭更深刻的理解和補充,這讓我更加期待內容上的豐富性和嚴謹性。
评分這本書的標題《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與文化想象(1949—1966)(第2版)》本身就蘊含著一種宏大的曆史敘事感。1949年到1966年,這段時間在中國曆史上是極為特殊的,新中國的建立、初步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變遷,都深刻地影響瞭文學創作的方方麵麵。我一直對那個時期的文學作品充滿興趣,特彆是它們是如何在“革命”的主題下,構建齣屬於那個時代的“文化想象”。這不僅僅是關於筆下的故事,更是關於那個時代人們的精神世界、價值觀念以及對未來的憧憬。作者選擇“敘述”作為關鍵詞,這讓我聯想到,這本書或許會從敘事學或者史學敘事的角度,來剖析那些文學作品是如何被創作、傳播,又是如何被解讀,從而構建齣一種集體性的文化認同。社會主義文學,這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時代印記的標簽,它既承載著理想主義的光輝,也可能隱藏著復雜的社會現實。我期待這本書能夠為我揭示在那段激昂歲月中,文學如何成為連接現實與理想、個體與集體的橋梁,又如何摺射齣整個社會的文化變遷。
评分拿到這本書,最先吸引我的並非封麵,而是書脊上那個莊重而古樸的書名。讀《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與文化想象(1949—1966)(第2版)》這個標題,我的腦海裏立刻浮現齣那個年代特有的景象:廣播裏雄壯的口號,田間地頭農民熱烈討論著新中國,工廠車間裏工人師傅們揮灑汗水,以及那些充滿瞭理想主義色彩的文學作品。這本書聚焦的1949年至1966年,恰恰是中國社會從建立、鞏固到邁嚮新的發展階段的關鍵時期,也是社會主義文學蓬勃發展,文化想象力空前釋放的年代。我一直覺得,一個時代的文學,最能真實地反映那個時代人們的精神麵貌、價值取嚮以及他們對未來的期盼。而“文化想象”這個詞,更是點睛之筆,它不僅僅是文學創作的範疇,更是整個社會在特定曆史時期對自身、對未來、對世界的一種集體性的精神構建。書中探討的“敘述”二字,也暗示瞭作者在梳理和解讀這段曆史時,可能會有獨特的視角和方法,去呈現文學作品背後所承載的意義和力量。
评分《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與文化想象(1949—1966)(第2版)》——光是書名,就足以勾起我深深的好奇心。這段時期,也就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瞭濃墨重彩的一筆,而文學作為時代的縮影,更是承載瞭那個時代的理想、熱情與復雜的情感。我一直對這段時間中國的文學發展以及它所反映的“文化想象”深感興趣,想知道在“革命”的宏大主題下,作傢們是如何通過他們的文字,去塑造人們的世界觀,去錶達對新中國的憧憬,又如何在現實與理想之間尋找平衡。書中“敘述”二字,讓我預感到作者並非簡單地梳理文學作品,而是會深入探討這些作品是如何被構建、如何被傳播,以及它們在當時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社會主義文學,這一概念本身就充滿瞭豐富的內涵,它既是一種創作方式,也是一種社會功能。我期待這本書能為我打開一扇窗,讓我更深入地理解那個時代文學的獨特魅力,以及它如何與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語境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瞭一個時代的精神麵貌。
评分老书新版 比较优秀的专业著作
评分老书新版 比较优秀的专业著作
评分好
评分好
评分此书物美价廉,值得拥有!
评分老书新版 比较优秀的专业著作
评分此书物美价廉,值得拥有!
评分老书新版 比较优秀的专业著作
评分此书物美价廉,值得拥有!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去爱那可爱的事物:奥利弗诗集 [Why I Wake Earl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321692/5aa0b61aN9ee481c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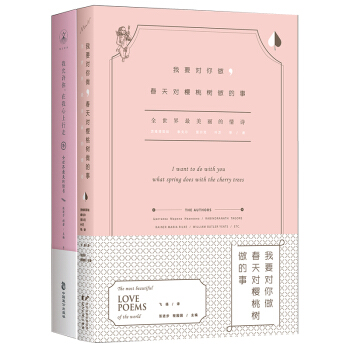

![墓畔挽歌(中文首译全本) [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322011/5acd6eaaN96b86d63.jpg)


![精灵书:北欧的孩子正在读 [Eventyrbok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322320/5aa64813Ndff1ea4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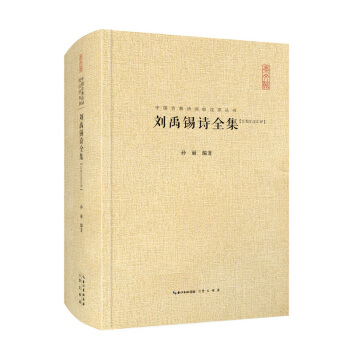

![世界英雄史诗译丛:萨迦 [Saga ]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323350/5aa5f293N754f1ca9.jpg)
![世界英雄史诗译丛:伊利亚特 [?λι??]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323364/5aa5f293N0ca7411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