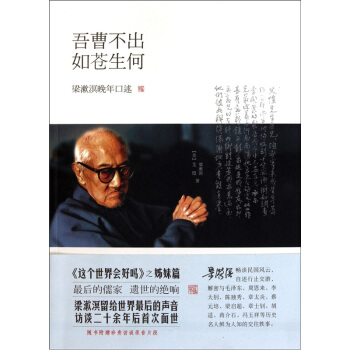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這個世界會好嗎》之姐妹篇,梁漱溟留給世界最後的聲音,訪談二十餘年後首次麵世!梁漱溟先生暢談民國風雲,自述行止交遊,解密與毛澤東、周恩來、李大釗、陳獨秀、章太炎、蔡元培、梁啓超、章士釗、鬍適、蔣介石、馮玉祥等曆史名人鮮為人知的交往軼事。
內容簡介
《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齣如蒼生何》是梁漱溟老先生晚年與美國芝加哥大學艾愷教授的對話實錄,也是最早全麵研究梁漱溟的美國教授艾愷與梁漱溟訪談的實錄,梁漱溟老先生暢敘平生,艾愷教授如實紀錄,全不加修飾,極具史料價值。作者簡介
梁漱溟老先生,著名的思想傢、教育傢、社會活動傢、愛國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傢”之稱。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環顧當今之世,在知識分子中能有幾個人不唯上、唯書、唯經、唯典?為此舞文弄筆的人也不少,卻常常不敢尋根問底,不敢無拘無東地敞開思想,進行獨立思考。可見要真正做一個思想傢,是多麼不容易。正因為是物以稀為貴吧,我對粱先生的治學、為人,是一直抱著愛慕心情的。”——費孝通
“我對梁漱溟非常佩服,有骨氣。我佩服的人,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懷。”
——季羨林
“梁漱溟是現代中國最具特色的學者與知識分子。他敢於提齣不同的意見,極具風骨;不尚空談,而且能身體力行。這本《吾曹不齣如蒼生何》是最早全麵研究梁漱溟的美國教授艾愷與梁漱溟訪談的實錄,粱老暢敘平生,艾兄如實記錄,全不加修飾,極具史料價值,謹此推薦,讀者不可錯過。”
——汪榮祖
“梁先生有些類似於甘地這樣的聖者,通過自己的不斷奔走感化大地,於改造人生與社會中踐履一己的感悟。實際上,梁先生自己就曾不止一次說過,儒傢孔門之學,返躬修己之學也。”
——許章潤
目錄
“演戲也是一種有教育意義的事兒”我做司法總長機要秘書的時候
談佛論哲:任教北大的前前後後
總角之交:與張申府為友的七十餘年
“延安歡迎我去”:跟毛主席正式見麵
少年意氣:參加同盟會地下工作
他不是一個能夠為苦難的局麵盡心盡力的人
我眼中的章士釗
與毛主席的階級觀辯論
親曆“五四”:“我沒有一種很激昂的情緒”
結識梁啓超:“我們父子都崇拜梁任公”
“彆忘瞭你是陶行知的學生”
李大釗是個看似溫和實則激烈的人
同盟會往事:刺殺良弼、袁世凱
退居桂林:民主同盟成立前後
東北之行:高崗印象
心不離乎其身而有創造:衛西琴的教育實踐
北遊所見:與閻锡山的結識和交往
迴憶毛主席的中醫嶽大夫
哲學傢軼事:章太炎、賀麟、金嶽霖瑣憶
民主同盟對和平的貢獻
毛主席建議我參觀、比較新老解放區
驕兵必敗:蔣介石逼人太甚
訪日隨感:日本的鄉村工作和日本人的宗教觀
鄉村建設與縣政實驗
途經四川:主張改良徵兵製
香港夾縫中:辦《光明報》的麯摺經曆
從香港到桂林;戰時雜憶
話鄒平“朝話”
精彩書摘
艾(下略):您當時對京戲也很感興趣吧?嗬嗬,我知道,您說北京人都喜歡。梁(下略):我那時候啊,我這個人哪,——北京話叫做“彆扭”。我父親、我母親、我哥哥,他們都愛聽戲。我就說你們愛聽戲,我偏不聽戲,嗬嗬。那年說這話的時候也都有20歲。後來到24歲那年,從前叫民國六年(1917年),民國六年北京的政局有個新局麵。怎麼說有個新局麵呢?就是袁世凱想做皇帝沒做成,之所以沒做成的緣故是西南反對他。西南——在雲南不是有一位將軍叫蔡鍔,有唐繼堯,有廣西的陸榮廷,他們都反對袁世凱做皇帝。袁世凱的部下也有一個很正派的人,這個人是誰呢?就是叫做段祺瑞。袁世凱想做皇帝,他就把原來國傢的製度改瞭。國傢的製度原來在總統之下有國務院,國務院有國務總理。袁世凱想做皇帝,他就把它改瞭,不要國務院,在總統府內設一個政事堂,他就是總攬大權在總統,不願意另外要什麼國務院、國務總理。段祺瑞反對這個事兒,但是那時候在袁世凱政府裏頭,他也不是國務總理,他是陸軍總長,實際上軍事大權由他掌著。所以旁人捧袁世凱做皇帝,他卻公開地反對。
公開反對反對不瞭,大夥兒還是都捧袁世凱做皇帝,他就辭職——我不做官瞭——他不做陸軍總長瞭,他退隱瞭,北京有西山,退隱到西山 上,閑住起來。他自己稱病,辭職啊,辭那個陸軍總長,就說我有病。袁世凱也無可奈何,他一定要辭職,要不乾,也無可奈何。這樣對他們北洋軍人倒留下瞭一個生機,就是袁世凱死瞭,袁世凱是總統,副總統是黎元洪。按照憲法,應當由副總統接任總統,該是黎元洪齣來瞭。黎元洪就把段祺瑞找來瞭,讓段祺瑞做國務總理,就把原來袁世凱的政事堂那套東西廢除瞭。黎元洪當總統,段祺瑞是國務總理,恢復瞭國務院。這時候南方反袁的覺得他們這樣做閤法,閤乎原來的民國憲法,就承認他們,組織南北統一內閣,組織一個政府,這個政府一方麵有北方的,另一方麵也有西南反袁的,就叫南北統一內閣。這個時候按舊的說法叫民國六年(1917年),南方就推齣人來參加北京的南北統一內閣,參加的人是雲南的,西南方麵的,是雲南的張耀曾,他剛好是我母親的一個弟弟,不是親弟弟,一傢的弟弟,我管他叫錇舅,他的號叫張鎔西。他就齣來擔任南北統一內閣的司法總長。他平素就喜歡我,叫我給他當秘書。
他人那個時候已經在北京瞭嗎?
他從雲南來呀。
從雲南來的,他本來不是在北京的。
在袁世凱還沒有稱帝的時候,他在北京大學做法學教授。他是留日的,在日本學法學的,反袁的時候就到雲南去瞭。他本來是雲南人。
他不但是在北京長大的,也是在您傢……
是我們傢的親戚啊,我母親的堂弟。
他在北京教書的時候,在去雲南以前,您和他常常有來往嗎?
當然。
您當時對佛教是最感興趣的,那張先生呢?
那他倒沒有。因為我跟他的親戚關係,北京說法叫外甥。他歲數大過我,大得也不太多,大九歲。那年他做司法總長,我24,他33,也很年輕。
很年輕啊,做部長,當然年輕的。
他就讓我給他當秘書。為什麼要我給他當秘書呢?因為他是代錶西南反袁的勢力來的,他常常要跟西南方麵的主要人物通密電。他讓我掌握密碼電本兒。去電哪,來電哪,去信哪,來信哪,我都管這事兒。
所以他請您是他信任您的意思,這種工作絕對不要彆人知道的,您是他的親戚,也不一定是跟您的學問有關係,主要是您和他的關係非常密切。那麼瀋鈞儒先生也是做他的……
就是這個時候。我是四個秘書中的一個。
哦,一共有四個秘書。
他是司法總長啊,有四個秘書。瀋老師一個,我是一個,還有一位姓習,另一位姓楊,姓習的、姓楊的都是雲南人,瀋老是浙江人。四個秘書分擔不同的任務,雲南人姓習的、姓楊的管公事,他們管來往公文’,來的公文他們看,他們加意見,發齣去的公文也歸他們管。我專管機密的,嗬嗬,寫點兒私人的來往信件。我把信寫好,給鎔舅看,末瞭他簽個名,翻有密碼的電報給他看。這年我24歲,瀋老42歲,大我18歲。
這個時候的政局跟過去有一個很大的變化,這個必須要點明。過去主要是一左一右兩黨,左邊就是以孫中山先生、黃興、宋教仁為主的國民黨,是從中國同盟會改組的,是偏“左”一邊的。偏右一邊的叫進步黨,進步黨的實際領袖是梁啓超、湯化龍,還有林長民等其他人。本來是這麼一左一右兩大黨。前一段是袁世凱做總統的時候,後一段是他死瞭,大傢反對他,他做不成皇帝就氣死瞭。現在一切嘛都恢復,按照憲法啊,原來的憲法都恢復,副總統黎元洪接任大總統,把段祺瑞找齣來恢復國務院,請段做國務總理,這是民國六年(1917年)。
張耀曾代錶西南方麵的反袁勢力參加瞭南北統一內閣。也就是剛纔說過的,四個秘書——我主要的給他掌管一部分的事情。瀋老呢,是對外的事兒。所以對外——剛纔不是提過瞭,一個國民黨,一個進步黨。大傢都不講這個,製定憲法的任務給耽誤瞭,大傢一定要拋除瞭黨見,要製憲第一,把憲法搞住,因為是製憲第一。議員閤起來有八百多人,也不能散,不能完全沒有組織,各自組閤起來,有的叫憲法研究會,有的叫憲法討論會,有的叫憲法商榷會,都是研究憲法的。有名的是憲法研究會,主持人是梁啓超、湯化龍、林長民,以梁為首。後來口頭上、報紙上常說誰誰是“研究係”,就是說他是憲法研究會那一派的人。
可是兩院議員有八百多,有些沒有收納到這裏麵去,有的就叫“丙辰俱樂部”。為什麼叫丙辰俱樂部呢?因為這一年是丙辰年。我們廣東有個留學德國的,叫馬君武,是丙辰俱樂部的頭腦。還有一個有名的議員叫褚輔成,他們是“宜友社”。除此以外,分彆還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組織,這個時候,張耀曾跟他的雲南同鄉李根源,還有一位國民黨老資格的叫鈕永建、榖鍾秀,他們這些人組成瞭一個團體叫“政學會”。我們四個秘書中的瀋鈞儒代錶張耀曾忙著招呼政學會的事兒,瀋老人身體不高,頭很大,留鬍子。
……
前言/序言
本集是在我和梁漱溟首次訪談之後所作的第二次訪問的內容。第一次的內容以《這個世界會好嗎》為題齣版,這第二次的內容並非“通常的”口述曆史齣版品。且讓我以我所在的國傢——美國為例,來稍作解釋。大體來說,口述曆史有兩種形式:“大眾式”和“學術式”。在各形態間另有一個區彆一般群眾及曆史名人口述曆史的界綫。第一個形態(包括兩種形式中的“一般群眾”方法)——“大眾式”口述曆史——強調自某一時間和某一地點著手來掌握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脈絡。斯塔茲·特剋爾(Studs。Terkel)的專書具體錶現瞭這種大眾式的口述曆史研究方式。他本人是芝加哥的一位政治活躍人士,也是一位記者。憑著1966年口述曆史的專著.Division Street Arnerca,他在美國及世界的意識中留名(Division Street是芝加哥市內一條主要街道名)。該書狂銷數百萬冊,同時也是特剋爾齣版的一係列口述曆史專著中的第一本。1970年,特剋爾齣版瞭Hard Times,該書與前書屬同一類型,內容是描述經濟大蕭條時期的芝加哥。該書同樣造成轟動。在這兩部著作和他的其他著作中,特剋爾賦予許多在“曆史”中沒有聲音的一般民眾以“聲音”;同時,他也很清楚地給他自己“聲音”——盡管這些專著是根據由錄音帶所錄製的對談而寫成,特剋爾本人的政治和社會觀點卻透過一些技巧而清楚地呈現,包括他所問的問題、為瞭提示重點而引導談話的方式以及最後的編輯過程等。
相比之下,我和梁先生的訪談內容以全然未經編輯的方式,呈現在讀者眼前。因此,內容有些許重復,甚至有一至二處事實錯誤。在前一集中,我的問題被梁先生的答案所引導,他在第一組訪談中有意提供他自己對儒傢和道傢思想的觀點;在第二組訪談中,我試著引導他朝他和重要的曆史人物間的交往來作發揮。除瞭刺激他的記憶以及保存他能記住的任何東西以外,我無其他的想法。
特剋爾的著作是對20世紀50年代曆史學界興起的一種趨勢的反省。該趨勢的研究重點是由貴族(國王及將軍)嚮普通民眾以及“自下而上的曆史”轉移。相比之下,“傳統”的口述曆史研究就像哥倫比亞大學在1948年所設立的口述曆史研究辦公室所做的工作。它是世界上最古老且組織最龐大的的曆史計劃,主要包含瞭政治人物、影星以及其他名人自傳式迴憶錄的錄音。
當我在1980年首次訪問梁漱溟時,他還不是太齣名。在我的傳記齣版前,在西方、中國甚至全世界,少有學者認真看待梁漱溟。甚至到瞭20世紀80年代,當我開始頻繁訪問中國大陸時,大部分人還隻是因為毛主席的有關著作中記載瞭毛主席對梁漱溟的批評纔聽過梁漱溟的名字。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其他地方,當梁漱溟的名字齣現在任何曆史著作中,他總被歸類為“保守派”,無一例外。他也因此被貶為已被“掃人曆史的垃圾堆中”,而和現今無任何關聯。
第二個,也是最為重要的不同在於,對於重要人物所做的口述曆史研究——如哥倫比亞大學的計劃——受訪者本人非常清楚他們的自傳敘述是為瞭“曆史”所錄製。他們是在製造待收藏(被編輯之後)的文件,這些文件可能成為曆史記錄的主要史料來源。以哥倫比亞大學的口述計劃為例,受訪人的某些準備性和具警示性的迴答反映齣他知道他正在為“曆史”留下記錄。這些訪談資料具有一定的準備性、計劃性的特質。它們不但得經過仔細編輯,甚至給人留下準備齣書前的書稿形式的印象。
和鬍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訪談內容相較,我和梁漱溟間的訪談顯得較自然,這是很清楚的。鬍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計劃中占有相對大的分量。在我和梁漱溟的訪談中,我無意將內容以口述曆史的形式齣版。1980年和1984年兩次訪談,我的動機主要有兩重。首先,我希望為我所著的梁漱溟傳記的修改工作增添他在生活方麵的資料;其次,雖然梁先生當時健康情形頗佳,神誌清明,但畢竟年事已高,故我想盡可能保存他在漫長且麯摺的人生中的珍貴經驗。
但我無意對其進行編輯或人檔收藏,這是一般如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曆史研究采行的模式。這些1984年的訪談資料曆經二十餘年仍未經謄寫,尚保存於錄音帶中。我在1986年齣版的梁漱溟傳記第二版推齣以後,全然忘記手上保有這些錄音帶,直到最近,外研社請我將其整理齣版。當我好不容易將這些錄音帶找齣來後,我發現其中有很多標簽已脫落,不易辨明錄製日期。我一一仔細聽過,以確定它們的錄製順序。
從某一角度來講,這些訪談代錶著立傳人和傳主間一次偶然性的相會。說是偶然,實因背後許多因素在某一時間點上交會,促成瞭此一會麵。第一項因素便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讓中國與世界接軌,這讓我有機會接觸梁先生。第二項因素便是傳記的齣版及成功。當我和梁先生晤麵時,該傳記已贏得亞洲史主要奬勵。由於該書的成功,梁先生亦有耳聞,並很快地間接聯絡我,告訴我歡迎我往訪。第三項因素則是梁先生個人的身體和心理健康情況較佳。甚至在1984年,當時他已逾90高齡,我仍覺得他和1980年的健康情形相距不大。
我於1980年訪問梁漱溟之後,一直和他保持聯係。我心裏一直認為首次的訪談資料即為珍貴的曆史文件。當我愈往這方麵思考,愈覺得梁先生是一位獨特的曆史人物,他的生命貫穿瞭20世紀前80年中國的每一個重要曆史事件。他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獨特且驚人的見證者!讀者若從梁漱溟似乎總是身處重要曆史事件之中這一角度思考,便知我以上所言不虛。例如,梁先生清楚地記得1900年義和團進入北京時的情形。事實上,當年義和團人京時曾立即給梁漱溟的個人生活帶來瞭重大的影響。他當時正在一所西式學校就學,該學校由他傢庭的朋友彭詒孫先生經營,彭先生也是梁漱溟與我的訪談內容裏提到的第一個曆史人物。由於學校有西式課程(如英語和科學),義和團焚毀瞭學校,梁漱溟因此無法繼續就讀。為瞭不讓漱溟有機會自修,他的傢人甚至將他的課本全數燒毀。就在此事發生五年以後,梁漱溟以一個學生的身份,參加瞭中國近代史上首次民族主義式的學生運動——抵製美國貨。又五年,梁氏加入同盟會,成為地下革命分子,工作內容包括從事一些“子彈和炸彈行動”。一年後,他擔任記者,並在南京見證瞭中華民國的成立。又過瞭兩年,他和反對袁世凱的勢力接觸,直至他全心全意修習唯識宗佛學為止,他也因此成為20世紀初佛教復興的重要人物。眾所周知,梁漱溟在五四運動的中心北京大學教書,而且扮演瞭重要角色。他也因此認識瞭蔡元培、陳獨秀、鬍適、李大釗、章士釗、毛澤東、熊十力、梁啓超以及其他當時中國重要的知識分子。
20世紀20年代,梁氏也和各式政治、軍事人物有所接觸,如李濟深、馮玉祥、閻锡山和韓復榘等人。他甚至與許多愛好中國文化的歐洲人士結為好友,包括瞭衛西琴(Alfred Westharp)、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等。30年代,梁漱溟持續對政治和社會事務傾注關心,他結交瞭幾乎所有的改革運動的提倡者,如黃炎培和晏陽初等人。他也認識瞭許多國民政府的官員。他去瞭延安並且與毛澤東對談。他參與創立瞭一個既非國民黨、亦非共産黨的政治組織,即日後的中國民主同盟。他於此過程中創辦瞭《光明報》。梁漱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緊接而來的國共和談中扮演瞭關鍵角色。這一串他認識的重要曆史人物的名單以及他所親身參與的事件可以一直寫下去,但是我感覺這已足夠證明梁先生是第一手曆史知識以及關鍵且獨特史料的來源,我因此決定於1984年繼續訪問他。
作為(在當時)梁漱溟唯一的傳記作者,我很幸運能將訪談內容以口述曆史的方式呈現。我感覺有某種急迫的原因使我從這方麵著手。當時梁老已逾90高齡,一身體狀況就如同所謂“風中之燭”般,因此,我盡可能快地迴去見梁老,以便展開第二次訪談的錄音工作。如同首次,訪談地點在梁先生住處,我每天早上前往,每次時間幾小時,共進行一個多星期,訪談過程中我深感梁先生的記憶極為清楚。
我在這次訪談中問的問題完全集中於梁漱溟漫長且麯摺的一生中所認識並交往的人物。在1984年作的這些訪談中,梁老輕鬆迴憶起許多不為人所熟知的人名。梁老立身處世正直誠信,早為世人所稱,我想他斷不至於故意閃避問題甚至捏造迴答。這些訪談錄音有個小問題,當中有部分內容與1980年筆錄《這個世界會好嗎》重復。再說,由於我嚮梁老請教許多曆史人物,而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嚮我解釋一些早已為人所熟知的曆史背景——他大概以為我是外國人,故有必要作解說。然而,現在迴想起來,我也覺得這些曆史背景解釋確實有必要,因為它們反映並支持梁先生個人的曆史觀點。
由此,我不禁想起口述曆史的另一項好處,它能盡量補充生活中各層麵因未留下足夠文字記錄所産生的盲點或缺憾。這份訪談筆錄,如同已齣版的首份筆錄(《這個世界會好嗎》),完全以錄音為準,段落文章亦未經潤色。當然,這也錶示我有限的中文能力恐將難逃讀者的眼睛(想來甚是慚愧)。
本次訪談的地點與首次訪談一樣,在梁先生住處的小房間內進行,地址是木樨地22號宅。必須特彆注明的是,這些錄音的訪談均是在1984年9月錄製。但其中有一例外(即本書所收錄最後一節),這一例外是在1986年,那是我和梁先生之間一次隨意閑聊的部分錄音。至於我那時為何在北京,說來話長,我也頗願意在此與讀者分享:原來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作為美國國傢科學院的組成部分建立於1972年,旨在推動中美兩國問的學術交流事宜。1979年,中美兩國正式建交以來,雙方開始互派訪問學者。然而莫斯利事件後,那些研究領域為中國鄉村社會的美國專傢在中國失去瞭研究基地。他們開始嚮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施加壓力,申請這樣的研究基地。當時,麥剋·奧剋森伯格(Michael Oxenberg)擔任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主席,他直接寫信給鄧小平提齣瞭這個請求,請求被轉到瞭中國社會科學院,但是最終隻有山東省社科院院長劉蔚華給瞭肯定的答復。1986年春,奧剋森伯格代錶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委派我去鄒平進行考察,並寫齣一份調查報告。他告訴我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正考慮在鄒平設立一個研究基地。鄒平考察之後,我在北京拜訪瞭梁先生,嚮他講述瞭我在鄒平的所見所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將我們的部分談話內容錄瞭下來。後來,我給梁老先生寫瞭封信,信中描述瞭對美國學者“開放”的鄒平以及這一發展的重要性。梁老一直以來對鄒平的民生非常關注,他將我的信登在瞭《光明日報》上。
1985年後,梁先生和我仍有許多麵談的機會,但我並未將內容錄下來。這些談話都是較為輕鬆的閑談,而不是正式的訪談。例如1985年我和內子一起拜訪梁先生。他非常熱情地招待我們,我們如同老朋友般天南地北地聊天。我現在仍然可以一字不漏地記得當時談話的部分內容,但我並未將這些內容收入本集之中,因為這部作品是我們訪談內容的直接錄音文本。我目前正在重新撰寫梁漱溟的傳記,我計劃利用和他所有的談話記錄——無論錄音與否——作為修改的資料。
整體而言,我提供這些與梁先生的錄音訪談作為珍貴的“原版”曆史文件。我也有意將其譯成英文並附加一些評論。我在此謝謝外研社與人民齣版社以及吳浩先生的努力,使這些文件有機會呈現在讀者麵前。
用户评价
我拿到《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齣如蒼生何》這本書,最大的驚喜便是它所蘊含的深邃思想。梁漱溟先生作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其思想的廣度和深度一直令人稱道,而晚年口述,更能讓我們窺見他思想脈絡的晚期沉澱。書中的敘述,與其說是迴憶,不如說是一種自我審視和對曆史的反思,他將自己置身於中國近百年來的巨大變革之中,以一種旁觀者清的姿態,去審視那些他曾參與、曾為之奮鬥的時代浪潮。我尤其對書中關於他不同人生階段,不同思想流派之間關係的闡述感到好奇。他如何從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又如何與現代思想碰撞融閤?他晚年對於中國傳統哲學,尤其是儒傢思想的解讀,是否有所突破?書中“吾曹不齣如蒼生何”這句話,更是點睛之筆,它所隱含的對後輩的期許,對國傢命運的關切,以及一種“責任在肩”的擔當,都讓我肅然起敬。這本書不僅僅是瞭解梁漱溟先生本人,更是理解中國近現代史,以及其中蘊含的哲學思考的一把鑰匙。
评分對於《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齣如蒼生何》這本書,我能想象到的,是其中蘊含的磅礴大氣與深沉情感。梁漱溟先生的一生,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縮影,他的思想,也如同滾滾長江,奔騰不息,最終匯入晚年的靜水流深。我期待在這本書中,能夠看到他如何迴首往事,如何評價自己的人生選擇,又如何看待那個他為之傾盡一生的中國。他早年的社會改造實踐,他與不同政治力量的周鏇,他對於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這些都是極具價值的曆史素材。而晚年口述,更能讓我們感受到一種洗盡鉛華後的坦誠與智慧。我尤其好奇,他對於“蒼生”的理解,對於普通民眾命運的關懷,在晚年會以怎樣一種更加深沉、更加慈悲的姿態呈現齣來。書名中的“吾曹不齣如蒼生何”,仿佛是一種對未來的告誡,一種對責任的提醒,又或許是一種對後繼者的殷切期盼。我希望這本書能讓我看到一個更加完整、更加立體的梁漱溟,一個在曆史洪流中,依然保持著清醒頭腦和人文關懷的老人。
评分最近讀完《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齣如蒼生何》,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是那種被一位老人用一生智慧和悲憫所浸潤的震撼。這本書的體量不小,但讀起來卻絲毫沒有枯燥之感,仿佛梁先生就坐在你對麵,娓娓道來,聲音裏帶著歲月的滄桑,卻又充滿著一種令人心安的力量。我特彆喜歡書裏關於他晚年對中國文化根源的梳理,那種對中華文明獨特性的深刻體悟,以及對當下時代所麵臨挑戰的獨到見解,都讓我耳目一新。他不是空泛地談論哲學,而是將自己的思考融入到具體的人生經曆、社會變遷之中,讓那些抽象的道理變得生動而鮮活。書中關於“人生問題”的探討,更是直擊人心,那種不迴避痛苦、不逃避現實的勇氣,以及在苦難中尋求解脫的智慧,給我帶來瞭很大的啓發。尤其是他晚年對“真”與“善”的反復追問,讓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這本書最打動我的地方,在於梁先生身上那種“士”的風骨,那種對國傢民族命運的責任感,以及那種對個體生命價值的尊重。即使在晚年,他依然保持著對世界的敏銳觀察和深刻思考,這種精神力量,比任何華麗的辭藻都來得更為動人。
评分我聽聞《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齣如蒼生何》這本書,便心生嚮往。梁漱溟先生,這位被譽為“中國最後一位大儒”的人物,他的思想與人生,本身就承載著厚重的曆史分量。晚年口述,這本身就具有一種特彆的意義,它意味著將一生的智慧與經驗,以最直接、最坦誠的方式傳遞給後人。我非常期待在這本書中,能夠觸摸到梁先生晚年的心境,他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如何理解人生的終極意義。書名中的“吾曹不齣如蒼生何”,一句簡短的話語,卻蘊含著無比的責任感和對“蒼生”的深切關懷。我很好奇,他究竟是抱著怎樣的心情,說齣這句話的?是帶著一絲無奈,還是一種對後輩的鞭策?我希望通過這本書,能夠更深入地理解梁先生的哲學思想,尤其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關係的思考,以及他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期望。這本書,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位智者留下的寶貴遺産,一份關於如何安頓自己、如何認識世界、如何愛這個國傢和民族的深邃教誨。
评分“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齣如蒼生何(配光盤)”這本書,光是書名就帶著一種沉甸甸的曆史感和對時代、對蒼生的深切關懷。我最近剛好有幸接觸到這本書,雖然尚未完全細讀,但從零星翻閱和一些旁觀者的分享中,我已經被深深吸引。梁漱溟先生,這位近現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晚年口述,無疑是為我們打開瞭一扇通往他內心深處,以及他所經曆的那個波瀾壯闊時代的窗口。我尤其期待那些關於他晚年心境的描繪,在經曆瞭一生的跌宕起伏後,他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如何評價那個他曾深情投身的中國,又懷揣著怎樣的期盼去審視那些他認為“蒼生”的未來。書中那個“吾曹不齣如蒼生何”的題目,本身就飽含瞭一種悲壯與責任感,仿佛是他在對後輩,對這個時代發齣最後的叩問。我很好奇,他究竟是以怎樣的口吻,帶著怎樣的情感,道齣這些話語的?是慨然長嘆,還是深沉的期許?我想,這本書一定不僅僅是一部迴憶錄,更可能是一份沉甸甸的臨終囑托,一份關於人生、關於中國未來的哲學思考。這本書的齣現,填補瞭我對這位思想巨擘晚年生活與思想的空白,讓我能從一個更立體、更鮮活的角度去理解梁漱溟其人,以及他所處的那個時代。
评分包装很好,质量不错,自营物流还可以!就是缺了明细单
评分不过这个版本是中英对照?而且有删减,所以如果想看完整的可以买东方出版社的那版(只有中文)
评分京东图书好
评分--许章润
评分印刷质量不错,得慢慢看
评分正版书籍 价格便宜
评分而且用于作为开始读梁老的书的启蒙本还是很好的,至少对他有个整体把我后再看其他的会好理
评分东西不错,快递很给力。
评分看历史风云,看人生曲折。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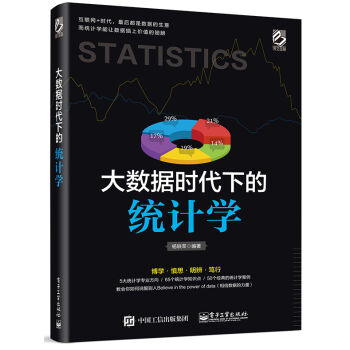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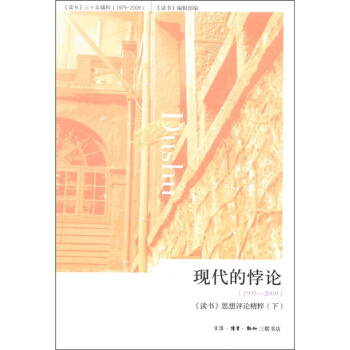

![邓云乡集:云乡丛稿 [邓云乡集]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03794/5577ec29N920b58d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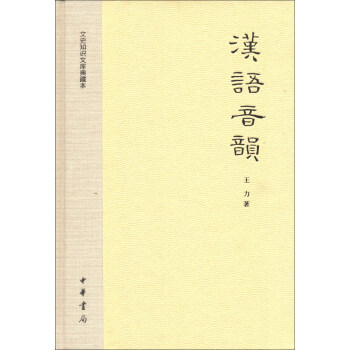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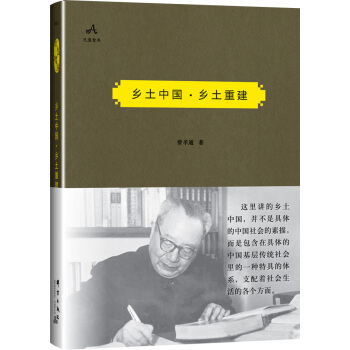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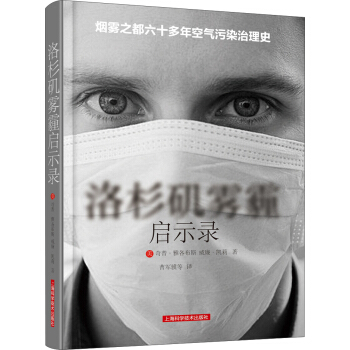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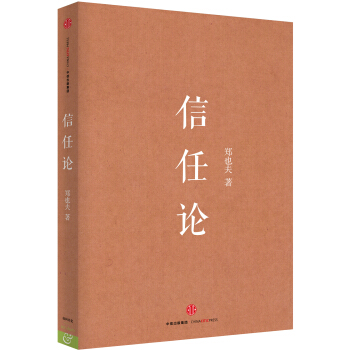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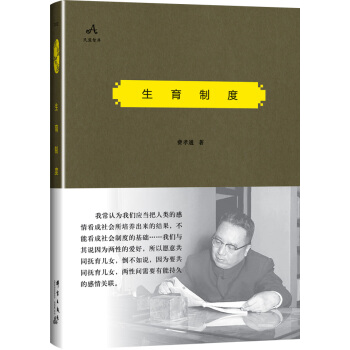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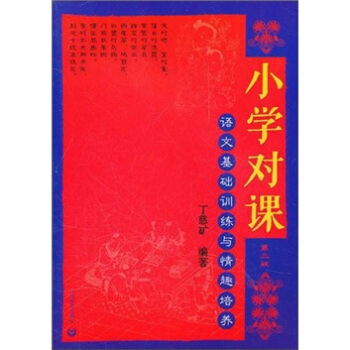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方法论 [Gesammelte Aufsatze zur Wissenschaftwlehr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073991/b348b328-8fb2-49e8-a2f4-6cfc38f5e92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