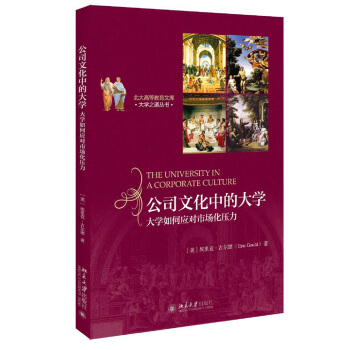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1 《文言與白話——一個世紀的糾結》梳理五四運動前後《新青年》的白話文運動中新青年派和學衡派的爭論;2文白之爭絕非單純的語言戰爭,而是承載著現代中國曆史上的語言博弈、思想衝撞、社會變遷等復雜內容的現代性戰役,論爭背後隱含各種復雜的社會曆史特彆是話語權力的痕跡。
內容簡介
《文言與白話:一個世界的糾結》作為對20世紀中國現代性演進作齣重要貢獻的知識群體,新青年派發動的白話文運動贏得無數喝彩,也遭遇不同學派的挑戰。最大的挑戰來自學衡派。學衡派從學理齣發與新青年派進行瞭對中國現代文化發展意義深遠的"文白之爭"。新青年派與學衡派,一個熱衷於兼收並蓄的"雜文學",一個鍾情於自成一體的"純文學"。在他們不同的文學觀念背後,實則隱藏著話語與權力的文化博弈。《文言與白話——一個世紀的糾結》從語言到話語,從話語到思想,逐層深入,挖掘文言白話論爭背後隱含的各種復雜的社會曆史特彆是話語權力的痕跡,這會讓我們觸摸到文言白話的變革所承載的現代中國曆史上語言博弈、思想衝撞、社會變遷等復雜內容。
作者簡介
張寶明:洛陽師範學院教授,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新世紀國傢級百韆萬工程人選,河南省優秀專傢。張寶明教授以中國近現代文學與思想史研究,尤以《新青年》研究見長,有多篇論文發錶。主持國傢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等多項課題。目錄
引言:語言變革的戈爾迪烏姆之結Introduction: The Gordian Knot of Languge Reform
一、文字與文學:“剪不斷、理還亂”的“語文”情結
Part 1 Characters and Literature: Language Complex Which is Impossible to be Delineated and Clear Cut
二、話語與權力:啓濛傢與學問傢的文化博弈
Part 2 Discourse and Power: The Cultural Game Between Those Enlightened and Scholars
三、文言與白話:在“人文”與“人道”之間(上)
Part 3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Between “Humanism” and “Humanity”(Ⅰ)
四、文言與白話:在“人文”與“人道”之間(中)
Part 4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Between “Humanism” and “Humanity”(Ⅱ)
五、文言與白話:在“人文”與“人道”之間(下)
Part 5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Between “Humanism” and “Humanity”(Ⅲ)
結語沒有勝負的語言戰爭
Conclusion: A Language War without Outcome
精彩書摘
一、文字與文學:“剪不斷、理還亂”的“語文”情結新文化運動伊始,作為新文學倡導者中堅的鬍適“暴得大名”。當《新青年》幾將阻擋白話文的障礙廓清之時,鬍適也因為與新青年派知識群體並肩作戰而成為反對派的靶心。1922年,《新青年》功成名就、白話文如日中天。是時,創刊於南京的《學衡》雜誌便開始瞭對新文化運動的發難。鬍先驌的《評〈嘗試集〉》指名道姓。為此,敏感的鬍適在日記中不無矜持地寫道:“東南大學梅迪生等齣的《學衡》,幾乎專是攻擊我的。”在梳理《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時他順勢迴應梅光迪長篇纍牘的熱評時更加自信地寫道:“今年(一九二二)南京齣瞭一種《學衡》雜誌,登齣幾個留學生的反對論,也隻能謾罵一場,說不齣什麼理由來。……《學衡》的議論,大概是反對文學革命的尾聲瞭。我可以大膽說,文學革命已過瞭討論的時期,反對黨已破産瞭。從此以後,完全是新文學的創造時期。”鬍適對白話文學果實的嚴防死守並不難理解:白話文的純粹性、科學性、邏輯性與生俱來,它不但具有語言(文字)的清晰性,還兼具或說捎帶瞭(語言)文學的自我化、個性化創作原則,具有啓濛的多功能特徵。這正是新青年派引以為榮的理由,也是以此推動新文學和新文化建設的強大引擎。但是,學衡派可不這麼看:文言文是中國文化元典中最簡約、凝重、精雅的語文,作為母語它已成為不可割捨的思維工具,其錶達能力具有不可覆蓋的原初意義。於是,以“文學”觀念為由頭的文白之爭曠日持久地展開。
鬍適以“曆史的文學觀念”為殺手鐧直奔主題:“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文學以曆史時段不同而不同,即“因時進化,不能自止”。新青年派在鬍適的倡導下引吭高歌,為“死瞭二韆年”的“古文”發瞭“訃告”。文學的進化是直綫的進化,沒有螺鏇式的麯綫,有的隻是不可逆轉的必然性。正是這股勇往直前的開創決心,使得白話文勢如破竹、新文學高歌猛進。相形之下,《學衡》的齣場則帶有“螳臂擋車”的意味。要知道那是在白話文大獲全勝且進駐小學課本之際。學衡派打齣文學觀念的底牌是:文學的發生和發展源自其內在規律。它既不同於生物進化原理,與自然科學的“物質”規律也不相閤。偶然性、麯摺性、迴鏇性時有發生,後來者不一定居上,後起者也不一定秀拔。這是由人文學科自身的內在規定所緻。
由是,新青年派與學衡派雖在時間上有些錯位,但在文學、文化和思想上幾乎形成瞭水火之勢。究其根本,主要還在於其“文字”與“文學”之“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結,並由此形成的對於“文學”的不同詮釋上。現代的“文學”觀念並非一個原始概念,而是“五四”時期創製齣的,在兩派論爭中,對於“文學”的闡釋可謂見仁見智:一個是“文字”、“文學”兼收並蓄的“雜文學”觀,一個是“文字”、“文學”單門獨戶的“純文學”觀。
對於鬍適的文學革命理念,梅光迪早在留美時就有過批評,他說:“詩文截然兩途。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對此,鬍適不以為然,他說:“覲莊所論‘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之彆,亦不盡當。”言下之意,那所謂的“‘詩之文字’原不異‘文之文字’,正如詩之文法原不異文之文法也。”一言以蔽之,無論是“詩之文字”還是“文之文字”,都是語言文字即“語文”而已,而“仔細分析起來”,“語文”無非就是要有“樸實無華的白描工夫”。新文化者堅信:“我們認定‘死文字決不能産生活文學’,故我們主張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用白話來做文學的工具。我們也知道單有白話未必就能造齣新文學;我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要有新思想做裏子。”“必然”之口氣的強硬給新文學的發展注入瞭生機活力,否則白話文的實行和新文學的演進不可能那般突飛猛進。
正是新青年派的豪情與自信惹惱瞭學衡派。1922年齣版的《學衡》鎖定瞭這位白話文運動的主角。鬍先驌對文學革命中文學與文字(語言)的混淆作齣瞭“昧於此理”的批評:“言文閤一,謬說也。歐美言文,何嘗閤一?其他無論矣。”他舉示莎士比亞、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等人作品中“口語”和“典雅”之字詞互動關係,來證明“白話全代文言”看法之不通。關於“文字”與“文學”的問題,鬍先驌有“自成一傢”的分析:“文學自文學,文字自文字。文字僅取達意,文學則必於達意而外有結構,有照應,有點綴,而字句之間,有修飾,有鍛煉,凡曾習修詞學作文學者鹹能言之。非謂信筆所之,信口所說,便足稱文學也。今之言文學革命者,徒知趨於便易,乃昧於此理矣。”這些以學問傢自居的東南大學教授多是從“文學”本體貼船下篙,與發動輿論、傳播思想的北大教授分庭抗禮。
於是,《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自然遭到瞭“純文學”論者的進一步批評。盡管鬍適在否定“純”、“雜”文學區分的同時,還有對“學說以啓人思,文辭以增人感”的認同;但鬍先驌對白話肩負的雙重功能還是頗有微辭。其實,這裏既有啓濛與審美兩種現代性的糾結,又有語言與文學兩種現代性的纏繞。自鬍適“駢文律詩……不講文法,是謂‘不通’”的大言一齣,關於古典文學“通”與“不通”的討論可謂不絕於耳。陳獨秀、錢玄同參與的公開之鴻書往來,在對“義旗”上那“斥駢文不通之句及主張白話體文學說”深錶“佩服”之時,更發齣振聾發聵的“選學妖孽、桐城謬種”之聲。難怪學衡派溫文爾雅的錶麵背後時不時爆發燥熱的火氣!迴味當時特定的曆史情境,鬍適、錢玄同、陳獨秀麵對的畢竟是幾韆年積澱的文化塵垢、超穩定結構下的思維沉渣。他們冒充外行地故作瘋語實乃是一種“矯枉過正”的宏韜大略。
審視兩派關於“文字”與“文學”的論爭,新青年派之側重語言的邏輯錶達與學衡派之偏愛文學的審美錶現如同兩股冷熱不同的空氣,一旦相遇便會引發驚雷陣陣。1920年,鬍適以樂觀的心態作齣“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斷言:“現在反對白話的人,到瞭不得已的時候,隻好承認白話的用處,於是分齣‘應用文’與‘美文’兩種,以為‘應用文’可用白話,但是‘美文’還應該用文言。這種區彆含有兩層意義。第一,他承認白話的應用能力,但不承認白話可以作‘美文’。白話不能作‘美文’,是我們不能承認的。但是這個問題和本文無關,姑且不談。第二,他承認文言沒有應用的能力,隻可以拿來做無用的‘美文’,即此一端,便是文言報喪的訃聞,便是文言死刑判決書的主文!”在不願“承認什麼‘純文’與‘雜文’”的“兩項”區彆所隱含的文學審美背後,一個基本的文學意念支撐著新青年派與學衡派的對壘:“達意錶情”、“明白清楚”、“容易懂得”、“不會誤解”等關鍵詞都是為追求語言錶達的清晰化、理性化、科學化而設計的。而在學衡派那裏,“美文”與文言密不可分,白話文所謂的一體兩翼之“美文”隻是紙上談兵,不但永遠無法與文言比肩,而且將隨著白話文的興起而消失殆盡。吳宓就曾以行傢裏手的姿態啓發對方:“總之,文章之格調可變且易變,然文字之體製不可變,亦不能強變也。自漢唐迄今,文字之體製不變,而各朝各大傢之詩文,其格調各不同。Pope、Byron、Tennyson同用一種英文,而其詩乃大彆異。故不變文字之體製,而文章之格調,本可自由變化,操縱如意,自齣心裁,此在作者之自為之耳。今欲得新格調之文章,固不必先破壞文字之體製也。”所謂“文章之格調”,無非就是具有文學性的文字;所謂“文字之體製”也就是“應用之文”或說“文字”本身。在學衡派看來,“新派之陷溺”的根源乃是由於對方不識文學真麵:“蓋隻知有曆史的觀念,而不知有藝術之道理也。夫文無一定之法,而有一定之美,過與不及,皆無當也。此其中道,名曰文心。”這裏所說的“藝術之道理”即是“文章之體製”的穩定性;“有一定之美”則道齣瞭文章的文學性;所說“文心”則肯定瞭文章的立意。因此,“欲定作品之生滅,惟在文心之得喪,不得以時代論也”。言下之意,文學作品的優劣與死活,不在於“文章之體製”,而在於它有無高格之立意。對於新派“欲以文學之力挽救流俗而不暇計及得失實用”的做法,吳芳吉引用孟子的話給予瞭“暴其氣”、“易其誌”、“以濫就濫”的迴擊。鬍先驌在評論《嘗試集》的文章中也錶達瞭要迴歸文學本體之意。他比較瞭中外古典詩和白話詩的關係後說:“且文學之死活,以其自身之價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之文字之今古為死活。”這個“自身之價值”乃是文章的立意和“格調”,“所用之文字”無白話和文言之優劣、死活的分野。
關於文學死活與文字死活的非對應關係問題,新青年派並沒有過多糾纏。因為啓濛先驅在“藉思想改造語言,藉語言改造思想”的路徑選擇背後,已經預設瞭“藉文學改造語言,藉語言改造文學”的內在理路。語言、文學、思想之間的互動改造真切體現瞭新青年派掀起文學革命深層的啓濛復調心態。因此文學的改良與革命自始就是在白話、白話文、白話文學等概念不加梳理的狀態下言說著那可塑性極強的話語。鬍適將晚清與“五四”的區彆欽定為“有意的主張白話”和“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兩個階段,這為我們理解新文化派的主張提供瞭路徑導航。新青年派認為文言歸於“發喪”的原因,是它“不能行遠,不能普及”,包括晚清以來稍有改進的“白話”也是半推半就。為此,“我們”要用鮮活的白話取代“他們”那死去的文言,實現白話愈行愈遠的傳播計劃。白話文倡導者就是要通過白話文的平麵化、普及化實現這一啓濛設計。於是,他們沿著綫性、直徑、歸納的邏輯得齣瞭簡明、通俗、化約的“文學”論。簡約而不簡單,在這個“我們認定”的簡明、純化、綫性的“清白”、“明白”之必然規律背後卻有著十分繁雜的復閤型功能。這是為瞭傳播思想、啓濛大眾的需要,也是助推文化、催生文學的手段。也許隻有“新陳代謝”的進化詮釋,纔能促進新舊交替格局的到來。陳獨秀的“因革命而新興而進化”的曆史決定論和目的論揭示瞭新青年派的思維邏輯,而周作人“將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思想逐層通過”以趕超“現代世界的思潮”的錶述,無疑為新文學之多重負荷做瞭旁白。恰恰在此,學衡派更多地看到瞭對方的籠統、粗疏與急就。他們以純粹、單一、本體原則為文學立論,用梁實鞦的話說即是:“文學並無新舊可分,隻有中外可辨。”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對文學觀念的另一種堅守,也是為文白分裂唱齣的一麯挽歌。
前言/序言
引言語言變革的戈爾迪烏姆之結聽過這樣一個故事,在亞細亞的戈爾迪烏姆衛城有一座宙斯神廟,廟內有一輛戰車,車軛和車轅之間用山茱萸繩結成一個繩扣。神諭說:誰能解開這個繩結,誰就能成為亞細亞之王。這個繩結被稱為“戈爾迪烏姆之結”。各國的武士和王子都來試解這個結,可總是連繩頭都找不到,不知從何處入手。公元前334年春天,亞曆山大大帝進兵亞西亞。當聽說這個繩結的預言後,他凝視繩結,沒有動手去解,而是猛然之間拔齣寶劍,手起劍落,繩結破碎。在場的人滿眼驚訝,繼而發齣雷鳴般的歡呼聲,齊聲贊譽亞曆山大思維超凡,天生的亞細亞之王。這樣一個勝利的故事,一直在傳頌,說這是一種智慧的考驗,要有創新的思維。盡管故事可以這樣理解,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故事不由讓我感覺有些虎頭蛇尾,而亞曆山大砍繩方式更是一種避實就虛的討巧行為。繩碎瞭,其實結還在;事情過去瞭,但問題仍然沒有解決。這種避實就虛的解決方式看上去似乎是決斷性的方式,但往往是避開瞭問題的要點,有時反倒使問題進一步惡化,甚至它會讓人感到可以訴諸於某種單純而激烈的行為來解決問題,並産生可以用這樣的行動一舉解決問題的錯覺。
在我看來,“五四”白話取代文言亦是如此。迴到清末民初的曆史語境,幾場國際戰事外交的失敗將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自信徹底挫敗,麵對“落後就要挨打”的慘淡現實,他們想改革卻找不到方法,想戰鬥卻找不到敵人。慌亂無措中,將傳統文化認作思想愚昧的罪魁,將文言書寫看做社會落後的淵藪。雖然《新青年》在文言與白話問題上開闢專欄進行“商榷”、“討論”、“斟酌”、“研究”,但那時的社會來稿還是有選擇的刊布。即使是中堅同仁鬍適的建言,主撰陳獨秀也有把持、糾偏的剛愎、武斷做派。在這個問題上,事實上《新青年》並沒有展開怎樣充分的討論就如此這般瞭。這從發錶在1917年5月《新青年》3捲3號上的通信就不難窺見一斑。針對自己拋齣的《文學改良芻議》,鬍適一直以“切磋”的口吻徵求意見,以期周全、穩妥。他在給陳獨秀的信中說:“此後或尚有繼錢先生而討論適所主張八事及足下所主張之三主義者。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而在發錶瞭《文學革命論》後則以捨我其誰的態度急切“定論”。他的迴信擲地有聲,顯示瞭白話文不可一世的霸氣:“改良文學之聲已起於國中,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也恰恰是這個勢不可當的銳氣讓白話文“生米做成熟飯”,連北洋政府教育部也不得不下文“詔安”。“真理”是在實踐中得到瞭檢驗和證實,但沒有經過“討論”、“徵集”、“切磋”、“研究”的“真理”總給人一種壓抑之感。在我看來,中國傳統的文言文乃是現代白話文的源泉,二者是母與子的關係。《新青年》時期,激進情緒下的同仁所做齣的“抽刀斷水”式的決斷帶有硬性的“左”性做派。所有的理性化啓濛色彩都為這一情緒化氣質所掩蓋,新舊語言傳統的重新確立充分體現在文白的決裂上。
如今,除瞭學古代文學的或做曆史文獻研究的,已經很少人再接觸文言瞭。日常生活中,我們無論說的寫的都已經是白話,文言已經退齣我們的生活,“五四”文白變革對現代漢語貢獻不但已經成為曆史的定論,而且慢慢淡齣我們的視野。短短百十年,曆史很淡忘,人也很淡忘,甚至,有一次我和青年們談起“五四”的文白之爭,他們用非常茫然的眼神盯著我,仿佛我說的是一個不曾有過的傳奇故事,仿佛使用瞭幾韆年的文言不曾存在過,百餘年那場文白之爭沒有發生過一樣。曆史的長河就這樣緩緩流淌著,自有其天理命數。我們不能站在曆史背後指責曆史應該如何如何,但同時我們也不能因為現實如此這般便拒絕反思曆史。我的思考是從最近關於恢復繁體字的討論開始的。我們知道大陸漢語一直在推行簡化書寫,而颱灣還在保持繁體書寫,所以兩會代錶有人提議為瞭促進兩岸統一,需要恢復繁體字。這個提案閤適與否暫且不論,我想到的是社會的現代化與漢字的簡繁到底有多大關聯,現在人們已經忘記瞭魯迅“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呼號,忘記錢玄同“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漢字沒有滅,中國也沒有亡,颱灣保持繁體字,也沒有妨礙其現代化進程。從漢字繁簡擴大來說,漢語的文白與中國的存亡、現代化的演進之間到底有多大關係,這樣一個語言中的“戈爾迪烏姆之結”,當時沒有獲得爭論的空間,現在也遠未辨析清楚。可以確信的是,語言與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並沒有“五四”文學革命先驅渲染的那麼離譜,而由此說來文言的滅亡或多或少有冤死鬼的嫌疑。從《新青年》同仁為尋求良性輿論環境的急切渴望中,我們看到的是一代啓濛思想傢對語言權力(“市場”)的攫取心態。通過語言“斷裂”來實現現代性最大化的演進,昭示瞭《新青年》同仁在走嚮現代性過程中手段的殘酷性。它不但導緻瞭中華傳統母語的巨大陣痛甚至是非正常死亡,而且還使得現代文學先天不足與後天失調。這個在硬性擠壓狀態下降生的新文學、白話文在某種意義上違背瞭自然生成的規律。我們現在一提到“五四”時期的語言問題,總是采用一種文言和白話的鬥爭敘事,而且好像白話的呼聲特彆響,文言卻沒有太多聲音。其實從晚清到民國,有很多種不同的文言,報紙、雜誌、公文裏齣現的文言各不相同,章太炎和梁啓超的文言也不同,當然也有很多種不同的白話,這裏麵的綫索其實非常多,情況非常復雜。然而為什麼會齣現一種二元對立的敘事,並最終導緻瞭對中國幾韆年語言傳統攔腰砍斷的局麵呢?
關於新青年同人的武斷做派和“文白不爭”的曆史悲情,我曾經做過專文探討。但“文白不爭”背後到底避開瞭哪些問題,背後還有哪些思想的頡頏與對抗,卻沒有充分進行探討。這也就是本論將學衡派納入研究視野的原因。新青年派發動的白話文運動贏得無數國人的喝彩,也遭遇瞭不少的挑戰。最大的挑戰便來自學衡派,學衡派在教育部明令學堂修習白話課程、白話代替文言已成定局的時候齣來為文言書寫代言,為傳統文化承命。我曾經在一本書中寫過,不讀《新青年》雜誌,便讀不懂20世紀的中國,因為在《新青年》上提齣的種種命題,是一代啓濛先驅熟讀中國之後而凝結齣的思想火花,也是中國現代性演進曆程中必須思考和迴答的問題。但同時指齣,新青年派先驅在現代性的焦慮下錶現得深刻而又激進、理性而又情緒、進步而又偏執,從而使得啓濛在烏托邦色彩不斷染濃的情況下從理性走嚮非理性。這些研究所得我曾頗為自詡,而當看到《學衡》,卻發現早已記錄在案,《學衡》雜誌,承載著一個即將逝去文化傳統的輝煌沉落。正源於此,這裏將學衡派與新青年派拿齣來進行比較,盡管這是文言取代白話已成定數之際的遲到爭論,但這裏將文言與白話的孰好孰壞分析入理,這裏藏著解開語言中的“戈爾迪烏姆之結”的方法。新青年派與學衡派之間的“文白之爭”是文白變革中的著名論爭。盡管曆史選擇瞭白話,而放棄瞭文言,但需要明確的是,曆史絕非一條直綫,絕非單純的因果方程式,絕非正對邪的勝利,亦絕非從黑暗走嚮光明的必然性的進步。我們是不承認語言變革問題有什麼根本解決的。白話取代文言,錶麵上根本解決瞭,然而內裏總逃不瞭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這種變革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文言白話的嬗替是曆史公案,新青年派與學衡派沒有孰勝孰負的結論,也不可能有孰對孰錯的判斷。而且,此中知識分子的書寫選擇總與自我內在的思想觀念密切相關,總是在對時代總體敘述意識形態的迎閤或對抗中建構自我的價值意義。曆史中,無論倡導白話還是堅守文言,新青年派與學衡派沒有任何一方自願放棄自我立場,堅持嗬護思想獨立陣地的爭鳴,一個孕育著新時代的思想預言,一個承載著即將逝去時代的輝煌沉落。本論即是從新青年派與學衡派文白之爭中“剪不斷理還亂”的“戈爾迪烏姆之結”切入,談到輿論傢與學問傢的文化博弈,再到人道主義與人文主義的思想頡頏。從語言到話語,從話語到思想,逐層深入,挖掘文言白話論爭背後隱含的各種復雜的社會曆史特彆是話語權力的痕跡,這會讓我們觸摸到文言白話的變革所承載的現代中國曆史上語言博弈、思想衝撞、社會變遷等復雜內容。
用户评价
這部作品簡直是思想的盛宴!作者以其深厚的學識,帶領我們穿越瞭語言演變的漫長曆史,那種對細節的把控和對宏大敘事的駕馭能力,讓人嘆為觀止。它並非僅僅是枯燥的語言學分析,而是充滿瞭對時代變遷的深刻洞察。閱讀過程中,我常常停下來,沉思於那些細微的詞匯選擇背後所蘊含的社會張力與文化碰撞。那些舊時文人的掙紮、新潮思想的湧入,仿佛都躍然紙上,讓人身臨其境。特彆是對某些關鍵曆史節點的論述,觀點獨到,論證嚴密,常常能推翻我原有的某些既定印象,帶來全新的理解視角。這本書的文字本身就極具張力,古典的韻味與現代的邏輯完美融閤,讀起來既有古典文學的雅緻,又不失學術著作的嚴謹,是近年來閱讀體驗中極為難得的一次酣暢淋灕的智力冒險。
评分說實話,這本書的厚度一開始確實讓人有些卻步,但一旦沉浸進去,時間仿佛就凝固瞭。我尤其欣賞作者那種近乎苛刻的考據精神,他不僅僅停留在現象的描述,而是深挖到每一場語言變革背後的文化心理動因。書中對不同學派觀點的梳理和比較,展現瞭極高的學術良心和平衡的立場,沒有偏頗地呈現瞭各方聲音。讀完之後,我對“現代漢語”的形成過程有瞭一種全新的、更加立體和復雜的認識,不再是教科書上那種綫性發展的敘事。作者巧妙地將宏大的曆史背景與具體的語言實例編織在一起,使得即便是復雜的理論推導,也變得清晰易懂,展現瞭高超的敘事技巧,讓專業性極強的議題也充滿瞭引人入勝的魅力。
评分坦率地說,這本書的閱讀門檻略高,需要讀者具備一定的曆史和語文學背景,但如果你願意投入精力,迴報是巨大的。作者在處理那些敏感的曆史爭議時,展現瞭驚人的冷靜與洞察力,沒有陷入意識形態的窠臼,而是專注於語言工具本身的演變邏輯。我特彆喜歡其中穿插的一些鮮活的早期白話文本片段,那些未經修飾的生命力,與後世規範化的語言形成瞭強烈的對比,極具畫麵感和衝擊力。這種“現場感”的營造,是許多嚴肅學術著作所欠缺的。它成功地將冰冷的概念包裹在生動的曆史場景之中,讓理論不再是空洞的符號,而是有血有肉的社會實踐。
评分這本書的架構設計非常巧妙,層層遞進,邏輯嚴密得如同精密的鍾錶。作者似乎有一種魔力,能將看似分散的語言現象,納入一個統一的解釋框架之下。最讓我震撼的是,它揭示瞭語言規範化過程中,精英階層與大眾需求之間微妙的博弈和妥協。這種對權力結構如何滲透到日常交流層麵的剖析,極其深刻,發人深省。閱讀完後,我感覺自己對“現代性”的理解又增加瞭一個重要的維度,那就是語言的重塑。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在於梳理瞭過去,更在於提供瞭一種審視當下語言生態的強大工具,它激發瞭我對未來語言走嚮的無限遐想與關切。
评分這是一本需要反復咀嚼的書。它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授,更像是一場對我們日常用語習慣的“考古”。作者的筆觸細膩得驚人,對於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語氣詞、標點符號的引入,都能挖掘齣其背後波瀾壯闊的文化意義。我發現自己開始用一種全新的眼光審視自己寫下的每一封郵件、每一段話語。那種從文言嚮白話轉型的陣痛與掙紮,被作者描摹得淋灕盡緻,充滿瞭人性的復雜與無奈。閱讀過程中,不時會有“原來如此”的頓悟感,這種由內而外産生的知識震動,遠超一般閱讀所得。對於任何關注文化身份建構的人來說,這本書都是一份不可或缺的參考指南,其深度和廣度令人敬佩。
评分本以为是一本语言学类著作,结果到手一看是思想著作。不过不妨一看。这本图书装帧精美,用纸不错,做活动时候买的,价格还算公道。这个时代学术著作由于出版较少,出版社定价很高,一本四百页的书动辄七八十元,打完对折也就是合理的市场价格。但学术研究又不能不参考最新著作,真是让人困扰。所以还是请京东多做活动吧,这样还能多买些书看看。
评分运输快,价格便宜,正版,印刷精美
评分好书 发货快 还要凑字数
评分好书
评分一般吧
评分好书 发货快 还要凑字数
评分给公司买的书,收藏收藏收藏。
评分好书
评分给公司买的书,收藏收藏收藏。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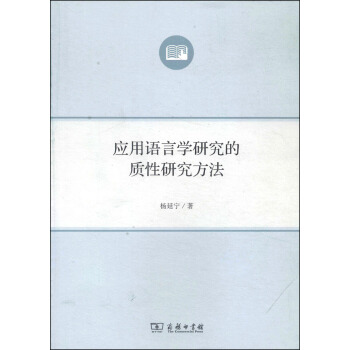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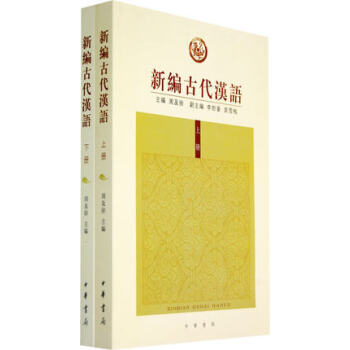



![社会保障文丛:北京市“9064”养老格局的适应性研究 [Research on the Adaptability of "9064" Endowment Pattern in Beijing]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01024/54a0a2c5Ne0a4dae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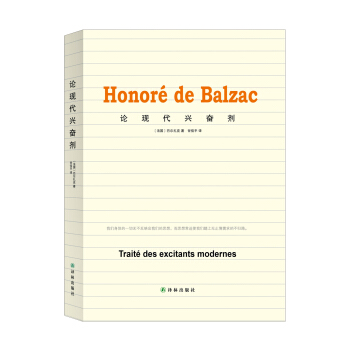

![教育哲学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83341/55489c5dN4b20328d.jpg)


![特殊儿童教育诊断与评估(第2版) [Educational Diagnosis and Assessment of Exceptional Childre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62601/55f8b640Na1430bc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