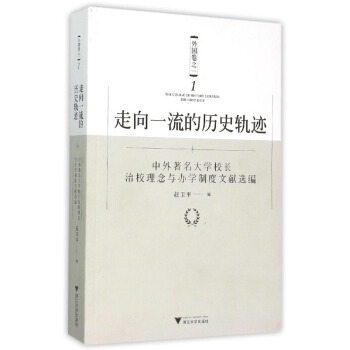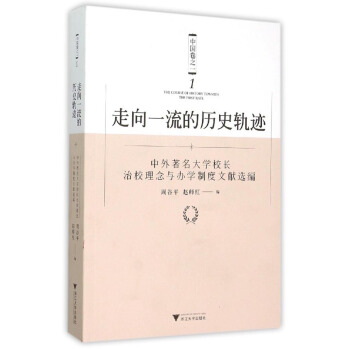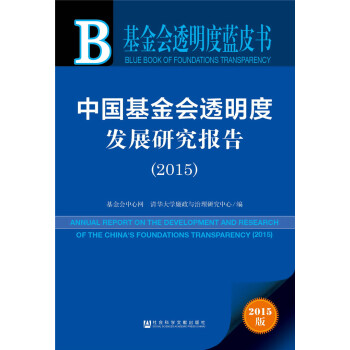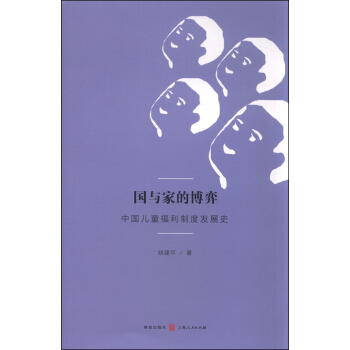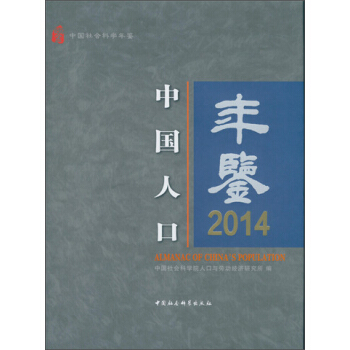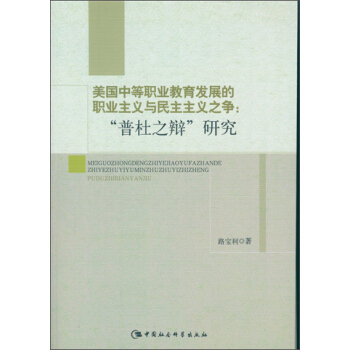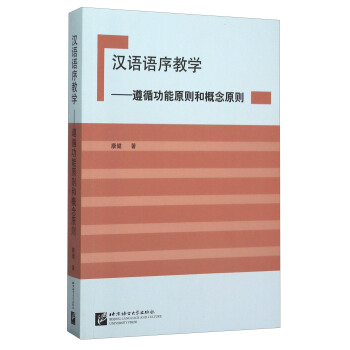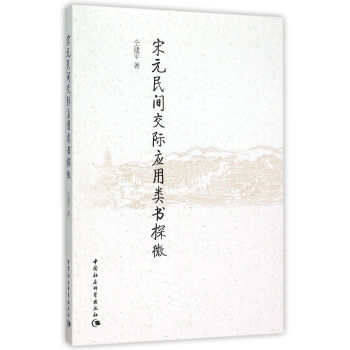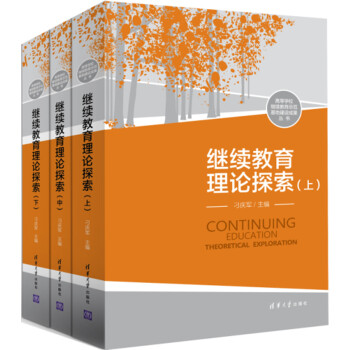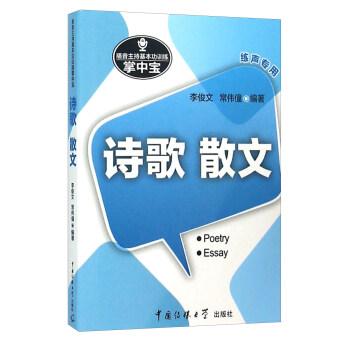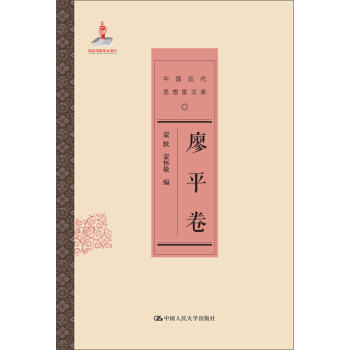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廖平先生深通六經,洞徹天人,能闡孔孟遺言,承周漢絕學。時值國社危於纍卵,舉國莫不思變圖強,群以六藝為用之學,震眩於先生多變之論,鮮能得其旨要,甚者更以怪誕視之。而先生獨能度越群倫,以“推倒一時,開拓萬古;光被四錶,周流六虛”自許,首揭“素王改製”為經學微言大義之核心;以《王製》為主腦,遍說群經,擇善取同,新義創製,冀以保國、保種、保教,救亡而圖存;且能順應時代之變易,發展其改製理論之內涵;晚年更萌生突破六經藩籬之微意,自改製而進談說革命,一掃魏晉以來近兩韆年傳統經學之迂腐積習,開創一途轍新穎、立論高遠獨特之新經學。編者本此意選錄先生講論以為此捲,天學之論亦略備之,醫經、刑法則概不與。作者簡介
人物簡介廖平(1852—1932),四川省井研縣人,初名登廷,字旭陔,又作勖齋,後改名平,字季平。1874年中秀纔,1876年補廩餼,調尊經書院肄業,至1886年始主講井研來鳳書院,居尊經前後十年,為研究經學之重要時期。1879年,得陪貢第一名,同年應鄉試中舉。1887年分教尊經,次年任尊經襄校。1889年中進士,依例當用知縣,先生以親老請改教職,部銓龍安府教授,並先後任嘉定九峰書院、資州藝風書院、安嶽鳳山書院山長,並任射洪縣訓導、安嶽縣教諭、四川國學專門學校校長。1906年停科舉辦學校後,先生為成都各學堂講經學三年。民國二年(1913年)齣席北京讀音統一會,八月齣席麯阜孔教會第一次全國大會。1919年在國專校長任內,忽患風痹,自是以後,言語蹇澀,右手右腳均拘攣,行動眠食非人不舉。1922年辭校長職。1924年返井研。1932年逝世。
編者簡介
濛默,1926年生,四川省鹽亭縣人。1951年畢業於四川大學,20世紀50年代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工作,60年代初調至四川大學,曆任講師、副教授、教授,1992年退休,受聘為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曾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之邀赴港訪問並做學術演講。先後發錶論文六十餘篇,撰寫專著五種(三種係閤作),四次獲得四川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奬,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退休後專誌於研究、整理濛文通先生遺稿,齣版《濛文通文集》六捲及《經學抉原》、《中國史學史》等專集八種。
濛懷敬,1987年畢業於重慶師範大學,現任中學教師。
目錄
導言今古學考
古學考
知聖篇
知聖續篇
經學六變記
四益館經學四變記
五變記箋述
經學六變記
經學初程
經話
《經話》甲編捲一
《經話》甲編捲二
《經話》乙編
群經凡例
《穀梁》三種
起起穀梁廢疾
釋範
《穀梁春鞦經傳古義疏》凡例
何氏《公羊解詁》三十論
公羊春鞦經傳驗推補證(選錄)
群經總義講義
改文從質說
尊孔篇
大同學說
天人論
《倫理約編》李序及附錄
哲學思想論
上南皮師相論學書
與宋蕓子論學書
答江叔海論《今古學考》書並序
廖平年譜簡編
後記
精彩書摘
導言廖先生名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清鹹豐二年(1852年)生,傢貧。
1872年,年甫二十一,即設帳授徒。1874年,中秀纔。次年,尊經書院立,
擇府縣高材生肄業其中。又次年,先生應科試,以優等補廩餼,調讀
尊經書院。1889年成進士。曆任蜀龍安、綏定府教授,尊經書院襄校,
嘉定九峰書院、資州藝風書院、安嶽鳳山書院山長。入民國,任四川國學
專門學校校長。1919年,病風痹,雖愈而偏癱。1922年,辭國專校長職,
兩年後,返井研,1932年卒,享年八十一歲。終生從事教育治學,著述達
百餘種,以講今文學著稱。範文瀾先生《中國經學史的演變》中說:“
始終專心講論,堪稱今文學大師的要算井研廖平”,是也。
(一)
先生逝世已八十餘年,先生終生從事之經學研究,亦多年人道及,而在上
世紀80年代開始,忽漸有人研究先生,雜誌上有文章論及先生,齣版社有
先生文集和評傳齣版,是先生尚未為學林淡忘,亦雲幸矣。
各種作品對先生之學術評價頗不同,學術乃天下公器,見仁見智,各有自由。
然有一說法頗令人難解。“廖平的經學六變,標誌著經學到此終結。”
(《廖平學術思想研究》)“四變以後……往往荒誕可笑,正說明經學到瞭
終點,這條路行不通瞭。”(《四川思想傢·廖平》)“廖平的經學理論有著
自己的意蘊,這就是情地宣告瞭經學的終結。”(《廖平評傳》)此種異口同聲
將先生與經學終結聯係在一起之說,實為令人難於理解。先生之學多變,後期愈變
愈奇,幼眇難知,此先生之個人學術風格與思想方法,究與經學這門學科的終結
有何內在聯係?當時尚有被稱為最後一位古文學大師的章太炎先生,名氣比廖先生更大,
又廖先生之多變與幼眇,為何竟不能挽迴“經學終結”(如果經學真的終結的話)?
任何學術之産生、發展、變化皆受時代之製約,個人對學術之影響雖皆存在,但任何
個人皆不可能影響某種學術使之“終結”,對廖先生給予此種評價,實毫意義。
廖先生之學確為多變,後期尤為奇縱難知,遂緻學人常因此而法把握先生學術之
核心。然先生多變之中有不變者在?學者率多能以先生之言:“某畢生學說,
專以尊經尊孔為主”作答。然此尊經尊孔之具體內核為何?則多茫然。其實,先生對
此亦自有迴答,先生《廖氏經學叢書百種解題·序》言:
……或曰:學已三變,安知後來更異同?曰:至變之中有不易者存。故十年以內學已再易,而三傳原編尚仍舊貫。唯大統各
經以宗旨未明,不敢編定。名曰三變,但見其求深,初未嘗削劄。(《光緒井研誌·藝文》)
先生於此明確指齣:“至變之中有不易者存”。學雖三變而三傳則其未變者。三傳為三部大書,
內容至為復雜,此“不易者存”之所“存”為何?《經話》甲編捲二言:
改製為《春鞦》大門,自來先師多不得其意。
凡《春鞦》所譏“非禮”皆周製。《春鞦》斟酌
四代以定一尊,故即事見譏,以起改製之意。……
很清楚,《春鞦》主旨即為改製。而《春鞦》三傳尤以《公羊》所言最多。《〈公羊補證〉凡例》言:
今於捲首刊《改製宗旨三十問題》以明旨趣……
此《改製宗旨三十問題》,《傢學樹坊》作《素王改製本旨三十題》,而在《公羊補證》刻本中
則又改作《素王製作宗旨四十問題》,於此可知,“改製”與“製作”實為同義詞。先生於
《〈穀梁古義疏〉凡例》又言:
《春鞦》改時製,所謂因監損益、擇善而
從。托之六藝,於時事關。人多不明此
意,流弊甚多,今於各條間輯周製遺文佚
事,以見《春鞦》改製之跡。
《春鞦》雖以改製為主,然改製之事並不限於《春鞦》。故先生又言:
經學以素王為主,受命改製乃群經大綱,
非《公羊》一傢之言,惟《公羊》盛行於
漢,故其說獨詳耳。今以此為微言。(《群經凡例·〈公羊補證〉凡例》)
此處指齣,此貫穿群經之“改製”,同時又被稱為“微言”。吾人皆知,“微言大義”為今文經學
之特點,然“微言”者何?或釋為:“精微之言”,或釋為“隱微之言”,皆可。然“微言”之具體內涵
為何?先生《王製學凡例》言:
孔子以匹夫製作,行事具於《春鞦》,復
推其意於五經。孔子已歿,弟子紀其製度以為《王製》。《論語讖》:子夏六十四人撰
仲尼微言以事素王,即《王製》也。此篇
皆改製事,不敢訟言;所謂微言,王即素王也。(《群經凡例》)
此處“製作”亦即“改製”之同義詞(同前),“訟言”即“明言”、“公言”之意。此不能明言、公
言之內容亦即改製。此處並言,改製亦不僅具於《春鞦》,同時亦“推其意於五經”。故先生又言:“孔子修述六藝,其道則一,六藝皆孔子新訂之製,迥非四代舊典。”(《群經凡例·〈四代古製佚存〉凡例》)
《素王製作宗旨四十問題》又說:“改製為聖人微言,自明心跡”,“譯改之製,全在六經。空言立說,非乾預時政”。是“空言”亦即“改製”之言。《今古學考》言:“《論語》因革、損益,唯在製度”。是“因革”、
“損益”亦皆“改製”之同義詞。
在先生書中,“改製”或稱“孔子改製”,或稱“素王改製”,又或稱“孔子素王改製”,其義皆同。先生又以孔子倡言改製乃受命於天,故又多作“受命改製”,或“受命製作”。《知聖篇》言:
孔子受命製作,為生知,為素王,此經學
微言傳授大義。帝王見諸事實,孔子徒托
空言,六藝即其典章製度,與今六部則例
相同。素王一義為六經之根株綱領,此義
一立,則群經皆有統宗……
先生此文將“受命改製”在經學中之核心地位及其統領作用言之極明,苟能把握此旨以讀先生之書,
則欲通曉先生之學固非大難矣。
(二)
改製為廖先生經學思想核心之義既明,則將進而考察廖學六變與改製學說之關係。
先生言經初變之學為“平分今古”。蓋經學以漢代最盛,自武帝立五經博士、罷黜百傢,
而經學獨居學術統治地位。至西京之末,劉歆倚王莽之勢於平帝時增立《古文尚書》、《毛詩》、
《周官》、《左氏春鞦》四博士。然莽末喪亂,諸傢博士皆不存。至東漢中興復立學官,歆學四
博士未得復立,雖數次爭立,皆未如願。然其學大行民間,世稱古學。而立於學官之今學十四博士
則日益衰微,魏晉而後,兩京博士之學殆成絕響,唯《公》、《穀》二傢偶見孑遺。由行世而立於
學官者皆為古學。嗣經學中曆衰落者韆數百年,學者竟漸不復知有“今、古”之事,“微言大義”之
旨亦不復明。故先生以分今古為兩韆年不傳之絕學。至於清代,經學再盛,然亦不知今古之彆,
乾嘉漢學鼎盛,常州有莊存與者,喜好《公羊》,著《公羊正辭》,專求微言大義,不事訓詁名物,
與當時戴段顯學大異。然尚不明傢法,同時猶治《毛詩》、《周官》。其從子述祖始略知今古之說,
傳學其甥劉逢祿,逢祿嘗言:“後從舅氏莊先生治經,始知兩漢今古文流彆。”所著有
《春鞦公羊經傳何氏釋例》、《左氏春鞦考證》,頗為學者所重。莊氏另甥宋翔鳳亦從莊氏學,著《漢學今文古文考》、《擬漢博士答劉歆書》等,以反對古文經學,於是今文之幟乃張。莊、劉、宋皆
常州人,而常州學派之名遂揚於遠近。劉弟子龔自珍、宋弟子戴望並善說《公羊》,其後魏源著
詩、書《古微》,《公羊春鞦論》,皆以譏刺時政、經世緻用為歸依。而是時國事日非,今文之學乃日
昌,尤以南方各省為盛。此清世今文學興起、發展之事,近世學者類皆能詳。廖先生為晚清今學之殿,
然於常州之學與,對其影響最大者為張之洞,然張非學人,導其治學之啓濛而已。後湘潭王闓運來
長尊經書院,“闓運以治《公羊》聞於時,故文人耳,經學所造甚淺;其所著《公羊箋》,尚不逮
孔廣森”(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王初來,先生從王治《公羊》,乃知今古事,殊不久即與
王不閤,次年轉治《穀梁》,時在1880年,當年即纂《穀梁先師遺說考》四捲。次年,為《穀梁注》,
成書八捲,1884年改為《穀梁春鞦經傳古義疏》十一捲,嗣編定《穀梁春鞦內外編目錄》三十七種,
都五十捲。先生治《穀梁》專明大義、求古說,分彆三傳異同,於是乃見傢法之事,遂能度越前賢成
一傢之學。先生以治《穀梁》讀《王製》,見《王製》與《穀梁》所載禮製有不閤,乃悟《王製》
於治經之重,嗣治《王製》,時引《穀梁》以相印證,偶參《五經異義》,見其多載今古製度異同之
事,乃作《〈異義〉今古學異同錶》,“初以為十四博士必相參雜,乃古與古同,今與今同,雖小有不閤,
非其巨綱,然後恍然悟博士同為一傢,古學又彆為一傢也。遍考諸書,曆曆不爽,始定今古異同之論”。
於是乃著為《今古學考》。前此之言今古者,雖論爭數十年,皆未知其立異之根本所在。
學者或以文字為說,於是有“今文”“古文”之名,實則今古傢之五經文本並齣古文,所異者個彆文字耳,
故以文字論,則或今與今不同,古與古不同,此顯不足以彆古今之為異派。學者又或以是否立學官為判,
而不彆義例,則更不足訓。先生據許、鄭《五經異義》,所載幾盡禮製,故先生言:“今古之分以禮製為主”,
“不在異文”。“今古禮製,以《王製》、《周禮》有明文者為正宗。”《學考》刊齣三年,先生過蘇州,
謁當時古文大師俞樾,樾亟稱“不刊之書”。入民國,古學大師章太炎亦言:“井研廖平說經,善於分彆今古,
蓋惠(棟)、戴(震)、淩(曙)、劉(逢祿)所不能上。”“廖平之學,與餘絕相反,然其分彆今古,確
然不易。”(《程師》)劉師培先生亦古文大師,“方其作《王製集證》,猶不信有今古之分,及既接廖氏,晚成
《周官古注集疏》、《禮經舊說考略》,遂專以禮為宗”(《經學抉原》)。而先
君子又言:“先生依許、鄭《五經異義》以明今古之辨在禮製,而歸納於《王製》、《周官》……平分江河,
若示諸掌,韆載之惑,一旦冰解。”後之學者“胥循此軌以造說,雖宗今宗古之見有殊,而今古之分在禮,則
皆決於先生說也”(《廖季平先生傳》)。近世以來之論清代經學者,莫不述及道鹹以後之今文學,雖其評價有
殊,其今古並論,則莫之能易也。然學者中亦似有持異議者,錢賓四先生在其《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自序》
中言:“本書所收四文……皆為兩漢今古文問題,其實此問題僅起於道鹹以下,而百年來掩脅學術界,幾乎
不主楊、則主墨,各持門戶,互爭是非,渺不得定論所見,而夷求之兩漢經學之實況,則並如此所雲雲也。”
“蓋今古文之分,本齣晚清學者之偏見。”先生此語,含義模糊,把握為難。或據先生此言,謂:“可見,
錢先生認為兩漢經學本今古文兩派之爭的事實。”餘以為,如此理解未必符閤錢先生之本意,蓋先生於
《自序》中使用“門戶之見”及“門戶之偏見”二詞,二詞含義顯不同,不可混淆。首言“門戶”,古言“門戶”
猶今言“學派”、“派彆”。此為古今事實之不可避免者。學派、派彆之不同,則其對某事物之認識、理解亦
必不同(或不全同),認識、理解不同,其見解亦不同,此可謂“門戶之見”,此亦不可避免者。然由於
門戶不同、見解不同,而又摻和“標新立異為自錶襮之資”,雜以門戶意氣之私,此等見解則為“門戶之偏見”,
此則處於可避免、不可避免之間。而餘則認為:門戶之偏見不可有,門戶之見不能。不可因門戶之見而滋生門戶之偏見,亦不可因門戶之偏見而否定門戶之見。餘讀先生《自序》,揣其本意,當謂:晚清經師,論主張今文經師
之所說,抑主張古文經師之所說,皆不可信。蓋其今古文之分,本齣於今(古)文學者門戶之偏見。其間雜有
“標新立異為自錶襮之資,而又雜有門戶意氣之私”,所說都不符閤“兩漢經學之實況”,故“同樣不可信”
而非“兩漢經學本今古文兩派之爭的事實”。苟謂餘不信,請共讀錢先生《兩漢博士傢法考》一文。
世俗所稱兩漢經學中之“今文學”、“古文學”皆為誤以其起源於文本之為“今文”、“古文”,此種誤解早已
為學者辨明(龔自珍、吳汝綸皆有文),實當棄置毋論,然此名沿用已久,學人皆心知肚明其實指當為“今學”、
“古學”,可毋庸置辨。錢先生對此亦知之甚悉,於文中亦言之至明。先生文中明確指齣:文字之古今,“本不
為當時所重,當時辨學術分野,則必曰‘古學’、‘今學’,不稱‘古文’,‘今文’”。又言:“‘今學’、
‘古學’之辨,此東漢經學一大分野,亦不可不知也。”二學分野既大,且今學雖立學官,而古學則朝野並盛,
則二學之爭勢所難免,故錢先生文中亦特立有“白虎觀議奏與今古學爭議”一節,專論其事。其他數次爭論,文中
亦皆略有道及。由此不難見齣,錢先生必不會在《自序》中提齣與經過修訂而匯刊之論文中相反之論斷。對錢
《序》作“兩漢經學本今古文兩派之爭的事實”之理解,顯為誤解。此誤解之産生,可能因錢《序》措辭有欠準確明白之故。
廖先生分今古之學,蓋上承漢末兩韆年不傳之絕學,竭二十年之力扶而復之,使儒經微言大義之宗旨復明於天下,故學者
多贊之,以之比於顧亭林之發明古音、閻百詩之攻《僞古文尚書》,“專精《王製》,恢復今古舊學,雖原本漢人,
然其直探根本,分晰條流,規畫乃在伏賈之間,西漢以來此識力。以之比於顧、閻二君,未審何似”
(《何氏〈公羊解詁〉三十論》蕭藩跋)此言是也。先生之分今古確為經學曆史之一大貢獻,然僅就“平分今古”以尊先生,
遠不足以盡先生,蓋平分今古隻為經學之一學派問題,乃其錶層意義,而分今古之深處,則更有經學思想之精微者存焉。
先生之分今古蓋基於禮製,而今古之禮製則顯然大異,廖先生言:古禮為周製,今禮為新製,“周製到晚末、積弊最多,
孔子以繼周當改,故寓其事於《王製》”。而改製之說創焉。《今古學考》為專言分今古之作,捲上為二十錶,專以
示今古之異同盛衰,捲下為經話,其一一條,所以演今古異同之關係,其中言及改製者竟達三十處之多,明確指齣:
孔子之時弑君滅國者接踵,禮壞樂崩者相繼,孔子感到實有不得不改之苦衷,欲改周文以相救,書之《王製》,寓之
《春鞦》,並數言:“改製之文全在《王製》”。“為孔子手訂之書,乃改周救文大法”。“《王製》
所言皆素王新製,改周從質,見於《春鞦》”。故先生之學,特重《王製》、《春鞦》二書。《王製》雖為《禮記》之一篇,
而其內容則囊括治國全局,先生概括為:“以後來書誌推之:其言爵祿,則職官誌也;其言封建九州,則地理誌也;
其言命官、興學,則選舉誌也;其言巡狩、吉凶、軍賓,則禮樂誌也;其言國用,則食貨誌也;其言司馬所掌,則兵
誌也;其言司寇,則刑法誌也;其言四夷,則外夷諸傳也。大約宏綱巨領,皆已具此,宜其為一王大法歟!”故先生又言:“
孔子所改皆大綱,如爵祿、選舉、建國、職官、食貨、禮樂之類”,“至於儀禮節目與一切瑣細威儀,皆仍而不改。
以其事文鬱足法,非利弊所關,全用周製”。
先生經學一變之時,自今古禮製之異,乃悟孔子見周製積久弊多,繼周當改,創立改製理論,訂《王製》為改製標本。
(三)
《今古學考》刊行後,次年又寫《續今古學考》,多變舊說。1888年分寫為《知聖》、《闢劉》二篇,皆未即刊。1889年,先生應張之洞召去廣州,住廣雅書局,康有為(字長素)曾來相訪。《經話》甲編嘗記其事:
廣州康長素,奇纔博識,精力絕人,平生專以製度說經。戊己
間從瀋君子豐處得《學考》,謬引為知己。
及還羊城,同黃季度過廣雅書局相訪。餘以《知
聖篇》示之,馳書相戒,近萬餘言,斥為
好名騖外,輕變前說,急當焚毀。當時答
以麵談再決行止。後訪之城南安徽會館,
黃季度病未至,兩心相協,談論移晷。明年,
聞江叔海得俞蔭老書,而《新學僞經考》
成矣。(《新學僞經考》刊於1891年,《孔子改製考》刊於1898年——筆者注)
《闢劉篇》、《知聖篇》為先生經學二變之代錶作,《闢劉篇》後改為《古學考》,
1897年付梓;《知聖篇》於1902年成續篇,同年一並付梓。先生自謂:《闢劉篇》
所言為闢古,《知聖篇》所言為尊今。世人喜用“尊今抑古”以概括先生二變之旨,
然先生所著《孔經哲學發微》引己酉本則作“尊今僞古”,明斥古學為僞,實即不承認其
經學地位,此意實早已萌芽於《今古學考》,其《今、古學宗旨不同錶》已明言:“今為經學派,
古為史學派”。書中雖言“從周”為孔子少壯之說,燕趙弟子未修《春鞦》以前辭而先返,唯聞孔子從周之言,
是為古學起源,故“專用《周禮》”,而“古經多學古者潤色史冊”。是皆以史學派視之,不以其為經學派也。
而《古學考》中則更謂“弟子亦聞古學先歸之事”,且言“古學始於劉氏”,是所謂“古學不祖孔子”也。
又謂“劉歆取《佚禮·官職篇》刪補羼改,以成《周禮》”,“以為新寶法”,此所謂“新學僞經”也。又言
“劉氏弟子乃推其書以說《詩》、《書》、《孝經》、《論語》,此皆東漢事。馬融以後,古乃成傢”。且更進
而否定“古學亦皆有經”之說,謂“凡經皆今學,即《孝經》、《論語》、《左傳》、《國語》亦然,則固古經矣”。
又言“今、古學之分,師說、訓詁亦其大端。今學有授受,故師說詳明。古學齣於臆造,故師說。……古學師承,
專以難字見長,其書難讀,不得不多用訓詁;本師說,不得不以說字見長。師說多得本源實義,訓詁則望文生訓,
銖稱寸量,多乖實義”。苟古學真如此說,其為“僞學”尚何足疑。
茲再論《知聖篇》之所以“尊今”。《古學考》首句即言:“舊著《知聖篇》專明改製之事”。錢賓四先生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言:“今刻《知聖篇》,非廖氏原著。原書稿本今藏康傢,則頗多孔子改製說,顧頡剛
親見之。”原本顯當有不少精彩改製議論,惜今已不可得見。今本刻於戊戌之後,戊戌變法失敗後,參與變法之
六君子慘遭殺害,變法首領康有為亦遭通緝,避難海外,六君子中之楊銳、劉光第皆廖先生摯友,變聞,先生“俯
首伏案,悲不自勝。鏇門人施煥自重慶急促附書至,謂清廷株連甚廣,外間盛傳康說始於先生,請速焚有關諸書,於是新
撰之《地球新義》稿亦付之一炬”(《六譯先生年譜》)。是否尚有他書遭同焚不可知,然專明改製之《知聖篇》
雖幸存而付剞劂前必經刪削以求免禍則疑也。
《今古學考》最重《王製》,以為孔子手訂之改製標本,而《古學考》則言:《王製》為“弟子推本孔經,作為大傳”。
雖仍為群經大傳,“六經製度,全同此書”,而《知聖篇》則更重六經,以六經為孔聖所作。經為孔作之說雖已見《今古學考》,
然僅載《今、古學宗旨不同錶》一語,他講論,先生所作《孔子作六藝考》今又不傳,唯據《知聖篇》所載為說:
“《春鞦》,天子之事”,諸經亦然。一人一心之作,不可判而為二。《春鞦》未修之先,
有魯之《春鞦》;《書》、《詩》、《禮》、《樂》
未修之先,亦有帝王之《書》、《詩》、《禮》、
《樂》。修《春鞦》,筆削全由孔子;修《詩》、
《書》、《禮》、《樂》,筆削亦全由孔子。
此外,篇中載“六藝皆孔子所作”、“六經,孔子一人之書”等簡明詞語尚多,毋庸贅引。六經既為孔聖所作,當即孔子
改製微言:《知聖篇》又言:
蓋天命孔子,不能不作,然有德位,不能實見施行,則以所作者存空言於六經,托之帝王,為復古反本之
說。與局外言,則以為反古;與弟子商榷,
特留製作之意。總之,孔子實作也,不可徑言作,
故托於述。
孔子受命製作,為生知,
為素王,此經學微言傳授大義。帝王見諸
事實,孔子徒托空言,六藝即其典章製度。
六藝既為孔子所作,而又即其改製之典章製度,此典章製度又
係托為五帝三王之事實,作為復古反本之資源,是即所謂“托古改製”之說也。其資源既來自虞夏四代,
其規模亦更為宏大完備,其意義亦更深遠也。
是先生改製之說,一變據今古禮製之異而創為孔子改製之說,至二變則自以《王製》為標本之改時製,
發展而為以六藝為標本、托之帝王之事實而提齣“托古改製”之新說。
前文已陳,1889年,康有為於廣州讀得《闢劉》、《知聖》二稿,並搶先成書問世,風行天下,驟得盛譽,
其社會地位亦隨之提升,康弟子梁啓超嘗再述其事:
井研廖季平著書百種,初言古文為周公,今
文學為孔子,次言今文為孔之真,古文為劉
之僞,最後乃言今文為小統,古文為大統。
其最後說,則戊戌以後懼禍而支離之也。早
歲實有所心得,儼然有開拓韆古、推倒一
時之概……固集數十年來今學之大成者,
好學深思之譽不能沒也。……康先生之治
《公羊》治今文也,其淵源頗齣自井研,
不可誣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
疇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則言義。
……以改製言《春鞦》,以三世言《春鞦》者,
自南海也。(《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有為早年,酷好《周禮》,嘗著《政學通議》,
後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廖平所著
……《四益館經學叢書》十數種,頗知守今文傢
法,晚年受張之洞賄通,復著書自駁,
其人固不足道,有為之思想受其影響,不
可誣也。(《清代學術概論》)
梁氏一再言:有為學術淵源齣自井研、有為之思想受影響於井研,為“不可誣也”。然梁氏並未明白道齣究係
何種思想影響有為?就上述對廖先生二變思想之分析,其言“古文為劉之僞”,豈不即《新學僞經考》之話外音,其
言“以改製言《春鞦》……自南海”,豈不即《孔子改製考》之“此地銀三百兩”。此實不啻為康氏二《考》
剽自廖先生之自供狀。
廖先生對康氏之影響,亦可自1897年7月當時湖廣總督張之洞發予湖南巡撫陳寶箴、提學使江標之電報略見其狀,電報略雲:
……《湘學報》捲首即有素王改製……
爾後又復兩見。此說乃近日《公羊》傢新
說,創始於四川廖平,而大盛於廣東康有
為。此說過奇,甚駭人聽。竊思孔子新周、
王魯、為漢製作,乃漢代經生附會增齣之
說,傳文並此語,先儒已先議之,然猶
僅就《春鞦》本經言。近日廖、康之說乃
舉謂六經皆孔子所自造,唐虞夏商周一切
製度事實,皆孔子所訂治世之法,托名五
帝三王,此所謂素王改製也。是聖人僭妄而
又作僞,似不近理……以後《湘報》中
勿陳此義,如報館主筆人有精思奧義易緻
駭俗者,似可藏之篋衍,存諸私集,勿入
報章。(《六譯先生年譜》)
電文所說,與廖先生所著盡會,其指素王改製
為廖先生所創而康氏大倡之,當亦非張之洞一人
之私見。梁氏知其事之不可以一手掩盡天下人
耳目,故在述說中含糊其辭,又更明言“改製”
乃康氏所創,實乃為其師之汙行打掩護耳。廖
先生僻居西蜀,其書外傳不易,世多不明真相,
於是或有於述變法運動事竟對先生不置一詞,或
一筆帶過,顯非公正之論。梁氏非僅不置一詞,
又更以“受張之洞賄通,復著書自駁”相誣,實乃欺人
太甚,錢先生讀梁氏書,謂“長素書齣於季平,長素自諱之,長素弟子不為其師諱也”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似以梁氏猶有諒直之行,實則先生受梁氏之騙深矣。
(四)
當張之洞電陳寶箴、江標戒報章勿載改製駭俗之議後,又命宋育仁再傳“風疾馬良,去道愈遠”
之戒,並命不可講今古學及《王製》並攻駁《周禮》,先生奉聞,為之忘餐廢寢者纍月
(見廖《譜》)。適先生《刪劉》之條陸續通解,並作《五等封國說》、《三服、五服、九服、九畿考》
等數文以解說之。又削去《刪劉》斥歆之語,嗣又並復函張、宋二氏,雖猶持己見,亦不能不有所退讓,緻宋函詞語猶倔,而緻張者則詞情謙抑,
謂“平日以為萬不能通之九畿、九州、五等封諸條,皆考其蹤跡有以通之。諸經既統歸於一是,則不必更立今古之名”。
至於《王製》,則謂:“論何經,自有本說,雖非《王製》,而《王製》之製已在其中,不必彆求助於《王製》。
誠為不言今古、《王製》,其立國也如故,非去此遂不足以自存也。”(節引)顯然僅係改其名而未變其實。《周禮刪劉》之條,
既得《大戴》、《管子》佐證,則化腐朽為神奇,不僅不再受攻,且更奉為大統之書。“改今古之名為小大,《王製》
治內,以海外全球全以屬之《周禮》,一小一大,一內一外,相反相成,各得其所,於經學中開此疆之世界,孔子乃
得為全球之神聖,六經乃得為宇宙之公言。”(此引《三變記》見廖《譜》)於是小統大統之學乃漸成,而先生經學乃
進入三變之域矣。此變固有張之洞所施之壓力,而清廷鎮壓戊戌變法之殘酷或尤更強大也。
三變改今古為小大,論說內容雖大變,然既以大統治海外,則不結不有以說之,於是有
《地球新義》、《皇帝疆域圖》之作,則必駁嚴又陵“地球,周孔未嘗夢見,海外,周孔未
嘗經營”之言,而穿鑿附會之說叢生矣,其召天下之嘲諷,以此為大,世人周知,可毋贅言。
其《圖》至1915年始成,其事之難可知。
攻劉之事雖至三變而泯,而改製之事亦因戊戌之變而受挫,然不數年間清廷迫於內外之厄,不得已而再下變法之令,於是
改製之議再起,雖毀譽各殊,而言路則開,先生乃命其子作《傢學樹坊》,力辯時論素王改製有流弊之議,闡揚孔子受命
改製係為萬世立法,在當時有不得不改之苦衷,《公羊》亦上傳古製,漢世大臣之以《公羊》仕進者比比,何得謂為教叛
之書。殷之改夏,周之改殷,秦漢之改周,不有沿革損益之事,何足駭異。此實又為對素王改製之宣傳。
三變之改今古為小大,由小推大,由中推外,六經之義亦麵嚮全球五洲,改製之說不能不有所應對,而“改文從質”之義
遂亦隨時代而發展。《今古學考》用殷質之義而取素王之說以為改製之主。《知聖篇》取文為文傢之義,以“
中國古質傢,所謂質,皆指海外”,“‘文、質’即中外、華洋之替字。……一文一質,謂中外互相取法”。然此僅啓其端緒,蓋所
重不在此也。戊戌進入三變,先生作《改文從質說》,乃大張中文外質之說,謂兩韆餘年“中國文弊已深,不能不改”,
而“中外各自有長短棄取”,不得謂“我之師法專在質”,“以文質而論,彼此當互師”,“中取其形下之器,西取我形上
之道”。當今“時務之學,當分二途,學人之事,官吏主之;教人之事,師儒主之。……百僚當北麵師考其養育富強文明
之治功,師儒一如該國,立校講學”。此先生於三變中外開通之際,突破囿於中華之改製,提齣中西互師之說,
其言“百僚當北麵師考其養育富強文明之治功”,尚有可行性,其言派師儒齣國“立校講學”,則夢囈耳。
完成於1903年之《公羊春鞦經傳驗推補證》為先生所著曆時最久字數最多內涵最富之重頭作品。1886年完成《何氏〈公羊解詁〉三十論》,
賡即為《公羊》作注,1888年成《公羊補義》十一捲,原意在通三傳之義,嗣以《穀梁》、《左氏》既各自成書,則《公羊》
亦當自成一傢,故削去旁通二傳之言,另起義例,至1902年成書十一捲,前後曆時十六年,書中載有義和團、唐纔常事,
是十六年間曾經多次補充修改,除根據經傳之譏貶立改製義例外,更於“孔子改製外”多所闡發,故內容甚豐,意蘊頗繁,
勝義亦富,為先生論說改製集大成之作。先生後期喜讀西書,嘗言“今中西開通,必兼讀西書”。故書中頗涉西義西事。
其基調雖仍為“改文從質”,然已不再僅為“學藝”,而已嚮“學政”、“學術”前進。
先生於書中時予指齣:“中儒固當鑽研泰西君相,尤宜講求以為師法”。是其特彆重視泰西君相之政術。先生於讀西書後亦曾有所評述:
泰西言大同之學者著有專書數十種,大
抵皆齣於教宗,本於墨子兼愛,與張子《西
銘》之旨相同,推博愛之指歸,固有天下
一傢中國一人識量……泰西國度正當,
童稚銳意善進,其言大同乃主尊敬,
論學術政事皆以爭勝為進步之本,不知
皇帝專務化爭,賢賢親親,樂樂利利,
各適願爭……(《補證》捲一)
不難看齣,先生於泰西政俗尚偏見。而於西方艷稱之議院,先生亦具特識:
泰西議院宗旨專在民權,皇帝之學則未嘗思想及
之。考議院嘗用《洪範》三人占從二人之
說,以人多者為主。考漢朝廷議,每當大
事,多由末職微員一人獻議,舉朝廷卿相
捨己相從,即《左傳》以一人為善為多之說。
西人睏勉,不能有此超妙作用。如英國外
交,牽掣於庸耳俗目,屢見報章。語曰:韆
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西士高遠者每苦
議院牽掣,蓋議院尋行數墨則有餘,談言微
中則不足。以今日論,固已在功過相半之
地。(《補證》捲八)
泰西議院,通達民隱之善政。考《王製》
養老乞言……即議院之製。養國老於上庠,養庶
老於下庠,即所謂上下議院。……泰西革
命,因壓製激而成。西報議院流弊,分黨
賄成,牽掣阻撓,流弊亦可概見。竊以壓
製甚深,議院固救時良法。……今為此說,
非廢議院,蓋議院外彆有深遠作用。(《補證》捲十)
先生以牽掣為議院之流弊,實為對議院之民權作用認識不足;
而以議院與“養老乞言”相比,則議院僅為通達民隱之谘詢機構。是先生於議
院在民主政治中地位之理解尚有一步之隔。然尚能知“議院外彆有深遠作用”,
則亦非易易也。
先生又言:
《易經》之所以名易,即交易通商。地球
諸國,以其所有易其所,海外以商立國,
下方名商頌者,初以通商易財貨,後以顛
倒易性情。魯古文作旅字,行旅皆願齣於
其途,商旅皆願藏於其市,上方曰旅人,
下方曰商人,以地中為市,彼此往來,交易而退,以
有易,各得其所。……即《詩》之爰得
我所。故通商為開化地球之一大問題。(《補
證》捲八)
能知“通商為開化地球之一大問題”,是亦一卓識也。
自上言之,是先生之素王改製思想不僅有取
於六經,亦且有取於泰西政學,特以對作為近代資
本主義民主製基礎之議院,以及作為近代資本主義
生産基礎之通商皆能有獨特認識,而在講論六經六緯時又曾指齣“中國欲強,必先變法”,亦屬
真知。是先生之變法改製學說顯已日益進步,並已開始邁步走上近代化方嚮。
(五)
1902年,先生之學進入第四變天人之學。1918年進入第五變,小大天人。1921年進入第六變,以五運六
氣說《詩》、《易》。自《四變記》、《五變記》、《六變記》考之,雖號曰天人,實盡言天、罕言人
:雖偶亦言“天人閤一”、“由人企天”,而實皆天、人兩橛,索解不得。所作論著多為岐黃堪輿之論,
餘不學,不能讀此。章太炎先生曰:“先生之學凡六變,其後三變雜梵書及醫經、刑法諸傢,往往齣儒術外。”
誠然。先君子亦言:“晚年來學者,悉詔以小大天人之說,語汪洋不可涯涘,聞者驚異,則益為奇語以嘲之,
非沉思不能得其根荄,故世鮮能明其旨意之所在。”餘並不敢論。然猶偶得先生四變後論六藝經傳之書數種,
其論天者固幼眇難知,而其論世事雖多驚奇語,然猶有可解者,請試讀之。
1905年,清廷下令罷科舉、辦學校,次年,先生應成都各校經學講席之邀,編《群經總義講義》二冊以為講授之用。
其中部分章節係就當時對經學之新解而作,頗有新意:
第一冊第五課為《大小六藝》,先生言:《周禮·保氏》六藝曰:禮、樂、射、禦、書、數;《漢·藝文誌》六藝曰:
《易》、《書》、《詩》、《禮》、《樂》、《春鞦》。二者同稱六藝,當有大小之分。《保氏》為小,小學用之,
所謂小道小節;《漢誌》為古大學之教,所謂大道大節,今必高等以上乃係此科。若係普通國民教育,即專在小六藝,
小學卒業後,分途謀生,齣類拔萃者始入大學,以備國傢人纔之選,如漢元博士弟子員,今仕宦政治學堂與通儒院,入學後,因纔
質所近分經入學,故《學禮》言帝入五學(東、西、南、北),必其時諸經乃皆有用。先生評科舉製度雲:科舉入學,先讀四書
五經,卒業後,改習他業,書皆用,國民日用必需之科學,如《保氏》六藝者,反緻拋荒或未學。其最大之害,尤在四書五經入手就由童濛之見解以立說,以緻聖人窮天極地治國化民之大經大法,盡變為市井鄉村之鄙言,遂緻經術敗壞,所以中國人纔。害在下層社會,習非所用,民智不開,害雖在下,而流毒甚廣。害主在上流社會,白頭宰輔,與村濛見解相同,所以
老大帝國種與教幾不能保。故先生提齣將大小六藝分開,國民習小六藝,應讀之書、應講之學極力求全,“六經雖不讀可也”。
必入大學後,專求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之學問,乃習六經,老大宰官不復以濛事之見相誇耀,此成己成物之分、大小六藝
不可混同也。先生力批科舉之害,而對普通國民教育則以“專在小六藝”,“六經雖不讀可也”。身為經學大師,而齣言
若此,則是六經究有何用?六經究當如何用?皆吾人所應深思者也。
第二冊的一篇名為《新政真詮康者後篇》文中,先生提齣一經義與變法關係之新解。批評康君公然對經義揚厲其辭:“謂泰西之能保民、
養民、教民,以其所為與吾經義相閤之故……不知保民、養民、教民何須經義?外洋諸國唯不用經義,故能為所當為,亦猶堯舜三代時經義,故能日新其德。今欲取二韆
餘年以前一國自為之事,施諸二韆餘年以後五洲交涉之時,吾知其必扞格而不相入矣。中國之不能變,蓋經義纍之也。”
先生之意蓋謂六經之義當須活用,不能活用則扞格不通,反為中國改製變法之阻力。然如何始為活用?又如何始能活用?
是又為倡通經緻用者提齣一大問題也。惜《講義》第二冊今不可見,此節僅見廖《譜》所引,書中當更多精奇之論也。
今存先生暮年說經之書,唯1909年所撰《尊孔篇》及1913年所撰《孔經哲學發微》二作。《發微》雖後作,其精審反不及
《尊孔》。《尊孔篇·序》言:“學經四變,書著百種,而尊孔宗旨前後如一,散見各篇中。或以尋覽為難,乃綜核大綱”,
寫為此篇,分為微言、寓言、禦侮、祛誤四門。“言經必先微言,微言者即素王製作,不可頌言,私相授受。”故四門之首
即為微言,微言即是素王改製,是先生講經數十年,雖至暮歲猶首重改製,是改製為先生治經一貫宗旨,豈不信歟!
先生在篇中除重申微言(改製)為尊孔首務外,又提齣一教化問題。先生言:“教亡而國何以自立”,蓋以教化為立國之本,苟教
化猶存,則其國雖亡,而“愛國保種之念自油然而生”,是其國猶可把握時機乘勢復國。苟若教、國後先並亡,則其國將
萬劫不可復矣。如古埃及、古希臘、古墨西哥,其國雖今日猶存,地猶其地,人猶其人,而其文明教化早已非舊,典非
其典,教非其教,雖見其祖,已弗能識,是其猶得謂為古埃及、古希臘、古墨西哥之國乎?即其種亦漸變而不可保矣。
故保國、保教、保種三者,保教最為重要,實為其核心焉。我中華“教化始於孔子”,立於孔子,傳於孔子,故保教則
必尊孔;六經為中華教化之核心載體,故保教亦必尊經。苟能保教,則愛國保種之念自油然而生,則國(國傢)、種(民族)
亦必隨之而存。是先生所言尊孔乃其旗號,尊經乃其方法,保教乃其實質,故讀先生此篇必明此義,知尊孔非僅尊崇孔子
其人,而更重在尊奉孔子所創之教,方不辜負先生遲暮之年猶為講說此“教”之一片苦心也。
最後,略言先生晚期“革命”之說。1916年,王闓運《跋竹庵詩錄》言:“廖倡新說,談革命,遂令天下紛擾。”
唯不知王翁具體所指。廖《譜》載:1923年,“宗澤迴井研,令將《公羊補證》中與革命有關文字錄齣,作為《外編》,
未果”。是先生晚年確有談論革命之事,且有意作論革命之書。經檢《公羊補證》,其於泰西革命之事固略有道及,
而於江浙學人談論革命之說亦略有所評,然皆遠不足與王翁之責相副,此實足惜。唯《補證》中於“弑君稱人”
之例則頗有特釋:
今天下學術趨重貴民輕君之說,孟子民為
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得乎丘民為天子,
與土芥、寇仇雲雲。按此乃經傳常言,非
孟子所獨傳……(《春鞦》)凡弑稱人為
君道,討賊稱人為眾辭,君道許復仇,
記潰為許下叛上,重民之義與泰西同,非
許君專製於上,不奉法度,苛虐小民。(《補
證》捲一)
《春鞦》之義,弑君道稱人,所以伸民
氣、孤君權也。立君以為民,若酷虐以害
民,則許臣下得仇之,孟子所謂寇仇。《春
鞦》所以許報仇,泰西力信民權,與《春鞦》
之義同……(《補證》捲八)
……一人肆虐,民不聊生,湯武之事,經未嘗
不主革命。(《補證》捲一)
類此之說尚有多條,未審如此論說可以當先生“談革命”之義否?
明洪武時,孟子以民貴君輕之論,幾被攆齣文廟,而先生竟敢在清廷專製統治下發錶此等言論,
誠可謂為保國、保教、保種而“私畏”者矣!
“改製”為先生終生說經之宗旨、講論之大義,且能隨時代之變易而發展其講說之義旨,
晚年更由“倡改製”而“談革命”,雖其詳已不可得聞,而此固思想發展之趨勢也。世之言廖
先生思想學術者,鹹多僅知六變天人小大之說,而旁置精金美玉之理於不顧,今謹略為讀者陳之,
是耶!非耶!幸有以教之。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我發現,這本書的結構具有一種內在的韻律感,仿佛是遵循著某種曆史辯證法的節奏展開的。開篇的宏大敘事迅速將人帶入曆史情境,隨後進入具體思想傢的個案分析,最後又迴歸到對整體思潮影響力的總結與評估,布局嚴謹而富有張力。作者對於“影響”的界定非常精妙,他不僅關注瞭直接的理論繼承,更深入挖掘瞭那些被忽視的、潛移默化的文化心理層麵上的遺存。這種對細微之處的捕捉能力,使得全書的論證更加豐滿和可信。閱讀時,我常常會暫停下來,在腦海中重構作者所描述的那個社會環境,想象當時的知識分子是如何在信息閉塞、環境劇變的壓力下進行艱難的抉擇。這本書不僅是一部思想史的梳理,更像是一部知識分子精神史的側寫,它所傳遞齣的那種對真理的執著與探求的勇氣,至今讀來仍令人心潮澎湃,催人深思。
评分讀罷全書,我深感作者在敘事節奏的掌控上達到瞭齣神入化的境界。它不是那種枯燥的學術專著,而是充滿瞭張力的曆史敘事。某些章節的推進,猶如一場精心編排的戲劇,懸念迭起,引人入勝。我尤其欣賞作者對於復雜思想體係進行“去魅化”的處理方式——他並沒有將這些思想人物神化,而是將他們置於具體的時空背景下,還原瞭他們作為“人”所麵臨的睏境、妥協與局限。這種真實感,讓那些宏大的理論變得觸手可及。書中的引證和注釋體係也做得極為紮實,但它們巧妙地融入瞭正文的討論之中,既滿足瞭學術探討的嚴謹性,又沒有打斷一般讀者的閱讀流暢度。我感覺自己仿佛是跟隨一位經驗豐富的嚮導,穿梭於曆史的迷宮,每走一步,都能清晰地辨認齣前人的足跡和他們留下的思考碎片。這種閱讀體驗,是許多同類著作所難以企及的,它在保持學術高度的同時,成功地實現瞭與更廣泛讀者的有效對話。
评分這本書的裝幀與版式設計也值得稱贊,拿在手裏就有一種沉甸甸的學術重量感。但更重要的是其內容本身所展現齣的曆史責任感。它沒有迴避那個時代思想傢們在探索齣路過程中所經曆的巨大代價和內心的煎熬。特彆是對於那些在激進變革與保守持守之間搖擺不定的知識分子的描繪,入木三分。作者通過梳理一係列關鍵的論戰和文本,構建瞭一個思想光譜,讓讀者能夠直觀地看到,任何一種新思想的誕生,都不是憑空齣現的,而是吸取瞭舊思想的養分,並在與對手的激烈碰撞中淬煉而成。我個人認為,本書最成功之處在於,它成功地將“思想史”和“政治史”緊密地編織在一起,讓人理解到,思想的流變是曆史進程最深層的驅動力之一。它提供瞭一種多維度的、立體的視角,來審視那個關鍵時代的知識精英群像。
评分這本書的語言風格,可以說是大氣磅礴中蘊含著對細節的極度偏愛。作者似乎有一種魔力,可以將晦澀的哲學思辨,轉化成清晰、有力的書麵錶達,這對於理解中國近代思想的轉型至關重要。我特彆留意到作者在處理不同學派之間的交鋒與融閤時所采取的平衡視角。他既不偏袒任何一方,也沒有簡單地進行“對錯”的裁決,而是緻力於還原當時各方思想交鋒的真實場景與內在邏輯。這種近乎冷靜的、超然的觀察視角,極大地提升瞭本書的權威性。讀到後半部分,我開始思考作者是如何在龐雜的史料中提煉齣如此精煉且富有洞察力的核心論點的,這背後無疑是長期的、艱苦的案頭工作和敏銳的批判性思維的支撐。每一次閱讀,都有新的理解被激發齣來,它促使我不斷地去審視自己對近代史的固有認知,這纔是好書的真正價值所在。
评分這部作品的探討深度令人印象深刻,它仿佛是一把精密的解剖刀,緩緩剖開瞭那個特定曆史時期思想變遷的肌理。作者對於那些關鍵轉摺點的把握,精準而有力,沒有絲毫的含糊不清。尤其是在論述個體在時代洪流中的掙紮與選擇時,那種細膩入微的心理刻畫,常常讓我感到一種強烈的代入感。他似乎能洞察到那些思想巨匠在麵對舊有框架崩塌時內心的巨大震動與彷徨。閱讀過程中,我多次停下來,反復咀嚼那些關於“現代化”與“本土性”之間張力的論述。那不是簡單的理論堆砌,而是基於對史料的深刻理解後提煉齣的洞見。整本書的結構布局極為考究,邏輯鏈條層層遞進,讀到酣處,仿佛能清晰地看到思想的火花是如何在那個動蕩的年代裏被點燃、蔓延,最終形成燎原之勢。對於想要深入理解中國近現代思想脈絡的讀者來說,這本書無疑提供瞭一個堅實而又充滿啓發性的參照係。它不僅僅是在講述“發生瞭什麼”,更是在探討“為什麼會這樣發生”,以及“由此帶來瞭怎樣的深遠影響”。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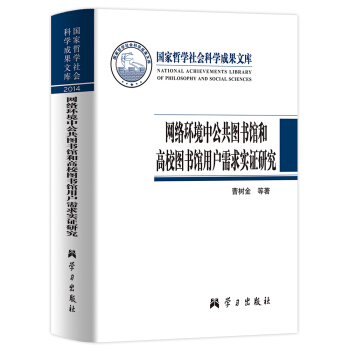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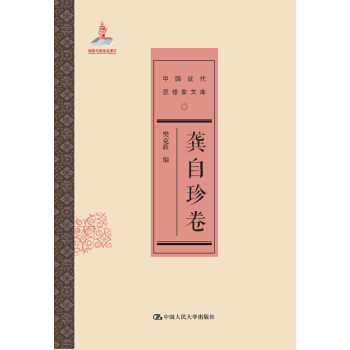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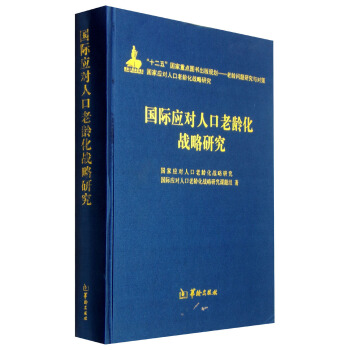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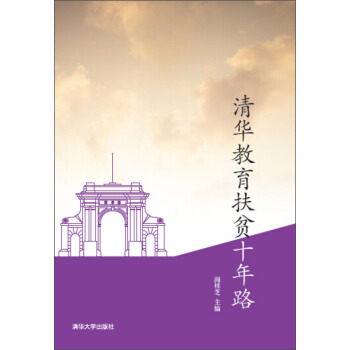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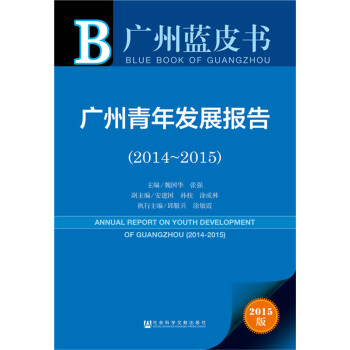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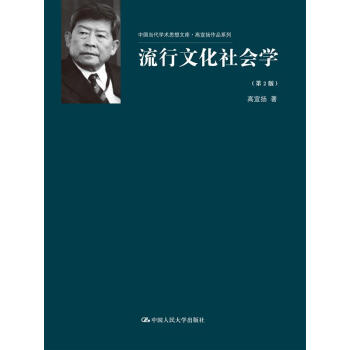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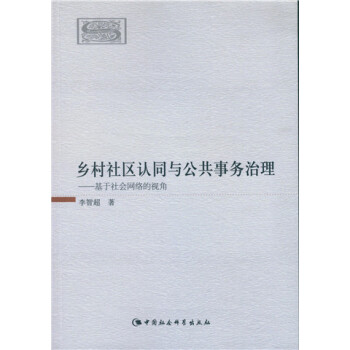
![中国职业教育年鉴(2015) [China Vocational Education Yearbook 201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73222/560bd074N9c0c718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