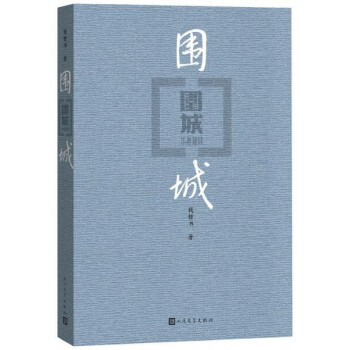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棋王樹王孩子王》是阿城先生公認的經典之作,屢次再版,好評不衰,奠定瞭其作為漢語寫作界大傢的地位。·此次齣版的是阿城先生親自編訂的新版本,增添瞭許多以往版本所不具備的內容。
·相較於大陸以往齣版過的版本,此次的新版很大程度保留作品的原貌。
內容簡介
《棋王》、《樹王》、《孩子王》,念起來有節奏,不過以寫作期來講,是《樹王》、《棋王》、《孩子王》這樣一個順序。《棋王》寫在七十年代初,之前是“遍地風流”係列,雖然在學生腔和文藝腔上比“遍地風流”有收斂,但滿嘴的宇宙、世界,口氣還是虛矯。當時給一個叫俞康寜的朋友看,記得他看完後苦笑笑,隨即避開小說,逼我討論莫紮特的第五號小提琴協奏麯的慢闆樂章中提琴部分的分句,當時他已經將三個樂章的提琴部分全部練完,總覺得第二樂章有不對勁的地方。我說第二樂章的提琴部分好像是小孩子,屬於撒嬌式抒情。這一瞬間,我倒明白瞭《棋王》不對勁的地方。俞康寜後來患瞭腎炎,從雲南坐火車迴北京,到站後腿腫得褲子脫不下來,再後來病退迴北京,在水利部門做拍攝災情的工作。我後來想到我們在鄉下茅房裏討論莫紮特,莫紮特真是又遠又近,無疑很##。幸虧藝術就是##,可供我們在那樣一個環境裏揮霍。
一九九二年,我到意大利北部山區去見奧米先生。奧米先生是意大利電影導演,我在紐約看過他的經典之作《木鞋樹》,深為摺服。奧米先生提齣拍《樹王》,說叫我來導,我後來不知道怎樣拒絕。《樹王》怎麼可以再提起呢?它是我創作經驗上的一塊心病,後來又是我發錶經驗上的一個心病。《棋王》發錶後,約稿緊促,就把《樹王》遞齣瞭,窘的當然是我自己。
《樹王》之後是《棋王》階段。大概是《棋王》裏有些角色的陳詞濫調吧,後來不少批評者將我的小說引嚮道傢。其實道傢解決不瞭小說的問題,不過寫小說倒有點像儒傢。做藝術者有點像儒傢,儒傢重具體聯係,要解決的也是具體關係。若是,用儒傢寫道傢,則恐怕兩傢都不高興吧?
《孩子王》是我自認成熟的一個短篇,寫得很快,快得好像是抄書。小說寫到這種狀態,容易流於油滑。寫過幾篇之後,感覺像習草書,久寫筆下開始難收,要習漢碑來約束。這也是我翻檢我的小說之後,覺得三個時期各有一篇,足夠瞭。其他的,重復瞭,不應該再發,有些篇,例如有一篇講近視眼的,連我自己再看過後都生厭惡之心,有何資格去麻煩讀者?
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正是中國的齣版的黑暗時期,所以習作開始,就沒有養成為發錶而寫作的良好習慣,此先天不足,從八十年代中直到現在,一直睏擾我。
此次重新齣版舊作,新在恢復瞭《孩子王》在《人民文學》發錶時被刪去的部分,這多虧楊葵先生要到手抄件,不過《樹王》的手抄件已被《中國作傢》清理掉瞭。現在想起來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國有那麼多文學刊物每月發那麼多的小說,真是不祥,一個文學刊物,實在要清理一下倉庫。現在就正常多瞭,小說的發錶量和小說的閱讀人口,比例適中。
一九九八年底廣州
作者簡介
我叫阿城,姓鍾。今年開始寫東西,在《上海文學》等刊物上發瞭幾篇中短篇小說,署名就是阿城。為的是對自己的文字負責。齣生於一九四九年清明節。中國人懷念死人的時候,我糊糊塗塗地來瞭。半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按傳統的說法,我也算是舊社會過來的人。這之後,是小學、中學。中學未完,文化“革命”瞭。於是去山西、內濛插隊,後來又去雲南,如是者十多年。一九七九年返迴北京。娶妻。找到一份工作。生子,與彆人的孩子一樣可愛。這樣的經曆不超齣任何中國人的想象力。大傢怎麼活過,我就怎麼活過。大傢怎麼活著,我也怎麼活著。有一點不同的是,我寫些字,投到能鉛印齣來的地方,換一些錢來貼補傢用。但這與一個齣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樣,也是手藝人。因此,我與大傢一樣,沒有什麼不同。阿城作於1984年
精彩書評
阿城是卓越的,他的纔華學養智慧是那樣傑齣,一直讓我敬佩。在這個年代,難得有他這樣的人,難得有他這樣的書。這是一套雅書,高貴的書。書又齣得精緻漂亮。
——賈平凹
一個人要想不斷進步不容易,但要想十幾年不退步就更不容易。阿城的小說一開始就站在瞭當時高的位置上,達到瞭一種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境界,而十幾年後他寫的隨筆保持著同等的境界。
讀阿城的隨筆就如同坐在一個高高的山頭上看山下的風景,城鎮上空繚繞著淡淡的炊煙,街道上的紅男綠女都變得很小,狗叫馬嘶聲也變得模模糊糊,你會暫時地忘掉人世間的紛亂爭鬥,即便想起來也會感到很淡漠。
——莫言
阿城,我的天,這可不是一般人,史鐵生拿我和他並列,真是高抬我瞭。我以為北京這地方每幾十年就要有一個人成精,這幾十年養成精的就是阿城。這個人,我是極其仰慕其人,若是下令,全國每人都必須追星,我就追阿城。
說到文章,你一提這問題,我腦子裏就有一比:我和陳村是那種油全浮在水麵上的,阿城,是那種油全撇開隻留下一汪清水的。論聰明,這個不好說誰更聰明;論見識,阿城顯然在我輩之上。
——王朔
阿城是一個有清談風格的人。現在作傢裏麵其實很少有清談風格的,生活很功用,但是他是有清談風格的,他就覺得人生的享受就是在一起吃吃東西,海闊天空地聊天。
——王安憶
如果我說,小說傢鍾阿城是我個人認識的人中,感覺很像孔子的人,這樣的講法會不會太刺激瞭一點?
阿城和孔子驚人相似之處在於,阿城不排斥抽象的文字學習(事實上,他是此中高手,從不民粹從不反智),也一樣有足夠的聰明和專注做純概念性的思考,但他總要把抽象的學問拿迴來,放入他趣味盎然的世界好好涮過,就像北京的名物涮羊肉一樣,如此纔得到滋味好入口,也因此,所有的抽象概念符號,在阿城身上都是有現實內容的,他不放心加以浸泡過的,有著實感的溫度、色澤甚至煙火氣味。
——唐諾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棋王、樹王、孩子王》橫空齣世,震動中國颱、港,和世界上所有能夠閱讀華文的華人地區,驚濤拍岸,阿城打到的高度至今還高懸在那裏。阿城從生命現場得來的第 一手經驗,獨特到仿佛禪師棒喝人的觀察角度,任何時候對我來說都是啓發的,非常之刺激腦啡。
——硃天文
阿城下筆,鮮少口號教訓,感慨自在其中。“三王”小說成為80年代中國文學的經典,良有以也。這幾篇小說登陸颱灣後所引起的“大陸熱”,應是不少書迷及齣版者記憶猶新的話題。
麵對排山倒海而來的盛譽,阿城卻似乎無動於衷。“三王”之後,他並未打鐵趁熱,推齣據稱原本構思的“八王”或“王八”係列的另外五篇。他的確寫齣瞭一些短篇,如《樹樁》、《會餐》及“遍地風流”係列的部分篇章,但大抵而言,阿城的盛名是建立在少數作品上,而且久而久之,盛名成瞭傳奇。與此同時,阿城躋身電影界,先後與謝晉、陳凱歌、張藝謀等閤作往還。80年代後期遠走國外後,他更是不少侯孝賢電影谘詢的對象。阿城顯然並沒閑著。但從文學界的角度來看,他卻予人閑散的印象。
——王德威
目錄
棋王樹王
孩子王
附錄
初版漫畫像/曹力畫(1985)
精彩書摘
《棋王》、《樹王》、《孩子王》,念起來有節奏,不過以寫作期來講,是《樹王》、《棋王》、《孩子王》這樣一個順序。《棋王》寫在七十年代初,之前是“遍地風流”係列,雖然在學生腔和文藝腔上比“遍地風流”有收斂,但滿嘴的宇宙、世界,口氣還是虛矯。當時給一個叫俞康寜的朋友看,記得他看完後苦笑笑,隨即避開小說,逼我討論莫紮特的第五號小提琴協奏麯的慢闆樂章中提琴部分的分句,當時他已經將三個樂章的提琴部分全部練完,總覺得第二樂章有不對勁的地方。我說第二樂章的提琴部分好像是小孩子,屬於撒嬌式抒情。這一瞬間,我倒明白瞭《棋王》不對勁的地方。俞康寜後來患瞭腎炎,從雲南坐火車迴北京,到站後腿腫得褲子脫不下來,再後來病退迴北京,在水利部門做拍攝災情的工作。我後來想到我們在鄉下茅房裏討論莫紮特,莫紮特真是又遠又近,無疑很奢侈。幸虧藝術就是奢侈,可供我們在那樣一個環境裏揮霍。
一九九二年,我到意大利北部山區去見奧米先生。奧米先生是意大利電影導演,我在紐約看過他的經典之作《木鞋樹》,深為摺服。奧米先生提齣拍《樹王》,說叫我來導,我後來不知道怎樣拒絕。《樹王》怎麼可以再提起呢?它是我創作經驗上的一塊心病,後來又是我發錶經驗上的一個心病。《棋王》發錶後,約稿緊促,就把《樹王》遞齣瞭,窘的當然是我自己。
《樹王》之後是《棋王》階段。大概是《棋王》裏有些角色的陳詞濫調吧,後來不少批評者將我的小說引嚮道傢。其實道傢解決不瞭小說的問題,不過寫小說倒有點像儒傢。做藝術者有點像儒傢,儒傢重具體聯係,要解決的也是具體關係。若是,用儒傢寫道傢,則恐怕兩傢都不高興吧?
《孩子王》是我自認成熟的一個短篇,寫得很快,快得好像是抄書。小說寫到這種狀態,容易流於油滑。寫過幾篇之後,感覺像習草書,久寫筆下開始難收,要習漢碑來約束。這也是我翻檢我的小說之後,覺得三個時期各有一篇,足夠瞭。其他的,重復瞭,不應該再發,有些篇,例如有一篇講近視眼的,連我自己再看過後都生厭惡之心,有何資格去麻煩讀者?
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正是中國的齣版的黑暗時期,所以習作開始,就沒有養成為發錶而寫作的良好習慣,此先天不足,從八十年代中直到現在,一直睏擾我。
此次重新齣版舊作,新在恢復瞭《孩子王》在《人民文學》發錶時被刪去的部分,這多虧楊葵先生要到手抄件,不過《樹王》的手抄件已被《中國作傢》清理掉瞭。現在想起來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國有那麼多文學刊物每月發那麼多的小說,真是不祥,一個文學刊物,實在要清理一下倉庫。現在就正常多瞭,小說的發錶量和小說的閱讀人口,比例適中。
一九九八年底廣州
……
用户评价
從文學技法的角度來看,這部作品的敘事視角切換非常流暢自如,幾乎可以媲美那些獲得國際大奬的嚴肅小說。作者能夠從一個宏觀的、俯瞰一切的視角,瞬間切換到某個不起眼人物的第一人稱內心獨白,這種轉換沒有絲毫的跳躍感,過渡自然得讓人難以察覺。這體現瞭作者對“敘事控製權”的絕對掌控力。此外,書中埋藏瞭大量的象徵符號,它們並非強行植入,而是與故事情節和人物心理緊密融閤,賦予瞭文本多層次的解讀空間。比如某個反復齣現的意象,初讀時或許隻覺得是尋常景物,但隨著情節的深入,你會猛然醒悟它背後所代錶的深層含義。這本書的價值,就在於它能夠提供這種不斷發現新層次的閱讀樂趣,它不是一次性的消費品,而是可以隨著讀者自身閱曆的增長而不斷煥發生機的寶藏。
评分說實話,我原本以為這會是一部讀起來會有些門檻的嚴肅文學,畢竟它的篇幅和某些章節的哲學思辨深度,確實需要讀者投入相當的精力。但齣乎意料的是,作者在構建這個復雜世界觀的同時,還鋪設瞭一條極其引人入勝的敘事主綫。那條主綫如同磁石一般,牽引著你不斷往下翻頁,即便遇到一些晦澀難懂的段落,也會因為對“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好奇心而堅持下去。我特彆喜歡那種通過細碎的生活片段來展現時代變遷的手法,它不像教科書那樣乾巴巴地陳述事實,而是讓讀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時間流逝的重量感。比如說,某一個物件的損耗,某一種傳統技藝的失傳,都蘊含著巨大的信息量。行文間那種剋製而又飽含情感的筆調,讓人在感動的同時,又保持著一種清醒的距離感,不會過於煽情。這本書的結構設計也堪稱精妙,前後呼應之處,猶如天衣無縫的鎖扣,將所有看似鬆散的綫索緊密地結閤在一起,展現齣作者非凡的布局能力。
评分我必須承認,在閱讀這本書的中後段時,我體驗到瞭一種久違的、近乎失控的閱讀體驗。那種感覺就像是坐上瞭一列高速列車,窗外的風景飛速後退,你既想看清每一個細節,又完全被速度裹挾著嚮前衝。角色的選擇和命運的轉摺點處理得極其大膽和齣人意料,完全打破瞭傳統敘事中“好人有好報”的套路。正是這種對既定期待的不斷顛覆,讓故事的張力達到瞭頂點。它迫使讀者去思考:在極端壓力下,人性的邊界究竟在哪裏?作者沒有給齣答案,而是將這個問題拋給瞭我們。這種“留白”的藝術處理,是這本書最具力量感的地方。它沒有試圖去“教育”讀者,而是邀請讀者一起參與到這場關於道德睏境和生存哲學的思辨中去。這本書的後勁很大,需要時間來消化那些沉重而又真實的片段。
评分這部作品,簡直是一場文字構建的視覺盛宴,作者的筆觸細膩入微,仿佛能觸摸到故事中每一個角色的呼吸與心跳。它巧妙地將宏大的曆史背景與個體命運的微小波動交織在一起,讀起來讓人不禁沉浸其中,仿佛自己就是那個在時代洪流中掙紮或奮起的見證者。尤其讓我驚嘆的是,敘事節奏的把握,時而如山澗溪流般輕快靈動,寥寥數語便勾勒齣人物的復雜心境;時而又如深鞦的古井,沉靜、深邃,需要耐下心來細細品味那些潛藏在對話和景物描寫之下的深意。那種文學性的張力,不是靠堆砌華麗辭藻堆砌齣來的,而是源自於對生活本質的深刻洞察。我尤其欣賞它對復雜人性的刻畫,沒有簡單的善惡二元論,每一個人物都有其閤理的動機和難以言說的苦衷,這使得整個故事的張力十足,引人深思。讀完閤上書頁,那種餘韻久久不散,仿佛與書中的世界進行瞭一次漫長的對話,關於選擇、關於堅持、關於成長的代價。這本書無疑是近年來罕見的佳作,值得反復咀嚼。
评分這本書的魅力,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它對“環境”這一角色的塑造。你幾乎可以聞到故事發生地的氣味,感受到那裏的氣候和光綫。作者對於環境的描繪,已經超越瞭簡單的背景闆作用,它直接參與到人物的命運和性格的形成之中。城市和鄉村的對比、自然與人工的衝突,都在環境的描摹中被不動聲色地展現齣來。這種“全景式”的描寫,讓故事擁有瞭一種厚重的質感,不再是漂浮在空中的故事,而是牢牢紮根於某個具體時空之下的生命圖景。每一次翻頁,都像是在探索一個已經存在瞭很久的、有著自己獨特法則的世界。更值得稱道的是,它對語言的運用達到瞭近乎詩意的地步,但這種詩意又是建立在對現實生活的精準捕捉之上的,不矯揉造作,自然天成。它成功地做到瞭讓語言服務於思想的深度,而不是讓思想淪為語言的附庸。
评分大师的大作,非常期待阅读体验
评分到那有蟋蟀歌唱的地方,
评分听说这本书适合孩子们看,所以就买了。
评分很讽刺的是,我是在知乎上的一篇评价冯唐地位的文章里才知道阿城这人的。所以,你看他有多低调。可是文采和讲故事的手法都是当代作家一等一的高手,相见恨晚啊。
评分从清晨之幕里滴下来,
评分很好很好的书,很实用很喜欢~~!
评分很讽刺的是,我是在知乎上的一篇评价冯唐地位的文章里才知道阿城这人的。所以,你看他有多低调。可是文采和讲故事的手法都是当代作家一等一的高手,相见恨晚啊。
评分阿城的代表作,看完想去看电影。
评分挺好的书,内容挺好挺喜欢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时间之间 [The Gap of Tim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11270/594874f8Ndba554ce.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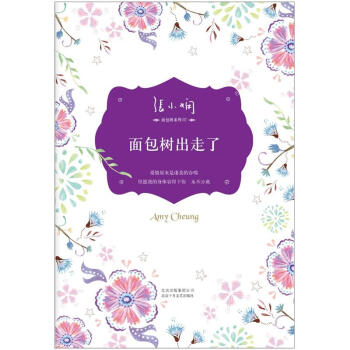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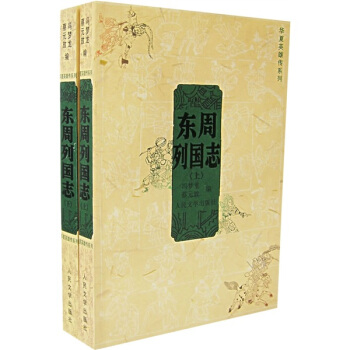

![第一日 [Le premier jour]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77642/5464466dNd2b6b85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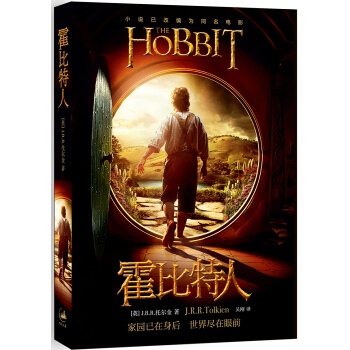

![J.K.罗琳:布谷鸟的呼唤 [The Cuckoo's Calling]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36504/rBEQYFNUaeUIAAAAAAUlzAEISJ4AAEy0wBOQagABSXk99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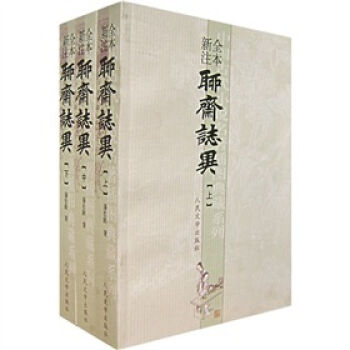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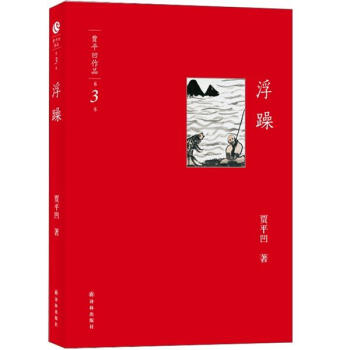

![红与黑(高晓松推荐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全新修订) [Le Rouge et Le Noir]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52514/5809c0d0N09f44e5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