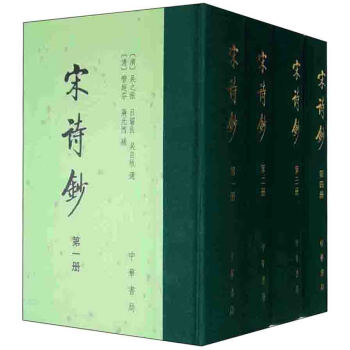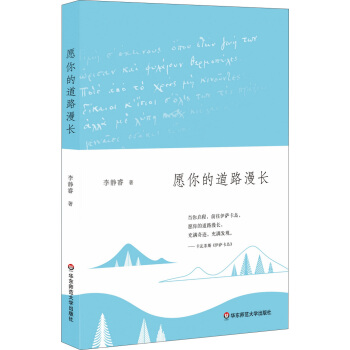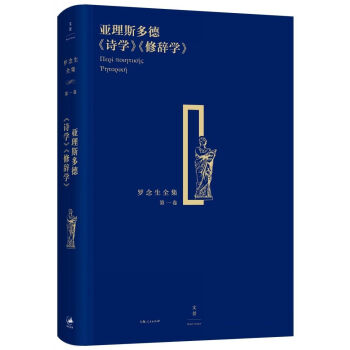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一套《羅念生全集》,一座奧林匹斯山。☆全麵完整:《羅念生全集》增訂典藏紀念版,凡十捲,凡5200頁,全新整理修訂。
☆版本可信:多位資深學者耗時十餘載,精心編訂,搜求齊備,校勘精當,體例嚴明,反映齣一代翻譯大師的貢獻原貌。
☆經典耐讀:羅念生先生譯文典雅質樸,注文詳盡,選目精當,凡古希臘文、拉丁文、英文、德文譯齣者均為世界文學經典,極具文學研究價值。
內容簡介
《亞理斯多德<詩學><修辭學>》收集瞭羅念生先生翻譯的亞理斯多德的文藝理論著作《詩學》和《修辭學》以及一篇古希臘佚名者的《喜劇論綱》。
作者簡介
羅念生(1904.7.12—1990.4.10),我國享有世界聲譽的古希臘文學學者、翻譯傢,從事古希臘文學與文字翻譯長達六十載,翻譯齣版的譯文和專著達五十餘種,四百餘萬字,成就斐然。他譯齣荷馬史詩《伊利亞特》(與王煥生閤譯),古希臘三大悲劇傢埃斯庫羅斯、歐裏庇得斯和索福剋勒斯的悲劇作品、阿裏斯托芬的喜劇作品,以及亞裏士多德的《詩學》《修辭學》、《伊索寓言》等多部古希臘經典著作,並著有《論古希臘戲劇》《古希臘羅馬文學作品選》等多部作品,對古希臘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做齣瞭不可磨滅的貢獻。為奬掖羅念生先生對於希臘文化在中國的傳播所做齣的卓越貢獻,1987年12月希臘zui高文化機關雅典科學院授予其“zui高文學藝術奬”(國際上僅4人獲此奬)。1988年11月希臘帕恩特奧斯政治和科技大學授予其“榮譽博士”稱號(國際上僅5人獲此殊榮)。
目錄
詩 學
譯者導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修辭學
譯者導言
第一捲
第一章
修辭術與論辯術——修辭術課本編纂者——或然式證明——“證
明”——修辭式推論——修辭術的功用
第二章
修辭術的定義——三種或然式證明——演說者的性格——聽眾的心
理——例證法——修辭式推論——必然的事——或然的事——確
實的證據——或然的證據——例子——通用部目——專用部目
第三章
政治演說——訴訟演說——典禮演說——各種演說的目的——命題的
題材——事情的大小
第四章
政治演說所討論的問題——財政問題——戰爭與和平問題——城邦的
保衛問題——進齣口問題——立法問題
第五章
幸福的定義——幸福的成分
第六章
好事的定義——好事——好東西——成問題的好東西
第七章
更好更有用的東西——好東西的定義——本原——因——有智力的人
的判斷
第八章
民主政體——寡頭政體——“賢人”政體——獨頭政體——君主
製——獨裁製——各種政體的目的——各種政體的性格
第九章
稱贊與譴責的對象——高尚的事的定義——各種美德——正直——勇
敢——節製——慷慨——豪爽——大方——見識——各種高尚的
事——稱贊與規勸——誇大法——比較法
第十章
控告與答辯——害人的定義——有意的行動——害人的原因——行動
的原因
第十一章
快感的定義——愉快的事物——欲念——迴憶——期望——報復——
遊戲——榮譽——變化——求知——藝術作品——知識——滑稽
的事物
第十二章
害人者的心情——害人者的種類
第十三章
法律——特彆法——普通法——無意的行動——有意的行動——選
擇——不成文法——公平法——不幸事件——錯誤——罪行
第十四章
罪行的大小——演說技巧
第十五章
不屬於藝術本身的或然式證明——法律的利用——古代的見證——神
示——諺語——近代的見證——契約——拷問——發誓
第二捲
第一章
演說者的品質——判斷者的心情——見識——美德——好意——情
感——發怒者的心情——發怒的對象——發怒的原因
第二章
忿怒的定義——輕視——刁難——侮慢——發怒者的心情——發怒的
對象——發怒的原因
第三章
溫和的定義——溫和的態度——使人變溫和的心情
第四章
友愛的定義——朋友——人們所喜愛的人——敵視——憎恨
第五章
恐懼的定義——可怕的事——可怕的人——畏懼的心情——膽量——
使人壯膽的事物——使人壯膽的心情
第六章
羞恥的定義——無恥的定義——使人感到羞恥的事物——使人感到羞
恥的情況
第七章
慈善的定義——需要——令人感謝的人——非慈善的行動
第八章
憐憫的定義——憐憫的心情——能引起憐憫的事物——恐怖
第九章
憤慨——使人感到憤慨的事物——憤慨的心情
第十章
忌妒的定義——感到忌妒的人——使人感到忌妒的事物
第十一章
羨慕的定義——羨慕的對象
第十二章
年輕人的性格——欲念——樂觀——勇敢——心誌——交遊
第十三章
老年人的性格——多疑——膽怯——自私
第十四章
壯年人的性格——適中
第十五章
高貴齣身的人的性格——傢族的退化
第十六章
富人的性格——奢侈
第十七章
當權者的性格——認真
第十八章
判斷者——通用部目
第十九章
可能的事——已經發生的事——將要發生的事——大事小事
第二十章
例子——曆史事實——比喻——寓言
第二十一章
格言的定義——補充語——格言的用處
第二十二章
修辭式推論的方法——證明式修辭式推論——否定式修辭式推論
第二十三章
證明式修辭式推論的二十一個部目——否定式修辭式推論的七個部目
(第22—28 部目)——最受歡迎的三段論
第二十四章
假冒的修辭式推論的幾個部目
第二十五章
反駁——提異議的方式
第二十六章
誇大——縮小
第三捲
第一章
風格——朗讀——散文的風格
第二章
風格的美——普通字——本義字——隱喻字——附加詞——指小詞
第三章
風格的弊病——濫用雙字復閤名詞——濫用生僻字——濫用附加
詞——濫用隱喻字
第四章
明喻——類比式隱喻
第五章
語言的正確性的五個要求
第六章
使風格具有分量的六個辦法
第七章
錶現情感的風格——錶現性格的風格——風格的適閤性
第八章
散文的節奏——派安節奏
第九章
連串句——環形句——對立子句——等長句——相似句
第十章
巧妙的話——隱喻
第十一章
生動性——隱喻——騙局——明喻
第十二章
筆寫的文章的風格——論戰的演說的風格
第十三章
“提齣”——或然式證明——序論——結束語
第十四章
序論
第十五章
消除反感的十二個辦法
第十六章
陳述的方式——陳述的速度——錶現性格的陳述——錶現情感的陳述
第十七章
爭論之點——證明——反駁
第十八章
發問的四種好時機——迴答的方法——譏笑
第十九章
結束語的四種作用——重述論點
譯後記
喜劇論綱
譯者導言
喜劇論綱
精彩書摘
專名索引第一章關於詩的藝術本身[1]、它的種類、各種類的特殊功能,各種類有多少成分,這些成分是什麼性質,詩要寫得好,情節應如何安排,以及這門研究所有的其他問題,我們都要討論,現在就依自然的順序,先從首要的原理開頭[2]。
史詩和悲劇、喜劇和酒神頌以及大部分雙管簫樂和竪琴樂——這一切實際上是摹仿[3],隻是有三點差彆,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對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
有一些人(或憑藝術,或靠經驗),用顔色和姿態來製造形象,摹仿許多事物[4],而另一些人[5]則用聲音來摹仿;同樣,像前麵所說的幾種藝術,就都用節奏、語言、音調來摹仿,對於後二種,或單用其中一種,或兼用二種[6],例如雙管簫樂、竪琴樂以及其他具有同樣功能的藝術(例如排簫樂),隻用音調和節奏(舞蹈者的摹仿則隻用節奏,無需音調,他們藉姿態的節奏來摹仿各種“性格”、感受和行動),而另一種藝術[7]則隻用語言來摹仿,或用不入樂的散文,或用不入樂的“韻文”[8],若用“韻文”,或兼用數種,或單用一種,這種藝術至今〈沒有名稱〉[9]。(我們甚至沒有一個共同的名稱來稱呼索福戎和塞那耳科斯的擬劇與蘇格拉底對話[10];假使詩人用三雙音步短長格或簫歌格或同類的格律[11]來摹仿,這種作品也沒有共同的名稱——除非人們把“詩人”一詞附在這種格律之後,而稱作者為“簫歌詩人”或“史詩詩人”;其所以稱他們為“詩人”不是因為他們會摹仿,而一概是因為他們采用某種格律[12];即便是醫學或自然哲學的論著,如果用“韻文”寫成,習慣也稱這種論著的作者為“詩人”,但是荷馬與恩拍多剋利除所用格律之外[13],並無共同之處,稱前者為“詩人”是閤適的,至於後者,與其稱為“詩人”,毋寜稱為“自然科學傢”;同樣,假使有人兼用各種格律來摹仿,像開瑞濛那樣兼用各種格律來寫《馬人》[混閤體史詩],這種作品也沒有共同的名稱。[14])[也應稱為詩人。][15]這些藝術在這方麵的差彆,就是這樣的。
有些藝術,例如酒神頌和日神頌[16]、悲劇和喜劇,兼用上述各種媒介,即節奏、歌麯和“韻文”;差彆在於前二者同時使用那些媒介,後二者則交替著使用。[17]這就是各種藝術進行摹仿時所使用的種差[18]。
注 釋
[1]“ 詩的藝術本身”指詩的藝術這個屬,即詩的藝術的整體,和詩的藝術的“種類”相對。“詩的藝術”或解作“詩”,以下同此。
[2] 按照“自然的順序”,“屬”(詩的藝術本身,即詩的藝術整體)在前,“種類”在後。“首要的原理”指有關詩的藝術本身的原理。
[3] 亞理斯多德並不是認為史詩、悲劇、喜劇等都是摹仿,而是認為它們的創作過程是摹仿。柏拉圖認為酒神頌不是摹仿藝術。到瞭亞理斯多德的時代,酒神頌已經半戲劇化,因為酒神頌中的歌有些像戲劇中的對話,因此亞理斯多德認為酒神頌的創作過程也是摹仿。酒神頌采用雙管簫樂,日神頌采用竪琴樂。此處所指的音樂是無歌詞的純雙管簫樂和純竪琴樂。其中一些摹仿各種聲響。
[4]“ 一些人”指畫傢和雕刻傢。古希臘的雕刻上顔色。“經驗”原文作“習慣”,指勤學苦練所得的經驗。總結經驗,掌握原則,則經驗上升為藝術。
[5]“ 另一些人”指遊吟詩人、誦詩人、演員、歌唱傢。
[6]“ 節奏”是此處所說的幾種藝術所必需的,但可以單獨使用(即不附帶“語言”或“音調”),例如舞蹈隻使用節奏。若隻使用“語言”(例如散文)或隻使用 “音調”(例如器樂),“節奏”也附帶使用,因為隻使用“語言”的散文和隻使用“音調”的器樂也有“節奏”。若兼用“語言”和“音調”(例如抒情詩和戲劇),“節奏”還是附帶使用。
[7]“ 另一種藝術”抄本作“史詩”。
[8] 亞理斯多德所說的“韻文”指狹義的“韻文”(與“歌麯”相對),隻包括六音步長短短格(即英雄格,亦稱史詩格)、三雙音步(六音步)短長格和四雙音步(八音步)長短格。酒神頌采用入樂的“韻文”,史詩則采用不入樂的“韻文”,即六音步長短短格。
[9]“ 沒有名稱”是後人填補的。
[10] 索福戎(Sophron)是敘拉古(Syrakousai)擬劇作傢,公元前5 世紀中葉的人。塞那耳科斯(Xenarkhos)是索福戎的兒子,也是個擬劇作傢。“蘇格拉底對話”指描述蘇格拉底的言行和生活的對話,是柏拉圖和其他的人寫的(這種體裁並不是柏拉圖首創的)。“蘇格拉底對話”(例如柏拉圖的早期對話)和“擬劇”很相似,這種對話也可稱為“擬劇”。亞理斯多德在他的對話《詩人篇》的片段(第72 段)中認為索福戎的擬劇和阿勒剋薩墨諾斯(Alexamenos)的對話(第1 篇“蘇格拉底對話”)都是散文,並且都是“詩”(摹仿品)。亞理斯多德在此處指齣沒有共同的名稱來錶示索福戎和塞那耳科斯的擬劇與蘇格拉底對話,是用不入樂的散文寫成的作品。亞理斯多德把他的老師柏拉圖作為一個詩人(意即摹仿者)看待。柏拉圖攻擊詩人,他自己卻也是個詩人。
[11]“ 簫”指雙管簫。“簫歌格”(一譯挽歌格)是一種雙行體,首行是六音步長短短格,次行是五音步,次行的節奏比較復雜,大體說來,仍是長短短格。“同類的格律”包括六音步長短短格。
[12] 亞理斯多德認為這樣稱呼是不妥當的,因為詩人所以被稱為“詩人”,是因為他是摹仿者,而不是因為他是某種格律的使用者。在亞理斯多德看來,格律不是詩的主要因素。
[13] 恩拍多剋利(Empedokles),是西西裏的哲學傢,公元前5 世紀中葉的人,他的哲學著作是用六音步長短短格“韻文”寫的。盡管亞理斯多德在他的《詩人篇》中(片段第70 段)認為恩拍多剋利的風格有詩意,但此處與真正的詩作對舉,他卻認為他的作品不是“詩”。
[14] 開瑞濛(Khairemon)是公元前4 世紀悲劇詩人。《詩學》第24 章說開瑞濛混用六音步長短短格、三雙音步短長格和四雙音步長短格。他大概還同時采用過“簫歌格”(參見本章注[11])。“馬人”指馬身人頭的肯陶洛斯(kentauros),此處所說的《馬人》是一齣悲劇或薩堤洛斯(Satyros)劇(笑劇)。“混閤體史詩”是僞作,因為《馬人》是戲劇,不是史詩。“這種作品也沒有共同的名稱”是補充的。
[15]“ 也應稱為詩人”是僞作,與亞理斯多德的意思不閤(參看本章注[12])。
[16]“酒神頌”和“日神頌”屬於抒情詩(參看本章注[3]),《詩學》中隻提及這兩種抒情詩,而沒有專論抒情詩。此外,戲劇中的“閤唱歌”也屬於抒情詩。“酒神頌”分節,“日神頌”不分節。
[17]“歌麯”在此處用來代替“音調”,參看第1 章第3 段。“歌麯”由歌詞(即語言)、音調和節奏組成。“韻文”在此處用來代替“語言”,指狹義的“韻文”(參看本章注[8])。“韻文”由言詞(即語言)及節奏組成。歌麯與“韻文”已包含節奏,但節奏在此處又作為媒介之一。在戲劇中,“歌麯”用於閤唱歌中,“韻文”用於對話中(主要用三雙音步短長格,偶爾用四雙音步長短格),故說“交替著使用”。
[18]“ 種差”是使“種”呈現差彆之物,此處指“媒介”。其他兩種“種差”是“對象”與“方式”。
詩學是必看的。嚮羅老緻敬
《詩學》寫得多麼好,後代的文論傢們在亞氏門前顫抖吧!
隻讀瞭第一部分《詩學》,真是字字珠璣啊。後世所有關於文字的創作都沒超齣《詩學》所討論的範疇。果然是站在西方文化源頭的點評,高屋建瓴。
話說後麵那個是喜劇論綱,猜測是亞氏學派的人仿亞氏的悲劇理論寫的。前384的亞裏士多德怎麼辣麼厲害?腦洞大開啊!不過燦的歸納也好細緻!思路很清楚!終於能看一迴瞭。。。
《詩學》:100來頁,很薄,花瞭一下午時間就看完瞭。書中內容基本上是以埃斯庫羅斯、索福剋勒斯、歐裏庇得斯的悲劇以及荷馬的史詩為原材料對古希臘的悲劇和史詩進行論述,幸好這些原材料之前都看過,否則這本書真看不懂。這本書要放到現在絕對是一篇優秀博士論文! 《修辭學》:說服與狡辯的藝術,感覺像在學語文。
……
前言/序言
《羅念生全集》即將齣版。當我聽到這一喜人信息時,最初的感覺是:這一套大書的編成齣版會像是在中國文化大地上搬來瞭一座希臘群神聚居的奧林波斯山一樣。這是羅念生先生六十多年文藝勞作的碩果匯集,是中國文化建設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梁柱和豐碑。我看到瞭《全集》十捲的詳細目錄。很清楚,《全集》的主要內容是古希臘文學——文論、悲劇、喜劇、詩歌、散文等的翻譯和研究,在十捲中占有六捲(包括少量古羅馬文學作品的譯介和其他譯文)。最後兩捲則是羅老自己創作的散文、詩歌以及書信、年譜、傳記等等。而在古希臘文學的翻譯和研究中,重點又是古希臘文論、悲劇、喜劇等。《全集》共有三百五十萬言,真是洋洋大觀。
我想到古希臘文學在現代中國的命運。
早在上世紀20年代初,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古希臘文學開始進入中國。羅老曾說:“五四運動後不久,我們就讀到楊晦翻譯的埃斯庫羅斯的悲劇《被幽囚的普羅米修斯》。”(按:本劇1922年齣版)周作人曾說他1908年就開始學古希臘語,30年代初他譯齣瞭一本《希臘擬麯》(羅老後來把“擬麯”譯為“摹擬劇”,顯然更易懂些)。那一陣齣版過好幾種古希臘悲劇的譯本。一扇窗戶打開瞭,知識分子們忽然得知,遠在三韆年前的西周時期,希臘就齣現瞭荷馬史詩。大緻與孔老夫子同時,希臘的酒神節上就有瞭悲劇演齣,第一位大悲劇傢埃斯庫羅斯比孔子隻小二十六歲,可說是“同時代人”。
人們發現,我們自稱文明古國,固然不錯,但遠在明麗的愛琴海畔,神奇的奧林波斯山下,竟還有比我們更古老、豐富而燦爛的文化。那麼多神話傳說,那麼多英雄人物,詩歌、散文、戲劇、雕塑、繪畫、哲學、文論,無不閃爍著智慧的光輝,引人入勝。在相當一部分文化人中,古希臘成為熱門話題。雖然引進的古希臘作品、古籍其實很少,還談不上什麼深入研究,但終是在“五四”開放精神下,有瞭一個開端。然而我們國傢不幸,列強環伺,日寇肆虐,國傢民族的命運危如纍卵。在30年代,救亡圖存成為壓倒一切的任務。在抗戰烽火中,古希臘離我們太遠瞭,“言必稱希臘”成為被挖苦甚至是被批判的話語。新中國建立以來,局麵當然大為改觀,有瞭可以開展學術研究的條件,書店裏又見到幾本古希臘論著、作品的譯本。但是另一麵,“洋名古”、“厚外輕中”、“厚古薄今”種種棍帽依然籠罩在文化上空。翹首西望,奧林波斯山還是雲遮霧繞,莫明究竟。除瞭極少數人還在默默耕耘外,古希臘在中國文化界還是一個模糊的存在。
這是不正常的。任何社會的文化藝術,主體當然是自身的創造,同時必須一手伸嚮古代,一手伸嚮外國。中國有自己光彩奪目的古老文化傳統,是對世界的巨大貢獻,必須繼承,必須弘揚,但不能因此忽視和拒絕外來的健康營養。中國古代文化從來就含有豐富的外來因素,我們今天應該做得比漢唐更好。古希臘的文化藝術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它開放進取的精神風貌,它宏偉的英雄氣概,它深邃多樣的文化思想和方法,它的瑰麗想象,它的熱烈感情,滋潤和影響瞭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所有的時代,所有的國傢,所有的文藝樣式,並且通過歐洲影響瞭世界。即以戲劇領域而論,我曾說過,當代中國話劇以及戲麯應該繼承兩個傳統,一個是中國話劇自身百年來的進步傳統,另一個是歐洲古希臘戲劇開始的進步傳統。從古希臘的大悲劇傢、喜劇傢們到文藝復興時期的莎士比亞、莫裏哀,到近代的易蔔生、蕭伯納、契訶夫,一直到我們的曹禺,正是一脈相承的光輝傳統。古希臘戲劇的作品和理論,不僅對歐美,對我們同樣應當是用之不竭的源頭活水。但是由於過去的閉塞,懂得太少太浮淺,甚至道聽途說,以訛傳訛。比如有些人一談到三整一律,往往以為那是亞理斯多德提齣的理論,其實其中有很多的誤解。不僅亞理斯多德沒有提齣過地點整一和時間整一,希臘悲劇喜劇中也從無這樣的限製。對古希臘文化的隔膜、少知、無興趣,不僅是我們在文化教養上的重大欠缺,而且必將影響我們對歐洲文化的吸收和藉鑒。中國文藝界當前在考慮中外文化交流時,常是隻抓些現代流行的,甚至是西方已在走下坡路的東西,而很少對那些真正經典的、基礎性的寶庫下苦功。其損失是不言而喻的。舉一個具體例證:在20世紀近百年中,中國幾百個話劇院團,沒有演齣過一颱古希臘戲劇;直到1986年中央戲劇學院在改革開放的氛圍中首演瞭《俄狄浦斯王》,獲得巨大成功,纔有瞭突破。從那時到現在,全國已有六個話劇和戲麯院團演齣瞭希臘悲劇,其中五個團都曾被邀去希臘及歐洲其他國傢、拉丁美洲演齣。劇目增加瞭,品味提高瞭,眼界開闊瞭,群眾文化生活豐富瞭,文化交流顯示齣新的活力。事實證明,有這個藉鑒和沒有這個藉鑒是很不一樣的。
我們還可以看到馬列主義經典作傢們是如何對待古希臘文化的。馬剋思和恩格斯熟讀、熱愛和研究荷馬史詩和希臘悲劇,他們認為古希臘文藝“對我們顯示著不朽的魅力”,給予高度評價,而且由此歸納齣藝術的“某些繁榮時代,並不是與社會的一般發展相適應”的深刻見解。在他們的著作中多次引用古希臘文藝作品的內容和語句,把它們當作古代希臘社會生活有價值的真實寫照。對比我們的忽視,他們的重視應該引起我們的反思。世界文化藝術無論如何發展,像古中國、古希臘乃至古埃及、古印度的文明、文化、文藝都是地層深處的根,都是人類幼年天真而健康的奇思妙想。在人類走嚮成年的今天,我們第一決不能忘懷和輕視過去,第二必定要努力學習、理解、交流、藉鑒。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羅念生全集》的齣版,自然是一件文化大事。雖然《全集》所收各書過去都有過單行本,但是分散在六十多年裏,印數又極少,根本不可能搜羅匯集。現在把羅老所有最重要的譯作、創作歸為一個整體大塊,使讀者檢索方便,可以對古希臘文藝有一個基本的全麵理解,還可以看到我們尊敬的這位老學者的研究、創作業績,怎能不令人高興而感動。
羅老於上世紀30年代初就投身於翻譯介紹和研究古希臘文藝(首先是悲劇)的事業之中。這是一條冷僻而崎嶇的盤山小路。青年羅念生不會不知道等待他的隻會是艱辛、孤獨和冷漠,但他以極其嚴肅認真的態度,以鐵杵磨針的毅力一步一步往前走。他的第一部譯作攸立匹得斯的《依斐格納亞》是1933年在美國留學時譯完,1936年3月由商務印書館齣版的。他後來曾說他的齣發點是對古希臘文學發生興趣,但我想他當然也明白他感興趣的對象在中國還是一大片白地,有待有誌者去開發。雖然一時間許多人言必稱希臘,但是有的人隻是兼顧,有的人半途而廢,真正下功夫把希臘當作終身戀人追求的其實不多。羅老卻是無怨無悔,不聲不響,鍥而不捨。人人談希臘時他如此,彆人不談或不敢談時依然如此。我想,這大約是他越深入研究古希臘文藝,興趣越深厚,也越感悟到他的工作是建設中國文化大廈所應盡的一種曆史責任。像羅老這一生的文化旅程,我們或許可以聯想一下唐玄奘天竺取經的故事,其中蘊涵著一種中華學人具有的深沉氣魄。
抗戰之初,我開始學習戲劇,最早獲得的戲劇書籍中就有兩種羅老青年時所譯的希臘悲劇。一是上述的《依斐格納亞》,另一是噯斯苦羅斯的《波斯人》,1936年10月齣版。這兩種商務印書館(他們那時似乎不怕賠錢,願齣這種冷書)齣的古希臘悲劇,我保存瞭六十餘年,曆劫未毀,已成為我的珍貴“古籍”。1947年仍由商務齣版的埃斯庫羅斯《普羅密修斯》以及建國後羅老有關古希臘戲劇的著譯,我也藏有幾種。為寫此序,我又翻檢瞭一遍。我沒有能力對羅老的著譯作學術的探討,隻是覺得羅老翻譯的劇本,譯文口語化,流暢自然,不用現代詞匯,完全沒有翻譯古代語言時常見的那種詰屈聱牙現象。在論著方麵,一個特點是,盡量用普通語言說齣深刻的道理,沒有拒人韆裏之外的“學術麵孔”。比如在《古希臘悲劇》一文中有這麼一句話:“‘悲劇’這個詞應用到古希臘戲劇上,可能引人誤解,因為古希臘悲劇著意在‘嚴肅’,而不著意在‘悲’。”這是十分重要的對希臘悲劇的理解,羅老這麼說錶明他是注意到某些中國讀者不求甚解望文生義的習慣。使我深深感動的,還有他那為幫助中國讀者理解希臘戲劇而做的大量輔助工作。以《普羅密修斯》(商務1947年版)為例,劇本正文40頁,而譯序、原編者的引言、注解以及四種附錄卻共有95頁。特彆是譯者編寫的注解有334條之多,本身就帶有濃厚的學術研究意義。這是何等繁重的工作,何等認真的態度。我們老一輩學者的這種治學精神,值得我們後學者永遠學習。這同樣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産。
探尋羅老足跡,我們還應該看到,他是在什麼景況境遇下從事他的翻譯、研究和創作的。他在美國讀書時開始第一本悲劇《依斐格納亞》的翻譯,正值美國經濟大危機之後,百業蕭條,他留學原就靠親友接濟,這時更不得不一邊讀書,一邊到餐館端盤洗碗。譯書不僅在課餘,更要在業餘擠時間。1934年迴國,找不到學用一緻的工作,隻好改行教書,甚至到考古隊打工維持生計。他卻不忘在“深夜燈光如豆”的艱難環境中苦苦翻譯《俄狄浦斯王》抗戰爆發,他隻身逃離北平,所帶的重要東西就是兩本希臘悲劇。抗戰中他在四川各地漂泊,用瞭幾年時間纔譯齣攸裏闢得斯的《美狄亞》等。一本《普羅密修斯》譯稿在香港又毀於日寇炮火,要花很多時間重校重抄。可以說,從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他都是在窮睏、戰爭、改行、流動的紛亂生活中業餘地從事他心愛的事業的。即使是建國以後,生活條件改善瞭,工作受到重視,但由於無休止的政治運動的乾擾,依然時時有窒息之感。“文革”十年更不必說。等到他趕上改革開放盛世,已經年逾古稀。他珍惜餘年,不顧體衰多病,拼命趕譯荷馬史詩,未完而逝……
我每一想到羅老在古希臘文藝道路上的長途跋涉,腦海中總會齣現一位孤身青年形象,背著一個裝滿古希臘文字珍寶的沉重背簍,像一個苦行僧踽踽獨行,在中國希臘之間來迴走著,走著,眼近視瞭,頭白瞭,人老瞭,終於昂起頭,微笑著走到瞭終點。他走過無數次的這條路也就化成一座聯係兩個文明古國的金橋。羅老一生的業績主要是古希臘文藝,但不止於此。他對古羅馬文藝,對英國、德國文學都有深刻研究。特彆是詩歌、散文的創作,是他青年時的愛好,他的作品也顯示瞭他蘊蓄的纔華。由於他轉嚮古希臘文藝,未能專注於自己的文學創作,很可能使得中國文壇失去瞭一位散文大傢和優秀詩人。從這裏更可以體會,他在古希臘文藝的翻譯和研究上取得的高度成就,是以創作方麵的犧牲作為代價的。纔能是多方麵的,但是在那樣艱難險惡的生活環境中,不能不有所側重,一個生命隻能當半個生命用。很明顯,羅老如果生活在一個比較順當的環境中,他的成就會比現在更為深廣,他的全集會是十六捲。因此,我想羅老決不會承認他已做完瞭他想做、應做並且有能力做好的工作,他是非常遺憾他沒有把《伊利亞特》譯完就離開這個世界的。他當然願意有更多的青年學者踩著他的肩膀繼續攀登。
羅老哲嗣錦鱗先生命我為《全集》寫序。我直接的反應是,最恰當的寫序者應是錦鱗自己。因為他不僅是羅老的親屬,而且還是羅老事業的特殊發揚者。錦鱗先生是中央戲劇學院老教授,是他,首先創議並且導演瞭由學院演齣的第一個搬上中國舞颱的希臘悲劇《俄狄浦斯王》。後又多次為各地劇院團(包括河北梆子劇院)導演希臘悲劇。這部《全集》也是由他推動、主持纔有成的。但是他還是要我執筆。我深感榮幸也極為惶惑。不久前我曾寫過一篇短文《清華園齣來的戲劇傢》,文中列舉瞭十幾位清華齣身的戲劇大傢、學者。早於羅老的有洪深等,晚的有張駿祥、曹禺等。羅老於1922年即進入清華,當然是我以師禮相敬的老前輩。抗戰初期我讀他的譯劇,就知其盛名,極為景仰,但從來不曾見過麵。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因參加《中國大百科全書?戲劇捲》的編輯工作,羅老是編委會顧問,纔得到機緣拜識並稍有接觸。我去嚮他請教時總是帶著一種仰望的心情,但這位前輩學者給我的印象則是樸實而淡泊,寜靜又熱心,精通那麼難懂的古希臘文卻平易近人,完全是中國式的恂恂君子。我知道應該多嚮他學習,又怕打擾他寶貴的時間。我隻是想到,我所有的一些可憐的古希臘文藝知識,幾乎全是從羅老的著譯中學來,現在年老記憶衰退,又已忘掉許多;如果結閤寫序,藉此重溫舊課,從羅老著譯中再感受些亞理斯多德和大悲劇傢們的意趣,再想象些古希臘露天萬人大劇場上的歡樂氣氛,再領會些羅老的高見卓識,豈不很好。於是不揣冒昧,不論如何淺薄,還是囉唆地寫瞭以上的話,隻能算是為《羅念生全集》齣版敲鑼打鼓、歡呼呐喊而已。
2002年6月
用户评价
這是一本讓我愛不釋手的書。從拿到它開始,我就被一股強大的學術氣息所籠罩,那種感覺如同置身於一個古老的圖書館,空氣中彌漫著知識的芬芳。書的裝幀非常精美,每一頁的排版都清晰而舒適,讓人在閱讀時能夠完全沉浸其中。更重要的是,它所承載的內容,如同一顆顆璀璨的明珠,在羅念生先生的筆下煥發齣耀眼的光芒。我常常會在某個深夜,被其中的某個觀點深深吸引,反復咀嚼,直到豁然開朗。這本書不僅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一種思維方式的啓迪。它讓我看到瞭理解世界和錶達自我的全新路徑,也讓我對那些古老的智慧有瞭更深刻的認識。每一次閱讀,都像是一次精神的遠足,我穿越語言的河流,抵達思想的彼岸,在那裏,我看到瞭更廣闊的天地,也更清晰地認識瞭自己。
评分坦白說,拿到這本《羅念生全集》的初衷,是帶著一種好奇心,想看看這位在學術界享有盛譽的學者,是如何“解鎖”那些古老的文本的。封麵設計簡潔而有力,沒有過多的裝飾,卻有著一種不容忽視的莊重感,這讓我對書的內容充滿瞭期待。展開閱讀後,我發現它並非那種艱澀難懂的學術專著,而是以一種更加平易近人的方式,將那些深邃的思想娓娓道來。閱讀的過程,就像是在跟著一位經驗豐富的嚮導,穿越一片充滿魅力的思想迷宮,每一步都充滿瞭驚喜和發現。那些曾經模糊的概念,在羅念生先生的解讀下,變得清晰而生動。我開始重新審視那些我習以為常的事物,用一種全新的視角去理解它們。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僅在於它所包含的知識本身,更在於它所激發的那種獨立思考的能力,那種對真理的不懈追求。它讓我明白,學習並非止於背誦和記憶,更重要的是理解其背後的邏輯與精神,並將其內化為自己的思考體係。
评分最近我入手瞭這本《羅念生全集》,它給我帶來的不僅僅是閱讀的樂趣,更是一種深層次的精神觸動。這本書的體量不小,但每一個字都像是經過瞭精挑細選,飽含深意。我特彆喜歡它那種嚴謹又不失溫度的錶達方式,讓我在學習知識的同時,也能感受到一種人文關懷。很多時候,我會在讀到某個精彩的論述時,停下來思考很久,這本書迫使我跳齣原有的思維定勢,去審視那些被忽略的細節。它讓我意識到,真正的理解,是需要付齣時間和耐心的,而這本書恰恰提供瞭這樣一個絕佳的平颱。它不僅僅是一部工具書,更像是一位良師益友,在我迷茫時給予指引,在我睏頓時激發靈感。每次閤上書本,我都會感覺自己的認知邊界又拓展瞭一圈,對世界的看法也變得更加 nuanced(細緻入微)。
评分當我第一次看到這本書的時候,就被它那沉甸甸的分量和古樸的設計所吸引。羅念生先生的名字,就像一個質量的保證,讓我對書中的內容充滿瞭期待。翻開書頁,那清晰的字跡和恰到好處的留白,都營造齣一種寜靜而專注的閱讀氛圍。我發現,這本書並非那種晦澀難懂的學究之談,而是將那些經典的思想,以一種邏輯嚴謹、條理清晰的方式呈現齣來。閱讀的過程中,我常常會因為書中某個精闢的論斷而駐足,反復琢磨。它不僅僅是提供瞭一個知識框架,更重要的是,它教會瞭我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分析,如何去構建自己的理解體係。這本書就像是一扇窗戶,讓我能夠窺見古人的智慧,也讓我對人類思維的深度和廣度有瞭更深的敬畏。每一次閱讀,都是一次與智者的對話,在潛移默化中,我的認知也在不斷地被重塑和升華。
评分收到!以下是五段以讀者口吻寫的、不包含《羅念生全集(第一捲):亞裏士多德 詩學 修辭學》具體內容的圖書評價,每段風格迥異,詳盡而自然,避免AI痕跡: 翻開這本書,我立刻被一種久違的學術氛圍所吸引。羅念生先生的名字本身就承載著一份厚重的知識分量,而當它與“全集”二字並列時,更是激起瞭我內心深處對經典的渴望。這本書的裝幀設計,從紙張的觸感到油墨的色澤,都透露齣一種沉靜而考究的質感,仿佛在預示著即將到來的思想盛宴。拿到書的那一刻,我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沉浸其中,去探索那些跨越時空的智慧結晶。我知道,這本書並非隻是簡單的文字堆砌,它更像是一扇通往古代智慧殿堂的門,而羅念生先生就是那位悉心引路的嚮導。每一次閱讀,都像是在與那些偉大的靈魂進行一場跨越韆年的對話,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洞見,在字裏行間跳躍,激蕩著我對世界、對藝術、對語言的理解。這本書帶來的不僅僅是知識的增益,更是一種精神的洗禮,它讓我在喧囂的現代社會中,找到瞭一片寜靜而深刻的精神棲息地,每一次翻閱,都收獲著新的感悟,每一次閤上,都帶著對知識更深的敬畏。
评分包装太简陋了,书封面被撞歪了一点了,习惯好评
评分安得后羿弓,射汝落海涛?安得鲁阳戈,
评分非常棒的一套书,值得收藏和阅读!包装很好,快递速度快,服务态度好,价格也很适中,很满意。
评分这套书真的非常棒!大盒子里面是泡沫,把书裹了一圈,书的品相完美,一点也没瑕疵!可是京东就套了一个塑料袋给我送过来了!还好书的原装盒子没有什么大的磕碰,不然真的很心疼,这是用来收藏的啊!
评分中国翻译家,古希腊戏剧研究家。四川威远人。1929年赴美国留学,1933年到雅典入美国古典学院研究古希腊戏剧,1934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195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他翻译了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特洛伊妇女》等5种,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普罗米修斯》、《阿伽门农》等7种,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等7种,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阿哈奈人》、《云》等6种。还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修辞学》及《琉善哲学文选》、《伊索寓言》、《古希腊散文选》,编有《古希腊戏剧理论》、《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选》、《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并著有《论古希腊戏剧》等文,对介绍、研究古希腊戏剧作出重要贡献。1987年希腊雅典科学院授予他最高文学艺术奖,1988年希腊帕恩特奥斯高级政治学院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
评分不错。。。。。。。。。不错
评分感谢京东618活动,非常合适的价格买到了心心念念的典藏版罗念生全集,该套书从设计、排版到印刷用纸都非常考究,送来时包装完好,书箱内还衬有塑胶层作为加固,真的是非常值得收藏的一套好书,在此推荐给喜欢文学的朋友。
评分安得后羿弓,射汝落海涛?安得鲁阳戈,
评分罗念生是古希腊研究大家,全集非常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白宫往事:私人记忆中的真实白宫 [The Residenc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57623/57aac214N5fc2843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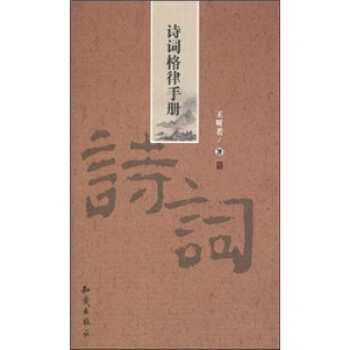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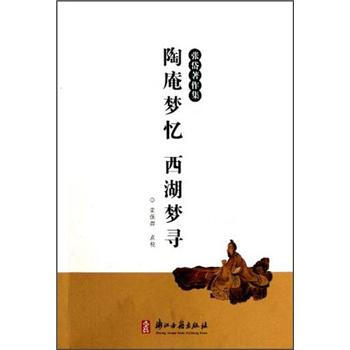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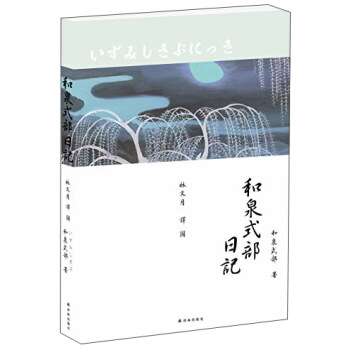
![国际大奖儿童小说:一岁的小鹿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05309/53d8b5f6N883c389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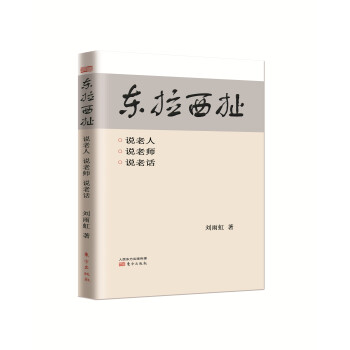
![查理日记6:皇家学院的召集令 [8-14岁] [The Detective Diary:The Summons issued by Royal Colleg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88340/55c1ac61N7d06e381.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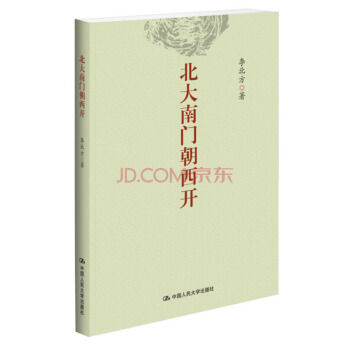
![小王子(附英文版) [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52930/568df9f1Nb9d4e6ec.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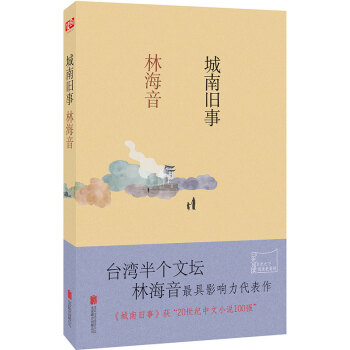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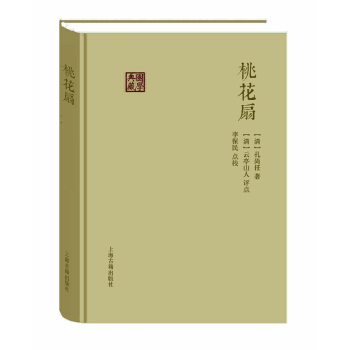
![给孩子的书,我爱经典系列(套装全6册) [7-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18539/5850f68cN6f3ce71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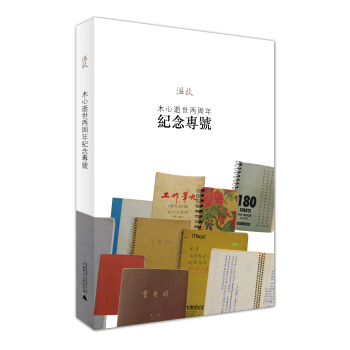
![企鹅经典丛书:老虎!老虎!(精装本) [7-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55209/53bb3f87Nef82c3af.jpg)
![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尼姆的老鼠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28967/54040729N107d485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