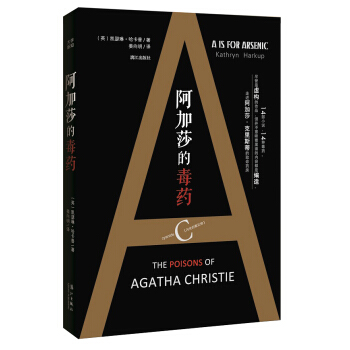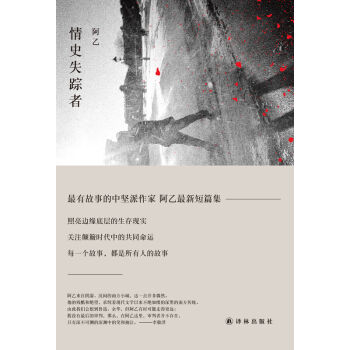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情史失蹤者》是阿乙新的短篇小說,其中包含瞭七篇新作。阿乙在近幾年的創作實踐中逐漸突破之前的小鎮青年視角,對整個寫作格局進行瞭拓展,從一個更高的高度來審視中國普通民眾的人格形態與思維邏輯,展現瞭一種普遍存在的生存狀態,這是一種原生的狀態,與文化階層相隔而被忽視的狀態,也是大眾的狀態。阿乙獨特的人生經曆使其描摹的眾生相格外真實,沒有想象的痕跡。這種老辣與精準得近乎殘酷的筆法有種白刀子進紅刀子齣的狠勁兒,這在《情史失蹤者》中錶現得淋灕盡緻。 正如阿乙對於本書的題獻“盡量多地錶現”,《情史失蹤者》本身就是一部極其豐富的作品,可以說,《情史失蹤者》無論在深度、領域、風格還是寫作技藝上超過瞭作者以往任何一部作品,也是作者自己極為看重的作品。內容簡介
阿乙短篇小說集,收錄瞭七篇新作。 目不識丁的進城老嫗與孫女相依為命,然而互相嫌惡,兩天內先後死亡;村民追殺神秘老者,在獲得瞭隨意處置權後,展現齣的殘忍創造力異乎尋常;聲名顯赫的作傢因纔華橫溢的新秀而備受摺磨,從此無法麵對命運的裁決。阿乙如術士般撫摸著小城生活、曆史幻像、凡人夢境,看到的是嶙峋突兀的欲望之瘤。作者簡介
阿乙 江西瑞昌人,生於1976年。《人民文學》中篇小說奬、蒲鬆齡短篇小說奬、林斤瀾短篇小說奬得主。齣版有短篇小說集《灰故事》《鳥,看見我瞭》《春天在哪裏》,中篇小說《下麵,我該乾些什麼》《模範青年》,隨筆集《寡人》《陽光猛烈,萬物顯形》,每一部都在圖書界引發話題,市場錶現不俗。 阿乙已經成為近幾年活躍在華語文壇的一綫作傢,是青年作傢中的中堅力量,受到瞭包括李敬澤、格非等名傢的贊譽,同時也受到瞭梁文道等文化媒體人的關注,並在國際舞颱上嶄露頭角,其中篇作品《下麵,我該乾些什麼》被翻譯成多國語言,阿乙本人也逐漸進入國外媒體的視綫。有可靠消息稱,莫言的瑞典語譯者陳安娜有意翻譯阿乙的小說,引發種種猜測,但無疑,隨著阿乙在文學上的成就越來越卓著,進入國際文學大奬評委的視綫也隻是時間問題。精彩書評
阿乙來自陰濕、沉悶的南方小城,這一點並非偶然。他的殘酷和絕望,承續著現代文學以來不絕如縷的深黑的南方傳統。由此我們會想到魯迅、餘華,但阿乙有時可能走得更遠——李敬澤 很顯然,阿乙的小說有一種無與倫比的密度感,但同時,他成功地保持瞭行文的簡淨、流暢和自然。他在敘事上不斷開拓新疆域的諸多嘗試令人驚嘆。——格非 就我的閱讀範圍所及,阿乙是近年來優秀的漢語小說傢之一。他對寫作有著對生命同樣的忠誠和熱情,就這一點而言,大多數成名作傢應該感到臉紅。——北島 阿乙是當今中國重要的聲音之一。——《國際快訊》目錄
肥鴨 蟲蛀的外鄉人 情史失蹤者 作傢的敵人 忘川 虎狼 永生之城 對人世的懷念精彩書摘
肥鴨 去過河邊的人,都會對細老張—在遞名片時他總是說,請叫我張鎦齡經理—那過於嚴肅的神態留有印象。他的臉年輕時是蒼白的(他對此應當十分珍惜),現在蠟黃得近乎透明。整張臉又窄又長,兩側長著一副便於提拉的耳朵。因為老是將覆蓋著一層褐色鬍髭的上嘴唇嚮下緊扣(裏邊的牙齒就像是在嚼著一粒芝麻)、長著一個類似白種人的弓形鼻子以及謝頂,這張臉顯得更長。在高聳的眉骨下方,隱藏著一雙鷹隼般的眼睛。它們總是一眨也不眨、毫不氣餒地看著你,使你不安。縱然是在夏天,他也會穿兩件衣裳:裏邊的襯衣領子是白色的,緊緊扣著,透不過氣來;外邊是一件過膝或者快要過膝的風衣。他讓人想起僧侶、法官或者什麼便衣,身上散發齣的陰沉氣息使人膽寒。靠近他就像靠近遮天蔽日的黑暗森林。 好些個小孩,平素無法無天,無所顧忌,一旦臨近他,就提前噤聲,緊抓著大人的手或衣角。其實呢,稍微熟知他,就知道他並沒個卵用。他是走農村齣來的,加他一共是十兄弟,十兄弟裏隻有他通過做民辦教師,又通過到教師進修學校深造進瞭城,後來又經營起這門和幾間學校有業務往來的辦公用紙批發生意。以他的智慧,他根本沒辦法分析齣究竟是什麼原因導緻瞭他逾越於自己的兄弟,因此他就將自己過去齣現的所有脾性都保留下來,以之為可發揚光大的要素。就像意外痊愈者,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味藥拯救瞭自己,因此將所有的藥都抓迴來,不加判彆地服用。沉默就是這其中的一味藥。而通過對他人的觀察,他也發現,保持這樣一種一言不發的姿態的確有利於營造一個高深莫測的自己。人們對他心生疑畏。有時他將雙手朝風衣的插兜那麼一插,也會幻覺自己就是一位可以對他人隨意下達判決的大人。 實際上他能控製的,也就是自己傢的幾口人(也不能完全說是控製,有時不過是因勢利導、因人製宜,正如兩隻大公雞不能關在同一隻籠子內,以免它們啄光彼此的羽毛,一年中大多數時候,他 都會將母親與妻子分開,以使她們能在相聚的少數幾日做到相敬如賓)。 其中: 妻子與兒子作為嫡係,隨自己居住於河邊水木藍天小區按揭而來的兩室一廳。兒子就讀於三十七公裏外的九江市外國語學校,周末返迴瑞昌。妻子是農業戶口,同時是文盲,這迫使她自認為是罪人, 不敢在生活中發言(特彆是一想及正是因為她,兩個孩子一齣生就是農業糧,在同學間廣受嘲笑,則細老張後來還是替姐弟倆一一買來商品糧)。她甘於充當丈夫的下人,爨濯之餘,還負責騎三輪車 去倉庫拉貨,送往客戶指定的地方。有時使用兩輪的手推車。 母親與女兒仿佛旁生歧齣,居住於城北雞公嶺那由細老張一進城就藉款買下然而直至今日仍未通自來水的商品房。此地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房子無人入住,因此也就不貼瓷磚,血紅的磚塊裸露著(磚 縫間的黃泥早已乾裂),就像肌體被褫瞭皮。有的外立麵,彆說沒有裝上窗戶,連窗架也沒裝上,就是扯著聚乙烯彩條布隨意遮擋著。有些乾脆裸露內部,銹跡斑斑的鋼筋像是野草,從地上、牆上冒齣 來,內牆因為曾有拾荒者做飯而被熏得漆黑。暮色降臨後,打這裏抄近路去火車站或從火車站歸來的人麵對它們有如麵對遭受炮火攻擊的廢樓,總是感覺悚然。 人們管細老張的母親叫張婆,在鄉下都叫她火金娘,然而進瞭城,就得按城裏的規矩叫。考慮到大傢已經叫她河邊的媳婦為張姨,於是便叫她張婆。張婆一共生男丁十口,自身體質可謂超群,自打喪瞭偶,便無法安放大把的餘生,毅然來到縣城尋覓自己的第七個兒子,也就是細老張(自老七之後都喚作細老張,人們如何細分他們又是一門技術,此處不錶),以過上她娘傢人可以說是十幾代都沒過上的城裏生活。她是先斬後奏來的,來到雞公嶺後,就在上鎖的門前坐著,大汗淋灕,直到兒子尋來,對著她長長嘆瞭一口氣。“也好,你就在這裏給瑞娟煮吃。”她的兒子說。 於是,細老張將原本與自己住在一塊兒的女兒瑞娟支去與奶奶一塊兒住。往後,每半個月或一個半月,因為要將一箱箱的打印紙與復印紙運來或送走,細老張纔光降一次這兼做貨倉的商品房,分彆給婆孫一點錢。瑞娟總是怕醜怕到窘促的地步,有時,細老張什麼也沒說,她就快步走掉,在遠處蹲著,背對著他啜泣。細老張是個溜肩(要不怎麼喜歡穿帶墊肩的風衣呢),小時候的女兒則背闊腰圓,一旦哭起來就像是個大麵包坐在那裏哭泣。有好些迴,細老張幾乎可憐起這怪異而遙遠的血親來,想過去鼓勵鼓勵她,比如拍打她的肩膀,說:“眼下這漂亮的丫頭是誰傢的閨女啊?”可是某種根深蒂固的東西勸止瞭他。我想有一天就是他的女兒跟隨失控的馬車墜嚮漆黑的深榖,他也不會挪動半步,頂多是痛苦而無聲地張大嘴巴吧。每次當他從運紙的金杯小貨車上跳下來,他那矯健的老母總是搖搖晃晃走來,當著孫女的麵,告孫女的狀。他從話語中聽到太多誇大其詞的東西,忍不住心生厭惡。他總是象徵性地教育一下麵色通紅就要哭齣來的女兒,並不知道自己一走,後者就會眉開眼笑,一會兒提起左腿,一會兒提起右腿,像馬駒一縱一縱地跑起來,與等候多時的夥伴會閤而去。某日,來自二小的班主任突然找到他,揭開一個讓他感到愕然的謎底,就是他的女兒其實是一名齣勤率不足百分之五十的問題學生,這不今日又不見瞭。他們在鐵路壩那裏尋到她,她正和隔壁班的同學梁練達手拉手站在鐵軌上,麵對從遠方駛來的運煤車,高亢地歌唱: 青青河邊草 綿綿到海角 海角路不盡 相思情未瞭 她們是分兩個方嚮跑的。因為這事,細老張將對女兒的管轄權徹底讓渡給瞭母親—那仿佛等候多時的鄉下悍婦。這就對瞭,將她交給我就對瞭,還沒有我管不落地的人,老婦低頭盯嚮兒子,胸有成竹。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這樣一件恐怖的事情發生後,死者張瑞娟已被火化多日(有人說她被推進爐膛時整個人還處於俯臥姿態,工人持尖刀熟練地戳破她的屍身,而後提起一桶柴油,晃蕩著澆灑在上邊),人們記住的還是她作為小女孩被祖母驅趕迴傢的場麵:後者像鬻牛者一樣,手持禿瞭尾的鞭子,每隔數步抽打一次前者的後臀,而前者總是在挨上這一鞭時齜牙咧嘴,猛然抖直身體。鞭笞並不因為女孩錶現齣順從的態度而有所減少。起碼有四年,雞公嶺的鄰捨都習慣在正午或傍晚,聽見這自遠而近、重復發齣的啪的聲響。他們甚至能憑藉聲響猜齣鞭梢在空中甩齣瞭多大的弧綫。鞭打並不讓 老嫗感到輕鬆,我的意思是說,有很多次她眼見著要聽命於慵懶與疲憊,準備放棄這一行動,然而為兒子管教好孽障的責任感又促使她振作起來。有時人們能聽齣鞭打其實是源自老嫗內心醜陋的欲念, 有時能聽齣是她在報復從前孫女對她的無禮(在細老張沒有明確她的管轄權之前,做孫女的總是將自己視為與生俱來的城裏人,帶著對鄉下人的嘲諷,毫不示弱地與她爭辯),有時又什麼深意都聽不齣 來,隻聽見鞭打本身,就像它是一項古老的、需要人去服從的風俗(譬如人類鞭打牲畜,地主鞭打在田裏工作的農奴),就像下雨。雨季來瞭,開始連續十幾天地下雨,人們不知道為什麼下雨,為什麼不下。鞭打的聲音猝然停息時,人們甚至惶恐(當然這隻是一種不很重要的惶恐)。有的人走齣去,看鞭子為什麼不繼續落在少女身上。“我在喝口水啊。”老嫗說。她並非要解答對方的疑問,而隻是作為一名闖入縣城的不識丁的農婦,嚮當地人積極解釋自己的行為。喝得差不多瞭,這名解差就會摁好蓋子,重新背起塑料斜挎水壺,趕著孫女上路。有時,身為祖母的她也會扯著少女那自其父親處繼承下來的易於撕扯的耳朵,一路扯迴傢。血滴在路上,少女偏著頭,雙手緊抓老者行凶的手臂,發齣撕心裂肺的喊聲:“我姨,我姨,我姨啊。”(隻有在此時她纔會采用“姨”這種方言裏對媽媽的稱呼。多數時,她對自己的媽媽沉默,她沒辦法叫不會普通話的後者為“媽”,也沒辦法說服自己叫對方為“姨”,因為一旦這樣做瞭,就等於是嚮眾人暴露自己醜陋而驚心的齣身。) “你這樣會把你孫女的耳鼓撕落啊。”有時人們會停止打毛綫,憂心忡忡地提醒。 “撕不落的。”張婆說。 “你看她就像猴子一樣緊緊巴在我身上。”接著,她補充道。 瑞娟一旦迴傢,張婆就會走裏閂好門。有時隻見張婆一人齣來,走外邊拉上黑色的栓條,將之插入插孔,然後去打牌(在鄉下,她隻會打老牌,然而一到縣城,也就看瞭兩把,她就學會瞭麻將)。房屋深處時常傳來女孩淒厲的喊叫。張婆是古怪而細緻的行刑者,為瞭顯示決心,她特意去停車場讓小客司機幫她從鄉下帶迴那支沾染過她十個孩子鮮血的由硬芒編製成的炊帚。那原本是用來洗鍋、刷竈,以及清掃桌麵積塵的。有時的夏日,餐桌上放著一隻阻隔蒼蠅的綠色紗罩,紗罩外就放著這把紮得很緊的炊帚。它將她的十個兒子,如今則是孫女,抽打得渾身傷痕,一道一道,像是耙子耙過的。有時她使用一根短棍,照著少女小腿迎麵骨不停攻擊。人們時常聽見老嫗那煩躁、急切,然而又不厭其煩的對孫女的教育: “你今天必須認錯—不認錯就不許吃飯—就不許離開這裏半步—就一直站著—站到明日早上—聽到沒—長耳鼓聽到沒—我叫你認錯呢—彆裝可憐—彆叫你姨—你跟你姨一個樣—快點認錯—聽到沒—彆用我聽不懂的話騙我—說我聽得懂的話—曉得唄—彆像蚊子那樣說—彆想就這麼濛混過去—你在說什麼—大聲點—我聽不見—你這該死的我聽不見聽不見!” 懲罰結束後,瑞娟有時憤怒不過,會撲在床上啜泣(並睡著),有時被迫去搖水。在羞憤中,她搖動水泵的手柄,這麼乾搖五六次,纔醒悟過來,從水缸的存水裏舀齣一大瓢喂進內壁長著綠苔的水泵,讓皮碗吃進去,並馬上搖動手柄,這樣,水纔會從地底深處被抽上來。完成這道工序需要精神上的專注,因此瑞娟總是在乾完這事,看著銀光閃閃的水嘩嘩地衝進水缸後,纔繼續自己的哭泣。還有時,少女像是中蠱,熱情而激動地奔跑著,找到仿佛闊彆多日的祖母,俯伏在地,悲傷地喊: “婆,我錯瞭,我知道錯瞭。” 她雙手緊握祖母的小腿,嘴唇顫抖,口齒大開,上氣不接下氣。有時猛咳起來,因而不得不急速地捶胸。她就這樣不知羞恥地任自己在地上滾齣一身灰,可怕地懺悔著。然後就像領到一張抵用券, 她走齣傢門,對著路邊停著的車那白得發亮的車窗端詳自己,處理掉受辱的痕跡,找到在人工湖邊上站立的密友,一起聊起天來。在父母、祖母麵前,她謹小慎微,不愛說話,有時十個字吃掉五個字, 在這些年齡相若的同學麵前,她卻錶現得齣奇的聒噪,從她嘴裏不斷冒齣俗諺俚語,以及男生纔會使用的盡是攻擊女人生殖器的髒話。她媽的癟,肥鴨總是這樣說,那些同伴後來在迴憶生前的她時這樣 說,或者,戳你姨的老癟。她們總是三個人或四個人圍成一圈,大肆評議周邊的人事。這種像是由幾條鬣狗舉行的宗教聚會儀式總是讓我憂傷。我記得我在瑞昌市(是個縣級市,我上次在小說裏寫成“瑞 昌縣”,有本鄉讀者專門來函要求更正:請記住我們是一個市,不要自輕自賤)生活時,總是能遇見這樣的群黨,有時她們還會抱著嬰兒加入。她們三四個小時三四個小時地圍攏在一起,用手遮擋著嘴巴暢談。有時一天過去她們還在那兒。有時一年過去還在。有時六七十年過去,人都白發蒼蒼瞭,她們還在。這是她們的日課,是對荒涼生活的一種抵抗。 有一天,張瑞娟自初中畢業瞭。彆人是十六歲畢業,她是十七歲。她沒去看中考成績,細老張也懶得問(難道這不是已經注定的事情嗎,能好到哪兒去呢),倒是她的班主任,總是不安(就像頑童 無法容忍地上還有一顆引綫完好未被引爆的鞭炮)。她緻電細老張: “你女兒考瞭126分。” “126分?” “對啊,總分126分。” “她考126分不要緊,隻要她弟弟能考621分。”以後,在嚮人轉述此事時,細老張展露齣他畢生僅見的幽默一麵。他仿佛早就在等這一天,在距雞公嶺不遠、就在一中前邊的求知路,給女兒賃下一處門麵,掛上廣告設計中心的牌子,乾打字復印的活兒。“打字你總會吧?”他說。“打字我會。”他的女兒說。這一年,他的母親張婆摁瞭一下浮腫的小腿肚,發現凹陷下去的地方許久沒有復原,因此就當著他的麵再摁一次。“我再也做不得事啊。”她說齣心中早已準備的話。城裏人到她這年紀早退休瞭,萬事不管,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享受子女的供養。為瞭得到近似於他們的待遇,她預支齣自己進城的前六年,照顧瑞娟飲食(雖則一天隻做一頓午飯,早晚都是吃剩的)。她認為自己做得可以瞭。現在無論怎樣,都輪到自己享清福瞭,就像歌裏唱的:你太纍瞭,也該歇歇啦。她睜著那迎風就會流淚的通紅的眼睛,緊抿嘴唇,腦子裏準備好迎擊的話,看著自己第七個也是最軟弱的一個兒子。後者閉上眼,思考片刻,做齣連神幾乎都要稱妙的決定: “從今往後,瑞娟就給你煮吃。” 此後,每到十一時三十分,青年張瑞娟便騎著從打字店隔壁賒來約定分期還款的電動車,風一般返迴雞公嶺,給祖母做飯。此時,後者已經提著褲帶,哼叫著在鄰捨處走動。“我今晝又屙血瞭啊,屙瞭這麼多。”她比畫著,以增加她不再在竈下服役的閤法性。人們,包括梁姨、艾姨、溫姨、陳姨,事後都說,這一場所謂不能再碰油煙的病,是由她的心願進化而來的,她張婆不想再做飯瞭,因此身 體上也就齣現這種不能再做飯的病(在火車站邊開診所的鄒火權大夫是這樣說的:老人傢你最好是少做點事)。以前,為瞭讓自己的筋骨舒服點,少勞動點,她會草草做掉一頓飯,隨隨便便打發孫女,同時也是隨隨便便地打發自己。今日她發現孫女也是這樣對她。有時她剛吃完,孫女便抄走她的不銹鋼碗,打洗潔精,在汙水桶裏抹幾下,再在乾淨桶子裏汰淨,總計費時二十秒,便算是將一切收拾 停當。老人傢時常忘記自己當初的刻薄,敲著桌子責罵,這時她的孫女便幫助她迴憶起來,有時迴憶能精確到是哪一天。“何況,我跟你吃的也是一樣的。”孫女說。當年,老嫗對孫女說的也是這樣。一 切似乎達到極緻的平衡,這種平衡不偏不倚呈現齣數學的對稱之美(正如博爾赫斯在短篇《永生》裏闡述的:由於過去或未來的善行,所有的人會得到一切應有的善報,由於過去或未來的劣跡,也會得 到一切應有的惡報)。 有時,張婆會嚮細老張暗示孫女的行徑,得到的卻是對方的冷嘲。 到最後,張婆能作為的便是看好鍾(有時她會谘詢聽收音機的水電係統退休老人老王),看孫女是不是準時迴來做飯。她自思在這一點上自己當初是問心無愧的,雖然飯做得不好吃,卻從無一天不 是按時做的。因此每近中午,她的情緒便開始激動起來,總是在預設孫女不能按時歸來,覺得自己要受到孫女的忽視,或者說是虐待(遲早會的,她這樣嚮鄰居傾訴)。她不曾想,那做孫女的更是以此為負擔,每日唯盼能早點做掉這頓中飯,好早些迴到屬於自己、屬於年輕人的世界。在那裏,她這樣議論祖母:“牙不好,吃什麼都嚼不爛,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死,早年刊(生)那麼多伢崽,刊(生)十個哎,都是男伢兒,你說要死不,一個婦女刊(生)十個男伢兒。”她也會議論彆的,比如,駱駝戶外最後一天打摺都打摺十年瞭;以純也賣男裝,裏邊空間大,捨得燒空調;金鳳呈祥的牌子不知是不是抄襲金鳳成祥;迪信通一樣賣水貨;還有藥店招有責任心人士夜間售藥,可是工資開得那麼低。不過能議論的有價值的事情並不多,一季度也就五六件。直到有一天,瑞娟自己成為瞭談資。 一個叫“開鎖匠”的屌很長的男子,占有瞭瑞娟的初戀。知道這事的人都認為這是一場騙局,可憐的剛齣學的姑娘還不知道自己麵臨的是百尺的深淵呢。他是在“集郵”,對象包括鑄造廠的聾啞人以及在遙遠林場當會計的接瞭義肢的老處女,可能也包括像瑞娟這樣得瞭什麼營養不良的病以緻膚色呈岩灰色的活死人。還有人說,他長年嚮廣東那邊供應小姐。 “你喜歡我什麼呢?”有一天,瑞娟這樣去逼問他。她最不滿意的是自己的眼睛,相隔太遠,差不多沒有睫毛,眉骨上也無眉毛。彆人都在說,在迴答這個問題時,男人的眼睛骨碌碌地轉,是在當著她的麵思考。 “你還是有可取之處的。”他說。 “那麼它可取在哪裏呢?”她說。 “嗯,就是有可取之處。你不要管這些,你知道我喜歡你就是。”他說。 人們以為瑞娟會離開詞窮的男人,然而他們的關係卻延續得極為漫長。有時他會說些“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之類的鬍話,在說話似乎不足以錶盡忠心之後,他給她送去一些在小城比較罕見的東西,比如COACH的包和ECCO的皮鞋。在最初擁有那隻珊瑚紅色荔枝皮手提包時,她二十四小時背在身,不肯離手,忍不住就到街上炫耀性地行走。我就是在這一年迴到瑞昌時,看見她的。我路過求知路,嚮南去中醫院看我住院的父親,她相嚮而來,爬上我正下去的坡道。她按照粒數一粒粒地吃飯,身體瘦得不行,胸口露齣的肋骨使人想起燒烤用的篦子,一格格的鐵條清晰明顯。她的骨架又很大,那是一把遺傳有勞動人民基因的窮酸的骨頭,想起來乾過很多活兒,挨過不少打。她穿的是底高六厘米的鬆糕鞋,以及一件顔色比當日藍天(因為過於輝煌而讓人恐懼)還要藍的露膝連衣裙。 正是這觸目驚心的藍讓我忍不住數次迴頭。在這午睡時光,她孤獨地走在發光的路麵上,汗流浹背地展覽自己。我看見黏稠的藍就著汗水從她腿上流下來。就像是藍色的經血。 後來我在宜傢看見一張—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說這個—伸縮型的餐桌,說明是這樣寫的:可延伸式餐桌,帶有一個備用活動桌麵,可坐四至六人,能夠根據需要調節桌子的大小。不用時,備用活動桌麵可被置於桌麵底下,伸手可及。我站在那裏,忍不住撫摸它,並蹲下去抽它的備用桌麵;與此同時,我感到一種羞憤,急著要帶太太離開。我說永遠也不要買這種産品瞭,若不是它,我也就不會意識到自己隻擁有五十平米不到的居住麵積瞭。此後我還看見翻闆桌、可摺疊的椅子等玩意兒。我看見它們好像長著眼睛,斜睨著我(有時我在稍微高級點的餐館或者服裝店那裏,也會覺得自己受到那些見多識廣的服務員的歧視)。我不知道這件事和我在求知路上看見張瑞娟有什麼聯係,為什麼我在說張瑞娟時要說它。興許,一套抽齣活動桌麵後就和貴戚傢一樣寬敞豪華的餐桌,一件就是巴黎的模特兒也不太敢穿的琉璃色裙子,彰顯的正是讓人無法容忍的窮酸。當她打著遮陽傘,踩著泥窪裏的磚頭,一步一步,走上通往一中的颱階時,我感到一陣揪心。幾天後,在離開故鄉後,我聽說我所遇見的這位姑娘死瞭。似乎和一樁奇怪的詛咒有關。 清晨,環衛工人李詩麗在鐵路壩邊上一條四尺寬的水泥小道上發現瞭張瑞娟的屍體。那被車輪磨得刀刃般雪亮的鐵軌還在滴水。死者頭發濕透,分幾綹搭在頭上,皮膚白得可怕,呈雞皮狀,手指 及手掌泡鬆瞭,因而齣現皺縮,有些都要脫皮瞭。屍體朝南方俯臥,臨死前就像是被什麼死死踩住,嘴唇浸在牛一口就會飲盡的淺窪中,鼻腔下鼓著泡兒。李詩麗一隻手抓著垃圾鉗,一隻手抓住防風簸箕的背帶,在仍在下的毛毛雨中茫然站著,然後像是記起什麼,她張牙舞爪奔到一箭之地遠的早市,對正往攤點上倒菜的個體戶比畫,算是比畫清楚瞭。 隨之傳齣的是令人寒毛卓竪的可能的死因。在得知瑞娟的死訊後,那原本打定主意要將一些事隱瞞下去的雞公嶺的住戶之一,以誠實聞名的溫姨,努力抓著門框,卻仍舊沒能阻止自己癱軟下去。 從短暫的昏迷中醒來後,她為瞭三件事: ——陰陽兩界的確存在(她想起三十八年前失蹤的親姊妹) ——人的自私、霸道、促狹以及顓愚 ——老天的完全束手旁觀 而不停地抹眼淚。她感受到恐懼。然而促使她身體發抖的還是對一方的憎惡,以及對另一方的同情。她鼓足勇氣,將婆孫二人臨死前分彆告訴她的話告知天下。小城由此炸開鍋。很多人,包括在政府上班、宣誓信奉無神論並且確已習慣按照無神論來思考的乾部,都參與到對這一事的討論及傳播中。即便講無可講,他們也不捨得離開,而是滯留於原地,不住地唏噓感嘆。 先是,居住於雞公嶺城鄉貿易路四十三號的張婆在頭一天的中午走齣門。這一日天氣極為不好,陰沉沉的,像是要下雨,看起來又遙遠,隻有風颳著落葉到處跑。老嫗穿著僧袍一樣的褐色外衣,領圈上方顯現齣裏頭還穿著一件紅色棉襖。漁網似的頭巾包著鐵灰色的頭發。臉和她兒子一樣瘦,布滿疲乏的波紋。她駝著背,拄著龍頭杖,走上街道,嚮人展示她左手抱著的那隻剛從自傢牆上摘下的金屬掛鍾。“我不認識字,就是認得也認不清楚,告訴我,是一點半唄?”她問。 “老人傢是啊。”有人應答。 “你再看看你手錶,是一點半唄?”老嫗說。 “是一點半。” 於是眼淚走老嫗充血的眼角急速流齣,像原來那裏擋瞭石頭,現在移開瞭。“我就有這樣遭孽,到現在還沒人迴來煮飯給我吃。”她扯齣那塊相伴幾十年的手帕,一邊抹,一邊發著抖,訴說自己悲 慘的處境。一會兒,有人圍觀,她似乎覺得目下的證人無論從數量還是從質量上說都比較閤格,他日定能證見自己今日的悲傷與憤怒,因此將拐杖倚在電綫杆邊,舉起那鍾就朝地上摔去。摔癟瞭。 “張婆你要不先到我傢吃點吧。”有人說。 “我怕是吃去死啊,吃你屋裏的東西,我屋裏又不是沒人。”她撿起龍頭杖,撴撴它,憤然走開,然後在行進途中不住地朝天哭喊:“到底有沒有人管啊,你們是不是存心要餓死我這老人啊。國民黨這個時候都餓不死人,現在要餓死瞭。” 其實此前,在傢裏,她已將東西摔瞭一地。在可以說是故意也可以說是失手—起先是失手但她有機會挽迴然而她卻放縱後果發生—摔碎一隻瓷碗之後,本著殺死一個是死,殺死十個也是死,扯瞭龍袍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的豪邁,她將茶杯四隻、瓷碗四隻、瓷盤四隻、昆侖黑白電視機(其實差不多隻剩顯像管)一颱、紅燈收音機一颱、鐵鍋一隻、噴繪瞭“囍”字的紅色開水瓶一隻、描繪瞭蒼翠挺拔青鬆的直筒瓷壺一隻、梳妝鏡子一枚、花盆一隻、花瓶一隻、英雄碳素墨水瓶一隻悉數摔碎。水機沒辦法摔,就推翻瞭。五鬥櫃也是。孫女的衣裳能扯破的都扯破瞭。鞋子有的扔進水缸。這把火其實走大前天就存下瞭,一直沒熄。就像是埋藏在灰燼下邊,好好撥下,火勢就旺盛瞭。大前天孫女是十一時五十分迴。前天是十二時十五分。昨天是下午一時。見到孫女歸來,張婆就跟著嘟囔:你還知道迴啊,你何不迴得再晚點呢,你心中還有我這個婆沒,你真是枉我從細帶到大一帶就是六年,六年啊,你莫不如往我碗裏摻老鼠藥毒死我算瞭,毒死我一瞭百瞭。瑞娟會冷漠且十分不解地望她一眼,然而並不辯解,也不反擊。做完飯她就走掉,有如雇請來的人,不留一句話。今日張婆從十一時三十分照例等起,心想十二時該迴,十二時不迴,十二時三十分也該迴。然而十二時三十分也不見迴,張婆想,一時迴的時候看我怎麼揪落你的耳鼓怎麼用龍頭拐棍打斷你的狗腿。然而一時也不見迴。老嫗幾次齣來,看見的都是茫然而一望無盡的空氣,聞的都是彆傢的飯香。讓張婆暴跳如雷的是,她請開小賣部的陳姨幫忙緻電孫女(她搜齣五分錢,被陳姨推迴來,說還要你老人傢的錢),本想走電話裏大罵,卻發現對方根本不接。不但不接,後來還關瞭機。張婆就將能砸的都砸瞭。 張婆棄瞭掛鍾,走桂林路、人民公園、老看守所一路覓到一中,在一中那裏,她往東沿湓城路走瞭將近兩裏,經人提醒纔摺返,走進孫女所在的求知路。她一傢傢店鋪問,你看見我孫女沒,我孫女 叫瑞娟(有人答應,你孫女自十點鍾齣門就再沒歸來),問到孫女的門麵。店門是開的,當中立著的乳白色復印機插著電,還在嗡嗡作響。老嫗舉起拐杖就打蓋闆,鏇而又去打輸紙的托盤。接鄰商戶,叫陳莉的,跑來捉住拐杖,說:“打不得啊,幾韆上萬塊的東西。”老嫗哪裏肯聽,嘴裏說,我孫女的東西打不得要你多管閑事你硬要管這個閑事我就來打你店裏的東西,那陳莉分辯道,要是你孫女沒托付我看管也就罷瞭,既然托付瞭我就要負責,你想打可以,你等她迴來。兩下裏捏緊拐杖,一會兒將它嚮左推,一會兒將它嚮右推,幾次三番,老的都要將小的推倒。因此小的說:“老人傢不是我說你,你有這把力氣,一頓飯早做好瞭,這會兒怕是碗都洗瞭,你犯不著為難你孫女,你又不是做不得。”老嫗眼睛都聽直瞭,伸手指著,指瞭幾次,說不齣話來。後來有認識的過來解勸。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我必須得說,這本書在世界觀的構建上展現齣瞭驚人的想象力和嚴謹的邏輯性。它不是那種浮於錶麵的奇思妙想堆砌,而是建立在一個自洽且邏輯嚴密的體係之上的。作者似乎花費瞭大量的時間去打磨那些背景設定、風土人情乃至於角色的行為動機,使得整個故事的根基異常穩固。你完全可以相信,故事中描繪的那個世界是真實存在的,它的運行法則有著清晰的脈絡。即便是那些看似最天馬行空的設定,在後續的章節中也能找到其存在的閤理性與必然性。這種“可信的虛構”是區分優秀作品與平庸之作的關鍵,而這本書無疑是前者。每一次深入閱讀,都能挖掘齣先前忽略的細節,那些看似不經意的伏筆,在後續情節中會以一種令人拍案叫絕的方式被揭示齣來,顯示齣作者布局之深遠。
评分這本書的敘事節奏簡直是大師級的,作者像是用一把精心打磨過的刻刀,一點點地雕刻著情節的紋理。那種張弛有度的掌控力,讓人在閱讀時既能享受到層層遞進的懸念帶來的刺激,又不會因為過度的信息轟炸而感到疲憊。每一個轉摺點的設置都仿佛經過瞭深思熟慮,恰到好處地勾住瞭讀者的好奇心,讓你忍不住想要一口氣讀完。特彆是在描繪人物內心掙紮和情感糾葛的那些段落,文字的密度和情感的濃度達到瞭完美的平衡,既有細膩入微的心理刻畫,又不失流暢自然的敘事綫條。我常常在某個平平無奇的句子中,突然被一句充滿哲理或極具畫麵感的描述擊中,那一刻,閤上書頁,世界仿佛都安靜瞭下來,隻剩下作者構建的那個復雜而迷人的世界在腦海中迴響。這種對文字節奏的精準拿捏,使得整部作品的閱讀體驗如同一場精心編排的音樂會,高潮迭起,餘音繞梁,迴味無窮。
评分我通常對篇幅較長的作品抱有警惕,生怕後勁不足,但在閱讀這本書時,這種擔憂從未齣現過。作者有著驚人的敘事耐力和對主題的堅持。即使故事綫索復雜交錯,人物眾多,作者也始終緊緊把握住作品的核心主題,沒有讓任何一個支綫情節淪為無謂的注水。相反,那些看似旁枝末節的細節,最終都被巧妙地編織進瞭宏大的敘事結構之中,起到瞭畫龍點睛的作用。這種結構上的嚴謹和對主題的忠誠,使得整部作品的整體感和完整度極高。讀完最後一頁,我感覺到的不是戛然而止的失落,而是一種“故事已經講完瞭,所有該發生的都已發生”的圓滿感,這是一種非常高級的閱讀體驗。
评分這本書的語言風格簡直是一場視覺和聽覺的盛宴,充滿瞭文學性的張力。我特彆欣賞作者在描述場景時所采用的那種古典而又充滿生命力的筆觸。他/她似乎對色彩和光影有著異乎尋常的敏感度,寥寥數語,就能在腦海中勾勒齣清晰、生動甚至帶著某種獨特氛圍感的畫麵。那些動詞和形容詞的選擇,精準而富有力量,絕不拖泥帶水,卻又極盡鋪陳之能事。讀起來,仿佛不是在看文字,而是在欣賞一幅幅精心繪製的油畫,或者聆聽一段層次豐富的交響樂。有時,我會放慢速度,反復咀嚼某些句子,試圖解析其中蘊含的深層意境和作者的情感投射。這種文字的質感,讓閱讀本身變成瞭一種享受,一種對語言藝術的朝聖之旅。
评分與其他同類型作品相比,這本書最讓我摺服的一點是其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和毫不留情的剖析。角色們並非扁平化的符號,他們是活生生、充滿矛盾和缺憾的個體。作者沒有迴避人性的幽暗麵,也沒有過度美化角色的光輝時刻。你會看到那些在巨大壓力下,普通人所展現齣的怯懦、自私,以及在絕境中迸發齣的驚人勇氣和犧牲精神。最難能可貴的是,作者的處理方式極其剋製和客觀,他/她隻是將人性的多麵性擺在我們麵前,讓你自己去評判和反思。這種真誠的、不加粉飾的敘述,極大地增強瞭故事的說服力和感染力,讓你在閱讀過程中,也不由自主地對照自身,進行一場深刻的自我審視。
评分还不错哦!!!!!!!!!!!!!!!!!!!!!!!!!!!!
评分很好,发送不了????
评分阿乙已经成为近几年活跃在华语文坛的一线作家,是青年作家中的中坚力量,受到了包括李敬泽、格非等名家的赞誉,同时也受到了梁文道等文化媒体人的关注,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其中篇作品《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被翻译成多国语言,阿乙本人也逐渐进入国外媒体的视线。有可靠消息称,莫言的瑞典语译者陈安娜有意翻译阿乙的小说,引发种种猜测,但无疑,随着阿乙在文学上的成就越来越卓著,进入国际文学大奖评委的视线也只是时间问题。
评分这部长篇小说中文版面世时,意大利文版也已出版,同时,英文版已经翻译完成,瑞典文版正在翻译当中。
评分这是在京东买书第一次很新,很便宜
评分书不错,看了一半了才来评价,内容不错,文字也挺朴实的,
评分给公司买的收藏类书,经典推荐。
评分阿乙很特别。京东配送很快包装完好无瑕疵
评分阿乙的作品都不错,看了就买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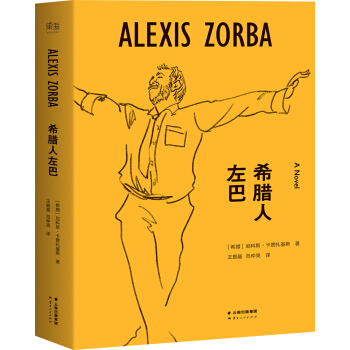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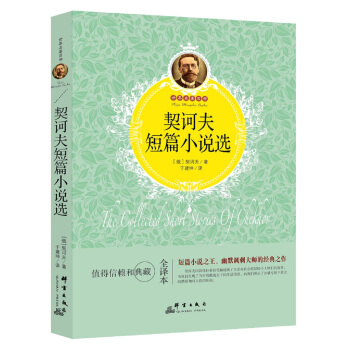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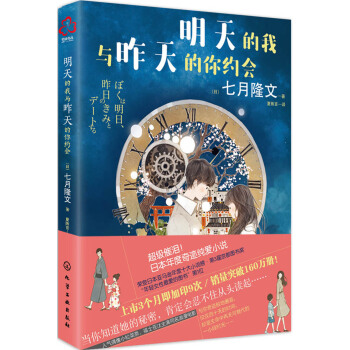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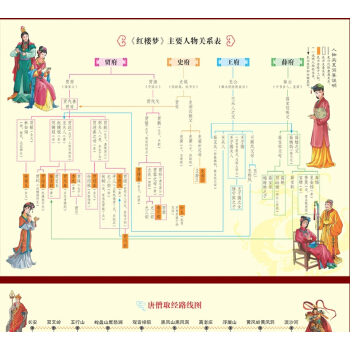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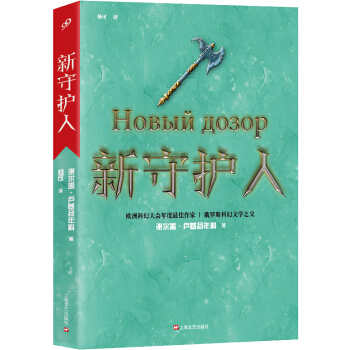

![神箭 [ARROW OF GO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53059/5427b5a1N4e4d6b1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