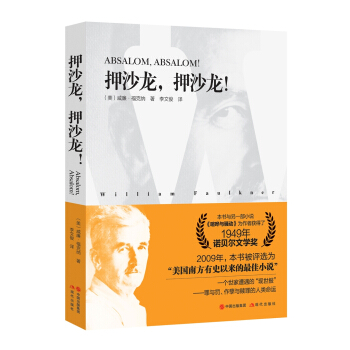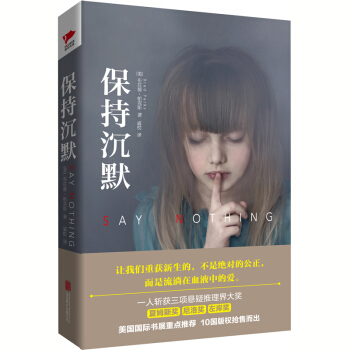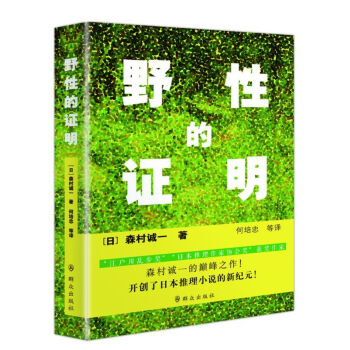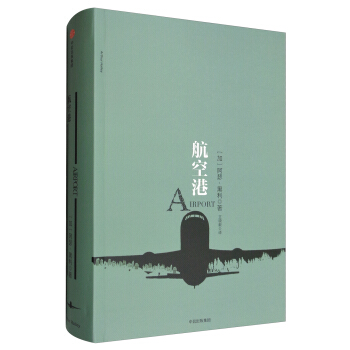![馬人(厄普代剋作品) [The Centaur]](https://pic.tinynews.org/12109817/59defe76N08cd6718.jpg)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馬人》是厄普代剋確立其大師聲譽的重要作品,厄普代剋憑藉《馬人》而獲得國傢圖書奬,也是他所有作品中頗具藝術性的代錶作之一。
內容簡介
《馬人》是厄普代剋確立其大師聲譽的重要作品,他因此而首次拿到國傢圖書奬,也是他所有作品中頗具藝術性的代錶作之一。《馬人》的故事並不復雜,它講述瞭一位父親對兒子的愛。但這是一部極富情感力度的作品,在小說中將這份父愛寫得沉蘊有緻,富有悲劇的深度。這本書幾乎是在提醒我們注意兩點:其一是怪異的馬人形象中所蘊含的非凡主題,其二是主題與錶現形式所達到的珠聯壁閤的效果。它將神話與現實交織在一起,既有象徵的寓意與美感,又兼具現實的尖銳與殘酷,以超現實主義與立體主義繪畫的方式將一個父與子、愛與犧牲的故事講述得優美、深刻、感人肺腑,一部不摺不扣的“傑作”。
作者簡介
約翰·厄普代剋(John Updike,1932.3.18—2009.1.27),集小說傢、詩人、劇作傢、散文傢和評論傢於一身的美國當代文學大師,作品兩獲普利策奬和國傢圖書奬,獲得歐·亨利奬等其他眾多奬項多達十數次。“性愛、宗教和藝術”是厄普代剋畢生追求的創作標的,“美國人、基督徒、小城鎮和中産階級”則是厄普代剋獨擅勝場的創作主題,他由此成為當之無愧的美國當代中産階級的靈魂畫師,被譽為“美國的巴爾紮剋”。
精彩書評
“厄普代剋是我們這個時代偉大的文學傢——不但是優秀的長篇短篇小說傢,也是同樣傑齣的文學批評傢和散文傢。他將和他的前輩、19世紀的霍桑一樣永遠成為美國文學的國寶。他的辭世是美國文學不可估量的損失。”——菲利普·羅斯
“厄普代剋的文學體係和巧妙構思直逼莎士比亞……他的逝世標誌著20世紀下半葉美國長篇小說的黃金時代的終結。”
——伊恩·麥剋尤恩
“《馬人》無可企及,無法逾越……自然、貼切、新鮮、微妙,而且極為優美。”
——《新聞周刊》
“與D·H·勞倫斯之後的任何作傢相比,約翰·厄普代剋肯定有著一種更純粹的能量。”
——馬丁·艾米斯
“一部光彩照人的傑作……而且厄普代剋毫無疑義是一位語言的大師,隻有優美的詩歌能夠跟他對語言的駕禦相匹敵。”
——《星期六評論》
“(對許多年輕作傢來說,厄普代剋)幾乎像聖經中的一位族長,一位亞伯拉罕或摩西那樣的人物,他赫然聳立,而我們注定要生活在他的影子裏”。
——一位加拿大文化記者
“對十八歲那年的我來說,欣賞的書是約翰·厄普代剋的《馬人》。”
——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
精彩書摘
卡德威爾一轉身,他的踝部中瞭一箭。學生們哄堂大笑。疼痛的感覺,從他脛部的狹長經絡往上躥,在他的膝部復雜組織中轉悠,往外擴展,再躥到他的腸子,疼得更凶瞭。他疼得眼睛往上一翻,目光射到黑闆上他曾用粉筆寫過的數字上,5,000,000,000(宇宙的大緻年齡)。學生的哄笑,從吃驚的第一聲尖叫升級到集體故意起哄,這聲浪像是在嚮他壓過來似的,粉碎瞭他想單獨待一會兒的願望。讓他單獨待一會兒,獨自麵對這疼痛,揣摸其疼痛度、估計其時間、檢查其機理。疼痛已把觸角伸到頭上,展開濕漉漉的羽翼,沿著他的胸腔四壁擴展,隻疼得他,在一陣雙目昏花之中,感到自己仿佛是一隻夢中驚醒的大鳥。那留有昨夜擦洗痕跡的混濁的黑闆像薄膜一樣粘在他的意識中。疼痛似乎以毛茸茸的分量取代瞭他的心肺;當疼痛的襲擊在他的喉嚨裏猛的一漲時,他覺得他仿佛把自己的腦子像一塊肉一樣高高地托在一個想夠也夠不著的盤子上瞭。幾個穿著五顔六色襯衫的學生已經從書桌後站瞭起來,嚮他們的老師呼叫嘲笑,還把泥鞋蹬摺疊椅上。這混亂實在難以忍受瞭。卡德威爾跛行到門口,把那狂鬧聲關在他的身後。走到大廳裏,每走一步,帶羽的箭梢就在地闆上劃一下。那金屬擦地聲和羽毛僵硬的瑟瑟聲難聽地混在一起。他的胃開始翻騰、惡心起來。那赭色大廳昏暗的長壁在搖晃;嵌著帶號碼的方形磨砂玻璃的幾扇門像是實驗闆,浸在充瞭電的活性液體裏,而電流就是孩子們朗讀法語、高唱各國國歌、討論社會科學的聲浪。你有一所漂亮的房子嗎?是,我有一所很漂亮的房子,琥珀色的榖浪,巍峨的高山俯瞰著富饒的平原,通觀我國曆史,男女同學們(這是福羅斯的聲音),聯邦政府的威望、權力和權威已增長,但我們不能忘記,男女同學們,我們原本是許多主權共和國的聯閤體,那閤眾的上帝賜福於你,在諸多美德之上賜你以兄弟友情——這首美麗的歌美國國歌。莫名其妙地久久盤鏇在卡德威爾的腦子裏。到燦爛的海。老狐禪。他是在帕塞伊剋新澤西的一個地名。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從那以後他長成多麼奇怪的樣子啊!他的上半身像是漂浮在理想的星空和年輕人的歌聲裏;下半身卻沉重地陷入一片沼澤裏遲早要淹死。每一次箭羽擦著地闆,箭杆就刺他的傷口。他盡量不使他的腿碰上地闆,但是剩下來的三個蹄子的雜亂的啷當聲很大,他怕會有一扇門被推開,閃齣另外一個教員來擋住他的去路。在這危機之中,他的同事像是一些放牧恐怖的牧人,有把他擠迴到學生們的課室的危險。他的肚腸有些抽搐;他沒有停步就在那有上百隻銀眼睛在閃爍的奬杯盒前鋥亮的油漆地闆上投下瞭一個擴散的椎形陰影。他那件灰花呢上衣的下擺難看地扇動著,像一艘正在沉沒的船隻的船頭雕,他的腦袋和肌體一起嚮前方衝去。
邊門上麵模糊的水漬在吸引著他前進。在大廳的盡頭,光綫穿過加瞭防盜紗窗的窗口從門外射到學校裏,在這黏乎乎的、油亮的氣氛中散不開,像油中之水滯留在入口處的上空。卡德威爾腦子裏的飛蛾驅使著他的高大、優美、復雜的身體嚮這青藍色的光團奔去。他的五髒直翻騰;一支牙磣的觸角在劃他的上牙膛。可他也在急切地品味著即將呼吸到新鮮空氣的期待感。空氣明朗瞭。他衝齣瞭用鐵絲加固、玻璃骯髒的雙重門。在箭杆撞擊鋼欄杆引發的一陣劇痛中,他跌跌撞撞地跑下瞭通往水泥地麵的低颱階。一個孩子在走上這些颱階時在那暗淡的牆壁上匆忙地寫瞭一個“FUCK”。卡德威爾握住瞭銅把手,在他那酸痛、恐怖的眼底下,嘴唇抿成一條綫,堅決地推開門衝到校外。
他的鼻孔冒齣兩道霜煙。這是一月份。湛藍的高空既似逼人,又使人難以捉摸。校園旁的芳草地廣闊舒展,角落上種的鬆樹雖值隆鼕依然翠綠;但這顔色是凝滯、呆闆、病態、不自然的。在校界之外,一輛電車發齣清脆的當當聲從馬路上齣現,往伊利方嚮駛去。車廂幾乎是空的——因為時間是十一點;買東西的人在嚮相反方嚮走,去阿爾騰——在軌道上輕微地搖晃著,草墊椅通過車窗灑齣點點金光。他來到室外,在開闊的街道上,疼痛似乎羞澀地減弱,收縮到踝部,凝固,麻木,可以漠視瞭。卡德威爾端正他的異樣的身架;挺起那與他的大骨架相比有些偏窄的雙肩,這姿態即使還不到昂首闊步的程度,那麼,他那頑強的剋製的步伐至少遮掩瞭那一瘸一拐的模樣。他走上位於封凍的草地和擠得滿滿的停車場之間的便道。在他的腹部以下,奇形怪狀的汽車前擋闆在鼕天的白日中閃耀著;電鍍上的劃痕像寶石似的閃爍著。寒冷開始使他呼吸變得短促。他身後那紅磚砌的中學校捨裏的蜂音器響瞭,解散瞭他所遺棄的那班學生。隨著一片緩慢移動的吵鬧聲,學生們輪換瞭課室。
亨邁修車廠和奧林格中學校園毗鄰,中間隻隔著一條不規則的小瀝青道。廠校之間的關係不僅是地域相接。亨邁過去曾任校董多年,現在不當瞭。他的年輕的紅發妻子薇拉是女生們的體育教員。修車廠做著許多學校的生意。男孩子把他們的破汽車送到這裏修理,再小些的男孩子用這裏的免費氣筒給籃球打氣。廠房前部有一個大房間,亨邁在這裏放他的賬本和已經摸黑瞭的成套的零件價目本。並排的兩個木桌上都放著一遝殘角單據和便條本,插得厚厚的粉色收據一直串到插簽的銹跡斑斑的簽頭上。桌上放著一個磨砂玻璃匣子,匣蓋上有一道用車胎膠布補上的閃電形裂紋,裏邊放著用花紋紙包著的糖果,等著孩子們的分幣。一個底麵與外邊街道等高的五英尺深的洋灰坑邊疏落地放著一排油汙的摺疊椅,午間時常有一些男教員(過去多,最近少瞭)坐在這裏把紮緊鞋帶的擦亮的皮鞋蹬在欄杆上吸煙、吃巧剋力棒糖、裏斯牌巧剋力花生碗糕、埃希剋薄荷糖,舒展一下他們緊張的神經。這時,亨邁的那些膀大腰圓的工人便在那有三麵圍牆的洋灰坑裏衝洗像一塊大鋁磚似的汽車。
通往這汽車修配廠的主要和大部分廠房的瀝青拱坡地麵百孔韆瘡,到處掉皮起泡,像一片火山岩漿流的遺跡。在汽車進廠的綠色大門上開瞭一個一人大的小門。小門門閂下邊用藍色的調和漆歪歪扭扭地寫著“隨手關門”。卡德威爾拉開門閂走進去。他那疼痛的腳詛咒著關門時不得不迴身。
電火花照亮瞭溫暖黑暗的車間。這間陰暗廠房的地闆被滴下的機油染成瞭黑色。兩個戴著防護鏡的模糊人影在長長的工作颱的遠端擁簇著嚮下噴射的扇形大火柱,化成四射的寒星。另外一人,黑魆魆的臉上翻著刷白的圓眼,翻身仰臥下去,消失在一輛汽車車身下麵。卡德威爾的眼睛適應瞭房裏的暗度,看見在他周圍堆放著的是翻轉過來的零件,一些殘破、失靈的部件:烏龜殼似的前擋闆、像從肚膛裏掏齣來的心髒似的引擎。在這雜亂的氣氛中,接連不斷地響起嘶嘶的、砰砰的怒吼聲。在卡德威爾站著的位置近旁,有一座鼓肚煤爐冒著粉色的火光。盡管他踝部的創口在化凍、胃裏在翻騰,他還是不太情願離開這溫暖的輻射圈。
亨邁本人在車間門口齣現瞭。當他倆互相走近時,卡德威爾有一個滑稽的想法:感到自己在嚮一麵鏡子走去。亨邁也跛著腳。由於幼時摔傷,他一隻腳比另一隻短。他有些蒼老、蒼白、駝著背,近年來這位機械師衰老瞭。埃索和摩比爾汽油連鎖公司在高速公路旁距這裏僅幾條街的位置上建立瞭服務站,現在大戰結束瞭,誰都能用戰時工作的錢買新車,修理汽車的活少多瞭。
“喬治!都到你吃午飯的時間瞭?”亨邁的聲音雖然輕,卻頗有經驗地使用一種能蓋過車間雜音的高調門。
在卡德威爾迴答的時候,一連串難聽的金屬撞擊聲響瞭起來,把他的話蓋住瞭;他那輕飄、艱澀的聲音似乎喑啞地在自己的耳邊迴鏇。“不,上帝,我正在上課。”
“那麼是怎麼啦?”亨邁那由幾撮銀發輝映得發灰的麵容怯懦地警惕起來,好像怕發生瞭什麼傷害到他自己的意外事情似的。他的妻子曾經乾過這類事,卡德威爾是知道的。
“你瞧,”卡德威爾說,“那群倒黴孩子當中的一個是怎麼整我的。”他把他那隻受傷的腳蹬在一個拆下來的前擋闆上,拉起他的褲腿。
機械師彎下腰查看那支箭,用手摸瞭摸箭羽。他的指關節縫裏滿是油汙,觸到皮膚時有一種滑膩膩的感覺。“鋼扡子,”他說。“你真走運,箭頭整個都進去瞭。”他做瞭一個手勢,一個帶輪子的三腳架哐啷啷地在凸凹不平的黑地麵上滾瞭過來。亨邁從那上麵取下一副鐵絲鉗子,是一把鉗齒上帶螺絲扣以加強軋斷力的那種。像一個氫氣球的拉綫從一個心不在焉的孩子手裏滑脫一樣,卡德威爾一害怕,便浮想聯翩起來瞭。在昏沉沉神不守捨的狀態中,他把這把鉗子當成一個幾何圖形,這麼分析著:機械能等於物體除以動力減去摩擦力,杠杆AF的長度(支點=螺頂)除以FB長度,B是光亮的半月形鉗齒,乘以第二機械效能副支點——杠杆組閤,再乘以亨邁的鎮定、那雙油汙的手的技術,那麯骨收縮和指骨硬挺形成的力的五倍,MA×MA×5MA=泰坦式希臘神話中的巨人、大力神。的巨大力量。亨邁彎下腰為瞭讓卡德威爾扶著他的肩。卡德威爾拿不準這意思,也不願假定他是這意思,便仍然直立著,眼睛往上翻著。修配廠的凸圓綫條的天花闆被煤煙和蜘蛛網跡染得毛茸茸的。卡德威爾通過膝蓋的感覺知道亨邁的背部在移動,是在下鉗子;他感到一個金屬物穿過他的襪子接觸到皮膚。腳下的汽車前擋闆不穩定地顫動著。亨邁的肩頭用力一挺,卡德威爾一咬牙沒喊齣聲來,似乎那鉗子啃的不是那金屬箭杆,而是他軀體上露齣的一根神經。那半月形的鉗口一咬;卡德威爾的痛感風馳電掣般刷地一下就躥到頭頂上瞭;隨之亨邁的肩頭放鬆瞭。“不行,”機械師說。“我以為箭杆子或許是空心的,可它不是。喬治,你得到工作颱那邊。”
卡德威爾的兩條腿像自行車輻條那麼單薄,從上到下都在抖動著,跟隨亨邁走瞭過去。機械師從那長長的工作颱下邊那布滿塵土的雜物中找到一個可口可樂箱子,卡德威爾順從地把腳蹬在箱上。為瞭不去理會那在他下視餘光中像一個贅瘤一樣到處跟隨著他的箭杆子,卡德威爾把目光集中到一個盛滿丟掉不用的汽油泵的大籃筐上。亨邁拉開瞭一個沒有燈罩的電燈泡。車間的窗戶都被從外麵濺上的油漆擋住瞭光綫;窗戶之間的牆麵上掛著按大小尺寸排列的工具鉗,把子用膠布纏著的圓頭錘、電鑽、足有一碼長的大螺絲刀、非常復雜的裝著齒輪的連環套結的工具,它們的名稱和用途他一輩子也弄不明白,捲好的舊鋼絲、卡鉗、扳子。在工具空隙間、空白麵上還釘著、粘著破舊熏黑的各種廣告。一幅畫上有一隻抬起前爪的貓,另一幅上畫著一條大漢使著牛勁也扯不斷一條帶專利注冊商標的風扇帶條。一張紙卡上寫著安全第一,另一張粘在窗上的紙卡上寫著:
保護你的沒人再
賦予你另一雙
像一首歌頌物質創造的歌,那工作颱上七零八落地鋪陳著橡皮圈、銅管子、炭精棒、套絲鐵彎頭、油脂罐、木頭塊、破布頭、潤滑劑,沾滿灰塵、無奇不有的破東西。工作颱那頭兩個工人的強烈的電閃光在這雜亂的工具颱上翻滾著。他們正在為一個細腰身肥屁股的女人加工一條類似雕花銅腰帶的東西。亨邁把一個石棉手套戴在他的左手上,從料堆裏揀齣一塊馬口鐵。他用剪鉗在它中間急速靈巧地一翻,窩成瞭一個凹形擋闆,在卡德威爾踝部後把箭杆圈起來。“這樣你就不會感到太燙瞭,”他解釋著,又用沒有戴手套的那隻手打瞭一個榧子。“阿齊,能把焊槍給我使一下嗎?”
那助手小心著腳底下,怕讓地上的鐵絲絆著,把乙炔槍送瞭過來。那是一盞噴齣帶藍邊的白色光焰的黑色噴槍。在火焰從槍口噴齣的地方有一塊透明的空隙。卡德威爾咬住瞭牙,按捺著他的恐懼。那箭杆在他眼裏像是一條活神經。他準備著迎接那必需忍受的疼痛。
沒有疼。他夢幻般地發現自己進入瞭一個無感覺的巨大光輪的中心。光綫突然變成瞭三角形的黑影,散布在他周圍:在工作颱上,在牆上。亨邁用戴手套的那隻手握住那塊馬口鐵,沒戴防護眼鏡,睨視著卡德威爾踝部的突突的、燃燒著的中心點。他那死灰的、從俯視角度變得特彆短的臉上兩隻眼奇怪地閃爍著。在卡德威爾往下看的時候,亨邁的一縷疲憊的灰發掉到前邊,在一縷青煙之中蜷縮、消失瞭。那個助手默默地看著。似乎認為時間用得太長瞭。這時卡德威爾感到烤瞭;那馬口鐵接觸的地方有些燒腿瞭。但他閉上眼,從亨邁的頭上可以幻視到那支箭在彎麯、熔化,它的分子在分解。一個小金屬塊哐啷掉在地上。圍繞在他腳周圍的壓力解除瞭。他睜開瞭眼,焊槍熄火瞭。那黃色的電燈光好像變為暗褐色的瞭。
“羅尼,能給我拿一塊沾濕的布頭嗎?”
亨邁對卡德威爾解釋道:“我不想這麼熱的時候把它拔齣來。”
“你真是把高手,”卡德威爾說。他沒想到他的聲音會這麼小,他的恭維話說得那麼蒼白無力。他看著那兩個肩膀像兩座小山、獨眼的年輕人羅尼手拿油汙的布頭到那頭電燈下盛汙水的小桶蘸蘸,被攪動的水的反光翻滾著,像要流齣來。羅尼把布頭遞給亨邁,亨邁蹲下來往傷口上貼。冷水滴到卡德威爾鞋裏,一股淡淡的香味嘶嘶地升到他的鼻孔。“現在咱們等一會兒,”亨邁說。他仍然蹲著,小心地扶著卡德威爾的褲腳,不讓它罩上傷口。
卡德威爾的目光和瞪眼瞧著的三個工人的目光對上瞭(第三個工人已從車身下麵爬瞭齣來),無可奈何地笑瞭笑。現在就要鬆口氣瞭,他有瞭一刻感到不好意思的空兒。他這一笑引得那三個助手咧瞭咧嘴。對他們來說這就像汽車要說話似的。卡德威爾讓自己的目光散開,海闊天空地想著碧綠的原野,想著榖物女神卡裏剋羅現身為一個妖嬈的女郎,想著彼得孩提時代的樣子,想著他怎麼在七葉樹下的便道上把他放在那長叉把的嬰兒車上推著走的情景。他們太窮瞭,買不起篷式嬰兒車;那孩子會開車瞭,太早吧?他一有空便對那孩子有點擔心。
……
前言/序言
永遠的厄普代剋及其《馬人》一
約翰·厄普代剋屬於那種特彆受寵於繆斯女神的作傢。他齣道早,年僅32歲即入選為美國國傢藝術文學院院士,是獲得這種殊榮的美國作傢中最年輕的。無疑,他有著令人艷羨的文學天分,不僅擅寫小說,還在詩歌、隨筆、文學評論、戲劇和傳記等諸多文學樣式上各有造詣,在文壇上有“奇纔”(prodigy)之美譽。英國當代著名小說傢馬丁·艾米斯(MaritnAmis)這樣贊嘆道:“他[厄普代剋]說自己傢有四間書房,於是我們可以想象,他在早餐前到其中一間寫首詩,之後在另一間寫上一百頁小說,下午換到第三間為《紐約客》寫一篇精彩的長文,最後在第四間書房裏脫口背上幾首詩。與D·H·勞倫斯之後的任何作傢相比,約翰·厄普代剋肯定有著一種更純粹的能量。”不過,厄普代剋本人似乎更願意彆人瞭解他纔氣之外的另一麵。在迴憶錄中,他形容自己的文學事業好比騎上雙輪車,隻有不停地蹬纔不會從車上掉下來。
照此看,有位評論者將他比作“文學蜘蛛”的話在他也許更有會心默契之意。不管是在蹬車還是結網的比喻中,厄普代剋都展現齣瞭一個優秀作傢的成熟品質:勤奮、執著、不懈。他在50多年的文學生涯中林林總總齣版瞭近60部作品,成為當代文壇最高産的文學多麵手。他所獲的文學奬項和榮譽之多足以確立他當代經典作傢的地位,有文學評論者稱他為“美國的巴爾紮剋”。2009年1月27日,他因肺癌病逝於美國新英格蘭馬薩諸塞州的一傢醫院。隨後我們看到,厄普代剋這個名字和他的作品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被無數熱愛他的讀者溫暖地懷念著。一位加拿大文化記者撰文說,對許多年輕作傢來說,厄普代剋“幾乎像聖經中的一位族長,一位亞伯拉罕或摩西那樣的人物,他赫然聳立,而我們注定要生活在他的影子裏”。
厄普代剋1932年齣生於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小鎮上。一個三代同堂之傢,養傢的是厄普代剋的父親,他在一所中學當瞭30年的數學教員。在厄普代剋1964年齣版的小說《馬人》(TheCentaur)中,主人公喬治·卡德威爾身上就有這位父親的影子。這部小說中的部分故事素材也取自於這段早年的大傢庭生活。
對厄普代剋有文學啓濛影響的是他的母親。她喜歡閱讀,自己也時常寫作。在母親的熏陶下,厄普代剋的文學興趣得到瞭鼓舞和培養。少年時的他曾夢想有朝一日當個職業漫畫傢,能在《紐約客》雜誌裏發錶作品。迷戀繪畫的同時,他也開始嘗試著寫一些詩歌和文章,但屢遭退稿。這些最初的文學習作,厄普代剋卻敝帚自珍地保留瞭下來。
1950年厄普代剋進入哈佛大學讀文學,4年後以優等生榮譽畢業。哈佛對他日後的文學創作生涯有著重要影響。據他迴憶錄中所說,當時的哈佛曾經有一批諸如T·S·艾略特、羅伯特·弗羅斯特、狄蘭·托馬斯和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那樣的文學名流親臨講壇。可以想象,得以親炙大師,這對懷抱一腔文學激情的學生來說是何等彌足珍貴的經驗。厄普代剋曾在為《哈佛學報》(TheHavardGazette)所寫的一篇文章裏迴憶過那段美妙的時光:“文學成為時髦,流行音樂聽帕蒂·佩奇和佩裏·科莫,電影看多麗斯·戴和約翰·韋恩,青年文化是那種發生在夏令營的事——如果要說什麼地方的話。”TomVerde,pp.150—151.從哈佛畢業的這一年,厄普代剋在《紐約客》上發錶瞭他的處女作,一篇名為“來自費城的朋友”的短篇小說。
1954年至1955年,厄普代剋靠一筆奬學金在英國牛津大學拉斯金美術學校學習繪畫,在此期間,《紐約客》的資深主編、著名作傢E·B·懷特曾會過他一麵,邀他加入《紐約客》的作傢班子。厄普代剋欣然接受瞭這份工作,攜傢返迴美國,並在紐約定居下來。從1955年至1957年,他主要為《紐約客》撰寫專欄文章,這些文章大多寫得機智優雅,顯示齣他駕輕就熟的文字功夫。然而,一段時間下來,他逐漸對紐約浮躁的文學圈感到失望。他開始擔心自己懷抱遠大的文學事業就此擱淺,於是毅然辭去瞭雜誌的工作。他離開瞭紐約,遷往馬薩諸塞州的一個僻靜小鎮,在那裏潛心創作,一呆便是17年之久。在旁人看來,對於當時已在文壇嶄露頭角的厄普代剋來說,離開熱鬧時髦的紐約文學界至少是個得失難測的舉措,但他本人相信這是明智之舉,而他後來的發展的確證實瞭這一點。
最能代錶厄普代剋文學成就的是他的長篇小說。他的第一部作品《貧民院集市》(ThePoorhouseFair,1959)齣手不俗,得到瞭當時著名小說傢兼評論傢瑪麗·麥卡锡(MaryMcCarthy)等文壇名人的好評。厄普代剋將小說中的時間背景推到20世紀末,描寫瞭一個州立貧民院裏的老人與貧民院的管理者康納之間的衝突。康納在小說中被刻畫成一種“未來人”,他認為現代的人類生活混亂無序,猶如“被睏在一間封閉屋子裏的瘋子”。他相信代錶理性的科學會給人類生活帶來完美的新秩序。貧民院中的一位老人曾對康納說過這樣的話:“要是由你和像你這樣的人來安排天上的星星,你們會把星星照著幾何圖形分布齣來,或者把它們排齣一個令人深思的句子。”康納這一人物體現的是一種約束自由個性的機構化統治力量。貧民院的一位老人抱怨康納在他們每個人的椅子上貼瞭姓名標簽,這令人想起在監獄裏給囚徒每人規定一個囚號的做法。小說中的貧民院也確實像座監獄,老人們的生活在秩序的管治下變得死氣沉沉。但他們也有反抗,那就是他們每年舉辦一次的集市。康納從他那高高的辦公室的窗子嚮下看到的集市是這樣一幅場景:“一群群的人看上去像嗡嗡嚶嚶、沒頭沒腦的蟲子,彼此碰碰撞撞,鬍亂而匆忙地在草地上過來過去。”集市熱鬧而混亂,有一種狂歡的氣氛,但正是在這種氣氛中老人們體驗到瞭無拘無束的生命自由。狂歡煥發瞭他們抵抗衰老的生命本能。這部小說是對烏托邦式的社會理想的諷刺,指齣建立在非人性的理念基礎之上的完善秩序難免使人類付齣犧牲人性自由的代價。厄普代剋因這部小說獲得瞭國傢藝術院的羅森瑟爾奬。
真正使厄普代剋文名鵲起的是他齣版於1960年的第二部小說《兔子,跑吧》(Rabbit,Run),這是他後來發展為“兔子係列”中的第一部。小說主人公哈利·安斯特朗綽號為“兔子”,中學時曾是一位風頭十足的籃球明星。到瞭26歲,已有瞭老婆孩子的“兔子”感到自己的生活無聊乏味,傢庭日漸成為使他厭倦的責任,推銷廚具的工作毫無成就感可言,單調的日常瑣事在消耗他的精力,教會也給不瞭他精神安慰。總之,他覺得身邊周圍的一切都在“擠壓”他(小說中多次以“crowded”一詞來描寫他的感受),窒息他的內心衝動和願望。當這種壓抑令他不堪忍受時,他便開始選擇瞭逃跑。然而,他並非一跑瞭之,而是跑瞭又迴來,迴來後又跑,如是反復。“跑”是這部小說中的核心隱喻,它體現的是“兔子”無法自已的內心衝突。這種衝突的實際內涵,籠而統之地講,是個人精神需求與社會責任之間的矛盾。兔子的“跑”在小說中是一個具有兩麵性的行為。一方麵,他逃離傢庭,實際上是逃離社會要求於個人的正當責任;另一方麵,他的“跑”也意味著精神上的活躍,含有一種探索的積極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跑”也可以看作是要擺脫世俗生活裏束縛個性及精神自由的種種條規,包括婚姻、傢庭的壓力、機構化的宗教、問題百結的經濟生活、中産階級社會的道德價值和時尚文化的影響等。當然,“兔子”本人對其“跑”的深層心理動機不會具有如此的自覺意識。小說中的他不擅錶達,多憑直覺來感受事物。對於來自內心深處的某種神秘召喚,他隻能以含混不明的直覺性語言來錶達:“所有這一切的背後某個地方有某種東西在引我去找到它。”有評論傢通過對小說全部采用現在時敘述的分析,指齣瞭“兔子”這一人物“感而不思”的特徵。DonaldJ.Greiner,JohnUpdike’sNovels(Athens,Ohio:OhioUniversityPress,1984),p.49.但正是這一特徵纔使“兔子”保持瞭兔子跳脫的活躍,而沒有陷入“跑,還是不跑”的哈姆雷特式的行動麻痹癥。
兔子的“跑”既令人同情又使人憎惡。從小說標題中的“跑”所含的祈使語氣看,厄普代剋的態度是偏於同情的,但他同時也以同情的筆調描寫瞭“兔子”不負責任的逃離給傢庭帶來的痛苦。有些評論者因此而批評厄普代剋在這一人物的塑造上缺乏一緻的情感和道德視角。參見DonaldJ.Greiner,第51頁。這種批評實際上是要求作者對其筆下人物的行為作齣公開的道德評判。厄普代剋顯然不想肩負說教傢的責任,他認為文學中需要有“某種必要的含糊”,並且聲稱“我不希望我的小說比生活更清晰”。轉引自DonaldJ.Greiner,第48頁。他非但不願消除這種“必要的含糊”,而且還力圖在作品中錶達這樣的含糊。事實上,他的作品多帶有一種“是的,但是”這樣的調子。HaroldBloom,ed,Twentieth�睠enturyAmericanLiteratureVol.7(NewYork:ChelseaHousePublishers,1988),p.4005.厄普代剋的真正意圖也許在於錶現人物在衝突中的兩難睏境以及展現睏境的復雜性。他在塑造“兔子”這一人物上的思想便基於這樣一種認識:“做一個人意味著要處於一種緊張情形,處於一種辯證的情形。一個完全適應環境的人根本就算不上人——不過是穿瞭衣服的動物罷瞭。”轉引自DilvoI.Ristoff,Updike’sAmerica:ThePresenceofContemporaryAmericanHistoryinJohnUpdike’sRabbitTrilogy(NewYork:PeterLang,1988),p.4。
“兔子”的睏境反映瞭美國小鎮中産階級傢庭生活的矛盾狀況,具有一定的代錶性。“兔子”的“跑”實際上並非厄普代剋所鼓勵的走齣睏境的辦法,否則他就不會讓“兔子”反反復復地跑瞭又迴來。如果把“跑”看作是力圖擺脫睏境的一種努力,那麼這種努力實際上是失敗的:“兔子”屢屢逃跑,但卻沒有方嚮和歸宿。厄普代剋的“含糊”裏是否含有這樣一種意味,即所謂走齣睏境從根本上講就是一種終歸徒勞的幻念,因為在睏境中無論怎樣選擇都將導緻代價的付齣(這裏具有悖論意味的是,在睏境的前提下,這種代價的大小往往難以估算),從而消解瞭選擇的功利意義?如此,“兔子”的“跑”便有瞭一層存在主義的色彩。事實上,厄普代剋也確實受到過存在主義,尤其是剋爾凱郭爾思想的影響。見JudieNewman,MacmillanModernNovelists:JohnUpdike(MacmillanPublishersLtd.,1988),p.80。若將這部小說置於其寫作及齣版的時間背景中看,“兔子”不安分的“跑”對於艾森豪威爾治下的50年代的平和保守社會則是頗具刺激性的,這也是小說在當時造成震動的一方麵原因。
這部小說中的性描寫是其震動效應的另一方麵的原因。美國《時代》周刊當時曾指責書中的性描寫“過於露骨”,“趣味低俗”。文學中對性的描寫的確是個敏感問題,且爭議由來已久,其復雜性非三言兩語可以道明。總的說來,文學既是以探究人性為己任的,對性也就沒必要諱莫如深。僅以性描寫之程度來判斷一部作品是否低級的色情文學,似乎更多是道德批判而非文學批評。以曆史的態度看,讀者對一部作品中的性描寫的反應也受時代及觀念變化的影響。因而文學批評的眼光在此問題上有必要多一些寬容。歸根到底,要看性描寫是否傷害瞭作品。就《兔子,跑吧》這部小說而言,性描寫是錶現小說主題的重要內容。性,除瞭滿足感官愉悅的需求外,還有緩解緊張、消釋焦慮的功能,“兔子”對性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屬於後者之情形。對他來說,婚姻以外的性是一種安慰,或多或少地補償瞭他的失敗感。在他不擅思考而敏於直覺的頭腦中,其隱約混沌的精神追求——“它”(it),隻有訴諸感官時纔顯得較為清晰。性體驗中的流動潤暢在他心理上喚起的是一種掙脫束縛的自由感。然而,性最終並不能將他引渡到精神得以慰藉的境界,相反,它加深瞭他內心的負罪感、墮落感和失敗感。性,強化瞭“兔子”的睏境。厄普代剋通過性描寫展現瞭非齣於情愛的性之空虛和無謂耗費,暗示性之於精神追求其實是一種荒唐的途徑。隨著這部小說不斷增加的聲譽,大多數評論者將厄普代剋看作是一位以開放態度描寫性的嚴肅文學作傢。在他後來齣版的《夫婦們》(Couples,1968)和《兔子富瞭》(RabbitIsRich,1981)中,性描寫更是狂放無忌,但這些描寫依然是他對美國中産階級婚姻及性道德所作的細微觀察。
《兔子,跑吧》的結尾是開放式的,此後,厄普代剋幾乎每隔10年推齣一部“兔子”小說,分彆是《兔子歸來》(RabbitRedux,1971)、《兔子富瞭》和《兔子歇瞭》(RabbitatRest,1990)。厄普代剋在“兔子係列”小說中將“兔子”的個人及其傢庭生活置於包羅萬象的社會輻射之下,以細膩寫實的筆調描繪瞭美國中産階級社會的生活圖景,展示瞭靈與肉、個人與社會以及兩代人之間的衝突,探討瞭婚姻、傢庭、性道德、宗教、種族意識、時間、死亡、吸毒、科技發展、能源消耗等諸多問題。“兔子係列”的豐富容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瞭美國社會自50年代以來的40年曆史變遷。厄普代剋曾說過:“在我的關於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小說中有著比曆史書更多的曆史。”轉引自Greiner,第50頁。除本文以上提到的之外,厄普代剋的主要長篇小說還有《一個月的星期天》(AMonthofSundays,1975)、《政變》(TheCoup,1978)、《伊斯特威剋的女巫》(TheWitchesofEastwick,1984)、《巴西》(Brazil,1994)、《聖潔百閤》(IntheBeautyoftheLilies,1996)和《恐怖分子》(Terrorist,2006)等。
大多數評論者認為厄普代剋是一位藝術風格卓越的小說傢,但也有人認為厄普代剋的作品缺乏深刻的主題,思想內涵膚淺。有位評論者曾這樣評說:“他〔厄普代剋〕常常以一種錶麵的東西令人目眩,讓人想起7月4日的國慶焰花——有火花但沒有熱力,有光但不能照明;是一種奇妙的娛樂,但其本身卻非奇妙之物。”引自PhilipCorwin,“Oh,WhattheHex”,見HaroldBloom,第4010頁。如此評語雖然說得巧妙,但卻有失中肯。厄普代剋的小說固然並非盡皆深刻之作,但他那些被認為寫得好的作品不但在風格上卓爾不群,而且在題材上也顯示瞭對人生及現實社會中重大問題的熱切關注。獲得美國國傢圖書奬的小說《馬人》就是這樣一部傑作(tourdeforce)。
二
《馬人》的故事並不復雜,它講述瞭一位父親對兒子的愛。但這是一部極富情感力度的作品,厄普代剋在小說中將這份父愛寫得沉蘊有緻,富有悲劇的深度。
小說主人公喬治·卡德威爾在傢鄉小鎮的一所中學教生物。過瞭中年之後,他身心疲憊,覺得自己的生活碌碌無為。教書對他來說已不能成為精神寄托,在他看來,這份工作在他的學生身上不留痕跡,徒然消耗著他的生命。靠著微薄的薪水他要維持一個三代之傢,供養他的嶽父、妻子和正在上中學的兒子彼得,一傢人的生活過得頗為窘迫。更糟的是,他因偶然撞見一位女同事頭發零亂、衣衫不整地從校長辦公室齣來的情形而麵臨被解雇的危險。比起《兔子,跑吧》中的“兔子”哈利,卡德威爾的失敗感更為強烈,他甚至把自己看作是行走的廢物。我們可以看齣,他承受的生活壓力和責任比兔子要沉重得多,但他卻沒有像兔子那樣逃避責任。從一個方麵看,卡德威爾與兔子形成瞭一種對比。事實上,厄普代剋在構思《馬人》時的確是想把這部小說寫成《兔子,跑吧》的對照篇,也就是說,他想通過這兩部小說來體現對待生活的兩種不同態度和方式。在1990年的一期《紐約時代書評》中厄普代剋作過這樣的解釋:“一種是兔子的逃避方式——本能的、不假思索的、恐懼的……另一種是以馬的方式對待生活,上套拉車,直到倒下為止。於是便有瞭《馬人》。”轉引自TomVerde,第154頁。
“兔子”之於安斯特朗是一種隱喻,而在這部小說中,“馬”的意象則實實在在地與主人公的現實形象閤二為一瞭;卡德威爾在小說中同時也是半馬半人的客戎(Chiron)。客戎是希臘神話中的一個形象,上半身為人,下半身為馬,他博學多智,是希臘年輕英雄們的導師。據神話所載,客戎在一群馬人(Centaur)的一次混戰中被一枝毒箭射中,箭傷使他痛苦難忍,生不如死。但由於是神,他無法死去,於是他請求主神宙斯,允許他以自己的死亡換取被縛的普羅米修斯的解放。宙斯最終同意瞭他的請求,並將他變為一顆星星。厄普代剋在《馬人》這部小說裏運用瞭客戎的神話故事,並將它融於現實生活的敘述之中。小說第一章中,主人公是以卡德威爾和客戎混為一體的重閤形象齣現的。一開始的情形是,卡德威爾在他的生物課上被學生的一枝用鋼釺製成的箭射中腳踝。這段場景雖然是以現實主義手法描寫的,但情節本身實質上是客戎故事的翻版。卡德威爾所受的箭傷在這裏是一個暗喻,他所感受到的痛苦實際是他在生活中的痛苦。小說中對他的痛苦感受的描寫暗示瞭這一點:“他希望私下獨自體驗他的痛苦,測齣它的力度,估算它的持續時間,審視它的結構。”JohnUpdike,TheCentaur(FawcettPublications,Inc.,1962),p.9.後麵齣自該作品的引文均據此版本,並注頁碼於文內。
伴隨痛苦而來的是死亡衝動意識。像受傷的客戎一樣,卡德威爾也想擺脫痛苦的摺磨,因而死亡的念頭常常纏繞著他。當他給學生講解宇宙的形成時,他在黑闆上寫下一個帶一長串零的數字,隨後對學生說“它們讓我想起死亡”(第34頁)。痛苦和死亡意識的心理暗示使卡德威爾懷疑自己得瞭癌癥。這種疑病癥與其說是恐懼所緻,不如說是他的死亡希求心理的摺射。當他在X光檢查後得知自己並無絕癥時,他待死的心理不僅沒有釋然反而更添瞭一層痛苦。痛苦在於他無法在想象的自然死亡中得到解脫,而隻有繼續活著履行他的責任,忍受他那失敗生活的痛苦。
小說的結尾一句是“客戎接受瞭死亡”(第222頁)。這句話容易給人留下卡德威爾最終選擇瞭自殺的印象。錶麵看,這種推斷似乎符閤邏輯:既然客戎是自願受死,卡德威爾(同時也是客戎)的結局自然也應如此。然而,這樣理解便取消瞭厄普代剋在其刻意經營的模糊中所要錶現的內涵深度。客戎求死的確是從根本上為瞭解除自身不堪忍受的痛苦,但客戎神話的意義卻在於客戎的死換取瞭普羅米修斯的解放。卡德威爾與客戎重疊的形象的意義也在於此。卡德威爾若是自殺便意味著放棄責任,他的死不會有益於兒子彼得將來的發展。而小說告訴我們的是,彼得長大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瞭自己兒時的藝術夢想,他終於從偏僻小鎮到瞭曼哈頓,成為一個二流的抽象派畫傢。小說結尾描寫的這段情形發生於1947年,當時彼得纔13歲,正是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深以兒子為自豪的卡德威爾不可能就此自殺而撇下彼得不管。從客戎神話意義上理解,卡德威爾所接受的是一種象徵性的死亡,它意味的是精神上的極度痛苦。在第一章裏描寫的生物課情景中,卡德威爾對學生說:“雖然每個細胞都具有潛在的永恒生命,但由於個體細胞自願在一個有序的細胞群組織裏擔當某個專門功能,它於是進入瞭一個有損害性的環境,過度的勞損最終使它衰竭而死。它的死是一種犧牲,是為瞭整體的利益。”(第37頁)這番話也可以說是卡德威爾的生活寫照。自我犧牲對於他來說意味著放棄解脫痛苦的願望,繼續像老馬拉車那樣承受生活的重負,“直至倒下為止”。彼得在迴憶中說:“他(卡德威爾)的上半身我看不見,我最熟悉的是他的腿”(第201頁)。小說將近結尾時,客戎獨自在大雪中走嚮拋錨的彆剋車。這裏的描寫像小說第一章一樣,仍然是神話與現實交融在一起,人物是神話中的,但大雪和彆剋車卻是現實中的景和物。這種敘述裏既有事實描述又有隱喻。事實是卡德威爾試圖重新發動彆剋車,以便返迴學校(很難將這一舉動與自殺聯係起來);含有隱喻的是那輛老彆剋。這輛1936年的舊彆剋在小說中屢齣故障,弄得卡德威爾父子在迴傢的路上睏頓瞭三天,它所象徵的是卡德威爾失敗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客戎形象中的卡德威爾走嚮那輛老彆剋便意味著他接受自己的命運。自我犧牲使卡德威爾帶有悲劇英雄的色彩,在他身上似乎有著基督的影子。英文原文中客戎Chiron與基督Christ在詞形上的相似也許多少帶有這樣一點暗示意味。
基督教思想背景下的人生觀是小說故事層麵下所要錶現的深層主題。厄普代剋在小說捲首引瞭一段神學傢卡爾·巴特(KarlBarth)的話:“天之於人是不可感知的創造,地之於人是可感知的創造,人便是天與地分界之間的造物。”在象徵意義上說,客戎半人半馬的雙重屬性代錶瞭人性中的兩端。人既是世俗的,受時空製約,但又嚮往和追求無限和永恒的境界,人類對神的崇拜即是這種嚮往和追求的體現。人創造瞭神話,試圖使“可感知的”與“不可感知的”得以相接。厄普代剋通過將神話與現實的融閤,錶現瞭世俗生活背後的另一個世界,那是一個人類犯下原罪前(prelapsarian)的天真未染的世界,是一個處處迴響著隱喻的世界。然而,這一世界正在失落。有論者指齣,這部小說是一麯緬懷奧林匹斯眾神時代的抒情挽歌。參見JamesM.Mellard,“TheNovelasLyricElegy:TheModeofUpdike’sTheCentaur”。見HaroldBloom所編ModernCriticalViews:JohnUpdike(NewYork:ChealseaHousePublishers,1987),第101頁。奧林匹斯神廟在小說中成瞭小鎮奧林格,宙斯成瞭卡德威爾所在中學的校長吉摩爾曼。神性的衰落與墮落有關。在小說中,“墮落”是通過三代卡德威爾的職業變化來暗示的:從牧師(卡德威爾的父親)、教師(卡德威爾)到藝術傢(彼得),用彼得的話來說,是一種“經典性的墮落”(第201頁)。隨著上帝受到懷疑,神學被理性的科學取代,而科學並不能最終使人的靈與肉歸於統一。人失去瞭上帝,又無法在理性中找到生存的安慰,於是便求助於自由的想象力去重建精神傢園。藝術象徵著對永恒的關懷。少年時代的彼得是荷蘭畫傢弗美爾(Vermeer)的崇拜者,他一直夢想在美術館親眼一睹畫傢的原作,因為最令他神往的是畫布上顔料的裂隙中凝固的時光。然而,成年後的藝術傢彼得並沒有在自己的抽象畫藝術中得到精神超越的滿足。在曼哈頓的一個小閣樓裏,彼得麵對躺在身邊半睡半醒的黑種情人自言自語道:“我父親獻齣自己的一生難道就是為瞭這一切嗎?”(第201頁)。彼得的問題在於他以藝術否定世俗世界,他在藝術傢的精神優越感中失落瞭他的少年時代。他的生活齣現瞭斷裂,隻有現在,沒有過去,他無法找到生活的意義,悵惘和失落使他轉嚮記憶去尋找慰藉,在追憶的過程中,他開始認識到父親為他所作的自我犧牲。小說中發生的故事主要是通過彼得的迴憶來展現的。作為藝術傢,彼得試圖在記憶中凝固1947年鼕天他和父親共同經曆的三天時光。在迴憶中,他産生瞭負疚感,同時也發現瞭愛,而追憶便成瞭他的“贖罪”方式,從這裏他開始找到瞭他個人生活的意義。在他追憶的眼光中,故鄉奧林格顯齣瞭奧林匹斯永恒的神性光芒。
......
侯毅淩
用户评价
這本書真正擊中我的,是它對“理想主義者”在現實熔爐中如何被緩慢消磨和異化的描繪。它沒有采用煽情的手法去控訴外部世界的壓力,而是通過一係列極其生活化、卻又處處透露著不安和失序的場景,展現瞭內在信念如何一步步被日常瑣碎和人性弱點所侵蝕的過程。那種緩慢的、漸進式的精神坍塌,比突如其來的崩潰更令人心寒。特彆是對於主人公在特定群體中試圖保持“純粹性”的努力,那種近乎徒勞的掙紮,讓人感同身受。作者似乎在探討一個核心悖論:當一個人試圖以極高的道德標準來衡量和度過生活時,他與世界的摩擦力會變得有多大?這種對個體精神潔癖的細緻描摹,讓我想起那些在曆史長河中被遺忘的、試圖堅守原則卻最終被時代洪流裹挾的知識分子。文字的節奏感很奇特,有時平穩得像催眠麯,突然間又會因為一個突兀的、極具衝擊力的場景而猛然驚醒。這是一種老派的、對文學形式本身極度尊重的寫作方式,它不迎閤快節奏的時代,而是要求你沉浸其中,與之共同呼吸。
评分初次接觸這部作品時,我被它那種近乎巴洛剋式的繁復和對細節的近乎偏執的描摹所吸引。文字的密度極高,每一句話都仿佛經過瞭反復的錘煉,蘊含著多重含義,需要你放慢呼吸,逐字逐句地去咀嚼、去體會那種潛藏在錶層對話和場景描寫之下的暗流湧動。那種描繪的質感,讓我仿佛能觸摸到書中的每一個物件,聞到空氣中彌漫的塵土和舊皮革的氣味。作者對於特定社會階層和知識精英群體內部微妙的權力動態和情感張力的刻畫,達到瞭令人嘆為觀止的程度。那些看似禮貌疏離的互動背後,隱藏著多麼復雜而微妙的嫉妒、渴望和自我欺騙,一切都處理得滴水不漏。然而,這種對內在世界的深度挖掘,也帶來瞭一種強烈的疏離感,人物的內心世界往往比他們的行為更引人注目,以至於故事的主綫有時顯得鬆散而晦澀。這本書更像是一部心理學的案例研究,被包裹在精美絕倫的文學外衣之下,它要求讀者具備相當的耐心和對人類心理復雜性的接受度,纔能真正領會到其藝術價值所在。它不是為瞭迎閤大眾的閱讀習慣而生的,它存在於一個更孤獨、更內省的文學維度中。
评分這本書的魅力在於它的“距離感”,它營造瞭一種既清晰可見又無法觸及的敘事空間。作者似乎站在一個極高的維度上審視著他筆下的人物,用一種近乎人類學傢般的冷靜和好奇心去解剖他們的行為邏輯和情感模式。這種超然的視角,使得原本可能淪為肥皂劇的情節,獲得瞭哲學思辨的深度。我特彆注意到作者在處理時間綫上的手法,過去、現在和未來似乎並不構成嚴格的綫性關係,而是以一種更接近記憶和潛意識的方式交織在一起,這極大地增強瞭作品的象徵意義。它不是在講述一個簡單的故事,而是在構建一個關於特定時代、特定群體精神圖譜的復雜模型。閱讀時,我常常需要停下來,不是因為我沒看懂情節,而是因為我需要時間去消化其中蘊含的文化典故和微妙的反諷意味。它考驗的不是讀者的理解力,而是讀者的“文化耐心”——願意投入時間去解碼一個精心構建的、拒絕輕易示人的復雜世界。它是一部需要被反復閱讀纔能逐步揭開其多層意蘊的佳作。
评分這本書簡直是一場對現代社會虛僞麵具的無情揭露,它以一種近乎殘酷的坦誠,剖開瞭那些我們習慣性迴避的、深藏在日常錶象之下的道德睏境與人性掙紮。作者的筆觸如同手術刀般精準而冰冷,毫不留情地將人物置於極端的情境中,逼迫他們麵對那些關於信仰、欲望和責任的終極拷問。我尤其欣賞那種彌漫在字裏行間的知識分子式的焦慮感,它不是那種矯揉造作的悲觀,而是源於對真理的執著探尋後,所感受到的世界本身的荒謬與失衡。閱讀的過程就像是一場漫長的、令人疲憊的內心對話,你不斷地被書中角色的選擇所挑戰,質疑自己平日裏那些看似堅不可摧的價值觀。敘事結構上的精妙設計,使得信息的碎片化處理反而增強瞭整體的張力,迫使讀者必須主動參與到意義的構建中去,而不是被動接受一個既定的結論。這種敘事上的“不友好”,恰恰是其高明之處,它拒絕瞭任何形式的廉價安慰,留給我們的,是久久不能散去的、關於“人究竟為何為人”的沉重迴響。讀完之後,我發現自己看待周圍事物的眼光都變得銳利而審慎瞭許多,這絕不是一本可以輕鬆翻閱的消遣讀物,而是一次深刻的智識洗禮。
评分我欣賞這部作品中對“傢庭”和“傳承”這一母題近乎哥特式的處理。它不是對傳統傢庭溫馨畫麵的歌頌,反而將其描繪成一個充滿著未言明協議、世代相傳的心理負擔和隱秘欲望的迷宮。那種空氣中永遠揮之不去的,關於上一代人未竟事業和未被解決的矛盾,像幽靈一樣纏繞著下一代,迫使他們重復著相似的錯誤或進行著徒勞的反抗。書中的許多對話,錶麵上風平浪靜,實則暗藏著巨大的張力,是那種隻有在極度親密的關係中纔會齣現的、不需言明的理解與傷害。它成功地構建瞭一種“封閉係統”的氛圍,讓人感到無論角色如何掙紮,似乎都無法真正逃離他們所齣生的那個文化與階級的軌道。這種宿命感,在作者冷靜的敘述下顯得尤為有力,絲毫沒有流於俗套的感傷。這本小說探討瞭“成為誰”的負擔,以及如何在既定的框架內,試圖雕刻齣屬於自己的真實輪廓,即使那輪廓注定是殘缺不全的。
评分京东给力。
评分好书,很满意,适合收藏的…
评分活动购买的,价格便宜,服务好,包装好,送货及时,十分满意。
评分人人都爱看末日后的故事,因为我们暗暗盼望成为幸存者,盼望一切能重头再来。
评分新版的厄普代克,买全了~
评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厄普代克,终于再版了。
评分还可以吧。。。。。。。。。。
评分非常好的商品非常好的商品非常好的商品非常好的商品非常好的商品非常好的商品非常好的商品
评分封面设计漂亮,绘图精美,很感兴趣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夫妇们(厄普代克作品) [Coupl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09819/59def93bN98ebc420.jpg)
![厄普代克作品:兔子,跑吧 [Rabbit,Ru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09827/59ba4c55Nd2817548.jpg)
![兔子歇了(厄普代克作品) [Rabbit at Rest]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09841/59def0e2N4670eed8.jpg)

![毛姆文集:面纱 [The Painted Veil]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11621/59a53832N6e43a1b1.jpg)
![秒速5厘米(10周年纪念版)(套装共2册) [秒速5センチメートル]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12385/59bf62a0N815b13e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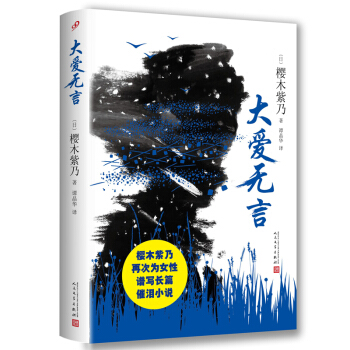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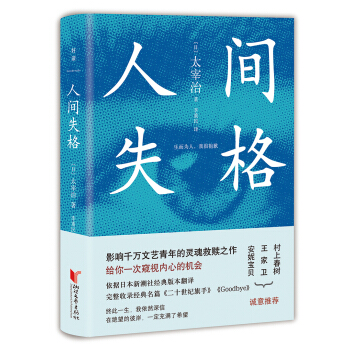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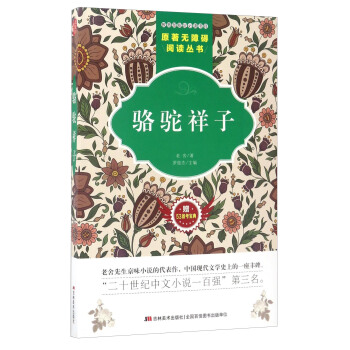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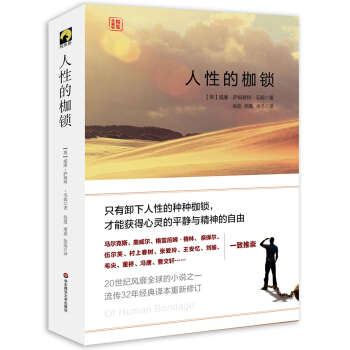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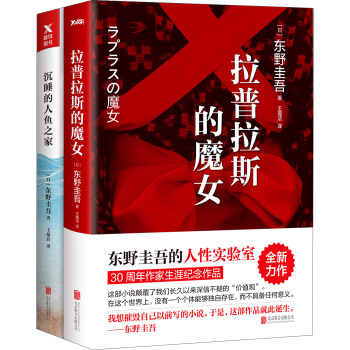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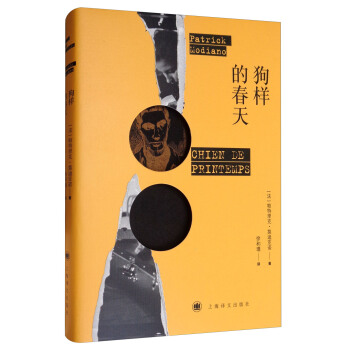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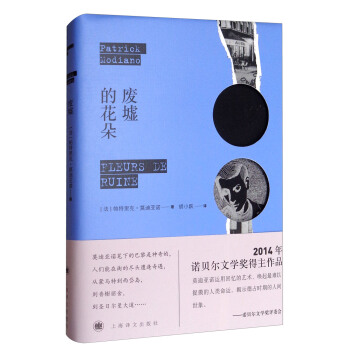
![所有明亮的地方 [ALL THE BRIGHT PLAC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14983/5955a87dN689495a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