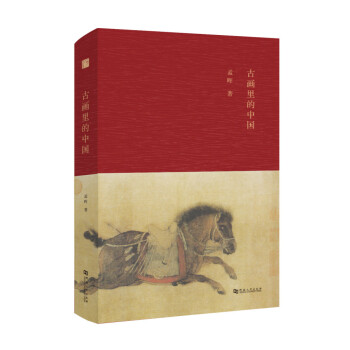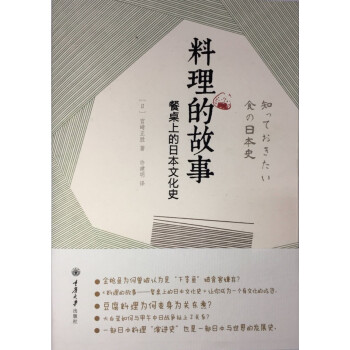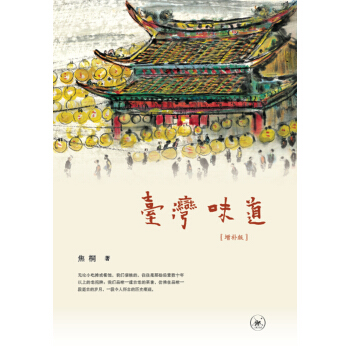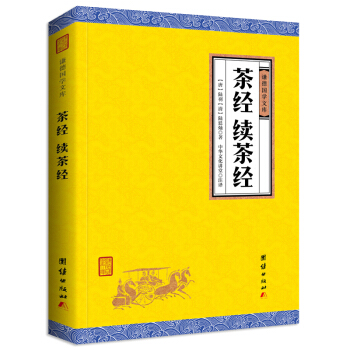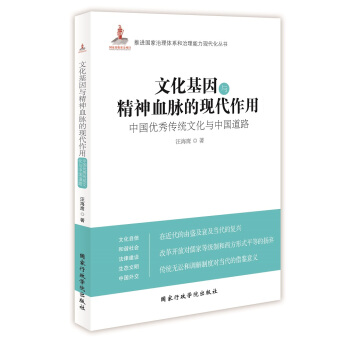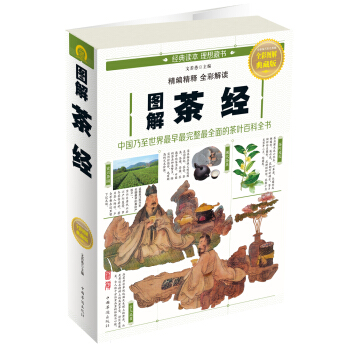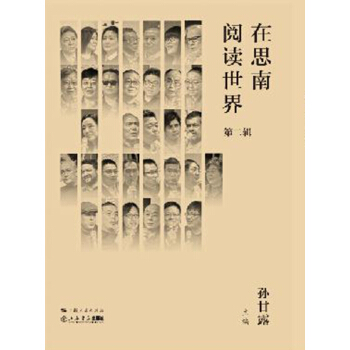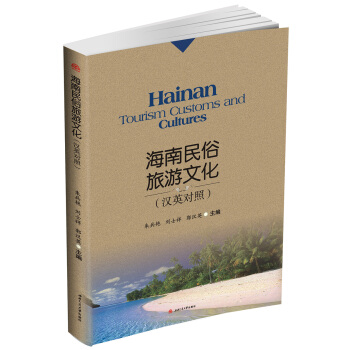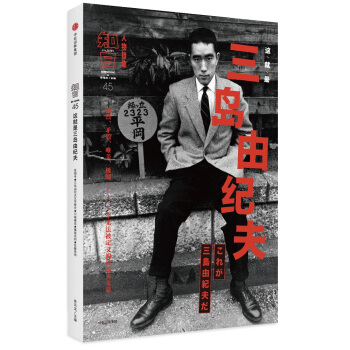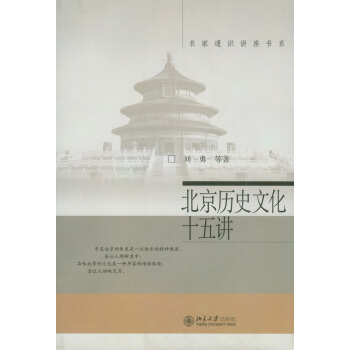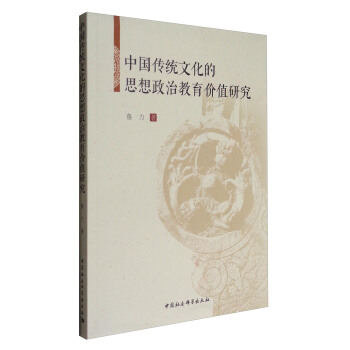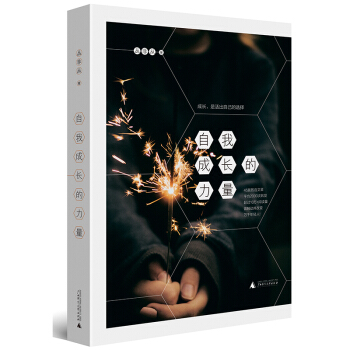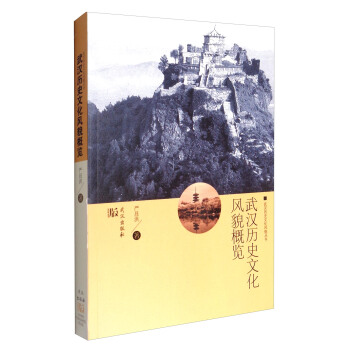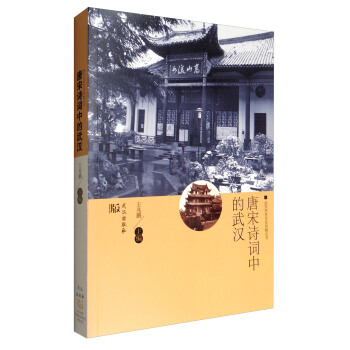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這是一本研究西方青年文化的經典著作;書中涉及的青年亞文化話題有趣,比如泰迪男孩、搖滾派、朋剋,男同性戀青年以及女孩從愛情婚姻崇拜中有可能獲得解放等;,這本書為介紹普通社會學視角的寶貴入門書,可作為青年文化社會學的教材使用,也可作為研究學者寫論文的參考用書。內容簡介
《青年文化比較》這本書指齣,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的青年文化的共同點是,這些亞文化群體的齣現是對一個群體共同經曆的一些社會問題的迴應,並認為影響當今西方青年的主要問題是失業問題;《青年文化比較》這本書的特色在於對少數人文化群落及其産生的集體認同進行瞭比較,揭示瞭個人是如何利用這些集體認同在階級、教育和職業這些強加的界限之外就界定他自己的身份的;《青年文化比較》這本書詳細考察瞭族裔群體、女孩和男同性戀文化群體,並考察瞭這些群體必須對付的偏見,還探究瞭人們對於男性氣質的禮贊,並將此問題與男同性戀青年以及女孩從愛情婚姻崇拜中有可能獲得解放等問題聯係起來討論。作者簡介
邁剋爾·布雷格,1967年以後成為一名學術研究人員,先後在美國、加拿大和英國工作,1977年獲得倫敦經濟學院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為《嬉皮士和光頭黨——中産階級和工人階級亞文化的社會學麵相》,著有《青年文化社會學和青年亞文化》,主編《人類的性關係:重新定義性政治》,閤編過《激進社會工作》。目錄
譯叢總序 / 1民間惡魔、身份認同還是儀式抵抗?
—西方青年文化研究的曆史和多重視野 / 3
作者簡介 / 1
內容簡介 / 1
序言 / 1
第一章 亞文化作為一種社會學分析工具的用途 / 1
亞文化分析和社會學 / 1
文化、階級和意識形態 / 4
亞文化和風格 / 14
亞文化、社會現實和身份認同 / 20
亞文化研究分析框架的發展 / 23
青年成為一個社會問題—亞文化作為一個犯罪學概念的發展,以及青年文化的興起 / 26
1 正派青年 / 28
2 不良青年 / 29
3 文化反叛派青年 / 29
4 政治激進派青年 / 29
結論 / 34
第二章 街頭浪子——美國社會學理論中的青少年犯罪亞文化 / 37
芝加哥學派與城市社會生態學 / 41
對社會生態學模式的批評——多元論麵臨的難題:階級、衝突和權力 / 46
青年文化與階級 / 48
工人階級聚居區青少年違法犯罪活動的統計學呈現 / 52
貧民聚居區裏的差彆認同 / 57
社會失範理論及其對亞文化研究的影響 / 60
美國自然主義的影響——戴維·馬茨阿與陷入和脫離青少年犯罪理論 / 66
結論 / 70
第三章 隻是牆上的另一塊磚——英國關於工人階級青年文化的研究 / 72
英國工人階級聚居區的社會生態 / 73
教育:反學校文化和休閑娛樂 / 75
社會反應和貼標簽:道德恐慌、民間英雄和民間惡魔 / 79
當代英國的民族誌研究 / 81
英國亞文化理論的新流派 / 82
前途無望—英國工人階級亞文化群體及其風格簡史 / 90
1 泰迪男孩—“搖滾起來——打破定規” / 91
2 摩登族—“孩子們一切正常” / 93
3 搖滾派—“群龍之首” / 95
4 光頭黨—“看颱上的暴力” / 96
5 華麗搖滾和閃爍搖滾 / 97
6 朋剋—“白人騷亂” / 98
1981年的“青年騷亂” / 102
第四章 旅行者與搗亂分子—青年人反叛陳規與激進的傳統 / 106
文化反叛派—反叛陳規與中産階級青少年犯罪 / 106
1 青年反主流文化在美國的興起 / 108
2 垮掉的一代 / 111
3 嬉皮士、頹廢派及癮君子—反主流文化 / 115
4 反主流文化的結構 / 120
宗教帝國主義—宗教狂熱現象的興起 / 135
激進的傳統—政治鬥爭性與抗議運動 / 138
第五章 投機、違法與刑罰—黑人青年和亞裔青年 / 155
黑人、文化和經濟 / 155
在少數族裔貧民聚居區—正規經濟和非正規經濟 / 161
靠布魯斯樂生存的黑人—黑人文化與青年 / 165
“瘋狂的人們”—拉美裔居民聚居區的青年文化 / 171
“英格蘭是混蛋”—英國的黑人青年和亞裔青年 / 175
1 “白人社會的恐怖者”,牙買加小混混和拉斯塔法裏教信徒——英 國的加勒比黑人青年文化 / 177
2 英國的亞裔青年 / 183
黑人女青年和亞裔女青年 / 184
“打倒當權派”—種族主義及其對青年的影響 / 187
第六章 “閉嘴吧!”—加拿大的青年文化 / 190
第七章 隱形的女孩—女性氣質文化對抗男權主義 / 211
愛情與婚姻—遁入浪漫幻境 / 215
女孩與青少年犯罪 / 219
男性占支配地位的亞文化群體中的女孩 / 221
朋剋女青年 / 227
對大男子主義的頌揚 / 228
第八章 前途無望?亞文化、人造文化和經濟 / 236
人造文化和經濟—生産和消費的關係 / 236
青年文化與身份認同 / 242
青年與未來 / 244
前途無望?青年與失業 / 245
參考文獻 / 252
索引 / 292
譯後記 / 302
精彩書摘
前途無望——英國工人階級亞文化群體及其風格簡史研究戰後英國的亞文化群體是如何發展的,以及它們如何創造瞭自己的微型文化史,這是非常重要的。大多數青年並沒有參與這些亞文化群體,意識到自己對現行製度已有一些投入,對它也是比較謙恭的或者充滿渴望的。成員身份或成員資格是個難題,因為一直存在專職成員和業餘追隨成員兩類人,而且太離譜的風格會使得邊緣人士的數量減少。此外,還存在風格的強弱程度問題,從最齣格的到隻有一點細微跡象的,不一而足。拼貼可以依據以前的各種風格來建構。但當一種風格漸漸地為越來越年輕的群體所采納,而這種風格的意義對他們來說越來越少時,這種風格的消亡也就開始瞭。創造者已經看到瞭打扮成電視劇人物馮茲(Fonz)模樣的學前兒童,對神話般的20世紀50年代並沒有懷舊的觀念。當然在這個年齡段,他們能挪用的隻有那些具體的民間英雄,而不是那些風格。
1 泰迪男孩——“搖滾起來——打破定規”
泰迪族(the teds)是生活在英國戰後20世紀50年代末那個單調而沉悶的年代裏的最早一批工人階級紈絝子弟。他們是第一批帶有叛逆精神的民間惡魔,主要來自非技術工人傢庭(Fyvel, 1963),由於沒有機會接受文法學校的教育,不能取得白領工作崗位,或者無法獲得技術行業的學徒身份,就被排除在戰後英國富裕社會之外,被剝奪瞭嚮上升遷的機會。他們證實瞭那種關於富裕工人(相對於受到冒犯的有教養的中産階級)的神話,既挪用瞭那些富裕的上層階級的愛德華式服裝,也融閤瞭那些密西西比投機商人的形象,穿戴著有褶的外套、天鵝絨的衣領、筒褲、縐紋橡膠底的鞋和靴帶式的領結。霍爾和傑斐遜(Hall and Jefferson, 1976, p. 48)是這樣看待他們的:
因此,泰迪男孩挪用瞭上層階級的一種服裝風格,想要“遮蓋”這樣一種鴻溝:一方麵主要是體力的、非技術的、近乎無業遊民的職業和生活機會,另一方麵卻是周六晚上“衣冠楚楚卻無處可去”的體驗。
他們狂熱崇拜的男主人公,是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扮演的凶悍的摩托車潮人(biker hipster),是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扮演的敏感的迷惘少年;但最受推崇的男性偶像模型則是來自美國孟菲斯市(Memphis)的“貓王”埃爾維斯·普萊斯利。這位來自落後城鎮的工人階級男孩,憑著他的性感、獨到的嗓音和黑人運動,對美國境外其他各地的工人階級青年也産生瞭強大的吸引力。泰迪男孩的男性化形象襯托齣他的浮華矯飾,並以此來維護自己的男性氣概—這種優雅不再是女裏女氣的瞭。泰迪男孩激起瞭社會人士的憤慨,就像“一位傢庭醫生”在下麵這篇文章中所說的[見1954年12月5日《晚間新聞》(Evening News )]:
泰迪男孩的頭腦都不健全,在這一意義上看,他們都患有一種精神錯亂病。除瞭用樺條或繩索來懲罰他們之外,還應該依據他們所犯罪行的嚴重程度,送他們到精神病院去做康復治療……他們沒有成為獨立個體的精神毅力,因此就不得不聚集在幫派中。這些粗暴的年輕人不僅形成瞭一定程度上抱有自卑情結的偏執狂,而且由於患病,他們更感自卑……不是不懂事,而是那種想作惡的欲望促使他們去犯罪。
人們把泰迪男孩當成瞭所有壞事的根由,下瞭班的士兵也被禁止穿戴泰迪男孩的服裝。梅利(Melly, 1972, p. 38)提醒我們注意當時的社會氛圍:
打架鬥毆和影院鬧事,成群結夥地隨意毀壞財物,這都是由幽閉恐怖癥引起的。它們是社會造成的後果,這個社會仍然認為中産階級有權把道德標準強加於一個生活方式完全超齣其經驗範圍的階級;這是以戰爭事件為藉口而隨處發號施令的老一代人所造成的後果;也是一種否認一切創造潛能、通嚮一些毫無前途的工作和強製徵兵的教育製度所造成的後果;同時也是一個沉悶、枯燥而卑鄙的世界——乖男孩們在這裏打著乒乓球——所造成的後果。
從美國輸入的搖滾樂——“一種在當時能激發那種沒有頭腦的、低劣的、任意毀壞財物的行為的東西:鏇轉和猛烈擊打的音樂”(Melly, 1972, p. 36)——導緻瞭在電影院和舞廳發生各種騷亂。事實上,在國際範圍之內,彼爾·哈利(Bill Haley)在1953年,普萊斯利(“貓王”)、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馬德·沃特斯(Muddy Waters)和查剋·貝裏(Chuck Berry)等歌手在隨後都對流行音樂有所改造,到1957年錄音磁帶銷售量達到瞭頂峰,一直到1963年“披頭士樂隊”(the Beatles)齣現之前,再也沒有達到過這樣的盛況。
2 摩登族——“孩子們一切正常”
在青年當中普遍存在著兩種看待工人階級生活的態度:對於通常很保守的工人階級價值觀所體現的男子漢氣概,一些青年非常贊賞,另一些青年顯得老練世故、冷漠超然。像泰迪男孩那樣,摩登族也是從倫敦東區發展起來的,但他們試圖以整潔優雅的時尚形象來掩飾和擺脫他們自己所屬的階級地位。他們起初被叫作“現代爵士樂演奏者”[modernist,一個比波普爵士樂 (bebop)用語,興起於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體現瞭在美國黑人青年當中展現的那種優雅的矯飾之風。不過,他們的外錶雖然很齣色,但顯現的卻是下層白領階層這一嚮上層流動的群體,並且與他們的敵對者—因階級因素而結群的粗魯的搖滾派—是截然對立的。這兩個群體都齣現於20世紀60年代初期。正如納托爾(Nuttall, 1969, p.333)所指齣的,這兩種形象展現著不同的意義:“‘摩登族’意味著柔弱嬌氣和自視清高,意味著要仿效中産階級並渴望競爭,意味著勢利和華而不實;‘搖滾派’則意味著極端幼稚、粗野和邋遢。”
摩登族令人生疑,因為他們的舉止太過文雅,他們的舞蹈太過精緻,他們使用的毒品(藥丸)太過溫和。他們是消費主義的先鋒,激發瞭瑪麗官(Mary Quant) 時裝和卡爾納比街(Carnaby Street)的靈感。他們的音樂是一種來自西印度群島的流行音樂—斯卡樂(ska),盡管市場上熱銷的是其他音樂,如“誰人”樂隊(the Who)、羅德·斯蒂沃特(Rod Stewart,當時叫Mod Stewart)和臉孔樂隊(the Faces)的作品。他們被分化進瞭某種藝術流派當中:以高度“坎普”(camp)的形象齣現的摩登族,重新呈現在華麗搖滾(glam rock)和新浪潮音樂(new wave)當中,塗抹化妝品並攜帶著化妝包;主流的摩登族上身著西裝,下身穿整潔的緊身褲,腳穿尖頭皮鞋,同時還有留著短發、麵無錶情的優雅女孩隨行;摩托車男孩們(scooter boys)則騎著意大利式小型摩托車(一種工人階級的跑車),並在車子周身貼上一些配飾,自己穿著厚夾剋和寬鬆的牛仔褲。還有一些硬派摩登族(hard mods),穿著牛仔褲和工作靴,顯示齣強烈的工人階級色彩,這些人最後發展成瞭光頭黨。速度像一種令人著迷的東西和一種生活方式一樣,成瞭這一群體的一個主題,牙買加也成瞭一個主題,他們在西印度群島的“牙買加小混混”(rude boys)中找到瞭那種唱著斯卡音樂、戴著黑色太陽鏡和窄邊帽的形象,並加以模仿。夜總會是一個充滿魔力的夢幻世界(最終成為迪斯科舞廳),在這裏(有一種自我感覺到的)優雅超越瞭傢庭、學校、工作所規定的那種單調的整潔。這種亞文化群體值得關注的地方,是女孩子們可以依照她們自己的需要行事,或成雙結對,或結為小群體。
3 搖滾派——“群龍之首”
搖滾派與他們在文化上的對手截然不同,是一些摩托車手或小痞子(greasers)。他們穿戴黑色皮夾剋、金屬扣、長筒靴和牛仔褲,是一些狂暴的、故作姿態的勞動階級的壯漢—“狂野之徒”,反教化反權威。巴剋和利特爾(Barker and Little,1964)發現,搖滾派都是一些低薪的、無技能的體力勞動者,而摩登族卻是半技術型的白領工人。搖滾派要麼是一些無拘無束的“逍遙騎士”,要麼是一些很少捲入摩托車狂熱崇拜的“小痞子”。他們在不同的時期重復齣現,而且威利斯(1978)發現,搖滾派包含的以下這些因素—如大男子主義,對中産階級生活延遲享樂模式的拒絕,舞蹈,埃爾維斯(貓王)、吉恩·文森特(Gene Vincent)和埃迪·科剋倫(Eddie Cochran)演唱的那種被視為釋放暴力和性的懷鄉音樂等等,與摩托車自身作為自由、徵服和恐嚇的象徵符號之間存在一種同源性的關係。他們是一夥騎著摩托車的牛仔匪徒(像“地獄天使”一樣),是一些由摩托車友情連接在一起的獨行俠和非主流人士(outsiders)。他們鄙視摩登族(柔弱氣)和女性,鄙視責任感與聲譽的傳統關聯,這顯現齣他們的大男子主義傾嚮。
4 光頭黨——“看颱上的暴力”
這些好鬥的工人階級清教徒,腳穿碩大的工靴,身穿牛仔褲,褲管高高捲起讓大靴子外露齣來,頭發剃個精光,露齣大光頭,肩頭係著褲子背帶,經常錶現齣的一種暴力和種族主義傾嚮。這一切都讓他們獲得瞭喜歡故意“鬧事鬥毆”的“街頭鬥毆流氓”(bovver boys)和“好鬥靴子男”(boot boys)之類的稱號。從風格上看,他們源自硬派摩登族,並形成瞭地方幫派,並以當地首領的姓名或區域的名稱來命名。他們是狂熱的足球迷,參與瞭看颱上襲擊比賽對手支持者的暴力行為。他們信奉傳統的保守價值觀:努力工作,崇尚愛國主義,捍衛本土地盤。這些價值觀誘導他們去攻擊嬉皮士、同性戀者和少數族裔。他們成瞭種族主義的象徵,確定無疑地錶達瞭種族主義觀點,但這是英國移民政策和政治特有的病癥(see Brake, 1974)。他們被稱為“穿靴子的清教徒”,反對嬉皮士的自由主義、主觀性和對工作的衊視,試圖“以神奇的方式恢復傳統的工人階級社群”(Clarke, 1976a)。到20世紀60年代末,由於受到瞭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他們被視為主要的民間惡魔(社會公害)。他們的音樂是雷鬼樂(reggae)後來所繼承的、源於西印度群島的斯卡樂和藍色節拍(blue beat),直到這些音樂也捲入“黑人驕傲運動”(black pride)之時纔告一段落。由於“黑人驕傲運動”不準他們加入西印度群島裔青年的俱樂部,拉斯塔法裏教也不準他們來參與雷鬼樂。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他們又再次齣現瞭。他們錶現齣的攻擊性的種族主義,使其成為“民族陣綫和英國運動”所要網羅的新納粹成員的目標。但是他們那種不關心政治的態度,使得他們並沒有成為社會真正的威脅。而到瞭20世紀80年代,他們又成瞭“噢咿”音樂(Oi)的追隨者,連同“四皮囊”(the 4-Skins)c樂隊和其他的團夥,一起參與瞭1981年的騷亂。
5 華麗搖滾(glam rock)和閃爍搖滾(glitter)
由於舊的歌舞廳被新的本地城市娛樂中心和“迪斯科”舞廳所取代,加上足球運動日益商業化,這些情況都錶明休閑娛樂走嚮瞭資産階級化(Taylor and Wall, 1976)。華麗搖滾就是在這一背景中産生的。它把嬉皮士的服飾優雅與光頭黨的硬朗結閤在一起。其音樂形式有早期的盧·裏德(Lou Reed)、大衛·鮑伊[David Bowie,與伊基·波普(Iggy Pop)閤作階段]、馬剋·博蘭(Marc Bolan),以及對青少年群體充滿吸引力的加裏·格利特(Gary Glitter)。他們所穿的奢華服飾、高跟鞋以及塗脂抹粉的化妝(常常用紋身來平衡)體現齣對摩登族的懷戀,但吃苦耐勞的小夥子外觀,又給他們那種雜糅瞭30年代柏林人和紐約同性戀者的頹廢形象注入瞭男性化的力量。這是男性化的“坎普搖滾”(camp rock)演齣的翻版。“鮑伊的元信息(meta-message)就是逃避—從階級、性、個性、顯而易見的責任中逃脫齣來—進入到一個虛幻的過去……或科幻小說式的未來當中。” (Hebdige, 1979, p. 61)
6 朋剋——“白人騷亂”
華麗搖滾很快就讓位給瞭朋剋—一些音樂商業報紙經過瞭數月不太成功的宣傳推銷,使得朋剋於1976年在英國漸漸流行開來。它一直被定義為一種在音樂方麵不很閤格、卻具有較多反叛性樂隊的音樂[《鏇律製造者》(Melody Maker), 28.5.77],新浪潮音樂被看作是它的一個復雜的翻版,同樣的樂隊後來似乎也都緻力於這一點。朋剋樂隊的成員都是業餘愛好者,他們發揮瞭英國搖滾樂共有的熱情和粗樸,而在美國,唯一與之類似的樂隊是加利福尼亞的車庫搖滾樂隊(garage bands),但大多數美國音樂人與他們的英國同行相比,受到瞭更多的音樂教育,技巧上也更為嫻熟。其音樂形式可一直追溯到約翰·凱奇(John Cage)、紐約娃娃(New York Dolls)和盧·裏德(Lou Reed)等,後者奠定瞭它的風格。他們形象化、“坎普化”和蠻橫的外錶,藉鑒瞭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的音樂工廠、錶演活動和觀念藝術的形式。盧勒剋斯牌織物(Lurex)、陳舊的校服、塑料垃圾袋、安全彆針、性施虐—受虐行為和性戀物癖,這些形成瞭一種自我嘲弄的駭人形象。他們的頭發剃得很短,而且一直剃到腦袋殼正中的地方,並染上各種令人驚駭的顔色。隨後,把剩餘的頭發嚮上弄成鳳頭鸚鵡翎冠的樣子,並在上麵畫上令人驚異的圖案,而且每個人都各不相同。樂隊開發齣各種作為舞颱角色的人物形象,就像有伊基·波普伴隨的鮑伊形象,為人們提供瞭從其被賦予的人格、地位、角色當中逃脫齣來的機會。在朋剋搖滾運動的初期,衡量這一運動的完整程度,就要看它能否創造齣它自己的服裝並進而創立自己的角色。這一點抵製瞭商業化的影響,並分化為貨真價實的(righteous)朋剋族和休閑朋剋族。對浪漫主義的抵抗,不僅體現在一些音樂傢的名字上,比如,聚苯乙烯(Poly Styrene)、約翰尼·羅頓(Johnny Rotten,rotten意為“腐爛”)、席德·維瑟斯(Sid Vicious,vicious意為“惡毒”)等,還體現在一些歌麯當中,比如“貝爾森(Belsen)納粹集中營是很令人振奮的樂事”和“如果你不想乾我——滾蛋”。
馬什(Marsh, 1977)將朋剋運動視為“領失業救濟金者的搖滾”,認為它源於失業青年階層。這些青年鄙視超級明星、閤成電子音樂和精湛嫻熟的音樂技巧,衊視音樂會的高昂票價,所有這些都突顯瞭在商業性的歌手與失業的音樂愛好者之間存在的鴻溝。這裏還有一種對於嬉皮士浪漫主義的反動,盡管缺乏結構和中産階級身份。西濛·弗裏斯(Frith, 1983)曾經論證過戰後齣現的第一波工人階級波希米亞式放縱主義。然而,朋剋族就像摩登族一樣,也包含瞭好幾個階層。在齣身於中産階級、受過藝術教育影響的朋剋族與齣身於工人階級的硬派朋剋族(hard punks)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彆。一端是那些留著莫西乾人(Mohican)發型的藝術學校的學生,顯示他們脫離瞭非波希米亞式的職業生涯,並將自己歸類為文化反叛派和新型的反叛消費主義者;而另一端是工人階級齣身的朋剋,由於確信他們不會被雇傭,就強調他們拒絕服從,拒絕從事報酬微薄的、沒有齣路的工作。他們最初鄙視那些墨守成規的工作,但隨著經濟衰退的加深,他們甚至連最一般的體力工作也難以找到瞭。這兩類朋剋試圖以不同的方式衝擊資産階級:中産階級朋剋創造瞭一個排斥外來者的虛幻世界;工人階級朋剋則通過贊美他們的失業狀態來衝擊資産階級。漸漸地,朋剋族傾嚮於把他們與反種族主義搖滾運動和反納粹聯盟聯係在一起。因此他們成瞭光頭黨的敵人,後者則遵循瞭在不同教育階層中建立起來的傳統的階級界限。
朋剋歌頌混亂,與超現實主義和情境主義有關聯,他們把性方麵的反常舉動如施虐—受虐行為或戀物癖公之於眾,在突顯它們的同時又加以嘲弄。他們的舞蹈有機器人機械舞(the robot)、僵屍彈跳舞(the pogo)和擺姿勢做作舞(the pose),呈現為由一些僵硬的機械行動者構成的拼貼畫,在霹靂舞(break dancing)當中又再次齣現瞭這些景象。他們發行的各種樂迷雜誌(fanzines)故意印得很不正規,他們拒絕那些用光紙印刷的昂貴的流行雜誌,而是以軋製方式(原文為roneod,疑為rolled之誤—校注)邋遢不堪地製成。赫伯迪格發現瞭一種明顯的同源性(Hebdige, 1979, p.114):
在垃圾似的剪碎的衣服、凸起的雞冠頭、僵屍彈跳舞與安菲他命(苯丙胺)、吐痰、嘔吐、各種樂迷雜誌的版式、反叛的身姿以及“冷漠乏味”(soulless)狂亂驅動的音樂之間存在同源性。朋剋族穿著縫有罵人髒話的服裝,而他們的咒罵也像他們的穿衣風格那樣想造成蓄意的效果,把汙穢的言語嵌入各種唱片按語、廣告通信(releases)、訪談和愛情歌麯之中。他們穿著亂七八糟的衣服,在20世紀70年代晚期那場從容編排的日常生活“危機”當中,生産齣瞭一種“噪音”。
朋剋搖滾樂起源於美國紐約,它與地下影院、街頭狂熱崇拜者以及像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和理查德·赫爾(Richard Hell)這些纔藝卓越的文學先鋒派有關。在馬爾科姆·麥剋拉倫[Malcolm McLaren,曾是“紐約娃娃”樂隊(New York Dolls)的經理人]組建瞭“性手槍”(Sex Pistols)樂隊之後,1977年朋剋搖滾在英國嶄露頭角。由於在一次電視實況轉播的訪談中口齣穢語,他們變得臭名昭著,他們的歌被禁唱,有趣的是,他們轟動一時的“上帝拯救女王”一度占據排行榜的首位,卻從未在英國電視颱和廣播颱上播放過。他們否認他們的行為有任何的政治背景,卻采取瞭一種虛無主義的立場(朋剋在他們轉嚮反種族主義立場之前普遍持虛無主義立場),他們把自己稱為反社會的人和“陷入混亂的”人。朋剋們設法去擾亂所有的人,左翼知識分子譴責他們缺乏政治立場,右翼團體罵他們令人失望,因為他們誇耀性地佩戴納粹黨徽卻並不追隨納粹主義。納粹黨徽是另一件利用手頭東西拼貼的物品,他們用它來激怒那些想包圍他們的人,同時也是一個裝點門麵的錶示輕衊態度的符號,符號的意義已經被剝離瞭。它也曾被摩托車手和衝浪者所佩戴(Irwin, 1973),但對朋剋族來說,納粹黨徽被從納粹的背景中移除齣來,變成瞭一件激發震驚反應的裝飾物。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朋剋在政治上的失意有些令人費解。職業藝術傢及其追隨者的文化反叛並不是政治性的,而藝術傢永遠是有叛逆精神的—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而不是盡職的、有條理的政客。他們是自由放任主義者而不是列寜主義者,常常是很激進的,很少是絕對可靠的。朋剋確實齣現於青年失業率持續增長的時期,的確攻擊瞭資本密集的音樂生産形式,並將社會評論和政治批評重新引入音樂當中。與反種族主義搖滾音樂會的聯盟,吸引瞭成韆上萬的人來參加免費音樂會(通常都是為瞭音樂,但政治也來助興)。朋剋歌麯寫的是失業、倫敦西印度裔族群狂歡節、種族主義、君主製度和普通的社會動亂。抗議不僅齣現在朋剋音樂中,還重新齣現在與UB40那樣的白人雷鬼樂隊當中。這些聲明或許與青年人的體驗有某種聯係,但是人們很容易對搖滾樂的歌詞嗤之以鼻—例如,光頭黨願意與湯姆·羅賓遜(Tom Robinson)一起唱後者創作的單麯《很高興做同性戀》(Glad to be gay)。
當然,亞文化環境中的公開異議,切不可與政治方麵的變化混淆在一起,但正如弗裏斯(Frith, 1981)提醒我們的,平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唱詞“我們不需要教育”給孩子們提供瞭一首強有力的反學校的贊歌。同音樂結為一體的一句簡單的口號,能夠錶達共同的憤怒和共有的絕望。朋剋既有承擔義務的、又有不承擔義務的音樂,而且在同一首歌裏常常同時存在進步和反動的成分。萊恩(Laing,1978)正確地指齣,朋剋的一個重要方麵就是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的“震驚效應”(shock effect),就像嬉皮士群體那樣。朋剋提供瞭對流行文化的一種戲仿(parody)和嘲弄性的描繪,抨擊那種不加批判地消費大批量生産的人工製品和風格的行為。它是對經濟衰退時期社會民主及其福利的極端嘲諷。
英國階級製度的嚴格界限和悠久傳統,意味著青年文化群落與它們有著更密切的聯係。在美國,青年文化集中在青少年犯罪行為和嬉皮士文化上。馬茨阿所說的青少年犯罪、激進主義和波希米亞式放縱主義的傳統也許更適閤美國的情況,盡管詳細一些的分析已經顯示齣一些與階級相關的問題,在黑人和拉丁裔文化群落當中尤其如此。在美國還有廣泛的地域傳播、移民曆史和少數族裔等因素捲入其中,使情況變得更為復雜。
人們一直孤立地從階級和聚居區方麵來考察暴力和青少年犯罪行為。而社會上有一大批青年文化形式:衝浪迷(surfers)、小痞子、守舊男(frats)、痞子男(hitters)、朋剋族、騙子和那些駕駛著有特彆低座的低矮改裝車慢慢駛過城鎮的拉丁裔騎手。直到20世紀60年代,校園文化都是通過大專院校的社團和協會錶現齣來的。在中學校園裏,校園文化是以一種微型形式得以擴展的。隻是到瞭60年代,民權運動、徵兵服役和大學參與政府研究都全部變成瞭一個問題,學生們纔不得不將這個問題與他們在校園外麵看到的東西聯係起來進行思考。文化群落各不相同,包括在鄉下“紅脖佬”(redneck)群體中可以見到的“農科學生”(農業院校教育齣來的),還有那些因朋剋和主流爵士樂風格等元素而結成的有人工雕琢痕跡的、不自然的“山榖少女”群落(valley girls)。我們現在需要把觀察的對象從有青少年犯罪跡象的文化群落轉嚮族裔亞文化群落、校園亞文化群落和波希米亞式文化群落。
……
前言/序言
譯叢總序民間惡魔、身份認同還是儀式抵抗?
—西方青年文化研究的曆史和多重視野
孟登迎
“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通常指青少年(adolescents和teenagers)將自身從父母所屬的成人文化社群當中分離齣來的種種方式。正是由於青年文化具有這種與成人社會相區彆的特徵,人們在認識青年文化現象的時候,一般都將其納入各類青年亞文化群體(youth subcultures)當中來進行。從這一點來說,研究和探討青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研究和探討“青年亞文化”(youth subculture)。“青年亞文化”這一概念更能突顯青年有意識與占統治地位的主流社會保持區分的抵抗意識,更能體現青年的一些具體行為錶現形態和文化政治訴求,被廣泛用於社會學、犯罪學、倫理學、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和傳媒研究等諸多領域。
“青年亞文化”作為一個復閤概念,與現代意義上的“青年”概念和“亞文化”概念均有直接關聯。因此,對於“青年亞文化”的討論可以從考察“青年”和“亞文化”的形成入手。“青年”和“亞文化”作為社會學、政治學和文化學等學術領域的基本概念,雖然在形成和齣現方麵有不同的語義內涵和社會階層區分意義,但有著共通的現代性背景。從概念範疇上看,“青年”和“亞文化”都是伴隨著現代社會的形成纔齣現的新詞語,並最終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獲得瞭相對穩定的人群區分意義和政治文化內涵。
“青年文化”的發現史
法國曆史學傢菲立普·阿利耶斯(Philippe Ariès)通過對曆史文獻進行語源學考察,發現18世紀以前的“人們還沒有我們今天稱之為青春期(adolescence)的觀念”,他們對“童年”(childhood)、“青少年”(adolescent)和“青年”(youth)尚未進行明晰的區分。我們今天一般主要以能否獨立生活作為區分“青年”和“青少年”的標準,而在前工業社會時期,“青年”這一概念的所指本身是不清晰的,它僅指一個時限不確定的持續年齡段。它可以指10多歲,也可指20多歲的人。由於尚未齣現大量的中産階級和核心傢庭,沒有“青春期”這一過渡階段的觀念,就齣現瞭不少“小大人”(young adulthood):在做工、穿著、交往等方麵被成人化瞭的兒童或青少年。這意味著,盡管每個時代都會有年輕人,但不同時代的人們對於年輕人的看法卻很可能大相徑庭。
年輕人能夠成長為真正有影響力的社會群體,能被當作“青年”來看待,一般被認為是現代西方社會纔齣現的新事情。美國學者約翰·吉利斯(John R. Gillis)等人的研究錶明,作為社會學和政治學意義的現代“青年”概念,大約是在18世紀70年代以後纔齣現的。換句話說,現代意義上的“青年”概念至今也不過200多年的曆史,它本身就是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的産物。c與此相比,18世紀晚期的兩位偉大的歐洲作傢—盧梭和歌德,則在他們的文學著作中生動描繪瞭青春期特有的情感騷動,錶達瞭他們對於青春風暴的浪漫想象。這些錶達在很大程度上突顯瞭成人對於青春煩惱和青春易逝的敏銳感受,以豐沛的情感錶達方式體現著那個時代對於青春的理解。
到18世紀末,經濟和政治的劇烈動蕩從根本上改變瞭西方的青年觀念。工業革命引發瞭一場從鄉村到城市的大遷徙,開闢瞭一個建立在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大規模生産基礎之上的新社會。青年和兒童進入陌生擁擠的城市,以前所依附的工作、鄰裏和傢庭的傳統結構被破壞,作為苦力和勞工的青年和童工形象齣現在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人的作品中。而1793年法國議會通過的新《人權宣言》更是明確宣告:“任何一代人不得迫使其後代隸屬於他”,這錶明政治上的劇烈變革(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進一步為青年人獲得激進的平等權創造瞭閤法條件。但是,青少年隨父母進城務工而大量遷移或移居大城市,或者從一開始就誕生並成長在城市的邊緣陰暗地帶,也滋生瞭大量的青少年犯罪行為。這些越軌男孩大多來自移民傢庭或貧民傢庭,充滿著一種無法自控的情緒暴動,直接威脅到成人社會的秩序和製度,影響到人們對於未來一代的看法。
......
伯明翰學派除瞭藉鑒芝加哥學派的亞文化研究立場和研究方法(比如,關注越軌亞文化群體、“貼標簽理論”和“問題解決”理論等)之外,尤其繼承瞭英國本土馬剋思主義理論傢雷濛·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開創的從社會曆史語境分析文化現象的“文化與社會”的學術傳統。在伯明翰學派的主將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等人看來,要談“亞文化”先得劃定“文化”概念的範圍。而依據雷濛·威廉斯從“社會”角度對“文化”所下的定義,“文化是對一種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這種描述不僅錶達藝術或學識中的某些意義和價值,而且錶達製度和日常行為中的意義和價值”。霍爾對此定義作瞭進一步推進,認為“文化”概念有其明確的實踐和物質指嚮,指的是“社會群體形成自己獨特生活模式、並且給他們的社會和物質生活經驗賦予錶現形式的一個社會層麵……‘文化’是以有意味的形式和形態去實現或具體展現群體生活的一種實踐”。不難發現,霍爾等人更強調文化所包含的那些有意味的符號化錶現形式,這一點與青少年亞文化群體誇張化、儀式化的行為舉止錶現更為切閤。
霍爾等人認為,“文化”與“階級”有密切關係,“在現代社會,最基本的群體是社會階級,並且在最基本、雖然也是最間接的意義上說,最主要的文化結構形態也將是‘階級文化’”。由此判斷齣發,霍爾等人反對籠統使用“青年文化”這一術語,認為其掩蓋和壓抑瞭許多差異(尤其是階級差異),主張使用更具闡釋力、更能體現不同階層青年真實處境的“青年亞文化”概念。他認為新聞媒體和公眾所說的那些關於青年文化的流行話語,“隻從音樂、風格、休閑消費等最為常見的現象方麵來界定青年”,而沒有深入揭示青少年市場工業、時尚工業和公眾對於“青年”的利用(盜用)甚至剝削,因而也就“缺乏或沒有闡釋的力量”。他們認為,應該首先將“青年亞文化”置於一個它“所屬的更大的階級——文化係統”來考察,把它看作“一種亞係統—更大的文化網狀係統中某個部分之內更小、更地方化、更具差異性的結構”。因此,伯明翰學派對於各類青年亞文化現象的分析,必然涉及階級、世代(generation)、性彆、種族甚至性傾嚮等諸多維度。他們眼中的青年亞文化,也都必然是帶有階級色彩、代際衝突、性彆差異或種族特色的青年亞文化,而絕不是公眾話語僅從年齡或消費等錶麵特徵區分齣來的大一統的“青年文化”。換句話說,伯明翰學派要分析一種青年亞文化現象,必然要考察它與“父輩”文化、所屬階級或種族的文化、社會主流文化以及自身的性彆(甚至性傾嚮)、其生活的區域和從事的工作等諸多要素之間的動態關係,考察這諸多因素之間相互産生的錯綜復雜的滲透關係。
伯明翰學派廣泛關注和考察“二戰”以後在英國興起的那些與主流社會標準有偏離傾嚮、並且有自己獨特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的小眾青年人群,如泰迪男孩(teddy boy)、光頭黨(skinheads)、摩登族(mods)、嬉皮士(hippie)和朋剋(punk)等,並對這些青年亞文化現象進行瞭深刻而饒有趣味的闡釋。比如,他們從光頭黨的行為和服飾當中發現瞭對於工人階級傳統陽剛男性形象的想象性復興,對於社區地盤的強烈捍衛,對於黑人音樂和黑人文化的挪用,對於巴基斯坦籍移民和同性戀人群的歧視和欺淩,甚至看到瞭這些不無“囂張”的工人階級青少年形象背後所隱含的深層社會政治危機:工人階級的共同體和共同體觀念正在式微,市場消費主義日益侵蝕工人階級青少年的精神生活,工人階級青少年文化以此類極端的符號化方式來緩解自己身份認同的睏惑,等等。這些既充滿同情性理解又不乏批判性審視的闡釋,為我們深入理解形形色色的青年亞文化現象提供瞭生動的啓示性參考。
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伯明翰學派的一些學者開始綜閤運用意大利馬剋思主義思想傢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ci)的文化領導權理論、法國馬剋思主義哲學傢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識形態主體建構理論以及結構主義符號學等歐陸思想資源[如列維-斯特勞斯 (Claude Lévi-Strauss) 的“修補拼貼”(bricolage) 理論和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的神話符號分析方法等]。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和文化抵抗思想,對伯明翰學派産生瞭尤為重要的方嚮性影響。結閤符號學理論,他們逐漸將“青年亞文化”看作某些小眾的青年社群展現(represent)日常生活的“有意味的形式”,看作一套構成青年小眾群體特定生活方式的符號係統—“風格”(style)。風格不僅包括一個群體的衣食住行所用的各類“物”件,而且包括他們如何穿用這些“物”的方式,以及這類人共通而特定的言談舉止方式等符號要素。伯明翰學派將前麵提到的階級、代際、性彆或種族等帶有社會階層衝突張力的維度最終都融閤到瞭“風格”這一概念當中,努力從“風格”當中發掘那些處於弱勢的青年亞文化群體所蘊藏的“儀式抵抗”潛能。在對這種“儀式抵抗”進行充分肯定的同時,他們還提醒要時時警惕主流強勢群體和商業文化對青年亞文化風格的“收編”企圖。
從這一視角和立場齣發,伯明翰學派的青年亞文化研究就不再停留在對青年亞文化現象進行多重文化分析這一層麵,還試圖挖掘青年亞文化現象背後的“革命性”能量(能指)。工人階級青年亞文化群體的一些生活行為(如光頭、飆車等),就被伯明翰學派的一些理論傢闡釋成以象徵性的、想象性的方式進行的“儀式抵抗”和政治反叛。在伯明翰學派看來,自“二戰”以後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英國齣現的各種青年亞文化群體和亞文化現象,基本上都具有明確的“儀式抵抗”意識和身份認同訴求。也就是說,青年亞文化群體都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去挑戰和顛覆那些占支配地位的階級所擁有的文化“領導權”。他們甚至認為,“青年亞文化”是以想象的方式、象徵性的方式“解決”現實政治社會難題(由階級、代際、種族、性彆等現實不平等要素造成)的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雖然伯明翰學派也明白,青年亞文化群體進行的這種儀式性抵抗和符號性“抗爭”,並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秩序,但是他們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依然對青年亞文化群體寄予瞭過高的政治熱情,甚至讓人感覺有“過度闡釋”的嫌疑。
20世紀70年代末,伯明翰學派的代錶性人物迪剋·赫伯迪格(DickHebdige)在他的名作《亞文化:風格的意義》(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1979)當中,不無遺憾地承認:現有的所有亞文化風格的抵抗性,最終都會被時尚工業所收編或者商品化,都會失去戰鬥鋒芒而變成摺中的東西。正如《亞文化之後:對於當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After Subculture: Crit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Youth Culture)一書的編者所概括的,伯明翰學派在此既看到瞭青年亞文化的成就,也看到瞭其具有的不可避免的局限。顯然,伯明翰學派由於對青年亞文化寄予瞭太多的情感和政治期待,在麵對無法迴避的現實法則時難免會感覺有些無奈。無論如何,他們對於青年亞文化所做的這些富有開創性和想象力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瞭成人社會對於下層階級青年日常生活方式的看法,而且會啓發並激勵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研究者去探究青年文化獨有的奧秘和魅力。
“後亞文化”理論及研究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新自由主義在英美的盛行,隨著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以及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階級政治和階級意識在全球日漸衰落。而與此同時,全球性的消費模式卻更顯同質化色彩,符號消費和全球互聯網文化日漸勃興,齣現瞭日益多樣化的新的亞文化群體和亞文化“風格”。這些新的亞文化群體及其身份錶現行為在當今(後現代)社會呈現齣多重混雜的狀態,這使得伯明翰學派曾經堅持的階級亞文化、種族亞文化立場和闡釋麵臨嚴峻挑戰。
實際上,伯明翰學派提齣的亞文化抵抗模式從一開始就受到瞭來自於該學派內外學人的批評。這些批評意見至少可歸為以下幾個方麵。第一,這種研究忽視瞭女孩在青年亞文化群體中的存在和作用。提齣此類批評者正是伯明翰中心自己培養的女研究生們[以安吉拉·默剋羅比(Angela McRobbie)和詹妮·嘉柏(Jenny Garber)為代錶]。第二,這種研究本質化地假定瞭青年消費行為的政治抵抗性,甚至想當然地認為生活消費品一律都會被用於各種抵抗策略,從未真正考慮過青年人為瞭“娛樂”而扮演各種“亞文化”角色這一問題。第三,這種研究忽視瞭青年亞文化的流動性和變異性,沒有考慮到青年對於音樂和時尚的響應會隨著地域的變化而齣現一些本地化的變種。第四,這種研究沒有認識到媒體在亞文化和亞文化身份方麵的創造作用。第五,這種亞文化研究方法最緻命的缺陷,是它提齣的關於“青年”的定義有很大的局限性,隻把青年看作一個年齡範疇(16~21歲),認識不到“風格”的象徵意義,認識不到可以把青年轉變為意識形態範疇、精神狀態而不是生活特定階段的其他流行文化資源,因而無法解釋成年人對於“年輕態”(youthfulness)的保持和紀念。平心而論,對於伯明翰學派的這些批評有些地方不無刻意麯解伯明翰學派亞文化理論和政治追求的意味,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抓住瞭伯明翰學派亞文化研究模式的理論局限性。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青年亞文化研究已經進入瞭“後伯明翰時代”。如何解釋在新的媒介傳播和消費時代齣現的各種更富流動性、虛擬錶現性和混雜性的青年亞文化風格,確實是一個擺在當今青年研究者麵前的新課題。
有些學者開始藉鑒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資本”理論和硃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錶演”理論,對新齣現的各種青年亞文化現象重新進行探討,提齣瞭“亞文化資本”(subculture capital)、“場景”(scene)和“部族”(tribe)等一係列新的範疇。這些新範疇有助於從符號政治經濟學角度和群體交往空間方麵來解釋各種新興的混雜性亞文化風格。比如,薩拉·桑頓(Sarah Thornton)提齣的“亞文化資本”概念,就有助於揭示夜總會亞文化在商業娛樂文化時代所依賴的深層文化經濟邏輯。當“頹廢”和“玩酷”成為一種被時下青年所崇尚的“亞文化資本”時,會催生齣一係列與“頹廢”和“玩酷”相關聯的文化産業鏈(衣食住行及其展示方式)和“場景”(夜總會、酒吧、廣場、馬路,尤其互聯網)來。這意味著,“亞文化”成瞭某一群人的“消費”對象和“錶演”內容,有資格“消費”亞文化的人群可能形成一種共通的品位感和群體歸屬感。從這些觀點來看,“亞文化”幾乎成瞭亞文化消費和被消費的代名詞。這是不是也有些誇大和簡單化的嫌疑?這裏難道一點也不涉及經濟購買力、階級政治或階級文化趣味的問題?
到瞭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西方學術界確實齣現瞭“後亞文化研究”(post-subcultures studies)或“後亞文化理論”(post-subcultural theory)之類的提法。“後亞文化”概念的提齣,旨在闡釋亞文化人群在多變繁復的新傳媒時代和日益普泛的文化符號消費時代所産生的身份混雜現象,比如全球化網絡時代的虛擬社群身份、消費主義彌漫下抵抗意識的消解,等等。這些學者受後現代主義思想的影響,基本得齣瞭如下的判斷:芝加哥學派和伯明翰學派時期有比較明確區分的全球/本地、虛擬/真實、商業/獨立、日常/邊緣等二元區分層麵,在當下的符號消費時代已經不復存在,即使存在也變得極其交錯混雜,呈現齣高度變異的文化麵貌。在他們看來,伯明翰學派以前看重的那些因弱勢身份歸屬(如無産階級、青少年、有色人種、女性或同性戀等)而聚結在一起的亞文化群體,在身份極度混雜和變異的當下消費文化時代,已經失去瞭自身能夠依附的現實社會基礎,也就自然失去瞭進行“儀式抵抗”的“英雄精神”,甚至沒有進行“儀式抵抗”的可能。
在這些學者看來,當下的青年亞文化社群活躍於各種亦真亦幻的“夜總會亞文化”或亞文化“場景”當中[如銳舞派對(rave party)、網上衝浪族等],已經演變成為碎片化、混雜性、短暫性和“無關政治”的“流動身份”。c在這些新齣現的亞文化“場景”(如全球互聯網平颱)中“遊走”的流動社群以及他們詭異多變的“再現”方式,成瞭“亞文化”的“能指鏈”,像雅剋·德裏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所說的“蹤跡”(trace)一樣時隱時現,飄忽不定。這樣的“亞文化”概念當然缺乏伯明翰學派所說的那種“抵抗”型亞文化的反叛性,簡直成瞭身份政治的“自戀”式錶演。
顯然,這些有關“後亞文化”的錶述對身份的流動性和媒介的虛擬性給予瞭過度的關注,但它們卻無法解釋這些在虛擬化、碎片化的文化空間“遊走”的青年亞文化群體與自身真實的經濟政治處境之間的復雜聯係。一個隻顧上網衝浪、衣食無憂的“宅男”或“宅女”,一個崇尚綠色簡樸消費、騎自行車上街的後現代青年,一名在建築工地流汗流血但也有時上網聊天的青年民工,都可以用這種“後亞文化”符號消費理論來概括嗎?
青年文化研究的未來
通過以上對青年文化研究史的追溯,我們不難發現,“青年亞文化”一般都指社會階層結構框架裏不斷齣現的那些帶有一定“反常”色彩或挑戰性的新興社群或新潮生活方式。但是,一旦涉及對這些青年新興社群或生活方式進行研究的時候,不同時代、不同政治立場和不同學派的看法就有瞭很大的差彆,當然,也會有一定的關聯性和連續性。
早期芝加哥學派認為,亞文化一般是指無傢可歸或移居的街頭幫派、犯罪的黑社會以及同性戀等非正常群體,這些人通常在外觀上就與普通人有明顯的區彆。這種判斷雖然有簡單化之嫌,但發現瞭亞文化群體的一些外觀特徵,這與後來人們重視亞文化群體的符號化錶現有深層關聯。後期芝加哥學派開始關注主流社會、大眾媒介對於越軌青年“貼標簽”、越軌青年如何認知自身等深層問題,將社會階層、成長環境、認同危機等社會因素納入瞭對於青年亞文化群體的分析當中。而到瞭伯明翰學派時期,則將青年亞文化研究納入範圍更為廣泛的文化研究事業當中,得以從階級、代際、種族、性彆等維度來深入探討青年亞文化群體的符號錶達。他們強調瞭青年作為弱勢群體而麵臨的身份政治問題,並將青年亞文化看作是對各種大眾文化形式和主流社會“收編”行為的“拒絕”或“儀式抵抗”。他們發現這些“拒絕”和“抵抗”也有區彆,有些是明顯展現齣來的,如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英國朋剋族;有些並不完全是對抗的,如滑闆運動族、衝浪族等,而隻是為瞭剋服在社群當中日常生活刻闆模式所帶來的束縛。到瞭當今時代,伴隨著各種夜總會文化的崛起,伴隨著科技虛擬因素的大量滲入,亞文化群體日益多元化、短暫化,這一概念原來被賦予的“抵抗”意義、階層區分意義,在亦真亦幻、無處不在的符號消費王國,似乎都變得更難以落實瞭。因此,就有學者開始新造“後亞文化”這樣的概念,試圖重新掌握對這種充滿流動性、分裂性和混雜性的青年亞文化身份的理解。
可以看齣,一方麵是青年亞文化群體自身隨著社會政治結構發生的重大變化,另一方麵是主流成人社會在如何看待這種變化,而後者更值得關注。正如《亞文化讀本》(The Subcultures Reader)的編者肯·蓋德爾(Ken Gelder)所總結的那樣,人們對於亞文化的描述和研究“始終在以下兩種方法之間來迴徘徊:一方麵將亞文化社群描述為各種獨特的社交形式,另一方麵又把他們的身份復數化、模糊化;以前曾經認為他們的文化角色是單一的,具有一套為所有成員都認同的共同興趣和信仰,現在則更多強調他們的異質性、多方位滲透性、可變性和短暫性”。人們對待青年亞文化群體的這種復雜的態度,一直貫穿於芝加哥學派、伯明翰學派和當今的亞文化研究當中。
青年亞文化研究方嚮的變化(包括“後亞文化”的提法),實際上給我們提齣瞭許多值得重新思考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已經超齣瞭青年人群的範圍。比如,現代社會的人們如何看待自身與他者(群體)的關係,現代“個體”與新興的“社群”究竟會結成什麼樣的關係?在符號化消費日益擴散、個體與群體關係日益混雜交錯的當今時代,社會學傢、文化研究學者應該以何種態度、以何種方法對待自己的研究對象?對於新興的青年亞文化的界定和研究,如何在保持相對客觀分析的同時,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研究者的政治指嚮—比如對弱勢青年群體,對各種新興的、健康的反主流生活方式的關注、理解和支持?如何看待隨著全球化進程加深,尤其是互聯網傳媒深刻影響下齣現的諸多新興的全球性的青年文化現象—比如那些通過網絡聯動而興起的全球青年誌願者運動、全球青年環境運動?
諸如此類的問題,必將成為未來的青年文化研究應當麵對的研究對象。對於青年文化的研究既需要研究者能夠進入青年亞文化社群內部去感受和體驗,又要求研究者能夠與其拉開一定的距離,發現該青年亞文化社群不同於其他群體的異質性和指嚮未來健康生活方式的創新性。經曆瞭半個多世紀的努力,成人社會和大眾傳媒終於可以俯下身段去傾聽被他們無數次“描繪”過的“青年”發齣的心聲。那些行為乖張、穿著奇異、打架鬥毆甚至縱火搶掠的青少年,再也不能被媒體簡單描述為“民間惡魔”或“社會公害”,而應該得到真正的重視和對待。那些為數不多的、舉止平和、喜好新奇、崇尚消費或者抗拒科技、尋求儉樸生活的遍布於這個星球的青少年們,因其承受著身份日益碎片化、混雜性和流動性的風險,更應該受到研究者和成人社會的同情性理解和幫助。
從根本上講,對於青年文化的研究,都必然會涉及成人社會對於未來社會的理想期待和想象。這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學術工作,需要更多的人來參與和推動。因為,我們不隻是在對青年文化進行研究,還在塑造我們自己的未來。
2015年1月 修改稿 北京
用户评价
在我眼中,《青年文化比較:青年文化社會學及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青年亞文化》這本書,就像一座宏偉的知識殿堂,其嚴謹的學術架構與生動的文化描繪完美融閤,為我打開瞭青年文化研究的新視野。作者並非僅僅停留在對青年亞文化現象的簡單描述,而是將其置於青年文化社會學的宏大理論框架之下,深入剖析瞭其形成機製、社會功能以及代際互動。我尤其欣賞作者在比較美國、英國和加拿大青年文化時的細緻與獨到。他深刻地揭示瞭美國青年文化中那種強調個體自由、反叛精神以及消費主義的文化特質,以及這些特質如何影響瞭如嬉皮士、朋剋、嘻哈等亞文化的興起。在轉嚮英國時,他又巧妙地將青年亞文化與社會階層、曆史傳承以及政治立場緊密聯係起來,展現瞭英國青年文化中那種帶有疏離感和反抗精神的獨特魅力。而對於加拿大,作者則展現瞭其在多元文化主義影響下,青年文化如何形成一種包容、融閤且富有創造力的獨特風格。這本書讓我深刻認識到,青年亞文化並非是年輕人一時興起的玩鬧,而是他們在這個快速變化的社會中,為瞭建構自我認同、錶達情感訴求、甚至挑戰主流價值觀而進行的一種積極的文化創造。作者的論證過程嚴謹而富有說服力,案例分析生動形象,讓我仿佛置身於這些青年亞文化的現場,感受他們的活力與激情。
评分這本書帶給我的,是一種如同剝洋蔥般層層深入的驚喜。它沒有一開始就拋齣枯燥的理論,而是以一種娓娓道來的方式,將我們引入青年文化的奇妙世界。作者的文筆流暢自然,但字裏行間卻蘊含著深厚的學術功底。我尤其喜歡作者在描述具體亞文化時所使用的生動形象的語言,仿佛我身臨其境地體驗到瞭那些音樂節的狂歡、街頭的塗鴉藝術、以及那些充滿個性的時尚宣言。從美國街頭文化的影響力,到英國工人階級青年文化的獨特錶達,再到加拿大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形成獨樹一幟的青年群體,作者的筆觸細膩且富有感染力。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並沒有將青年亞文化簡單地歸結為“叛逆”或“非主流”,而是深入剖析瞭它們在特定社會經濟和文化語境下的産生根源。例如,書中對於美國青年文化中對自由、個人主義和反叛精神的強調,以及英國青年文化中對階級身份的敏感和對權威的挑戰,都分析得鞭闢入裏。更讓我驚喜的是,作者並沒有停留在簡單的比較層麵,而是深入探討瞭這些亞文化是如何影響社會價值觀、藝術風格、甚至政治思潮的。它讓我明白,青年文化並非僅僅是青少年群體的自娛自樂,而是社會變遷的重要推動力之一。讀完這本書,我對“青年”這個概念有瞭更立體、更豐富的認識。它不僅僅是一個年齡段的標簽,更是一種充滿活力、創造力和挑戰精神的社會力量。
评分我一直認為,理解一個時代的青年文化,就如同打開瞭一扇瞭解該時代社會變遷的窗口。《青年文化比較:青年文化社會學及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青年亞文化》這本書,正是這樣一扇明亮而寬廣的窗口。作者以一種社會學傢的審慎和學者的洞察力,深入剖析瞭美國、英國和加拿大這三個國傢在不同曆史時期湧現齣的各類青年亞文化。我被作者分析的深度所摺服,他沒有停留在對錶麵流行元素的羅列,而是深入挖掘瞭這些亞文化形成的社會根源、文化背景以及其所承載的意義。比如,在探討美國青年亞文化時,他不僅描繪瞭街頭文化的活力,更分析瞭其背後對個體主義、自由以及反抗權威的追求。轉嚮英國時,他又生動地展現瞭社會階層對青年文化的影響,以及如朋剋、摩絲等亞文化如何成為一種社會批判的載體。而對於加拿大的青年文化,作者則呈現瞭其在多元文化融閤背景下的獨特發展路徑。這本書讓我意識到,青年亞文化並非是簡單的模仿或追隨,而是青年群體在特定社會語境下,為尋找歸屬感、錶達自我、甚至挑戰現有社會秩序而進行的一種創造性的實踐。
评分這本書就像打開瞭一個潘多拉的魔盒,讓我看到瞭青年文化背後隱藏的巨大能量和復雜性。我一直以為自己對青年文化有所瞭解,但讀完之後纔發現,我所見的不過是冰山一角。作者將視角聚焦在青年文化社會學這個宏大的理論框架下,然後巧妙地將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具體青年亞文化作為例證,進行瞭一次細緻入微的解剖。這本書最讓我震撼的是其理論的深度和實踐的廣度。它不是簡單地羅列一些青年群體的服飾、音樂或者行為習慣,而是深入探討瞭這些錶象之下,青年如何通過建構和解構亞文化來尋找身份認同、錶達反叛、甚至挑戰主流社會規範。作者在分析美國青年時,對嬉皮士、朋剋、嘻哈等亞文化的曆史淵源、社會背景以及對主流文化的影響進行瞭詳盡的闡述,讓我對這些熟悉的群體有瞭全新的認識。接著,在轉嚮英國時,我又被其獨特的社會階層對青年亞文化的影響所吸引,比如光頭黨、摩絲等,這些亞文化不僅是時尚的錶達,更是社會分層和政治態度的反映。最後,加拿大青年亞文化的分析則展現瞭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獨特性,以及與美國文化的交織與區彆。整本書的論證過程嚴謹而富有洞察力,數據和案例的運用也恰到好處,使得理論不再是空中樓閣,而是紮根於現實的土壤。我常常在閱讀過程中停下來,反復咀嚼書中的觀點,思考這些分析對於理解我們身邊層齣不窮的青年現象的意義。這本書不僅僅是學術研究的成果,更是一本引人深思的社會觀察日記,讓我對“青年”這個概念本身産生瞭更深層次的理解和尊重。它也讓我意識到,我們不能用成人的視角去簡單地評判或忽略青年的文化實踐,而是應該用一種更加開放和包容的態度去理解他們的世界。
评分我通常不太喜歡閱讀那些過於學術化的書籍,總覺得會像嚼蠟一樣枯燥乏味。但這本書,卻徹底顛覆瞭我的看法。作者在《青年文化比較:青年文化社會學及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青年亞文化》中,用一種極其吸引人的方式,將復雜的社會學理論與生動的青年文化現象巧妙地融閤在一起。閱讀的過程,就像是跟隨一位經驗豐富的嚮導,深入探索瞭美國、英國和加拿大三個國傢不同青年群體的文化圖景。作者對青年亞文化的分析,不僅僅停留在錶麵,而是深入挖掘瞭它們形成的社會根源、文化基因以及對個體和社會的影響。我特彆欣賞作者在描繪不同國傢青年文化時的細膩之處。例如,美國青年文化中那種強烈的個體主義和對自由的追求,如何催生瞭諸如嘻哈、滑闆等亞文化;英國青年文化中,那種對傳統和權威的挑戰,又如何體現在朋剋、哥特等風格中;而加拿大的青年文化,則展現瞭其在多元文化融閤中的獨特性。讓我驚喜的是,作者並沒有將青年文化簡單地臉譜化,而是深入探討瞭其背後隱藏的社會結構、經濟因素以及代際關係。這本書讓我認識到,青年亞文化並非是年輕人一時興起的玩鬧,而是他們在這個快速變化的社會中,尋求身份認同、錶達自我、甚至建構社會關係的重要途徑。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對“青年”這個群體有瞭更深刻的理解和尊重,也對這個不斷發展的世界有瞭更宏觀的認識。
评分我原本以為,關於青年文化的研究,無非是些關於潮流服飾、流行音樂的簡單羅列,但《青年文化比較:青年文化社會學及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青年亞文化》這本書,卻以一種我未曾預料到的深度和廣度,揭開瞭青年文化的神秘麵紗。作者不僅是一位齣色的社會學傢,更是一位敏銳的文化觀察者。他以美國、英國和加拿大這三個具有代錶性的國傢為切入點,深入剖析瞭不同社會語境下青年亞文化的形成、發展及其演變。我尤為佩服的是,作者並沒有僅僅停留在對現象的描述,而是將這些現象置於宏大的社會學理論框架下進行審視。例如,他分析瞭美國青年文化中對個人主義、自由和反叛精神的強調,以及這些特質如何在街頭文化、搖滾樂等亞文化中得到體現。在探討英國青年文化時,他又著重分析瞭社會階層、曆史傳統如何塑造瞭像光頭黨、摩絲等具有鮮明社會標簽的亞文化。而加拿大,則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展現瞭青年文化融閤與創新的獨特魅力。這本書讓我認識到,青年亞文化並非是孤立的個體行為,而是青年群體在特定社會、經濟、文化環境中,為瞭尋求身份認同、錶達自我、甚至進行社會批判而采取的一種復雜而有意義的文化實踐。作者的分析嚴謹而富有洞察力,數據和案例的運用也恰到好處,使得原本抽象的理論變得生動而具象。
评分我一直對青年文化抱有濃厚的興趣,但往往止步於一些淺顯的瞭解,比如他們喜歡什麼音樂,穿什麼衣服。而《青年文化比較:青年文化社會學及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青年亞文化》這本書,則徹底改變瞭我對青年文化的認知。作者用一種非常社會學的方式,為我打開瞭一個全新的世界。他不是簡單地羅列青年群體的特徵,而是深入分析瞭這些特徵背後所蘊含的社會、經濟、政治因素。我尤其欣賞作者在比較美國、英國和加拿大青年文化時的深度和廣度。美國青年文化的那種自由、反叛、以及對個人主義的極緻追求,如何催生瞭諸如嘻哈、滑闆等亞文化,我從中看到瞭美國社會特質的縮影。而英國青年文化,則在作者的筆下,呈現齣一種與階級、曆史傳承緊密相連的獨特氣質,比如光頭黨、摩絲等,它們不僅僅是時尚,更是社會身份的象徵。加拿大青年文化則在多元文化的土壤上,展現齣一種融閤與創新的活力。這本書讓我明白,青年亞文化並非是“非主流”的代名詞,而是青年群體在特定社會曆史背景下,為瞭尋找身份認同、錶達內心訴求、甚至挑戰現有秩序而進行的有意義的文化實踐。作者的分析嚴謹而富有洞察力,案例豐富且具有說服力,讓我對青年群體以及他們所處的社會有瞭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讀完《青年文化比較:青年文化社會學及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青年亞文化》,我感覺自己的世界觀被徹底刷新瞭。這本書不是那種輕鬆易讀的消遣讀物,它更像是一本需要靜下心來,帶著批判性思維去啃的學術著作。作者顯然在這上麵花費瞭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從社會學的基礎理論齣發,層層遞進,將青年文化的形成、發展、以及它所承載的社會功能一一呈現。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不同國傢青年文化時的差異化視角。比如,美國青年亞文化常常被描繪成一種充滿活力的、個體主義的、甚至帶有商業色彩的存在,而英國的青年亞文化則似乎更與階級、政治立場緊密相連,帶著一種天生的疏離感和反抗精神。加拿大的部分則展現瞭其獨特的融閤性和包容性,在吸收美國文化影響的同時,也保持著自己獨立的特色。書中對“亞文化”這個概念的界定和分析,也讓我受益匪淺。它不再僅僅是“非主流”的代名詞,而是青年群體在特定社會曆史背景下,為瞭應對各種社會壓力、尋求歸屬感、以及錶達自我而主動建構的一種文化空間。我特彆對書中關於青年與消費文化、青年與媒介傳播、以及青年與代際衝突的分析印象深刻。這些章節的討論,讓我能夠更清晰地看到,青年文化是如何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又如何反過來作用於社會變遷的。作者並沒有迴避青年文化中的負麵現象,比如暴力、毒品等,而是以一種客觀的態度去分析其根源,並嘗試從社會學的角度去解釋。這種審慎而全麵的分析,使得這本書的價值遠超一般的青年文化讀物。它提供瞭一個看待青年群體的全新視角,讓我能夠更深刻地理解他們,也更理解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
评分我一直以為自己對青年文化有著相當的瞭解,畢竟我也曾經是青年,也經曆過那個充滿迷茫與探索的年紀。然而,《青年文化比較:青年文化社會學及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青年亞文化》這本書,狠狠地打破瞭我固有的認知。它不是那種一本正經的教科書,也不是獵奇的八卦雜誌,而是將社會學理論的嚴謹與對青年文化的敏銳洞察完美地結閤在瞭一起。作者的分析非常到位,從宏觀的社會結構入手,到微觀的個體行為模式,層層剝離,將青年亞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規律展現得淋灕盡緻。我尤其贊賞作者在比較美國、英國和加拿大青年文化時的獨到之處。美國那種強調個人主義、崇尚自由的文化背景,如何孕育齣五花八門的流行亞文化;英國那種根植於社會階級和曆史傳統的青年文化,又是如何帶著一種特有的疏離感和反叛色彩;而加拿大,作為一個移民國傢,其青年文化又呈現齣一種怎樣的多元融閤與獨特魅力。這本書讓我看到瞭,青年亞文化不僅僅是錶麵的衣著、音樂或發型,它更是青年群體在社會變遷中,尋找身份認同、錶達內心訴求、甚至挑戰現有秩序的一種復雜而深刻的文化實踐。作者對這些亞文化背後所蘊含的社會、政治、經濟因素的分析,讓我對青年群體有瞭更深刻的理解和尊重。它促使我反思,我們是否對青年文化存在著片麵的、甚至帶有偏見的認知。
评分拿到《青年文化比較:青年文化社會學及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青年亞文化》這本書時,我抱持著一種探究的心態,但閱讀過程遠超我的預期。這不僅僅是一本關於青年文化的書籍,更是一次關於社會結構、文化演變以及人類身份認同的深刻反思。作者的分析視角非常獨特,他沒有簡單地將青年文化視為一種孤立的現象,而是將其置於青年文化社會學的宏大理論框架之下,並以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青年亞文化為具體案例,進行瞭細緻入微的比較研究。我尤其贊賞作者在分析美國青年亞文化時,對嬉皮士、朋剋、嘻哈等群體背後所蘊含的反叛精神、消費主義批判以及身份焦慮的深入挖掘。在轉嚮英國時,他又巧妙地將青年亞文化與社會階層、工人階級文化以及曆史傳承聯係起來,展現瞭英國青年文化獨特的社會屬性。而對於加拿大,作者則展現瞭其在多元文化主義影響下,青年文化如何形成一種包容、融閤且充滿創造力的獨特風格。這本書讓我深刻地意識到,青年亞文化不僅僅是服飾、音樂或生活方式的某種組閤,更是青年群體在復雜社會環境中,為瞭建構自我認同、錶達情感訴求、甚至挑戰主流價值觀而進行的一種積極的文化創造。作者的論證過程嚴謹而富有說服力,案例分析生動形象,讓我在閱讀過程中,仿佛置身於這些青年亞文化的現場,感受他們的活力與激情。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