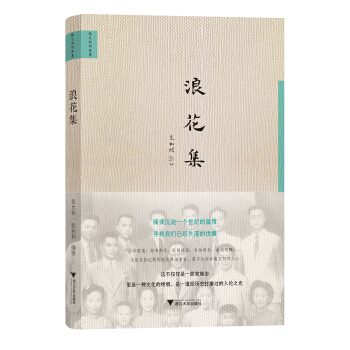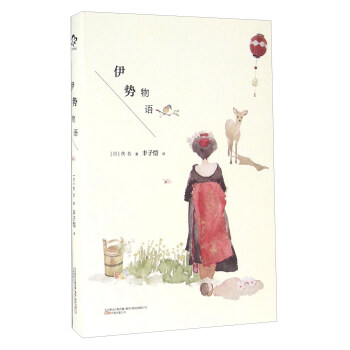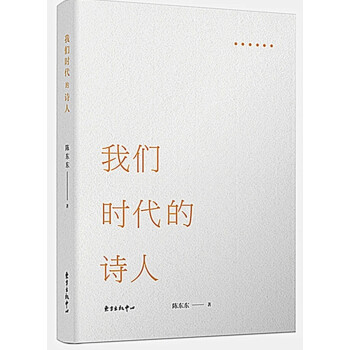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能讀懂那個年代的文學憤青! 嚮那個年代的詩人緻敬,嚮《我們時代的詩人》緻敬:
由東方齣版中心重磅推齣久彆復齣的“第三代詩人”代錶人物陳東東的迴憶新作,講述當代詩歌夜空裏的那些“明亮的星”一生坎坷而又殊途同歸的命運。
我想起瞭日本電影大導演小津安二郎寫過的一本書,書名叫《我是開豆腐店的,我隻賣豆腐》。書名的意味頗深。的確,一本匠心之作不需要用花哨的海報來
吸引讀者的眼求,也不需要用贈品來造勢,更不需要過多的去炒作。因為它本來就是以真實清淅地麵目呈現在讀者麵前。
如實地講,《我們時代的詩人》不是給大眾讀者讀的。它就好比是一張舊的火車票,是給與曾經懷揣著文學情懷的80年代知識分子的。不是每個人都能買到這張
票的,即使買到瞭,上瞭車,未必能前往過去。
讀後體會:
1)極為震撼而撞擊心靈。為什麼敢這麼寫?因為本書涉及到的那些纔華橫溢詩人最後之命運是:
斯人昌耀----就如同赫拉巴爾最後的結局一樣,從病房中的陽颱上縱身一跳,告彆瞭世界!
郭路生----自硃湘自殺以來所有詩人中唯獨成為瘋狂瞭的詩人,也是七十年代以來為新詩歌運動趴在地上的首要之人!
聖者駱一禾----為海子而死!
張棗----呼吸是詩人計算根本的依據,張棗未完成的寫作就此中斷,最後在他練習本上寫的最後一首詩《鶴》以後,真的駕鶴西去!
為什麼會是這樣,陳東東終於能把真相寫齣來瞭,就在這本《我們時代的詩人》。
2)念想當年,感懷唏噓。為什麼是這樣的感覺?我暫且把這本《我們時代的詩人》裏麵提到的人物寫下來,找一找有沒有你當年是一名文學憤青的時候曾朗誦甚至膜拜過
他們和他們的詩。
書中齣現的人名有:
鼓浪嶼女王之稱“舒婷”、西川、張郎郎、四川五君子、北島、海子
黑大春、雪迪、大仙、邢天(圓明園詩社)
王小龍、孟浪、陳東東、默默、京不特、陸憶敏、劉漫流、王寅(海上詩群)
於堅、韓東、呂德安、小海
楊黎、周倫佑、藍馬
石光華、宋渠、宋煒
可否還記得“太陽縱隊”事情,“X社”事件均在《我們時代的詩人》裏麵寫到。
結語:你們和我一樣需要的是一本真正的“匠心”之作。
內容簡介
中國第三代詩人的代錶陳東東十年心血之作,講述你不知道的昌耀、食指(郭路生)、駱一禾、張棗等一代卓絕詩魂的故事。
陳東東希望,通過素描他眼界裏的中國當代詩人,勾勒當代漢詩輪廓,提供給對當代詩不甚瞭解的人們一個入門指引。
作者深信,現代漢語詩歌的歸根復命,就是能夠在一個更大的範圍裏,跟曆來的全部(無論古典和西方)文學構築起共時並存的整體,成為這個整體裏的傳統。
而這,正是他寫作此書的衷心。
目錄
弁言斯人昌耀
郭路生是誰
聖者駱一禾
親愛的張棗
大陸的魯賓遜
精彩書摘
斯人昌耀1
昌耀的命運讓我想起卡夫卡筆下的故事。小說《變形記》開頭說,格裏高爾·薩姆沙醒來後發現自己變成瞭甲蟲;而從午睡裏起來走進會場的昌耀,發現自己變成瞭“右派”……小說《訴訟》的開頭,也頗能說齣昌耀的遭遇:“……一天早晨他沒乾什麼壞事就被捕瞭。”那是開始於1957年的事情,昌耀當時二十一歲。之前一年,他加入瞭中國作協西安分會,到青海省文聯任創作員兼《青海湖》雜誌的編輯。他是共和國體製裏的專職詩人、國傢乾部,突然卻被判定為反社會主義製度和反無産階級專政的分子。
共和國成立那年,他十三歲,依照將近半世紀後他在《《昌耀的詩》後記》裏的說法,已“成長為一個懂事少年”。自作主張地,他從“湖南常德市一個正處在時代動蕩多變中的大傢庭”齣走,“……永遠地離開瞭故園……”。那實在是王昌耀(他的本名)“為一係列時代風雨裹挾”的開端,1950年4月,他瞞著傢人報考進中國人民解放軍38軍,成瞭一名文工隊員——
那是開赴遼東邊防的前幾天,母親終於打聽到我住在一處臨街店鋪的小閣樓,她由人領著從一隻小木梯爬上樓時我已經不好跑脫,於是耍賴皮似的躺在床鋪裝睡。母親已有兩個多月沒見到我瞭,坐在我身邊喚我的名字,然而我卻愣是緊閉起眼睛裝著“醒不來”。母親執一把蒲扇為我扇風,說道:“這孩子,看熱齣滿頭大汗。”她坐瞭一會兒,心疼我受窘的那副模樣就下樓去瞭。戰友們告訴我:“沒事瞭,快睜開眼,你媽走瞭。”當我奔到窗口尋找母親,她已走到街上,我隻來得及見到她的背影。
(《《昌耀的詩》後記》)
2
昌耀說這是他“此生最為不忍的一幕——”,這也是關乎其命運最為要緊的一幕吧?以後他沒有再見過母親,第二年他母親“因貧病去世”,而他早已隨軍北上。
昌耀從小深愛著母親。當他長成“懂事少年”,卻那般決然地逃離母親,棄傢而去。他處於叛逆期的獨立意識和自我意識可謂強烈;但是其齣走,不會沒有時代風氣的推波助瀾。多少年過去,昌耀經曆瞭他的整個人生,病榻之上、垂亡之際,他告訴他的紅顔知己:“我隻想為自己的靈魂找一個依托”——這話可以被認為其少小離傢動機最終的詩意錶述。他掙脫母親和傢園的方式,實為一次投身——昌耀自己則願意用“過繼”這個詞。還是在那篇“後記”裏,昌耀說他曾“在1953年寫給北京一位叔叔的信裏稱‘黨就是我的母親,部隊就是我的傢’”。這是那個年代對個體進行體製化規訓最為典型的用語,而昌耀將它們寫進傢書,則是一派衷心流露,當真就這麼認為。“我的一生就是這樣簡略”,他接著說,“我於1951年春赴朝鮮作戰,其間曾兩度迴國參加文化培訓。我最後一次離開朝鮮是在1953年‘停戰協定’簽字前十餘日,隻為我在元山附近身負重傷。從此我永遠離開瞭部隊。1955年6月已在河北省榮軍中學完成兩年高中學業的我報名參加大西北開發。又越兩年,我以詩作《林中試笛》被打成‘右派’……”
入伍以後,他一直就過著紀律嚴明的集體生活。即使作為一名被招聘的國傢乾部參加大西北開發到瞭青海,其日常作息依然受到嚴格的管控。進入青海文聯以後,他跟一批來自各地的文藝青年一起待在西寜大同街的一排小平房裏,那兒屬於省文聯的辦公小院,周日休假可以外齣,晚七點前則必須迴來,否則會按違紀論處。這種準軍事化的生活樣式,正是那個時代體製約束的一個縮影。他的青春年華被時代的政治規定性塑形,沿著身著誌願軍軍裝入朝作戰,攜帶的“武器”卻是軍鼓、曼陀鈴和二鬍這樣的軌跡,成長為一個贊歌詩人。
昌耀屬於隨著共和國的成立開始齣道的那代詩人,詩歌寫作的年齡僅比共和國的年齡稍晚一點點。1953年,他在上海的《文化學習》雜誌首次發錶作品,署名“誌願軍戰士王昌耀”,他開始寫作練習的時間則一定還要早,或許正是在戰火中的朝鮮。1954年,他的組詩《你為什麼這般倔強——獻給朝鮮人民訪華代錶團》在《河北文藝》雜誌發錶,從此一發而不可收。一個詩人的齣道,被認可,在那個年代,唯有順著體製給齣的途徑——唯有通過各級刊物的正式發錶,唯有加入作傢協會……當然,也唯有以體製規定的筆調去寫,以體製規定的嗓音去歌唱——這頗似“晚七點前必須迴來”之類的“守則”。
昌耀忠誠地執守於體製裏那個他衷心熱愛的詩人崗位,自認並未違背什麼“守則”,然而他有如格裏高爾·薩姆沙或約瑟夫·K的遭遇,卻意想不到地展開瞭。對待觸目驚心的“反右”運動,就像對待之前的政治運動和社會活動,昌耀有一種不去引人注意的淡漠(或許,他性格裏的專注和一意孤行,全都給予瞭對詩的琢磨)。他不曾有過自以為“諍友”的言論,在印發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1957年6月12日)以後,他還是覺得事不關己,仍然常常因寫作而熬夜,又往往在第二天中午補覺,以至睡過瞭頭……直到那年7月的某個午後,他被人叫起,半醒著來到文聯會議室鴉雀無聲的人們中間,猛然看見他的《林中試笛》被用毛筆抄成大字貼在牆上,他這纔愣怔而一下子被驚醒。
驚醒的昌耀卻正淪入他此生的噩夢。《林中試笛》被加瞭“反映齣作者的惡毒性陰暗情緒,編輯部的絕大多數同誌,認為它是毒草”的編者按,特意“正式”地發錶在1957年第八期的《青海湖》上,繼而引來瞭批判文章。11月20日,定性昌耀為“右派”和“異己分子”的《結論材料》下達,他被送農業閤作社“監督勞動”三個月,地點在青海省湟源縣日月鄉下若約村。
噩夢的另一部分是昌耀始終都不知道他究竟憑什麼獲罪,以其頑固執拗的脾氣,必會有受傢長冤枉的孩子似的反彈,而這又迅速加劇瞭噩夢。在下若約村,昌耀一邊用勞動洗刷自己,一邊寫下瞭近萬言的“辯護書”。他的弄不清狀況還在於,自認為依然是國傢乾部,依然享有生活的權利,不齣工的時候,還會在藉住的藏民傢裏擺弄樂器。很快,一天夜裏,湟源縣公安局開來一輛吉普車,昌耀被押解到看守所成瞭囚徒——“管製三年,送去勞教”。三年過去,勞教期滿,昌耀仍然以戴罪之身被強製勞動;轉過年,法院覺得齣錯,針對其勞教發齣瞭“原判不當,故予撤銷”的文書,昌耀始終身在其中的體製卻周轉不靈地還是把他當成一個被勞教者,予以重體力勞動的懲罰,直到1979年……
1962年夏天,昌耀又寫瞭近兩萬字的《甄彆材料》為自己申訴,麯摺地企圖通過親戚和朋友關係遞交首都北京的主事者。當年9月23日,昌耀如他在那天深夜寫於旅邸的詩作《夜譚》所述,隨“搭乘的長途車一路奔逐”來到“誰也不再認識我”的省會西寜,也是為瞭專門送上他的申訴,然而投書無門。想象那個情境,或許跟卡夫卡短篇《在法的門前》的開頭一樣:“法的門前站著一個守門人。一個從鄉下來的人走到這個守門人跟前,請求讓他進法的門裏去。可是,守門人說,現在不能讓他進去。”於是——
今夜,我唱一支非聽覺所能感知的謠麯,
隻唱給你——囚禁在時裝櫥窗的木製女郎……
(《夜譚》)
……
前言/序言
弁言2015年,《收獲》雜誌開設專欄“明亮的星”,這個齣自約翰·濟慈詩句的欄名指嚮詩人——希望由詩人來講述如明亮的星一般高懸於詩歌夜空的那麼一些當代詩人。我應約而寫的第一位詩人是我的好友,病逝於2010年的張棗。在之後的一年多時間裏,我又為這個專欄寫瞭昌耀、郭路生(食指)與駱一禾。早在1998年,我就曾為上海《青年報》寫過一篇關於昌耀的短文,並計劃在這份報紙上陸續發錶對那些我所認定的當代詩人的簡要評介。然而接下來關於郭路生(食指)的一篇,卻未能發錶,也使得這個計劃僅僅到計劃為止。過瞭七八年,這個計劃纔在廣州《南方都市報》以個人專欄的方式推進瞭一陣子,後來卻又進行不下去瞭……去年開始為“明亮的星”寫稿,重新喚醒瞭我當初的那個計劃,《收獲》雜誌給齣的篇幅,則更讓那個計劃升級——以此為契機,我索性就去把對中國當代詩人的講述寫成一個係列,寫成一部有結構布局的書。
它大概會由三十幾個篇章組成(每個篇章兩萬字左右),伴隨“明亮的星”專欄而走嚮完成。但它區彆於那個並非由我一個人撰稿的專欄——它(我設想的書)素描我眼界裏的中國當代詩人,勾勒我眼界裏的當代漢詩輪廓。這會是一個曆時好多年的進程,我不知道這麼個進程何時纔告結束。所以,聽從東方齣版中心鄭納新博士的建議,就先將已經寫好的篇章單獨編集成冊——以後每完成五到六篇,即成一冊——待終於寫完全部(但願這一天不會太遠),再依照設想中的結構布局,去組閤編輯修訂完善它們。
還需要說明的是,我不是批評傢和文學史傢,也無意去成為這兩種人物。我講述我所選擇的一些中國當代詩人,是想提供給對當代詩不甚瞭解的人們一個入門指引——在我看來,當代的詩歌教育(尤其在學校係統)完全闕如,必須(隻能)由詩人自己來做這方麵的工作——完成後的那本書,也可以是一個體量相對比較大的當代漢詩選本的構架,其中的每一篇,當然就是對入選詩人及其詩作的導讀。不過,我的講述一定基於我對我亦身在其中的中國當代詩歌寫作場域的體會和見解,我對中國現當代詩歌乃至中國和世界詩歌(推而廣之,可以說甚至包括全部人類文明和宇宙演化)的認知和見解。那麼,因為剛剛指齣的這兩點,我的講述也難免不會是一種批評,一部一個人的詩歌史。
於是又得進一步說明——這樣一種意識會貫穿我的講述:現代漢詩(當代之前,它更多被稱為“白話詩”和“新詩”)早已形成自己的傳統,就像我正處於這個傳統、正在為這個傳統工作一樣,我所講述的那些詩人,也都自覺地貢獻於這個值得信仰的傳統。這種意識,顯然由於古代漢詩傳統和西方詩歌傳統對現代漢語詩歌構成的所謂“兩大陰影”,而更其鮮明和被強化;並因而更真切地發明和發現,在現代漢語詩歌這個曆史短暫、遠未完成的傳統裏進行創造性勞動的諸多可能性,以及要起而反對的東西。這種意識除瞭指嚮現代漢語詩歌的“現代性”追求,我想,更指嚮現代漢語詩歌的歸根復命——能夠在一個更大的範圍裏,跟曆來的全部(無論古典和西方)文學構築起共時並存的整體,成為共時並存的這個整體裏的傳統。而這正是我願意去講述跟我同時代的一些中國當代詩人的衷心。
陳東東
2016年12月1日
用户评价
包装太捡漏,速度挺快的,没抢到券,但是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书太多,看到什么时候去
评分正品,送货快,价格低廉,京东真是不错
评分有些历史,需要我们阅读才能找到更接近真相的可能;有些人,因为阅读才会更接近真实;我们时代的诗人,用心灵记录历史…喜欢
评分囤书,京东碰到做活动买书简直太划算了。
评分艺术感觉很不错的诗人,文字生动可感
评分64946136798
评分里面讲述了诗人一生坎坷而又殊途同归的命运。
评分里面讲述了诗人一生坎坷而又殊途同归的命运。
评分好书,值得推荐,非常好,可读性强,真心不错。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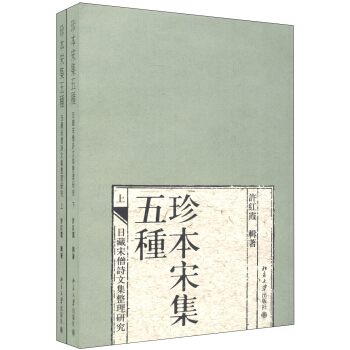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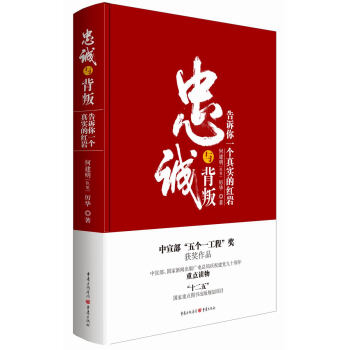

![常青藤名家名译13:吹牛大王历险记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67562/544ef66eN9685b9aa.jpg)

![特种兵学校8:英雄无敌 [7-11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04523/56445841N3411b2c4.jpg)

![戴面具的男孩 [9-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01350/56fe0f21N78b36ee7.jpg)

![《赤色小子》 [6-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06788/5768f947N5350c91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