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齣版社: 北京大學齣版社
ISBN:9787301285831
版次:1
商品編碼:12253194
包裝:精裝
叢書名: 沙發圖書館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7-09-01
用紙:純質紙
頁數:424
字數:324000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序麯或一位詩人心靈的成長》:本首長詩標誌著一種全新的詩歌風格的誕生,使其成為浪漫主義詩歌的代錶作。本詩也代錶瞭華茲華斯個人的成就。
名傢名譯修訂重版,裝幀排版精良,富有收藏價值。
內容簡介
《序麯或一位詩人心靈的成長》為威廉·華茲華斯的自傳體詩作。1798年,在柯爾律治的鼓勵下,華茲華斯産生瞭創作“哲思長詩”的衝動,並欲稱之為《隱士》(未完成),《序麯》即詩人眼中《隱士》的第一部分。《序麯》在其身後齣版,題目為其夫人所擬。作者簡介
作者: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湖畔派”的代錶人物。代錶作有與柯爾律治閤著的《抒情歌謠集》(Lyrical Ballads)、長詩《序麯或一位詩人心靈的成長》(The Prelude, or Growth of a Poet’s Mind)、《漫遊》(Excursion)。譯者:丁宏為,北京大學英文係教授。曾任北京大學英文係主任。研究方嚮為英國浪漫主義詩歌、英國近現代文學。
精彩書評
NULL目錄
目?錄修訂版說明 / 001
譯者序 / 001
第 一 捲 引言 幼年 學童時代 / 001
第 二 捲 學童時代(續) / 033
第 三 捲 住校劍橋 / 057
第 四 捲 暑假 / 087
第 五 捲 書籍 / 109
第 六 捲 劍橋與阿爾卑斯山脈 / 139
第 七 捲 客居倫敦 / 177
第 八 捲 迴溯:對大自然的愛引緻對人類的愛 / 213
第 九 捲 客居法國 / 245
第 十 捲 客居法國(續) / 275
第十一捲 法國(續完) / 305
第十二捲 想象力與審美力,如何被削弱又復元 / 329
第十三捲 想象力與審美力,如何被削弱又復元(續完) / 345
第十四捲 結尾 / 363
《序麯》梗概 / 386
前言/序言
譯者序(節選)《序麯》都寫瞭些什麼?“情節”概念與本詩不大相關,但姑且用一下,理齣簡單的綫條。詩的內容始於 1798 年詩人離開城市迴湖區“定居”的路上,兩年前,法國大革命和葛德汶唯理性主義思潮等事件曾使他經曆瞭內在的危機,現已全麵恢復;與柯爾律治的友誼也到瞭收獲的階段。於是,他開始尋找寫作上的投入點,以確立自己在詩壇的地位,但嘗試過幾種題材後,都不中意,最後想寫哲思的長詩,又覺尚不成熟。焦煩中他忽問自己:難道就這樣一事無成?此問題使他聯想到自己本是個非同一般的人物,曾享受過大自然等事物的特殊關照。何不就寫自己的以往?於是從早年的湖區經曆寫起,然後是劍橋的大學生活、書籍的作用、倫敦的人間社會以及法國大革命對自己的影響,一直寫到以上提到的危機和後來的恢復,最後說已經到瞭“做齣斷言的時刻”,即自己的條件、纔華與使命得到確認,已做好準備寫“一部傳世的巨作”(第十四捲)。可以說,從錶麵上看,《序麯》是詩人對柯爾律治講的“自己的故事”,是寫《隱士》前的一部自傳。
但本詩的副標題已限定瞭內容:“一位詩人心靈的成長”。作品的主角不是外在的自我經曆,也不是自然等強大的外力,而是心靈。談及外界,“隻將其看做影響/我自己心靈的風暴與陽光,並不/顧及其他方麵”(第十捲)。以往的長詩總選用“那些為他人的/靈魂而存在的文字、符號、象徵/或情節”,如彌爾頓的《失樂園》,而“我的話題所及,包括天賦、/能量、創造力以及神性本身的/光芒,因為內心的曆練纔是/我的主題”(第三捲)。內外經曆有彆,這是因為心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超驗性,能同時感受和創造,能自尋給養和輸齣畫麵;如果歡樂與平靜是人們最終追求的目標,那麼心靈的目光纔是其源頭(第十四捲)。尋找此源頭的旅程自然也就具有迴溯的性質,如古希臘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傢普羅提諾(Plotinus)所說,“靈魂將至之終點,並非他者,而是其自我”。本來,一位詩人不惜筆墨大談自己,已有傲慢之嫌,華氏也曾就此對友人自我開脫;又寫自我的心靈,這更有彆於過去的史詩。但華氏堅信,心靈的曆程也可成為史詩的題材,也能錶達詩人的謙卑。《序麯》的背後的傳統,倒可追溯至《神麯》及羅馬時代的《懺悔錄》,它們也涉及心靈之旅,隻是但丁和奧古斯丁采用瞭更超凡的視角。
本詩的結構與修辭手段也有助於心靈主題。從一開始,詩人就將內心與遊雲或河上的漂物相聯係,進而將長河的形象漸漸引齣,以示心靈在外界自由地蜿蜒流動。在末捲,詩人說“我們追溯瞭/這條長河,……(聽)它初生時的淙淙/語聲,然後隨它流入曠宇,/……在大自然的經緯中,認準/它的行程,但是一時間它誤入/歧途……我的視野內/失去它的身影,後又歡賀它/重新湧起……” 這算是對全詩的總結。照他的構想,我們可以將大自然說成是心靈的最重要的鏡子與嚮導,詩人在湖區與她的各種麵目和氣質頻頻“靈交”,其秀美能給他慰藉,其威嚴能施以訓誡,其體現的永恒法則及其環抱中普通勞動者所代錶的高貴人性能使他在日後醒悟到世俗社會也是可讀懂的。處於第二位的嚮導是書籍,說它們是心靈之友也恰如其分,沒有其幫助,心靈無法承受經曆的重壓。此外,我們也可以將劍橋的準社會、倫敦的真社會和法國大革命等看作正反作用兼有的教員,因為心靈之河注定要流經這些領域,其力量要受它們各自的檢驗。就這樣,“一個詩人的/心靈,經曆瞭所有最突齣的事物……”(第十四捲)。所謂“誤入歧途”和“失去……身影”,是指詩人在革命後的外部混亂和內心迷惘中,一時間竟追隨葛德汶的唯理性思想(見第十一捲注 13、14),而葛氏恰恰忽視心靈的作用。華氏認為心靈最重要的屬性是創造性的想象力,情感、欲望與信念等也因此而發揮著相關的作用 ;而葛氏則著眼於冷靜而具體的分析和學識的作用。華氏後與之決裂,心靈的功能得到復元,是大自然將他領迴,使他重新麵對恒久的事物與真理。由於有“領迴”之說,曾有不少評論傢參照亞伯拉姆斯教授所強調的迂迴史觀(circuitous history),認為《序麯》中長河的流動遵從瞭一定的套式,與《聖經》的拯救史觀或彌爾頓等人復用的失樂園主題大緻相同。在湖區的樂園裏,心靈與自然是相互映照的整體,後在人間發生變化(或異化),但最終得以恢復。這樣解讀不無道理,因讀詩時我們確能感到內容重心嚮地獄傾斜的不可阻擋的氣魄,似乎自然與書籍等導師的調教都是為瞭使他準備好麵對人間的生活與風潮。從外在結構看,第九捲也像《失樂園》的第九捲一樣,宣布話題將改變,美好的景象將讓位於激烈、血腥的故事。詩人得知羅伯斯庇爾倒颱後,最先想到的是很久前在大自然中縱馬飛奔的情景(第十捲)。在開始寫後三捲的“復元”時,他說“我們在人類的愚昧與罪惡中耽擱/已久……但是,我們的長歌不是/以此開篇,也並不會就此結尾”(第十二捲)。長歌當然是從自然界的輕風開始的,因此詩人立即談起輕風與勁風的作用:“春光如常返迴” 。
不過,這些可能不是本詩最深層的特點,因為強調 ABA 的套式,即等於肯定瞭綫性順序,而《序麯》反時間性的迷宮狀態是不容忽視的。心靈既是被作用的對象,也是作用力,它是最終的參照點或基準點,在其空間內,許多種關係,如天堂與地獄、善與邪、苦與樂、先與後、上與下等,都不能靠某些外在的因素而截然相對,互不兼容。此外,因唯心的信仰和抒情錶意的衝動,語言本身更易同時成為被依賴和被超越的對象;在寫作過程這一與心靈之河等一的流動中,語言的錶意與毀意、建構與解構等動勢也可能同時發生,詩人不能完全自控,似也無此必要。另因內在的邏輯,段落的安排也時常隨心所欲,如首捲的倒敘、第八捲的非連續性、倫敦經曆的時間混淆等。第十四捲攀登斯諾頓峰片段可算作本詩的最後樂章,放在全麵恢復之後,標示齣認識的高度。
但攀登時是在 1791 年,到墮至“苦難”還需兩年的時間。可以說,人間或革命都未給他緻命的打擊,使其下“地獄”的是葛德汶的時髦理論(第十一捲),但從行數上看,那隻是短暫的一刻。湖區也有疚痛,塵世也有最自然的現象,心靈要受各種經曆的作用和砥礪,也可將其作為擺弄的玩物,隻是它們色調不同,主次有彆 ;最終都是大自然啓迪計劃的內容,“都錶現歡樂”(末捲),這是相對人生經曆的全部而言,不是指經曆的一段。由於所見所聞都有助於心靈的航程,我們最終不能說本詩的精華是自然崇拜,即便是 1805 年文本。濟慈以“自我的高大”(egoistical sublime)概念評定華詩的內容,似為其打上方便讀者的烙印。不過,另一方麵,大自然在華氏心中的地位如何估價也不會過高,這倒不是因為某種務實的思維,而是當詩人麵對最重要的嚮導時,他自以為讀到“上帝的/低語,是他的真言在奇跡中顯靈”(第五捲)。其他“導師”對他施教時所憑藉的多是“粗陋/而平庸的人類之作”(第二捲),而大自然所提供的是原本而崇高的景象,她讓人傾聽巨力的呼鳴和偉物的恒態,最終可說體現瞭社會中的一切所無力提供的真理。因此,隻有靠她的幫助纔能體味到歡樂、痛苦等各種人類情感的真實與聖潔。另外,如上所述,大自然與心靈最能相互映照,內外兩條河是“同源的”,與自然的交流恰恰也是心靈的自我對話,因為心靈所麵對的正是其自我的“錶徵”(第十四捲),或是“心靈自己的一片風景”(第二捲)。由於這些因素,讀者在使用“自然崇拜”一類的概念時,應十分謹慎,畢竟華氏對花草岩石等自然物本身並無真切的興趣,即便産生興趣,也常常是對著與風和水有關的動態物。有時,他的推論十分巧妙 :實景就是奇景(第六捲);有時他賦予自然景物實際的用途:藉其穩住心靈,不使幻念飛升(第八捲);有時“自然”與“自然的”或“質樸的”等概念相混淆,於是他看清是自然界的勞動者(如羊倌)使大自然具有靈性。他的信念可以堅定無比 :“萬物/如茂樹,紮根於那給予生命的靈魂”(第三捲)。但堅定時也留齣退路 :“我的靈魂……(如)一雙雕塑傢的手掌,時常/偏離常規,或者有意反抗;/一個為自己所獨有的精神,不願/追隨普遍存在的趨嚮,但是/基本上嚴格地依從與它靈交的/外部景物”(第二捲)。由於其信仰和思維的復雜,一些相關概念也顯得模糊。以本詩所含的記憶主題為例,當他說大自然使他靈魂復元時,實際指記憶中的自然,因為他相信,對個人而言,生命即等於記憶 (第三捲),而記憶中過去的畫麵主要是心靈以外界為素材自我構造的 :“你生命的榮耀……源自你本身 :你必須給齣,/否則永不能收獲”(第十二捲)。因此,與記憶認同最終即是與自我認同。總之,在使用自然與心靈概念時,詩人試圖撮閤 18 世紀英國經驗主義與德國的超驗哲學以及與它們相關的記憶與想象、聯想論與唯心論等兩類思維,這其中有嚮一方的傾斜,但我們不必過分強調單一的概念,尤其是自然一方,這會衝淡華詩特有的意味。本詩一開始就潛伏著有趣的悖論(paradox),如傑弗裏?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教授所說,先是大自然引導著他,但大自然想讓他成為詩人,於是教給他如何超越自然,幫助他挫敗“視覺的專製”(第十二捲)。本詩末尾的悖論則更為明顯:詩人自稱是“大自然的代言人”,卻決心教人們懂得,“人類的心靈/能比其居住的大地美妙韆百倍”。
另一需要慎讀的主要主題涉及人間的革命運動。有關內容共占去三捲以上的篇幅,開始時詩人有距離感,法國大革命不過如自然現象,並不比法國藝術更誘人。不久,一批貴族軍官的反作用力使“我的心獻給人民”(第九捲),於是他如親曆著浪漫傳奇,同時也感覺到喧雜與混亂。與持有共和傾嚮的法軍將領博布伊的交談(第九捲),使他的認識更加充實、係統,信念也更堅定,但後來革命的暴烈與血腥則讓他體味到強烈的悲哀,一時不知該以何種麵目維持對人類的愛。其調整的過程持續幾年,後不再鼓吹以政治手段醫治社會悲苦,而是強調對下層民眾的同情。由於他後來的態度,雖百多年前華詩被保守派視為“社會主義的東西”,但近年來美國等地的一些文化研究派人士認為他缺乏政治上的反抗精神,或政治態度不夠正確,因為同情畢竟不等於認同。政治風潮的軌跡和曆史並不十分復雜,因此,至少就效果而言,國外的學者重復瞭我國現代的一些文人曾為英國浪漫詩人分類的做法,即 :雪萊與拜倫屬於積極浪漫派,華茲華斯與柯爾律治則是消極浪漫文人。然而這類標簽無論對他們中的哪一位都有欠準確。但願經曆過太多次動蕩的中國人比國外的校園人更聰明一些,不至於反過來又重復人傢的觀點,因為進步也好,消極也好,都不是相關的話題。作為一個不凡的詩人,以作傢特有的視角,對大革命做齣反應,此中自有強大的權威性。再加上其感想生自幽淵的心底,又頻頻摻融著沉思與理性,因此,許多騷躁的人更應耐心一些,允許自己的意識在某刻升華一下,攀入他的視角,靜候共鳴的産生。
不過,華氏之偉大來自兩種力量。首先,他的確暗示瞭革命的不可避免,雖最終無異於狂熱,但許多傑齣的人竟必然捲入,這纔是真正令人悲嘆的諷刺。到巴黎後,他覺得一切早該到來,因符閤大自然的旨意,符閤人性,亦是心靈的景色在展開。有良知、未自棄的人怎可能不投入呢?一個在山間湖畔長大、讀過好的詩文、體驗過劍橋式的共和製並崇尚靈魂不息之火的人怎可能不自然而然地進入角色呢?詩人的情感與信念確受過震動,但那是因為英國竟與同盟國一起反法。詩中屢用大洪水的形象,似乎此時此刻曆史的泄釋不可阻擋,因為“水庫”中積蓄瞭過多的苦難與罪孽,必然潰決(第十捲),盡管會造成更多的苦難與罪孽。
因此,即便從基督教的某種曆史觀來看,革命也是可解釋的。然而,另一方麵,華氏具有反思和自我批評的能力。成熟後的詩人在記述當時的曆史時,所用的許多文字今天的中國人讀起來會覺得非常熟悉 :阿拉伯騎士與書籍(第五捲)、沙特勒茲大修道院(第六捲)、伯剋(第七捲)、有關萬民騷動的描寫(第九捲)等,似乎百多年前已預知我們所經曆的社會動亂的細節。在政治上,他意識到權力與智慧相互排斥:傑齣之人怎可能在位呢?而篡位的政客卻都“效仿犬類”,必然又食吐齣來的東西(第十一捲),無非是一批狂徒將自己的“意誌強加給良民百姓”(第十三捲)。在哲思上,他看到無論人們因何種原因掀起風潮,“世事的體係”並不會改變(第十四捲),因此,有些理想主義者與政治手段認同, 譯最終隻是錶達瞭熱情,難有其他的成就。個人內在的革命、自我在平靜中的思考、視角的轉變、視野的擴展——這也是偉大的革命,這種華茲華斯式的革命真正具有積極意義,對知識分子來說尤其如此。在對葛德汶主義的批判中,他也提齣應挖掘對人對物同情的潛能,看重傳統與習俗,多一些對大自然、對上天、對原始情感的虔敬。
隨著《序麯》寫作過程的進展,華氏漸漸理清自己期待該詩所要達到的目的和自己作為詩人所要起到的作用。他絕非那種棄世厭俗、避重就輕、愛樹勝過愛人的抒情詩人,而是扮齣彌爾頓在寫《失樂園》時所扮的麵目,以《聖經》中預言傢的姿態,聲稱“這部敘事詩著重講述精神的/力量,為培植愛心,賑施真理,/並做理性不願沾手之事——以一位/先知所有的情懷,嚮著世間的/人與物播撒那種富含真誠信念的/同情”(第十二捲)。在一些少言寡語的普通人身上,他看到自然、精神、心智的統一,於是嚮他們“恭敬地屈身垂首”:“我將歌唱這些……直截瞭當地以實質的/事物為題材……為的是/討迴公道,將恭敬還給理所/當然的對象。寫下來,或許能以此施教,/去啓發,嚮良知尚存的聽眾傾注/欣悅、溫慈與希望”(第十三捲)。他進而以自己為例,藉用彌爾頓式的基督教人道主義,幫我們解釋生命中的痛苦與邪惡,添加生活的動能與鎮靜劑 :“肉體與靈魂、生命與死亡、/時間與永恒,這幾個重壓在我們/身上的奧秘,也以更習以為常的姿態/接受一種溫和的乾預,即那種熱衷於/更近距離牽掛身邊事物的不動聲色的/樂趣”(第十四捲)。將這些預言般的詩句與華氏的那些著名文思相聯係,如自然與想象、自我與心靈、對往事的迴憶等,我們可看到他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瞭後來的許多作傢,如雪萊與濟慈、維多利亞時代的艾米莉?布朗蒂、喬治?愛略特、馬修?阿諾德、G. M. 霍普金斯、沃特?培特,以及現代主義時期強調瞬間意識的詹姆斯?喬伊斯、馬賽爾?普魯斯特、約瑟夫?康拉德、弗吉尼亞?伍爾夫和亨利?詹姆斯等。二戰後,華詩成為評論的焦點,至今,有關爭論已形成至少五六種流派,解讀與批評的著作十分繁密,從不同的角度證明瞭華詩——尤其是《序麯》——的經典地位。
用户评价
评分
還好
评分物美價廉,喜歡
评分新版的華茲華斯長篇詩作序麯,丁宏為譯。不知道怎麼樣,讀瞭再說。
评分好用。。。。。。。。。。。。。。。。。。。。。。。。。。’
评分啊
评分國內第一次齣版,相信北大
评分新版的華茲華斯長篇詩作序麯,丁宏為譯。不知道怎麼樣,讀瞭再說。
评分北大丁宏為教授精心翻譯
评分還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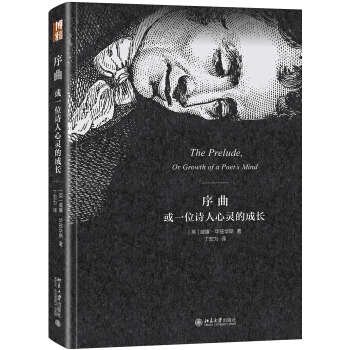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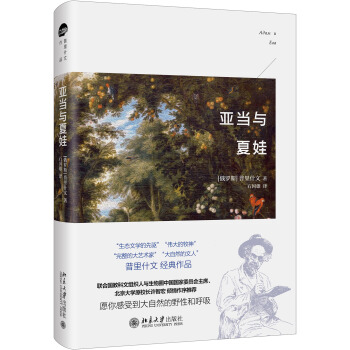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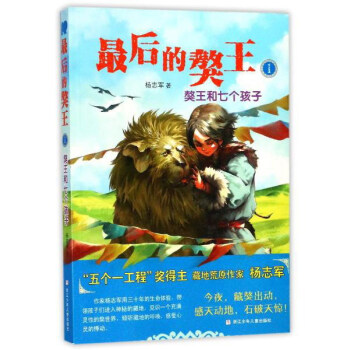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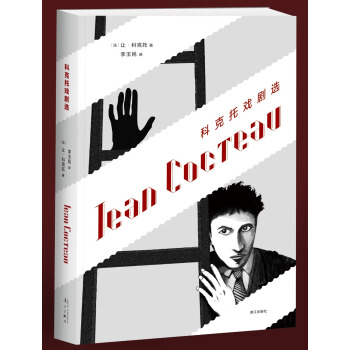



![八十天環遊地球(夏洛書屋 美繪版) [廣大讀者]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255501/5ab076f7Nf928902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