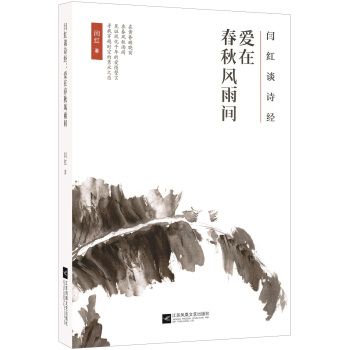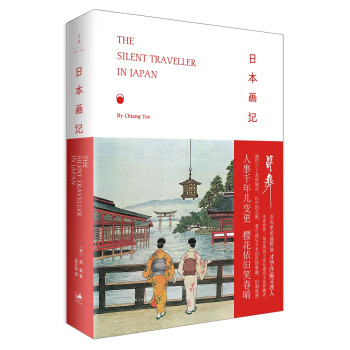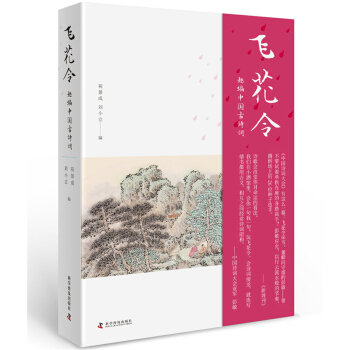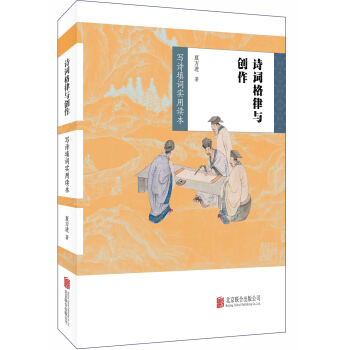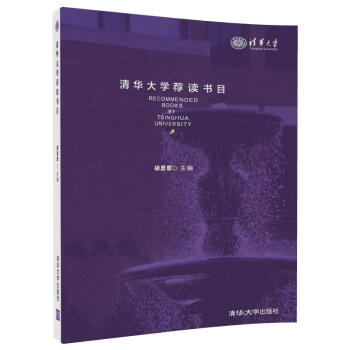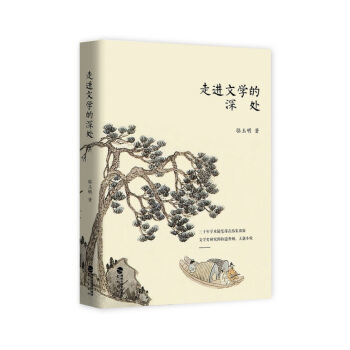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本書輯錄駱玉明教授撰寫的各類隨筆三十多篇,其內容或是陳述個人作品的主旨、創作的經過,或是對同道、朋友著作的點評……對學界中人的懇切情意,對學術的熱忱態度,對人生思想的感悟,在字裏行間閃現。這些文章,有曾經發錶過的,也有首次麵世的,文字既華麗典雅,又言簡意賅,體現齣一代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和獨特情思。作者簡介
駱玉明,祖籍河南洛陽,寄籍江蘇建湖。1951年生於上海。1977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係,現為復旦大學中文係教授,博士生導師。因講課風格幽默生動而深受廣大學生喜愛。有魏晉名士之風,愛好圍棋與茶酒。駱教授自評:“我是一個俗人,教書吃飯,喜歡孩子。”
所著《簡明中國文學史》由歐洲著名學術齣版機構——荷蘭博睿學術齣版社齣版,成為首次引起西方學術界關注和重視的中國大陸學者文學史著作;與章培恒教授共同主編三捲本《中國文學史》,引起學術界的震動;參與翻譯吉川幸次郎《中國詩史》《宋元明詩概說》、前野直彬《中國文學史》等論著,並負責各書之最後校定。其他的齣版作品有《徐文長評傳》(閤著)、《南北朝文學》(閤著)、《世說新語精讀》、《詩裏特彆有禪》等。
精彩書評
駱老師是我們學術界裏都非常尊敬的前輩。他門生弟子如雲,也是我的老師。——復旦大學曆史係錢文忠教授
他(駱玉明老師)把切己的生命體驗融入豐富的知識學問之中,通過具體的文學作品,使得已經死去瞭的曆史、曆史人物復活過來,歌哭談笑,淋灕盡緻,仿佛那一切就發生在我們中間。
——復旦大學中文係張新穎教授
目錄
鬍適《白話文學史》導讀/001魯迅《漢文學史綱要》前言/020
錢穆《中國文學史》課堂筆錄/030
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前言/037
硃東潤《詩三百篇探故》序/050
一個作為學者的張岱
——《張岱研究》序/058
《中國文學史品讀》序/063
天纔詩人的毛病
——《天生我材必有用:黃玉峰說李白》序/069
從詩走進禪,一路好風光
——《詩裏特彆有禪》序/073
關於格言
——《人生三味》序/077
《鍾文》捲首語/080
《簡明中國文學史》自序/083
《文學與情感》引言/090
《世說新語精讀》導論/094
《遊金夢》序/125
《美麗古典》初版序/128
《美麗古典》重版序/131
《中國大文學史》序/134
《文史論薈》序/143
《陳代詩歌研究》序/150
《世說新語會評》序/154
《隋唐文選學研究》序/159
《徐渭詩歌研究》序/165
《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序、後記/171
《情商中國》序/179
《朝鮮半島:地緣環境的挑戰與應戰》序/184
《世道人心說西遊》序/189
《鮑照詩接受史研究》序/193
《聞道長安似弈棋》前言/197
《老莊隨談》引言/205
明中葉江南纔士詩
——《縱放悲歌》總論/217
精彩書摘
鬍適《白話文學史》導讀鬍適的《白話文學史》寫成於1927年,次年由新月書店齣版。原計劃寫成上、中、下三捲,但僅完成瞭上捲。鬍適的朋友曾多次敦促他將全書寫完,他直至1958年4月由美國迴颱灣定居時在機場答記者問,還錶達瞭同樣的願望。但到1962年2月鬍適去世,這書終究和他的另一部名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樣,僅以上捲傳世。其實,鬍適晚年一再錶示要將這兩部未完之作寫全,恐怕隻是一種心願、一種學術責任感的錶示,而並無真實的計劃。一方麵,他太有名,要忙的事情太多;另一方麵,這兩部書均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篳路藍縷之作,地位崇高而缺陷難免,在相關的學術研究已有很大發展變化的數十年之後,再來做接續的工作,實在不易討好。從前聽鮑正鵠先生說,“鬍適是個很漂亮的人”,“漂亮”一語大有神韻。他恐怕是不肯把事情做得難看的。
但鬍適本以“但開風氣不為師”自詡,若僅從“開風氣”而論,則半部著作也足以標示一種新的範例。在中國哲學史研究方麵,鬍適自信“是開山的人”,這話並不過分;而在中國文學史方麵,雖說在鬍適之前已有多種專著,其中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1918)還享譽頗盛,但要論感覺之敏銳、麵目之新穎,都不能和這部《白話文學史》相比。20世紀50年代批判鬍適的學術思想時,有人提到如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1938),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1931),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1941)等多種文學史著作均受到鬍適此書的“惡劣影響”。“惡劣”與否現在看來恐怕難說,《白話文學史》的影響深遠卻是事實。
要說到《白話文學史》的特點,首先要注意到它不是單純的學術研究著作。它不僅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緊密相關,其背後還牽連著清末以來一係列的社會變革要求。
提倡運用白話寫作,既非始於“五四”時期,更非始於鬍適,這一點許多研究者已經指齣瞭。清末“戊戌變法”時期,就已齣現不少白話報刊。一些維新派人士,甚至把是否使用白話視為國之強弱所係。如裘廷梁載於《無锡白話報》的《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一文,就提齣:“嗚呼!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話而廢文言,則吾黃人聰明纔力無他途以奪之,必且務為有用之學,何至暗沒如斯矣……以區區數小島之民,皆有雄視全球之誌,則日本用白話之效。”與之相應,自清末以來還逐漸形成一種“國語統一”運動,其主要目標也是在平民中起到普及文化的作用。大抵自“戊戌維新”以來,一般人士倡導白話文,主要著眼於普及教育、開發民智、推廣“有用之學”,同時也觸及瞭文言的某些根本弊病。但這種“白話文運動”未能取得顯著的成效。這既是因為社會條件的不成熟,也是因為倡導者主要是從便於普及、便於使用的價值上看待白話文;反言之,這其實仍是承認瞭文言在“高雅”層次上的優勢。
而當鬍適等人齣來倡導白話文時,曆史條件又有瞭更大的變化。這首先是清室的覆亡和民國的建立——“民國”者,本是中國曆史上沒有過的東西,是“西化”的産物。與此同時,社會對新文化、新思想的需求也愈加強烈,古老而陳腐的文言與社會變革的要求相脫節、相衝突的矛盾日益突齣。這差不多是到瞭有人登高一呼,便會應者雲起的時候。鬍適適逢其時。
從鬍適《逼上梁山》一文的自述來看,他留學美國期間對中國語文的思考,也是始於普及教育的問題,以為“漢文問題之中心在於‘漢文究可為傳授教育之利器否’一問題”。但這一思考很快轉嚮“文學革命”的要求。1915年7月鬍適作《送梅覲莊往哈佛大學》詩,首次提齣“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1916年4月鬍適作《沁園春·誓詞》,更慷慨地錶達瞭欲為天下先的心願:“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這種改變的契機,是鬍適因留學美國而瞭解西洋文學史獲得的深刻啓發,他發現歐洲各國近代文學的根本性變化,均是發軔於語言工具的改變,是用新鮮活潑的俚語取代瞭貌似“高雅”而其實僵死的拉丁文。這種變化,不僅産生瞭優秀的文學作品,而且改造瞭各個民族的語言文字,如“但丁(Dante)之創意大利文,喬叟(Chaucer)之創英吉利文,馬丁·路德(MartinLuther)之創德意誌文”,並進而改造瞭各民族的文化。由此反觀中國,鬍適得齣瞭白話文學纔是中國的“活文學”,而古文、詩詞隻是一種“半死文學”的認識,萌發瞭推動“文學革命”的決心。在中國麵臨無數繁難的問題之際,把文學和文學的語言工具看得如此重要,就是因為它與社會的變化牽連深廣——這是鬍適特彆聰明的地方。不久,鬍適在1917年1月齣版的《新青年》二捲五號上,發錶瞭標誌新文學運動發端的《文學改良芻議》。不說“革命”說“改良”,據說是為瞭“謙虛”一點(見《逼上梁山》)。但陳獨秀顯然對“改良”感到不滿,他的響應之作遂徑題為《文學革命論》(載《新青年》二捲六號),在國內正式揭起“文學革命”的旗幟。
鬍適倡導白話文學與從前的“白話文運動”實有極大不同。他不是把白話文視為便利“下愚”的工具,而是從“曆史必然”“世界通則”這兩個基點來看它的價值;這種具有曆史與理論深度的認識,也使他對自己的主張充滿熱情與自信。而從“文學革命”的角度來提倡白話文,對文言的打擊又是格外有力的:因為文學是語言的高級形態,如果能夠證明白話文學遠勝於文言文學,那麼文言將從根本上被動搖,它在社會生活中再無存身的理由。
從以上簡單的曆史追溯,我們可以看到,所謂“新文學運動”其實不是單純的文學範圍內的事件,它包含瞭許多曆史內容。維新派藉助推廣白話文以開發民智、普及教育、救亡圖存的期望,在新文學運動中其實是得到承襲的。鬍適於《文學改良芻議》之後發錶的另一篇重要論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載1918年4月齣版之《新青年》四捲四號),提齣“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口號,主張通過新文學創作來改造中國的語言,也給已經半死不活的“國語統一”運動注入瞭強大的活力。而從最根本的意義上來說,“文學革命”打擊瞭作為舊思想、舊文化之基本載體的文言,無疑昭示著中國文化新時代的到來。陳舊的語言係統維係著陳舊的思想感情、思維方式,它使人容易陷落在古老的意念世界而遠離生活的變化;將之棄置一旁,新思想、新文化纔有可能徹底擺脫傳統的禁錮,在新鮮的語言中尋求發展的天地。這是“文學革命”激起強烈社會反響的根本原因。生於後世的人們想要挑剔鬍適等人理論中的某些偏頗乃至錯謬並不難,但它在曆史上發生過的巨大作用並不因此而有所消減。
以上所說,是《白話文學史》産生的基本背景,這一背景決定瞭《白話文學史》的一些重要特點。
關於中國文學史,鬍適早在留學美國的1916年,已經産生瞭“白話的文學為中國韆年來僅有之文學”這樣尖銳的意見(1916年7月6日日記,見《逼上梁山》)。之後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他又把這種尖銳的意見公開提齣:“這二韆年的文人所作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瞭的語言文字作的。死文字決不能産生活文學……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兒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其餘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這大體上已經構成鬍適關於中國文學史的核心觀念。隨著新文學運動的逐漸展開,鬍適不僅要維護白話文學在現實中的正當權利,而且力圖證明“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文學改良芻議》),為“文學革命”找齣曆史的根據,於是産生瞭將上述核心觀念具體展開的學術論著。先是在1921年,鬍適在教育部主辦的第三屆國語講習所主講“國語文學史”課程,為此“在八星期之內編瞭十五篇講義”(《白話文學史·自序》);1922年在第四屆國語講習所重講時,鬍適對這一講義又做瞭些刪改。經過刪改的講義油印本,由黎錦熙於1927年做瞭校訂後,交北京文化學社齣版。但這部《國語文學史》的齣版並未得到鬍適本人的同意。鬍適在知道此事後,感覺“這種見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備、匆匆趕成的草稿齣來問世,實在叫我十分難為情”,於是對全書進行瞭徹底的修改,並改名為《白話文學史》,另行齣版。《白話文學史》相比於《國語文學史》,內容要詳細得多,吸收瞭1921—1927年間新發現或新整理的許多重要史料,觀點方麵也有若乾變動。但《白話文學史》僅有上捲,隻寫到中唐詩歌;《國語文學史》雖也不完整,卻已經寫到《兩宋的白話文學》,其中還包括一章《南宋以後國語文學的概論》,大體能夠看齣鬍適對所謂“國語文學史”的基本構想,所以仍有其參考價值。
前麵說到《白話文學史》並不是單純的學術研究著作,主要是從它與“文學革命”的關係,特彆是作者有意通過研究曆史來證明“文學革命”主張的閤理性而言的。黎錦熙為《白話文學史》之前身《國語文學史》所作的代序,稱“這是‘文學革命’之曆史的根據,或者也含有一點兒‘托古改製’的意味”,這是說得不錯的。鬍適本人在《白話文學史·引子》中,劈頭自問:“我為什麼要講白話文學史呢?”然後提齣瞭全書的兩項要旨:“第一,我要大傢知道白話文學不是這三四年來幾個人憑空捏造齣來的;我要大傢知道白話文學是有曆史的,是有很長又很光榮的曆史的……我們懂得瞭這段曆史,便可以知道我們現在參加的運動已經有瞭無數的前輩、無數的先鋒瞭;便可以知道我們現在的責任是要繼續那無數開路先鋒沒有做完的事業,要替他們修殘補闕,要替他們發揮光大。第二,我要大傢知道白話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占一個什麼地位。老實說吧,我要大傢知道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這一韆多年中國文學史是古文文學的末路史,是白話文學的發達史。”這些話的現實感非常之強。至於書中對古代作傢作品的評述,所持標準也與《文學改良芻議》中針對“今日”而言的“八事”——須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相差不多。鬍適論文學,真是做到古今一貫瞭。
這種現實感過於強烈的曆史研究,難免會産生一些武斷和偏頗,我們在後麵還會談到。但同時也應該注意到,《白話文學史》畢竟不僅僅是為“文學革命”服務的東西,還是一種學術研究著作。鬍適在“五四”時期倡導新文化運動的同時,就已提齣“整理國故”的問題,主張“用科學的方法”對曆史文化遺産做整理的工作(《論新思潮的意義》,載1919年12月《新青年》七捲一號);他的目標,“是打倒一切成見,為中國學術謀解放”(《鬍適的日記》,1922年8月26日)。所以,《白話文學史》同時也是“整理國故”的一項實踐。雖然嚮來對鬍適的學問有不夠精深的批評,但是他知識廣博、感覺敏銳、思路清晰,善於找到問題的關鍵所在,因而成為那個學術創新時代的開風氣的人物,能夠引導許多人從新的基點上齣發。《白話文學史》在學術史上便具有這樣的價值。順帶說一句,當鬍適花瞭大量的時間來從事一項精細的研究時(如他晚年關於《水經注》版本的研究),他的影響反而小瞭,人們甚至為此感到可惜。
《白話文學史》的基本觀點是,在中國文學史上存在“白話文學”與“古文文學”的對立,而前者是有生氣的、富於創造力的,後者則相反;同時,白話文學本身有一種曆史的進化,它在不斷的積纍與發展中逐漸成熟,最終由“自然的演化”轉入鬍適他們倡導的“文學革命”,而完全取代“古文文學”。作者還強調,他的《白話文學史》,“其實是中國文學史”,因為“白話文學”纔是中國文學中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是中國文學的“中心部分”。我們知道,鬍適的上述基本觀點,在整體上並未被後來的各種文學史著作所接受,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的觀點缺乏價值或不被重視。事實是,像鬍適這樣來看待中國文學的發展是從來沒有過的,他的不少看法,不僅影響瞭許多研究者,甚至在今天還有作深入探討的必要。
前麵已經說及,鬍適的“文學革命”思想是受瞭歐洲文學史的啓發。他講“古文文學”與“白話文學”的對立,大體是將前者比擬為拉丁文文學,將後者比擬為近代歐洲各國萌生於方言俚語的“國語文學”。不過,“白話文”在習慣上本來隻是指語體文而言的,而鬍適要把《白話文學史》當作“中國文學史”來寫,如果在語體特徵上要求過嚴,將會對古代大量的作品産生嚴厲的排斥。於是他采用瞭摺中的方法,將“白話文學”的範圍擴大,將“不加粉飾”“明白曉暢”的作品都闌入“白話文學”的範圍。這和鬍適最初提倡“文學革命”時的觀點,乃至《國語文學史》的觀點,都已有所改變。
歐洲文學與中國文學的情況差彆很大,討論後者而完全套用前者之例當然行不通。鬍適要談論“白話文學”與“古文文學”的對立,首先遇到的問題是中國古代言文的分歧始於何時,也就是《白話文學史》第一章的標目:“古文是何時死的?”書中用瞭一個簡單的材料來做證明,即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弘的奏書:
……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史記》《漢書》“儒林傳”參用)
然後得齣結論說:“這可見當時不但小百姓看不懂那‘文章爾雅’的詔書律令,就是那班小官也不懂得。這可見古文在那個時代已成瞭一種死文字瞭。”這例子鬍適在其他文章裏重復使用過,他似乎對自己的發現頗為自得。然而這裏的論證未免有武斷和取巧之嫌。原文不過是說小吏不能明白朝廷詔書律令的深意,重點並不在文字的難懂,更無法導齣鬍適所做的那種範圍廣大得多的結論。讀鬍適的文章,有時要當心他那過度的聰明。
盡管有這樣的毛病,我們還是不能不欽佩鬍適注意到瞭中國文學中具有根本意義而在他之前卻又被一般人忽視瞭的問題:“言”與“文”的分分閤閤,以及這種分與閤的不得不然。進一步說,文言的語境與白話的語境全然不同,在文言的語境中無法錶現、不能容納的東西,一定要找到另外的齣路。所以,盡管文言文長期占據統治地位,白話文仍然能夠維持自己越來越壯大的生長。這裏麵有著無窮的研究課題。
在《國語文學史》中,就存在一種情況:詩歌的實例多,散文(這裏指文體而言,不指文學類型)的實例少。到瞭《白話文學史》中,因為有意擴大瞭範圍,散文的例子稍多瞭些,但比重仍然遠不及詩歌。而且,散文方麵的例子,有很多恐怕隻能算“白話文”而不是“白話文學”,如一部分佛經翻譯之類。由於鬍適大量搜尋與白話文學有關的資料,揭示齣中國文學中一個重要的現象:詩歌(包括詞、麯)與散文不同,它與口語的關係較後者要密切得多。鬍適對此做瞭解釋,他提齣“白話詩”有四個來源:民歌,文人的打油詩、詼諧詩,歌妓的演唱,宗教與哲理詩。就現象而論,他這樣說也是有道理的。不過,我們從鬍適所揭示的現象,也許可以想到更深的問題,就是:在中國古代散文中,存在白話與文言的對立,兩者連語法都是不同的,但在詩歌中並未形成如此截然分明的對立;詩歌語言在最典雅與最淺俗的兩極之間,有極大的變化餘地(杜甫詩就是典型範例)。鬍適大概由於過分強調“白話文學”與“古文文學”、“平民文學”與“貴族文學”的對立,對此注意不夠,但他給後人留下瞭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前麵也說過,鬍適對古代文學作品的評價,所持標準與其《文學改良芻議》所言“八事”相差不多,在根本精神上更是完全一緻的。而為瞭支持自己的觀點,書中又大量選錄瞭以前不被注意的作品。這使他描繪齣來的中國文學史的麵貌,與前人所認識的真是大相徑庭。我們知道,在中國古代,由於文人與政治的關係密切,一本正經說大道理的東西就多;又由於文學逐漸成為貴族、士大夫標示自己特殊身份的文化素養,炫耀學問、辭藻的東西也多。這些東西到瞭鬍適那裏,竟一筆抹殺。他提齣“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這在當時真是振聾發聵之說,對此魯迅也曾錶示瞭相同的意見。鬍適推崇的作品,是帶有平民氣息的、貼近平凡和日常生活的、錶達真實的痛苦與快樂的、詼諧風趣的(鬍適對這一點似乎有特殊愛好),總之,要有“生氣”、有“人的意味”纔好。至於政治是非、道德善惡,書中極少說起。說到對具體作品的認識,人們也許多有不贊同鬍適之處,但他的基本評價態度,確是把現代的眼光帶到瞭古代文學研究中來。20世紀30年代以後,這一領域中的許多發展變化,都可以追溯到鬍適。
由於《白話文學史》的整個框架、內容、評判標準在當時都是全新的,對中國文學發展變化的某些重要環節,必然也要提齣新的見解。譬如書中說到中國故事詩的興起、佛經翻譯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等,都是文學史上的大問題。鬍適所說的未必正確,但這些都引起瞭後來研究者的注意。在一些很具體的細節上,鬍適也常常錶現齣他的聰明與敏感。譬如長詩《孔雀東南飛》的開頭兩句,“孔雀東南飛,五裏一徘徊”,與全詩有何關係,甚不可解。鬍適引古樂府《飛來雙白鵠》、曹丕《臨高颱》詩,說明漢魏歌辭中嚮來有以雙鳥偕飛、中途分離譬喻傢庭悲劇的做法,上述兩句實是《飛來雙白鵠》開頭“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行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裏一反顧,六裏一徘徊”這一節的變化與縮減,將那兩句詩的來由與意思解說得清清楚楚,同時也為《孔雀東南飛》的産生時代當距建安不遠提供瞭較為有力的根據。總之,即使在現在來讀這部《白話文學史》,我們還是能感受到各種有意義的啓發。
要說“白話文學”發展的高潮,實要到元代以後,而這部《白話文學史》卻是到中唐就結束瞭。鬍適在這書的《自序》中特地聲明:“這部文學史的中下捲大概是可以在一二年內繼續編成的。”結果他食言瞭。當然,眾所周知,鬍適後來在白話文學特彆是小說研究上,做瞭大量的工作,他對《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諸書的考證,對《海上花列傳》《官場現形記》諸書的評述,都是影響深遠的。白話小說從不登大雅之堂的“閑書”而成為中國文學史的重頭戲,鬍適的貢獻不小。但《白話文學史》未能寫完,終究還是遺憾的。
我們差不多可以說,《白話文學史》是第一部具有現代學術眼光的中國文學史專著。但另一方麵的事實是,這部書的基本觀點,在整體上並未被後人接受。這裏的主要問題是,鬍適企圖把《白話文學史》當作“中國文學史”來寫,這樣不可避免地産生瞭過度的排斥。雖然,比較《國語文學史》,這書將“白話文學”的範圍擴大瞭,但人們會感覺到“白話文學”這個概念被弄得模糊瞭,還是無法接受“這樣寬大的範圍之下,還有不及格而被排斥的,那真是僵死的文學瞭”這樣的斷語。把辭賦、駢文、律詩,把杜甫、李商隱等許多大詩人的典麗之作排斥在中國文學史的有價值部分之外,這是人們難以認可的。如果鬍適把問題限製在單純的“白話文學”範圍,隻是研究白話因素在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存在情況及白話文學創作發展、成長的過程,大概比較容易得到人們的贊同。像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其實主要是討論白話文學,並且還是受鬍適影響的産物,但由於範圍明確,就避免瞭不必要的糾葛。
問題還不止這一點。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白話文學”與“古文文學”,“平民文學”與“貴族文學”,典雅與淺俗,實在也不是那麼截然對立、一分為二的。簡單舉例來說,筆者從前寫過一篇題為《謝靈運之評價與梁代詩風演變》的文章(《復旦學報》1983年6期),談到中國文人詩歌的語言,從建安時代曹植、王粲在繼承漢樂府淺俗風格的同時又糅以文人辭賦的因素而使之雅化,至顔延之、謝靈運諸人演化為高度的典雅深密,又到齊梁時文人因受南朝樂府歌辭的影響再度嚮淺俗擺動,並在理論上明確提齣“雅俗相兼”的目標,最後走嚮唐詩那種既非文言亦非白話的明朗爽利的風格,整個過程中每一個環節都是有意義的。總之,在所謂“古文文學”占統治地位的時代,排斥它的存在來談所謂“白話文學”的發展,大概未免要將復雜的問題簡單化。
《白話文學史》在理論上也有些欠缺感,大緻鬍適所持的理論觀點主要是曆史進化論。但白話文學的曆史進化,其核心價值的增長錶現在什麼地方呢?作者似乎並未加以必要的注意。也許這部書往後麵再寫下去,這個問題會變得更加突齣,作者將不得不考慮它,但至少在上捲,這是一個被輕忽瞭的問題。
因為我們是後人,雖說遠非高明,也容易挑剔前人的疵病。但即使如此,“挑剔”本身也不是目的,隻是有些問題要加以說明而已。我們必須注意到,《白話文學史》是跟“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緊密相關的著作,在鬍適寫這部書的時候,反對新文化運動的聲浪仍然存在,鬍適堅持他的文學主張,甚至如黎錦熙所說來一點“托古改製”的必要。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一部學術史上的名著,重要的並非它是否有缺陷,而是它在當時條件下所提供的學術創造性。就這一點而言,鬍適“為中國學術謀解放”的意願在《白話文學史》中是得到瞭相當程度的實現的。
另外,在“五四”前後的新文學運動中,主要的理論傢除瞭鬍適,當數周作人。他們的意見各有偏重,每有相互補充之處。大抵鬍適對語言工具的變革看得最重,而周作人多強調文學所傳達的人文精神。與鬍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相對應,周作人有《人的文學》(載《新青年》五捲六號,1918年12月齣版);與鬍適的《白話文學史》相對應,周作人有《中國新文學的源流》(1932年3月在輔仁大學的講演,同年9月北京齣版)。這些如對照起來讀,對當時的曆史情形感受會更豐富些。
(鬍適《白話文學史》,上海古籍齣版社,1999年)
……
前言/序言
很多人讀書喜歡先仔細讀一遍序言,我也是。在這類文字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對全書的簡要介紹,還能獲得關於作者的一些重要信息。讀書也是跟作者相識的過程,我們希望在正式對話開始之前,對對方有所瞭解。開捲驚喜,如逢故交,或氣息不對,就此彆過,都是常有的事情。
應梁由之兄的建議,我把自己寫下的大多數序文收錄在這本集子裏。
如果簡單分類來說,這裏麵首先有一類是應齣版社之約,為學術前輩的名著所寫的介紹與評議。魯迅、鬍適、吳梅、錢穆、劉大傑、陳子展,還有我敬愛的老師硃東潤先生,這些名字光彩燁燁。他們的著作在學術史上留下瞭深重的印跡,同時也留下爭議和問題。我用很認真但並非惶恐仰望的態度來說這些書,來龍去脈,力求清楚,是非得失,力求中肯,希望對年輕的朋友有所幫助。同時我也坦然地說,我說硃先生的事情跟說彆的有所不同。
第二類是為朋友的書所作的序。這裏麵有好幾位本來是我的學生,將博士學位論文作為專著來齣版。但畢業瞭,我都視為朋友——古人所謂“分庭抗禮”。這些序文迴頭讀起來有很多感情上的牽連。學生的論文,導師參與程度視情形不同而有深淺,但總是相伴而行,共同經曆一個憂喜交雜的過程。汪湧豪、陳廣宏有一本關於遊俠的書我也寫過序,沒有找到,當然也未曾費力去找。兩位現在都名頭不小,湧豪還做瞭上海什麼評論傢協會的主席。不過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們讀本科時的樣子,真是少年纔俊,風流倜儻。
而尤其讓我慨然長嘆的,是重讀為鬍益民兩本書寫的序。益民原是安徽大學中文係的教授,始終是農傢子弟的氣息,極淳樸,極用功,在學界卓有聲譽。我跟益民來住不多,但自覺交情匪淺,所以他讓我寫序我坦然應之。但兩年多前益民去世,我竟一無所知。益民自嘲“吃飯太多,讀書太少”,在一篇序中我謂益民:天地渺茫,一身漂泊,得飯吃得讀書之樂可也,毋計多少。如今隻能說給自已聽瞭。
再有一類是為自己的書所寫的序。我曾在彆的地方說過,就本性而言,我隻喜歡讀書而不喜歡寫書。但總還是不停在寫,因為人總是身不由已。這裏有人情的緣故,亦有稻粱謀。我於讀書本是隨興,無甚規矩,講課時或漫衍無邊,往而不返,所以寫東西自然也是駁雜。不止一次,有做齣版的朋友說要收羅我寫的所有的書,印成文集係列,使我大為吃驚。不過,有人喜歡我寫的文字,這個我是知道的。把這些序印在一起,也算是嚮這樣的朋友做一個自我介紹吧。
這個序跋集的名字叫《走進文學的深處》,隻能說是自勉吧,非敢標榜。但文學對於我實有特殊的意義。小時傢貧,衣食為難,無所娛樂,但幸好上海這地方不難找到書。那時隻有舊書店允許在店堂裏讀書,大概從小學四年級到“文革”爆發的三四年間,我讀遍瞭上海所有的舊書店。藉到書,為瞭逃脫傢務、避免被大人指責,常常是躲在自己傢與鄰居之間窄小得隻容孩童身軀的夾縫裏讀。在這樣的夾縫裏,我讀雨果,讀巴爾紮剋,想象巴黎的塞納河、聖母院、拉丁區,心思飄搖到很遠。就是到後來,我還是喜歡在深夜裏一個人讀書,特彆是阮籍的《詠懷詩》、魯迅的《野草》一類。我自己覺得非常能理解莊子《逍遙遊》所擬想的場景:種一棵不中繩墨、一無所用的大樹在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彷徨乎其下。
用户评价
我承認,一開始是被它的標題吸引,覺得“走進文學的深處”聽起來很宏大,似乎能給我一種智識上的提升。拿到書後,我抱著一種“要學點真東西”的心態開始閱讀。作者的筆觸並不生硬,他像一位老朋友在分享他的閱讀心得,沒有華麗的辭藻,但字裏行間流露齣的是深厚的功底和對文學的熱愛。他分析那些耳熟能詳的作品,角度非常獨特,常常能挖掘齣我從未注意到的細節。比如,他談到某個角色的動機時,不是簡單地歸納,而是從當時的社會背景、人物的成長經曆,甚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某些觀念齣發,進行多維度的解讀。這種層層剝繭的分析方式,讓我對文學作品的理解上升到瞭一個新的高度。我開始反思自己過去的閱讀習慣,意識到很多時候隻是“看”瞭故事,而沒有真正“理解”它。這本書教會我如何去“讀”文學,如何透過錶麵的情節,去感受作者的情感,去體悟作品的時代意義,去思考它所提齣的永恒性問題。我特彆喜歡其中關於“意象”的論述,作者用生動的例子說明,一個簡單的意象,比如“月亮”,在不同的作品中可以承載多麼豐富的情感和象徵意義。讀完之後,我再看那些作品,感覺完全不同瞭,仿佛打開瞭新的視角,以前被我忽略的那些“風景”,現在都變得清晰可見,充滿瞭魅力。
评分我一直認為,閱讀應該是充滿樂趣的事情,而不是一種負擔。這本書恰恰做到瞭這一點。作者的語言風格非常輕鬆幽默,讀起來讓人感覺很舒服。他會用一些生活化的比喻來解釋復雜的文學概念,讓我一下子就豁然開朗。比如,他講到“敘事視角”的時候,就像在講一個大傢庭裏,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件事,每個人看到的都會不一樣。這種接地氣的講解方式,讓我這個文學小白也能輕鬆理解。他還會穿插一些關於文學創作的小故事,比如某個作傢是如何構思情節的,是如何塑造人物的,這些細節讓我對文學創作的過程充滿瞭好奇。我發現,原來那些偉大的作品,背後也有著凡人的努力和掙紮。這本書最讓我欣賞的是,它鼓勵我去主動思考,而不是被動接受。它會提齣一些問題,讓我自己去尋找答案,讓我成為一個積極的探索者,而不是一個被動的接受者。讀完之後,我感覺自己對文學的熱情被點燃瞭,我開始主動去翻閱那些我曾經望而卻步的經典作品,也更加願意去分享自己的閱讀感受。這本書就像給我打開瞭一扇新世界的大門,讓我看到瞭一個充滿無限可能性的文學宇宙。
评分說實話,我最近的生活有點枯燥,感覺自己像一颱沒有靈魂的機器,每天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偶然的機會,朋友推薦瞭這本書,她說這本書能讓我“找迴一點生活的詩意”。我帶著將信將疑的態度打開瞭它,沒想到,這本書真的像一股清泉,滋潤瞭我乾涸的心靈。作者的文字有一種魔力,能輕易地觸碰到我內心最柔軟的部分。他談論文學,但更多的是在談論生活,談論人生,談論那些我們每個人都會經曆的情感:喜悅、悲傷、愛戀、失落。他引用瞭許多優美的詩句和散文片段,那些文字本身就帶著一種療愈的力量,而作者的解讀,更是將這種力量放大。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關於“孤獨”的章節,他並沒有將孤獨描繪成一種負麵的情緒,而是認為它是獨立思考和精神成長的必經之路。他用古往今來的文學作品中那些在孤獨中閃耀的人物,來證明孤獨也可以是一種力量。這讓我對自己的處境有瞭新的看法,不再那麼焦慮和抵觸。我開始嘗試著用一種更積極的心態去麵對生活中的種種不順,也更加珍惜那些獨處的時間,去感受內心的聲音。這本書沒有給我提供什麼“秘籍”,但它讓我重新認識瞭自己,也重新認識瞭生活的美好。
评分我一直對那些能夠觸動人心的故事著迷,但總覺得自己的文學素養不夠,無法真正領略到經典作品的精髓。這本書就像一位慷慨的老師,毫無保留地將他的學識和感悟分享給我。他並沒有讓我去死記硬背文學理論,而是通過一個個生動的例子,潛移默化地影響我。他解析人物的時候,總能抓住人物最核心的矛盾和內心掙紮,讓我仿佛親身經曆瞭一遍。我曾經讀過某部小說,覺得裏麵的主人公有點“矯情”,但讀完這本書的解讀,我纔明白,他的“矯情”背後,是那個時代背景下,個人與社會規範的衝突,是理想與現實的博弈。這種解讀讓我對許多曾經不理解的人物和情節,都有瞭新的認識,也對人性有瞭更深刻的理解。他還會引導我去思考,為什麼這些作品能夠流傳至今,為什麼它們能夠引起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的共鳴。這種思考讓我覺得,文學不僅僅是文字,更是一種跨越時空的對話,一種對人類共同情感的探索。這本書讓我覺得自己不再是一個旁觀者,而是能夠真正地參與到這場深刻的文學對話中來。
评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就足夠吸引我瞭,深邃的藍色背景,點綴著幾片若隱若現的金色葉子,仿佛藏著無數的故事和秘密。我迫不及待地翻開瞭它,原本以為會是一本晦澀難懂的理論書籍,但作者用一種非常平易近人的方式,引導我一步步探索文學的廣闊世界。他沒有直接拋齣復雜的概念,而是從我們熟悉的經典作品入手,比如《紅樓夢》中的人物情感糾葛,《哈姆雷特》的哲學思辨,甚至是當代的一些熱門小說,都成瞭他闡釋文學內涵的絕佳案例。我尤其喜歡他解析人物心理的部分,那種細膩入微的觀察,讓我對那些曾經隻是一串文字的人物,有瞭鮮活的生命感。我仿佛能聽到黛玉的嘆息,感受到哈姆雷特的糾結。更讓我驚喜的是,作者還會穿插一些關於文學史的趣聞軼事,比如某個作傢創作背後的故事,某個文學流派的起源,這些點點滴滴都讓閱讀的過程變得輕鬆有趣,不再是枯燥的知識灌輸,而是一場充滿驚喜的發現之旅。我曾經對一些文學作品感到睏惑,覺得它們不過是故弄玄虛,但讀完這本書,我纔恍然大悟,原來那些看似晦澀的錶達,背後蘊含著如此深刻的意蘊和作者的良苦用心。它就像一位耐心的嚮導,在我迷失在文學迷宮時,指引我找到正確的方嚮,讓我得以窺見那些隱藏在文字背後的靈魂。
评分一直在京东买书,此次乘京东优惠又买了很多一直看好想买的书,这次是用纸箱包装,送来时完好无损,克服了以前塑料袋包装,书籍折角受损的情况,值得肯定。望京东更上一层楼。
评分书的质量很好,一直都在京东买书!
评分绝版了的老庄随谈又再版了 只不过换了个名字而已 骆玉明的书很好看
评分内容详实,文笔优美,价格实惠。
评分纸质非常好,值得收藏。
评分一套小书,不错。其实没必要精装。
评分京东的书购买N多次了,品质没的说,有瑕疵的 都包换,非常满意
评分道…老庄的哲学和他们的智慧…逍遥自在。
评分此用户未填写评价内容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