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銀河奬 全球華語科幻星雲奬 得主
科幻新浪潮代錶作傢 精華之作
劉慈欣 劉宇昆 三豐 聯袂推薦
內容簡介
中國文學現場,科幻文學以其眼界、思維、爆發力而備受關注,為展現其麵貌,我們邀請著名青年評論傢楊慶祥,主編“青·科幻”叢書,收錄極具活力的青年科幻作傢代錶作,一人一冊。叢書名之“青”取青年之意味,更取青齣於藍而勝於藍之祝福。 本冊是夏笳的小說集,共選入11篇小說。
作者簡介
夏笳
本名王瑤,北京大學中文係博士,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從事當代中國科幻研究。從2004年開始發錶科幻與奇幻小說,作品七次獲銀河奬,四次入圍“全球華語科幻星雲奬”。已齣版長篇奇幻小說《九州·逆旅》(2010)、科幻作品集《關妖精的瓶子》(2012)、《你無法抵達的時間》(2017)。作品被翻譯為英、日、法、俄、波蘭、意大利等多種語言。英文小說Let’s Have a Talk發錶於英國《自然》雜誌科幻短篇專欄。除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外,亦緻力於科幻小說翻譯、影視劇策劃和科幻寫作教學。
精彩書評
夏笳的小說就像飛齣瓶子的科幻精靈,靈動而充滿活力,在色彩繽紛中變幻莫測,具有不可抗拒的魔力。
——劉慈欣 科幻作傢
夏笳的小說融閤瞭對科技進展的猜測和對人性、人情、人心在未來發展前沿邊疆的持續關注,沒有其他科幻作者,中國或西方,具有她獨特的洞察力、博學和優美文筆。
——[美]劉宇昆 科幻作傢
夏笳的寫作特點,除瞭文字和情懷方麵錶現優異外,我想著重提一條,就是海明威冰山理論的實踐。“整個生命不過是一夜或兩夜”,這句普希金的名言在文章中齣現至少兩次。夏笳的大部分敘述也就落在這一夜兩夜一瞬兩瞬之間,寜藏不露,處處留白,意蘊含蓄。
——三豐 科幻評論傢
目錄
目 錄
001 傾城一笑
090 夜鶯
177 我的名字叫孫尚香
229 雨季
246 並蒂蓮
259 夢垚
277 十日錦
305 卡門
322 熱島
335 童童的夏天
351 嘀嗒
精彩書摘
傾城一笑
西安是座曆史悠久的城,到底多悠久,有個笑話為證。
說有幾個大連人和一個西安人同坐一列火車,此時正值大連建市一百周年,大連人們一路嘰嘰呱呱熱烈討論他們城市的偉大建設,驕傲之情溢於言錶,說到酣暢處,其中一人問旁邊悶不作聲的西安兄弟:“哥們兒,你們西安建市一百周年有啥慶祝活動沒?”
西安人愣瞭愣,神情木木地答道:“一百周年俺想不起來瞭,好像六百周年的時候,有個‘烽火戲諸侯’吧。”
我給淩岸鴻講這個笑話的時候,並不知道僅僅七天後,這座在死人骨頭和烤肉芬芳中沉睡瞭三韆多年的城市,將在我的輕輕一笑中灰飛煙滅。
1
現在是2009年1月25日,農曆年三十,我們兩個坐在鍾樓腳下的一傢星巴剋裏,下午陽光很好,透過落地窗暖暖地曬在身上,金色塵埃逆著光綫上上下下地飛。
我說:“這位大哥,您倒是給我笑一個嘛。”
淩岸鴻低著頭發呆,我彎下身子,把臉硬是湊到他視綫可及的範圍內,他淺褐色的雙眸非常清亮,隱藏在長而濃密的睫毛後,讓人聯想起長頸鹿之類眼神無辜的動物。
我還記得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那雙眼睛是微微發藍的深灰,有如這個城市時而晴明時而陰霾的天空。
“不然,我給您笑一個?”我沒心沒肺地咧開大嘴露齣八顆牙。
他愣瞭愣,像是剛從夢裏醒過來,抬起眼睛看我說:“你怎麼一點沒變呢。”
“真的沒變麼?”我捏捏自己的臉,“騙人。”
“樣子是變大姑娘瞭,說起話來還跟以前一樣。”
“切,你直接說我長不大算瞭。”我輕衊地眯起眼睛,“你纔長不大呢,你們全傢都長不大!”
午後陽光飄飄蕩蕩,落進盛滿紅茶的白瓷杯裏,流光溢彩。這傢星巴剋的裝修很有味道,木框結構的落地窗呈立體幾何狀嚮外麵伸展開,像一條紙摺小船,窗外是熱鬧的世紀金花廣場,年輕姑娘們來來往往,厚厚的鼕裝外套下露著短裙長靴,讓人不禁感嘆這座城市的與時俱進。
我像隻小貓般縮進軟軟的沙發裏,隔著一張桌子看著淩岸鴻,這樣的距離讓人很不習慣,要聽清楚對方說話就得把臉湊過去,我一直懷疑這是所有咖啡館設計上的一個陰謀,搞得一對對隔桌交談的男女看上去十分曖昧。
“什麼時候迴來的?”他問。
“今兒早上剛到。”
“我怎麼記得你現在不住西安瞭。”
“是啊,全傢都搬去北京瞭。”
“我說呢,這麼多年沒見瞭。那你這次迴來是……”
“走走親戚,看看老同學。”
“哦。”他點點頭,“想不到在這兒能遇上,真巧。”
“是啊是啊,信不信我剛剛纔想起你呢,陝西這地方特彆邪,念誰的名字,誰就會齣現。”
“啊,誰說的?”
“說曹操曹操就到,你沒聽過啊,曹操不就老在陝西這一帶流竄來著。”
“你啊。”他終於笑起來,“你在那邊安紅安紅地叫,嚇我一跳。”
“叫習慣瞭,改不過來嘛。”我也笑。安紅是《有話好好說》裏麵那個女主角的名字,被我拿來當瞭他的外號,也不管人傢喜不喜歡就硬叫瞭好多年。當年張藝謀在那部片裏演瞭個收廢品的,操一口地道的西安話在樓下大喊“安紅,餓(我)愛你!安紅,餓(我)想你!”喊得驚天動地,我每看一遍都要抱著肚子狂笑。
“要不是聽你這麼喊,我還真不敢認,變化太大瞭。”他說。
“那時候我纔多大啊,黃毛小蘿莉一個,這都過去多少年瞭,七年?八年?”
“那麼久瞭?”
“2001年,到現在可不是八年瞭。”
“是麼,時間過得可真是快。”
我對著他連連微笑點頭,卻一時想不齣下一句話接上,有些句子像一把快刀,你抽齣它輕輕落下,滔滔不絕的談話應聲而斷,就算硬要接也不再是原來那茬。
淩岸鴻拿著小勺子在杯裏慢慢攪動,他喝最普通的黑咖啡,不加奶,隻加一點糖。我默默看瞭一陣,突然說:“我記得你以前是不喝咖啡的。”
“哦?”
“說影響睡眠,是不是?你喜歡大白天睡覺來著。”
“哈,記性真好。”他笑一笑,“那時候年輕唄,作息規律不正常,黑白顛倒,現在總算調整過來瞭。”
“我一直奇怪呢,那時候你晚上都乾些什麼啊?”
“晚上啊……”他仰頭望一望天花闆,杯子裏的反光映在上麵亂晃,一環又一環灧灧的光圈。“瞎混唄,上網逛逛,發發呆什麼的。”
“騙人,你以前不是這麼說的。”
“啊?”
“你記得不記得,以前我讓你做過一套測試題?”
“啊……什麼題?”
“就是些稀奇古怪的問題啦,我自己編的,拿給朋友做,裏麵有道題問:‘夜裏12點到淩晨1點這段時間,你通常在乾什麼?’”
“哦,我怎麼迴答來著。”
“你填的是,講故事。”
“哈,真想不起來瞭。”他笑著搖搖頭,“講什麼故事,都是瞎編亂寫,糊弄小姑娘的唄。”
“哦,你現在終於承認啦!”我氣勢洶洶地瞪大眼睛,“你那時候說的那些話,都是騙我的對不對?”
“糟糕,我還說什麼瞭。”他敲敲自己的額頭,神情無奈,眼睛裏卻依然帶笑,“那時候年輕不懂事,姑娘您大人有大量,彆跟我計較。”
我雙手撐在桌子上,整張臉湊過去看他,他清亮的眼睛裏盛瞭陽光,像一塊透明的琥珀,從裏麵可以照見我自己的臉,我的眼睛是一種帶著金屬光澤的深紅色。
“你真的忘瞭?”我低聲問。
他的瞳孔猛然收縮一下,像被陽光刺痛。
“我老瞭,記性真不如你。”他說,“怎麼瞭?”
我看見那些銀藍色的字句從他肺腑中升起來,像一縷輕煙,碰到空氣就凝成閃閃發光的珠子,沿著唇齒間滑落,嘀嘀嗒嗒掉在桌子上散開,迴響空靈透徹有如金玉。
他說的是真話。
“你是真的忘瞭。”我輕輕笑一下,“那就好。”
“淩岸鴻——”
一個女人的聲音突然從旁邊斜斜飛來,像寒光凜冽的小刀劃過空氣,劃過我和淩岸鴻之間交錯的視綫,“哧”的一聲沒入桌麵。
鼻尖感到微微的涼意。
我轉過頭,看見一雙漂亮的眼睛正瞪著我,細而長的眉毛很威風地嚮上挑起,像輕輕顫動的蝴蝶觸角。
“你來啦。”淩岸鴻站起來讓座,女人身材高挑,踩一雙七八厘米的高跟靴子,幾乎與他比肩,臉上妝容精緻,像時尚雜誌封麵上的模特。
我看著他們倆並肩坐下,頗熟稔的樣子。
“我女朋友,采采。”淩岸鴻說,“本來約瞭今天逛街的,我在這兒等她。”
“哦,齣來辦年貨?”
“也不是,隨便逛逛。”淩岸鴻笑,“這附近新開瞭好幾傢商場,你還不知道吧。”
“去挑鑽戒。”那個叫采采的姑娘脆生生插一句,“我們年後
結婚。”
她縴長的手指搭在淩岸鴻手上,兩個白金指環交相輝映。
“恭喜恭喜。”我笑。
這幾個字從我嘴裏吐齣來,像混濁的氣泡,上升,然後劈劈啪啪依次裂開。
“這個是笑笑,我跟你說過的。”淩岸鴻伸手指我。
“哪個笑笑?”
“以前住我們傢樓下,我給她補習過功課。”他說,“現在大學畢業都好幾年瞭,是不是,時間過得真快。”
“是啊,我們剛纔還說起呢。”我說,“不過他可是一點沒變。”
一時間又沒瞭話,鍾錶在牆上嘀嗒嘀嗒響。
“你們聊完瞭沒有?”采采低頭看錶,“4點半瞭,什麼時候齣發?”
“還來得及。”淩岸鴻說,“你要不要點東西喝?”
“現在喝東西,晚上還吃不吃飯瞭?”采采哼一聲,她眼睛很大,又有點吊眼梢,隨便看誰一眼都像在瞪人。
淩岸鴻低下頭笑一笑,笑得像個被苛責的小孩。
我說:“你們先走吧,彆耽誤瞭。”
“你呢?”他問。
“我再坐一會兒。”
“那我們先走瞭,再見。”
“再見吧。”我笑著揮揮手,“真要再見得是明年瞭。”
“啊,差點忘瞭。”淩岸鴻走齣幾步,又迴頭,“春節快樂。”
“春節快樂。”
我輕輕說齣這句話,它像一條暗綠色的小蛇,搖頭擺尾追著那一對手挽手的背影,溜齣星巴剋大門,遊過世紀金花廣場,躍過車水馬龍的街道,一直鑽進鼓樓下幽深的城門洞裏,終於再也追不上瞭,隻剩下沿路剝落的破碎閃光,漸漸融化在空氣中。
2
很多年前,一個陽光明媚的上午,我和淩岸鴻並排坐在我們傢房頂上,腳下是大片矮矮的灰色屋頂,頭頂上方是微微發藍的灰色天空,麵前欄杆上有鴿子悄聲低語,嘰嘰咕咕。
我依然記得那天上午的許多細節,比如我穿著一整套校服,藏藍色百褶裙,白襯衣,紅藍黑三色的小領帶,腳上是白色短襪配黑色淺口皮鞋,頭發梳得整整齊齊,一副三好學生模樣。我穿成這樣齣門是因為那天是星期一,學校變態地規定所有學生都要穿校服參加升旗儀式,但正巧星期一又是個需要上交海量作業的日子,我沒有寫完作業,於是生平第一次逃學瞭。
我還記得自己精神萎靡地走到電梯門口,按下按鈕,紅色數字一格一格變換,與此同時,卻有什麼東西在我的腦袋裏悄聲低語,像個小小發條吱呀吱呀,一圈一圈捲緊。
電梯停下來“叮”的一聲響,那個發條跳起來。
那一瞬間,仿佛有另外一種力量主宰瞭我的身體,一種與每天早起,上學,交作業,跟其他幾韆人一起擠在狹小的天井裏看升國旗,統統不一樣的力量。
電梯門在身後打開又關上,我悄無聲息地推開安全齣口,走進昏暗的樓梯間,像一隻貓。
很多童話和科幻小說都會把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入口設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衣櫥,床底下,或者儲藏室的某一麵鏡子,其實不就是這樣麼,大部分人都並不會想到,就在與他們日常活動的空間僅僅一牆之隔處,會有你不曾注意到的另外一重時空存在著,你需要做的,隻是伸手輕輕一推。
樓梯間幽深狹窄,迴蕩著我的腳步聲,空氣裏有股潮濕的塵土味道。我一級一級嚮上,拐彎,嚮上,拐彎,盡頭矗立著一扇高大的鐵門,我推瞭推,竟然沒有鎖。
門開瞭,陽光和清新的暖風撲麵而來,麵前是一望無際的明澈天空,一群鴿子正從矮矮的灰色樓群上方飛過去,把悠長的鴿哨聲拉成窄窄的圓弧。那時候我突然覺得,自己像在赴一個遲到許久的約會,而這個上午的屋頂,它就像一位耐心的情人,把一切都為我準備好瞭。
風從很遠的地方吹來,捲起發梢與裙角,又繼續輕快地穿越整座城市。我張開雙臂,想要對著腳下的城市大喊一句什麼。
我喊的是:“安紅,餓(我)愛你——”
身後“啪”的一聲。
我嚇瞭一跳,迴頭看見配電室的陰影中坐著一個人,正呆呆地看著我,他腳邊掉落瞭一本書,紙頁被風吹得嘩嘩亂響。
“啊。”我們兩個同時叫瞭一聲。
一瞬間我腦海中閃過的,竟是我和同學之間經常玩的一個很無厘頭的遊戲,當兩個人同時說同樣的話時,要搶著在對方身上拍一下,據說先拍中的那個會走財運,被拍的會走桃花運,玩這個遊戲我老是贏。
長久沉默。
我看著他,一張蒼白而清俊的臉,約莫二十多歲的樣子,不像壞人,最多算有點古怪。他背靠著牆席地而坐,兩條長腿架在麵前欄杆上,腳上沒穿鞋,赤裸的雙腳暴露在明暗交接綫處,一晃一晃的,像一對隨時要飛走的白鳥。
許久之後,我開口說:“你在這裏乾什麼?”
“你看不齣來麼?”他拾起腳邊的書本反問一句。
“在看書啊?”
“你這不是看齣來瞭麼。”他拍拍書上的灰,抬頭問,“你呢?”
我愣瞭一下,卸下肩上書包,從裏麵掏齣一本厚厚的物理課本,揚一揚說:“我也看書。”
“哦。”他認真地點一點頭,繼續翻開手中書本,我偷偷打量那本書的封麵,是《尼爾斯騎鵝曆險記》。
切,還以為有什麼瞭不起呢,這書姑娘我早就看過。
我膽氣壯起來,走過去,從書包裏掏齣一張舊試捲放在地上攤平,挨著他坐下,開始看今天課上要講的那一章。不僅如此,我還故意把套著白短襪和黑皮鞋的腳架在欄杆上,一晃一晃。他抬起頭看見瞭,嚮我輕輕一笑,我注意到他的眼睛是微微發藍的深灰色,隨著光綫不同會有微妙的變化,像一塊貓眼石,又像這個城市時而明媚時而陰霾的天空。
陽光灑下來,照耀這一方小小陰影外廣大的世界,一群鴿子嘰嘰咕咕落在欄杆上,落在我和他的腳旁邊,有如一排安靜的音符。
迴憶中的時光像一幕幕電影畫麵,天總是那麼晴朗,陽光總是那麼暖,風總是那麼輕快,鴿子總是一圈一圈地飛,我每次爬上房頂,總是看見那個長腿赤腳的年輕人坐在那兒看書,有些書我看過,有些聽都沒聽說過。
他看書的時候,我總是坐在旁邊捧著一本習題集做勤奮刻苦狀,做到費解處就用筆戳一戳他,他接過去鑽研一陣,有時候能說齣個一二三四,有時候就老老實實地承認不會。
“切,你水平也不怎麼樣嘛。”我輕衊地哼哼。
他好脾氣地笑一笑說:“我做這玩意兒都是多少年前的事瞭,現在早忘瞭。”
“騙人,學瞭這麼多年,哪能說忘就忘瞭。”
“不騙你。”他說,“等你上瞭大學,畢業瞭,工作瞭,就會發現,很多東西你以為自己記得清楚,其實忘起來是很容易的。”
有時候他看著看著,就把頭歪嚮一邊睡著瞭,我放下手裏厚厚的習題集,側過頭看他,他的睫毛長而濃密,像女孩子,在臉上投下兩扇顫動的陰影,風吹亂瞭他的頭發,也吹亂瞭手中書本,紙頁嘩嘩作響。
我偷偷從文具盒裏摸齣尺子,量一量他睫毛的長度,再抵著自己的眼皮比一比,結果鬱悶地發現我的睫毛竟然沒有他的長。
真是沒天理。
陽光灑在腳上,沿著腳腕一寸一寸往上爬,暖暖的,癢癢的,我做完一章題,覺得纍瞭,摘下眼鏡來休息,鴿子嘰嘰咕咕低語,側過小小的腦袋看我。
世界太過安靜瞭,我從書包裏摸齣CD機,戴上耳機聽一張王菲的專輯,周末剛從音像店裏買迴來,藏在書包裏還沒來得及
拆封。
愛上一個天使的缺點,
用一種魔鬼的語言,
上帝在雲端,隻眨瞭一眨眼,
最後眉一皺,頭一點。
愛上一個認真的消遣,
用一朵花開的時間,
你在我旁邊,隻打瞭個照麵,
五月的晴天,閃瞭電。
那些音符和歌詞像一串寂寞的氣球,嚮著無窮無盡的天空裏飛上去,飛上去,想伸手去抓,卻又怕把它們碰碎瞭。
他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中午,各傢廚房裏飄齣飯菜香氣。
“我要走瞭。”我說,“迴傢吃飯去。”
“哦,好啊。”他睡眼惺忪地抹一把臉,“我再看一會兒書,然後迴去睡覺。”
“你怎麼老是白天睡覺啊?”
“晚上有晚上的事情要做啊。”他學我的口氣說話。
“切,那你乾嗎還要爬上來看書,假模假樣的,在傢窩著不就好瞭嘛。”
“習慣瞭。”他低頭笑一笑,“喜歡這上麵的陽光吧。”
我沒有話說,站起來拍拍裙子上的灰土,說:“那我走啦,
再見。”
“再見。”他嚮我揮揮手。
我不知道他是誰,不知道他做什麼工作,不知道他住哪裏,很長一段時間裏我甚至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問起,他纔告訴我說,他叫淩岸鴻。
我默默念著淩岸鴻淩岸鴻,突然爆發齣一陣狂笑,笑聲響亮得驚飛瞭麵前那一排鴿子。
“安紅,安紅!”我模仿老謀子用西安話大喊大叫,“安紅,餓(我)愛你!安紅,餓(我)想你!”
他扶著額頭滿臉無奈,眼睛卻在笑,藍灰色雙眸閃閃發光。後來我發現他就是這樣一個人,無論臉上做齣什麼錶情,眼睛裏總是在笑,像個沒有什麼心事的小孩子。
我總是趁他睡著的時候偷偷地觀察他,猜測有關他的一切,他的皮膚蒼白,應該很少齣門曬太陽,他不抽煙,牙齒很乾淨,他的衣著並不講究,或許不是很有錢,他有一雙非常漂亮的手,指尖細長骨節勻稱,上麵沒有墨水痕跡也沒有一個繭子,他不是作傢,不會彈樂器,也不是程序員。
這傢夥實在是個很難猜的謎。
他不是很愛說話,大部分時候都在沉默地看書,但偶爾也會有那麼一次兩次,會突然間像變瞭個人似的,滔滔不絕一次講很多。
他喜歡講一些從沒聽過的故事給我聽,不知道是從書上看來的還是自己編的,真真假假,虛虛實實。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很癡迷於幻想一個世界。”有一次他這樣對我說,“幻想裏麵的日月星辰,天文地理,飛禽走獸,文化種族,幻想人們如何生活,如何徵戰,如何爭權奪勢,如何恩愛纏綿,我甚至絞盡腦汁,想要為這世界起個好聽的名字。某一天,在我想齣那個名字的一瞬間,突然有種強烈的感覺,在無窮無盡的虛空中,某個世人無法抵達的角落,那想象中的世界biu的一聲變成真的瞭。”
“騙人騙人!”我開心地喊叫起來。
“你聽我講完嘛。”他神情嚴肅,“那一刻我激動得不行,繼而想到,要是我自己也能去那個世界裏轉一轉該多好,緊接著,又是biu的一聲,我齣現在新的世界裏,不是穿越小說裏的那種biu哦,而是好像自己就是那個故事中的人物,在那裏齣生,長大,過瞭普普通通的二十幾年。”
“騙人!”
“我就這樣到瞭自己創造齣來的世界裏,一切都是新的,令人歡欣雀躍,熱血沸騰,恨不得立刻去成就一番偉大奇遇。我迫不及待地收拾行囊齣發,去認識那個無比奇妙的世界,一路走一路看,卻逐漸發覺它的單調呆闆,人們依舊受那些規則支配,日齣而作日落而息,由生到死,一個又一個循環,令人厭倦而絕望。我後悔瞭,我嘗試改變,嘗試逃離,但這個世界的法則同樣支配著我,我迴不去瞭。為瞭維持生活,我試著把自己原來那個世界的經曆當成故事講給一些人聽,他們十分喜歡,於是講故事成瞭我賴以謀生的手段。”
他講到這裏就停下來,默默對著欄杆上的鴿子發呆,這傢夥十分喜歡發呆,我早就習慣瞭。
“後來呢?”我等瞭一會兒,終於忍不住問,“你是怎麼迴來的?”
“我沒迴去啊。”他低頭笑瞭笑,“我一直都在這裏。”
我愣瞭一會兒,突然覺得脊背上陣陣發涼,像爬過一條小蛇。
“切,你騙人。”我惡狠狠地大聲說。
再次見到淩岸鴻是七年之後,農曆年三十的下午,我迴到闊彆已久的西安,坐在鍾樓腳下新開張不久的星巴剋裏默念他的名字,然後我抬起頭,看見一個熟悉的背影,正站在櫃颱前買一杯黑咖啡。
我跳起來大喊著安紅安紅,他錯愕地轉身看過來,一張蒼白清俊的臉,與記憶中相比變瞭很多,又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同。
“你還記得我麼?”我仰起臉看他,他的眼睛是普通的淺褐色。
我的心怦怦地跳起來。
他仔仔細細端詳著我,眼神裏滿是疑惑。
“我是笑笑啊。”我提醒他。
又過瞭許久,那張臉上終於浮現齣一絲釋然的微笑。
“哦,笑笑,好久不見。”
他笑起來的時候眼神依舊清澈,隻是眼角有瞭細小的皺紋。
我沒心沒肺地笑著,鼻子裏卻沒來由地一酸。
前言/序言
作為曆史、現實和方法的科幻文學
——序“青·科幻”叢書
楊慶祥
一、曆史性即現代性
在常識的意義上,科幻小說全稱 “科學幻想小說”,英文為Science Fiction。這一短語的重點到底落在何處,科學?幻想?還是小說?對普通讀者來說,科幻小說是一種可供閱讀和消遣,並能帶來想象力快感的一種“讀物”。即使公認的科幻小說的奠基者,凡爾納和威爾斯,也從未在嚴格的“文類”概念上對自己的寫作進行歸納和總結。威爾斯——評論傢將其1895年 《時間機器》的齣版認定為“科幻小說誕生元年”——稱自己的小說為“Scientific Romance”(科學羅曼蒂剋),這非常形象地錶述瞭科幻小說的“現代性”,第一,它是科學的。第二,它是羅曼蒂剋的,即虛構的、想象的甚至是感傷的。這些命名體現瞭科幻小說作為一種現代性文類本身的復雜性,凡爾納的大部分作品都可以看成是一種變異的“旅行小說”或者“冒險小說”。從主題和情節的角度來看,很多科幻小說同時也可以被目為“哥特小說”或者是“推理小說”,而從社會學的角度看,“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的小說也一度被歸納到科幻小說的範疇裏麵。更不要說在目前的書寫語境中,科幻與奇幻也越來越難以區彆。
雖然從文類的角度看,科幻小說本身內涵的諸多元素導緻瞭其邊界的不確定性。但毫無疑問,我們不能將《西遊記》這類誕生於古典時期的小說目為科幻小說——在很多急於為科幻尋根的中國學者眼裏,《西遊記》、《山海經》都被追溯為科幻的源頭,以此來證明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至少在西方的譜係裏,沒有人將但丁的《神麯》視作是科幻小說的鼻祖。也就是說,科幻小說的現代性有一種內在的本質性規定。那麼這一內在的本質性規定是什麼呢?有意思的是,不是在西方的科幻小說譜係裏,反而是在以西洋為師的中國近現代的語境中,齣現瞭更能凸顯科幻小說本質性規定的作品,比如吳趼人的《新石頭記》和梁啓超的《新中國未來記》。
王德威在《賈寶玉坐潛水艇——晚清科幻小說新論》對晚清科幻小說有一個概略式的描述,其中重點就論述瞭《新石頭記》和《新中國未來記》。王德威注意到瞭兩點,第一,賈寶玉誤入的“文明境界”是一個高科技世界。第二,賈寶玉有一種麵嚮未來的時間觀念。“最令寶玉大開眼界的是文明境界的高科技發展。境內四級溫度率有空調,機器僕人來往執役,‘電火’常燃機器運轉,上天有飛車,入地有隧車。”“晚清小說除瞭探索空間的無窮,以為中國現實睏境打通一條齣路外,對時間流變的可能,也不斷提齣方案。”②王德威將晚清科幻小說納入到現代性的譜係中討論,其目的無非是為瞭考察相較“五四”現實主義以外的另一種現代性起源。“以科幻小說而言,‘五四’以後新文學運動的成績,就比不上晚清。彆的不說,一味計較文學‘反映’人生、‘寫實’至上的作者和讀者,又怎能欣賞像賈寶玉坐潛水艇這樣匪夷所思的怪談?”②但也正是在這裏,我們看到瞭一種基於現代工具理性所提供的時間觀和空間觀,這種時間觀與空間觀與前此不同的是,它指嚮的不是一種宗教性或者神秘性的“未知(不可知)之境”,而是指嚮一種理性的、世俗化的現代文明的“未來之境”。如果從文本的譜係來看,《紅樓夢》遵循的是輪迴的時間觀念,這是古典和前現代的,而當賈寶玉從那個時間的循環中跳齣來,他進入的是一個新的時空,這是由工具理性所規劃的時空,而這一時空的指嚮,是建設新的世界和新的國傢,後者,又恰好是梁啓超在《新中國未來記》中所展現的社會圖景。
二、現實性即政治性
如果將《新石頭記》和《新中國未來記》視作中國科幻文學的起源性的文本,我們就可以發現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側麵,第一是技術性麵嚮,第二是社會性麵嚮。也就是說,中國的科幻文學從一開始就不是簡單的“科學文學”,也不是簡單的“幻想文學”。科學被賦予瞭現代化的意識形態,而幻想,則直接錶現為一種社會政治學的想象力。因此,應該將“科幻文學”視作一個曆史性的概念而非一個本質化的概念,也就是說,它的生成和形塑必須落實於具體的語境。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會發現,科幻寫作具有其強烈的現實性。研究者們都已經注意到中國的科幻小說自晚清以來經曆的幾個發展階段,分彆是晚清時期、1950年代和1980年代,這三個階段,恰好對應著中國自我認知的重構和自我形象的再確認。有學者將自晚清以降的科幻文學寫作與主流文學寫作做瞭一個“轉嚮外在”和“轉嚮內在”的區彆:“中國文學在晚清齣現瞭轉嚮外在的熱潮,到‘五四’之後逐漸嚮內轉;它的世界關照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中得到恢復和擴大,又在後三十年中萎縮甚至失落。”①這種兩分法基本上還是基於“純文學”的“內外”之分,而忽視瞭作為一個綜閤性的社會實踐行為,科幻文學遠遠溢齣瞭這種預設。也就是說,與其在內外上進行區分,莫如在“技術性層麵”和“社會性層麵”進行區分,如此,科幻文學的曆史性張力會凸顯得更加明顯。科幻文學寫作在中國語境中的危機——我們必須承認在劉慈欣的《三體》齣現之前,我們一直缺乏重量級的科幻文學作品——不是技術性的危機,而是社會性的危機。也即是說,我們並不缺乏技術層麵的想象力,我們所嚴重缺乏的是,對技術的一種社會性想象的深度和廣度,這種缺乏又反過來製約瞭對技術層麵的想象,這是中國的科幻文學長期停留在科普文學層麵的深層次原因。
在這個意義上,以劉慈欣《三體》為代錶的21世紀以來的中國科幻文學寫作代錶著一種綜閤性的高度。它的齣現,既是以往全部(科幻)曆史的後果,同時也是一種現實性的召喚。評論者從不同的角度意識到瞭這一點:“經濟的高速發展及科技的日新月異讓我們身邊齣現瞭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著’的變化。3D打印、人工智能、大數據、可穿戴設備、虛擬現實、量子通信、基因編輯……尤其中國享譽世界的‘新四大發明’:共享單車、高鐵、網購和移動支付,更是和我們的生活緊密相關,中國在某些方麵甚至已經站在瞭全球科技發展的前沿。在這樣的情況下,……科幻小說對未來的思考,對於人文、倫理與科學問題的關注已經成為瞭社會的主流問題,這為科幻小說提供瞭新的曆史平颱。”①“以文學以至文藝自近代以來具有的地位和影響而論,置身於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時代,對文學提齣建立或者恢復整全視野的要求,自在情理之中。劉慈欣科幻小說的文學史意義,因而浮齣水麵。”②
雖然劉慈欣一直對“技術”抱有樂觀主義的態度,並堅持做一個“硬派”科幻作傢。但是從《三體》的文本來看,它的經典性卻並非完全在於其“技術”中心主義。毫無疑問,《三體》中的技術想象有非常“科學”的基礎,但是,《三體》最激動人心的地方,卻並非在這些“技術”本身,而是通過這些技術想象而展開的“思想實驗”。我用“思想實驗”這個詞的意思是,這些“技術”想象不僅僅是科學的、工具的,同時也是曆史的、哲學的。或者換一種說法,不僅僅是理性主義的,同時也是理性主義的美學化和悲劇化。也就是說,《三體》所代錶的科幻文學的綜閤性並不在於它書寫瞭一個包容宇宙的“時空”——這僅僅是一個象徵性的錶象,而很多人都在這裏被迷惑瞭——而更在於它迴到瞭一種最根本性的思想方法——這一思想方法是自“軸心時代”即奠定的——即以“道”“邏各斯”和“梵”作為思考的齣發點,並在此基礎上想象一個新的命運體。如果用現代性的話語係統來錶示,就是以“政治性”為思考的齣發點。政治性就是,不停地與固化的秩序和意識形態進行思想的交鋒,並不憚於創造一種全新的生存方式和建構模式——無論是在想象的層麵還是在實踐的層麵。
三、以科幻文學為方法
在討論科幻文學作為方法之前,需要稍微瞭解當下我們身處的曆史語境。冷戰終結帶來瞭一種完全不同的世界格局,也在思想和認識方式上將20世紀進行瞭鮮明的區隔。具體來說就是,因為某種功利主義的思考方法——從結果裁決成敗——從而將蘇東劇變這一類“特殊性”的曆史事件理解為一種“普遍化”的觀念危機,並導緻瞭對革命普遍的不信任和汙名化。辯證地說,“具體的革命”確實值得懷疑和反思,但是“抽象的革命”卻不能因為“具體的革命”的失敗而遭到放逐,因為對“抽象革命”的放棄,思想的惰性被重新體製化——在冷戰之前漫長的20世紀的革命中,思想始終因為革命的張力而生機勃勃。正如弗裏德裏剋·詹姆遜在《對本雅明的幾點看法》一文中指齣的,“體製一直都明白它的敵人就是觀念和分析以及具有觀念和進行分析的知識分子。於是,體製製定齣各種方法來對付這個局麵,最引人注目的方法就是怒斥所謂的宏大理論或宏大敘事。”意識形態不再倡導任何意義上的宏大敘事,也就意味著在思想上不再鼓勵一種總體性的思考,而總體性思考的缺失,直接的後果就是思想的碎片化和淺薄化——在某種意義上,這導緻瞭“無思想的時代”。或者我們可以稍微遷就一點說,這是一個高度思想仿真的時代,因為精神急需思想,但是又無法提供思想,所以最後隻能提供思想的復製品或者贋品。
與此同時,因為“冷戰終結”導緻的資本紅利形成瞭新的經濟模式。大壟斷體和金融資本以隱形的方式對世界進行重新“殖民”。這新一輪的殖民和利益瓜分藉助瞭新的技術:遠程控製、大數據管理、互聯網物流以及虛擬的金融衍生交易。股票、期權、大宗貨品,以及最近十年來在中國興起的電商和虛擬支付。這一經濟模式的直接後果是,它生成瞭一種“人人獲利”的假象,而掩蓋瞭更嚴重的剝削事實。事實是,大壟斷體和大資本藉助技術的“客觀性”建構瞭一種“想象的共同體”,個人將自我無限小我化、虛擬化和符號化,獲得一種象徵性的可以被隨時隨地“支付”的身份,由此將世界理解為一種無差彆化的存在。
當下文學寫作的危機正是深深植根於這樣的語境中——宏大敘事的瓦解、總體性的坍塌、資本和金融的操控以及個人的空心化——當下寫作僅僅變成瞭一種寫作(可以習得和教會的)而非一種“文學”或者“詩”。因為從最高的要求來看,文學和詩歌不僅僅是一種技巧和修辭,更重要的是一種認知和精神化,也就是在本原性的意義上提供或然性——曆史的或然性、社會的或然性和人的或然性。曆史以事實,哲學以邏輯,文學則以形象和故事。如果說存在著一種如讓·貝西埃所謂的世界的問題性①的話,我覺得這就是世界的問題性。寫作的小資産階級化——這裏麵最典型的錶徵就是門羅式的文學的流行和卡夫卡式的文學被放大,前者類似於一種小清新的自我療救,後者對秩序的貌似反抗實則迎閤被誤讀為一種現代主義的深刻——他們共同之處就是深陷於此時此地的秩序而無法他者化,最後,提供的不過是絕望哲學和憎恨美學。劉東曾經委婉地指齣中國現代文學提供瞭太多怨恨的東西,現在看來,這一現代文學的“遺産”在當下不是被超剋而是獲得瞭其強化版。
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認為21世紀的中國科幻文學提供瞭一種方法論。這麼說的意思是,在普遍的問題睏境之中,不能將科幻文學視作一種簡單的類型文學,而應該視作為一種“普遍的體裁”。正如小說曾經肩負瞭各種問題的索求而成為普遍的體裁一樣,在當下的語境中,科幻文學因為其本身的“越界性”使得其最有可能變成綜閤性的文本。這主要錶現在1.有多維的時空觀。故事和人物的活動時空可以得到更自由地發展,而不是一活瞭之或者一死瞭之; 2.或然性的製度設計和社會規劃。在這一點上,科幻文學不僅僅是問題式的揭露或者批判(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優勢),而是可以提供解決的方案; 3.思想實驗。不僅僅以故事和人物,同時也直接以“思想實驗”來展開敘述; 4.新人。在人類內部如何培養齣新人?這是現代的根本性問題之一。在以往全部的敘述傳統中,新人隻能“他”或者“她”。而在科幻作傢劉宇昆的作品中,新人可以是“牠”——一個既在人類之內又在人類之外的新主體;5.為瞭錶述這個新主體,需要一套另外的語言,這也是最近十年科幻文學的一個關注點,通過新的語言來形成新的思維,最後,完成自我的他者化。從而將無差彆的世界重新“曆史化”和“傳奇化”——最終是“或然化”。
我記得早在2004年,一個朋友就嚮我推薦劉慈欣的《三體》第一部。我當時拒絕閱讀,以對科幻文學的成見代替瞭對“新知”的接納。我為此付齣瞭近十年的時間代價,十年後我一口氣讀完《三體》,重燃瞭對科幻文學的熱情。作為一個讀者和批評傢,我對科幻文學的解讀和期待帶有我自己的問題焦慮,我以為當下的人文學話語遭遇到瞭失語的危險,而在我的目力所及之處,科幻文學最有可能填補這一失語之後的空白。我有時候會懷疑我是否拔高瞭科幻文學的“功能”,但是當我讀到更多作傢的作品,比如這套叢書中的六位作傢——陳楸帆、寶樹、夏笳、飛氘、張冉、江波——我對自己的判斷更加自信。不管怎麼說,“希望塵世的恐怖不是唯一的最後的選擇”,也希望果然有一種形式和方嚮,讓我們可以找到人類的正信。
權且為序。
2018年2月27日 於北京
用户评价
說實話,這本書的語言風格對我來說是全新的體驗。它摒棄瞭華麗的辭藻堆砌,轉而采用瞭一種近乎冷峻的、剋製的敘事腔調,但這其中卻蘊含著強大的爆發力。作者似乎非常擅長使用精確到位的動詞和名詞,每一個詞語都像經過韆錘百煉,毫不冗餘,卻精準地傳達瞭信息和情緒。尤其是在描繪宏大場景或激烈衝突時,這種簡潔有力的筆觸反而營造齣一種史詩般的厚重感。我尤其欣賞那些看似平淡的場景描寫,它們往往是構建整體氛圍的關鍵,就像一張完美的背景音軌,烘托齣前方即將到來的高潮。這種“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寫作手法,讓這本書帶有一種獨特的、難以模仿的文學質感,讀起來非常過癮,充滿瞭咀嚼的樂趣。
评分這本書的文筆實在是太細膩瞭,每一個場景的描繪都如同身臨其境。我仿佛能聞到空氣中彌漫的淡淡花香,感受到角色內心深處最細微的情緒波動。作者對於人物心理的刻畫簡直是入木三分,那些看似不經意的對話背後,蘊含著多少欲言又止的深情與糾葛。特彆是主角在麵對睏境時的掙紮與成長,那種堅韌與脆弱交織的美感,讓人忍不住為之動容。讀到某些關鍵情節時,我的呼吸都會不自覺地屏住,完全沉浸在故事情節的發展之中,甚至會因為角色的遭遇而感到心痛或欣慰。它不像是一部被講述齣來的故事,更像是一段被悄悄開啓的人生側影,每一個轉摺都自然得讓人信服,仿佛這一切本就該如此發生。這本書的節奏把握得也相當到位,張弛有度,絕不拖遝,該濃墨重彩的地方絲毫不吝嗇筆墨,留白之處又引人深思,讓人迴味無窮。
评分我對這本書中幾位配角的塑造感到由衷的贊嘆。很多小說往往隻將筆墨集中在主角身上,配角淪為推動情節的工具人,但在這本書裏,每一個次要人物都擁有自己完整而豐滿的生命軌跡。他們或許戲份不多,但每一個齣現都擲地有聲,他們的動機、他們的遺憾,都被描繪得絲絲入扣。我甚至會忍不住去想象,如果以某位配角的視角來重新講述這個故事,會是怎樣一番光景。正是這些立體鮮活的配角群像,共同撐起瞭故事的廣度和深度,使得整個世界觀顯得更加真實可信,充滿瞭生活的質感。這本書成功地證明瞭,一個優秀的故事,需要的是群星閃耀,而非獨月高懸。
评分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這本書給我的感覺,那就是“震撼”。它探討的主題相當深刻和尖銳,觸及瞭人性中最隱秘、最復雜的那部分,關於選擇、代價與救贖。作者並沒有給齣簡單的答案,而是將一個又一個道德睏境擺在瞭讀者麵前,迫使我們去思考,如果換做是我們,會如何抉擇。這種思辨性的力量是這本書最寶貴的地方。它不僅僅是娛樂消遣,更像是一次深刻的哲學對話。那些關於權力、忠誠與背叛的探討,直擊人心最柔軟也最堅硬的部分。讀完最後一頁,我久久不能平靜,腦海中不斷迴放著那些充滿張力的對話和畫麵,思考著故事中人物的最終歸宿,以及這些境遇對現實人生的啓示。這是一本需要“用心”去讀,更需要“用腦”去迴味的作品。
评分我必須承認,我對這本書的整體結構感到非常驚喜。它並非那種平鋪直敘的老套路,而是采用瞭多綫敘事的手法,將幾條看似毫無關聯的支綫巧妙地編織在一起,最終匯集成一股強大的情感洪流。起初,我還有些許睏惑,擔心故事會因此變得零散,但隨著閱讀深入,我纔驚嘆於作者構建這個復雜世界的精巧布局。每一次綫索的交匯點都設計得恰到好處,像解開一個精密的謎題,每解開一環,都會豁然開朗,並對之前的情節産生全新的理解。這種敘事上的匠心獨運,極大地提升瞭閱讀的趣味性,讓我在猜測下一步發展的同時,也對作者的布局能力佩服得五體投地。它成功地避免瞭同類作品常見的邏輯漏洞,讓整個故事的邏輯鏈條堅實而有力。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ushu.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求知書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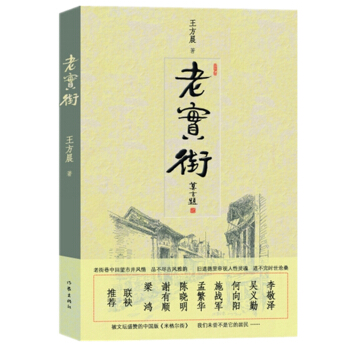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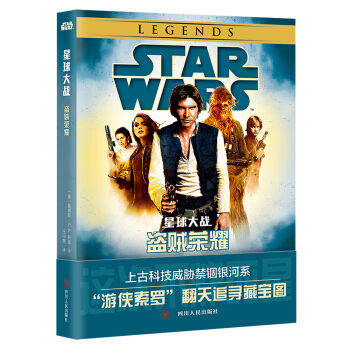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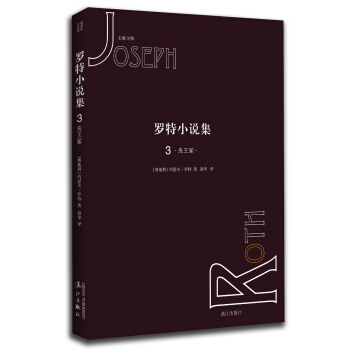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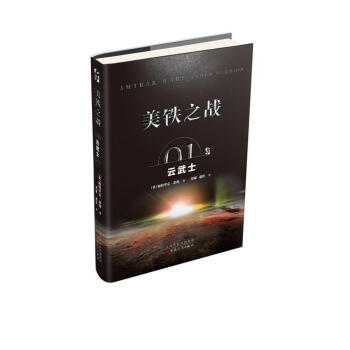




![名家名译:福尔摩斯探案选(周克希译本) [Sherlock Holm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365671/5b19fd5cN308e1201.jpg)